六 文化多元视域中的东亚儒学
| 内容出处: | 《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上册》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6954 |
| 颗粒名称: | 六 文化多元视域中的东亚儒学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0 |
| 页码: | 104-113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子安宣邦和黄俊杰对于“东亚”论述的不同观点,以及黄俊杰对于东亚儒学研究的立场和方法。子安宣邦认为“东亚”并不是自明的概念,需要历史清算,而黄俊杰则从学理上建构了“东亚儒学”的概念,并从方法论上解答了“东亚儒学”何以可能的问题。黄俊杰认为东亚儒学是一个多元性的学术领域,不存在前近代式的“一元论”的预设,反对文化一元论,强调东亚儒学的多元文化性。由此出发,21世纪台湾学界提倡东亚儒学研究便在文化多元立场上成为可能。 |
| 关键词: | 东亚儒学 研究 方法 |
内容
当然,对于21世纪台湾地区的东亚儒学研究,特别是对2000年以降台湾大学推动的东亚儒学研究的系列计划,子安宣邦原本是充满期待的,而且他对黄俊杰的东亚研究也曾给予很高评价①,另一方面,黄俊杰对子安宣邦的“东亚”研究也非常重视,他曾亲自为子安的《东亚儒学:批判与方法》一书撰写了长篇“跋文”,颇多赞誉肯定之词②。同时,上述子安对“东亚”论述的批评也引起了黄俊杰的关注,他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故有《“东亚儒学”如何可能》③(以下简称黄文)之作,试图从学理上来建构“东亚儒学”这一概念,并从方法论上解答“东亚儒学”何以可能的问题。
黄文首先同意子安的观点,认为“东亚儒学”并不是不证自明的概念,黄文进而指出“东亚儒学”受到“东亚”与“儒学”这两个概念的互相规范或限制,所以一方面,“东亚儒学”的研究对象受到中国、韩国、日本、越南这些被称为“东亚”的这一地理概念的限制,另一方面,“东亚”又被“儒学”所界定,亦即“东亚儒学”中的“东亚”是指受到儒学传统所浸润的东亚地域为其范围。前者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解答什么是“东亚儒学”,后者从文化传统的角度(儒学传统)来解答什么是“东亚”。这个说法非常平稳,是容易接受的。不过,黄文对“东亚”论述的历史渊源及其日本因素并没有展开正面的讨论,这就使得在他人的眼里看来,黄文对“东亚”的理解缺乏批判。
的确,从历史上看,在东亚论述中有两种背景因素:一是在传统中华帝国的“华夷秩序”意义上的所谓“东亚”,一是在近代日本帝国的“东亚共同体”意义上的所谓“东亚”。不妨称之为“二种东亚论”。诚然,对于前一种东亚论,中国学者应当有自觉的反省和批判,而对于后一种东亚论,则是日本学者首先应该努力解构和批判的对象,重要的是,这两种批判应当建立起必要的联系,甚至可以形成互相批判。对于“二种东亚论”,黄文没有从正面探讨,应该说这是黄文的一个不足之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黄文探讨东亚儒学问题之目的在于重构中华帝国的“话语”。对于黄文的这种批评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归根结底,将“中国”乃至“东亚”他者化、方法化,这是作为日本学者子安宣邦所能直言的,但能否将此观点上升为普遍之共法,则尚有探讨之余地。根据我目前的初步了解,台湾学界之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末重提东亚儒学研究,自有其自身的“东亚意识”以及“台湾意识”为背景,只是这一背景问题所涉台湾地区的政治文化等因素十分复杂,笔者一时尚未理清,容当别论。①重要的是,对“东亚”的历史论述进行批判固然是东亚儒学研究的一个必要前提,但是反过来,东亚儒学之研究也必将推动我们对“东亚”论述进行深刻的反思,也正由此,所以东亚儒学研究具有批判和建构的双重意义。就此而言,21世纪台湾地区东亚儒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那么,何谓“东亚儒学”呢?关于这一问题,黄俊杰在《东亚儒学:经典与诠释的辩证》“自序”中提出了一个较为明确清晰的定义,大致有三层意思:1.作为空间概念的“东亚儒学”,是指儒学思想及其价值理念在东亚地区的发展及其内涵;2.作为时间概念的“东亚儒学”,是指在东亚各国儒者的思想互动之中应时而变、与时俱进,而不是一个抽离于各国儒学传统之上的一套僵硬不变的意识形态;3.因此,“东亚儒学”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性的学术领域,在这个领域里面并不存在前近代式的“一元论”的预设。我觉得黄俊杰有关“东亚儒学”的上述定义大致是不错的。
关于“东亚儒学”之研究立场的问题,黄俊杰也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观点:“在承认儒学传统在东亚……各地域,各自展开其多彩多姿、多元多样的面貌与内涵,但却又异中有同。”因此质言之,“‘东亚儒学’的特质在于‘寓一于多’,在儒学传统的大框架中展现东亚文化的多元性”。①这是说东亚儒学并不是文化一元论,它具有“文化多元性”之特质,呈现为“异中有同”“寓一于多”的特性。②也就是说,东亚儒学既有多元性又有同一性。然而,异与同、一与多的结构关系正表明东亚儒学存在着一种内部张力,用黄俊杰的话说,也就是“中国儒学价值理念与东亚地域特性之间的张力”③,按照我们的理解,也就是东亚文化的普遍性与东亚各地域文化的特殊性之间的张力,关于这一点,上述未刊稿已有较详的讨论,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要之,黄俊杰主张“东亚儒学”所预设的是一文化多元性的学术立场,这与子安宣邦主张东亚儒学研究不应指向重建中华文化一元论的立场是一致的。
平心而论,子安批判近代以来日本的东亚论述,这一点值得肯定,而黄俊杰则以“多元文化”①作为自己的学术立场,强调东亚儒学并不是以中国为绝对的中心,也不预设“中心对边缘”的结构关系②,这就为解答“东亚儒学”何以可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质言之,这是以文化多元论来反对文化一元论。由此出发,21世纪台湾学界提倡东亚儒学研究便在文化多元立场上成为可能,具体地说,东亚儒学研究既能“建构深具各地民族特色的地域性儒学传统”,同时又能“在儒学传统的大框架中展现东亚文化的多元性”。③毫无疑问,黄俊杰对东亚儒学如何可能之问题所做的上述回答有其自身多年来东亚儒学研究实践作为背景。的确,我们唯有通过对前近代的一元论思维模式的克服,从多元文化的立场出发,才能真正建立起东亚儒学的研究领域。
然而对于黄文的观点,子安并没有做正面的回应。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特别是2010年,子安多次参与学术会议,话题仍然主要围绕东亚问题而展开。④尤当一提的是其中的一场报告:《再论“作为方法的东亚”》(2010年3月26日于成功大学)。子安在报告中回顾了多年来参与台湾地区东亚研究之过程,特别提到2002年6月的那场“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表明当他读到“研讨会缘起与背景”的主旨说明之后,便对“这场研讨会所抱持的态度不禁由期待转为警戒”。
为什么呢?因为在子安看来:“这篇文章像在陈述历史事实的同时极具政治意涵。‘东亚’这个概念,并不是地图上有的地域概念,而是政治地理概念,是与政治支配、文化支配的欲望共存而成立的概念。”所以在子安的眼里,这场会议的性质是“以实体的中国文化圈作为东亚文化圈,为探究其形成与发展而举行的学术研讨会”。这是子安由其“作为方法的东亚”之立场出发而断然不能接受的。所谓“政治地理概念”“政治支配、文化支配”以及“实体”性的中国文化圈之概念,正是子安的东亚论述中所欲竭力解构的对象。至此,我们终于明了子安对于以黄俊杰为代表的台湾大学东亚文化研究计划是否意在建构“实体性”的中华文化秩序始终不能释怀,这是导致子安对台湾地区东亚儒学研究由期待转而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
行文至此,不由得使我联想起王汎森的一个看似无奈却又严肃的说法:“近代中国与日本的爱恨情结,使得任何有关这个问题(引者按,指戊戌前后中国思想中的日本因素问题)的研究都难以下笔,而且不容易被平情看待,总觉得在字面之后,应该还有潜在的动机。这种情形当然不是全然子虚乌有。”①如今,我们仿佛看到台湾地区的东亚研究正被人怀疑另有“潜在的动机”。其实,据我近几年对台湾学界的观察,其东亚儒学研究是否想把“东亚”纳入“地政学”范围来定义?是否想把实体的中国文化圈来覆盖东亚并进而将“东亚”实体化?纯属子虚乌有。
值得一提的是,杨儒宾曾在与子安宣邦的一场对话中坦率地指出,尽管“东亚”一词很容易使人想起“大东亚共荣圈”,“但就在台湾成长的这一辈学者(引者按,指杨儒宾这一辈)的印象,这样的负面意象却是不太有的,至少我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很容易使用‘东亚’这个很中性化的语言”。②“中性化”这个说法很引人注目,意谓当今台湾学界所说的“东亚”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再含有20世纪帝国日本的那种将东亚“实体化”的含义。这个说法看似平实,然而从中反映出战后台湾人对“日本”的基本认知。所以我想在20世纪90年代末,台湾地区之所以会有一股“东亚热”,或许正是由于当地社会对“东亚”乃至“日本”的这种认同态度为基础的。不过依我之见,严格说来,东亚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合而言之,东亚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这一点也是不能否认的。我们将在下一节,对此问题稍加详细的探讨。这里只需指出,批评台湾学者将东亚理解为“地政学”意义上的东亚,显然言过其实。
那么,21世纪台湾学界重提东亚儒学又有何背景因素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梅约翰教授在上面提到的武大会议以后,特意提供给笔者一篇论文,他指出近年来台湾地区之所以兴起东亚研究,乃是一部分学者为了应对“去中国化”的新形势而采取的一种“策略”。①这个分析虽是外缘性的,但作为第三者的一种审视观点,值得引起重视。因为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与“台湾”可以同时被置入“东亚”而显得堂堂正正。然须指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地区东亚儒学的研究已经受到关注。②根据李明辉提供的一份资料表明,1992年9月,台湾清华大学与大阪大学合作举办了“东亚儒学与近代‘国际’研讨会”③,这或许是以“东亚儒学”命名的“国际”会议在台湾地区的滥觞。
次年1993年,“中研院”中国文哲所制订了“当代儒学研究主题计划”,由戴琏璋、刘述先主持,黄俊杰亦一同参与,其背景之一在于扭转“中研院”自成立以来对于儒学研究一贯轻视之偏向以及应对80年代末中国大陆推动的“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课题”。三年后的1996年,为继续推进该项“主题计划”,制订了该项目的第二期计划,揭示了“儒家思想在近代东亚的发展及其现代意义”这一新主题,目的之一在于反思历来在儒学研究中隐然存在的“中国中心论”之偏向,并明确了该项研究的旨趣在于:“由于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儒家思想也以极为不同的方式在这些地区(引者按,指东亚)发生作用,而各自形成同中有异的传统。因此,我们不但有必要将东亚视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有必要就这些地区的不同历史、文化背景来探讨儒家思想在其中所呈现的殊异性。”①
显而易见,这一立场也反映在2000年以后台湾大学推动的各项“东亚儒学”研究计划之中。当然,21世纪台湾地区的东亚儒学研究迅猛发展的社会背景及其学术背景还有待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的东亚社会大背景中来加以观察。重要的是,对于学术背景的观察之目的在于探寻东亚研究中学术与社会的积极互动关系,摆脱意识形态口号对学术研究的干扰②,进而展望儒学在东亚社会中的未来走向。
通过上述回顾可以看出,在“东亚儒学”隐然成为当今学界一种新的学术研究领域的过程中,不断出现何谓“东亚儒学”以及何谓“东亚”这类问题。子安宣邦对帝国日本的“东亚”论述的历史批判发人深省,黄俊杰对“东亚儒学”何以可能等学理性问题的深入阐发亦极具启发意义。接下来,我要谈一些有关东亚儒学问题的个人意见。在我看来,所谓“东亚儒学”,指的是儒学在东亚,这是一种历史现象学的描述,其意是说,儒学在历史时间上曾经存在于东亚这个地域空间,也就是说“东亚儒学”所内含的时间与空间的概念,是一个史学概念,是在历史的构架中所存在的。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东亚儒学”这一概念构架中的所谓“东亚”到底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含有价值内涵的文化概念?抑或是地域与文化两者兼而有之的文化地理概念?能否说由于“东亚”概念创立之初便烙上了帝国日本的意识形态影子,其中已内含有文化地域的含义①,因此我们就应该弃若敝屣?我以为东亚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我们从“儒学”思考“东亚”或者从“东亚”思考“儒学”,那么所谓“东亚”无疑是一复合型概念,而非单纯的地理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提出“文化东亚”这一概念。
其意何在呢?其实,从“儒学”所看到的“东亚”,已然不是纬度和经度都十分清晰的自然地理学的概念,而是一人文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按照人文地理学的基本规定来说,东亚就是含指东亚地域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的人文地理。若将历史的因素考虑在内,那么可以说,“东亚儒学”中的“东亚”乃是一历史人文地理之概念。因为事实上,儒学之在“东亚”,既不能脱离历史的时间,也不能脱离人文的空间,也就是说,作为中国这一地域文化之产物的儒学在向“东亚”进行传播之时,既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有与“东亚”其他地域的文化历史发生冲撞、摩擦、糅合的过程。反过来说,例如作为“东亚”地域之一的日本,他们在接受儒学之际,自身绝不是文化上的一片空白而可以任由儒学一统天下。历史表明,日本自身的文化对于外来儒学的传播有一个吸收、容纳乃至反拨等复杂的过程,要之,儒学之在日本有一个“本土化”过程,从而构成了不同于中国理论形态的日本儒学。
可见,“东亚”乃是一个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文化地理概念。若从“文化交涉”①的角度看,东亚所构成的正是一种多元文化体系。这种多元性不仅是不同地域之间的表现,而且在同一地域的内部也有多元性文化表现,即如台湾地区而言,自有文献记载的明郑时期(1662—1683)以来,历经清朝领台时期(1683—1895)、日据时期(1895—1945)及至光复以后至“解严”以前(1945—1987),当地社会所呈现的便是一个多元并存、多元融合的文化融合体。因此,儒学之在台湾,就不得不与“台湾意识”发生关联,表现出其不同于大陆儒学的发展形态,例如20世纪50年代以降台湾地区的学院派“当代新儒学”不仅是对中国传统儒学的一个新发展,在我看来更是构成了当今“台湾儒学”运动的一部分,当然就其本质而言,“当代新儒学”更是“中国底儒学”,因为它仍然是以“中国儒家道德慧命为根柢”的。②
那么,为什么强调“文化东亚”这一点很重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首先,从文化传播的“本土化”这一审视角度看,任何一种文化向其他地域进行传播之际,都有一个与当地文化如何磨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本土化”过程,因为文化传播绝不是出口商品那样,进口国只能被动接受,而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对话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传播就有了“文化交涉”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东亚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如果我们片面地强调东亚只是一个地理概念,那么东亚儒学之概念的提出就含有了这样一种意味:亦即意味着主张由于东亚本身并没有文化的内涵,所以儒学之在东亚只是单向传播而没有与当地文化如何交涉的过程。这个观点就将导致一个十分严重的后果,儒学成了一个覆盖东亚地域的宰制性概念,因为东亚本身只是白板一块的缺乏文化的地理存在,如此一来,东亚儒学就必然成为一种“中华文化一元论”或“中国中心论”的变相说法,显然在当今世界文化日趋多元的格局中,这是亟应克服的偏见,否则的话,真会被人怀疑是否有“潜在的动机”。
其次,我们强调指出“东亚”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要注意另一种理解,亦即将东亚理解成政治秩序或地理政治的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东亚”概念盛行于日本之际便蒙上了“地政学”的浓厚色彩,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并有沉痛记忆的“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一种地政学概念,其中含有强烈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意味,这一概念随着二战终结已经成为“死语”,只要是正直的知识分子是不会希望它复活的。我们强调作为文化地理概念的东亚,就是为了杜绝这种作为地政学概念的“东亚”死灰复燃。将东亚视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地理存在,既可以使我们注意到东亚本身构成一个意义世界,同时又可突破史学研究中传统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带来的困扰,以更为明确的多元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儒学在东亚区域文化中的历史问题。
黄文首先同意子安的观点,认为“东亚儒学”并不是不证自明的概念,黄文进而指出“东亚儒学”受到“东亚”与“儒学”这两个概念的互相规范或限制,所以一方面,“东亚儒学”的研究对象受到中国、韩国、日本、越南这些被称为“东亚”的这一地理概念的限制,另一方面,“东亚”又被“儒学”所界定,亦即“东亚儒学”中的“东亚”是指受到儒学传统所浸润的东亚地域为其范围。前者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解答什么是“东亚儒学”,后者从文化传统的角度(儒学传统)来解答什么是“东亚”。这个说法非常平稳,是容易接受的。不过,黄文对“东亚”论述的历史渊源及其日本因素并没有展开正面的讨论,这就使得在他人的眼里看来,黄文对“东亚”的理解缺乏批判。
的确,从历史上看,在东亚论述中有两种背景因素:一是在传统中华帝国的“华夷秩序”意义上的所谓“东亚”,一是在近代日本帝国的“东亚共同体”意义上的所谓“东亚”。不妨称之为“二种东亚论”。诚然,对于前一种东亚论,中国学者应当有自觉的反省和批判,而对于后一种东亚论,则是日本学者首先应该努力解构和批判的对象,重要的是,这两种批判应当建立起必要的联系,甚至可以形成互相批判。对于“二种东亚论”,黄文没有从正面探讨,应该说这是黄文的一个不足之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黄文探讨东亚儒学问题之目的在于重构中华帝国的“话语”。对于黄文的这种批评显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归根结底,将“中国”乃至“东亚”他者化、方法化,这是作为日本学者子安宣邦所能直言的,但能否将此观点上升为普遍之共法,则尚有探讨之余地。根据我目前的初步了解,台湾学界之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末重提东亚儒学研究,自有其自身的“东亚意识”以及“台湾意识”为背景,只是这一背景问题所涉台湾地区的政治文化等因素十分复杂,笔者一时尚未理清,容当别论。①重要的是,对“东亚”的历史论述进行批判固然是东亚儒学研究的一个必要前提,但是反过来,东亚儒学之研究也必将推动我们对“东亚”论述进行深刻的反思,也正由此,所以东亚儒学研究具有批判和建构的双重意义。就此而言,21世纪台湾地区东亚儒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那么,何谓“东亚儒学”呢?关于这一问题,黄俊杰在《东亚儒学:经典与诠释的辩证》“自序”中提出了一个较为明确清晰的定义,大致有三层意思:1.作为空间概念的“东亚儒学”,是指儒学思想及其价值理念在东亚地区的发展及其内涵;2.作为时间概念的“东亚儒学”,是指在东亚各国儒者的思想互动之中应时而变、与时俱进,而不是一个抽离于各国儒学传统之上的一套僵硬不变的意识形态;3.因此,“东亚儒学”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性的学术领域,在这个领域里面并不存在前近代式的“一元论”的预设。我觉得黄俊杰有关“东亚儒学”的上述定义大致是不错的。
关于“东亚儒学”之研究立场的问题,黄俊杰也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观点:“在承认儒学传统在东亚……各地域,各自展开其多彩多姿、多元多样的面貌与内涵,但却又异中有同。”因此质言之,“‘东亚儒学’的特质在于‘寓一于多’,在儒学传统的大框架中展现东亚文化的多元性”。①这是说东亚儒学并不是文化一元论,它具有“文化多元性”之特质,呈现为“异中有同”“寓一于多”的特性。②也就是说,东亚儒学既有多元性又有同一性。然而,异与同、一与多的结构关系正表明东亚儒学存在着一种内部张力,用黄俊杰的话说,也就是“中国儒学价值理念与东亚地域特性之间的张力”③,按照我们的理解,也就是东亚文化的普遍性与东亚各地域文化的特殊性之间的张力,关于这一点,上述未刊稿已有较详的讨论,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要之,黄俊杰主张“东亚儒学”所预设的是一文化多元性的学术立场,这与子安宣邦主张东亚儒学研究不应指向重建中华文化一元论的立场是一致的。
平心而论,子安批判近代以来日本的东亚论述,这一点值得肯定,而黄俊杰则以“多元文化”①作为自己的学术立场,强调东亚儒学并不是以中国为绝对的中心,也不预设“中心对边缘”的结构关系②,这就为解答“东亚儒学”何以可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前提,质言之,这是以文化多元论来反对文化一元论。由此出发,21世纪台湾学界提倡东亚儒学研究便在文化多元立场上成为可能,具体地说,东亚儒学研究既能“建构深具各地民族特色的地域性儒学传统”,同时又能“在儒学传统的大框架中展现东亚文化的多元性”。③毫无疑问,黄俊杰对东亚儒学如何可能之问题所做的上述回答有其自身多年来东亚儒学研究实践作为背景。的确,我们唯有通过对前近代的一元论思维模式的克服,从多元文化的立场出发,才能真正建立起东亚儒学的研究领域。
然而对于黄文的观点,子安并没有做正面的回应。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特别是2010年,子安多次参与学术会议,话题仍然主要围绕东亚问题而展开。④尤当一提的是其中的一场报告:《再论“作为方法的东亚”》(2010年3月26日于成功大学)。子安在报告中回顾了多年来参与台湾地区东亚研究之过程,特别提到2002年6月的那场“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表明当他读到“研讨会缘起与背景”的主旨说明之后,便对“这场研讨会所抱持的态度不禁由期待转为警戒”。
为什么呢?因为在子安看来:“这篇文章像在陈述历史事实的同时极具政治意涵。‘东亚’这个概念,并不是地图上有的地域概念,而是政治地理概念,是与政治支配、文化支配的欲望共存而成立的概念。”所以在子安的眼里,这场会议的性质是“以实体的中国文化圈作为东亚文化圈,为探究其形成与发展而举行的学术研讨会”。这是子安由其“作为方法的东亚”之立场出发而断然不能接受的。所谓“政治地理概念”“政治支配、文化支配”以及“实体”性的中国文化圈之概念,正是子安的东亚论述中所欲竭力解构的对象。至此,我们终于明了子安对于以黄俊杰为代表的台湾大学东亚文化研究计划是否意在建构“实体性”的中华文化秩序始终不能释怀,这是导致子安对台湾地区东亚儒学研究由期待转而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
行文至此,不由得使我联想起王汎森的一个看似无奈却又严肃的说法:“近代中国与日本的爱恨情结,使得任何有关这个问题(引者按,指戊戌前后中国思想中的日本因素问题)的研究都难以下笔,而且不容易被平情看待,总觉得在字面之后,应该还有潜在的动机。这种情形当然不是全然子虚乌有。”①如今,我们仿佛看到台湾地区的东亚研究正被人怀疑另有“潜在的动机”。其实,据我近几年对台湾学界的观察,其东亚儒学研究是否想把“东亚”纳入“地政学”范围来定义?是否想把实体的中国文化圈来覆盖东亚并进而将“东亚”实体化?纯属子虚乌有。
值得一提的是,杨儒宾曾在与子安宣邦的一场对话中坦率地指出,尽管“东亚”一词很容易使人想起“大东亚共荣圈”,“但就在台湾成长的这一辈学者(引者按,指杨儒宾这一辈)的印象,这样的负面意象却是不太有的,至少我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很容易使用‘东亚’这个很中性化的语言”。②“中性化”这个说法很引人注目,意谓当今台湾学界所说的“东亚”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再含有20世纪帝国日本的那种将东亚“实体化”的含义。这个说法看似平实,然而从中反映出战后台湾人对“日本”的基本认知。所以我想在20世纪90年代末,台湾地区之所以会有一股“东亚热”,或许正是由于当地社会对“东亚”乃至“日本”的这种认同态度为基础的。不过依我之见,严格说来,东亚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合而言之,东亚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这一点也是不能否认的。我们将在下一节,对此问题稍加详细的探讨。这里只需指出,批评台湾学者将东亚理解为“地政学”意义上的东亚,显然言过其实。
那么,21世纪台湾学界重提东亚儒学又有何背景因素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梅约翰教授在上面提到的武大会议以后,特意提供给笔者一篇论文,他指出近年来台湾地区之所以兴起东亚研究,乃是一部分学者为了应对“去中国化”的新形势而采取的一种“策略”。①这个分析虽是外缘性的,但作为第三者的一种审视观点,值得引起重视。因为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与“台湾”可以同时被置入“东亚”而显得堂堂正正。然须指出,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地区东亚儒学的研究已经受到关注。②根据李明辉提供的一份资料表明,1992年9月,台湾清华大学与大阪大学合作举办了“东亚儒学与近代‘国际’研讨会”③,这或许是以“东亚儒学”命名的“国际”会议在台湾地区的滥觞。
次年1993年,“中研院”中国文哲所制订了“当代儒学研究主题计划”,由戴琏璋、刘述先主持,黄俊杰亦一同参与,其背景之一在于扭转“中研院”自成立以来对于儒学研究一贯轻视之偏向以及应对80年代末中国大陆推动的“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课题”。三年后的1996年,为继续推进该项“主题计划”,制订了该项目的第二期计划,揭示了“儒家思想在近代东亚的发展及其现代意义”这一新主题,目的之一在于反思历来在儒学研究中隐然存在的“中国中心论”之偏向,并明确了该项研究的旨趣在于:“由于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儒家思想也以极为不同的方式在这些地区(引者按,指东亚)发生作用,而各自形成同中有异的传统。因此,我们不但有必要将东亚视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儒家思想的影响,也有必要就这些地区的不同历史、文化背景来探讨儒家思想在其中所呈现的殊异性。”①
显而易见,这一立场也反映在2000年以后台湾大学推动的各项“东亚儒学”研究计划之中。当然,21世纪台湾地区的东亚儒学研究迅猛发展的社会背景及其学术背景还有待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的东亚社会大背景中来加以观察。重要的是,对于学术背景的观察之目的在于探寻东亚研究中学术与社会的积极互动关系,摆脱意识形态口号对学术研究的干扰②,进而展望儒学在东亚社会中的未来走向。
通过上述回顾可以看出,在“东亚儒学”隐然成为当今学界一种新的学术研究领域的过程中,不断出现何谓“东亚儒学”以及何谓“东亚”这类问题。子安宣邦对帝国日本的“东亚”论述的历史批判发人深省,黄俊杰对“东亚儒学”何以可能等学理性问题的深入阐发亦极具启发意义。接下来,我要谈一些有关东亚儒学问题的个人意见。在我看来,所谓“东亚儒学”,指的是儒学在东亚,这是一种历史现象学的描述,其意是说,儒学在历史时间上曾经存在于东亚这个地域空间,也就是说“东亚儒学”所内含的时间与空间的概念,是一个史学概念,是在历史的构架中所存在的。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东亚儒学”这一概念构架中的所谓“东亚”到底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含有价值内涵的文化概念?抑或是地域与文化两者兼而有之的文化地理概念?能否说由于“东亚”概念创立之初便烙上了帝国日本的意识形态影子,其中已内含有文化地域的含义①,因此我们就应该弃若敝屣?我以为东亚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我们从“儒学”思考“东亚”或者从“东亚”思考“儒学”,那么所谓“东亚”无疑是一复合型概念,而非单纯的地理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提出“文化东亚”这一概念。
其意何在呢?其实,从“儒学”所看到的“东亚”,已然不是纬度和经度都十分清晰的自然地理学的概念,而是一人文地理学意义上的概念,按照人文地理学的基本规定来说,东亚就是含指东亚地域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的人文地理。若将历史的因素考虑在内,那么可以说,“东亚儒学”中的“东亚”乃是一历史人文地理之概念。因为事实上,儒学之在“东亚”,既不能脱离历史的时间,也不能脱离人文的空间,也就是说,作为中国这一地域文化之产物的儒学在向“东亚”进行传播之时,既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同时又有与“东亚”其他地域的文化历史发生冲撞、摩擦、糅合的过程。反过来说,例如作为“东亚”地域之一的日本,他们在接受儒学之际,自身绝不是文化上的一片空白而可以任由儒学一统天下。历史表明,日本自身的文化对于外来儒学的传播有一个吸收、容纳乃至反拨等复杂的过程,要之,儒学之在日本有一个“本土化”过程,从而构成了不同于中国理论形态的日本儒学。
可见,“东亚”乃是一个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文化地理概念。若从“文化交涉”①的角度看,东亚所构成的正是一种多元文化体系。这种多元性不仅是不同地域之间的表现,而且在同一地域的内部也有多元性文化表现,即如台湾地区而言,自有文献记载的明郑时期(1662—1683)以来,历经清朝领台时期(1683—1895)、日据时期(1895—1945)及至光复以后至“解严”以前(1945—1987),当地社会所呈现的便是一个多元并存、多元融合的文化融合体。因此,儒学之在台湾,就不得不与“台湾意识”发生关联,表现出其不同于大陆儒学的发展形态,例如20世纪50年代以降台湾地区的学院派“当代新儒学”不仅是对中国传统儒学的一个新发展,在我看来更是构成了当今“台湾儒学”运动的一部分,当然就其本质而言,“当代新儒学”更是“中国底儒学”,因为它仍然是以“中国儒家道德慧命为根柢”的。②
那么,为什么强调“文化东亚”这一点很重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首先,从文化传播的“本土化”这一审视角度看,任何一种文化向其他地域进行传播之际,都有一个与当地文化如何磨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本土化”过程,因为文化传播绝不是出口商品那样,进口国只能被动接受,而是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对话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传播就有了“文化交涉”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东亚既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如果我们片面地强调东亚只是一个地理概念,那么东亚儒学之概念的提出就含有了这样一种意味:亦即意味着主张由于东亚本身并没有文化的内涵,所以儒学之在东亚只是单向传播而没有与当地文化如何交涉的过程。这个观点就将导致一个十分严重的后果,儒学成了一个覆盖东亚地域的宰制性概念,因为东亚本身只是白板一块的缺乏文化的地理存在,如此一来,东亚儒学就必然成为一种“中华文化一元论”或“中国中心论”的变相说法,显然在当今世界文化日趋多元的格局中,这是亟应克服的偏见,否则的话,真会被人怀疑是否有“潜在的动机”。
其次,我们强调指出“东亚”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的原因还在于,我们要注意另一种理解,亦即将东亚理解成政治秩序或地理政治的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东亚”概念盛行于日本之际便蒙上了“地政学”的浓厚色彩,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并有沉痛记忆的“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一种地政学概念,其中含有强烈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意味,这一概念随着二战终结已经成为“死语”,只要是正直的知识分子是不会希望它复活的。我们强调作为文化地理概念的东亚,就是为了杜绝这种作为地政学概念的“东亚”死灰复燃。将东亚视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地理存在,既可以使我们注意到东亚本身构成一个意义世界,同时又可突破史学研究中传统民族国家(Nation-State)概念带来的困扰,以更为明确的多元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的儒学在东亚区域文化中的历史问题。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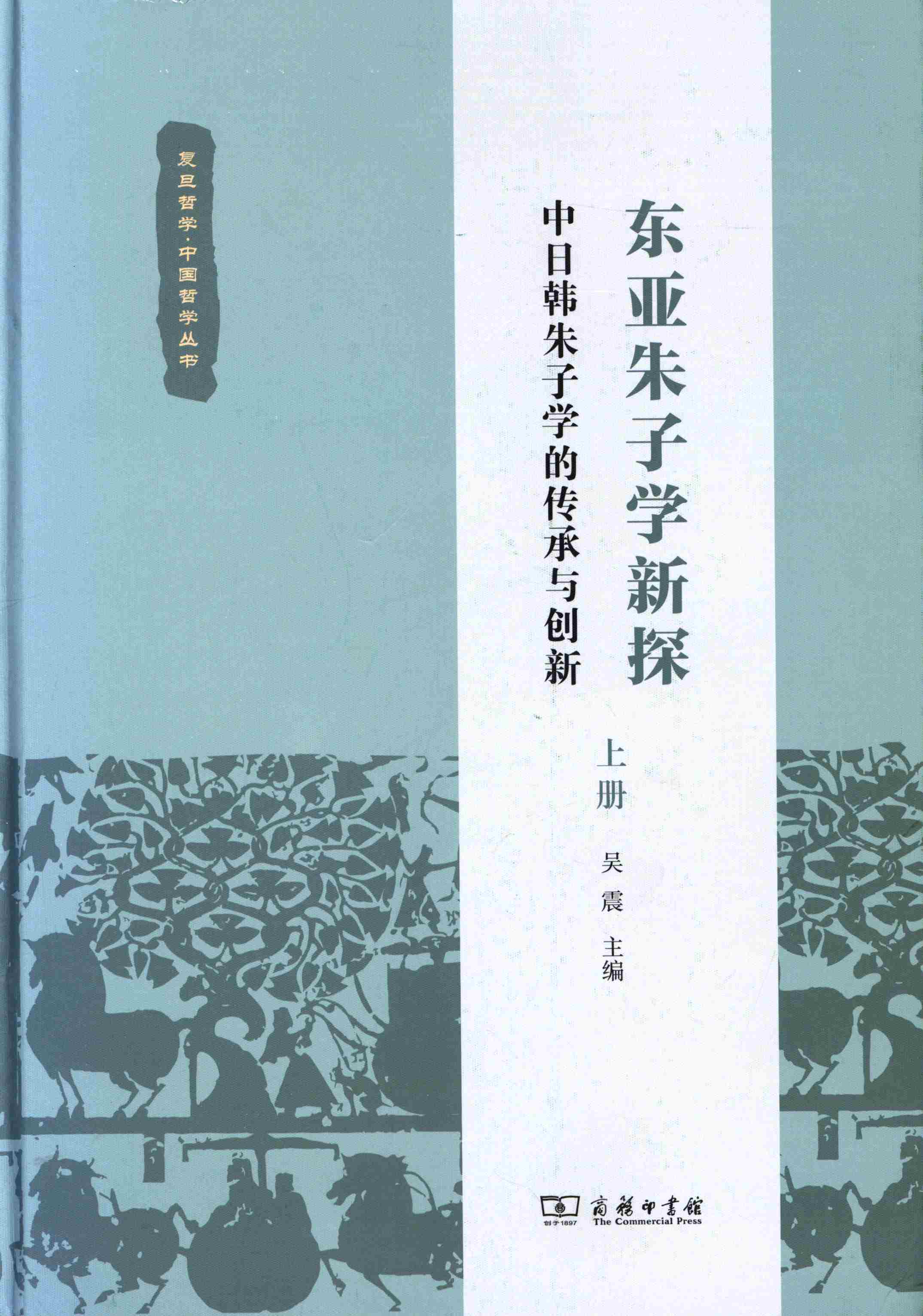
《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上册》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
这部《东亚朱子学新探——中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是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日韩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的结项成果,并于今年被认定为是成果。全书共由四篇三十七章组成,近九十万字,吴震教授主编,由海内外中国哲学领域的一线学者组成的性团队合作分篇撰写,代表了当代朱子学研究的前沿的成果。本书的四篇结构是:一、“东亚儒学与中国朱子学”;二、“日本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三、“韩国朱子学的传承与创新”;“比较研究与回顾综述”;后是两篇“附录”,分别是“近十年来日本朱子学研究论著简目”、“近十年来韩国朱子学研究论著简目”。本书进一步拓展了朱子学研究领域的深度与广度,可以认为,通过本书的出版,“东亚朱子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有充分理由得以成立(如同有别于“西方哲学”的“东亚儒学”或“东亚哲学”已渐形成一般),进而,本书的出版也得以重新展现了中国哲学等。
阅读
相关人物
吴震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