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家禮》一書真僞問題
| 内容出处: | 《《朱子家禮》在朝鮮傳播中的“諸具”疏證》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5215 |
| 颗粒名称: | 一 《家禮》一書真僞問題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4 |
| 页码: | 2-5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家礼》真伪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家礼》是他人伪窜,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是朱子未定稿。但至今无法找到朱子《家礼》初稿底本,关键史料缺失,因此无法定论。 |
| 关键词: | 朱子家礼 真伪问题 底本缺失 |
内容
《朱子家禮》又名《朱文公家禮》《文公家禮》《家禮》等。“據《四庫全書》的著録統計,朱子現存的著作共二十五種,六百餘卷,總字數在二千萬字左右”①,《家禮》比諸朱子旁論,篇幅最爲精微,然却是其接受人群最廣的禮學讀本,亦是最具争議的著述之一,其癥結主要集中在《家禮》真僞問題上。舉以言之,分述如下。
(一)《家禮》係他人“僞竄”説
楊復云:“《家禮》始成而失之,不及再加考訂。先生既没而書始出。”②《家禮》初成即爲僧童竊去,未得先生匡正,故而引致僞作之嫌。據楊士奇《跋文公家禮》及丘濬《文公家禮儀節》(以下簡稱《儀節》)所載,元末至正年間(1341—1370年),武林人應本(字中甫)作《家禮辨》③,首倡《家禮》非朱子手編,斷其出於門人附會。迄至清初,疑古辨僞風潮漸盛,白田王懋竑重申應氏之説,作《朱子年譜考異》《家禮考》《家禮後考》《家禮考誤》,更於《家禮考》開首以“《家禮》非朱子之書也”④爲確論,出陳例證數十則,引古禮及諸説相辯難。
王氏的疑竇從內容角度考察,突出强調《家禮》與《儀禮》《司馬氏書儀》(以下簡稱《書儀》)等舊典及朱子晚時學術論斷的不合之處,且《家禮》自身内容亦存在前後矛盾之處。從文獻記載角度考察,王氏關注點在於除李方子《紫陽年譜》載《家禮》成書於乾道六年(1170年)外,並没有其他關於《家禮》完成具體年月的確切表述;且除了《朱子文集》卷75載《家禮序》外,朱子的其他著述中從未提及《家禮》的編纂,基於此王氏將《家禮序》也視作僞竄之作。
王説厥後爲《四庫全書總目》采納,並於“家禮五卷附録一卷”條全盤承襲,云:“是書之不出朱子,可灼然無疑。”①由於《四庫總目》的官修權威性,經此裁斷,僞作説遂成定論。然近代沿用兹説者甚鮮,直至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他一反學界駁應詰王之風,試圖從“《家禮》內部考察,伸張王説,以期引起更深層之討論”②。其述論從《家禮》文本毫末處入手,呈列疑誤舉要十則,指出《家禮》虚擡宗法、喪服制度、儀節錯亂、昧於經義、前後不照、取捨失當等諸多錯謬③,從而讞決《家禮》之水準尚下於《書儀》,斷不能歸於晦庵名下。
(二)《家禮》係朱子“草就而未定”説
應、王之説一出,時賢訟奪即興。然“僞作説”由於鮮有後人提出進一步佐證,故清後逐步式微。相反,自丘濬《儀節》及夏炘《述朱質疑·跋家禮》分别對照應、王二説,按次摘録並提出相應的糾辨,肯定《家禮》爲朱子所撰這一事實後,今人錢穆、高明、上山春平、陳來、束景南、吾妻重二諸學者亦拳拳於《家禮》成書真僞問題之證①,他們一方面依循先賢路徑,釐析過往論説中史料釋讀的正繆得失;另一方面廣泛搜羅考訂朱子親筆詩文書札,以及朱門高弟所述的序跋、語録、傳記,企圖勾稽《家禮》成書過程中朱子思想的流變;此外,還參酌現存版本系統,勘校文字異同,追溯《家禮》原貌,裁斷其被後人竄亂改易之處。
對於上述學人的論辯往還,此不贅言,僅就確認《家禮》是否爲朱子所作不可規避之兩點稍加闡明,一則宋刊本《纂圖集注文公家禮》卷首翻刻有朱子親筆《家禮序》一篇;二則朱子後嗣及門人於其生前便知《家禮》“草定”,佚而復出,經弟子取用刊行。
就結論而言,正如黄榦《朱子行狀》:“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②及陳淳《代陳憲跋家禮》:“惜其書既亡而復出,不出於先生無恙之前,而出於先生既没之後,不幸而不能垂爲一定之成儀以幸萬世,而反爲未成之缺典,至貽後世千古無窮之恨,甚可痛也!”③采照較妥帖的説法,《家禮》稿本確係朱子草定,然修整未訖便被付梓流布,故文本内容間有與朱子晚歲語論相牴牾之處。後世“不僅其弟子曾有臆補增改,且宋元以來被人竄亂移易”④。兹如現今通行的永樂十三年(1415年)敕修《性理大全》本《家禮》,其卷首所載28幅家禮圖便是原封蹈襲元黄瑞節所撰《朱子成書》①。此即學者語及《家禮》,不免是非相眩、議論多歧的根源。
綜而述之,由於至今無法覓得朱子《家禮》初稿底本,關鍵史料缺失,一味汲汲追尋《家禮》真僞之謎,終究未能定讞。筆者傾向於在研究《家禮》播遷朝鮮半島致使其社會意識形態儒家化的進程中,應將《家禮》看作朱熹學術體系中不可剥離的有機組成部分。②
(一)《家禮》係他人“僞竄”説
楊復云:“《家禮》始成而失之,不及再加考訂。先生既没而書始出。”②《家禮》初成即爲僧童竊去,未得先生匡正,故而引致僞作之嫌。據楊士奇《跋文公家禮》及丘濬《文公家禮儀節》(以下簡稱《儀節》)所載,元末至正年間(1341—1370年),武林人應本(字中甫)作《家禮辨》③,首倡《家禮》非朱子手編,斷其出於門人附會。迄至清初,疑古辨僞風潮漸盛,白田王懋竑重申應氏之説,作《朱子年譜考異》《家禮考》《家禮後考》《家禮考誤》,更於《家禮考》開首以“《家禮》非朱子之書也”④爲確論,出陳例證數十則,引古禮及諸説相辯難。
王氏的疑竇從內容角度考察,突出强調《家禮》與《儀禮》《司馬氏書儀》(以下簡稱《書儀》)等舊典及朱子晚時學術論斷的不合之處,且《家禮》自身内容亦存在前後矛盾之處。從文獻記載角度考察,王氏關注點在於除李方子《紫陽年譜》載《家禮》成書於乾道六年(1170年)外,並没有其他關於《家禮》完成具體年月的確切表述;且除了《朱子文集》卷75載《家禮序》外,朱子的其他著述中從未提及《家禮》的編纂,基於此王氏將《家禮序》也視作僞竄之作。
王説厥後爲《四庫全書總目》采納,並於“家禮五卷附録一卷”條全盤承襲,云:“是書之不出朱子,可灼然無疑。”①由於《四庫總目》的官修權威性,經此裁斷,僞作説遂成定論。然近代沿用兹説者甚鮮,直至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他一反學界駁應詰王之風,試圖從“《家禮》內部考察,伸張王説,以期引起更深層之討論”②。其述論從《家禮》文本毫末處入手,呈列疑誤舉要十則,指出《家禮》虚擡宗法、喪服制度、儀節錯亂、昧於經義、前後不照、取捨失當等諸多錯謬③,從而讞決《家禮》之水準尚下於《書儀》,斷不能歸於晦庵名下。
(二)《家禮》係朱子“草就而未定”説
應、王之説一出,時賢訟奪即興。然“僞作説”由於鮮有後人提出進一步佐證,故清後逐步式微。相反,自丘濬《儀節》及夏炘《述朱質疑·跋家禮》分别對照應、王二説,按次摘録並提出相應的糾辨,肯定《家禮》爲朱子所撰這一事實後,今人錢穆、高明、上山春平、陳來、束景南、吾妻重二諸學者亦拳拳於《家禮》成書真僞問題之證①,他們一方面依循先賢路徑,釐析過往論説中史料釋讀的正繆得失;另一方面廣泛搜羅考訂朱子親筆詩文書札,以及朱門高弟所述的序跋、語録、傳記,企圖勾稽《家禮》成書過程中朱子思想的流變;此外,還參酌現存版本系統,勘校文字異同,追溯《家禮》原貌,裁斷其被後人竄亂改易之處。
對於上述學人的論辯往還,此不贅言,僅就確認《家禮》是否爲朱子所作不可規避之兩點稍加闡明,一則宋刊本《纂圖集注文公家禮》卷首翻刻有朱子親筆《家禮序》一篇;二則朱子後嗣及門人於其生前便知《家禮》“草定”,佚而復出,經弟子取用刊行。
就結論而言,正如黄榦《朱子行狀》:“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②及陳淳《代陳憲跋家禮》:“惜其書既亡而復出,不出於先生無恙之前,而出於先生既没之後,不幸而不能垂爲一定之成儀以幸萬世,而反爲未成之缺典,至貽後世千古無窮之恨,甚可痛也!”③采照較妥帖的説法,《家禮》稿本確係朱子草定,然修整未訖便被付梓流布,故文本内容間有與朱子晚歲語論相牴牾之處。後世“不僅其弟子曾有臆補增改,且宋元以來被人竄亂移易”④。兹如現今通行的永樂十三年(1415年)敕修《性理大全》本《家禮》,其卷首所載28幅家禮圖便是原封蹈襲元黄瑞節所撰《朱子成書》①。此即學者語及《家禮》,不免是非相眩、議論多歧的根源。
綜而述之,由於至今無法覓得朱子《家禮》初稿底本,關鍵史料缺失,一味汲汲追尋《家禮》真僞之謎,終究未能定讞。筆者傾向於在研究《家禮》播遷朝鮮半島致使其社會意識形態儒家化的進程中,應將《家禮》看作朱熹學術體系中不可剥離的有機組成部分。②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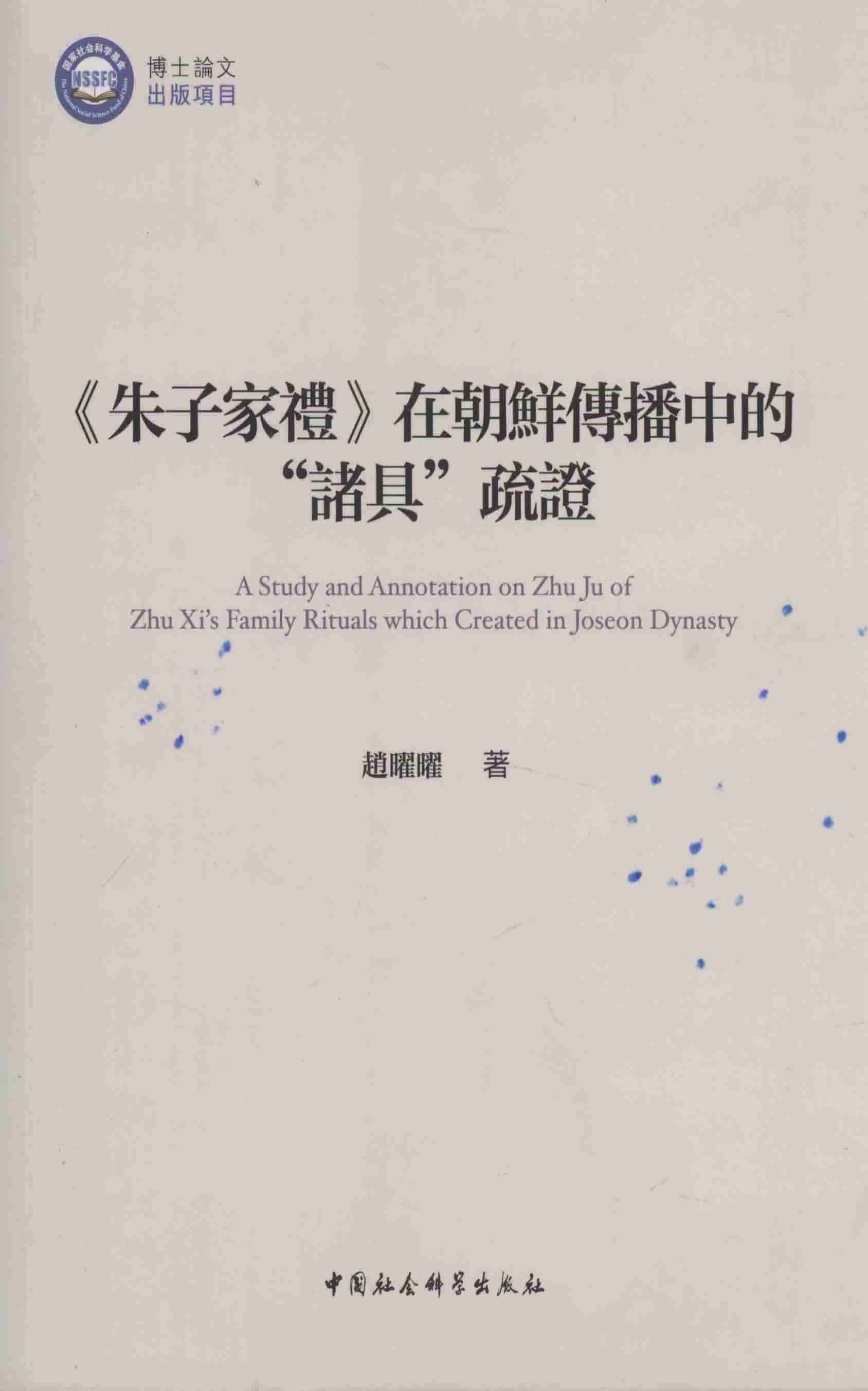
《《朱子家禮》在朝鮮傳播中的“諸具”疏證》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共分五章。首章,推究朝鲜时代礼书中“诸具”这一名目产生、发展、定型之过程。其中第二至五章,依通、冠、婚、祭礼的次序,将提炼的“诸具”作爲词头,着重稽考《丛书》较《家礼》衍变及创发的物具,分三端进行细化的处理:第一,所谓“创发”者,即《家礼》文本所无,凭半岛民俗所用而增设。所增之物,皆有本源可考,未敢有一字赘入。第二,所谓“删汰”者,即《家礼》所载服器已不合朝鲜之用,或李朝世人更不知其爲何物,故需依后贤议论对部分“诸具”进行裁革。“诸具”的适时删减,体现了礼因时、因俗而变的原则。第三,所谓“衍变”者,主要是指“诸具”名称、位置、形制、隆杀等,与《家礼》描述相去甚远,《丛书》或改换俗用,或係以俗称,或补充所明。结语部分从器物性质上对疏证对象安排了大致的分类,并就疏证过程中的难点和不足作了概括,另着眼于宏观意义上的“训诂学”方法,对“诸具”疏证的理想形式及目标给予了有限的期待。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