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論
| 内容出处: | 《《朱子家禮》在朝鮮傳播中的“諸具”疏證》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5213 |
| 颗粒名称: | 引論 |
| 分类号: | K892.27 |
| 页数: | 29 |
| 页码: | 1-29 |
| 摘要: | 本文探讨了《朱子家礼》的源流及其在朝鲜的传播和影响,并对《丛书》中特色“诸具”进行解题,进一步理解其在文化和历史背景下的意义。 |
| 关键词: | 朱子 研究 传播影响 |
内容
紫陽朱夫子感於“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疏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①的現世情狀,立於修己安身之本,衍布於士庶階層宗族内部的人倫風教、綱常節度,撰輯爲《家禮》一書。其所發明雖區區數萬言,却熔鑄漢唐群經舊學,博采衆家禮説之長,化繁爲簡、約古從俗,成爲時人履踐冠、婚、喪、祭禮之大端的日用手册。《家禮》的問世,“是其將‘天理’與人間世對接的一個重要嘗試,是其將形而上的理學思想世俗化的一次社會實驗”②,誠可謂“集大成而緒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③。
本章係以《家禮》爲依歸,探賾索隱,考其著述淵源、歷程、內容特色,並就該書真僞及版本問題作扼要的引介,以期對《家禮》完整之概念有通盤的了解。其次剖析是書東傳朝鮮半島之内因外緣,查檢其土著化、庶民化、大衆化之流衍始末。最末,針對補苴《家禮》類禮書中朝鮮化的“諸具”頊,參酌群經,旁及史典,剔抉爬梳,勾繪出“諸具”在遞嬗過程中的大致輪廓。
第一節 《朱子家禮》源流考鏡
一《家禮》一書真僞問題
《朱子家禮》又名《朱文公家禮》《文公家禮》《家禮》等。“據《四庫全書》的著録統計,朱子現存的著作共二十五種,六百餘卷,總字數在二千萬字左右”①,《家禮》比諸朱子旁論,篇幅最爲精微,然却是其接受人群最廣的禮學讀本,亦是最具争議的著述之一,其癥結主要集中在《家禮》真僞問題上。舉以言之,分述如下。
(一)《家禮》係他人“僞竄”説
楊復云:“《家禮》始成而失之,不及再加考訂。先生既没而書始出。”②《家禮》初成即爲僧童竊去,未得先生匡正,故而引致僞作之嫌。據楊士奇《跋文公家禮》及丘濬《文公家禮儀節》(以下簡稱《儀節》)所載,元末至正年間(1341—1370年),武林人應本(字中甫)作《家禮辨》③,首倡《家禮》非朱子手編,斷其出於門人附會。迄至清初,疑古辨僞風潮漸盛,白田王懋竑重申應氏之説,作《朱子年譜考異》《家禮考》《家禮後考》《家禮考誤》,更於《家禮考》開首以“《家禮》非朱子之書也”④爲確論,出陳例證數十則,引古禮及諸説相辯難。
王氏的疑竇從內容角度考察,突出强調《家禮》與《儀禮》《司馬氏書儀》(以下簡稱《書儀》)等舊典及朱子晚時學術論斷的不合之處,且《家禮》自身内容亦存在前後矛盾之處。從文獻記載角度考察,王氏關注點在於除李方子《紫陽年譜》載《家禮》成書於乾道六年(1170年)外,並没有其他關於《家禮》完成具體年月的確切表述;且除了《朱子文集》卷75載《家禮序》外,朱子的其他著述中從未提及《家禮》的編纂,基於此王氏將《家禮序》也視作僞竄之作。
王説厥後爲《四庫全書總目》采納,並於“家禮五卷附録一卷”條全盤承襲,云:“是書之不出朱子,可灼然無疑。”①由於《四庫總目》的官修權威性,經此裁斷,僞作説遂成定論。然近代沿用兹説者甚鮮,直至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他一反學界駁應詰王之風,試圖從“《家禮》內部考察,伸張王説,以期引起更深層之討論”②。其述論從《家禮》文本毫末處入手,呈列疑誤舉要十則,指出《家禮》虚擡宗法、喪服制度、儀節錯亂、昧於經義、前後不照、取捨失當等諸多錯謬③,從而讞決《家禮》之水準尚下於《書儀》,斷不能歸於晦庵名下。
(二)《家禮》係朱子“草就而未定”説
應、王之説一出,時賢訟奪即興。然“僞作説”由於鮮有後人提出進一步佐證,故清後逐步式微。相反,自丘濬《儀節》及夏炘《述朱質疑·跋家禮》分别對照應、王二説,按次摘録並提出相應的糾辨,肯定《家禮》爲朱子所撰這一事實後,今人錢穆、高明、上山春平、陳來、束景南、吾妻重二諸學者亦拳拳於《家禮》成書真僞問題之證①,他們一方面依循先賢路徑,釐析過往論説中史料釋讀的正繆得失;另一方面廣泛搜羅考訂朱子親筆詩文書札,以及朱門高弟所述的序跋、語録、傳記,企圖勾稽《家禮》成書過程中朱子思想的流變;此外,還參酌現存版本系統,勘校文字異同,追溯《家禮》原貌,裁斷其被後人竄亂改易之處。
對於上述學人的論辯往還,此不贅言,僅就確認《家禮》是否爲朱子所作不可規避之兩點稍加闡明,一則宋刊本《纂圖集注文公家禮》卷首翻刻有朱子親筆《家禮序》一篇;二則朱子後嗣及門人於其生前便知《家禮》“草定”,佚而復出,經弟子取用刊行。
就結論而言,正如黄榦《朱子行狀》:“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②及陳淳《代陳憲跋家禮》:“惜其書既亡而復出,不出於先生無恙之前,而出於先生既没之後,不幸而不能垂爲一定之成儀以幸萬世,而反爲未成之缺典,至貽後世千古無窮之恨,甚可痛也!”③采照較妥帖的説法,《家禮》稿本確係朱子草定,然修整未訖便被付梓流布,故文本内容間有與朱子晚歲語論相牴牾之處。後世“不僅其弟子曾有臆補增改,且宋元以來被人竄亂移易”④。兹如現今通行的永樂十三年(1415年)敕修《性理大全》本《家禮》,其卷首所載28幅家禮圖便是原封蹈襲元黄瑞節所撰《朱子成書》①。此即學者語及《家禮》,不免是非相眩、議論多歧的根源。
綜而述之,由於至今無法覓得朱子《家禮》初稿底本,關鍵史料缺失,一味汲汲追尋《家禮》真僞之謎,終究未能定讞。筆者傾向於在研究《家禮》播遷朝鮮半島致使其社會意識形態儒家化的進程中,應將《家禮》看作朱熹學術體系中不可剥離的有機組成部分。②
二 《家禮》之撰述背景及歷程
“家禮”一詞最早出現於《周禮·春官·家宗人》:“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掌家禮與其衣服、宫室、車旗之禁令。”表示貴族大夫采邑内所需遵循的法則,後用以通指私家常用之禮儀規範,“六朝時已有之,或曰書儀,或曰家禮,名目異耳”③。由於朱子《家禮》的駸駸始盛,此後獨擅朱子撰著之專名。本節主要以朱子編撰《家禮》之背景及其著作歷程爲着力點,考察如下。
(一)朱子編撰《家禮》之背景
1.社會關係變遷,禮下庶人
唐末五代兵革不息,世道衰微,禮廢樂壞,“庶人服侯服,墙壁被文繡。公卿與皂隸同制,倡優下賤得爲后飾。昏冠喪祭、宫室器用,家殊俗異,人自爲制,無復綱紀”①。門閥等級性的宗族制解體,家庭組織結構形態發生變化。隨着士族退出歷史舞臺,寒門庶族借科舉躋身政治權力的中心,貴賤等差觀念日趨淡漠,門第高下的界限逐漸消失。此外,宋代以来社會結構和政治格局發生重大改變,“庶人在數量上占人口的絕大多數,經濟上擔負着社會絕大部分的生產勞動。文化方面,也成爲重要的創造者;政治上,則是官府不能忽視的最廣大的社會基礎”②。庶人社會地位的提升,“迫切需要與其政治地位、經濟狀況相適應的禮學禮制來滿足其社會生活的需要”③。於是禮由以往貴族階層的文化特權,向社會下層轉移,完成了“禮下庶人”的平民化轉捩。其標志是徽宗所頒《政和五禮新儀》,第一次在官方禮典中單列了針對庶民階層的禮儀條文。而司馬光《書儀》及朱子《家禮》等籍册,也是在政府企圖通過緩驅以令、勸曉以文、使民徐而知禮的大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2.古禮難明,且不合時宜,私家禮範興起
《儀禮》等古禮文本最早記載了關於古代家庭的禮儀規範,在宋代禮樂復興運動的浪潮中,儒者提倡重新審視和挖掘古禮的精神內涵,以期來穩定社會人倫秩序,規範民衆道德行爲,對抗釋老以及民間信仰的浸染。然而古禮距宋已久,且其文義古奧、名物度數難詳、儀節煩瑣細碎,自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依王安石的提議更定科舉科目廢置《儀禮》後④,研治古禮者更是寥若晨星。朱子也曾感歎道:“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家。”⑤爲了使古制禮法在民間切實可行,依“從俗、從衆、從便”的原則,因情循俗地對其進行删改變通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另外,唐宋後禮書編纂“重心由公禮轉向到家禮”①,宋代公卿士大夫中的有識之士,洞悉朝廷禮文缺陋不行的現狀,繼承六朝以來的家禮制訂傳統,積極關注和修撰私家禮儀規範②,其著述主要有司馬光《書儀》及《温公家範》、張載《横渠張氏祭儀》、范祖禹《祭儀》、葉夢得《石林家訓》、袁采《袁氏世範》、高閌《送終禮》、陸九韶《陸氏家制》等。此中,司馬光《書儀》可謂“前期家禮、書儀長期醞釀發展後一次示範性的集成”③,除記載有關表奏、公文、書信格式外,還涉及“冠儀、婚儀、喪儀(含‘祭’在内)”等内容。全書以《儀禮》爲本,芟蕪存要,與時俱變,第一次爲士民禮書設定了冠、婚、喪、祭四禮爲基礎的框架結構,亦爲後世家禮的格局及世俗化開了先河。但由於對庶民接受禮的知識水平,及實踐禮的經濟能力缺乏明晰的估量,在民衆中推行《書儀》時頻頻遭受冷遇。綜之,古禮的不合時宜,私家禮書的無所折衷、難以推用,均爲朱子《家禮》這一符合時代緊迫性和社會必要性的新禮書的編纂提出了要求。
(二)《家禮》之撰述歷程
朱熹措意於禮學,並留心搜集整理考訂諸家禮説,蓋緣起於紹興十三年(1143年)其父朱松病逝的早年人生經歷。他與弟子談及時曾説:“某自十四歲而孤,十六而免喪。是時祭祀,只依家中舊禮,禮文雖未備,却甚齊整。先妣執祭事甚虔。及某年十七八,方考訂得諸家禮,禮文稍備。”①
後二十餘年,其母祝氏於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辭世,同年《祭儀》稿成。朱子自紹興十七年(1147年)編《祭儀》初稿,經與張栻、吕祖謙、林用中、汪應辰等人的函商及反復修訂,在其母喪年《祭儀》終成。②《祭儀》分祭説、祭儀、祝詞三卷,體例上未分綱目,《祭儀》爲《家禮》之最早雛形,其内容亦被《家禮》所吸收,故陳淳稱其爲《家禮》的“最初本”③。
淳熙二年至三年(1175—1176年)間《家禮》草就④,然未及完稿,即在淳熙三年三月朱熹赴婺源省墓途中失竊於僧寺。關於《家禮》成書時間,朱門高足及後學者多認爲是乾道五年(1169年)或六年(1170年),該説濫觴於李方子《紫陽年譜》,李譜全帙雖早失,但其説尚留存於他人序跋及札記中,如楊復《家禮附録》引:“李方子曰:乾道五年九月,先生丁母祝令人憂,居喪盡禮,參酌古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⑤真德秀《西山讀書記》:“李方子爲《文公年譜》,今剟其要附此……(乾道)六年,先生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蓋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①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録外集》中所録此段與真德秀《讀書記》全同②,而《言行録》是采“李方子撰行實”編成,故《讀書記》及《言行録》所載即李氏《紫陽年譜》原貌。筆者以爲,李果齋言乾道五年或六年,是朱子始作《家禮》的時間,而不是其完成時間。朱門後學方大琮、李性傳由於“對李方子的文字有誤讀,没有考慮到李氏所言的時間跨度問題”③,故謬記爲《家禮》成稿時間。後世編纂的朱子諸年譜,如明汪仲魯本、葉公回本、李默本,清洪璟本等,皆云“乾道六年《家禮》成”,其臆斷訛誤因同上述。
慶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子卒於建陽縣考亭寓所,同年十一月歸葬於建陽西北唐石里(今福建省南平市黄坑鎮)大林谷九頂峰下,會葬者近千人,與葬士子將所録《家禮》副本攜來交給朱熹季子朱在,《家禮》終在遺失25年後始得歸璧。
三 《家禮》之特色及主要版本
(一)家禮之特色
《家禮》以司馬氏《書儀》爲藍本,化裁古禮,酌采衆家禮説④,在明人倫、守名分、崇愛敬的根本原則下,以“古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⑤爲指導思想,因事制禮、緣時設宜,對百姓之家日常生活中起居飲食、冠笄婚嫁、喪葬時祭等各頊禮事活動所需的儀節、陳設、器用、服飾等都進行了翔實的規定。全書綱目明了、體例完備、文字簡潔、內容詳略適度,從而形成了一個格局完善的家族禮儀系統,“使覽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①。
相較其他禮書,《家禮》於形式上的特色主要有:其一,就禮節形式安排而言,《家禮》除承襲《書儀》四禮的章節次第外,還首列“通禮”一章,冠於書首。含祠堂、深衣制度、司馬氏居家雜儀三類目頊,此三者皆是民衆旦夕所用不可缺之禮。其中,“祠堂”原屬《書儀》“喪儀”章“影堂雜儀”條;“深衣制度”本列於“冠儀”章之末;“司馬氏居家雜儀”則對應“婚儀”中“居家雜儀”。其二,《家禮》全篇分正文及注文兩部分,正文關涉儀節程序的大要,使人對禮儀的主要環節及步驟一目瞭然。朱子補述及論説則悉置“注”內,這樣不僅使禮儀排布更趨緊湊、連貫,也便於人們參考和執行。《家禮》於内容上的特色主要在於:重視宗法制度,使其與祠堂、祭田緊密相連。王懋竑曾説:“《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②就内涵而言,重視宗法思想是《家禮》的主要特徵。它“强調通過‘敬宗收族’的方法來凝聚人心”③,具體表現在祠堂制度的創設。《家禮》將唐代品官所用“家廟”及《書儀》的“影堂”演化爲“祠堂”之制,置於通篇之首,使之成爲貫穿整個《家禮》體系的主綫,朱子的深意在於反映“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④。此外,祠堂還將奉祀四世神主與提倡“宗子法”和置族產(祭田)結合起來。《家禮》規定“在家族祠堂初建之際,由家族成員從其田產中提取1/20,作爲家族祭田”①,祭田由宗子直接管理,所獲穀物佃租作爲家族共同財產用於祭祀花銷,這樣“實際上是把祭祀權與控制族產結合了起來,這就使得宗子的權力進一步擴大,地位也更加牢固,有利於維護家族秩序,收合人心,增强宗族的凝聚力與血緣關係的認同感,確保了宗法制的順利實施”②。縱觀《家禮》,雖未見專門討論宗法的章節,但全篇都圍繞家族活動的中心場所“祠堂”展開,作爲維係家族團結靈魂和紐帶作用的宗法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家禮》之主要版本
《家禮》所擬禮儀大多於古有徵且簡約易行,切近閭巷百姓的生活,故而自“唐石會葬”稿本復現以來,便屢經傳抄、刊刻,並間有對其校證、注釋、删汰、补苴及改易之作。爲此,梳爬出一個較爲清晰的《家禮》版本流衍脈絡,是此後揭示《家禮》傳播朝鮮半島歷程之管鑰。現將《家禮》主要版本分述如次。
1.石卷本:現存最早的《家禮》版本,爲上饒周復於淳祐五年(1245年)所刊的《家禮》五卷加《附録》一卷(以下簡稱“附録本”),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室(編號852),卷一至卷三爲配清影宋抄本。“附録本”抽出原來分散在《家禮》正文各條下的楊復注,並對其進行取捨改易,集作《附録》一卷,置於書末。卷首在黄榦的序文後,附有尺式、木主式等5幅禮圖,以及程頤、潘時舉的識語。該本清代曾著録於黄丕烈《百宋一廛書録》、汪士鍾《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楊紹和《楹書隅録》③,“近代以後,傅增湘曾於天津鹽業銀行庫房内見過此本,並著録於《藏園群書經眼録》一書中”①。今《孔子文化大全》《中華再造善本》及《朱子著述宋刻集成》皆將原刻本影印出版。此外,“附録本”主要還有上海圖書館善本室藏盧文弨舊藏明刻本、《四庫全書》本、光緒六年(1880年)公善堂據宋版翻刻本等。2.十卷本:現存最早的《家禮》十卷本,是楊復附注、劉垓孫增注的《纂圖集注文公家禮》(以下簡稱“增注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室藏有此版足本(編號6699),别館所藏均爲殘本。此本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均題爲宋刻②。它將原五卷本《家禮》“喪禮”卷析分爲五,“祭禮”卷析之爲二;書前有朱子親筆手書《家禮序》;大宗小宗圖、祠堂圖、深衣圖等諸多禮圖散見於各節中;楊氏附注、劉氏增注俱以陰文標注於《家禮》正文各條之下。今《中華再造善本》及《元明刻本朱子著述集成》將原刻本影印出版。此外,現存的十卷本主要還有著録於周中孚《鄭堂讀書記》的《纂圖集證文公家禮》,周氏考述“其屬元刊”③,殆元人就宋刊本《纂圖集注文公家禮》增入劉璋補注。該本的特點是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三家注文的原貌,使檢者一覽即明。上海圖書館尚有一明刻版《纂圖集注文公家禮》,亦屬劉璋補注本(此本以下簡稱“補注本”)。
3.不分卷本(一卷本);現存最早的一卷本《家禮》,是藏於“臺北故宫博物院”至正元年(1341年)日新書堂所刊黄瑞節《朱子成書》本(以下簡稱“成書本”)。黄氏於其書中彙録了10種朱子學方面的相關著述,不分卷目,《家禮》位列第六。“成書本”與“增注本”關係最爲密切,它將散見於“增注本”中的禮圖整理後統一置於卷首,並增補了11幅未有的禮圖①。除《家禮》正文及本注外,“成書本”内有楊復“附注”、劉垓孫“增注”(僅見2處)及黄瑞節自撰注解。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的《朱子成書》亦是至正元年(1341年)日新書堂刊本,惜僅剩零本,闕“喪禮治葬”至“祭禮墓祭”近一半的内容。《中華再造善本》中録有此殘本。此外,現存一卷本尚有景泰元年(1450年)善敬堂《朱子成書》本。
4.七卷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室(編號6700)藏有明刻本《文公先生家禮》七卷,此本原屬常熟瞿氏舊有,除五卷《家禮》正文外,書前增入“家禮圖”一卷,乃合宋刻散見之圖而成共28幅;書末將“通禮”中的“深衣制度”抽出,另爲《深衣考》一卷。除《深衣考》外,該本與明初《性理大全》所收《家禮》在主體内容、禮圖、注釋上全部相同。
通過對《家禮》的主要版本的簡述可知,其較爲明確的分卷系統有五卷、十卷、一卷、七卷諸類。明清後《家禮》版本日臻複雜,然大體不脱上述系統,衹是卷數分合、篇章删改上的調整。需要突出説明的是,明永樂十三年(1415年)敕修《性理大全》收纂《家禮》四卷②,兩年後《性理大全》與《四書五經大全》正式頒布天下,《家禮》由宋元以來私相傳授的禮撰升格爲體現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官修”典制。《性理大全》在其成書後四年(1419年)便傳入朝鮮①,故半島流行的《家禮》類著述,皆屬《性理大全》本之翻刻。另外明成化十年(1474年)海南瓊山人丘濬作《家禮儀節》八卷,其以五卷本《家禮》爲考釋底本,於朱子本注外益以儀節、書式、祝文、考證、按语及明代俗禮等。《家禮儀節》刊行後,逐步取代《家禮》而廣行於世,並通過朝鮮使臣的購書渠道在16世紀初東傳至朝鮮半島,丘氏之説遂蔚然成風。此後,借助李朝政府的頒印及兩班貴族的踐履,《家禮》及其相關羽翼之作,以强勢的姿態在朝鮮社會滲透,從而開啟了禮學領域中國漢籍域外傳播的新局面。
第二節 《朱子家禮》朝鮮化溯程②
《家禮》在中國多被當作工具書,雖有名分上的“一尊”地位,却始終佇於多元化的評價體系中③。伴隨著朱子學遭逢“慶元黨禁”等政治桎梏,陽明心學、乾嘉漢學的思想衝擊,諸類意識形態的變動包含禮學思想的轉向,造成民衆對《家禮》的疑義甚至蔑棄。明中期以降,《家禮》的施用陷入困頓,難以貼近黎庶階層。入清後漢人薙髮易服,民間禮法崩壞,《家禮》提倡的冠、婚、喪、祭之制更是被《大清通禮》《大清會典》篡改的面目全非,“《家禮》一書,世多不行,學士亦往往不肯求觀,而坊間所看率皆俗本”④。
不同於中國分散、間斷的禮學範式,向來作爲中國藩屬,素有“小中華”之譽的朝鮮,則“將中國經學的研究定義在相對單一、獨立、自成宗派的空間當中”①。由古朝鮮的原始多神崇拜,到統一新羅時期的佛儒並立,再到高麗末的辟佛揚儒乃至李朝的唯朱子獨尊,朝鮮半島最終完成了將移植自中國,以程朱理學爲代表新儒學本土化、庶民化的歷程。
一 《朱子家禮》東傳之初
公元918年,王建推翻弓裔政權建立高麗朝,接受國師道詵的建議,將王權與佛教的神權相結合,立佛教为国教,推行儒佛道並用、互为表裹的多元化治國方针,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以儒治世。單就儒學發展來説,以朱子學的傳入爲前後期的分水嶺,前期“約370多年的儒學是以漢唐儒學爲基本内容,後一百多年的儒學則以朱子學爲主,又稱性理學”②。具體析之,前期高麗儒學其學風專主辭章、訓詁,旨在獲得文論寫作技能與積累經史知識。執政者感興趣的“主要是詩歌禮樂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對於用中國禮制來移風易俗,則不以爲然”③。此間,在思想界佔支配地位的仍是佛教,“而儒教則恒常趨附佛教驥尾”④。然至高麗末葉,王朝版蕩,國政糜爛,北有蒙元武力脅迫及經濟壓榨,南有倭寇肆意侵襲殺掠。統治階級内部矛盾日趨激化,土地所有關係混亂,私田日增,造成了“父母凍餒而不能養,妻子離散而不能保,無告流亡,户口一空”⑤的人倫慘劇。加之時日已久的佞佛之習,產生了衆多大莊園經濟豪寺,恶僧败髡驕奢淫逸,佛教界流弊百出,以致斥佛之聲日漸高漲,“爲了挽救國家和民族危機,安定人民之生活,迫切需要有新的統治思想。朱子學正是適應這種需要而引進並普及的”①。
“經與禮,一遵朱子,無敢少差。”②作爲朱子禮學落腳點之一的《家禮》,值此風雲際會之時,經由忠烈王(1275—1308年)臣子集賢殿大學士安珦(1243—1306年)之手,裹挾在朱子學東遷的浪潮中,傳入了動蕩飄搖的朝鮮半島③。《家禮》所凸顯的冠、婚、喪、祭四禮之規範,要而不煩、明快簡易,展現了儒家禮儀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對於在全社會層面消除佛教積弊,匡救世道人心,推行儒家禮俗最爲便捷。故而自《家禮》傳入之初,即爲白頤正、權溥、禹倬、李齊賢、李穡等儒者所注目,且以身爲天下先,起而踐行之。圃隱鄭夢周遭父喪,依《家禮》所定的守孝制度,“廬墓三年,東國之俗爲之一變”④。此後他更是“令士庶仿《朱子家禮》,立家廟,奉先祀”⑤。鄭夢周可謂士林階級中將《家禮》之制付諸實踐的第一人,李朝成俔(1439—1504年)曾高度評價他説:“自三國高麗以來,專奉釋氏,家廟之制不明,士大夫皆不以禮祀先。自圃隱文忠公倡明道學,嚴立祭祀之儀,然後家家立祠堂,始傳家舍於嫡嗣,始重嫡庶之分,無子者必取族子以爲嗣。國家大享用孟月,士大夫時享用四仲月,是有序也。”①除鄭夢周外,同期儒者趙浚、文益漸、鄭習仁、尹龜生、全五倫等,皆將《家禮》儀文施用於治喪、祭祀諸活動。恭讓王二年(1390年)《家禮》正式爲王廷所接納,並以政府律令的形式强制推行。據載,高麗依《家禮》制定了大夫至庶人各階層立家廟和明祭禮的法令:“判大夫以上祭三世,六品以上祭二世,七品以下至於庶人止祭父母,並立家廟……行禮儀式,一依《朱文公家禮》,随宜損益。三年(1391年)六月己巳,命申行家廟之制。”②雖然《家禮》中有關喪祭的禮儀已成法制,但正如《高麗圖經》所説:“其實污僻澆薄,厖雜夷風,終未可革也。冠、婚、喪、祭,鮮克由禮。”③《家禮》的影響力尚未達至民間。
由上可窺知,高麗後期《家禮》的初步引入、認識和傳播,顯得零散且不成體系,此時的《家禮》僅在少數儒者或士大夫間仿行,其“未能推廣於天下,故按官職身份之等次區分,漸次推行”④。但作爲半島學術思想史上的重大轉變,《家禮》的東傳爲此後李氏朝鮮的完全儒家化提供了理論基礎,標志着一個新時代——“家禮學”時代的即將到來。
二《朱子家禮》在李朝之受容與開展
通過高麗朝近百年的引進、傳播、理解,逮到朝鮮太祖李成桂(1392—1398年)以儒教立國,迄至最後一位君主純宗李坧李朝之初“‘崇儒排佛’政策在理論和制度上開始確立,佛教受到批判和壓抑”①。基此背景,新王朝將《家禮》視爲蕩滌佛教殘弊,建立儒家化鄉風民俗的樞要。鮮初至成宗(1470—1494年)末,《家禮》和國俗交互參照融合,《經國大典》《國朝五禮儀》編成,標志着以六典爲代表的國家行政體系和以五禮爲代表的王室禮制正式確立。李朝統治階層爲推廣《家禮》,令國內各階層都熟悉其內容儀式,采取了以下幾種方式:首先,王庭率先遵照履行《家禮》法度,如太祖1408年薨,“治喪一依《朱子家禮》”②;世宗六年(1424年)“王女虞祭,請依《文公家禮》,以魂魄返魂行三虞祭”③等。其次,政府還大力刊行《家禮》及相關禮書,如太宗三年(1403年),“分賜《朱文公家禮》於各司,印《家禮》一百五十部於平壤府而頒之”④。又如成宗二年(1471年),“又今諸道廣刊《小學》《三綱行實》等書,教民誦習”⑤。世宗大王創制朝鮮文字後,諺文版儒教倫理籍册進一步向全社會普及。再次,重視家廟奉祀之制。高麗末期,部分地區已設立有家廟,李朝延續和擴展了這一趨勢,並在此基礎上制定了相關的懲罰措施,“願自今刻日立廟,敢有違令,尚循舊弊者,令憲司糾理”①。最後,爲了推廣《家禮》的傳習,太宗三年(1403年)將《家禮》作爲人才登用的考試科目。以上諸多舉措促使了時人在思想上對《家禮》的重視。總體來説,朝鮮的15世紀,是“國家鼓勵實行在高麗末期與性理學一起引進的《朱子家禮》的時期……是國家建立法和禮的同時開始實行家禮的時期”②。以兩班、士林爲代表的統治階層致力於《家禮》生活化,而民間信仰及舊式生活習俗的保留,使得《家禮》並未深入半島各個階層。
16世紀初中宗李懌(1506—1544年)之後的兩百年間,以退溪李滉爲宗的嶺南學派和以栗谷李珥爲宗的畿湖學派迭起,《家禮》在庶民生活中得以進一步推行,“邦國之遠,閭巷之僻,家無不有,人莫不講矣”③。其間,朝鮮碩學一本《家禮》之説,彙成了爲數可觀的考辨、通論、問答、禮説、祝辭等羽翼之作。誠如阿部吉雄所云:“其(朝鮮朱子學者)禮論無非是與《家禮》相關的,時俗也大多依從《家禮》,這是史家所公認的。因此,《家禮》的注釋纂述之書可謂汗牛充棟。”④沙溪金長生《家禮輯覽》《喪禮備要》,尤庵宋時烈《尤庵先生問答》《尤庵先生禮説》,市南俞棨《家禮源流》,陶庵李縡《四禮便覽》,星湖李瀷《家禮疾書》,鏡湖李宜朝《家禮增解》,茶山丁若鏞《喪禮節要》《禮疑問答》等專著相繼問世。禮學大儒就《家禮》的記録及闡發,促進了“家禮學”研究的體系化及普世化,造就了卷帙宏富、異彩紛呈的禮經著述,朝鮮禮學“從行禮層次轉至學問的層次”①,壬辰倭亂及丙子胡亂等家國危機亦未能使之中斷。
英祖(1725—1776年)之後,隨着《國朝續五禮儀》《國朝續五禮儀補》《國朝喪禮補編》等禮典不斷編修和補充,《家禮》淡化了对王權的約束力。然而《家禮》研究却漸趨大衆化,禮學的述論不再僅是部分性理大儒的特權,斯時的煌煌禮書大多未得刊印,憑靠寫本流傳閭里,一些禮書著者及書寫年亦無據可考。同時,禮籍的書寫方式也不再衹局限於《家禮》式“四禮”研究的範疇,還擴延到對古禮本源問題的探討。如夏時贊《八禮節要》、趙鎮球《儀禮九選》、張錫英《九禮笏記》、宋俊弼《六禮修略》等書,在冠、婚、喪、祭之外,尚關涉有鄉射、鄉飲酒、士相見、投壺等禮説。此外,除兩班貴族外的朝鮮中人或平民依賴自身經濟實力的提升,在鄉黨應酬及宗族關係中也開始重點關注並研究《家禮》所涉及的儀節、祝辭、禮器等具體事務,《家禮》深入社會底層,樵叟野老皆曉儀文禮式,其真正成爲朝鮮半島的“垂世大典”②。
要之,《家禮》朝鮮化過程中具有自身鮮明的特色:一則李朝整個政治體系和國家機構都建立在以《家禮》爲中軸的禮學基礎之上,於内聖外王的過程中,實現了“道統”與“政統”的結合,完成了禮學的法制化,“政教合一所產生的‘禮學’,對於大一統的朝鮮封建王朝的迅速形成和發展起到了相當有效的作用。‘禮’相當於當時人爲的‘法’的作用”③。二則禮學研究始終處於相對穩定、封閉的發展狀態,即所謂一切皆由《家禮》而衍生。“《家禮》式之四禮研究風氣頗盛”①,且突出集中在以“慎終追遠”爲旨意的喪、祭二禮上。《家禮》類著述打破了以注釋及札録爲形式的初步研究,擴展至辨證、類聚、折衷爲主的方法論層面。三則《家禮》在與韓民族自身文化特色、儀禮制度衝突和融合的过程中,既達到了革除鄙陋、齊一朝鮮民俗的效果,又“吸收朝鮮半島固有文化傳統和生活習俗中的合理成分,使之與《家禮》的禮學原則對接”②。通過兩班官僚的實踐躬行及不同身份等差民衆間的篤信遵循,“家禮學”逐步趨向土著化、庶民化、大衆化,並深深融匯到國人的血脈和靈魂之中。
三《韓國禮學叢書》所含朝鮮時代禮經考略
朝鮮時代禮學主要圍繞《家禮》展開,既有針對《家禮》文句的基礎性札録和注釋,又有依托其禮學精神並結合朝鮮半島國情及禮俗的高層次禮論。禮學研究成果洋洋大觀,而不見經傳者更是無法估量,即便朝鮮目録學大家李圭景在面對這些鬱鬱巨著時也歎息説:“此外禮説所漏,未嘗知詳有幾家,隨得随録,以便考閲,兼作證辨也。”③加之禮書寫本和刻本存留、搜集、編纂難度較高,從而造成漢學界對朝鮮禮籍,特别是《家禮》類著述的通盤整理及全面統計仍處於模棱不清的境況中。而《韓國禮學叢書》(以下簡稱《叢書》)的出版則基本囊括了朝鮮諸儒及門人的禮俗成果,全面反映了朝鮮禮學研究的盛況,這是收録集成域外禮經漢籍工作中規模最大、網羅最豐富的一次。
《叢書》由韓國慶星大學校(KyungsungUniversity)韓國學研究所編輯整理,分爲正編(包括前編和續編)、補遺兩部分,正編凡122册,收録禮學家125人(其中10人未詳),禮書163種。補遺的編纂尚未告罄,後續還會有邦國禮、鄉禮、學校禮等刊出,就目前所收目録來看,已有16册,禮學家21人(1人未詳),禮書22種。《叢書》收録的文本以木刻本和寫本爲主,也有少量的石本、古活字、鉛活字、新活字、木活字、全史字及影印本。纂者將這批文獻重新影印裝訂,每册前附有《發刊詞》《解題》及新編目録。由於文獻傳遞的延後性,現可檢視的《叢書》主要爲正編部分120册①,禮書共155種。《叢書》選録的著作特點有二:首先,就其時段性來看,大致可分爲朝鮮王朝前中期(1475—1850年,約成宗至憲宗時期)、19世紀後(1850—1950年,約哲宗至純宗時期)兩個階段。前中期的著作在士庶間的影響力較大,而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前期這百年間的禮學著作,或散佚難觀,或作者未詳。其次,就其内容上來看,又可分爲以下幾點。
1.禮書之中獨重《家禮》。以《家禮》爲綱目並與之密切相關的禮書著作佔較大比重——約40%,它們或直接冠有“家禮”二字,或以“四禮”爲名。如曹好益《家禮考證》、金長生《家禮輯覽》、安■《家禮附贅》、柳慶輝《家禮輯説》、辛夢參《家禮輯解》、李衡祥《家禮便考》、李瀷《星湖先生家禮疾書》、金鍾厚《家禮集考》、李宜朝《家禮增解》、張福樞《家禮補疑》、金秉宗《聞韶家禮》、李恒福《四禮訓蒙》、李縡《四禮便覽》、魏道僩《四禮祝辭常變通解》、李震相《四禮輯要》等。
2.《家禮》之中重喪、祭二禮,尤重喪禮。儒家倫理之中,特重“慎終追遠”,因而古來禮經都十分重視喪禮和祭禮。這種格局在《叢書》中也有體現。如李彦迪《奉先雜儀》、金誠一《喪禮考證》、金長生《喪禮備要》、李象靖《決訟場補》、丁若鏞《喪禮四箋》及《二禮鈔》、金恒穆《喪禮輯解》、朴建中《初終禮要覽》、禹德鄰《二禮演輯》、綏山《廣禮覽》等。其中《訣訟場補》《二禮鈔》《廣禮覽》等書將冠、婚二禮的內容作爲附録呈於書末,冠、婚與喪、祭孰輕孰重,自不待言。
3.問答、禮説别具一格。“我東賢儒輩出,禮學大明,疑而有問,問而有解,又或有自爲著説,雖其詳略同異之不齊,而要皆爲參互援據之資”①,某些賢哲在治禮過程中,弟子或師友獻疑解惑,往復申辯探討,原本錯出於文集或雜著中,先生易簀後門人及後學重新抄録,裒輯而成專書。此類書有李滉《退溪先生喪祭禮問答》、鄭逑《寒岡先生四禮問答彙類》、李惟樟《二先生禮説》、朴世采《南溪先生禮説》、朴胤源《近齋禮説》、丁若鏞《禮疑問答》等。
4.韓國本土化的諺解、懸吐。《叢書》中雖然衹存申湜《家禮諺解》、白斗鏞《懸吐士小節》、南宫濬《懸吐詳注喪祭類抄》和金東縉《諺文喪禮》②四種,但它們的重要性不容小覷。諺解是用韓國自創的字母系統對漢字進行通俗的解釋;懸吐則是在漢文文句後加上朝鮮語符號,從而起到標識句讀及表明句子成分和詞性的作用。《懸吐士小節·序》:“字法硬澀,淺見服識難以曉解,心齋白君斗鏞慨文獻之淆灕,廣裒我東書籍,校訛而鋟梓者幾汗牛之背。而又摭此書逐處懸諺而句節之。”③這類禮書的出現,一方面説明禮學傳入朝鮮後開始慢慢本土化,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説明朱子《家禮》已經深入社會的各個階層,除了能夠熟練使用漢字的士儒大夫階層外,平常之家也在踐行《家禮》。
5.《家禮》之外兼及古禮。《叢書》中雖然《家禮》系列佔絕對的數量,但仍有小部分典籍是對《周禮》《儀禮》《禮記》等古禮進行考證,或是讀這些禮書的紙頭札記。如金尚憲《讀禮隨鈔》專事《禮記》,許穆《禮經類纂》:“本之以《禮記》,參之以《周禮》,會之以注疏,辨之以衆説。”①趙鎮球《儀禮九選》、張錫英《儀禮集傳》則是專門對《儀禮》一門的注説,而朴世采《六禮疑輯》、夏時贊《八禮節要》、郭鍾錫《六禮笏記》、朴文鎬《四禮集儀》、宋俊弼《六禮修略》、宋在奎《禮笏》等都是在朱子《家禮》之外,另附鄉飲酒禮、鄉射禮、士相見禮、投壺禮、邦禮、學校禮等而成。
如前所揭,李朝歷史上與禮學研究相關的傳世著述,《叢書》大抵已納十之七八。其雖皆以《家禮》爲研究主軸,然各家又自有側重。總言之,有的重於疏通文字、判别句讀、詮解基本名詞。這類著作原本便是爲學力薄弱者減少閲讀障礙而作,抑或是普及《家禮》時的講稿;有的重於補苴器物、人員、文書格式,並闡釋名物度數、形制及位序等。在此過程中秉持著變通且貼合朝鮮風土的原則,避免了因器妨禮;有的重於申明禮義,以冠責成人,以婚正匹偶,以喪考慎毖,以祭盡誠敬,從而最終達到律身正家、匡正陋俗的目的。
第三節 《叢書》特色“諸具”解題
曾子云“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則爲有司之末事。然一如李秉遠《冠禮考定·跋》所説:“器服名物之間,尚多有未盡通曉者,況可望究其禮而責其實乎?”②禮學之難在於“名物度數”繁複瑣細,大義奧旨難明,加之《家禮》傳至朝鮮,方域有别、異名迭出、殊類科迥、文獻闕徵、物證難求等因素,多數物目早已不爲後世所熟諳。而酌於名物器數的精確把握,在朝鮮王朝篇帙浩穰的祖述《家禮》類禮説中,孕育產生了“諸具”這一獨一無二的文獻記録形式。它將行禮所需修造預備的禮器、物具,輔助指引儀式實施的人員和禮節往來的文書格式,以全備且細微的面貌呈現了出來。文字表意不明處還配以圖繪,以圖彰其形,使“諸具”具象化,體現了强烈的視覺感和現場感。在禮式和實物殆已迷昧的今天,“諸具”文圖的保留對於研究、復原禮儀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一 “諸具”的定性
對於未曾在中國禮書中出現的“諸具”項,首先要明確其所指。然而如何給“諸具”下一個確切的定義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單從語法結構來看,“諸具”作爲偏正短語,它與“諸位”“諸人”“諸事”相似,而後者因爲使用廣泛,早已被《漢語大詞典》收録,有了約定俗成的意義。而“諸具”脱離上下文,我們就無從了解其指代的具體對象。如孫文臣《對祭星判》:“既俎豆而式陳,冀珪璧而必薦。諸具已備,惟玉未陳。謂監祀而罔知,何糾事而斯當。”①引文中“諸具”指俎豆、珪璧等祀神供祖所需陳列的祭品。再如,馮夢龍《甲申紀事》:“發李、戈兩僞將,嚴刑追比。有炮烙、腦箍、夾棍諸具,血肉滿前,以資笑樂。”②“諸具”指代“炮烙、腦箍、夾棍”等殘酷刑具。
單審“具”字,在漢語語境中很容易理解爲“用具”“器械”,進而“諸具”被詮釋爲“諸般用具、器械”。但在《叢書》中,“諸具”頊下除了涵蓋儀節進程中使用到的用具、器械外,還常常包含舉行禮儀的處所、佐助人員、飲食車馬、服飾章采及動植物等。探尋其語源,《説文·升部》:“具,共置也。從升,從貝省。”即準備、備辦之義,“具”僅僅表示動作的發出,並未指明具體的施用對象。因此從“具”的本義出發,將“諸具”解釋爲“諸般需要備辦“諸具”在《叢書》中以固定的名稱出現,首推李縡《四禮便覽》:“家禮諸具之見載於本注者,或欠詳備,故别爲蒐輯,且采世俗之所遵行者以附於每條之下。”①據李縡所説,將行禮過程中的各個器具單獨列出是他的創舉。其實不然,早在金長生《喪禮備要》中“喪具”一頊便已專列,“凡喪具略書容入之數,雖或不中亦不甚遠。且名目之難以文字爲解者,直用俗名,使倉猝易曉”②。禮儀進行所需的物品人員在《家禮》正文及注文中都有臚列,但專門提煉出來,歸納彙集,放在每條之前,在朝鮮確實是金長生的首創。③同時作爲韓國禮學一代宗師的沙溪金氏,爲了解決家禮於朝鮮民衆中踐行的現實問題,他因民之便、量民之力,對喪、祭二禮諸具熔舊鑄新,進行了合乎半島民衆實用的改造。並且不憚煩瑣,對諸具數目、式樣、結構、作用等都進行了詳明的闡釋。然而作爲“諸具”文化的發軔者,該書並非盡善盡美,一方面,對於“諸具”頊的命名,金氏以各儀節名爲標識,定爲“×之具”或“×具”,如“初終之具”“易服之具”“襲具”“奠具”等,諸具雖已成體例,然未有確名;另一方面,金氏獨取喪、祭二禮,冠、婚二禮並未涉獵,割裂了《家禮》文本的完整性。而後李縡《四禮便覽》在沿用金氏體例的基礎上,將諸具條目拓展到四禮當中,並移於儀節之後,每物目下剖析考訂越發精研,“諸具”最終從經文中分離並凝固成項。至此,我們在針對禮經中器具、人員進行考證時,統一采用李縡之定名,以“諸具”爲稱。
《叢書》中將“諸具”全部或部分摘出,一並置於儀節之前或之後進行考證的共有37種禮書。分别是《喪禮備要》《改葬備要》《疑禮通考》《四禮便覽》《禮疑類輯》《家禮增解》《九峰瞽見》《四禮類會》《喪禮四箋》《竹僑便覽》《士儀》《士儀節要》《二禮演輯》《喪禮便覽》《全禮類輯》《家禮補疑》《廣禮覽》《四禮輯要》《臨事便考》《四禮節略》《增補四禮便覽》《喪祭類抄》《四禮汰記》《四禮纂笏》《六禮修略》《四禮提要》《四禮要選》《四禮常變纂要》《常變輯略》《四禮撮要》《禮笏》《喪祭禮抄》《四禮要覽》《二禮便考》《二禮通考》《四禮儀》《補遺喪祭禮抄》。其他禮書雖未單列,然皆在行文中對需要辨考的具體事頊,旁引曲證,參互諸説異同,給予了切要的詮釋。如《常變通考》中“勒帛非行縢”“魂帛用同心結及雜制之非”“瀝青無益”條。
“諸具”項被李朝學者關注,其研究逐漸隆盛的原因,可自兩方面觀之:一則爲斯時研究深入化、專門化的必然趋势。隨着性理學的開展,體現《家禮》細枝末節的物用禮器、祝辭、書式、禮圖等,從經文中分離而自成體系,《家禮》研究邁入學術化的境界,名物諸具成爲群儒争相探討的對象。再則由於世人實踐《家禮》的迫切需要。有宋一朝與朝鮮時代相較,天異時,地異勢,古今異制,若想使《家禮》成爲李朝民衆讀之易懂、據之可行的儀軌,禮器諸具聽熒不明,遑論行禮之順暢。禮書中“諸具”一目稽考的强勁勢頭,正是解禮、行禮的先提條件。
二 “諸具”研究的價值
張伯偉先生曾談及一門新學問的成立,需滿足若干條件:具備豐富的材料來源,能夠提出新的問題以及相應的新方法、新理論。①本書研究《家禮》在朝鮮傳播中產生的“諸具”頊,使用的“新材料”——《韓國禮學叢書》並非傳統常見的域内經籍,而是數百年來不爲國内學界所知的域外文獻;同時“諸具”項並不見於中國的禮學論著,且不爲學術界所關注,是一個“新問題”。作爲“域外漢學”這一方興未艾的新學問的一個支脈,“諸具”研究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價值。
首先,對於朝鮮時代《家禮》中“諸具”的疏證,填補了學術的空白。《家禮》自清以降少人問津,中國的禮器研究涉及《家禮》處更是少之又少,比之《周禮》《儀禮》《禮記》著述如山、學者如林的盛況不啻雲泥之别。歷代禮書中更無“諸具”一頊,與之相關的名物考釋類辭書,如《中國古代名物大典》《三禮辭典》《中國古代器物大詞典》等,其編纂多致力於其得名由來、形制體貌,於具體的適用範圍、數量序列及改换調整等情況未曾涉及。而依托於《韓國禮學叢書》,通過對《家禮》中“諸具”的董理,對於出土文獻、文物互證,相關禮學、民俗辭書的編纂,以及儀節形式的再現均有十分重要的借鑒價值。
其次,從文化學角度對禮書中“諸具”的研究,是對“小學”尤其是文字、訓詁之學的一次傳統回歸。許嘉璐先生在《漢字闡釋與文化傳統》的序言中提出,訓詁學、文字學必須向文化學領域延伸。他指出在學術由綜合走向分析的過程中,是以“小學”脱離文化爲代價的,然而文化是傳統“小學”產生和發展的土壤,“小學”本身即爲文化的闡釋而產生。因此“‘小學’觀照文化學,從文化學和廣泛的文化現象中吸收營養,同時文化學得到‘小學’這一利器的幫助可以挖掘得更深,更接近真實,這種雙向的介入和靠攏,或者稱之爲交叉、滲透,是歷史的必然”①。“諸具”雖是開放在朝鮮禮書中的一朵奇葩,然追溯其源,又與中國禮學傳統關涉頗深。通過“諸具”疏證過程中訓詁、文字、音韻學的綜合運用,揭櫫同一部著作——《家禮》,在中朝兩種文化環境中不同的學術發展脈絡及學術旨趣:中國重闡釋,故《家禮》學多爲腳注之學;朝鮮重實踐,故將“諸具”單獨采摭。中國重傳承,故自宋至清皆秉《家禮》爲聖經不敢妄自改换;朝鮮重變通,“諸具”或承或易、或删或增,皆以朝鮮國俗爲準繩。中國《家禮》與國禮多相分離;朝鮮《家禮》與國禮融合交匯、互相制約等。
最後,朝鮮《家禮》中的“諸具”,其文獻載體是漢字,當我們對其進行觀察和研究的視野超越“一鄉一國”,將其作爲禮學整體研究乃至東亞漢字文化圈中的一部分,所得出的結論必定具有不同以往的意義,“域外漢籍的價值就不衹是中國典籍的域外延伸,不衹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現,不衹是‘吾國之舊籍’的補充增益。它們是漢文化之林的獨特品種,是作爲中國文化的對話者、比較者和批判者的‘異域之眼’”①。因此,“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②,摒棄固有的以中國爲本體的單綫性研究方式,以“諸具”爲契機,回考中國《家禮》於版本、文字、禮圖、名物考證上的不足,做到“禮失而求諸野”。
另外,《叢書》“諸具”疏證也爲越南、日本等國的《家禮》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和參照。以此爲基點,描繪出《家禮》在整個東亞漢字文化圈中傳承和演變的脈絡。不同的地域和民族群體,對同一種文獻的解讀和實踐——對禮義的闡釋與生發、對禮儀的增益與減損,都自有其秉持的基準和變通的法則。惟有在“全視角”的高度,纔能從根本上把握“禮”的價值和本質。從構建這樣一個“全視角”的圖景出發,本書願成爲日本、越南等國《家禮》研究的引玉之磚。
本章係以《家禮》爲依歸,探賾索隱,考其著述淵源、歷程、內容特色,並就該書真僞及版本問題作扼要的引介,以期對《家禮》完整之概念有通盤的了解。其次剖析是書東傳朝鮮半島之内因外緣,查檢其土著化、庶民化、大衆化之流衍始末。最末,針對補苴《家禮》類禮書中朝鮮化的“諸具”頊,參酌群經,旁及史典,剔抉爬梳,勾繪出“諸具”在遞嬗過程中的大致輪廓。
第一節 《朱子家禮》源流考鏡
一《家禮》一書真僞問題
《朱子家禮》又名《朱文公家禮》《文公家禮》《家禮》等。“據《四庫全書》的著録統計,朱子現存的著作共二十五種,六百餘卷,總字數在二千萬字左右”①,《家禮》比諸朱子旁論,篇幅最爲精微,然却是其接受人群最廣的禮學讀本,亦是最具争議的著述之一,其癥結主要集中在《家禮》真僞問題上。舉以言之,分述如下。
(一)《家禮》係他人“僞竄”説
楊復云:“《家禮》始成而失之,不及再加考訂。先生既没而書始出。”②《家禮》初成即爲僧童竊去,未得先生匡正,故而引致僞作之嫌。據楊士奇《跋文公家禮》及丘濬《文公家禮儀節》(以下簡稱《儀節》)所載,元末至正年間(1341—1370年),武林人應本(字中甫)作《家禮辨》③,首倡《家禮》非朱子手編,斷其出於門人附會。迄至清初,疑古辨僞風潮漸盛,白田王懋竑重申應氏之説,作《朱子年譜考異》《家禮考》《家禮後考》《家禮考誤》,更於《家禮考》開首以“《家禮》非朱子之書也”④爲確論,出陳例證數十則,引古禮及諸説相辯難。
王氏的疑竇從內容角度考察,突出强調《家禮》與《儀禮》《司馬氏書儀》(以下簡稱《書儀》)等舊典及朱子晚時學術論斷的不合之處,且《家禮》自身内容亦存在前後矛盾之處。從文獻記載角度考察,王氏關注點在於除李方子《紫陽年譜》載《家禮》成書於乾道六年(1170年)外,並没有其他關於《家禮》完成具體年月的確切表述;且除了《朱子文集》卷75載《家禮序》外,朱子的其他著述中從未提及《家禮》的編纂,基於此王氏將《家禮序》也視作僞竄之作。
王説厥後爲《四庫全書總目》采納,並於“家禮五卷附録一卷”條全盤承襲,云:“是書之不出朱子,可灼然無疑。”①由於《四庫總目》的官修權威性,經此裁斷,僞作説遂成定論。然近代沿用兹説者甚鮮,直至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他一反學界駁應詰王之風,試圖從“《家禮》內部考察,伸張王説,以期引起更深層之討論”②。其述論從《家禮》文本毫末處入手,呈列疑誤舉要十則,指出《家禮》虚擡宗法、喪服制度、儀節錯亂、昧於經義、前後不照、取捨失當等諸多錯謬③,從而讞決《家禮》之水準尚下於《書儀》,斷不能歸於晦庵名下。
(二)《家禮》係朱子“草就而未定”説
應、王之説一出,時賢訟奪即興。然“僞作説”由於鮮有後人提出進一步佐證,故清後逐步式微。相反,自丘濬《儀節》及夏炘《述朱質疑·跋家禮》分别對照應、王二説,按次摘録並提出相應的糾辨,肯定《家禮》爲朱子所撰這一事實後,今人錢穆、高明、上山春平、陳來、束景南、吾妻重二諸學者亦拳拳於《家禮》成書真僞問題之證①,他們一方面依循先賢路徑,釐析過往論説中史料釋讀的正繆得失;另一方面廣泛搜羅考訂朱子親筆詩文書札,以及朱門高弟所述的序跋、語録、傳記,企圖勾稽《家禮》成書過程中朱子思想的流變;此外,還參酌現存版本系統,勘校文字異同,追溯《家禮》原貌,裁斷其被後人竄亂改易之處。
對於上述學人的論辯往還,此不贅言,僅就確認《家禮》是否爲朱子所作不可規避之兩點稍加闡明,一則宋刊本《纂圖集注文公家禮》卷首翻刻有朱子親筆《家禮序》一篇;二則朱子後嗣及門人於其生前便知《家禮》“草定”,佚而復出,經弟子取用刊行。
就結論而言,正如黄榦《朱子行狀》:“所輯《家禮》,世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②及陳淳《代陳憲跋家禮》:“惜其書既亡而復出,不出於先生無恙之前,而出於先生既没之後,不幸而不能垂爲一定之成儀以幸萬世,而反爲未成之缺典,至貽後世千古無窮之恨,甚可痛也!”③采照較妥帖的説法,《家禮》稿本確係朱子草定,然修整未訖便被付梓流布,故文本内容間有與朱子晚歲語論相牴牾之處。後世“不僅其弟子曾有臆補增改,且宋元以來被人竄亂移易”④。兹如現今通行的永樂十三年(1415年)敕修《性理大全》本《家禮》,其卷首所載28幅家禮圖便是原封蹈襲元黄瑞節所撰《朱子成書》①。此即學者語及《家禮》,不免是非相眩、議論多歧的根源。
綜而述之,由於至今無法覓得朱子《家禮》初稿底本,關鍵史料缺失,一味汲汲追尋《家禮》真僞之謎,終究未能定讞。筆者傾向於在研究《家禮》播遷朝鮮半島致使其社會意識形態儒家化的進程中,應將《家禮》看作朱熹學術體系中不可剥離的有機組成部分。②
二 《家禮》之撰述背景及歷程
“家禮”一詞最早出現於《周禮·春官·家宗人》:“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掌家禮與其衣服、宫室、車旗之禁令。”表示貴族大夫采邑内所需遵循的法則,後用以通指私家常用之禮儀規範,“六朝時已有之,或曰書儀,或曰家禮,名目異耳”③。由於朱子《家禮》的駸駸始盛,此後獨擅朱子撰著之專名。本節主要以朱子編撰《家禮》之背景及其著作歷程爲着力點,考察如下。
(一)朱子編撰《家禮》之背景
1.社會關係變遷,禮下庶人
唐末五代兵革不息,世道衰微,禮廢樂壞,“庶人服侯服,墙壁被文繡。公卿與皂隸同制,倡優下賤得爲后飾。昏冠喪祭、宫室器用,家殊俗異,人自爲制,無復綱紀”①。門閥等級性的宗族制解體,家庭組織結構形態發生變化。隨着士族退出歷史舞臺,寒門庶族借科舉躋身政治權力的中心,貴賤等差觀念日趨淡漠,門第高下的界限逐漸消失。此外,宋代以来社會結構和政治格局發生重大改變,“庶人在數量上占人口的絕大多數,經濟上擔負着社會絕大部分的生產勞動。文化方面,也成爲重要的創造者;政治上,則是官府不能忽視的最廣大的社會基礎”②。庶人社會地位的提升,“迫切需要與其政治地位、經濟狀況相適應的禮學禮制來滿足其社會生活的需要”③。於是禮由以往貴族階層的文化特權,向社會下層轉移,完成了“禮下庶人”的平民化轉捩。其標志是徽宗所頒《政和五禮新儀》,第一次在官方禮典中單列了針對庶民階層的禮儀條文。而司馬光《書儀》及朱子《家禮》等籍册,也是在政府企圖通過緩驅以令、勸曉以文、使民徐而知禮的大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2.古禮難明,且不合時宜,私家禮範興起
《儀禮》等古禮文本最早記載了關於古代家庭的禮儀規範,在宋代禮樂復興運動的浪潮中,儒者提倡重新審視和挖掘古禮的精神內涵,以期來穩定社會人倫秩序,規範民衆道德行爲,對抗釋老以及民間信仰的浸染。然而古禮距宋已久,且其文義古奧、名物度數難詳、儀節煩瑣細碎,自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依王安石的提議更定科舉科目廢置《儀禮》後④,研治古禮者更是寥若晨星。朱子也曾感歎道:“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家。”⑤爲了使古制禮法在民間切實可行,依“從俗、從衆、從便”的原則,因情循俗地對其進行删改變通是迫在眉睫的事情。另外,唐宋後禮書編纂“重心由公禮轉向到家禮”①,宋代公卿士大夫中的有識之士,洞悉朝廷禮文缺陋不行的現狀,繼承六朝以來的家禮制訂傳統,積極關注和修撰私家禮儀規範②,其著述主要有司馬光《書儀》及《温公家範》、張載《横渠張氏祭儀》、范祖禹《祭儀》、葉夢得《石林家訓》、袁采《袁氏世範》、高閌《送終禮》、陸九韶《陸氏家制》等。此中,司馬光《書儀》可謂“前期家禮、書儀長期醞釀發展後一次示範性的集成”③,除記載有關表奏、公文、書信格式外,還涉及“冠儀、婚儀、喪儀(含‘祭’在内)”等内容。全書以《儀禮》爲本,芟蕪存要,與時俱變,第一次爲士民禮書設定了冠、婚、喪、祭四禮爲基礎的框架結構,亦爲後世家禮的格局及世俗化開了先河。但由於對庶民接受禮的知識水平,及實踐禮的經濟能力缺乏明晰的估量,在民衆中推行《書儀》時頻頻遭受冷遇。綜之,古禮的不合時宜,私家禮書的無所折衷、難以推用,均爲朱子《家禮》這一符合時代緊迫性和社會必要性的新禮書的編纂提出了要求。
(二)《家禮》之撰述歷程
朱熹措意於禮學,並留心搜集整理考訂諸家禮説,蓋緣起於紹興十三年(1143年)其父朱松病逝的早年人生經歷。他與弟子談及時曾説:“某自十四歲而孤,十六而免喪。是時祭祀,只依家中舊禮,禮文雖未備,却甚齊整。先妣執祭事甚虔。及某年十七八,方考訂得諸家禮,禮文稍備。”①
後二十餘年,其母祝氏於乾道五年(1169年)九月辭世,同年《祭儀》稿成。朱子自紹興十七年(1147年)編《祭儀》初稿,經與張栻、吕祖謙、林用中、汪應辰等人的函商及反復修訂,在其母喪年《祭儀》終成。②《祭儀》分祭説、祭儀、祝詞三卷,體例上未分綱目,《祭儀》爲《家禮》之最早雛形,其内容亦被《家禮》所吸收,故陳淳稱其爲《家禮》的“最初本”③。
淳熙二年至三年(1175—1176年)間《家禮》草就④,然未及完稿,即在淳熙三年三月朱熹赴婺源省墓途中失竊於僧寺。關於《家禮》成書時間,朱門高足及後學者多認爲是乾道五年(1169年)或六年(1170年),該説濫觴於李方子《紫陽年譜》,李譜全帙雖早失,但其説尚留存於他人序跋及札記中,如楊復《家禮附録》引:“李方子曰:乾道五年九月,先生丁母祝令人憂,居喪盡禮,參酌古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⑤真德秀《西山讀書記》:“李方子爲《文公年譜》,今剟其要附此……(乾道)六年,先生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蓋自始死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共爲一編,命曰《家禮》。”①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録外集》中所録此段與真德秀《讀書記》全同②,而《言行録》是采“李方子撰行實”編成,故《讀書記》及《言行録》所載即李氏《紫陽年譜》原貌。筆者以爲,李果齋言乾道五年或六年,是朱子始作《家禮》的時間,而不是其完成時間。朱門後學方大琮、李性傳由於“對李方子的文字有誤讀,没有考慮到李氏所言的時間跨度問題”③,故謬記爲《家禮》成稿時間。後世編纂的朱子諸年譜,如明汪仲魯本、葉公回本、李默本,清洪璟本等,皆云“乾道六年《家禮》成”,其臆斷訛誤因同上述。
慶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子卒於建陽縣考亭寓所,同年十一月歸葬於建陽西北唐石里(今福建省南平市黄坑鎮)大林谷九頂峰下,會葬者近千人,與葬士子將所録《家禮》副本攜來交給朱熹季子朱在,《家禮》終在遺失25年後始得歸璧。
三 《家禮》之特色及主要版本
(一)家禮之特色
《家禮》以司馬氏《書儀》爲藍本,化裁古禮,酌采衆家禮説④,在明人倫、守名分、崇愛敬的根本原則下,以“古禮減殺,從今世俗之禮”⑤爲指導思想,因事制禮、緣時設宜,對百姓之家日常生活中起居飲食、冠笄婚嫁、喪葬時祭等各頊禮事活動所需的儀節、陳設、器用、服飾等都進行了翔實的規定。全書綱目明了、體例完備、文字簡潔、內容詳略適度,從而形成了一個格局完善的家族禮儀系統,“使覽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①。
相較其他禮書,《家禮》於形式上的特色主要有:其一,就禮節形式安排而言,《家禮》除承襲《書儀》四禮的章節次第外,還首列“通禮”一章,冠於書首。含祠堂、深衣制度、司馬氏居家雜儀三類目頊,此三者皆是民衆旦夕所用不可缺之禮。其中,“祠堂”原屬《書儀》“喪儀”章“影堂雜儀”條;“深衣制度”本列於“冠儀”章之末;“司馬氏居家雜儀”則對應“婚儀”中“居家雜儀”。其二,《家禮》全篇分正文及注文兩部分,正文關涉儀節程序的大要,使人對禮儀的主要環節及步驟一目瞭然。朱子補述及論説則悉置“注”內,這樣不僅使禮儀排布更趨緊湊、連貫,也便於人們參考和執行。《家禮》於内容上的特色主要在於:重視宗法制度,使其與祠堂、祭田緊密相連。王懋竑曾説:“《家禮》重宗法,此程、張、司馬氏所未及。”②就内涵而言,重視宗法思想是《家禮》的主要特徵。它“强調通過‘敬宗收族’的方法來凝聚人心”③,具體表現在祠堂制度的創設。《家禮》將唐代品官所用“家廟”及《書儀》的“影堂”演化爲“祠堂”之制,置於通篇之首,使之成爲貫穿整個《家禮》體系的主綫,朱子的深意在於反映“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④。此外,祠堂還將奉祀四世神主與提倡“宗子法”和置族產(祭田)結合起來。《家禮》規定“在家族祠堂初建之際,由家族成員從其田產中提取1/20,作爲家族祭田”①,祭田由宗子直接管理,所獲穀物佃租作爲家族共同財產用於祭祀花銷,這樣“實際上是把祭祀權與控制族產結合了起來,這就使得宗子的權力進一步擴大,地位也更加牢固,有利於維護家族秩序,收合人心,增强宗族的凝聚力與血緣關係的認同感,確保了宗法制的順利實施”②。縱觀《家禮》,雖未見專門討論宗法的章節,但全篇都圍繞家族活動的中心場所“祠堂”展開,作爲維係家族團結靈魂和紐帶作用的宗法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家禮》之主要版本
《家禮》所擬禮儀大多於古有徵且簡約易行,切近閭巷百姓的生活,故而自“唐石會葬”稿本復現以來,便屢經傳抄、刊刻,並間有對其校證、注釋、删汰、补苴及改易之作。爲此,梳爬出一個較爲清晰的《家禮》版本流衍脈絡,是此後揭示《家禮》傳播朝鮮半島歷程之管鑰。現將《家禮》主要版本分述如次。
1.石卷本:現存最早的《家禮》版本,爲上饒周復於淳祐五年(1245年)所刊的《家禮》五卷加《附録》一卷(以下簡稱“附録本”),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室(編號852),卷一至卷三爲配清影宋抄本。“附録本”抽出原來分散在《家禮》正文各條下的楊復注,並對其進行取捨改易,集作《附録》一卷,置於書末。卷首在黄榦的序文後,附有尺式、木主式等5幅禮圖,以及程頤、潘時舉的識語。該本清代曾著録於黄丕烈《百宋一廛書録》、汪士鍾《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楊紹和《楹書隅録》③,“近代以後,傅增湘曾於天津鹽業銀行庫房内見過此本,並著録於《藏園群書經眼録》一書中”①。今《孔子文化大全》《中華再造善本》及《朱子著述宋刻集成》皆將原刻本影印出版。此外,“附録本”主要還有上海圖書館善本室藏盧文弨舊藏明刻本、《四庫全書》本、光緒六年(1880年)公善堂據宋版翻刻本等。2.十卷本:現存最早的《家禮》十卷本,是楊復附注、劉垓孫增注的《纂圖集注文公家禮》(以下簡稱“增注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室藏有此版足本(編號6699),别館所藏均爲殘本。此本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及《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均題爲宋刻②。它將原五卷本《家禮》“喪禮”卷析分爲五,“祭禮”卷析之爲二;書前有朱子親筆手書《家禮序》;大宗小宗圖、祠堂圖、深衣圖等諸多禮圖散見於各節中;楊氏附注、劉氏增注俱以陰文標注於《家禮》正文各條之下。今《中華再造善本》及《元明刻本朱子著述集成》將原刻本影印出版。此外,現存的十卷本主要還有著録於周中孚《鄭堂讀書記》的《纂圖集證文公家禮》,周氏考述“其屬元刊”③,殆元人就宋刊本《纂圖集注文公家禮》增入劉璋補注。該本的特點是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三家注文的原貌,使檢者一覽即明。上海圖書館尚有一明刻版《纂圖集注文公家禮》,亦屬劉璋補注本(此本以下簡稱“補注本”)。
3.不分卷本(一卷本);現存最早的一卷本《家禮》,是藏於“臺北故宫博物院”至正元年(1341年)日新書堂所刊黄瑞節《朱子成書》本(以下簡稱“成書本”)。黄氏於其書中彙録了10種朱子學方面的相關著述,不分卷目,《家禮》位列第六。“成書本”與“增注本”關係最爲密切,它將散見於“增注本”中的禮圖整理後統一置於卷首,並增補了11幅未有的禮圖①。除《家禮》正文及本注外,“成書本”内有楊復“附注”、劉垓孫“增注”(僅見2處)及黄瑞節自撰注解。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的《朱子成書》亦是至正元年(1341年)日新書堂刊本,惜僅剩零本,闕“喪禮治葬”至“祭禮墓祭”近一半的内容。《中華再造善本》中録有此殘本。此外,現存一卷本尚有景泰元年(1450年)善敬堂《朱子成書》本。
4.七卷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室(編號6700)藏有明刻本《文公先生家禮》七卷,此本原屬常熟瞿氏舊有,除五卷《家禮》正文外,書前增入“家禮圖”一卷,乃合宋刻散見之圖而成共28幅;書末將“通禮”中的“深衣制度”抽出,另爲《深衣考》一卷。除《深衣考》外,該本與明初《性理大全》所收《家禮》在主體内容、禮圖、注釋上全部相同。
通過對《家禮》的主要版本的簡述可知,其較爲明確的分卷系統有五卷、十卷、一卷、七卷諸類。明清後《家禮》版本日臻複雜,然大體不脱上述系統,衹是卷數分合、篇章删改上的調整。需要突出説明的是,明永樂十三年(1415年)敕修《性理大全》收纂《家禮》四卷②,兩年後《性理大全》與《四書五經大全》正式頒布天下,《家禮》由宋元以來私相傳授的禮撰升格爲體現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官修”典制。《性理大全》在其成書後四年(1419年)便傳入朝鮮①,故半島流行的《家禮》類著述,皆屬《性理大全》本之翻刻。另外明成化十年(1474年)海南瓊山人丘濬作《家禮儀節》八卷,其以五卷本《家禮》爲考釋底本,於朱子本注外益以儀節、書式、祝文、考證、按语及明代俗禮等。《家禮儀節》刊行後,逐步取代《家禮》而廣行於世,並通過朝鮮使臣的購書渠道在16世紀初東傳至朝鮮半島,丘氏之説遂蔚然成風。此後,借助李朝政府的頒印及兩班貴族的踐履,《家禮》及其相關羽翼之作,以强勢的姿態在朝鮮社會滲透,從而開啟了禮學領域中國漢籍域外傳播的新局面。
第二節 《朱子家禮》朝鮮化溯程②
《家禮》在中國多被當作工具書,雖有名分上的“一尊”地位,却始終佇於多元化的評價體系中③。伴隨著朱子學遭逢“慶元黨禁”等政治桎梏,陽明心學、乾嘉漢學的思想衝擊,諸類意識形態的變動包含禮學思想的轉向,造成民衆對《家禮》的疑義甚至蔑棄。明中期以降,《家禮》的施用陷入困頓,難以貼近黎庶階層。入清後漢人薙髮易服,民間禮法崩壞,《家禮》提倡的冠、婚、喪、祭之制更是被《大清通禮》《大清會典》篡改的面目全非,“《家禮》一書,世多不行,學士亦往往不肯求觀,而坊間所看率皆俗本”④。
不同於中國分散、間斷的禮學範式,向來作爲中國藩屬,素有“小中華”之譽的朝鮮,則“將中國經學的研究定義在相對單一、獨立、自成宗派的空間當中”①。由古朝鮮的原始多神崇拜,到統一新羅時期的佛儒並立,再到高麗末的辟佛揚儒乃至李朝的唯朱子獨尊,朝鮮半島最終完成了將移植自中國,以程朱理學爲代表新儒學本土化、庶民化的歷程。
一 《朱子家禮》東傳之初
公元918年,王建推翻弓裔政權建立高麗朝,接受國師道詵的建議,將王權與佛教的神權相結合,立佛教为国教,推行儒佛道並用、互为表裹的多元化治國方针,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以儒治世。單就儒學發展來説,以朱子學的傳入爲前後期的分水嶺,前期“約370多年的儒學是以漢唐儒學爲基本内容,後一百多年的儒學則以朱子學爲主,又稱性理學”②。具體析之,前期高麗儒學其學風專主辭章、訓詁,旨在獲得文論寫作技能與積累經史知識。執政者感興趣的“主要是詩歌禮樂之教、君臣父子之道,對於用中國禮制來移風易俗,則不以爲然”③。此間,在思想界佔支配地位的仍是佛教,“而儒教則恒常趨附佛教驥尾”④。然至高麗末葉,王朝版蕩,國政糜爛,北有蒙元武力脅迫及經濟壓榨,南有倭寇肆意侵襲殺掠。統治階級内部矛盾日趨激化,土地所有關係混亂,私田日增,造成了“父母凍餒而不能養,妻子離散而不能保,無告流亡,户口一空”⑤的人倫慘劇。加之時日已久的佞佛之習,產生了衆多大莊園經濟豪寺,恶僧败髡驕奢淫逸,佛教界流弊百出,以致斥佛之聲日漸高漲,“爲了挽救國家和民族危機,安定人民之生活,迫切需要有新的統治思想。朱子學正是適應這種需要而引進並普及的”①。
“經與禮,一遵朱子,無敢少差。”②作爲朱子禮學落腳點之一的《家禮》,值此風雲際會之時,經由忠烈王(1275—1308年)臣子集賢殿大學士安珦(1243—1306年)之手,裹挾在朱子學東遷的浪潮中,傳入了動蕩飄搖的朝鮮半島③。《家禮》所凸顯的冠、婚、喪、祭四禮之規範,要而不煩、明快簡易,展現了儒家禮儀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對於在全社會層面消除佛教積弊,匡救世道人心,推行儒家禮俗最爲便捷。故而自《家禮》傳入之初,即爲白頤正、權溥、禹倬、李齊賢、李穡等儒者所注目,且以身爲天下先,起而踐行之。圃隱鄭夢周遭父喪,依《家禮》所定的守孝制度,“廬墓三年,東國之俗爲之一變”④。此後他更是“令士庶仿《朱子家禮》,立家廟,奉先祀”⑤。鄭夢周可謂士林階級中將《家禮》之制付諸實踐的第一人,李朝成俔(1439—1504年)曾高度評價他説:“自三國高麗以來,專奉釋氏,家廟之制不明,士大夫皆不以禮祀先。自圃隱文忠公倡明道學,嚴立祭祀之儀,然後家家立祠堂,始傳家舍於嫡嗣,始重嫡庶之分,無子者必取族子以爲嗣。國家大享用孟月,士大夫時享用四仲月,是有序也。”①除鄭夢周外,同期儒者趙浚、文益漸、鄭習仁、尹龜生、全五倫等,皆將《家禮》儀文施用於治喪、祭祀諸活動。恭讓王二年(1390年)《家禮》正式爲王廷所接納,並以政府律令的形式强制推行。據載,高麗依《家禮》制定了大夫至庶人各階層立家廟和明祭禮的法令:“判大夫以上祭三世,六品以上祭二世,七品以下至於庶人止祭父母,並立家廟……行禮儀式,一依《朱文公家禮》,随宜損益。三年(1391年)六月己巳,命申行家廟之制。”②雖然《家禮》中有關喪祭的禮儀已成法制,但正如《高麗圖經》所説:“其實污僻澆薄,厖雜夷風,終未可革也。冠、婚、喪、祭,鮮克由禮。”③《家禮》的影響力尚未達至民間。
由上可窺知,高麗後期《家禮》的初步引入、認識和傳播,顯得零散且不成體系,此時的《家禮》僅在少數儒者或士大夫間仿行,其“未能推廣於天下,故按官職身份之等次區分,漸次推行”④。但作爲半島學術思想史上的重大轉變,《家禮》的東傳爲此後李氏朝鮮的完全儒家化提供了理論基礎,標志着一個新時代——“家禮學”時代的即將到來。
二《朱子家禮》在李朝之受容與開展
通過高麗朝近百年的引進、傳播、理解,逮到朝鮮太祖李成桂(1392—1398年)以儒教立國,迄至最後一位君主純宗李坧李朝之初“‘崇儒排佛’政策在理論和制度上開始確立,佛教受到批判和壓抑”①。基此背景,新王朝將《家禮》視爲蕩滌佛教殘弊,建立儒家化鄉風民俗的樞要。鮮初至成宗(1470—1494年)末,《家禮》和國俗交互參照融合,《經國大典》《國朝五禮儀》編成,標志着以六典爲代表的國家行政體系和以五禮爲代表的王室禮制正式確立。李朝統治階層爲推廣《家禮》,令國內各階層都熟悉其內容儀式,采取了以下幾種方式:首先,王庭率先遵照履行《家禮》法度,如太祖1408年薨,“治喪一依《朱子家禮》”②;世宗六年(1424年)“王女虞祭,請依《文公家禮》,以魂魄返魂行三虞祭”③等。其次,政府還大力刊行《家禮》及相關禮書,如太宗三年(1403年),“分賜《朱文公家禮》於各司,印《家禮》一百五十部於平壤府而頒之”④。又如成宗二年(1471年),“又今諸道廣刊《小學》《三綱行實》等書,教民誦習”⑤。世宗大王創制朝鮮文字後,諺文版儒教倫理籍册進一步向全社會普及。再次,重視家廟奉祀之制。高麗末期,部分地區已設立有家廟,李朝延續和擴展了這一趨勢,並在此基礎上制定了相關的懲罰措施,“願自今刻日立廟,敢有違令,尚循舊弊者,令憲司糾理”①。最後,爲了推廣《家禮》的傳習,太宗三年(1403年)將《家禮》作爲人才登用的考試科目。以上諸多舉措促使了時人在思想上對《家禮》的重視。總體來説,朝鮮的15世紀,是“國家鼓勵實行在高麗末期與性理學一起引進的《朱子家禮》的時期……是國家建立法和禮的同時開始實行家禮的時期”②。以兩班、士林爲代表的統治階層致力於《家禮》生活化,而民間信仰及舊式生活習俗的保留,使得《家禮》並未深入半島各個階層。
16世紀初中宗李懌(1506—1544年)之後的兩百年間,以退溪李滉爲宗的嶺南學派和以栗谷李珥爲宗的畿湖學派迭起,《家禮》在庶民生活中得以進一步推行,“邦國之遠,閭巷之僻,家無不有,人莫不講矣”③。其間,朝鮮碩學一本《家禮》之説,彙成了爲數可觀的考辨、通論、問答、禮説、祝辭等羽翼之作。誠如阿部吉雄所云:“其(朝鮮朱子學者)禮論無非是與《家禮》相關的,時俗也大多依從《家禮》,這是史家所公認的。因此,《家禮》的注釋纂述之書可謂汗牛充棟。”④沙溪金長生《家禮輯覽》《喪禮備要》,尤庵宋時烈《尤庵先生問答》《尤庵先生禮説》,市南俞棨《家禮源流》,陶庵李縡《四禮便覽》,星湖李瀷《家禮疾書》,鏡湖李宜朝《家禮增解》,茶山丁若鏞《喪禮節要》《禮疑問答》等專著相繼問世。禮學大儒就《家禮》的記録及闡發,促進了“家禮學”研究的體系化及普世化,造就了卷帙宏富、異彩紛呈的禮經著述,朝鮮禮學“從行禮層次轉至學問的層次”①,壬辰倭亂及丙子胡亂等家國危機亦未能使之中斷。
英祖(1725—1776年)之後,隨着《國朝續五禮儀》《國朝續五禮儀補》《國朝喪禮補編》等禮典不斷編修和補充,《家禮》淡化了对王權的約束力。然而《家禮》研究却漸趨大衆化,禮學的述論不再僅是部分性理大儒的特權,斯時的煌煌禮書大多未得刊印,憑靠寫本流傳閭里,一些禮書著者及書寫年亦無據可考。同時,禮籍的書寫方式也不再衹局限於《家禮》式“四禮”研究的範疇,還擴延到對古禮本源問題的探討。如夏時贊《八禮節要》、趙鎮球《儀禮九選》、張錫英《九禮笏記》、宋俊弼《六禮修略》等書,在冠、婚、喪、祭之外,尚關涉有鄉射、鄉飲酒、士相見、投壺等禮説。此外,除兩班貴族外的朝鮮中人或平民依賴自身經濟實力的提升,在鄉黨應酬及宗族關係中也開始重點關注並研究《家禮》所涉及的儀節、祝辭、禮器等具體事務,《家禮》深入社會底層,樵叟野老皆曉儀文禮式,其真正成爲朝鮮半島的“垂世大典”②。
要之,《家禮》朝鮮化過程中具有自身鮮明的特色:一則李朝整個政治體系和國家機構都建立在以《家禮》爲中軸的禮學基礎之上,於内聖外王的過程中,實現了“道統”與“政統”的結合,完成了禮學的法制化,“政教合一所產生的‘禮學’,對於大一統的朝鮮封建王朝的迅速形成和發展起到了相當有效的作用。‘禮’相當於當時人爲的‘法’的作用”③。二則禮學研究始終處於相對穩定、封閉的發展狀態,即所謂一切皆由《家禮》而衍生。“《家禮》式之四禮研究風氣頗盛”①,且突出集中在以“慎終追遠”爲旨意的喪、祭二禮上。《家禮》類著述打破了以注釋及札録爲形式的初步研究,擴展至辨證、類聚、折衷爲主的方法論層面。三則《家禮》在與韓民族自身文化特色、儀禮制度衝突和融合的过程中,既達到了革除鄙陋、齊一朝鮮民俗的效果,又“吸收朝鮮半島固有文化傳統和生活習俗中的合理成分,使之與《家禮》的禮學原則對接”②。通過兩班官僚的實踐躬行及不同身份等差民衆間的篤信遵循,“家禮學”逐步趨向土著化、庶民化、大衆化,並深深融匯到國人的血脈和靈魂之中。
三《韓國禮學叢書》所含朝鮮時代禮經考略
朝鮮時代禮學主要圍繞《家禮》展開,既有針對《家禮》文句的基礎性札録和注釋,又有依托其禮學精神並結合朝鮮半島國情及禮俗的高層次禮論。禮學研究成果洋洋大觀,而不見經傳者更是無法估量,即便朝鮮目録學大家李圭景在面對這些鬱鬱巨著時也歎息説:“此外禮説所漏,未嘗知詳有幾家,隨得随録,以便考閲,兼作證辨也。”③加之禮書寫本和刻本存留、搜集、編纂難度較高,從而造成漢學界對朝鮮禮籍,特别是《家禮》類著述的通盤整理及全面統計仍處於模棱不清的境況中。而《韓國禮學叢書》(以下簡稱《叢書》)的出版則基本囊括了朝鮮諸儒及門人的禮俗成果,全面反映了朝鮮禮學研究的盛況,這是收録集成域外禮經漢籍工作中規模最大、網羅最豐富的一次。
《叢書》由韓國慶星大學校(KyungsungUniversity)韓國學研究所編輯整理,分爲正編(包括前編和續編)、補遺兩部分,正編凡122册,收録禮學家125人(其中10人未詳),禮書163種。補遺的編纂尚未告罄,後續還會有邦國禮、鄉禮、學校禮等刊出,就目前所收目録來看,已有16册,禮學家21人(1人未詳),禮書22種。《叢書》收録的文本以木刻本和寫本爲主,也有少量的石本、古活字、鉛活字、新活字、木活字、全史字及影印本。纂者將這批文獻重新影印裝訂,每册前附有《發刊詞》《解題》及新編目録。由於文獻傳遞的延後性,現可檢視的《叢書》主要爲正編部分120册①,禮書共155種。《叢書》選録的著作特點有二:首先,就其時段性來看,大致可分爲朝鮮王朝前中期(1475—1850年,約成宗至憲宗時期)、19世紀後(1850—1950年,約哲宗至純宗時期)兩個階段。前中期的著作在士庶間的影響力較大,而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前期這百年間的禮學著作,或散佚難觀,或作者未詳。其次,就其内容上來看,又可分爲以下幾點。
1.禮書之中獨重《家禮》。以《家禮》爲綱目並與之密切相關的禮書著作佔較大比重——約40%,它們或直接冠有“家禮”二字,或以“四禮”爲名。如曹好益《家禮考證》、金長生《家禮輯覽》、安■《家禮附贅》、柳慶輝《家禮輯説》、辛夢參《家禮輯解》、李衡祥《家禮便考》、李瀷《星湖先生家禮疾書》、金鍾厚《家禮集考》、李宜朝《家禮增解》、張福樞《家禮補疑》、金秉宗《聞韶家禮》、李恒福《四禮訓蒙》、李縡《四禮便覽》、魏道僩《四禮祝辭常變通解》、李震相《四禮輯要》等。
2.《家禮》之中重喪、祭二禮,尤重喪禮。儒家倫理之中,特重“慎終追遠”,因而古來禮經都十分重視喪禮和祭禮。這種格局在《叢書》中也有體現。如李彦迪《奉先雜儀》、金誠一《喪禮考證》、金長生《喪禮備要》、李象靖《決訟場補》、丁若鏞《喪禮四箋》及《二禮鈔》、金恒穆《喪禮輯解》、朴建中《初終禮要覽》、禹德鄰《二禮演輯》、綏山《廣禮覽》等。其中《訣訟場補》《二禮鈔》《廣禮覽》等書將冠、婚二禮的內容作爲附録呈於書末,冠、婚與喪、祭孰輕孰重,自不待言。
3.問答、禮説别具一格。“我東賢儒輩出,禮學大明,疑而有問,問而有解,又或有自爲著説,雖其詳略同異之不齊,而要皆爲參互援據之資”①,某些賢哲在治禮過程中,弟子或師友獻疑解惑,往復申辯探討,原本錯出於文集或雜著中,先生易簀後門人及後學重新抄録,裒輯而成專書。此類書有李滉《退溪先生喪祭禮問答》、鄭逑《寒岡先生四禮問答彙類》、李惟樟《二先生禮説》、朴世采《南溪先生禮説》、朴胤源《近齋禮説》、丁若鏞《禮疑問答》等。
4.韓國本土化的諺解、懸吐。《叢書》中雖然衹存申湜《家禮諺解》、白斗鏞《懸吐士小節》、南宫濬《懸吐詳注喪祭類抄》和金東縉《諺文喪禮》②四種,但它們的重要性不容小覷。諺解是用韓國自創的字母系統對漢字進行通俗的解釋;懸吐則是在漢文文句後加上朝鮮語符號,從而起到標識句讀及表明句子成分和詞性的作用。《懸吐士小節·序》:“字法硬澀,淺見服識難以曉解,心齋白君斗鏞慨文獻之淆灕,廣裒我東書籍,校訛而鋟梓者幾汗牛之背。而又摭此書逐處懸諺而句節之。”③這類禮書的出現,一方面説明禮學傳入朝鮮後開始慢慢本土化,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説明朱子《家禮》已經深入社會的各個階層,除了能夠熟練使用漢字的士儒大夫階層外,平常之家也在踐行《家禮》。
5.《家禮》之外兼及古禮。《叢書》中雖然《家禮》系列佔絕對的數量,但仍有小部分典籍是對《周禮》《儀禮》《禮記》等古禮進行考證,或是讀這些禮書的紙頭札記。如金尚憲《讀禮隨鈔》專事《禮記》,許穆《禮經類纂》:“本之以《禮記》,參之以《周禮》,會之以注疏,辨之以衆説。”①趙鎮球《儀禮九選》、張錫英《儀禮集傳》則是專門對《儀禮》一門的注説,而朴世采《六禮疑輯》、夏時贊《八禮節要》、郭鍾錫《六禮笏記》、朴文鎬《四禮集儀》、宋俊弼《六禮修略》、宋在奎《禮笏》等都是在朱子《家禮》之外,另附鄉飲酒禮、鄉射禮、士相見禮、投壺禮、邦禮、學校禮等而成。
如前所揭,李朝歷史上與禮學研究相關的傳世著述,《叢書》大抵已納十之七八。其雖皆以《家禮》爲研究主軸,然各家又自有側重。總言之,有的重於疏通文字、判别句讀、詮解基本名詞。這類著作原本便是爲學力薄弱者減少閲讀障礙而作,抑或是普及《家禮》時的講稿;有的重於補苴器物、人員、文書格式,並闡釋名物度數、形制及位序等。在此過程中秉持著變通且貼合朝鮮風土的原則,避免了因器妨禮;有的重於申明禮義,以冠責成人,以婚正匹偶,以喪考慎毖,以祭盡誠敬,從而最終達到律身正家、匡正陋俗的目的。
第三節 《叢書》特色“諸具”解題
曾子云“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則爲有司之末事。然一如李秉遠《冠禮考定·跋》所説:“器服名物之間,尚多有未盡通曉者,況可望究其禮而責其實乎?”②禮學之難在於“名物度數”繁複瑣細,大義奧旨難明,加之《家禮》傳至朝鮮,方域有别、異名迭出、殊類科迥、文獻闕徵、物證難求等因素,多數物目早已不爲後世所熟諳。而酌於名物器數的精確把握,在朝鮮王朝篇帙浩穰的祖述《家禮》類禮説中,孕育產生了“諸具”這一獨一無二的文獻記録形式。它將行禮所需修造預備的禮器、物具,輔助指引儀式實施的人員和禮節往來的文書格式,以全備且細微的面貌呈現了出來。文字表意不明處還配以圖繪,以圖彰其形,使“諸具”具象化,體現了强烈的視覺感和現場感。在禮式和實物殆已迷昧的今天,“諸具”文圖的保留對於研究、復原禮儀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一 “諸具”的定性
對於未曾在中國禮書中出現的“諸具”項,首先要明確其所指。然而如何給“諸具”下一個確切的定義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單從語法結構來看,“諸具”作爲偏正短語,它與“諸位”“諸人”“諸事”相似,而後者因爲使用廣泛,早已被《漢語大詞典》收録,有了約定俗成的意義。而“諸具”脱離上下文,我們就無從了解其指代的具體對象。如孫文臣《對祭星判》:“既俎豆而式陳,冀珪璧而必薦。諸具已備,惟玉未陳。謂監祀而罔知,何糾事而斯當。”①引文中“諸具”指俎豆、珪璧等祀神供祖所需陳列的祭品。再如,馮夢龍《甲申紀事》:“發李、戈兩僞將,嚴刑追比。有炮烙、腦箍、夾棍諸具,血肉滿前,以資笑樂。”②“諸具”指代“炮烙、腦箍、夾棍”等殘酷刑具。
單審“具”字,在漢語語境中很容易理解爲“用具”“器械”,進而“諸具”被詮釋爲“諸般用具、器械”。但在《叢書》中,“諸具”頊下除了涵蓋儀節進程中使用到的用具、器械外,還常常包含舉行禮儀的處所、佐助人員、飲食車馬、服飾章采及動植物等。探尋其語源,《説文·升部》:“具,共置也。從升,從貝省。”即準備、備辦之義,“具”僅僅表示動作的發出,並未指明具體的施用對象。因此從“具”的本義出發,將“諸具”解釋爲“諸般需要備辦“諸具”在《叢書》中以固定的名稱出現,首推李縡《四禮便覽》:“家禮諸具之見載於本注者,或欠詳備,故别爲蒐輯,且采世俗之所遵行者以附於每條之下。”①據李縡所説,將行禮過程中的各個器具單獨列出是他的創舉。其實不然,早在金長生《喪禮備要》中“喪具”一頊便已專列,“凡喪具略書容入之數,雖或不中亦不甚遠。且名目之難以文字爲解者,直用俗名,使倉猝易曉”②。禮儀進行所需的物品人員在《家禮》正文及注文中都有臚列,但專門提煉出來,歸納彙集,放在每條之前,在朝鮮確實是金長生的首創。③同時作爲韓國禮學一代宗師的沙溪金氏,爲了解決家禮於朝鮮民衆中踐行的現實問題,他因民之便、量民之力,對喪、祭二禮諸具熔舊鑄新,進行了合乎半島民衆實用的改造。並且不憚煩瑣,對諸具數目、式樣、結構、作用等都進行了詳明的闡釋。然而作爲“諸具”文化的發軔者,該書並非盡善盡美,一方面,對於“諸具”頊的命名,金氏以各儀節名爲標識,定爲“×之具”或“×具”,如“初終之具”“易服之具”“襲具”“奠具”等,諸具雖已成體例,然未有確名;另一方面,金氏獨取喪、祭二禮,冠、婚二禮並未涉獵,割裂了《家禮》文本的完整性。而後李縡《四禮便覽》在沿用金氏體例的基礎上,將諸具條目拓展到四禮當中,並移於儀節之後,每物目下剖析考訂越發精研,“諸具”最終從經文中分離並凝固成項。至此,我們在針對禮經中器具、人員進行考證時,統一采用李縡之定名,以“諸具”爲稱。
《叢書》中將“諸具”全部或部分摘出,一並置於儀節之前或之後進行考證的共有37種禮書。分别是《喪禮備要》《改葬備要》《疑禮通考》《四禮便覽》《禮疑類輯》《家禮增解》《九峰瞽見》《四禮類會》《喪禮四箋》《竹僑便覽》《士儀》《士儀節要》《二禮演輯》《喪禮便覽》《全禮類輯》《家禮補疑》《廣禮覽》《四禮輯要》《臨事便考》《四禮節略》《增補四禮便覽》《喪祭類抄》《四禮汰記》《四禮纂笏》《六禮修略》《四禮提要》《四禮要選》《四禮常變纂要》《常變輯略》《四禮撮要》《禮笏》《喪祭禮抄》《四禮要覽》《二禮便考》《二禮通考》《四禮儀》《補遺喪祭禮抄》。其他禮書雖未單列,然皆在行文中對需要辨考的具體事頊,旁引曲證,參互諸説異同,給予了切要的詮釋。如《常變通考》中“勒帛非行縢”“魂帛用同心結及雜制之非”“瀝青無益”條。
“諸具”項被李朝學者關注,其研究逐漸隆盛的原因,可自兩方面觀之:一則爲斯時研究深入化、專門化的必然趋势。隨着性理學的開展,體現《家禮》細枝末節的物用禮器、祝辭、書式、禮圖等,從經文中分離而自成體系,《家禮》研究邁入學術化的境界,名物諸具成爲群儒争相探討的對象。再則由於世人實踐《家禮》的迫切需要。有宋一朝與朝鮮時代相較,天異時,地異勢,古今異制,若想使《家禮》成爲李朝民衆讀之易懂、據之可行的儀軌,禮器諸具聽熒不明,遑論行禮之順暢。禮書中“諸具”一目稽考的强勁勢頭,正是解禮、行禮的先提條件。
二 “諸具”研究的價值
張伯偉先生曾談及一門新學問的成立,需滿足若干條件:具備豐富的材料來源,能夠提出新的問題以及相應的新方法、新理論。①本書研究《家禮》在朝鮮傳播中產生的“諸具”頊,使用的“新材料”——《韓國禮學叢書》並非傳統常見的域内經籍,而是數百年來不爲國内學界所知的域外文獻;同時“諸具”項並不見於中國的禮學論著,且不爲學術界所關注,是一個“新問題”。作爲“域外漢學”這一方興未艾的新學問的一個支脈,“諸具”研究具有以下三方面的價值。
首先,對於朝鮮時代《家禮》中“諸具”的疏證,填補了學術的空白。《家禮》自清以降少人問津,中國的禮器研究涉及《家禮》處更是少之又少,比之《周禮》《儀禮》《禮記》著述如山、學者如林的盛況不啻雲泥之别。歷代禮書中更無“諸具”一頊,與之相關的名物考釋類辭書,如《中國古代名物大典》《三禮辭典》《中國古代器物大詞典》等,其編纂多致力於其得名由來、形制體貌,於具體的適用範圍、數量序列及改换調整等情況未曾涉及。而依托於《韓國禮學叢書》,通過對《家禮》中“諸具”的董理,對於出土文獻、文物互證,相關禮學、民俗辭書的編纂,以及儀節形式的再現均有十分重要的借鑒價值。
其次,從文化學角度對禮書中“諸具”的研究,是對“小學”尤其是文字、訓詁之學的一次傳統回歸。許嘉璐先生在《漢字闡釋與文化傳統》的序言中提出,訓詁學、文字學必須向文化學領域延伸。他指出在學術由綜合走向分析的過程中,是以“小學”脱離文化爲代價的,然而文化是傳統“小學”產生和發展的土壤,“小學”本身即爲文化的闡釋而產生。因此“‘小學’觀照文化學,從文化學和廣泛的文化現象中吸收營養,同時文化學得到‘小學’這一利器的幫助可以挖掘得更深,更接近真實,這種雙向的介入和靠攏,或者稱之爲交叉、滲透,是歷史的必然”①。“諸具”雖是開放在朝鮮禮書中的一朵奇葩,然追溯其源,又與中國禮學傳統關涉頗深。通過“諸具”疏證過程中訓詁、文字、音韻學的綜合運用,揭櫫同一部著作——《家禮》,在中朝兩種文化環境中不同的學術發展脈絡及學術旨趣:中國重闡釋,故《家禮》學多爲腳注之學;朝鮮重實踐,故將“諸具”單獨采摭。中國重傳承,故自宋至清皆秉《家禮》爲聖經不敢妄自改换;朝鮮重變通,“諸具”或承或易、或删或增,皆以朝鮮國俗爲準繩。中國《家禮》與國禮多相分離;朝鮮《家禮》與國禮融合交匯、互相制約等。
最後,朝鮮《家禮》中的“諸具”,其文獻載體是漢字,當我們對其進行觀察和研究的視野超越“一鄉一國”,將其作爲禮學整體研究乃至東亞漢字文化圈中的一部分,所得出的結論必定具有不同以往的意義,“域外漢籍的價值就不衹是中國典籍的域外延伸,不衹是本土文化在域外的局部性呈現,不衹是‘吾國之舊籍’的補充增益。它們是漢文化之林的獨特品種,是作爲中國文化的對話者、比較者和批判者的‘異域之眼’”①。因此,“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②,摒棄固有的以中國爲本體的單綫性研究方式,以“諸具”爲契機,回考中國《家禮》於版本、文字、禮圖、名物考證上的不足,做到“禮失而求諸野”。
另外,《叢書》“諸具”疏證也爲越南、日本等國的《家禮》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和參照。以此爲基點,描繪出《家禮》在整個東亞漢字文化圈中傳承和演變的脈絡。不同的地域和民族群體,對同一種文獻的解讀和實踐——對禮義的闡釋與生發、對禮儀的增益與減損,都自有其秉持的基準和變通的法則。惟有在“全視角”的高度,纔能從根本上把握“禮”的價值和本質。從構建這樣一個“全視角”的圖景出發,本書願成爲日本、越南等國《家禮》研究的引玉之磚。
附注
①朱熹:《朱子語類》卷84《禮一》,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877頁。
②朱傑人:《〈朱子家禮〉解讀——以婚禮爲例》,《歷史文獻研究》第30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頁。
③玄燁:《御製朱子全書序》,《序跋》,《朱子全書》第27册,第845頁。
①《朱子全書·前言》,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8頁。
②楊復:《家禮附録》,《家禮》,《朱子全書》第7册,第947頁。
③武林應氏名諱,考自黄潛《應中甫墓誌銘》及楊士奇《東里續集》。《家禮辨》其文亡佚,丘濬於《儀節》中約略謄其大意。此外,學者湯勤福認爲《家禮》僞書説的“首創者”應追溯到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的“陳櫟”。(見湯勤福《半甲集》下,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510頁)應氏爲肇端已是學界共識,湯氏之説姑且識之,可作另參。
④王懋竑:《白田雜著》卷2《家禮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5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62頁。
①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81頁。
②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文史》第3輯,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363頁。
③彭林:《朱子作〈家禮〉説考辨》,第370—382頁。
①近現代以來關於《家禮》真僞問題的著述和文論,肖永明、殷慧《朱熹禮學研究綜述》(《朱子學刊》第20輯,黄山書社2010年版,第38—48頁)、周鑫《〈朱子家禮〉研究回顧與展望》(《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12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32—446頁)及毛國民《〈朱子家禮〉真僞考的歷史回顧與探索》(《現代哲學》2018年第1期)中有較爲全面的彙總,可以參閲。
②黄榦:《黄勉齋先生文集》卷8《朝奉大夫文華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叢書集成初編》第2410册,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87頁。
③陳淳:《北溪大全集》卷14《代陳憲跋家禮》,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6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09頁。
④束景南:《朱熹〈家禮〉真僞考辨》,《朱熹佚文輯考》,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84頁。
①誠如丘濬《儀節》中所述“文公《家禮》五卷而不聞有圖,今刻本載於卷首而不言作者”。卷首圖示爲何人贅入,直至日本學者吾妻重二的闡發和考訂才得以解惑:“家禮圖”的編者即黄瑞節。具體可參考《性理大全の成立と朱子成書》(《名古屋大學中國哲學論集》2006年第5號)及《朱熹〈家禮〉實證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88—91頁)。
②與國内討論《家禮》真僞兩方相持不下的局面不同,朝鮮半島學者幾乎都篤信《家禮》出於朱熹手作,且不同身份等差的民衆將其儀節條目作爲行禮的圭臬,躬親踐行。因此本書在以朝鮮半島所存的《家禮》類禮經著述爲研究材料時,面對《家禮》是否爲朱熹所作的問題,采信朝鮮學人的觀點。
③章太炎:《國學概論》,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72頁。
①宋徽宗:《政和五禮新儀·原序》,《政和五禮新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4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頁。
②楊志剛:《中國禮儀制度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03頁。
③惠吉興:《宋代禮學研究》,河北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頁。
④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卷38《學校科舉之制》,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371頁。
⑤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3《跋三家禮範》,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920頁。
①張文昌:《唐宋禮書研究——從公禮到家禮》,轉引自趙克生《修書、刻圖與觀禮:明代地方社會的家禮傳播》,《中國史研究》2010年第1期。
②彭林先生曾説:“至遲從隋代起,就已有私家儀注出現。”(見彭林《中國禮學在古代朝鮮的播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頁)入宋後,修撰私家儀注之風更熾,撰述的禮書煌煌可見,且形成了更爲完備、更具特色的禮學範式。兩宋私家制禮的簡況可參閲姚永輝《從“偏向經注”到“實用儀注”:〈司馬氏書儀〉與〈家禮〉之比較——兼論兩宋私修士庶儀典的演變》(《孔子研究》2014年第2期)一文。
③吕振宇:《〈家禮〉源流編年輯考》,博士學位論文,華東師範大學,2013年,第2頁。
①朱熹:《朱子語類》卷90《禮七》,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052頁。
②《祭儀》成稿時間,據陳來先生《朱子〈家禮〉真僞考議》“《祭禮》小考”一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3期]及其《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增訂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考證,朱子《祭儀》完成於喪母之前。而束景南先生認爲《祭儀》完成於朱母去世同年(參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22頁)。本書采束先生之説,將陳先生所説作另論旁參,以俟後考。
③陳淳:《北溪大全集》卷14《代陳憲跋家禮》,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6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08頁。
④《家禮》草就於淳熙年間之説,參酌束景南先生《朱熹年譜長編》卷上“始作家禮”條(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43—545頁)。
⑤楊復:《家禮附録》,《家禮》,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947頁。
①真德秀:《西山讀書記》卷31《朱子傳授》,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70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122頁。
②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録外集》卷12,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4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74頁。
③陳國代:《文獻家朱熹:朱熹著述活動及其著作版本考察》,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27。
④釐清《家禮》内容上取自經傳及各家禮説處,可參閲盧仁淑《朱子家禮與韓國之禮學》一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0頁)。
⑤朱熹:《朱子語類》卷84《論修禮書》,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886頁。
①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3《跋三家禮範》,《朱子全書》第24册,第3920頁。
②王懋竑:《白田雜著》卷2《家禮考》,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5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63頁。
③趙振:《中國歷代家訓文獻敘録》,齊魯書社2014年版,第86頁。
④朱熹:《家禮》卷1《通禮》,《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經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影印宋刻本。
①李啟成:《外來規則與固有習慣:祭田法制的近代轉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9頁。
②高會霞:《理學與社會》,長春出版社2011年版,第87頁。
③王燕均:《〈家禮〉新題解》,《版本目録學研究》第2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頁。
①徐德明:《朱熹著作版本源流考》,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頁。
②國圖所藏《纂圖集注文公家禮》(編號6699)被《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藏園群書經眼録》《中華再造善本書總目提要(金元編)》及冀淑英、張國風等先生定爲元刊本,吾妻重二根據《刻誌石》一節“有宋”的字樣,加之元初《朱子成書》所收《家禮》引用了劉垓孫的注,裁定爲宋刊。吾妻重二氏論説充分,今從(參看吾妻重二《朱熹〈家禮〉實證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頁)。
③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6《經部三之四·禮類四》,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92—93頁。
①《朱子成書》本較“增注本”新添的禮圖有:家廟之圖、深衣冠履之圖、婚禮親迎之圖、衿鞶笥楎椸圖、斬衰杖屨圖、齊衰杖屨圖、喪祭器具之圖、喪轝圖、三父八母服制之圖、櫝韜藉式、櫝式。
②所謂《性理大全》係明胡廣等人奉成祖之命編纂,成書於永樂十三年(1415年)。全書凡70卷,雜匯宋儒之説120家,集宋代理學著作與理學家言論之大成。《性理大全》中《家禮》居18至21卷,它蹈襲了《朱子成書》本《家禮》的内容結構,其分卷如下:卷一家禮圖,卷二家禮序、通禮、冠禮、婚禮,卷三喪禮,卷四喪禮(始自“虞祭”)、祭禮。
①劉寶全:《明初〈性理大全〉的刊行及其在朝鮮的傳播》,《朝鮮·韓國歷史研究》第1輯,延邊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08頁。
②本書所稱的“朝鮮”,即“朝鮮王朝”,又稱爲“李氏朝鮮”,簡稱“李朝”,指的是1392年李成桂廢王氏高麗恭讓王所建立的王朝1910年被日本吞併,李朝遂亡。下不出注。
③參閲楊志剛《明清時代〈朱子家禮〉的普及與傳播》中“《朱子家禮》‘一尊’地位及在多元評價中的延續”一節(載臺灣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經學研究集刊》2010年第9期,第35—39頁)。
④賀瑞麟:《重刻朱子家禮原本書後》,光绪六年(1880年)西安省城重刊馬雜貨鋪藏板,第2頁。
①彭衛民:《〈家禮〉朝鮮化與朝鮮王朝的中華觀》,碩士學位論文,西南政法大學,2014年,第17頁。
②李甦平:《韓國儒學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頁。
③彭林:《中國古禮與朝鮮半島的儒家化》,《中國文哲研究通訊》2001年第11卷第4期,第43頁。
④[韓]玄相允:《朝鮮思想史》,轉引自[韓]盧仁淑《朱子家禮與韓國之禮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頁。
⑤[韓]鄭麒趾:《高麗史》卷78《志》卷第32《食貨一》“田制”條,首爾大學奎章閣藏本。
①朱七星:《朱子學在朝鮮的傳播與影響》,《朱子學新論——紀念朱熹誕辰860週年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1930—1990)》,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版,第641頁。
②[韓]洪大容:《湛軒書外集》卷7《燕記·孫蓉洲》,[韓]林基中編《燕行録全集》第49册,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年版,第105頁。
③《家禮》東傳至朝鮮半島的時間及關鍵人物,史書失載。多數韓國、日本及國内學者認爲是在高麗王朝末期,即13世紀末,通過遣元使臣安珦於燕京獲得並攜入朝鮮半島。另有學者張品瑞(《〈朱子家禮〉與朝鮮禮學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1年第1期)及喻小紅、姜波等(《〈朱子家禮〉在韓國的傳播與影響》,《西南科技大學學報》2016年第1期)認爲《家禮》在南宋寧宗嘉定十七年(高麗高宗十一年,即1224年),通過民間傳播渠道,由朱熹曾孫朱潛浮海東傳至朝鮮半島。筆者看來,在討論《家禮》朝鮮化過程問題時,《家禮》東傳時間及人物已不重要,可先存而不論。
④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00頁。
⑤[韓]鄭麒趾:《高麗史》卷117《列傳》卷第30“鄭夢周”條,首爾大學奎章閣藏本。
①[韓]成俔:《慵齋叢話》卷8《大東野乘》,朝鮮古書刊行會1909年版,第639—640頁。
②[韓]鄭麒趾:《高麗史》卷63《志》卷第17《禮五》“大夫士庶人祭禮”條,首爾大學奎章閣藏本。
③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22《雜俗一》,《叢書集成初編》第3238册,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75頁。
④[韓]鄭仁在:《朱子學在韓國的展開》,黄俊傑、林維傑編《東亞朱子學的同調與異趣》,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317頁。
(1907—1910年)爲政的518年間,《家禮》成爲李朝27位統治者革除流弊、構建王朝禮制儀軌、重整地方社會秩序、延續文化脈絡的理論武器及精神依托。
①[韓]柳承國:《韓國儒學與現代精神》,姜日天、朴光海譯,東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93頁。
②《太宗實録》卷15,《李朝實録》第3册,日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54年版,第239頁。
③《世宗實録》卷23,《李朝實録》第7册,日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56年版,第343頁。
④《太宗實録》卷6,《李朝實録》第2册,日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54年版,第342頁。
⑤[韓]弘文館編:《增補文獻備考》卷84《禮考三十一》,朝鮮隆熙二年(1908年)鉛印本。
①《太祖實録》卷11,《李朝實録》第1册,日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53年版,第418頁。
②[韓]高英津:《朝鮮時代的國法和家禮》,高明士編《東亞傳統家禮、教育與國法(二):家内秩序與國法》,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04頁。
③[韓]辛夢參:《家禮輯解·序》,韓國慶星大學校韓國學研究所編《韓國禮學叢書》第25册,民族文化圖書出版社2008年版,第7頁。
④[日]阿部吉雄:《關於文公家禮》,服部先生古稀祝賀紀念論文集刊行會編《服部先生古稀祝賀紀念論文集》,富山房1936年版,第37頁。
①[韓]裴相賢:《〈朱子家禮〉及其在韓國的實踐》,《漢學研究》第1集,中國和平出版社1996年版,第386頁。
②[韓]李植:《澤堂先生别集》卷5《家禮剥解·序》,韓國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88輯,景仁文化社1992年版,第337頁。
③張敏:《韓國思想史綱》,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頁。
①[韓]盧仁淑:《朱子家禮與韓國之禮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頁。
②彭林:《中國禮學在古代朝鮮的播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頁。
③[韓]李圭景:《家禮辨證説》,《五洲衍文長箋散稿·經史篇·經史雜類》,首爾東國文化社1959年版,第1051頁。
①參看附録一:本書取用《韓國禮學叢書》表。
①[韓]朴聖源:《禮疑類輯·序》,《韓國禮學叢書》第45册,民族文化圖書出版社2008年版,第19頁。
②《諺文喪禮》位列《叢書》正編第122册,筆者所見僅爲前120册,故暫存目待驗。
③[韓]白斗鏞:《懸吐士小節·序》,《韓國禮學叢書》第114册,民族文化圖書出版社2011年版,第481頁
①[韓]许憲:《禮經類纂·跋》,《韓國禮學叢書》第10册,民族文化圖書出版社2008年版,第357頁。
②[韓]李秉遠:《冠禮考定·跋》,《韓國禮學叢書》第57册,民族文化圖書出版社2008年版,第103頁。
①周紹良主編:《全唐文新編》第2部第3册,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614頁。
②馮夢龍輯:《甲申紀事》卷6《燕都日紀》,魏同賢主編《馮夢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370的人、事、物”較爲妥帖,這也恰合了《叢書》中“諸具”項所涉的物類。
①[韓]李縡:《四禮便覽·凡例》,《韓國禮學叢書》第40册,民族文化圖書出版社2008年版,第6頁。
②[韓]金長生:《喪禮備要·凡例》,《韓國禮學叢書》第4册,民族文化圖書出版社2008年版,第528頁。
③追溯“諸具”類輯的本源,起於明儒丘濬《家禮儀節》所擬設“合用之人”“合備之物”,見下文第一章第一節。
①張伯偉:《作爲方法的漢文化圈》,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7頁。
②陳寅恪:《王静安先生遺書·序》,《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頁。
①黄德寬、常森:《漢字闡釋與文化傳統》,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頁。
①具體參看張伯偉《域外漢籍研究——一個嶄新的學術領域》,《學習與探索》2006年第2期。他在《新材料·新問題·新方法——域外漢籍研究三階段》(《史學理論研究》2016年第2期)中,又重申“三新”作爲域外漢籍研究三階段的重要性,可一並參閲。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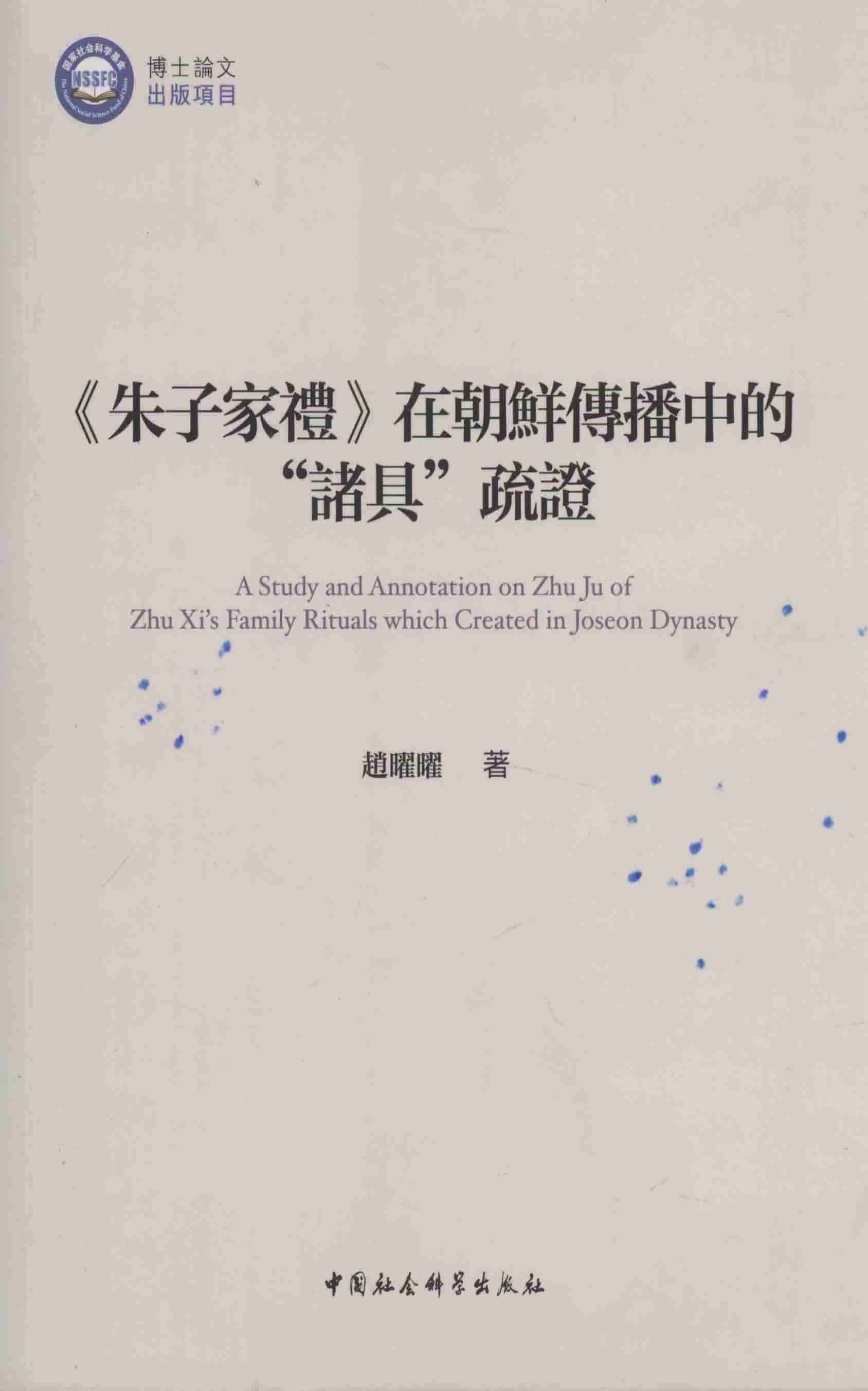
《《朱子家禮》在朝鮮傳播中的“諸具”疏證》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共分五章。首章,推究朝鲜时代礼书中“诸具”这一名目产生、发展、定型之过程。其中第二至五章,依通、冠、婚、祭礼的次序,将提炼的“诸具”作爲词头,着重稽考《丛书》较《家礼》衍变及创发的物具,分三端进行细化的处理:第一,所谓“创发”者,即《家礼》文本所无,凭半岛民俗所用而增设。所增之物,皆有本源可考,未敢有一字赘入。第二,所谓“删汰”者,即《家礼》所载服器已不合朝鲜之用,或李朝世人更不知其爲何物,故需依后贤议论对部分“诸具”进行裁革。“诸具”的适时删减,体现了礼因时、因俗而变的原则。第三,所谓“衍变”者,主要是指“诸具”名称、位置、形制、隆杀等,与《家礼》描述相去甚远,《丛书》或改换俗用,或係以俗称,或补充所明。结语部分从器物性质上对疏证对象安排了大致的分类,并就疏证过程中的难点和不足作了概括,另着眼于宏观意义上的“训诂学”方法,对“诸具”疏证的理想形式及目标给予了有限的期待。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