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刘子翚的《圣传论》
| 内容出处: | 《《诸儒鸣道集》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5186 |
| 颗粒名称: | 四 刘子翚的《圣传论》 |
| 分类号: | B244.99 |
| 页数: | 4 |
| 页码: | 253-256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刘子翚的《圣传论》以心论为基础,主张制心为成圣的关键,提出以礼制心和人心同体的观点,并对易学、性情论有所探讨,具有独特的理论特色。 |
| 关键词: | 刘子翚 圣传论 心论 |
内容
《诸儒鸣道集》还收录有朱熹之师刘子翚的著作《圣传论》。《圣传论》长期以来被认为已经遗失,学者多认为《诸儒鸣道集》所收的《崇安圣传论》为该书仅见的版本,但是据笔者发现,其实在四库全书集部所收录刘子翚的《屏山集》中,就完整地收录有《圣传论十首》一书,二者只是略有差异,①这一点是需要说明的,以免后人以讹传讹。
概言之,《圣传论》的立论基石是心论,并由此而展开对“尧舜(一)、禹(仁)、汤(学)、文王(力)、周公(谦牧)、孔子(死生)、颜子(复)、曹子(孝)、子思(中)、孟子(自得)”十个问题的讨论。其对制心学说、道统论、易学思想的讨论颇具特色。
以制心为根本的思想体系。刘子翚的思想主要围绕制心来展开。他提出:“道一而已。尧舜之心不间乎此试听言动,必有司也……《书》论人心道心,本之惟精惟一,此相传之密旨也……能一者,心也。心与道应,尧舜所以为圣人也。”②这是说,尧舜与常人的区别就在于他们能做到心的“常一”,而常人则会“见立情生,莫之主宰”。因此,制心就成为人是否能成圣的关键,乃至他提出“此惟一之旨,所以为六艺之渊源,九流之管辖”③的结论。
在制心的手段方面,刘子翚则提出了“以礼制心”的观点:
礼者,内外之卫也。夫人心一也,今曰有制之者,是复有一心也。盖心之念有邪有正,有妄有诚,合而观之,皆一心也。犹手有翻覆,实一形也;犹声有笑哭,实一音也。心过则邪,制邪为正;心过则妄,制妄为诚。圣人不能使人必无过心,而能使人常存制心。制心胜则动静语默惟吾是令,过心不二,制心亦无。①
刘的这一观点,较之当时的心性论而论,有很大差距:刘子翚对孟子的赞扬,仅限于自得。而对于同时期人特别关注的孟子性善论,却只字不提。由此,刘子翚对心的理解仍然陷于经验的层面。相对于程门的心性论,刘子翚的心性论思想极为粗疏。
在工夫论层面,刘子翚明确反对不历阶级,而主张力行、真积力久:“彼谓圣道一言可契,非由阶级,不假修为,以日就月将为初学,以真积力久为钝才,是自诬也”②在当时,主张为学不历阶级者渐成潮流,刘子翚早于朱熹提出了对此的批判,可谓有先见之明。
以心制心,在佛家和儒家都是大忌,但是刘子翚却对此做出了别具新意的说明,后来朱熹提出以道心制人心的说法,与此是一致的。
刘子翚还提出了人心同体的说法:
圣人宅心广大,一视同仁,赢衣枵腹,食如己饫;温萎膏愦,醒如已苏,决非强为博爱之名也,有生之类实同体耳。禹视天下之溺犹已溺之,何其责己太深切哉?滔滔之害天实为之恻然,不忍斯民葬鱼腹中,极力牵援,此仁心之常也。若曰昬垫万灵如己所致,焦心劳思,胼手胝足,逆旅其家,惟爱人利物是图,无乃差过乎!然而万世无异词,圣贤共推尊者,岂不以伟人所行无可拟议,理当然耶?因知泣辜祝网,惠困思饥,视民如伤,无异骨肉者,圣人之心不约而同也。③
在宋代,宣扬万物同体的说法很多,而朱熹尤其担心其会流于有体无用的玄虚之论,或者墨家的兼爱之学(实质是渲染无差别的同一)。刘子翚的同体说则是建立在人的“不容己”之真实感情之上,与孟子的提法也是一贯的。另外,刘子翚对儒学的人心同体说的特殊性也有所说明:“圣人之于生类,虽有差别,莫不欲爱利之焉……人莫不尊头目而贱足髀也,抉之则痛均焉,必失色营护之,是尊贱之名异而爱重之实同也……”①“禹虽一视同仁,而纳五典于皋陶、陈九功于虞舜,其于藩饰等衰之别,固己甚严。若翟之薄死过矣,故明禹致孝乎鬼神;翟毁礼过矣,故明禹致美乎黻冕。大抵皆指其同推其异,所以约其失而归之正也。”②刘子翚的这一说法和例子,具有一定的理一分殊意味,这也被认为是儒家在强调“同体说”时,不同于佛老的独特讲法。这在朱熹和王阳明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代表了理学的主流观点,成为儒学境界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易学观:刘子翚对易的诠释并不多,但却有其特色:“易故多术,或尚其辞、或尚其占、或尚其象,皆末也。尽其本则末自应。何谓本?复是已。”③他同时强调,“复”是学易之门户:“学易者必有门户,复卦易之门户也……学易者必自复始得。”那么,复卦在易中何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刘子翚认为,复卦与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之说相通。在他看来,“固有之仁本无彼此”,但是如果人“迷而不复”就会与仁隔绝,被私心汩没。因此,他强调复这一真实践履功夫也就成为成仁的关键。
刘子翚又强调,虽然学易入门在复,而其真谛在于忘:“虽然,学易当自复始,而复非易也。愚夫昧易,才士口易,贤人体易,圣人忘易。体而不忘,易之病也。”④从他后文所引自己所作的《复斋铭》看,他所强调的“忘”,与自王弼而后人们多强调“得意忘言”、“得意忘象”的精神是相通的。这一点与当时儒学的主流观点有很大的差距。程朱对于周敦颐的主静观点都有微词,对于“忘”自然更难接受了。
性情论:刘子翚的性情论主要系针对李翱的灭情复性思想而发,认为:情与生俱生,如果情可灭,那就意味着性也会可灭了。由此,他强调“善养性者,不汩于情,亦不灭情。流于喜怒哀乐以为中不可,离喜怒哀乐以为中亦不可……非合非离,中即与焉。”⑤我们知道,基于性情一体的思想,宋儒对立翱的性情论基本上都持反对的态度。刘子翚的性情论与此是一致的。
道统观:刘子翚所提出的道统论与韩愈、二程的说法均不同。较之于潘殖的道统谱系说纳入了黄石公、张良这样近似道家的人物不同,刘子翚的“圣贤十传”谱系与程朱的表述无异。不过,刘子翚则强调道统自孔孟之后的两千年间始终并未中断:“圣贤相传一道也。前乎尧舜传有自来,后乎孔孟,传固不泯。”①刘子翚认为,自尧舜以来,“密契圣心,如相受授,故恐无世无之”,而这些人不为人所识的原因就在于缺乏伯乐:“时无孔子,颜渊殒于陋巷而少正卯为闻人,时无孟子,康章陷与不孝儿仲子为廉士,岂易识哉”?②依照刘子翚的上述说法,道统传承的标准就大大降低了,而圣贤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指导意义也会大大降低。这正是朱熹所不愿看到的,难怪他会认为刘子翚这样的说法是“只要说释子道流皆得其传耳。”③
与佛学的关系:在朱熹对刘子翚的介绍中,非常强调其与佛学的关联,说他“后读儒书,以为与佛和,故作圣传论”④云云。但是,我们在《圣传论》中没有发现刘子翚有一个字提到佛老,也没有借用佛老的观念和概念。仅就《圣传论》而言,我们只能说朱熹对刘子翚的评论是不很准确的。⑤不过,《朱子语类》的这段记录很值得我们注意:
问:“如《十论》(田按,即《圣传论》)之作,于夫子全以死生为言,似以此为大事了?”(朱子)……乃曰:他本是释学,但只是翻誊出来,说许话耳。”⑥
朱子认为,《圣传论》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不离个人,偏在佛学的一面为多。
概言之,《圣传论》的立论基石是心论,并由此而展开对“尧舜(一)、禹(仁)、汤(学)、文王(力)、周公(谦牧)、孔子(死生)、颜子(复)、曹子(孝)、子思(中)、孟子(自得)”十个问题的讨论。其对制心学说、道统论、易学思想的讨论颇具特色。
以制心为根本的思想体系。刘子翚的思想主要围绕制心来展开。他提出:“道一而已。尧舜之心不间乎此试听言动,必有司也……《书》论人心道心,本之惟精惟一,此相传之密旨也……能一者,心也。心与道应,尧舜所以为圣人也。”②这是说,尧舜与常人的区别就在于他们能做到心的“常一”,而常人则会“见立情生,莫之主宰”。因此,制心就成为人是否能成圣的关键,乃至他提出“此惟一之旨,所以为六艺之渊源,九流之管辖”③的结论。
在制心的手段方面,刘子翚则提出了“以礼制心”的观点:
礼者,内外之卫也。夫人心一也,今曰有制之者,是复有一心也。盖心之念有邪有正,有妄有诚,合而观之,皆一心也。犹手有翻覆,实一形也;犹声有笑哭,实一音也。心过则邪,制邪为正;心过则妄,制妄为诚。圣人不能使人必无过心,而能使人常存制心。制心胜则动静语默惟吾是令,过心不二,制心亦无。①
刘的这一观点,较之当时的心性论而论,有很大差距:刘子翚对孟子的赞扬,仅限于自得。而对于同时期人特别关注的孟子性善论,却只字不提。由此,刘子翚对心的理解仍然陷于经验的层面。相对于程门的心性论,刘子翚的心性论思想极为粗疏。
在工夫论层面,刘子翚明确反对不历阶级,而主张力行、真积力久:“彼谓圣道一言可契,非由阶级,不假修为,以日就月将为初学,以真积力久为钝才,是自诬也”②在当时,主张为学不历阶级者渐成潮流,刘子翚早于朱熹提出了对此的批判,可谓有先见之明。
以心制心,在佛家和儒家都是大忌,但是刘子翚却对此做出了别具新意的说明,后来朱熹提出以道心制人心的说法,与此是一致的。
刘子翚还提出了人心同体的说法:
圣人宅心广大,一视同仁,赢衣枵腹,食如己饫;温萎膏愦,醒如已苏,决非强为博爱之名也,有生之类实同体耳。禹视天下之溺犹已溺之,何其责己太深切哉?滔滔之害天实为之恻然,不忍斯民葬鱼腹中,极力牵援,此仁心之常也。若曰昬垫万灵如己所致,焦心劳思,胼手胝足,逆旅其家,惟爱人利物是图,无乃差过乎!然而万世无异词,圣贤共推尊者,岂不以伟人所行无可拟议,理当然耶?因知泣辜祝网,惠困思饥,视民如伤,无异骨肉者,圣人之心不约而同也。③
在宋代,宣扬万物同体的说法很多,而朱熹尤其担心其会流于有体无用的玄虚之论,或者墨家的兼爱之学(实质是渲染无差别的同一)。刘子翚的同体说则是建立在人的“不容己”之真实感情之上,与孟子的提法也是一贯的。另外,刘子翚对儒学的人心同体说的特殊性也有所说明:“圣人之于生类,虽有差别,莫不欲爱利之焉……人莫不尊头目而贱足髀也,抉之则痛均焉,必失色营护之,是尊贱之名异而爱重之实同也……”①“禹虽一视同仁,而纳五典于皋陶、陈九功于虞舜,其于藩饰等衰之别,固己甚严。若翟之薄死过矣,故明禹致孝乎鬼神;翟毁礼过矣,故明禹致美乎黻冕。大抵皆指其同推其异,所以约其失而归之正也。”②刘子翚的这一说法和例子,具有一定的理一分殊意味,这也被认为是儒家在强调“同体说”时,不同于佛老的独特讲法。这在朱熹和王阳明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代表了理学的主流观点,成为儒学境界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易学观:刘子翚对易的诠释并不多,但却有其特色:“易故多术,或尚其辞、或尚其占、或尚其象,皆末也。尽其本则末自应。何谓本?复是已。”③他同时强调,“复”是学易之门户:“学易者必有门户,复卦易之门户也……学易者必自复始得。”那么,复卦在易中何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刘子翚认为,复卦与孔子“克己复礼为仁”之说相通。在他看来,“固有之仁本无彼此”,但是如果人“迷而不复”就会与仁隔绝,被私心汩没。因此,他强调复这一真实践履功夫也就成为成仁的关键。
刘子翚又强调,虽然学易入门在复,而其真谛在于忘:“虽然,学易当自复始,而复非易也。愚夫昧易,才士口易,贤人体易,圣人忘易。体而不忘,易之病也。”④从他后文所引自己所作的《复斋铭》看,他所强调的“忘”,与自王弼而后人们多强调“得意忘言”、“得意忘象”的精神是相通的。这一点与当时儒学的主流观点有很大的差距。程朱对于周敦颐的主静观点都有微词,对于“忘”自然更难接受了。
性情论:刘子翚的性情论主要系针对李翱的灭情复性思想而发,认为:情与生俱生,如果情可灭,那就意味着性也会可灭了。由此,他强调“善养性者,不汩于情,亦不灭情。流于喜怒哀乐以为中不可,离喜怒哀乐以为中亦不可……非合非离,中即与焉。”⑤我们知道,基于性情一体的思想,宋儒对立翱的性情论基本上都持反对的态度。刘子翚的性情论与此是一致的。
道统观:刘子翚所提出的道统论与韩愈、二程的说法均不同。较之于潘殖的道统谱系说纳入了黄石公、张良这样近似道家的人物不同,刘子翚的“圣贤十传”谱系与程朱的表述无异。不过,刘子翚则强调道统自孔孟之后的两千年间始终并未中断:“圣贤相传一道也。前乎尧舜传有自来,后乎孔孟,传固不泯。”①刘子翚认为,自尧舜以来,“密契圣心,如相受授,故恐无世无之”,而这些人不为人所识的原因就在于缺乏伯乐:“时无孔子,颜渊殒于陋巷而少正卯为闻人,时无孟子,康章陷与不孝儿仲子为廉士,岂易识哉”?②依照刘子翚的上述说法,道统传承的标准就大大降低了,而圣贤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指导意义也会大大降低。这正是朱熹所不愿看到的,难怪他会认为刘子翚这样的说法是“只要说释子道流皆得其传耳。”③
与佛学的关系:在朱熹对刘子翚的介绍中,非常强调其与佛学的关联,说他“后读儒书,以为与佛和,故作圣传论”④云云。但是,我们在《圣传论》中没有发现刘子翚有一个字提到佛老,也没有借用佛老的观念和概念。仅就《圣传论》而言,我们只能说朱熹对刘子翚的评论是不很准确的。⑤不过,《朱子语类》的这段记录很值得我们注意:
问:“如《十论》(田按,即《圣传论》)之作,于夫子全以死生为言,似以此为大事了?”(朱子)……乃曰:他本是释学,但只是翻誊出来,说许话耳。”⑥
朱子认为,《圣传论》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不离个人,偏在佛学的一面为多。
附注
①具体的差距有:其一,《屏山集》所收《圣传十论》的小节仅为“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颜子、曹子、子思、孟子”;其二,经初步比对,二者各有脱文,但“屏山集本”有在前者基础上进行修订的痕迹。
②(宋)刘子翚:《圣传论·尧舜(一)》,见《诸儒鸣道集》卷七十,第1596页。
③同上书,第1597—1598页。
①此为屏山集本,“鸣道本”此段则为:“人心一也……犹手有翻覆,实一形也;犹声有笑哭,实一音也……能使人常存制心。心正则动静语■惟吾是令,过心不二,制心亦无”,略有出入。
②《圣传论·禹(仁)》,见《诸儒鸣道集》卷六十九,第1603页。
③同上书,第1598—1599页。
①《圣传论·禹(仁)》,见《诸儒鸣道集》卷六十九,第1600页。
②这一段,仅见于《屏山集》本。
③《圣传论·颜子(复)》,见《诸儒鸣道集》卷七十,第1616—1617页。
④《圣传论·颜子》,见《诸儒鸣道集》卷七十,第1618页。
⑤《圣传论·子思(中)》,见《诸儒鸣道集》卷七十,第1624—1625页。
①《圣传论·孟子(自得)》,见《诸儒鸣道集》卷七十,第1628页。
②同上。
③《朱子语类》卷九十六,载《朱子全书》第十七册,第3253页。
④《朱子语类》卷一零四,载《朱子全书》第十七册,第3436页。
⑤四库馆臣曾提到,刘子翚的诗文中有一定的佛老气息,见四库本该书的提要。
⑥《朱子语类》卷九十六,载《朱子全书》第十七册,第3253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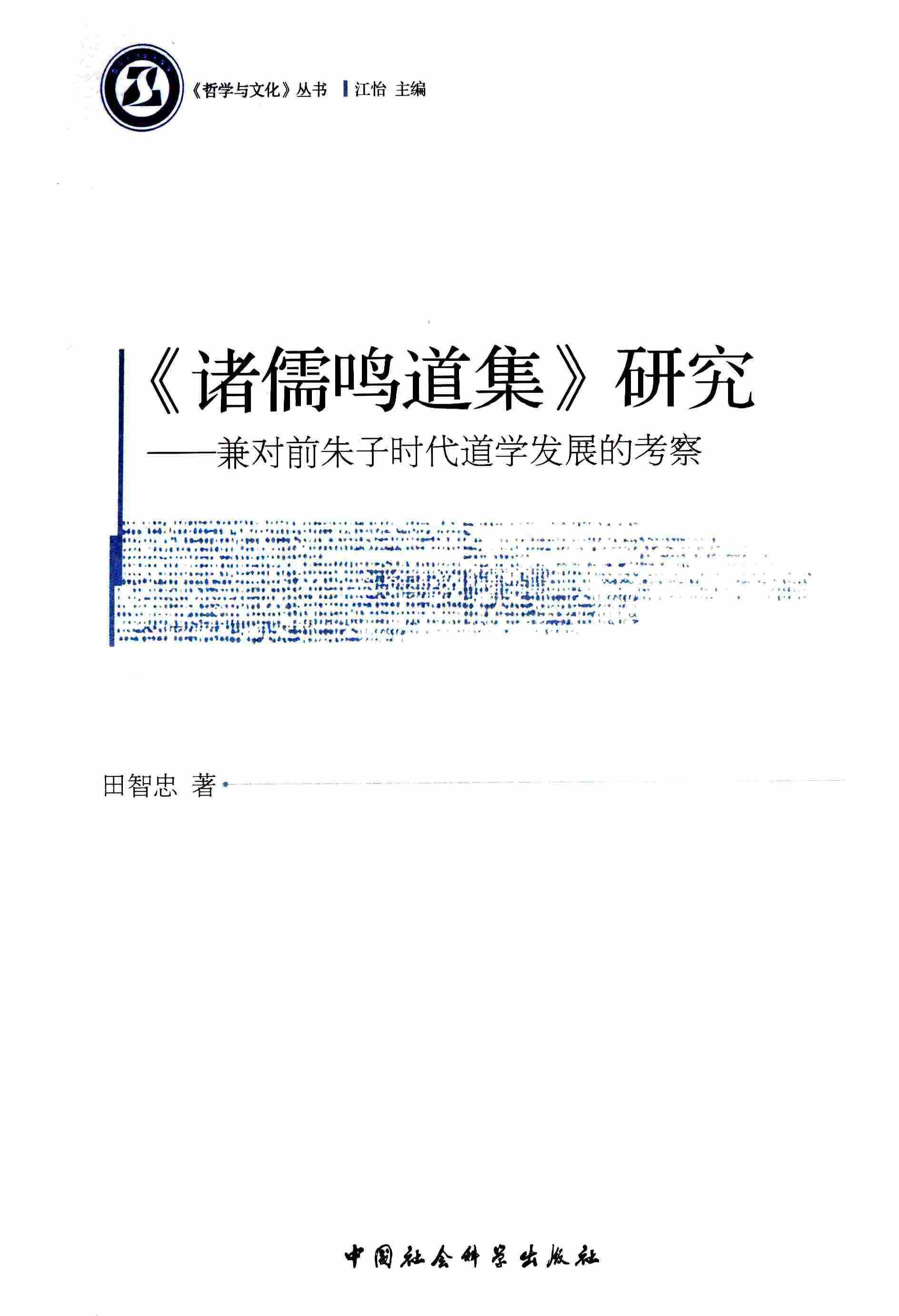
《《诸儒鸣道集》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内容包括:《诸儒鸣道集》原刻年代考、关于《诸儒鸣道集》编者身份的初步推测、《诸儒鸣道集》视野下的宋代儒学多元性研究、周敦颐与张载的道学话语构建、二程对道学话语的构建、谢良佐与杨时对道学话语的构建等。
阅读
相关人物
刘子翚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