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合《语录》《濂溪通书》看《图》与《说》早期的分合情况
| 内容出处: | 《《诸儒鸣道集》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5180 |
| 颗粒名称: | 四 结合《语录》《濂溪通书》看《图》与《说》早期的分合情况 |
| 分类号: | B244.99 |
| 页数: | 4 |
| 页码: | 228-231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祁宽所言《通书》的程门传本将《图》附于《通书》之后,早于朱子所编订的“长沙本”和“建安本”。陈来师认为,《濂溪通书》所依据的底本不是“九江本”,也不同于朱子所整理的“长沙本”、“建安本”和“南康本”。 |
| 关键词: | 周敦颐 濂溪通书 分合情况 |
内容
在讨论《诸儒鸣道集》一书中所收录的《濂溪通书》时,陈来师曾经提到,朱子在编订《太极通书》一书的过程中,先是据此前流行的版本,把《图》和《说》附于《通书》之后,是为“长沙本”,后又据潘的“墓志铭”而“置图篇端”,是为“建安本”,陈来师认为:
但是朱熹这个说法与历史事实并不完全相符。比朱熹更早一些的祁宽在《通书后跋》中说,《通书》一书“始出于程门侯师圣,传之荆门高元举、朱子发。宽初得于高,后得于朱。又后得和靖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所传本是也……逮卜居九江,得九江本于共家,比前所见无《太极图》,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这就是说《通书》的程门传本有太极图,而九江周敦颐家藏旧本则没有。换言之,《通书》本无太极图,是程门传本将它附于《通书》之后的。按照祁氏的说法,周氏旧本既无太极图,也应无太极图说,祁氏仅及太极图当系简言之。今《鸣道集》本亦无太极图,因此,如果可以断定鸣道集本早于朱子定本,那就进一步证实了祁宽的说法。①
陈来师的这段话也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图》与《说》之早期关系的又一种思路。为了充分了解“九江本”,我们不妨再完整地看一下《又·延平本》②这段文字:
临汀杨方得九江故家传本,校(田按:清刻本《周子全书》误为“核”字)此本,不同者十有九处,然亦互有得失。其两条此本之误,当从“九江本”。如《理性命》章云“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章(当自“道义者”以下析为下章);其十四条,义可两通,当并存之;如《诚几德》章云:“理曰礼”(理,一作履);《慎动》章云:“邪动”(一作动邪)、“化章”(一作顺化);《爱敬章》云:“有善”(此下一有是苟字)、“学焉”(此下一有“有”字)、“曰有不善”(一无此四字)、“曰不善”(此下一有“否”字);《乐》章云“优柔平中”(平,一作乎)、“轻生败伦”(伦,一作常);《圣学章》云:“请闻焉”(闻,一作问);《颜子章》云:“独何心哉”(心,一作以)、“能化而齐”(齐,一作济、一作消);《过》章(一作《仲由》);《刑》章云:“不止即过焉”(即,一作则)。其三条,“九江本”误,而当以此本为正。如《太极说》云:“无极而太极”(而下误多一生字);《诚》章云:“诚斯立焉”(立误作生);《家人暌复无妄》章云:“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
(心,误作以)凡十九条。今附见于此,学者得以考焉。①
从这则文献可知,“鸣道本”《濂溪通书》的底本,肯定不会是“九江本”,也与朱子自己所整理的“长沙本”、“建安本”和“南康本”《通书》均有不同。具体分述如下。
第一,《濂溪通书》明显不同于“九江本”。如上文中提道:“其(此处指建安本)两条此本之误,当从‘九江本’。如《理性命》章云‘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章》(当自‘道义者’以下析为下章)”云云。同时,《濂溪通书》的《理性命》章正作“柔如之”,而《师友》章自“道义”以下也没有分章,这是其不同于“九江本”之处。再如:为朱子所指出的“九江本”的三条错误,都没有出现在《濂溪通书》中。
第二,《濂溪通书》亦不同于“长沙本”。朱子提道:“‘长沙通书’因胡氏所传,篇章非复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别以‘周子曰’者加之,于书之大义虽若无所害,然要非先生之旧,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晓者”②,以此为准,《濂溪通书》与“长沙本”的差距甚大,因此也与胡宏所编订的《通书》不同。当然,“长沙本”在末尾收录有《图》和《说》,这也是其与《语录》的不同之处。事实上,多数学者认为,《诸儒鸣道集》的刊刻时间当在1168年朱子刊刻《程氏遗书》之前,而《濂溪通书》所采用的底本更要在此之前,自然要早于朱子编订的“长沙本”(刊刻于1169年之前)。
第三,《濂溪通书》与“建安本”也有明显的不同。我们知道,“建安本”起手即收录有《图》和《书》,此外,朱子亦提道:“建安本……又即潘志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记先生行事之实,删去重复,参互考订,合为事状一篇”③云云,《濂溪通书》同样也没有收入朱子整理的《事状》。这是“建安本”与《濂溪通书》的显著不同。不过,在上文中提到的十九条“建安本”不同于“九江本”之处,《濂溪通书》与“建安本”完全一致(这十九条也应该与“长沙本”一致,因为“长沙本”与“建安本”在这些地方应该没有差别),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这也说明,《濂溪通书》实际上与“建安本”的四十章《通书》部分是高度一致的。只不过,《濂溪通书》既无《图》也无《书》而已。
第四,《濂溪通书》亦不同于“南康本”。显然,二者无论是在卷数上,还是在具体内容上,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再者,“南康本”刻印于1179年,恐怕此时《诸儒鸣道集》早已经刊刻多年了。
资料显示,朱子似乎对于《濂溪通书》的底本也是熟悉的:如《濂溪通书》《理性命》章云:“厥彰厥微,匪虚(后有双行夹注:一作灵)弗莹。”与之相对,朱子在《朱子语类》中提道:“别一本‘灵’作‘虚’,义短(万正淳录,当在朱子晚年)”①,而《濂溪通书》正在朱子所说的“别一本”之列。②我们知道,在朱子编订“长沙本”之前,社会上即流行着诸如“舂陵本”、“零陵本”、“九江本”等多种《通书》版本,《濂溪通书》当为其中之一。而《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之选择刊刻《濂溪通书》,既可能意味着其与程门的关系较为疏远(因此才不选在当时较为流行的程门各传本),也可能意味着朱子所整理的“最为完善”的“长沙本”《通书》尚未面世(至少是他们还没有见到)。但是,《濂溪通书》由于未经过朱子的整理,因此在保留宋代的原始材料上显得更为弥足珍贵。
总之,引入对“鸣道本”《濂溪通书》和“九江本”《通书》的分析表明,在朱子编订《太极通书》之前,未收录《图》的《通书》版本仍然在一定范围内流行,而且它也可能更接近周敦颐著作的本来面目。我们在讨论《图》与《说》的关系时,更不能无条件地把二者视为一体的关系,而是应该正视《图》与道家思想的渊源关系。
但是朱熹这个说法与历史事实并不完全相符。比朱熹更早一些的祁宽在《通书后跋》中说,《通书》一书“始出于程门侯师圣,传之荆门高元举、朱子发。宽初得于高,后得于朱。又后得和靖先生所藏,亦云得之程氏,今所传本是也……逮卜居九江,得九江本于共家,比前所见无《太极图》,或云图乃手授二程故程本附之卷末”。这就是说《通书》的程门传本有太极图,而九江周敦颐家藏旧本则没有。换言之,《通书》本无太极图,是程门传本将它附于《通书》之后的。按照祁氏的说法,周氏旧本既无太极图,也应无太极图说,祁氏仅及太极图当系简言之。今《鸣道集》本亦无太极图,因此,如果可以断定鸣道集本早于朱子定本,那就进一步证实了祁宽的说法。①
陈来师的这段话也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图》与《说》之早期关系的又一种思路。为了充分了解“九江本”,我们不妨再完整地看一下《又·延平本》②这段文字:
临汀杨方得九江故家传本,校(田按:清刻本《周子全书》误为“核”字)此本,不同者十有九处,然亦互有得失。其两条此本之误,当从“九江本”。如《理性命》章云“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章(当自“道义者”以下析为下章);其十四条,义可两通,当并存之;如《诚几德》章云:“理曰礼”(理,一作履);《慎动》章云:“邪动”(一作动邪)、“化章”(一作顺化);《爱敬章》云:“有善”(此下一有是苟字)、“学焉”(此下一有“有”字)、“曰有不善”(一无此四字)、“曰不善”(此下一有“否”字);《乐》章云“优柔平中”(平,一作乎)、“轻生败伦”(伦,一作常);《圣学章》云:“请闻焉”(闻,一作问);《颜子章》云:“独何心哉”(心,一作以)、“能化而齐”(齐,一作济、一作消);《过》章(一作《仲由》);《刑》章云:“不止即过焉”(即,一作则)。其三条,“九江本”误,而当以此本为正。如《太极说》云:“无极而太极”(而下误多一生字);《诚》章云:“诚斯立焉”(立误作生);《家人暌复无妄》章云:“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
(心,误作以)凡十九条。今附见于此,学者得以考焉。①
从这则文献可知,“鸣道本”《濂溪通书》的底本,肯定不会是“九江本”,也与朱子自己所整理的“长沙本”、“建安本”和“南康本”《通书》均有不同。具体分述如下。
第一,《濂溪通书》明显不同于“九江本”。如上文中提道:“其(此处指建安本)两条此本之误,当从‘九江本’。如《理性命》章云‘柔如之’(当作‘柔亦如之’);《师友章》(当自‘道义者’以下析为下章)”云云。同时,《濂溪通书》的《理性命》章正作“柔如之”,而《师友》章自“道义”以下也没有分章,这是其不同于“九江本”之处。再如:为朱子所指出的“九江本”的三条错误,都没有出现在《濂溪通书》中。
第二,《濂溪通书》亦不同于“长沙本”。朱子提道:“‘长沙通书’因胡氏所传,篇章非复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别以‘周子曰’者加之,于书之大义虽若无所害,然要非先生之旧,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晓者”②,以此为准,《濂溪通书》与“长沙本”的差距甚大,因此也与胡宏所编订的《通书》不同。当然,“长沙本”在末尾收录有《图》和《说》,这也是其与《语录》的不同之处。事实上,多数学者认为,《诸儒鸣道集》的刊刻时间当在1168年朱子刊刻《程氏遗书》之前,而《濂溪通书》所采用的底本更要在此之前,自然要早于朱子编订的“长沙本”(刊刻于1169年之前)。
第三,《濂溪通书》与“建安本”也有明显的不同。我们知道,“建安本”起手即收录有《图》和《书》,此外,朱子亦提道:“建安本……又即潘志及蒲左丞、孔司封、黄太史所记先生行事之实,删去重复,参互考订,合为事状一篇”③云云,《濂溪通书》同样也没有收入朱子整理的《事状》。这是“建安本”与《濂溪通书》的显著不同。不过,在上文中提到的十九条“建安本”不同于“九江本”之处,《濂溪通书》与“建安本”完全一致(这十九条也应该与“长沙本”一致,因为“长沙本”与“建安本”在这些地方应该没有差别),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注意。这也说明,《濂溪通书》实际上与“建安本”的四十章《通书》部分是高度一致的。只不过,《濂溪通书》既无《图》也无《书》而已。
第四,《濂溪通书》亦不同于“南康本”。显然,二者无论是在卷数上,还是在具体内容上,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再者,“南康本”刻印于1179年,恐怕此时《诸儒鸣道集》早已经刊刻多年了。
资料显示,朱子似乎对于《濂溪通书》的底本也是熟悉的:如《濂溪通书》《理性命》章云:“厥彰厥微,匪虚(后有双行夹注:一作灵)弗莹。”与之相对,朱子在《朱子语类》中提道:“别一本‘灵’作‘虚’,义短(万正淳录,当在朱子晚年)”①,而《濂溪通书》正在朱子所说的“别一本”之列。②我们知道,在朱子编订“长沙本”之前,社会上即流行着诸如“舂陵本”、“零陵本”、“九江本”等多种《通书》版本,《濂溪通书》当为其中之一。而《诸儒鸣道集》的编者之选择刊刻《濂溪通书》,既可能意味着其与程门的关系较为疏远(因此才不选在当时较为流行的程门各传本),也可能意味着朱子所整理的“最为完善”的“长沙本”《通书》尚未面世(至少是他们还没有见到)。但是,《濂溪通书》由于未经过朱子的整理,因此在保留宋代的原始材料上显得更为弥足珍贵。
总之,引入对“鸣道本”《濂溪通书》和“九江本”《通书》的分析表明,在朱子编订《太极通书》之前,未收录《图》的《通书》版本仍然在一定范围内流行,而且它也可能更接近周敦颐著作的本来面目。我们在讨论《图》与《说》的关系时,更不能无条件地把二者视为一体的关系,而是应该正视《图》与道家思想的渊源关系。
附注
②《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第3652页。
③《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八,第186页。
④《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第3653页。
①《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第3652页。
②《朱子全书》第二十一册,第1341页。
①《朱子全书》第二十二册,第1901页。
①《周敦颐集·通书后跋》,第4页。
①《略论〈诸儒鸣道集〉》,第31页。
②束景南先生给这段文字起名为《跋延平本太极通书》。
①《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四,第115页。
②《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第3628页。
③同上书,第3653页。
①《朱子全书》第十七册,第3166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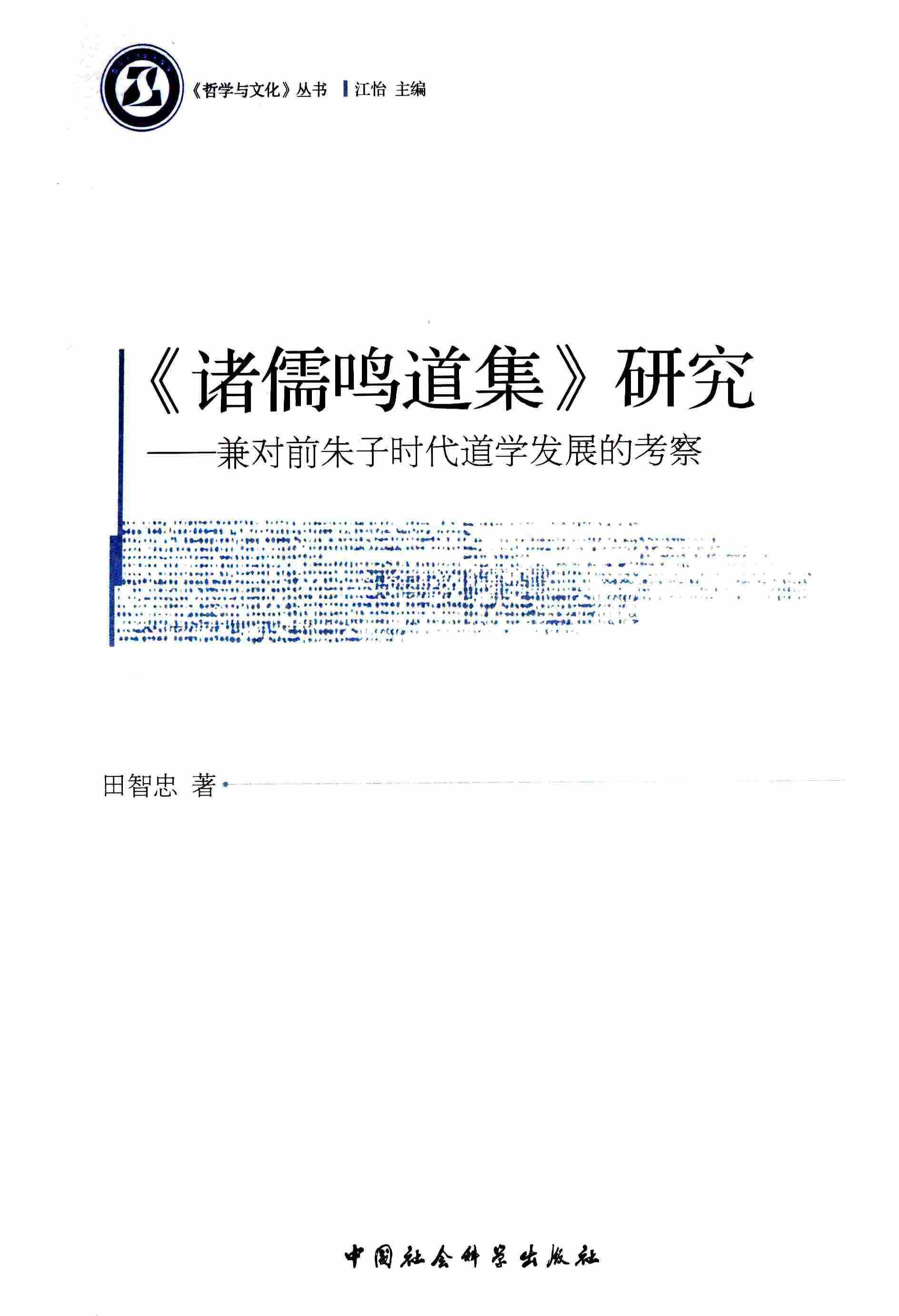
《《诸儒鸣道集》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内容包括:《诸儒鸣道集》原刻年代考、关于《诸儒鸣道集》编者身份的初步推测、《诸儒鸣道集》视野下的宋代儒学多元性研究、周敦颐与张载的道学话语构建、二程对道学话语的构建、谢良佐与杨时对道学话语的构建等。
阅读
相关人物
周敦颐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