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对“潘志”所记载周敦颐著作的新解读
| 内容出处: | 《《诸儒鸣道集》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5179 |
| 颗粒名称: | 三 对“潘志”所记载周敦颐著作的新解读 |
| 分类号: | B244.99 |
| 页数: | 4 |
| 页码: | 225-228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周敦颐只作《太极图易说》和《易通》两部书,未作《易说》。朱震编订的《周氏太极图》最接近周敦颐所解说之《图》的本来面目,但朱熹不满意进行了调整。 |
| 关键词: | 周敦颐 太极图易说 著作解读 |
内容
对上述材料准确解读,还能帮助我们解决许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潘兴嗣所作的《先生墓志铭》(在中华书局本《周敦颐集》中,又作《周敦颐墓志铭》)中一段话的点断问题。潘在此文中提道:“(周敦颐)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今藏于家……”③对于这句话的点断,多年来一直争论不断。朱子认为,这句话中提到周敦颐的作品包括“《太极图》(朱子的意思,此《太极图》包括《图》和《说》)、《易说》和《易通》”三种。但是问题是,除了这句比较模糊的话之外,《易说》一书再也没有在其他文献中出现过,究竟存在不存在都是个问题。朱子自己则推测说:“盖《易说》既依经以解义,此(指《易通》)则通论其大旨,而不系于经者也”④云云。朱子的意思,《易说》不会是“通论”性质,否则就会和只有一篇的《太极图说》重复了。但是他的这一推测也很难成立:既然《易说》“依经以解义”为分说,《易通》“不系于经者”为总说,那么前者在篇幅上肯定是要多于后者。但是,“太极图易说易通”总共只有区区“数十篇”,其中就包括《太极图》一篇和《易通》四十篇,那么其总数又怎么可能只有这区区的“数十篇”?当然,《易说》也可能只是周敦颐尚未完成的且篇幅不大的残稿。对此问题,材料所限,我们只能存疑。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朱子关于《易说》的推测明显存在着漏洞。
那么,潘的这段话为什么就不能点断为“……作《太极图易说》(即《太极图说》)和《易通》(即《通书》)数十篇……”,也就是说周敦颐只是作了这两部书呢?值得注意的是,假设周敦颐真的是作了三书,而且它们也都被其后人“藏于家”的话,那么何以后来周的家人在编订“九江本”时,却没有收入已经是成文,而且又被藏于家的《图》呢?再者,据潘的这段话来看,根本不可能是像祁宽后来所说的那样,周敦颐只是把《图》单独传授给了二程(否则“藏于家”的《太极图》又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就是祁宽本人对自己的表述也将信将疑,所以才使用了“或云”二字,而当今的许多学者却对此二字视而不见)。再进一步说,既然潘兴嗣说过《图》与《说》都早已公开流传(至少是潘自己知道此事),而程门弟子们又说周敦颐又曾把《图》传授给了二程,何以二程自己却从来没有明确提及过事实上早已经被公开的《图》呢?自从朱子以来,许多人都试图对此疑问做出过解答,却都难以令人满意。仅以朱子的回答为例。一方面,朱子强调二程确有祖述《图》的文字:“程氏之书,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乃或并其语而道之”①;另一方面,朱子则强调二程不言《图》和《说》,是因为“《太极图》立象尽意,剖析幽微,周子盖不得已而作也。观其手授之意,盖以为唯程子为能受之;程子之秘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尔”②。此二说都难以成立:朱子提到的三篇文章,都没有表现出与《图》的确切关联(至多能说在义理上与《说》有一些联系),更没有出现《图》和《书》的具体名称与内容,难怪朱子只能以“乃或”二字作为结论。
另外,朱子说“观其手授之意,盖以为唯程子为能受之”云云,更是与事实不符(见潘志)。再者,二程与周敦颐的接触,都在其早年。我们很难想象周会把自己甚为私密的东西单独传给两个十几岁的少年。况且,二程对周子的著作并未热心整理,却听任其散失(假如《易说》真的存在的话),这其中就包括所谓“秘传”的《太极图》,这绝对不合常理。最后,据祁宽的记述,“《通书》始出于程门侯师圣”云云。我们也很难想象,二程最终选定的“能受之者”,就是默默无闻的侯师圣。
其实,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潘的这段话只是说周敦颐作了《太极图易说》和《易通》这两部书,而且此两书也都被其后人“藏于家”,并且又都被其后人收入了“故家传本”中。潘的这段话和“九江本”中,都只是没有提到《图》罢了。由此,《图》很有可能长期处于秘传状态,直到后来才被二程的弟子们所公开。他们又显然认为,《太极图易说》就是对“太极图”(而非“太极”)的解说,所以才会在刊刻周敦颐的著作时,把《图》附在《通书》之后。从这方面来说,《图》的原始出处的确令人生疑。当然,也存在另一种情况,即周敦颐在晚年直接把《图》传给了侯师圣,而侯师圣则据此编订了《通书》,这中间并没有转手于二程。事实上,这一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图》的最初面貌的问题。关于此问题,大家也有许多争论。简言之,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图》,最早见于朱震《汉上易传》中的《周氏太极图》(编订于绍兴五年,即1135年)。应该说,此幅“图”也最接近周教颐所解说之“图”的本来面目。但是,朱子后来在编订《太极通书》时,却对此《图》甚为不满。他在未说出确切版本依据的情况下,就对此图做出了调整:把旧图第一圈标注“阴静”、第二圈标注“阳动”的格局,改为第一圈为“无极而太极”,第二圈左侧标“阳动”,右侧标“阴静”;又对此图第三圈的五行相生顺序做出了调整(关于这一点,笔者曾有专文论述,此不赘述)。朱子提出改动的理由为:“既以第一圈为阴静,第二圈为阳动,则夫所谓太极者,果安在耶……且所论先有专一之阴,后有兼体之阳,是乃截然之甚者。”①我们说,朱子不能接受“阴静”在上、“阳动”在下、阴阳截然分开的旧图,这完全是其个人认为《图》一定出自淳儒之手的信念所致。而朱子反复述说“旧图”的安排与《说》中的理念不合,这反倒是有舍本逐末的嫌疑:《说》本来就是来解释《图》的,它应该要符合《图》所体现出的理念才对,朱子反而要让《图》去迁就《说》,这在逻辑上有些不尽合理。总之,《图》很有可能包含着有道家思想的因素,至少是《图》的作者对于儒道之间的界限并不像朱子那样的敏感。《通书》的早期版本不收《图》的这一事实,能进一步证实此《图》源出道家的猜测。
另外,对于所谓“太极安在”的问题,《说》中既已经有所回答:“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①这就是说,五行之统体即是阴阳之统体,也即是太极之统体(该图的第三层只是对其第二层的进一步展开与细化。同理,其第四层也是对第三层的进一步展开与细化)。显然,“太极安在”在最初的《图》中,本来就不应该是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图》与道家的渊源问题。其实,上述关于周与《图》及《书》的种种争论,最后都落脚在了《图》与道家的渊源问题上:无论是《图》“阴静”在上、“阳动”在下的表述,还是《说》“无极而生太极”或“自无极而为太极”的表述,都能使人联想到某些道家理念:“无极生太极”、“有生于无”、“静为动本”等等。可以说,无论是《图》还是《说》的最初版本,都显示出了与道家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资料所限,我们目前只能说,不管《图》是不是为周敦颐所首创,它本身都明显带有道家思想的痕迹。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潘兴嗣所作的《先生墓志铭》(在中华书局本《周敦颐集》中,又作《周敦颐墓志铭》)中一段话的点断问题。潘在此文中提道:“(周敦颐)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今藏于家……”③对于这句话的点断,多年来一直争论不断。朱子认为,这句话中提到周敦颐的作品包括“《太极图》(朱子的意思,此《太极图》包括《图》和《说》)、《易说》和《易通》”三种。但是问题是,除了这句比较模糊的话之外,《易说》一书再也没有在其他文献中出现过,究竟存在不存在都是个问题。朱子自己则推测说:“盖《易说》既依经以解义,此(指《易通》)则通论其大旨,而不系于经者也”④云云。朱子的意思,《易说》不会是“通论”性质,否则就会和只有一篇的《太极图说》重复了。但是他的这一推测也很难成立:既然《易说》“依经以解义”为分说,《易通》“不系于经者”为总说,那么前者在篇幅上肯定是要多于后者。但是,“太极图易说易通”总共只有区区“数十篇”,其中就包括《太极图》一篇和《易通》四十篇,那么其总数又怎么可能只有这区区的“数十篇”?当然,《易说》也可能只是周敦颐尚未完成的且篇幅不大的残稿。对此问题,材料所限,我们只能存疑。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朱子关于《易说》的推测明显存在着漏洞。
那么,潘的这段话为什么就不能点断为“……作《太极图易说》(即《太极图说》)和《易通》(即《通书》)数十篇……”,也就是说周敦颐只是作了这两部书呢?值得注意的是,假设周敦颐真的是作了三书,而且它们也都被其后人“藏于家”的话,那么何以后来周的家人在编订“九江本”时,却没有收入已经是成文,而且又被藏于家的《图》呢?再者,据潘的这段话来看,根本不可能是像祁宽后来所说的那样,周敦颐只是把《图》单独传授给了二程(否则“藏于家”的《太极图》又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就是祁宽本人对自己的表述也将信将疑,所以才使用了“或云”二字,而当今的许多学者却对此二字视而不见)。再进一步说,既然潘兴嗣说过《图》与《说》都早已公开流传(至少是潘自己知道此事),而程门弟子们又说周敦颐又曾把《图》传授给了二程,何以二程自己却从来没有明确提及过事实上早已经被公开的《图》呢?自从朱子以来,许多人都试图对此疑问做出过解答,却都难以令人满意。仅以朱子的回答为例。一方面,朱子强调二程确有祖述《图》的文字:“程氏之书,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铭》、《程邵公志》、《颜子好学论》等篇,乃或并其语而道之”①;另一方面,朱子则强调二程不言《图》和《说》,是因为“《太极图》立象尽意,剖析幽微,周子盖不得已而作也。观其手授之意,盖以为唯程子为能受之;程子之秘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尔”②。此二说都难以成立:朱子提到的三篇文章,都没有表现出与《图》的确切关联(至多能说在义理上与《说》有一些联系),更没有出现《图》和《书》的具体名称与内容,难怪朱子只能以“乃或”二字作为结论。
另外,朱子说“观其手授之意,盖以为唯程子为能受之”云云,更是与事实不符(见潘志)。再者,二程与周敦颐的接触,都在其早年。我们很难想象周会把自己甚为私密的东西单独传给两个十几岁的少年。况且,二程对周子的著作并未热心整理,却听任其散失(假如《易说》真的存在的话),这其中就包括所谓“秘传”的《太极图》,这绝对不合常理。最后,据祁宽的记述,“《通书》始出于程门侯师圣”云云。我们也很难想象,二程最终选定的“能受之者”,就是默默无闻的侯师圣。
其实,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潘的这段话只是说周敦颐作了《太极图易说》和《易通》这两部书,而且此两书也都被其后人“藏于家”,并且又都被其后人收入了“故家传本”中。潘的这段话和“九江本”中,都只是没有提到《图》罢了。由此,《图》很有可能长期处于秘传状态,直到后来才被二程的弟子们所公开。他们又显然认为,《太极图易说》就是对“太极图”(而非“太极”)的解说,所以才会在刊刻周敦颐的著作时,把《图》附在《通书》之后。从这方面来说,《图》的原始出处的确令人生疑。当然,也存在另一种情况,即周敦颐在晚年直接把《图》传给了侯师圣,而侯师圣则据此编订了《通书》,这中间并没有转手于二程。事实上,这一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图》的最初面貌的问题。关于此问题,大家也有许多争论。简言之,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图》,最早见于朱震《汉上易传》中的《周氏太极图》(编订于绍兴五年,即1135年)。应该说,此幅“图”也最接近周教颐所解说之“图”的本来面目。但是,朱子后来在编订《太极通书》时,却对此《图》甚为不满。他在未说出确切版本依据的情况下,就对此图做出了调整:把旧图第一圈标注“阴静”、第二圈标注“阳动”的格局,改为第一圈为“无极而太极”,第二圈左侧标“阳动”,右侧标“阴静”;又对此图第三圈的五行相生顺序做出了调整(关于这一点,笔者曾有专文论述,此不赘述)。朱子提出改动的理由为:“既以第一圈为阴静,第二圈为阳动,则夫所谓太极者,果安在耶……且所论先有专一之阴,后有兼体之阳,是乃截然之甚者。”①我们说,朱子不能接受“阴静”在上、“阳动”在下、阴阳截然分开的旧图,这完全是其个人认为《图》一定出自淳儒之手的信念所致。而朱子反复述说“旧图”的安排与《说》中的理念不合,这反倒是有舍本逐末的嫌疑:《说》本来就是来解释《图》的,它应该要符合《图》所体现出的理念才对,朱子反而要让《图》去迁就《说》,这在逻辑上有些不尽合理。总之,《图》很有可能包含着有道家思想的因素,至少是《图》的作者对于儒道之间的界限并不像朱子那样的敏感。《通书》的早期版本不收《图》的这一事实,能进一步证实此《图》源出道家的猜测。
另外,对于所谓“太极安在”的问题,《说》中既已经有所回答:“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①这就是说,五行之统体即是阴阳之统体,也即是太极之统体(该图的第三层只是对其第二层的进一步展开与细化。同理,其第四层也是对第三层的进一步展开与细化)。显然,“太极安在”在最初的《图》中,本来就不应该是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图》与道家的渊源问题。其实,上述关于周与《图》及《书》的种种争论,最后都落脚在了《图》与道家的渊源问题上:无论是《图》“阴静”在上、“阳动”在下的表述,还是《说》“无极而生太极”或“自无极而为太极”的表述,都能使人联想到某些道家理念:“无极生太极”、“有生于无”、“静为动本”等等。可以说,无论是《图》还是《说》的最初版本,都显示出了与道家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资料所限,我们目前只能说,不管《图》是不是为周敦颐所首创,它本身都明显带有道家思想的痕迹。
附注
③《朱子全书》第二十六册,第776页。
④《略论〈诸儒鸣道集〉》,第31页。
⑤《道学宗主》,第26页。
⑥《朱子全书》第二十六册,第776页。又见束景南著《朱熹年谱长编》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27页。
①束景南《周敦颐〈太极图说〉新考》,《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②朱子编订“长沙本”通书的具体年代不详,据后来编订于1169年的“建安本”《通书》的后续来看,“长沙本”的编订要在此之前。束景南以为“长沙本”刻于1166年,未有确证,见其《朱熹年谱长编》,第348—349页。据本人考证,“长沙本”确实刊刻于1166年,证据将另文刊发。
③朱子早年即接触到了周敦颐的著作,他在《周子通书后记》中提道,“熹自早岁即幸得其遗编而伏读之,初盖茫然不知其所谓,而甚或不能以句。壮岁获游延平先生之门,然后始得闻其说之一二,比年,潜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见《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第3857页。其最初接触的应该是《通书》的程门传本,但他后来编订“长沙本”,既已经提到了“九江本”。从祁宽提出“九江旧本”到朱子参考“九江本”编订“长沙本”,前后不过短短十几年,这中间很难再冒出一个所谓后出的“九江本”,却不被人发现。
④朱子在对《说》首句的问题上,从来都不妥协,因此才会与洪适发生那么大的冲突。如果朱子比较出杨方本“九江本”为后出,而且又作“无极而生太极”的话,那么他是不会视而不见的。
①(宋)朱震《汉上易传》,《汉上易传卦图》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页。
①《周敦颐集·通书后跋》,第111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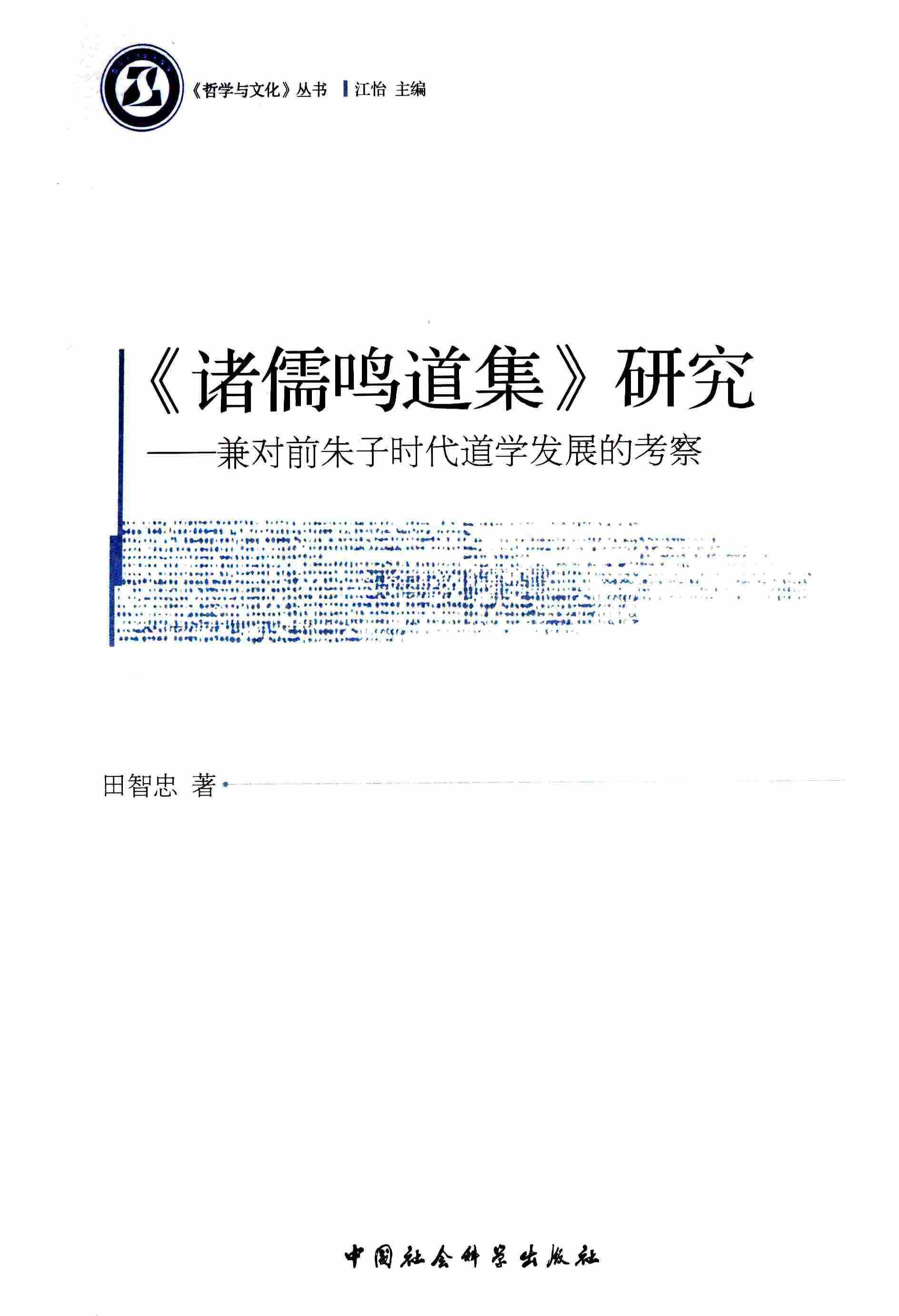
《《诸儒鸣道集》研究》
出版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内容包括:《诸儒鸣道集》原刻年代考、关于《诸儒鸣道集》编者身份的初步推测、《诸儒鸣道集》视野下的宋代儒学多元性研究、周敦颐与张载的道学话语构建、二程对道学话语的构建、谢良佐与杨时对道学话语的构建等。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