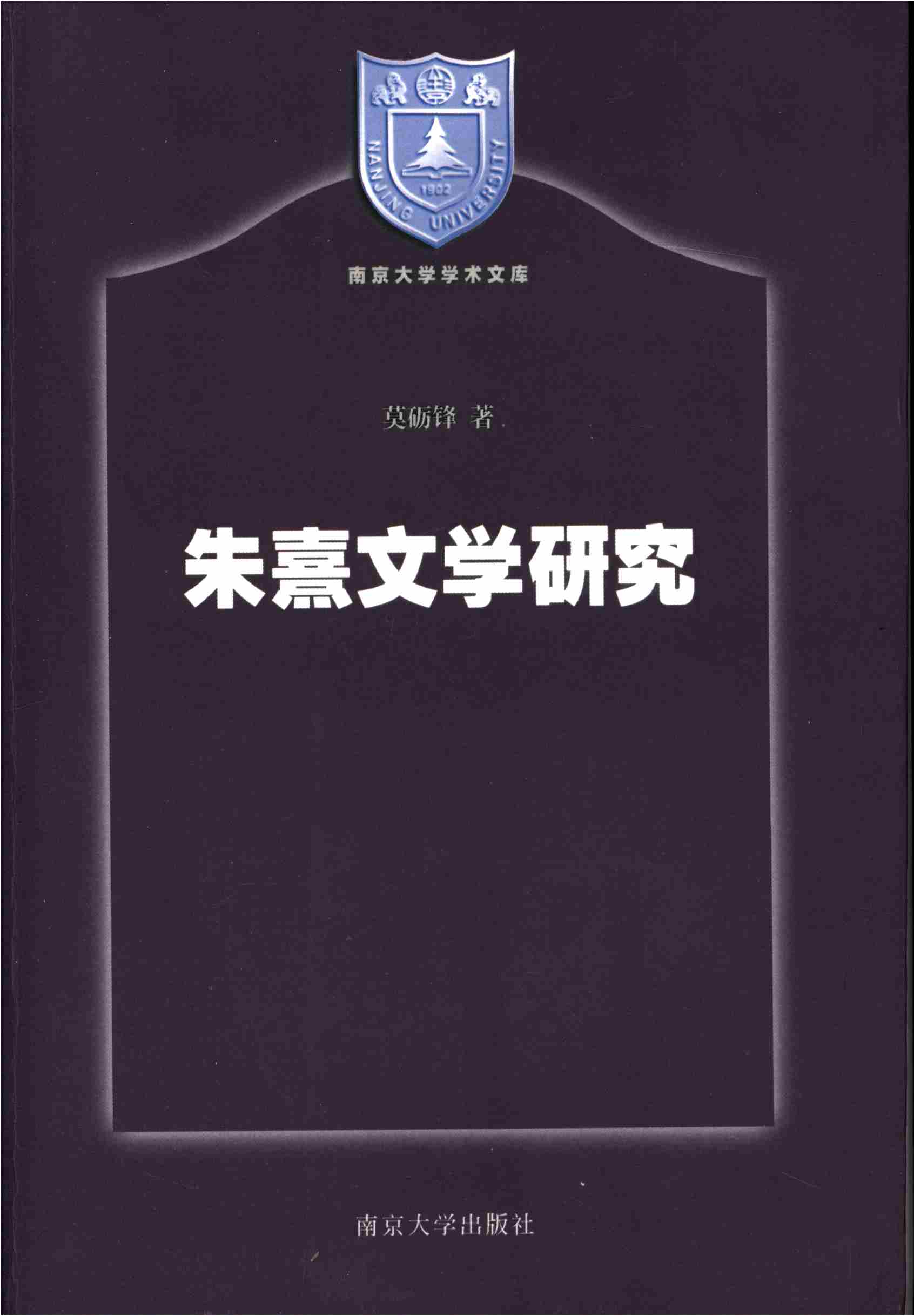内容
朱熹晚年回忆自己学诗的经历说:“向来初见拟古诗,将谓只是学古人之诗。元来却是如古人说‘灼灼园中花’,自家也做一句如此;‘迟迟涧底松’,自家也做一句如此;‘磊磊涧中石’,自家也做一句如此;‘人生天地间’,自家也做一句如此。意思语脉,皆要似他底,只换却字。某后来依他如此做得二三十首诗,便觉得长进。盖意思句语血脉势向,皆效他底。大率古人文章皆是行正路,后来杜撰底皆是行狭隘邪路去了。”①他所见到的“拟古诗”,当是指陆机、江淹等人的拟古之作,所拟对象应是汉魏古诗。上述四个例句中后两句皆出自《古诗十九首》之三②,便为明证。朱熹青年时的写作确是经过了这么一个“拟古”阶段,例如《文集》卷一所收的《拟古八首》,便是分别摹拟《古诗十九首》之二、五、六、七、八、十二、十八、十九诸首的,现举一例与所拟之古诗对照如下:
拟古八首(其六)
高楼一何高,俯瞰穷山河。秋风一夕至,憔悴已复多。寒暑递推迁,岁月如颓波。离骚感迟暮,惜誓闵蹉跎。放意极欢虞,咄此可奈何。邯郸多名姬,素艳凌朝华。妖歌掩齐右,缓舞倾阳阿。徘徊起梁尘,綷縩纷衣罗。丽服秉奇芬,顾我长咨嗟。愿生乔木阴,夤缘若丝萝。
古诗十九首(其十二)
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回风动地起,秋草萎已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驰情整中带,沈吟聊踯躅。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两诗的内容及其层次是完全一致的:建筑巍峨—秋季忽至—时光迅速—岁暮之感—纵情娱乐—美女如云—歌舞之美—音乐之悲—转乐为叹—思结佳偶。有些句子也与原作如出一辙,如“放意极欢娱”与“荡涤放情志”,“邯郸多名妓”与“燕赵多美人”,真可谓“自家也做一句如此”。那么是否可以说朱熹的拟古诗毫无艺术价值呢?也不尽然,我们不妨再举一首陆机的拟古诗作为参照:
拟古诗十二首(其九) 陆机
西山何其峻,曾屈郁崔巍。零露弥天坠,蕙叶凭林衰。寒暑相因袭,时逝忽如颓。三闾结飞辔,大耋嗟落晖。曷为牵世务,中心若有违。京洛多妖丽,玉颜侔琼蕤。闲夜抚鸣琴,惠音清且悲。长歌赴促节,哀响逐高徽。一唱万夫和,再唱梁尘飞。思为河曲鸟,双游丰水湄。
陆机此诗被选入了《文选》,可见它的价值受到相当的重视。然而朱熹的拟作后来居上:一是对原诗的旨意理解得更准确,如原诗“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两句引用《诗经》的篇章以抒忧生感时之情怀,①朱诗引《离骚》、《惜誓》这两篇楚辞作品以写类似之情,可谓铢两相称。而陆诗上句以“三闾”指代屈原,以“结飞辔”缩写《离骚》中“总余辔乎扶桑”句意;下句则隐括《周易·离第三十》中“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句意,句法既与原作不类,句意也不够显豁。二是朱诗仿其意而不仿其句,颇能推陈出新,如尾联与原诗一样写思结佳偶之意,但以丝萝附乔木取代燕子结巢之喻,辞意俱新。而陆诗却仍沿用飞鸟为喻,且缺少了依附对方之意,显得很笨拙。由此可见,朱熹的拟古之作并不是简单的亦步亦趋,而是在深入体会原诗意旨后的成功模仿。
当然,像《拟古八首》那样逐句模仿古诗的作品是朱熹早年的一种练习,他后来很快就摆脱了这种初学者之窗课的做法,但是部分地模仿前人的痕迹却存在于很多朱诗中,例如:
一、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晋诗》卷一七)朱熹仿之有两例,《寄题梅川溪堂》云:“静有山水乐,而无车马喧。”(《文集》卷二,第7页。)又《夏日二首》之一云:“静有图史乐,寂有车马喧。”(《文集》卷二,第21页)
二、陶渊明《和郭主簿二首》之一云:“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晋诗》卷一六)朱熹《夏日二首》之二云:“季夏园木暗,窗户贮清阴。”(《文集》卷二,第22页)
三、谢灵运《登江中孤屿》云:“乱流趋孤屿,孤屿媚中川。”(《宋诗》卷二)朱熹《汲清泉渍奇石置熏炉其后香烟披之江山云物居然有万里趣因作四小诗》之一云:“晴窗出寸碧,倒影媚中川。”(《文集》卷二,第22页)
四、谢灵运《登江中孤屿》云:“想象昆山姿,缅邈区中缘。”朱熹《寄山中旧知七首》之一云:“未谐物外期,已绝区中缘。”(《文集》卷一,第15页)
五、杜甫《远游》云:“似闻胡骑走,失喜问京华。”(《杜诗详注》卷一一)朱熹《和张彦辅初到南康之句》云:“失喜清诗还入手。”(《文集》卷七,第8页)
六、杜甫《江畔寻花七绝句》之五云:“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杜诗详注》卷一〇)又杜甫《曲江对雨》云:“暂醉佳人锦瑟傍。”(《杜诗详注》卷六)朱熹《次韵秀野早梅》云:“可爱红芳爱素芳。”又云:“肯醉佳人锦瑟傍。”(《文集》卷三,第11页)
七、杜甫《拨闷》云:“闻道云安麴米春,才倾一盏即愁人。”(《杜诗详注》卷一四)朱熹《酒市二首》之一云:“闻说崇安市,家家麴米春。”又云:“一酌便还醇。”(《文集》卷三,第17页)
八、杜甫《江汉》云:“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杜诗详注》卷二三)朱熹《至上封用择之韵》云:“天高云共色,夜永月同明。”(《文集》卷五,第6页)
九、韦应物《东郊》云:“微雨霭芳原。”(《全唐诗》卷一八六)朱熹《社日诸人集西冈》云:“郊原暧芳物,细雨青春时。”(《文集》卷一,第9页)按:“霭”与“暧”虽然是两字,但音相近,且都有遮蔽、昏暗之义,①朱熹当是模仿韦诗时误“霭”作“暧”,或他所见的韦诗原作“暧”。
十、苏轼《吊徐德占》云:“一遭儿女污,始觉山林尊。”(《苏轼诗集》卷二一)朱熹《承事卓丈置酒白云山居饮饯致政储丈叔通因出佳句诸公皆和熹辄亦继韵聊发座中一笑》云:“山林儿女定谁尊。”(《文集》卷九,第8页)
上面十个例证中,五、九两例是模仿前人的用字之法的,其余诸例是模仿前人句法的。这些被模仿的对象大多是立意精警、构思新颖的范例,故朱熹熟记于心,写诗时便受其影响,所以一篇作品中仅有一两句或一两字有模仿痕迹,这显然已经不是“自家也做一句如此”式的有意模仿,而是触境而生的随机性借鉴了。
从上述例证来看,朱熹在字句细节上的借鉴对象并无什么倾向性,因为这些诗人的时代、风格各不相同,朱熹对他们的评价也高低不一,可见他在这方面采取了“清词丽句必为邻”①的态度。然而朱熹在风格论上实有很强的倾向性,他非常推崇“选诗”即魏晋古诗,尤其推崇陶诗,并下及与陶诗风格相近的韦应物诗。如果说朱熹诗在整体风格上有所仿效的话,那么最明显的就是仿效陶、韦诗那种萧散淡远之风,例如:
正月五日欲用斜川故事结客载酒过伯休新居风雨不果二月五日始克践约坐间以陶公卒章二十字分韵熹得中字赋呈诸同游者
玄景凋暮节,青阳变暄风。忽得斜川句,感此胜日逢。
驾言当出游,一写浩荡胸。云物疑异候,凄迷久连空。
今朝复何朝,顿觉芳景融。畴曩庶复践,邻曲欢来同。
伊雅一篮舆,连翩数枝筇。绿野生远思,清川照衰容。
遥瞻西山足,突兀弥亩宫。庭宇豁清旷,林园郁青葱。
于焉一逍遥,芳樽间鸣桐。既爵日树隐,班荆汀草丰。
纤鳞动微波,新荑冠幽丛。惆怅景易晏,徘徊思无穷。
愿书今日怀,远寄柴桑翁。仰止固穷节,愧兹百年中。
与诸同僚谒奠北山过白岩小憩
联车涉修坂,览物穷山川。疏林泛朝景,翠岭含云烟。祠殿何沉邃,古木郁苍然。明灵自安宅,牲酒告恭虔。肹响理潜通,神蚪亦蜿蜒。既欣岁事举,重喜景物妍。解带憩精庐,尊酌且留连。纵谈遗名迹,烦虑绝拘牵。迅晷谅难留,归轸忽已骞。苍苍暮色起,反旆东城阡。
客舍听雨
沉沉苍山郭,暮景含余清。春霭起林际,满空寒雨生。投装即虚馆,檐响通夕鸣。遥想山斋夜,萧萧木叶声。
试院即事
端居惜春晚,庭树绿已深。重门掩昼静,高馆正阴沉。披衣步前除,悟物怀贞心。淡泊方自适,好鸟鸣高林。
第一首是作者声明的学陶之作,陶渊明《游斜川》序云:“辛酉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①朱熹效此故事,偕友游山而作此诗。因陶诗最后四句为“中肠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朱熹分韵得“中”字,遂以包含“中”字的“东”及“冬”二部为韵。此诗不但表达了对陶渊明的敬仰之情,而且全诗风格也极类陶诗:从出游的原因写到游览的经过,从邻曲的欢聚写到对昔贤的追慕,娓娓道来,如话家常。诗意的层次全依事情的顺序而自然展开,绝无章法上的有意安排。情感上虽有欢愉与惆怅的变化,但心情相当平淡,变化也很舒缓,一切都是襟怀的自然流露。朱熹曾评陶说:“渊明所以为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费安排处。”①从此诗来看,他对陶诗特点不仅有深刻的认识,而且曾身体力行地进行学习,所以在理性的论析中含有感性的把握。
第二首也体现出陶诗的影响,尤其是在诗意的自然推进方面,但它同时又融入了谢灵运诗风的一些因素,比如全诗共十联二十句,其中基本形成对仗的即多达七联,即只有“肹响”、“解带”、“苍苍”三联为散句。又如“纵谈遗名迹,烦虑绝拘牵”二句颇似谢诗中的玄言部分,还有少数句子如“肹响”、“迅晷”句稍形雕琢而欠自然,这些都或多或少地显示出谢灵运影响的痕迹。
三、四两首诗也与陶、谢诗风有渊源关系,例如“暮景含余清”一句显然受谢诗“密林含余清”②之启发,而全诗的朴素风格则类陶诗。然而,它们的直接仿效对象却是韦应物诗,这不是体现在字句的借鉴如“重门掩昼静”之于韦诗“绿阴生昼静”③,而是整体风格的神似,请对照韦诗:
寺居独夜寄崔主簿
幽人寂不寐,木叶纷纷落。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坐使青灯晓,还伤夏衣薄。宁知岁方晏,离居更萧索。
新秋夜寄诸弟
两地俱秋夕,相望共星河。高梧一叶下,空斋归思多。方用忧人瘼,况自抱微疴。无将别来近,颜鬓已蹉跎。
朱熹对韦应物是特加推许的,他说:“韦苏州诗高于王维、孟浩然诸人,以其无声色臭味也。”①他还评“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二句:“此景色可想,但只是自在说了……其诗无一字做作,直是自在。”②韦应物的诗本来是呈多样性面貌的,正如白居易所说:“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③然而使韦诗自成一家从而以“韦苏州体”而跻身于唐代诸体之列的却正是他那闲淡自然的风格,④朱熹对此极表称赏,可谓独具只眼。简单地说,韦诗是淡泊的情感内蕴和平淡的艺术外貌的完美结合,比如上举二例,岁月流逝的感喟,亲友离别的惆怅,都是淡淡说来,仿佛是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在平静地回忆往事。与之相称的是,它们在语言上自然朴素,举凡典故、比喻等修辞技巧,一概不用。写景则纯为白描,几乎没有什么颜色和音响方面的形容。第一首中仅有“青灯”一词涉及色彩,然而在“寒雨暗深更”的背景下,一点青荧荧的灯光反而更衬托出氛围的暗淡。第二首中写到高梧落叶,这在韩愈笔下会有“空阶一片下,琤若摧琅玕”⑤的奇妙声响,可是在韦诗中却只是用一个“下”字写其飘落而已。朱熹说韦诗“无声色臭味”,即不诉诸读者的听觉、视觉或嗅觉,从而实现了真正的平淡。朱熹的两首诗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体现出对韦诗意境的逼近:凄清寂寞的环境,恬淡宁静的心情,简练明白的叙述,朴实无华的语言。虽说朱诗的内蕴与韦诗并不相同,后者是历经荣枯者的归真返朴,而前者却是一位睿智的哲人对世俗的超越,但是那种淡泊而未至于枯寂的情趣却十分相似。朱熹推崇韦诗且进行模仿,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从“选诗”到韦应物诗,它们对朱熹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五言古诗中。朱熹的近体诗,尤其是他的律诗,则另有其艺术渊源。例如:
九日登天湖以菊花须插满头归分韵赋诗得归字
去岁潇湘重九时,满城寒雨客思归。故山此日还佳节,黄菊清樽更晚晖。短发无多休落帽,长风不断且吹衣。相看下视人寰小,只合从今老翠微。
次韵雪后书事二首(其一)
惆怅江头几树梅,杖藜行绕去还来。前时雪压无寻处,昨夜月明依旧开。折寄遥怜人似玉,相思应恨劫成灰。沉吟日落寒鸦起,却望柴荆独徘徊。
这两首七律分别被方回选入《瀛奎律髓》卷一六和卷二〇,方回评前一首说:“予尝谓文公诗深得后山三昧,而世人不识。山谷、简斋皆有此格。此诗后四句尤意气阔远。”清人冯舒驳之:“若谓晦翁学黄、陈,晦翁必不服。”①平心而论,方回说朱熹此诗近于陈师道诗是相当准确的,下面举陈诗一首为例:
九日寄秦觏
疾风回雨水明霞,沙步丛祠欲暮鸦。九日清尊欺白发,十年为客负黄花。登高怀远心如在,向老逢辰意有加。淮海少年天下士,可能无地落乌纱。
我们不必认定朱诗的次联在文字上有借鉴陈诗次联之痕,但两诗在风格上的相似是一目了然的:平淡的感情中渗透着沉雄之气,质朴的语言中暗藏着凝练之美。中间两联的对仗在工整之中颇见疏放之致,上下句的意思相去甚远,断无类似合掌的缺点。两诗都只用了一个典故,即孟嘉在九日风吹落帽的故事①,但这是人所共知的常典,用在九日诗中又很妥贴,毫无深奥难解之病。朱熹论诗,推重“不为雕刻纂组之工,而其平易从容不费力处,乃有余味”②的老成之境,上述二诗就是这种风格的典范之作,这正是朱熹有取于陈师道诗的关键。朱熹的后一首诗其实是咏梅诗,方回《瀛奎律髓》中选入卷二〇“咏梅类”,甚确。然而此诗几乎无一字一句涉及梅花的色香,而注重于环境的烘托和感情的渲染,从而刻画梅花的精神和标格。这种遗貌取神、虚处着笔的手法和剥落浮华、苍老劲健的风格也正是陈师道诗风的因素。③
有一个问题需要稍作辨析。方回论朱熹诗的艺术渊源,有时是黄、陈并称的,他曾在《夜读朱文公年谱》之一中说:“澹庵老荐此诗人,屈道何妨可致身。负鼎干汤公岂肯,本来余事压黄陈。”④但更多的则是仅及陈师道,如《瀛奎律髓》卷二〇中云:“文公诗似陈后山,劲瘦清绝,而世人不识。”后人往往责备方回一意维护江西诗派并依托道学,①而对方回言及黄、陈实有轩轾之别却未予注意。其实,方回对整个江西诗派诸子的评价是有所区别的,而这直接影响到他对朱熹诗学渊源的看法。黄庭坚、陈师道虽然都是江西诗派巨擘,而且陈师道本人还自认身属黄门弟子之列,但正如陈振孙所云:“后山虽曰‘见豫章之诗,尽弃所学而学焉。’然其造诣平淡,真趣自然,实豫章之所缺也。”②黄诗平淡、自然的一面主要体现在晚期诗风归真返朴之时,而其最引人注目的风格特征却是早期诗的生新瘦硬,方回正是这样体认黄诗的。《瀛奎律髓》中选入的黄诗多数作于早期,只有四首作于晚年,其中又偏偏包括拗峭生新的《题胡逸老致虚庵》和语言精丽的《次韵雨丝云鹤二首》③,可见方回对晚期黄诗的风格转变未予重视。陈诗则不然,陈诗中虽然也偶有华美之作,但其主导风格无疑是质朴平淡,且终身以之,无怪乎方回要对之情有独钟了。《瀛奎律髓》中选黄诗仅三十五首,而陈诗却高达一百三十一首,颇能说明方回的倾向性。朱熹对黄、陈没有明显的轩轾之见,但他认为“山谷则刻意为之”,“山谷诗忒好了”④。又认为“后山雅健强似山谷,然气力不似山谷较大,但却无山谷许多轻浮底意思。”⑤这种态度与方回很相似,所以朱熹诗风与陈师道较接近,是合于逻辑的文学现象。
那么,朱熹的古诗仿效陶、韦,而他的律诗则受陈师道的影响,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内在的统一性呢?或者说,这是否反映出同样的风格追求呢?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陶、韦诗风的萧散淡远与陈师道诗风的质朴劲瘦可以用一个外延更大的概念来统摄,那就是平淡自然。众所周知,自从欧阳修、梅尧臣以来,宋诗的整体艺术趋向就是平淡自然。因为从魏晋到唐代,古典诗歌最重要的变化是在声律、丽辞等艺术手段上的巨大进步,这一进步至李白、杜甫而达到巅峰状态。虽说唐人在追求艺术完美的同时也念念不忘向清真自然的回归,但以陶诗为代表的较少人工雕琢而更为自然朴素的诗美境界毕竟是一去不复返了。于是,当宋人怀着与唐人争胜的心态回顾诗歌史时,他们的目光就有意无意地越过唐诗的巅峰而追溯至先唐时代,苏轼说:“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恣,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①这是北宋后期诗坛上颇有代表性的看法。朱熹之父朱松对此亦持相近的观点,他说:
至汉,苏、李浑然天成,去古未远。魏晋以降,迨及江左,虽已不复古人制作之本意,然清新富丽,亦各名家,而皆萧然有拔俗之韵。至今读之,使人有世表意。唐李、杜出,而古今诗人皆废。自是而后,贱儒小生,膏吻鼓舌,决章裂句,青黄相配,组绣错出。(《上赵漕书》,《韦斋集》卷九)
朱熹的看法与之一脉相承,他说:“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②所不同的是,朱熹进而认为苏轼等北宋诗人尚未能复归平淡,他指出:“坡公病李、杜而推韦、柳,盖亦自悔其平时之作而未能自拔者。”①在朱熹看来,苏轼等元祐诗人虽然已看到了复归陶、韦诗的平淡境界的必要性,但他们的创作仍有太工、太奇的缺点,他批评说:“东坡则华艳处多。”②“黄鲁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气。”③因此,朱熹对苏、黄以后的诗人趋于平淡的表现都深表赞赏,除了陈师道外,他还称赞陆游诗“不费力,好。”④称赞刘叔通诗“平易从容不费力处,乃有余味。”⑤所以说,在朱熹心目中,平淡自然的风格本是诗歌的最高境界,陶、韦等人的诗是这种诗风的典范,而宋人的艺术追求也是以此为终极目标的。虽说陈师道等人所体现的质朴诗风并不完全等同于陶、韦诗风,但其本质都是以平淡自然为特征的,仅仅是诗体或古或律,有所不同而已。
其次,朱熹在重道轻文的思想的支配下,反对在诗歌写作中多费心力,他说:“近世诸公作诗费工夫,要何用?”又说:“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陷溺尔。当其不应事时,平淡自摄,岂不胜如思量诗句?至如真味发溢,又却与寻常好吟者不同。”⑥既要作诗,又不肯多耗心力于此,其必然的结果便是趋于平易。朱熹幼时颇用力于诗文,但很快便把主要精力投入理学之研讨,而对诗文则不甚措意了。他晚年对弟子说:“某四十以前,尚要学人做文章,后来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后来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岁做底文字。”⑦所以在朱熹看来,作诗的关键在于言志,即在于思想内涵,而形式上的工拙是无关紧要的。他说:
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辞之善否,今以魏晋以前诸贤之作考之,盖未有用意于其间者,而况于古诗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于此,故诗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答杨宋卿》,《文集》卷三九,第3页)
显然,“格律”、“属对”(即对仗)等专属于律诗的形式因素,先唐诗中当然是没有的,但朱熹特地拈出“魏晋以前”,可见他对谢灵运等人的讲究骈偶,永明体诗人的讲求声病也是不以为然的。至于连“比事”(即用典)、“遣辞”(即炼字炼句)的“善否”都不用意的,那当然应以汉魏古诗和晋代以朴素为尚的陶诗为典范。然而朱熹毕竟是生活在近体诗格律早已建立、近体早已成为与古体平分秋色的主要诗体的时代,他不能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所以他对近体诗采取了尽量淡化其形式特征的态度,也即希望不多留意于“格律之精粗”,以追求一种与“葩藻之词胜”相反的美学倾向。这样,他当然会对北宋以来的追求平淡之美的诗学风尚表示认同,从而在七律的写作中与朴拙平淡的陈师道诗风比较接近了。
综上所述,朱熹是这样的一位诗人:他具有很丰富的诗学史知识、很明确的诗学观点,他崇尚平淡自然的美学境界,反对在形式、技巧上多费心力。他具有敏锐的审美能力,常常把自然景色当作纯粹的审美对象加以吟咏。当然他同时又是一位理学家,难免要写一些述志明理而缺少审美意味的作品。然而在平易自然这个方面,他的各类诗作都表现出同样的倾向。试看二例:
屡游庐阜欲赋一篇而不能就六月中休董役卧龙偶成此诗
登车闽岭徼,息驾康山阳。康山高不极,连峰郁苍苍。金轮西嵯峨,五老东昂藏。想象仙圣集,似闻笙鹤翔。林谷下凄迷,云关杳相望。千岩虽竞秀,二胜终莫量。仰瞻银河翻,俯看交龙骧。长吟谪仙句,和以玉局章。畴昔劳梦想,兹今幸徜徉。尚恨忝符竹,未惬栖云房。已寻两峰间,结屋依阳冈。上有飞瀑驶,下有清流长。循名协心期,吊古增悲凉。壮齿乏奇节,颓年矧昏荒。誓将尘土踪,暂寄水云乡。封章倘从欲,归哉澡沧浪。
鹅湖寺和陆子寿
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前一首作于淳熙六年(1179),时朱熹五十岁。朱熹于前一年被任为知南康军,屡辞不允,不得不于六年三月到达南康任所。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距庐山主峰仅二十余里。朱熹到任后虽然忙于政事,但仍常有机会游览庐山。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非常努力地进行学术和教育工作,他修复了庐山南麓的白鹿洞书院,刻经求书,聚徒讲学,以一代儒宗的面目出现于庐山之中。然而此诗却是一首纯粹的游览抒情诗,从中嗅不出丝毫的理学家气息。首二句说自己离开武夷来到庐山,极其简明地交代了游踪。接下去用二十二句写庐山之景和游览过程:连峰极天,郁郁葱葱,令人想象有神仙居于其巅。然山峰之美比诸峡间瀑流,尚逊一筹。“二胜”当指开先漱玉亭和栖贤院三峡桥,因苏轼游庐山时作诗咏此二景,称为“庐山二胜”①,故而得名。朱熹面对着飞湍瀑流之奇景,不由得吟咏李白和苏轼的诗篇②。然而李白、苏轼的庐山诗都写得雄奇俊逸,壮伟不凡,朱熹此诗却相当平易、质朴,显然这并不完全是才力大小之原因,而是由于朱熹独特的审美追求所致。
后一首也作于淳熙六年。四年以前,也即淳熙二年(1775),朱熹曾与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在铅山鹅湖寺会晤论学,因意见不合而未能取得结论。当时陆九龄曾作诗一首表明他的观点。如今朱熹赴南康任途经铅山,寄寓在观音寺,陆九龄专程从抚州赶来相会。显然这一次的朱陆晤谈比前一次较有创获,而自由讨论的空气也更加活跃。所以朱熹追和四年前的陆诗而写了这首诗。应该承认,朱、陆双方的思想分歧是原则性的,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尤其是南辕北辙,水火不能相容,所以他们的论学文字往往语气激烈,措辞尖锐。然而这首诗却不同,它字句平易,语气舒缓,洋溢着心平气和、谦逊乐群的气息。前半首写自己对二陆的敬佩之情以及这次相晤的经过,娓娓写来,如道家常。后半首写论学的情形,深邃细密的思想内容却出之以平实质朴的语言外表,颇有绚烂之极复归平淡的意味。由此可见,朱熹诗的平易自然倾向是全局性的,并不把某些特殊的题材作为载体。
当然,最典型地反映其诗风的作品当推那些写景抒怀之作:
淳熙甲辰春精舍闲居戏作武夷棹歌十首呈诸同游相与一笑
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
一曲溪边上钓船,幔亭峰影蘸晴川。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
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道人不复阳台梦,兴入前山翠几重。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棹几何年?桑田海水今如许,泡沫风灯敢自怜。
四曲东西两石岩,岩花垂露碧㲯毵。金鸡叫罢无人见,月满空山水满潭。
五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雨暗平林。林间有客无人识,欸乃声中万古心。
六曲苍屏绕碧湾,茆茨终日掩柴关。客来倚棹岩花落,猿鸟不惊春意闲。
七曲移舟上碧滩,隐屏仙掌更回看。却怜昨夜峰头雨,添得飞泉几道寒。
八曲风烟势欲开,鼓楼岩下水萦洄。莫言此地无佳景,自是游人不上来。
九曲将穷眼豁然,桑麻雨露见平川。渔郎更觅桃源路,除是人间别有天。
如果说朱熹的有些诗作由于过多地展示一代学术宗师的严肃形象从而减损了自然活泼的气息,那么这组诗正以其宛肖民歌风调而使上述损害减低到最低程度了。“棹歌”本为民歌,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〇收入《櫂歌行》十四首,编入《相和歌辞》,且引《乐府解题》曰:“晋乐奏魏明帝辞云‘王者布大化’,备言平吴之勋。若晋陆机‘迟迟春欲暮’、梁简文帝‘妾住在湘川’,但言乘舟鼓櫂而已。”其实究其本质,“棹歌”的原貌就应该是“但言乘舟鼓櫂”,是舟子的“劳者歌其事”,是劳动生活中自然节拍的流露。不但魏明帝“备言平吴之勋”是外加于民歌的政治含义,就是陆机写龙舟、羽旗的贵族出游与简文帝咏及宫嫔美貌等内容也不是题中应有之义。朱熹这组诗则完全摆脱了文人拟作乐府的陈辞滥调,还民歌以清新自然的生活本色。我们知道,朱熹在武夷九曲溪边结庐而居,但他的主要时间都忙于著书讲学,并未沉迷于明山秀水。诚如其友韩元吉在《武夷精舍记》中所描写的:“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学行其乡,善其徒,非若畸人隐士,遁藏山谷,服气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夫子,圣人也,其步与趋莫不有则。至于登泰山之巅,而诵言于舞雩之下,未尝不游,胸中盖自有地。”①然而在这组诗中,我们却看不到朱熹著书讲学生涯的蛛丝马迹,山川景物也没有被当作证道参禅的物质载体,也就是说,这组诗与理学家朱熹没多少关系,它们是诗人朱熹以活泼的诗心摹仿民歌而写成的天籁之作。武夷山下的九曲溪,溪水萦回九折,两岸山峰随步移形,各成胜景。对这种风光,民歌的惯例是依空间顺序逐一吟唱,再合成一个整体。朱熹此诗有没有以民间船歌为蓝本已不可考,但这种从一曲写到九曲的手法则分明是借鉴民歌的。诗中对景物的形容多与民间传说有关,如写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便是因玉女峰峰顶多杂树野花,故民间传说玉女喜爱插花,这个传说至今尚存。又如“一曲”诗中的“虹桥”、“四曲”诗中的“金鸡”,也都源于神话传说。这组诗的语言也具有民歌的风韵:自然,流畅,生动,活泼。诗中偶有成语典故,如“三曲”诗中“桑田海水”用《神仙传》中麻姑之语,“泡沫风灯”用佛典语,①但这些成语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且与此诗慨叹岩船之年代荒远事十分贴切,读来不觉其中有典,没有减损诗语的自然之趣。诗的立意构思则活泼而饶谐趣,如“二曲”诗以拟人手法写玉女峰,插花临水,楚楚动人,可是第三句却说“道人不复阳台梦”,意谓不受玉女之撩拨而想入非非,极有风趣,理学大师道貌岸然的严肃性荡然无存。然而这组诗又不是单纯写景之作,除了诗人对山水自然的喜爱心情外,诗中还渗入了他对自然的感受和思考。岩船之古老使诗人兴时光迅速之叹,数声柔橹也使他悟得万古寂寞之心。然而,这些感受和思考都没有用深奥晦涩的哲理性语言来表达,而是不着形迹地渗入了清丽的艺术形象中间。也就是说,这组诗的写景和抒情是高度融合的,心物相感,情景相融,已经形成浑然一体的意境。如此清新流丽的模山范水、吟风弄月之作竟然出现在朱熹这位理学大师的笔下,真是艺术的奇迹。难怪虽然在当时就有许多人作诗唱和,后世的继作者更是代不乏人,但至今为止还得推朱熹十歌为咏武夷九曲的千古绝唱。真正的好诗是不可重复的。
拟古八首(其六)
高楼一何高,俯瞰穷山河。秋风一夕至,憔悴已复多。寒暑递推迁,岁月如颓波。离骚感迟暮,惜誓闵蹉跎。放意极欢虞,咄此可奈何。邯郸多名姬,素艳凌朝华。妖歌掩齐右,缓舞倾阳阿。徘徊起梁尘,綷縩纷衣罗。丽服秉奇芬,顾我长咨嗟。愿生乔木阴,夤缘若丝萝。
古诗十九首(其十二)
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回风动地起,秋草萎已绿。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驰情整中带,沈吟聊踯躅。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两诗的内容及其层次是完全一致的:建筑巍峨—秋季忽至—时光迅速—岁暮之感—纵情娱乐—美女如云—歌舞之美—音乐之悲—转乐为叹—思结佳偶。有些句子也与原作如出一辙,如“放意极欢娱”与“荡涤放情志”,“邯郸多名妓”与“燕赵多美人”,真可谓“自家也做一句如此”。那么是否可以说朱熹的拟古诗毫无艺术价值呢?也不尽然,我们不妨再举一首陆机的拟古诗作为参照:
拟古诗十二首(其九) 陆机
西山何其峻,曾屈郁崔巍。零露弥天坠,蕙叶凭林衰。寒暑相因袭,时逝忽如颓。三闾结飞辔,大耋嗟落晖。曷为牵世务,中心若有违。京洛多妖丽,玉颜侔琼蕤。闲夜抚鸣琴,惠音清且悲。长歌赴促节,哀响逐高徽。一唱万夫和,再唱梁尘飞。思为河曲鸟,双游丰水湄。
陆机此诗被选入了《文选》,可见它的价值受到相当的重视。然而朱熹的拟作后来居上:一是对原诗的旨意理解得更准确,如原诗“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两句引用《诗经》的篇章以抒忧生感时之情怀,①朱诗引《离骚》、《惜誓》这两篇楚辞作品以写类似之情,可谓铢两相称。而陆诗上句以“三闾”指代屈原,以“结飞辔”缩写《离骚》中“总余辔乎扶桑”句意;下句则隐括《周易·离第三十》中“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句意,句法既与原作不类,句意也不够显豁。二是朱诗仿其意而不仿其句,颇能推陈出新,如尾联与原诗一样写思结佳偶之意,但以丝萝附乔木取代燕子结巢之喻,辞意俱新。而陆诗却仍沿用飞鸟为喻,且缺少了依附对方之意,显得很笨拙。由此可见,朱熹的拟古之作并不是简单的亦步亦趋,而是在深入体会原诗意旨后的成功模仿。
当然,像《拟古八首》那样逐句模仿古诗的作品是朱熹早年的一种练习,他后来很快就摆脱了这种初学者之窗课的做法,但是部分地模仿前人的痕迹却存在于很多朱诗中,例如:
一、陶渊明《饮酒二十首》之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晋诗》卷一七)朱熹仿之有两例,《寄题梅川溪堂》云:“静有山水乐,而无车马喧。”(《文集》卷二,第7页。)又《夏日二首》之一云:“静有图史乐,寂有车马喧。”(《文集》卷二,第21页)
二、陶渊明《和郭主簿二首》之一云:“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晋诗》卷一六)朱熹《夏日二首》之二云:“季夏园木暗,窗户贮清阴。”(《文集》卷二,第22页)
三、谢灵运《登江中孤屿》云:“乱流趋孤屿,孤屿媚中川。”(《宋诗》卷二)朱熹《汲清泉渍奇石置熏炉其后香烟披之江山云物居然有万里趣因作四小诗》之一云:“晴窗出寸碧,倒影媚中川。”(《文集》卷二,第22页)
四、谢灵运《登江中孤屿》云:“想象昆山姿,缅邈区中缘。”朱熹《寄山中旧知七首》之一云:“未谐物外期,已绝区中缘。”(《文集》卷一,第15页)
五、杜甫《远游》云:“似闻胡骑走,失喜问京华。”(《杜诗详注》卷一一)朱熹《和张彦辅初到南康之句》云:“失喜清诗还入手。”(《文集》卷七,第8页)
六、杜甫《江畔寻花七绝句》之五云:“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杜诗详注》卷一〇)又杜甫《曲江对雨》云:“暂醉佳人锦瑟傍。”(《杜诗详注》卷六)朱熹《次韵秀野早梅》云:“可爱红芳爱素芳。”又云:“肯醉佳人锦瑟傍。”(《文集》卷三,第11页)
七、杜甫《拨闷》云:“闻道云安麴米春,才倾一盏即愁人。”(《杜诗详注》卷一四)朱熹《酒市二首》之一云:“闻说崇安市,家家麴米春。”又云:“一酌便还醇。”(《文集》卷三,第17页)
八、杜甫《江汉》云:“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杜诗详注》卷二三)朱熹《至上封用择之韵》云:“天高云共色,夜永月同明。”(《文集》卷五,第6页)
九、韦应物《东郊》云:“微雨霭芳原。”(《全唐诗》卷一八六)朱熹《社日诸人集西冈》云:“郊原暧芳物,细雨青春时。”(《文集》卷一,第9页)按:“霭”与“暧”虽然是两字,但音相近,且都有遮蔽、昏暗之义,①朱熹当是模仿韦诗时误“霭”作“暧”,或他所见的韦诗原作“暧”。
十、苏轼《吊徐德占》云:“一遭儿女污,始觉山林尊。”(《苏轼诗集》卷二一)朱熹《承事卓丈置酒白云山居饮饯致政储丈叔通因出佳句诸公皆和熹辄亦继韵聊发座中一笑》云:“山林儿女定谁尊。”(《文集》卷九,第8页)
上面十个例证中,五、九两例是模仿前人的用字之法的,其余诸例是模仿前人句法的。这些被模仿的对象大多是立意精警、构思新颖的范例,故朱熹熟记于心,写诗时便受其影响,所以一篇作品中仅有一两句或一两字有模仿痕迹,这显然已经不是“自家也做一句如此”式的有意模仿,而是触境而生的随机性借鉴了。
从上述例证来看,朱熹在字句细节上的借鉴对象并无什么倾向性,因为这些诗人的时代、风格各不相同,朱熹对他们的评价也高低不一,可见他在这方面采取了“清词丽句必为邻”①的态度。然而朱熹在风格论上实有很强的倾向性,他非常推崇“选诗”即魏晋古诗,尤其推崇陶诗,并下及与陶诗风格相近的韦应物诗。如果说朱熹诗在整体风格上有所仿效的话,那么最明显的就是仿效陶、韦诗那种萧散淡远之风,例如:
正月五日欲用斜川故事结客载酒过伯休新居风雨不果二月五日始克践约坐间以陶公卒章二十字分韵熹得中字赋呈诸同游者
玄景凋暮节,青阳变暄风。忽得斜川句,感此胜日逢。
驾言当出游,一写浩荡胸。云物疑异候,凄迷久连空。
今朝复何朝,顿觉芳景融。畴曩庶复践,邻曲欢来同。
伊雅一篮舆,连翩数枝筇。绿野生远思,清川照衰容。
遥瞻西山足,突兀弥亩宫。庭宇豁清旷,林园郁青葱。
于焉一逍遥,芳樽间鸣桐。既爵日树隐,班荆汀草丰。
纤鳞动微波,新荑冠幽丛。惆怅景易晏,徘徊思无穷。
愿书今日怀,远寄柴桑翁。仰止固穷节,愧兹百年中。
与诸同僚谒奠北山过白岩小憩
联车涉修坂,览物穷山川。疏林泛朝景,翠岭含云烟。祠殿何沉邃,古木郁苍然。明灵自安宅,牲酒告恭虔。肹响理潜通,神蚪亦蜿蜒。既欣岁事举,重喜景物妍。解带憩精庐,尊酌且留连。纵谈遗名迹,烦虑绝拘牵。迅晷谅难留,归轸忽已骞。苍苍暮色起,反旆东城阡。
客舍听雨
沉沉苍山郭,暮景含余清。春霭起林际,满空寒雨生。投装即虚馆,檐响通夕鸣。遥想山斋夜,萧萧木叶声。
试院即事
端居惜春晚,庭树绿已深。重门掩昼静,高馆正阴沉。披衣步前除,悟物怀贞心。淡泊方自适,好鸟鸣高林。
第一首是作者声明的学陶之作,陶渊明《游斜川》序云:“辛酉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①朱熹效此故事,偕友游山而作此诗。因陶诗最后四句为“中肠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朱熹分韵得“中”字,遂以包含“中”字的“东”及“冬”二部为韵。此诗不但表达了对陶渊明的敬仰之情,而且全诗风格也极类陶诗:从出游的原因写到游览的经过,从邻曲的欢聚写到对昔贤的追慕,娓娓道来,如话家常。诗意的层次全依事情的顺序而自然展开,绝无章法上的有意安排。情感上虽有欢愉与惆怅的变化,但心情相当平淡,变化也很舒缓,一切都是襟怀的自然流露。朱熹曾评陶说:“渊明所以为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费安排处。”①从此诗来看,他对陶诗特点不仅有深刻的认识,而且曾身体力行地进行学习,所以在理性的论析中含有感性的把握。
第二首也体现出陶诗的影响,尤其是在诗意的自然推进方面,但它同时又融入了谢灵运诗风的一些因素,比如全诗共十联二十句,其中基本形成对仗的即多达七联,即只有“肹响”、“解带”、“苍苍”三联为散句。又如“纵谈遗名迹,烦虑绝拘牵”二句颇似谢诗中的玄言部分,还有少数句子如“肹响”、“迅晷”句稍形雕琢而欠自然,这些都或多或少地显示出谢灵运影响的痕迹。
三、四两首诗也与陶、谢诗风有渊源关系,例如“暮景含余清”一句显然受谢诗“密林含余清”②之启发,而全诗的朴素风格则类陶诗。然而,它们的直接仿效对象却是韦应物诗,这不是体现在字句的借鉴如“重门掩昼静”之于韦诗“绿阴生昼静”③,而是整体风格的神似,请对照韦诗:
寺居独夜寄崔主簿
幽人寂不寐,木叶纷纷落。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坐使青灯晓,还伤夏衣薄。宁知岁方晏,离居更萧索。
新秋夜寄诸弟
两地俱秋夕,相望共星河。高梧一叶下,空斋归思多。方用忧人瘼,况自抱微疴。无将别来近,颜鬓已蹉跎。
朱熹对韦应物是特加推许的,他说:“韦苏州诗高于王维、孟浩然诸人,以其无声色臭味也。”①他还评“寒雨暗深更,流萤度高阁”二句:“此景色可想,但只是自在说了……其诗无一字做作,直是自在。”②韦应物的诗本来是呈多样性面貌的,正如白居易所说:“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③然而使韦诗自成一家从而以“韦苏州体”而跻身于唐代诸体之列的却正是他那闲淡自然的风格,④朱熹对此极表称赏,可谓独具只眼。简单地说,韦诗是淡泊的情感内蕴和平淡的艺术外貌的完美结合,比如上举二例,岁月流逝的感喟,亲友离别的惆怅,都是淡淡说来,仿佛是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在平静地回忆往事。与之相称的是,它们在语言上自然朴素,举凡典故、比喻等修辞技巧,一概不用。写景则纯为白描,几乎没有什么颜色和音响方面的形容。第一首中仅有“青灯”一词涉及色彩,然而在“寒雨暗深更”的背景下,一点青荧荧的灯光反而更衬托出氛围的暗淡。第二首中写到高梧落叶,这在韩愈笔下会有“空阶一片下,琤若摧琅玕”⑤的奇妙声响,可是在韦诗中却只是用一个“下”字写其飘落而已。朱熹说韦诗“无声色臭味”,即不诉诸读者的听觉、视觉或嗅觉,从而实现了真正的平淡。朱熹的两首诗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体现出对韦诗意境的逼近:凄清寂寞的环境,恬淡宁静的心情,简练明白的叙述,朴实无华的语言。虽说朱诗的内蕴与韦诗并不相同,后者是历经荣枯者的归真返朴,而前者却是一位睿智的哲人对世俗的超越,但是那种淡泊而未至于枯寂的情趣却十分相似。朱熹推崇韦诗且进行模仿,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从“选诗”到韦应物诗,它们对朱熹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五言古诗中。朱熹的近体诗,尤其是他的律诗,则另有其艺术渊源。例如:
九日登天湖以菊花须插满头归分韵赋诗得归字
去岁潇湘重九时,满城寒雨客思归。故山此日还佳节,黄菊清樽更晚晖。短发无多休落帽,长风不断且吹衣。相看下视人寰小,只合从今老翠微。
次韵雪后书事二首(其一)
惆怅江头几树梅,杖藜行绕去还来。前时雪压无寻处,昨夜月明依旧开。折寄遥怜人似玉,相思应恨劫成灰。沉吟日落寒鸦起,却望柴荆独徘徊。
这两首七律分别被方回选入《瀛奎律髓》卷一六和卷二〇,方回评前一首说:“予尝谓文公诗深得后山三昧,而世人不识。山谷、简斋皆有此格。此诗后四句尤意气阔远。”清人冯舒驳之:“若谓晦翁学黄、陈,晦翁必不服。”①平心而论,方回说朱熹此诗近于陈师道诗是相当准确的,下面举陈诗一首为例:
九日寄秦觏
疾风回雨水明霞,沙步丛祠欲暮鸦。九日清尊欺白发,十年为客负黄花。登高怀远心如在,向老逢辰意有加。淮海少年天下士,可能无地落乌纱。
我们不必认定朱诗的次联在文字上有借鉴陈诗次联之痕,但两诗在风格上的相似是一目了然的:平淡的感情中渗透着沉雄之气,质朴的语言中暗藏着凝练之美。中间两联的对仗在工整之中颇见疏放之致,上下句的意思相去甚远,断无类似合掌的缺点。两诗都只用了一个典故,即孟嘉在九日风吹落帽的故事①,但这是人所共知的常典,用在九日诗中又很妥贴,毫无深奥难解之病。朱熹论诗,推重“不为雕刻纂组之工,而其平易从容不费力处,乃有余味”②的老成之境,上述二诗就是这种风格的典范之作,这正是朱熹有取于陈师道诗的关键。朱熹的后一首诗其实是咏梅诗,方回《瀛奎律髓》中选入卷二〇“咏梅类”,甚确。然而此诗几乎无一字一句涉及梅花的色香,而注重于环境的烘托和感情的渲染,从而刻画梅花的精神和标格。这种遗貌取神、虚处着笔的手法和剥落浮华、苍老劲健的风格也正是陈师道诗风的因素。③
有一个问题需要稍作辨析。方回论朱熹诗的艺术渊源,有时是黄、陈并称的,他曾在《夜读朱文公年谱》之一中说:“澹庵老荐此诗人,屈道何妨可致身。负鼎干汤公岂肯,本来余事压黄陈。”④但更多的则是仅及陈师道,如《瀛奎律髓》卷二〇中云:“文公诗似陈后山,劲瘦清绝,而世人不识。”后人往往责备方回一意维护江西诗派并依托道学,①而对方回言及黄、陈实有轩轾之别却未予注意。其实,方回对整个江西诗派诸子的评价是有所区别的,而这直接影响到他对朱熹诗学渊源的看法。黄庭坚、陈师道虽然都是江西诗派巨擘,而且陈师道本人还自认身属黄门弟子之列,但正如陈振孙所云:“后山虽曰‘见豫章之诗,尽弃所学而学焉。’然其造诣平淡,真趣自然,实豫章之所缺也。”②黄诗平淡、自然的一面主要体现在晚期诗风归真返朴之时,而其最引人注目的风格特征却是早期诗的生新瘦硬,方回正是这样体认黄诗的。《瀛奎律髓》中选入的黄诗多数作于早期,只有四首作于晚年,其中又偏偏包括拗峭生新的《题胡逸老致虚庵》和语言精丽的《次韵雨丝云鹤二首》③,可见方回对晚期黄诗的风格转变未予重视。陈诗则不然,陈诗中虽然也偶有华美之作,但其主导风格无疑是质朴平淡,且终身以之,无怪乎方回要对之情有独钟了。《瀛奎律髓》中选黄诗仅三十五首,而陈诗却高达一百三十一首,颇能说明方回的倾向性。朱熹对黄、陈没有明显的轩轾之见,但他认为“山谷则刻意为之”,“山谷诗忒好了”④。又认为“后山雅健强似山谷,然气力不似山谷较大,但却无山谷许多轻浮底意思。”⑤这种态度与方回很相似,所以朱熹诗风与陈师道较接近,是合于逻辑的文学现象。
那么,朱熹的古诗仿效陶、韦,而他的律诗则受陈师道的影响,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内在的统一性呢?或者说,这是否反映出同样的风格追求呢?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陶、韦诗风的萧散淡远与陈师道诗风的质朴劲瘦可以用一个外延更大的概念来统摄,那就是平淡自然。众所周知,自从欧阳修、梅尧臣以来,宋诗的整体艺术趋向就是平淡自然。因为从魏晋到唐代,古典诗歌最重要的变化是在声律、丽辞等艺术手段上的巨大进步,这一进步至李白、杜甫而达到巅峰状态。虽说唐人在追求艺术完美的同时也念念不忘向清真自然的回归,但以陶诗为代表的较少人工雕琢而更为自然朴素的诗美境界毕竟是一去不复返了。于是,当宋人怀着与唐人争胜的心态回顾诗歌史时,他们的目光就有意无意地越过唐诗的巅峰而追溯至先唐时代,苏轼说:“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恣,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①这是北宋后期诗坛上颇有代表性的看法。朱熹之父朱松对此亦持相近的观点,他说:
至汉,苏、李浑然天成,去古未远。魏晋以降,迨及江左,虽已不复古人制作之本意,然清新富丽,亦各名家,而皆萧然有拔俗之韵。至今读之,使人有世表意。唐李、杜出,而古今诗人皆废。自是而后,贱儒小生,膏吻鼓舌,决章裂句,青黄相配,组绣错出。(《上赵漕书》,《韦斋集》卷九)
朱熹的看法与之一脉相承,他说:“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②所不同的是,朱熹进而认为苏轼等北宋诗人尚未能复归平淡,他指出:“坡公病李、杜而推韦、柳,盖亦自悔其平时之作而未能自拔者。”①在朱熹看来,苏轼等元祐诗人虽然已看到了复归陶、韦诗的平淡境界的必要性,但他们的创作仍有太工、太奇的缺点,他批评说:“东坡则华艳处多。”②“黄鲁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气。”③因此,朱熹对苏、黄以后的诗人趋于平淡的表现都深表赞赏,除了陈师道外,他还称赞陆游诗“不费力,好。”④称赞刘叔通诗“平易从容不费力处,乃有余味。”⑤所以说,在朱熹心目中,平淡自然的风格本是诗歌的最高境界,陶、韦等人的诗是这种诗风的典范,而宋人的艺术追求也是以此为终极目标的。虽说陈师道等人所体现的质朴诗风并不完全等同于陶、韦诗风,但其本质都是以平淡自然为特征的,仅仅是诗体或古或律,有所不同而已。
其次,朱熹在重道轻文的思想的支配下,反对在诗歌写作中多费心力,他说:“近世诸公作诗费工夫,要何用?”又说:“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陷溺尔。当其不应事时,平淡自摄,岂不胜如思量诗句?至如真味发溢,又却与寻常好吟者不同。”⑥既要作诗,又不肯多耗心力于此,其必然的结果便是趋于平易。朱熹幼时颇用力于诗文,但很快便把主要精力投入理学之研讨,而对诗文则不甚措意了。他晚年对弟子说:“某四十以前,尚要学人做文章,后来亦不暇及此矣。然而后来做底文字,便只是二十左右岁做底文字。”⑦所以在朱熹看来,作诗的关键在于言志,即在于思想内涵,而形式上的工拙是无关紧要的。他说:
诗者,志之所之。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然则诗者岂复有工拙哉?亦视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辞之善否,今以魏晋以前诸贤之作考之,盖未有用意于其间者,而况于古诗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于此,故诗有工拙之论,而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隐矣。(《答杨宋卿》,《文集》卷三九,第3页)
显然,“格律”、“属对”(即对仗)等专属于律诗的形式因素,先唐诗中当然是没有的,但朱熹特地拈出“魏晋以前”,可见他对谢灵运等人的讲究骈偶,永明体诗人的讲求声病也是不以为然的。至于连“比事”(即用典)、“遣辞”(即炼字炼句)的“善否”都不用意的,那当然应以汉魏古诗和晋代以朴素为尚的陶诗为典范。然而朱熹毕竟是生活在近体诗格律早已建立、近体早已成为与古体平分秋色的主要诗体的时代,他不能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所以他对近体诗采取了尽量淡化其形式特征的态度,也即希望不多留意于“格律之精粗”,以追求一种与“葩藻之词胜”相反的美学倾向。这样,他当然会对北宋以来的追求平淡之美的诗学风尚表示认同,从而在七律的写作中与朴拙平淡的陈师道诗风比较接近了。
综上所述,朱熹是这样的一位诗人:他具有很丰富的诗学史知识、很明确的诗学观点,他崇尚平淡自然的美学境界,反对在形式、技巧上多费心力。他具有敏锐的审美能力,常常把自然景色当作纯粹的审美对象加以吟咏。当然他同时又是一位理学家,难免要写一些述志明理而缺少审美意味的作品。然而在平易自然这个方面,他的各类诗作都表现出同样的倾向。试看二例:
屡游庐阜欲赋一篇而不能就六月中休董役卧龙偶成此诗
登车闽岭徼,息驾康山阳。康山高不极,连峰郁苍苍。金轮西嵯峨,五老东昂藏。想象仙圣集,似闻笙鹤翔。林谷下凄迷,云关杳相望。千岩虽竞秀,二胜终莫量。仰瞻银河翻,俯看交龙骧。长吟谪仙句,和以玉局章。畴昔劳梦想,兹今幸徜徉。尚恨忝符竹,未惬栖云房。已寻两峰间,结屋依阳冈。上有飞瀑驶,下有清流长。循名协心期,吊古增悲凉。壮齿乏奇节,颓年矧昏荒。誓将尘土踪,暂寄水云乡。封章倘从欲,归哉澡沧浪。
鹅湖寺和陆子寿
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前一首作于淳熙六年(1179),时朱熹五十岁。朱熹于前一年被任为知南康军,屡辞不允,不得不于六年三月到达南康任所。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距庐山主峰仅二十余里。朱熹到任后虽然忙于政事,但仍常有机会游览庐山。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非常努力地进行学术和教育工作,他修复了庐山南麓的白鹿洞书院,刻经求书,聚徒讲学,以一代儒宗的面目出现于庐山之中。然而此诗却是一首纯粹的游览抒情诗,从中嗅不出丝毫的理学家气息。首二句说自己离开武夷来到庐山,极其简明地交代了游踪。接下去用二十二句写庐山之景和游览过程:连峰极天,郁郁葱葱,令人想象有神仙居于其巅。然山峰之美比诸峡间瀑流,尚逊一筹。“二胜”当指开先漱玉亭和栖贤院三峡桥,因苏轼游庐山时作诗咏此二景,称为“庐山二胜”①,故而得名。朱熹面对着飞湍瀑流之奇景,不由得吟咏李白和苏轼的诗篇②。然而李白、苏轼的庐山诗都写得雄奇俊逸,壮伟不凡,朱熹此诗却相当平易、质朴,显然这并不完全是才力大小之原因,而是由于朱熹独特的审美追求所致。
后一首也作于淳熙六年。四年以前,也即淳熙二年(1775),朱熹曾与陆九龄、陆九渊兄弟在铅山鹅湖寺会晤论学,因意见不合而未能取得结论。当时陆九龄曾作诗一首表明他的观点。如今朱熹赴南康任途经铅山,寄寓在观音寺,陆九龄专程从抚州赶来相会。显然这一次的朱陆晤谈比前一次较有创获,而自由讨论的空气也更加活跃。所以朱熹追和四年前的陆诗而写了这首诗。应该承认,朱、陆双方的思想分歧是原则性的,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尤其是南辕北辙,水火不能相容,所以他们的论学文字往往语气激烈,措辞尖锐。然而这首诗却不同,它字句平易,语气舒缓,洋溢着心平气和、谦逊乐群的气息。前半首写自己对二陆的敬佩之情以及这次相晤的经过,娓娓写来,如道家常。后半首写论学的情形,深邃细密的思想内容却出之以平实质朴的语言外表,颇有绚烂之极复归平淡的意味。由此可见,朱熹诗的平易自然倾向是全局性的,并不把某些特殊的题材作为载体。
当然,最典型地反映其诗风的作品当推那些写景抒怀之作:
淳熙甲辰春精舍闲居戏作武夷棹歌十首呈诸同游相与一笑
武夷山上有仙灵,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识个中奇绝处,棹歌闲听两三声。
一曲溪边上钓船,幔亭峰影蘸晴川。虹桥一断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
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道人不复阳台梦,兴入前山翠几重。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棹几何年?桑田海水今如许,泡沫风灯敢自怜。
四曲东西两石岩,岩花垂露碧㲯毵。金鸡叫罢无人见,月满空山水满潭。
五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雨暗平林。林间有客无人识,欸乃声中万古心。
六曲苍屏绕碧湾,茆茨终日掩柴关。客来倚棹岩花落,猿鸟不惊春意闲。
七曲移舟上碧滩,隐屏仙掌更回看。却怜昨夜峰头雨,添得飞泉几道寒。
八曲风烟势欲开,鼓楼岩下水萦洄。莫言此地无佳景,自是游人不上来。
九曲将穷眼豁然,桑麻雨露见平川。渔郎更觅桃源路,除是人间别有天。
如果说朱熹的有些诗作由于过多地展示一代学术宗师的严肃形象从而减损了自然活泼的气息,那么这组诗正以其宛肖民歌风调而使上述损害减低到最低程度了。“棹歌”本为民歌,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〇收入《櫂歌行》十四首,编入《相和歌辞》,且引《乐府解题》曰:“晋乐奏魏明帝辞云‘王者布大化’,备言平吴之勋。若晋陆机‘迟迟春欲暮’、梁简文帝‘妾住在湘川’,但言乘舟鼓櫂而已。”其实究其本质,“棹歌”的原貌就应该是“但言乘舟鼓櫂”,是舟子的“劳者歌其事”,是劳动生活中自然节拍的流露。不但魏明帝“备言平吴之勋”是外加于民歌的政治含义,就是陆机写龙舟、羽旗的贵族出游与简文帝咏及宫嫔美貌等内容也不是题中应有之义。朱熹这组诗则完全摆脱了文人拟作乐府的陈辞滥调,还民歌以清新自然的生活本色。我们知道,朱熹在武夷九曲溪边结庐而居,但他的主要时间都忙于著书讲学,并未沉迷于明山秀水。诚如其友韩元吉在《武夷精舍记》中所描写的:“夫元晦,儒者也。方以学行其乡,善其徒,非若畸人隐士,遁藏山谷,服气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夫子,圣人也,其步与趋莫不有则。至于登泰山之巅,而诵言于舞雩之下,未尝不游,胸中盖自有地。”①然而在这组诗中,我们却看不到朱熹著书讲学生涯的蛛丝马迹,山川景物也没有被当作证道参禅的物质载体,也就是说,这组诗与理学家朱熹没多少关系,它们是诗人朱熹以活泼的诗心摹仿民歌而写成的天籁之作。武夷山下的九曲溪,溪水萦回九折,两岸山峰随步移形,各成胜景。对这种风光,民歌的惯例是依空间顺序逐一吟唱,再合成一个整体。朱熹此诗有没有以民间船歌为蓝本已不可考,但这种从一曲写到九曲的手法则分明是借鉴民歌的。诗中对景物的形容多与民间传说有关,如写玉女峰“插花临水为谁容”,便是因玉女峰峰顶多杂树野花,故民间传说玉女喜爱插花,这个传说至今尚存。又如“一曲”诗中的“虹桥”、“四曲”诗中的“金鸡”,也都源于神话传说。这组诗的语言也具有民歌的风韵:自然,流畅,生动,活泼。诗中偶有成语典故,如“三曲”诗中“桑田海水”用《神仙传》中麻姑之语,“泡沫风灯”用佛典语,①但这些成语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且与此诗慨叹岩船之年代荒远事十分贴切,读来不觉其中有典,没有减损诗语的自然之趣。诗的立意构思则活泼而饶谐趣,如“二曲”诗以拟人手法写玉女峰,插花临水,楚楚动人,可是第三句却说“道人不复阳台梦”,意谓不受玉女之撩拨而想入非非,极有风趣,理学大师道貌岸然的严肃性荡然无存。然而这组诗又不是单纯写景之作,除了诗人对山水自然的喜爱心情外,诗中还渗入了他对自然的感受和思考。岩船之古老使诗人兴时光迅速之叹,数声柔橹也使他悟得万古寂寞之心。然而,这些感受和思考都没有用深奥晦涩的哲理性语言来表达,而是不着形迹地渗入了清丽的艺术形象中间。也就是说,这组诗的写景和抒情是高度融合的,心物相感,情景相融,已经形成浑然一体的意境。如此清新流丽的模山范水、吟风弄月之作竟然出现在朱熹这位理学大师的笔下,真是艺术的奇迹。难怪虽然在当时就有许多人作诗唱和,后世的继作者更是代不乏人,但至今为止还得推朱熹十歌为咏武夷九曲的千古绝唱。真正的好诗是不可重复的。
相关人物
朱熹
相关人物
相关作品
拟古八首(其六)
相关作品
古诗十九首(其十二)
相关作品
拟古诗十二首(其九)
相关作品
正月五日欲用斜川故事...
相关作品
与诸同僚谒奠北山过白...
相关作品
客舍听雨
相关作品
试院即事
相关作品
寺居独夜寄崔主簿
相关作品
新秋夜寄诸弟
相关作品
九日登天湖以菊花须插...
相关作品
次韵雪后书事二首(其...
相关作品
九日寄秦觏
相关作品
屡游庐阜欲赋一篇而不...
相关作品
鹅湖寺和陆子寿
相关作品
淳熙甲辰春精舍闲居戏...
相关作品
淳熙甲辰春精舍闲居戏...
相关作品
淳熙甲辰春精舍闲居戏...
相关作品
淳熙甲辰春精舍闲居戏...
相关作品
淳熙甲辰春精舍闲居戏...
相关作品
淳熙甲辰春精舍闲居戏...
相关作品
淳熙甲辰春精舍闲居戏...
相关作品
淳熙甲辰春精舍闲居戏...
相关作品
淳熙甲辰春精舍闲居戏...
相关作品
淳熙甲辰春精舍闲居戏...
相关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