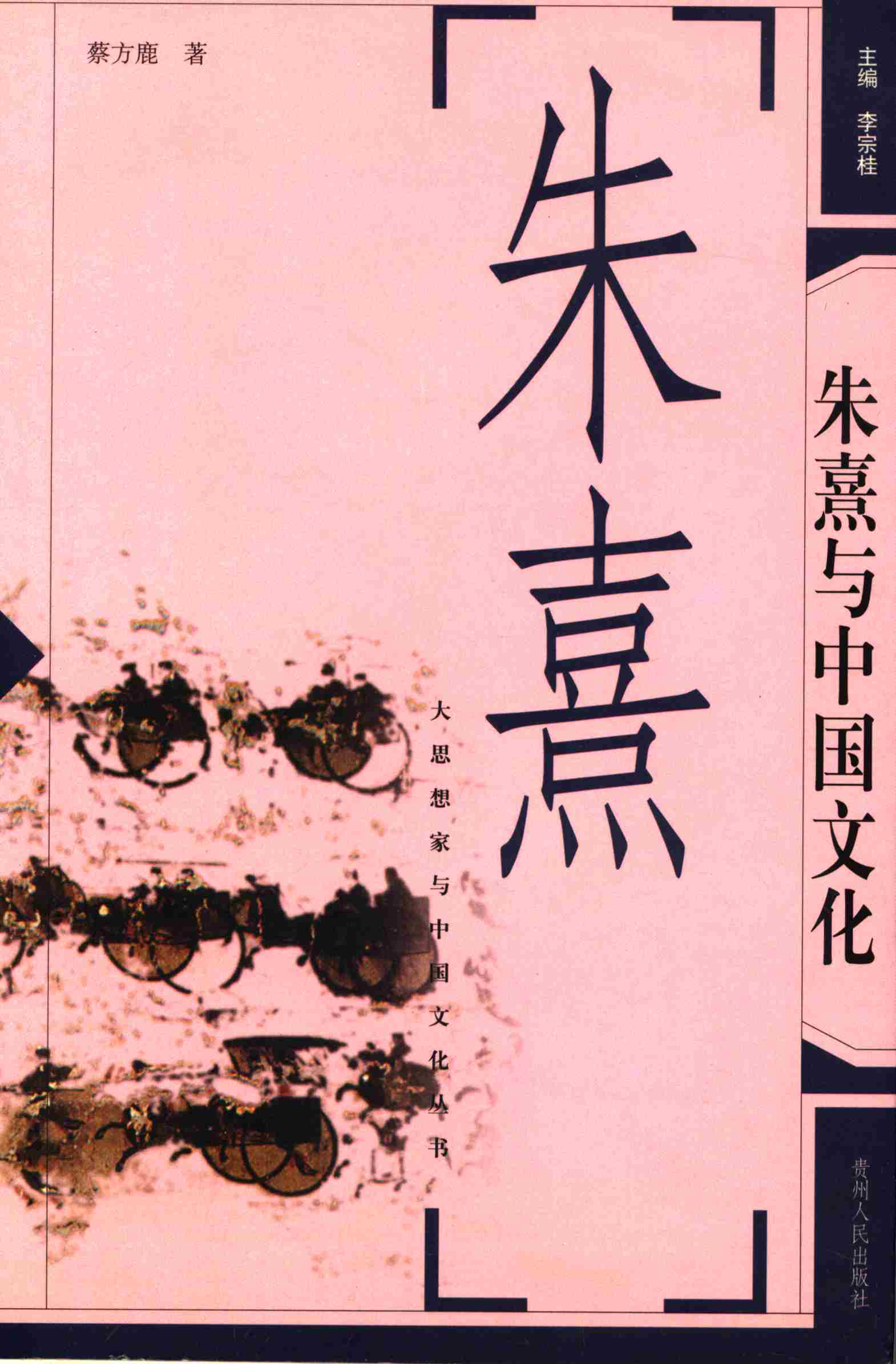第二节 朱熹全面系统总结、创新了中国传统文化
内容
在中国文化史上,前有孔、老,后有朱熹,均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果说,孔子和老子在先秦时期分别创立儒家和道家学派,形成儒道互补格局,对中国文化产生重大影响,那么,朱熹在一千多年后的宋代,适应中国社会与文化发展的需要,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包括孔、老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创新之功,恐无人堪与相比。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宋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发生了历史的转折和变革。在经济领域,土地制度国有逐渐转化为土地私有。随着土地占有制度的变革及门阀士族的消亡,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士庶界限被打破。宋朝廷完善发展了科举制度,大量庶族平民经科举加入官僚行列,形成文官统政的局面,这有利于思想文化的发展。面对唐五代社会动乱、伦常扫地带来的严重后果,思想家们要求复兴儒学,革新经学,重整纲常,这成为社会的普遍要求。中央集权制在宋代发展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并一定程度地出现君臣共治天下的“治体”。佛道宗教文化经大多数宋学学者的批判,已走向衰落,不能与前代盛极一时的情形相比,但其精致的思辨哲学又为理学家所吸取,用以提高儒学的哲学思辨水平。针对统治者和民间因感性欲望的过度泛滥而造成人无廉耻,社会生活失序,以及宗教冲击人文,逃父出家,不尽社会责任的局面,理学家提倡理性主义文化,以理性指导感性,以人文回应宗教;在理欲、公私、义利观方面,批评对个人欲望的放纵、追逐私利、以及宗教对个人责任的逃避等社会流弊,形成理性主义的文化氛围,但也因此而出现压抑个性和人欲的弊端。
朱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既以弘扬儒学及儒家圣人之道为己任,又发扬开放和超越精神,全面系统地总结并创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文化的经学、政治、哲学、伦理、宗教等各个领域,广泛涉猎,潜心钻研,总结传统文化包括北宋以来理学发展的成就,使中国文化更加丰富,更具理性色彩,进一步体现了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把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和总结者。
(一)遍注群经,对传统经学的总结
儒家经学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对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熹是经学中宋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遍注群经,对传统经学作了全面总结,既以阐发义理为治经之目的,这是他超出汉唐经学之处;又重训诂考据,对诸经详加训释,这是他对汉学的吸取,亦是他对宋学流弊的修正。由此朱熹对以往经学作出了总结。
朱熹遍注群经,表现在“四书”方面,便是在二程重视“四书”的基础上,总结唐以来开始出现的“四书”独立于“六经”的趋向,结合自己创建新经学思想体系的需要,以毕生精力注解《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书”。在阐发义理的同时,亦重对“四书”文字的训诂考据,把阐发义理与文字训诂结合起来,既批评汉魏诸儒只是训诂,而未玩味义理的倾向,亦不赞同宋学学者只讲义理,而轻视训诂考据的治学方法。一方面通过总结二程的“四书”学,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六经”训诂之学在经学发展史上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不废弃训诂考据之学,强调“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从而对汉、宋学都加以总结吸取,既以宋学为主,又超越汉、宋学之对立,由此发展了传统经学,并对后世的新汉学产生重要影响。
不仅如此,朱熹还注释了《周易》,撰《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总结以往易学之图书象数派和义理派的思想资料和观点,既重本义,重象数,又以义理为指导,把义理、卜筮、象数、图书相结合,从而总结发展了传统易学。
朱熹注解《诗经》,先主《小序》,而作《诗集解》;后悟前说之非,尽去《小序》,以《诗》说《诗》,而作《诗集传》,体现了朱熹诗学对旧说的总结和超越。
朱熹将自己治《尚书》之旨和有关注《尚书》的材料传授给学生蔡沈,令其作《书集传》。所以《书集传》亦可视为朱熹注《尚书》思想的反映。朱熹对《尚书》的注解和阐发,总结了以往的《尚书》辨伪工作,重视对心传说的阐发,在尚书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朱熹训解《礼》书,早年作《祭仪》和《家礼》,后酝酿修三礼书,晚年与弟子黄榦合撰《仪礼经传通解》。损益前代之礼,对以往礼学加以总结,提出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以《周礼》为纲领的思想,主张以礼来治国立教,体现了儒家礼治的精神。
朱熹又根据《春秋》大义,编纂《通鉴纲目》,定其凡例,法《春秋》大旨,明正统顺逆。以义理作为评判《春秋》经传的标准,把义理史学贯穿于春秋学的研究中,这也是对以往春秋学的总结和发展。
此外,朱熹依据《古文孝经》,撰《孝经刊误》,对以往的《孝经》版本和文字加以考释。认为《孝经》非孔子所自作,其经文部分是曾子门人记孔子、曾子问答之言。并删减《孝经》文字,重排其章目次序,一定程度地体现了他疑经惑传,改易经文,以义理释经的经学特点。
以上可见,朱熹学养深厚,遍注群经,对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诗》、《书》、《礼》、《春秋》、《孝经》等诸经加以注解、考释,全面总结了传统经学,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中国经学,成为经学史上宋学的集大成者。
(二)以天理治国,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总结
天理治国论是朱熹政治思想的核心,亦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总结和发展。二程提出以天理治国的思想,朱熹加以总结、完善和发展,把内在于人心的天理,贯彻到外在的政治事务中去,由内圣开出外王。并把天理上升为宇宙的根本法则,认为天理是治国的根本,其权威在君主的权威之上,要求包括帝王在内的统治者顺应天理,按天理的原则治理国家而不得违背。这充分体现了理学家政治思想的特点,亦是对以往政治文化的扬弃和总结。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多元复合型文化,除儒家文化外,其他各家的思想都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影响,如法家、道家、墨家、农家、名家,以及道教和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等,都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墨家的影响在先秦后大为减弱,农家、名家的思想影响有限,佛、道二教作为出世主义的宗教,少讲社会治理。真正对中国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首推儒家,以及法家和道家。儒家在吸取各家政治思想的过程中,前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和发展。
儒、法、道三家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既相互论争,又互相融合,其中儒家的政治思想以重人伦,讲仁义,施德政,道重于君为主;法家的政治思想以任刑罚,重权术,讲法治为主;道家则崇尚自然清静,无为而治,它们各自程度不同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然而,自汉代以来,儒术独尊,儒学在统治者的提倡下,不仅逐渐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而且演变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但儒家政治思想与封建统治者的专制政治有相当的区别,而不可混同。一般说,封建统治者的专制独裁以吸取法家思想为多,而儒学则反对专制独裁,反对统治者滥施暴政以虐民。孟子盛赞汤武革命,认为汤武革桀纣之命,杀暴君,只是诛独夫,而不是“臣弑其君”。荀子进而提出道高于君的思想,强调“从道不从君”,仁义之道重于君主之权位。这些思想得到了朱熹的继承,他提出天理治国论,从“治体”的高度批判了君主的“独断”,主张以道即天理对君权和封建统治者的特权加以一定的限制,认为治理国家,以道为本,道比权位更为重要,这也是对法家思想的扬弃。朱熹天理治国的思想主张“正君心”,把君主置于天理即道的约束之下,认为尽管君主权位至尊,但君主也不得违背天理,为了维护天理的最高权威,要求敢于矫君正君,不向邪恶势力低头。这具有道统高于君统,以道与专制君权相抗争的意义。亦是对传统政治文化尤其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总结。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其主要原因是封建专制主义和君主个人专制独裁阻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而这恰恰是专制统治者背弃了朱熹天理治国论中约束君权的思想所造成的恶果。
(三)“心统性情”,对中国心性哲学的总结
心性论是先秦儒家哲学、佛教哲学、宋明理学以至整个中国哲学的重要内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特点。朱熹吸取、改造先秦儒学心性论、佛教哲学心性论,又受到理学家张载、二程、胡宏思想的一定影响,与同时代学者相互辩学,提出了自己以“心统性情”说为纲领的心性论。这是对以往心性哲学的系统总结,达到了中国哲学心性论思想发展的高峰,并对后世中国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先秦是儒家心性之学的创立时期。孔子对心性问题论述不多,但其“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为仁由己”等思想却启发了孟子。在中国哲学史上,孟子最早给心以高度重视,并把心性联系起来加以论述,从而确立了儒家的心性哲学。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对后世包括对佛教心性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儒家心性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荀子进一步阐发了心的认识论功能,并提出与孟子性善论主张相对的性恶论。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先是受儒家心性之学特别是孟子思想的影响,大讲“尽心知性”及“穷理尽性”。后来佛教发展了儒学心性论,主要是以本体论心性,其哲学理论的思辨性明显高于先秦儒学心性论,但却抛弃了儒家心性论中的伦理道德内涵,因此与先秦儒家心性论有别。这遭到了朱熹等理学家的抨击。
朱熹在总结、吸取先前心性哲学思想资料的过程中,批评佛教心学的心本论思想及其心中无理、性中无德的倾向,同时又吸收了佛教心性论的思辨哲学,提出系统的“心统性情”思想,把儒家伦理与思辨哲学紧密结合,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心性论。朱熹以性为本,把儒家伦理提升为形上宇宙本体,又把心性与天理相联,这既丰富了儒家哲学心性论的内涵,又发展了中国心性哲学,使理性的、伦理的、人文的世俗思辨哲学逐步取代隋唐盛行的宗教哲学,改变了由唐至宋,儒、佛、道三家鼎立的局面,为宋以后儒家哲学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
(四)存理去欲,对传统伦理思想的总结
朱熹的理欲之辨不仅对后世影响甚大,而且亦是对以往伦理思想的总结。由于朱熹等理学家认为,理欲关系的理与义、公相通;理欲关系的欲与利、私相联。故其存理去欲思想与重义轻利、以义制利以及尊公蔑私、大公无私的思想相互沟通,在逻辑上构成一致,共同体现了宋代新儒学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伦理思想的总结。其利弊得失任凭后人评说,但在客观上却成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主导思想。由于朱熹的存理去欲思想集中体现了传统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价值观,故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朱熹的理欲之分原出于《礼记·乐记》篇:“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是说人容易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以至好恶无节,这样会造成人欲横流而天理灭绝的后果。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局面,历代思想家对此作了理论探讨,大多要求用天理节制人欲。
至宋代理欲问题成为伦理学讨论的中心问题。在朱熹以前关于理欲之辨的主要观点有二程的“灭私欲则天理明”,强调天理人欲的区分和对立,以及胡宏的“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既主张理欲相分,又认为理欲同体。朱熹对二程、胡宏的思想认真加以总结。他继承了二程“灭私欲则天理明”的思想,倡天理与私欲的对立,强调存理去欲,以公私、是非来区分理欲,要求克私立公,“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同时又把二程“男女之欲,理之常”的思想加以发展,提出天理安顿在人欲中,理欲互相依存的思想,并区别欲之二义。对于人的客观物质欲求,朱熹认为即使圣人也有此欲,因而不可去掉,并批判了佛教的禁欲主义;对于超过基本的客观物质欲望之上的私欲,朱熹主张去掉,强调“明天理,灭人欲”,此人欲即指私欲。
朱熹从理本论思想出发,又批评了胡宏天理人欲同体的思想,认为“本体实然只一天理,更无人欲”(《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三,《胡子知言疑义》),强调天理人欲之辨中理的主导地位,反对把理欲混为一体。由此,朱熹在对以往理欲之辨的总结中,提出了自己的独具特色的存理去欲思想,这对传统伦理思想影响很大。
(五)批判、吸取佛、道二教,对宗教文化的总结
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和本土生长的道教是中国最主要的两大宗教。宗教文化别具特色,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虽不及儒学大,但在隋唐时期也曾盛行一时,与儒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甚至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
朱熹早年出入佛老,拜禅师道谦和道士虚谷子为师,深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像朱熹这样的理学大师都曾受到过道佛的影响,表明佛道宗教文化自有其“高妙”处。一般说,佛教长于治心,以心性哲学和思辨哲理来论证其教旨教义,发挥宗教消除内心紧张,求得心灵安宁的社会功能;道教长于养身,通过修炼,得道成仙,与大自然合一,宣扬道为宇宙本体、万物之源。但佛道二教均有其短处,即不讲社会治理,其出世主义的宗教信仰与中国宗法社会及其制度形成矛盾,与儒家文化难以适调。
朱熹拜李侗为师后,弃佛老而归儒,以儒为宗,通过李侗而服膺理学,并集其大成。这与对佛道思想的批判吸取分不开。朱熹对佛教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批判佛教不讲儒家伦理纲常的出世主义的教旨教义及其与出世思想紧密联系的佛教哲学的“空”论、心本论、只内不外的思想等。在批佛的过程中,朱熹又一定程度地吸取借鉴了佛教的理事说、心性论、“宾主颂”、修养论等思想。
朱熹对道教包括道家的批评主要表现在,批评道教及道家厌世避祸,崇尚空寂以保全其身的思想,并批评其神仙思想和长生不死说。朱熹对道教的吸取主要表现在,借鉴道教之图,以阐发自己的易学及太极说;又考释道书,探讨道教修炼之术,以修养身心,并吸取道教的宇宙生成论等。
朱熹对佛道的批判和吸取,不仅对建构新儒学思想体系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对宗教文化的总结。朱熹批评佛道,表明宗教文化存在着与世俗的中国传统文化不相协调之处,因而需要协调,以适应以儒学为基础的中国文化。于是佛教逐步被改造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道教也由出世主义向世俗化逐渐转化。朱熹吸取佛道,表明佛道思想的优长之处对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朱熹所吸取的佛道思想的优长之处,既是其各自思想的精要,又是与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相互适应的部分。朱熹以儒学为本位即是以儒学作为取舍佛道思想的标准,在取舍佛道思想的过程中,必然对以佛道为代表的宗教文化作了一番全面的总结,凡与儒学价值观不合的,则加以排斥批判;凡有助于提高儒学思辨水平,促进儒学发展的,则加以吸收借鉴。从而在总结宗教文化的基础上,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以上可见,朱熹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开展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他遍注群经,对传统经学加以总结;提出以天理治国,对传统政治文化作出总结;提出“心统性情”论,对中国心性哲学作出总结;强调存理去欲,对传统伦理思想加以总结;既批判又吸取佛道二教,对宗教文化加以总结。朱熹在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总结反思中,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见解和独到的理论,从而创新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
朱熹不仅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在总结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加以综合创新。其对传统文化的创新,尤其体现了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朱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是综合性的、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首创“四书”之名,集“四书”学之大成
“四书”学的提出和确立,是程朱对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然二程只是开“四书”学之先河,提出基本的思想线索,其“四书”学的思想理论并不完备。朱熹则在二程提出的思想线索的基础上,在中国思想史上首创“四书”之名,把《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结集,合为四部最重要的儒家经典,其地位在“六经”之上。并以毕生精力集注“四书”,著《四书章句集注》,以重义理的理学思维模式取代汉学单纯重训诂的注经模式,集宋代“四书”学之大成,完成了中国经学史上的一大变革。朱熹的理学与其经学紧密联系,其理学思想也基本通过《四书集注》得以阐发,由此体现了朱熹“四书”学的重要性。
(二)首创“道统”二字,集道统论之大成
道统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传统文化产生重要影响。道统思想源远流长,历经发展演变,至宋代趋于成熟。但“道统”之名实由朱熹所首创,二字连用也始自朱熹。也就是说,道统的思想内涵古已有之,而“道统”的外在名称,其发明权却在朱熹①。朱熹不仅发明了道统二字,而且创新发展了道统的思想内涵,形式与内容相结合,从而集道统论之大成。
(三)兼采汉宋,把章句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
朱熹经学的一大特征是既以阐发义理作为治经的最高目标,又重对经文的训诂考据,把阐发义理建立在对经典章句文字训诂的基础上,从而兼采汉宋,把章句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既以宋学义理为主,同时也不废汉学文字考据的功夫。既批评汉学为考据而考据,重训诂而不及义理的治经倾向,亦修正宋学重义理轻考据,其义理缺乏根据的经学流弊。兼取汉宋之长而去其短,成为在宋学内部扬弃和发展宋学的代表人物,开明清之际汉宋兼采经学之先声。
(四)提出经传相分,直求经文之本义
超越传注,直求经文之本义是朱熹经学的又一特色。针对汉学但守注疏,“疏不破注”,以传代经,脱离经文本义而繁琐释经的弊端,和宋学只求传文之义理,援传于经,经传相混,使经文本义晦而不明的流弊,朱熹提出经传相分,直求经文之本义的思想,以作为普遍的经学方法论原则,强调分别经传,不以传注之学和推说之理取代对经文本义的探求。这是朱熹经学的一大创新,把义理的阐发建立在经文本义的基础上。以易学为例,朱熹强调《易经》的本义为卜筮,而《易传》所讲之义理也不得脱离经文的卜筮本义。由此他对程颐未讲《易经》的卜筮本义而专去阐发义理的倾向提出批评。朱熹的经传相分,直求经文之本义的思想贯穿在他经学诸经思想的各个方面,目的在于以经为本,而不以传注为本,反对学者把注意力转向传注之学,以致“看注而忘经”。但在以经为本,区分经传的前提下,朱熹也重视借鉴传文来探明经义,即重视借鉴先儒对经的训诂注疏来理解经文之本义。朱熹的这一思想具有辩证的因素,与批评前儒以传代经,以传注解经,看注而忘经并不矛盾。两者相辅相成,都是以经为本,目的在探求经文之本义。
(五)重经书辨伪,疑伪古文
重视经书辨伪工作,疑伪古文,这是朱熹经学研究的一大贡献。朱熹在对《尚书》学的研究中,在吴棫疑辨的基础上,进一步详加考订,辨西汉伏生与托名孔安国两家所传今古文之差异,黜《孔传》、《孔序》,以区别经文与伪《孔传》,直求经文之本义;又疑《书序》(朱熹称为《小序》),认为《书小序》不是孔子所作,而是周秦时的低手人所作,以恢复《尚书》的本来面目;朱熹对梅本《古文尚书》,即《孔传》本《古文尚书》提出怀疑,认为其书至东晋方出,疑其书是假书。这启发了后世的经书辨伪工作,最终判明梅本古文是伪《古文尚书》,《孔安国尚书传》是伪《孔传》。
(六)阐发“十六字心传”
朱熹据《论语·尧曰》、《中庸》、《荀子·解蔽》和《尚书·大禹谟》,阐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传。这一思想在理学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亦是朱熹的创新。朱熹认为,“十六字心传”作为圣人相传之“密旨”和“心法”,是以义理之心即道心为标准,随时而为“中”,通过心心相传,心灵感悟,把圣人之道传授下来。这为理学家所看重,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虽然《尚书·大禹谟》是朱熹所疑之伪古文,但《大禹谟》的作者提出的“十六字传心诀”,其依据却在《论语·尧曰》、《荀子·解蔽》以及《中庸》等儒家著作。朱熹也是根据上述著作来阐发其“十六字心传”思想,并把“十六字传心诀”与《中庸》的“孔门传授心法”结合起来,这体现了朱熹对接续圣人之心的重视。
(七)黜《毛序》,以《诗》说《诗》
朱熹在对《诗经》的研究中,提出与汉唐《诗》学传统迥然相异的废弃《毛诗序》,以《诗》说《诗》,而反对以《序》说《诗》的思想。对传统《毛序》的美刺说、“止乎礼义”说提出批评。认为《诗序》出自汉儒卫宏等,而与《诗》文本义不符,如果按《序》的意思解《诗》,只能是牵强附会,而有违诗人作《诗》之本意。所以朱熹作《诗集传》,便把《序》从各诗中除去,而弃置于《诗》后。此外,朱熹于《诗》三百篇中,指出有二十多篇淫奔之诗,为淫佚之人所自叙之辞,而非皆为圣贤教人之作。故对孔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诗说提出异议。朱熹对《毛序》的批评和废弃,以及对“思无邪”说的异议,使得千年来的诗学传统遭到了有力的挑战,体现了朱熹的创新精神。
(八)图书象数与义理合一
有宋一代易学,大抵分为象数和义理两派,其象数派又衍出图书之学。宋易发展到南宋,朱熹针对程颐过分讲义理而轻视象数,以及象数派穿凿附会入于末流,而忽视义理的两种偏向,提出以义理思想为指导,重本义,重象数,以图书作为象数之源,图书中蕴涵着《易》理。主张以象数求《易》理,强调义理、卜筮、象数相结合,集理、占、数为一体。从而在克服程颐义理易学和邵雍象数易学之不足的基础上,又吸取道教以图解《易》的治学方法,把图书象数与义理统一起来,为阐发义理作论证。这在易学发展史上是一创新。
(九)以太极论阐释天理
朱熹把《易传·系辞》的“《易》有太极”说视为“易学纲领,开卷第一义”,将其与他的天理论哲学相结合,以太极论阐释天理,发展了程朱理学的天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朱熹借鉴周敦颐的太极说,而提出自己的太极论。指出所谓“无极而太极”,是说无形而有理,认为太极即理,无极是指太极的无形而言。太极生两仪,即是理派生阴阳,把太极论与其天理论相互沟通,这对宋代易学与宋代理学的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十)倡主宾之辨,提出主客体对立的心物范畴
在哲学认识论上,朱熹以己意增补《大学》传文,即增加第五章《格物致知补传》134字,以作为其格物致知论的纲领,概括了朱熹认识论的要点。明确提出主客体对立的心物范畴,强调“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宾之辨。”(《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四,《答江德功二》)把吾心之知确定为主,把事物之理归结为宾。并吸取佛教临济宗的“宾主颂”,主张内外结合,以己知彼。其所谓宾,相对于主体而言,指客体、对象。朱熹明确提出主客体对立的“主宾之辨”,这是对中国哲学认识论发展的贡献。
(十一)强调“正君心”,批判君主“独断”
在政治理论上,朱熹“正君心是大本”的思想别具特色,把纠正君主心中不符合天理的坏念头作为治天下的大根本,提高到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则的高度,这是对儒家限制君主特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由此出发,朱熹提出君臣共治天下的主张,反对君主一人“独任”天下之事。更从治体的高度,批判君主的“独断”。他批评宋宁宗“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骤进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经筵留身面陈四事劄子》)朱熹大胆批判封建君主的专制“独断”,要求君主与大臣相谋而共治天下,指出君主“独断”与治体不合,“非为治之体”,并留下了隐患和祸害。正因为朱熹批判君主“独断”,而遭到宋宁宗及权臣韩侂胄的打击迫害,可见朱熹的政治思想与封建专制主义不相合,这亦是朱熹思想的独到之处。
(十二)对仁说的发展
仁的学说作为儒家思想的基石,在儒学理论体系里占有重要位置。孔子首先把仁作为儒家最高道德规范,提出以仁为核心的一套学说。孟子在孔子仁说的基础上,提出著名的仁政说,把仁的学说落实到政治治理。并以心性言仁,把仁与义礼智并称,作为性的内涵。宋代理学家把仁纳入其思想体系,而给予充分重视。尤其是朱熹,对仁的学说,讨论最多,阐发最详,思想最深刻,集前人仁说之大成。朱熹对孔孟仁说的发展表现在,首先,朱熹以仁为四德之长,其地位在义礼智之上,把仁与天理联系起来,并以仁为体,以爱为情、为用,以体用论仁、爱,从本体论的高度发展了孔孟的仁爱思想。其次,朱熹以仁为心之德,虽然“心非仁”,但心与仁有密切联系,强调发挥人的主观道德自觉,克己私,以廓然大公来实现仁,这是对孔子“为仁由己”思想的发展。此外,朱熹既提出仁与爱的体用之分、仁与公的相互区别,更重视仁与爱、仁与公的相互联系,强调通过爱和公来体现仁,反对二者脱离,“离爱而言仁”的倾向。这对于把孔孟的仁爱思想落实到道德实践中去,具有重要的意义。经朱熹提出成体系的仁说,仁作为天理的内涵,具有宇宙本体和伦理规范双重意义,使儒家仁的学说上升为宇宙本体论哲学,把中国古代的仁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十三)提出义理史学
朱熹的整个学术思想贯穿着天理论的指导,其史学也不例外。朱熹把天理论哲学引入史学领域,以天理作为评判标准来研究历史,建构起与前代史论不同的义理史学,这在中国史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义理史学的特点是以义理评判历史,陶铸历史,而会归于一理。在方法论上,提出治经史以先识义理为前提,强调掌握了义理才能治史,形成与以往单纯读经史而不及义理的史学不同的特点。并强调明正统,别夷夏,接续孔孟之正传,认为一部历史就是圣人之道即天理流行演变的历史。元丞相脱脱等据此以修《宋史》,首创《道学传》,以理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体现了义理史学的影响。朱熹坚持的正统观念也是其义理史学的重要表现。
(十四)提出文道合一,诗理结合的思想
朱熹既是著名理学家,又是杰出诗人和文学家,在文学理论上亦有创新。这主要表现在他提出文道合一,诗理结合的思想,把文学与理学相互沟通,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朱熹主张“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与汪尚书六》)强调不得脱离文而讲道,把文、道统一起来,避免二者相互脱离的“两失”之弊。朱熹在诗词创作中提出诗理结合的思想,既重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又以内在之理作为诗学精神。重视诗情描写和抒发,“未觉诗情与道妨”,认为诗情与道并行而不相悖,把诗情与理结合起来。并主张深入到诗文内部,去探求其言外之意,即内在的义理,认为明其理,才作得好诗,否则流于文辞华丽,而缺乏思想内涵以打动人。朱熹在文学理论上提出文道合一、诗理结合的思想,体现了朱熹对文学的重视和理学对文学的影响,其理论的特点虽产生一定的流弊,但也不可全然抹煞其思想的价值。
以上只是大致概括了朱熹对传统文化创新的主要方面,而在其他一些方面,如自然科学、理气论、教育、经济思想、礼学等方面,朱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却未能一一论及。这固然是由于朱熹思想博大精深,在各个领域均对中国文化作出发展创新而不便全部论述,同时也是为了突出朱熹对传统文化的主要创新之点。即便是以上这些主要创新之处,也足以体现出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朱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和创新对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完成了理性主义的文化超越,进一步体现了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宋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发生了历史的转折和变革。在经济领域,土地制度国有逐渐转化为土地私有。随着土地占有制度的变革及门阀士族的消亡,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士庶界限被打破。宋朝廷完善发展了科举制度,大量庶族平民经科举加入官僚行列,形成文官统政的局面,这有利于思想文化的发展。面对唐五代社会动乱、伦常扫地带来的严重后果,思想家们要求复兴儒学,革新经学,重整纲常,这成为社会的普遍要求。中央集权制在宋代发展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并一定程度地出现君臣共治天下的“治体”。佛道宗教文化经大多数宋学学者的批判,已走向衰落,不能与前代盛极一时的情形相比,但其精致的思辨哲学又为理学家所吸取,用以提高儒学的哲学思辨水平。针对统治者和民间因感性欲望的过度泛滥而造成人无廉耻,社会生活失序,以及宗教冲击人文,逃父出家,不尽社会责任的局面,理学家提倡理性主义文化,以理性指导感性,以人文回应宗教;在理欲、公私、义利观方面,批评对个人欲望的放纵、追逐私利、以及宗教对个人责任的逃避等社会流弊,形成理性主义的文化氛围,但也因此而出现压抑个性和人欲的弊端。
朱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既以弘扬儒学及儒家圣人之道为己任,又发扬开放和超越精神,全面系统地总结并创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文化的经学、政治、哲学、伦理、宗教等各个领域,广泛涉猎,潜心钻研,总结传统文化包括北宋以来理学发展的成就,使中国文化更加丰富,更具理性色彩,进一步体现了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把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和总结者。
(一)遍注群经,对传统经学的总结
儒家经学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对中国文化及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熹是经学中宋学的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遍注群经,对传统经学作了全面总结,既以阐发义理为治经之目的,这是他超出汉唐经学之处;又重训诂考据,对诸经详加训释,这是他对汉学的吸取,亦是他对宋学流弊的修正。由此朱熹对以往经学作出了总结。
朱熹遍注群经,表现在“四书”方面,便是在二程重视“四书”的基础上,总结唐以来开始出现的“四书”独立于“六经”的趋向,结合自己创建新经学思想体系的需要,以毕生精力注解《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四书”。在阐发义理的同时,亦重对“四书”文字的训诂考据,把阐发义理与文字训诂结合起来,既批评汉魏诸儒只是训诂,而未玩味义理的倾向,亦不赞同宋学学者只讲义理,而轻视训诂考据的治学方法。一方面通过总结二程的“四书”学,以“四书”义理之学取代“六经”训诂之学在经学发展史上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不废弃训诂考据之学,强调“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从而对汉、宋学都加以总结吸取,既以宋学为主,又超越汉、宋学之对立,由此发展了传统经学,并对后世的新汉学产生重要影响。
不仅如此,朱熹还注释了《周易》,撰《周易本义》和《易学启蒙》,总结以往易学之图书象数派和义理派的思想资料和观点,既重本义,重象数,又以义理为指导,把义理、卜筮、象数、图书相结合,从而总结发展了传统易学。
朱熹注解《诗经》,先主《小序》,而作《诗集解》;后悟前说之非,尽去《小序》,以《诗》说《诗》,而作《诗集传》,体现了朱熹诗学对旧说的总结和超越。
朱熹将自己治《尚书》之旨和有关注《尚书》的材料传授给学生蔡沈,令其作《书集传》。所以《书集传》亦可视为朱熹注《尚书》思想的反映。朱熹对《尚书》的注解和阐发,总结了以往的《尚书》辨伪工作,重视对心传说的阐发,在尚书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朱熹训解《礼》书,早年作《祭仪》和《家礼》,后酝酿修三礼书,晚年与弟子黄榦合撰《仪礼经传通解》。损益前代之礼,对以往礼学加以总结,提出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以《周礼》为纲领的思想,主张以礼来治国立教,体现了儒家礼治的精神。
朱熹又根据《春秋》大义,编纂《通鉴纲目》,定其凡例,法《春秋》大旨,明正统顺逆。以义理作为评判《春秋》经传的标准,把义理史学贯穿于春秋学的研究中,这也是对以往春秋学的总结和发展。
此外,朱熹依据《古文孝经》,撰《孝经刊误》,对以往的《孝经》版本和文字加以考释。认为《孝经》非孔子所自作,其经文部分是曾子门人记孔子、曾子问答之言。并删减《孝经》文字,重排其章目次序,一定程度地体现了他疑经惑传,改易经文,以义理释经的经学特点。
以上可见,朱熹学养深厚,遍注群经,对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诗》、《书》、《礼》、《春秋》、《孝经》等诸经加以注解、考释,全面总结了传统经学,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中国经学,成为经学史上宋学的集大成者。
(二)以天理治国,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总结
天理治国论是朱熹政治思想的核心,亦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总结和发展。二程提出以天理治国的思想,朱熹加以总结、完善和发展,把内在于人心的天理,贯彻到外在的政治事务中去,由内圣开出外王。并把天理上升为宇宙的根本法则,认为天理是治国的根本,其权威在君主的权威之上,要求包括帝王在内的统治者顺应天理,按天理的原则治理国家而不得违背。这充分体现了理学家政治思想的特点,亦是对以往政治文化的扬弃和总结。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多元复合型文化,除儒家文化外,其他各家的思想都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影响,如法家、道家、墨家、农家、名家,以及道教和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等,都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墨家的影响在先秦后大为减弱,农家、名家的思想影响有限,佛、道二教作为出世主义的宗教,少讲社会治理。真正对中国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首推儒家,以及法家和道家。儒家在吸取各家政治思想的过程中,前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和发展。
儒、法、道三家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既相互论争,又互相融合,其中儒家的政治思想以重人伦,讲仁义,施德政,道重于君为主;法家的政治思想以任刑罚,重权术,讲法治为主;道家则崇尚自然清静,无为而治,它们各自程度不同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然而,自汉代以来,儒术独尊,儒学在统治者的提倡下,不仅逐渐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而且演变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但儒家政治思想与封建统治者的专制政治有相当的区别,而不可混同。一般说,封建统治者的专制独裁以吸取法家思想为多,而儒学则反对专制独裁,反对统治者滥施暴政以虐民。孟子盛赞汤武革命,认为汤武革桀纣之命,杀暴君,只是诛独夫,而不是“臣弑其君”。荀子进而提出道高于君的思想,强调“从道不从君”,仁义之道重于君主之权位。这些思想得到了朱熹的继承,他提出天理治国论,从“治体”的高度批判了君主的“独断”,主张以道即天理对君权和封建统治者的特权加以一定的限制,认为治理国家,以道为本,道比权位更为重要,这也是对法家思想的扬弃。朱熹天理治国的思想主张“正君心”,把君主置于天理即道的约束之下,认为尽管君主权位至尊,但君主也不得违背天理,为了维护天理的最高权威,要求敢于矫君正君,不向邪恶势力低头。这具有道统高于君统,以道与专制君权相抗争的意义。亦是对传统政治文化尤其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总结。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其主要原因是封建专制主义和君主个人专制独裁阻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而这恰恰是专制统治者背弃了朱熹天理治国论中约束君权的思想所造成的恶果。
(三)“心统性情”,对中国心性哲学的总结
心性论是先秦儒家哲学、佛教哲学、宋明理学以至整个中国哲学的重要内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特点。朱熹吸取、改造先秦儒学心性论、佛教哲学心性论,又受到理学家张载、二程、胡宏思想的一定影响,与同时代学者相互辩学,提出了自己以“心统性情”说为纲领的心性论。这是对以往心性哲学的系统总结,达到了中国哲学心性论思想发展的高峰,并对后世中国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先秦是儒家心性之学的创立时期。孔子对心性问题论述不多,但其“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为仁由己”等思想却启发了孟子。在中国哲学史上,孟子最早给心以高度重视,并把心性联系起来加以论述,从而确立了儒家的心性哲学。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对后世包括对佛教心性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儒家心性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荀子进一步阐发了心的认识论功能,并提出与孟子性善论主张相对的性恶论。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先是受儒家心性之学特别是孟子思想的影响,大讲“尽心知性”及“穷理尽性”。后来佛教发展了儒学心性论,主要是以本体论心性,其哲学理论的思辨性明显高于先秦儒学心性论,但却抛弃了儒家心性论中的伦理道德内涵,因此与先秦儒家心性论有别。这遭到了朱熹等理学家的抨击。
朱熹在总结、吸取先前心性哲学思想资料的过程中,批评佛教心学的心本论思想及其心中无理、性中无德的倾向,同时又吸收了佛教心性论的思辨哲学,提出系统的“心统性情”思想,把儒家伦理与思辨哲学紧密结合,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心性论。朱熹以性为本,把儒家伦理提升为形上宇宙本体,又把心性与天理相联,这既丰富了儒家哲学心性论的内涵,又发展了中国心性哲学,使理性的、伦理的、人文的世俗思辨哲学逐步取代隋唐盛行的宗教哲学,改变了由唐至宋,儒、佛、道三家鼎立的局面,为宋以后儒家哲学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
(四)存理去欲,对传统伦理思想的总结
朱熹的理欲之辨不仅对后世影响甚大,而且亦是对以往伦理思想的总结。由于朱熹等理学家认为,理欲关系的理与义、公相通;理欲关系的欲与利、私相联。故其存理去欲思想与重义轻利、以义制利以及尊公蔑私、大公无私的思想相互沟通,在逻辑上构成一致,共同体现了宋代新儒学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伦理思想的总结。其利弊得失任凭后人评说,但在客观上却成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主导思想。由于朱熹的存理去欲思想集中体现了传统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价值观,故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朱熹的理欲之分原出于《礼记·乐记》篇:“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是说人容易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以至好恶无节,这样会造成人欲横流而天理灭绝的后果。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局面,历代思想家对此作了理论探讨,大多要求用天理节制人欲。
至宋代理欲问题成为伦理学讨论的中心问题。在朱熹以前关于理欲之辨的主要观点有二程的“灭私欲则天理明”,强调天理人欲的区分和对立,以及胡宏的“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既主张理欲相分,又认为理欲同体。朱熹对二程、胡宏的思想认真加以总结。他继承了二程“灭私欲则天理明”的思想,倡天理与私欲的对立,强调存理去欲,以公私、是非来区分理欲,要求克私立公,“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同时又把二程“男女之欲,理之常”的思想加以发展,提出天理安顿在人欲中,理欲互相依存的思想,并区别欲之二义。对于人的客观物质欲求,朱熹认为即使圣人也有此欲,因而不可去掉,并批判了佛教的禁欲主义;对于超过基本的客观物质欲望之上的私欲,朱熹主张去掉,强调“明天理,灭人欲”,此人欲即指私欲。
朱熹从理本论思想出发,又批评了胡宏天理人欲同体的思想,认为“本体实然只一天理,更无人欲”(《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三,《胡子知言疑义》),强调天理人欲之辨中理的主导地位,反对把理欲混为一体。由此,朱熹在对以往理欲之辨的总结中,提出了自己的独具特色的存理去欲思想,这对传统伦理思想影响很大。
(五)批判、吸取佛、道二教,对宗教文化的总结
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和本土生长的道教是中国最主要的两大宗教。宗教文化别具特色,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虽不及儒学大,但在隋唐时期也曾盛行一时,与儒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甚至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
朱熹早年出入佛老,拜禅师道谦和道士虚谷子为师,深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像朱熹这样的理学大师都曾受到过道佛的影响,表明佛道宗教文化自有其“高妙”处。一般说,佛教长于治心,以心性哲学和思辨哲理来论证其教旨教义,发挥宗教消除内心紧张,求得心灵安宁的社会功能;道教长于养身,通过修炼,得道成仙,与大自然合一,宣扬道为宇宙本体、万物之源。但佛道二教均有其短处,即不讲社会治理,其出世主义的宗教信仰与中国宗法社会及其制度形成矛盾,与儒家文化难以适调。
朱熹拜李侗为师后,弃佛老而归儒,以儒为宗,通过李侗而服膺理学,并集其大成。这与对佛道思想的批判吸取分不开。朱熹对佛教的批判主要集中在批判佛教不讲儒家伦理纲常的出世主义的教旨教义及其与出世思想紧密联系的佛教哲学的“空”论、心本论、只内不外的思想等。在批佛的过程中,朱熹又一定程度地吸取借鉴了佛教的理事说、心性论、“宾主颂”、修养论等思想。
朱熹对道教包括道家的批评主要表现在,批评道教及道家厌世避祸,崇尚空寂以保全其身的思想,并批评其神仙思想和长生不死说。朱熹对道教的吸取主要表现在,借鉴道教之图,以阐发自己的易学及太极说;又考释道书,探讨道教修炼之术,以修养身心,并吸取道教的宇宙生成论等。
朱熹对佛道的批判和吸取,不仅对建构新儒学思想体系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是对宗教文化的总结。朱熹批评佛道,表明宗教文化存在着与世俗的中国传统文化不相协调之处,因而需要协调,以适应以儒学为基础的中国文化。于是佛教逐步被改造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道教也由出世主义向世俗化逐渐转化。朱熹吸取佛道,表明佛道思想的优长之处对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朱熹所吸取的佛道思想的优长之处,既是其各自思想的精要,又是与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相互适应的部分。朱熹以儒学为本位即是以儒学作为取舍佛道思想的标准,在取舍佛道思想的过程中,必然对以佛道为代表的宗教文化作了一番全面的总结,凡与儒学价值观不合的,则加以排斥批判;凡有助于提高儒学思辨水平,促进儒学发展的,则加以吸收借鉴。从而在总结宗教文化的基础上,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以上可见,朱熹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开展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他遍注群经,对传统经学加以总结;提出以天理治国,对传统政治文化作出总结;提出“心统性情”论,对中国心性哲学作出总结;强调存理去欲,对传统伦理思想加以总结;既批判又吸取佛道二教,对宗教文化加以总结。朱熹在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总结反思中,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见解和独到的理论,从而创新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
朱熹不仅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在总结的基础上,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加以综合创新。其对传统文化的创新,尤其体现了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朱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是综合性的、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首创“四书”之名,集“四书”学之大成
“四书”学的提出和确立,是程朱对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然二程只是开“四书”学之先河,提出基本的思想线索,其“四书”学的思想理论并不完备。朱熹则在二程提出的思想线索的基础上,在中国思想史上首创“四书”之名,把《大学》、《论语》、《孟子》、《中庸》结集,合为四部最重要的儒家经典,其地位在“六经”之上。并以毕生精力集注“四书”,著《四书章句集注》,以重义理的理学思维模式取代汉学单纯重训诂的注经模式,集宋代“四书”学之大成,完成了中国经学史上的一大变革。朱熹的理学与其经学紧密联系,其理学思想也基本通过《四书集注》得以阐发,由此体现了朱熹“四书”学的重要性。
(二)首创“道统”二字,集道统论之大成
道统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传统文化产生重要影响。道统思想源远流长,历经发展演变,至宋代趋于成熟。但“道统”之名实由朱熹所首创,二字连用也始自朱熹。也就是说,道统的思想内涵古已有之,而“道统”的外在名称,其发明权却在朱熹①。朱熹不仅发明了道统二字,而且创新发展了道统的思想内涵,形式与内容相结合,从而集道统论之大成。
(三)兼采汉宋,把章句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
朱熹经学的一大特征是既以阐发义理作为治经的最高目标,又重对经文的训诂考据,把阐发义理建立在对经典章句文字训诂的基础上,从而兼采汉宋,把章句训诂之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既以宋学义理为主,同时也不废汉学文字考据的功夫。既批评汉学为考据而考据,重训诂而不及义理的治经倾向,亦修正宋学重义理轻考据,其义理缺乏根据的经学流弊。兼取汉宋之长而去其短,成为在宋学内部扬弃和发展宋学的代表人物,开明清之际汉宋兼采经学之先声。
(四)提出经传相分,直求经文之本义
超越传注,直求经文之本义是朱熹经学的又一特色。针对汉学但守注疏,“疏不破注”,以传代经,脱离经文本义而繁琐释经的弊端,和宋学只求传文之义理,援传于经,经传相混,使经文本义晦而不明的流弊,朱熹提出经传相分,直求经文之本义的思想,以作为普遍的经学方法论原则,强调分别经传,不以传注之学和推说之理取代对经文本义的探求。这是朱熹经学的一大创新,把义理的阐发建立在经文本义的基础上。以易学为例,朱熹强调《易经》的本义为卜筮,而《易传》所讲之义理也不得脱离经文的卜筮本义。由此他对程颐未讲《易经》的卜筮本义而专去阐发义理的倾向提出批评。朱熹的经传相分,直求经文之本义的思想贯穿在他经学诸经思想的各个方面,目的在于以经为本,而不以传注为本,反对学者把注意力转向传注之学,以致“看注而忘经”。但在以经为本,区分经传的前提下,朱熹也重视借鉴传文来探明经义,即重视借鉴先儒对经的训诂注疏来理解经文之本义。朱熹的这一思想具有辩证的因素,与批评前儒以传代经,以传注解经,看注而忘经并不矛盾。两者相辅相成,都是以经为本,目的在探求经文之本义。
(五)重经书辨伪,疑伪古文
重视经书辨伪工作,疑伪古文,这是朱熹经学研究的一大贡献。朱熹在对《尚书》学的研究中,在吴棫疑辨的基础上,进一步详加考订,辨西汉伏生与托名孔安国两家所传今古文之差异,黜《孔传》、《孔序》,以区别经文与伪《孔传》,直求经文之本义;又疑《书序》(朱熹称为《小序》),认为《书小序》不是孔子所作,而是周秦时的低手人所作,以恢复《尚书》的本来面目;朱熹对梅本《古文尚书》,即《孔传》本《古文尚书》提出怀疑,认为其书至东晋方出,疑其书是假书。这启发了后世的经书辨伪工作,最终判明梅本古文是伪《古文尚书》,《孔安国尚书传》是伪《孔传》。
(六)阐发“十六字心传”
朱熹据《论语·尧曰》、《中庸》、《荀子·解蔽》和《尚书·大禹谟》,阐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传。这一思想在理学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亦是朱熹的创新。朱熹认为,“十六字心传”作为圣人相传之“密旨”和“心法”,是以义理之心即道心为标准,随时而为“中”,通过心心相传,心灵感悟,把圣人之道传授下来。这为理学家所看重,对后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虽然《尚书·大禹谟》是朱熹所疑之伪古文,但《大禹谟》的作者提出的“十六字传心诀”,其依据却在《论语·尧曰》、《荀子·解蔽》以及《中庸》等儒家著作。朱熹也是根据上述著作来阐发其“十六字心传”思想,并把“十六字传心诀”与《中庸》的“孔门传授心法”结合起来,这体现了朱熹对接续圣人之心的重视。
(七)黜《毛序》,以《诗》说《诗》
朱熹在对《诗经》的研究中,提出与汉唐《诗》学传统迥然相异的废弃《毛诗序》,以《诗》说《诗》,而反对以《序》说《诗》的思想。对传统《毛序》的美刺说、“止乎礼义”说提出批评。认为《诗序》出自汉儒卫宏等,而与《诗》文本义不符,如果按《序》的意思解《诗》,只能是牵强附会,而有违诗人作《诗》之本意。所以朱熹作《诗集传》,便把《序》从各诗中除去,而弃置于《诗》后。此外,朱熹于《诗》三百篇中,指出有二十多篇淫奔之诗,为淫佚之人所自叙之辞,而非皆为圣贤教人之作。故对孔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的诗说提出异议。朱熹对《毛序》的批评和废弃,以及对“思无邪”说的异议,使得千年来的诗学传统遭到了有力的挑战,体现了朱熹的创新精神。
(八)图书象数与义理合一
有宋一代易学,大抵分为象数和义理两派,其象数派又衍出图书之学。宋易发展到南宋,朱熹针对程颐过分讲义理而轻视象数,以及象数派穿凿附会入于末流,而忽视义理的两种偏向,提出以义理思想为指导,重本义,重象数,以图书作为象数之源,图书中蕴涵着《易》理。主张以象数求《易》理,强调义理、卜筮、象数相结合,集理、占、数为一体。从而在克服程颐义理易学和邵雍象数易学之不足的基础上,又吸取道教以图解《易》的治学方法,把图书象数与义理统一起来,为阐发义理作论证。这在易学发展史上是一创新。
(九)以太极论阐释天理
朱熹把《易传·系辞》的“《易》有太极”说视为“易学纲领,开卷第一义”,将其与他的天理论哲学相结合,以太极论阐释天理,发展了程朱理学的天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朱熹借鉴周敦颐的太极说,而提出自己的太极论。指出所谓“无极而太极”,是说无形而有理,认为太极即理,无极是指太极的无形而言。太极生两仪,即是理派生阴阳,把太极论与其天理论相互沟通,这对宋代易学与宋代理学的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十)倡主宾之辨,提出主客体对立的心物范畴
在哲学认识论上,朱熹以己意增补《大学》传文,即增加第五章《格物致知补传》134字,以作为其格物致知论的纲领,概括了朱熹认识论的要点。明确提出主客体对立的心物范畴,强调“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宾之辨。”(《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四,《答江德功二》)把吾心之知确定为主,把事物之理归结为宾。并吸取佛教临济宗的“宾主颂”,主张内外结合,以己知彼。其所谓宾,相对于主体而言,指客体、对象。朱熹明确提出主客体对立的“主宾之辨”,这是对中国哲学认识论发展的贡献。
(十一)强调“正君心”,批判君主“独断”
在政治理论上,朱熹“正君心是大本”的思想别具特色,把纠正君主心中不符合天理的坏念头作为治天下的大根本,提高到治理国家的根本法则的高度,这是对儒家限制君主特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由此出发,朱熹提出君臣共治天下的主张,反对君主一人“独任”天下之事。更从治体的高度,批判君主的“独断”。他批评宋宁宗“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甚者方骤进而忽退之,皆出于陛下之独断,而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非为治之体,以启将来之弊。”(《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经筵留身面陈四事劄子》)朱熹大胆批判封建君主的专制“独断”,要求君主与大臣相谋而共治天下,指出君主“独断”与治体不合,“非为治之体”,并留下了隐患和祸害。正因为朱熹批判君主“独断”,而遭到宋宁宗及权臣韩侂胄的打击迫害,可见朱熹的政治思想与封建专制主义不相合,这亦是朱熹思想的独到之处。
(十二)对仁说的发展
仁的学说作为儒家思想的基石,在儒学理论体系里占有重要位置。孔子首先把仁作为儒家最高道德规范,提出以仁为核心的一套学说。孟子在孔子仁说的基础上,提出著名的仁政说,把仁的学说落实到政治治理。并以心性言仁,把仁与义礼智并称,作为性的内涵。宋代理学家把仁纳入其思想体系,而给予充分重视。尤其是朱熹,对仁的学说,讨论最多,阐发最详,思想最深刻,集前人仁说之大成。朱熹对孔孟仁说的发展表现在,首先,朱熹以仁为四德之长,其地位在义礼智之上,把仁与天理联系起来,并以仁为体,以爱为情、为用,以体用论仁、爱,从本体论的高度发展了孔孟的仁爱思想。其次,朱熹以仁为心之德,虽然“心非仁”,但心与仁有密切联系,强调发挥人的主观道德自觉,克己私,以廓然大公来实现仁,这是对孔子“为仁由己”思想的发展。此外,朱熹既提出仁与爱的体用之分、仁与公的相互区别,更重视仁与爱、仁与公的相互联系,强调通过爱和公来体现仁,反对二者脱离,“离爱而言仁”的倾向。这对于把孔孟的仁爱思想落实到道德实践中去,具有重要的意义。经朱熹提出成体系的仁说,仁作为天理的内涵,具有宇宙本体和伦理规范双重意义,使儒家仁的学说上升为宇宙本体论哲学,把中国古代的仁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十三)提出义理史学
朱熹的整个学术思想贯穿着天理论的指导,其史学也不例外。朱熹把天理论哲学引入史学领域,以天理作为评判标准来研究历史,建构起与前代史论不同的义理史学,这在中国史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朱熹义理史学的特点是以义理评判历史,陶铸历史,而会归于一理。在方法论上,提出治经史以先识义理为前提,强调掌握了义理才能治史,形成与以往单纯读经史而不及义理的史学不同的特点。并强调明正统,别夷夏,接续孔孟之正传,认为一部历史就是圣人之道即天理流行演变的历史。元丞相脱脱等据此以修《宋史》,首创《道学传》,以理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体现了义理史学的影响。朱熹坚持的正统观念也是其义理史学的重要表现。
(十四)提出文道合一,诗理结合的思想
朱熹既是著名理学家,又是杰出诗人和文学家,在文学理论上亦有创新。这主要表现在他提出文道合一,诗理结合的思想,把文学与理学相互沟通,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朱熹主张“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与汪尚书六》)强调不得脱离文而讲道,把文、道统一起来,避免二者相互脱离的“两失”之弊。朱熹在诗词创作中提出诗理结合的思想,既重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又以内在之理作为诗学精神。重视诗情描写和抒发,“未觉诗情与道妨”,认为诗情与道并行而不相悖,把诗情与理结合起来。并主张深入到诗文内部,去探求其言外之意,即内在的义理,认为明其理,才作得好诗,否则流于文辞华丽,而缺乏思想内涵以打动人。朱熹在文学理论上提出文道合一、诗理结合的思想,体现了朱熹对文学的重视和理学对文学的影响,其理论的特点虽产生一定的流弊,但也不可全然抹煞其思想的价值。
以上只是大致概括了朱熹对传统文化创新的主要方面,而在其他一些方面,如自然科学、理气论、教育、经济思想、礼学等方面,朱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却未能一一论及。这固然是由于朱熹思想博大精深,在各个领域均对中国文化作出发展创新而不便全部论述,同时也是为了突出朱熹对传统文化的主要创新之点。即便是以上这些主要创新之处,也足以体现出朱熹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朱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和创新对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完成了理性主义的文化超越,进一步体现了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
相关人物
朱熹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