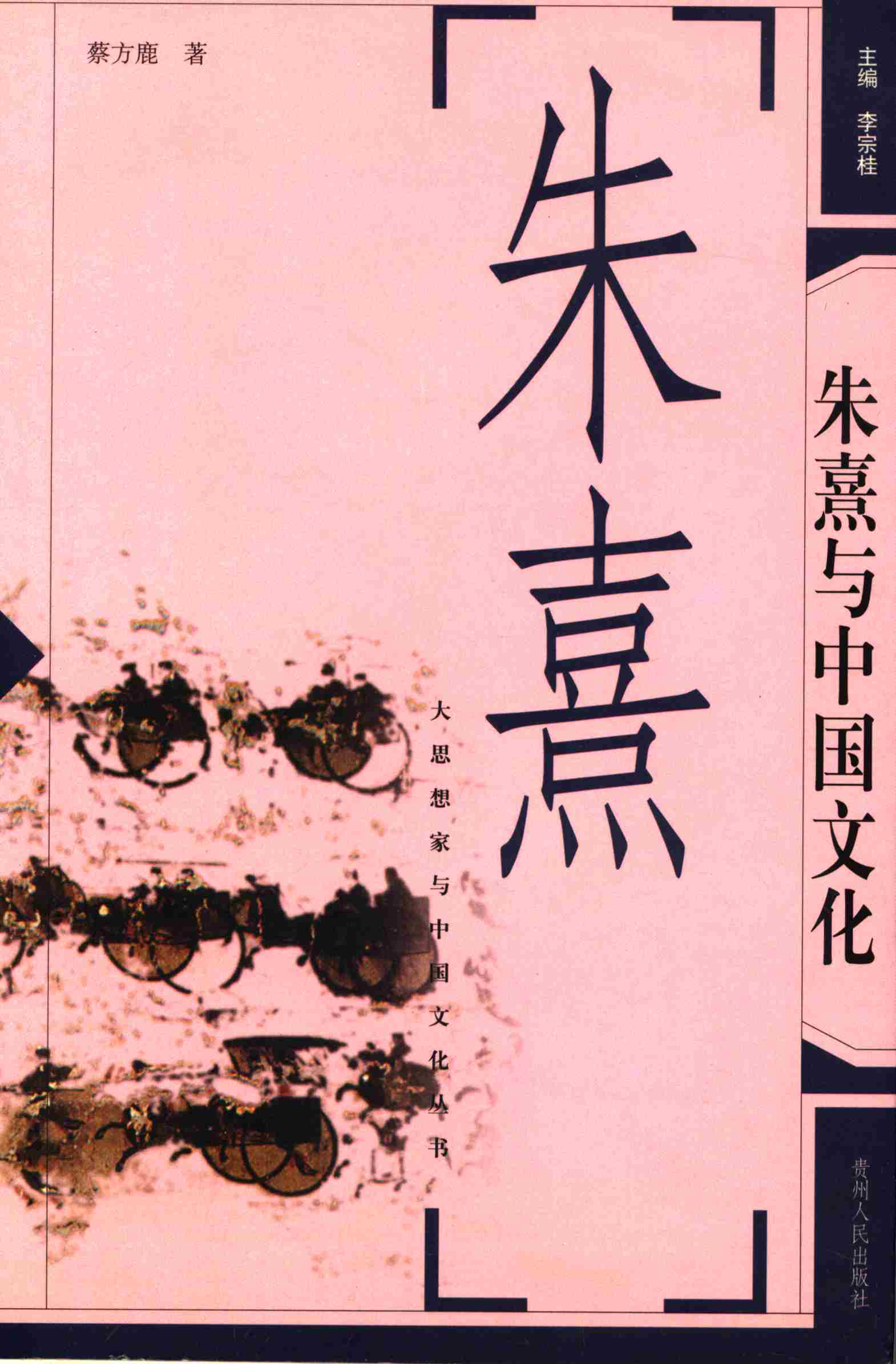内容
朱熹诗学的特点是在唯求《诗》文之本义的基础上以义理解《诗》。这不仅体现了朱熹经学的特点及其义理诗学的时代特征,而且与《毛传》、《诗序》的汉学系统以及程颐重义理轻本义的诗说形成对比。
(一)以义理解《诗》,不着意训解
由于《诗经》属文学作品,与其他如说理的、叙事的、占卜的经典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着不同,所以朱熹依据《诗》自身的特性,着重以赋比兴的文学表现手法去解《诗》,而不着意于对《诗》文作一字一句的训解,朱熹批评旧儒囿于注疏训诂,而不及义理的倾向,主张涵泳《诗》文本义。他说:“大凡读书,先晓得文义了,只是常常熟读。如看《诗》,不须得着意去里面训解,但只平平地涵泳自好。”(《朱子语类》第2087页,卷八十)所谓不须着意训解,是指从诗歌自身的特点出发,不必逐字去训解其意,而“只是看大意”,只要熟读涵泳,道理便会自见。“此是读《诗》之要法,看来书只是要读,读得熟时,道理自见。”(同上第2086页)需要指出,朱熹不着意训解的思想,主要是就解《诗》而言,并非是对训诂注疏弃之不用。
朱熹在探明《诗》文之本义的前提下以义理解《诗》,除表现在重视《诗》之“二南”外,还表现在以义理批判淫奔之诗和以天理论阐发《诗》之雅、颂上。
关于以义理批判淫奔之诗。朱熹以理学之义理为价值标准,对男女之情持严谨态度,既适当地肯定合乎礼义的男女之情,更对不合礼义的男女自然之情爱以及贵族的淫乱行为提出批判。他于变风的郑卫之诗中,找出二十多篇淫奔之诗,批判其不合于义理的男女之情。如注《风雨》篇云:“淫奔之女,言当此之时,见其所期之人而心悦也。”(《诗集传》卷三)《静女》篇为“淫奔期会之诗”(同上卷二)。《遵大路》篇是讲“淫妇为人所弃”(同上卷三)。而在《桑中》篇里,朱熹批判了“卫俗淫乱,世族在位,相窃妻妾”(同上卷二)的诗文描写。这些方面是朱熹以义理解《诗》的表现。
关于以天理论解《诗》。朱熹在对《大雅·文王》的注解中指出:“命,天理也。……言欲念尔祖,在于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无不合于天理,则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同上卷六)把天命解为天理,强调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为此要求统治者修德自省,使其行为不违背天理,这样才能保其天命之不易,而国长存。又在解释《周颂·维天之命》时指出:“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无穷也。纯,不杂也。此亦祭文王之诗,言天道无穷,而文王之德,纯一不杂,与天无间。……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纯于天道亦不已。”(同上卷八)在朱熹的哲学思想体系里,天道亦即天理,二者互用。朱熹把天命解为天道,也就是解为天理。他认为,文王之德治仁政与天道无二,亦是天理的体现,从而把圣人与天合为一体,以赞美文王之德。朱熹把天理论贯彻到解《诗》中去,这体现了其诗学的时代特征。
(二)重视“二南”
重视《诗》之国风的《周南》、《召南》,是朱熹以义理解《诗》的集中体现。朱熹以“二南”为其整个诗学的根本,他在述其诗学的大旨时说:“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诗集传序》)朱熹以“二南”为本,他认为,《诗》三百篇中,“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同上)在以“二南”二十五篇诗为诗学之本的基础上,朱熹建构起其义理诗学的思想体系。
朱熹之所以重视“二南”,将其作为诗学的根本,是因为在他看来,“二南”虽是周公采之于民间风俗之诗,但却体现了文王之世的风化,其理义贯穿在诗篇中,足以为后世所效法。他说:
周公相之(成王),制作礼乐,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被之管弦,以为房中之乐,而又推之以及于乡党邦国,所以著明先王风俗之盛,而使天下后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诗集传》卷一,《周南》)
儒家仁礼思想的产生的提出,受周公制礼作乐的影响很大,周礼是周公在文王之治的基础上,损益夏殷两代之礼而成。对此,朱熹甚为推崇,他认为惟有在“二南”之中最能反映文王之治美好的风俗,而风俗之盛则是理义的体现。他从二程“天下之治,正家为先”的义理思想出发,认为“二南,正家之道也”(同上,《召南》)。“二南”之诗中,包含着正家的道理,只有家正,国才能正,天下也才能得到治理;通过家正、男女正,就可看到文王之世的德政。他说:“文王之化,自家而国,男女以正,婚姻以时,故诗人因所见以起兴,而叹其女子之贤,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同上,《周南·桃夭》)这与宋代理学重视伦理道德包括家庭男女道德的培养,由修身到齐家,由家治到天下国家治的思想相一致。
朱熹以义理解说“二南”,主要是从“二南”之诗的实际描写出发,加以义理化的归纳和解说,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强调得其性情之正,以为其诗学之本。虽然包括“二南”在内的整个《诗经》充满了自然的情爱描写,朱熹也客观地承认《诗》“发乎情”,但朱熹对一部“发乎情”的《诗经》,从“二南”入手,建立起以义理解《诗》的体系,来作为解《诗》的典范和指导思想。凡符合义理的,则加以肯定和赞美,以为后世之法;凡不合义理的,则加以贬斥,直视为淫奔之诗,以为后世之戒。在“二南”之中虽有关于性情的自然描写,但由于“二南”被文王之化,其后妃、夫人、女子等虽发乎情,却能够守之以礼义,故能得性情之正,而与放纵情感不同。朱熹引《论语·八佾》孔子之言“《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加以解释:“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关睢》之诗,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盖其忧虽深而不害于和,其乐虽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称之如此。欲学者玩其辞,审其音,而有以识其性情之正也。”(《四书章句集注》第66页,《论语集注》卷二)以孔子的诗教为指导思想,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虽追求享乐,但不得过而失其正;失其正则为淫,也就是朱熹所指斥的淫奔之诗。他还要求“学者姑即其辞,而玩其理,以养心焉,则亦可以得学《诗》之本矣”(《诗集传》卷一,《周南·关睢》)。强调以理义解《诗》,颐养性情,以之为诗学之本。故朱熹把“二南”视为一个整体,在被文王之化的形式下,理贯于其中,而深入人心,泽及于物。他说:“文王之化,始于《关睢》,而至于《麟趾》,则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于《鹊巢》,而及于《驺虞》,则其泽之及物者广矣。盖意诚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同上,《召南·驺虞》)“二南”作为一个整体系统,二十五篇诗均体现了文王之风化。其中《周南》始于《关睢》,终于《麟趾》,十一篇诗中前五首皆言后妃之德,而《关睢》是从全体上言其纲要,其他诗则是指具体一事而言,虽然其诗文是讲后妃,但实际上是文王身修家齐的表现;后六首诗既有体现家齐而国治的,又有反映天下渐平的,总之是以《大学》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来解释《周南》。而《召南》始于《鹊巢》,终于《驺虞》,十四篇诗既讲南国诸侯被文王之化,而能正心修身以齐其家,又讲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能守德以正其家,体现了文王之化的影响。
朱熹把“二南”视为一个整体,在被文王之化的形式下,以义理解说之,表明其对“二南”的重视。并以对“二南”的解说为指导,作为其诗学之本,把“发乎情”纳入“乐而不淫”的诗教的规范之下,以得性情之正,反对过而失其正为淫,从而建立起义理诗学的思想体系,这对中国诗经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讽诵中见义理”
朱熹以义理解《诗》,重视“二南”,这体现了他义理诗学的时代特色。然而朱熹以义理解《诗》,并不排斥《诗》的“感物道情、吟咏情性”之本义,而是在本义的基础上,于讽诵之中见义理。也就是说,《诗》作为一部诗歌体裁的文学性经典,一般来讲,义理并不是如“四书”那样,直接用文字说出来,而是通过赋、比、兴的文学表现手法,委曲折旋地表达诗人之寓意,所以须在反复讽诵之中,把握诗中蕴含的义理。他说:
读《诗》者须当讽味,看他诗人之意是在甚处。(《朱子语类》第2102页,卷八十一)
大凡读书,多在讽诵中见义理。况《诗》又全在讽诵之功。(同上第2612页,卷一百四)
《诗》,如今恁地注解了,自是分晓,易理会。但须是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同上第2086页,卷八十)
朱熹强调反复诵读体会,玩味义理,甚至主张“涵泳读取百来遍,方见得那好处”(《朱子语类》第2087页)。朱熹历来主张多读书以见义理,这是他与忽视知识,不立文字,但求本心的陆氏心学的区别之一,尤其对《诗经》这种文学性经典,朱熹更是主张沉潜讽诵,道理得之于后,而不得先自立说,有违诗文之本义。他说:“当时解《诗》时,且读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却看诸人说与我意如何,大纲都得之,又读三四十遍,则道理流通自得矣。”(同上第2091页)朱熹读《诗》大致分两步骤,一是熟读,了解文义和大纲,并看他人之注解;二是在了解文义的基础上再反复涵泳,“百遍自是强五十遍时,二百遍自是强一百遍时”(同上第2087页),如此道理便自然见得。应该说,朱熹提倡的这种“在讽诵中见义理”的读书法,正是文学与理学结合的方法。朱熹认为,义理须在反复讽诵中见得,故他对诵读《诗》文十分重视。但在讽咏诵读中存在着由于古今音读不同而韵不和谐的问题,为了便于讽咏,朱熹也注意吸取两宋之际吴棫的叶韵说以读《诗》。吴棫的叶韵说认为古人用韵较宽,有古韵通转之说。朱熹加以吸取,并作增减,以便押韵上口,自然和谐。他说:“叶韵乃吴才老(棫)所作,其又续添减之。盖古人作诗皆押韵,与今人歌曲一般。今人信口读之,全失古人咏歌之意。”(同上第2081页)可见其用叶韵的目的在于得古人咏歌之意,避免以宋代的读音去读古人之《诗》文,而造成韵不和谐,失去古人之意的情形。朱熹虽以叶韵读《诗》,但他认为音韵之设,为便于讽咏,而不必特意去追求字韵上的严整。他说:“古人情意温厚宽和,道得言语自恁地好。当时叶韵,只是要便于讽咏而已。到得后来,一向于字韵上严切,却无意思。”(同上)正因为用叶韵是为了便于讽诵,而讽诵熟则义理自见,所以朱熹主张在诵读中以主要精力放在理会义理上,而把理会叶韵放在次要位置。他说:“只要音韵相叶,好吟哦讽诵,易见道理,亦无甚要紧。今且要将七分工夫理会义理,三二分工夫理会这般去处。若只管留心此处,而于《诗》之义却见不得,亦何益也!”(《朱子语类》第2079页,卷八十)指出如果只留心叶韵,却不能从中见《诗》义,那么叶韵是没有用处的。表达了他叶韵服务于《诗》义的思想。由此可见,朱熹的叶韵说是为了便于讽诵,通过讽诵掌握《诗》义,阐发义理,最终把叶韵说纳入其“讽诵中见义理”的解《诗》说中。
质言之,朱熹在宋学学者批《毛传》、《郑笺》、《诗序》之失的基础上,以《诗》说《诗》,反对以《序》说《诗》,提出了自己以把涵泳诗文求其本义与阐发义理相结合为特色的诗学思想。他以义理思想为指导,把文学与理学相结合,既认为《诗》为“感物道情”而作,又指出其中有淫奔之诗的内容,批评《诗序》的美刺说、“止乎礼义”说,以及孔子的“思无邪”说等,注重雅郑邪正之辨;以文学家的眼光,重视《诗》对于情的抒发,吟咏情性,理会《诗》的赋、比、兴表现手法;又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以义理解《诗》,重视“二南”,不着意训解,理会诗之大意,主张于讽诵中见义理,以叶韵读《诗》,为讽诵《诗》文,发明义理服务。这些方面都是朱熹本义与义理相结合诗学特色的表现。其本义与义理、文学与理学相结合的诗学思想的提出,不仅是对前代诗学的创新和发展,从而集宋代义理诗学之大成;而且在追求本义与阐发义理上,以及把义理的阐发建立在经文本义的基础上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其整个经学思想的特色,因而成为朱熹整个经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诗学史和宋代经学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以义理解《诗》,不着意训解
由于《诗经》属文学作品,与其他如说理的、叙事的、占卜的经典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着不同,所以朱熹依据《诗》自身的特性,着重以赋比兴的文学表现手法去解《诗》,而不着意于对《诗》文作一字一句的训解,朱熹批评旧儒囿于注疏训诂,而不及义理的倾向,主张涵泳《诗》文本义。他说:“大凡读书,先晓得文义了,只是常常熟读。如看《诗》,不须得着意去里面训解,但只平平地涵泳自好。”(《朱子语类》第2087页,卷八十)所谓不须着意训解,是指从诗歌自身的特点出发,不必逐字去训解其意,而“只是看大意”,只要熟读涵泳,道理便会自见。“此是读《诗》之要法,看来书只是要读,读得熟时,道理自见。”(同上第2086页)需要指出,朱熹不着意训解的思想,主要是就解《诗》而言,并非是对训诂注疏弃之不用。
朱熹在探明《诗》文之本义的前提下以义理解《诗》,除表现在重视《诗》之“二南”外,还表现在以义理批判淫奔之诗和以天理论阐发《诗》之雅、颂上。
关于以义理批判淫奔之诗。朱熹以理学之义理为价值标准,对男女之情持严谨态度,既适当地肯定合乎礼义的男女之情,更对不合礼义的男女自然之情爱以及贵族的淫乱行为提出批判。他于变风的郑卫之诗中,找出二十多篇淫奔之诗,批判其不合于义理的男女之情。如注《风雨》篇云:“淫奔之女,言当此之时,见其所期之人而心悦也。”(《诗集传》卷三)《静女》篇为“淫奔期会之诗”(同上卷二)。《遵大路》篇是讲“淫妇为人所弃”(同上卷三)。而在《桑中》篇里,朱熹批判了“卫俗淫乱,世族在位,相窃妻妾”(同上卷二)的诗文描写。这些方面是朱熹以义理解《诗》的表现。
关于以天理论解《诗》。朱熹在对《大雅·文王》的注解中指出:“命,天理也。……言欲念尔祖,在于自修其德,而又常自省察,使其所行,无不合于天理,则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同上卷六)把天命解为天理,强调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为此要求统治者修德自省,使其行为不违背天理,这样才能保其天命之不易,而国长存。又在解释《周颂·维天之命》时指出:“天命,即天道也。不已,言无穷也。纯,不杂也。此亦祭文王之诗,言天道无穷,而文王之德,纯一不杂,与天无间。……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纯于天道亦不已。”(同上卷八)在朱熹的哲学思想体系里,天道亦即天理,二者互用。朱熹把天命解为天道,也就是解为天理。他认为,文王之德治仁政与天道无二,亦是天理的体现,从而把圣人与天合为一体,以赞美文王之德。朱熹把天理论贯彻到解《诗》中去,这体现了其诗学的时代特征。
(二)重视“二南”
重视《诗》之国风的《周南》、《召南》,是朱熹以义理解《诗》的集中体现。朱熹以“二南”为其整个诗学的根本,他在述其诗学的大旨时说:“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止。此学《诗》之大旨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诗集传序》)朱熹以“二南”为本,他认为,《诗》三百篇中,“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同上)在以“二南”二十五篇诗为诗学之本的基础上,朱熹建构起其义理诗学的思想体系。
朱熹之所以重视“二南”,将其作为诗学的根本,是因为在他看来,“二南”虽是周公采之于民间风俗之诗,但却体现了文王之世的风化,其理义贯穿在诗篇中,足以为后世所效法。他说:
周公相之(成王),制作礼乐,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被之管弦,以为房中之乐,而又推之以及于乡党邦国,所以著明先王风俗之盛,而使天下后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诗集传》卷一,《周南》)
儒家仁礼思想的产生的提出,受周公制礼作乐的影响很大,周礼是周公在文王之治的基础上,损益夏殷两代之礼而成。对此,朱熹甚为推崇,他认为惟有在“二南”之中最能反映文王之治美好的风俗,而风俗之盛则是理义的体现。他从二程“天下之治,正家为先”的义理思想出发,认为“二南,正家之道也”(同上,《召南》)。“二南”之诗中,包含着正家的道理,只有家正,国才能正,天下也才能得到治理;通过家正、男女正,就可看到文王之世的德政。他说:“文王之化,自家而国,男女以正,婚姻以时,故诗人因所见以起兴,而叹其女子之贤,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同上,《周南·桃夭》)这与宋代理学重视伦理道德包括家庭男女道德的培养,由修身到齐家,由家治到天下国家治的思想相一致。
朱熹以义理解说“二南”,主要是从“二南”之诗的实际描写出发,加以义理化的归纳和解说,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强调得其性情之正,以为其诗学之本。虽然包括“二南”在内的整个《诗经》充满了自然的情爱描写,朱熹也客观地承认《诗》“发乎情”,但朱熹对一部“发乎情”的《诗经》,从“二南”入手,建立起以义理解《诗》的体系,来作为解《诗》的典范和指导思想。凡符合义理的,则加以肯定和赞美,以为后世之法;凡不合义理的,则加以贬斥,直视为淫奔之诗,以为后世之戒。在“二南”之中虽有关于性情的自然描写,但由于“二南”被文王之化,其后妃、夫人、女子等虽发乎情,却能够守之以礼义,故能得性情之正,而与放纵情感不同。朱熹引《论语·八佾》孔子之言“《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加以解释:“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关睢》之诗,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盖其忧虽深而不害于和,其乐虽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称之如此。欲学者玩其辞,审其音,而有以识其性情之正也。”(《四书章句集注》第66页,《论语集注》卷二)以孔子的诗教为指导思想,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虽追求享乐,但不得过而失其正;失其正则为淫,也就是朱熹所指斥的淫奔之诗。他还要求“学者姑即其辞,而玩其理,以养心焉,则亦可以得学《诗》之本矣”(《诗集传》卷一,《周南·关睢》)。强调以理义解《诗》,颐养性情,以之为诗学之本。故朱熹把“二南”视为一个整体,在被文王之化的形式下,理贯于其中,而深入人心,泽及于物。他说:“文王之化,始于《关睢》,而至于《麟趾》,则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于《鹊巢》,而及于《驺虞》,则其泽之及物者广矣。盖意诚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同上,《召南·驺虞》)“二南”作为一个整体系统,二十五篇诗均体现了文王之风化。其中《周南》始于《关睢》,终于《麟趾》,十一篇诗中前五首皆言后妃之德,而《关睢》是从全体上言其纲要,其他诗则是指具体一事而言,虽然其诗文是讲后妃,但实际上是文王身修家齐的表现;后六首诗既有体现家齐而国治的,又有反映天下渐平的,总之是以《大学》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来解释《周南》。而《召南》始于《鹊巢》,终于《驺虞》,十四篇诗既讲南国诸侯被文王之化,而能正心修身以齐其家,又讲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能守德以正其家,体现了文王之化的影响。
朱熹把“二南”视为一个整体,在被文王之化的形式下,以义理解说之,表明其对“二南”的重视。并以对“二南”的解说为指导,作为其诗学之本,把“发乎情”纳入“乐而不淫”的诗教的规范之下,以得性情之正,反对过而失其正为淫,从而建立起义理诗学的思想体系,这对中国诗经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讽诵中见义理”
朱熹以义理解《诗》,重视“二南”,这体现了他义理诗学的时代特色。然而朱熹以义理解《诗》,并不排斥《诗》的“感物道情、吟咏情性”之本义,而是在本义的基础上,于讽诵之中见义理。也就是说,《诗》作为一部诗歌体裁的文学性经典,一般来讲,义理并不是如“四书”那样,直接用文字说出来,而是通过赋、比、兴的文学表现手法,委曲折旋地表达诗人之寓意,所以须在反复讽诵之中,把握诗中蕴含的义理。他说:
读《诗》者须当讽味,看他诗人之意是在甚处。(《朱子语类》第2102页,卷八十一)
大凡读书,多在讽诵中见义理。况《诗》又全在讽诵之功。(同上第2612页,卷一百四)
《诗》,如今恁地注解了,自是分晓,易理会。但须是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同上第2086页,卷八十)
朱熹强调反复诵读体会,玩味义理,甚至主张“涵泳读取百来遍,方见得那好处”(《朱子语类》第2087页)。朱熹历来主张多读书以见义理,这是他与忽视知识,不立文字,但求本心的陆氏心学的区别之一,尤其对《诗经》这种文学性经典,朱熹更是主张沉潜讽诵,道理得之于后,而不得先自立说,有违诗文之本义。他说:“当时解《诗》时,且读本文四五十遍,已得六七分。却看诸人说与我意如何,大纲都得之,又读三四十遍,则道理流通自得矣。”(同上第2091页)朱熹读《诗》大致分两步骤,一是熟读,了解文义和大纲,并看他人之注解;二是在了解文义的基础上再反复涵泳,“百遍自是强五十遍时,二百遍自是强一百遍时”(同上第2087页),如此道理便自然见得。应该说,朱熹提倡的这种“在讽诵中见义理”的读书法,正是文学与理学结合的方法。朱熹认为,义理须在反复讽诵中见得,故他对诵读《诗》文十分重视。但在讽咏诵读中存在着由于古今音读不同而韵不和谐的问题,为了便于讽咏,朱熹也注意吸取两宋之际吴棫的叶韵说以读《诗》。吴棫的叶韵说认为古人用韵较宽,有古韵通转之说。朱熹加以吸取,并作增减,以便押韵上口,自然和谐。他说:“叶韵乃吴才老(棫)所作,其又续添减之。盖古人作诗皆押韵,与今人歌曲一般。今人信口读之,全失古人咏歌之意。”(同上第2081页)可见其用叶韵的目的在于得古人咏歌之意,避免以宋代的读音去读古人之《诗》文,而造成韵不和谐,失去古人之意的情形。朱熹虽以叶韵读《诗》,但他认为音韵之设,为便于讽咏,而不必特意去追求字韵上的严整。他说:“古人情意温厚宽和,道得言语自恁地好。当时叶韵,只是要便于讽咏而已。到得后来,一向于字韵上严切,却无意思。”(同上)正因为用叶韵是为了便于讽诵,而讽诵熟则义理自见,所以朱熹主张在诵读中以主要精力放在理会义理上,而把理会叶韵放在次要位置。他说:“只要音韵相叶,好吟哦讽诵,易见道理,亦无甚要紧。今且要将七分工夫理会义理,三二分工夫理会这般去处。若只管留心此处,而于《诗》之义却见不得,亦何益也!”(《朱子语类》第2079页,卷八十)指出如果只留心叶韵,却不能从中见《诗》义,那么叶韵是没有用处的。表达了他叶韵服务于《诗》义的思想。由此可见,朱熹的叶韵说是为了便于讽诵,通过讽诵掌握《诗》义,阐发义理,最终把叶韵说纳入其“讽诵中见义理”的解《诗》说中。
质言之,朱熹在宋学学者批《毛传》、《郑笺》、《诗序》之失的基础上,以《诗》说《诗》,反对以《序》说《诗》,提出了自己以把涵泳诗文求其本义与阐发义理相结合为特色的诗学思想。他以义理思想为指导,把文学与理学相结合,既认为《诗》为“感物道情”而作,又指出其中有淫奔之诗的内容,批评《诗序》的美刺说、“止乎礼义”说,以及孔子的“思无邪”说等,注重雅郑邪正之辨;以文学家的眼光,重视《诗》对于情的抒发,吟咏情性,理会《诗》的赋、比、兴表现手法;又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以义理解《诗》,重视“二南”,不着意训解,理会诗之大意,主张于讽诵中见义理,以叶韵读《诗》,为讽诵《诗》文,发明义理服务。这些方面都是朱熹本义与义理相结合诗学特色的表现。其本义与义理、文学与理学相结合的诗学思想的提出,不仅是对前代诗学的创新和发展,从而集宋代义理诗学之大成;而且在追求本义与阐发义理上,以及把义理的阐发建立在经文本义的基础上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其整个经学思想的特色,因而成为朱熹整个经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诗学史和宋代经学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相关人物
朱熹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