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经学思想
| 内容出处: | 《朱熹:孔子之后第一儒》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3761 |
| 颗粒名称: | 第十一章 经学思想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5 |
| 页码: | 122-136 |
| 摘要: | 本文讲述了经学是研究儒家经典的专门学问。西汉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著作被尊称为经,出现“六经”之说。所谓“六经”,指《易》《诗》《书》《礼》《乐》《春秋》六部著作。但是《乐》有声无书,所以实际上只有“五经”。唐代时,将《礼经》中的《仪礼》《礼记》《周礼》和解释《春秋》的《公羊》《穀梁》《左传》分别称为经,出现“九经”之说。到宋代,增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四部书,共为“十三经”。北宋前期,学术思想大体沿袭前代,没有特别的建树;北宋中后期,疑古辨伪思潮兴起。学者们不仅怀疑汉代以来的解经、说经之作,而且也逐渐怀疑到了经文本身。朱熹是这一方面的重要代表人物。 |
| 关键词: | 儒家 经学思想 朱熹 |
内容
经学是研究儒家经典的专门学问。西汉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著作被尊称为经,出现“六经”之说。所谓“六经”,指《易》《诗》《书》《礼》《乐》《春秋》六部著作。但是《乐》有声无书,所以实际上只有“五经”。唐代时,将《礼经》中的《仪礼》《礼记》《周礼》和解释《春秋》的《公羊》《穀梁》《左传》分别称为经,出现“九经”之说。到宋代,增加《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四部书,共为“十三经”。
北宋前期,学术思想大体沿袭前代,没有特别的建树;北宋中后期,疑古辨伪思潮兴起。学者们不仅怀疑汉代以来的解经、说经之作,而且也逐渐怀疑到了经文本身。朱熹是这一方面的重要代表人物。
一、《易经》
《易经》是先秦时代的一部神秘的典籍,由符号和文字两部分组成,居于儒家所定经籍中的首位,长期受到尊崇。但是关于它的性质和面貌,却有种种说法。
朱熹对《易经》做过多年研究,著有《周易本义》,是道学家注《易》的代表作。此外,他还著有《易学启蒙》一书,另有大量关于《易》的言论,散见于其语录和文集中。因此,在易学研究史上,朱熹具有重要地位。明初,朝廷曾将《周易本义》和程颐的《周易程氏传》颁行天下,作为知识分子科举考试的标准读物。
朱熹说过许多推崇《易经》的话,如“洁净精微,《易》之教也”“《易》之为书,广大悉备,人皆可得而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大小精粗,无所不备”等等。(《朱子语类》卷六八、七四)但是,朱熹却直指《易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卜筮书。他说:
“熹尝以为《易经》本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训诫,故其言虽约,而所包甚广。”
“古时人蠢蠢然,事事都不晓,做得是也不知,做得不是也不知。圣人便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恁地便吉,恁地便凶。所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者,即是此也。”(《朱子语类》卷六六)
人类社会初期,对大自然所知甚少,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处于“蠢蠢然”的阶段,不得不借助占卜来求得对自己行动的指导。周王朝时期,“巫史”们用四十九条蓍草(今之蚰蜒草或锯齿草),进行排列组合,为人们判定事物或行为的吉凶祸福。这类占卜活动极为频繁,“巫史”们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易》就是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规范化之后的结果,所以又称《周易》。朱熹指出《易》本为卜筮而作,这就揭开了长期笼罩于《易》的神秘面纱,正确地说明了《易》的来源。
历史常常有这种情况,谬误被普遍视为真理,而真理却被普遍视为谬误。朱熹的“卜筮”说在当时就得不到承认。他曾慨叹说:“如《易》,某便说道圣人只是为卜筮而作,不解有许多说话。但是此说难向人道,人不肯信。向来诸公力来与某辨,某煞费气力与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说,只做放那里。信也得,不信也得,无许多气力分疏。”(《朱子语类》卷六六)
旧时普遍认为,《易经》起源于伏羲画八卦,朱熹承袭了这一说法,但是他同时声称:“伏羲当时,偶然见得一便是阳,二便是阴,从而画放那里。”“(伏羲)当初也只是理会网罟等事,也不曾有许多峣崎,如后世《经世书》之类。而今人便要说伏羲如神明样,无所不晓。伏羲也自纯朴,也不曾去理会许多事来。”(《朱子语类》卷六六)伏羲只是传说中的人物,朱熹确信实有其人,未必妥当,但他把伏羲看成“纯朴”的普通人,在剥去《易》的神秘外衣上仍然有其积极意义。
《易经》分“经”和“传”两部分。“经”是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组成,反映古代卜筮书的原貌,“传”是对于“经”的解释,由《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等七种十篇组成,称为“十翼”。“经”与“传”最初分别刊行,东汉时,为了阅读方便,将《彖》《象》等解经之“传”附于“经”文之下,合并刊行。南宋时,吕祖谦根据嵩山晁氏发现的《易经》古本,将《易经》定为《经》两卷、《传》十卷。朱熹大力肯定这一发现,又详加考证,说明《易》的“经”与“传”两部分在古代各自刊行,“中间颇为诸儒所乱”的状况。这样,古本《易经》的面貌就清晰地被呈现出来了。
《易经》的“经”与“传”不仅在古代各自刊行,而且成于不同时代。除旧传伏羲画八卦外,古人又传说文王衍六十四卦,孔子作《彖》《象》等“十翼”。朱熹承袭这些说法,但强调的是彼此之间的不同。他说:“今人读《易》,当分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朱子语类》卷六六)又说:“《“《易》之为书,更历三圣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辞,皆依卜筮以为教,而其法则异。至若孔子之赞,则又一以义理为教而不专于卜筮也。”(《书伊川先生易传版本后》,《朱子文集》卷八一)这就是说:伏羲、文王都只停留在卜筮阶段,到了孔子,才将卜筮语言发展为哲学语言,“因那阴阳消长盈虚,说出个进退存亡之道理来”(《朱子语类》卷六七)。朱熹关于“《易》经三圣”的说法虽然或与事实不合(伏羲、文王),或缺乏有力证明(孔子),但他指出“经”“传”有别,“传”在易学发展史上有巨大作用,仍是很有见地的。
《易经》由符号和文字两部分组成,后来的研究者各有重点,从而形成象数和义理两大派别。象数派着重以奇偶之数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来解说《易经》,兴起于汉朝;义理派则着重阐发《易经》中所包含的哲理,兴起于晋朝。到了宋朝,两派均有发展。象数派以陈抟(?—989)、周敦颐、邵雍为代表。他们推尊汉儒假托的《河图》与《洛书》,喜欢用图式来解释《易经》所包含的哲理,说明宇宙生成和发展过程,被后人称为“图书派”。义理派以欧阳修(1007—1072)、程颐、张载为代表。他们竭力排斥王弼(226—249)以来用老庄之道来解《易》的倾向,主张用传统的儒学来说明《易》理。朱熹对上述两派都有所推崇,也都有所批评,力图加以综合,形成“大一统”的易学体系。
朱熹对“图书派”给过很高评价,例如他赞誉周敦颐的《太极图》“不由师傅,默契道体,建图属书,根极要领”。他的《周易本义》一书首刊邵雍等人的《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等九图,但是,他又批评邵雍“近于附会穿凿”。对于义理派,他也给过很高的评价,例如他推崇程颐的《易传》“因时立教,以承三圣”,但是他又批评其“支离散漫”。朱熹认为象数是作《易》的根本,因而必须通过象数去研究义理。他问道:“若果为义理作,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学》之书,言义理以晓人,须得画八卦则甚?”“何故要假卜筮来说?又何故说许多吉凶悔吝?”(《朱子语类》卷六六)基于此,朱熹反对离开卜筮之书这一特点去对《易》“茫昧臆度”,任意解释,以致凭虚失实。他说:“近世言《易》者,直弃卜筮而虚谈义理,致文义牵强无归宿,此弊久矣!要须先以卜筮占决之意求经文本义,而复以传释之,则其命词之意与其所自来之故,皆可渐次而见矣。”(《孙季和》(五),《朱文公别集》卷三)
从学术角度看,研究古人著作,解说经书,必须精确地了解并阐述古人的“本义”,而不可借解经之名,实际上阐述自己的一套。朱熹认为程颐的《易传》就有此弊病,他说:“《易传》义理精。”“只是于本义不相合。”(《朱子语类》卷六七)朱熹提出,程颐如要“立议论教人,可向别处说,不可硬配在《易》上说”(《朱子语类》卷六九)。他痛感后代的许多解《易》者“说道理太多”,因而《易》的本来面目也就沉埋得愈深。
为了忠于“本义”,朱熹有时甚至敢于向孔子挑战。《易经》中的《既济》与《未济》卦,有“濡首濡尾”之句。朱熹说:“分明是说野狐过水。今孔子解云‘饮酒濡首’,亦不知是如何?只要孔子说,人便不敢议。他人便恁地不得。”(《朱子语类》卷七三)朱熹的时代是个只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时代,但是他却敢于提出异见,“与孔子分疏”,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朱熹承认《易》难读,有许多地方不明白。他说:“经书难读,而《易》为尤难。”因此,他劝人读“四书”,而不劝人学《易》。他说:“《易》自别是一个道理,不是教人底书。”(《朱子语类》卷六七)甚至说:“(孔子)元不曾教人去读《易》。”(《朱子语类》卷六六)有时,他甚至说自己费了许多精神读《易》,其结果却有如吃鸡肋(《朱子语类》卷一〇四)。这在当时而言,也是“离经叛道”的。
二、《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古的一部诗歌总集。朱熹对《诗经》进行过长期、深入的研究,著有《诗集传》八卷。
相传《诗经》为孔子删订,孔子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汉儒著《诗序》,为了恪遵圣训,便使用穿凿附会的办法,将所有《诗经》中的作品都说成“主文谲谏,化下刺上”之作,结果,隔碍难通,完全遮蔽了《诗经》的真实面目。朱熹研究《诗经》的最大贡献在于否定汉儒的《诗序》,从而部分地揭示了《诗经》的真面目。
朱熹最初也相信《诗序》的说法,遇到解说不通之处,还曲意为之解释,但总觉得不安。后来索性抛开《诗序》,只是玩味《诗经》本身的文词,自此走进新天地,“觉得道理透彻”“诗意方活”。他的《诗集传》一书就诗论诗,每篇述其主旨,每章言其大意,有不少新见解。例如《诗经》中的《狡童》,其中有“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等句,旧说解释成“思见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也”,但朱熹却正确地指出,此类诗歌完全是“闾巷风土,男女情思之词”(《楚辞集注》卷一)。根据他的研究,《诗经》中此类作品有《静女》《桑中》《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将仲子》《有女同车》《山有扶苏》等共二十四篇。
朱熹是个道学家,不赞成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他虽然看出了《诗经》中《国风》的性质,但是,并不肯定这些作品。相反,却斥之为“淫乱”之作。他批评《卫风》“淫靡”,“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诗》卷第三),又批评《郑风》“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诗》卷第四)。在朱熹看来,《卫风》是“男子戏妇女”,还可以容忍,而《郑风》则“多是妇人戏男子”,简直可恶至极(《朱子语类》卷八十)。在《诗集传·序》中,朱熹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以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悯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他认为《诗经》中的《雅》《颂》都是周初朝廷上使用的作品,作者往往是“圣人之徒”,因此水平最高,可以作为万世不变的学习榜样。《雅》中有一部分“变雅”,其作者是当时的“贤人君子”,心地“忠厚恻怛”,目的是为了“陈善闭邪”,也为圣人所肯定。至于《国风》,则需要区别。《周南》《召南》,其地区因为受到文王的教化,所以作品正派,但是《邶风》以下,人有好有坏,作品也就有正有邪,他要人们“考其得失,善者师之,恶者改焉”(《诗经传·序》)。
至此,朱熹就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既然《诗经》中的作品有善有恶、有正有邪,怎样解释孔子所说的“思无邪”呢?
在这一问题面前,朱熹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宣称孔子的话不对,这是朱熹所不敢的;另一种回答是“曲为之说”,想方设法证明孔子的话不错。朱熹选择的是后者。他说:“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今必曰彼以无邪之思铺陈淫乱之事,而悯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则曷若曰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耶?”(《读吕氏诗纪桑中篇》,《朱子文集》卷七〇)将“思无邪”的主体从作者转移到读者,既维护了孔子的权威,又维护了礼教的尊严。
《诗经》有所谓“赋、比、兴”三种写作手法。赋是据事直陈,比是借彼喻此,都比较易于理解,唯独“兴”,前人的解释常常不知所云。朱熹指出:“诗之兴,全无巴鼻。后人诗犹有此体。如‘青青陵上陌,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朱子语类》卷八十)它和后面的诗句并无意义上的关联,只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或“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这就正确地指出了“兴”的特征和作用(《朱子语类》卷八十)。
三、《书经》
《书经》又称《尚书》,是上古时期的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史迹的著作的汇篇,传说由孔子编订,是孔子用以讲学的主要典籍。朱熹没有专门研究《书经》的著作,但是,他对于东晋时晚出的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的伪《尚书传》提出质疑,在中国辨伪史上有一定地位。
《尚书》相传原有百篇。秦始皇焚书后,至西汉时仅存二十八篇,为原秦博士伏胜所传,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被称为《今文尚书》,计虞夏书四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九篇。其中虞夏书是儒家根据传说材料编造而成,商书、周书则是比较可靠的历史文献。到了汉武帝时,鲁恭王刘馀从孔子故宅墙壁中发现以先秦古文写成的本子,为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所得,于今文二十九篇之外,增加十六篇,共四十五篇,称《古文尚书》,但是,很不幸,这四十五篇用古文写成的古文献在发现之后又散佚了(或说有目无文)。至东晋时,梅颐献出《尚书》五十九篇,其中据原《今文尚书》而加以离析的三十三篇、新增的二十五篇及孔安国《书序》一篇。此后,历代相传。唐代孔颖达(574—648)撰《五经正义》,即以之为据。自五代以至宋明,开科取士,都以此本为准。至清代才经学者考证,证明梅颐新增的二十五篇和《书序》均为伪作。梅颐与《古文尚书》同时献出的还有托名孔安国解释《尚书》的《尚书传》,计十三卷,也是伪作。
朱熹是最早指出《尚书传》是伪作的学者。他说:“《尚书》孔安国传,此恐是魏晋间人所作,托安国为名。与毛公《诗传》大段不同。今观序文亦不类汉文章(汉时文字粗,魏晋间文字细)。如《孔丛子》亦然,皆是那一时人所为。”(《朱子语类》卷七八)
对于梅颐所献《古文尚书》,朱熹虽未直揭其伪,但从语言风格上提出了疑问。他说:“汉儒以伏生所传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为记录之实语难正,而润色之雅词易好;则暗诵者不应偏得所难,而考文者反专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书临漳所刊四经后》,《朱子文集》卷八二)又说:“只疑伏生偏记得艰的,却不记得易的。”自朱熹提出疑问之后,元朝的吴澄(1249—1333),明朝的梅,清朝的阎若璩(1636—1704)、惠栋(1697—1758)、丁晏等人继起,考证日益精密,终于揭出了梅颐作伪的真相。
四、《春秋》
《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所记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原是鲁国的国史,相传经孔子删削而成。《孟子·滕文公》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进一步宣称:“《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春秋》行文极为简洁,短时只有一个字,最长也不过四十多字。传统有所谓“一字褒贬说”,认为《春秋》在简洁的文字中寄寓圣人的褒贬深意。朱熹反对这种说法,认为“《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朱子语类》卷八三)。他反对在读《春秋》时,刻意求深,穿凿附会地去探寻圣人的言外之意,明确表示:“生乎千百载之下,逆推乎千百载上圣人之心。况自家之心又未如得圣人,如何知得圣人肚里事?”(《朱子语类》卷八三)他对于诸家解释,以及所谓《春秋》“凡例”,都不敢相信:“近世说《春秋》者太巧,皆失圣人之意。又立为凡例,加某字其例为如何,去某字其例为如何,尽是胡说!”(《朱子语类》卷五五)
朱熹不很赞成将《春秋》视为经书。有学生问他,《春秋》当如何看?他明确表示:“只如看史样看。”(《朱子语类》卷八三)
五、《礼经》
儒家有所谓“三礼”之说,指的是《周礼》《仪礼》《礼记》三本书。它们都是战国至西汉初年儒家关于社会伦理和政治思想的论著。《周礼》或称《周官》,是古文经中的重要典籍。旧说以为周公所作,今文经学者则指为西汉末年刘歆(?—23)所伪造,两派长期争论不休。根据近人研究,它依托周制,反映的则是战国时期儒家对政治制度的设想。《仪礼》亦称《士礼》,是今文经的要籍,记述周代贵族的各种礼节和仪式。旧说以为周公所作,或经孔子手定。近人则以为是战国儒家作品而为汉儒编订。《礼记》指西汉戴圣所编《小戴礼记》,为西汉中期儒家的礼仪论文选集。另有戴德所编《大戴礼记》,但旧时不被称为经。
朱熹相信《周礼》是“周公遗典”。他说:“《周礼》一书好看,广大精密,周家法度在里。”又说:“今人不信《周官》,若据某言,却不恁地。”(《朱子语类》卷八六)对《仪礼》,他也采取尊信态度,但认为流传本不完备。他说:“今仪礼多是士礼,天子、诸侯丧祭之礼皆不存”,“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朱子语类》卷八五)在《仪礼》和《礼记》的关系上,他认为《仪礼》是经,《礼记》是对《仪礼》的解释。他说:“《礼记》要兼《仪礼》读。如冠礼、丧礼、乡饮酒礼之类,《仪礼》皆载其事,《礼记》只发明其理。”(《朱子语类》卷八七)为此,他计划写作《仪礼经传集解》一书,将《仪礼》作为本经,取《礼记》及各种经史杂著有关礼的记载附于本经之下,但此书未能完成。
朱熹也不很主张学生学《礼》。他说:“礼学多不可考。盖其为书不全。考来考去,考得更没下梢,故学《礼》者多迂阔。”(《朱子语类》卷八四)
六、《孝经》
《孝经》托名孔子与他的弟子曾参(前505—前436)互为问答,论述孝道,宣扬宗法思想。关于其作者,班固(32—92)、郑玄(127—200)均认为是孔子,司马迁则认为是曾参。近人研究,认为成书于秦汉之际,应属孔门后学之作,共十八章,约三千字,有今文、古文两种版本。唐开元七年(719),玄宗命刘知几等人鉴定,并汇集王肃(195—256)等六家之说为注,刻石太学。天宝二年(743),玄宗又亲自作注,颁行天下。
朱熹著有《孝经刊误》一书。他否定《孝经》为孔子所著,将该书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改经文约二百二十三字。他说:“窃尝考之,传文固多附会,而经文不免有离析增加之失。顾自汉以来,诸儒传诵,莫觉其非。至或以为孔子所自著,则又可笑之尤者”(《礼书纲目》卷七八)。
朱熹没有版本根据,就擅自删改《孝经》文本、强分经传的做法受到后人的批评,清人毛奇龄(1623—1713)著《孝经问》,就对朱熹的武断行为提出了责难。
七、“四书”
所谓“四书”,亦称“四子书”,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本书。《论语》是孔子的语录。《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孟子》是孟子及其弟子的言论与活动记录。北宋时程颐首先将这四本书并提,认为学者必先学此四书,然后学习“六经”。朱熹非常赞赏程颐的这一观点,以毕生精力从事这四本书的注释和研究工作。南宋绍熙元年(1190),朱熹在漳州刊刻此四书,“四书”之名自此成立。此后,他先后完成《四书章句集注》十九卷、《四书或问》三十九卷,其他关于“四书”的著作尚有《论孟要义》《论孟精义》《学庸详说》等多种。他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一卷,其中“四书”占五十一卷。除此之外,朱熹还选辑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人的语录,编为《近思录》十四卷,作为“四书”的导读。
朱熹非常重视“四书”,视为人一生“立其规模”“定其根本”的经典。他说:“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在次序上,他主张先读《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他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卷十四)他又认为“四书”易,“六经”难,读“四书”的功夫少而得效多,主张将“四书”作为学习“六经”的阶梯。元代以后,孔孟并称,“四书”及朱熹的注解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模板,发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钱穆曾说:“(朱熹)退‘六经’于‘四书’之后,必使学者先‘四书’后‘六经’,更为在中国学术史上有旋转乾坤之大力。”(《朱子新学案》)
北宋前期,学术思想大体沿袭前代,没有特别的建树;北宋中后期,疑古辨伪思潮兴起。学者们不仅怀疑汉代以来的解经、说经之作,而且也逐渐怀疑到了经文本身。朱熹是这一方面的重要代表人物。
一、《易经》
《易经》是先秦时代的一部神秘的典籍,由符号和文字两部分组成,居于儒家所定经籍中的首位,长期受到尊崇。但是关于它的性质和面貌,却有种种说法。
朱熹对《易经》做过多年研究,著有《周易本义》,是道学家注《易》的代表作。此外,他还著有《易学启蒙》一书,另有大量关于《易》的言论,散见于其语录和文集中。因此,在易学研究史上,朱熹具有重要地位。明初,朝廷曾将《周易本义》和程颐的《周易程氏传》颁行天下,作为知识分子科举考试的标准读物。
朱熹说过许多推崇《易经》的话,如“洁净精微,《易》之教也”“《易》之为书,广大悉备,人皆可得而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大小精粗,无所不备”等等。(《朱子语类》卷六八、七四)但是,朱熹却直指《易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卜筮书。他说:
“熹尝以为《易经》本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训诫,故其言虽约,而所包甚广。”
“古时人蠢蠢然,事事都不晓,做得是也不知,做得不是也不知。圣人便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恁地便吉,恁地便凶。所谓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者,即是此也。”(《朱子语类》卷六六)
人类社会初期,对大自然所知甚少,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处于“蠢蠢然”的阶段,不得不借助占卜来求得对自己行动的指导。周王朝时期,“巫史”们用四十九条蓍草(今之蚰蜒草或锯齿草),进行排列组合,为人们判定事物或行为的吉凶祸福。这类占卜活动极为频繁,“巫史”们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易》就是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和规范化之后的结果,所以又称《周易》。朱熹指出《易》本为卜筮而作,这就揭开了长期笼罩于《易》的神秘面纱,正确地说明了《易》的来源。
历史常常有这种情况,谬误被普遍视为真理,而真理却被普遍视为谬误。朱熹的“卜筮”说在当时就得不到承认。他曾慨叹说:“如《易》,某便说道圣人只是为卜筮而作,不解有许多说话。但是此说难向人道,人不肯信。向来诸公力来与某辨,某煞费气力与他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说,只做放那里。信也得,不信也得,无许多气力分疏。”(《朱子语类》卷六六)
旧时普遍认为,《易经》起源于伏羲画八卦,朱熹承袭了这一说法,但是他同时声称:“伏羲当时,偶然见得一便是阳,二便是阴,从而画放那里。”“(伏羲)当初也只是理会网罟等事,也不曾有许多峣崎,如后世《经世书》之类。而今人便要说伏羲如神明样,无所不晓。伏羲也自纯朴,也不曾去理会许多事来。”(《朱子语类》卷六六)伏羲只是传说中的人物,朱熹确信实有其人,未必妥当,但他把伏羲看成“纯朴”的普通人,在剥去《易》的神秘外衣上仍然有其积极意义。
《易经》分“经”和“传”两部分。“经”是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组成,反映古代卜筮书的原貌,“传”是对于“经”的解释,由《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等七种十篇组成,称为“十翼”。“经”与“传”最初分别刊行,东汉时,为了阅读方便,将《彖》《象》等解经之“传”附于“经”文之下,合并刊行。南宋时,吕祖谦根据嵩山晁氏发现的《易经》古本,将《易经》定为《经》两卷、《传》十卷。朱熹大力肯定这一发现,又详加考证,说明《易》的“经”与“传”两部分在古代各自刊行,“中间颇为诸儒所乱”的状况。这样,古本《易经》的面貌就清晰地被呈现出来了。
《易经》的“经”与“传”不仅在古代各自刊行,而且成于不同时代。除旧传伏羲画八卦外,古人又传说文王衍六十四卦,孔子作《彖》《象》等“十翼”。朱熹承袭这些说法,但强调的是彼此之间的不同。他说:“今人读《易》,当分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朱子语类》卷六六)又说:“《“《易》之为书,更历三圣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辞,皆依卜筮以为教,而其法则异。至若孔子之赞,则又一以义理为教而不专于卜筮也。”(《书伊川先生易传版本后》,《朱子文集》卷八一)这就是说:伏羲、文王都只停留在卜筮阶段,到了孔子,才将卜筮语言发展为哲学语言,“因那阴阳消长盈虚,说出个进退存亡之道理来”(《朱子语类》卷六七)。朱熹关于“《易》经三圣”的说法虽然或与事实不合(伏羲、文王),或缺乏有力证明(孔子),但他指出“经”“传”有别,“传”在易学发展史上有巨大作用,仍是很有见地的。
《易经》由符号和文字两部分组成,后来的研究者各有重点,从而形成象数和义理两大派别。象数派着重以奇偶之数和八卦所象征的物象来解说《易经》,兴起于汉朝;义理派则着重阐发《易经》中所包含的哲理,兴起于晋朝。到了宋朝,两派均有发展。象数派以陈抟(?—989)、周敦颐、邵雍为代表。他们推尊汉儒假托的《河图》与《洛书》,喜欢用图式来解释《易经》所包含的哲理,说明宇宙生成和发展过程,被后人称为“图书派”。义理派以欧阳修(1007—1072)、程颐、张载为代表。他们竭力排斥王弼(226—249)以来用老庄之道来解《易》的倾向,主张用传统的儒学来说明《易》理。朱熹对上述两派都有所推崇,也都有所批评,力图加以综合,形成“大一统”的易学体系。
朱熹对“图书派”给过很高评价,例如他赞誉周敦颐的《太极图》“不由师傅,默契道体,建图属书,根极要领”。他的《周易本义》一书首刊邵雍等人的《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等九图,但是,他又批评邵雍“近于附会穿凿”。对于义理派,他也给过很高的评价,例如他推崇程颐的《易传》“因时立教,以承三圣”,但是他又批评其“支离散漫”。朱熹认为象数是作《易》的根本,因而必须通过象数去研究义理。他问道:“若果为义理作,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学》之书,言义理以晓人,须得画八卦则甚?”“何故要假卜筮来说?又何故说许多吉凶悔吝?”(《朱子语类》卷六六)基于此,朱熹反对离开卜筮之书这一特点去对《易》“茫昧臆度”,任意解释,以致凭虚失实。他说:“近世言《易》者,直弃卜筮而虚谈义理,致文义牵强无归宿,此弊久矣!要须先以卜筮占决之意求经文本义,而复以传释之,则其命词之意与其所自来之故,皆可渐次而见矣。”(《孙季和》(五),《朱文公别集》卷三)
从学术角度看,研究古人著作,解说经书,必须精确地了解并阐述古人的“本义”,而不可借解经之名,实际上阐述自己的一套。朱熹认为程颐的《易传》就有此弊病,他说:“《易传》义理精。”“只是于本义不相合。”(《朱子语类》卷六七)朱熹提出,程颐如要“立议论教人,可向别处说,不可硬配在《易》上说”(《朱子语类》卷六九)。他痛感后代的许多解《易》者“说道理太多”,因而《易》的本来面目也就沉埋得愈深。
为了忠于“本义”,朱熹有时甚至敢于向孔子挑战。《易经》中的《既济》与《未济》卦,有“濡首濡尾”之句。朱熹说:“分明是说野狐过水。今孔子解云‘饮酒濡首’,亦不知是如何?只要孔子说,人便不敢议。他人便恁地不得。”(《朱子语类》卷七三)朱熹的时代是个只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时代,但是他却敢于提出异见,“与孔子分疏”,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朱熹承认《易》难读,有许多地方不明白。他说:“经书难读,而《易》为尤难。”因此,他劝人读“四书”,而不劝人学《易》。他说:“《易》自别是一个道理,不是教人底书。”(《朱子语类》卷六七)甚至说:“(孔子)元不曾教人去读《易》。”(《朱子语类》卷六六)有时,他甚至说自己费了许多精神读《易》,其结果却有如吃鸡肋(《朱子语类》卷一〇四)。这在当时而言,也是“离经叛道”的。
二、《诗经》
《诗经》是中国最古的一部诗歌总集。朱熹对《诗经》进行过长期、深入的研究,著有《诗集传》八卷。
相传《诗经》为孔子删订,孔子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汉儒著《诗序》,为了恪遵圣训,便使用穿凿附会的办法,将所有《诗经》中的作品都说成“主文谲谏,化下刺上”之作,结果,隔碍难通,完全遮蔽了《诗经》的真实面目。朱熹研究《诗经》的最大贡献在于否定汉儒的《诗序》,从而部分地揭示了《诗经》的真面目。
朱熹最初也相信《诗序》的说法,遇到解说不通之处,还曲意为之解释,但总觉得不安。后来索性抛开《诗序》,只是玩味《诗经》本身的文词,自此走进新天地,“觉得道理透彻”“诗意方活”。他的《诗集传》一书就诗论诗,每篇述其主旨,每章言其大意,有不少新见解。例如《诗经》中的《狡童》,其中有“彼狡童兮,不与我言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等句,旧说解释成“思见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也”,但朱熹却正确地指出,此类诗歌完全是“闾巷风土,男女情思之词”(《楚辞集注》卷一)。根据他的研究,《诗经》中此类作品有《静女》《桑中》《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将仲子》《有女同车》《山有扶苏》等共二十四篇。
朱熹是个道学家,不赞成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他虽然看出了《诗经》中《国风》的性质,但是,并不肯定这些作品。相反,却斥之为“淫乱”之作。他批评《卫风》“淫靡”,“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诗》卷第三),又批评《郑风》“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诗》卷第四)。在朱熹看来,《卫风》是“男子戏妇女”,还可以容忍,而《郑风》则“多是妇人戏男子”,简直可恶至极(《朱子语类》卷八十)。在《诗集传·序》中,朱熹说:“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自《邶》以下,则其国之治乱不同,人之贤否亦异,其所感而发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齐,而所谓先王之风者于此焉变矣。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其作者,往往圣人之徒,固所以为万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于《雅》之变者,亦皆一时贤人君子悯时病俗之所为,而圣人取之。”他认为《诗经》中的《雅》《颂》都是周初朝廷上使用的作品,作者往往是“圣人之徒”,因此水平最高,可以作为万世不变的学习榜样。《雅》中有一部分“变雅”,其作者是当时的“贤人君子”,心地“忠厚恻怛”,目的是为了“陈善闭邪”,也为圣人所肯定。至于《国风》,则需要区别。《周南》《召南》,其地区因为受到文王的教化,所以作品正派,但是《邶风》以下,人有好有坏,作品也就有正有邪,他要人们“考其得失,善者师之,恶者改焉”(《诗经传·序》)。
至此,朱熹就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既然《诗经》中的作品有善有恶、有正有邪,怎样解释孔子所说的“思无邪”呢?
在这一问题面前,朱熹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宣称孔子的话不对,这是朱熹所不敢的;另一种回答是“曲为之说”,想方设法证明孔子的话不错。朱熹选择的是后者。他说:“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今必曰彼以无邪之思铺陈淫乱之事,而悯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则曷若曰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耶?”(《读吕氏诗纪桑中篇》,《朱子文集》卷七〇)将“思无邪”的主体从作者转移到读者,既维护了孔子的权威,又维护了礼教的尊严。
《诗经》有所谓“赋、比、兴”三种写作手法。赋是据事直陈,比是借彼喻此,都比较易于理解,唯独“兴”,前人的解释常常不知所云。朱熹指出:“诗之兴,全无巴鼻。后人诗犹有此体。如‘青青陵上陌,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朱子语类》卷八十)它和后面的诗句并无意义上的关联,只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或“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这就正确地指出了“兴”的特征和作用(《朱子语类》卷八十)。
三、《书经》
《书经》又称《尚书》,是上古时期的历史文献和部分追述古代史迹的著作的汇篇,传说由孔子编订,是孔子用以讲学的主要典籍。朱熹没有专门研究《书经》的著作,但是,他对于东晋时晚出的伪《古文尚书》及孔安国的伪《尚书传》提出质疑,在中国辨伪史上有一定地位。
《尚书》相传原有百篇。秦始皇焚书后,至西汉时仅存二十八篇,为原秦博士伏胜所传,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被称为《今文尚书》,计虞夏书四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九篇。其中虞夏书是儒家根据传说材料编造而成,商书、周书则是比较可靠的历史文献。到了汉武帝时,鲁恭王刘馀从孔子故宅墙壁中发现以先秦古文写成的本子,为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所得,于今文二十九篇之外,增加十六篇,共四十五篇,称《古文尚书》,但是,很不幸,这四十五篇用古文写成的古文献在发现之后又散佚了(或说有目无文)。至东晋时,梅颐献出《尚书》五十九篇,其中据原《今文尚书》而加以离析的三十三篇、新增的二十五篇及孔安国《书序》一篇。此后,历代相传。唐代孔颖达(574—648)撰《五经正义》,即以之为据。自五代以至宋明,开科取士,都以此本为准。至清代才经学者考证,证明梅颐新增的二十五篇和《书序》均为伪作。梅颐与《古文尚书》同时献出的还有托名孔安国解释《尚书》的《尚书传》,计十三卷,也是伪作。
朱熹是最早指出《尚书传》是伪作的学者。他说:“《尚书》孔安国传,此恐是魏晋间人所作,托安国为名。与毛公《诗传》大段不同。今观序文亦不类汉文章(汉时文字粗,魏晋间文字细)。如《孔丛子》亦然,皆是那一时人所为。”(《朱子语类》卷七八)
对于梅颐所献《古文尚书》,朱熹虽未直揭其伪,但从语言风格上提出了疑问。他说:“汉儒以伏生所传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或者以为记录之实语难正,而润色之雅词易好;则暗诵者不应偏得所难,而考文者反专得其所易,是皆有不可知者。”(《书临漳所刊四经后》,《朱子文集》卷八二)又说:“只疑伏生偏记得艰的,却不记得易的。”自朱熹提出疑问之后,元朝的吴澄(1249—1333),明朝的梅,清朝的阎若璩(1636—1704)、惠栋(1697—1758)、丁晏等人继起,考证日益精密,终于揭出了梅颐作伪的真相。
四、《春秋》
《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所记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原是鲁国的国史,相传经孔子删削而成。《孟子·滕文公》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进一步宣称:“《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春秋》行文极为简洁,短时只有一个字,最长也不过四十多字。传统有所谓“一字褒贬说”,认为《春秋》在简洁的文字中寄寓圣人的褒贬深意。朱熹反对这种说法,认为“《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要见当时治乱兴衰,非是于一字上定褒贬”(《朱子语类》卷八三)。他反对在读《春秋》时,刻意求深,穿凿附会地去探寻圣人的言外之意,明确表示:“生乎千百载之下,逆推乎千百载上圣人之心。况自家之心又未如得圣人,如何知得圣人肚里事?”(《朱子语类》卷八三)他对于诸家解释,以及所谓《春秋》“凡例”,都不敢相信:“近世说《春秋》者太巧,皆失圣人之意。又立为凡例,加某字其例为如何,去某字其例为如何,尽是胡说!”(《朱子语类》卷五五)
朱熹不很赞成将《春秋》视为经书。有学生问他,《春秋》当如何看?他明确表示:“只如看史样看。”(《朱子语类》卷八三)
五、《礼经》
儒家有所谓“三礼”之说,指的是《周礼》《仪礼》《礼记》三本书。它们都是战国至西汉初年儒家关于社会伦理和政治思想的论著。《周礼》或称《周官》,是古文经中的重要典籍。旧说以为周公所作,今文经学者则指为西汉末年刘歆(?—23)所伪造,两派长期争论不休。根据近人研究,它依托周制,反映的则是战国时期儒家对政治制度的设想。《仪礼》亦称《士礼》,是今文经的要籍,记述周代贵族的各种礼节和仪式。旧说以为周公所作,或经孔子手定。近人则以为是战国儒家作品而为汉儒编订。《礼记》指西汉戴圣所编《小戴礼记》,为西汉中期儒家的礼仪论文选集。另有戴德所编《大戴礼记》,但旧时不被称为经。
朱熹相信《周礼》是“周公遗典”。他说:“《周礼》一书好看,广大精密,周家法度在里。”又说:“今人不信《周官》,若据某言,却不恁地。”(《朱子语类》卷八六)对《仪礼》,他也采取尊信态度,但认为流传本不完备。他说:“今仪礼多是士礼,天子、诸侯丧祭之礼皆不存”,“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朱子语类》卷八五)在《仪礼》和《礼记》的关系上,他认为《仪礼》是经,《礼记》是对《仪礼》的解释。他说:“《礼记》要兼《仪礼》读。如冠礼、丧礼、乡饮酒礼之类,《仪礼》皆载其事,《礼记》只发明其理。”(《朱子语类》卷八七)为此,他计划写作《仪礼经传集解》一书,将《仪礼》作为本经,取《礼记》及各种经史杂著有关礼的记载附于本经之下,但此书未能完成。
朱熹也不很主张学生学《礼》。他说:“礼学多不可考。盖其为书不全。考来考去,考得更没下梢,故学《礼》者多迂阔。”(《朱子语类》卷八四)
六、《孝经》
《孝经》托名孔子与他的弟子曾参(前505—前436)互为问答,论述孝道,宣扬宗法思想。关于其作者,班固(32—92)、郑玄(127—200)均认为是孔子,司马迁则认为是曾参。近人研究,认为成书于秦汉之际,应属孔门后学之作,共十八章,约三千字,有今文、古文两种版本。唐开元七年(719),玄宗命刘知几等人鉴定,并汇集王肃(195—256)等六家之说为注,刻石太学。天宝二年(743),玄宗又亲自作注,颁行天下。
朱熹著有《孝经刊误》一书。他否定《孝经》为孔子所著,将该书分为经一章、传十四章,删改经文约二百二十三字。他说:“窃尝考之,传文固多附会,而经文不免有离析增加之失。顾自汉以来,诸儒传诵,莫觉其非。至或以为孔子所自著,则又可笑之尤者”(《礼书纲目》卷七八)。
朱熹没有版本根据,就擅自删改《孝经》文本、强分经传的做法受到后人的批评,清人毛奇龄(1623—1713)著《孝经问》,就对朱熹的武断行为提出了责难。
七、“四书”
所谓“四书”,亦称“四子书”,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本书。《论语》是孔子的语录。《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孟子》是孟子及其弟子的言论与活动记录。北宋时程颐首先将这四本书并提,认为学者必先学此四书,然后学习“六经”。朱熹非常赞赏程颐的这一观点,以毕生精力从事这四本书的注释和研究工作。南宋绍熙元年(1190),朱熹在漳州刊刻此四书,“四书”之名自此成立。此后,他先后完成《四书章句集注》十九卷、《四书或问》三十九卷,其他关于“四书”的著作尚有《论孟要义》《论孟精义》《学庸详说》等多种。他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一卷,其中“四书”占五十一卷。除此之外,朱熹还选辑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等人的语录,编为《近思录》十四卷,作为“四书”的导读。
朱熹非常重视“四书”,视为人一生“立其规模”“定其根本”的经典。他说:“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在次序上,他主张先读《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他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卷十四)他又认为“四书”易,“六经”难,读“四书”的功夫少而得效多,主张将“四书”作为学习“六经”的阶梯。元代以后,孔孟并称,“四书”及朱熹的注解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模板,发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钱穆曾说:“(朱熹)退‘六经’于‘四书’之后,必使学者先‘四书’后‘六经’,更为在中国学术史上有旋转乾坤之大力。”(《朱子新学案》)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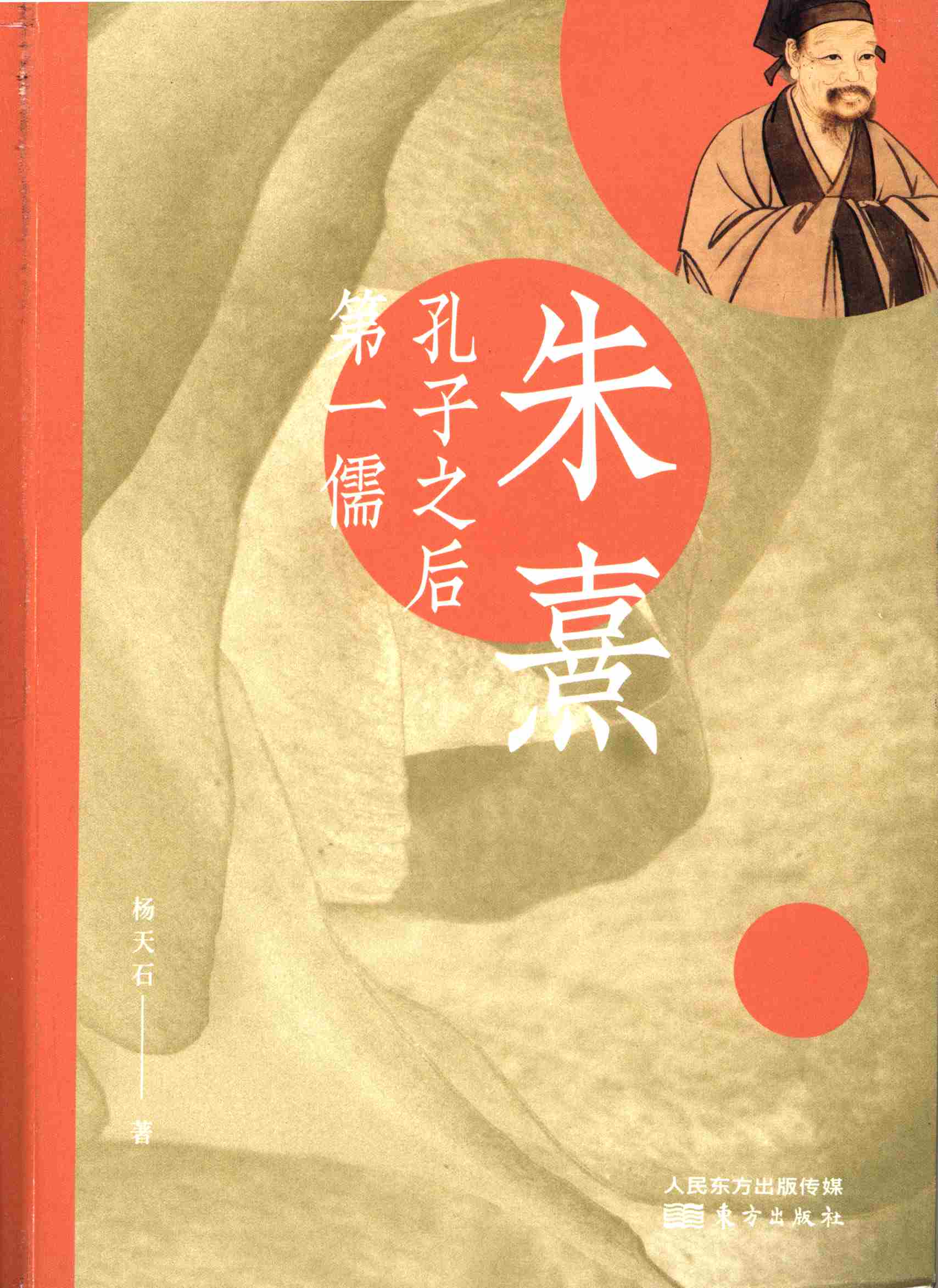
《朱熹:孔子之后第一儒》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本文讲述了以理制欲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道德要求——宋明儒学关于“理”“欲”关系论述的现代启示、改铸儒学的新需要、生于忧患,长于坎坷的大思想家、社会政治思想、理为“天地万物之根”的世界本原论、“天命”与“气质”相结合的双重人性论、唤醒天赋观念的“格物致知”论、克人欲、存天理 、“一中又自有对”的辩证法等。
阅读
相关人物
朱熹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