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唤醒天赋观念的“格物致知”论
| 内容出处: | 《朱熹:孔子之后第一儒》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3739 |
| 颗粒名称: | 第六章 唤醒天赋观念的“格物致知”论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15 |
| 页码: | 69-83 |
| 摘要: | 本文讲述了朱熹唤醒天赋观念的“格物致知”论包括“醒与睡”、在外的“儿子”与在家的“儿子”、自“铢积寸累”以至“一旦豁然贯通”、对知行关系的全面展开情况。 |
| 关键词: | 朱熹 儒家 著作 |
内容
秦汉之际的儒家著作《礼记》中有一篇《大学》,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项“纲领”,又提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项“条目”。北宋时,司马光特别赞赏这篇文章,为之单独注解,著成《大学广义》。程颢、程颐继续表彰它,详加论说。南宋时,朱熹又把它和《论语》《中庸》《孟子》并列,作为“四书”之一。朱熹并打乱原本次序,分全文为“经”一章、“传”十章,宣称“经”是孔子的话,由曾子叙述,“传”则是曾子的意思,由门人所录。
《大学》称:“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朱熹认为解释这一段话的“传”文大部分亡佚了,因此,他自己写了一段,放进《大学》里作为“传”:“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这段话是朱熹“格物致知”论的纲领性的叙述。
朱熹认为,人的道德修养和认识过程很像用铜镜照人。本来,镜子可以毛发毕具地照出人的形貌,但是,当它蒙受污垢后,就失去作用,必须括垢磨光,才能重新照人。这里,朱熹虽在理论上承认,人可以不学而知,但是在实际上,他还是认为人必须做主观努力。
一、“醒与睡”
朱熹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天赋的。他说:“人心至灵,有什么事不知,有什么事不晓,有什么道理不具在这里!”但是,正像镜面蒙垢一般,人由于气禀的局限和物欲的蒙蔽,天赋观念就不能很好地发生作用。他说:“以其气质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昧其性,以乱其伦、败其则而不知反,必学以开之。”(《行宫便殿奏札》二,《朱子文集》卷一四)气质之有偏,这在上文已经分析过。物欲之有蔽,指的是人对于色、声、香、味、安逸等享受的追求。朱熹认为气禀和物欲这两个东西蒙蔽了人的本性,扰乱了伦理观念,败坏了老天爷制订的行为准则,结果,人就陷于邪恶,必须通过“格物”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这样,在朱熹的哲学体系里,认识的任务只是使原来万理具足的受蒙蔽的人心恢复其本来面目。在这一过程中,人不曾从外界增加任何一丝一毫的新知识、新观念。他把这一
过程比喻为人的睡与醒,认为人醒时,耳目聪明,应事接物,不会发生差错,但“若被私欲所引,便一似睡着相似,只更与他唤醒”。因此,在朱熹看来,所谓修养就是唤醒沉睡着的人心,消除蒙蔽,使天赋观念得以发扬。他认为人在经过长久的“用力”之后,就会“豁然贯通”,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可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说:“鄙贱之事虽琐屑,然孰非天理之流行者,但此理既得,自然不习而无不能耳。”张载曾将人的认识区别为“天德良知”和“闻见小知”,认为前者是天赋的,后者是“物交”的,即与客观世界接触的结果。朱熹认为一切都是天赋的,这就将张载的错误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朱熹的“唤醒”论类似于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的“回忆”说。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天赋地具有一切理念,但是当“灵魂”和肉体结合的时候,却由于肉体的影响而把这些理念忘记了,因此,必须通过学习,回忆“灵魂”原先旧有的知识。
人的认识能力是人脑的一种特殊功能,形成于人类的漫长进化中,但是人的认识内容(知识、观念)则是后天实践、学习的结果。朱熹的“唤醒”论貌似荒唐,然而却包含着合理的内核:人的认识能力是与生俱有的一种先天潜在能力,依赖于后天的“唤醒”——开掘与发扬。
二、在外的“儿子”与在家的“儿子”
据朱熹说,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格是“尽”的意思,又是“至”的意思。朱熹认为只有把事物之理穷尽到十分了,才能算格物;致知就是推展、扩充自己的知识以至于极点。朱熹认为人都有知识,例如儿童懂得爱父亲,长大了懂得敬兄长等,但是这种知识只停留在大略的水平上,必须从这里推展开去,达到知无不尽的极限。他说:“格物致知,彼我相对而言耳。格物所以致知。于这一物上穷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于物之理穷得二分,即我之知亦知得二分;于物之理穷得愈多,则我之知愈广。”(《朱子语类》卷十八)物是彼,知是我,二者相对,朱熹把这种关系称为“主宾”关系。他说:“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宾之辨。”在认识过程中,人是主体,事物是客体,即所谓“宾”。例如人去认识山,人便是主体,山是客体,这是不错的。“主宾之辨”的提出,是朱熹对中国认识论史的贡献。
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两条途径。
按朱熹的说法,理既存在于外物,也存在于人心,都是太极的分别的、完整的体现。前者被朱熹比作在外的儿子,后者被比作在家的儿子。某次,有人对他的“从外去讨得来”的认识途径发生怀疑,朱熹笑着说:“某常说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家,一个在外去干家事,其父却说道在家底是自家儿子,在外底不是!”(《朱子语类》卷十五)既然在外的儿子、在家的儿子都是儿子,则在物之理与在心之理都是理。因此,逻辑的结论必然是:既可以向外去认识在物之理,也可以向内去认识在心之理。
认识在物之理就是所谓向外用功。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与他理会过。(《朱子语类》卷十五)在朱熹的哲学体系里,物不仅指客观事物,也指人的行为动作,甚至还包括“一念之微”。因此,他的格物的内涵就相当广泛。他要人读书时便就文字上格,听人说话时便就说话上格,待人处世时就在待人处世上格。其中,他特别重视读书,把它列为“穷理”过程的起点。据他说,天下之理都具备于圣人所著的“经训史册”中,要想穷理,就必先读圣人之书。
有时,朱熹也提倡“格”所谓天地万物以至草木虫鱼之理,如天如何而能高、地如何而能厚、山岳如何而能凝结,以至炭的白黑、水的冷湿、车之行陆、舟之行水,“这底是可以如何使,那底是可以如何用”等,朱熹认为,一一皆在“理会”之列。他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朱子语类》卷十八)他广泛地观察、研究并思考过自然现象,在天文学、地质学、气象学、生物学等方面提出过不少重要的见解。如他认为:“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初间极软,后来方凝得硬。”又如他从高山化石推断地质变迁:“常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变而为刚。”再如,他认为月“常受日光为明”。又如,他认为人是自然变化而来:“天地之初,如何讨个人种?自是气蒸结成两个人后,方生许多万物。”“那两个人,便如而今人身上虱,是自然变化出来。”这些见解,在当时说来,都是先进的,符合或接近科学认识。
朱熹反对轻信前人,重视亲身的实践和考察。他说:“前人恁地说,亦未必尽,须是自把来横看、竖看。”(《朱子语类》卷九)他认为在认识的初级阶段,必须“先在见闻上做功夫”。他说:“如今人理会学,须是有见闻,岂能舍此?先是于见闻上做功夫,到然后脱然贯通。”(《朱子语类》卷九八)《禹贡》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地理著作。朱熹曾以其亲身考察的结果纠正了其中的错误。他说:“著书者多是臆度,未必身到足历,故其说亦难尽据,未必如今目见之亲切著明耳!”他不仅家藏浑仪,而且曾用胶泥自制立体地图模型。他的学生蔡元定向他请教天文、历法方面的问题,朱熹回答说:“历法恐亦只可略论大概规模。盖欲其详,即须仰观俯察乃可验。今无其器,殆亦难尽究也。”朱熹认为只有亲身经历的知识才是真知,例如喝酒才懂得醉,吃饭才懂得饱,“人不曾吃底,见人说道是解醉、解饱,他也道是解醉、解饱,只是见得不亲切”(《朱子语类》卷一八)。一切真知都发源于直接经验。朱熹的上述思想完全符合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对后代的影响是良好的。明代的药物学家李时珍(1517—1593)即将自己的学问称为“吾儒格物之学”。
但是,朱熹提倡“格物”,主要是为了要人们借物为踏脚石去认识那个先于物而又派生物的“理”,利用有形象的“器”去掌握无形象的“道”,并由此进入圣贤之域。因此,他在表示要逐事逐物“一一根究”的同时,马上声明,学者们用功,不可不讲先后缓急。他在《答陈齐仲》函中说:“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朱子文集》卷三九)因此,他特别强调格物要“切己”,又强调要“反身”,一再表示不能“徇外夸多”,放纵自己的精力于“汗漫纷纶不可知之域”(《答吴伯丰》,《朱子文集》卷五二)。
在“向外用功”之外,朱熹还提倡过另一条认识途径,这就是“向内用功”,认识在心之理。他说:“天下之理,逼塞满前,耳之所闻,目之所见,无非物也,若之何而穷之哉?须当察之于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后于物之所在,从而察之,则不至泛滥矣。”(《朱子语类》卷十八)朱熹把这个过程称之为“由中而外,自近而远”。
在朱熹的哲学体系里,向外用功亦称“博观”,向内用功亦称“反求”或“内省”。在二者的关系上,朱熹主张不可偏废。有时,他激烈地批评杨时“反身而诚”的观点:“万物之理须你逐一去看,理会过方可。如何会反身而诚了,天下万物之理便自然备于我,成个什么?”(《朱子语类》卷六二)但是,朱熹有时又明确表示,必须以向内用功为主。他说:“要知学者用功六分内面,四分外面便好,一半已难,若六分外面,财尤不可。”(《朱子语类》卷一五)
人的认识过程确有向外用功和向内用功两个方面。向外用功是实践的过程;向内用功是对从实践中得来的材料进行思考、分析的过程。朱熹指出了认识过程有两个方面,这也是他对中国认识论史的贡献。但是,向外用功是基础,是认识世界、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离开了向外用功,向内用功就成了虚想胡猜。朱熹将二者并列起来,而且主张“六七分去里面体会”,这就又背离真理了。
必须指出的是,当朱熹感到永康、永嘉等事功学派的强大威胁时,他连“三四分去外面理会”也不要。在《与刘子澄》函中称:“近觉向来为学,实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误,而误人亦不少。方别寻得一头绪,似差简约。端的始知文字、言语之外,真别有用心处,恨未得面论也。浙中后来事体,大段支离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朱子文集》卷三五)这里所说的“浙中后来事体”,乃是指永康、永嘉等事功学派的发展,所说“似差简约”的另一“头绪”,正是向内用功。他说:“切须去了外慕之心”,“有一分心向里,得一分力,两分心向里,得两分力”(《朱子语类》卷二)。晚年,他有时连书也不主张读。当时,他因为目疾不能观书,但自称“道理”却看得格外简约明白。因此,他提倡“闲中静坐,收敛身心”,甚至希望自己早日失明,说是:“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颇恨盲废之不早也。”(《朱子文集》卷四六)
朱熹在认识论上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早年,主张“默会诸心”,是向内用功的禅学一路;中年,强调“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是向外用功一路。晚年,主张“闲中静坐,收敛身心”,这就又是向内用功的禅学一路了。
朱熹在认识论上的思想变迁,反映了道学中理学一派向心学一派发展的必然趋势。后来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不仅继承了陆九渊,实际上也继承朱熹。王阳明编有《朱子晚年定论》一书,其中既有朱熹的早年之论,也确有朱熹的晚年之论。应该承认,朱熹的这部分言论和陆王之学是并无多大差别的。
三、自“铢积寸累”以至“一旦豁然贯通”
在成佛问题上,佛教有渐修和顿悟两派。渐修论者主张长期的,甚至是累世的修行,顿悟论者主张参一两句“话头”,因一两件事启发,就顿悟成佛。唐代中期之后,惠(慧)能(638—722)所创立的禅宗南派大盛;因此,顿悟之说大为流行。据说,有的人因为听了“手作拳,拳全手”的比喻就“豁然开悟”。石头和尚自回,则因在凿石时,一锤下去,火光迸出,于是就“忽然彻悟”。
在成圣问题上,道学也有渐修和顿悟两种观点。所谓渐修,指的是长期的个人修养;所谓顿悟,指的是刹那间的突然领悟。程颐曾经向往过一种“言下即悟”的境界,幻想用一两次谈话,甚至一两句话使人成圣(《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杨简(1141—1225)也自称听了陆九渊几句话后,就忽然“省悟”了(《谥议》,《象山集》卷三二)。
朱熹不赞成“顿悟”,认为这种观点使人“癫狂粗率”,忽略日常功夫,是“今日学者大病”。(《答胡季随》,《朱子文集》卷五三)他主张人的道德修养只能持之以渐,“铢积寸累”,一点点地积累、一步步地前进。他说:“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做。如左脚进得一步,右脚又进得一步,左脚又进,持续不已。”(《朱子语类》卷一八)
朱熹认为人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表至里、由粗而精的过程。开始时,只能“看个大胚模”,然后才能“逐旋做细”。他说:“穷理须穷得尽,得其皮肤是表也,见得深奥是里也。知其粗不知其精,皆不可谓之格。”(《朱子语类》卷一八)
人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人们在获得了丰富的感觉材料之后,还必须对它们加以改造制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概念和理论,从而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朱熹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朱子语类》卷六八)朱熹这里所说的“形而上之道理”,正是指理性认识。他认为,如果人的认识达不到这个阶段,就不能算作学问。当然,朱熹并不懂得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区别,但他看出了理有“表里精粗”的不同,人的认识是一个由下而上,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这是有其合理因素的。
朱熹主张通过“万殊”去认识“理一”,由认识个别的事物而“四面凑合”,发展为对诸种事物共同本质的认识。他说:
“学者且要去万理中千头万绪都理会,四面凑合来,自见得是一理。不去理会那万理,只管去理会那一理……只是空想象。”(《朱子语类》卷一一七)
人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朱熹这里的思想完全符合人的认识秩序。
朱熹主张由“万”到“一”,由博而约,是不是主张天下之物都要“格”到呢?并不。朱熹主张类推。他说:“只要以类而推。”他并举例说:“如识得这灯有许多光,便因这灯推将去,识得那烛亦恁地光。”(《朱子语类》卷一八)他认为有了这个方法之后,十件事穷得八九件,其他一二件虽没有去穷,也可以“类推”而知。
类推是一种推理方法。它使人的认识从一个事物转进到另一个事物,是人们认识新事物、发现新原理的一种思维方法。但是,用于类比的两个事物必须在本质上有共同点或相似点,否则就是一种生拉硬扯的错误比拟,逻辑上叫作无类比附。朱熹从“这灯‘推到’那烛”是合理的,而由水之必寒、火之必热,推到为臣必忠、为子必孝,则是无类比附。
据朱熹说,经过了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长期积累和“类推”之后,人的认识就发生飞跃,进入“豁然贯通”的境界了。这个境界是突然到来的,即所谓“一旦”;又是极端神秘地到来的,即所谓“忽然爆开”,“不知不觉,自然醒悟”,而一旦到达这个境界之后,人的认识和道德修养就达到极限。他描写这时的状况是:“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大学章》)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出神入化了。
人的认识过程中有飞跃,亦即所谓突变。朱熹意识到,在“铢积寸累”的渐变基础上会产生质的飞跃——“豁然贯通”,同样有其合理因素。但是,他不了解任何这种飞跃都只是人们在认识真、善、美的历史长途中的一个阶段,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所谓“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的境界永远不可能出现。
四、对知行关系的全面展开
从程颐起,道学家们很喜欢讨论走路问题。程颐说:“今有人欲之京师,必知所出之门、所由之道,然后可往;未尝知也,虽有欲往之心,其能进乎?”(《河南程氏粹言,论学篇》)程颐此时住在洛阳,他的意思是:从洛阳到开封,要先知道出哪道门,走哪条道,然后才能出发;如果不知道,出了别的门,走了别的道,就不知道会走到哪儿去了。程颐的话有没有道理呢?很有道理。所以他又说:“说到底,须是知了方行得。”
朱熹也主张知先行后。他说:“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学》先说致知。”朱熹这样说,主要是为了强调儒学伦理对于个人修养和行为的指导作用。他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者,皆明明德事。格物、致知便是要知得分明;诚意、正心、修身便是要行得分明。”(《朱子语类》卷十四)明德,指的是天赋于人的道德观念;明明德,指消除气禀、物欲对于人的锢蔽,发扬天赋于人的道德观念;诚意、正心、修身,指按“明德”的要求进行个人修养。朱熹认为致知是知的开始,诚意则是行的开始。
知和行有着明确的界限。知属于思想,是主观;行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属于实践。朱熹把“诚意”“正心”一类活动也算作“行”,说明他关于“行”的概念和今人不同。在此之外,朱熹还有一个概念,叫“笃行”。他说:“须修身、齐家以下,乃可谓之笃行。”(《朱子语类》卷五一)这里,朱熹所说的“行”就超出了个人修养的范围,而包含着“治国”“平天下”一类的政治实践了。
“先知得,方行得”,先懂得了儒学伦理,然后才能进行道德修养,有所行动。否则,个人的道德修养就会走到别的方向,行为也就可能越出规矩。所以朱熹强调“万事皆在穷理后”,认为“经不正,理不明”,不管“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他曾把知行关系比为眼睛和脚的关系,说是:“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九)意思是有了眼睛,才会看清道路;没有眼睛,两只脚就不知道会迈到哪儿去了。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自然,知对行有指导作用。但是,一切知包括道德观念、理论体系都来源于行。例如要从洛阳到开封,先要“穷究”路线,要“知”。但是,开封在东,出东门、往东走的知识还是从走路中得来的。所以从认识过程的总体上看,只能是行先于知,而不能知先于行。
朱熹部分地看出了知行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朱子语类》卷九四)这里,知行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他又说:“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朱子语类》卷九)从书本或别人的口述得来的知识往往感受肤浅,经过亲身实践之后,这种感受才会深刻并明晰起来。上述一段话表明,朱熹在一定程度上懂得行可以使知深化。
在知行轻重问题上,朱熹有时强调“知字上重”。曾经有人问他:“有知其如此,而行不如此者,是如何?”朱熹答道:“此只是知之未至。”他认为一个人只要真正体认了儒学伦理,就会“自然”地以之作为个人修养和行为的准绳。
在某些时候,朱熹又强调“行为重”。他说:“学之之要,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卷十三)理论上懂得了“善”是什么,这是必要的,但是重要的还是“行”,只有通过“行”,才能使“善”与“我”合而为一,达到指导道德修养的目的。有时,他甚至主张以“行”来考察“知”。他说:“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诚不诚,只看做不做如何!”
在伦理领域内,一个人对于善是真懂,还是假懂;是诚心向善,还是三心二意,要看“做不做”。朱熹的这一思想是正确的、有价值的,他的“行为重”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朱熹也讨论到了对于行的评价标准问题。他说:“然穷理不深,则安知所行之可否哉!”朱熹认为行的是与非、可与否的评价标准是理,只有“穷理”愈深,才能对行做出正确的评价。朱熹的这一思想是错误的。真、善、美都存在于客观现实中,评价行的标准只能是社会效果。
对于知行难易问题,朱熹有时认为知易行难,有时认为知难行易。其实,难易并不是知行问题的科学表述。以往的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大都因不同的情况和条件而异。朱熹摇摆于两种看法之间,既说明了他对此尚无定见,也说明了对这一问题不宜作简单的回答。
朱熹空前全面地展开了对知行关系多方面的论述,其中“真理颗粒”颇多,须要仔细地加以捡拾。
《大学》称:“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朱熹认为解释这一段话的“传”文大部分亡佚了,因此,他自己写了一段,放进《大学》里作为“传”:“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这段话是朱熹“格物致知”论的纲领性的叙述。
朱熹认为,人的道德修养和认识过程很像用铜镜照人。本来,镜子可以毛发毕具地照出人的形貌,但是,当它蒙受污垢后,就失去作用,必须括垢磨光,才能重新照人。这里,朱熹虽在理论上承认,人可以不学而知,但是在实际上,他还是认为人必须做主观努力。
一、“醒与睡”
朱熹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天赋的。他说:“人心至灵,有什么事不知,有什么事不晓,有什么道理不具在这里!”但是,正像镜面蒙垢一般,人由于气禀的局限和物欲的蒙蔽,天赋观念就不能很好地发生作用。他说:“以其气质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昧其性,以乱其伦、败其则而不知反,必学以开之。”(《行宫便殿奏札》二,《朱子文集》卷一四)气质之有偏,这在上文已经分析过。物欲之有蔽,指的是人对于色、声、香、味、安逸等享受的追求。朱熹认为气禀和物欲这两个东西蒙蔽了人的本性,扰乱了伦理观念,败坏了老天爷制订的行为准则,结果,人就陷于邪恶,必须通过“格物”才能改变这种状况。
这样,在朱熹的哲学体系里,认识的任务只是使原来万理具足的受蒙蔽的人心恢复其本来面目。在这一过程中,人不曾从外界增加任何一丝一毫的新知识、新观念。他把这一
过程比喻为人的睡与醒,认为人醒时,耳目聪明,应事接物,不会发生差错,但“若被私欲所引,便一似睡着相似,只更与他唤醒”。因此,在朱熹看来,所谓修养就是唤醒沉睡着的人心,消除蒙蔽,使天赋观念得以发扬。他认为人在经过长久的“用力”之后,就会“豁然贯通”,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境界,可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说:“鄙贱之事虽琐屑,然孰非天理之流行者,但此理既得,自然不习而无不能耳。”张载曾将人的认识区别为“天德良知”和“闻见小知”,认为前者是天赋的,后者是“物交”的,即与客观世界接触的结果。朱熹认为一切都是天赋的,这就将张载的错误又向前发展了一步。
朱熹的“唤醒”论类似于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的“回忆”说。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天赋地具有一切理念,但是当“灵魂”和肉体结合的时候,却由于肉体的影响而把这些理念忘记了,因此,必须通过学习,回忆“灵魂”原先旧有的知识。
人的认识能力是人脑的一种特殊功能,形成于人类的漫长进化中,但是人的认识内容(知识、观念)则是后天实践、学习的结果。朱熹的“唤醒”论貌似荒唐,然而却包含着合理的内核:人的认识能力是与生俱有的一种先天潜在能力,依赖于后天的“唤醒”——开掘与发扬。
二、在外的“儿子”与在家的“儿子”
据朱熹说,格物就是穷尽事物之理。格是“尽”的意思,又是“至”的意思。朱熹认为只有把事物之理穷尽到十分了,才能算格物;致知就是推展、扩充自己的知识以至于极点。朱熹认为人都有知识,例如儿童懂得爱父亲,长大了懂得敬兄长等,但是这种知识只停留在大略的水平上,必须从这里推展开去,达到知无不尽的极限。他说:“格物致知,彼我相对而言耳。格物所以致知。于这一物上穷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于物之理穷得二分,即我之知亦知得二分;于物之理穷得愈多,则我之知愈广。”(《朱子语类》卷十八)物是彼,知是我,二者相对,朱熹把这种关系称为“主宾”关系。他说:“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宾之辨。”在认识过程中,人是主体,事物是客体,即所谓“宾”。例如人去认识山,人便是主体,山是客体,这是不错的。“主宾之辨”的提出,是朱熹对中国认识论史的贡献。
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两条途径。
按朱熹的说法,理既存在于外物,也存在于人心,都是太极的分别的、完整的体现。前者被朱熹比作在外的儿子,后者被比作在家的儿子。某次,有人对他的“从外去讨得来”的认识途径发生怀疑,朱熹笑着说:“某常说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家,一个在外去干家事,其父却说道在家底是自家儿子,在外底不是!”(《朱子语类》卷十五)既然在外的儿子、在家的儿子都是儿子,则在物之理与在心之理都是理。因此,逻辑的结论必然是:既可以向外去认识在物之理,也可以向内去认识在心之理。
认识在物之理就是所谓向外用功。他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与他理会过。(《朱子语类》卷十五)在朱熹的哲学体系里,物不仅指客观事物,也指人的行为动作,甚至还包括“一念之微”。因此,他的格物的内涵就相当广泛。他要人读书时便就文字上格,听人说话时便就说话上格,待人处世时就在待人处世上格。其中,他特别重视读书,把它列为“穷理”过程的起点。据他说,天下之理都具备于圣人所著的“经训史册”中,要想穷理,就必先读圣人之书。
有时,朱熹也提倡“格”所谓天地万物以至草木虫鱼之理,如天如何而能高、地如何而能厚、山岳如何而能凝结,以至炭的白黑、水的冷湿、车之行陆、舟之行水,“这底是可以如何使,那底是可以如何用”等,朱熹认为,一一皆在“理会”之列。他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朱子语类》卷十八)他广泛地观察、研究并思考过自然现象,在天文学、地质学、气象学、生物学等方面提出过不少重要的见解。如他认为:“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时,想只有水火二者。”“初间极软,后来方凝得硬。”又如他从高山化石推断地质变迁:“常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变而为刚。”再如,他认为月“常受日光为明”。又如,他认为人是自然变化而来:“天地之初,如何讨个人种?自是气蒸结成两个人后,方生许多万物。”“那两个人,便如而今人身上虱,是自然变化出来。”这些见解,在当时说来,都是先进的,符合或接近科学认识。
朱熹反对轻信前人,重视亲身的实践和考察。他说:“前人恁地说,亦未必尽,须是自把来横看、竖看。”(《朱子语类》卷九)他认为在认识的初级阶段,必须“先在见闻上做功夫”。他说:“如今人理会学,须是有见闻,岂能舍此?先是于见闻上做功夫,到然后脱然贯通。”(《朱子语类》卷九八)《禹贡》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地理著作。朱熹曾以其亲身考察的结果纠正了其中的错误。他说:“著书者多是臆度,未必身到足历,故其说亦难尽据,未必如今目见之亲切著明耳!”他不仅家藏浑仪,而且曾用胶泥自制立体地图模型。他的学生蔡元定向他请教天文、历法方面的问题,朱熹回答说:“历法恐亦只可略论大概规模。盖欲其详,即须仰观俯察乃可验。今无其器,殆亦难尽究也。”朱熹认为只有亲身经历的知识才是真知,例如喝酒才懂得醉,吃饭才懂得饱,“人不曾吃底,见人说道是解醉、解饱,他也道是解醉、解饱,只是见得不亲切”(《朱子语类》卷一八)。一切真知都发源于直接经验。朱熹的上述思想完全符合唯物主义的经验论,对后代的影响是良好的。明代的药物学家李时珍(1517—1593)即将自己的学问称为“吾儒格物之学”。
但是,朱熹提倡“格物”,主要是为了要人们借物为踏脚石去认识那个先于物而又派生物的“理”,利用有形象的“器”去掌握无形象的“道”,并由此进入圣贤之域。因此,他在表示要逐事逐物“一一根究”的同时,马上声明,学者们用功,不可不讲先后缓急。他在《答陈齐仲》函中说:“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朱子文集》卷三九)因此,他特别强调格物要“切己”,又强调要“反身”,一再表示不能“徇外夸多”,放纵自己的精力于“汗漫纷纶不可知之域”(《答吴伯丰》,《朱子文集》卷五二)。
在“向外用功”之外,朱熹还提倡过另一条认识途径,这就是“向内用功”,认识在心之理。他说:“天下之理,逼塞满前,耳之所闻,目之所见,无非物也,若之何而穷之哉?须当察之于心,使此心之理既明,然后于物之所在,从而察之,则不至泛滥矣。”(《朱子语类》卷十八)朱熹把这个过程称之为“由中而外,自近而远”。
在朱熹的哲学体系里,向外用功亦称“博观”,向内用功亦称“反求”或“内省”。在二者的关系上,朱熹主张不可偏废。有时,他激烈地批评杨时“反身而诚”的观点:“万物之理须你逐一去看,理会过方可。如何会反身而诚了,天下万物之理便自然备于我,成个什么?”(《朱子语类》卷六二)但是,朱熹有时又明确表示,必须以向内用功为主。他说:“要知学者用功六分内面,四分外面便好,一半已难,若六分外面,财尤不可。”(《朱子语类》卷一五)
人的认识过程确有向外用功和向内用功两个方面。向外用功是实践的过程;向内用功是对从实践中得来的材料进行思考、分析的过程。朱熹指出了认识过程有两个方面,这也是他对中国认识论史的贡献。但是,向外用功是基础,是认识世界、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离开了向外用功,向内用功就成了虚想胡猜。朱熹将二者并列起来,而且主张“六七分去里面体会”,这就又背离真理了。
必须指出的是,当朱熹感到永康、永嘉等事功学派的强大威胁时,他连“三四分去外面理会”也不要。在《与刘子澄》函中称:“近觉向来为学,实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误,而误人亦不少。方别寻得一头绪,似差简约。端的始知文字、言语之外,真别有用心处,恨未得面论也。浙中后来事体,大段支离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朱子文集》卷三五)这里所说的“浙中后来事体”,乃是指永康、永嘉等事功学派的发展,所说“似差简约”的另一“头绪”,正是向内用功。他说:“切须去了外慕之心”,“有一分心向里,得一分力,两分心向里,得两分力”(《朱子语类》卷二)。晚年,他有时连书也不主张读。当时,他因为目疾不能观书,但自称“道理”却看得格外简约明白。因此,他提倡“闲中静坐,收敛身心”,甚至希望自己早日失明,说是:“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颇恨盲废之不早也。”(《朱子文集》卷四六)
朱熹在认识论上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早年,主张“默会诸心”,是向内用功的禅学一路;中年,强调“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是向外用功一路。晚年,主张“闲中静坐,收敛身心”,这就又是向内用功的禅学一路了。
朱熹在认识论上的思想变迁,反映了道学中理学一派向心学一派发展的必然趋势。后来王阳明的“致良知”说,不仅继承了陆九渊,实际上也继承朱熹。王阳明编有《朱子晚年定论》一书,其中既有朱熹的早年之论,也确有朱熹的晚年之论。应该承认,朱熹的这部分言论和陆王之学是并无多大差别的。
三、自“铢积寸累”以至“一旦豁然贯通”
在成佛问题上,佛教有渐修和顿悟两派。渐修论者主张长期的,甚至是累世的修行,顿悟论者主张参一两句“话头”,因一两件事启发,就顿悟成佛。唐代中期之后,惠(慧)能(638—722)所创立的禅宗南派大盛;因此,顿悟之说大为流行。据说,有的人因为听了“手作拳,拳全手”的比喻就“豁然开悟”。石头和尚自回,则因在凿石时,一锤下去,火光迸出,于是就“忽然彻悟”。
在成圣问题上,道学也有渐修和顿悟两种观点。所谓渐修,指的是长期的个人修养;所谓顿悟,指的是刹那间的突然领悟。程颐曾经向往过一种“言下即悟”的境界,幻想用一两次谈话,甚至一两句话使人成圣(《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杨简(1141—1225)也自称听了陆九渊几句话后,就忽然“省悟”了(《谥议》,《象山集》卷三二)。
朱熹不赞成“顿悟”,认为这种观点使人“癫狂粗率”,忽略日常功夫,是“今日学者大病”。(《答胡季随》,《朱子文集》卷五三)他主张人的道德修养只能持之以渐,“铢积寸累”,一点点地积累、一步步地前进。他说:“今日既格得一物,明日又格得一物,工夫更不住地做。如左脚进得一步,右脚又进得一步,左脚又进,持续不已。”(《朱子语类》卷一八)
朱熹认为人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由表至里、由粗而精的过程。开始时,只能“看个大胚模”,然后才能“逐旋做细”。他说:“穷理须穷得尽,得其皮肤是表也,见得深奥是里也。知其粗不知其精,皆不可谓之格。”(《朱子语类》卷一八)
人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人们在获得了丰富的感觉材料之后,还必须对它们加以改造制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概念和理论,从而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朱熹说:“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朱子语类》卷六八)朱熹这里所说的“形而上之道理”,正是指理性认识。他认为,如果人的认识达不到这个阶段,就不能算作学问。当然,朱熹并不懂得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区别,但他看出了理有“表里精粗”的不同,人的认识是一个由下而上,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这是有其合理因素的。
朱熹主张通过“万殊”去认识“理一”,由认识个别的事物而“四面凑合”,发展为对诸种事物共同本质的认识。他说:
“学者且要去万理中千头万绪都理会,四面凑合来,自见得是一理。不去理会那万理,只管去理会那一理……只是空想象。”(《朱子语类》卷一一七)
人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朱熹这里的思想完全符合人的认识秩序。
朱熹主张由“万”到“一”,由博而约,是不是主张天下之物都要“格”到呢?并不。朱熹主张类推。他说:“只要以类而推。”他并举例说:“如识得这灯有许多光,便因这灯推将去,识得那烛亦恁地光。”(《朱子语类》卷一八)他认为有了这个方法之后,十件事穷得八九件,其他一二件虽没有去穷,也可以“类推”而知。
类推是一种推理方法。它使人的认识从一个事物转进到另一个事物,是人们认识新事物、发现新原理的一种思维方法。但是,用于类比的两个事物必须在本质上有共同点或相似点,否则就是一种生拉硬扯的错误比拟,逻辑上叫作无类比附。朱熹从“这灯‘推到’那烛”是合理的,而由水之必寒、火之必热,推到为臣必忠、为子必孝,则是无类比附。
据朱熹说,经过了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长期积累和“类推”之后,人的认识就发生飞跃,进入“豁然贯通”的境界了。这个境界是突然到来的,即所谓“一旦”;又是极端神秘地到来的,即所谓“忽然爆开”,“不知不觉,自然醒悟”,而一旦到达这个境界之后,人的认识和道德修养就达到极限。他描写这时的状况是:“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大学章》)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出神入化了。
人的认识过程中有飞跃,亦即所谓突变。朱熹意识到,在“铢积寸累”的渐变基础上会产生质的飞跃——“豁然贯通”,同样有其合理因素。但是,他不了解任何这种飞跃都只是人们在认识真、善、美的历史长途中的一个阶段,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所谓“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的境界永远不可能出现。
四、对知行关系的全面展开
从程颐起,道学家们很喜欢讨论走路问题。程颐说:“今有人欲之京师,必知所出之门、所由之道,然后可往;未尝知也,虽有欲往之心,其能进乎?”(《河南程氏粹言,论学篇》)程颐此时住在洛阳,他的意思是:从洛阳到开封,要先知道出哪道门,走哪条道,然后才能出发;如果不知道,出了别的门,走了别的道,就不知道会走到哪儿去了。程颐的话有没有道理呢?很有道理。所以他又说:“说到底,须是知了方行得。”
朱熹也主张知先行后。他说:“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学》先说致知。”朱熹这样说,主要是为了强调儒学伦理对于个人修养和行为的指导作用。他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五者,皆明明德事。格物、致知便是要知得分明;诚意、正心、修身便是要行得分明。”(《朱子语类》卷十四)明德,指的是天赋于人的道德观念;明明德,指消除气禀、物欲对于人的锢蔽,发扬天赋于人的道德观念;诚意、正心、修身,指按“明德”的要求进行个人修养。朱熹认为致知是知的开始,诚意则是行的开始。
知和行有着明确的界限。知属于思想,是主观;行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属于实践。朱熹把“诚意”“正心”一类活动也算作“行”,说明他关于“行”的概念和今人不同。在此之外,朱熹还有一个概念,叫“笃行”。他说:“须修身、齐家以下,乃可谓之笃行。”(《朱子语类》卷五一)这里,朱熹所说的“行”就超出了个人修养的范围,而包含着“治国”“平天下”一类的政治实践了。
“先知得,方行得”,先懂得了儒学伦理,然后才能进行道德修养,有所行动。否则,个人的道德修养就会走到别的方向,行为也就可能越出规矩。所以朱熹强调“万事皆在穷理后”,认为“经不正,理不明”,不管“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他曾把知行关系比为眼睛和脚的关系,说是:“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九)意思是有了眼睛,才会看清道路;没有眼睛,两只脚就不知道会迈到哪儿去了。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自然,知对行有指导作用。但是,一切知包括道德观念、理论体系都来源于行。例如要从洛阳到开封,先要“穷究”路线,要“知”。但是,开封在东,出东门、往东走的知识还是从走路中得来的。所以从认识过程的总体上看,只能是行先于知,而不能知先于行。
朱熹部分地看出了知行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朱子语类》卷九四)这里,知行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他又说:“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朱子语类》卷九)从书本或别人的口述得来的知识往往感受肤浅,经过亲身实践之后,这种感受才会深刻并明晰起来。上述一段话表明,朱熹在一定程度上懂得行可以使知深化。
在知行轻重问题上,朱熹有时强调“知字上重”。曾经有人问他:“有知其如此,而行不如此者,是如何?”朱熹答道:“此只是知之未至。”他认为一个人只要真正体认了儒学伦理,就会“自然”地以之作为个人修养和行为的准绳。
在某些时候,朱熹又强调“行为重”。他说:“学之之要,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朱子语类》卷十三)理论上懂得了“善”是什么,这是必要的,但是重要的还是“行”,只有通过“行”,才能使“善”与“我”合而为一,达到指导道德修养的目的。有时,他甚至主张以“行”来考察“知”。他说:“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诚不诚,只看做不做如何!”
在伦理领域内,一个人对于善是真懂,还是假懂;是诚心向善,还是三心二意,要看“做不做”。朱熹的这一思想是正确的、有价值的,他的“行为重”的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朱熹也讨论到了对于行的评价标准问题。他说:“然穷理不深,则安知所行之可否哉!”朱熹认为行的是与非、可与否的评价标准是理,只有“穷理”愈深,才能对行做出正确的评价。朱熹的这一思想是错误的。真、善、美都存在于客观现实中,评价行的标准只能是社会效果。
对于知行难易问题,朱熹有时认为知易行难,有时认为知难行易。其实,难易并不是知行问题的科学表述。以往的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大都因不同的情况和条件而异。朱熹摇摆于两种看法之间,既说明了他对此尚无定见,也说明了对这一问题不宜作简单的回答。
朱熹空前全面地展开了对知行关系多方面的论述,其中“真理颗粒”颇多,须要仔细地加以捡拾。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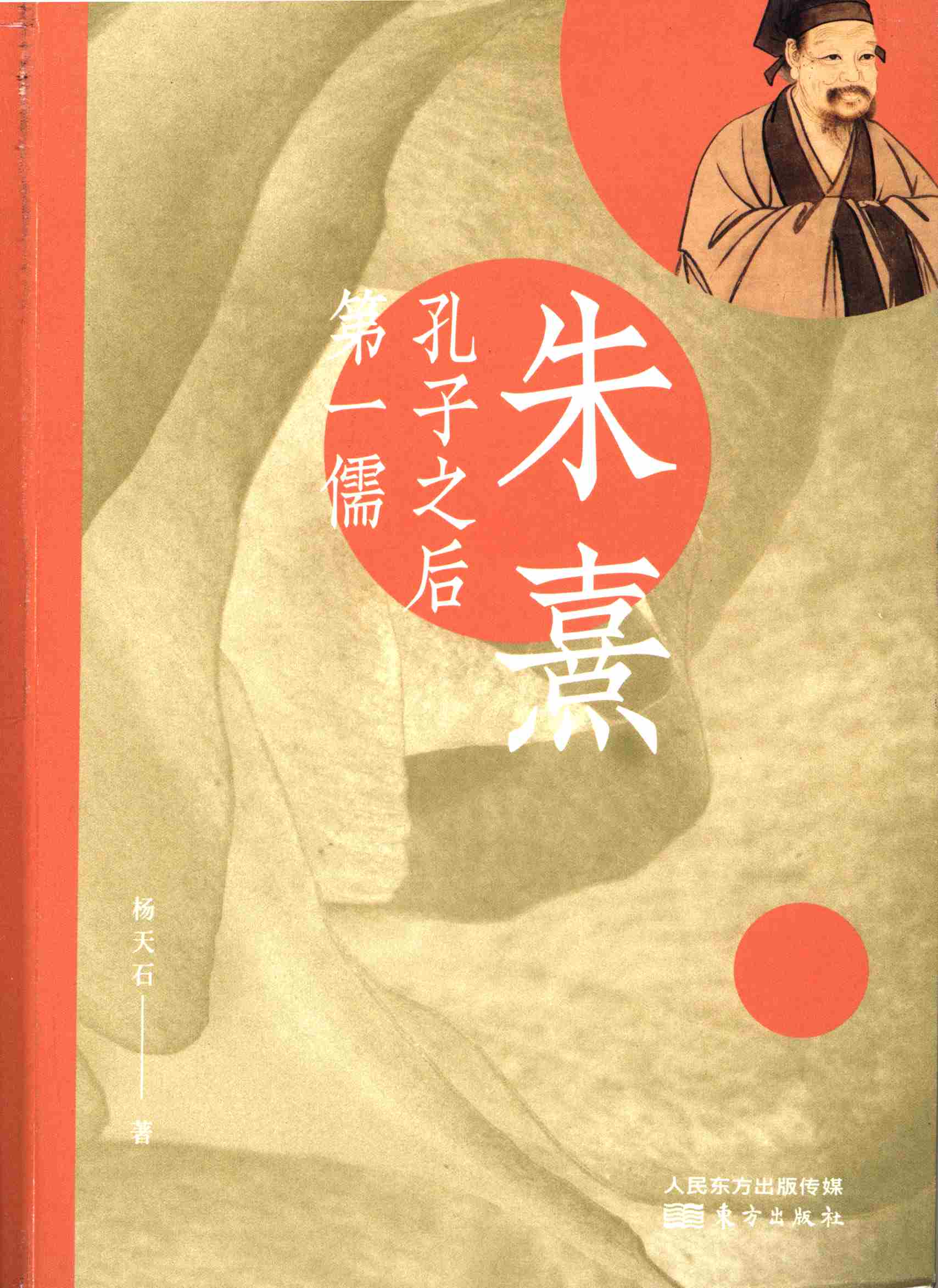
《朱熹:孔子之后第一儒》
出版者:东方出版社
本文讲述了以理制欲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道德要求——宋明儒学关于“理”“欲”关系论述的现代启示、改铸儒学的新需要、生于忧患,长于坎坷的大思想家、社会政治思想、理为“天地万物之根”的世界本原论、“天命”与“气质”相结合的双重人性论、唤醒天赋观念的“格物致知”论、克人欲、存天理 、“一中又自有对”的辩证法等。
阅读
相关人物
朱熹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