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朱熹文集编年评注》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20》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2927 |
| 颗粒名称: | 读《朱熹文集编年评注》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10 |
| 页码: | 195-204 |
| 摘要: | 本篇文章记述了《朱熹文集编年评注》是朱熹著作的整理和注释工作的专著,由郭齐和尹波编注,于2019年12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他们在之前整理出版《朱熹集》的基础上进行的深入研究和学术工作,该书对朱熹的文集进行了通校,尤其注重了宋元版的校勘,吸取了历代校勘成果,并成为学术界朱熹研究和理学与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
| 关键词: | 朱熹 文集 评注 |
内容
一
《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全十三册),朱熹著,郭齐、尹波编注,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朱熹文集是研究朱熹思想及其学术活动的主要材料。《朱熹文集编年评注》的二位作者以往就整理出版了《朱熹集》(全十册,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该书对传世的朱熹文集重要版本逐一进行了通校,尤其注重宋元版(包括海内外罕见孤本、珍本)的比勘,广泛吸取历代校勘成果,使之成为精校本。是当年出版时最为完备的版本,为学术界的朱熹研究和理学与中国文化研究作出重要贡献。1997年获第八次四川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除整理出版《朱熹集》外,二位作者还是国内研究朱熹的著名专家,长期从事朱熹研究,出版了诸如《朱熹新考》(郭齐著,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朱熹诗词编年笺注》(上、下册,朱熹著,郭齐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朱熹传》(郭齐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朱子学新探》(郭齐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发表了诸如《宋刊闽浙二本<朱熹文集>关系考论》(郭齐、尹波,《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04)、《<朱熹文集>版本源流考》(尹波、郭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03)、《新发现朱熹书信发覆》(尹波、郭齐,《文学遗产》2019-03)等一系列重要成果。
在长期研究和整理工作的基础上,二位作者校勘辑佚,对朱熹文集中的每篇诗文,考订撰作年月,添加解题、注释,整理历代评论,并附有版本考略、传记数据、文集序跋、篇名索引、朱熹年表、历代评论、伪托误题朱熹诗文存目等参考数据,是为朱熹文集的首个深度整理本。首次对全部诗文逐篇系年。《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全面、深入的解析,详细的编年,对于推动朱熹研究,乃至于宋代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深入与拓展,扩大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比以往出版的朱熹文集有明显的优势。
读罢该书,可知《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在古籍整理研究上,做了以下重要工作:
1.校勘
校勘现存重要文集版本二十余种。其中,海内孤本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宋淳熙、绍熙年间所刊《晦庵先生文集》前、后集系首次进行通校,增补文四篇,增补内容数千字,纠正今本文集若干错误,提供了《明筮占》《皇极辨》《云谷记》《少傅刘公神道碑》等众多异文;首次对现存宋刊闽、浙两大系统二十余种文集残本作了全面校勘;首次对元刻本《朱文公大同集》作了深入研究,成果发表在(日本)《东方学报》第91期、《文学遗产》2017年第3期,并采校记六十余条,移正错简数处(如卷六十六《蓍卦考误》等)。全书凡出校勘记七千余条。
2.辑佚
新发现佚文十余篇,经初步研究,已作为阶段性成果发表于《历史文献研究》2018年第40辑、《光明日报》2018年4月14日、《文学遗产》2019年第3期、(日本)《儒教学会报》2020年第4号等刊物。
3.辨伪
先后于《宋史研究论丛》第25辑等刊物发表了《朱熹两件手书作品真伪考辨》(2019)、《朱熹佚作疑伪考(一)》(2017)、《朱熹佚诗文三篇考论》(2017)、《朱熹佚作疑伪考(二)》(2018)、《朱熹佚文与子澄寺薄书、建昌帖考辨》(2018)、《朱熹佚作疑伪考(三)》(2019)、《朱熹谱序五篇辨伪》(2019)等文。该书附录《伪托误题朱熹诗文存目》,集八百余年朱文辨伪之大成,为史上首个朱熹佚文伪托误题目录。
4.注释
对全部诗词逐篇作了解题和笺注。解题提供有关背景材料,从总体上概括全篇意旨及疏释篇题中有碍理解的词语。笺注重在疏通文意,帮助读者达到对作品的正确理解。全书总计注释五千三百余条,朱熹文集之有注释,在史上尚不多见。
5.编年
首次对全部诗文逐篇系年。二位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的研究整理,新考定年及纠正、补充前人结论,重要者凡二百余条,一般性更正不在此数。
6.评论
在曾枣庄主编《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朱熹部分基础上,进行了相关的搜寻补充,首次将历代学者关于朱熹诗文的研究评论数据附于集中,总计一千三百余条。其中,有关某篇诗文的评论附于该篇之后,关于诗文的总体评论附于全书之后。
7.附录
包括:(1)传记数据;(2)文集序跋;(3)版本考略;(4)朱熹年表;(5)历代评论;(6)伪托误题朱熹诗文存目;(7)主要参考文献;(8)本书篇名索引。其中文集序跋特别注意收录海外所藏、所刻朱熹文集之序跋,为目前所收海外序跋最多之本。朱熹年表、历代评论、伪托误题朱熹诗文存目、主要参考文献系首次附入。
由于做了以上七条卓有成效的整理研究工作,从而形成了该书以下的突出特点:
1.补足全文:《朱子全书》第26册P630据《池北偶谈》卷9录《与某人帖》残文,其云:“十年前,率尔记张魏公行状,当时只是据渠家文字做成,后见它书所记不同,尝以为恨。”而在清李佐贤《书画鉴影》卷三(同治十年利津李氏刻本)有此全文。文前题“朱文公手札卷,纸本,高一尺四寸七分,长七尺四寸,凡三纸,计三札,字经(按:疑当作“径”)一寸内外。”此书题为“第一札”。文后题“草书,十八行。札前白文安德口口世家刀印,又一印不辨。札后白文吴越忠孝之家方印,君载方印。”文云:
熹伏蒙别纸督过,伏读震悚。顾实病衰,不堪思虑。若所记者一身一家一官之事,则犹可以勉强。至如元臣故老,动关国政,则首尾长阔,曲折精微,实非病余昏昧之人所能熟考传载。此熹所以不得词于潘、李诸丈之文,而于先正铭识之属则有取(按:疑当作“所”)不敢当也。卅年前,率尔记张魏公行事,当时只据渠家文字草成,后见它书所记多或未同,常以为愧。故于赵忠简家文字初已许之,而后亦不敢承当,已恳其改属陈太史矣,不知今竟如何也。况今词官万一不遂,则又将有王事之劳,比之家居,见扰弥甚。切望矜闵,贷此余生,毋劳竭其精神,以速就于溘然之地,则千万之幸也。若无性命之忧,则岂敢有所爱于先世恩契之门如此哉。俯伏布恳,惶恐之剧!右谨具呈。朝散郎、秘阁修撰朱熹札子。
2.删除衍文:《朱子全书》第26册P617据《朱子大同集》录《答许平仲》文:“仁人之心,未尝忘天下之忧,故如此也。漳、泉、汀三州经界未行,许公条究甚悉,监司郡守未有举行者。”“漳、泉、汀三州”以下明显为后来者所加衍文,故予删除也。
3.剔除误收:朱熹佚文有诸多伪作误题,如不仔细考证,必然误收不断。如《朱熹集》P5619、《朱子全书》第26册P612据宋人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所收《上殿札子》,乃馆阁上奏之文;《朱熹集》P5699、《朱子全书》第26册P809据《翰墨大全》所收《祭李三溪文》、P810《祭胡古潭文》,此二人乃宋末元初人,焉能为朱熹所祭?
4.移正错简:《朱熹集》卷66P3490“过揲二十八策”至“挂扐三十五策”原错简在“又曰苏氏所载一行之学”前,据宋浙本、《文公易说》移正至“尤不可以不辨”后。《朱子全书》23册已经移正,但P3252校记云“据淳熙本”移正。淳熙本根本没有此文,故误也。
5.校改误字:如《朱熹集》卷86P4445、《朱子全书》第24册P4050《修三闾忠节侯庙奉安祝文》“敢馔灵神,敢陈椒醑”,不仅二“敢”字彼此重复,“神”字与上文二“神”字重复,且文意几乎不通,显然失校。此据《永乐大典》卷五千七百六十九改“馔”“神”为“择”“辰”,改后“敢”字为“敬”字,则文从字顺矣。
6.考订月曰:《朱熹集》卷86P4445、《朱子全书》第24册P4049《谒修道州三先生祠文》首句“维绍熙五年岁次甲寅八月日”,其“日”字,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8作“己丑朔二下缺八日丙辰”,八月己丑朔,二十八日正是丙辰,故据以补正为二十八日丙辰。又上述1补足全文据残文“十年前”系之于淳熙三年,而据《书画鉴影》所载全文“卅年前”句,考订其作年当在绍熙五年正月。
7.订正序跋作者:《朱子全书》第27册P781有《朱子文语纂编目录后跋》,其作者署邵车,而据其跋末,明确云楚邵车鼎丰书。理解之误也。
8.增补佚文,补充事迹:朱熹佚文甚伙,但凡细细考订,定能有所收获。除第1条外,还有从《翰墨全书》首次发现的《与五六弟》三封,《与三六弟》一封,其详细论证,已刊于《文学遗产》2019年3期《新发现朱熹书信发覆》。不仅辑出了佚文,还首次考订出了朱熹祖墓纷争还有第二次,其时间在朱熹淳熙七年知南康军时。又如《答石天民书》,乃出自于乾隆间《南明石氏宗谱》,已考订出淳熙十四年作;《简十四表叔》九封,出自于《娶源韩溪程氏梅山支谱》,俱绍兴、隆兴间作,等等。
9.纠正它误:朱熹文集卷二有《次晦叔寄弟韵二首》,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上P516系于淳熙元年与吴翌,非也。其实乃朱熹淳熙十年与王炎,盖因吴翌、王炎二人都字晦叔,朱熹与吴翌屡有通问,而王炎则仅此一见,故历来都归于朱熹与吴翌诗。王炎《双溪文集》(清抄本)卷七《寄德莹弟二首》附录此诗,注云:朱晦庵和韵二首。是证也。
此外,朱熹与诸人有书信多封,原书或仅置于一题之下。此次编年,以年代为题,以示区分。此亦特色之一。
以上该书的这些突出的学术特色,值得充分肯定。
二
由于笔者长期从事朱熹研究,出版了《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朱熹与中国文化》《朱熹思想探讨》等多部朱熹研究的专著,发表了七十余篇朱熹研究的论文,从自身从事的研究工作来考虑,相比较朱熹文集整理研究工作的各个方面,我更关心《朱熹文集编年评注》中所涉及的对朱熹每一篇诗文的编年,因为这对于研究掌握朱熹学术思想前后发生的变化,进而动态地把握朱熹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最后的定论,意义重大。
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研究朱熹。研究之初,苦于没有朱熹的著作,后来我认识了四川广汉师范学校的历史老师刘雨涛先生(毕业于“中央大学”哲学系),他保存有一套四部备要本的《朱文公文集》,线装书,排印本,三十六册。我从他家借出阅读,但时间还不能长了,因为刘先生他也要看。我只得看一段时间后,还给刘雨涛老师。过一段时间再到广汉他家里借出来带到成都再看。后来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了《朱子语类》,可以部分解决阅读朱熹资料的问题。但《朱文公文集》还是只能断断续续地看。直到郭齐、尹波二先生整理点校的《朱熹集》于1996年在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后,才解决了阅读朱熹文集的难题。
此次出版的《朱熹文集编年评注》,与过去二位先生出版的《朱熹集》相比,把朱熹撰写的每一篇诗文,包括文章、书信、诗词等,都作了考订,标出其撰写的年代,有的详细到某月,或某季,如春、夏、秋、冬、年末等。这对于掌握朱熹思想前后发生的演变、转化很有帮助。即朱熹的思想体现在某一篇诗文书信里,其写作于什么年代?后来这一思想又发生了什么变化,通过查找原文及写作的年代,便可清楚地掌握。如朱熹的关于察识与涵养的关系的思想,察识与涵养谁先谁后,怎么理解,后来形成的定论是什么?确切了解了写作于哪一年,就可掌握朱熹思想形成、变化,到最后定论的情况,就有了可靠的原本材料作依据。
对此,我通过查阅该书——《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对照以前的研究成果,可进一步推进朱熹研究的深入开展。比如对朱熹与张栻“中和之辩”(被学者称为“南宋哲学史上最精彩的场面”①)的重大理论问题——察识与涵养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朱熹和张栻围绕着中和的察识与涵养问题展开的辩论,开始张栻以先察识后涵养的观点影响了朱熹,朱熹接受了张拭的观点,也持先察识后涵养之说。不久,朱熹悟前说之非,而主先涵养后察识的观点,指出张栻的观点缺少前面涵养一截工夫。张栻经朱熹批评,认识到自己存养处不深厚的毛病,在与吕祖谦等人的讨论中,提出涵养、省察相兼并进,以涵养为本的思想,但没有接受朱熹先涵养后省察的观点。后来朱熹亦由先涵养后察识,而主涵养与察识交相助的观点,这就与张栻涵养、省察相兼并进的思想基本一致了。朱熹说:“未发已发,只是一件工夫。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耳。……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②其“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便是指无论何时,都既要涵养,又要省察,打破了涵养与察识的先后之分,而与张栻的观点比较接近。以上便是朱熹与张栻讨论中和之察识、涵养问题的始末。③
虽然这个认识有材料的根据,但对于朱熹思想具体是怎么转变的,何时转变?则没有具体时间点。现根据该著《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再查朱熹的原文,则可依据此文写作时间的考订,来判断朱熹、张栻二人思想发生变化,尤其是朱熹思想最后形成定论的情况。
朱熹在他的《已发未发说》一文里说道:“向来讲论思索,直以心为已发,而所论致知格物亦以察识端倪为初下手处,以故缺却平日涵养一段功夫。”①在这里朱熹提到,自己以往持先察识后涵养的观点。但不知系于何年?通过查阅《朱熹文集编年评注》,上面标明是“乾道五年(1169)”。可知朱熹在乾道五年时检讨自己先察识后涵养观点的偏差。说明朱熹先察识后涵养的思想在乾道五年以前就产生了。只不过后来通过与张栻辩论、与学者交流,改变了前说,而主察识与涵养不分先后,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交相助,不相对,这在《朱子语类》卷六十二里有记载。但在《朱子语类》里,看不到具体时间,这对掌握思想的变化不太有利。即以往的研究虽然可知朱熹后来的思想转到了“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察识与涵养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交相助”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对立的“交相待”的关系这个认识上。但出自于《朱子语类》这些文字材料,并不知道作于何时。经查《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可以查到类似的文字:
穷理涵养要当并进,盖非稍有所知,无以致涵养之功;非深有所存,无以尽义理之奥。正当交相为用,而各致其功耳。②
朱熹主张将穷理与涵养相互促进,“交相为用”,而“各致其功”。穷理与察识,是相互联系的。查此文作于乾道九年(1173),表明经学术交流,朱熹已改变乾道五年以前形成的先察识后涵养的观点,而主穷理与涵养交相为用。此处的穷理,即指要“有所知”,通过察识来“致涵养之功”,又以存养即涵养来认识义理即掌握天理。朱熹说:“日用功夫,比复何如?文字虽不可废,然涵养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动静之间不可顷刻间断底事。若于此处见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权谋里去矣。”③经查《朱熹文集编年评注》,此文作于淳熙十二年(1185),可见朱熹是把涵养本原与察识天理人欲之分别视为一体,可证朱熹所说“穷理涵养要当并进”,即是把察识与涵养视为一体,交相为用,又各致其功。认为这是不可分割的,要贯彻到日用之间而不可有顷刻分离。说明经朱熹与张栻的中和之辩,由分别察识与涵养、未发与已发及其先后,到后来主张二者相兼并进,不分先后。这个时间与思想的转变很重要。查这两文的写作时间,亦可补充《朱子语类》对此的记载缺乏时间之不足。
后来朱熹对此问题有明确的说法:“究观圣门教学,循循有序,无有合下先求顿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渐久渐熟,自然贯通,即自有安稳受用处耳。”④在这里,朱熹批评顿悟,主张将持守与省察结合起来,久而久之,则自然贯通,以求正道。此处持守,指保持坚守正道,类似于通过涵养功夫来守候、护持圣人之道。亦是表达了涵养、存养之意。经查《朱熹文集编年评注》,该文写作年代是在绍熙二年(1191)以后,应该是比较接近朱熹晚年的定论了。
除对朱熹察识与涵养关系的思想转变与朱熹文集写作年代的考察外,如果增加关于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所列朱熹书信的写作年代的考察,便可进一步辨清朱熹思想的倾向以及与心学及其治学方法一定程度的相融,并不是完全扦格不入。
王阳明(1472—1529)于正德三年(1508)三十七岁龙场之悟后,思想由朱学转向了心学。为了减轻传统的压力,他写作了《朱子晚年定论》(以下简称《定论》),表明自己虽与朱子有“相抵牾”的部分,但这部分正是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与朱子“晚岁”所“悔悟”而转向心学相同。即阳明“龙场之悟”虽然与朱子“中年”相“异”,却与其“晚岁”相同。
从文本形式上看,《定论》是阳明从朱熹《文集》中节录朱熹与人论学书三十四通。《定论》始出即引起众议,其是非得失莫衷一是,正如陈荣捷所言,“此论出后,即引起强烈反动,弄成一巨大风波,鼓动一百五十年,为我国思想一大公案”①,可见在当时产生的广泛影响。现代学者亦以各异的切入点作出评议。总的来说,《定论》最受诟病之处在于其“年岁颠倒”与“朱陆异同”争论。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朱熹文集编年评注》,把《定论》所采朱熹与人论学书,一一核查其“年岁”,以此来客观评价朱熹与人论学的思想倾向,以及《定论》的地位和价值。
1.《答黄直卿》(“为学直是先要立本”)在绍熙二年②(1191),朱熹六十二岁。2.《答吕子约》(“日用工夫”)在淳熙十二年③(1185),朱熹五十六岁。3.《答何叔京》(“前此僭易拜禀博观之敝”)在乾道四年④(1168),朱熹三十九岁。4.《答潘叔昌》(“示喻天上无不识字底神仙”)在淳熙十一年⑤(1184),朱熹五十五岁。5.《答潘叔度》(“熹衰病”)在淳熙末⑥,朱熹约六十岁。6.《与吕子约》(“孟子言学问之道”)在淳熙十二年⑦(1185),朱熹五十六岁。7.《与周叔谨》(“应之甚恨”)在淳熙十二年⑧(1185),朱熹五十六岁。8.《答陆子静》(“熹衰病日侵”)在淳熙十三年⑨(1186),朱熹五十七岁。9.《答符复仲》(“闻向道之意”)为淳熙十年(1183)以后⑩,即朱熹五十四岁之后所作。10.《答吕子约》(“日用功夫不敢”)在淳熙十三年①(1186),朱熹五十七岁。11.《与吴茂实》(“近来自觉向时”)在淳熙七年②(1180),朱熹五十一岁。12.《答张敬夫》(“熹穷居如昨”)在淳熙二年③(1175),朱熹四十六岁。13.《答吕伯恭》(“道间与季通讲论”)在淳熙三年④(1176),朱熹四十七岁。14.《答周纯仁》(“闲中无事”)在庆元四年⑤(1198),朱熹六十九岁。15.《答窦文卿》(“为学之要”)在淳熙十三年(1186)以后⑥,即朱熹五十七岁之后。16.《答吕子约》(“闻欲与二友俱来”)在淳熙十三年⑦(1186),朱熹五十七岁。17.《答林择之》(“熹哀苦之余”)在乾道六年⑧(1170),朱熹四十一岁。18.《答林择之》(“此中见有朋友”)在淳熙七年⑨(1180),朱熹五十一岁。19.《答梁文叔》(“近看孟子”)疑在淳熙十一年(1184)前后⑩,朱熹五十五岁前后。20.《答潘恭叔》(“学问根本”)在淳熙十三年⑪(1186),朱熹五十七岁。21.《答林充之》(“充之近读何书”)当在乾道中⑩,即朱熹四十岁左右。22.《答何叔京》(“李先生教人”)在乾道二年⑬(1166),朱熹三十七岁。23.《答何叔京》(“熹近来尤觉昏愦”)在乾道三年⑭(1167),朱熹三十八岁。24.《答何叔京》(“向来妄论持敬之说”)在乾道三年⑮(1167),朱熹三十八岁。25.《答林择之》(“所论颜孟不同”)在乾道五年⑯(1169),朱熹四十岁。26.《答杨子直》(“学者堕在语言”)作于绍熙二年(1191)以后⑩,即朱熹六十二岁以后。27.《与田侍郎子真》(“吾辈今日”)在庆元元年⑱(1195),朱熹六十六岁。28.《答陈才卿》(“详来示”)在庆元元年⑲(1195),朱熹六十六岁。29.《与刘子澄》(“居官无修业之益”)在淳熙十三年⑳(1186),朱熹五十七岁。30.《与林择之》(“某近觉向来”)在乾道六年①(1170),朱熹四十一岁。31.《答吕子约》,此处包括两封《答吕子约》书——“示喻日用工夫”与“诲喻‘工夫且要得见’”,王阳明将两书合在一起,都是在庆元元年②(1195),朱熹六十六岁。32.《答吴德夫》(“承喻仁字之说”)且置淳熙中③,朱熹五十岁左右。33.《答或人》④(“中和二字”)在乾道五年⑤(1169),朱熹四十岁。34.《答刘子澄》(“日前为学”)在淳熙十年⑥(1183),朱熹五十四岁。
以上是朱熹三十四封书信较为具体的时间。如果按照李绂对朱熹年岁早、中、晚的划分,即“朱子得年七十一岁,定以三十岁以前为早年,以三十一至五十岁为中年,以五十一岁至七十一岁为晚年”⑦,在朱熹五十一岁到七十一岁之间就占有二十二封,在三十多岁到五十岁则有十二封,阳明所谓“多出于晚年者”是比较明显的,这或许是阳明《定论》问世之后获得始料不及的效果的原因。如钱德洪称:“自是为朱子论异同者寡矣。师曰:‘无意中得此一助!’”⑧袁庆麟跋曰:“及读是编,始释然……若夫直求本原于言语之外,真有以验其必然而无疑者,则存乎其人之自力,是编特为之指迷耳。”⑨钱、袁氏均对《定论》持正面的肯定意见,认为《定论》自有其启迪为学者之益处,如从钱德洪所记阳明之语——“无意中得此一助”可知,如若无人畅和,阳明何有此叹?
虽然在王阳明所引朱熹《朱子晚年定论》的三十四封书信中,晚年占到二十二封,中早年有十二封,但毕竟不都是晚年所作,在年岁上有失误之处。所以王阳明亦说:“某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⑩王阳明《定论》即使有“年岁早晚”考证之缺憾,但在另一方面,从王阳明以收敛身心、反己立本、向内用功的角度来采摘朱熹书信,无疑发掘了一个新的审视朱熹学说的理论切入点,这也无怪乎阳明能得到后儒的支持和赞同,而体现了学术发展由朱学到心学的趋向,以及《定论》的地位和价值。
王阳明所列举的朱熹之书信不论其是否作于朱熹晚年,然其中确实包括了朱熹本人对自己存在着的更多重视读书求义理、而不太重视反求诸心的前说的检讨。王阳明客观地看到了朱熹对自己前说的反省,亦表现出某种重视内在的治心之学的工夫。即在某种程度上朱熹对自己以往泥守书册、支离无纪的治学倾向加以反省,以做到收敛身心,反己立本。只不过阳明看到的朱熹一定程度上重视收敛身心,是否就是类似于陆九渊的心本论之心学?重视心,以己意说经,是否就是以心为本的心学?当然也受到陆九渊简易工夫治学方法的影响。所以不能因为王阳明所列举的朱熹书信有的不是晚年所作,就否定朱熹思想中确实存在着由读书穷理向重视内在反求诸己,并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倾向。即把博与约、泛观博览与反己立本相结合。
值得思考的是,根据《朱熹文集编年评注》能够确定下来的朱熹不仅在晚年,而且在中早年也有倾向于心学方法论的地方,而检讨了自己在收敛身心、反己立本方面存在着不足的问题。这说明了朱熹的什么思想?尽管它与陆王的心本论宇宙观有别,但毕竟检讨了自己思想于尊德性上的不足,而主张将道问学与尊德性结合起来。这对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王阳明在朱熹这种倾向(自我检讨)的基础上,发展出心学来,进一步纠正朱熹已发现了的自己学说的偏向。这也是学术发展倾向的一个表现。
通过《朱熹文集编年评注》来查阅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中朱熹文章的写作年代及所体现的思想倾向,可以看出,朱熹已认识到了自己思想上存在着的相对忽视内在的尊德性,而偏重于外在的道问学的偏差,而且有的还是在中青年时,朱熹就已经通过写书信来修正自己的观点。就此而言,朱熹思想中亦存在着某种倾向于心学之处。这些都是通过考订朱熹文章写作于哪一年,才能得出的结论。由此可见《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对朱熹文集编年的重要性,其编年与学术具有密切的联系。
(原载《中国文化》2020年第2期,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全十三册),朱熹著,郭齐、尹波编注,福建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版。
朱熹文集是研究朱熹思想及其学术活动的主要材料。《朱熹文集编年评注》的二位作者以往就整理出版了《朱熹集》(全十册,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该书对传世的朱熹文集重要版本逐一进行了通校,尤其注重宋元版(包括海内外罕见孤本、珍本)的比勘,广泛吸取历代校勘成果,使之成为精校本。是当年出版时最为完备的版本,为学术界的朱熹研究和理学与中国文化研究作出重要贡献。1997年获第八次四川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除整理出版《朱熹集》外,二位作者还是国内研究朱熹的著名专家,长期从事朱熹研究,出版了诸如《朱熹新考》(郭齐著,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朱熹诗词编年笺注》(上、下册,朱熹著,郭齐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朱熹传》(郭齐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朱子学新探》(郭齐著,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发表了诸如《宋刊闽浙二本<朱熹文集>关系考论》(郭齐、尹波,《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04)、《<朱熹文集>版本源流考》(尹波、郭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03)、《新发现朱熹书信发覆》(尹波、郭齐,《文学遗产》2019-03)等一系列重要成果。
在长期研究和整理工作的基础上,二位作者校勘辑佚,对朱熹文集中的每篇诗文,考订撰作年月,添加解题、注释,整理历代评论,并附有版本考略、传记数据、文集序跋、篇名索引、朱熹年表、历代评论、伪托误题朱熹诗文存目等参考数据,是为朱熹文集的首个深度整理本。首次对全部诗文逐篇系年。《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全面、深入的解析,详细的编年,对于推动朱熹研究,乃至于宋代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深入与拓展,扩大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比以往出版的朱熹文集有明显的优势。
读罢该书,可知《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在古籍整理研究上,做了以下重要工作:
1.校勘
校勘现存重要文集版本二十余种。其中,海内孤本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宋淳熙、绍熙年间所刊《晦庵先生文集》前、后集系首次进行通校,增补文四篇,增补内容数千字,纠正今本文集若干错误,提供了《明筮占》《皇极辨》《云谷记》《少傅刘公神道碑》等众多异文;首次对现存宋刊闽、浙两大系统二十余种文集残本作了全面校勘;首次对元刻本《朱文公大同集》作了深入研究,成果发表在(日本)《东方学报》第91期、《文学遗产》2017年第3期,并采校记六十余条,移正错简数处(如卷六十六《蓍卦考误》等)。全书凡出校勘记七千余条。
2.辑佚
新发现佚文十余篇,经初步研究,已作为阶段性成果发表于《历史文献研究》2018年第40辑、《光明日报》2018年4月14日、《文学遗产》2019年第3期、(日本)《儒教学会报》2020年第4号等刊物。
3.辨伪
先后于《宋史研究论丛》第25辑等刊物发表了《朱熹两件手书作品真伪考辨》(2019)、《朱熹佚作疑伪考(一)》(2017)、《朱熹佚诗文三篇考论》(2017)、《朱熹佚作疑伪考(二)》(2018)、《朱熹佚文与子澄寺薄书、建昌帖考辨》(2018)、《朱熹佚作疑伪考(三)》(2019)、《朱熹谱序五篇辨伪》(2019)等文。该书附录《伪托误题朱熹诗文存目》,集八百余年朱文辨伪之大成,为史上首个朱熹佚文伪托误题目录。
4.注释
对全部诗词逐篇作了解题和笺注。解题提供有关背景材料,从总体上概括全篇意旨及疏释篇题中有碍理解的词语。笺注重在疏通文意,帮助读者达到对作品的正确理解。全书总计注释五千三百余条,朱熹文集之有注释,在史上尚不多见。
5.编年
首次对全部诗文逐篇系年。二位作者根据自己长期的研究整理,新考定年及纠正、补充前人结论,重要者凡二百余条,一般性更正不在此数。
6.评论
在曾枣庄主编《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朱熹部分基础上,进行了相关的搜寻补充,首次将历代学者关于朱熹诗文的研究评论数据附于集中,总计一千三百余条。其中,有关某篇诗文的评论附于该篇之后,关于诗文的总体评论附于全书之后。
7.附录
包括:(1)传记数据;(2)文集序跋;(3)版本考略;(4)朱熹年表;(5)历代评论;(6)伪托误题朱熹诗文存目;(7)主要参考文献;(8)本书篇名索引。其中文集序跋特别注意收录海外所藏、所刻朱熹文集之序跋,为目前所收海外序跋最多之本。朱熹年表、历代评论、伪托误题朱熹诗文存目、主要参考文献系首次附入。
由于做了以上七条卓有成效的整理研究工作,从而形成了该书以下的突出特点:
1.补足全文:《朱子全书》第26册P630据《池北偶谈》卷9录《与某人帖》残文,其云:“十年前,率尔记张魏公行状,当时只是据渠家文字做成,后见它书所记不同,尝以为恨。”而在清李佐贤《书画鉴影》卷三(同治十年利津李氏刻本)有此全文。文前题“朱文公手札卷,纸本,高一尺四寸七分,长七尺四寸,凡三纸,计三札,字经(按:疑当作“径”)一寸内外。”此书题为“第一札”。文后题“草书,十八行。札前白文安德口口世家刀印,又一印不辨。札后白文吴越忠孝之家方印,君载方印。”文云:
熹伏蒙别纸督过,伏读震悚。顾实病衰,不堪思虑。若所记者一身一家一官之事,则犹可以勉强。至如元臣故老,动关国政,则首尾长阔,曲折精微,实非病余昏昧之人所能熟考传载。此熹所以不得词于潘、李诸丈之文,而于先正铭识之属则有取(按:疑当作“所”)不敢当也。卅年前,率尔记张魏公行事,当时只据渠家文字草成,后见它书所记多或未同,常以为愧。故于赵忠简家文字初已许之,而后亦不敢承当,已恳其改属陈太史矣,不知今竟如何也。况今词官万一不遂,则又将有王事之劳,比之家居,见扰弥甚。切望矜闵,贷此余生,毋劳竭其精神,以速就于溘然之地,则千万之幸也。若无性命之忧,则岂敢有所爱于先世恩契之门如此哉。俯伏布恳,惶恐之剧!右谨具呈。朝散郎、秘阁修撰朱熹札子。
2.删除衍文:《朱子全书》第26册P617据《朱子大同集》录《答许平仲》文:“仁人之心,未尝忘天下之忧,故如此也。漳、泉、汀三州经界未行,许公条究甚悉,监司郡守未有举行者。”“漳、泉、汀三州”以下明显为后来者所加衍文,故予删除也。
3.剔除误收:朱熹佚文有诸多伪作误题,如不仔细考证,必然误收不断。如《朱熹集》P5619、《朱子全书》第26册P612据宋人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所收《上殿札子》,乃馆阁上奏之文;《朱熹集》P5699、《朱子全书》第26册P809据《翰墨大全》所收《祭李三溪文》、P810《祭胡古潭文》,此二人乃宋末元初人,焉能为朱熹所祭?
4.移正错简:《朱熹集》卷66P3490“过揲二十八策”至“挂扐三十五策”原错简在“又曰苏氏所载一行之学”前,据宋浙本、《文公易说》移正至“尤不可以不辨”后。《朱子全书》23册已经移正,但P3252校记云“据淳熙本”移正。淳熙本根本没有此文,故误也。
5.校改误字:如《朱熹集》卷86P4445、《朱子全书》第24册P4050《修三闾忠节侯庙奉安祝文》“敢馔灵神,敢陈椒醑”,不仅二“敢”字彼此重复,“神”字与上文二“神”字重复,且文意几乎不通,显然失校。此据《永乐大典》卷五千七百六十九改“馔”“神”为“择”“辰”,改后“敢”字为“敬”字,则文从字顺矣。
6.考订月曰:《朱熹集》卷86P4445、《朱子全书》第24册P4049《谒修道州三先生祠文》首句“维绍熙五年岁次甲寅八月日”,其“日”字,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8作“己丑朔二下缺八日丙辰”,八月己丑朔,二十八日正是丙辰,故据以补正为二十八日丙辰。又上述1补足全文据残文“十年前”系之于淳熙三年,而据《书画鉴影》所载全文“卅年前”句,考订其作年当在绍熙五年正月。
7.订正序跋作者:《朱子全书》第27册P781有《朱子文语纂编目录后跋》,其作者署邵车,而据其跋末,明确云楚邵车鼎丰书。理解之误也。
8.增补佚文,补充事迹:朱熹佚文甚伙,但凡细细考订,定能有所收获。除第1条外,还有从《翰墨全书》首次发现的《与五六弟》三封,《与三六弟》一封,其详细论证,已刊于《文学遗产》2019年3期《新发现朱熹书信发覆》。不仅辑出了佚文,还首次考订出了朱熹祖墓纷争还有第二次,其时间在朱熹淳熙七年知南康军时。又如《答石天民书》,乃出自于乾隆间《南明石氏宗谱》,已考订出淳熙十四年作;《简十四表叔》九封,出自于《娶源韩溪程氏梅山支谱》,俱绍兴、隆兴间作,等等。
9.纠正它误:朱熹文集卷二有《次晦叔寄弟韵二首》,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卷上P516系于淳熙元年与吴翌,非也。其实乃朱熹淳熙十年与王炎,盖因吴翌、王炎二人都字晦叔,朱熹与吴翌屡有通问,而王炎则仅此一见,故历来都归于朱熹与吴翌诗。王炎《双溪文集》(清抄本)卷七《寄德莹弟二首》附录此诗,注云:朱晦庵和韵二首。是证也。
此外,朱熹与诸人有书信多封,原书或仅置于一题之下。此次编年,以年代为题,以示区分。此亦特色之一。
以上该书的这些突出的学术特色,值得充分肯定。
二
由于笔者长期从事朱熹研究,出版了《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朱熹与中国文化》《朱熹思想探讨》等多部朱熹研究的专著,发表了七十余篇朱熹研究的论文,从自身从事的研究工作来考虑,相比较朱熹文集整理研究工作的各个方面,我更关心《朱熹文集编年评注》中所涉及的对朱熹每一篇诗文的编年,因为这对于研究掌握朱熹学术思想前后发生的变化,进而动态地把握朱熹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其最后的定论,意义重大。
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研究朱熹。研究之初,苦于没有朱熹的著作,后来我认识了四川广汉师范学校的历史老师刘雨涛先生(毕业于“中央大学”哲学系),他保存有一套四部备要本的《朱文公文集》,线装书,排印本,三十六册。我从他家借出阅读,但时间还不能长了,因为刘先生他也要看。我只得看一段时间后,还给刘雨涛老师。过一段时间再到广汉他家里借出来带到成都再看。后来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了《朱子语类》,可以部分解决阅读朱熹资料的问题。但《朱文公文集》还是只能断断续续地看。直到郭齐、尹波二先生整理点校的《朱熹集》于1996年在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后,才解决了阅读朱熹文集的难题。
此次出版的《朱熹文集编年评注》,与过去二位先生出版的《朱熹集》相比,把朱熹撰写的每一篇诗文,包括文章、书信、诗词等,都作了考订,标出其撰写的年代,有的详细到某月,或某季,如春、夏、秋、冬、年末等。这对于掌握朱熹思想前后发生的演变、转化很有帮助。即朱熹的思想体现在某一篇诗文书信里,其写作于什么年代?后来这一思想又发生了什么变化,通过查找原文及写作的年代,便可清楚地掌握。如朱熹的关于察识与涵养的关系的思想,察识与涵养谁先谁后,怎么理解,后来形成的定论是什么?确切了解了写作于哪一年,就可掌握朱熹思想形成、变化,到最后定论的情况,就有了可靠的原本材料作依据。
对此,我通过查阅该书——《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对照以前的研究成果,可进一步推进朱熹研究的深入开展。比如对朱熹与张栻“中和之辩”(被学者称为“南宋哲学史上最精彩的场面”①)的重大理论问题——察识与涵养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朱熹和张栻围绕着中和的察识与涵养问题展开的辩论,开始张栻以先察识后涵养的观点影响了朱熹,朱熹接受了张拭的观点,也持先察识后涵养之说。不久,朱熹悟前说之非,而主先涵养后察识的观点,指出张栻的观点缺少前面涵养一截工夫。张栻经朱熹批评,认识到自己存养处不深厚的毛病,在与吕祖谦等人的讨论中,提出涵养、省察相兼并进,以涵养为本的思想,但没有接受朱熹先涵养后省察的观点。后来朱熹亦由先涵养后察识,而主涵养与察识交相助的观点,这就与张栻涵养、省察相兼并进的思想基本一致了。朱熹说:“未发已发,只是一件工夫。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耳。……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交相待。”②其“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便是指无论何时,都既要涵养,又要省察,打破了涵养与察识的先后之分,而与张栻的观点比较接近。以上便是朱熹与张栻讨论中和之察识、涵养问题的始末。③
虽然这个认识有材料的根据,但对于朱熹思想具体是怎么转变的,何时转变?则没有具体时间点。现根据该著《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再查朱熹的原文,则可依据此文写作时间的考订,来判断朱熹、张栻二人思想发生变化,尤其是朱熹思想最后形成定论的情况。
朱熹在他的《已发未发说》一文里说道:“向来讲论思索,直以心为已发,而所论致知格物亦以察识端倪为初下手处,以故缺却平日涵养一段功夫。”①在这里朱熹提到,自己以往持先察识后涵养的观点。但不知系于何年?通过查阅《朱熹文集编年评注》,上面标明是“乾道五年(1169)”。可知朱熹在乾道五年时检讨自己先察识后涵养观点的偏差。说明朱熹先察识后涵养的思想在乾道五年以前就产生了。只不过后来通过与张栻辩论、与学者交流,改变了前说,而主察识与涵养不分先后,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交相助,不相对,这在《朱子语类》卷六十二里有记载。但在《朱子语类》里,看不到具体时间,这对掌握思想的变化不太有利。即以往的研究虽然可知朱熹后来的思想转到了“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察识与涵养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交相助”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对立的“交相待”的关系这个认识上。但出自于《朱子语类》这些文字材料,并不知道作于何时。经查《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可以查到类似的文字:
穷理涵养要当并进,盖非稍有所知,无以致涵养之功;非深有所存,无以尽义理之奥。正当交相为用,而各致其功耳。②
朱熹主张将穷理与涵养相互促进,“交相为用”,而“各致其功”。穷理与察识,是相互联系的。查此文作于乾道九年(1173),表明经学术交流,朱熹已改变乾道五年以前形成的先察识后涵养的观点,而主穷理与涵养交相为用。此处的穷理,即指要“有所知”,通过察识来“致涵养之功”,又以存养即涵养来认识义理即掌握天理。朱熹说:“日用功夫,比复何如?文字虽不可废,然涵养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动静之间不可顷刻间断底事。若于此处见得分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权谋里去矣。”③经查《朱熹文集编年评注》,此文作于淳熙十二年(1185),可见朱熹是把涵养本原与察识天理人欲之分别视为一体,可证朱熹所说“穷理涵养要当并进”,即是把察识与涵养视为一体,交相为用,又各致其功。认为这是不可分割的,要贯彻到日用之间而不可有顷刻分离。说明经朱熹与张栻的中和之辩,由分别察识与涵养、未发与已发及其先后,到后来主张二者相兼并进,不分先后。这个时间与思想的转变很重要。查这两文的写作时间,亦可补充《朱子语类》对此的记载缺乏时间之不足。
后来朱熹对此问题有明确的说法:“究观圣门教学,循循有序,无有合下先求顿悟之理。但要持守、省察,渐久渐熟,自然贯通,即自有安稳受用处耳。”④在这里,朱熹批评顿悟,主张将持守与省察结合起来,久而久之,则自然贯通,以求正道。此处持守,指保持坚守正道,类似于通过涵养功夫来守候、护持圣人之道。亦是表达了涵养、存养之意。经查《朱熹文集编年评注》,该文写作年代是在绍熙二年(1191)以后,应该是比较接近朱熹晚年的定论了。
除对朱熹察识与涵养关系的思想转变与朱熹文集写作年代的考察外,如果增加关于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所列朱熹书信的写作年代的考察,便可进一步辨清朱熹思想的倾向以及与心学及其治学方法一定程度的相融,并不是完全扦格不入。
王阳明(1472—1529)于正德三年(1508)三十七岁龙场之悟后,思想由朱学转向了心学。为了减轻传统的压力,他写作了《朱子晚年定论》(以下简称《定论》),表明自己虽与朱子有“相抵牾”的部分,但这部分正是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与朱子“晚岁”所“悔悟”而转向心学相同。即阳明“龙场之悟”虽然与朱子“中年”相“异”,却与其“晚岁”相同。
从文本形式上看,《定论》是阳明从朱熹《文集》中节录朱熹与人论学书三十四通。《定论》始出即引起众议,其是非得失莫衷一是,正如陈荣捷所言,“此论出后,即引起强烈反动,弄成一巨大风波,鼓动一百五十年,为我国思想一大公案”①,可见在当时产生的广泛影响。现代学者亦以各异的切入点作出评议。总的来说,《定论》最受诟病之处在于其“年岁颠倒”与“朱陆异同”争论。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朱熹文集编年评注》,把《定论》所采朱熹与人论学书,一一核查其“年岁”,以此来客观评价朱熹与人论学的思想倾向,以及《定论》的地位和价值。
1.《答黄直卿》(“为学直是先要立本”)在绍熙二年②(1191),朱熹六十二岁。2.《答吕子约》(“日用工夫”)在淳熙十二年③(1185),朱熹五十六岁。3.《答何叔京》(“前此僭易拜禀博观之敝”)在乾道四年④(1168),朱熹三十九岁。4.《答潘叔昌》(“示喻天上无不识字底神仙”)在淳熙十一年⑤(1184),朱熹五十五岁。5.《答潘叔度》(“熹衰病”)在淳熙末⑥,朱熹约六十岁。6.《与吕子约》(“孟子言学问之道”)在淳熙十二年⑦(1185),朱熹五十六岁。7.《与周叔谨》(“应之甚恨”)在淳熙十二年⑧(1185),朱熹五十六岁。8.《答陆子静》(“熹衰病日侵”)在淳熙十三年⑨(1186),朱熹五十七岁。9.《答符复仲》(“闻向道之意”)为淳熙十年(1183)以后⑩,即朱熹五十四岁之后所作。10.《答吕子约》(“日用功夫不敢”)在淳熙十三年①(1186),朱熹五十七岁。11.《与吴茂实》(“近来自觉向时”)在淳熙七年②(1180),朱熹五十一岁。12.《答张敬夫》(“熹穷居如昨”)在淳熙二年③(1175),朱熹四十六岁。13.《答吕伯恭》(“道间与季通讲论”)在淳熙三年④(1176),朱熹四十七岁。14.《答周纯仁》(“闲中无事”)在庆元四年⑤(1198),朱熹六十九岁。15.《答窦文卿》(“为学之要”)在淳熙十三年(1186)以后⑥,即朱熹五十七岁之后。16.《答吕子约》(“闻欲与二友俱来”)在淳熙十三年⑦(1186),朱熹五十七岁。17.《答林择之》(“熹哀苦之余”)在乾道六年⑧(1170),朱熹四十一岁。18.《答林择之》(“此中见有朋友”)在淳熙七年⑨(1180),朱熹五十一岁。19.《答梁文叔》(“近看孟子”)疑在淳熙十一年(1184)前后⑩,朱熹五十五岁前后。20.《答潘恭叔》(“学问根本”)在淳熙十三年⑪(1186),朱熹五十七岁。21.《答林充之》(“充之近读何书”)当在乾道中⑩,即朱熹四十岁左右。22.《答何叔京》(“李先生教人”)在乾道二年⑬(1166),朱熹三十七岁。23.《答何叔京》(“熹近来尤觉昏愦”)在乾道三年⑭(1167),朱熹三十八岁。24.《答何叔京》(“向来妄论持敬之说”)在乾道三年⑮(1167),朱熹三十八岁。25.《答林择之》(“所论颜孟不同”)在乾道五年⑯(1169),朱熹四十岁。26.《答杨子直》(“学者堕在语言”)作于绍熙二年(1191)以后⑩,即朱熹六十二岁以后。27.《与田侍郎子真》(“吾辈今日”)在庆元元年⑱(1195),朱熹六十六岁。28.《答陈才卿》(“详来示”)在庆元元年⑲(1195),朱熹六十六岁。29.《与刘子澄》(“居官无修业之益”)在淳熙十三年⑳(1186),朱熹五十七岁。30.《与林择之》(“某近觉向来”)在乾道六年①(1170),朱熹四十一岁。31.《答吕子约》,此处包括两封《答吕子约》书——“示喻日用工夫”与“诲喻‘工夫且要得见’”,王阳明将两书合在一起,都是在庆元元年②(1195),朱熹六十六岁。32.《答吴德夫》(“承喻仁字之说”)且置淳熙中③,朱熹五十岁左右。33.《答或人》④(“中和二字”)在乾道五年⑤(1169),朱熹四十岁。34.《答刘子澄》(“日前为学”)在淳熙十年⑥(1183),朱熹五十四岁。
以上是朱熹三十四封书信较为具体的时间。如果按照李绂对朱熹年岁早、中、晚的划分,即“朱子得年七十一岁,定以三十岁以前为早年,以三十一至五十岁为中年,以五十一岁至七十一岁为晚年”⑦,在朱熹五十一岁到七十一岁之间就占有二十二封,在三十多岁到五十岁则有十二封,阳明所谓“多出于晚年者”是比较明显的,这或许是阳明《定论》问世之后获得始料不及的效果的原因。如钱德洪称:“自是为朱子论异同者寡矣。师曰:‘无意中得此一助!’”⑧袁庆麟跋曰:“及读是编,始释然……若夫直求本原于言语之外,真有以验其必然而无疑者,则存乎其人之自力,是编特为之指迷耳。”⑨钱、袁氏均对《定论》持正面的肯定意见,认为《定论》自有其启迪为学者之益处,如从钱德洪所记阳明之语——“无意中得此一助”可知,如若无人畅和,阳明何有此叹?
虽然在王阳明所引朱熹《朱子晚年定论》的三十四封书信中,晚年占到二十二封,中早年有十二封,但毕竟不都是晚年所作,在年岁上有失误之处。所以王阳明亦说:“某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⑩王阳明《定论》即使有“年岁早晚”考证之缺憾,但在另一方面,从王阳明以收敛身心、反己立本、向内用功的角度来采摘朱熹书信,无疑发掘了一个新的审视朱熹学说的理论切入点,这也无怪乎阳明能得到后儒的支持和赞同,而体现了学术发展由朱学到心学的趋向,以及《定论》的地位和价值。
王阳明所列举的朱熹之书信不论其是否作于朱熹晚年,然其中确实包括了朱熹本人对自己存在着的更多重视读书求义理、而不太重视反求诸心的前说的检讨。王阳明客观地看到了朱熹对自己前说的反省,亦表现出某种重视内在的治心之学的工夫。即在某种程度上朱熹对自己以往泥守书册、支离无纪的治学倾向加以反省,以做到收敛身心,反己立本。只不过阳明看到的朱熹一定程度上重视收敛身心,是否就是类似于陆九渊的心本论之心学?重视心,以己意说经,是否就是以心为本的心学?当然也受到陆九渊简易工夫治学方法的影响。所以不能因为王阳明所列举的朱熹书信有的不是晚年所作,就否定朱熹思想中确实存在着由读书穷理向重视内在反求诸己,并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的倾向。即把博与约、泛观博览与反己立本相结合。
值得思考的是,根据《朱熹文集编年评注》能够确定下来的朱熹不仅在晚年,而且在中早年也有倾向于心学方法论的地方,而检讨了自己在收敛身心、反己立本方面存在着不足的问题。这说明了朱熹的什么思想?尽管它与陆王的心本论宇宙观有别,但毕竟检讨了自己思想于尊德性上的不足,而主张将道问学与尊德性结合起来。这对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王阳明在朱熹这种倾向(自我检讨)的基础上,发展出心学来,进一步纠正朱熹已发现了的自己学说的偏向。这也是学术发展倾向的一个表现。
通过《朱熹文集编年评注》来查阅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中朱熹文章的写作年代及所体现的思想倾向,可以看出,朱熹已认识到了自己思想上存在着的相对忽视内在的尊德性,而偏重于外在的道问学的偏差,而且有的还是在中青年时,朱熹就已经通过写书信来修正自己的观点。就此而言,朱熹思想中亦存在着某种倾向于心学之处。这些都是通过考订朱熹文章写作于哪一年,才能得出的结论。由此可见《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对朱熹文集编年的重要性,其编年与学术具有密切的联系。
(原载《中国文化》2020年第2期,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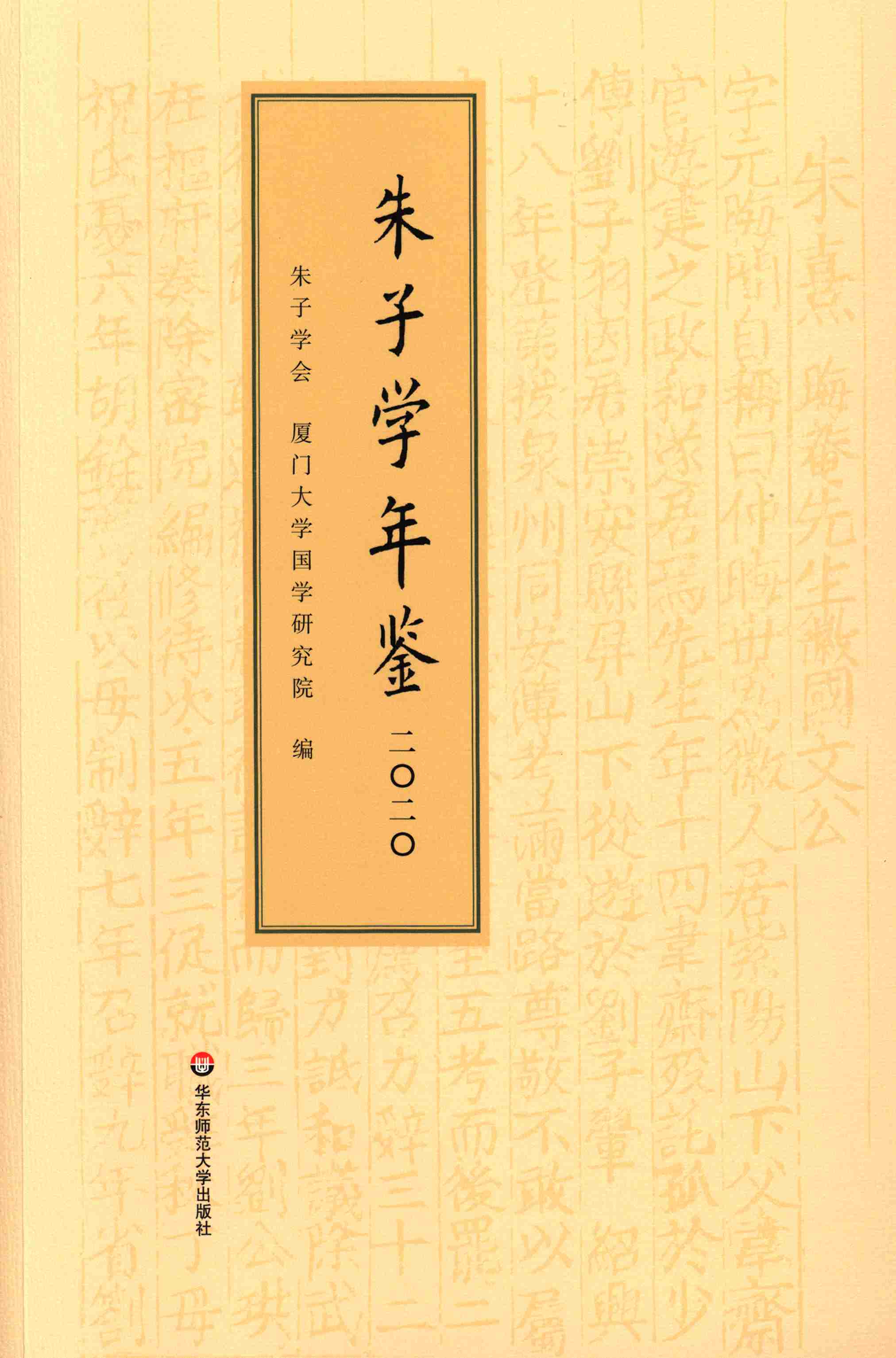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20》
出版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以礼释仁的路径和意义》《2020年度欧洲朱子学研究综述》《全球化时代与朱子学研究》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蔡方鹿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