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闽中理学及其理论特征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与地域文化研究》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2763 |
| 颗粒名称: | 早期闽中理学及其理论特征 |
| 分类号: | B244.75;G127 |
| 页数: | 14 |
| 页码: | 54-67 |
| 摘要: | 这篇文章主要介绍了早期闽中理学的概念和特征。早期闽中理学是指朱熹闽学产生和形成之前的福建理学,对于后来朱熹闽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和成熟作了理论准备。早期闽中理学形成的三个阶段福建古时称之为闽中,地处祖国东南,远离中原政治与文化中心,一直是文化学问的边缘地带。虽然早期闽中理学与朱熹闽学存在着思想上的渊源关系,但它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历史,独特的学术风格和思想文化特点。由于朱熹闽学在中国哲学史上显赫的地位,而早期闽中理学的存在并没有引起学者足够的注意,因此对早期闽中理学的深入研究可以丰富唐朝中后期至南宋初这段历史时期的中国哲学。 |
| 关键词: | 朱熹 理学 哲学史 |
内容
早期闽中理学指的是朱熹闽学产生和形成之前的福建理学。而闽学是指以朱熹为首包括其门人在内的南宋朱子学派的思想。闽学是指朱子学而言的,它与早期闽中理学之间存在着思想上的渊源关系。早期闽中理学学者对理学思想的传播和阐发,为后来朱熹闽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和成熟作了理论准备。应当指出,从本质上说,早期闽中理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历史,独特的学术风格和思想文化特点。但由于朱熹闽学在中国哲学史上显赫的地位,受到学术思想界的普遍关注,而早期闽中理学的存在并没有引起学者足够的注意。中国哲学史和宋明理学史著作都只论述朱熹的理学思想,而对早期闽中理学很少有涉及。由此,我们对早期闽中理学的深入研究,可以丰富唐朝中后期至南宋初这段历史时期的中国哲学。一早期闽中理学形成的三个阶段福建古时称之为闽中,地处祖国东南,远离中原政治与文化中心,一直是文化学术的蛮荒之地。然而,汉以后,由于中原战乱,大量中州人士入闽,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从而使十分落后的闽中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特别是中唐以降,随着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闽中文化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为早期闽中理学的出现带来了历史机遇。早期闽中理学的形成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重要的阶段。
(一)唐朝中后期早期闽中理学的发端
安史之乱给唐王朝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暴露出盛行一时的佛教和道教的软弱无力。它表明佛道思想并非是封建统治的最合理的统治思想。于是,当时一批封建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在为唐王朝寻求更有力的精神武器时,打出了复兴儒学的旗帜,力图恢复儒家在思想领域中的正统地位。以韩愈为代表的一批卫道者认为,佛教让人们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佛教的教义和它的僧侣实践违背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纲常伦理,因此任其发展就会破坏这个社会的伦理秩序,使社会无法维持。所以,韩愈推出《大学》,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来打击和压制标举出世主义的佛教。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儒学影响,开始了儒学复兴运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早期闽中理学开始萌芽。
与韩愈同登“龙虎榜”(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年)进士的闽中晋江人欧阳詹(字行周),不仅与韩愈情同手足,而且志同道合。他们都以儒家思想为正统,以周公孔子为楷模,差不多同时提出了儒家道统。欧阳詹在闽中写给韩愈的诗中曾公开声明自己与韩愈一样,是“志在周孔堂,道适尧舜门”①。清人李清馥在《闽中理学渊源考》中说:“闽中儒学开先始于唐欧阳四门。”②而与欧阳詹同时的闽中莆田人林蕴(字复梦,唐德宗贞元四年进士)亦与韩愈、欧阳詹一起提倡儒家道统,反对佛教。欧阳詹和林蕴为代表的理学(道学)思想的出现,说明早在唐朝中后期,闽中就有了理学的端倪。值得注意的是,早期闽中理学形成伊始,就代表了传统儒家思想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二)北宋初早期闽中理学的开创
北宋建立之初,统治者推行倚文重儒,崇信佛道的三教兼容并用的方针,使得宋初仍然继续保持着多元文化的格局,这对于巩固当时的封建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新的统一局面的出现和统治方式的实行,佛教、道教与儒学并立所造成的“学术不一”的状况,已很难适应现实的需要。重新建立一种适应于宋朝中央集权统治需要的统一的思想,“一道德”③便成为当务之急。这时,以“庆历新政”为背景的儒学运动,在社会改革家范仲淹的倡导下,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从经济、政治、教育、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掀起了一股改革思潮。作为这一思潮的理论指导而成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则通过全面研究和发挥儒家经典,进而对自然、社会、人生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各自提出了具有理学特色的学说,从而揭开了理学的序幕。北宋初年的这一儒学运动,松动了思想界的重重大山,造成了秦汉以来中国学术史上罕见的活跃气氛。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文化氛围中,早期闽中理学得以酝酿成长起来。入宋以后,随着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进一步南移,闽中与外地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闽中的刘彝、游烈、徐唐俱、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与胡瑗、孙復、石介三先生在朝廷往来,共同倡导理学,后来又倡道于闽中。他们提倡儒家道统,宣扬知天尽性之说,讲《中庸》明经笃行,是早期闽中理学的开创者。全祖望曾说:“安定(胡瑗)、泰山(孙復)并起之时,闽中四先生亦讲学海上,其所得虽未能底于粹深,然而略见大体矣。”①又说,“闽海古灵先生于安定稍后,其孜孜讲通,则与之相垺。安定之门,先后至一千七百余弟子,泰山弗逮也,而古灵亦过千人。”②李清馥说:“宋初所谓‘海滨四先生’与安定、泰山、组徕(石介)同时,其学已有近里之功,彼时未孚也。”③这里所说的“海滨四先生”,就是指闽中的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四先生。
(三)北宋末南宋初早期闽中理学的形成
到了北宋中期,理学思潮终于取代佛教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这时,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等一批理学家相继而起,开始了对儒学的再创造活动。他们以儒家的六经,特别是《周易》以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著作为根据,以此批判佛道,同时又不同程度地吸收、融合了佛道思想,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所谓的“天地万物之源”、“道德性命之源”以及“天人之际”等哲学基本问题。他们都各自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了各种学派,掀起了理学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早期闽中理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理学在北方形成后,闽中的杨时、游酢和胡安国等一批学者纷纷北上,拜程颢、程颐、张载为师,以传播理学为己任。他们学成“载道南归”①后,在闽中续传“北宋五子”的理学思想。清人蒋垣说:“周敦颐理学之教得二程而益盛。闽福清王蘋,将乐杨时,沙县陈渊、陈瓘,崇安游酢皆从二程受业。濂、洛之教入闽,由此而盛。”②当时,闽中不但出现了像杨时、胡安国等一批重要的理学家,而且形成了诸如道南龟山学派、武夷学派、艾轩学派等理学学派。他们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互相辩论、相互启发,思想异常活跃,开辟了早期闽中理学的新时代。应该指出,正是由于闽中一批推崇理学的学者,将北宋中期在北方形成的理学移植到南方,才可能有后来朱熹闽学的创立。如果没有早期闽中理学的出现,没有杨时、游酢、胡安国等一批闽中学者续传濂学、洛学、关学等,奠定理学闽化的基础,那朱熹闽学的出现应该是没有前提的,也就是没有可能的。
二、早期闽中理学的理论特征
早期闽中理学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它除了与北方中原理学有思想渊源关系,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外,还受到闽中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及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应该说,早期闽中理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着独特的学术风格和思想文化特点。这一理论特征可以从早期闽中理学的代表者思想中得到体现。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理论特征,早期闽中理学才能成为一个区别于其他学派的理学流派。早期闽中理学的理论特征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以理阐释太极,强调太极是至理之源
太极一词始见于《易·系辞上》:“易有太极。”理学家讲“太极”,肇始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自无极而为太极。”“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周氏把“无极”作为产生世界万物的本源,而以太极为阴阳混沌未分之气。张载以“气”为本体,同时用太极一词来说明“气”。他说:“一物两体,气也。”①“一物而两体其太极之谓与?”②二程以“理”为本体,他说:“万物皆是一理。”③二程讲理本,“太极”未提到基本范畴。邵雍主象数学,是最早把“太极”作为宇宙万物的根本。他说:“生天地之始,太极也。”“能造万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极也。”④邵雍以“太极”为本体,而“理”则只是物的自然属性的表现而已。早期闽中理学学者对北宋五子的理学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发。闽中学者杨时作为二程的门人,也是以“理”为宇宙万物的终极根源。他说,“盖天下只是一理”⑤这个理是宇宙的最高原则,无论是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还是社会的伦理纲常,都“本于一理”。杨时认为,理贯穿于一切事物,“有物必有则也,物即是形色,则即是天性”。⑥每个事物都是天理的体现。但是,与北宋五子所不同的是,杨时以理为太极,他说:“既有太极,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后;有左右前后四方,便有四维,皆自然之理也。”⑦太极就是自然之理,它是万物变化的根本原因。杨时的这一思想到再传弟子李侗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李侗发挥了二程“天下只有一个理”的理本论,以其“理”的一元论来诠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他认为太极动而生阳,“此只是理”,“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只是动静阖辟。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到得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时,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在天地只是理也”。①在这里,李侗提出了太极是“至理之源”,是最高的理。这一思想是对周敦颐、二程本体论思想的一个很好发挥。应该说,以太极为至理之源,是早期闽中理学的重要特征,也是它区别其他学派的标志之一。
(二)阐发理一分殊,强调以殊求一
“理一分殊”思想是程颐在回答杨时关于张载《西铭》的疑问时提出来的。绍圣三年(1096),杨时去信给程颐请教:“《西铭》之书,发明圣人微意至深,然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②认为《西铭》虽阐发了“仁之体”,却没有讲“仁之用”,如此就可能导致墨子之兼爱说。程颐在复信中说:《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分殊之弊,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③。程颐认为理一与分殊均不可偏废,就如仁与义。杨时正是通过对“理一分殊”概念的阐发,既继承了二程之学的立场,又说出了张载《西铭》之中的未尽之意,并且将“理一分殊”赋予普遍意义,使之成为早期闽中理学的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
杨时认为“理一分殊”具有普遍意义的同时,进而以仁与义诠释理一与分殊。他说:“天下万物,理一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①这就将本体的“理”和现实的伦理紧密地联系起来,丰富了其伦理道德的意蕴。杨时还用体用关系来阐述“理一分殊”,认为理一是体,分殊是用,体用不同,但又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他说:“用未尝离体也。且以一身观之,四体百骸皆具,所谓体也。至其用处,则履不可加之于首,冠不可纳之于足,则即体而言,分在其中也。”②体用就如人的身体与百骸,从人的全身来看,这是理一之体;从四体的百骸来看,这是分殊之用。故用不离体,分在理中。杨时从体用处说“理一分殊”,把“理一分殊”之说应用到道德修养上,知如何去实现仁的品德修养,知所谓“分殊”,使二程超越时空绝对的“理”,与现实沟通更密切了。
杨时的门人罗从彦继承了其师的观点,亦用体用关系阐发“理一分殊”思想。他说:“仁,体也;义,用也;行而宜之之谓也。”③这就使其师杨时的观点更加明确。李侗对“理一分殊”的认识又有新的发展。他在杨时“体用兼备”思想的基础上,更重视分殊,强调阐明“理之用”的重要性。他认为:“理不患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④又说,“然要见一视同仁气象却不难,须是理会万殊,虽毫发不可失,方是儒者气象。”⑤可见,李侗特别重视“分殊”,而且对分殊的认识强调要很细致,做到毫发不可失。同时,李侗还认为,知其理一要在“知”字上用力。他说:“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龟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说。而先生以为全在知字上用着力,恐亦是此意也。”①李侗对“理一分殊”的认识,着眼于“知”字,强调对分殊的认识,因而也就具有“穷理”的认识论意义。早期闽中理学的格物穷理方法,正是注重从具体的分殊的事物入手,认为经过对分殊的积累,自然会上升到对理的认识。这种注重对“理一分殊”思想的阐发,强调以“殊”求“一”的理论,亦是早期闽中理学的明显理论特征。
(三)既注重格物穷理,又强调反身而诚
格物致知说是早期闽中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思想的形成与二程格物致知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二程的诸多弟子中,闽中杨时是比较注重对格物致知说进行阐发的。就杨时“格物致知”的路向而言,明显地存在着把外求的格物功夫与内省的明心涵养相结合的倾向。杨时说:“为是道着,必先乎明善,然后知所以为道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②又说,“致知必先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③这就是说,要“明善”就必须致知,格物是致知的有效途径。杨时又认为:“致知格物,盖言致知当极尽物理也。理有不尽,则天下之物皆足以乱吾心之知。”④“凡形色之具于吾身者,无非物也,而各有则焉。目之于色,耳之于声,口鼻之于臭味,接乎外而不得循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体物而不可遗,则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则物与吾一也。”⑤杨时主张通过主体接触客体,以获得关于事物的道理或规律的认识,其格物之道就是要求通过多种途径遍格众物,以“极尽物理”。但是,天下万物,如何穷尽?要格尽天下万物,杨时提出了“反身而诚,则举天下之物在我矣”①的办法。可见,杨时的格物致知论既强调向外求索,又要求“反身而诚”,并且认为,只有在向外求索中,又“反身而诚”,才能“举天下之物在我矣”。在这里要指出的是,杨时讲“反身而诚”是作为“格物”过程中为了格尽天下万物而提出来的。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讨论“格物”与“反身而诚”的先后次序关系。
李侗在主张静坐体认天理的同时,又强调要“于日用处着力”,“须就事体用下功夫”。他说:“大率有疑处,须静坐体究,人伦必明,天理必察。于日用处着力,可见端绪,在勉之尔。”②李侗还提出了“融释”说。他说:“为学之初,且常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穷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少进,而别穷一事。如此既久,积累之多,胸中自当有洒然处,非文字言语所及也。”③这里所说的“常存此心”,就是要时时保持持敬之心,排除不符合天理,即排除一切不符合伦理道德的干扰,做到“心与理一”。遇事“反复推寻,以究其理”,实际上也就是格物穷理。“融释”就是程颐所谓的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后,自然有贯通处。可见,早期闽中理学学者是采取外向探索和内省工夫,渐次积累和豁然贯通结合起来,从而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格物致知论。(四)默坐澄心,静中体认未发
早期闽中理学学者十分注重对《中庸》之中道思想的阐发,从《中庸》中寻找所谓未发之旨。杨时作《中庸义》曰:“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执而勿失,无人欲之私焉,发必中节矣。”①杨时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亦说:“夫至道之归,固非笔舌能尽也。要以身体之,心验之,雍容自尽,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诵数之学也。”②杨时这种“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之法,在于他认为通过默而识之的内心体验工夫,最终能够超然自得。但这所得既然来源于言意之表,也就无法言说传诵。由此可知,杨时由《中庸》而来的这种涵养心性,体验喜怒哀乐未发的功夫,不是如禅门的“悟无所得”,而是有确定的内容,即“至道”的。道出于书言意象之外,所以忘言忘象才能体道,而非口耳诵数所得识。杨时提出“以身体之,心验之”默识中道的存养工夫,后来成为闽中道南学派的重要课题。
罗从彦对其师杨时“默识中道”的存养功夫,认真予以践履。他曾入罗浮山筑室静坐三年,“以体验天地万物之理”。他作诗云:“静处观心尘不染,闲中稽古意尤深,周诚程敬应初会,奥理休从此外寻。”③罗从彦“观心”所追求的“奥理”,他认为可以从周敦颐的“诚”和二程的“敬”中去寻求。心中一尘不染,闲中体验天地万物之理,便可进入一种“彩笔书空空不染,利刀割水水无痕。人心但得如空水,与物自然无怨恩”④的境界。如何体验“喜怒哀乐未发”的状态,罗从彦明确提出了“静中体验未发”之说。故后人多说罗从彦为学是“以主静为宗”①,理由有:一是罗从彦曾筑室于罗浮山,静坐穷理,即通过内心的体悟把握天理;二是罗从彦主张“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这种“以主静为宗”的修养论经过罗从彦的阐发,构成了早期闽中理学学者追求“静养”的境界的特征。
李侗对“静中体认未发”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说:“某曩时从罗先生问学,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未尝及一杂语。先生极好静坐,某时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静坐而已。先生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此意不唯于进学有力,兼亦是养心之要。”②李侗的学生亦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旨诀。”③未发之“中”作何“气象”,实际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但毕竟包含“进学”和“养心”的双重内容,二者之间是一体互发的关系。李侗认为,进学与养心的目的都在于“大本”未发时的“气象”。如此的“气象”,既是指圣贤洒落超脱的境界,又同时意味着哲学的本体,后者也就是所谓的“中”。可见,早期闽中理学学者体验未发之中的心性锻炼,是一种追寻哲学本体和提升道德境界的综合进程。
(五)重视对“四书”的诠释
宋代以后,中国正宗的儒家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书”之中。《宋史·列传·道学一》说:二程“表彰《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从这段文字可见,“四书”并行,最初是出于二程的提倡。闽中学者游酢师承二程,对“四书”予以高度的重视。他为学重在发挥经书中的义理,“本其躬行心得之言以说经”①。游酢所撰写的《中庸义》《论语杂解》《孟子杂解》等,都是对“四书”诠释的重要著作。在他的这些著作中,“足资深发者固已多矣”②。清人方宗诚说:“自二程夫子起,始独得于章句笺疏之外,而见圣贤立言之本心。先生(指游酢)及同门诸子,互有以发明之,于是经之大体大用始著。”③杨时亦非常重视“四书”。他认为:“《大学》者,其学者之门乎,不由其门而欲望其堂奥,非余所知也。”④“《论语》之书,孔子所以告其门人,群弟子所以学于孔子者也,圣学之传其不在兹乎?”⑤“《孟子》以睿知刚明之材,出于道学陵夷之后……《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为知言也。今其书存其要,皆言行之迹而已。……世之学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观其言,则圣人之庭户可渐而进矣。”⑥“《中庸》之书,盖圣学之渊源,入德之大方也。”⑦杨时对门人说:“余以为圣学所传具在此书,学者宜尽心焉。”⑧罗从彦于政和元年(1111),在南京(今河南商丘)杨时门下学“四书”,后写成《语孟师说》、《中庸说》和《议论要语》等名著,对“四书”亦进行了阐发。李侗拜师罗从彦后,“从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语》《孟》之说”①。李侗在《延平答问》中,诸多条是回答学生关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中的疑问的。闽中武夷学派的胡宪对“四书”中的《论语》有极深的研究。他广泛收集数十家《论语》解说,后来以二程说为本,抄摘各家精要,并附以己意而写成《论语会义》。该书为后来朱熹以《论语》为核心的“四书”学奠定了根基。宋代以后,儒家从注重“五经”到注重“四书”的转变。这个转变始自二程,而由朱熹所完成。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早期闽中理学家们提供了丰富思想资料。据美国著名朱子学家陈荣捷教授统计,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用了32位学者的731条语录,其中引述闽中学者杨时之论73条,李侗之论13条。此外,还有引用游酢等闽中学者的语录。可见,早期闽中理学家推崇“四书”,诠释“四书”,为朱熹诠释“四书”提供了重要依据。
从上述可见,早期闽中理学的形成,不是一个孤立的理学文化现象,它是整个理学思潮的一部分。它同中原理学的发展,闽中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就理学渊源关系而言,它是中原理学南移后的一个发展。就理论特征而言,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着自身独特的学术风格和思想文化特点。应该说,早期闽中理学的形成,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都为后来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来源和有益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
(一)唐朝中后期早期闽中理学的发端
安史之乱给唐王朝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危机,暴露出盛行一时的佛教和道教的软弱无力。它表明佛道思想并非是封建统治的最合理的统治思想。于是,当时一批封建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在为唐王朝寻求更有力的精神武器时,打出了复兴儒学的旗帜,力图恢复儒家在思想领域中的正统地位。以韩愈为代表的一批卫道者认为,佛教让人们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佛教的教义和它的僧侣实践违背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纲常伦理,因此任其发展就会破坏这个社会的伦理秩序,使社会无法维持。所以,韩愈推出《大学》,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来打击和压制标举出世主义的佛教。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儒学影响,开始了儒学复兴运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早期闽中理学开始萌芽。
与韩愈同登“龙虎榜”(唐德宗贞元七年,791年)进士的闽中晋江人欧阳詹(字行周),不仅与韩愈情同手足,而且志同道合。他们都以儒家思想为正统,以周公孔子为楷模,差不多同时提出了儒家道统。欧阳詹在闽中写给韩愈的诗中曾公开声明自己与韩愈一样,是“志在周孔堂,道适尧舜门”①。清人李清馥在《闽中理学渊源考》中说:“闽中儒学开先始于唐欧阳四门。”②而与欧阳詹同时的闽中莆田人林蕴(字复梦,唐德宗贞元四年进士)亦与韩愈、欧阳詹一起提倡儒家道统,反对佛教。欧阳詹和林蕴为代表的理学(道学)思想的出现,说明早在唐朝中后期,闽中就有了理学的端倪。值得注意的是,早期闽中理学形成伊始,就代表了传统儒家思想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二)北宋初早期闽中理学的开创
北宋建立之初,统治者推行倚文重儒,崇信佛道的三教兼容并用的方针,使得宋初仍然继续保持着多元文化的格局,这对于巩固当时的封建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新的统一局面的出现和统治方式的实行,佛教、道教与儒学并立所造成的“学术不一”的状况,已很难适应现实的需要。重新建立一种适应于宋朝中央集权统治需要的统一的思想,“一道德”③便成为当务之急。这时,以“庆历新政”为背景的儒学运动,在社会改革家范仲淹的倡导下,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从经济、政治、教育、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掀起了一股改革思潮。作为这一思潮的理论指导而成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哲学,则通过全面研究和发挥儒家经典,进而对自然、社会、人生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各自提出了具有理学特色的学说,从而揭开了理学的序幕。北宋初年的这一儒学运动,松动了思想界的重重大山,造成了秦汉以来中国学术史上罕见的活跃气氛。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文化氛围中,早期闽中理学得以酝酿成长起来。入宋以后,随着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进一步南移,闽中与外地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闽中的刘彝、游烈、徐唐俱、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与胡瑗、孙復、石介三先生在朝廷往来,共同倡导理学,后来又倡道于闽中。他们提倡儒家道统,宣扬知天尽性之说,讲《中庸》明经笃行,是早期闽中理学的开创者。全祖望曾说:“安定(胡瑗)、泰山(孙復)并起之时,闽中四先生亦讲学海上,其所得虽未能底于粹深,然而略见大体矣。”①又说,“闽海古灵先生于安定稍后,其孜孜讲通,则与之相垺。安定之门,先后至一千七百余弟子,泰山弗逮也,而古灵亦过千人。”②李清馥说:“宋初所谓‘海滨四先生’与安定、泰山、组徕(石介)同时,其学已有近里之功,彼时未孚也。”③这里所说的“海滨四先生”,就是指闽中的陈襄、陈烈、周希孟、郑穆四先生。
(三)北宋末南宋初早期闽中理学的形成
到了北宋中期,理学思潮终于取代佛教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这时,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等一批理学家相继而起,开始了对儒学的再创造活动。他们以儒家的六经,特别是《周易》以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著作为根据,以此批判佛道,同时又不同程度地吸收、融合了佛道思想,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所谓的“天地万物之源”、“道德性命之源”以及“天人之际”等哲学基本问题。他们都各自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了各种学派,掀起了理学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早期闽中理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理学在北方形成后,闽中的杨时、游酢和胡安国等一批学者纷纷北上,拜程颢、程颐、张载为师,以传播理学为己任。他们学成“载道南归”①后,在闽中续传“北宋五子”的理学思想。清人蒋垣说:“周敦颐理学之教得二程而益盛。闽福清王蘋,将乐杨时,沙县陈渊、陈瓘,崇安游酢皆从二程受业。濂、洛之教入闽,由此而盛。”②当时,闽中不但出现了像杨时、胡安国等一批重要的理学家,而且形成了诸如道南龟山学派、武夷学派、艾轩学派等理学学派。他们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互相辩论、相互启发,思想异常活跃,开辟了早期闽中理学的新时代。应该指出,正是由于闽中一批推崇理学的学者,将北宋中期在北方形成的理学移植到南方,才可能有后来朱熹闽学的创立。如果没有早期闽中理学的出现,没有杨时、游酢、胡安国等一批闽中学者续传濂学、洛学、关学等,奠定理学闽化的基础,那朱熹闽学的出现应该是没有前提的,也就是没有可能的。
二、早期闽中理学的理论特征
早期闽中理学的形成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它除了与北方中原理学有思想渊源关系,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外,还受到闽中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及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应该说,早期闽中理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着独特的学术风格和思想文化特点。这一理论特征可以从早期闽中理学的代表者思想中得到体现。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理论特征,早期闽中理学才能成为一个区别于其他学派的理学流派。早期闽中理学的理论特征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以理阐释太极,强调太极是至理之源
太极一词始见于《易·系辞上》:“易有太极。”理学家讲“太极”,肇始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自无极而为太极。”“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周氏把“无极”作为产生世界万物的本源,而以太极为阴阳混沌未分之气。张载以“气”为本体,同时用太极一词来说明“气”。他说:“一物两体,气也。”①“一物而两体其太极之谓与?”②二程以“理”为本体,他说:“万物皆是一理。”③二程讲理本,“太极”未提到基本范畴。邵雍主象数学,是最早把“太极”作为宇宙万物的根本。他说:“生天地之始,太极也。”“能造万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极也。”④邵雍以“太极”为本体,而“理”则只是物的自然属性的表现而已。早期闽中理学学者对北宋五子的理学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发。闽中学者杨时作为二程的门人,也是以“理”为宇宙万物的终极根源。他说,“盖天下只是一理”⑤这个理是宇宙的最高原则,无论是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还是社会的伦理纲常,都“本于一理”。杨时认为,理贯穿于一切事物,“有物必有则也,物即是形色,则即是天性”。⑥每个事物都是天理的体现。但是,与北宋五子所不同的是,杨时以理为太极,他说:“既有太极,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后;有左右前后四方,便有四维,皆自然之理也。”⑦太极就是自然之理,它是万物变化的根本原因。杨时的这一思想到再传弟子李侗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李侗发挥了二程“天下只有一个理”的理本论,以其“理”的一元论来诠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他认为太极动而生阳,“此只是理”,“太极动而生阳,至理之源,只是动静阖辟。至于终万物、始万物,亦只是此理一贯也。到得二气交感,化生万物时,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在天地只是理也”。①在这里,李侗提出了太极是“至理之源”,是最高的理。这一思想是对周敦颐、二程本体论思想的一个很好发挥。应该说,以太极为至理之源,是早期闽中理学的重要特征,也是它区别其他学派的标志之一。
(二)阐发理一分殊,强调以殊求一
“理一分殊”思想是程颐在回答杨时关于张载《西铭》的疑问时提出来的。绍圣三年(1096),杨时去信给程颐请教:“《西铭》之书,发明圣人微意至深,然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②认为《西铭》虽阐发了“仁之体”,却没有讲“仁之用”,如此就可能导致墨子之兼爱说。程颐在复信中说:《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分殊之弊,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③。程颐认为理一与分殊均不可偏废,就如仁与义。杨时正是通过对“理一分殊”概念的阐发,既继承了二程之学的立场,又说出了张载《西铭》之中的未尽之意,并且将“理一分殊”赋予普遍意义,使之成为早期闽中理学的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
杨时认为“理一分殊”具有普遍意义的同时,进而以仁与义诠释理一与分殊。他说:“天下万物,理一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①这就将本体的“理”和现实的伦理紧密地联系起来,丰富了其伦理道德的意蕴。杨时还用体用关系来阐述“理一分殊”,认为理一是体,分殊是用,体用不同,但又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他说:“用未尝离体也。且以一身观之,四体百骸皆具,所谓体也。至其用处,则履不可加之于首,冠不可纳之于足,则即体而言,分在其中也。”②体用就如人的身体与百骸,从人的全身来看,这是理一之体;从四体的百骸来看,这是分殊之用。故用不离体,分在理中。杨时从体用处说“理一分殊”,把“理一分殊”之说应用到道德修养上,知如何去实现仁的品德修养,知所谓“分殊”,使二程超越时空绝对的“理”,与现实沟通更密切了。
杨时的门人罗从彦继承了其师的观点,亦用体用关系阐发“理一分殊”思想。他说:“仁,体也;义,用也;行而宜之之谓也。”③这就使其师杨时的观点更加明确。李侗对“理一分殊”的认识又有新的发展。他在杨时“体用兼备”思想的基础上,更重视分殊,强调阐明“理之用”的重要性。他认为:“理不患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其要也。”④又说,“然要见一视同仁气象却不难,须是理会万殊,虽毫发不可失,方是儒者气象。”⑤可见,李侗特别重视“分殊”,而且对分殊的认识强调要很细致,做到毫发不可失。同时,李侗还认为,知其理一要在“知”字上用力。他说:“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龟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说。而先生以为全在知字上用着力,恐亦是此意也。”①李侗对“理一分殊”的认识,着眼于“知”字,强调对分殊的认识,因而也就具有“穷理”的认识论意义。早期闽中理学的格物穷理方法,正是注重从具体的分殊的事物入手,认为经过对分殊的积累,自然会上升到对理的认识。这种注重对“理一分殊”思想的阐发,强调以“殊”求“一”的理论,亦是早期闽中理学的明显理论特征。
(三)既注重格物穷理,又强调反身而诚
格物致知说是早期闽中理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思想的形成与二程格物致知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二程的诸多弟子中,闽中杨时是比较注重对格物致知说进行阐发的。就杨时“格物致知”的路向而言,明显地存在着把外求的格物功夫与内省的明心涵养相结合的倾向。杨时说:“为是道着,必先乎明善,然后知所以为道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②又说,“致知必先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斯知止矣,此其序也!”③这就是说,要“明善”就必须致知,格物是致知的有效途径。杨时又认为:“致知格物,盖言致知当极尽物理也。理有不尽,则天下之物皆足以乱吾心之知。”④“凡形色之具于吾身者,无非物也,而各有则焉。目之于色,耳之于声,口鼻之于臭味,接乎外而不得循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体物而不可遗,则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则物与吾一也。”⑤杨时主张通过主体接触客体,以获得关于事物的道理或规律的认识,其格物之道就是要求通过多种途径遍格众物,以“极尽物理”。但是,天下万物,如何穷尽?要格尽天下万物,杨时提出了“反身而诚,则举天下之物在我矣”①的办法。可见,杨时的格物致知论既强调向外求索,又要求“反身而诚”,并且认为,只有在向外求索中,又“反身而诚”,才能“举天下之物在我矣”。在这里要指出的是,杨时讲“反身而诚”是作为“格物”过程中为了格尽天下万物而提出来的。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讨论“格物”与“反身而诚”的先后次序关系。
李侗在主张静坐体认天理的同时,又强调要“于日用处着力”,“须就事体用下功夫”。他说:“大率有疑处,须静坐体究,人伦必明,天理必察。于日用处着力,可见端绪,在勉之尔。”②李侗还提出了“融释”说。他说:“为学之初,且常常存此心,勿为他事所胜。凡遇一事,即当且就此事反复推寻,以究穷理,待此一事融释脱落,然后循序少进,而别穷一事。如此既久,积累之多,胸中自当有洒然处,非文字言语所及也。”③这里所说的“常存此心”,就是要时时保持持敬之心,排除不符合天理,即排除一切不符合伦理道德的干扰,做到“心与理一”。遇事“反复推寻,以究其理”,实际上也就是格物穷理。“融释”就是程颐所谓的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后,自然有贯通处。可见,早期闽中理学学者是采取外向探索和内省工夫,渐次积累和豁然贯通结合起来,从而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格物致知论。(四)默坐澄心,静中体认未发
早期闽中理学学者十分注重对《中庸》之中道思想的阐发,从《中庸》中寻找所谓未发之旨。杨时作《中庸义》曰:“学者当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则中之义自见。执而勿失,无人欲之私焉,发必中节矣。”①杨时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亦说:“夫至道之归,固非笔舌能尽也。要以身体之,心验之,雍容自尽,燕闲静一之中,默而识之,兼忘于书言意象之表,则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诵数之学也。”②杨时这种“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以心体之”之法,在于他认为通过默而识之的内心体验工夫,最终能够超然自得。但这所得既然来源于言意之表,也就无法言说传诵。由此可知,杨时由《中庸》而来的这种涵养心性,体验喜怒哀乐未发的功夫,不是如禅门的“悟无所得”,而是有确定的内容,即“至道”的。道出于书言意象之外,所以忘言忘象才能体道,而非口耳诵数所得识。杨时提出“以身体之,心验之”默识中道的存养工夫,后来成为闽中道南学派的重要课题。
罗从彦对其师杨时“默识中道”的存养功夫,认真予以践履。他曾入罗浮山筑室静坐三年,“以体验天地万物之理”。他作诗云:“静处观心尘不染,闲中稽古意尤深,周诚程敬应初会,奥理休从此外寻。”③罗从彦“观心”所追求的“奥理”,他认为可以从周敦颐的“诚”和二程的“敬”中去寻求。心中一尘不染,闲中体验天地万物之理,便可进入一种“彩笔书空空不染,利刀割水水无痕。人心但得如空水,与物自然无怨恩”④的境界。如何体验“喜怒哀乐未发”的状态,罗从彦明确提出了“静中体验未发”之说。故后人多说罗从彦为学是“以主静为宗”①,理由有:一是罗从彦曾筑室于罗浮山,静坐穷理,即通过内心的体悟把握天理;二是罗从彦主张“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这种“以主静为宗”的修养论经过罗从彦的阐发,构成了早期闽中理学学者追求“静养”的境界的特征。
李侗对“静中体认未发”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他说:“某曩时从罗先生问学,终日相对静坐,只说文字,未尝及一杂语。先生极好静坐,某时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静坐而已。先生看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未发时作何气象。此意不唯于进学有力,兼亦是养心之要。”②李侗的学生亦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旨诀。”③未发之“中”作何“气象”,实际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但毕竟包含“进学”和“养心”的双重内容,二者之间是一体互发的关系。李侗认为,进学与养心的目的都在于“大本”未发时的“气象”。如此的“气象”,既是指圣贤洒落超脱的境界,又同时意味着哲学的本体,后者也就是所谓的“中”。可见,早期闽中理学学者体验未发之中的心性锻炼,是一种追寻哲学本体和提升道德境界的综合进程。
(五)重视对“四书”的诠释
宋代以后,中国正宗的儒家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书”之中。《宋史·列传·道学一》说:二程“表彰《大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自帝王传心之奥,下至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复余蕴”。从这段文字可见,“四书”并行,最初是出于二程的提倡。闽中学者游酢师承二程,对“四书”予以高度的重视。他为学重在发挥经书中的义理,“本其躬行心得之言以说经”①。游酢所撰写的《中庸义》《论语杂解》《孟子杂解》等,都是对“四书”诠释的重要著作。在他的这些著作中,“足资深发者固已多矣”②。清人方宗诚说:“自二程夫子起,始独得于章句笺疏之外,而见圣贤立言之本心。先生(指游酢)及同门诸子,互有以发明之,于是经之大体大用始著。”③杨时亦非常重视“四书”。他认为:“《大学》者,其学者之门乎,不由其门而欲望其堂奥,非余所知也。”④“《论语》之书,孔子所以告其门人,群弟子所以学于孔子者也,圣学之传其不在兹乎?”⑤“《孟子》以睿知刚明之材,出于道学陵夷之后……《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为知言也。今其书存其要,皆言行之迹而已。……世之学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观其言,则圣人之庭户可渐而进矣。”⑥“《中庸》之书,盖圣学之渊源,入德之大方也。”⑦杨时对门人说:“余以为圣学所传具在此书,学者宜尽心焉。”⑧罗从彦于政和元年(1111),在南京(今河南商丘)杨时门下学“四书”,后写成《语孟师说》、《中庸说》和《议论要语》等名著,对“四书”亦进行了阐发。李侗拜师罗从彦后,“从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语》《孟》之说”①。李侗在《延平答问》中,诸多条是回答学生关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书中的疑问的。闽中武夷学派的胡宪对“四书”中的《论语》有极深的研究。他广泛收集数十家《论语》解说,后来以二程说为本,抄摘各家精要,并附以己意而写成《论语会义》。该书为后来朱熹以《论语》为核心的“四书”学奠定了根基。宋代以后,儒家从注重“五经”到注重“四书”的转变。这个转变始自二程,而由朱熹所完成。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早期闽中理学家们提供了丰富思想资料。据美国著名朱子学家陈荣捷教授统计,朱子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用了32位学者的731条语录,其中引述闽中学者杨时之论73条,李侗之论13条。此外,还有引用游酢等闽中学者的语录。可见,早期闽中理学家推崇“四书”,诠释“四书”,为朱熹诠释“四书”提供了重要依据。
从上述可见,早期闽中理学的形成,不是一个孤立的理学文化现象,它是整个理学思潮的一部分。它同中原理学的发展,闽中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就理学渊源关系而言,它是中原理学南移后的一个发展。就理论特征而言,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有着自身独特的学术风格和思想文化特点。应该说,早期闽中理学的形成,无论在理论上或是在实践上都为后来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来源和有益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
附注
①张品端,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
①《欧阳行周集·李贻孙序》。
②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首《原序》。
③马端临:《文献通考·选举考》四。
①《古灵四先生学案》,《宋元学案》卷五。
②《古灵四先生学案》,《宋元学案》卷五。
③《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一。
①《杨时传》,《宋史》卷四二八。
②《八闽理学源流》卷一。
①《正蒙·参两》。
②《正蒙·大易》。
③《伊川先生语》,《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五。
④《邵子全书·无名公传》。
⑤《余杭所闻》,《龟山集》卷一三。
⑥《南都所闻》,《龟山集》卷一三。
⑦《南都所闻》,《龟山集》卷一三。
①《延平答问》。
②《寄伊川先生书》,《龟山集》卷一六。
③《答杨时论西铭书》,《河南程氏文集》卷九。
①《龟山学案》,《宋元学案》卷二五。
②《京师所闻》,《龟山集》卷一一。
③《遵尧录二》,《豫章文集》卷二。
④《宋嘉定姑孰刻本延平答问跋》,《延平答问·附录》。
⑤《延平答问》。
①《延平答问》。
②《答李杭》,《龟山集》卷一八。
③《答李杭》,《龟山集》卷一八。
④《答胡康侯其一》,《龟山集》卷二〇。
⑤《题萧欲仁大学篇后》,《龟山集》卷二六。
①《龟山学案》,《宋元学案》卷二五。
②《延平答问》。
③《豫章学案》,《宋元学案》卷三九。
①《龟山学案》,《宋元学案》卷二五。
②《龟山学案》,《宋元学案》卷二五。
③《观书有感》,《豫章文集》卷一三。
④《勉李愿中五首》,《豫章文集》卷一三。
①罗天广:《重刻豫章先生集序》,《罗豫章集》卷首。
②《延平答问》。
③《答何叔京》书二,《朱文公文集》卷四〇。
①《游定夫先生集·序》。
②《诸儒论述》,《游定夫先生集》卷首。
③《诸儒论述》,《游定夫先生集》卷首。
④《题萧欲仁大学篇后》,《龟山集》卷二六。
⑤《论语义序》,《龟山集》卷二五。
⑥《孟子义序》,《龟山集》卷二五。
⑦《中庸义序》,《龟山集》二五。
⑧《题中庸后示陈知默》,《龟山集》卷二六。
㊽《李侗传》,《宋史》卷四。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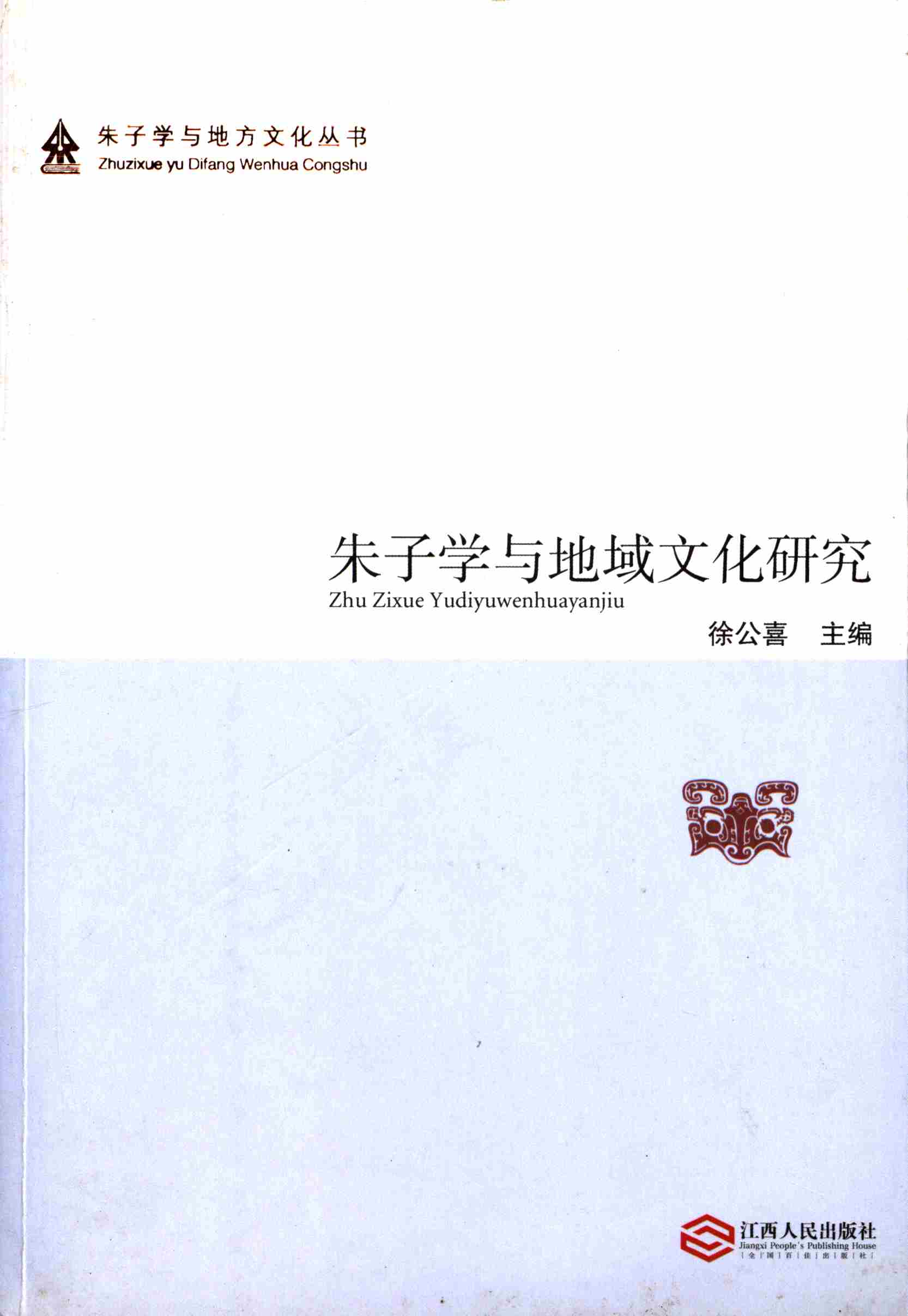
《朱子学与地域文化研究》
出版者:江西人民出版社
本书为2013年“朱子学与地域文化研究”研讨会的成果汇编,收录《新安理学特质》、《试论饶鲁的学术思想与心学化的双峰学派》、《朱子理学与关帝信仰》、《韩国九曲园林雏形阶段》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张品端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