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审美观探究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8)》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1312 |
| 颗粒名称: | 朱熹审美观探究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11 |
| 页码: | 098-108 |
| 摘要: | 本文探讨了朱熹的审美观,认为其审美观念是在原始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文章解释了“感性”活动是审美活动的首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并介绍了朱熹对于原始儒家感性课题的诠释和讨论。文章指出,在孔子的言论中,“视”“观”“察”分为三个层次来分析和视觉有关的活动,而朱熹则认为“观,比视为详矣……察,则又加详矣”。在讨论伦理行为的考察与目的时,这些感性活动亦有可以扩及一般非伦理行为的描述。 |
| 关键词: | 朱熹 审美观 儒家 |
内容
一、前言
从严格意义而言,关于中国“哲学”或中国“美学”的探究,都会有中西学术传统上的差异,进而引发中国是否有“哲学”或“美学”的论战。但是如果我们从各种学术领域当中,得到钻研其研究对象之究极意义的思想理论,就可以说在广义上,中国的诸子百家一系列发展下来的思想就是“中国哲学”。同理,在西洋美学的传统上极注重美的形上学意义,艺术的界定,以及如何产生美感等问题,形成一系列的美学理论。狭义上而言,中国也没有类似西洋美学的理论。但是,中国一样有各种从自身文化发展的艺术表现,论述艺术与道之关系的理论,品味各种知觉活动的审美鉴赏标准。所以我们可以说,从广义而言,存在中国美学思想。
中西美学的发展历史上,有一共同的现象,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有关于美的课题的理论,大多来自哲学家或思想家的谈论。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等到艺术家的地位逐渐受到肯定与重视之后,艺术家们的美学思想才慢慢开展出来。所以关于早期思想家们与美学相关的论述,并没有意图在当今我们所理解的系统化美学理论架构下,有意识地、自觉地发展所谓“美学”理论。我们只能说他们对于从感性方面所延伸的课题,结合其哲学思想,予以根源性的说明与论述。这些论述在起初并无意于专论感性问题以形成一特殊理论系统,但是对后世而言,确实为后来的美学理论提供了理论建设的基石。例如:原始儒家与原始道家的思想,原来的论述要旨在于说明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但是其中有许多涉及感性活动的论述,却可用来指导后世的艺术创作活动与艺术鉴赏活动,因而使我们现在可以说有某种“儒家美学”或“道家美学”。
朱熹留下许多优美的诗词文章,也有许多关于感性问题的论述,并有与弟子们互相切磋讨论的对话记录流传后世。在当年应该也没有所谓“美学”学科的概念,但是因为有许多关于感性问题而延伸出来的论述,使我们可以在广义的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来进行关于朱熹的审美观的探究。这是一种根源于朱熹的理学思想所发展出来的审美观念。这个审美观念透过经典的传递,可以进而实质影响到艺术作品的创作者,以及审美对象之鉴赏者的[1]
本文对于所谓“审美观”的理解,意指通过感性的觉察进而引发某种精神性的观念或情感。所以“感性”活动是审美活动的首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单纯的感觉活动并不必然产生审美活动,但是审美活动必要以感觉活动作为起始。对认知活动和审美活动而言,都需要感觉活动作为起点。认知活动以分析、抽象、推理等理性运作,将“具体”“个别”的感觉内容,抽取出“普遍”“抽象”的概念,因着这些概念而成为传达思想的基本单元。审美活动以直觉或直观的方式处理感觉内容,将这个感觉内容直接联结到某种情感或观念。如果在审美活动中所引发的情感或观念,愈是普及于多数的人使之可以领受到,愈能产生更大的共鸣。
本文期待能通过筛选朱熹有关上述说明之审美活动的言论,加以整理,并尝试理解朱熹哲学理论和审美观之间的理论关系。笔者阐述的方式,将首先检视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有关先秦儒家之审美观的批注,再从《朱子语类》中查找朱子与弟子的相关讨论。之后,也寻找朱熹更具个人特色的审美观。
二、朱熹对原始儒家的感性课题的诠释与讨论
儒家哲学对于感官知觉的活动,所采取的态度是肯定此知觉活动的实在性以及此种活动为后续的理性活动提供的一个思想基础,对于知觉活动所提供的内容并不怀疑。
1.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
朱熹注:
以,为也。为善者为君子,为恶者为小人。观,比视为详矣。由,从也。事虽为善,而意之所从来者有未善焉,则亦不得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谓所以行其所为者也。”察,则又加详矣。安,所乐也。所由虽善,而心之所乐者不在于是,则亦伪耳,岂能久而不变哉?焉,于虔反。廋,所留反。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穷理,则能以此察人如圣人也。”[2]
《朱子语类》中的讨论:
所以,只是个大概。所由,便看他所从之道,如为义,为利。又也看他所由处有是有非。至所安处,便是心之所以安,方定得。且如看得如此,又须着自反,看自家所以、所由、所安如何,只是一个道理。[3]《论语·为政篇》“观其所以章”本旨是讨论伦理行为的考察与目的,但是
其阶段历程,就其感性活动面而言,亦有可以扩及一般非伦理行为的描述。首先在孔子的言论中,把“视”“观”“察”分为三个层次来分析与视觉有关的活动。朱熹批注:“观,比视为详矣……察,则又加详矣。”从视觉活动来说,后者比前者增加了更多有意识的聚焦活动,只是在伦理行为的观察上,其聚焦的对象分别是“所以”“所由”“所安”。所“以”是外在可见的“行为表现”;所“由”是“发动行为的内在意念或动机”;所“安”是“享受行为所带来的效果”。在孔子与朱子的原始文脉中,明显地在讨论伦理行为的历程与效果。“视”“观”“察”是源自“主体”有意识的知觉活动,而且有逐级提升加密的意涵。“所以”“所由”“所安”是被观察的“行为者”(作为“客体”)产生的外显行为、行为动机、行为效果。
与视觉有关的词汇,除了以上“视”“观”“察”三个动词之外,朱熹也提及“看”“见”。他说:“阴阳五行之理,须常常看得在目前,则自然牢固矣。”[41
又:
曾点见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与几个好朋友行乐。他看那几个说底功名事业,都不是了。他看见日用之间,莫非天理,在在处处,莫非可乐。他自见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处,此是可乐天理。[5]上引的“看”或“看见”不是指光学原理上的看见,而是事理上的或人生
境界上的看见,亦即是一种“理会”或“意会”。这些与视觉经验有关的词汇,都不是单指生理性的视觉,而是会加上有意识的或具有“意向性”的观看。在以上的引文中虽然多以伦理行为作为讨论的事例,但是其分析的层次仍然可以运用于美感经验的描述中,只是把观看的对象从伦理行为转换为鉴赏对象即可达成。朱熹从经验上的看见“良辰美景”“日用之间”,向上提升到天理遍在四方流行。因此,由单纯的感性经验上的觉知,变成“可乐天理”。这说明从具象的感性经验提升到对遍在流行的大道的直观,会产生精神愉悦。
2.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
朱熹注:
《史记》三月上有“学之”二字。不知肉味,盖心一于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乐至于如此之美,则有以极其情文之备,而不觉其叹息之深也,盖非圣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尽美又尽善,乐之无以加此也。故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而叹美之如此。诚之至,感之深也。”[6]
《朱子语类》中的讨论:石丈问:“齐何以有韶?”曰:“人说公子完带来,亦有甚据?”淳问:“伊川以‘三月不知肉味’为圣人滞于物。今‘添学之’二字,则此意便无妨否?”曰:“是。”石丈引“三月”之证。曰:“不要理会‘三月’字。须看韶是甚么音调,便使得人如此;孔子是如何闻之便恁地。须就舜之德、孔子之心处看。”[7]
“‘子在齐闻韶,学之三月,不知肉味’。上蔡只要说得泊然处,便有些庄老。某谓正好看圣人忘肉味处,始见圣人之心如是之诚,韶乐如是之美。”又举《史记》载孔子至齐,促从者行,曰:“韶乐作。”从者曰:“何以知之?”曰:“吾见童子视端而行直。”“虽是说得异,亦容有此理。”[8]
按照朱熹的意见,他首先根据《史记》增补“学之”二字,使一般人断句的“三月不知肉味”,成为“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又根据《史记》记载孔子“见童子视端而行直”,间接看见“韶乐作”。其次,强调“始见圣人之心如是之诚,韶乐如是之美”,据此教人“不要理会‘三月’字”,并否定“伊川以‘三月不知肉味’为圣人滞于物”的负面看法。
关于“三月不知肉味”或“学之三月,不知肉味”两种句读,孰是孰非,其实各有其理由。一般句读的“三月”不是具体的三个月时间,应是表示很长时间的夸示法。而“学之‘三月'”,就是具体的三个月时间,但是除了《史记》之外似乎没有其他佐证。所以,朱熹下断语“不要理会‘三月’字”,因为“三月”是否为实指名词都对于本章之解释无关宏旨。
本章的主旨在于记载孔子听《韶乐》的审美经验导致“不知肉味”。这一描述对比了“听”韶乐与“知”肉味,两种不同的知觉经验导致在美感层次上的差异。这个例子肯定抽象的、具空间距离的听觉,压倒具体的、直接的官能接触的味觉。朱熹的解释是“圣人之心如是之诚,韶乐如是之美”。用现代美学的语汇来转述就是在鉴赏一首作品时,必须有“主体”的鉴赏能力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同时“客体”也必须内含相应的质量,在“主客合一”的状态下完成这个美妙的审美鉴赏活动。
附带一提,根据《史记》记载孔子“见童子视端而行直”,间接看见“韶乐作”。从这一段文献,可以分辨出认知历程与审美历程的差异与交互作用。这段记载所显示的是一种推理过程,说明孔子从“一个特定的行为”,推理出“一个作品正在演奏”。这是一个逻辑上的省略推理。但是这两者之间产生关联性的“联结”,即被省略的前提,却是一种源自美感经验的效果。在文字的背后,没有提及的是“韶乐演奏使人视端而行直”。这个推理严格而言,不是正确的有效推理,但是从孔子当时的有限、特殊情境,可以理解其特定的结论。
3.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朱熹注:
夫,音扶。舍,上声。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程子曰:“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纯亦不已焉。”又曰:“自汉以来,儒者皆不识此义。此见圣人之心,纯亦不已也。纯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语王道,其要只在谨独。”愚按:自此至篇终,皆勉人进学不已之辞。[91]
《朱子语类》中的讨论: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体而言。如“‘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人杰问:“‘乐’字之义,释曰‘喜好’。是知者之所喜好在水,仁者之所喜好在山否?”曰:“且看水之为体,运用不穷,或浅或深,或流或激;山之安静笃实,观之尽有余味。”某谓:“如仲尼之称水曰:‘水哉!水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皆是此意否?旧看伊川说‘非体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理会未透。自今观之,真是如此。”曰:“不必如此泛滥。且理会乐水乐山,直看得意思穷尽,然后四旁莫不贯通。苟先及四旁,却终至于与本说都理会不得也。”[10]
本节引述《论语·子罕》《子在川上》章,但是关于《朱子语类》则引述《论语·雍也》《知者乐水》章,因为后者的讨论更加简洁与周全。宋儒大致认为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之叹是对于“道体”之伟大的赞叹,而非议汉儒把它解释为“伤逝”(例如郑玄、何晏、邢昺等人的批注被归类为“伤逝”型)。根据朱熹的批注,具体的“水”的千变万化正是抽象的“道体”的具象表现。再回到鉴赏的主体来看,所谓“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不能拘泥“知者”与“仁者”的根本差异,或“山”与“水”的本质差异。“知者”与“仁者”就如同“水”的激荡或平静,都是水的同体与不同样态。而“山”与“水”在中国的山水观中也是互相包容与互相依赖,以共成“山光水色、滉漾夺目”的景观,即是“山以水为血脉……山得水而活……水以山为面……水得山而媚”(郭熙,《林泉高致》)。
本章文献彰显具象观察活动,可以引发超越境界的体验。这种历程不只在纯粹学问性的追索历程上显现,而展示出一种超越直观的境界,也可以解释从具象观察一个审美对象而直观天理大道。说明了思辨活动与审美活动,虽然起点与历程不同,但却是殊途同归,一同指向永恒大道。
4.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朱熹注:
韶,舜乐。武,武王乐。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舜绍尧致治,武王伐纣救民,其功一也,故其乐皆尽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逊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诛而得天下,故其实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汤放桀,惟有惭德,武王亦然,故未尽善。尧、舜、汤、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时然尔。”[11]
《朱子语类》的讨论:问“善者美之实”。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如舜‘九功惟叙,九叙惟歌’,与武王仗大义以救民,此其功都一般,不争多。只是德处,武王便不同。”曰:“‘未尽善’,亦是征伐处未满意否?”曰:“善只说德,是武王身上事,不干征伐事。”曰:“是就武王反之处看否?”曰:“是。”谢教,曰:“毕竟揖逊与征伐也自是不同,征伐是个不得已。”曰:“亦在其中,然不专就此说。”淳曰:“既征伐底是了,何故又有不得已意?”曰:“征伐底固是,毕竟莫如此也好。所以孔子再三诵文王至德,其意亦可见矣。乐便是圣人影子,这处‘未尽善’,便是那里有未满处。”[12]
孔子极度称美于韶乐,认为它同时满足了“美”“善”的极致标准,但是对于武乐则只认为它是具有充分“美”的条件,而缺乏“尽善”的条件。在朱熹的诠释上,认为武王的事功不下于舜,但是在为“德”方面,武王是有“未尽善”的。而此“未尽善”不是武王所愿意或故意的,而是就当时的时局有所“不得已”处。这个解释澄清武乐的“未尽善”不是源自武王的征伐行动的动机不善,而是就其行动本身以及反映在音乐上的属性有“未满处”。这个事例说明对于音乐作品或艺术作品,“美”“善”不是等同的,两者可以兼容,也可以分离存在。但是,以儒家的审美标准而言,一件作品必须以“尽善尽美”作为最终极的目标。
三、朱熹在审美上的发展
(一)感官经验的扩增
儒家审美思想对于感性的肯定是确实的,并且重视视觉经验与听觉经验。在许多讨论中多有触及视、听两种经验。《论语·为政》《视其所以》章把视觉经验更加细致地区分为不同的等级,《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章又把听觉的经验压倒味觉的经验。儒家对于味觉在审美上的地位未给予充分的讨论,但是《老子》的思想却是首开先例对其予以肯定。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第12章),“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第35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第63章)。《老子》从否定面来看待“无味”之味,扩张了味觉的意涵,延伸它的应用于抽象观念。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论及“味”字共有320段落,对关于“味”的使用有如下各种组合词汇:滋味、玩味、咀味、意味、涵味、无味、知味、熟味、美味、涵泳讽味、余味、忘味、别味、奇羞异味、气味、声色臭味、味别地脉、辨味点茶、味道之腴、诵味、详味、亲切有味、五味、从容涵泳之味、真味。
这些词汇多半出现在讨论读书功夫方面,把有关味觉的词汇使用在知识之追求,我们不能说这些词汇只适用于知识追求,而是应该反过来思考,朱熹大量借用味觉上的动词、名词、形容词来说明如何在读书功夫上精进。而这些味觉上的词汇应该都是源自审美经验的。这种借用的目的最主要在于体验,而不是词类批注。举例来说:
或问:“孟子说‘仁’字,义甚分明,孔子都不曾分晓说,是如何?”曰:“孔子未尝不说,只是公自不会看耳。譬如今沙糖,孟子但说糖味甜耳。孔子虽不如此说,却只将那糖与人吃。人若肯吃,则其味之甜,自不待说而知也。”[13]
朱熹诠释孔子的教导方式,举例,若要人认识糖的甜味,那就直接给那人吃糖便知道了。这是一种直接体证的方式,也是一种审美体验必然经历的方式。
(二)审美范畴的新解
关于审美经验,我们在本文前言就已提及审美经验不只是感觉经验,必须是经过专注、提炼的经验才能成为审美经验。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有一则讨论:
“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所谓道者是如此,何尝说物便是则!龟山便只指那物做则,只是就这物上分精粗为物则。如云目是物也,目之视乃则
也;耳物也,耳之听乃则也。殊不知目视耳听,依旧是物;其视之明,听之聪,方是则也。龟山又云:“伊尹之耕于莘野,此农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乐在是。”如此,则世间伊尹甚多矣!龟山说话,大概有此病。”[14]
以上引文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目视耳听,依旧是物;其视之明,听之聪,方是则也”。在这个文脉中“目视耳听”之为“物”,因为它们都是个别的知觉经验,未经有意识的筛选,所以不具备普遍性的意义与价值。能够把视听的能力发挥到它这个官能的理想境界,或优越境地,也就是耳聪目明,能在知觉中得出一个值得“玩味”“涵泳”的形式,那才符合“则”的意思。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朱熹的思想中隐含着审美经验必须从一般感觉经验加以提炼才可获得的原则。
在朱熹的审美思想中,仍然以儒家美学观为主轴而有别于道家美学观,从《朱子语类》有关《邵子之书》可以看出一些分辨。
因论康节之学,曰:“似老子。只是自要寻个宽间快活处,人皆害它不得。后来张子房亦是如此。方众人纷拏扰扰时,它自在背处。”人杰因问:“《击壤集序》有‘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治则治矣,犹未离乎害也’。上四句自说得好,却云‘未离乎害’。其下云:‘不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虽欲相伤,其可得乎?若然,则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亦从而可知也。’恐如上四句,似合圣人之中道;‘以道观道’而下,皆付之自然,未免有差否?”曰:“公且说前四句。”曰:“性只是仁义礼智,乃是道也。心则统乎性,身则主乎心,此三句可解。至于物,则身之所资以为用者也。”曰:“此非康节之意。既不得其意,如何议论它?”人杰因请教。先生曰:“‘以道观性’者,道是自然底道理,性则有刚柔善恶参差不齐处,是道不能以该尽此性也。性有仁义礼智之善,心却千思万虑,出入无时,是性不能以该尽此心也。心欲如此,而身却不能如此,是心有不能检其身处。以一身而观物,亦有不能尽其情状变态处,此则未离乎害之意也。且以一事言之:若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是‘以物观物’之意;若以己之好恶律人,则是‘以身观物’者也。”又问:“如此,则康节‘以道观道等’说,果为无病否?”曰:“谓之无病不可,谓之有病亦不可。若使孔孟言之,必不肯如此说。渠自是一样意思。如‘以天下观天下’,其说出于老子。”又问:“如此,则‘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三句,义理有可通者,但‘以身观物’一句为不可通耳。”曰:“若论‘万物皆备于我’,则以‘身观物’,亦何不可之有?”[15]
从邵康节的《击壤集序》先提出:“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四句,又提出“不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在整个讨论中,前四句被认为可以用儒家观念说得通,符合儒家的基本观念。但是后来修订的七句,被认为倾向道家,不符合儒家的传统观念。笔者认为“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从最大的范畴逐层含摄较小范畴,这个“观”的功能就在于连接上层观念与下层观念的隶属关系。这个连接为进德修业、修身养性,产生一种逐层进阶的提升,有助于伦理教化之功,也符合儒家的社会秩序建构。但是“不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它不再在乎上下层次的含摄关系。
邵雍之所以舍弃纯粹儒家的思路,在于他点出这层层约制关系中有“未离乎害”,亦即在含摄过程中有所保留与舍弃,而不能保全整体。而“以道观道……”并不是一个逻辑上的套套逻辑论式,而是就“道”自身的本质而考究其作为“道”的展现,以下类推。所以他说:“虽欲相伤,其可得乎?”如此,得以保全各实体的整全面貌。
犹如《易·乾卦·彖传》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道是道,性是性,心是心,等等,从一个万事万物作为存有者的角度,各自保有其本质的特征。就如同《朱子语类》中对于“各正性命”的讨论:
又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圣人于乾卦发此两句,最好。人之所以为人,物之所以为物,都是正个性命。保合得个和气性命,便是当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是有个皮壳包裹在里。如人以刀破其腹,此个物事便散,却便死。”[16]
到那万物各得其所时,便是物物如此。“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是那一草一木各得其理,变化是个浑全底。”[17]
因此,再回到邵康节所称许的“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对照《易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两者可以相通,不必然要把邵子的思想立即推向道家那一边去。如此“观”字在此的功能要比前段文字的“以道观性……”的应用范围更广泛,既可以说明形上学的存有状态,也可以作为鉴赏活动或审美经验上的一个核心动作。因此,如果朱熹不再拘泥儒家伦理观,而能从儒家形上学的立场来思考,就可以融通邵雍的思想,扩大审美经验的范围与高度。[18]
(三)“悦乐”作为审美经验的最高境界
以儒家的观点人生乐处在于成德,或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朱子语类》提及“孔颜乐处”:
问:“濂溪教程子寻孔颜乐处,盖自有其乐,然求之亦甚难。”曰:“先贤到乐处,已自成就向上去了,非初学所能求。况今之师,非濂溪之师,所谓友者,非二程之友,所以说此事却似莽广,不如且就圣贤着实用功处求之。如‘克己复礼’,致谨于视听言动之间,久久自当纯熟,充达向上去。”[19]颜回所乐之事不在于“箪瓢陋巷”本身,因为“箪瓢陋巷”其实对于颜回而言,是一种身心的考验,身处于一个物质条件简陋的环境,其简陋足以挠其心志,挫折其志向。而颜回仍然能不改其乐,在于他已经有了体道的经验,其快乐足以超越一切物质条件的种种不便。从儒家思想的角度来看,即使在美感经验的追求上,这种颜回之乐,也是符合美感经验的最高境界的。
或问:明道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则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又安得乐?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横渠曰:“‘万物皆备于我’,言万事皆有素于我也。‘反身而诚’,谓行无不慊于心,则‘乐莫大焉’。”如明道之说,则物只是物,更不须做事,且于下文‘求仁’之说意思贯串。横渠解‘反身而诚’为行无不慊之义,又似来不得。不唯以物为事,如下文‘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如何通贯得为一意?”曰:“横渠之说亦好。‘反身而诚’,实也。谓实有此理,更无不慊处,则仰不愧,俯不怍,‘乐莫大焉’。‘强恕而行’,即是推此理以及人也。我诚有此理,在人亦各有此理。能使人有此理亦如我焉,则近于仁矣。如明道这般说话极好,只是说得太广,学者难入。”[20]
对于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表示我已无所需求,自身达至完满阶段。而且也不自欺,对自己诚实以对。这是最大可乐之事。综合所述,孔颜之乐在于“忘我”“忘忧”;“万物皆备于我”在于“完满”“充实”;“反身而诚”在于“行无不慊于心”,带来心境上的“心安”。这些源自进德修业的功夫,仍然适用于审美经验,因为美、善境界相合,可以达成“尽善尽美”。
在伦理行为上的“完满”,在于行为本身符合正道,符合人性之自然。在迈向行为的完善历程上,行为者必须借着感性的觉察与理性的判断来修正或验证行为的正当性。当一切符合伦理价值时,行为者感受到行为的完满而享受着实践伦理价值所带来的精神悦乐。而作为一位审美鉴赏者,则是从鉴赏主体默观被鉴赏对象的形象,直观到此形象与大道或“理型”的符合而得到心灵的悦乐。此行为上所践履的“大道”与心灵直观所见到的“大道”是同一的。儒家思想虽没有充分讨论审美的境界,但是由审美鉴赏与伦理实践的共同趋向,可以贯通伦理的悦乐与审美的悦乐,认为两者是属于同一层次的价值。我们便可以透过伦理上的悦乐来理解审美上的悦乐所带来的精神境界。[21]
四、结论
综合以上所述,朱熹虽然没有明确地以审美为主题的论述,但是从他对感官经验的描述,可以运用于建立以朱熹思想为依据的在朱熹的大多数著述中,中心价值在于穷究天理与人性,与师友的讨论也多论及如何行善避恶,或如何读书的方法。整体来看是一种以伦理学为主轴的思想体系,并以天道观作为伦理思想的形上学依据。孔子以降的儒家学者也多是如此。但是,如何于人情、人欲上合理安排,仍是实践上必要的课题。经由感性问题的讨论,可以发现他们对美感经验的态度。基于美善同源的理由,我们可以尝试整理出一种儒家式的审美观,以对比于其他思想理论的审美观。
从严格意义而言,关于中国“哲学”或中国“美学”的探究,都会有中西学术传统上的差异,进而引发中国是否有“哲学”或“美学”的论战。但是如果我们从各种学术领域当中,得到钻研其研究对象之究极意义的思想理论,就可以说在广义上,中国的诸子百家一系列发展下来的思想就是“中国哲学”。同理,在西洋美学的传统上极注重美的形上学意义,艺术的界定,以及如何产生美感等问题,形成一系列的美学理论。狭义上而言,中国也没有类似西洋美学的理论。但是,中国一样有各种从自身文化发展的艺术表现,论述艺术与道之关系的理论,品味各种知觉活动的审美鉴赏标准。所以我们可以说,从广义而言,存在中国美学思想。
中西美学的发展历史上,有一共同的现象,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有关于美的课题的理论,大多来自哲学家或思想家的谈论。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等到艺术家的地位逐渐受到肯定与重视之后,艺术家们的美学思想才慢慢开展出来。所以关于早期思想家们与美学相关的论述,并没有意图在当今我们所理解的系统化美学理论架构下,有意识地、自觉地发展所谓“美学”理论。我们只能说他们对于从感性方面所延伸的课题,结合其哲学思想,予以根源性的说明与论述。这些论述在起初并无意于专论感性问题以形成一特殊理论系统,但是对后世而言,确实为后来的美学理论提供了理论建设的基石。例如:原始儒家与原始道家的思想,原来的论述要旨在于说明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但是其中有许多涉及感性活动的论述,却可用来指导后世的艺术创作活动与艺术鉴赏活动,因而使我们现在可以说有某种“儒家美学”或“道家美学”。
朱熹留下许多优美的诗词文章,也有许多关于感性问题的论述,并有与弟子们互相切磋讨论的对话记录流传后世。在当年应该也没有所谓“美学”学科的概念,但是因为有许多关于感性问题而延伸出来的论述,使我们可以在广义的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来进行关于朱熹的审美观的探究。这是一种根源于朱熹的理学思想所发展出来的审美观念。这个审美观念透过经典的传递,可以进而实质影响到艺术作品的创作者,以及审美对象之鉴赏者的[1]
本文对于所谓“审美观”的理解,意指通过感性的觉察进而引发某种精神性的观念或情感。所以“感性”活动是审美活动的首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单纯的感觉活动并不必然产生审美活动,但是审美活动必要以感觉活动作为起始。对认知活动和审美活动而言,都需要感觉活动作为起点。认知活动以分析、抽象、推理等理性运作,将“具体”“个别”的感觉内容,抽取出“普遍”“抽象”的概念,因着这些概念而成为传达思想的基本单元。审美活动以直觉或直观的方式处理感觉内容,将这个感觉内容直接联结到某种情感或观念。如果在审美活动中所引发的情感或观念,愈是普及于多数的人使之可以领受到,愈能产生更大的共鸣。
本文期待能通过筛选朱熹有关上述说明之审美活动的言论,加以整理,并尝试理解朱熹哲学理论和审美观之间的理论关系。笔者阐述的方式,将首先检视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有关先秦儒家之审美观的批注,再从《朱子语类》中查找朱子与弟子的相关讨论。之后,也寻找朱熹更具个人特色的审美观。
二、朱熹对原始儒家的感性课题的诠释与讨论
儒家哲学对于感官知觉的活动,所采取的态度是肯定此知觉活动的实在性以及此种活动为后续的理性活动提供的一个思想基础,对于知觉活动所提供的内容并不怀疑。
1.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论语·为政》)
朱熹注:
以,为也。为善者为君子,为恶者为小人。观,比视为详矣。由,从也。事虽为善,而意之所从来者有未善焉,则亦不得为君子矣。或曰:“由,行也。谓所以行其所为者也。”察,则又加详矣。安,所乐也。所由虽善,而心之所乐者不在于是,则亦伪耳,岂能久而不变哉?焉,于虔反。廋,所留反。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穷理,则能以此察人如圣人也。”[2]
《朱子语类》中的讨论:
所以,只是个大概。所由,便看他所从之道,如为义,为利。又也看他所由处有是有非。至所安处,便是心之所以安,方定得。且如看得如此,又须着自反,看自家所以、所由、所安如何,只是一个道理。[3]《论语·为政篇》“观其所以章”本旨是讨论伦理行为的考察与目的,但是
其阶段历程,就其感性活动面而言,亦有可以扩及一般非伦理行为的描述。首先在孔子的言论中,把“视”“观”“察”分为三个层次来分析与视觉有关的活动。朱熹批注:“观,比视为详矣……察,则又加详矣。”从视觉活动来说,后者比前者增加了更多有意识的聚焦活动,只是在伦理行为的观察上,其聚焦的对象分别是“所以”“所由”“所安”。所“以”是外在可见的“行为表现”;所“由”是“发动行为的内在意念或动机”;所“安”是“享受行为所带来的效果”。在孔子与朱子的原始文脉中,明显地在讨论伦理行为的历程与效果。“视”“观”“察”是源自“主体”有意识的知觉活动,而且有逐级提升加密的意涵。“所以”“所由”“所安”是被观察的“行为者”(作为“客体”)产生的外显行为、行为动机、行为效果。
与视觉有关的词汇,除了以上“视”“观”“察”三个动词之外,朱熹也提及“看”“见”。他说:“阴阳五行之理,须常常看得在目前,则自然牢固矣。”[41
又:
曾点见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与几个好朋友行乐。他看那几个说底功名事业,都不是了。他看见日用之间,莫非天理,在在处处,莫非可乐。他自见得那“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处,此是可乐天理。[5]上引的“看”或“看见”不是指光学原理上的看见,而是事理上的或人生
境界上的看见,亦即是一种“理会”或“意会”。这些与视觉经验有关的词汇,都不是单指生理性的视觉,而是会加上有意识的或具有“意向性”的观看。在以上的引文中虽然多以伦理行为作为讨论的事例,但是其分析的层次仍然可以运用于美感经验的描述中,只是把观看的对象从伦理行为转换为鉴赏对象即可达成。朱熹从经验上的看见“良辰美景”“日用之间”,向上提升到天理遍在四方流行。因此,由单纯的感性经验上的觉知,变成“可乐天理”。这说明从具象的感性经验提升到对遍在流行的大道的直观,会产生精神愉悦。
2.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
朱熹注:
《史记》三月上有“学之”二字。不知肉味,盖心一于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乐至于如此之美,则有以极其情文之备,而不觉其叹息之深也,盖非圣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尽美又尽善,乐之无以加此也。故学之三月,不知肉味,而叹美之如此。诚之至,感之深也。”[6]
《朱子语类》中的讨论:石丈问:“齐何以有韶?”曰:“人说公子完带来,亦有甚据?”淳问:“伊川以‘三月不知肉味’为圣人滞于物。今‘添学之’二字,则此意便无妨否?”曰:“是。”石丈引“三月”之证。曰:“不要理会‘三月’字。须看韶是甚么音调,便使得人如此;孔子是如何闻之便恁地。须就舜之德、孔子之心处看。”[7]
“‘子在齐闻韶,学之三月,不知肉味’。上蔡只要说得泊然处,便有些庄老。某谓正好看圣人忘肉味处,始见圣人之心如是之诚,韶乐如是之美。”又举《史记》载孔子至齐,促从者行,曰:“韶乐作。”从者曰:“何以知之?”曰:“吾见童子视端而行直。”“虽是说得异,亦容有此理。”[8]
按照朱熹的意见,他首先根据《史记》增补“学之”二字,使一般人断句的“三月不知肉味”,成为“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又根据《史记》记载孔子“见童子视端而行直”,间接看见“韶乐作”。其次,强调“始见圣人之心如是之诚,韶乐如是之美”,据此教人“不要理会‘三月’字”,并否定“伊川以‘三月不知肉味’为圣人滞于物”的负面看法。
关于“三月不知肉味”或“学之三月,不知肉味”两种句读,孰是孰非,其实各有其理由。一般句读的“三月”不是具体的三个月时间,应是表示很长时间的夸示法。而“学之‘三月'”,就是具体的三个月时间,但是除了《史记》之外似乎没有其他佐证。所以,朱熹下断语“不要理会‘三月’字”,因为“三月”是否为实指名词都对于本章之解释无关宏旨。
本章的主旨在于记载孔子听《韶乐》的审美经验导致“不知肉味”。这一描述对比了“听”韶乐与“知”肉味,两种不同的知觉经验导致在美感层次上的差异。这个例子肯定抽象的、具空间距离的听觉,压倒具体的、直接的官能接触的味觉。朱熹的解释是“圣人之心如是之诚,韶乐如是之美”。用现代美学的语汇来转述就是在鉴赏一首作品时,必须有“主体”的鉴赏能力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同时“客体”也必须内含相应的质量,在“主客合一”的状态下完成这个美妙的审美鉴赏活动。
附带一提,根据《史记》记载孔子“见童子视端而行直”,间接看见“韶乐作”。从这一段文献,可以分辨出认知历程与审美历程的差异与交互作用。这段记载所显示的是一种推理过程,说明孔子从“一个特定的行为”,推理出“一个作品正在演奏”。这是一个逻辑上的省略推理。但是这两者之间产生关联性的“联结”,即被省略的前提,却是一种源自美感经验的效果。在文字的背后,没有提及的是“韶乐演奏使人视端而行直”。这个推理严格而言,不是正确的有效推理,但是从孔子当时的有限、特殊情境,可以理解其特定的结论。
3.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
朱熹注:
夫,音扶。舍,上声。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程子曰:“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纯亦不已焉。”又曰:“自汉以来,儒者皆不识此义。此见圣人之心,纯亦不已也。纯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语王道,其要只在谨独。”愚按:自此至篇终,皆勉人进学不已之辞。[91]
《朱子语类》中的讨论: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体而言。如“‘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人杰问:“‘乐’字之义,释曰‘喜好’。是知者之所喜好在水,仁者之所喜好在山否?”曰:“且看水之为体,运用不穷,或浅或深,或流或激;山之安静笃实,观之尽有余味。”某谓:“如仲尼之称水曰:‘水哉!水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皆是此意否?旧看伊川说‘非体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理会未透。自今观之,真是如此。”曰:“不必如此泛滥。且理会乐水乐山,直看得意思穷尽,然后四旁莫不贯通。苟先及四旁,却终至于与本说都理会不得也。”[10]
本节引述《论语·子罕》《子在川上》章,但是关于《朱子语类》则引述《论语·雍也》《知者乐水》章,因为后者的讨论更加简洁与周全。宋儒大致认为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之叹是对于“道体”之伟大的赞叹,而非议汉儒把它解释为“伤逝”(例如郑玄、何晏、邢昺等人的批注被归类为“伤逝”型)。根据朱熹的批注,具体的“水”的千变万化正是抽象的“道体”的具象表现。再回到鉴赏的主体来看,所谓“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不能拘泥“知者”与“仁者”的根本差异,或“山”与“水”的本质差异。“知者”与“仁者”就如同“水”的激荡或平静,都是水的同体与不同样态。而“山”与“水”在中国的山水观中也是互相包容与互相依赖,以共成“山光水色、滉漾夺目”的景观,即是“山以水为血脉……山得水而活……水以山为面……水得山而媚”(郭熙,《林泉高致》)。
本章文献彰显具象观察活动,可以引发超越境界的体验。这种历程不只在纯粹学问性的追索历程上显现,而展示出一种超越直观的境界,也可以解释从具象观察一个审美对象而直观天理大道。说明了思辨活动与审美活动,虽然起点与历程不同,但却是殊途同归,一同指向永恒大道。
4.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
朱熹注:
韶,舜乐。武,武王乐。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舜绍尧致治,武王伐纣救民,其功一也,故其乐皆尽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逊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诛而得天下,故其实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汤放桀,惟有惭德,武王亦然,故未尽善。尧、舜、汤、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时然尔。”[11]
《朱子语类》的讨论:问“善者美之实”。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如舜‘九功惟叙,九叙惟歌’,与武王仗大义以救民,此其功都一般,不争多。只是德处,武王便不同。”曰:“‘未尽善’,亦是征伐处未满意否?”曰:“善只说德,是武王身上事,不干征伐事。”曰:“是就武王反之处看否?”曰:“是。”谢教,曰:“毕竟揖逊与征伐也自是不同,征伐是个不得已。”曰:“亦在其中,然不专就此说。”淳曰:“既征伐底是了,何故又有不得已意?”曰:“征伐底固是,毕竟莫如此也好。所以孔子再三诵文王至德,其意亦可见矣。乐便是圣人影子,这处‘未尽善’,便是那里有未满处。”[12]
孔子极度称美于韶乐,认为它同时满足了“美”“善”的极致标准,但是对于武乐则只认为它是具有充分“美”的条件,而缺乏“尽善”的条件。在朱熹的诠释上,认为武王的事功不下于舜,但是在为“德”方面,武王是有“未尽善”的。而此“未尽善”不是武王所愿意或故意的,而是就当时的时局有所“不得已”处。这个解释澄清武乐的“未尽善”不是源自武王的征伐行动的动机不善,而是就其行动本身以及反映在音乐上的属性有“未满处”。这个事例说明对于音乐作品或艺术作品,“美”“善”不是等同的,两者可以兼容,也可以分离存在。但是,以儒家的审美标准而言,一件作品必须以“尽善尽美”作为最终极的目标。
三、朱熹在审美上的发展
(一)感官经验的扩增
儒家审美思想对于感性的肯定是确实的,并且重视视觉经验与听觉经验。在许多讨论中多有触及视、听两种经验。《论语·为政》《视其所以》章把视觉经验更加细致地区分为不同的等级,《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章又把听觉的经验压倒味觉的经验。儒家对于味觉在审美上的地位未给予充分的讨论,但是《老子》的思想却是首开先例对其予以肯定。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第12章),“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第35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第63章)。《老子》从否定面来看待“无味”之味,扩张了味觉的意涵,延伸它的应用于抽象观念。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论及“味”字共有320段落,对关于“味”的使用有如下各种组合词汇:滋味、玩味、咀味、意味、涵味、无味、知味、熟味、美味、涵泳讽味、余味、忘味、别味、奇羞异味、气味、声色臭味、味别地脉、辨味点茶、味道之腴、诵味、详味、亲切有味、五味、从容涵泳之味、真味。
这些词汇多半出现在讨论读书功夫方面,把有关味觉的词汇使用在知识之追求,我们不能说这些词汇只适用于知识追求,而是应该反过来思考,朱熹大量借用味觉上的动词、名词、形容词来说明如何在读书功夫上精进。而这些味觉上的词汇应该都是源自审美经验的。这种借用的目的最主要在于体验,而不是词类批注。举例来说:
或问:“孟子说‘仁’字,义甚分明,孔子都不曾分晓说,是如何?”曰:“孔子未尝不说,只是公自不会看耳。譬如今沙糖,孟子但说糖味甜耳。孔子虽不如此说,却只将那糖与人吃。人若肯吃,则其味之甜,自不待说而知也。”[13]
朱熹诠释孔子的教导方式,举例,若要人认识糖的甜味,那就直接给那人吃糖便知道了。这是一种直接体证的方式,也是一种审美体验必然经历的方式。
(二)审美范畴的新解
关于审美经验,我们在本文前言就已提及审美经验不只是感觉经验,必须是经过专注、提炼的经验才能成为审美经验。朱熹在《朱子语类》中有一则讨论:
“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所谓道者是如此,何尝说物便是则!龟山便只指那物做则,只是就这物上分精粗为物则。如云目是物也,目之视乃则
也;耳物也,耳之听乃则也。殊不知目视耳听,依旧是物;其视之明,听之聪,方是则也。龟山又云:“伊尹之耕于莘野,此农夫田父之所日用者,而乐在是。”如此,则世间伊尹甚多矣!龟山说话,大概有此病。”[14]
以上引文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目视耳听,依旧是物;其视之明,听之聪,方是则也”。在这个文脉中“目视耳听”之为“物”,因为它们都是个别的知觉经验,未经有意识的筛选,所以不具备普遍性的意义与价值。能够把视听的能力发挥到它这个官能的理想境界,或优越境地,也就是耳聪目明,能在知觉中得出一个值得“玩味”“涵泳”的形式,那才符合“则”的意思。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朱熹的思想中隐含着审美经验必须从一般感觉经验加以提炼才可获得的原则。
在朱熹的审美思想中,仍然以儒家美学观为主轴而有别于道家美学观,从《朱子语类》有关《邵子之书》可以看出一些分辨。
因论康节之学,曰:“似老子。只是自要寻个宽间快活处,人皆害它不得。后来张子房亦是如此。方众人纷拏扰扰时,它自在背处。”人杰因问:“《击壤集序》有‘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治则治矣,犹未离乎害也’。上四句自说得好,却云‘未离乎害’。其下云:‘不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虽欲相伤,其可得乎?若然,则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亦从而可知也。’恐如上四句,似合圣人之中道;‘以道观道’而下,皆付之自然,未免有差否?”曰:“公且说前四句。”曰:“性只是仁义礼智,乃是道也。心则统乎性,身则主乎心,此三句可解。至于物,则身之所资以为用者也。”曰:“此非康节之意。既不得其意,如何议论它?”人杰因请教。先生曰:“‘以道观性’者,道是自然底道理,性则有刚柔善恶参差不齐处,是道不能以该尽此性也。性有仁义礼智之善,心却千思万虑,出入无时,是性不能以该尽此心也。心欲如此,而身却不能如此,是心有不能检其身处。以一身而观物,亦有不能尽其情状变态处,此则未离乎害之意也。且以一事言之:若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是‘以物观物’之意;若以己之好恶律人,则是‘以身观物’者也。”又问:“如此,则康节‘以道观道等’说,果为无病否?”曰:“谓之无病不可,谓之有病亦不可。若使孔孟言之,必不肯如此说。渠自是一样意思。如‘以天下观天下’,其说出于老子。”又问:“如此,则‘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三句,义理有可通者,但‘以身观物’一句为不可通耳。”曰:“若论‘万物皆备于我’,则以‘身观物’,亦何不可之有?”[15]
从邵康节的《击壤集序》先提出:“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四句,又提出“不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在整个讨论中,前四句被认为可以用儒家观念说得通,符合儒家的基本观念。但是后来修订的七句,被认为倾向道家,不符合儒家的传统观念。笔者认为“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从最大的范畴逐层含摄较小范畴,这个“观”的功能就在于连接上层观念与下层观念的隶属关系。这个连接为进德修业、修身养性,产生一种逐层进阶的提升,有助于伦理教化之功,也符合儒家的社会秩序建构。但是“不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它不再在乎上下层次的含摄关系。
邵雍之所以舍弃纯粹儒家的思路,在于他点出这层层约制关系中有“未离乎害”,亦即在含摄过程中有所保留与舍弃,而不能保全整体。而“以道观道……”并不是一个逻辑上的套套逻辑论式,而是就“道”自身的本质而考究其作为“道”的展现,以下类推。所以他说:“虽欲相伤,其可得乎?”如此,得以保全各实体的整全面貌。
犹如《易·乾卦·彖传》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道是道,性是性,心是心,等等,从一个万事万物作为存有者的角度,各自保有其本质的特征。就如同《朱子语类》中对于“各正性命”的讨论:
又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圣人于乾卦发此两句,最好。人之所以为人,物之所以为物,都是正个性命。保合得个和气性命,便是当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是有个皮壳包裹在里。如人以刀破其腹,此个物事便散,却便死。”[16]
到那万物各得其所时,便是物物如此。“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是那一草一木各得其理,变化是个浑全底。”[17]
因此,再回到邵康节所称许的“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对照《易传》“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两者可以相通,不必然要把邵子的思想立即推向道家那一边去。如此“观”字在此的功能要比前段文字的“以道观性……”的应用范围更广泛,既可以说明形上学的存有状态,也可以作为鉴赏活动或审美经验上的一个核心动作。因此,如果朱熹不再拘泥儒家伦理观,而能从儒家形上学的立场来思考,就可以融通邵雍的思想,扩大审美经验的范围与高度。[18]
(三)“悦乐”作为审美经验的最高境界
以儒家的观点人生乐处在于成德,或所谓“万物皆备于我”。《朱子语类》提及“孔颜乐处”:
问:“濂溪教程子寻孔颜乐处,盖自有其乐,然求之亦甚难。”曰:“先贤到乐处,已自成就向上去了,非初学所能求。况今之师,非濂溪之师,所谓友者,非二程之友,所以说此事却似莽广,不如且就圣贤着实用功处求之。如‘克己复礼’,致谨于视听言动之间,久久自当纯熟,充达向上去。”[19]颜回所乐之事不在于“箪瓢陋巷”本身,因为“箪瓢陋巷”其实对于颜回而言,是一种身心的考验,身处于一个物质条件简陋的环境,其简陋足以挠其心志,挫折其志向。而颜回仍然能不改其乐,在于他已经有了体道的经验,其快乐足以超越一切物质条件的种种不便。从儒家思想的角度来看,即使在美感经验的追求上,这种颜回之乐,也是符合美感经验的最高境界的。
或问:明道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则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又安得乐?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横渠曰:“‘万物皆备于我’,言万事皆有素于我也。‘反身而诚’,谓行无不慊于心,则‘乐莫大焉’。”如明道之说,则物只是物,更不须做事,且于下文‘求仁’之说意思贯串。横渠解‘反身而诚’为行无不慊之义,又似来不得。不唯以物为事,如下文‘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如何通贯得为一意?”曰:“横渠之说亦好。‘反身而诚’,实也。谓实有此理,更无不慊处,则仰不愧,俯不怍,‘乐莫大焉’。‘强恕而行’,即是推此理以及人也。我诚有此理,在人亦各有此理。能使人有此理亦如我焉,则近于仁矣。如明道这般说话极好,只是说得太广,学者难入。”[20]
对于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表示我已无所需求,自身达至完满阶段。而且也不自欺,对自己诚实以对。这是最大可乐之事。综合所述,孔颜之乐在于“忘我”“忘忧”;“万物皆备于我”在于“完满”“充实”;“反身而诚”在于“行无不慊于心”,带来心境上的“心安”。这些源自进德修业的功夫,仍然适用于审美经验,因为美、善境界相合,可以达成“尽善尽美”。
在伦理行为上的“完满”,在于行为本身符合正道,符合人性之自然。在迈向行为的完善历程上,行为者必须借着感性的觉察与理性的判断来修正或验证行为的正当性。当一切符合伦理价值时,行为者感受到行为的完满而享受着实践伦理价值所带来的精神悦乐。而作为一位审美鉴赏者,则是从鉴赏主体默观被鉴赏对象的形象,直观到此形象与大道或“理型”的符合而得到心灵的悦乐。此行为上所践履的“大道”与心灵直观所见到的“大道”是同一的。儒家思想虽没有充分讨论审美的境界,但是由审美鉴赏与伦理实践的共同趋向,可以贯通伦理的悦乐与审美的悦乐,认为两者是属于同一层次的价值。我们便可以透过伦理上的悦乐来理解审美上的悦乐所带来的精神境界。[21]
四、结论
综合以上所述,朱熹虽然没有明确地以审美为主题的论述,但是从他对感官经验的描述,可以运用于建立以朱熹思想为依据的在朱熹的大多数著述中,中心价值在于穷究天理与人性,与师友的讨论也多论及如何行善避恶,或如何读书的方法。整体来看是一种以伦理学为主轴的思想体系,并以天道观作为伦理思想的形上学依据。孔子以降的儒家学者也多是如此。但是,如何于人情、人欲上合理安排,仍是实践上必要的课题。经由感性问题的讨论,可以发现他们对美感经验的态度。基于美善同源的理由,我们可以尝试整理出一种儒家式的审美观,以对比于其他思想理论的审美观。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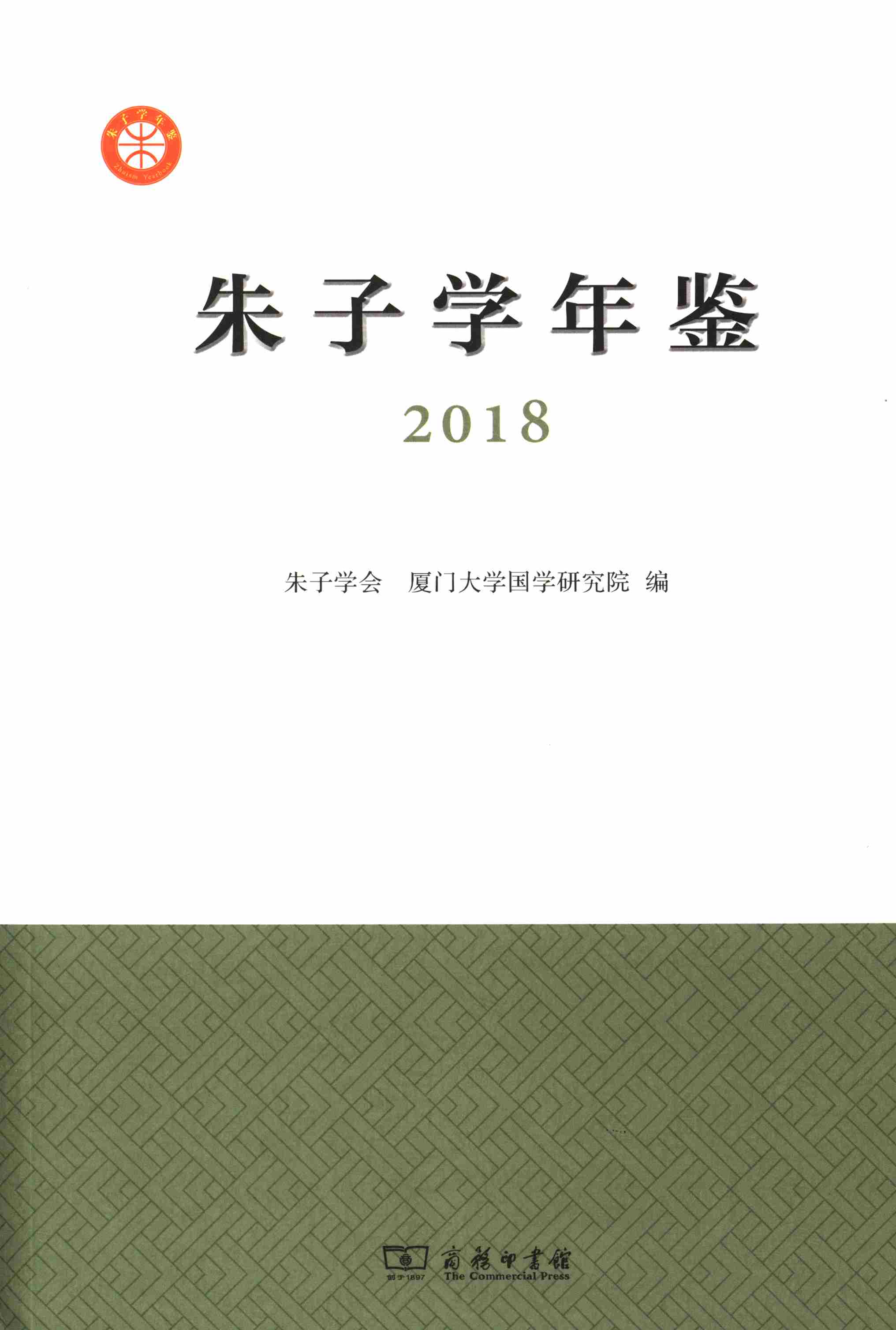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8)》
出版者:商务印书馆出版
本书设有“特稿”“朱子学研究新视野”“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朱子学书评”等栏目,收录了《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二程与朱子道统说》《2018年度中国台湾朱子学研究成果综述》等文章。
阅读
相关地名
南平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