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研究新视野
| 内容出处: | 《朱子学年鉴-2011-2012》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0362 |
| 颗粒名称: | 朱子学研究新视野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108 |
| 页码: | 27-134 |
| 摘要: | 本文列举了多个关于朱熹和朱子学的研究课题,包括对朱子思想中的四德论的研究、朱子学术的世俗关怀及时代意义、朱子与儒家精神传统的关系等。此外,还提到了对朱熹的“敬论”、《大学》“明明德”的诠释以及朱熹的子学思想和理气动静问题等方面的研究。 |
| 关键词: | 朱熹 朱子学 四德论 |
内容
朱子思想中的四德论
陈来
朱子思想中有关四德以及五常的讨论,以往受到的关注不多。事实上,朱子有关四德五常的思想对后来的哲学、特别是明代哲学的讨论影响甚大。本文就朱子在四德五常方面的论述,以《朱子语类》的资料为主,作一梳理,并加以分析,藉以了解朱子学德目论或德性理论的结构和意义。
一、北宋道学论四德
“四德”本指乾之四德“元亨利贞”,“四德”统称源出《周易·文言传》,所谓“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本于孟子,汉儒始用“五常”的概念。北宋以来,道学的讨论中开始把二者加以联结,而在后来的宋明理学发展中仁义礼智也往往被称为四德。汉以来的思想中,元亨利贞属天道,仁义礼智属人道。天道的四德和人道的四德,二者的关系在道学中渐渐成为重要的论题。
周敦颐在《通书》中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1]元亨利贞在《周易》本指天道而言,周敦颐虽然还没有把元亨利贞与仁义礼智联系起来,但开始把元亨利贞与本属人道的“诚”联系起来,这也是有意义的。而且,他还表现出把元亨利贞看作一个流行的过程,并用“通”、“复”来把这一过程截分为两个阶段,元亨属于“通”的阶段,利贞属于“复”的阶段。按朱子的解释,元亨是万物资始,利贞是各正性命;前者是造化流行,后者是归藏为物。这种用类似“流行”的观念来解释易之四德的性质与联系,是有示范意义的。
程明道则最重视四德中的“元”与五常中的“仁”的对应,言“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2]明确肯定“元”就是“仁”。这就把宇宙论的范畴和道德论的范畴连接起来,互为对应,从一个具体的方面把天和人贯通起来,使道德论获得了宇宙论的支持,也使宇宙论具有了贯通向道德的含义。“‘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个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长’,万物皆有春意,便是‘继之者善也’。”[3]善是继承了天道的生生之理而来的,所以善体现了元的意思,元即是善的根源。“‘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性情犹言资质体段。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贞也。诗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者,贞也。”[4]于是,在道学中,德性概念不再是纯粹道德哲学的概念,同时也具有宇宙论的意谓或根源。
二程已经把四德和五常联系起来讨论,如伊川《程氏易传》的《乾》卦卦辞注:“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5]又解释《乾》卦彖辞“大哉乾元”句说:“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6]又如伊川言:“读易须先识卦体。如乾有元亨利贞四德,缺却一个,便不是乾,须要认得。”[7]“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义,须于道中与他分别五常,若只是兼体,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头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虽言‘元者善之长’,然亦须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义在乎此,亦无人曾解来。”[8]他认为元必须通四德而言,仁必须通五常而言,兼体是指元可以兼亨利贞,仁可以兼义礼智信。这些地方都是以四德和五常并提,把它们看成结构相同的事物。
二程又说:“孟子将四端便为四体,仁便是一个木气象,恻隐之心便是一个生物春底气象,羞恶之心便是一个秋底气象,只有一个去就断割底气象,便是义也。推之四端皆然。此个事,又着个甚安排得也?此个道理,虽牛马血气之类亦然,都恁备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随形气,后便昏了佗气”。[9]这里所说的“气象”,就是后来朱子所说的“意思”,即一个道德概念的精神、取向及一个价值概念在形象上的表达。这种讲法认为每一道德概念都有其“气象”、“意思”,即都有其蕴涵并洋溢的特定气息、态度,如说仁有春风和气的气象(意思),义有萧肃割杀的气象(意思),等。这个讲法很特别,讲一个道德德目的实践所发散的“气”,这种德气论的讲法得到了朱子四德论的继承和发展。
二、论道与德
《朱子语类》卷六收录了朱子论“仁义礼智等名义”的讲学语录,名义即名之义,在这里指道德概念的意义。为集中和简便起见,本文以下主要使用该卷的资料进行分析。
朱子把传统德目置于“理”的概念下进行讨论,首先是关于一理与五常的关系:
问:既是一理,又谓五常,何也?曰:谓之一理亦可,五理亦可。以一包之则一,分之则五。问分为五之序。曰:浑然不可分。节。[10]
这是用理一分殊的模式处理五常与理一的关系:一方面五常的仁义礼智信五者都是理,仁是理,义是理,礼智信皆是理;但另一方面五常的理是分殊的理,不是理一的理,是具体的理,不是普遍的理。就理一和五常的发生关系来说,五常是由理一所分出来的,这就是“分之则五”。就理一和五常的逻辑关系说,理一可以包含五常,这就是“以一包之则一”。总之,仁义礼智信五常是五种分殊之理,是作为理一的天理在具体事物不同方面的表现。当然,朱子在另外的讨论中也提出,偏言之仁,其中也含具其他各常之理,[11]这种提法体现了太极论的思维,此处不拟详论。
在理学中,“理”在哲学概念体系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也是涵盖性最大的概念,但理学的体系仍然需要“道”和“德”这些传统道德概念:
问:“仁与道如何分别?”曰:“道是统言,仁是一事。如‘道路’之道,千枝百派,皆有一路去。故《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为天下之达道,智仁勇为天下之达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个行道底。故为君主于仁,为臣主于敬。仁敬可唤做德,不可唤做道。”榦(以下兼论德)。[12]
道和仁的关系也如理一分殊的关系,道是统言当然之则,仁只是一事之德。所以仁是德,但不是道。在这里朱子下了一个定义:“德便是行道底”,这就是说德是用来践行道德原则的内在德性。
至德、至道: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独得。盛德、至善: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至善以理之极致而言。诚、忠、孚、信:一心之谓诚,尽己之谓忠;存于中之谓孚,见于事之谓信。端蒙。[13]
如果分析起来,孚存于中,是德性;信见于事,是德行。道是人所共由,即道是指客观普遍的法则,德是指一个人特有的品质,至善是理的极致。用“得”或“得之于身”来申释德,这是源自先秦的传统,即德者得也。
就心性论而言,朱子认为:“存之于中谓理,得之于心为德,发见于行事为百行。节。”[14]此言分析最明:理是存之于中的,即心之所具的;德是得之于心的,是心的一种品质、属性;行是见之于行事的行为。不过仁义礼智之为理,是人之性,存于心中;仁义礼智又是德,是得之于心的。这两者如何安顿衔接?朱子的名言“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也”,就仁是爱之理说,爱是情,仁作为性理是情的内在根据,这是清楚的。但就仁者心之德说,仁既然已经是理,理和心之德是什么关系?情之理,心之德,是同是异?从朱子的这些表述看来,情之理不等于心之德,是说仁既是存之于中的情之理,也是得之于心的心之德,既是性,也是心,而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这样看来,四德有性理和心德的不同用法。
朱子又说:“德是得于天者,讲学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节。”[15]存于中是性理,这应当是清楚的。在理学思想中,德性作为品质,是属心还是属性?抑或是用心、性以外的概念来表达?理学有没有品质概念?从这段所说看,如果说徳是得自于天的,那就是性;如果说徳是“讲学而得之”,则不是性,只能是作为心之品质的德,这里的“徳”就是品质、德性的概念。
三、意思与气象
朱子讲五常,因为要与乾之四德对应,往往仅举仁义礼智,而不及信。这不仅是要把人之四德与天之四德相对,也与朱子对信的定位及五常与五行对应的思想有关。朱子认为信如五行之土,信只是证实仁义礼智的实有,这个说法与先秦两汉的思想是不同的。
下面来看朱子论仁义礼智的意思与气象,“意思”在这里具有字义解释的意义,但不是定义式的解释,而是一种价值含义的解释。
吉甫问:“仁义礼智,立名还有意义否?”曰:“说仁,便有慈爱底意思;说义,便有刚果底意思。声音气象,自然如此。”直卿云:“六经中专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义而不言礼智者,仁包礼,义包智。”方子。节同。佐同。[16]
仁义作为价值概念,其本身带有价值的意味,意思、气象都是指价值概念含蕴和发显的价值气息。可见,人道四德的“意思”,是指德目的价值蕴涵,是属于道德哲学的讨论。仁的“意思”是慈爱温和,义的“意思”是刚毅果断,如此等等。
朱子又说:“生底意思是仁,杀底意思是义,发见会通是礼,深藏不测是智。节。”[17]这里所谓生的意思是指宇宙间生命、生生的意思,本属宇宙论,但在朱子这里,宇宙论的意思和道德论的意思可以互通互换,如说仁的意思是生,也可以说生的意思是仁,仁和生成为相互说明的概念;又如义是杀的意思,也可以说杀的意思是义,等等。生与仁的连接是道学的一大发明,到朱子则将此种连接扩大,把仁义礼智通通和自然世界的属性连接起来,使仁义礼智更加普遍化,即具有宇宙论的普遍意义。这可以说是一种天人合一思维的体现。
蜚卿问:“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唯为私意所汩,故生意不得流行。克去己私,则全体大用,无时不流行矣。”曰:“此是众人公共说底,毕竟紧要处不知如何。今要见‘仁’字意思,须将仁义礼智四者共看,便见‘仁’字分明。如何是义,如何是礼,如何是智,如何是仁,便‘仁’字自分明。若只看‘仁’字,越看越不出。”曰:“‘仁’字恐只是生意,故其发而为恻隐,为羞恶,为辞逊,为是非。”曰:“且只得就‘恻隐’字上看。”道夫问:“先生尝说‘仁’字就初处看,只是乍见孺子入井,而怵惕恻隐之心盖有不期然而然,便是初处否?”曰:“恁地靠着他不得。大抵人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仁,便是个温和底意思;义,便是惨烈刚断底意思;礼,便是宣著发挥底意思;智,便是个收敛无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圣门却只以求仁为急者,缘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温厚底意思在这里,到宣著发挥时,便自然会宣著发挥;到刚断时,便自然会刚断;到收敛时,便自然会收敛。若将别个做主,便都对副不着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问:“仁即性,则‘性’字可以言仁否?”曰:“性是统言。性如人身,仁是左手,礼是右手,义是左脚,智是右脚。”道夫。[18]
仁是生生不已的思想,从北宋道学如明道强调以来,把仁和宇宙流行的趋向打通,扩大了仁学的范围,加深了对仁的理解。朱子在此基础上强调,仁的理解也要结合义礼智一起来看。但朱子也指出,以仁为生意,是通向宇宙论的说法,不是价值论的说法,不是德性论的说法。朱子指出,仁义礼智是人之德性,这里所用的“德性”应当与朱子一般所用的“性”有所不同,而接近心,即心之德。所以朱子主张“常存得温厚底意思在这里”,这里的“存得”、“在这里”,应当不仅指性,而且指心之德性,即心中常存温厚的意思。
至于四德的意思,照这里所说,仁是温和的意思,义是惨烈刚断的意思,礼是宣著发挥的意思,智是收敛的意思。以礼的意思为“宣著发挥”,与前面一条所说“发见会通”是一致的;以智的意思为“收敛”,与前面所说的“深藏不测”也是一致的。这种“意思”的说法,与单纯的“理”或“性理”的说法,还是有差别的。
总之,意思说是朱子四德论的一个特色,值得进一步讨论。当然,朱子不仅讨论仁义礼智四德,也讨论元亨利贞四德。朱子曾说:“元亨利贞本非四德,但为大亨而利于正之占耳,《乾》卦之《彖传》、《文言》乃借为四德,在他卦,尤不当以德论也。”[19]朱子认为《周易》本文的元亨利贞只是占辞,没有道德意义,但《彖传》和《文言》把元亨利贞发挥为四德,这已不是《周易》的《乾》卦经文的本义了。但《彖传》和《文言》发挥的四德,在后来的哲学讨论中越来越有意义,成为易学哲学史在宇宙论方面的重要讨论,为后世的宇宙论提供了基本的模式。
四、生气流行
朱子四德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贯彻了“生气流行”的观念来理解四德:
郑问:“仁是生底意,义礼智则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气。春生时,全见是生;到夏长时,也只是这底;到秋来成遂,也只是这底;到冬天藏敛,也只是这底。仁义礼智割做四段,一个便是一个;浑沦看,只是一个。”淳[20]
这是说,天地之间只是一气流行,这个一气流行又称一元之气。一元之气就是从整体上看,不分别阴阳二气。一气是流行反复的:“流行”即不断运行,“反复”是说流行是有阶段的、反复的,如一年四季不断流行反复。四季分开来看,每个不同;连接起来看,则只是一元之气流行的不同阶段。朱子认为,仁义礼智的关系也是如此:分别来看,仁义礼智各是一个道德概念;连接起来看,仁义礼智都是仁,都是作为生意的仁在不同阶段的表现。
所以,朱子又说:“仁,浑沦言,则浑沦都是一个生意,义礼智都是仁;对言,则仁与义礼智一般。淳。”[21]就分别来说,与义礼智相区别的“仁”是生意,“生意”即生生不息之倾向;而就整体来说,仁义礼智都是仁的表现,都是生生之意的不同阶段、不同方面的表现。
“仁有两般:有作为底,有自然底。看来人之生便自然如此,不待作为。……大凡人心中皆有仁义礼智,然元只是一物,发用出来,自然成四派。如破梨相似,破开成四片。如东对著西,便有南北相对;仁对著义,便有礼智相对。以一岁言之,便有寒暑;以气言之,便有春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便有金木水火土。且如阴阳之间,尽有次第。大寒后,不成便热,须是且做个春温,渐次到热田地。大热后,不成便寒,须是且做个秋叙,渐次到寒田地。所以仁义礼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仁流行到那田地时,义处便成义,礼、智处便成礼、智。且如万物收藏,何尝休了,都有生意在里面。如穀种、桃仁、杏仁之类,种著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见得都是生意。如春之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渐渐收敛,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进去,秋冬是退后去。正如人呵气,呵出时便热,吸入时便冷。”明作。[22]
仁是生意,有流行。“元只是一物”,这里指仁;“发用出来,自然成四派”,指仁义礼智。朱子认为天地间事物都是如此,一元流行,而自然形成几个次第界限,如气之流行便成春夏秋冬,木之流行便成金木水火土,循环往复。冬至一阳来复,生意又复发起,生长收藏,不断循环。仁之流行,循着四个阶段往复不断,不管仁的流行所形成的仁义礼智四阶段与生物流行自然成春夏秋冬四季如何对应一致,仁作为生意流行的实体,已经不是静而不动的理、性了。
那么,仁是生意,仁是不是生气呢?上面引用的陈淳录的材料只是把仁义礼智与一元之气的流行加以类比,认为仁相当于一元生气,两者的结构是完全一样的,还没有说明仁是生气。
下面的材料则更进了一步。
问:“仁是天地之生气,义礼智又于其中分别。然其初只是生气,故为全体。”曰:“然。”问:“肃杀之气,亦只是生气?”曰:“不是二物,只是敛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气。”可学。[23]
分别来看,春是生气,冬是肃杀之气,但春夏秋冬,只是一气流行的不同阶段;以冬之肃杀而言,冬季的肃杀之气并不是与春季开始的生气不同的另一种气,只是生气运行到此阶段,有所收敛。照这里的答问来看,朱子不仅认为仁是生意,也肯定仁是生气;不仅仁是生气,仁义礼智全体也是生气。在这个意义上朱子也采用二程“专言之则包四者”的说法,说仁包义礼智(信),只是他已赋予仁包四者以生气流行的意义。从理论上来分析,如果仁是生气流行,这个仁就不能是理,不能是性,而近于生气流行的总体了。在心性论上,这样的仁就接近于心体流行的总体了。只是,朱子并没有把这一思想彻底贯彻到心性论。
《朱子语类》又载:
蜚卿问:“仁包得四者,谓手能包四支可乎?”曰:“且是譬喻如此。手固不能包四支,然人言手足,亦须先手而后足;言左右,亦须先左而后右。”直卿问:“此恐如五行之木,若不是先有个木,便亦自生下面四个不得。”曰:“若无木便无火,无火便无土,无土便无金,无金便无水。”道夫问:“向闻先生语学者:‘五行不是相生,合下有时都有。’如何?”曰:“此难说,若会得底,便自然不相悖,唤做一齐有也得,唤做相生也得。便虽不是相生,他气亦自相灌注。如人五脏,固不曾有先后,但其灌注时,自有次序。”久之,又曰:“‘仁’字如人酿酒:酒方微发时,带些温气,便是仁;到发到极热时,便是礼;到得熟时,便是义;到得成酒后,却只与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间,早间天气清明,便是仁;午间极热时,便是礼;晚下渐叙,便是义;到夜半全然收敛,无些形迹时,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道夫。[24]
这也是用酿酒的过程和一日早晚的过程,来类比说明四德是流行的不同阶段。这样一来,仁义礼智四德不再只是道德的德目,而变为与元亨利贞四德一样,也是自然之德,仁义礼智也可以用来描述自然流行的阶段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仁义礼智四德也自然化了,仁义礼智与元亨利贞的同一,导致自然与社会节度的混一。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灌注”即流住、流行,指五行之气自相灌注,灌注的次序便是五行展开的次序。朱子这里所说,也意味着仁义礼智四德与五行之气一样,是按一定的灌注次序展开的。只是,这里四德展开的次序是仁礼义智,而不是仁义礼智,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把仁义礼智四德类比于五行之气的流行灌注,这本身就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显示出气的思维对朱子四德论的影响。
当然,在朱子的论述中,酿酒和一日早晚的例子,不如一年四季变化更为常用:
只如四时:春为仁,有个生意;在夏,则见其有个亨通意;在秋,则见其有个诚实意;在冬,则见其有个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尝息!本虽凋零,生意则常存。大抵天地间只一理,随其到处,分许多名字出来。四者于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见仁义礼智实有此理,不是虚说。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贞亦重,以明终始之义。非元则无以生,非贞则无以终,非终则无以为始,不始则不能成终矣。如此循环无穷,此所谓‘大明终始’也。”大雅。[25]
这样来看,自然流行的节度,总是生、长、遂、成,不断循环往复;与生、长、遂、成四个阶段相对应,便是元、亨、利、贞四德,四德分别是生、长、遂、成各自阶段的性质、属性、性向,也可以说是每个阶段的德性。照朱子看来,与生、长、遂、成相对应的属性、德性,既可以说是元、亨、利、贞,也可以说是仁、义、礼、智,这两个说法是一致的。这无异于说,仁义礼智在这里是自然属性的范畴。这就把仁义礼智自然化、宇宙论化了,这样的仁义礼智就不仅有道德的意义,也具有宇宙论的意义。要强调的是,当朱子把仁义礼智作为自然化的范畴时,绝不表示作为自然化了的仁义礼智与作为人道的仁义礼智概念已经根本不同,已经是两回事;不,在朱子哲学,自然化的仁义礼智与人道的仁义礼智仍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只是用法与意义有广有狭而已。
所以,朱子更断言仁义礼智便是元亨利贞:“仁义礼智,便是元亨利贞。若春间不曾发生,得到夏无缘得长,秋冬亦无可收藏。泳。”[26]这就把仁义礼智之间的关系看成与元亨利贞同样的流行,这在无形之中使仁义礼智在一定程度上也变成为具有宇宙论流行意义的实体——气。而这里的元亨利贞也不能说只是性了。
《朱子语类》:“问:‘元亨利贞有次第;仁义礼智因发而感,则无次第。’曰:‘发时无次第,生时有次第。’佐。”[27]“发时无次第”是指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感发生是没有一定次序的,“生时有次第”是指仁义礼智作为生气流行具有一定的先后次序。按学生的提问,元亨利贞的次序即春夏秋冬的流行次序,是实际流行的次第,而仁义礼智都是由感而发,不一定有固定的次序。这样,二者不就是不一致了吗?学生所说的仁义礼智还是局限于性情的仁义礼智,而朱子所说的流行的仁义礼智已不限于性情之发,“生时有次第”就是指作为生气流行的仁义礼智有其次序。这些都再次体现了四德具有生气流行的意义。当然,在最低的程度上,也可以说“生时有次第”包含着仁义礼智四者在逻辑上的次序。
仁所以包三者,盖义礼智皆是流动底物,所以皆从仁上渐渐推出。仁智、元贞,是终始之事,这两头却重。如坎与震,是始万物、终万物处,艮则是中间接续处。[28]
说“义礼智皆是流动底物”,即是把仁义礼智看作流行的事物,而流行是一个过程,一个渐渐起伏变化的过程;这一无尽的过程是由一系列不断延伸的单元所组成,每个单元都由开始、中间、结束构成内部三个阶段,或由生、长、遂、成构成内部四个阶段。一方面,每个单元的后续阶段都是由开始阶段渐渐衍生出来的;另一方面,每个单元中开始的阶段和终结的阶段更为重要。
味道问:“仁包义礼智,恻隐包羞恶、辞逊、是非,元包亨利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不知木如何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气。有生气,然后物可得而生;若无生气,则火金水皆无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时举。[29]
元是生气,元包亨利贞;仁是生意,仁包义礼智;木是生气,木包火金水。于是四德、五常、五行三者被看成是同一生气流行的不同截面而已。至于五常中的信、五行中的土,在这种看法中都被消解了实体意义,而起保障其他四者为实存的作用。这是另外的问题,不在这里讨论。
朱子说:
“仁”字须兼义礼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知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于春:春则生意之生也,夏则生意之长也,秋则生意之成也,冬则生意之藏也。自四而两,两而一,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又曰:“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而成终;犹元为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故不贞则无以为元也。”又曰:“贞而不固,则非贞。贞,如板筑之有干,不贞则无以为元。”又曰:“文言上四句说天德之自然,下四句说人事之当然。元者,乃众善之长也;亨者,乃嘉之会也。嘉会,犹言一齐好也。会,犹齐也,言万物至此通畅茂盛,一齐皆好也。利者,义之和处也;贞者,乃事之桢干也。‘体仁足以长人’,以仁为体,而温厚慈爱之理由此发出也。体,犹所谓‘公而以人体之’之‘体’。嘉会者,嘉其所会也。一一以礼文节之,使之无不中节,乃嘉其所会也。‘利物足以和义’,义者,事之宜也;利物,则合乎事之宜矣。此句乃翻转,‘义’字愈明白,不利物则非义矣。贞固以贞为骨子,则坚定不可移易。”铢。[30]
与中年的仁说不同,后期朱子更强调对仁的理解要合义礼智三者一起看,而这种四德兼看的方法要求与四季的看法相参照。如春夏秋冬四季不同,但夏秋冬都出于春起的生意,四季都是生意流行的不同阶段,即生、长、成、藏。本来,元亨利贞是生长收藏的性,不就是生长收藏的过程,而在这里,仁义礼智不像是性,而成了流行总体和过程本身。与四季类似,仁是仁的本体,礼是仁的节文,义是仁的断制,知是仁的分别,四德都出于仁,是仁的由始至终的不同阶段。于是,仁义礼智作为人事之当然,与元亨利贞作为天德之自然,成为完全同构的东西。虽然朱子并没有说人事四德即来源于自然天德,但他把这些都看成天地之化的法则或机轴。虽然生意流行与生气流行不一定就是一回事,但整体上看,两种说法应是一致的。
朱子下面的话讲得很有意味:
“今日要识得仁之意思是如何。圣贤说仁处最多,那边如彼说,这边如此说,文义各不同。看得个意思定了,将圣贤星散说体看,处处皆是这意思,初不相背,始得。……人之所以为人,其理则天地之理,其气则天地之气。理无迹,不可见,故于气观之。要识仁之意思,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今只就人身己上看有这意思是如何。才有这意思,便自恁地好,便不恁地干燥。……这不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有这个浑全流行物事。此意思才无私意间隔,便自见得人与己一,物与己一,公道自流行。须是如此看。孔门弟子所问,都只是问做工夫。若是仁之体段意思,也各各自理会得了。今却是这个未曾理会得,如何说要做工夫!且如程先生云:‘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上云:‘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恰似有一个小小底仁,有一个大大底仁。‘偏言则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仁之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礼义智底。若如此说,是有两样仁。不知仁只是一个,虽是偏言,那许多道理也都在里面;虽是专言,那许多道理也都在里面。”致道云:“如春是生物之时,已包得夏长、秋成、冬藏意思在。”曰:“春是生物之时,到夏秋冬,也只是这气流注去。但春则是方始生荣意思,到夏便是结里定了,是这生意到后只渐老了。”贺孙曰:“如温和之气,固是见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节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贺孙。[31]
朱子在这里特别强调要从气观仁,从气识仁,这种观、识是要把握仁的“意思”,而仁的意思就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朱子强调,这一浑然温和之气并非仅仅是仁的道德气息,而是指出此气就是天地阳春之气。值得注意的是,朱子也并非只是纯粹从气观仁,也同时从理观仁,故说了“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后,即说“其理便是天地生物之心”。浑然温和之气之中有理,此理即天地生物之心。人的存在本来是理气合一、浑然流行的,而现实的人必须自觉地在自己身上体现这种浑然流行,培养此种德性。如果在自家身上能体现这种仁的意思,使这个意思遍润己身,这个意思便能无间隔地流行于人己人物之间。如叶贺孙和赵致道所言,温和之气可以见仁,而温和之气的流行(流注)自然有节文(礼),自然得宜(义),自然明辨(智)。
或问《论语》言仁处。曰:“理难见,气易见。但就气上看便见,如看元亨利贞是也。元亨利贞也难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时尽是温厚之气,仁便是这般气象。夏秋冬虽不同,皆是阳春生育之气行乎其中。故‘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如知福州是这个人,此偏言也;及专言之,为九州安抚,亦是这一个人,不是两人也。故明道谓:‘义礼智,皆仁也。若见得此理,则圣人言仁处,或就人上说,或就事上说,皆是这一个道理。’正叔云:‘满腔子是恻隐之心。’”曰:“仁便是恻隐之母。”又曰:“若晓得此理,便见得‘克己复礼’,私欲尽去,便纯是温和冲粹之气,乃天地生物之心。其余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气象。《论语》但云求仁之方者,是其门人必尝理会得此一个道理。今但问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随其人而告之。……南升。(疑与上条同闻。)[32]
照这里所说,天地生发之理是看不见的,但可以就天地之生气来看,元亨利贞是气,是可见的;更容易看的是四季,春夏秋冬便是气的流行。在这里,四季的四个阶段的更换不是最重要的,四季中贯通的生育之气才是最重要的。这个生气便是仁。这里所说的“私欲尽去,便纯是温和冲粹之气”,显然是指人的身心而言:朱子认为,这种人在私欲尽去后达到的温和之气,也就是天地生物之心、天地生物之气,这是以人合天的状态。这些都体现了朱子以温和之气为仁的思想。
可见,在朱子哲学中,仁义礼智四德不仅仅是性理,在不同的讨论中,四德也具有其他的意义,如与存于中不同的心德说,如意思说所表达的道德信息说,如宇宙论意义的生气流行说,等。就天地造化而言,仁既是理,也是气;就人心性命而言,仁既是性,也是心。虽然仁的这几层意义是不同的,但它们之间不一定是互相否定的,而是可以共存的。
总之,上述仁论与四德论的讨论,使得朱子思想中心、性、气的关系不再像以前人们所理解的那么简单,其中包含的哲学意义值得作更深入的探讨。朱子的这些思想,使我们得以了解朱子不仅发挥继承了伊川的理学思想,也与明道的仁学思想有其内在的联系。对朱子仁学的思想,以往整体研究不够,需要更深入地分疏和诠释。从一定的意义上来看,朱子的哲学思想体系可以从两个基本方面来呈现:一是理学,一是仁学。从理学的体系去呈现朱子哲学,是我们以往关注的主体;从仁学的体系去呈现朱子思想,以往甚少。如果说理气是二元分疏的,则仁在广义上是包括理气的一元总体。在这一点上,说朱子学总体上是仁学,比说朱子学是理学的习惯说法,也许更能凸显其儒学体系的整体面貌。
朱子四德说续论
陈来
在《朱子思想中的四德论》一文中,我们主要是利用《朱子语类》卷六《仁义礼智等名义》的资料来说明朱子的关于仁义礼智四德(以及与之关联的元亨利贞四德)的思想。[1]这里,我们依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下简称《文集》)、《朱子语类》(下简称《语类》)的其他材料来进一步讨论其四德说,主要使用《文集》中的《元亨利贞说》、《周礼三德说》、《仁说》,《玉山讲义》及相关讨论,以及《语类》及《周易本义》论《易·乾卦》的资料。
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七有《元亨利贞说》,文云:
元亨利贞,性也;生长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长、以利收、以贞藏者,心也。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正谓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言天之付与万物者,谓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为心”,亦谓此也。[2]
《元亨利贞说》写于朱子四十二岁前后,属于其前期思想。朱子当时以元亨利贞四者为性,与生长收藏相对待;这和以仁义礼智为性、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为情,是相对应的也是一致的。元亨利贞是天地之性,天地之化以天地之性为根据,而实现生长收藏的过程。同理,仁义礼智是人之性,人心之动以人之性为根据,而发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情感。这种分析体现了朱子当时对性情之辨的重视。在这种话语中,元亨利贞只是性,与生长收藏的现实过程被严格分别开来,生长收藏相当于情,也就是用。
不久,朱子又有《仁说》之作,其中说: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请试详之。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块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3]
依朱子这里的看法,仁是“人心”之德,元亨利贞是“天地之心”之德,这是明确把仁和元、亨、利、贞都作为“德”。就心之德作为性而言,“元”包“亨利贞”,这是从体上来看的。朱子还认为,四季运行是天地之化的过程,是用,而天地之德则是运行过程的内在根据。从天地运行的大用着眼,春生之气贯通于春夏秋冬的有序连接,无所不通。如果从人的方面看,就心之徳言,“仁”包“义礼智”;就四德的发用言,恻隐贯通于爱恭宜别四种情感。在这种论述中,春生之气相当于恻隐,都属用的层面,在这个意义上,运行、流行是就“用”言,而仁义礼智或元亨利贞是“体”,是“性”,是无所谓流行的。既然性无所谓流行,这说明前期朱子思想在性情体用之辨的意识主导下,不采用“流行”一类的观念解释四德。我们在前文已说明,以“流行”的观念解释四德关系,见于朱子后期思想,而“运用流行”的哲学观念,本质上,是和气的哲学思维分不开的。从哲学上看,还应当注意的是,在性和情两者的分析之外,还有一种总体的了解,这就是所谓“以元生、以亨长、以利收、以贞藏者,心也”,心不是本性、体,也不是过程、用,而是包涵体用的、存在与活动的总体。
二
《文集》卷七四有《玉山讲义》,是朱子晚年六十五岁经过江西玉山时所作,其中论述了四德说。此讲义可分为三部分,其第一部分云:
时有程珙起而请曰:“《论语》多是说仁,《孟子》却兼说仁义。意者夫子说元气,孟子说阴阳,仁恐是体,义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异,固所当讲。然今且当理会何者为仁?何者为义?晓此两字义理分明,方于自己分上有用力处,然后孔孟之言有同异处可得而论。如其不晓,自己分上元无工夫,说得虽工,何益于事?且道如何说个‘仁义’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个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于此。韩文公云‘人之所以为性者五’,其说最为得之。却为后世之言性者多杂佛老而言,所以将‘性’字作知觉心意看了,非圣贤所说‘性’字本指也。”[4]
程珙的问题很有意思,他说孔子只说仁,不说仁义,因为孔子说仁是讲元气;而孟子说仁义,是讲阴阳二气。这个讲法其实合于朱子晚年以仁为生气流行贯通四者的思想。程珙还把仁义的关系理解为体用的关系。朱子认为他讲的不分明,强调“仁义”二字的前提先要从人性论上去理解。天赋予每个所生之物一个道理,人身得到的这个道理便是性,性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五者。所以这五种都是人性的道理。就五者都是人性的内容而言,彼此并无体用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不能说仁是体、义是用。
其第二部分云:
五者之中,所谓信者是个真实无妄底道理,如仁义礼智皆真实而无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须说,只“仁义礼智”四字于中各有分别,不可不辨。盖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礼则是个恭敬撙节底道理,智则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体。方其未发,漠然无形象之可见;及其发而为用,则仁者为恻隐,义者为羞恶,礼者为恭敬,智者为是非,随事发见,各有苗脉,不相淆乱,所谓情也。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谓之端者,犹有物在中而不可见,必因其端绪发见于外,然后可得而寻也。盖一心之中,仁义礼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体用又自各有分别,须是见得分明。[5]
“仁是温和慈爱的道理”,道理即理,道理之在我者即性,说明这里是把“仁”作为理看待的。所谓温和慈爱的道理,与《四书章句集注》所说“仁者爱之理”[6]的意思相通,也就是说,“仁”是发为慈爱的内在根据。慈爱是已发而为用的,属于发见的层次;仁则是体,是未发的层次。义、礼、智皆然。仁义礼智之间的分别,亦表现在他们各自的发见不同,仁发为慈爱,义发为断制,礼发为恭敬,智发为是非。“仁”是发为慈爱的根据道理,“义”是发为断制的根据道理,“礼”是发为恭敬的根据道理,“智”是发为是非的根据道理。但朱子晚年并不简单直截地说仁是恻隐之理,义是羞恶之理,礼是恭敬之理,智是是非之理,而常常说“仁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截割底道理”等,表示朱子的这种“道理”的表述还是有其特殊意义,这就是,朱子这时已经常常用“意思说”来表达其四德说了(详见前文)。此外,在这种说法中,朱子所体现的态度是即用明体、即用论体、不可离用说体,这与体用分析的说法有别。
第三部分云:
然后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见得“仁义”两字是个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实不过于一阴一阳而已。于此见得分明,然后就此又自见得“仁”字是个生底意思,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之断制也,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正如春之生气贯彻四时,春则生之生也,夏则生之长也,秋则生之收也,冬则生之藏也。故程子谓“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正谓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专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义礼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义,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于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个“义”字,但于一理之中分别出来耳。其又兼言礼智,亦是如此。盖礼又是仁之着,智又是义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尝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论体用亦有两说,盖以仁存于心而义形于外言之,则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而以仁义相为体用。若以仁对恻隐、义对羞恶而言,则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发、已发相为体用。若认得熟、看得透,则玲珑穿穴、纵横颠倒无处不通,而日用之间,行着习察,无不是着功夫处矣。”[7]
这里就用了“意思说”,强调仁是生的意思,即仁作为“生意”的思想。朱子认为仁之生意通贯周流于仁义礼智四者之中,初看起来,仁之生意贯通的讲法似是指仁的普遍性,而以四者为特殊性;其实这种“通贯周流”的讲法与普遍性体现为特殊性的思维还是有所不同的,要言之,“通贯周流”是气论的表达方式。分别而言,仁是仁之生意的本体的表现,义是仁之生意表现为断制的阶段,礼是仁之生意的节文,智是仁之生意表现为分别。朱子认为,这正如春之生气贯彻四时之中一样,朱子用这种周流贯通之气的流行论,发挥了程颢的生意说与程颐仁“包”四德的观念,使得“仁”也成为或具有流行贯通能力的实体。这样的仁,既不是内在的性体,又不是外发的用,而是兼体用而言的了。气论的思维在这里也明显发生作用。这些就与前期的思想有所不同了。朱子的这一思想与程珙所提的“仁是元气”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元气不如生气说得更清楚,“元气”必须落在“生”字上讲,这是二程到朱子的仁说所一直强调的。关于礼是仁之著,智是义之藏的说法,以及仁义的体用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结合《语类》再予讨论。
由此可见,《玉山讲义》主要包含两个思想,一个是四德与四端的未发已发说,一个是仁之生意流行于四德说。在稍后答陈器之书中,朱子复述了这两点,并对“对立成两”、“仁智终始”等问题做了进一步阐述。
三
《文集》卷五八载《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该信可分为四节,其开首言:
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孔门未尝备言,至孟子而始备言之者,盖孔子时性善之理素明,虽不详著其条而说自具。至孟子时,异端蜂起,往往以性为不善,孟子惧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浑然全体,则恐其如无星之秤、无寸之尺,终不足以晓天下,于是别而言之,界为四破,而四端之说于是而立。[8]
这是解释为什么孔子不必讲四端,而孟子必须讲四端。朱子指出,从整体上看,性即太极;如果从具体内容上看,性具众理;性中的众理以仁义礼智四者为主,孟子发明四端之说即是发明仁义礼智之性,是为了更好地证明性善说。此为第一节。
盖四端之未发也,虽寂然不动,而其中自有条理,自有间架,不是儱侗都无一物,所以外边才感,中间便应。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而恻隐之心于是乎形。如过庙、过朝之事,感则礼之理便应,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盖由其中间众理浑具,各各分明,故外边所遇,随感而应,所以四端之发,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为四,以示学者,使知浑然全体之中而粲然有条若此,则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发也,所谓浑然全体,无声臭之可言,无形象之可见,何以知其粲然有条如此?盖是理之可验,乃依然就他发处验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虽无形,而端的之发最可验。故由其恻隐,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恶,所以必知其有义;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礼;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无是理于内,则何以有是端于外?由其有是端于外,所以必知有是理于内,而不可诬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是则孟子之言性善,盖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9]
此为第二节。性虽然是太极,但其中自有条理,即包含仁义礼智各不同的理。这些理本来是内在心中的,当一定的外事来感时,一定的理便有所应,于是便有四端之发。与性情对言的已发未发说有所不同,这里强调从已发到未发需要“外感”作为媒介、中介。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而恻隐之心于是乎“形”。“感—应—形”的分别和联系是与朱子“心具众理而应万事”的思想一致的。朱子在这里强调性中自有条理,不同的外感引起不同的性理的响应,从而表达出不同的情。朱子论心的思想在前期注重已发未发,后期更重视具众理而应万事。由外证内,以情证性,溯用知体,这是朱子立足于四端而证明四德的方法。
仁义礼智既知得界限分晓,又须知四者之中仁义是个对立底关键。盖仁,仁也,而礼则仁之著;义,义也,而智则义之藏。犹春夏秋冬虽为四时,然春夏皆阳之属也,秋冬皆阴之属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是知天地之道不两则不能以立,故端虽有四,而立之者则两耳。仁义虽对立而成两,然仁实贯通乎四者之中,盖“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则春之生也,夏则春之长也,秋则春之成也,冬则春之藏也。自四而两,自两而一,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是天地之理固然也。[10]
朱子指出,天地之道不两则不能以立,“两”就是对立的两个要素,就是说任何事物,其内部都必有两个对立的要素,事物才能存在。从这个意义来说,四端中应有两个使整体得以存在的要素,这两个要素就是仁和义。在这种理解下,仁和礼归于仁,礼是仁的显发;义和智归于义,智是义的退藏。这个思想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到。朱子又指出,仁和义对立而成两,符合事物存在发展的辩证法,但四者又贯通着“一”,“一”使事物获得整体性和连续性,这个一就是仁。四归于二,二归于一,于是仁成为四者最终统一的根源。这是第三节。
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则恻隐、羞恶、恭敬是三者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为非尔,是以谓之藏也。又恻隐、羞恶、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则有两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故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能成终,犹元气虽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此也。[11]
这最后一节是讲智的意义,由于朱子把四德的关系看成是流行终始的关系,于是不仅突出了仁,也突出了智。朱子认为元亨利贞流行不已,贞是前一个过程的结束,又孕育了新的过程开始,故言元生于贞。朱子认为仁义礼智和元亨利贞相同,贞元之际与仁智之际相同,智和贞一样,具有成终成始的地位,仁智之交,就是旧的流行结束而新的流行开始。《语类》也说:
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贞亦重,以明终始之义。非元则无以生,非贞则无以终,非终则无以为始,不始则不能成终矣。如此循环无穷,此所谓“大明终始”也。大雅。[12]
这种四德论的讲法是由于把仁义礼智与元亨利贞完全对应所引起的,宇宙论的元亨利贞模式深刻影响了他对仁义礼智四德的理解。在这一节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此即把“元”说为“元气”。于是,朱子对于元或仁的说法,越来越不就性、理而言,而更多就具有生成形态的气而言了。
第二节所说的已发未发,涉及仁义体用的问题。前面说到,《玉山讲义》的第三部分言:“若论体用亦有两说,盖以仁存于心而义形于外言之,则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而以仁义相为体用。若以仁对恻隐义对羞恶而言,则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发、已发相为体用。若认得熟、看得透,则玲珑穿穴、纵横颠倒无处不通,而日用之间,行著习察,无不是著功夫处矣。”仁义礼智四德作为性理,为未发,为体;恻隐羞恶四端为情,为已发,为用。分言之,仁为体而恻隐为用,义为体而羞恶为用,这就是已发未发相为体用。朱子亦认为,孟子所说仁人心,义人路,则是以仁存于心,义形于外而言,是另一种体用的对待。
四
《文集》卷六七有《周礼三德说》,该文虽然不是讨论四德之说,但其中讨论周礼三德说涉及的对德、行的理解也值得注意。文之开首云:
或问:师氏之官,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何也?曰:至德云者,诚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则天人性命之理、事物当然之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也。敏德云者,强志力行、畜德广业之事;“行”则理之所当为,日可见之迹也。孝德云者,尊祖爱亲,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恶,则以得于己者笃实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恶,而自不忍为者也。(至德以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为行本,司马温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恶,则赵无愧、徐仲车之徒是已。)凡此三者,虽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资质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专务其一而可以为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见其相须为用而不可偏废之意。盖不知至德,则敏德者散漫无统,固不免乎笃学力行而不知道之讥。然不务敏德而一于至,则又无以广业,而有空虚之弊。不知敏德,则孝德者仅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于神明。然不务孝德而一于敏,则又无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陈备举而无所遗,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资、精粗两尽而不倚于一偏也。[13]
“三德”、“三行”之说出于《周礼·地官·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14]这是古代德行论的早期表达。
朱子对三德、三行作了明确的哲学的、伦理学的解说。在朱子看来,以三种德行教国子,至德是指心而言,是关于正心诚意的内心修养。所谓至德以为道本,是说至德是掌握性命之理、践行当然之则、实行治国平天下之术的根本与基础,突出了德性对哲学理解、道德实践、政治施行的根本意义,强调心徳是道术的根本基础。强志力行,即《礼记·儒行》第一条所说的强学力行;一切行为都是由心志而发,人能强化心志,力行理所当为,使心志在行为事迹上表现出来,这是敏德。所谓敏德以为行本,是指由心志落实到行为是德行的一般特性。照朱子的这个说法,从德行论来看,可以说正心诚意是根本的德行,称为至德;强志力行是一般意义的德行,称为敏德;尊祖爱亲是专指孝的特殊德行,称为孝德。三徳可以说区别了根本德行、一般德行、特殊德行。
以三德教国子,说明这是一种道德教育,其目的是培养成人。但把国子培养为成人,必须使他们同时培养三德,不可偏专其中之一。朱子认为三德互相补充、互相需要,“未有专务其一而可以为成人者也”,也就是说三德具有统一性。没有至德,敏德只能笃行,而没有方向,不能知“道”;没有敏德,至德就会流于空洞,无法具体落实,也无法拓宽事业;不落实到孝德,敏德就失去基础。至德是方向,敏德是分殊,孝德是基础。
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何也?曰:德也者,得于心而无所勉者也;行则其所行之法而已。盖不本之以其德,则无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实之以其行,则无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进。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继之,则虽其至末至粗亦无不尽,而德之修也不自觉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于至德、敏德,则无与焉。盖二者之行,本无常师,必协于一,然后有以独见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预言也。唯孝德则其事为可指,故又推其类而兼为友顺之目以详教之,以为学者虽或未得于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于心焉,则进乎德而无待于勉矣。况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于事而溯其原,则孰谓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学之学也;三行之教,小学之学也,乡三物之为教也亦然,而已详。[15]
三德之教和三行之教,涉及对德与行的分别。在对教三行的解释上,朱子解释了什么是德、行,他说“德也者,得于心而无所勉者也;行则其所行之法而已”。这是说,“德”是得于心的状态或性质,“行”是对规范的实行。朱子认为,德和行互相支持、互相连接,不以内心之德为本,就达不到自得,行为也不能自修;心之德不落实在行为表现出来,心难以持循,心德也不能进步。朱子也指出,人有时未得于心,但能勉而行之,在这种状态下不能说德在心中。但如此勉而行之,久而久之,合乎道德的行为的不断实行便可使人达到“得于心”,即促使德在心中形成,这时的行为便是从心中之德出发,不待勉强了。这是朱子对德性形成的一种看法。
朱子还说过:
耳之德聪,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将这意去思量体认。泳。[16]
聪、明是耳目的根本属性,仁是心的根本属性,德即指根本属性而言。
百行皆仁义礼智中出。节。[17]
百行是行为,仁义礼智是本性,这是强调一切行为都是发自于内在的本性,也体现了朱子德性论强调性理的特色。
五
《周易·说卦》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18]此后,儒学思想家常常依此思路,努力把仁义与阴阳、刚柔对应起来,以建立宇宙论的统一性说明。
问仁义礼智体用之别。曰:“自阴阳上看下来,仁礼属阳,义智属阴;仁礼是用,义智是体。春夏是阳,秋冬是阴。只将仁义说,则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若将仁义礼智说,则春,仁也;夏,礼也;秋,义也;冬,智也。仁礼是敷施出来底,义是肃杀果断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脏有许多事,如何见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解者多以仁为柔,以义为刚,非也。却是以仁为刚,义为柔。盖仁是个发出来了,便硬而强;义便是收敛向里底,外面见之便是柔。”僴。[19]
理学倾向于把“阴阳”作为普遍的哲学分析方法。按照这种分析,如果把仁义礼智四者归为阴阳两类,那么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何者为阳,何者为阴?朱子的主张是,仁和礼属于阳,义和智属于阴。在他看来,以流行的次序而言,是仁、礼、义、智,也就是仁相当于春,礼相当于夏,义相当于秋,智相当于冬。因此若要把四德分为阴阳的话,仁、礼为阳,义、智为阴;正如要把一年四季分为阴阳的话,以春夏为阳,以秋冬为阴。反过来说,如果把四季分为仁义二者,则以春夏为仁,以秋冬为义。这种思维是汉代以来阴阳气论的影响下形成的。
不过,这样一来,仁、礼、义、智的次序便和习惯所用的仁、义、礼、智的顺序有所不同了,朱子回答学生的疑问:
问:“孟子说仁义礼智,义在第二;《太极图》以义配利,则在第三。”曰:“礼是阳,故曰亨。仁义礼智,犹言东西南北;元亨利贞,犹言东南西北。一个是对说,一个是从一边说起。”夔孙。[20]
按朱子的理解,如同一个圆圈,顺着圆圈的次序是流行的次序,即仁、礼、义、智的排序。以流行言,仁对应元,礼对应亨,义对应利,智对应贞。如果不顺着圆圈,而以南北相对,东西相对,这样的次序就不是流行的次序,而是对待的次序,这就是仁、义、礼、智的排序。
问:“‘元亨利贞’,《乾》之四德;仁义礼智,人之四德。然亨却是礼,次序却不同,何也?”曰:“此仁礼义智,犹言春夏秋冬也;仁义礼智,犹言春秋夏冬也。”铢。[21]
这也是说明四德有两种排序。仁、礼、义、智的顺序是合乎元气流行的自然次序,这样的元亨利贞、仁义礼智都是被用气的流行来刻划的东西了,也就成为他所说的“流行之统体”了。
中国哲学中与“阴阳”分析相配合的是“刚柔”的分析。按上面的说法,仁属于阳,义属于阴,那么仁义与刚柔又如何对应呢?在一般人看来,仁有柔软的意思,应当属柔,不应当属刚,而朱子却认为仁应当属刚,不属于柔。如其晚年《答董叔重》书论此最明:
(董问)阴阳以气言,刚柔则有形质可见矣。至仁与义,则又合气与形而理具焉。然仁为阳刚,义为阴柔,仁主发生,义主收敛,故其分属如此。或谓杨子云“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盖取其相济而相为用之意。
(朱答)仁体刚而用柔,义体柔而用刚。[22]
汉代的扬雄以仁为柔,以义为刚,这是讲得通的。而朱子与之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是来自朱子从宇宙生化论讲四德,主张以发生论仁,以收敛论义,由于是以收敛为阴柔,所以便以发生为阳刚了。仁是发生原则,故仁属阳刚。值得注意的是,董铢在这里提出“仁义”是“合气与形而理具焉”,按这个说法,仁、义似乎不仅仅是性理,而是实存的气形统一整体或总体,其中具有理。当然,也可以说理气合而后生人,而有仁义礼智之性。这个说法应该是顺就朱子的说法而来,故朱子没有加以评论。
朱子曾与袁枢反复辨析阴阳刚柔之义,其《答袁机仲》书云:
凡此崎岖反复,终不可通,不若直以阳刚为仁、阴柔为义之明白而简易也。盖如此,则发生为仁、肃杀为义,三家之说皆无所牾,肃杀虽似乎刚,然实天地收敛退藏之气,自不妨其为阴柔也。
……又读来书,以为不可以仁义礼智分四时,此亦似太草草矣。夫五行五常五方四时之相配,其为理甚明而为说甚久,非熹独于今日创为此论也。[23]
这里朱子自己界定得很清楚,发生为刚,肃杀为柔,肃杀收敛退藏应属于阴柔,义为肃杀退藏,故当属于阴柔。故阳刚为仁,阴柔为义。
而朱子的这一说法,遭到了不少质疑,引发了朱子与这些质疑的辩难。如其《答袁机仲别幅》云:
……来喻以东南之温厚为仁、西北之严凝为义,此《乡饮酒义》之言也。然本其言虽分仁义,而无阴阳柔刚之别,但于其后复有阳气发于东方之说,则固以仁为属乎阳,而义之当属乎阴,从可推矣。来谕乃不察此而必欲以仁为柔、以义为刚,此既失之,而又病夫柔之不可属乎阳、刚之不可属乎阴也,于是强以温厚为柔、严凝为刚。又移北之阴以就南,而使主乎仁之柔;移南之阳以就北,而使主乎义之刚,其于方位气候悉反易之,而其所以为说者,率皆参差乖迕而不可合。又使东北之为阳、西南之为阴,亦皆得其半而失其半。愚于图子已具见其失矣。盖尝论之:阳主进而阴主退,阳主息而阴主消,进而息者其气强,退而消者其气弱,此阴阳之所以为柔刚也。阳刚温厚居东南,主春夏,而以作长为事;阴柔严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敛藏为事。作长为生,敛藏为杀,此刚柔之所以为仁义也。以此观之,则阴阳刚柔仁义之位岂不晓然?而彼杨子云之所谓“于仁也柔,于义也刚”者,乃自其用处之末流言之,盖亦所谓阳中之阴、阴中之阳,固不妨自为一义,但不可以杂乎此而论之尔。[24]
袁枢并不反对仁为阳,义为阴,但反对以仁为刚,以义为柔,而主张温厚为柔,严凝为刚,故仁为柔为阳,义为刚为阴。朱子坚持仁属于阳刚,义属于阴柔,阳刚主生长,阴柔主敛藏。他认为杨雄所说的“于仁也柔,于义也刚”,不是从本体上说的,而是从发用上说的,所以朱子主张“仁体刚而用柔,义体柔而用刚”,认为这样就可以全面地解决这个问题了。朱子又说:
前书所论仁义礼智分属五行四时,此是先儒旧说,未可轻诋。今者来书虽不及之,然此大义也,或恐前书有所未尽,不可不究其说。盖天地之间,一气而已,分阴分阳,便是两物,故阳为仁而阴为义。然阴阳又各分而为二,故阳之初为木为春为仁,阳之盛为火为夏为礼,阴之初为金为秋为义,阴之极为水为冬为智。盖仁之恻隐方自中出,而礼之恭敬则已尽发于外,义之羞恶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则已全伏于中,故其象类如此,非是假合附会。若能默会于心,便自可见。“元亨利贞”,其理亦然。《文言》取类,尤为明白,非区区今日之臆说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属,而土居中宫,为四行之地、四时之主,在人则为信、为真实之义,而为四德之地、众善之主也。五声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虫,其分放此。盖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若不见得,则虽生于天地间,而不知所以为天地之理,虽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为人之理矣。故此一义切于吾身,比前数段尤为要紧,非但小小节目而已也。[25]
照此说法,天地一气,分阴分阳,阳为仁、阴为义;阳中又分为二,即春仁和夏礼;阴中亦分为二,即秋义和冬智。一气分为阴阳,并无先后,而阳再分为二,春仁在先,夏礼在后;阴之分二亦然,秋义在先,冬智在后,这是一气流行的次序。而人性的仁义礼智之间及其发作为情,并无先后。总之,论元亨利贞、仁义礼智都不能离开一气阴阳四时五行这些宇宙论要素,从而使得元亨利贞、仁义礼智也成为与一气阴阳纠缠在一起的流行实体了。
六
朱子《周易本义》论元亨利贞四德:
盖尝统而论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畅茂,利则向于实也,贞则实之成也。实之既成,则其根蒂脱落,可复种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环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间,生气流行,初无间断,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统天也。[26]
这是把元亨利贞四德作为“物”的发生成长的不同阶段来理解的,同时,又说明这四个连续无间段的流行,是生气流行,元就是生气,所以四者的连续流行就是体现了“元”贯通四者而作为天道的统一性。
以“生”字说仁,生自是上一节事。当来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须要自体认得。泳。[27]
当来即当初。以生说仁,把生作为天地间的普遍原理,这是“人生而静以上”事,即生化论属于宇宙论之事,不是人生论之事。因此宇宙论对于人生论来说是“上一节事”。人之生亦接受天地之生理,人生而静以下此生理即体于人而为仁之理,而人生的目标就是要体认从天地接受的生意生理,因为这是人的生命的根源。
《语类》卷六八论乾卦四德:
文王本说“元亨利贞”为大亨利正,夫子以为四德。梅蘂初生为元,开花为亨,结子为利,成熟为贞。物生为元,长为亨,成而未全为利,成熟为贞。节。[28]
这是以元亨利贞为生长成熟,而不是以元亨利贞为性。
致道问“元亨利贞”。曰:“元是未通底,亨、利是收未成底,贞是已成底。譬如春夏秋冬,冬夏便是阴阳极处,其间春秋便是过接处。”恪。[29]
这是以元亨利贞为生长成熟之外,又以元亨利贞对应春夏秋冬。
《乾》之四德,元,譬之则人之首也;手足之运动,则有亨底意思;利则配之胸脏;贞则元气之所藏也。又曰:“以五脏配之尤明白,且如肝属木,木便是元;心属火,火便是亨;肺属金,金便是利;肾属水,水便是贞。”道夫。[30]
这是以元亨利贞对木火金水。这就使元亨利贞成为更普遍的模式了。
“元亨利贞”,譬诸谷可见,谷之生,萌芽是元,苗是亨,穟是利,成实是贞。谷之实又复能生,循环无穷。德明。[31]
这也是以物之生长遂成体现元亨利贞。以上都是以元亨利贞为物之形态或阶段。
以物之生长收藏说元亨利贞四德之义,始于程伊川,朱子亦明言之:
“元亨利贞”,理也;有这四段,气也。有这四段,理便在气中,两个不曾相离。若是说时,则有那未涉于气底四德,要就气上看也得。所以伊川说:“元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遂;利者,物之实;贞者,物之成。”这虽是就气上说,然理便在其中。伊川这说话改不得,谓是有气则理便具。所以伊川只恁地说,便可见得物里面便有这理。若要亲切,莫若只就自家身上看,恻隐须有恻隐底根子,羞恶须有羞恶底根子,这便是仁义。仁义礼智,便是元亨利贞。孟子所以只得恁地说,更无说处。仁义礼智,似一个包子,里面合下都具了。一理浑然,非有先后,元亨利贞便是如此,不是说道有元之时,有亨之时。渊。[32]
有这四段,即指生长遂成四个阶段,朱子在这里以生长遂成四阶段为气,而以元亨利贞为生长遂成的现实过程所体现和依据的理。按前面所述多见以元亨利贞为气这类的说法,而以元亨利贞四德为理,以生长收藏四段为气,此说似不多见。照这个说法,以生长遂成说元亨利贞,是就气上说,而理在气中。但朱子特别强调,程颐不从理上说元亨利贞,而从物上说,并没有错,他甚至声称程颐此说不可更改,认为讲气讲物,理便在其中了。此中理气的分析是很清楚的。这里所说的从气上看或从物上看的思想,不是从性、从理、从体上看,而都是近于从总体上看的方法。
“元亨利贞”无断处,贞了又元。今日子时前,便是昨日亥时。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这里方感得生气,他自有个小小元亨利贞。渊。[33]
这里又把元亨利贞说成四阶段连接循环,元是生气发生的阶段。元之前是贞,贞之后是元,循环无间断处。
气无始无终,且从元处说起,元之前又是贞了。如子时是今日,子之前又是昨日之亥,无空阙时。然天地间有个局定底,如四方是也;有个推行底,如四时是也。理都如此。元亨利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是有此气;所以有此气,便是有此理。故《易传》只说“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不说气,只说物者,言物则气与理皆在其中。伊川所说四句自动不得,只为“遂”字、“成”字说不尽,故某略添字说尽。高。[34]
“局定底”与“推行底”,与朱子说《易》的方法“定位底”和“流行底”的分别相近,显然,元亨利贞是属于“流行底”道理。由于伊川论元亨利贞是指“物”之生、长、遂、成言,故朱子说元亨利贞“就物上看亦分明”,他甚至认为《易传》也是就“万物”而言四德,就万物之生长遂成的阶段言元亨利贞。这种“就物上说”的方法并没有忽视理和气,因为言物则气和理皆在其中。这似乎是说,元亨利贞四德的论法可以有三种,物上说的方法如生长遂成说,气上说的方法如春夏秋冬说,理上说的方法即元亨利贞说。这三者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说明的。
朱子又说:
以天道言之,为“元亨利贞”;以四时言之,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为仁义礼智;以气候言之,为温凉燥湿;以四方言之,为东西南北。节。[35]
这就把元亨利贞之理更普遍化了,就天道言,即就宇宙普遍法则而言,是元亨利贞;这样普遍法则理一而分殊,有不同的体现,如在四时体现为春夏秋冬,在人道体现为仁义礼智,在气候体现为温凉燥湿,在四方体现为东南西北。温凉燥湿又说为温热凉寒:“温底是元,热底是亨,凉底是利,寒底是贞。”[36]这实际上是用四季的气候变化循环说元亨利贞。在这个意义上,元亨利贞如同理一分殊,已经成为一种论述模式。
“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此段只于《易》“元者善之长”与《论语》言仁处看。……“元者,善之长也”,善之首也。“亨者,嘉之会也”,好底会聚也。义者,宜也,宜即义也;万物各得其所,义之合也。“干事”,事之骨也,犹言体物也。看此一段,须与《太极图》通看。贺孙。[37]
《文言传》对元亨利贞的解释是就人事道德上说,朱子具体解释了什么是善之长,什么是嘉之会,什么是义之合,什么是事之干,但朱子对元亨利贞的解释并不是按这种方式进行的。朱子强调,根据二程的说法,对“元”的理解要与“仁”联系一起、贯通在一起。
光祖问“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曰:“元是初发生出来,生后方会通,通后方始向成。利者物之遂,方是六七分,到贞处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然发生中已具后许多道理,此专言也。恻隐是仁之端,羞恶是义之端,辞逊是礼之端,是非是智之端。若无恻隐,便都没下许多。到羞恶,也是仁发在羞恶上;到辞逊,也是仁发在辞逊上;到是非,也是仁发在是非上。”问:“这犹金木水火否?”曰:“然。仁是木,礼是火,义是金,智是水。”贺孙。[38]
按朱子的解释,元是初发生,则这就不是从理上看,而是从气上看或从物上看。其次,发生后必然向会通发展,会通后必然向成熟发展。就四个阶段的不同展开说,这是“偏言”的角度。就四个阶段贯穿着作为统一性的“元”而言,这是“专言”的角度。专言包四者,朱子的解释是,一方面,元中具亨利贞许多道理,亨利贞都是元的发现的不同形态,同理,仁不仅发在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都是仁之发。
《语类》又载:
曾兄亦问此。答曰:“元者,乃天地生物之端。《乾》言:‘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则生意之长,在利则生意之遂,在贞则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这意思。仁本生意,乃恻隐之心也。苟伤着这生意,则恻隐之心便发。若羞恶,也是仁去那义上发;若辞逊,也是仁去那礼上发;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发。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义礼智!”卓。[39]
元是生物的发端,元是生意的开始,亨是生意的长,利是生意的遂,贞是生意的成。于是生长遂成就是“生意”的生长遂成。这都不是从理上看的方法,也说明,四德的意义在朱子思想中并不仅仅是理。
《周易本义》云: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则为仁,而众善之长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于时为夏,于人则为礼,而众美之会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而得其分之和。贞者,生物之成。实理具备,随在各足,故于时为冬,于人则为智,而为众事之干。干,木之身,枝叶所依以立者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以仁为体,则无一物不在所爱之中,故足以长人。嘉其所会,则无不合礼。使物各得其所利,则义无不和。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谓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为事之干。[40]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刚以体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过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纯者,不杂于阴柔。粹者,不杂于邪恶。盖刚健中正之至极而精者,又纯粹之至极也。或疑乾刚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间,本一气之流行,而有动静耳。以其流行之统体而言,则但谓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动静分之,然后有阴阳刚柔之别也。[41]
元既是生物之始,又是天地之德,作为生物之始,亦体现为四时之春;作为天地之德,亦体现为人道之仁。可见,元亨利贞四德既是论生物过程与阶段,又是论天地之德,于是既体现为四时春夏秋冬,又体现为人道的仁义礼智。“流行之统体”就是兼体用的变易总体,元亨利贞是此一统体不同流行的阶段及其特征。
虽然可以说,对于四德而言,朱子的讨论包含了三种分析的论述,即“从理看”,“从气看”,“从物看”。但总起来看,应当承认,朱子的思想中不断发展出一种论述的倾向,就是不再把元亨利贞仅仅理解为理,而注重将其看作兼赅体用的流行之统体的不同阶段,如将其看作元气流行的不同阶段。由于天人对应,于是对仁义礼智的理解也依照元亨利贞的模式发生变化,即仁义礼智不仅仅是性理,也被看作生气流行的不同发作形态。这导致朱子的四德论在其后期更多地趋向“从气看”、“从物看”、从“流行之统体”看,使得朱子的哲学世界观不仅有理气分析的一面,也有流行统体的一面,而后者更可显现出朱子思想的总体方向。
世俗化的朱子:朱子学术的世俗关怀及其时代意义
——以“礼”学为例
朱杰人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大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中说:“在一般哲学史或理学史的论述中,我们通常只看到关于心、性、理、气等等观念的分析与解说。至于道学家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活动,则哲学家往往置之不论,即使在涉及他们的生平时也是如此。”[1]他指出,这一现象带来的一个后果是造成了一种“普遍的印象”,即儒学进入南宋以后便转而内向了,即儒学的重点在“内圣”而不是在“外王”。但是,余先生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他认为以朱熹和陆九渊为代表的南宋理学家们“念兹在兹的仍然是追求‘外王’的实现”,他们转向“内圣”主要是为“外王”的实现做准备的。
八年以后(2008年),余先生在为田浩先生的著作《朱熹的思维世界》(增订版)所作的序中,对以上观点又作了一次详细的阐释。他说:
作者在“祈祷文”一章的结尾处,特别强调朱熹的“使命感”,并清楚地指出:“在朱熹的思想中,社会关怀—理论上的实践—是首要的。”这正是我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允晨,2003年)一书中所展开的基本论旨之一。中国史在宋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治、社会、宗教、经济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动。“士”阶层乘势跃起,取得了新的政治社会地位。这一阶层中的少数精英(elites)更以政治社会的主体自居,而发展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普遍意识。这便是作者所说的“使命感”。他们的“使命感”主要体现在儒家的整体规划上面,即借“回向三代”之名,全面地重建新秩序。根据“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古训,他们首先以朝廷为中心,发动全面的政治革新,所以庆历、熙宁变法相继出现。但地方性或局部性的社会、道德秩序的推行也同时展开,故有义庄、族规、乡约、书院的创建。张载“有意于三代之治”,但从朝廷回到关中之后,立即在本乡以“礼”化“俗”,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为“在下则美俗”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事例。无论在朝野,士的“使命感”在南宋依然十分旺盛,朱熹便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他在政治上向往王安石“得君行道”的机遇,所以期待晚年的孝宗可以成为他的神宗,重新掀起一场“大更改”运动。绍熙五年(1194年)他立朝四十日便是为了领导朝廷上的理学集团推行改革(即所谓“孝宗末年之政”)。但在奉祠禄或外任时他则转而致力于地方上局部秩序的重建,如设立社仓、书院,以及重订吕氏乡约之类。不仅朱熹如此,同时的陆九渊、张栻、吕祖谦等也无不如此。现在本书作者通过“祈祷文”的专题研究,也进一步发现“政治、社会关怀”在朱熹思想中居于“首要的”位置,和我的整体观察恰好可以互相印证,我当然有闻空谷足音的喜悦。[21
余英时、田浩师徒二人,都不约而同地关注朱子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关怀,绝不是偶然的,他们的结论实质上是对朱子理学思想及其学术抱负的再发现,是对朱子一生学术活动与社会政治、文化实践的全面考察与完整的呈现。这一发现再次提醒我们,对理学、理学家的认识决不能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正如余先生指出,他们的“内圣”是为“外王”做准备的,他们的学术关怀,最终还是指向社会、人心和组成这个物质和精神世界的芸芸众生,关注着世俗社会。
而礼学,正是朱子学术世俗关怀最集中和典型的表现。
(一)
什么是“礼”?朱子认为,“礼”即“理”,礼是天理的外在形式,“礼”与“理”是互为表里的。他说:“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3]他认为“礼”与“理”的主要区别是,“理”是形而上的,是一种无形无迹的观念形态,而“礼”则是形而下的、可见、可行、可凭据的实践形态。他说:“礼即理也,但谓之理,则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为礼,则有品节文章之可见矣。”[4]他进一步解释说:“所以礼谓之‘天理之节文’者,盖天下皆有当然之理。今复礼,便是天理。但此理无形无影,故作此礼文,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教有规矩可以凭据,故谓之‘天理之节文’。”[5]有学生问朱子,“礼”之所以叫做“礼”而不谓之“理”,是不是因为“礼”是实在的、具体的、有可以落实的地方?朱子回答说:“只说理,却空去了。这个礼,是那天理节文,教人有准则处。”[6]
朱子又认为,礼是“人事之仪则”,也就是说,礼是人们行为处世及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礼仪制度。朱子在解释《孟子》“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时说:“何谓约?礼是也。”[7]他认为,礼就是约。什么是约呢?他说就是“上自朝廷,下达闾巷,其仪品有章,动作有节。”[8]约,有二层含义,一为“要”,一为“约束”。要就是主要的原则、规范,而这些原则规范是用来约束人的行为举止的。细察朱子在各种场合使用“约”字的情况,可以发现,他有时用第一义,有时用第二义,而更多的时候则二种含义兼而有之。在解释孔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时,他先引用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约我以礼,克己复礼也。”[9]再引胡氏曰:“惟夫子循循善诱,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达事变,然后约我以礼,使我尊所闻,行所知。”[10]这里约的主要含义在“要”、在“知”——即原则、规范。在解释“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时,他说:“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如此,则可以不背于道矣。”[11]并引程子曰:“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于礼,必至于汗漫。博学矣,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则亦可以不畔道矣。”[12]这里他强调的是约的“约束”之义。所以,他说,有君臣关系,就必然有君臣相处的原则、规范;有夫妇关系,就必然会有夫妇相处的原则、规范;父子、朋友、师长莫不如此,这就是礼。
朱子的理学思想,特别重视礼的实行和执行。他认为,既然礼具有天理的本质及其规范性,那么,践履就是天理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所以,他认为,“礼者,履也,谓昔之诵而说者,至是可践而履也。”[13]他认为,礼的践履是第一性的。古代未必有礼经(文字),他指出:“然古礼非必有经,盖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达闾巷,其仪品有章,动作有节,所谓礼之实者,皆践而履之矣。故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则岂必简策而后传哉!”[14]他还特别强调“知崇礼卑”,指出,践履礼,不能好高骛远,更不能厌弃礼的卑微与琐碎,礼正是在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中体现出来的。惟其如此,才能够“成性存存,而道义出矣”[15]。
在朱子庞大的理学体系中,礼学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朱子集理学之大成,构建了以性理学说为核心的形而上的理学体系。但是,他同样关注与重视“天理”与“人心”的连接与过渡,重视“天理”对形而下的世俗社会的影响与干预。在他看来,“礼”就是进行这种影响和干预的最有力的手段。所以他说:“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他的学生兼女婿黄榦对此解释说:“盖自天高而地下,万物散殊,礼之制已存乎其中矣……人禀五常之性以生,则礼之体始具于有生之初。形而为恭敬辞逊,著而为威仪度数,则又皆人事之当然而不容已也。圣人因人情而制礼,既本于天理之正。隆古之世,习俗醇厚,亦安行于是理之中。世降俗末,人心邪僻,天理堙晦,于是始以礼为强世之具矣。先儒取其施于家者,著为一家之书,为斯世虑至切也。晦庵朱先生以其本末详略犹有可疑,斟酌损益,更为《家礼》。务从本实,以惠后学。盖以天理不可一日而不存,则是礼亦不可一日而或缺也。先生教人,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修其身,皆所以正人心复天理也。则礼其可缓与?”在他看来,理与礼互为表里,理,是管人的内心——心性;礼是管人的行为——节文。理与礼的结合,就实现了一个文明人所必须具备的由内而外的天衣无缝的塑造。他认为,礼是理的“事”化和“物”化,“礼”中自然包含着“理”。他把这比喻为形和影的关系。
在一次与学生讨论《论语·子路》“卫君待子为政”章时,学生问他“何以谓之‘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朱子回答说:“‘事不成’以事言;‘礼乐不兴’以理言。盖事不成,则事上都无道理了,说甚礼乐!”[16]学生又问:“此是礼乐之实,还是礼乐之文?”朱子说:“实与文元相离不得。譬如影便有形,要离那形说影不得。”[17]又说:“事不成,如何得有礼乐耶?”“事若不成,则礼乐无安顿处。”[18]
理蕴含在礼中,礼表现在“事”、“物”中。
(二)
朱子不是一个空头理论家,他生活在理性的象牙塔的顶端,但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世俗社会和现实政治,他是一个具有社会抱负和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他之所以关注礼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把“礼”视为改造社会、重塑社会秩序和移风易俗的重要工具。
他认为,“礼”之为用,一个重要的功能是规范“秩序”,这秩序包括人伦之序、君臣之序及各种社会关系之序。他说:“礼是有序,乐是和乐。”[19]“大凡事须要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事若不成,则礼乐无安顿处。礼乐不兴,则无序不和。”[20]“礼乐只是一件物事,安顿得齐齐整整,有次序,便是礼。”[21]朱子有很多与友人的书信讨论“礼”,讨论的问题非常具体,如论庙室之向与座位的方向,如讨论丧礼的服制,这些仪式、形式、服饰,在朱子的眼中体现了一个“序”字。他认为,礼仪是社会秩序的物化、形式化,不能乱,一乱就失序了,而失序则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瓦解和动荡。
钱穆先生在《朱子新学案》中说:“盖礼之传世,在上则为典章制度,在下则为风俗教化。朱子所用力者,实欲汇通义理考据,溯往古之旧文,应当前之实用。其议丧服,议庙祧,皆当时朝廷大典礼,而亦有关教化之大,固非区区徒为钩沉炫博,媚古专经之比。至其为古经定制,非一字不可增损,而汉儒之学有补世教,此又非徒争程门义理为直接孔孟传统者所与知。亦非清儒专意尊汉抑宋,惟尚文字考据者所能测。至于议礼而遭忌逐,党禁之祸因此而起。治史者于此,可知在朱子当时,礼学仍为治国立政宣教化民一要项,非可用今人眼光忖测。”[22]绍熙五年(1194年)邵囦刻张栻的《三家礼范》于长沙郡学,朱子为作跋,曰:“呜呼,礼废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尝习于身,是以长而无以行于家。长而无以行于家,是以进而无以议于朝廷,施于郡县;退而无以教于闾里,传之子孙,而莫或知其职之不修也。长沙郡博士邵君囦得吾亡友敬夫所次《三家礼范》之书,而刻之学宫,盖欲吾党之士相与深考而力行之,以厚彝伦而新陋俗,其意美矣。”[23]朱子于此明确揭示“礼”对于移风易俗的重要作用。按《三家礼范》今佚,据朱子之跋语可以推知其为“家礼”一类著作。朱子对“家礼”、“乡约”、“乡仪”一类著作非常重视,他多次为此类著作写序作跋并鼓励刊刻广为发行。这是因为他明白,此类民间之“礼”书,具有十分有效的“厚彝伦而新陋俗”的作用。据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考订,淳熙二年(1175年),朱子始作《家礼》,同年修订《祭仪》,作《增损吕氏乡约》,为《蓝田吕氏乡约》、《蓝田吕氏乡仪》作跋。乾道元年至九年(1169—1173年)修订《祭仪》。如此密集地修礼、论礼是事出有因的,是朱子初任地方官以后对民间风俗、风气作深入考察而有了切身体验后,对整顿礼制,推行礼制之迫切性所作出的学术反应。
(三)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7月,朱子赴任同安主簿,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个地方官职。到任以后,他除了大力整顿县学外,上书“申严婚礼”曰:
窃惟礼律之文,婚姻为重,所以别男女、经夫妇,正风俗而防祸乱之原也。访闻本县自旧相承,无婚姻之礼,里巷之民贫不能聘,或至奔诱,则谓之引伴为妻,习以成风。其流及于士子富室,亦或为之,无复忌惮。其弊非特乖违礼典、渎乱国章而已,至于姤媢相形,稔成祸衅,则或以此杀身而不悔。习俗昏愚,深可悲悯。[24]
朱熹同时作《民臣礼议》,建议朝廷颁布州县予以实行。同安主簿的地方官经历,使朱子对民间习俗的混乱、迷失与糜烂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他说:“臣窃观今日天下之势,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盖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25]他把“振举纲维、变化风俗”列为“今日之急务”。正是出于对现实社会风气败坏的担忧,所以,朱子在编修礼书时作出了十分有针对性的安排。
宋廷南迁以后,由于退守仓皇,北宋时代长期积累而成的各种礼仪制度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连年的战争又使统治者无暇重拾礼制,于是民间邪教、淫祠趁虚而入,占领了本应属于儒学传统的各种祭礼及婚丧仪式。尤其是佛、道两教在民间传播影响之大,已对儒学的传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朱子在《乞增修礼书状》中揭示了这种情况:“今州郡封域不减古之诸侯,而封内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礼,其有祠庙,亦是民间所立,淫诬鄙野,非复古制。顾乃舍其崇高深广、能出云雨之实,而伛偻拜伏于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所谓滋养润泽者,于义既无所当,又其牲牢器服一切循用流俗亵味燕器,欲礼又无所稽。至于有山川而无祠庙者,其岁时祈祷,遂不复禜于山川,而反求诸异教淫祠之鬼。此则尤无义理,而习俗相承,莫知其谬。”[26]所以,他要求朝廷镂版颁降《政和五礼新仪》,并称此举乃“化民善俗之本,天下幸甚”。[27]
在朱子的时代,另一种社会风气也是令朱子十分警惕的,那就是奢靡之风。绍熙五年(1194年),上《乞讨论丧服札子》论嫡孙承重之服,主张应“以布衣布冠视朝听政,以代太上皇帝躬执三年之丧”。而用“漆纱浅黄之服,不唯上违礼律,无以风示天下,且将使寿皇已革之弊去而复留,已行之礼举而复坠。”[28]所以,他希望宁宗能够“明诏礼官稽考礼律,预行指定,其官吏军民男女方丧之礼,亦宜稍为之制,勿使过为华靡”。[29]
此乃宫廷奢靡,而民间奢靡之风同样令朱子十分忧虑。朱子《家礼·通礼》章全引司马光《居家杂仪》,其第一条即告诫曰:
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分之以职,授之以事,而责其成功。制财用之节,量入以为出,称家之有无以给,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费,皆有品节,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费,禁止奢华。[30]
“亲迎”章,朱子保留了司马光《书仪》中之“铺房”,这是自北宋时已形成的一种民间习俗,即在亲迎前一日,女方派人到男方家中陈设新房,并将陪嫁之物陈列展示。这是古礼中所没有的内容,但民间已非常普及,故司马光的《书仪》中予以保留,但规定:“床榻荐席桌椅之类,婿家当具之,毡褥帐幔衾绹之类女家当具之。所张陈者,但毡褥帐幔帷幕之类应用之物,其衣服、袜履等不用者,皆锁之箧笥。”[31]这正是为了避免当时竞相奢华,互相攀比之陋习。朱子《家礼》亦保留了司马光的内容,语言则更简洁和明确:“世俗谓之铺房。然所张陈者,但毡褥帐幔帷幙应用之物,其衣服鏁之箧笥,不必陈也。”[32]接着,朱子又引用了司马光的一大段议论曰:“文中子曰:‘婚娶而论财,夷虏之道也。’夫婚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至于立契约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复欺绐负约者,是乃驵侩卖婢鬻奴之法,岂得谓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绐,则残虐其妇,以摅其忿,由是爱其女者,务厚其资装,以悦其舅姑者,殊不知彼贪鄙之人,不可盈厌,资装既竭,则安用汝女哉?于是质其女以责货于女氏,货有尽而责无穷,故婚姻之家往往终为仇雠矣。是以世俗生男则喜,生女则戚,至有不举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则议婚姻有及于财者,皆勿与为婚姻可也。”[33]这真是一段振聋发聩的高论。从司马光的时代到朱子的时代,跨度长达一个多世纪,但从北宋到南宋,社会竞靡的风气依然不见改观,故朱子作《家礼》,不得不再次引用前贤之论,以警示时人。
(四)
余英时先生在其大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反复强调了宋代士阶层政治意识的觉醒及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自觉性,而秩序的重建则是贯穿于宋代理学从发生、发展到壮大全过程的永恒主题。他指出,张载“有意三代之治,但他的着手点却是本乡以‘礼’化‘俗’,即所谓‘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吕氏兄弟在张载逝世之年(1077年)正式建立著名的‘乡约’,便是继承其师‘验之一乡’的遗志。范仲淹首创‘义庄’这一事实,则更进一步说明士大夫重建秩序的理想同样可以‘验之一族’。‘义庄’与‘乡约’同是地方性的制度,也同具有以‘礼’化‘俗’的功能。他们同时出现在11世纪中叶,表示士大夫已明确地认识到:‘治天下’必须从建立稳定的地方制度开始。这本是儒家的老传统,即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但北宋士大夫所面对的是一个转变了的社会结构,他们不得不设计新的制度来重建儒家秩序,无论是王安石的新法、吕氏‘乡约’或范氏‘义庄’,虽有全国性与地方性之异,都应作如是观。所以分析到最后,宋代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革新活动,背后都有一股共同的精神力量,这便是当时所谓‘以天下为己任’。朱熹释张载《西铭》‘吾其体,吾其性’说:‘有我去承当之意。’总之,宋代的‘士’以政治、社会的主体自居,因而显现出高度的责任意识,这是无法否认的。”[34]
如果说,张载者流是在一乡一村做着理学家们的以“礼”化“俗”的社会实践的话,那么王安石则是希望通过君主的支持而进行一场全国性的化俗之运动。他的“变法”主张,其实就是一个不满于社会现实政治、文化、经济秩序的儒者试图变易旧法而改造社会的变革实验。其实,王安石欲行改革,起初朝野上下的有识之士都是认可的。“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35]可见,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到了不变不行的时候。“合变时节”一词,正说明了易风移俗已成了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他的改革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朱子认为除了王安石性格上的问题外,最主要的是他的“学术不正”。他说:“王荆公遇神宗,可谓千载一时,惜乎渠学术不是,后来直坏到恁地。”[36]他认为,王安石的问题是对儒学的传统及其内涵,没有一个正确和完整的理解,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见道理不透彻”。“先生论荆公之学所以差者,以其见道理不透彻。因云:‘洞视千古,无有见道理不透彻而所说所行不差者。但无力量做得来,半上落下底,则其肤浅。如庸医不识病,只胡乱下那没紧要底药,便不至于杀人。若荆公辈,他硬见从那一边去,则如不识病证,而便下大黄、附子底药,便至于杀人。’”[37]王安石的失败,给了朱子以反面的教育,他体悟出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理论的指导,所以,他从儒学的基本经典入手,加以思辨地、深入地和形而上的研究,构筑了一套完整的理学体系。就“礼”学而言,他在建构自己的“礼”学体系时,首先下大力气研究的是儒学关于“礼”的基本经典——“三礼”,及其三者之关系。他认为,《周礼》为礼乐之纲领,《仪礼》乃礼之本经,《礼记》乃《仪礼》之义疏。当他理顺了三礼之间的关系时,他意识到《仪礼》是礼之经,于是转而深研《仪礼》,花了毕生精力予以整理、注释,《仪礼经传通解》便是他心血的结晶。其子朱在曰:“先君所著《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王朝礼》十四卷,今刊于南康道院。其曰《经传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盖先君晚岁之所亲定,是为绝笔之书。”[38]正因为有了对儒家“礼”学经典的深入与整体的把握,所以他能游刃有余地、因时制宜地、与时俱进地制定出《家礼》等新礼书。
历时三百余年的宋朝,由于战乱频仍,似乎始终处于不停地“稳定—变革—战争—稳定—变革—战争”的循环之中。从大环境看,有宋一朝,稳定时间短,而战争(或准战争)时间长。而一旦社会稍趋稳定,那些有志于社会改革和重建儒学政治社会秩序的知识分子便会发出改革的呼声并付诸实践,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再到南宋理学的大兴,无不印证了这一规律。而几乎绵延于南宋朝始终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理学运动,则是贯穿于整个宋代社会改良与儒家秩序重建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其之所以最具影响力,除了因为以朱子为代表的儒学理论体系已达到了当时不可逾越的思想与学术高度外,还因为,朱子注意到了形而下的世俗的向度,这一向度使他的理论能深植于民间和草根,以致成为中国人生命与思维方式的组成部分而影响中国社会长达八百余年。
余论
笔者认为,朱子的学术,绝不仅仅是一种“文本的儒学”,而是一种“行动的儒学”。所谓行动的儒学,就是说,这种理论,并不仅仅是供把玩的、研究的、推演的、思辨的,而是除此之外还应该实行的、践履的。
朱子是中国古代复兴儒学的最伟大和最成功的思想家。他重视“天理”对世俗社会的影响与干预。在他看来,儒家的礼仪就是把天理与人世间进行对接和过渡的最好方式。他把“礼”看作是对“理”的践履。如果“理”是“知”,那么,“礼”就是行。同时他又强调礼对人的约束作用,他认为,人只有“动必以礼”,才能“不背于道”。朱子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使内容与形式互为表里,这使他的理学体系成为一个严整和周密的系统,同时也使理学的理论能够起到反哺社会、维护和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
今天当我们仔细地回顾和研究朱子的学术之路,我们不能不说,他的理论、思想、方法依然对当今中国社会具有深刻的启迪与借鉴作用。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余年来,取得了经济高速发展的世界奇迹。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会因为经济的复兴而自然实现,它还必须依赖于文化的复兴。而文化的复兴,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复兴。其中“礼”学的复兴,则更具有现实的迫切性。
改革开放以后,国门大开,中国社会对外来文化(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采取了不加甄别地全盘开放与照单全收的态度,以致西方文化如水银泻地般渗入中国社会的各种肌体。由此而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传统道德的迷失与基本行为规范的缺位。现在中国人被西方人诟病最甚的“不诚信”、造假,即是传统道德迷失的最集中的表现。现代中国人被西方人指为“不文明”的“粗鲁”、“野蛮”,则是中国传统的基本行为规范缺位的必然后果。所以,我们要重拾传统(请注意,不是“重建”)、回归传统,这“传统”就是中国的“礼”。
近年来,中国大陆提倡“和谐”,之所以倡导和谐,当然是因为不和谐,实际上,“和谐”背后反映的恰恰是社会秩序混乱。提倡和谐,实质上就是要重建合理的、科学的和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一社会诉求,也许正可以从以朱子为代表的“礼”学复兴的社会实践中汲取教益。
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其中民间习俗的被西化与被边缘化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面对西风席卷、西俗泛滥、中华传统的社会礼俗被全盘西化的社会现实,代表本土文化和传统的儒家“礼仪”完全可以从朱子“礼”学的精神宝库中获得武器以对全盘西化发起挑战,从而夺得中华文化自我救赎的一席之地。
社会的和谐离不开民众素养的培育与养成。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民族素养严重滑坡,以俗为美,以粗野为高雅,以鄙陋为文明,几乎成了整个社会的正常风气。此外,中国社会千百年来由儒家“礼俗”养育而成的各种社会规范,如尊师重教,如敬老爱幼,如礼让为先,如尊卑有序,如父慈子孝,如夫妇有别等等均被当作封建意识形态之病患而破坏殆尽。所以,如何提升全民族的文明素质,实在是当今中国社会非常迫切要解决的大事。社会规范是社会大众共同认可而自觉遵守的约定俗成,一个社会的成熟与否,这种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是其主要的内涵。中国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好不容易有了一种被世人称为“礼仪之邦”的社会约定俗成,可惜被一旦毁弃,而如今要恢复它,谈何容易。朱子曰:“礼不难行于上,而欲其行于下者难也。”[39]就是看到了礼之成俗之难,这需要长时间地不懈地推行、实施和潜移默化。
这也许正是我们今天来讨论朱子“礼”学的现时代意义。
朱子与儒家的精神传统
刘述先
通过当代新儒家的努力,儒家不再被误解为仅是一俗世伦理,这一传统被归入世界精神传统系列就是一个明证。[1]“儒家”(Confucianism)一词歧义甚多。我提议分别开三个不同而互相关联的面相来讨论:精神的儒家(spiritual Confucianism)、政治化的儒家(politicized Confucianism)与民间的儒家(popular Confucianism)。很自然地,我主要的关注集中在儒家精神的大传统方面。牟宗三先生首先提出儒家哲学三个大时代的说法,由杜维明广布于天下,我也认同这一说法。2005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邀请我回去做第十八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我讲的正是:“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抒发我自己对先秦儒学、宋(元)明儒学、现代新儒学的诠释与理解。[2]
先秦儒学最关键性的人物是孔子,他并不是儒家传统的创始者,他继承的是周文。但到春秋时代,周文疲弊,礼教不兴,他为礼找到内在的根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3]。生命以仁为终极关怀,这开启了儒家内圣的道路。孔子透过具体的行事因材施教给门徒以指引,表面上看来不成体系,其实“吾道一以贯之。”曾子的阐释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朱熹《四书集注》谓:“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大体得之。孔子学问的核心是“为己之学”。中国缺少近代西方式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但绝非不重视个体。除了推己及人之外,还强调:“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5]天是超越的层面,在过去一直未受到充分的重视和讨论。表面上看,孔子的“天”也可以理解成为人格神,但与亚伯拉罕传统(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的上帝不同,不显意志,也不创造奇迹。孔子的“无言之教”是一真正的突破,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6]天在这里已完全没有人格神的特征,但又不可以把天道化约为自然运行的规律。孔子一生对天敬畏,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7]小人怕的是上天的震怒,爱的是上天的眷顾,故多避祸祈福的举动,对默运的天道不只没有感应,还加以排斥。但孔子加以扭转,天是无时无刻不以默运的方式在宇宙之中不断创造的既内在而超越的精神力量,也是一切存在价值的终极根源。
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牟宗三先生说:孟子的思想纲领是“仁义内在,性由心显”,大体得之。孟子道性善,他说的是“本性”,这又是一个突破。由恻隐之心这样“本”的呈现,不只可以接上内在的本性,还可以通往超越的天道。所谓尽心、知性、知天,我们所以能够知天,正因为我们生命的根源来自上天的禀赋。但荀子却回到“生之谓性”的老传统,主张性恶,与孟子缺乏交集,讲的是经验现实的层面,又主张自然的天论,完全失落了超越的层面,所以被宋儒摒弃在“道统”以外。但荀子讲“化性起伪”,也认为人有巨大的可能性。他隆礼、传经,对儒家传统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8]宋儒又从《小戴礼记》抽出《大学》与《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组成四书,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大学》讲三纲领: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后世“内圣外王”的理想竖立了一个大体的准绳。《中庸》是儒家典籍中最富有哲学意味的一篇,前半讲未发、已发的修养工夫,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后半集中在“诚”的体证与阐发,所谓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展示了通过实践体现形而上睿慧的意涵。最后,孔子与其后学藉《易传》的阐发,把原来只是一部卜筮之书化腐朽为神奇,转化成为一部哲学宝典。[9]
由以上所述,可见先秦儒学在理念、典籍、实践三个层面已树立了规模,有待后来者进一步阐发与拓展。但在历史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儒学首先经过了汉代的曲折。汉初因受暴秦夭亡的教训,鄙弃法家,用黄老之术,与民休息。到汉武帝时国势强盛,乃转趋儒家,利用儒生巩固君王的统治,自此以往,“政治化的儒家”成为主流。士成为君王与百姓的中介阶层,形成一超稳定结构,一直到西风东渐,清廷覆亡,制度化的儒家(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划下句点,儒家才由中心被逐到边缘,这是后话,暂先搁置。汉代虽无与于道统,但以德治国,所谓“独崇儒术,罢黜百家”固然过分夸张,然而推动儒家教化,建造伟大中华文明,还是可以大书特书。老百姓勤劳节俭,崇尚教育,接受阶层秩序,倾向服从权威。所谓“民间的儒家“只是一种不自觉的心习,民俗兼融道佛信仰,乐天安命,由于缺乏声音,一向受到漠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东亚四小龙(台、港、新、韩)创造经济奇迹,才引起社会学家的注目。然而这些都不是本文中心关注所在,一笔带过算数。
回到精神传统,汉末天下大乱,除了科举为晋身之阶以外,经学根本不能满足知识分子精神的需要。他们倾向三玄(易、老、庄),被新玄学所吸引。而佛教自汉明帝之时传入中国,经过长期发酵以后,隋唐佛学人才鼎盛,中国式佛学:华严、天台、禅,吸引了知识分子的关心。经历五代,宋代儒学必须面对两大挑战,一则道德沦丧,不堪闻问;二则异学(道佛二氏)兴盛,儒学低迷。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宋明理学开创一条新的道路,力抗时流回归孔孟,并转化华严的“空理”为儒家的“性理”。这在某一意义下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文艺复兴,下开了儒家哲学的第二个黄金时代。[10]
北宋理学代表人物无疑是洛学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兄弟。伊川作《明道先生行状》云:“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后,未有臻斯理也。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11]
这说明了明道虽受到濂溪的启发,但并不传濂溪的学问。他面对二氏的挑战,回归圣学的传统,超越汉唐,直承孟子,跨越千年,担起传承道统的责任。但基础何在呢?必须归本于性命,明道自承:“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12]与横渠不同,明道不作宇宙论的铺陈,直截地体证了内在于自己生命的超越的天理。二程兄弟大方向一致,但明道圆融,伊川分解,也有重大的差别。[13]把宋明理学发展成为时代主流最关键性的一个人物就是南宋的朱熹。他继承的是伊川的思路,将之发展为整体的哲学,建构了一个心、性、情三分架局,完成了他的理气二元不离不杂的形上学。[14]我首先要强调的是朱子是圣学的一支。他少年时便已关注“为己之学“。苦参中和多年,回归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如此“静养动察”分有所属,“敬贯动静”,涵养于未发,察识于已发,这才走上了他自己成熟思想的路数。他一生强探力索,学问博大精深,日后被推许为集大成,绝不是偶然的。然而他所作出的综合,却不是没有问题的,但非当前重点所在,本文不及。
二程担负道统,但道统的建构要到朱子才完成。在《中庸章句序》中,他说:“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子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又再传以得孟氏。……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乎千载不传之绪。”[15]
这是何等的大手笔!朱子很清楚,他所面对的不是历史考据的问题。尧、舜、禹三圣在上古之世,孔子的时代已经文献不足,怎么能够证明舜、禹之间有“危、微、精、一”的十六字心传?这明显是精神信仰的传承。清儒阎若璩指出,十六字心传出于伪《古文尚书》、《大禹谟》,表面上看,似乎对宋儒建构的道统造成致命的打击,其实不然。因为这是“信仰”(faith)的领域,不是“知识”(knowledge)的领域。以生命投注的精神信仰是不会因为文献考证的“臆说”(opinions)而动摇的。而令人惊诧的是,朱子对道统的理解还有进于孟子处。孟子慨叹,夫子因得不到举荐,故不得其位,而感到遗憾。[16]朱子却掉转师道与君道的位置,推崇夫子“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想想这在当时引起了多大的震撼!仕人臣服君王只是尊君王之位,而君王必须对德低头。朱子正因有这样的精神传统做后盾,才敢于面圣斥君之非,并贬抑汉唐(功利)。这或者不免过分,但有精神传统为终极关怀的儒者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岂是一般俗儒可以了解于其万一的。
犹有进者,对于朱子,回归孔孟固然重要,但更有必要重视当前的资源。于是他和吕东莱合编《近思录》,选录北宋濂溪、明道、伊川、横渠的文字,共十四卷:(1)道体,(2)为学,(3)致知,(4)存养,(5)克治,(6)家道,(7)出处,(8)治体,(9)治法,(10)政事,(11)教学,(12)警戒,(13)辨异端,(14)观圣贤。卷一论义理之本原,然后自近及远,自卑升高,形成整个的体系。[17]
“近思”二字出自《论语》,其曰:“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18]正如朱子的门徒叶采(平岩)《集思录集解》原序曰:
尝闻朱子曰: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盖时有远近,言有详约不同,学者必自近而详者,推求远而约者,斯可矣。
我们现在讲宋明理学,习惯讲濂、洛、关、闽,中学教科书就是这样讲,却没有意识到,原来这正是朱子迈越时流,通过编纂《近思录》建构起来的思路。周濂溪无籍贯名,官阶也不高,仅只是二程的家庭教师而已,虽然对他们有所启发,但二程并不推崇濂溪的学问。但因朱子激赏濂溪的《太极图说》,竟推尊他为宋明理学的开祖。[19]而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无极而太极”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由于“无极”一词出自《老子》,陆象山兄弟质疑此文非濂溪所作,或者是他不成熟的少作。但朱子为之辩护,否定了“自无极而太极”的版本,那隐涵了“有生于无”的道家思想。朱子将“无极而太极”理解成为“无形而有理”,乃一体之两面,自也可以言之成理。其实濂溪把道家修炼图倒转为创生的宇宙论,《太极图说》的思想与他的《通书》互相融贯,象山兄弟的质疑并没有很好的理据。后世接纳了朱子的提议,把濂溪当作开启理学思潮的人物。
接下来应该讲横渠,他年辈与濂溪相若,著《西铭》一文,是在《太极图说》之外影响整个理学思潮至深至巨的另一篇大文章。[20]文章开始讲乾父坤母,气势磅礴,宣扬“民胞物与”之旨,归结于“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杨龟山怀疑此文“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伊川作出响应:“《西铭》之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岂墨氏之比哉!《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子比而同之,过矣。”这是“理一分殊”见诸文字的首次,意义重大,以后发展成为宋明儒的共法。但二程都批评横渠《正蒙》讲“清、虚、一、大”表达未醇,这显然是基于误解,但横渠的表达有些滞词,的确容易引起误解,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朱子追随二程,为了哲学的原因,把洛学移到关学之前,由此建构了濂、洛、关、闽的线索,后世以为当然,其实由思想史实际发展的线索来看,并没有必然性。由上所述,要没有横渠的《西铭》,根本不会有伊川“理一分殊”的阐发,还得先由横渠说起,而伊川讲“理一分殊”原来的论述是在道德伦理的层面,朱子才作出“一理化为万殊”的更普遍化的论旨。另一个案例是,横渠率先划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二程加以首肯,才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此语《近思录》卷二归之于明道,但伊川也有同样的说法。
朱子自己的确推尊二程,以之为正统。《近思录》卷二收入了明道的《定性书》答横渠问,这加强了横渠向明道问道的印象。横渠是二程的表叔,伊川虽否认横渠曾经学于他们两兄弟,但印象既已形成,先入为主,也就难以改变了。其实横渠的思想最富原创性,他和濂溪一样有宇宙论的兴趣,对《易》有相当研究,又是礼学的专家,注重躬行实践,有多方面开启的可能性。但他喜欢作异乎寻常的表达方式不免引起误解,以至未能得到充分重视。这是很可以遗憾的一件事。就圣学的体证与阐发来看,二程的确醇化,但不免偏向内圣一边。他们完全缺乏宇宙论的兴趣,阻抑了往多方面开展的可能性,不期而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配合上重文轻武的国势,不免偏向一边,失去了应有的均衡,也是可憾之事。
而朱子虽推尊二程,还是在明道、伊川之间作出了明白的分疏。明道一本,伊川二元,二者的同异,此处未能深论。然而朱子明显地不契于明道浑沦的体证,故《近思录》不收《识仁篇》。朱子继承并充分加以发扬的是伊川“性即理”、“爱情仁性”的思路。他建构了一个心、性、情三分架局,服膺横渠“心统性情”之说。性理超越,只存有而不活动。情内在,有流于情欲的倾向。心是气之精爽者,具有动能;心具众理,通过工夫实践,乃能以理御情,倡导一渐教的工夫论。平心而论,程朱是圣学的一支。伊川明白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分别,而依《大学》所教“格物穷理”,日积月累,也可达致一种透彻的体悟。朱子把这样的思路在他著名的《大学格物补传》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
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道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这绝不是通过归纳的方法去追求科学知识的途径。所谓“豁然贯通”乃是一种异质的跳跃。朱子渐教的途径到最后还是达到一种悟:通天下只是一理,这已超过了经验实证科学知识的层次。朱子的问题在他没有清楚划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不同的层次。但朱子虽有经验实在论的倾向,毕竟是圣学的苗裔,也有强烈的理想主义的倾向,这由他与陈亮辩汉唐就可以看得出来。[21]就这方面而言,陆象山与朱子是同道,同属圣学中人。[22]吕东莱与朱子一同编完《近思录》之后,约陆氏兄弟与朱子作鹅湖之会,结果朱以陆之教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朱子以象山为畏友,意存调停,乃谓:“子静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多了。……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但象山拒绝这样的调和折中,曰:“朱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23]由圣学的观点来看,象山是占优位。而他直承孟子,肯定心即理。不似朱子以心具众理,走迂回的道路,力道不足。朱子也不是看不到象山的优点,但感到象山的表达过分简截,不重典籍,直下承担,难免有流弊。然而朱子以象山有禅的意味,是无谓的牵扯。值得注意的是,顿的功夫论未必通体是本性的发扬,象山有些追随者竟以气质之杂为天理,则渐的工夫论虽无急效,不失为一条比较稳妥的道路。其实两派的确互有优劣,可以平衡彼此。可惜象山早逝,思想过分简截,未能致曲,门庭狭窄。陆学根本不能与朱学抗衡,到王阳明的时代,几成绝响。
朱子长寿,学问博大精深,成为道学一派宗师,绝非幸致。他死时被诬为“伪学”,但送丧者还超过千人,而且很快在宋理宗时即得到平反。元代科举,自1313年起,以朱子编纂的《四书集注》取士,一直到清末,1905年废科举为止,近六百年的时间,仕子童而习之。影响之大,自孔子以后一人,洵非虚语。
到了明代,王阳明虽重刻《象山文集》,反对诋以为禅,但以象山粗,不取其直截的表达方式。只他深以流行的朱学,习尚功利,务外遗内,忘失圣学的宗旨为病,乃提倡致良知,一新耳目,使心学成为显学。但他的思想表达由朱子转手,挑战朱子的《大学》解,回归《大学》原本,反对析心与理为二,提倡心理合一,知行合一,晚年讲《大学问》,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而他对朱子意存调停,编《朱子晚年定论》,想拉近与朱子的距离,却因书函考据失实,未能达到目的。但他思想理论的规模要借与朱学之对反而彰显,却是不争的事实。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阳明《传习录》中《致周道通书》,平章朱陆,《致陆原静书》则通过对濂溪、明道思想的诠释以阐发自己的思想。由此可见,阳明接受了朱子建构的道统的线索,但并不盲从朱子的意见而作出了自己的阐解。同样的情况也见于明末的刘蕺山,牟宗三先生以之为宋明理学的殿军。[24]蕺山主静,自推尊濂溪。他对朱子思想的理解颇多差谬。而他强调诚意慎独,又提出另一《大学》新解以阐发自己的思想。他同样接受朱子建构的道统的线索,而作出了自己的阐解。宋明理学既内在而超越的精神传统到明末清初因遭逢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失落了超越的层面而画下句点;清代的统治者虽仍维持朱子为正统,但清儒将天理虚化,礼教的终极权威归之于皇权,丧失了朱子的精神,外在权威提升,内在体证减弱,体制日趋僵固,终于演变成为所谓的“杀人的礼教”,也就不足怪了。[25]
清末废科举已令儒学由中心退到边缘,1911年清廷颠覆,制度的儒家宣告终结。西潮疾卷,民国肇建,军阀割据,内忧外患,政治并未转趋清明,儒家成为代罪羔羊,一切反动负面因素都归咎于这一传统。五四时期(1919年)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不意现代对儒家浴火重生的契机也正在同时,可谓异数!一战后梁启超到巴黎参加和会,亲眼目睹欧洲的凋敝与残破,所谓进步的西方反而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决不可以作为中国走向未来的楷模。他重新看到传统之中一些有价值的成分,而打开了现代新儒学复兴的机运。[26]追究其所以可能,正因为精神的儒家蕴含可以与时推移的万古常新的智能的缘故。长话短说,经过“三代四群”的努力,现代新儒学被肯认为现代中国最有潜力的思潮之一,另外两个思潮是西方思想与马克思主义。[27]当代新儒家的反省,见1958年元旦发表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由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四位学者签署。他们坦承中国文化不足,必须吸纳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但西方文化也有不足,应吸纳中国文化:(1)“当下即是”之精神,与“一切放下”之襟抱,(2)圆而神的智能,(3)温润而恻怛或悲悯之情,(4)使文化悠久的智能,(5)天下一家之情怀。而不了解中国的心性之学,也就不了解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而不能掌握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28]这无疑是继承自先秦与宋明的精神传统。
当代对儒家最富原创性的思想家是牟宗三。他精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展示了知识的限度。《实践理性批判》才有必要以“自由意志”、“灵魂不朽”、“上帝存在”为基设(postulate)。牟先生认为康德是受限于他的基督宗教背景才会认定只有上帝才能有“智的直觉”(intellectual intui-tion)。但中土三教儒(性智)、释(空智)、道(玄智)都确信人可以有智的直觉。这是中西哲学传统最大的差别。由西方的进路可以建构“执的形上学”,由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进路可以体证超越名相“无执的形上学”。事实上,“现象”与“物自身”不可偏废,二者分别有其定位。无限心的“坎陷”成就知识,而道的体认、心灵的解放与超脱并不需要脱离世间。像《大乘起信论》那样“一心开二门”,即可以找到会通中西的津梁。[29]
第二代新儒家适当存亡继倾之际,展示了强烈的护教心态,像牟宗三即强调中国文化以儒家为正统(突出创造性)的常道性格,不免引起巨大争议。但第三代新儒家却有幸在宁静的校园中成长,部分留学外国,受到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并在异域谋求一枝之栖,默认西方开放多元的学术文化,像杜维明和我展示的,是一个与上一代十分不同的国际面相。
20世纪80年代与60年代情况迥异。中国崛起,不再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两岸三地情况稳定,看不到战争的危机。进入新的世纪,知识分子要面对的是“全球地域化”(glocalization)的问题。[30]世界不知不觉缩小成为一个地球村,不像以往西方、印度、中华文明分别发展,各族群信仰接触频繁,如果不调整心态,听任矛盾冲突加剧,地球与人类的毁灭危在旦夕,故孔汉思(Hans Kung)呼吁必须面对典范重构的大问题,建构“全球伦理”(global ethic),祈求地球与人类的持存与永续。[31]第三代新儒家感到责无旁贷,积极予以呼应。但第二代过分强调儒家思想之正统与常道明显地不合时宜,无助于当前的宗教对话。故我倡议给予“理一分殊”以创造性的诠释,因应当前多元互济、和而不同的时代潮流作出积极的响应,继承孔子知其不可而为的精神,重构朱子理一分殊的睿慧,寻求切合当前的表达与践履,寄无穷的希望于未来。
注释
全球化时代朱子“理一分殊”说的新意义与新挑战
黄俊杰
一、引言
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从工业革命以后就逐渐形成,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茁壮的全球化潮流加速发展,蔚为新时代历史之主流。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甚多,知识本身成为生产资材的“知识经济”,是一个新的趋势。全球化时代另一项主流趋势就是当代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 )所说的,全球化创造了一种世界各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结性(inter-connectedness)大幅提升的生活方式。[1]全球各地“相互联结性”的日益加强,固然使全球各地的人才、物资与资金的流通更加通畅,但却也意味着各地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大幅提升。2001年“911事件”以及后美国在世界各地所展开的反恐行动,都印证全球化时代文明冲突的可能性。
为了因应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新挑战,我们可以跃入传统的巨流中,汲取新时代的灵感。在中华文化与思想传统之中,南宋大儒朱子(晦庵,1130—1200)的“理一分殊”说有其21世纪的新意涵,但在全球化时代各地互动的新脉络中,也面临诸多新的挑战。本文循朱子学之思路探讨全球化发展之相关问题,并提出“理一分殊”说在新时代的意义及其转化的可能性。
二、朱子学中“理—”与“分殊”
之关系:兼论“理”的诡谲性
(一)“理一”与“分殊”
“理一分殊”是朱子学的核心概念,朱子说:
世间事虽千头万绪,其实只一个道理,“理一分殊”之谓也。到感通处,自然首尾相应。或自此发出而感于外,或自外来而感于我,皆一理也。[2]
但是,“理一”与“分殊”并不是一种对抗的关系,“理一”遍在于作为“分殊”的万事万物之中。朱子说:
其所谓理一者,贯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离耳。盖乾之为父,坤之为母,所谓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则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为同胞,物为吾与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谓理一者也。然谓之民,则非真以为吾之同胞;谓之物,则非真以为我之同类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谓分殊者也。[3]
在朱子的”理一分殊”论中,“理一”与“分殊”并不相离,“理一”融渗于“分殊”之中。换言之,只有从具体而特殊的“事”之中,才能观察并抽离出抽象而普遍的“理”。也就是说,“共相”存在于“殊相”之中。
朱子在所有著述以及言谈中,屡次申论“理一”与“分殊”不相离,例如他在《中庸或问》中说:
天下之理,未尝不一,而语其分,则未尝不殊,此自然之势也。盖人生天地之间,禀天地之气,其体即天地之体,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岂有二物哉?……若以其分言之,则天之所为,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4]
朱子在这一段话中,为“理一”与“分殊”的必然性安立一个宇宙论的基础。朱子认为人间秩序本于宇宙秩序而生成发展,此所谓“理一”,但“理一”之具体之表现方式则多元多样,互不相同,此所谓“分殊”。
为了进一步说明朱子思想中“理一”与“分殊”的关系及其方法论问题,我们可以从朱子对孔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一语的解释开始。
朱子针对孔子在《论语·里仁》所说“吾道一以贯之”一语,提出以下的解释:
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而已矣者,竭尽而无余之辞也。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无余法,而亦无待于推矣。曾子有见于此而难言之,故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晓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或曰:“中心为忠,如心为恕。”于义亦通。[5]
朱子这一段解释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这句话[6]。朱子以“体”与“用”之关系说明“一本”与“万殊”之不相分离,对13世纪以后东亚思想界影响很大,几乎主导了以后的解释。南宋真德秀(景元,希元,景希,文忠,1178—1235)说:“一以贯之,只是万事一理。”[7]明代薛瑄(德温,1389—1464)说:“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原,故一以贯之。”[8]都可以视为朱子以“理一分殊”说解释孔学的进一步推衍,足证朱子之解释对后学影响深远,朝鲜时代(1392—1910)的朝鲜儒者更是完全浸润在朱子学的诠释典范之中。
从方法论的观点来看,朱子对“理一”与“分殊”的解释,实潜藏着某种方法论的个体论之思维倾向。《朱子语类》卷二十七及卷四十五解释“吾道一以贯之”时,充分展现方法论的个体论倾向。朱子说:“贯,如散钱;一,是索子。曾子尽晓得许多散钱,只是无这索子,夫子便把这索子与他。”[9]朱子以铜钱与绳索作比喻,主张必先积得许多铜钱,才有物可“贯”。朱子进一步解释说:
而今只管悬想说道“一贯”,却不知贯个甚么?圣人直是事事理会得,如云“好古敏以求之”,不是蓦直恁地去贯得它。……近见永嘉有一两相识,只管去考制度,却都不曾理会个根本。一旦临利害,那个都未有用处,却都不济事。吕伯恭向来教人亦云:“《论语》皆虚言,不如论实事。”便要去考史。如陆子静又只说个虚静,云:“全无许多事。颜子不会学,‘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勿失。’善则一矣,何用更择?‘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一闻之外,何用再闻?”便都与禅家说话一般了。圣人道理,都不恁地,直是周遍。10]
朱子在上文中一方面批评永嘉学派诸君子论史只考制度,而忽略人心等根本问题,可谓失之琐碎;但朱子另一方面又批评陆九渊(象山,1139—1193)只说“虚静”,不理会分殊之理。
再从朱子“理一分殊”说的整体特质来看,朱子也具有某种程度的“知识主义”的思想倾向,而与他的“理一分殊”及“格物穷理”等学说互相呼应。朱子说:“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11],他强调在“分殊”之中才能觅得“理一”的消息。诚如朱子所说,作为“普遍之理”的“太极”,实寓于作为“分殊之理”的“两仪”、“四象”或“八卦”之中。[12]
(二)朱子学中“理”的诡谲性
细绎朱子“理一分殊”说有关“理”的细部论述,我们可以归纳朱子思想中的“理”具有以下特点:首先,“理”是抽象而一元的概念;其次,“理”可以在林林总总的具体事实之中以不同方式呈现出来;第三,“理”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存在,永不灭绝;第四,“理”的延续或发展,有待于圣贤的心的觉醒与倡导;最后,在具体的历史流变之中所渗透出来的“理”具有双重性格,“理”既是规律又是规范,既是“所以然”又是“所当然”。朱子学中的“理”既属道德学与伦理学,又属宇宙论的范畴,而且两者融合为一。[13]
从“理”的发生程序与本质状态来看,朱子学中抽象而普遍的“理一”是从具体而特殊的“分殊”之中生成的,但是,一旦“理”被圣人从“事”中抽离而出或如朱子所说“流出来”[14]之后,“理”就取得了独立性与自主性,而不再受“事”所拘束,成为“多”之上的“一”(theoneoverthemany),因而对“多”具有支配力与宰制力。
三、全球化时代朱子“理一分殊”
说的新启示与新挑战
(一)新启示
从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观点来看,朱子“理一分殊”说最重要的新启示是:抽象而普世的规范,必须在具体而特殊的情境之中自然生成。我们从“全球化”的本质谈起。正如本文起首所论,全球化发展趋势强化了世界各地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纽约股市的变化连带影响东京、台北或上海的股票市场。全球化发展创造了表面的一体感,但在“地球村”的口号与荣景之下,却潜藏着巨大的压迫与宰制——全球化发展促使居于全球化中心位置的国家,对于居于全球化边陲位置的国家,更肆无忌惮的剥削与控制。居于全球化中心位置的国家掌控国际性政治组织如联合国、经济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WTO)、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会(IMF),也掌控全球最先进的航天科技、生命科学知识等,使全球化“中心”国家的影响力更是无远弗届。
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之后,不论在国际间或是在国内脉络,所得分配的不平等也更加严重。经济学者研究告诉我们:从1980年代以降,因全球化而带来的不平等日益严重,1980年代以后在寿命与教育方面虽然看似减缓了不平等的趋势,但是实际上可能只是假象而已。[15]“全球化”已俨然成为全球化发展的“中心国家”宰制“边陲”国家的凭借。
“全球化”趋势发展至今,之所以成为强凌弱、众暴寡的工具,原因甚多,最重要的原因是“全球化”成为抽离于世界各国之具体互动脉络之上的抽象理念或具有宰制力的机制,而不是处在于世界各国互动的具体脉络之中,而与时俱进、随时修正的潮流。
针对“全球化”趋势所创造的国际间以及各国国内的不平等现象,朱子学的“理一分殊”说有其新时代的启示。朱子强调“所谓理一者,贯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离耳”[16],这句话启示我们:作为一种理念或某种机制的所谓“全球化”,应该只能存在于各国的互动关系之中。换言之,作为抽象性的“全球化”,只能存在于具体性的国际关系之中,才能随时调整,与时俱进,才能免于成为国际上强权压制弱国,国内的资产阶级压迫农工阶级的借口。
(二)新挑战
但是,从21世纪的今日世局来看,“全球化”显然已成为抽离于各国具体的国际关系之上的具有宰制力的论述与机制,而被全球化的“中心”国家所垄断,“全球化”在很大的程度上与范围内,等同于“美国化”,早在1991年就有人为文指出,总部设在美国的全球性跨国大公司的领导阶层,只有2%不具有美国国籍的事实。[17]这种状态在21世纪的今日,并无重大改变。
正如朱子“理一分殊”说中“理”的吊诡性一样,“全球化”论述就好像朱子的“理一”一旦被从“分殊”之中抽离出来之后,就取得了独立性,而被强者所垄断,成为压迫“边陲”国家与人民的工具。这种情况很像18世纪戴震(东原,1724—1777)痛批“理”学被统治者所利用而成为杀人之工具,戴震说:
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着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18]
二百年前戴东原所谓“今之治人者”以“理”杀人的状况,很近似于21世纪的今天居于全球化“中心”位置的国家,以“全球化”这个“理”作为控制“边陲”国家的情形。用朱子的语言来说,“全球化”这个“理一”已经从世界各国的“分殊”这个具体情况中剥离出来,而成为全球政经秩序的掌权者手中玩弄的工具。“全球化”的吊诡性与朱子“理”的吊诡性,如出一辙。
为了进一步思考作为21世纪之“理”的“全球化”价值理念之吊诡性,我们可以再回到朱子“理一分殊”说中“理”与“心”之关系。朱子一向强调经由“格物致知”的程序之后,人的“心”可以有效地掌握并理解万物及宇宙之“理”,甚至可以达到他在<大学格物补传>所谓“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19]的境界。
朱子强调以人“心”掌握万物之“理”的这项思想遗产,对朝鲜时代(1392—1911)的朝鲜思想界影响极为深远,亦衍伸出两个新命题。正如我最近所指出的,朝鲜儒者从朱子学中进一步发展的第一项新命题是:以“吾心之理”贯通“万物之理”。[20]金谨行(字敬甫,号庸斋,1712—?)说: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者,一者,理也。贯者,心之事也。理在吾心,以吾心之理,贯乎万物之理也。[21]
朝鲜儒者金谨行将孔子的“一以贯之”解释为“理在吾心,以吾心之理贯乎万物之理”,所谓“理在吾心”一语显示相对于朱子的“穷理”之学而言的更进一步“内转”。
朝鲜儒者从朱子学所发挥的第二项新命题是强调“一本”与“万殊”皆本于心。17世纪朝鲜儒者朴知诫(字仁之,号潜治,1573—1635)说: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朱子曰:“人之为学,心与理而已”。“心”即“一本”也;“理”即“万殊”也。古圣人垂教之说,无非一与万而已。从事于小学而存此心于端庄静一之中者,从一上做工也;从事于格致,而穷众理之妙者,从万上做工也。…自一而万,自万而一,复自一而为万,乃圣人之学也。一本万殊,两仪之象也。知上行上皆有此两端。知觉不昧之在心,曰:“知上之一本”。明烛事物之理,曰:“知上之万殊”,一心之浑然在中,曰:“行上之一本”;躬行践履之在事物,曰:“行上之万殊”,所谓忠恕是也。[22]
朴知诫所说的这一段解释之特殊之处,在于将朱子的“一本”与“万殊”,再细分为“知上之一本”与“知上之万殊”,以及“行上之一本”与“行上之万殊”,而归结在“心”的作用之上。金谨行进一步发挥朝鲜儒者将“一本”与“万殊”汇归于“心”之上的解释立场,他说:
以道之总在一心者贯之于万事,则为散殊之道。以道之散在万事者本之于一心,则为总会之道。[23]
金谨行以“心”将“散殊之道”与“总会之道”加以统一,确较朱子之解释更进一层。
从朝鲜朱子学者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朱子“理一分殊”说中的“理”,如果完全归结于人(尤其是圣人)的“心”的解释与掌握,就难以避免“理”的解释之任意性,并且使“理”失却其客观性,易于被少数人所掌握与宰制。21世纪的“全球化”的解释权之被强权国家所宰制,在某种意义上正与朱子与宋儒的“理”在18世纪中国之被统治阶级所掌握相似。
朱子“理一分殊”说中的“理”之有其被垄断这项危险性,更因朱子的“理”之同源性而大大提高。在《朱子语类》卷18中,就有学生请教有关“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原”这个问题,朱子回答说:
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24]
朱子虽然强调“理”的同源性(“理皆同出一原”),但是,他也同时强调在实际运作的层次上,各种事物的“理之用”则有互不相同的特殊之理,而且各个具体的事物又分享普遍的“一理”。
从朱子的理论来看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趋势,我们可以说,不仅各个不同的文明或国家的分殊之“理”剧烈碰撞,甚至“理”的解释权又被居于全球化的“中心”位置的国家所垄断,“全球化”发展竟为人类前途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那么,如何从朱子的“理一分殊”说中提炼新意义以因应21世纪“全球化”的这项新挑战呢?21世纪全球化发展使世界各文明、各国家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与日俱增,各种源自不同历史与文化背景的“理”也互相碰撞激烈冲突。因此,如果朱子的“理一”只有一人或少数人的“心”才能加以解释或掌握,恐难以适应新时代的挑战,而必须别创新解。
四、结论:在诸多“理”之中求同存异
在上文的论述中,我们通过朱子的“理一分殊”说,分析21世纪全球化时代中,诸多的国家之“理”互相冲突而并存,“理”被全球化的“中心”国家所控制,以致成为压制“边陲”国家的工具。我们也指出,朱子“理一分殊”说中的“理”贯通并浸润在诸多分殊的“事”之中。但是,吊诡的是,一旦“理”从“事”中“流出来”(朱子用语)之后,“理”取得了独立性,因而容易因为“去脉络化”而被少数人或强权所控制,而反过来压制分殊的“事”。因此,本来是“多”中的“一”,遂转化成为“多”上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里,“理一”可能必须转化为诸多分殊而并存之“理”,才能适应不同的文化传统在文明对话新时代的需求。而且,我们也必须将朱子学中的“理一”所潜藏的从属原则(Principle of Subordination)——指文化中的诸多主体(如社会、经济等主体)均服从于单一主体(如政治主体)的支配——逐渐转化为“并立原则”(Principle of Coordi-nation)——指文化中的诸多主体处于并立及竞争之状态。[25]
在21世纪各文化传统所蕴蓄的多元之“理”互相对话的新时代中,求同存异是一条必然的道路。传统中华文化重视“同”而忽视“异”。古代儒家就非常强调“同”的价值。孟子在谈到舜的美德时曾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26]他又认为“尧舜与人同耳”[27]。诚如余英时(1930— )所指出的,在中国思想史上,“同”之作为一个价值意识一直受到强调,到了汉末,“异”之作为价值意识才受到重视,这与汉末儒学衰微,新道家兴起,“个人”被重新发现等发展都有关系。[28]因此,就21世纪大中华文化圈及其与世界之互动而言,如何开发求“同”而存“异”的价值观,如何落实宋儒陈亮(同甫,1143—1194)所谓“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29],如何实践明儒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1465—1517)所说的“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30]的原则,就成为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
——关于朱熹“敬论”的几个问题
吴震
前言
众所周知,在宋明理学史上,自北宋程颐(世称伊川先生,1033—1107)提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1]以来,经南宋朱熹(号晦庵,1130—1200)的阐扬发挥,主敬与致知构成了缺一不可、互相为用的一套工夫论体系。就朱熹哲学而言,主敬思想无疑是其整个理论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就当今中文世界有关朱熹哲学的研究来看,却有不少重量级的经典论著对朱熹之“敬论”竟然未加重视或论之甚略,这里我们仅举三例,例如牟宗三《心体与性体》[2]第三册为朱熹专论,其中就看不到有关朱熹敬论思想的章节安排,只是在讨论朱熹心论问题时顺便涉及且有严厉之批评;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3]一书之于朱熹有专章论其心而无专章论其敬;陈来《朱熹哲学研究》[4]也没有安排章节来专论朱熹敬说,只是在后来撰述的《宋明理学》[5]这部教材中对此有概括性的论述。[6]
最近牟宗三弟子杨祖汉发表了《从朱子的“敬”论看朱子思想的归属》[7]一文,打破了以往略于朱熹主敬思想之讨论的局面,而以“敬的形态”来为朱熹思想定位[8],指出朱熹之言敬是由敬“契入本心”,而恭敬亦是“道德心本有之内容”,[9]故可说朱熹的主敬思想“确立了儒家重恭敬这一义理形态,彰明了恭敬之心之道德涵义”。[10]依杨文,如此理解朱熹思想之形态,庶可对朱熹的心性论、工夫论有更妥当的整体理解,“不会将朱子学归于意志的他律的形态,以其言持敬,只是空头的涵养,也不会忽略朱子重礼文的部分。”[11]不用说,对朱子学的这一同情之了解难能可贵,不唯与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异趣,更可启发吾人以朱熹敬论为切入点来重新省思朱子学的思想特质及其相关理论问题。不过,以笔者之见,若依事实判断而言,朱熹思想固然重视主敬以涵养心性,然其工夫理论亦重格物穷理,更重要的是,若从理论判断的角度看,朱熹之敬论何以能使良心呈现出来,也就是主敬工夫的依据问题依然存在。正如杨文所言,正是这一点“值得深入研究”。[12]而这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
事实上,朱熹的敬论与其心论、性论有十分密切的理论关联。正如朱熹己丑之悟所表明的那样,朱熹之所以归宗于二程主敬,乃是缘自其对“心为已发”、“性为未发”之心性问题的最终解决。笔者最近撰文指出,由于朱熹之论心始终将视野限于工夫论领域而缺乏本体论的关怀,故其心论详密有余而意欠圆融。尽管从儒学传统看,孟子所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可谓是儒学即工夫而言心的一句至理名言,宋明理学家也几乎无不奉为圭臬,由此以观朱熹所言“心是做工夫处”这一心论观点亦应是儒学的一种理论形态。然而,朱熹之心论何以成立,则需要与其敬论思想合以观之始能获得充分之了解,因为在朱熹的理论构造中,“心是做工夫处”也只有在其“敬义夹持”的“居敬”理论中才能落实。[13]反过来说,若要真正理解朱熹的心性论,亦须对其主敬思想的理论构造有一相应的了解。这便是继拙文之后,进而探讨朱熹敬论的一个缘起。
本文的任务分三步走,首先从概念史的角度来探讨朱熹敬论的问题之由来;其次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朱熹敬论的几个重要方面做一番梳理;最后对其敬论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思考,以就正于学界。
一、问题的由来
朱熹对程颐评价之高,这是众所周知的,例如他认为程颐的“性即理”揭示了“颠扑不破”的普世真理,[14]而且是“自孔孟后,无人见得到此,亦是从古无人敢如此道”[15]的。事实上,朱熹对程颐的称赞还不止于此,他认为程颐的主敬思想也同样是对儒学的一大贡献,甚至是孔子以后、秦汉以来的一大发明,他说:
圣人言语,当初未曾关聚,如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等类,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关聚说出一个敬来教人。[16]
自秦汉以来,诸儒皆不识这敬字,直至程子方说得亲切,学者知所用力。[17]
程先生所以有功于后学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18]
不用说,我们可以从这种赞美声中读取出朱熹自身的思想倾向:这被程子“关聚说出”的、“说得亲切”的、“有功于后学”的“敬之一字”无疑也正是朱熹所取的一个思想立场。
朱熹曾对宋代理学以来的“敬论”史及其内涵有一个概要性的总结:
然则所谓敬者,又若何而用力邪?曰:程子于此,尝以“主一无适”言之矣,尝以“整齐严肃”言之矣。至其门人谢氏之说,则又有所谓“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说,则又有所谓“其心收敛不容一物”者焉。观是数说,足以见其用力之方矣。[19]
这是将程颐的“主一无适”、“整齐严肃”与程门弟子谢良佐(号上蔡,1050—1121)的“常惺惺法”《上蔡语录》卷中)以及尹焞(号和靖,1061—1132)的“其心收敛不容一物”(《和靖尹先生文集》卷八《师说附录》)作为理学主敬思想的四大要点,这个说法在《朱子语类》也到处可见[20],可谓是朱熹对主敬问题的一个基本认识,也是程颐之后朱熹之前,理学之论主敬的主要脉络。
质言之,主一无适是就心上做工夫,保持意识的高度集中而不走失;整齐严肃则是就外貌上做工夫,要求仪容整齐、举止端庄;常惺惺法则是“心不昏昧之谓”[21],常令此心保持唤醒而不间断的状态,重在“唤醒”而令此心不间断;此心收敛不容一物则是“心主这一事,不为他事所乱”[22]之意,重在“收敛”而令此心为主。显然,除了整齐严肃是就外貌仪容而言以外,其余三种工夫均与内心有关,故可归为一类。至于外貌与内心的关系,依程颐,又可叫做外与中的关系,如其《四箴·视箴》所言“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强调通过“制外”——即外部的整齐严肃,以通向“安内”——即内心的安定宁静。然而“制外”与“安内”又是互为连贯的,程颐《四箴序》指出“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也”,便是对主一无适与整齐严肃这套主敬工夫之关系的恰当说明。要之,“制外”和“养中”均属“涵养”工夫,故结论可以说:“敬只是涵养一事。”[23]
不过,这里的“内外”只具相对意义而不能截然两分,因为事实上,若从程颐的另一重要命题“敬义夹持”的角度看,相对于“义外”而言,“直内”的敬字工夫便“只是内”,[24]即意谓敬是一种内在工夫。程颐说:
君子主敬以直其内,守义以方其外。敬立而内直,义形而外方。义形于外,非在外也。敬义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25]
可见,敬是一种“内”的工夫,“方其外”的“义外”工夫最终也取决于“直其内”,所以说“义形于外,非在外也”。程颐虽然注重“整齐严肃”作为主敬工夫的入手处,强调从外貌上做工夫的基础性意义,但在他的问题意识中,不论是端正容貌还是集中意识,都最终指向“直内”的内心工夫。甚至可以说,程颐之所以极力倡导主敬工夫论,其问题意识就在于如何安定人心。
例如程颐指出: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个翻车,流转动摇,无须臾停,所感万端。又如悬镜空中,无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学则却都不察,及有所学,便觉察得是为害。著一个意思,则与人成就得个甚好见识?心若不做一个主,怎生奈何?张天祺昔常言,“自约数年,自上著床,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后,须强把佗这心来制缚,亦须寄寓在一个形象,皆非自然。君实自谓“吾得术矣,只管念个中字。”此则又为中系缚,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虑,冥然无知,此又过与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常若有两人焉,欲为善,如有恶以为之间;欲为不善,又若有羞恶之心者。本无二人,此正交战之验也。持其志便气不能乱,此大可验。要之,圣贤必不害心疾,其佗疾却未可知。佗藏府只为元不曾养,养之却在修养家。[26]
程颐以“翻车”来比喻“人心作主不定”的各种现象,如“流转动摇,无须臾停,所感万端”等等;又以“悬镜”为喻,指出人心作主就好比“悬镜空中”,万物自来而又无一定之形状可以把捉(“有甚定形”),因此重要的是,人心作主而又不能“著一个意思”。他所列举的张天祺“不思量”和司马光“念中”的事例则从一个侧面表明,寻求心定乃是当时的一个普遍问题。
不过在程颐看来,张天祺和司马光在寻求心定的问题上犯了“著一个意思”的根本错误,具体表现为“寄寓在一个形象”——亦即追求某种“定形”,而这个错误的本质在于二心“交战”(“本无二人”的二人,意谓二心)、“皆非自然”。须指出,这里“交战”一词生动地揭示了“人心作主不定”的所有症结之所在——即程颐所说的“心疾”,而且是所有疾病中最为根本的疾病,所以说尧舜等圣贤或许也有其他疾病,但却不会有“心疾”,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没有“心疾”,所以尧舜才得以成为尧舜。针对常人的“心疾”,程颐提出的对治方法则是孟子的“持志养气”说,以为这是从根本上克服“心疾”的良方,因为“持其志便气不能乱”。事实上,程颐是以孟子的“持志养气”作为主敬思想的理论支持,关于这一点,这里也就不必深究了。
毫无疑问,以上这段叙述所揭示的“人心作主不定”的问题,其实也就是如何解决“心疾”的问题,程颐所得出的结论既不是张天祺的“不思量”,也不是司马光以“中”定心,而是以主敬来对治“心疾”,因为主敬才是解决“心主不定”的根本方法,换言之,程颐在工夫论上强调的主敬工夫所要应对的问题就是人心如何做主以及如何克服二心交战的问题。事实上,就宋代以来的理学思潮来看,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不妨来看两段程颐的语录:
学者先务,固在心志。有谓欲屏去闻见知思,则是“绝圣弃智”。有欲屏去思虑,患其纷乱,则是须坐禅入定。如明鉴在此,万物毕照,是鉴之常,难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万物,亦难为使之不思虑。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如何为主?敬而已矣。有主则虚,虚谓邪不能入。无主则实,实谓物来夺之。今夫瓶罂,有水实内,则虽江海之浸,无所能入,安得不虚?无水于内,则停注之水,不可胜注,安得不实?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则他事更不能入者,事为之主也。事为之主,尚无思虑纷扰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且欲涵泳主一之义,一则无二三矣。[27]
人多思虑不能自宁,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于事,为人君止于仁之类。如舜之诛四凶,四凶已作恶,舜从而诛之,舜何与焉?人不止于事,只是揽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则是役物。为物所役,则是役于物。有物必有则,须是止于事。[28]
可以说,以上两段语录集中反映了程颐主敬思想的问题意识,程颐所欲解决的根本问题无疑在于人心做主这一点。以下,我们对这两段语录略做解释。
在第一段,程颐明确指出“学者先务固在心志”,重要的是,若要使不得不交感、不得不思虑的人心安定下来,“唯是心有主”。那么“如何为主”呢?答案只有一个:“敬而已矣。”为什么呢?程颐指出:“有主则虚,虚谓邪不能入;无主则实,实谓物来夺之。”这是以虚实来做一个比喻,人心之虚,故能应万事,人心若实(如心中若有一物),则人心已然有种种阻塞,便不能“作主”;程颐进而指出:“事为之主,尚无思虑纷扰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这是说,“止于事”是使人心作主的一个条件,况且使人心“主于敬”,则更无“思虑纷扰之患”。[29]那么,究竟如何做到“主敬”呢?程颐提出了一个命题式的答案:“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须是直内,乃是主一之义”。这是将“主一无适”和“直内方外”结合起来——用程颐的另一种说法,亦即敬义夹持的方法,做到内外交互使用、合作并进,便是主敬工夫的全部内容。这样一种主敬工夫,在程颐看来,就是“涵养”工夫,其下手处不能脱离“事”(如“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其最终目标则是“自然天理明”。
在第二段,程颐以舜诛四凶为例,一方面强调了人心做主须落实在“事”上,即所谓“止于事”,同时又强调“止于事”必须按照“有物必有则”的原则顺而从之,而不能强“揽他事”,他以“物各付物”而不为物“所役”作为定心的重要方法,告诉人们实现“作得心主”的关键在于“止于事”而又不为“事”所扰乱。在这里程颐虽然没有提到“主敬”,然而事实上若要做到“作得心主”,唯有从敬入手,这就是程颐通过对主敬内涵的阐发而欲再三强调的由敬定心、心要做主的思想。合而言之,以上这套说法,既是程颐对其主敬思想的完整解释,同时也是程颐何以极力主张主敬工夫的思想缘由。
那么,对于自觉继承了程颐主敬思想的朱熹来说,他强调主敬的问题意识究竟何在呢?
二、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
朱熹之言敬,不胜枚举,所涉义理极为繁复。不过他在《大学或问》一上来讲到大学与小学之分的问题,就对“敬”字工夫在儒学体系中的重要性表明了一个基本的看法:
盖吾闻之,敬之一字,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发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为说焉。不幸过时而后学者,诚能用力于此,以进乎大,而不害兼补乎其小,则其所以进者,将不患于无本而不能以自达矣。其或摧颓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则其所以固其肌肤之会、筋骸之束,而养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于此,而不患其失之于前也。……若徒归咎于既往,而所以补之于后者,又不能以自力,则吾见其扦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颠倒,眩瞀迷惑,终无以为致知力行之地矣,况欲有以及乎天下国家也哉![30]
在这段叙述中,朱熹首先将“敬之一字”定位为儒家圣学“成始成终”之工夫,继而论述了此一工夫可由小学阶段的“涵养本原”而进之于大学阶段的“进德修业”,最终实现“明德新民”、“治国平天下”这一儒家终极理想。须指出的是,这里虽将主敬比作小学工夫,但并不意味着主敬只是针对15岁之前的小学之工夫而言,其方法也不仅仅是“洒扫应对进退”三项工夫或“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而已[31];朱熹之用意在于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大学虽是针对15岁之后的“大人”而言,但“大学之道”则是一以贯之的,也必然表现在小学工夫的过程当中,这就是“敬之一字”。所以朱熹的意思并不是说,先在小学阶段做一番“涵养本原”的主敬工夫,然后在大学阶段才能进之于格物工夫,事实上,在大学阶段何尝不需要主敬?所以程子在讲格物的同时,也必然讲主敬。朱熹最后指出,如果我们只是把主敬看作是以往的小学阶段之工夫,以为当今做大学工夫已经无法弥补而只能放弃主敬,那么就必将导致“身心颠倒,眩瞀迷惑”,根本不能有进于“致知力行”,更谈不上去实现“治国平天下”。要之,朱熹在这里阐述的核心思想是:“敬之一字”是贯穿小学和大学的根本工夫。
既然主敬是贯穿小学与大学的“涵养本原”之根本工夫,那么具体地说,主敬又主要是一种什么样的工夫呢?显然,虽说主敬贯穿于“洒扫应对”及“致知力行”,但主敬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洒扫应对”或“致知力行”。同样,虽说涵养本原之主敬含有“养其良知良能之本”的涵义,但“敬之一字”本身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良知良能”。其实在我们看来,若以一言以蔽之,则可说“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32]乃是朱熹之敬论的最为重要的核心观点。
对照以上程颐言敬重在心要作主、以心为主的观点,可以说朱熹之论敬同样重在心做主宰这一点上,只是朱熹更为突出强调“自做主宰”,也就是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心的“自存”义、“自省”义。接下来,我们就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朱熹为什么强调此心自做主宰?一是敬又如何才能使此心自做主宰?在本节中,我们首先来考察第一个“为什么”的问题,亦即朱熹之论敬的思想缘由、问题意识究竟何在的问题,至于第二个“怎么做”的问题,则有待以下各节来展开讨论。
如所周知,朱熹的两次“中和”之悟,均与心性问题有关,特别是标志着朱熹思想最终确立的第二次己丑之悟,不惟从根本上解决了心性的名义问题——即如何从哲学上来定义心性关系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朱熹确立了以“敬”为“日用本领工夫”的思想——即居敬工夫。向来讨论朱熹“中和”之悟,较多关注朱熹由“心为已发,性为未发”转向“性为未发,情为已发”而心贯未发已发的心性名义问题之解决,并以此作为朱熹最终建立心性情三分构架之理论的标志。当然,这一分析有诸多朱熹文献可以提供支持,无疑有充分的说服力。然而,就在己丑之悟以后,朱熹自己是怎么说的呢?他在己丑之悟以后的第一时间,给湖南学者发出的那封著名的《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中这样说道:“……乃知前日之说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当,而日用功夫全无本领,盖所失者不但文义之间而已。”在这里,朱熹无疑表明以往在心性名义问题上的“所失”虽大犹小,而在日用本领工夫问题上的“所失”虽小犹大。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朱熹所谓的“日用功夫全无本领”,现在我们就来读一读《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
《中庸》未发已发之义,前此认得此心流行之体,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遂目心为已发,性为未发。然观程子之书,多所不合,因复思之,乃知前日之说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当,而日用功夫全无本领,盖所失者不但文义之间而已。
按《文集》、《遗书》诸说,似皆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此心寂然不动之体,而天命之性当体具焉。以其无过不及,不偏不倚,故谓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喜怒哀乐之性发焉,而心之用可见,以其无不中节,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此则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
然未发之前不可寻觅,已发之后不容安排。但平日庄敬涵养之功至,而无人欲之私以乱之,则其未发也,镜明水止,而其发也,无不中节矣。此是日用本领工夫。至于随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为本,而于已发之际观之,则其具于未发之前者,固可默识。
故程子之答苏季明反复论辨,极于详密,而卒之不过以敬为言。又曰“敬而无失,即所以中”,又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盖为此也。向来讲论思索,直以心为已发,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识端倪为最初下手处,以故缺却平日涵养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扰扰,无深潜纯一之味,而其发之言语事为之间,亦常急迫浮露,无复雍容深厚之风。盖所见一差,其害乃至于此,不可以不审也。……[33]
此函颇长,然其要点无非有二:一是朱熹反省了“以心为已发”这一心性名义上的错误,导致平常一味就已发之后着手做“察识端倪”的工夫而“欠缺平日涵养一段工夫”;一是朱熹明确了“平日庄敬涵养”才是“日用本领工夫”。他引用三段有关“敬”的语录,以强调程子的为学宗旨“不过以敬为言”,这也就意味着朱熹自己的主敬思想的确立。
当然,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封书信所透露出来的思想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其中令人关注的是相对于“平日涵养”而言的“察识端倪”。不用说,于宋代思想之史实稍熟悉者便可知这是指以胡宏(号五峰,1102—1161)为首的湖湘学派的标志性观点:先察识后涵养。朱熹的己丑之悟正是标志着他从湖湘学的先察识后涵养这一工夫论思想的阴影中摆脱了出来,确立了以敬来贯穿先后、上下、动静以及未发已发的工夫论立场。然而,从理论上看,先察识后涵养的主张又究竟错在哪里呢?也就是问,朱熹对湖湘学的批评与其主敬思想的确立又有何理论上的必然关联呢?
我们知道,其实胡宏所谓的“察识”工夫也就是“识心”工夫,因为察识的对象就是已发之心,若已发之心为良心则存而养之,若已发之心为人欲则制而去之,可见察识工夫的理论预设是“心为已发”,由于“此心在人,其发见之端不同”,因此工夫的关键就在于“识之而已”。[34]依胡宏,所谓“察识”是就已发之际,对已发之心做正面的自觉反省,然后“操而存之,存而养之,养而充之”,[35]这就与杨时(号龟山,1044—1130)至李侗(世称延平先生,1093—1163)的“道南一脉”所言由静摄心并于未发之际涵养之指向不同。在中和新悟之前,朱熹的工夫论便在湖湘一路与道南一路之间流连忘返,结果与此二者均未能相契[36],最终向程颐的主敬说回归。
要之,正是对于湖湘学的这一“知之而已”的“识心”说,朱熹在己丑之悟之后,开始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态度。为什么呢?因为在朱熹看来,心是知觉,心自会识,如果说“识心”,那么这个“识”的主体又是谁呢?难道是以一个心去“识”另一个心?朱熹打了一个比方,就好比人的眼睛自会看见东西,但是眼睛绝不能看自己的眼睛,他说:
如湖南五峰多说“人要识心”。心自是个识底,却又把甚底去识此心?且如人眼自是见物,却如何见得眼?故学者只要去其物欲之蔽,此心便明。如人用药以治眼,然后眼明。[37]
所论近世识心之弊,则深中其失。古人之学,所贵于存心者,盖将即此而穷天下之理。今之所谓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其得失之端,于此亦可见矣。故近日之弊,无不流于狂妄恣肆而不自知其非也。[38]
这里的第一段是说,胡宏“识心”无非是以心识心,其错误犹如以“人眼”见“人眼”,而在朱熹看来,“人眼自是见物,却如何见得眼”,这是非常荒唐的。第二段是指“识心”说一味向内用功而忘却了天下之理——亦即置穷理工夫于不顾。朱熹以为以上两点便是湖湘学“识心”说的主要弊病。
关于“识心”何以导致排斥穷理,这里且不深究,重要的是朱熹的第一点批评,正是在这一批评的背后,朱熹想要表达的一个观点十分重要。可以这么说,假设识心说成立的话,就必将导致两种后果:要么承认在人心之上之外存在另一个心之本体[39],要么承认心既是知觉的主体又是知觉的客体。当然须看到,这两种后果的假设其实都是朱熹依其理论所做的诠释和判断,未必就是湖湘学主张“识心”的必然结论。若依胡宏,心体本无善恶,心体之发动有善有恶,故于心之已发之际察识其端倪,见其善者涵养之,见其不善者克服之,此便是胡宏“识心”说的真实涵义,其中并没有“以心识心”之意。但不管怎么说,在朱熹看来,上述两种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错误,更是己丑之悟后的朱熹所遇到的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若结合本节开首所提示的“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的命题来看,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此心何以能做到“自做主宰”?
三、以敬为主而心自存
事实上,自己丑之悟后,朱熹的思想体系虽已基本确立,但他所面对的问题仍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与其“心论”密切相关的工夫论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同时,他所要面对的却是当时的湖湘学派,而他所用的理论武器便是由程颐那里继承而来的主敬思想。那么,敬与心又有什么理论上的关联呢?
朱熹曾在给当时湖湘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张栻(号南轩,1133—1180)的书信中指出:
以敬为主,则内外肃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为主而欲存心,则不免将一个心把捉一个心。外面未有一事时,里面已是三头两绪,不胜其扰矣。就使实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释之异,亦只于此便分了。如云“常见此心光烁烁地”,便是有两个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见者是真心乎?[40]
这里讲了三层意思:第一,朱熹从正面指出“以敬为主”的主敬工夫能够使内心和外表获得整齐肃然的效果,并使内心达到“不忘不助”的状态,最终实现“心自存”的境地;第二,如果不以敬为主而企图做一番“存心”工夫,则其结果必将导致“将一个心把捉一个心”,还未等到应接事物,内心已经纷乱不堪,退一步说,即便能做到“把捉”此心,这种“把捉”方法本身已是“大病”,何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第三,是根据“以敬为主”、“而心自存”的工夫去做,还是按照“将一个心把捉一个心”的方法去做,这是儒家与佛教的根本分歧之所在,佛教所说的“常见此心光烁烁”,其实已经表明存在着两个“主宰”,不知到底“光”之本身是“真心”?还是“见”此光者是“真心”?
无疑地,朱熹在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愈发关键,一言以蔽之,由主敬立场出发,便可实现此心“自存”而从根本上消解二心之间的“把捉”问题(即“一个心把捉一个心”),这正是朱熹敬论的一个核心观点。那么,何谓“把捉”呢?事实上,由这封寄给张栻的书信来看,朱熹的话是有针对性的,他所针对的就是湖湘学的“识心”说。在朱熹看来,正是胡宏等人主张的“识心”说未免陷入“以一个心把捉一个心”的弊端。
上面提到胡宏所言“察识”工夫其实就是“识心”工夫,对此,我们须再做稍详的探讨。向来以为,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胡宏的思想经由其父胡安国(谥文定,1074—1138)、谢良佐而上溯至程颢(号明道,1032—1085),相对于程颢重“识仁”,胡宏则重“识心”。他说:“知天之道,必先识心,识心之道,必先识心之性情。”(《知言》卷五)可见,他将“识心”提到了“知天之道”的高度,同时他也强调“识心”须从“识心之性情”入手。那么,何谓“心”呢?在胡宏,大致可以两段话来阐明:“心无不在,本天道变化,与世俗酬酢,参天地,备万物,人之为道,至大也。”(《知言》卷五)“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知言》卷一)可见,就客观上看,心是一种“参天地,备万物”的存在,能与天道为一;从主观面看,心具有“知天地,宰万物”的能力,最终达到“心以成性”。牟宗三以“以心著性”四字来概括胡宏思想之宗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心性关系问题上,胡宏指出:“心纯则性定而气正。”(《知言》卷二)“气之流行,性为之主;性之流行,心为之主。”(《知言》卷三)“未发只可言性,已发乃可言心。”(《知言》卷四)“圣人指明其体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知言》卷六)“有而不能无者,性之谓欤!宰物不死者,心之谓欤!”(《知言》卷四)再三强调“心”是工夫的着手处、落脚点。对于胡宏以上所言,唐君毅总结道:
观此五峰之言,乃明以心为形而上的普遍而永恒之一流行之体,而大同于象山之所谓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之言。……此所谓心之已发,同于心之呈现,故无论在事物思虑之交,或无思无为之际,但有此心之呈现,即是发。……故性之流行,心为之主,而性亦由心而成。……心乃居于一切有形有气者上一层次,与形气不直接相关者。[41]
这是说胡宏所言“心”乃一形上的普遍之心体,同于象山心学意义上的“吾心”,由此以观胡宏所言“心之已发”,实即“心之呈现”之意,而“性之流行”亦取决于“心之呈现”,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性亦由心而成”。总之,胡宏所说的“心”是超越于形气之上的本体存在。据此,胡宏所谓的“识心”之“识”同于程颢的“识仁”之“识”,“皆当顺孔子所谓默识之识去了解”。何谓孔子的“默识之识”?唐君毅进而指出:“孔子之默识,正当为一无言之自识,而自顺理以生其心者,固非往识事一物、一对象、而涵把捉或捕捉意味之认识也。”[42]由此推知,故胡宏“识心”之“识”绝非是以外在事物为对象的认识活动意义上的“识”——内含把捉或捕捉之意味,而是指向内心的一种“默识”——亦即“无言之自识”。换言之,胡宏“识心”之“识”绝非寻求把捉之意,而是对心体的一种“默识”。唐氏此说值得参考。
不过,唐君毅的上述分析是针对朱熹对胡宏“识心”的批评而提出的反批评,然在朱熹则未必能完全承受,其云:“若‘默而识之’,乃不言而存诸心,非心与理契,安能如此!”[43]意谓“默识”已是“心与理一”之境界,非常人所能做到。故在朱熹看来,胡宏的“识”谈不上是什么“默识”,而仍然是一种“把捉”而已。更重要的是,朱熹认为若依胡宏所说,在心之已发处去做察识之工夫,则将导致“此心遂成间断”之后果,而且若就“已放之心”而后去察识、操存,则其工夫转辗繁难而“无复有用功”之处,如果总是等待已发之后,才去察识操存,其结果也不过是“发用之一端”而已,对于心体之“本源全体”未能做到“一日涵养之功”,以为由此“扩充”便可达到“与天同大”,也就未免太过狂妄了[44]。在这里,朱熹显然强调工夫不能片面地追求于心之已发后察识,更有必要在未发前涵养“本源全体”,并以此来打通未发已发之工夫。此可见朱熹主敬之最终确立,与其反省湖湘学“先察识”之工夫理路密切相关,其关节点有二:一是“察识”已不免“把捉”之意,与儒学所言操存涵养此心而令此心自做“主宰之味不同”,即所谓“今人著个‘察识’字,便有寻求捕捉之意,与圣贤所谓操存、主宰之味不同。……如胡氏之言,未免此弊也”[45];一是若无主敬之涵养工夫而欲察识已发之心体,则终无成功之日,即所谓“若必待其发而后察,察而后存,则工夫之所不至者多矣”[46],“盖发处固当察,但人自有未发时,此处便只合存,岂可待发而后察、察而后存耶?”[47]正是针对以上两种弊端,所以朱熹强调以敬为主而心自存。
至此,我们终于了解朱熹之主敬并非单纯地向程颐思想的回归,而是通过对湖湘学派(亦含道南一派)的反省与批判而逐渐形成的,他所强调的主敬更为强调心在未发与已发的过程中自做主宰。当然,心之主宰义也是程颐主一以及胡宏识心的固有主张,但朱熹论心之主宰则强调须由敬契入,以提撕唤醒心的自存自省,而这一点才是朱熹敬论的最大特色之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朱熹说敬就是心的自做主宰处。
其实,从字义上说,敬就是提撕唤醒、令其警觉之意,所谓心的自存自省,也就是在此意义上说的,朱熹指出:
“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无事时,且存养在这里,提撕警觉,不要放肆。到讲习应接时,便当思量义理。[48]
敬是个莹彻底物事。今人却块坐了,相似昏倦,要须提撕著。提撕便敬;昏倦便是肆,肆便不敬。[49]
此一个心,须每日提撕,令常惺觉。[50]
何者为心?只是个敬。人才敬时,这心便在身上了。[51]
只敬则心便一。[52]
敬者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本根也。[53]
可见,提撕警觉便是涵养用敬之意。但须注意的是,敬毕竟不是心体本身,敬只是一种工夫,所以可以用“持”、“居”、“主”、“存”等动词加在“敬”字之上,如其所云:
摄心只是敬。[54]
只是要收敛此心,莫要走作,走作便是不敬。[55]
人能存得敬,则吾心湛然,天理灿然,无一分着力处,亦无一分不着力处。[56]
这都是说,敬是一种工夫,敬之本身不是湛然之“吾心”或灿然之“天理”。所以,朱熹极力反对在主敬过程中去寻求什么“敬之体”,例如:
敬只是敬,更寻甚敬之体?[57]
静坐而不能遣思虑,便是静坐时不曾敬。敬则只是敬,更寻甚敬之体?[58]
其实,在朱熹,敬并不是如性理那样的终极实在,也不是心之本体(朱子学意义上的心之本然状态)之本身,故根本谈不上“敬体”这一概念。
然而,何以又有所谓“敬之体”的问题出现呢?这部分原因也许出在朱熹自己的某些表述,例如他说:“敬字通贯动静,但未发时,则浑然是敬之体。非是知其未发,方下敬底工夫也。”[59]然细按其意,“体”字并非实指,意谓未发正是做主敬工夫的理想状态。不过,朱熹接着又说:“既发,则随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60]这样一来,“敬之体”与“敬之用”成为相对而言的对句,不免引起后人将“体用”套在对敬的解释上,仿佛“敬”是一种有体有用的独立存在。诚然,从名义的角度看,以体用言敬,确有失严密。然朱熹无非是借“体用”一语以表明持敬工夫贯穿于心之未发与已发,并没有将敬字本身提升至本体地位的丝毫想法。
问题在于,既然“敬”的工夫能令此心“自做主宰”、“自省自存”,那么这个被称为“敬只是敬”的工夫本身是否需要由“心”来主导?事实上,从学理上说,我们可以问:敬的工夫何以只是敬的工夫而已?如果没有“心”(且不论是否是孟子的本心抑或是象山的吾心、阳明的良心)的引领,敬的工夫何以可能?更为直截了当地问,敬与心究竟何者为先(非时间在先而是形上在先)?何者为本?能否用先后、本末、体用这类范畴来规定敬与心的关系——例如心本敬末、心先敬后、心体敬用?恕笔者直言,在朱熹的文字中,完全看不到有此类的说法,也就是说,在朱熹,他根本不曾想把敬字工夫的理据诉诸心体。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倒是赞同牟宗三以“空头的涵养”来批评朱熹之敬论,只是此所谓“空头”应理解为朱熹的主敬工夫缺乏心体的指引,而不是指朱熹主敬缺乏内容。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结语中再做稍详的讨论。
四、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
按照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以敬为主而心自存等命题来看,敬是令此心“作主”、“自存”、“常存”的保证,但不能倒过来说,以心为敬作主。与此思路一致,朱熹还有一个重要说法,即“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而且朱熹将此提到了“为学”之“大要”的高度来加以肯定,换言之,以敬收心,可谓是朱子学的为学宗旨。他说:
为学有大要。若论看文字,则逐句看将去。若论为学,则自有个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个敬字与学者说。要且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放在模匣子里面,不走作了,然后逐事逐物看道理。尝爱古人说得学有缉熙于光明,此句最好。盖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为学者,要令其光明处转光明,所以下缉熙字(缉如缉麻之缉,连缉不已之意。熙则训明字)。心地光明,则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见得。且如人心何尝不光明?见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尝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种人自谓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见。似此光明,亦不济得事。今释氏自谓光明,然父子则不知其所谓亲,君臣则不知其所谓义,说他光明,则是乱道。[61]
这是说,做学问是有根本方法的,如果读书,可以逐字逐句地读,但若是说做学问,则自有根本之法,这就是程子向学者所说的“敬”。这个“敬”是什么意思呢?要而言之,就是要用“敬”来收敛身心,如同把身心放在一个“模子”里面那样,能使身心运作不走样,然后随事就物上去穷究事物之理。朱熹接着说:就本来意义上而言,心地原是“光明”的,本无污染,犹如人见他人做得对便说对,做得不对便说不对那样,心里面的是非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人心易受后天环境的不良影响,染上利欲熏心等毛病,使得心地昏暗了。至于佛教所说的“光明”则全不着地、脱离事物,如父子不知亲、君臣不知义,这种所谓的心地“光明”最为危险可怕。
朱熹在这里所欲表明的观点有互为关联的两层意思:第一,为学大要在于以敬之工夫来收敛身心;第二,这是由于人心“才明便昏了”的缘故。至于另一层意思——心地原是光明,则不是主敬工夫的前提设定。朱熹的思路是:心地虽然原本光明,但不可以光明之心去主导敬之工夫,否则的话,就必须承认有一个形上的、普遍的、永恒的心之本体或道德本心的存在。由此可见,朱熹所说的“光明”只是就心地的原初意义上而言,而非就心地的超越意义上立论。要之,不能在主敬工夫之前之上预设心之本体的存在,这是朱熹不可退让的原则立场,他之所以强烈反对湖湘学的“以心观心”(当然这是朱熹的诠释而不一定是胡宏“识心”说的真实内涵)并将其喻作佛教的“以心求心”,其思想缘由便在于此。
值得一提的是,朱熹所说的“放在模匣子里面”的比喻性说法非常生动有趣,这是由于朱熹很担心“身心”容易脱离轨道、胡乱运作,故有必要用“模匣子”来规范它、约束它。这个“模匣子”就是比喻“敬”,由此推论,由“敬”摄心便是指知觉层面上的人心而不能是道德层面上的本心。例如朱熹还有一些说法,也表明了同样的意思:
人只有个心,若不降伏得,做甚么人?[62]
人心万事之主,走东走西,如何了得?[63]
心既常惺惺,又以规矩绳检之,此内外交相养之道也。[64]
今于日用间空闲时,收得此心在这里截然。……常常恁地收拾得这心在,便如执权衡以度物。[65]
且要收拾此心,令有个顿放处。若收敛都在义理上安顿,无许多胡思乱想,则久久自于物欲上轻,于义理上重[66]
这里所说的“降伏”、“收拾”、“收敛”、“绳检”等动词的主体都是“敬”,相对地说,“心”则是“敬”的客体对象。要把心安顿下来,安顿在“义理上”,便是主敬工夫的主要任务。其云去“物欲”存“义理”而令此心不至于“东走西走”、“胡思乱想”,亦是将心之状态规定为敬之工夫的对象。正是通过上述“收拾”、“收敛”等等主敬工夫的程序,然后才能实现人心为主(“万事之主”)的目标,朱熹喻作“如执权衡以度物”,意谓由敬摄心,方能使此心成为“度物”之标准。也正由此,所以朱熹说敬既是“一心之主宰”又是“万事之本根”,不能倒过来说,心是敬之主宰。其云“人之心性,敬则常存,不敬则不存”[67],亦同此义,意谓敬才是存心养性的根本方法而不是相反。由此出发,故朱熹说,敬是为学之根本大法,是圣学第一义之工夫。朱熹断然指出:
敬之一字,万善根本。涵养省察、格物致知,种种功夫皆从此出,方有据依。[68]
圣门之学,别无要妙,彻头彻尾,只是个敬字而已。[69]
其中的“据依”亦即“依据”。这是说,“敬之一字”乃是“涵养省察,格物致知,如种种功夫”的依据。但须指出的是,此所谓“依据”,只是就方法论而言的本源之意而非就本体论而言的理据之意,换言之,就方法论而言,各种工夫方法虽然名目繁多,但其中有一个根本的方法,那就是主敬,显然这是平铺地说主敬是一切工夫的“据依”,而不是形上地说“敬”是心性之“理据”,因为“敬”并非是独立存在的实体。不过令人注意的是,朱熹的上述说法涉及主敬与致知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主敬与集义、居敬与穷理的关系问题,这里须稍加考察。
由上所述,主敬工夫主要是指向人心而言,属于一种内心之工夫,这一点殆无疑义,然而如果说只要“守定一个敬字”,便可一了百了,于应事接物亦可全然不顾,则非但不是朱熹之主张,而正是朱熹所批评的偏见。他指出:
敬不是万事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70]
若学者,当求无邪思,而于正心诚意处着力。然不先致知,则正心诚意之功何所施?所谓敬者,何处顿放?今人但守一个“敬”字,全不去择义,所以应事接物处皆颠倒了。[71]
这里以“随事专一”言“敬”,表明主敬工夫必落在“事”上,也就是后一段所强调的在“应事接物处”做一番“集义”工夫的观点。关于这一点,朱熹常常用程颐的“敬义夹持”说来加以强调,他说:“敬义夹持,循环无端。”[72]那么,如何来理解这种“夹持”关系呢?朱熹有一个解释,可谓曲尽其详:
彼专务集义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虚骄急迫之病,而所谓义者或非其义;然专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间念虑起处分别其公私义利之所在,而决取舍之几焉,则恐亦未免于昏愦杂扰,而所谓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谓集义,正是要得看破那边物欲之私,却来这下认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头头处处,无不如此体察,触手便作两片,则天理日见分明,所谓物欲之诱,亦不待痛加遏绝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领,则固当以敬为主,但更得集义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则于敬益有助。盖有不待著意安排而无昏愦杂扰之病。……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谈义、去本逐末,正欲两处用功,交相为助,正如程子所谓“敬义夹持”,直上达天德,自此者耳。[73]
在这里,朱熹强调居敬与集义交相为用的观点,不过从中仍然可以看出,朱熹还是坚持“若其本领,则固当以敬为主”的观点,这是朱熹己丑之悟后所坚持的“日用本领工夫”的一贯立场,不容改变。
朱熹还用“互相发”的说法来解释居敬与穷理的关系:
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两足,左足行则右足止,右足行则左足止。又如一物悬空中,右抑则左昂,左抑则右昂,其实只是一事。[74]
问题是这种“互相发”的工夫,何者更为根本?从上述这段话的字面来看,朱熹只是说两者互以他者为必要条件,缺一不可,亦即两者是平行的关系,而其最后一句“其实只是一事”,则意谓两种工夫其实只是同一个工夫的过程。这一思维方式,颇类似于朱熹的“知行并进”说,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节还有讨论,这里须指出这一并行关系的两种工夫虽同处在一个工夫过程中,可以说穷理离不开居敬,也可说居敬离不开穷理,但是只有居敬工夫具有贯动静、通上下、成始终、无间断、常惺惺之特征,显然比穷理工夫更为根本。故有学者认为朱熹在工夫论问题上,以主敬为第一义,穷理为第二义,亦不无道理。[75]如朱熹曾说:
为学两途,诚如所喻。然循其序而进之,亦一而已矣。心有不存,物何可格?然所谓存心者,非拘执系缚而加桎梏焉也。盖尝于纷扰外驰之际,一念之间,一有觉焉,则即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长,不加一毫智力于其间,则是心也,其庶几乎![76]
这段论述非常重要,虽然没有提到“敬”字,但我们却可以将此放在“敬”的脉络下来观察朱熹有关心物关系问题的立场。从其表述看,存心与格物并存不悖、相互为用,故谓“一而已矣”,然而心若不存,则格物工夫亦无可下手,显然存心较诸格物更为根本。如朱熹曾明确指出:
《大学》须自格物入,格物从敬入最好。只敬,便能格物。敬是个莹彻底物事。[77]
至于如何存心,朱熹强调只是在一念之间,一觉此心,则此心在也,其间容不得丝毫的智力安排。其实,这里的“觉”字,便是敬字工夫的提撕义。关于觉、心、敬的彼此关联,我们可以归纳为八个字:觉底是敬,觉处即心[78]。要之,存心其实就是由居敬工夫“一觉此心”之意。重要的是,由“一觉此心”便可令此心自在(“即此而在”),而觉此心者端在于敬字工夫,此即朱熹再三强调的主敬可使“自心自省”之意,也就是“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之意。
最后顺便指出,在有关敬与心的关系问题上,朱熹曾有这样一个定义:“敬则心之贞也。”[79]这是说,敬就是指心之贞定。按,此《答张钦夫书》非常著名,即所谓“诸说例蒙印可”书,为朱熹40岁时所作,然清儒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于“38岁”条却谓“后来都无此语”,意指该说为朱熹未定之论,不明理由何在。牟宗三则断定王说为非,并对“敬则心之贞也”有所肯定:“此语实甚佳。在朱子系统中,其意即是心气之贞定与凝聚,非从本体性的超越心而言也。”并说:“此义亦不悖于朱子静涵静摄之系统”[80]。可以看出,牟氏之肯定是顺着朱熹而说,若依牟氏之判教立场而言,则此“静涵静摄”盖谓朱熹思想之特质为理“存有而不动”,其动者为心气,而这一点正是牟氏所不能认同的。不过在笔者看来,于朱熹之主敬则不可以“静”字概之,朱熹所言主敬工夫意义上的“自心自省”之“心”亦非“心气”一词可以概之。诚然,由“敬则心之贞也”之命题的内涵来看,心是敬之对象,此即朱熹所言由敬摄心的题中应有之意,若此,则心莫非是现象实然之存在而可归于“气”之范畴?关于心是否就是气的问题,上引拙文已有讨论,这里不必赘述。要而言之,至少在朱熹敬论的思想脉络中,由敬而提撕唤醒之心乃是一“为主”而不“为客”之存在[81],绝非“心气”一词所能涵盖。朱熹所用的“心气”一词,例如:“讽诵歌咏之间,足以和其心气”[82],“心平气和”、“心气和平”[83]等等,均是日常语言所说的心平气和之意,并不具有特殊的思想意涵。事实上,如何结合朱熹所说的“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来看,那么“敬则心之贞也”便不难理解,其意无非是说敬能令此心“贞定”而发挥“主宰”之作用。
五、主敬工夫诸说
以上我们初步探讨了朱熹敬论的问题意识之由来以及由敬而令此心自做主宰、自省自存、收敛身心等问题,这些探讨还不足以覆盖朱熹敬论的全部内涵。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再对朱熹敬论的其他相关论述做相应的了解。
须指出,朱熹工夫论之特质表现为以主敬“立本”、以穷理“致知”,然其论敬主要指向“心定理明”[84],亦即属于如何使内心得以贞定之工夫,但是主敬工夫又必落在“事为”上讲,如其所云“(敬)只是随事专一”,这是其敬论的一项原则,同时也是指主敬工夫的着手处,朱熹这方面的言论甚多,例如:
持敬之说,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齐严肃”、“严威俨恪”、“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此等数语,而实加工焉,则所谓直内,所谓主一,自然不费安排,而身心肃然,表里如一矣。[85]
夫持敬用功处,伊川言之详矣。只云:“但庄整齐肃,则心便一,一则自无非僻之干。”又云:“但动容貌,整思虑,则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处,不待先有所见而后能也。须是如此,方能穷理而有所见。惟其有所见,则可欲之几,了然在目,自然乐于从事,欲罢不能,而“其敬日跻”矣。伊川又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若能持敬以穷理,则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按,指佛教)之邪妄,将不攻而自破矣。[86]
朱熹认为主敬工夫非常简单,即从平常的整齐严肃、严威俨恪、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等这些外部层面做起即可,重要的是,在施行这些工夫之前,不须“先有所见”,这里的“见”,大致是指意见或见解,意思是说,不必在持敬之前,先有什么“意见”安排,因为一旦做到“动容貌,整思虑”,就“自然生敬”,所以说“敬以直内”的工夫是“自然不费安排”的。这个说法值得回味,这是否意味着敬字已含有道德心之涵义,故不必另以道德之本心来主导引领,这一点还须另做探讨。简言之,由其“庄整严肃,则心便一”、“动容貌、整思虑,则自然生敬”的表述来看,整齐严肃就是持敬工夫之本身,甚至可谓是主敬之“至论”,[87]但是却不能看出整齐严肃之前另须设定一个“心”的存在。相反,“身心肃然,表里如一”乃是整齐严肃等一套持敬工夫的结果而不是前提。
也正由此,所以朱熹对程颐以来的主敬四句,就特别重视“整齐严肃”,以为时常保持此心警觉而不间断的谢良佐“心常惺惺”之说固然“极精切”,但“不如程子整齐严肃之说为好。盖人能如此,其心即在此,便惺惺。未有外面整齐严肃,而内不惺惺者。”[88]尽管朱熹也承认“四句不须分析,只做一句看”,[89]但从根本上说,“整齐严肃便是敬,散乱不收敛便是不敬”[90],仍然强调整齐严肃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心常惺惺则是主敬工夫过程中的一种效果,尹和靖的“其心收敛不容一物”,亦复如此。事实上,所谓整齐严肃,在儒家的教学体系中,原本属于“小学”一段工夫,无甚高妙之可言,如朱熹所云:“问:‘《大学》首云明德,而不曾说主敬,莫是已具于《小学》?’曰:‘固然。自《小学》不传,伊川却是带补一敬字。’”[91]又说:“持敬以补《小学》之阙。《小学》且是拘检住身心,到后来‘克己复礼’,又是一段事。”[92]尽管如此,持敬乃具有贯穿儒门工夫的根本特性。
上面曾提到朱熹论敬必落在事上讲,但是并不等于说主敬工夫没有独立的意义,切不可误认为敬只具有针对特定事物而言的相对意义。例如朱熹曾针对程迥(号沙随)反对单独说“敬”的观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近世程沙随犹非之,以为圣贤无单独说“敬”字时,只是敬亲、敬君、敬长,方着个“敬”字。全不成说话。圣人说“修己以敬”(《论语·宪问篇》),曰“敬而无失”(《论语·颜渊篇》),曰“圣敬日跻”(《诗·商颂·长发篇》),何尝不单独说来?若说有君、有亲、有长时用敬,则无君亲、无长之时,将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说![93]
朱熹的意思是说,主敬既“主于事”而言,同时也“主于心”而言,因此虽然持敬须在事上落实,但在无事时持敬涵养也同样重要;如果执定持敬工夫只能在有事时做,则完全有可能忽视无事时的主敬工夫。关于无事时做涵养工夫,朱熹曾说:
谓当涵养者,本谓无事之时,常有存主也。……谓省察于将发之际者,谓谨之于念虑之始萌也;谓省察于已发之后者,谓审之于言动已见之后也。[94]
按照程颐“涵养须用敬”的说法,显然朱熹所说的涵养,意同主敬。相对而言,“省察”则是已发以后的工夫。在朱熹,格物致知亦相当于已发后知工夫。但是,究竟是涵养在先省察在后,还是两者应同时并进,却成了困扰朱熹的一个问题。
从根本上说,既然主敬是圣门彻上彻下之工夫,因此就必须说:“当以涵养为本。”朱熹曾说:“涵养、体认、致知、力行……四者本不可先后,又不可无先后,须当以涵养为本。”[95]这个说法很微妙。所谓本无先后,这是指在具体的工夫过程中,涵养至力行的四项工夫应当同时并进;所谓不可无先后,则是指从原则上说,涵养更为根本,应以涵养为先。[96]这一观点的正式确立应当是在己丑之悟以后,对湖湘学的“先察识后涵养”之工夫次序的彻底扭转而实现的,此亦不待赘言。
但是,在反映朱熹晚年思想的《语类》中,朱熹的种种说法却表明其对涵养省察的工夫次第之看法并不严格,他一方面说“须先涵养清明,然后能格物”,但接着又说“亦不必专执此说”[97];他一方面说“须是平日有涵养之功,临事方能识得,若茫然都无主宰,事至然后安排,则已缓而不及于事矣”[98],但另一方面又说“须先致知而后涵养”[99],“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100],“义理不明,如何践履”[101],显然又在主张穷理在涵养之先。朱熹又说:
某向时亦曾说,未有事时且涵养,到得有事却将此去应物,却成两截事。[102]
已发未发,不必太泥,只是既涵养又省察,无时不涵养省察。[103]
未发已发,只是一件工夫,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耳。……不曾涵养者亦当省察。不可道我无涵养工夫后,于已发处更不管他。……今言涵养,则曰不先知理义底涵养不得;言省察,则曰无涵养,省察不得。二者相捱,却成耽搁。”[104]
可见朱熹晚年于涵养省察之工夫次第的看法很宽松,认为两者既互相独立又相辅相成。据此可知,朱熹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以涵养为主,只是就“大纲说”,[105]而就具体的工夫过程而言,则如同“知行并进”的命题一样,朱熹不得不说:“涵养穷索,二者不可废一,如车两轮,如鸟两翼。”[106]
由此以观,我们就很难说,朱熹思想只是一重敬的义理形态,因为朱熹始终不能放弃的一个立场是《大学》之要领在于“格物”两字,所以他就不能单方面地强调涵养可以取代致知而致知亦有助于涵养的想法。准此,我们则不妨可说,朱熹思想亦是一重格物的义理形态。当然也须看到,若是就“大纲说”——亦即从原则上说,无疑地以敬为本乃是朱熹工夫论的基本立场,敬可令此心自做主宰、可以自省自存、可以收敛个身心等观点才是朱熹工夫论思想的核心所在。故云:“《大学》须自格物入,格物从敬入最好。只敬,便能格物。”107]至于朱熹的主敬理论能否真正地实现“此心自做主宰”,而朱熹的这套工夫理论是否蕴含有以此主宰之心来引领格物致知之想法,则属于理论评判的问题,已经越出了朱熹思想本身的范围。
最后与朱熹敬论有关,有必要探讨一下朱熹对孟子“求放心”说的看法。上已提及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求放心而已矣”可谓是宋明理学家莫不关注的一个工夫论问题。在朱熹的时代,他便遇到其门人不断的提问,究竟应该如何“求放心”?我们翻开《语类》卷59《孟子九·告子上》“牛山之木章”及“仁也人心章”,便可看到朱熹与其门人有关这一问题的大量讨论,这里仅就其所论“求放心”与主敬有何关联略做探讨。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最为学第一义也。故程子(按,指程颢)云:“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某近因病中兀坐存息,遂觉有进步处。大抵人心流滥四极,何有定止?一日十二时中有几时在躯壳内?与其四散闲走,无所归著,何不收拾令在腔子中。且令纵其营营思虑,假饶求有所得,譬如无家之商,四方营求,得钱虽多,若无处安顿,亦是徒费心力耳。[108]
这段话肯定了孟子“求放心”说的重要性,以为是“最为学第一义”,这个说法与其将主敬视为圣学工夫第一义的观点是相通的,因为“求放心”其实与主敬工夫是有关联的。朱熹又说:
季成问“放心”。曰:“如‘求其放心’,‘主一之谓敬’之类,不待商量,便合做起。若放迟霎时,则失之。”
孟子言“求放心”,你今只理会这物事常常在时,私欲自无著处。且须持敬。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可煞是说得切。子细看来,却反是说得宽了。孔子只云:“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若能如此,则此心自无去处,自不容不存,此孟子所以不及孔子。
这里所说均与敬字工夫有关,特别是第三段说孟子“求放心”“却反是说得宽了”值得引起注意,显然这是朱熹在将“求放心”与孔子“居处恭,执事敬”进行比较后所做出的判断,至于朱熹所说“若能如此,则此心自无去处,自不容不存”,若能对上述朱熹主敬思想有所了解,显然一望便知,这正是朱熹的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自省自存之意。也就是说,在朱熹看来,毕竟孔子的“执事敬”要比孟子的“求放心”说得更为严密。
那么,何以有此一说呢?事实上,朱熹对“求放心”的“求”字如何解读有所困惑,他指出:
人心才觉时便在。孟子说“求放心”,“求”字早是迟了。
孟子云“求放心”,已是说得缓了。心不待求,只警省处便见。“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其快如此。盖人能知其心不在,则其心已在了,更不待寻。[109]
这里的第一句“人心才觉时便在”以及最后一句“人能知其心不在,则其心已在了,更不待寻”不就是朱熹在论述主敬时常说的“一念之间,一有觉焉,则即此而在”的意思吗?也就是我们所总结的觉底是敬、觉处是心的意思。依朱熹,“觉”字即提撕义、唤醒义,乃是主敬工夫的要领所在,而孟子的“求”字“早是迟了”,意思是说“求”的前提必有一主一客的对峙、时间先后的差异。由时间上“迟了”来反推,则可看出,“求”也有可能导致“来不及”,正是在此意义上,朱熹又说“求”字亦是一“剩语”:
或问“求放心”。曰:“知得心放,此心便在这里,更何用求?适见道人题壁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说得极好!《知言》中或问‘求放心’,答语举‘齐王见牛’事。某谓不必如此说,不成不见牛时,此心便求不得!若使某答之,只曰:‘知其放而求之,斯不放矣。’‘而求之’三字,亦自剩了。”
或问:“求放心。愈求则愈昏乱,如何?”曰:“即求者便是贤心也。知求,则心在矣。今以已在之心复求心,即是有两心矣。虽曰譬之鸡犬,鸡犬却须寻求乃得;此心不待宛转寻求,即觉其失,觉处即心,何更求为?自此更求,自然愈失。此用力甚不多,但只要常知提醒尔。醒则自然光明,不假把捉。今言‘操之则存’,又岂在用把捉!亦只是说欲常常醒觉,莫令放失便是。”这两段话已经说得十分明确,“即觉其失,觉处即心,何更求为”其实便是朱熹的主敬论述,包括“常知提醒”、“不假把捉”、“常常醒觉”等等说法,无不都是朱熹之论敬的重要观念表述。重要的是,在朱熹看来,“求”字已不免“以已在之心复求心,即是有两心”之弊,质言之,亦即“以心求心”之弊。对此一问题的态度,朱熹通过对湖湘学的清算已经表达得十分清楚,这里也就不必赘言了。
不过须指出的是,朱熹对“求”字虽有种种苛求,但并不意味着他对孟子“求放心”采取的是否定之态度,其实朱熹的意图在于欲将“求放心”纳入其主敬思想的轨道,这才是朱熹对孟子“求放心”的一种创造性诠释,例如:
孟子盖谓,鸡犬不见,尚知求之;至于心,则不知求。鸡犬之出,或遭伤害,或有去失,且有求而不得之时。至于此心,无有求而不得者。便求便在,更不用去寻讨。那失底自是失了,这后底又在。节节求,节节在。只恐段段恁地失去,便不得。今日这段失去了,明日那段又失,一向失却,便不是。
或问“求放心”。曰:“此心非如鸡犬出外,又著去捉他;但存之,只在此,不用去捉他。放心,不独是走作唤做
放,才昏睡去,也是放。只有些昏惰,便是放。”
不待说,这里用“便求便在,更不用去寻讨”、“但存之”、“不用去捉他”等说法来解释“求放心”,已有明显的朱熹主敬的诠释思路。
要之,朱熹的思路是,“求”字不免有“寻讨”义、“把捉”义,相比之下,“敬”字的“自存”义、“提撕”义更为重要。关于这一点,由朱熹对“持敬”的批评可见一斑,他说:
只一个持敬,也易得做病。若只持敬,不时时提撕著,亦易以昏困。须是提撕,才见有私欲底意思来,便屏去。且谨守著,到得复来,又屏去。时时提撕,私意自当去也。[110]
六、几点讨论
由上可见,朱熹“敬论”在其整个工夫论系统中实占有核心的地位。事实上,宋代以来,在以理学或道学(亦含心学)为主流的儒学思想史上,本体与工夫这对重要观念,乃是儒学思想家在思考宇宙人生问题之际的核心关怀。也就是说,理学家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并不仅仅是天道性命的形上建构,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工夫论上对于儒家圣人之道在现实人生中的意义和价值做一番真实的体验和践履。因此,工夫论问题从来就是理学史上的一大核心问题。上引朱熹《大学或问》所云“盖吾闻之,敬之一字,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这段表述充分说明,“敬之一字”作为一种“圣学”工夫是贯穿始终的。具体而言,它是贯穿《大学》三纲领八条目的根本工夫,同时也是贯穿人之一生(包括小学阶段与大学阶段)的根本工夫。朱熹弟子黄榦(1152—1221)在《朱子行状》中对朱子之“为学”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概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以为小学大学皆本于此。”[111]这是说,朱熹的“居敬”工夫乃是贯穿“穷理致知”与“反躬实践”的两大领域,换言之,“敬”乃是贯彻于知识活动和道德活动的共同要求。至此已很明显,即便称朱熹的工夫论思想乃是一“敬”的思想形态亦无不可。但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仍有必要追问朱熹之言“敬”的义理根据究竟何在?
笔者曾在上述拙文中,就朱熹的主敬思想提出了一个质疑:
若一言以蔽之,则可说“主敬”工夫所对治的仍是人心意识,何为“主敬”之头脑的问题,依然无法找到确切的答案。事实上,如果不讲头脑,只讲“主一无适”的“主敬”——即意识的高度集中,那么这种说法就只具有心理学的意义,而不具有伦理学的意义,因为即便是盗贼在行窃之时,意识也能达到高度集中。所以,若从哲学上讲“主敬”,便须要追问“主敬”之所以可能的依据何在的问题。显然,朱熹所欠缺的正是此一追问,故其虽把“主敬”提到“圣门第一义”的高度,却仍然不免落空。[112]
由于拙文的核心问题在于朱熹的心论,对其敬论只是顺便提及,故未能展开详细的讨论。在这里则有必要对其心论与敬论的理论关联再做稍详的探讨。
事实上,或有读者已经察觉,上述质疑之关键在于“头脑”一词,由此出发,所追问的便是主敬之所以可能的依据问题。不容否认,这里所谓的“头脑”,其实是阳明学所喜欢使用的思想术语,特指心体良知,而朱熹所用“头脑”一词大多属于日常用语,如“凡看道理,要见得大头脑处分明”[113]之类,并没有特殊的思想涵义,这里不必细说。重要的是,阳明曾从“心即理”这一“头脑”处出发,对朱熹(亦含程颐)的居敬穷理说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全文颇长,但很值得回味,故全段录出:
梁日孚问:“居敬穷理是两事,先生以为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间只有此一事,安有两事?若论万殊,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又何止两?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穷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养工夫,穷理是穷事物之理。”曰:“存养个甚?”曰:“是存养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穷理矣。”曰:“且道如何穷事物之理?”曰:“如事亲便要穷孝之理,事君便要穷忠之理。”曰:“忠与孝之理在君亲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穷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如何是主一?”曰:“如读书便一心在读书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则饮酒便一心在饮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却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日孚请问。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时便是逐物,无事时便是着空。惟其有事无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穷理。就穷理专一处说,便谓之居敬;就居敬精密处说,便谓之穷理;却不是居敬了别有个心穷理,穷理时别有个心居敬:名虽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即是无事时义,义即是有事时敬,两句合说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须言义,孟子言‘集义’即不须言敬,会得时横说竖说,工夫总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识本领,即支离决裂,工夫都无下落。”问:“穷理何以即是尽性?”曰:“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穷仁之理,真要仁极仁,穷义之理,真要义极义:仁义只是吾性,故穷理即是尽性。如孟子说充其恻隐之心,至仁不可胜用,这便是穷理工夫。”日孚曰:“先儒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则不暇。公且先去理会自己性情,须能尽人之性,然后能尽物之性。”日孚悚然有悟。[114]
其中涉及对程朱理学的工夫论两大支柱——居敬与穷理——的关系究竟应如何理解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其实也就关涉到朱子学与阳明学的思想歧义究竟何在的问题。至于阳明依何理路坚持居敬穷理只是一事,并非这里所欲讨论的主题,我想提请注意的是:“如此则饮酒便一心在饮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却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显然这是针对“如读书便一心在读书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来解释“主一”(即居敬)所提出的批评。
阳明的思路非常明确,在他看来,不论是居敬还是穷理,也不论是读书还是接事,固然需要由“一心”来主导,但更要追问的是,此所谓“一心”究为何意?如果只是指意识集中,那么譬如“饮酒”、“好色”之行为,也会达到意识集中的状态,因此如果我们放弃对“一心”之本质内涵的追问,仅仅强调主一无适、收拾身心,那不仅是毫无意义的,甚至会使人心走入歧途却又茫然不知。依我们的理解,阳明的意思是说,将“主一”解释为“一心在读书上”、“一心在接事上”,那么这只不过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精神集中,如同“饮酒”、“好色”也能做到“一心”那样,这种“一心”状态并不具有伦理学的意义。至此,阳明的结论已很明显:须将“一心”往上提升,理解为形而上的“心体”,亦即“心即理”意义上的超越之道德本心,唯有从道德本心的立场出发,主敬工夫才具有相应的思想意义。
须指出的是,向来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阳明心学过于推崇心体的能动力量,从而未免导致道德上的乐观主义态度而缺乏对人心负面因素保持应有的戒慎恐惧之态度115],其依据之一便是阳明在《大学古本序》中对朱熹在《大学》八条目之外添入“居敬”工夫所表示的不满,亦即“合之以敬而益缀,补之以传而益离”[116],意谓朱熹在工夫论上突出“居敬”,完全是多此一举。依阳明,“《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117],故本领工夫不在格物也不在居敬而在于诚意。所以阳明强调指出:
《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如新本(按,指朱熹《大学章句》)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源。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于此不察,直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工夫总是一般。今说这里补个敬字,那里补个诚字,未免画蛇添足。[118]
这是批评朱熹居敬说“没根源”,意即“没头脑”。在阳明看来,《大学》一书为足本,其自身的义理自成一套体系,更不必添“敬”字以补其不足,否则的话则不免“画蛇添足”。
但是这里须注意的有两点:第一,朱熹《大学章句》并没有用居敬来补充解释格物,朱熹只是对《大学》文本出现的“缉熙敬止”、“止于敬”、“畏敬而辟”等三处的“敬”字做了文字学的解释,并没有采用程颐以来的主敬观点(如“主一无适”)来加以附会,所以阳明提出“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这一质疑,以此批评朱熹则是不公平的,况且孔门从来没有遗落这个“敬”字[119];第二,同时也须看到,阳明所针对的其实是朱熹《大学或问》将敬字来贯通大学与小学的观点。尽管如此,阳明之意并不在于否认“敬”字本身在儒学史上的应有地位,只是对于阳明而言,朱熹以主敬来穿凿附会《大学》的义理体系,以为不如此则《大学》的义理就无法彰显,这完全是庸人自扰、多此一举,因为《大学》既无缺字亦无错简,其自身便构成了一套义理圆融的体系。
其实,阳明虽对朱熹以“敬”字穿凿附会《大学》不以为然,但这并不意味着阳明对于“敬”字在儒学工夫论中的重要性有所轻忽,他指出:“尧舜之兢兢业业,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谓也,皆出乎其心体之自然也。出乎心体,非有所为而为之者,自然之谓也。敬畏之功无间于动静,是所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也。敬义立而天道达,则不疑其所行矣。”[120]此可见阳明之于《尚书》“敬畏”、《周易》“敬义”既有充分了解,又认定敬畏工夫出于“心体之自然”,亦是可以实现“天道”的。要之可说,阳明是以“心体”作为“主敬”之头脑,以克服朱熹之主敬“没根源”之弊病。
诚然,阳明心学亦有“乐是心之本体”[121]的命题,继承了周敦颐至程颢以来倡导的“寻孔颜乐处”的精神,但阳明对心体的戒惧义、敬畏义亦有一定的重视。只是阳明的基本立场在心体良知,故在敬与心的关系问题上,他的基本想法是,如果脱离心体而谈居敬,则是一种“没根源”的说法而已,如朱熹之言敬便是此类。总之,如以“敬畏”与“洒落”作为一种类型学概念来区别朱子学与阳明学为两种形态,则恐怕与整个宋明理学的历史实情并不相符。[122]
问题是,设问由心学立场以批评朱熹敬论“没根源”,这在理论上是否有效?回答应当是肯定的。但是,任何理论判断必涉及思想立场的问题,由立场之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自然不同,这一点本来无可争议。然而由心学立场出发,注重在心之本体的主宰下随时用功,所谓即本体之工夫,自有其一贯之理路,由此以观朱熹之主敬,可以看出其谓由敬定心、由敬存心,的确欠缺心体对居敬工夫的主导,在此意义上,即便说朱熹之主敬“没根源”亦有一定道理,我认为牟宗三以“空头的涵养”来批评朱熹主敬亦源自于此。当然这一理论判断已然越出了朱熹思想的义理范围,亦不意谓朱熹敬论是毫无内容、不成体系的一套空话。其实若就朱熹的义理系统看,其敬论不惟完全可以自立自足,而且自有其心性论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正如上文既已指出的那样,朱熹之主敬的问题意识在于,他要应对二程以来以体验喜怒哀乐未发为主的道南学派以及以察识已发之端倪为主的湖湘学派之观点的挑战,以防止由“以心察心”[123]、“以觉求心,以觉用心”[124]以及“以心求心,以心使心”[125]等观点而导致“心有二主,自相攫拿”[126]之弊端,由此来杜绝可能出现心的实体化、本体化之趋向,而这些弊端的根源既来自儒学内部(如湖湘学乃至象山学)又与佛教不无关联。[127]要之,朱熹所关注的始终是人心意识的现实状态及其分解状态,如何就现实当中扭转人心的错误走向乃是其思想的核心关怀,故他要求通过层层下就的脚踏实地的居敬工夫以解决如何上达天德、实现心理合一的问题,由此看来,朱熹之主敬亦在另一层面开辟出一条工夫入路的途径,亦不失为儒学的一种理论形态。
但是从记录朱熹晚年之语的《语类》中,我们却可看到朱熹又常以两翼两轮来为居敬穷理的关系定位,据此则可说在朱熹的工夫论系统中穷理仍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非居敬可以替代。表面看来,在居敬与穷理的关系问题上,朱熹主张应做统一的把握,然而这种观点如同朱熹所言“知行相须”并不能归为阳明学意义上的“知行合一”那样,理由在于朱熹所言知行相须,其前提是知行属于一种平行关系,而当阳明讲知行合一之时,则意谓在良知本体的统领之下,知行必然合一。倘若说朱熹思想属于“敬的形态”,则必须肯认朱熹所主张的“此心自做主宰”之“敬”不仅贯穿于格物工夫的过程中,而且还是格物工夫的前提和依据。然而事实上,朱熹晚年不仅坦承自己平日在“道问学”上著力尤多,而且他的《大学》诠释所透露出来的一个思想立场无疑是:唯有“格物”二字才是儒学工夫之核心。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朱熹之敬论与其心性理论密切相关,当朱熹说由敬而生心之精明,乃是就心的“自省自存”处言,故其所言“若知敬字只是自心自省,当体便是,则自无此病矣”,[128]按此所谓“病”,则是指“将此敬字别作一物,又以一心守之”之病,意指将居敬工夫的敬与心割裂开来所生之人病。朱熹以为由敬定心而使心自省自存庶能从根本上对治此病。这里的“自心自省,当体便是”以及上文提及的“以敬为主”、“而心自存”可以合而观之,这两句话十六个字可谓是朱熹敬论的核心观点,也是其敬论思想的意义所在。其意义就在于:由心之自省自存,使得在“主宰之谓”意义下的心具有了实践主体的地位,[129]而不只是被动地包总性情、涵摄众理,由此心出发,自能判断是非,实现“当体便是”的效果,如此则居敬工夫确能贯彻于格物穷理的工夫进程当中。
同时也须看到,朱熹所谓由敬而立的心的主宰义毕竟是就功能而言,而不是就本体而言,这是因为朱熹始终不能承认有一超越义的本体心,而其所谓“当体便是”亦不能想当然地等同于陆九渊心学在心即理的意义上所主张的“当下便是”[130],更与阳明后学所谓的良知“当下论”、“现成论”不可同日而语,关于其间的义理纠缠,这里已无法深究了。[131]只是有一点须指出,在朱熹看来,若能真正做到以敬为主而心自存,通过居敬工夫以使心体自做主宰,那么此心之发用便必定是合理的,这又叫做“心定理明”,也就是朱熹所言“自心自省,当体便是”的真实内涵。倘若如此,则朱熹所云“当体便是”乃是对工夫效应的一种状态描述而不是指向道德本心之当下呈现,因为这种“自心自省”的状态取决于工夫程度的不同而会发生变化,故“当体便是”并不能获得本体的必然保证。这是由于朱熹之论心所指向的是工夫论问题而不是本体论问题[132]。
总之,朱熹的敬论继承了程颐以来的主敬思想,接受了“主一无适”、“整齐严肃”、“常惺惺法”、“其心收敛,不容一物”以及“敬义夹持,循环无端”等有关主敬学说的内涵,同时又有更深入的理论发挥[133]。与程颐当时须要应对“心疾”问题相比,朱熹所要应对的理论问题及其敬论中所蕴含的理论问题也显然更为复杂。朱熹的主敬思想之形成与其应对道南学派的“体验未发”以及湖湘学派的“先察识后涵养”等理论问题有关,更是其通过“中和新悟”所建构的心性情之理论体系的一个结果。
朱熹的心性论有一个基本的思想立场:作为“主乎性而行乎情”的心,只具有工夫论的意义,其云“心是做工夫处”、“心字只一个字母”[134],便充分反映了朱熹之论心的基本立场。正是由此立场出发,故朱熹极力反对在心的操舍存亡的工夫论问题上设定“另有心之本体”的前提,亦即不能在居敬之前预设超越义的本心存在,依朱熹的说法,这就必然陷入“以一个心把捉一个心”的窠臼之中。朱熹的主敬工夫并不是道德本心的直接发动,而是对心的知觉意识之功能的控制调整,其云“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以敬为主而心自存”、“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都应当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当然,朱熹主敬亦有其心性论作为基础,故其主敬思想自有一套理路,而其核心关怀则在于如何解决现实人心的障蔽问题,因而不必同于阳明心学由良知本心直接悟入、当下呈现的这套理路。归结而言,朱熹的主敬思想乃是对儒学工夫论的一项重要理论贡献。
朱熹对《大学》“明明德”的诠释
朱汉民 周之翔
朱熹对《大学》所提出的命题“明明德”极为重视,他常教导学生为学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进而指出:“为学只在‘明明德’一句”。他对《大学》“明明德”的诠释,内涵丰富而思想深刻,是他研习并运用先秦儒家学说与宋代理学思想,分析和探讨人及其生活世界本质的全面总结。如我们所见,经过朱熹对“明明德”的诠释,这一原本只是普通政治道德的概念,获得了丰富的哲学内涵和宗教意义。
从一个先秦贵族教育的普通文本中,为什么朱熹可以读出这么多的新意义来呢?全面分析和总结朱熹“明明德”观的内涵,对于理解其经典诠释学的特点及价值,有着重要意义。
一、朱熹诠释“明明德”的新意义
朱熹对《大学》“明明德”内涵的思考与揭示,历经数十年。最初,他以孟子的“良知良能”、“良心”等阐释“明德”的内涵;晚年,他又以两宋理学家所掌握的孟子心性论进行分析与阐释,思考“明德”与“心”、“性”等概念的关系;去世前数年,他还运用宋代理学家的理气论思想揭示“明德”的来源,从而完成了对《大学》“明明德”的理学化诠释。
朱熹对《大学章句》“明明德”注释的最后修订在1196年左右。他于注中说:
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万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1]
这是朱熹晚年定论,也是其“明明德”思想的精粹表述。在这里,朱熹用短短67个字的篇幅,从工夫论、心性论、天理论的角度,阐明了“明德”的来源与本质,“明德”不明的原因及其根源,和“明德”可明的依据与道路。语言简洁,语义完备,逻辑严密,实际上是其毕生学问的总结。众所周知,这个定义,在朱熹理学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理学思想的继续演进也产生过深刻影响。
而事实上,无论是《大学》的文本本身,还是汉唐经学家的注疏里,《大学》中的“明明德”的意义都非常平易,只是对承担治理食邑、国家等责任的贵族的道德要求,并无理学思想的复杂而深刻的意义。如《大学》文本中的“明明德”,只是要求贵族博闻多识,注意自身的情绪管理,能够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从民众的角度制订并实施治理国家的政策;而郑玄注曰:“明明德,谓显明其至德也”,孔颖达疏曰:“在明明德者,言大学之道,在于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谓身有明德,而更章显之”[2],都不涉及心性修养的义涵。但是,朱熹正是通过对《大学》“明明德”命题的不断阐释,将先秦儒家与宋代理学思想成果进行整合,而从“明明德”中读出理学的工夫论、心性论、天理论等思想的意义。朱熹认为,“明明德”能够作为《大学》全书的纲领,就在于它将理学的天理本体论、心性论与儒家修身工夫论统一起来了。
其一,朱熹通过对“明明德”的哲学阐释,读出“明明德”的工夫论内涵。他认为“明”即“明之也”,又说“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这显然是从儒家工夫论角度进行的解读。所谓“因其所发”指“明德”的发露,即“明明德”工夫的起点和基础所在;所谓“遂明之”,指的工夫正是《大学》中提出的系统的儒家修身工夫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
其二,朱熹通过对“明德”的哲学阐释,读出了“明德”的心性论思想内涵。他在阐发《大学》的过程中,不仅对性的本源问题进行了说明,特别是通过阐释《大学》的“明德”为“虚灵不昧,以具万理而应万事者”,对心的内容及心与性、心与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而朱熹对《大学》“明德”内涵的探究,在如何确定和表述心性与“明德”之关系上,实际上一直未曾离开孟子的心性论。
其三,朱熹通过对“明德”的理论考察与哲学阐释,从“明德”中读出“自然之理”的宇宙本体论意义。他的“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的思想,立足在理学天理论基础之上。他以早期儒家、北宋理学的“性与天道”合一为理论基础,阐述人物的化生,以说明人的“明德”的来源,从而揭示了《大学》的宇宙论背景。他指出:“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为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脏百骸之身。”[3]他论证了人的“明德”的来源。
我们发现,朱熹对《大学》“明明德”的哲学诠释,与他的理学思想的“先见”有关。他显然是运用“六经注我”的方法,从《大学》中读出宇宙论、心性论、工夫论等理学思想。毫无疑问,朱熹对《大学》“明明德”的哲学诠释,具有“六经注我”的特点。但是,我们还应该知道,朱熹的“我”不是主观任意的“我”,而是对先儒先贤的全面理解和思考而形成的“先见”。深入考察他的治学历程与治学特点,可知他对《大学》“明明德”的哲学诠释与理学建构,其实是建立在“我注六经”的基础之上的。他晚年能够从儒家经典中读出这么多的新意义来,正是由于他早年和中年能够全面地阅读、深刻地理解孔孟以来先儒先贤的著作,并且各取所长,融会贯通。应该说,朱熹的经典诠释是经由“我注六经”的“六经注我”,两者是同一个经典诠释过程前后自然接续的不同阶段,并非对立关系。
二、明明德的工夫论诠释
《大学》相传为曾子所作,《大学》所以被列为学问之先,视为修身治人的规模,是因为它提出了为学工夫的八目,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将其称之为“教人之法”、“修身治人底规模”等等,至于其他儒家经典所列的工夫论,均可分别纳入到这个序列、体系之中。
朱熹早年已认为“良知良能”就是“明德”,在为学工夫方面,他认同通过察识此心之良知而明其“明德”。他认为圣人本身之“明德”无遮无掩,光明朗彻,是一个完全实现了的人。而人既与天地万物同理,又与圣人同性,皆具同等的潜在能力,所以人人也都是潜在的圣人。但普通人的“明德”为气禀、物欲所拘蔽和遮掩,失去其本有的光明,不仅不能照亮别人,也不能照亮自己,而未能自我实现。那么普通人实现为人的途径,也就是通往圣人的道路是什么?朱熹指出:“因其所发而遂明之”。这是因为,人必定具有“明德”,这“明德”无论怎样遮掩、拘蔽,也会有显露的时候,如孟子所说的四端与良知良能,只要将显露的“明德”加以扩充的工夫,即可实现本体之明。
朱熹后来认识到,良知良能只是“明德”之发现,是“明德”能明的依据与道路,但最终来说,明德之明,必须通过学者自己的“明明德”工夫,也就是《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功来实现。朱熹指出,本体之明的显露是“明”的工夫的依据与起点,而他所极为重视的《大学》修身治人底规模、为学工夫,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则是“明”的工夫的内容与程序。《朱子语类》载:
所谓明之者,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皆明之之事,五者不可缺一。若缺一,则明德有所不明。盖致知、格物,是要知得分明;诚意、正心、修身,是要行得分明。然既明其明德,又要功夫无间断,使无时而不明,方得。若知有一之不尽,物有一之未穷,意有顷刻之不诚,心有顷刻之不正,身有顷刻之不修,则明德又暗了。惟知无不尽,物无不格,意无不诚,心无不正,身无不修,即是尽明明德之工夫也。[4]
可见,朱熹是从理学的工夫论角度解读“明明德”的。朱熹重视《大学》之道,正是因为《大学》提出了系统的儒家修身工夫论,即格物、致知,阐明了儒家心性修养“知”的工夫;正心、诚意、修身,阐明了“行”的工夫。朱熹揭示了“明明德”工夫的基础与依据,又从《孟子》回归《大学》文本本身,阐明了“明明德”工夫的具体内容与程序,从而对《大学》“明明德”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朱熹从《大学》文本中的格物致知等工夫论角度解读“明明德之工夫”,显然比郑玄注“明”为“显明”,孔颖达疏为“章显之”要合乎文意得多。傅伟勋提出“创造的诠释学”,共分成五个层次,即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5]朱熹以《大学》文本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工夫论角度解读“明明德之工夫”,这是《大学》文本本来就有的内容,即所谓“实谓”的层次;但又属于没有明确的内容,即所谓“意谓”的层次。朱熹通过对《大学》文本的语义澄清、脉胳分析、前后文意贯通的考察等等,尽量“客观忠实地”了解并诠释《大学》的意思,探问了其“实谓”、“意谓”两个层次的意义,体现了他忠于经典文本、即“我注六经”的诠释态度。
三、以思孟学派的
心性论解读“明德”
《大学》文本本身对“明德”的内涵没有具体的论述,更没有作出深入的心性论探讨。朱熹要对《大学》的为学工夫做出深入探讨,揭示其通过个体的心性修养而成己成物的理论价值,就必须对“明德”的心性论内涵做出思考。
在儒家经典中,《孟子》以心性论的深刻思考而为朱熹所特别重视。所以,朱熹对“明德”的思考,一直是以《孟子》为理论依据的。朱熹早年已经认识到“明德”的内在性和普遍性,亦即认为人人皆有“明德”,最初也曾以孟子的“良知良能”、“良心”等阐释“明德”的内涵。他指出“明德”同“良心”一样,非由外铄,而是根于人心,被人的私欲所蔽而不明。他说:
明德,谓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
此条是廖德明所录,时间在1186年。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朱熹仍然重视孟子的“良知良能”之说及其与《大学》“明德”之间的思想关联,但主要是从“明德”与“良知良能”都是人所固有,为天所赋予的相同特性加以考虑。显然,“良知良能”只是一个基于观察获得的经验与体验,还不足以揭示《大学》中“明德”的意蕴,更不能与精密严谨、系统深刻的佛教的心性论抗衡。他还必须继续追问“良知良能”在人的心性结构中的位阶,才能明了“明德”的内涵。
“明德”的内涵既然与心性问题紧密关联,要阐释“明德”的内涵,就必须要辨明心性与“明德”的关系。在《经筵讲义》中,朱熹将“明德”解释为“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者也”,直接以“性”释“明德”。但这又与《大学》文本中的“明德”有差异,因为《大学》文本中的“明德”是个“浑全”的事物,不仅仅是指内在的“德性”,也指能彰显于行动的德行,因而,是经由人的思想认识的结果,而思想认识是由“心”来承担的,所谓“心之官则思”。朱子也指出“心者,气之精爽”,“心官至灵,藏往知来”。所以他知道,单独以“性”释“明德”并不妥当。《朱子语类》记载:
问:“‘天之付与人物者为命,人物之受于天者为性,主于身者为心,有得于天而光明正大者为明徳’否?”
曰:“心与性如何分别?明如何安顿?受与得又何以异?人与物与身又何间别?明德合是心?合是性?曰性却实,以感应虚明言之,则心之意亦多。”曰:“此两个说着一个则一个随到,元不可相离,亦自难与分别。舍心则无以见性,舍性又无以见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随说,仁义礼智是性,又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逊、是非之心,更细思量。”[6]
这是门人余大雅直接以朱熹的原话求证于朱熹,表明余大雅对朱熹将“明德”与心性相联系而产生了许多疑问。在这里,朱熹一口气提出了六个问题,表明了他在揭示“明德”内涵时的问题意识所在。他指出,“明德”是“感应虚明”的,因而“心之意亦多”;同时他也注意到,孟子总是将心与性联系起来论说的特点。
实际上,朱熹1189年所修订的《大学章句》中,对“明德”的注释,是不判分心德,即从心性一体的角度进行解释的:
问:“《大学注》言:‘其体虚灵而不昧,其用鉴照而不遗。’此二句是说心?说德?”
曰:“心、德皆在其中,更仔细看。”
又问:“德是心中之理否?”
曰:“便是心中许多道理,光明鉴照,毫发不差。”[7]
本条是徐寓于1190年至1191年之间,在漳州问学朱熹时所记,其中《大学注》指朱熹1189年修订的《大学章句》,1191年刊刻于漳州学宫。显然,《大学注》中,“其体”之“其”是指“明德”,“虚灵不昧”是对“明德”的本质特征的描述,也是对“明德”之“明”字内涵的揭示;“鉴照不遗”是言“明德”之用。在这条注释中,朱熹显然是以心释“明德”。“虚灵不昧”、“鉴照不遗”实际上就是心之体与用。但以“虚灵不昧”言“明德”之“体”,等于直接说心就是“明德”之“体”,但是他又指出“明德”是人心中“许多道理”。人之心合理气、统性情,故而德性必蕴涵于心,德行亦必为心之发。由心言明德,才能整全而无所偏废,但又必须兼性而言,否则,“明德”亦没有本原。在最终定论,即通行本《大学章句中》,朱熹回到孟子兼心言性、兼性言心的立场,指出人之明德是“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万理而应万事者也”,以“人之所得乎天”、“具万理”阐释“性”之明,以“虚灵不昧”、“应万事”阐明“心”之明,合心与性,而阐释“明德”之内涵。可见,朱熹注释“明德”,是兼心性为一体而言的。
又,人禽之辨是孟子提出的重要课题,但孟子的目的在于强调“仁义”的价值与基于仁义的内在人性。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8]史次耘先生指出,《孟子》此章的主旨是“强调人性本善,君子全顺自然之性而由仁义行。”[9]到了宋儒这里,则发展为探究人的本质,即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依据是什么的问题。朱熹总结周敦颐、张载、二程及其后学的思想,深入探讨了人禽之差异的根源。他注释孟子的人禽之辨说:
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其不同者,独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为少异尔。虽曰少异,然人物之所以分,实在于此。[10]
朱熹认为,从人物的化生来看,人与物之理是相同的,这是万物一体、人能与天合一的依据。人物之界分主要在禀受的气不同,人得气之正且通者,而物得气之偏且塞者。所以人能全其性,明天理,自觉按照天理行事,而物则不能。放到《大学》中来看,人禽之异或者说人物之界分就是人具有明德,而物没有。在《大学或问》中,朱熹指出:
惟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者,而其性为最贵,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盖其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是则所谓明德者也。11]
实际上,朱熹说“明德”是“人之所得乎天者”,已经强调“明德”是人所有,含有界分人物之内涵,而“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从而使人能识其本性进而全齐本性,则是人的本质——人的规定性所在。可见,在这里,朱熹又以孟子兼说心性的方式阐明了明德作为人物界分的意义,从而深化了孟子的人禽之辨,使孟子的人禽之辨由强调人性本善的论据上升为探讨人的内在规定性的哲学命题。
我们发现,朱熹既以《孟子》诠释《大学》,又以《大学》诠释《孟子》,这取决于那部经典的长处和特点。在工夫论方面,他更认同《大学》中“格物”、“致知”的知识理性对人格形成的作用,所以他用《大学》中的“格物”、“致知”的理念来诠释《孟子》中的“养气”、“尽性”。他说:“知言正是格物致知。苟不知言,则不能辨天下许多淫、邪、诐、遁。将以为仁,不知其非仁;将以为义,不知其非义,则将何以集义而生此浩然之气?”[12]但是在心性论方面他更认同《孟子》,故而他在心性论方面以《孟子》诠释《大学》。这样,既保证了他对先秦儒家经典的尊重态度,又满足了不同儒学典籍的整合要求。从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来说,这是“蕴谓”层次,即朱熹在思考《大学》可能蕴涵的是什么。在这一层面朱熹已跳出文本本身,而采取“以经解经”的诠释方法,他以《孟子》的心性思想回答《大学》蕴涵的心性论是什么。
四、以天理论解读“明德”的来源
朱熹在《大学章句》注释中,首先指出“明德”是“人之所得乎天”者。这是朱熹一贯的看法。如1194年《经筵讲义》中,朱熹指出“明德”是“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者也”,[13]到《大学章句》通行本中,朱熹改掉了“至明而不昧”,而“人所得乎天”只字未改。显然,这句话中的关键概念是“天”,其理论背景是自人文初始后,数千年来古圣先贤一直不断探求的天人关系的思想。
在《四书》中,《大学》并没有讲“明德”的来源,而《中庸》、《孟子》(以及《易传》)的重要贡献就是正式确立了“性与天道”的联系,从而为孔子的心理情感的仁心与人性确立了形而上之道的终极实体。当然,这种“性与天道”的联结主要是精神信仰的。《中庸》与《孟子》在论述“性与天道”的关系时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4]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15]
在子思、孟子那里,“天命”、“天道”是作为仁心、人性的形而上依据。那个作为道德人文根源的“人性”,原来体现着作为终极实体的天道的神圣性。“天道”是一个表达终极本体的概念,但它与心、性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天人一体的思想体系。在早期儒家学派的《易传》中,还有这个天人一体的宇宙论演变发展的更为系统、详尽的论述。朱熹在《大学章句》注释中,指出“明德”是“人之所得乎天”者,其实就是继承了《中庸》、《孟子》(以及《易传》)的“性与天道”的思想。
《中庸》、《孟子》虽然回答了“性与天道”问题,但是语焉不详。而真正建立系统的天地之理的形上学说的是“北宋五子”,他们通过对《周易》、《中庸》、《孟子》的重新诠释,建构了一个以“太极”、“太虚”、“天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为了更进一步从学理上论证人文准则与终极实在的联结,北宋五子特别建立了一个“性与天道”合一的宇宙论体系。他们以《四书》中有限的资料对“性与天道”的重大问题作出创造性的诠释。而朱熹对“明德”来源的诠释,主要是继承了北宋五子的思想学说。
在朱熹这里,人之“明德”所得乎“天”的这个“天”,正是周子所讲的以阴阳五行造化人与万物的“天”,和二程的主宰天地万物的“天理”。朱熹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指出天地万物的存在是以天理为依据的,而人就存在于这个天理的世界中,其本身也是天理的呈现。在《大学或问》中,朱熹对“明德”来源作了系统的的论证,他指出:
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其所以为造化者,阴阳五行而已。而所谓阴阳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后有是气。及其生物,则又必因是气之聚而后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为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脏百骸之身。周子所谓“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谓是也。[16]
朱熹此处所指之“天”,是经过北宋五子,特别是北宋五子之首周濂溪的创发。其中所引宇宙论演变过程,出自周子《太极图说》。周子通过“无极而太极”为依据建立的宇宙图式中,天道流行,万物化生,人在其中而最为灵秀,为儒家士人建构了一个以现实人生为依据的存在家园,人们的生、老、病、死、功名利禄、生命价值,一一得到安顿。魏晋以来数百年间,儒家士人逃老逃释,精神与生命无法安顿的局面,实际上得以解决。在这里,周子和朱熹实际上将为儒家所继承的华夏文明中人文主义17]的性格和思想,推进到了极致,真正确立了儒家文化的价值内核与独特品格。朱熹逃入释老十余年,故深知周子《太极图说》之价值。他萃取周子《太极图说》的思想,阐述人物的化生,正是为了说明人的“明德”的来源,从而揭示了《大学》的宇宙论背景,将孔子、子思、孟子的心性论思想,建构在了周子的这个宇宙论上。在朱熹这里,人之“明德”所得乎“天”的这个“天”,正是周子所讲的以阴阳五行造化人与万物,无人格而又以生物为心、至仁至实的“天”。
《大学》本来并没有讲“明德”的来源,而朱熹以《中庸》、《孟子》(以及《易传》)的“性与天道”思想诠释“明德”的来源,属于“当谓”层次,即朱熹以《中庸》、《孟子》(以及《易传》)的“性与天道”思想考察出《大学》本来应当说些什么。到这一层面,朱熹发掘出《大学》更为深刻的内涵,从中显现最有诠释理据或强度的深层意蕴和根本义理出来。而朱熹以北宋理学的“性与天道”合一为理论基础,阐述人物的化生,以说明人的“明德”的来源,从而揭示了《大学》的宇宙论背景,这是“创造的诠释学”的“必谓”层次。也就是说,朱熹通过北宋理学家和自己对“明德”来源的理解,表达了《大学》到了宋代必然说出什么。
五、朱熹诠释“明明德”
的思想贡献与学术价值
经典诠释往往可以理解成“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种不同的方式。前者注重学术传承,后者注重思想创新。故而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往往会对“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做出不同的评价。本文以朱熹对《大学》所提出的命题“明明德”诠释为例,特别要加以说明,其实这两种诠释方法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对于朱熹来说,他对《大学》“明明德”诠释的学术成就、思想贡献正得益于这两种方法的同时使用。朱熹在谈到自己的读书方法时说:
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18]
那么,朱熹是如何从儒家经典中读出“圣贤之意”、“自然之理”的呢?
我们认为,这段话既可以理解成“我注六经”,也可以理解成“六经注我”。一方面,可以理解他是运用“六经注我”的方法从儒家经典中读出“圣贤之意”、“自然之理”,故而从《大学》“明明德”中读出了宇宙论、心性论、工夫论等理学思想,开拓、丰富了《大学》“明明德”的思想内涵。无论是《大学》的文本,还是汉唐经学家的注疏,“明明德”的意义都非常平易,并无宇宙论、心性论等理学思想的复杂而深刻的意义。由于朱熹在经典诠释过程中运用“六经注我”的方法,并且依照那个时代的要求,对儒家传统作了系统化的思想阐释。朱熹通过诠释《大学》而论述的理学思想,实现了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创新。因此,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学术思想体系很快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古代中国主流的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这一切,均证明朱熹的《大学》诠释充分体现唐宋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变革发展的时代要求。
但另一方面,朱熹作为一个儒家学者,他忠实地继承了儒家的精神传统和学术传统,他运用“我注六经”的方法,通过潜心从事学术研究,从儒家经典中领悟“圣贤之意”。具体而言,他通过对经典文字的音读训诂以及语义澄清、脉络分析、前后文意贯通等等研究工作,以实现对圣人之意的领悟。朱熹对《大学》工夫论的解读,对儒家经典中心性论及其天道论的论述,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朱熹所做的这一系列的经典诠释工作,均是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19]为其学术宗旨的。通过学术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其实这些也均是早期儒家经典中早已存在的思想学说。在郭店楚简中有不少与之非常接近的思想,这就说明朱熹的经典诠释确有其历史文献学依据。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家们应该是比汉唐诸儒更准确地抓住了先秦儒学及其经典文本的学术宗旨和历史本义,从一定意义上说确是承传了先秦儒家“千载不传之学”。
可见,朱熹从《大学》“明明德”中读出的“圣贤之意”、“自然之理”,与他运用“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种诠释相关。进一步说,他正是通过“我注六经”来实现“六经注我”,从而使先秦儒家思想与宋代理学思想融贯于他对“明明德”命题的注释中。对于朱熹对《大学》“明明德”的诠释,我们既要充分肯定其思想创新的意义,又要充分肯定其学术传承的价值。
朱熹的子学思想及其特征和地位
蔡方鹿 解茗
朱熹思想的重要价值使多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对朱熹思想进行了深入持久的研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然而,尽管对朱熹思想的研究已相当深刻系统,但从子学的角度来对其思想进行研究的却很少。多年来,国内外对这方面研究的著作竟然没有,论文也是寥寥无几。事实上,朱熹以自己的理学思想为标准来评判、论定子学人物及其观点时,体现了他的子学思想,尽管比较零散,但也有内在理路可循。从朱熹对这些子学人物和著作的批评或一定程度地认可的评价中,可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朱熹思想的认识,亦可从中掌握朱熹子学思想的特点及其在朱熹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并从一个侧面把握子学在宋代的流传及对朱熹思想的影响,这与朱熹所处的时代背景及自身思想发展的基本倾向和脉络相联系。
一、朱熹子学思想论要
所谓子学,指先秦至汉初诸子百家学术之总称,亦指研究诸子思想的学问,内容包括对诸子及其著作的研究,历代学者研究诸子的学问。从诸子学时期至宋代,社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朝代的更迭,子学思想作为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步流传演变并得到人们的检验取舍。朱熹以一位宋代理学代表人物的立场和眼光对诸子百家思想加以检视和评判,而得出了自己的子学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一)朱熹对道家的评判
朱熹对道家的思想比较熟悉,他曾批评历代那些注解《老子》和《庄子》的人,认为他们的注解多是为就己意而对老、庄经典进行“臆说”,歪曲了老、庄的本义。他说:“《庄》、《老》二书,解注者甚多,竟无一人说得他本义出,只据他臆说。某若拈出,便别,只是不欲得。”[1]由此可见,朱熹不但对老、庄之学比较熟悉,且自认是明白老、庄本义的。朱熹身为儒家,却并没有拘泥于门户之见对道家之学进行简单的否定,而是站在一种较为客观的立场对道家思想进行中肯的分析。
对于道家创始人老子的思想,朱熹有这样的评价:“老子之术,自有退后一著。事也不搀前去做,说也不曾说将出,但任你做得狼狈了,自家徐出以应之。如人当纷争之际,自去僻静处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长短,一一都冷看破了,从旁下一著,定是的当。……因举老子语:‘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若客,涣若冰将释。’”[幻可见朱熹认为老子的柔弱不争不仅是其主要思想,同时也是其处事的谋略和手段,是一种“术”,这种退让不完全是消极避世,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手段,认为老子“取天下便是用此道”[3]。老子思想在汉初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让经历多年战乱、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的西汉社会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朱熹对此评价道:“其言易入,其教易行。当汉之初,时君世主皆信其说,而民亦化之。虽以萧何、曹参、汲黯、太史谈辈亦皆主之,以为真足以先于六经,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4]肯定了老子思想在政治教化、治国治民方面有可取之处。“其学也要出来治天下,清虚无为,所谓‘因者君之纲’,事事只是因而为之。如汉文帝、曹参,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肤,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将去。老氏之学最忍,它闲时似个虚无卑弱底人,莫教紧要处发出来,更教你枝梧不住,如张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学。”[5]认为老子之学看似清虚无为、卑弱不争,实则无为而治,柔弱胜刚强。朱熹更曾多次直接表达他对老子的欣赏之意:“今观老子书,自有许多说话,人如何不爱!”[6]“老子说他一个道理甚缜密。”[7]朱熹更明确指出二程理学受到了老子的影响,“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取老氏之说也。”[8]既然二程学说从老子思想中有所取,作为二程后学的朱熹实际上等于间接承认了他也受到了老学的影响。朱熹虽对老子之学多有肯定和赞赏,但二人毕竟分属不同的学派,思想上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因此朱熹不可避免地也对老子的一些思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儒家最重伦理,而老子却认为道与仁义不并存,因此对孝慈礼仪废弃不讲,朱熹由此批评老子“害伦理”:“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声,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伦理。”[9]朱熹对道家一派于乱世中为保全自身而厌世避祸、崇尚空寂的思想提出批评:“儒教自开辟以来,二帝三王述天理,顺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礼之道,后世圣贤遂著书立言,以示后世。及世之衰乱,方外之士厌一世之纷拏,畏一身之祸害,耽空寂以求全身于乱世而已。及老子倡其端,而列御寇、庄周、杨朱之徒和之。孟子尝辟之以为无父无君,比之禽兽。”[10]同时朱熹也对老子的价值观加以针砭:“老子之术,须自家占得十分稳便,方肯做;才有一毫于己不便,便不肯做。”[11]从朱熹对老子的这些批评,可见儒、道两家思想存在的差异。
对于道家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庄子,朱熹也同样是肯定与批判兼而有之。朱熹认为庄子才高识远,“其才高,如《庄子·天下》篇言‘《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若见不分晓,焉敢如此道!”[12]并指出庄子与佛教有区别,佛与儒对立,而庄子的思想可以和儒家互相沟通。“或问:‘《中庸》说道之费隐,如是其大且妙,后面却只归在‘造端乎夫妇’上,此中庸之道所以异于佛老之谓道也。’曰:‘须更看所谓‘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处,圣人之道,弥满充塞,无少空阙处。若于此有一毫之差,便于道体有亏欠也。若佛则只说道无不在,无适而非道;政使于礼仪有差错处,亦不妨,故它于此都理会不得。庄子却理会得,又不肯去做。如《天下》篇首一段皆是说孔子,恰似快刀利剑斫将去,更无些子窒碍,又且句句有著落。如所谓‘《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可煞说得好。’”[13]正因为此,朱熹对庄子思想的评价较高:“盖自孟子之后,荀卿诸公皆不能及。”[14]“庄子比康节亦仿佛相似。然庄子见较高,气较豪。”[15]将儒家先贤和北宋著名理学家邵雍置于庄子之后,可见其对庄子评价之高。朱熹还把庄子与老子进行对比,认为《庄子》的文风豪放跌荡,说理方式独具风格,“将许多道理掀翻说,不拘绳墨”[16],肯定庄子说理“较开阔,较高远”[17]。虽说朱熹对庄子思想多有肯定,但站在理学家的立场,朱熹也对其作了批评。例如说庄子在入世方面比老子更加消极,“老子犹要做事在,庄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说道他会做,只是不肯做。”[18]对于庄子宣扬的一些神异思想,朱熹也进行了斥责:“若曰‘旁月日,扶宇宙,挥斥八极,神气不变’者,是乃庄生之荒唐。”[19]对庄子等人于乱世中追求全身养生的道家思想朱熹亦加以批评,甚至指斥庄子专计利害,更将晋室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清谈老庄:“庄子之意则不论义理专计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盖迹其本心,实无以异乎世俗乡原之所见,而其揣摩精巧,校计深切,则又非世俗乡原之所及。是乃贼徳之尤者。所以清谈盛而晋俗衰,盖其势有所必至。而王通犹以为非老庄之罪,则吾不能识其何说也。”[20]认为正是由于清谈老庄,才引得纲纪大坏,法度无存,而导致天下大乱。朱熹这种评价显然是对受老庄思想影响的魏晋玄学的批评。
朱熹口中的道家有时并不全指先秦的老庄之学,他把道教也称为道家。然而虽然称呼相同,但先秦道家与道教的区别,朱熹心里是明白的。朱熹指出,从老子道家到道教,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老氏初只是清净无为。清净无为,却带得长生不死。后来却只说得长生不死一项。如今恰成个巫祝,专只理会厌禳祈祷。这自经两节变了。”[21]认为道教已然偏离了老子的原意,由世俗文化派别转变为讲巫祝祈祷的宗教。他认为道教后来衰落与虚妄,佛教思想却日益精妙高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道、佛二教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互相错位的现象。佛教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吸取融会了老庄之学的优长,而道教徒们在发展自己的教义时,却不重视道家固有之书,反而吸取了释氏的糟粕:“道家有《老》、《庄》书,却不知看,尽为释氏窃而用之,却去仿效释氏经教之属。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宝悉为人所盗去,却去收拾人家破甕破釜。”[22]讥讽道教拾取了释氏的破甕破釜,却被释氏盗走了自己的珍宝。因此,朱熹一方面不遗余力的批评道教,另一方面又对正宗的老庄道家之学加以一定程度的肯定和称赞,将其与道教区分开来。朱熹更明确地告诉其弟子,老庄“言有可取”[23],其书是值得读的,不可随意否定。而读老庄的关键是要弄清老庄思想与儒家圣人学说的区别之处,以便能够扬长避短,为我所用。朱熹正是在深入研究了道家思想后,吸取道家哲学的道本论等思想,以天理论道,把道与天理结合起来。由于朱熹不拘于门户之见,博采众家之长,最终建立起一个中国哲学史上最为完备、缜密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一代理学大师。
(二)朱熹对法家的评判
法家学说的核心是“法治”,提倡以严刑峻法治民,这与先秦儒家所倡导的“礼治”、“德政”堪称相对,因此儒家历来批判法家都是不遗余力的。但到了南宋时期,法家学说经过上千年时光的检验,证明其学说并非一无是处,事实上,法家的很多理论在维护社会稳定、富国强兵方面确实起到积极的作用。所以,朱熹在评判法家时,一方面固然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以批评为主,另一方面,又给予法家之学以适当的肯定并有所吸收。
朱熹对法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只见刑名,学问浅陋。他说:“盖老氏之学浅于佛,而其失亦浅。正如申韩之学浅于杨墨,而其害亦浅。”[24]朱熹在《孟子精义》中又说:“如申韩只见刑名,便谓可以治国,此目不见大道,如坐井观天井蛙,不可以语东海之乐。”[25]并引程颢的话加以批评:“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杨氏为我疑于仁,墨氏兼爱疑于义,申韩则浅陋易见。”[26]法家之学偏向功利性和实用性,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较偏向政治学说,在哲学思辨方面则显不足,朱熹就是针对这一点,批评申韩之学关于治道的途径过于简单化,认为只见刑名是不足以治天下的;第二,刻板严峻,惨刻无恩。朱熹认同对法家人物“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东坡谓商鞅、韩非得老子,所以轻天下者,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27]的评论,更将其斥为“误人主之术”。他说:“韩非、李斯惨刻无恩,诖误人主之术,非仁人之所忍言也。”[28]朱熹认为法家实施严刑峻法、重赋税,是残忍、无恩的表现,是误主的行为,非仁人所为;第三,擅用阴谋机心。他说:“而其实必用机心,扶阴谋然后可,……彼管仲、商君、吴起、申不害非无一切之功,而所以卒得罪于圣人之门者,正在于此。”[29]朱熹认为申不害等用“机心”、“阴谋”之道治理国家,虽然也有一定的功效,但是却违背了圣人治国之道,所以要求人们加以熟察;第四,急功近利,不讲仁义。“‘如李悝尽地力之类,不过欲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谓任土地者亦次于刑?’曰:‘只为他是欲富国,不是欲为民。但强占土地开垦将去,欲为己物耳,皆为君聚敛之徒也……如李悝尽地力,商鞅开阡陌,他欲致富强而已,无教化仁爱之本,所以为可罪也。’”[30]儒家最重仁义道德,而法家则倾向功利,两家在价值观上有着根本的区别。朱熹认为,法家虽然有时也做一些看似有益于人民的事,但他们的出发点却并不是真的爱民、为民着想,而只是为了富国,替君主敛财而已。因此朱熹站在以儒家仁义教化为治国之本的立场,批评法家追求富国强兵而不重视教化。他说:“彼非以仁义为不美也,但急于近功,谓仁义为迂阔,不切时务,不若进富国强兵之术也。若其诚然,商鞅之徒为之,孟子不为也。”[31]一句“商鞅之徒为之,孟子不为也”,充分表现出儒、法两家思想的差异。
朱熹对法家思想虽有诸多批评,但同时也有所肯定和吸取。他在批评商鞅重利轻义的同时,也承认商鞅开阡陌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他说:“商鞅开之,乃是当时井田既不存,便以此物为无用,一切破荡了。”[323朱熹也肯定法家对于诚信的重视。“无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虽商鞅之徒亦不可为政。”[33]同时朱熹也认可法家所说的治国要“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34],肯定法家“辟以止辟”的法价值观念。他说:“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过于惨刻。今之士大夫耻为法官,更相循袭,以宽大为事,于法之当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虽舜亦不免。教之不从,刑以督之,惩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劝戒,所谓‘辟以止辟’,虽曰杀之,而仁爱之实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则人无所惩惧,陷于法者愈众,虽曰仁之,适以害之。”[35]朱熹认为士大夫们以“宽大为事”的立法、执法准则虽是出于一片善意,是由于对他人怀有的一份慈悲、怜悯之心而起,但若犯法者不能受到相应的惩罚,就会使他们因为无所畏惧而更加的肆无忌惮,从而令更多的无辜者受难,这片善心的结果就会导致反而害了更多人。从这个层面来讲,法家所提倡的对犯罪者所实施的严刑峻法,实际上也是对更多无辜百姓的一种保护,也算是另一种仁爱。因此他建议天子不讳于“深于用法,而果于杀人”[36],“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刑”[37]。朱熹还融合了法家法无等级的观念,确立了公天下的法律价值观。认为法的公正性,是韩非法治思想的精华所在。朱熹对此是赞同的:“盖谓法者,天下之大公,……舜不敢禁者,不以私恩废天下之公法也。……盖以法者先王之制,与天下公共。为之士者受法于先王,非可为一人而私之。”[38]朱熹对法家思想既批判又吸取,形成了一套人治与法治相结合,以正君心、严吏治、举贤才、公平慎刑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体系,力图为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服务。
(三)朱熹对杂家的评判
朱熹对于杂家,总体来说评价不高。诸葛诚之对《吕氏春秋》十分推崇,曾盛赞其煞有道理,甚有好处。朱熹对此有这样的评价:“尝见他(诸葛诚之)执得一部吕不韦《吕览》到,道里面煞有道理,不知他见得是如何。”[39]“诚之常袖吕不韦《春秋》,云其中甚有好处。及举起,皆小小术数耳。”[40]前一句“不知他见得是如何”表达出朱熹对于诸葛诚之对杂家学说的推崇态度不以为然;而后一句更是直接批评杂家之学不过是不值一提的术数之学。由此可见朱熹对于杂家学说抱有贬低轻视之意。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认为杂家之学过于驳杂。朱熹为学虽讲求博学,但他强调,“博学,亦非谓欲求异闻杂学方谓之博”[41],而应是指“博学,谓天地万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当学。然亦各有次序,当以其大而急者为先,不可杂而无统也。”[42]可见朱熹所指的“博”应是掌握“天地万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的广博道理,而且在学习时还要有一定的次序,不能杂而无序。博学的目的是为了穷理,所以在博的基础上,还必须返约。博而不能返于约,就无法穷理,只会流于杂。“学之博者似杂,其约者似陋。惟先博而后约,然后能不流于杂,而不掩于陋也。”[43]在朱熹看来,杂家既没有在博的环节掌握好轻重缓急、先后次序,又缺失了约的环节,以致流于驳杂,难登大雅之堂。
其二,认为杂家少讲仁义,而多说权谋功利。杂家学说虽是博采众家之长,但并非没有侧重。在《吕氏春秋》的思想体系里,明显是以道家的哲学思想为尊。在提及各学派时,《吕氏春秋》一般都按照老、孔、墨……的顺序排列,将老子置于最前;在涉及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等方面,《吕氏春秋》较多吸取了儒、墨两家以及管仲的内容;在哲学思想领域,则对老子大加推崇,同时也充分肯定了法家思想中的合理部分。而且《吕氏春秋》作为一部以为现实政治提供理论依据为编写目的的著作,其整体风格难免倾向于实用性及功利性,与儒家圣人之道的价值观有所抵触。对于这一点,朱熹并未直接批评吕不韦或《吕氏春秋》,而是通过对贾谊、司马迁以及苏辙等人的批评表达了他的态度。“贾谊、司马迁皆驳杂,大意是说权谋功利。说得深了,觉见不是,又说一两句仁义,然权谋已多了,救不转。苏子由《古史》前数卷好,后亦合杂权谋了。”[44]朱熹虽对杂家多有批评,但并未认为杂家一无是处。在《别本韩文考异》的《读仪礼》中载有这样一句话:“百氏杂家尚有可取,况圣人之制度耶。”从“百氏杂家尚有可取”一句可以看出,朱熹并不完全否定杂家,而是承认其亦有可取之处。
(四)朱熹对墨家的评判
朱熹对墨家、阴阳家、纵横家这三家的评论都不是很多,但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对于墨家,朱熹通常将墨子与杨朱相联系,一起进行评论。朱熹远承孟子,以杨墨为异端邪说。他说:“墨子爱无差等,而视其至亲无异众人,故无父。无父无君,则人道灭绝,是亦禽兽而已。”[45]又说:“墨氏‘爱无差等’,故视其父如路人。……如杨墨逆理,无父无君,邪说诬民,仁义充塞,便至于‘率兽食人,人相食’。”[46]同时,朱熹十分注意纠正韩愈“孔墨必相为用”的说法,毫不客气地批评:“昌黎之言有甚凭据?”[47]以清理儒学传承中前儒对杨墨学说的异论。而在杨墨学说的比较方面,朱熹也与孟子一样,对墨子的评价要更低一些。孟子在《尽心下》中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而朱熹则认为,虽然杨墨皆是邪说,但是墨子之说相对杨朱而言更加的矫伪不近人情而难行。关于杨墨之学的源头,朱熹前后态度的变化值得注意。二程认为杨、墨其实都是出自于儒门,在《二程遗书》中载有这样几句话:“杨、墨,皆学仁义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张,杨子似子夏。”[48]“大凡儒者学道,差之毫厘,缪以千里。杨朱本是学义,墨子本是学仁,但所学者稍偏,故其流遂至于无父无君。”[49]早期朱熹在《孟子精义》一书中,继承了二程这一观点,同样不怀疑杨墨学出儒门。但后来他否认了这一观点,认为“杨墨之说恐未然。杨氏之学出于老聃之书,墨子则晏子时已有其说也,非二子之流也”[50]。朱熹的态度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从认可其学出于儒门到将其逐出门视为异端,除了有学术思想不认同方面的原因,其实也有着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在孟子生活的时代,杨墨之学是当时的显学,当时孟子之所以会如此激烈的“辟杨墨”,也是为了显圣人之道。而朱熹当时所处的环境与孟子相仿,只是对象从杨墨之学换成了佛老之学。在朱熹看来,佛、道二教的危害类似于孟子时杨墨的危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佛老学说对儒家学说正统地位的威胁,令朱熹意识到必须要像孟子当年“辟杨墨”一样辟佛老;而将杨墨从儒门逐出,则是为了维护儒门的纯粹性,赋予自己对当时佛、道二教的批判以更权威的理由和说服力。
(五)朱熹对阴阳家的批评
朱熹对阴阳家的评价较低,在朱熹的著作中他对阴阳家轻视的态度非常明显。朱熹对阴阳家的批评不仅是因学术观点或价值观的冲突,而且是对其学术价值的一种彻底否决。在《朱子语类》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问‘索隐集注云:深求隐僻之理,如汉儒灾异之类,是否?’曰:‘汉儒灾异犹自有说得是处,如战国邹衍推五德之事,后汉谶纬之书便是隐僻。’”[51]从这段对话可见朱熹对邹衍“五德终始”之说和后汉谶纬之学的蔑视,认为其根本没有说得是处。而在另一段对话里,朱熹的这种态度则表现得尤为明显。他说:“游氏引邹衍谈天、公孙龙诡辨为智者之过,亦未当。若佛老者,知之过也。谈天诡辨,不足以为知者之过。知者之过非一端,如权谋术数之类亦是。龙、衍乃是诳妄,又不足以及此。”[52]朱熹认为,如果说佛老是“知者之过”,那么像公孙龙、邹衍之类谈天诡辨的人甚至还不足以称之为知者之过,将邹衍视为诳妄之辈,可见对其评价之低。朱熹对阴阳家的这种态度不排除也有些现实原因,因为他当时极力要抗争的佛、道之学中的道教,其学说中就吸取了不少阴阳家的学说内容,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朱熹对这种带有神秘色彩学说发自内心的排斥。
(六)朱熹对纵横家的评判
朱熹对纵横家的评价也是以贬为主。首先,朱熹对纵横家学说评价不高:“问《孟子》‘好辩’一节。曰:‘当时如纵横刑名之徒,孟子却不管他,盖他只坏得个粗底,若杨墨则害了人心,须着与之辩。’”[53]从这句对话可见,朱熹将纵横之学与刑名之学置于杨墨之学下面,认为其道理粗浅,所害亦浅。而从他对贾谊的评价中也可见他对纵横之学的不满:“贾谊之学杂,他本是战国纵横之学,只是较近道理,不至如仪、秦、蔡、范之甚尔。他于这边道理见得分数稍多,所以说得较好。然终是有纵横之习。缘他根脚只是从战国中来故也”。[54]可见朱熹认为贾谊也属纵横家之列,是纵横家里面较为懂得道理的人。而多数纵横家在朱熹心中即是不近道理之人。另外,纵横家偏向政客,不讲忠义,亦不讲原则,对于他们来说,只要可以达到目的,获得荣华富贵,基本上所采取什么手段、要对自己进行怎样的改变都不是问题,这一行为准则一直为儒家学者所不齿,孟子就称其为“妾妇之道”,而朱熹也通过讽刺的方式来表达了他的态度:“古之圣贤以枉尺直寻为大病,今日议论乃以枉尺直寻为根本。若果如此,即孟子果然迂阔,而公孙衍、张仪真可谓大丈夫矣。”[55]说明公孙衍、张仪之类纵横家在朱熹心中并不能算是大丈夫。朱熹更认为纵横学对当时社会起到了不好作用:“周衰之末,战国纵横,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当时处士务先权谋,以为上贤。先王大道陵迟隳废,异端并起……天下岂复有王道哉,岂复知有仁义哉!”[56]但朱熹对纵横家也并非全无肯定之处,“古人有取于登高能赋,这也须是敏,须是会说得通畅。如古者或以言扬,说得也是一件事,后世只就纸上做。如就纸上做,则班扬便不如已前文字。当时如苏秦张仪,都是会说。《史记》所载,想皆是当时说出。”[57]肯定了纵横家善辩之才。
二、朱熹子学思想的特征、
地位和影响
(一)朱熹子学思想的主要特征
从上述朱熹对各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价来看,虽然朱熹的子学思想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评价的语句较为零散,但也并非没有内在理路可循,朱熹的子学思想主要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既有批评,也有肯定,但总体来说,以贬斥为主。朱熹对诸子学说的态度既不同于荀子对其他学派的大加批判,也不同于以吕不韦为首的杂家对各家思想的只赞不贬,而是力求客观,多半从肯定与否定两个方面着手,很少有一面倒的情况出现。对于一些不但在当时是显学,到了朱熹的时代依然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说,如道家、法家等,朱熹的态度就比较认真,他不但深入研究了它们,而且也从他的立场、思想出发,尽量客观地评价,对其有害之处更是精心分析,以免后人误入歧途。仔细看他的语句就会发现,尽管朱熹已极力保持中立,但毕竟立场有别,学术思想有所抵触,朱熹对这些诸子之学的贬低要多于他所给予的肯定。而朱熹所站的立场,就是他子学思想的第二个特征。
第二,站在儒家的立场,以儒学的价值观作为其对诸子学评判的标准。朱熹对各家思想有肯定、有吸取,但批评的语句更多,而他所批判的方面,都是其与儒学思想相抵触的方面。儒家思想要求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施行仁政,重义轻利,也强调纲常礼法,上下有别。以这些儒学基本原则为出发点,朱熹批评道家的消极避世、乱世中只求保全自身;指责法家刻薄寡恩、知刑而不知德;认为阴阳家诳妄谈天,不值一提;批评墨家“兼爱”是学“义”之偏,有违伦理纲常;指出法家、杂家和纵横家都有功利主义倾向,重利轻义。可见无论朱熹如何客观,他心中这条儒学基本原则的底线是不能冲破的,也正是这条底线,使得朱熹的子学思想呈现出与杂家截然不同的特征。
第三,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这也是朱熹子学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质。朱熹论诸子学说,有些不一定完全从其学术角度考虑,现实社会环境也会对朱熹的态度和倾向造成一定的影响。朱熹理学产生的针对性在于佛、道二教由于有着精致的思辨性和对普通百姓希望长生不死或拥有美好来世的愿望具有一定的诱惑性和吸引力而一时大盛,甚至对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所以说为了确保儒学的权威和正统地位,儒家学者们在完善自己学说的同时,也须削弱佛、道二教的影响,而要想让理学真正成为显学,王安石新学也是必须要排斥、针对的对象。朱熹子学的这一特征在他评价道家、法家和阴阳家的学说时体现得尤为明显。他斥责庄子对神异思想的宣扬“若曰‘旁月日,扶宇宙,挥斥八极,神气不变’者,是乃庄生之荒唐”;并对阴阳家神秘诳妄之学大加贬低,皆因这两方面是道教学说最初的来源之一。而佛教思想能够顺利地完成本土化并进一步的发展完善,也与道家思想脱不了关系。其视法家为浅陋刻薄的批判态度,则多少是因为王安石新学被视为多有得于包括法家和名家在内的刑名度数之学。对墨子之学先认为其源自儒学,而后又否认的态度上的改变也是出于能够更好的辟佛老的需要。故而朱熹对这几家学说的态度不仅是出于学术上的考量,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
(二)子学思想在朱熹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
在朱熹的整个思想体系中,他的子学思想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朱熹的子学思想并不像他的理学或经学等思想那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缜密的、系统的思想体系,而是通过一些较为零散的语句体现出来;另一方面则是受到尊经抑子的传统观念影响。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诸子之学视为经术的支流与畸变,“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58]这种视诸子学为道术分裂的产物的思想影响了很多后来的学者,导致自汉以来子学的地位始终被置于经学之下的结果。所以以朱熹理学大家和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的地位,其重大的研究价值虽然使得多年来国内外对其思想的研究者众多,但大多数学者多是从哲学、美学、史学、文学、经学、教育学、自然科学、政治、经济、伦理、中西比较及文献考据等角度来对朱熹思想进行研究,从子学的角度来对其思想进行研究的却很少,至今尚未有一个整体的、综合性的系统研究。
朱熹的子学思想虽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这并不代表其不重要。首先,朱熹之所以能够最终建立起一个庞大、缜密、精致的理学思想体系,除了有对儒家思想精华的吸取和完善外,也离不开他对诸子思想的融合和吸收。他吸取了道家哲学的道本论思想,把道与天理相结合,从而为儒家的伦理道德寻找到形而上的本体论哲学依据,使儒学具有了思辨性;他将法家“辟以止辟”和法无等级的理念与儒家的德政、人治思想相融合,形成了一套以正君心、严吏治、举贤才、公平慎刑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体系,基本适应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需要;他在对道、心、性、阴阳、太极、器、物、体用、本末、动静、已发未发、情、欲、知行、形神、变化等众多中国哲学范畴的内涵及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论述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命题、理论和独到的见解,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思辨水平,多少也是受到了道家、玄学及佛教思想的影响。其余像墨家和名家名辨等思想他也多少有所借鉴和采纳。所以全祖望会在《宋元学案·晦翁学案序录》中认为朱熹是“遍求诸家,以收去短集长之益。若墨守而屏弃一切焉,则非朱子之学也。”正是由于朱熹这种不拘于门户之见,广泛吸取各派学说包括诸子思想的合理内核的学术态度,他才能最终成为继孔孟之后中国儒学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代宗师。另外,朱熹的子学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朱熹的学术思想,自宋末以后,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都是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思想,他所撰写的《四书章句集注》等更是科举考试的官方教科书和标准答案,所有要通过科举晋身仕途的学子都必须熟读精研朱熹著作,而子学思想作为朱熹思想体系的一部分,自然也不例外。朱熹的子学思想就在这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学子的思维,使他们对先秦诸子的评价和判断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朱熹的影响而有所倾向。所以说朱熹的子学思想虽说不是最被重视,但也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对朱熹子学思想的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推动对朱熹思想的全面研究和完善,使其更加体系化和整体化。
论朱子的理气动静问题
乔清举
一、问题的提出
太极或理的动静问题,是朱子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学界历来争议较大甚至观点截然相反的一个问题。冯友兰先生是在哲学范式下进行朱子哲学研究的首创者,他认为在朱子哲学中,有动之理,亦有静之理,但理不动亦不静。他说:“太极亦无动静。”[1]又说:
太极中有动静之理,故气得本此理以有动静之实例。其动者便为阳,其静者便为阴。阴阳亦形而下者。至于形而上之动静之理,则无动无静,所谓“不可以动静言”也。[2]
冯先生晚年仍然坚持此观点,并批评“理可以动、可以生气”之说。他说:
一般是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的,有情意,有计度,有造作的是特殊。情意之理并没有情意,计度之理并没有计度,造作之理也不会造作。举一个例说,动之理并不动,静之理也并不静。只有具体的动的东西才动,只有具体的静的东西才静。[3]
理“不动说”的又一著名代表是牟宗三先生,其为学界所耳熟能详的观点是朱子之理“是但理,只存有而不活动”。[4]他说:
(伊川朱子系)此系是以《中庸》《易传》与《大学》合,而以《大学》为主。于《中庸》、《易传》所讲之道体性体只收缩提练而为一本体论的存有,即“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于孔子之仁亦只视为理,于孟子之本心则转为实然的心气之心,因此,于工夫特重后天之涵养(“涵养须用敬”)以及格物致知之认知的横摄“进学则在致知”,总之是“心静理明”,工夫的落实处全在格物致知,此大体是“顺取之路”。[5]
冯友兰言朱子之理不动亦不静,是为了强调朱子之理的先验性与形上性,以揭示中国哲学概念的抽象性质,或曰“哲学”性质,以与西方哲学颉颃媲美,从而使中国哲学研究同时亦成为引进与建立“哲学”的思维方式之渠道。此实为冯友兰那一代学者的中国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牟宗三的中国哲学研究亦属于“哲学”范式,他认为朱子之理“只存有而不活动”,此点实同于冯友兰。然其意图则在于批评朱子之理不能创生万物,由此判定朱子哲学非儒家正宗,乃“别子为宗”。在主张“不动说”之学者序列中,还可以加上陈来、刘述先、李明辉诸位先生[6]。在学术方法与旨趣上,大体陈来承冯友兰,刘述先、李明辉承牟宗三。
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与以上诸论截然不同的观点。贺麟、成中英等先生主张,在朱子哲学中,理是能动的。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贺麟、张荫麟、冯友兰之间曾发生过关于理的动静问题的争论。据贺麟1938年6月15日日记记载:“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中已提出太极之动静与有限事物之动静不同的观点,但因被张荫麟质问‘太极是理,如何能动’后,遂声明太极动静说不通,且以周子的太极为形而下之气。”[7]贺麟于20世纪50年代又指出:“朱熹把太极说成理,无声无臭是无极,至高无上是太极,理有动有静。朱熹发现理是能动的,这是一绝大的贡献,可以与黑格尔媲美。”[8]成中英先生认为:“朱子所谓理气,亦如太极之阴阳相互为用,并非静者恒静、动者恒动的分为二橛。更有进者,朱子一方面说理‘无作为’,另一又说‘未动而能动者,理也。未动而欲动者,意也’(《语类》)。可见朱子对理的了解有多层次多方面的意涵,而不可简化为一单向面的静止之理。”[9]
上述观点分歧表明了太极动静问题在朱子哲学中的复杂性,可见,非充分地占有材料、深入地进行分析,不能穷究朱子之意也。
二、形而上下两种动静
受分析哲学语言分层理论的启发,笔者认为,朱子“动”、“静”概念的内涵,亦可分为形而上、形而下两个层次。换言之,其动静概念之使用可同时指涉形上、形下两个层次。前者为理或太极的动静,可谓本体意义的动静;后者为气的动静,可谓现象意义之动静。动静之分为两个层次,在朱子哲学中是十分明显的。周子《通书》谓:“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朱子解释说: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者,物也。”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下者,则不能通,故方其动时,则无了那静;方其静时,则无了那动。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就人言之,语则不默,默则不语;以物言之,飞则不植,植则不飞是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则神而莫测,方其动时,未尝不静,故曰:“无动”;方其静时,未尝不动,故曰“无静”。静中有动,动中有静,静而能动,动而能静,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错综无穷是也。端蒙。[10]
此段中,朱子主张理与物各有动静;物之动与静相互隔离不通,理之动与静则相互贯通,可见其动静说是分为两个层次的。所以,辨别动静的两个层次是我们理解朱子理之动静问题的关键。在朱子那里,理无动静是说理无形而下的动静,非谓其无形而上的动静;太极有动静,是谓其有形而上的动静,非谓其有形而下的动静。如他说:“太极理也,理如何有动静?有形,则有动静。太极无形,恐不可以动静言。南轩言‘太极不能无动静’。未达其意。”[11]又,“若谓太极便是动静,则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极之言亦赘矣。”[12]此两段中之动静,显然为形下意义的动静。朱子又云:“未动而能动者,理也。未动而欲动者,意也。”[13]此处描述理的第一个“动”,显然是形而下的动,第二个则是形而上的。朱子没有把两个层次的动静分别开来陈述,而是形而上下混说,其理之动静问题研究中出现之分歧,多与此种言说方式有关。明乎此,则分析朱子的理之动静思想,须辨别其所指究竟是形上抑或形下,庶几可以避免误解。
朱子严形而上下之别,故两种动静的差异在他那里是十分明显的。此差异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为显与微的区别。形下之动静是显,处于可感知的经验世界;形上之动静则是微,处于不可感知的抽象世界。其二为偏滞与兼通的区别。形下之动静各偏于一方,不能贯通;形上之动静则是兼通的,动静一如的。从现代哲学来看,朱子之所以区别两种动静,意在表明形上之动静是本体性的、永恒的、价值性的,是理实现于外部世界和规范事物样态的本体性力量。理若无价值性,则混同于现实世界的任何一物,从而不具有规范意义;理若无永恒性,则沦为生灭不定之具体物,从而不足以具有规范性。此两者均可使人类社会因失据陷入无序、使自然世界因失律而陷入混沌。所以,理必须具有价值性、永恒性,此两种性质则来自理的本体性、超越性,一言以蔽之,即形上性。此种形上性使得理一定会实现于外部世界,成为世界之规范,这就是理的动,也是它的本体性力量的表现。这意味着理既不是“但理”,也不是“纯概念”。
三、理之动静的指涉
概念:兼、有、涵、该贯
朱子关于太极或理与动静的指涉关系,有“兼”、“有”、“涵”、“该贯”等说法。众所周知,在古代哲学家中,朱子可谓思维缜密、用词审慎的一位,故其关于理之动静的不同说法,值得深入分析。“太极兼动静”乃其门人梁文叔提出,朱子反对此说法,云:
不是兼动静,太极有动静。喜怒哀乐未发,也有个太极;喜怒哀乐已发,也有个太极。只是一个太极,流行于已发之际,敛藏于未发之时。”[14]
此处之动静是喜怒哀乐之未发与已发,是心理活动,可见是形而下的。若证之以下二条,则此义愈加明显。
太极无方所,无形体,无地位可顿放。若以未发时言之,未发却只是静。动静阴阳,皆只是形而下者。然动亦太极之动,静亦太极之静,但动静非太极耳。[15]
此段明言动静为形而下者,动静之主体非太极。故朱子所谓太极不兼动静,实为太极无形而下之动静。“兼”为形而下地具有。按朱子哲学之思想,若太极有形而下之动静,则其沦为普通经验之物,失去其超越性、永恒性与价值性。太极若无价值性,则朱子之哲学、甚而言之理学已不能建立,人类亦不必存在矣,因其可沦为与动植物一类。此盖为朱子不以经验之动静指涉太极之深意所在。朱子强调太极流行于已发,敛藏于未发,其意为流行时有个太极在,非流行为太极也;敛藏时亦有个太极在,非敛藏为太极也。流行和敛藏皆形而下之动静。
“太极之有动静”是朱子的主张。《通书解》谓:
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诚者圣人之本,物之终始、而命之道也。其动也、诚之通也,继之者善,万物之所资以始也。其静也,诚之复也,成之者性,万物各正其性命也。动极而静,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16]
此段含有形而上下两种动静。“物之终始”、“万物之所资始”、“万物之所成性”,显系形而下之动静。外部世界之动静乃各种现象的交替不已之运动,乃是天命之流行的表现。朱子在此是把形下之动静与“诚”、“太极”相关联而言。“太极之有动静”,乃是强调太极诚固不可以形下之动静指涉,因其为形上也;然亦不可离形下之动静而言。否则,太极、理、形上即沦为孤绝之死理,经验世界即沦为无理之气运世界,上下割断,体用殊绝,非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之义矣。此断非朱子哲学之义。在朱子哲学中,形上世界之孤存或可勉强言之,因其有理之逻辑在先之义,而其所谓经验世界则断然为理气统一之过程世界。故此处之“太极之有动静”,系合形而上下而统言之,言太极既为理,亦表现于气之运动,两者统一。故天命流行亦可谓太极之动静,此即太极之“有”动静。朱子之天命之流行,大抵同于“与道为体”。
太极含动静,在《朱子语类》中又作“函”、“涵”,三者义同。
盖谓太极含动静则可。(朱子自注:以本体而言也。)谓太极有动静则可。(朱子自注:以流行而言也。)17]
以此处朱子之表述来看,所谓“含”,指本体而言,故当为含动静之理。朱子亦明言“太极自是涵动静之理”[18]。如前所述,“有”是一个包含形而下的过程,不纯是本体。
朱子还有一个说法是“实理该贯动静”。周子《通书》有“诚无为,几善恶”一条。朱子释云:
诚,实理也;无为,犹“寂然不动”也。实理该贯动静,而其本体则无为也。“几善恶。”“几者,动之微”,动则有为,而善恶形矣。“诚无为”,则善而已。动而有为,则有善有恶。”[19]
“该”是包含、包括,“贯”是贯穿、统摄。“实理该贯动静”即理包含、统摄并表现于动静。朱子云“无极之真是包动静而言”[20],即是此义;而理之本体却是“无为”的,即“无造作”,无形而下的动静。理既超乎形而下的动静,故其为形上之静、本体之静。“静者为主。植。”[21]此即所谓“静”为太极之本的思想。此段到“几”之后,进入形而下之动静世界,故有善恶产生。在朱子哲学中,本体之静,可对应形而下的动静。图示如下:
但是,既然太极是动而能静、静而能动,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则其动静实质上是形而上的动静一如,相互贯通,故言本体为静亦可、为动亦可。
太极只是涵动静之理,却不可以动静分体用。盖静即太极之体也,动即太极之用也。譬如扇子只是一个扇子,动摇便是用,放下便是体。才放下时,便只是这一个道理。及摇动时,亦只是这一个道理。[22]
若言太极或理为静,则易于与形而下之静相混淆,以形下之静为太极之体、形上之动为太极之用。这样就把太极有限化、具体化了,此是朱子所反对的。此段“不可以动静分体用”的动静,乃是形而下的动静,不能为太极之体、用。所谓“静即太极之体”之静,乃是本体的静,是理之本然的存在状态;而“动”则为理在现实世界的发用、实现,表现为形而下的动。此处须注意者,朱子之表述本体之静,是与形下之动相对而言出的,故易被误解为形下之静。所以,朱子后来废除了太极为体、动静为用的说法,提出“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23],明确地把太极和形而下的动静分开。此意还见于朱子与杨子直第一书。但是,这并不代表朱子彻底否认太极具有动静的意味。
直卿云:“兼两意言之,方备。言理之动静,则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其体也;静而能动,动而能静,其用也。言物之动静,则动者无静,静者无动,其体也;动者则不能静,静者则不能动,其用也。端蒙。”[24]
黄榦此说,以理之动静互涵为理之体,以理之动而能静和静而能动为理之用,可谓朱子的“未动而能动者理也”之说的一个深化,是符合朱子思想的。
四、太极或理如何动静
朱子关于太极或理的动静思想的材料十分丰富,略整理为以下若干条。
1.“主”、太极使气运动:太极的本体力量
在朱子哲学中,太极具有本体性力量。此种力量从太极本身来说,是它一定实现于现实之中的必然性;而自形下世界而言,则为形下世界必如此不已之表现,即朱子所谓“不容已”者。此种力量的直接表现是太极主导气的运动,使气运动。根据《语类》记载:
问:“‘太极动而生阳’,是有这动之理,便能动而生阳否?”曰:“有这动之理,便能动而生阳;有这静之理,便能静而生阴。既动,则理又在动之中;既静,则理又在静之中。”曰:“动静是气也,有此理为气之主,气便能如此否?”曰:“是也。既有理,便有气;既有气,则理又在乎气之中。”[25]
有理“为气之主”,气便能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这表明,理具有使气动的力量,此即理的本体性力量。换言之,太极是有力量的本体,能使天地万物生生不已。《语类》说:
问:“《或问》云:‘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所谓‘不容已’,是如何?”曰:“春生了便秋杀,他住不得。阴极了,阳便生。如人在背后,只管来相趱,如何住得!”淳。[26]
理“不容已”,物“自住不得”,如有人背后在推动,此即理的本体性力量的表现。
2.“生”、“理生气”义之一:太极之本体论的展开
朱子哲学严理气之分、形而上下之别,故有冯友兰所谓理“逻辑在先”之说。在此我们还可补充一个“逻辑在后”说。因朱子曾说“万一山河大地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这意味着在气消亡之后,理依然存在。“逻辑在先”与“逻辑在后”肯定了理的先验性、永恒性、价值性和力量性。这些可谓理或太极的实质性内涵。以往的中国哲学研究,重点在“哲学”范式,注重于太极或理的形式分析,未曾适当地留意其实质性内涵。故在以往的表述中,理似乎成为一独立、孤立的影子或相片世界。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创立新理学体系,其真际世界便类似于一个相片世界。可是理在朱子那里,并不是相片式的死理,而是有本体力量的活理。任何将世界分为形而上下两个者,都面临一个如何使两者合拢的问题。朱子、黑格尔、冯友兰都不例外。朱子沟通形而上下所依靠的,即是作为理的实质内涵的本体性力量。其沟通形而上下的方式之一是主张“理生气”。在朱子哲学中,至少有三种他所认可的文献促使他得出这一结论。第一种是《易传》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第二种是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第三种是邵雍的《伏羲先天六十四卦图》。前两种文献都明确地指出太极“生”两仪或阴阳,后一种文献则以图示方式形象地说明了太极是如何生成六十四卦的。朱子根据这些材料推出了“理生气”的结论:
周子、康节说太极,和阴阳滚说。易中便抬起说。周子言“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如言太极动是阳,动极而静,静便是阴;动时便是阳之太极,静时便是阴之太极,盖太极即在阴阳里。如“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则先从实理处说。若论其生则俱生,太极依旧在阴阳里。但言其次序,须有这实理,方始有阴阳也。其理则一。虽然,自见在事物而观之,则阴阳函太极;推其本,则太极生阴阳。学履。[271
在这段话中,朱子把“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解释为“动是阳”,“静便是阴”。这样,太极和阴阳的关系就不是宇宙论的生与被生的关系,两者形成对立的两个;而是说太极自身表现为阳,又表现为阴,太极和阴阳仍为一体。此种“生”,可谓表现、显现、展开,乃是太极之“本体论地展开”。诚如朱伯崑先生所言,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乃本体论的命题”[28]。朱子强调此“生”与老子之“有生于无”不同,更表明了其本体意义:
曰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则非无极之后别生太极,而太极之上先有无极也。又曰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则非太极之后别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极也。以至于成男成女,化生万物,而无极之妙盖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图之纲领,大易之遗意,与老子所谓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而以造化为真有始终者,正南北矣。[29]
既然太极生阴阳之生是本体论的展开,则两者便不存在时间性的先后关系,而是有则俱有、无则俱无的体用关系。太极之此种本体论的动静,如前所述又被朱子表述为诚之“通”与“复”。然而,此形上之活动并非囿于形上领域的自动自静而已,而是仍要表现于形下世界的。表现的方式之一是“理”宇宙论地生“气”。
3.“生”、“理生气”义之二:太极本体—宇宙论地“生气”
在朱子哲学中,“理”生“气”尚有一本体—宇宙论之说法,即从本体论之展开说生、说动静,进而延伸到宇宙论的生成,实际地“生此阴阳之气”:
“无极而太极”,“而”字轻,无次序故也。“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即太极之动,静即太极之静。动而后生阳,静而后生阴,生此阴阳之气。谓之“动而生”,“静而生”,则有渐次也。“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动而静,静而动,辟阖往来,更无休息。谟。[30]
此段说“无极而太极”之“而”无次序,属于本体论;而“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之“而”“有渐次”,则显然进入了时间,属于宇宙论。“生此阴阳之气”亦为实际之太极生气。朱子又云:“自太极至万物化生,只是一个道理包括,非是先有此而后有彼。但统是一个大源,由体而达用,从微而至著耳。”[31]按照朱子用词习惯来看,此段“微”和“著”亦应是形而上下之别,则其所谓本体论之“生”虽然“发生”在形上之域,却又进入了形下之域。朱子又讲,“气虽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则理管他不得。”[32]其形下之生的意思亦十分明白。客观地说,诚如陈来所言,在朱子的体系中,既然理逻辑在先,自然就会产生理生气的结论[33]。不过,朱子仍然强调,理生气之后,理仍在气中。“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阴阳既生,太极在其中,理复在气之内也。”[34]理气在经验世界构成一体的思想亦是朱子的结论,故朱子的理生气,是本体-宇宙论地生,是本体宇宙论性质的,不单纯是其中的一面。朱子以此解决形而上下之合拢或沟通问题。至于此种解决是否合理,则是另一问题。
4.“应”、“继”、“行”:理之自我实现
在朱子哲学中,理自身有体用,体为未发之本然,用为已发之感应。“应”、“继”、“行”是朱子说明理实现于现实世界的用语。
本然而未发者,实理之体;善应而不测者,实理之用。动静体用之间,介然有顷之际,则实理发见之端,而众事吉凶之兆也。[35]
此段中,“应”即是本体之动,是理的实现,此实现最终落实为现实世界之吉凶。朱子的理可以实现于现实世界,乃是贺麟之观点;贺麟以此为理之动。只是理如何实现,贺麟尚未明言。笔者此处之论可视作对贺麟观点的一个推进。朱子表达理动的说法还有“继”和“行”。他指出,继善成性的“继”就是“动”。他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这“继”字便是动之端。若只一开一阖而无继,便是阖杀了。又问:“继是动静之间否?”曰:“是静之终,动之始也。且如四时,到得冬月,万物都归窠了;若不生,来年便都息了。盖是贞复生元,无穷如此。”夔孙。义刚录同。[36]朱子又云:
“继之者善”是动处,“成之者性”是静处。“继之者善”是流行出来,“成之者性”则各自成个物事。“继善”便是“元亨”,“成性”便是“利贞”。及至“成之者性”,各自成个物事,恰似造化都无可做了;及至春来,又流行出来,又是“继之者善”。譬如禾谷一般,到秋敛冬藏,千条万穟,自各成一个物事了;及至春,又各自发生出。以至人物,以至禽兽,皆是如此。义刚。[37]
仔细体察此段之动静说,结合前文朱子“以诚之通、复为形上之动静”之论可知,和通、复、相比,继、成有过渡的特点,由形上开始向形下过渡;始、正则进入形下之动静。此数个动静,可用下面图标表示:
太极动而生阳,朱子认为,“动”为理之“行”。此“行”显然是理的实现,即理之动:
问:“此理在天地间,则为阴阳,而生五行以化生万物;在人,则为动静,而生五常以应万事。”曰:“动则此理行,此动中之太极也;静则此理存,此静中之太极也。”洽。[38]
5.“妙”、“神妙万物”:理对于物或物支配、主宰与决定
在朱子的材料中,“神”至少有六种用法。其一是人的感知性能:“知觉便是神。触其手则手知痛,触其足则足知痛,便是神。”[39]其二是心的思维和主宰性能:“神即是心之至妙处,滚在气里说,又只是气,然神又是气之精妙处。”[40]其三是气之运动的微妙之处:“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这里,又忽然在那裹,便是神。’”[41]其四是神彩:“神便在心里,凝在里面为精,发出光彩为神。”[42]其五是圣人之德:“神即圣人之德,妙而不可测者。”[43]其六是形上之理对于事物的神妙莫测的决定作用,此即理的形而上的动静,甚值得注意。
问“动而无动,静而无静”。曰:“此说‘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此自有个神在其间,不属阴,不属阳,故曰‘阴阳不测之谓神’。且如昼动夜静,在昼间神不与之俱动,在夜间神不与之俱静。神又自是神,神却变得昼夜,昼夜却变不得神。神妙万物。如说‘水阴根阳,火阳根阴’,已是有形象底,是说粗底了。”植。[44]
在这段话中,事物的形下的动静是由神所决定或主宰的。神能够使昼变为夜或使变夜为昼,昼夜却不能使神发生改变,亦不能使神与之俱动俱静。陈来认为,此处理含有使气由静复动的“几”,可谓灼见。[45]关于神之不随物动静,朱子又进一步解释说:
昼固是属动,然动却来管那神不得;夜固是属静,静亦来管那神不得。盖神之为物,自是超然于形器之表,贯动静而言,其体常如是而已矣。时举。[46]
什么是“贯动静”?按照朱子的表述来看,是连接形而下的动静,并主导两者发生的节奏及转换。
《动静》章所谓神者,初不离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敛,岂专乎动?地之发生,岂专乎静?此即神也。闳祖[47]
在朱子哲学中,动静转化、阴阳互根,皆是神对事物的奇妙的控制,即所谓的“神妙万物”。“妙”为动词,是主导、主宰、控制、使之奇妙之义,此可谓神的形上之运动。那么,“妙万物而为言之神”是什么?朱子明确地说,是理:
曰:“所谓神者,是天地之造化否?”曰:“神,即此理也。”……又问神,曰:“神在天地中,所以妙万物者,如水为阴则根阳,火为阳则根阴”云云。寓。[48]
关于理的主宰义,《朱子语类》中有“帝是理为主。淳。”此是化帝为理,以理为主导、主宰。《语类》又云:“苍苍之谓天。运转周流不已,便是那个。而今说天有个人在那里批判罪恶,固不可;说道全无主之者,又不可。这里要人见得。僴。”此段中,帝非人格神,而为主宰世界之理的含义甚为明显。理如何主宰天地之运行,朱子亦有解释: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无心。近思之,窃谓天地无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虑,有营为。天地曷尝有思虑来!然其所以‘四时行,百物生’者,盖以其合当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维,此所以为天地之道。”
曰:“如此,则易所谓‘复其见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又如何?如公所说,祇说得他无心处尔。若果无心,则须牛生出马,桃树上发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谓之帝,以性情谓之乾。’他这名义自定,心便是他个主宰处,所以谓天地以生物为心。中间钦夫以为某不合如此说。某谓天地别无勾当,只是以生物为心。一元之气,运转流通,略无停间,只是生出许多万物而已。”道夫。[49]
可见,在朱子看来,天地之心即是理,理的主宰使得天地万化正常运转,不至于出现牛生马、桃开李花一类的紊乱。
在此有必要对前人关于朱子之理之“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的解释重新加以审视。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之初,如何使中国哲学史是“哲学”之史,成为学界之共同努力。照冯友兰等人的看法,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概念思维,概念是抽象的、不夹杂有物质的内涵,“不拖泥带水”。朱子之理因其逻辑在先的先验性,“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洁净空阔”的抽象性和纯粹性,被当时学者认为是可与柏拉图、黑格尔之理念相对应之纯概念。这一认识无疑是很有见地的,所以冯友兰采用新实在论的思路来研究朱子哲学;贺麟欲将“绝对理念”译为太极。在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中,真际甚或成为实际世界的一个影子或相片。冯友兰对于朱子之理的认识具有极大影响,学界基本上接受了他的结论。即使是对宋明理学的总体认识与之截然相反的牟宗三,其朱子之理为“只存有不活动”之说,显然为冯友兰观点的又一版本。可是,这种路径也有重大缺陷。它只注重对概念的思维形式的分析,而严重地忽略了其实质性内涵,失去了朱子形而上概念的价值性、力量性和与形下世界的一体性。如果说形而上下暌隔,理世界只是事世界的一个影子或相片,不能对后者发生影响,则理即果真沦为不活不妙、可有可无之“死理”了。诚如前人所批评的那样,此种理,纵然在坑满坑、在谷满谷,又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即使是从史料上看,只强调理“无情义”亦是不全面的。“无情义”之说出自沈僩“问理气先后”条,朱子显然不赞成纠缠于此问题,指出:
不消如此说。而今知得他合下是先有理,后有气邪;后有理,先有气邪?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则疑此气是依傍这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子白地生出一个物事,这个都是气。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气,则理便在其中。”僴。[50]
朱子在此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认识,其一是学界通常注意的“无情义”一类的理的抽象性、消极性、无为性方面,其二是“此气是依傍这理行”和“此气之聚,理亦赋焉”一类关于气对理之依附性或理对气之支配性的认识。朱子与此略近的思想亦表现于对于周子《通书》第五章的解释中,云此章“言道之体用不外乎阴阳,而其所以然者,则未尝倚于阴阳也。”[51]此“未尝倚于阴阳”十分值得注意。不离不杂是朱子理气关系的要点,但此处朱子不说理不杂于阴阳,而说其“未尝倚于阴阳”。“倚”有依凭、取决于之义。显然,朱子在此表述的是道决定阴阳而非相反,强调的是道的先验性力量。这体现了道、理、神的“妙”义。
当然,理之无为亦非全是对朱子的误解。其思想中有此内容,主要表现在他强调形而上下的区别之时,以及说明恶和异常时所主张的气强理弱的观点之中。如前所述,朱子有形而上下两层动静的思想。然而,形上之动静不可见,须因形下之动静而显现,故在形下层面,理显得有些被动。朱子说:“盖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52]什么是“机”?朱子曰:“机,是关捩子。踏着动底机,便挑拨得那静底;踏着静底机,便挑拨得那动底。”[53]与此相同的还有一条:“机,言气机也。诗云:‘出入乘气机。’”,[54]朱子又有颇引后人诟病的人跨马之喻:
阳动阴静,非太极动静,只是理有动静。理不可见,因阴阳而后知,理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相似。[55]又说:
曰:太极理也,动静气也。气行则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尝相离也。太极犹人,动静犹马。马所以载人,人所以乘马。马之一出一入,人亦与之一出一入。盖一动一静,而太极之妙未尝不在焉。此所谓‘所乘之机’,无极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铢。[56]
理既能被气所驱动,自然是“气强理弱”:
问:“季通主张气质太过。”曰:“形质也是重。且如水之气,如何似长江大河,有许多洪流!金之气,如何似一块铁恁地硬!形质也是重。被此生坏了后,理终是拗不转来。”[57]
此段所谓“拗转”,是改变金属的物理或化学形态,限于当时之科技水平,这样做显然是困难的,所以叫作“理终是拗不转来”。朱子以此喻人气质沉重难以变化,终究是被气所决定,不能向善。朱子此语,是为了说明现实中的恶。恶不能归于理,否则即获得本体基础而不能排斥,故只能归之于气。朱子云“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58],即是此意。因为恶实质上只是人文世界之事,故朱子谈及此时一般限于气质而言。朱子还有一条谈到“气强理弱”,亦是为了说明恶的来源:
谦之问:“天地之气,当其昏明驳杂之时,则其理亦随而昏明驳杂否?”
曰:“理却只恁地,只是气自如此。”
又问:“若气如此,理不如此,则是理与气相离矣!”
曰:“气虽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则理管他不得。如这理寓于气了,日用间运用都由这个气,只是气强理弱。譬如大礼赦文,一时将税都放了相似,有那村知县硬自捉缚须要他纳,缘被他近了,更自叫上面不应,便见得那气粗而理微。又如父子,若子不肖,父亦管他不得。圣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这些子。”时举。柄录云:“问:‘天地之性既善,则气禀之性如何不善?’曰:‘理固无不善,才赋于气质,便有清浊、偏正、刚柔、缓急之不同。盖气强而理弱,理管摄他不得。如父子本是一气,子乃父所生;父贤而子不肖,父也管他不得。又如君臣同心一体,臣乃君所命;上欲行而下沮格,上之人亦不能一一去督责得他。’”[59]
我们理解朱子的理乘气行、气强理弱时须注意,此皆是理在形下之中的一种存在状态,而非其本然的存在状态。形下之动静绝非形上之动静,两者不可相提并论。前者具有先验性、本体性与价值性,后者则只是物理世界的一时的事实而已。形而下地说,固然存在气强理弱之现象;形而上地说,则当然是理强气弱,否则理就没有意义和价值了。故理主宰气是本体意义的,应然的;理随气之动静则非本体意义的,不是气对理本体上就有决定作用。毕竟,在理气关系中,理的决定性、主宰性是优先的。若人只是唯马首是瞻,形上之理之动静只为气所驱动,则理便沦为形下之一具体物,无任何先验性、永恒性、价值性、力量性可言矣。正如马行终究由人决定一样,在价值上,气之运动终究还是由理所决定的。恰如气“志壹动气”、“德胜气”一样。这是理的尊严和力量,也是理的形而上的动静。
五、道体流行之境界:太极之动静表现于气之动静
在朱子哲学中,气世界在本体上之如此表现,是由理来主宰、主导与发动的,故当现实世界之气之运动合乎理时,即为“天命流行”之状态,亦为道体流行之状态。此时,形而上下融为一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可直指形而下之世界而谓其为形而上之世界。朱子对于“夫子川上之叹”的解释,颇能体现此意:
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60]
此处的天地之化,乃是大化流行的过程,是吾人可以目视手触的形下过程。但其往者过、来者续之生生不息的状态,乃是道体的本然状态之体现或实现,故吾人可径谓此过程即是道体之流行,或曰天命流行;此时形而下所表现的即是形而上;形而上下合一,形而下之动静即是形而上之动静。吾人亦可曰,在朱子处,在理想状态下,理气浑论为一,气之动静即理之动静。对于《中庸》“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朱子解释道:
子思引此诗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谓费也。然其所以然者,则非见闻所及,所谓隐也。故程子曰:“此一节,子思吃紧为人处,活泼泼地,读者其致思焉。”[61]
此处所谓流行不息之境界,即是以费显隐、隐费一体,太极之动静体表现于现实世界之事事无碍的境界。《语类》记载,陈淳问“鸢飞鱼跃,皆理之流行发见处否?”朱子回答说,“固是”。朱子又说:“那个满山青黄碧绿,无非是这太极。”[62]朱子言太极为本然之妙,动静为所乘之机,亦是说太极之动静或曰理之动静由气之动静表现出。至此,我们可以对朱子备受诟病的“人跨马之喻”给予新的理解。朱子在比喻之后又说:“盖一动一静,而太极之妙未尝不在焉。此所谓‘所乘之机’,无极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这是理气一体、以形而下之动表达形而上之动的意思,只是比喻有些不当。曹端以来的诸多批评未能把握朱子此意。
朱子此思想在其解释“仁”时更为明显,他把仁作为生气之流行。朱子有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他把元亨利贞、春夏秋冬作为天地生物之四个阶段,仁义礼智与元亨利贞相比配。元为生意。但此生意非只限于春。朱子继承程子之说,把仁分为“专言”与“偏言”两种。专言的仁包括义礼智三德,偏言者则只为四德之一。故其所谓仁之生意,亦包括亨、利、贞,夏、秋、冬,此三阶段或三季皆为统一之生意之表现。据《语类》记载:
或问论语言仁处。曰:“理难见,气易见。但就气上看便见,如看元亨利贞是也。元亨利贞也难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时尽是温厚之气,仁便是这般气象。夏秋冬虽不同,皆是阳春生育之气行乎其中。故‘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南升。[63]
理无迹,不可见,故于气观之。要识仁之意思,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这不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有这个浑全流行物事。此意思才无私意间隔,便自见得人与己一,物与己一,公道自流行。须是如此看。……致道云:“如春是生物之时,已包得夏长、秋成、冬藏意思在。”曰:“春是生物之时,到夏秋冬,也只是这气流注去。但春则是方始生荣意思,到夏便是结里定了,是这生意到后只渐老了。”贺孙曰:“如温和之气,固是见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节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贺孙。[64]
此两段中,仁为“温厚之气”、“浑然温和之气”,其理又为“天地生物之心”,这便是理气浑然合一之状态。此时仁之流行,即表现为“浑然温和之气”之流行,或者说,温和之气的流行便是仁的流行。此理、此气之浑然一体,朱子也通过理一分殊来说明:
周子谓:“五殊二实,二本则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大小有定。”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气,二气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来,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然总又只是一个理。此理处处皆浑沦,如一粒粟生为苗,苗便生花,花便结实,又成粟,还复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个个完全;又将这百粒去种,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间只是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总只是一个理。淳。[65]
可以说,在此处,理的实现即表现为生气的流行,具体言之又表现为粟生为苗、苗又开花结实复成为粟的过程。如果说仁也可以表现为气,那就与通常我们强调仁为“爱之理”、理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的认识不尽相同了。这种差异实质上是我们对于“哲学”范式进行自觉反思、更加贴近朱子本身来理解朱子哲学得出的结论。这意味着朱子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待于方法论的突破。
陈来
朱子思想中有关四德以及五常的讨论,以往受到的关注不多。事实上,朱子有关四德五常的思想对后来的哲学、特别是明代哲学的讨论影响甚大。本文就朱子在四德五常方面的论述,以《朱子语类》的资料为主,作一梳理,并加以分析,藉以了解朱子学德目论或德性理论的结构和意义。
一、北宋道学论四德
“四德”本指乾之四德“元亨利贞”,“四德”统称源出《周易·文言传》,所谓“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本于孟子,汉儒始用“五常”的概念。北宋以来,道学的讨论中开始把二者加以联结,而在后来的宋明理学发展中仁义礼智也往往被称为四德。汉以来的思想中,元亨利贞属天道,仁义礼智属人道。天道的四德和人道的四德,二者的关系在道学中渐渐成为重要的论题。
周敦颐在《通书》中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1]元亨利贞在《周易》本指天道而言,周敦颐虽然还没有把元亨利贞与仁义礼智联系起来,但开始把元亨利贞与本属人道的“诚”联系起来,这也是有意义的。而且,他还表现出把元亨利贞看作一个流行的过程,并用“通”、“复”来把这一过程截分为两个阶段,元亨属于“通”的阶段,利贞属于“复”的阶段。按朱子的解释,元亨是万物资始,利贞是各正性命;前者是造化流行,后者是归藏为物。这种用类似“流行”的观念来解释易之四德的性质与联系,是有示范意义的。
程明道则最重视四德中的“元”与五常中的“仁”的对应,言“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2]明确肯定“元”就是“仁”。这就把宇宙论的范畴和道德论的范畴连接起来,互为对应,从一个具体的方面把天和人贯通起来,使道德论获得了宇宙论的支持,也使宇宙论具有了贯通向道德的含义。“‘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个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长’,万物皆有春意,便是‘继之者善也’。”[3]善是继承了天道的生生之理而来的,所以善体现了元的意思,元即是善的根源。“‘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性情犹言资质体段。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贞也。诗曰:‘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者,贞也。”[4]于是,在道学中,德性概念不再是纯粹道德哲学的概念,同时也具有宇宙论的意谓或根源。
二程已经把四德和五常联系起来讨论,如伊川《程氏易传》的《乾》卦卦辞注:“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5]又解释《乾》卦彖辞“大哉乾元”句说:“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6]又如伊川言:“读易须先识卦体。如乾有元亨利贞四德,缺却一个,便不是乾,须要认得。”[7]“自古元不曾有人解仁字之义,须于道中与他分别五常,若只是兼体,却只有四也。且譬一身:仁,头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虽言‘元者善之长’,然亦须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义在乎此,亦无人曾解来。”[8]他认为元必须通四德而言,仁必须通五常而言,兼体是指元可以兼亨利贞,仁可以兼义礼智信。这些地方都是以四德和五常并提,把它们看成结构相同的事物。
二程又说:“孟子将四端便为四体,仁便是一个木气象,恻隐之心便是一个生物春底气象,羞恶之心便是一个秋底气象,只有一个去就断割底气象,便是义也。推之四端皆然。此个事,又着个甚安排得也?此个道理,虽牛马血气之类亦然,都恁备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随形气,后便昏了佗气”。[9]这里所说的“气象”,就是后来朱子所说的“意思”,即一个道德概念的精神、取向及一个价值概念在形象上的表达。这种讲法认为每一道德概念都有其“气象”、“意思”,即都有其蕴涵并洋溢的特定气息、态度,如说仁有春风和气的气象(意思),义有萧肃割杀的气象(意思),等。这个讲法很特别,讲一个道德德目的实践所发散的“气”,这种德气论的讲法得到了朱子四德论的继承和发展。
二、论道与德
《朱子语类》卷六收录了朱子论“仁义礼智等名义”的讲学语录,名义即名之义,在这里指道德概念的意义。为集中和简便起见,本文以下主要使用该卷的资料进行分析。
朱子把传统德目置于“理”的概念下进行讨论,首先是关于一理与五常的关系:
问:既是一理,又谓五常,何也?曰:谓之一理亦可,五理亦可。以一包之则一,分之则五。问分为五之序。曰:浑然不可分。节。[10]
这是用理一分殊的模式处理五常与理一的关系:一方面五常的仁义礼智信五者都是理,仁是理,义是理,礼智信皆是理;但另一方面五常的理是分殊的理,不是理一的理,是具体的理,不是普遍的理。就理一和五常的发生关系来说,五常是由理一所分出来的,这就是“分之则五”。就理一和五常的逻辑关系说,理一可以包含五常,这就是“以一包之则一”。总之,仁义礼智信五常是五种分殊之理,是作为理一的天理在具体事物不同方面的表现。当然,朱子在另外的讨论中也提出,偏言之仁,其中也含具其他各常之理,[11]这种提法体现了太极论的思维,此处不拟详论。
在理学中,“理”在哲学概念体系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也是涵盖性最大的概念,但理学的体系仍然需要“道”和“德”这些传统道德概念:
问:“仁与道如何分别?”曰:“道是统言,仁是一事。如‘道路’之道,千枝百派,皆有一路去。故《中庸》分道德曰,父子、君臣以下为天下之达道,智仁勇为天下之达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个行道底。故为君主于仁,为臣主于敬。仁敬可唤做德,不可唤做道。”榦(以下兼论德)。[12]
道和仁的关系也如理一分殊的关系,道是统言当然之则,仁只是一事之德。所以仁是德,但不是道。在这里朱子下了一个定义:“德便是行道底”,这就是说德是用来践行道德原则的内在德性。
至德、至道: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独得。盛德、至善: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至善以理之极致而言。诚、忠、孚、信:一心之谓诚,尽己之谓忠;存于中之谓孚,见于事之谓信。端蒙。[13]
如果分析起来,孚存于中,是德性;信见于事,是德行。道是人所共由,即道是指客观普遍的法则,德是指一个人特有的品质,至善是理的极致。用“得”或“得之于身”来申释德,这是源自先秦的传统,即德者得也。
就心性论而言,朱子认为:“存之于中谓理,得之于心为德,发见于行事为百行。节。”[14]此言分析最明:理是存之于中的,即心之所具的;德是得之于心的,是心的一种品质、属性;行是见之于行事的行为。不过仁义礼智之为理,是人之性,存于心中;仁义礼智又是德,是得之于心的。这两者如何安顿衔接?朱子的名言“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也”,就仁是爱之理说,爱是情,仁作为性理是情的内在根据,这是清楚的。但就仁者心之德说,仁既然已经是理,理和心之德是什么关系?情之理,心之德,是同是异?从朱子的这些表述看来,情之理不等于心之德,是说仁既是存之于中的情之理,也是得之于心的心之德,既是性,也是心,而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这样看来,四德有性理和心德的不同用法。
朱子又说:“德是得于天者,讲学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节。”[15]存于中是性理,这应当是清楚的。在理学思想中,德性作为品质,是属心还是属性?抑或是用心、性以外的概念来表达?理学有没有品质概念?从这段所说看,如果说徳是得自于天的,那就是性;如果说徳是“讲学而得之”,则不是性,只能是作为心之品质的德,这里的“徳”就是品质、德性的概念。
三、意思与气象
朱子讲五常,因为要与乾之四德对应,往往仅举仁义礼智,而不及信。这不仅是要把人之四德与天之四德相对,也与朱子对信的定位及五常与五行对应的思想有关。朱子认为信如五行之土,信只是证实仁义礼智的实有,这个说法与先秦两汉的思想是不同的。
下面来看朱子论仁义礼智的意思与气象,“意思”在这里具有字义解释的意义,但不是定义式的解释,而是一种价值含义的解释。
吉甫问:“仁义礼智,立名还有意义否?”曰:“说仁,便有慈爱底意思;说义,便有刚果底意思。声音气象,自然如此。”直卿云:“六经中专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义而不言礼智者,仁包礼,义包智。”方子。节同。佐同。[16]
仁义作为价值概念,其本身带有价值的意味,意思、气象都是指价值概念含蕴和发显的价值气息。可见,人道四德的“意思”,是指德目的价值蕴涵,是属于道德哲学的讨论。仁的“意思”是慈爱温和,义的“意思”是刚毅果断,如此等等。
朱子又说:“生底意思是仁,杀底意思是义,发见会通是礼,深藏不测是智。节。”[17]这里所谓生的意思是指宇宙间生命、生生的意思,本属宇宙论,但在朱子这里,宇宙论的意思和道德论的意思可以互通互换,如说仁的意思是生,也可以说生的意思是仁,仁和生成为相互说明的概念;又如义是杀的意思,也可以说杀的意思是义,等等。生与仁的连接是道学的一大发明,到朱子则将此种连接扩大,把仁义礼智通通和自然世界的属性连接起来,使仁义礼智更加普遍化,即具有宇宙论的普遍意义。这可以说是一种天人合一思维的体现。
蜚卿问:“仁恐是生生不已之意。人唯为私意所汩,故生意不得流行。克去己私,则全体大用,无时不流行矣。”曰:“此是众人公共说底,毕竟紧要处不知如何。今要见‘仁’字意思,须将仁义礼智四者共看,便见‘仁’字分明。如何是义,如何是礼,如何是智,如何是仁,便‘仁’字自分明。若只看‘仁’字,越看越不出。”曰:“‘仁’字恐只是生意,故其发而为恻隐,为羞恶,为辞逊,为是非。”曰:“且只得就‘恻隐’字上看。”道夫问:“先生尝说‘仁’字就初处看,只是乍见孺子入井,而怵惕恻隐之心盖有不期然而然,便是初处否?”曰:“恁地靠着他不得。大抵人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仁,便是个温和底意思;义,便是惨烈刚断底意思;礼,便是宣著发挥底意思;智,便是个收敛无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圣门却只以求仁为急者,缘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温厚底意思在这里,到宣著发挥时,便自然会宣著发挥;到刚断时,便自然会刚断;到收敛时,便自然会收敛。若将别个做主,便都对副不着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问:“仁即性,则‘性’字可以言仁否?”曰:“性是统言。性如人身,仁是左手,礼是右手,义是左脚,智是右脚。”道夫。[18]
仁是生生不已的思想,从北宋道学如明道强调以来,把仁和宇宙流行的趋向打通,扩大了仁学的范围,加深了对仁的理解。朱子在此基础上强调,仁的理解也要结合义礼智一起来看。但朱子也指出,以仁为生意,是通向宇宙论的说法,不是价值论的说法,不是德性论的说法。朱子指出,仁义礼智是人之德性,这里所用的“德性”应当与朱子一般所用的“性”有所不同,而接近心,即心之德。所以朱子主张“常存得温厚底意思在这里”,这里的“存得”、“在这里”,应当不仅指性,而且指心之德性,即心中常存温厚的意思。
至于四德的意思,照这里所说,仁是温和的意思,义是惨烈刚断的意思,礼是宣著发挥的意思,智是收敛的意思。以礼的意思为“宣著发挥”,与前面一条所说“发见会通”是一致的;以智的意思为“收敛”,与前面所说的“深藏不测”也是一致的。这种“意思”的说法,与单纯的“理”或“性理”的说法,还是有差别的。
总之,意思说是朱子四德论的一个特色,值得进一步讨论。当然,朱子不仅讨论仁义礼智四德,也讨论元亨利贞四德。朱子曾说:“元亨利贞本非四德,但为大亨而利于正之占耳,《乾》卦之《彖传》、《文言》乃借为四德,在他卦,尤不当以德论也。”[19]朱子认为《周易》本文的元亨利贞只是占辞,没有道德意义,但《彖传》和《文言》把元亨利贞发挥为四德,这已不是《周易》的《乾》卦经文的本义了。但《彖传》和《文言》发挥的四德,在后来的哲学讨论中越来越有意义,成为易学哲学史在宇宙论方面的重要讨论,为后世的宇宙论提供了基本的模式。
四、生气流行
朱子四德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贯彻了“生气流行”的观念来理解四德:
郑问:“仁是生底意,义礼智则如何?”曰:“天只是一元之气。春生时,全见是生;到夏长时,也只是这底;到秋来成遂,也只是这底;到冬天藏敛,也只是这底。仁义礼智割做四段,一个便是一个;浑沦看,只是一个。”淳[20]
这是说,天地之间只是一气流行,这个一气流行又称一元之气。一元之气就是从整体上看,不分别阴阳二气。一气是流行反复的:“流行”即不断运行,“反复”是说流行是有阶段的、反复的,如一年四季不断流行反复。四季分开来看,每个不同;连接起来看,则只是一元之气流行的不同阶段。朱子认为,仁义礼智的关系也是如此:分别来看,仁义礼智各是一个道德概念;连接起来看,仁义礼智都是仁,都是作为生意的仁在不同阶段的表现。
所以,朱子又说:“仁,浑沦言,则浑沦都是一个生意,义礼智都是仁;对言,则仁与义礼智一般。淳。”[21]就分别来说,与义礼智相区别的“仁”是生意,“生意”即生生不息之倾向;而就整体来说,仁义礼智都是仁的表现,都是生生之意的不同阶段、不同方面的表现。
“仁有两般:有作为底,有自然底。看来人之生便自然如此,不待作为。……大凡人心中皆有仁义礼智,然元只是一物,发用出来,自然成四派。如破梨相似,破开成四片。如东对著西,便有南北相对;仁对著义,便有礼智相对。以一岁言之,便有寒暑;以气言之,便有春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便有金木水火土。且如阴阳之间,尽有次第。大寒后,不成便热,须是且做个春温,渐次到热田地。大热后,不成便寒,须是且做个秋叙,渐次到寒田地。所以仁义礼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仁流行到那田地时,义处便成义,礼、智处便成礼、智。且如万物收藏,何尝休了,都有生意在里面。如穀种、桃仁、杏仁之类,种著便生,不是死物,所以名之曰仁,见得都是生意。如春之生物,夏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渐渐收敛,冬是生意收藏。”又曰:“春夏是行进去,秋冬是退后去。正如人呵气,呵出时便热,吸入时便冷。”明作。[22]
仁是生意,有流行。“元只是一物”,这里指仁;“发用出来,自然成四派”,指仁义礼智。朱子认为天地间事物都是如此,一元流行,而自然形成几个次第界限,如气之流行便成春夏秋冬,木之流行便成金木水火土,循环往复。冬至一阳来复,生意又复发起,生长收藏,不断循环。仁之流行,循着四个阶段往复不断,不管仁的流行所形成的仁义礼智四阶段与生物流行自然成春夏秋冬四季如何对应一致,仁作为生意流行的实体,已经不是静而不动的理、性了。
那么,仁是生意,仁是不是生气呢?上面引用的陈淳录的材料只是把仁义礼智与一元之气的流行加以类比,认为仁相当于一元生气,两者的结构是完全一样的,还没有说明仁是生气。
下面的材料则更进了一步。
问:“仁是天地之生气,义礼智又于其中分别。然其初只是生气,故为全体。”曰:“然。”问:“肃杀之气,亦只是生气?”曰:“不是二物,只是敛些。春夏秋冬,亦只是一气。”可学。[23]
分别来看,春是生气,冬是肃杀之气,但春夏秋冬,只是一气流行的不同阶段;以冬之肃杀而言,冬季的肃杀之气并不是与春季开始的生气不同的另一种气,只是生气运行到此阶段,有所收敛。照这里的答问来看,朱子不仅认为仁是生意,也肯定仁是生气;不仅仁是生气,仁义礼智全体也是生气。在这个意义上朱子也采用二程“专言之则包四者”的说法,说仁包义礼智(信),只是他已赋予仁包四者以生气流行的意义。从理论上来分析,如果仁是生气流行,这个仁就不能是理,不能是性,而近于生气流行的总体了。在心性论上,这样的仁就接近于心体流行的总体了。只是,朱子并没有把这一思想彻底贯彻到心性论。
《朱子语类》又载:
蜚卿问:“仁包得四者,谓手能包四支可乎?”曰:“且是譬喻如此。手固不能包四支,然人言手足,亦须先手而后足;言左右,亦须先左而后右。”直卿问:“此恐如五行之木,若不是先有个木,便亦自生下面四个不得。”曰:“若无木便无火,无火便无土,无土便无金,无金便无水。”道夫问:“向闻先生语学者:‘五行不是相生,合下有时都有。’如何?”曰:“此难说,若会得底,便自然不相悖,唤做一齐有也得,唤做相生也得。便虽不是相生,他气亦自相灌注。如人五脏,固不曾有先后,但其灌注时,自有次序。”久之,又曰:“‘仁’字如人酿酒:酒方微发时,带些温气,便是仁;到发到极热时,便是礼;到得熟时,便是义;到得成酒后,却只与水一般,便是智。又如一日之间,早间天气清明,便是仁;午间极热时,便是礼;晚下渐叙,便是义;到夜半全然收敛,无些形迹时,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道夫。[24]
这也是用酿酒的过程和一日早晚的过程,来类比说明四德是流行的不同阶段。这样一来,仁义礼智四德不再只是道德的德目,而变为与元亨利贞四德一样,也是自然之德,仁义礼智也可以用来描述自然流行的阶段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仁义礼智四德也自然化了,仁义礼智与元亨利贞的同一,导致自然与社会节度的混一。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灌注”即流住、流行,指五行之气自相灌注,灌注的次序便是五行展开的次序。朱子这里所说,也意味着仁义礼智四德与五行之气一样,是按一定的灌注次序展开的。只是,这里四德展开的次序是仁礼义智,而不是仁义礼智,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把仁义礼智四德类比于五行之气的流行灌注,这本身就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显示出气的思维对朱子四德论的影响。
当然,在朱子的论述中,酿酒和一日早晚的例子,不如一年四季变化更为常用:
只如四时:春为仁,有个生意;在夏,则见其有个亨通意;在秋,则见其有个诚实意;在冬,则见其有个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尝息!本虽凋零,生意则常存。大抵天地间只一理,随其到处,分许多名字出来。四者于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见仁义礼智实有此理,不是虚说。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贞亦重,以明终始之义。非元则无以生,非贞则无以终,非终则无以为始,不始则不能成终矣。如此循环无穷,此所谓‘大明终始’也。”大雅。[25]
这样来看,自然流行的节度,总是生、长、遂、成,不断循环往复;与生、长、遂、成四个阶段相对应,便是元、亨、利、贞四德,四德分别是生、长、遂、成各自阶段的性质、属性、性向,也可以说是每个阶段的德性。照朱子看来,与生、长、遂、成相对应的属性、德性,既可以说是元、亨、利、贞,也可以说是仁、义、礼、智,这两个说法是一致的。这无异于说,仁义礼智在这里是自然属性的范畴。这就把仁义礼智自然化、宇宙论化了,这样的仁义礼智就不仅有道德的意义,也具有宇宙论的意义。要强调的是,当朱子把仁义礼智作为自然化的范畴时,绝不表示作为自然化了的仁义礼智与作为人道的仁义礼智概念已经根本不同,已经是两回事;不,在朱子哲学,自然化的仁义礼智与人道的仁义礼智仍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只是用法与意义有广有狭而已。
所以,朱子更断言仁义礼智便是元亨利贞:“仁义礼智,便是元亨利贞。若春间不曾发生,得到夏无缘得长,秋冬亦无可收藏。泳。”[26]这就把仁义礼智之间的关系看成与元亨利贞同样的流行,这在无形之中使仁义礼智在一定程度上也变成为具有宇宙论流行意义的实体——气。而这里的元亨利贞也不能说只是性了。
《朱子语类》:“问:‘元亨利贞有次第;仁义礼智因发而感,则无次第。’曰:‘发时无次第,生时有次第。’佐。”[27]“发时无次第”是指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感发生是没有一定次序的,“生时有次第”是指仁义礼智作为生气流行具有一定的先后次序。按学生的提问,元亨利贞的次序即春夏秋冬的流行次序,是实际流行的次第,而仁义礼智都是由感而发,不一定有固定的次序。这样,二者不就是不一致了吗?学生所说的仁义礼智还是局限于性情的仁义礼智,而朱子所说的流行的仁义礼智已不限于性情之发,“生时有次第”就是指作为生气流行的仁义礼智有其次序。这些都再次体现了四德具有生气流行的意义。当然,在最低的程度上,也可以说“生时有次第”包含着仁义礼智四者在逻辑上的次序。
仁所以包三者,盖义礼智皆是流动底物,所以皆从仁上渐渐推出。仁智、元贞,是终始之事,这两头却重。如坎与震,是始万物、终万物处,艮则是中间接续处。[28]
说“义礼智皆是流动底物”,即是把仁义礼智看作流行的事物,而流行是一个过程,一个渐渐起伏变化的过程;这一无尽的过程是由一系列不断延伸的单元所组成,每个单元都由开始、中间、结束构成内部三个阶段,或由生、长、遂、成构成内部四个阶段。一方面,每个单元的后续阶段都是由开始阶段渐渐衍生出来的;另一方面,每个单元中开始的阶段和终结的阶段更为重要。
味道问:“仁包义礼智,恻隐包羞恶、辞逊、是非,元包亨利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不知木如何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气。有生气,然后物可得而生;若无生气,则火金水皆无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时举。[29]
元是生气,元包亨利贞;仁是生意,仁包义礼智;木是生气,木包火金水。于是四德、五常、五行三者被看成是同一生气流行的不同截面而已。至于五常中的信、五行中的土,在这种看法中都被消解了实体意义,而起保障其他四者为实存的作用。这是另外的问题,不在这里讨论。
朱子说:
“仁”字须兼义礼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知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于春:春则生意之生也,夏则生意之长也,秋则生意之成也,冬则生意之藏也。自四而两,两而一,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又曰:“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而成终;犹元为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故不贞则无以为元也。”又曰:“贞而不固,则非贞。贞,如板筑之有干,不贞则无以为元。”又曰:“文言上四句说天德之自然,下四句说人事之当然。元者,乃众善之长也;亨者,乃嘉之会也。嘉会,犹言一齐好也。会,犹齐也,言万物至此通畅茂盛,一齐皆好也。利者,义之和处也;贞者,乃事之桢干也。‘体仁足以长人’,以仁为体,而温厚慈爱之理由此发出也。体,犹所谓‘公而以人体之’之‘体’。嘉会者,嘉其所会也。一一以礼文节之,使之无不中节,乃嘉其所会也。‘利物足以和义’,义者,事之宜也;利物,则合乎事之宜矣。此句乃翻转,‘义’字愈明白,不利物则非义矣。贞固以贞为骨子,则坚定不可移易。”铢。[30]
与中年的仁说不同,后期朱子更强调对仁的理解要合义礼智三者一起看,而这种四德兼看的方法要求与四季的看法相参照。如春夏秋冬四季不同,但夏秋冬都出于春起的生意,四季都是生意流行的不同阶段,即生、长、成、藏。本来,元亨利贞是生长收藏的性,不就是生长收藏的过程,而在这里,仁义礼智不像是性,而成了流行总体和过程本身。与四季类似,仁是仁的本体,礼是仁的节文,义是仁的断制,知是仁的分别,四德都出于仁,是仁的由始至终的不同阶段。于是,仁义礼智作为人事之当然,与元亨利贞作为天德之自然,成为完全同构的东西。虽然朱子并没有说人事四德即来源于自然天德,但他把这些都看成天地之化的法则或机轴。虽然生意流行与生气流行不一定就是一回事,但整体上看,两种说法应是一致的。
朱子下面的话讲得很有意味:
“今日要识得仁之意思是如何。圣贤说仁处最多,那边如彼说,这边如此说,文义各不同。看得个意思定了,将圣贤星散说体看,处处皆是这意思,初不相背,始得。……人之所以为人,其理则天地之理,其气则天地之气。理无迹,不可见,故于气观之。要识仁之意思,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今只就人身己上看有这意思是如何。才有这意思,便自恁地好,便不恁地干燥。……这不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有这个浑全流行物事。此意思才无私意间隔,便自见得人与己一,物与己一,公道自流行。须是如此看。孔门弟子所问,都只是问做工夫。若是仁之体段意思,也各各自理会得了。今却是这个未曾理会得,如何说要做工夫!且如程先生云:‘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上云:‘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恰似有一个小小底仁,有一个大大底仁。‘偏言则一事’,是小小底仁,只做得仁之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是大大底仁,又是包得礼义智底。若如此说,是有两样仁。不知仁只是一个,虽是偏言,那许多道理也都在里面;虽是专言,那许多道理也都在里面。”致道云:“如春是生物之时,已包得夏长、秋成、冬藏意思在。”曰:“春是生物之时,到夏秋冬,也只是这气流注去。但春则是方始生荣意思,到夏便是结里定了,是这生意到后只渐老了。”贺孙曰:“如温和之气,固是见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节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贺孙。[31]
朱子在这里特别强调要从气观仁,从气识仁,这种观、识是要把握仁的“意思”,而仁的意思就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朱子强调,这一浑然温和之气并非仅仅是仁的道德气息,而是指出此气就是天地阳春之气。值得注意的是,朱子也并非只是纯粹从气观仁,也同时从理观仁,故说了“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后,即说“其理便是天地生物之心”。浑然温和之气之中有理,此理即天地生物之心。人的存在本来是理气合一、浑然流行的,而现实的人必须自觉地在自己身上体现这种浑然流行,培养此种德性。如果在自家身上能体现这种仁的意思,使这个意思遍润己身,这个意思便能无间隔地流行于人己人物之间。如叶贺孙和赵致道所言,温和之气可以见仁,而温和之气的流行(流注)自然有节文(礼),自然得宜(义),自然明辨(智)。
或问《论语》言仁处。曰:“理难见,气易见。但就气上看便见,如看元亨利贞是也。元亨利贞也难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时尽是温厚之气,仁便是这般气象。夏秋冬虽不同,皆是阳春生育之气行乎其中。故‘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如知福州是这个人,此偏言也;及专言之,为九州安抚,亦是这一个人,不是两人也。故明道谓:‘义礼智,皆仁也。若见得此理,则圣人言仁处,或就人上说,或就事上说,皆是这一个道理。’正叔云:‘满腔子是恻隐之心。’”曰:“仁便是恻隐之母。”又曰:“若晓得此理,便见得‘克己复礼’,私欲尽去,便纯是温和冲粹之气,乃天地生物之心。其余人所以未仁者,只是心中未有此气象。《论语》但云求仁之方者,是其门人必尝理会得此一个道理。今但问其求仁之方,故夫子随其人而告之。……南升。(疑与上条同闻。)[32]
照这里所说,天地生发之理是看不见的,但可以就天地之生气来看,元亨利贞是气,是可见的;更容易看的是四季,春夏秋冬便是气的流行。在这里,四季的四个阶段的更换不是最重要的,四季中贯通的生育之气才是最重要的。这个生气便是仁。这里所说的“私欲尽去,便纯是温和冲粹之气”,显然是指人的身心而言:朱子认为,这种人在私欲尽去后达到的温和之气,也就是天地生物之心、天地生物之气,这是以人合天的状态。这些都体现了朱子以温和之气为仁的思想。
可见,在朱子哲学中,仁义礼智四德不仅仅是性理,在不同的讨论中,四德也具有其他的意义,如与存于中不同的心德说,如意思说所表达的道德信息说,如宇宙论意义的生气流行说,等。就天地造化而言,仁既是理,也是气;就人心性命而言,仁既是性,也是心。虽然仁的这几层意义是不同的,但它们之间不一定是互相否定的,而是可以共存的。
总之,上述仁论与四德论的讨论,使得朱子思想中心、性、气的关系不再像以前人们所理解的那么简单,其中包含的哲学意义值得作更深入的探讨。朱子的这些思想,使我们得以了解朱子不仅发挥继承了伊川的理学思想,也与明道的仁学思想有其内在的联系。对朱子仁学的思想,以往整体研究不够,需要更深入地分疏和诠释。从一定的意义上来看,朱子的哲学思想体系可以从两个基本方面来呈现:一是理学,一是仁学。从理学的体系去呈现朱子哲学,是我们以往关注的主体;从仁学的体系去呈现朱子思想,以往甚少。如果说理气是二元分疏的,则仁在广义上是包括理气的一元总体。在这一点上,说朱子学总体上是仁学,比说朱子学是理学的习惯说法,也许更能凸显其儒学体系的整体面貌。
朱子四德说续论
陈来
在《朱子思想中的四德论》一文中,我们主要是利用《朱子语类》卷六《仁义礼智等名义》的资料来说明朱子的关于仁义礼智四德(以及与之关联的元亨利贞四德)的思想。[1]这里,我们依据《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下简称《文集》)、《朱子语类》(下简称《语类》)的其他材料来进一步讨论其四德说,主要使用《文集》中的《元亨利贞说》、《周礼三德说》、《仁说》,《玉山讲义》及相关讨论,以及《语类》及《周易本义》论《易·乾卦》的资料。
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七有《元亨利贞说》,文云:
元亨利贞,性也;生长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长、以利收、以贞藏者,心也。仁义礼智,性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以仁爱、以义恶、以礼让、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正谓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言天之付与万物者,谓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为心”,亦谓此也。[2]
《元亨利贞说》写于朱子四十二岁前后,属于其前期思想。朱子当时以元亨利贞四者为性,与生长收藏相对待;这和以仁义礼智为性、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为情,是相对应的也是一致的。元亨利贞是天地之性,天地之化以天地之性为根据,而实现生长收藏的过程。同理,仁义礼智是人之性,人心之动以人之性为根据,而发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情感。这种分析体现了朱子当时对性情之辨的重视。在这种话语中,元亨利贞只是性,与生长收藏的现实过程被严格分别开来,生长收藏相当于情,也就是用。
不久,朱子又有《仁说》之作,其中说:
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请试详之。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块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3]
依朱子这里的看法,仁是“人心”之德,元亨利贞是“天地之心”之德,这是明确把仁和元、亨、利、贞都作为“德”。就心之德作为性而言,“元”包“亨利贞”,这是从体上来看的。朱子还认为,四季运行是天地之化的过程,是用,而天地之德则是运行过程的内在根据。从天地运行的大用着眼,春生之气贯通于春夏秋冬的有序连接,无所不通。如果从人的方面看,就心之徳言,“仁”包“义礼智”;就四德的发用言,恻隐贯通于爱恭宜别四种情感。在这种论述中,春生之气相当于恻隐,都属用的层面,在这个意义上,运行、流行是就“用”言,而仁义礼智或元亨利贞是“体”,是“性”,是无所谓流行的。既然性无所谓流行,这说明前期朱子思想在性情体用之辨的意识主导下,不采用“流行”一类的观念解释四德。我们在前文已说明,以“流行”的观念解释四德关系,见于朱子后期思想,而“运用流行”的哲学观念,本质上,是和气的哲学思维分不开的。从哲学上看,还应当注意的是,在性和情两者的分析之外,还有一种总体的了解,这就是所谓“以元生、以亨长、以利收、以贞藏者,心也”,心不是本性、体,也不是过程、用,而是包涵体用的、存在与活动的总体。
二
《文集》卷七四有《玉山讲义》,是朱子晚年六十五岁经过江西玉山时所作,其中论述了四德说。此讲义可分为三部分,其第一部分云:
时有程珙起而请曰:“《论语》多是说仁,《孟子》却兼说仁义。意者夫子说元气,孟子说阴阳,仁恐是体,义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异,固所当讲。然今且当理会何者为仁?何者为义?晓此两字义理分明,方于自己分上有用力处,然后孔孟之言有同异处可得而论。如其不晓,自己分上元无工夫,说得虽工,何益于事?且道如何说个‘仁义’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个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为体,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于此。韩文公云‘人之所以为性者五’,其说最为得之。却为后世之言性者多杂佛老而言,所以将‘性’字作知觉心意看了,非圣贤所说‘性’字本指也。”[4]
程珙的问题很有意思,他说孔子只说仁,不说仁义,因为孔子说仁是讲元气;而孟子说仁义,是讲阴阳二气。这个讲法其实合于朱子晚年以仁为生气流行贯通四者的思想。程珙还把仁义的关系理解为体用的关系。朱子认为他讲的不分明,强调“仁义”二字的前提先要从人性论上去理解。天赋予每个所生之物一个道理,人身得到的这个道理便是性,性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五者。所以这五种都是人性的道理。就五者都是人性的内容而言,彼此并无体用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不能说仁是体、义是用。
其第二部分云:
五者之中,所谓信者是个真实无妄底道理,如仁义礼智皆真实而无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须说,只“仁义礼智”四字于中各有分别,不可不辨。盖仁则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裁割底道理,礼则是个恭敬撙节底道理,智则是个分别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于人心,乃是性之本体。方其未发,漠然无形象之可见;及其发而为用,则仁者为恻隐,义者为羞恶,礼者为恭敬,智者为是非,随事发见,各有苗脉,不相淆乱,所谓情也。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谓之端者,犹有物在中而不可见,必因其端绪发见于外,然后可得而寻也。盖一心之中,仁义礼智各有界限,而其性情体用又自各有分别,须是见得分明。[5]
“仁是温和慈爱的道理”,道理即理,道理之在我者即性,说明这里是把“仁”作为理看待的。所谓温和慈爱的道理,与《四书章句集注》所说“仁者爱之理”[6]的意思相通,也就是说,“仁”是发为慈爱的内在根据。慈爱是已发而为用的,属于发见的层次;仁则是体,是未发的层次。义、礼、智皆然。仁义礼智之间的分别,亦表现在他们各自的发见不同,仁发为慈爱,义发为断制,礼发为恭敬,智发为是非。“仁”是发为慈爱的根据道理,“义”是发为断制的根据道理,“礼”是发为恭敬的根据道理,“智”是发为是非的根据道理。但朱子晚年并不简单直截地说仁是恻隐之理,义是羞恶之理,礼是恭敬之理,智是是非之理,而常常说“仁是个温和慈爱底道理”,“义则是个断制截割底道理”等,表示朱子的这种“道理”的表述还是有其特殊意义,这就是,朱子这时已经常常用“意思说”来表达其四德说了(详见前文)。此外,在这种说法中,朱子所体现的态度是即用明体、即用论体、不可离用说体,这与体用分析的说法有别。
第三部分云:
然后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见得“仁义”两字是个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实不过于一阴一阳而已。于此见得分明,然后就此又自见得“仁”字是个生底意思,通贯周流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体也,义则仁之断制也,礼则仁之节文也,智则仁之分别也。正如春之生气贯彻四时,春则生之生也,夏则生之长也,秋则生之收也,冬则生之藏也。故程子谓“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正谓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专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义礼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义,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于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个“义”字,但于一理之中分别出来耳。其又兼言礼智,亦是如此。盖礼又是仁之着,智又是义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尝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论体用亦有两说,盖以仁存于心而义形于外言之,则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而以仁义相为体用。若以仁对恻隐、义对羞恶而言,则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发、已发相为体用。若认得熟、看得透,则玲珑穿穴、纵横颠倒无处不通,而日用之间,行着习察,无不是着功夫处矣。”[7]
这里就用了“意思说”,强调仁是生的意思,即仁作为“生意”的思想。朱子认为仁之生意通贯周流于仁义礼智四者之中,初看起来,仁之生意贯通的讲法似是指仁的普遍性,而以四者为特殊性;其实这种“通贯周流”的讲法与普遍性体现为特殊性的思维还是有所不同的,要言之,“通贯周流”是气论的表达方式。分别而言,仁是仁之生意的本体的表现,义是仁之生意表现为断制的阶段,礼是仁之生意的节文,智是仁之生意表现为分别。朱子认为,这正如春之生气贯彻四时之中一样,朱子用这种周流贯通之气的流行论,发挥了程颢的生意说与程颐仁“包”四德的观念,使得“仁”也成为或具有流行贯通能力的实体。这样的仁,既不是内在的性体,又不是外发的用,而是兼体用而言的了。气论的思维在这里也明显发生作用。这些就与前期的思想有所不同了。朱子的这一思想与程珙所提的“仁是元气”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元气不如生气说得更清楚,“元气”必须落在“生”字上讲,这是二程到朱子的仁说所一直强调的。关于礼是仁之著,智是义之藏的说法,以及仁义的体用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结合《语类》再予讨论。
由此可见,《玉山讲义》主要包含两个思想,一个是四德与四端的未发已发说,一个是仁之生意流行于四德说。在稍后答陈器之书中,朱子复述了这两点,并对“对立成两”、“仁智终始”等问题做了进一步阐述。
三
《文集》卷五八载《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该信可分为四节,其开首言:
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孔门未尝备言,至孟子而始备言之者,盖孔子时性善之理素明,虽不详著其条而说自具。至孟子时,异端蜂起,往往以性为不善,孟子惧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浑然全体,则恐其如无星之秤、无寸之尺,终不足以晓天下,于是别而言之,界为四破,而四端之说于是而立。[8]
这是解释为什么孔子不必讲四端,而孟子必须讲四端。朱子指出,从整体上看,性即太极;如果从具体内容上看,性具众理;性中的众理以仁义礼智四者为主,孟子发明四端之说即是发明仁义礼智之性,是为了更好地证明性善说。此为第一节。
盖四端之未发也,虽寂然不动,而其中自有条理,自有间架,不是儱侗都无一物,所以外边才感,中间便应。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而恻隐之心于是乎形。如过庙、过朝之事,感则礼之理便应,而恭敬之心于是乎形。盖由其中间众理浑具,各各分明,故外边所遇,随感而应,所以四端之发,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为四,以示学者,使知浑然全体之中而粲然有条若此,则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发也,所谓浑然全体,无声臭之可言,无形象之可见,何以知其粲然有条如此?盖是理之可验,乃依然就他发处验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虽无形,而端的之发最可验。故由其恻隐,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恶,所以必知其有义;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礼;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无是理于内,则何以有是端于外?由其有是端于外,所以必知有是理于内,而不可诬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是则孟子之言性善,盖亦溯其情而逆知之耳。[9]
此为第二节。性虽然是太极,但其中自有条理,即包含仁义礼智各不同的理。这些理本来是内在心中的,当一定的外事来感时,一定的理便有所应,于是便有四端之发。与性情对言的已发未发说有所不同,这里强调从已发到未发需要“外感”作为媒介、中介。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则仁之理便“应”,而恻隐之心于是乎“形”。“感—应—形”的分别和联系是与朱子“心具众理而应万事”的思想一致的。朱子在这里强调性中自有条理,不同的外感引起不同的性理的响应,从而表达出不同的情。朱子论心的思想在前期注重已发未发,后期更重视具众理而应万事。由外证内,以情证性,溯用知体,这是朱子立足于四端而证明四德的方法。
仁义礼智既知得界限分晓,又须知四者之中仁义是个对立底关键。盖仁,仁也,而礼则仁之著;义,义也,而智则义之藏。犹春夏秋冬虽为四时,然春夏皆阳之属也,秋冬皆阴之属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是知天地之道不两则不能以立,故端虽有四,而立之者则两耳。仁义虽对立而成两,然仁实贯通乎四者之中,盖“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犹春夏秋冬虽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则春之生也,夏则春之长也,秋则春之成也,冬则春之藏也。自四而两,自两而一,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是天地之理固然也。[10]
朱子指出,天地之道不两则不能以立,“两”就是对立的两个要素,就是说任何事物,其内部都必有两个对立的要素,事物才能存在。从这个意义来说,四端中应有两个使整体得以存在的要素,这两个要素就是仁和义。在这种理解下,仁和礼归于仁,礼是仁的显发;义和智归于义,智是义的退藏。这个思想我们在后面还会提到。朱子又指出,仁和义对立而成两,符合事物存在发展的辩证法,但四者又贯通着“一”,“一”使事物获得整体性和连续性,这个一就是仁。四归于二,二归于一,于是仁成为四者最终统一的根源。这是第三节。
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盖冬者藏也,所以始万物而终万物者也。智有藏之义焉,有终始之义焉,则恻隐、羞恶、恭敬是三者皆有可为之事,而智则无事可为,但分别其为是为非尔,是以谓之藏也。又恻隐、羞恶、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则有两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终始万物之象,故仁为四端之首而智则能成始能成终,犹元气虽四德之长,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盖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则不能发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际之间,乃万化之机轴,此理循环不穷,吻合无间。程子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者,此也。[11]
这最后一节是讲智的意义,由于朱子把四德的关系看成是流行终始的关系,于是不仅突出了仁,也突出了智。朱子认为元亨利贞流行不已,贞是前一个过程的结束,又孕育了新的过程开始,故言元生于贞。朱子认为仁义礼智和元亨利贞相同,贞元之际与仁智之际相同,智和贞一样,具有成终成始的地位,仁智之交,就是旧的流行结束而新的流行开始。《语类》也说:
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贞亦重,以明终始之义。非元则无以生,非贞则无以终,非终则无以为始,不始则不能成终矣。如此循环无穷,此所谓“大明终始”也。大雅。[12]
这种四德论的讲法是由于把仁义礼智与元亨利贞完全对应所引起的,宇宙论的元亨利贞模式深刻影响了他对仁义礼智四德的理解。在这一节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此即把“元”说为“元气”。于是,朱子对于元或仁的说法,越来越不就性、理而言,而更多就具有生成形态的气而言了。
第二节所说的已发未发,涉及仁义体用的问题。前面说到,《玉山讲义》的第三部分言:“若论体用亦有两说,盖以仁存于心而义形于外言之,则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而以仁义相为体用。若以仁对恻隐义对羞恶而言,则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发、已发相为体用。若认得熟、看得透,则玲珑穿穴、纵横颠倒无处不通,而日用之间,行著习察,无不是著功夫处矣。”仁义礼智四德作为性理,为未发,为体;恻隐羞恶四端为情,为已发,为用。分言之,仁为体而恻隐为用,义为体而羞恶为用,这就是已发未发相为体用。朱子亦认为,孟子所说仁人心,义人路,则是以仁存于心,义形于外而言,是另一种体用的对待。
四
《文集》卷六七有《周礼三德说》,该文虽然不是讨论四德之说,但其中讨论周礼三德说涉及的对德、行的理解也值得注意。文之开首云:
或问:师氏之官,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何也?曰:至德云者,诚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则天人性命之理、事物当然之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术也。敏德云者,强志力行、畜德广业之事;“行”则理之所当为,日可见之迹也。孝德云者,尊祖爱亲,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恶,则以得于己者笃实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恶,而自不忍为者也。(至德以为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为行本,司马温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恶,则赵无愧、徐仲车之徒是已。)凡此三者,虽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资质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专务其一而可以为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见其相须为用而不可偏废之意。盖不知至德,则敏德者散漫无统,固不免乎笃学力行而不知道之讥。然不务敏德而一于至,则又无以广业,而有空虚之弊。不知敏德,则孝德者仅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于神明。然不务孝德而一于敏,则又无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陈备举而无所遗,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资、精粗两尽而不倚于一偏也。[13]
“三德”、“三行”之说出于《周礼·地官·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14]这是古代德行论的早期表达。
朱子对三德、三行作了明确的哲学的、伦理学的解说。在朱子看来,以三种德行教国子,至德是指心而言,是关于正心诚意的内心修养。所谓至德以为道本,是说至德是掌握性命之理、践行当然之则、实行治国平天下之术的根本与基础,突出了德性对哲学理解、道德实践、政治施行的根本意义,强调心徳是道术的根本基础。强志力行,即《礼记·儒行》第一条所说的强学力行;一切行为都是由心志而发,人能强化心志,力行理所当为,使心志在行为事迹上表现出来,这是敏德。所谓敏德以为行本,是指由心志落实到行为是德行的一般特性。照朱子的这个说法,从德行论来看,可以说正心诚意是根本的德行,称为至德;强志力行是一般意义的德行,称为敏德;尊祖爱亲是专指孝的特殊德行,称为孝德。三徳可以说区别了根本德行、一般德行、特殊德行。
以三德教国子,说明这是一种道德教育,其目的是培养成人。但把国子培养为成人,必须使他们同时培养三德,不可偏专其中之一。朱子认为三德互相补充、互相需要,“未有专务其一而可以为成人者也”,也就是说三德具有统一性。没有至德,敏德只能笃行,而没有方向,不能知“道”;没有敏德,至德就会流于空洞,无法具体落实,也无法拓宽事业;不落实到孝德,敏德就失去基础。至德是方向,敏德是分殊,孝德是基础。
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何也?曰:德也者,得于心而无所勉者也;行则其所行之法而已。盖不本之以其德,则无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实之以其行,则无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进。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继之,则虽其至末至粗亦无不尽,而德之修也不自觉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于至德、敏德,则无与焉。盖二者之行,本无常师,必协于一,然后有以独见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预言也。唯孝德则其事为可指,故又推其类而兼为友顺之目以详教之,以为学者虽或未得于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于心焉,则进乎德而无待于勉矣。况其又能即是而充之,以周于事而溯其原,则孰谓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学之学也;三行之教,小学之学也,乡三物之为教也亦然,而已详。[15]
三德之教和三行之教,涉及对德与行的分别。在对教三行的解释上,朱子解释了什么是德、行,他说“德也者,得于心而无所勉者也;行则其所行之法而已”。这是说,“德”是得于心的状态或性质,“行”是对规范的实行。朱子认为,德和行互相支持、互相连接,不以内心之德为本,就达不到自得,行为也不能自修;心之德不落实在行为表现出来,心难以持循,心德也不能进步。朱子也指出,人有时未得于心,但能勉而行之,在这种状态下不能说德在心中。但如此勉而行之,久而久之,合乎道德的行为的不断实行便可使人达到“得于心”,即促使德在心中形成,这时的行为便是从心中之德出发,不待勉强了。这是朱子对德性形成的一种看法。
朱子还说过:
耳之德聪,目之德明,心之德仁,且将这意去思量体认。泳。[16]
聪、明是耳目的根本属性,仁是心的根本属性,德即指根本属性而言。
百行皆仁义礼智中出。节。[17]
百行是行为,仁义礼智是本性,这是强调一切行为都是发自于内在的本性,也体现了朱子德性论强调性理的特色。
五
《周易·说卦》云:“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18]此后,儒学思想家常常依此思路,努力把仁义与阴阳、刚柔对应起来,以建立宇宙论的统一性说明。
问仁义礼智体用之别。曰:“自阴阳上看下来,仁礼属阳,义智属阴;仁礼是用,义智是体。春夏是阳,秋冬是阴。只将仁义说,则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若将仁义礼智说,则春,仁也;夏,礼也;秋,义也;冬,智也。仁礼是敷施出来底,义是肃杀果断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脏有许多事,如何见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解者多以仁为柔,以义为刚,非也。却是以仁为刚,义为柔。盖仁是个发出来了,便硬而强;义便是收敛向里底,外面见之便是柔。”僴。[19]
理学倾向于把“阴阳”作为普遍的哲学分析方法。按照这种分析,如果把仁义礼智四者归为阴阳两类,那么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何者为阳,何者为阴?朱子的主张是,仁和礼属于阳,义和智属于阴。在他看来,以流行的次序而言,是仁、礼、义、智,也就是仁相当于春,礼相当于夏,义相当于秋,智相当于冬。因此若要把四德分为阴阳的话,仁、礼为阳,义、智为阴;正如要把一年四季分为阴阳的话,以春夏为阳,以秋冬为阴。反过来说,如果把四季分为仁义二者,则以春夏为仁,以秋冬为义。这种思维是汉代以来阴阳气论的影响下形成的。
不过,这样一来,仁、礼、义、智的次序便和习惯所用的仁、义、礼、智的顺序有所不同了,朱子回答学生的疑问:
问:“孟子说仁义礼智,义在第二;《太极图》以义配利,则在第三。”曰:“礼是阳,故曰亨。仁义礼智,犹言东西南北;元亨利贞,犹言东南西北。一个是对说,一个是从一边说起。”夔孙。[20]
按朱子的理解,如同一个圆圈,顺着圆圈的次序是流行的次序,即仁、礼、义、智的排序。以流行言,仁对应元,礼对应亨,义对应利,智对应贞。如果不顺着圆圈,而以南北相对,东西相对,这样的次序就不是流行的次序,而是对待的次序,这就是仁、义、礼、智的排序。
问:“‘元亨利贞’,《乾》之四德;仁义礼智,人之四德。然亨却是礼,次序却不同,何也?”曰:“此仁礼义智,犹言春夏秋冬也;仁义礼智,犹言春秋夏冬也。”铢。[21]
这也是说明四德有两种排序。仁、礼、义、智的顺序是合乎元气流行的自然次序,这样的元亨利贞、仁义礼智都是被用气的流行来刻划的东西了,也就成为他所说的“流行之统体”了。
中国哲学中与“阴阳”分析相配合的是“刚柔”的分析。按上面的说法,仁属于阳,义属于阴,那么仁义与刚柔又如何对应呢?在一般人看来,仁有柔软的意思,应当属柔,不应当属刚,而朱子却认为仁应当属刚,不属于柔。如其晚年《答董叔重》书论此最明:
(董问)阴阳以气言,刚柔则有形质可见矣。至仁与义,则又合气与形而理具焉。然仁为阳刚,义为阴柔,仁主发生,义主收敛,故其分属如此。或谓杨子云“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盖取其相济而相为用之意。
(朱答)仁体刚而用柔,义体柔而用刚。[22]
汉代的扬雄以仁为柔,以义为刚,这是讲得通的。而朱子与之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是来自朱子从宇宙生化论讲四德,主张以发生论仁,以收敛论义,由于是以收敛为阴柔,所以便以发生为阳刚了。仁是发生原则,故仁属阳刚。值得注意的是,董铢在这里提出“仁义”是“合气与形而理具焉”,按这个说法,仁、义似乎不仅仅是性理,而是实存的气形统一整体或总体,其中具有理。当然,也可以说理气合而后生人,而有仁义礼智之性。这个说法应该是顺就朱子的说法而来,故朱子没有加以评论。
朱子曾与袁枢反复辨析阴阳刚柔之义,其《答袁机仲》书云:
凡此崎岖反复,终不可通,不若直以阳刚为仁、阴柔为义之明白而简易也。盖如此,则发生为仁、肃杀为义,三家之说皆无所牾,肃杀虽似乎刚,然实天地收敛退藏之气,自不妨其为阴柔也。
……又读来书,以为不可以仁义礼智分四时,此亦似太草草矣。夫五行五常五方四时之相配,其为理甚明而为说甚久,非熹独于今日创为此论也。[23]
这里朱子自己界定得很清楚,发生为刚,肃杀为柔,肃杀收敛退藏应属于阴柔,义为肃杀退藏,故当属于阴柔。故阳刚为仁,阴柔为义。
而朱子的这一说法,遭到了不少质疑,引发了朱子与这些质疑的辩难。如其《答袁机仲别幅》云:
……来喻以东南之温厚为仁、西北之严凝为义,此《乡饮酒义》之言也。然本其言虽分仁义,而无阴阳柔刚之别,但于其后复有阳气发于东方之说,则固以仁为属乎阳,而义之当属乎阴,从可推矣。来谕乃不察此而必欲以仁为柔、以义为刚,此既失之,而又病夫柔之不可属乎阳、刚之不可属乎阴也,于是强以温厚为柔、严凝为刚。又移北之阴以就南,而使主乎仁之柔;移南之阳以就北,而使主乎义之刚,其于方位气候悉反易之,而其所以为说者,率皆参差乖迕而不可合。又使东北之为阳、西南之为阴,亦皆得其半而失其半。愚于图子已具见其失矣。盖尝论之:阳主进而阴主退,阳主息而阴主消,进而息者其气强,退而消者其气弱,此阴阳之所以为柔刚也。阳刚温厚居东南,主春夏,而以作长为事;阴柔严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敛藏为事。作长为生,敛藏为杀,此刚柔之所以为仁义也。以此观之,则阴阳刚柔仁义之位岂不晓然?而彼杨子云之所谓“于仁也柔,于义也刚”者,乃自其用处之末流言之,盖亦所谓阳中之阴、阴中之阳,固不妨自为一义,但不可以杂乎此而论之尔。[24]
袁枢并不反对仁为阳,义为阴,但反对以仁为刚,以义为柔,而主张温厚为柔,严凝为刚,故仁为柔为阳,义为刚为阴。朱子坚持仁属于阳刚,义属于阴柔,阳刚主生长,阴柔主敛藏。他认为杨雄所说的“于仁也柔,于义也刚”,不是从本体上说的,而是从发用上说的,所以朱子主张“仁体刚而用柔,义体柔而用刚”,认为这样就可以全面地解决这个问题了。朱子又说:
前书所论仁义礼智分属五行四时,此是先儒旧说,未可轻诋。今者来书虽不及之,然此大义也,或恐前书有所未尽,不可不究其说。盖天地之间,一气而已,分阴分阳,便是两物,故阳为仁而阴为义。然阴阳又各分而为二,故阳之初为木为春为仁,阳之盛为火为夏为礼,阴之初为金为秋为义,阴之极为水为冬为智。盖仁之恻隐方自中出,而礼之恭敬则已尽发于外,义之羞恶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则已全伏于中,故其象类如此,非是假合附会。若能默会于心,便自可见。“元亨利贞”,其理亦然。《文言》取类,尤为明白,非区区今日之臆说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属,而土居中宫,为四行之地、四时之主,在人则为信、为真实之义,而为四德之地、众善之主也。五声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虫,其分放此。盖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若不见得,则虽生于天地间,而不知所以为天地之理,虽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为人之理矣。故此一义切于吾身,比前数段尤为要紧,非但小小节目而已也。[25]
照此说法,天地一气,分阴分阳,阳为仁、阴为义;阳中又分为二,即春仁和夏礼;阴中亦分为二,即秋义和冬智。一气分为阴阳,并无先后,而阳再分为二,春仁在先,夏礼在后;阴之分二亦然,秋义在先,冬智在后,这是一气流行的次序。而人性的仁义礼智之间及其发作为情,并无先后。总之,论元亨利贞、仁义礼智都不能离开一气阴阳四时五行这些宇宙论要素,从而使得元亨利贞、仁义礼智也成为与一气阴阳纠缠在一起的流行实体了。
六
朱子《周易本义》论元亨利贞四德:
盖尝统而论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畅茂,利则向于实也,贞则实之成也。实之既成,则其根蒂脱落,可复种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环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间,生气流行,初无间断,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统天也。[26]
这是把元亨利贞四德作为“物”的发生成长的不同阶段来理解的,同时,又说明这四个连续无间段的流行,是生气流行,元就是生气,所以四者的连续流行就是体现了“元”贯通四者而作为天道的统一性。
以“生”字说仁,生自是上一节事。当来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须要自体认得。泳。[27]
当来即当初。以生说仁,把生作为天地间的普遍原理,这是“人生而静以上”事,即生化论属于宇宙论之事,不是人生论之事。因此宇宙论对于人生论来说是“上一节事”。人之生亦接受天地之生理,人生而静以下此生理即体于人而为仁之理,而人生的目标就是要体认从天地接受的生意生理,因为这是人的生命的根源。
《语类》卷六八论乾卦四德:
文王本说“元亨利贞”为大亨利正,夫子以为四德。梅蘂初生为元,开花为亨,结子为利,成熟为贞。物生为元,长为亨,成而未全为利,成熟为贞。节。[28]
这是以元亨利贞为生长成熟,而不是以元亨利贞为性。
致道问“元亨利贞”。曰:“元是未通底,亨、利是收未成底,贞是已成底。譬如春夏秋冬,冬夏便是阴阳极处,其间春秋便是过接处。”恪。[29]
这是以元亨利贞为生长成熟之外,又以元亨利贞对应春夏秋冬。
《乾》之四德,元,譬之则人之首也;手足之运动,则有亨底意思;利则配之胸脏;贞则元气之所藏也。又曰:“以五脏配之尤明白,且如肝属木,木便是元;心属火,火便是亨;肺属金,金便是利;肾属水,水便是贞。”道夫。[30]
这是以元亨利贞对木火金水。这就使元亨利贞成为更普遍的模式了。
“元亨利贞”,譬诸谷可见,谷之生,萌芽是元,苗是亨,穟是利,成实是贞。谷之实又复能生,循环无穷。德明。[31]
这也是以物之生长遂成体现元亨利贞。以上都是以元亨利贞为物之形态或阶段。
以物之生长收藏说元亨利贞四德之义,始于程伊川,朱子亦明言之:
“元亨利贞”,理也;有这四段,气也。有这四段,理便在气中,两个不曾相离。若是说时,则有那未涉于气底四德,要就气上看也得。所以伊川说:“元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遂;利者,物之实;贞者,物之成。”这虽是就气上说,然理便在其中。伊川这说话改不得,谓是有气则理便具。所以伊川只恁地说,便可见得物里面便有这理。若要亲切,莫若只就自家身上看,恻隐须有恻隐底根子,羞恶须有羞恶底根子,这便是仁义。仁义礼智,便是元亨利贞。孟子所以只得恁地说,更无说处。仁义礼智,似一个包子,里面合下都具了。一理浑然,非有先后,元亨利贞便是如此,不是说道有元之时,有亨之时。渊。[32]
有这四段,即指生长遂成四个阶段,朱子在这里以生长遂成四阶段为气,而以元亨利贞为生长遂成的现实过程所体现和依据的理。按前面所述多见以元亨利贞为气这类的说法,而以元亨利贞四德为理,以生长收藏四段为气,此说似不多见。照这个说法,以生长遂成说元亨利贞,是就气上说,而理在气中。但朱子特别强调,程颐不从理上说元亨利贞,而从物上说,并没有错,他甚至声称程颐此说不可更改,认为讲气讲物,理便在其中了。此中理气的分析是很清楚的。这里所说的从气上看或从物上看的思想,不是从性、从理、从体上看,而都是近于从总体上看的方法。
“元亨利贞”无断处,贞了又元。今日子时前,便是昨日亥时。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这里方感得生气,他自有个小小元亨利贞。渊。[33]
这里又把元亨利贞说成四阶段连接循环,元是生气发生的阶段。元之前是贞,贞之后是元,循环无间断处。
气无始无终,且从元处说起,元之前又是贞了。如子时是今日,子之前又是昨日之亥,无空阙时。然天地间有个局定底,如四方是也;有个推行底,如四时是也。理都如此。元亨利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是有此气;所以有此气,便是有此理。故《易传》只说“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不说气,只说物者,言物则气与理皆在其中。伊川所说四句自动不得,只为“遂”字、“成”字说不尽,故某略添字说尽。高。[34]
“局定底”与“推行底”,与朱子说《易》的方法“定位底”和“流行底”的分别相近,显然,元亨利贞是属于“流行底”道理。由于伊川论元亨利贞是指“物”之生、长、遂、成言,故朱子说元亨利贞“就物上看亦分明”,他甚至认为《易传》也是就“万物”而言四德,就万物之生长遂成的阶段言元亨利贞。这种“就物上说”的方法并没有忽视理和气,因为言物则气和理皆在其中。这似乎是说,元亨利贞四德的论法可以有三种,物上说的方法如生长遂成说,气上说的方法如春夏秋冬说,理上说的方法即元亨利贞说。这三者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说明的。
朱子又说:
以天道言之,为“元亨利贞”;以四时言之,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为仁义礼智;以气候言之,为温凉燥湿;以四方言之,为东西南北。节。[35]
这就把元亨利贞之理更普遍化了,就天道言,即就宇宙普遍法则而言,是元亨利贞;这样普遍法则理一而分殊,有不同的体现,如在四时体现为春夏秋冬,在人道体现为仁义礼智,在气候体现为温凉燥湿,在四方体现为东南西北。温凉燥湿又说为温热凉寒:“温底是元,热底是亨,凉底是利,寒底是贞。”[36]这实际上是用四季的气候变化循环说元亨利贞。在这个意义上,元亨利贞如同理一分殊,已经成为一种论述模式。
“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此段只于《易》“元者善之长”与《论语》言仁处看。……“元者,善之长也”,善之首也。“亨者,嘉之会也”,好底会聚也。义者,宜也,宜即义也;万物各得其所,义之合也。“干事”,事之骨也,犹言体物也。看此一段,须与《太极图》通看。贺孙。[37]
《文言传》对元亨利贞的解释是就人事道德上说,朱子具体解释了什么是善之长,什么是嘉之会,什么是义之合,什么是事之干,但朱子对元亨利贞的解释并不是按这种方式进行的。朱子强调,根据二程的说法,对“元”的理解要与“仁”联系一起、贯通在一起。
光祖问“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曰:“元是初发生出来,生后方会通,通后方始向成。利者物之遂,方是六七分,到贞处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然发生中已具后许多道理,此专言也。恻隐是仁之端,羞恶是义之端,辞逊是礼之端,是非是智之端。若无恻隐,便都没下许多。到羞恶,也是仁发在羞恶上;到辞逊,也是仁发在辞逊上;到是非,也是仁发在是非上。”问:“这犹金木水火否?”曰:“然。仁是木,礼是火,义是金,智是水。”贺孙。[38]
按朱子的解释,元是初发生,则这就不是从理上看,而是从气上看或从物上看。其次,发生后必然向会通发展,会通后必然向成熟发展。就四个阶段的不同展开说,这是“偏言”的角度。就四个阶段贯穿着作为统一性的“元”而言,这是“专言”的角度。专言包四者,朱子的解释是,一方面,元中具亨利贞许多道理,亨利贞都是元的发现的不同形态,同理,仁不仅发在恻隐,羞恶、辞让、是非都是仁之发。
《语类》又载:
曾兄亦问此。答曰:“元者,乃天地生物之端。《乾》言:‘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知元者,天地生物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则生意之长,在利则生意之遂,在贞则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这意思。仁本生意,乃恻隐之心也。苟伤着这生意,则恻隐之心便发。若羞恶,也是仁去那义上发;若辞逊,也是仁去那礼上发;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发。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义礼智!”卓。[39]
元是生物的发端,元是生意的开始,亨是生意的长,利是生意的遂,贞是生意的成。于是生长遂成就是“生意”的生长遂成。这都不是从理上看的方法,也说明,四德的意义在朱子思想中并不仅仅是理。
《周易本义》云: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则为仁,而众善之长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于时为夏,于人则为礼,而众美之会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而得其分之和。贞者,生物之成。实理具备,随在各足,故于时为冬,于人则为智,而为众事之干。干,木之身,枝叶所依以立者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以仁为体,则无一物不在所爱之中,故足以长人。嘉其所会,则无不合礼。使物各得其所利,则义无不和。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谓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为事之干。[40]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刚以体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过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纯者,不杂于阴柔。粹者,不杂于邪恶。盖刚健中正之至极而精者,又纯粹之至极也。或疑乾刚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间,本一气之流行,而有动静耳。以其流行之统体而言,则但谓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动静分之,然后有阴阳刚柔之别也。[41]
元既是生物之始,又是天地之德,作为生物之始,亦体现为四时之春;作为天地之德,亦体现为人道之仁。可见,元亨利贞四德既是论生物过程与阶段,又是论天地之德,于是既体现为四时春夏秋冬,又体现为人道的仁义礼智。“流行之统体”就是兼体用的变易总体,元亨利贞是此一统体不同流行的阶段及其特征。
虽然可以说,对于四德而言,朱子的讨论包含了三种分析的论述,即“从理看”,“从气看”,“从物看”。但总起来看,应当承认,朱子的思想中不断发展出一种论述的倾向,就是不再把元亨利贞仅仅理解为理,而注重将其看作兼赅体用的流行之统体的不同阶段,如将其看作元气流行的不同阶段。由于天人对应,于是对仁义礼智的理解也依照元亨利贞的模式发生变化,即仁义礼智不仅仅是性理,也被看作生气流行的不同发作形态。这导致朱子的四德论在其后期更多地趋向“从气看”、“从物看”、从“流行之统体”看,使得朱子的哲学世界观不仅有理气分析的一面,也有流行统体的一面,而后者更可显现出朱子思想的总体方向。
世俗化的朱子:朱子学术的世俗关怀及其时代意义
——以“礼”学为例
朱杰人
余英时先生在他的大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中说:“在一般哲学史或理学史的论述中,我们通常只看到关于心、性、理、气等等观念的分析与解说。至于道学家的政治思想与政治活动,则哲学家往往置之不论,即使在涉及他们的生平时也是如此。”[1]他指出,这一现象带来的一个后果是造成了一种“普遍的印象”,即儒学进入南宋以后便转而内向了,即儒学的重点在“内圣”而不是在“外王”。但是,余先生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他认为以朱熹和陆九渊为代表的南宋理学家们“念兹在兹的仍然是追求‘外王’的实现”,他们转向“内圣”主要是为“外王”的实现做准备的。
八年以后(2008年),余先生在为田浩先生的著作《朱熹的思维世界》(增订版)所作的序中,对以上观点又作了一次详细的阐释。他说:
作者在“祈祷文”一章的结尾处,特别强调朱熹的“使命感”,并清楚地指出:“在朱熹的思想中,社会关怀—理论上的实践—是首要的。”这正是我在《朱熹的历史世界》(允晨,2003年)一书中所展开的基本论旨之一。中国史在宋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政治、社会、宗教、经济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动。“士”阶层乘势跃起,取得了新的政治社会地位。这一阶层中的少数精英(elites)更以政治社会的主体自居,而发展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普遍意识。这便是作者所说的“使命感”。他们的“使命感”主要体现在儒家的整体规划上面,即借“回向三代”之名,全面地重建新秩序。根据“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古训,他们首先以朝廷为中心,发动全面的政治革新,所以庆历、熙宁变法相继出现。但地方性或局部性的社会、道德秩序的推行也同时展开,故有义庄、族规、乡约、书院的创建。张载“有意于三代之治”,但从朝廷回到关中之后,立即在本乡以“礼”化“俗”,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为“在下则美俗”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事例。无论在朝野,士的“使命感”在南宋依然十分旺盛,朱熹便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他在政治上向往王安石“得君行道”的机遇,所以期待晚年的孝宗可以成为他的神宗,重新掀起一场“大更改”运动。绍熙五年(1194年)他立朝四十日便是为了领导朝廷上的理学集团推行改革(即所谓“孝宗末年之政”)。但在奉祠禄或外任时他则转而致力于地方上局部秩序的重建,如设立社仓、书院,以及重订吕氏乡约之类。不仅朱熹如此,同时的陆九渊、张栻、吕祖谦等也无不如此。现在本书作者通过“祈祷文”的专题研究,也进一步发现“政治、社会关怀”在朱熹思想中居于“首要的”位置,和我的整体观察恰好可以互相印证,我当然有闻空谷足音的喜悦。[21
余英时、田浩师徒二人,都不约而同地关注朱子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关怀,绝不是偶然的,他们的结论实质上是对朱子理学思想及其学术抱负的再发现,是对朱子一生学术活动与社会政治、文化实践的全面考察与完整的呈现。这一发现再次提醒我们,对理学、理学家的认识决不能停留在形而上的层面。正如余先生指出,他们的“内圣”是为“外王”做准备的,他们的学术关怀,最终还是指向社会、人心和组成这个物质和精神世界的芸芸众生,关注着世俗社会。
而礼学,正是朱子学术世俗关怀最集中和典型的表现。
(一)
什么是“礼”?朱子认为,“礼”即“理”,礼是天理的外在形式,“礼”与“理”是互为表里的。他说:“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3]他认为“礼”与“理”的主要区别是,“理”是形而上的,是一种无形无迹的观念形态,而“礼”则是形而下的、可见、可行、可凭据的实践形态。他说:“礼即理也,但谓之理,则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为礼,则有品节文章之可见矣。”[4]他进一步解释说:“所以礼谓之‘天理之节文’者,盖天下皆有当然之理。今复礼,便是天理。但此理无形无影,故作此礼文,画出一个天理与人看,教有规矩可以凭据,故谓之‘天理之节文’。”[5]有学生问朱子,“礼”之所以叫做“礼”而不谓之“理”,是不是因为“礼”是实在的、具体的、有可以落实的地方?朱子回答说:“只说理,却空去了。这个礼,是那天理节文,教人有准则处。”[6]
朱子又认为,礼是“人事之仪则”,也就是说,礼是人们行为处世及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礼仪制度。朱子在解释《孟子》“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时说:“何谓约?礼是也。”[7]他认为,礼就是约。什么是约呢?他说就是“上自朝廷,下达闾巷,其仪品有章,动作有节。”[8]约,有二层含义,一为“要”,一为“约束”。要就是主要的原则、规范,而这些原则规范是用来约束人的行为举止的。细察朱子在各种场合使用“约”字的情况,可以发现,他有时用第一义,有时用第二义,而更多的时候则二种含义兼而有之。在解释孔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时,他先引用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约我以礼,克己复礼也。”[9]再引胡氏曰:“惟夫子循循善诱,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达事变,然后约我以礼,使我尊所闻,行所知。”[10]这里约的主要含义在“要”、在“知”——即原则、规范。在解释“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时,他说:“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如此,则可以不背于道矣。”[11]并引程子曰:“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于礼,必至于汗漫。博学矣,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则亦可以不畔道矣。”[12]这里他强调的是约的“约束”之义。所以,他说,有君臣关系,就必然有君臣相处的原则、规范;有夫妇关系,就必然会有夫妇相处的原则、规范;父子、朋友、师长莫不如此,这就是礼。
朱子的理学思想,特别重视礼的实行和执行。他认为,既然礼具有天理的本质及其规范性,那么,践履就是天理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所以,他认为,“礼者,履也,谓昔之诵而说者,至是可践而履也。”[13]他认为,礼的践履是第一性的。古代未必有礼经(文字),他指出:“然古礼非必有经,盖先王之世,上自朝廷,下达闾巷,其仪品有章,动作有节,所谓礼之实者,皆践而履之矣。故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则岂必简策而后传哉!”[14]他还特别强调“知崇礼卑”,指出,践履礼,不能好高骛远,更不能厌弃礼的卑微与琐碎,礼正是在日常生活的各种细节中体现出来的。惟其如此,才能够“成性存存,而道义出矣”[15]。
在朱子庞大的理学体系中,礼学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朱子集理学之大成,构建了以性理学说为核心的形而上的理学体系。但是,他同样关注与重视“天理”与“人心”的连接与过渡,重视“天理”对形而下的世俗社会的影响与干预。在他看来,“礼”就是进行这种影响和干预的最有力的手段。所以他说:“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他的学生兼女婿黄榦对此解释说:“盖自天高而地下,万物散殊,礼之制已存乎其中矣……人禀五常之性以生,则礼之体始具于有生之初。形而为恭敬辞逊,著而为威仪度数,则又皆人事之当然而不容已也。圣人因人情而制礼,既本于天理之正。隆古之世,习俗醇厚,亦安行于是理之中。世降俗末,人心邪僻,天理堙晦,于是始以礼为强世之具矣。先儒取其施于家者,著为一家之书,为斯世虑至切也。晦庵朱先生以其本末详略犹有可疑,斟酌损益,更为《家礼》。务从本实,以惠后学。盖以天理不可一日而不存,则是礼亦不可一日而或缺也。先生教人,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修其身,皆所以正人心复天理也。则礼其可缓与?”在他看来,理与礼互为表里,理,是管人的内心——心性;礼是管人的行为——节文。理与礼的结合,就实现了一个文明人所必须具备的由内而外的天衣无缝的塑造。他认为,礼是理的“事”化和“物”化,“礼”中自然包含着“理”。他把这比喻为形和影的关系。
在一次与学生讨论《论语·子路》“卫君待子为政”章时,学生问他“何以谓之‘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朱子回答说:“‘事不成’以事言;‘礼乐不兴’以理言。盖事不成,则事上都无道理了,说甚礼乐!”[16]学生又问:“此是礼乐之实,还是礼乐之文?”朱子说:“实与文元相离不得。譬如影便有形,要离那形说影不得。”[17]又说:“事不成,如何得有礼乐耶?”“事若不成,则礼乐无安顿处。”[18]
理蕴含在礼中,礼表现在“事”、“物”中。
(二)
朱子不是一个空头理论家,他生活在理性的象牙塔的顶端,但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着世俗社会和现实政治,他是一个具有社会抱负和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他之所以关注礼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把“礼”视为改造社会、重塑社会秩序和移风易俗的重要工具。
他认为,“礼”之为用,一个重要的功能是规范“秩序”,这秩序包括人伦之序、君臣之序及各种社会关系之序。他说:“礼是有序,乐是和乐。”[19]“大凡事须要节之以礼,和之以乐。事若不成,则礼乐无安顿处。礼乐不兴,则无序不和。”[20]“礼乐只是一件物事,安顿得齐齐整整,有次序,便是礼。”[21]朱子有很多与友人的书信讨论“礼”,讨论的问题非常具体,如论庙室之向与座位的方向,如讨论丧礼的服制,这些仪式、形式、服饰,在朱子的眼中体现了一个“序”字。他认为,礼仪是社会秩序的物化、形式化,不能乱,一乱就失序了,而失序则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瓦解和动荡。
钱穆先生在《朱子新学案》中说:“盖礼之传世,在上则为典章制度,在下则为风俗教化。朱子所用力者,实欲汇通义理考据,溯往古之旧文,应当前之实用。其议丧服,议庙祧,皆当时朝廷大典礼,而亦有关教化之大,固非区区徒为钩沉炫博,媚古专经之比。至其为古经定制,非一字不可增损,而汉儒之学有补世教,此又非徒争程门义理为直接孔孟传统者所与知。亦非清儒专意尊汉抑宋,惟尚文字考据者所能测。至于议礼而遭忌逐,党禁之祸因此而起。治史者于此,可知在朱子当时,礼学仍为治国立政宣教化民一要项,非可用今人眼光忖测。”[22]绍熙五年(1194年)邵囦刻张栻的《三家礼范》于长沙郡学,朱子为作跋,曰:“呜呼,礼废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尝习于身,是以长而无以行于家。长而无以行于家,是以进而无以议于朝廷,施于郡县;退而无以教于闾里,传之子孙,而莫或知其职之不修也。长沙郡博士邵君囦得吾亡友敬夫所次《三家礼范》之书,而刻之学宫,盖欲吾党之士相与深考而力行之,以厚彝伦而新陋俗,其意美矣。”[23]朱子于此明确揭示“礼”对于移风易俗的重要作用。按《三家礼范》今佚,据朱子之跋语可以推知其为“家礼”一类著作。朱子对“家礼”、“乡约”、“乡仪”一类著作非常重视,他多次为此类著作写序作跋并鼓励刊刻广为发行。这是因为他明白,此类民间之“礼”书,具有十分有效的“厚彝伦而新陋俗”的作用。据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考订,淳熙二年(1175年),朱子始作《家礼》,同年修订《祭仪》,作《增损吕氏乡约》,为《蓝田吕氏乡约》、《蓝田吕氏乡仪》作跋。乾道元年至九年(1169—1173年)修订《祭仪》。如此密集地修礼、论礼是事出有因的,是朱子初任地方官以后对民间风俗、风气作深入考察而有了切身体验后,对整顿礼制,推行礼制之迫切性所作出的学术反应。
(三)
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7月,朱子赴任同安主簿,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个地方官职。到任以后,他除了大力整顿县学外,上书“申严婚礼”曰:
窃惟礼律之文,婚姻为重,所以别男女、经夫妇,正风俗而防祸乱之原也。访闻本县自旧相承,无婚姻之礼,里巷之民贫不能聘,或至奔诱,则谓之引伴为妻,习以成风。其流及于士子富室,亦或为之,无复忌惮。其弊非特乖违礼典、渎乱国章而已,至于姤媢相形,稔成祸衅,则或以此杀身而不悔。习俗昏愚,深可悲悯。[24]
朱熹同时作《民臣礼议》,建议朝廷颁布州县予以实行。同安主簿的地方官经历,使朱子对民间习俗的混乱、迷失与糜烂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他说:“臣窃观今日天下之势,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盖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25]他把“振举纲维、变化风俗”列为“今日之急务”。正是出于对现实社会风气败坏的担忧,所以,朱子在编修礼书时作出了十分有针对性的安排。
宋廷南迁以后,由于退守仓皇,北宋时代长期积累而成的各种礼仪制度都受到了极大的破坏,连年的战争又使统治者无暇重拾礼制,于是民间邪教、淫祠趁虚而入,占领了本应属于儒学传统的各种祭礼及婚丧仪式。尤其是佛、道两教在民间传播影响之大,已对儒学的传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朱子在《乞增修礼书状》中揭示了这种情况:“今州郡封域不减古之诸侯,而封内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礼,其有祠庙,亦是民间所立,淫诬鄙野,非复古制。顾乃舍其崇高深广、能出云雨之实,而伛偻拜伏于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所谓滋养润泽者,于义既无所当,又其牲牢器服一切循用流俗亵味燕器,欲礼又无所稽。至于有山川而无祠庙者,其岁时祈祷,遂不复禜于山川,而反求诸异教淫祠之鬼。此则尤无义理,而习俗相承,莫知其谬。”[26]所以,他要求朝廷镂版颁降《政和五礼新仪》,并称此举乃“化民善俗之本,天下幸甚”。[27]
在朱子的时代,另一种社会风气也是令朱子十分警惕的,那就是奢靡之风。绍熙五年(1194年),上《乞讨论丧服札子》论嫡孙承重之服,主张应“以布衣布冠视朝听政,以代太上皇帝躬执三年之丧”。而用“漆纱浅黄之服,不唯上违礼律,无以风示天下,且将使寿皇已革之弊去而复留,已行之礼举而复坠。”[28]所以,他希望宁宗能够“明诏礼官稽考礼律,预行指定,其官吏军民男女方丧之礼,亦宜稍为之制,勿使过为华靡”。[29]
此乃宫廷奢靡,而民间奢靡之风同样令朱子十分忧虑。朱子《家礼·通礼》章全引司马光《居家杂仪》,其第一条即告诫曰:
凡为家长,必谨守礼法,以御群子弟及家众。分之以职,授之以事,而责其成功。制财用之节,量入以为出,称家之有无以给,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费,皆有品节,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费,禁止奢华。[30]
“亲迎”章,朱子保留了司马光《书仪》中之“铺房”,这是自北宋时已形成的一种民间习俗,即在亲迎前一日,女方派人到男方家中陈设新房,并将陪嫁之物陈列展示。这是古礼中所没有的内容,但民间已非常普及,故司马光的《书仪》中予以保留,但规定:“床榻荐席桌椅之类,婿家当具之,毡褥帐幔衾绹之类女家当具之。所张陈者,但毡褥帐幔帷幕之类应用之物,其衣服、袜履等不用者,皆锁之箧笥。”[31]这正是为了避免当时竞相奢华,互相攀比之陋习。朱子《家礼》亦保留了司马光的内容,语言则更简洁和明确:“世俗谓之铺房。然所张陈者,但毡褥帐幔帷幙应用之物,其衣服鏁之箧笥,不必陈也。”[32]接着,朱子又引用了司马光的一大段议论曰:“文中子曰:‘婚娶而论财,夷虏之道也。’夫婚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今世俗之贪鄙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至于立契约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复欺绐负约者,是乃驵侩卖婢鬻奴之法,岂得谓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绐,则残虐其妇,以摅其忿,由是爱其女者,务厚其资装,以悦其舅姑者,殊不知彼贪鄙之人,不可盈厌,资装既竭,则安用汝女哉?于是质其女以责货于女氏,货有尽而责无穷,故婚姻之家往往终为仇雠矣。是以世俗生男则喜,生女则戚,至有不举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则议婚姻有及于财者,皆勿与为婚姻可也。”[33]这真是一段振聋发聩的高论。从司马光的时代到朱子的时代,跨度长达一个多世纪,但从北宋到南宋,社会竞靡的风气依然不见改观,故朱子作《家礼》,不得不再次引用前贤之论,以警示时人。
(四)
余英时先生在其大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反复强调了宋代士阶层政治意识的觉醒及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自觉性,而秩序的重建则是贯穿于宋代理学从发生、发展到壮大全过程的永恒主题。他指出,张载“有意三代之治,但他的着手点却是本乡以‘礼’化‘俗’,即所谓‘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吕氏兄弟在张载逝世之年(1077年)正式建立著名的‘乡约’,便是继承其师‘验之一乡’的遗志。范仲淹首创‘义庄’这一事实,则更进一步说明士大夫重建秩序的理想同样可以‘验之一族’。‘义庄’与‘乡约’同是地方性的制度,也同具有以‘礼’化‘俗’的功能。他们同时出现在11世纪中叶,表示士大夫已明确地认识到:‘治天下’必须从建立稳定的地方制度开始。这本是儒家的老传统,即所谓‘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但北宋士大夫所面对的是一个转变了的社会结构,他们不得不设计新的制度来重建儒家秩序,无论是王安石的新法、吕氏‘乡约’或范氏‘义庄’,虽有全国性与地方性之异,都应作如是观。所以分析到最后,宋代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革新活动,背后都有一股共同的精神力量,这便是当时所谓‘以天下为己任’。朱熹释张载《西铭》‘吾其体,吾其性’说:‘有我去承当之意。’总之,宋代的‘士’以政治、社会的主体自居,因而显现出高度的责任意识,这是无法否认的。”[34]
如果说,张载者流是在一乡一村做着理学家们的以“礼”化“俗”的社会实践的话,那么王安石则是希望通过君主的支持而进行一场全国性的化俗之运动。他的“变法”主张,其实就是一个不满于社会现实政治、文化、经济秩序的儒者试图变易旧法而改造社会的变革实验。其实,王安石欲行改革,起初朝野上下的有识之士都是认可的。“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35]可见,当时的社会现实,是到了不变不行的时候。“合变时节”一词,正说明了易风移俗已成了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他的改革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朱子认为除了王安石性格上的问题外,最主要的是他的“学术不正”。他说:“王荆公遇神宗,可谓千载一时,惜乎渠学术不是,后来直坏到恁地。”[36]他认为,王安石的问题是对儒学的传统及其内涵,没有一个正确和完整的理解,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见道理不透彻”。“先生论荆公之学所以差者,以其见道理不透彻。因云:‘洞视千古,无有见道理不透彻而所说所行不差者。但无力量做得来,半上落下底,则其肤浅。如庸医不识病,只胡乱下那没紧要底药,便不至于杀人。若荆公辈,他硬见从那一边去,则如不识病证,而便下大黄、附子底药,便至于杀人。’”[37]王安石的失败,给了朱子以反面的教育,他体悟出一场大的社会变革,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理论的指导,所以,他从儒学的基本经典入手,加以思辨地、深入地和形而上的研究,构筑了一套完整的理学体系。就“礼”学而言,他在建构自己的“礼”学体系时,首先下大力气研究的是儒学关于“礼”的基本经典——“三礼”,及其三者之关系。他认为,《周礼》为礼乐之纲领,《仪礼》乃礼之本经,《礼记》乃《仪礼》之义疏。当他理顺了三礼之间的关系时,他意识到《仪礼》是礼之经,于是转而深研《仪礼》,花了毕生精力予以整理、注释,《仪礼经传通解》便是他心血的结晶。其子朱在曰:“先君所著《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王朝礼》十四卷,今刊于南康道院。其曰《经传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盖先君晚岁之所亲定,是为绝笔之书。”[38]正因为有了对儒家“礼”学经典的深入与整体的把握,所以他能游刃有余地、因时制宜地、与时俱进地制定出《家礼》等新礼书。
历时三百余年的宋朝,由于战乱频仍,似乎始终处于不停地“稳定—变革—战争—稳定—变革—战争”的循环之中。从大环境看,有宋一朝,稳定时间短,而战争(或准战争)时间长。而一旦社会稍趋稳定,那些有志于社会改革和重建儒学政治社会秩序的知识分子便会发出改革的呼声并付诸实践,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再到南宋理学的大兴,无不印证了这一规律。而几乎绵延于南宋朝始终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理学运动,则是贯穿于整个宋代社会改良与儒家秩序重建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其之所以最具影响力,除了因为以朱子为代表的儒学理论体系已达到了当时不可逾越的思想与学术高度外,还因为,朱子注意到了形而下的世俗的向度,这一向度使他的理论能深植于民间和草根,以致成为中国人生命与思维方式的组成部分而影响中国社会长达八百余年。
余论
笔者认为,朱子的学术,绝不仅仅是一种“文本的儒学”,而是一种“行动的儒学”。所谓行动的儒学,就是说,这种理论,并不仅仅是供把玩的、研究的、推演的、思辨的,而是除此之外还应该实行的、践履的。
朱子是中国古代复兴儒学的最伟大和最成功的思想家。他重视“天理”对世俗社会的影响与干预。在他看来,儒家的礼仪就是把天理与人世间进行对接和过渡的最好方式。他把“礼”看作是对“理”的践履。如果“理”是“知”,那么,“礼”就是行。同时他又强调礼对人的约束作用,他认为,人只有“动必以礼”,才能“不背于道”。朱子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使内容与形式互为表里,这使他的理学体系成为一个严整和周密的系统,同时也使理学的理论能够起到反哺社会、维护和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
今天当我们仔细地回顾和研究朱子的学术之路,我们不能不说,他的理论、思想、方法依然对当今中国社会具有深刻的启迪与借鉴作用。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30余年来,取得了经济高速发展的世界奇迹。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会因为经济的复兴而自然实现,它还必须依赖于文化的复兴。而文化的复兴,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复兴。其中“礼”学的复兴,则更具有现实的迫切性。
改革开放以后,国门大开,中国社会对外来文化(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采取了不加甄别地全盘开放与照单全收的态度,以致西方文化如水银泻地般渗入中国社会的各种肌体。由此而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传统道德的迷失与基本行为规范的缺位。现在中国人被西方人诟病最甚的“不诚信”、造假,即是传统道德迷失的最集中的表现。现代中国人被西方人指为“不文明”的“粗鲁”、“野蛮”,则是中国传统的基本行为规范缺位的必然后果。所以,我们要重拾传统(请注意,不是“重建”)、回归传统,这“传统”就是中国的“礼”。
近年来,中国大陆提倡“和谐”,之所以倡导和谐,当然是因为不和谐,实际上,“和谐”背后反映的恰恰是社会秩序混乱。提倡和谐,实质上就是要重建合理的、科学的和稳定的社会秩序。这一社会诉求,也许正可以从以朱子为代表的“礼”学复兴的社会实践中汲取教益。
西方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冲击是全方位的,其中民间习俗的被西化与被边缘化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面对西风席卷、西俗泛滥、中华传统的社会礼俗被全盘西化的社会现实,代表本土文化和传统的儒家“礼仪”完全可以从朱子“礼”学的精神宝库中获得武器以对全盘西化发起挑战,从而夺得中华文化自我救赎的一席之地。
社会的和谐离不开民众素养的培育与养成。中国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民族素养严重滑坡,以俗为美,以粗野为高雅,以鄙陋为文明,几乎成了整个社会的正常风气。此外,中国社会千百年来由儒家“礼俗”养育而成的各种社会规范,如尊师重教,如敬老爱幼,如礼让为先,如尊卑有序,如父慈子孝,如夫妇有别等等均被当作封建意识形态之病患而破坏殆尽。所以,如何提升全民族的文明素质,实在是当今中国社会非常迫切要解决的大事。社会规范是社会大众共同认可而自觉遵守的约定俗成,一个社会的成熟与否,这种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是其主要的内涵。中国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好不容易有了一种被世人称为“礼仪之邦”的社会约定俗成,可惜被一旦毁弃,而如今要恢复它,谈何容易。朱子曰:“礼不难行于上,而欲其行于下者难也。”[39]就是看到了礼之成俗之难,这需要长时间地不懈地推行、实施和潜移默化。
这也许正是我们今天来讨论朱子“礼”学的现时代意义。
朱子与儒家的精神传统
刘述先
通过当代新儒家的努力,儒家不再被误解为仅是一俗世伦理,这一传统被归入世界精神传统系列就是一个明证。[1]“儒家”(Confucianism)一词歧义甚多。我提议分别开三个不同而互相关联的面相来讨论:精神的儒家(spiritual Confucianism)、政治化的儒家(politicized Confucianism)与民间的儒家(popular Confucianism)。很自然地,我主要的关注集中在儒家精神的大传统方面。牟宗三先生首先提出儒家哲学三个大时代的说法,由杜维明广布于天下,我也认同这一说法。2005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邀请我回去做第十八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我讲的正是:“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抒发我自己对先秦儒学、宋(元)明儒学、现代新儒学的诠释与理解。[2]
先秦儒学最关键性的人物是孔子,他并不是儒家传统的创始者,他继承的是周文。但到春秋时代,周文疲弊,礼教不兴,他为礼找到内在的根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3]。生命以仁为终极关怀,这开启了儒家内圣的道路。孔子透过具体的行事因材施教给门徒以指引,表面上看来不成体系,其实“吾道一以贯之。”曾子的阐释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4]朱熹《四书集注》谓:“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大体得之。孔子学问的核心是“为己之学”。中国缺少近代西方式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但绝非不重视个体。除了推己及人之外,还强调:“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5]天是超越的层面,在过去一直未受到充分的重视和讨论。表面上看,孔子的“天”也可以理解成为人格神,但与亚伯拉罕传统(犹太教、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的上帝不同,不显意志,也不创造奇迹。孔子的“无言之教”是一真正的突破,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6]天在这里已完全没有人格神的特征,但又不可以把天道化约为自然运行的规律。孔子一生对天敬畏,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7]小人怕的是上天的震怒,爱的是上天的眷顾,故多避祸祈福的举动,对默运的天道不只没有感应,还加以排斥。但孔子加以扭转,天是无时无刻不以默运的方式在宇宙之中不断创造的既内在而超越的精神力量,也是一切存在价值的终极根源。
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牟宗三先生说:孟子的思想纲领是“仁义内在,性由心显”,大体得之。孟子道性善,他说的是“本性”,这又是一个突破。由恻隐之心这样“本”的呈现,不只可以接上内在的本性,还可以通往超越的天道。所谓尽心、知性、知天,我们所以能够知天,正因为我们生命的根源来自上天的禀赋。但荀子却回到“生之谓性”的老传统,主张性恶,与孟子缺乏交集,讲的是经验现实的层面,又主张自然的天论,完全失落了超越的层面,所以被宋儒摒弃在“道统”以外。但荀子讲“化性起伪”,也认为人有巨大的可能性。他隆礼、传经,对儒家传统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8]宋儒又从《小戴礼记》抽出《大学》与《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组成四书,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大学》讲三纲领: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后世“内圣外王”的理想竖立了一个大体的准绳。《中庸》是儒家典籍中最富有哲学意味的一篇,前半讲未发、已发的修养工夫,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后半集中在“诚”的体证与阐发,所谓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展示了通过实践体现形而上睿慧的意涵。最后,孔子与其后学藉《易传》的阐发,把原来只是一部卜筮之书化腐朽为神奇,转化成为一部哲学宝典。[9]
由以上所述,可见先秦儒学在理念、典籍、实践三个层面已树立了规模,有待后来者进一步阐发与拓展。但在历史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儒学首先经过了汉代的曲折。汉初因受暴秦夭亡的教训,鄙弃法家,用黄老之术,与民休息。到汉武帝时国势强盛,乃转趋儒家,利用儒生巩固君王的统治,自此以往,“政治化的儒家”成为主流。士成为君王与百姓的中介阶层,形成一超稳定结构,一直到西风东渐,清廷覆亡,制度化的儒家(institutional Confucianism)划下句点,儒家才由中心被逐到边缘,这是后话,暂先搁置。汉代虽无与于道统,但以德治国,所谓“独崇儒术,罢黜百家”固然过分夸张,然而推动儒家教化,建造伟大中华文明,还是可以大书特书。老百姓勤劳节俭,崇尚教育,接受阶层秩序,倾向服从权威。所谓“民间的儒家“只是一种不自觉的心习,民俗兼融道佛信仰,乐天安命,由于缺乏声音,一向受到漠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东亚四小龙(台、港、新、韩)创造经济奇迹,才引起社会学家的注目。然而这些都不是本文中心关注所在,一笔带过算数。
回到精神传统,汉末天下大乱,除了科举为晋身之阶以外,经学根本不能满足知识分子精神的需要。他们倾向三玄(易、老、庄),被新玄学所吸引。而佛教自汉明帝之时传入中国,经过长期发酵以后,隋唐佛学人才鼎盛,中国式佛学:华严、天台、禅,吸引了知识分子的关心。经历五代,宋代儒学必须面对两大挑战,一则道德沦丧,不堪闻问;二则异学(道佛二氏)兴盛,儒学低迷。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宋明理学开创一条新的道路,力抗时流回归孔孟,并转化华严的“空理”为儒家的“性理”。这在某一意义下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文艺复兴,下开了儒家哲学的第二个黄金时代。[10]
北宋理学代表人物无疑是洛学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兄弟。伊川作《明道先生行状》云:“先生为学,自十五六时,闻汝南周茂叔论道,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后,未有臻斯理也。谓孟子没而圣学不传,以兴起斯文为己任。”[11]
这说明了明道虽受到濂溪的启发,但并不传濂溪的学问。他面对二氏的挑战,回归圣学的传统,超越汉唐,直承孟子,跨越千年,担起传承道统的责任。但基础何在呢?必须归本于性命,明道自承:“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12]与横渠不同,明道不作宇宙论的铺陈,直截地体证了内在于自己生命的超越的天理。二程兄弟大方向一致,但明道圆融,伊川分解,也有重大的差别。[13]把宋明理学发展成为时代主流最关键性的一个人物就是南宋的朱熹。他继承的是伊川的思路,将之发展为整体的哲学,建构了一个心、性、情三分架局,完成了他的理气二元不离不杂的形上学。[14]我首先要强调的是朱子是圣学的一支。他少年时便已关注“为己之学“。苦参中和多年,回归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如此“静养动察”分有所属,“敬贯动静”,涵养于未发,察识于已发,这才走上了他自己成熟思想的路数。他一生强探力索,学问博大精深,日后被推许为集大成,绝不是偶然的。然而他所作出的综合,却不是没有问题的,但非当前重点所在,本文不及。
二程担负道统,但道统的建构要到朱子才完成。在《中庸章句序》中,他说:“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然当是时,见而知之者,惟颜氏、曾氏之传得其宗。及曾子之再传,而复得夫子之孙子思。……又再传以得孟氏。……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续乎千载不传之绪。”[15]
这是何等的大手笔!朱子很清楚,他所面对的不是历史考据的问题。尧、舜、禹三圣在上古之世,孔子的时代已经文献不足,怎么能够证明舜、禹之间有“危、微、精、一”的十六字心传?这明显是精神信仰的传承。清儒阎若璩指出,十六字心传出于伪《古文尚书》、《大禹谟》,表面上看,似乎对宋儒建构的道统造成致命的打击,其实不然。因为这是“信仰”(faith)的领域,不是“知识”(knowledge)的领域。以生命投注的精神信仰是不会因为文献考证的“臆说”(opinions)而动摇的。而令人惊诧的是,朱子对道统的理解还有进于孟子处。孟子慨叹,夫子因得不到举荐,故不得其位,而感到遗憾。[16]朱子却掉转师道与君道的位置,推崇夫子“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想想这在当时引起了多大的震撼!仕人臣服君王只是尊君王之位,而君王必须对德低头。朱子正因有这样的精神传统做后盾,才敢于面圣斥君之非,并贬抑汉唐(功利)。这或者不免过分,但有精神传统为终极关怀的儒者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精神,岂是一般俗儒可以了解于其万一的。
犹有进者,对于朱子,回归孔孟固然重要,但更有必要重视当前的资源。于是他和吕东莱合编《近思录》,选录北宋濂溪、明道、伊川、横渠的文字,共十四卷:(1)道体,(2)为学,(3)致知,(4)存养,(5)克治,(6)家道,(7)出处,(8)治体,(9)治法,(10)政事,(11)教学,(12)警戒,(13)辨异端,(14)观圣贤。卷一论义理之本原,然后自近及远,自卑升高,形成整个的体系。[17]
“近思”二字出自《论语》,其曰:“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18]正如朱子的门徒叶采(平岩)《集思录集解》原序曰:
尝闻朱子曰: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盖时有远近,言有详约不同,学者必自近而详者,推求远而约者,斯可矣。
我们现在讲宋明理学,习惯讲濂、洛、关、闽,中学教科书就是这样讲,却没有意识到,原来这正是朱子迈越时流,通过编纂《近思录》建构起来的思路。周濂溪无籍贯名,官阶也不高,仅只是二程的家庭教师而已,虽然对他们有所启发,但二程并不推崇濂溪的学问。但因朱子激赏濂溪的《太极图说》,竟推尊他为宋明理学的开祖。[19]而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无极而太极”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由于“无极”一词出自《老子》,陆象山兄弟质疑此文非濂溪所作,或者是他不成熟的少作。但朱子为之辩护,否定了“自无极而太极”的版本,那隐涵了“有生于无”的道家思想。朱子将“无极而太极”理解成为“无形而有理”,乃一体之两面,自也可以言之成理。其实濂溪把道家修炼图倒转为创生的宇宙论,《太极图说》的思想与他的《通书》互相融贯,象山兄弟的质疑并没有很好的理据。后世接纳了朱子的提议,把濂溪当作开启理学思潮的人物。
接下来应该讲横渠,他年辈与濂溪相若,著《西铭》一文,是在《太极图说》之外影响整个理学思潮至深至巨的另一篇大文章。[20]文章开始讲乾父坤母,气势磅礴,宣扬“民胞物与”之旨,归结于“存吾顺事,殁吾宁也”。杨龟山怀疑此文“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伊川作出响应:“《西铭》之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岂墨氏之比哉!《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子比而同之,过矣。”这是“理一分殊”见诸文字的首次,意义重大,以后发展成为宋明儒的共法。但二程都批评横渠《正蒙》讲“清、虚、一、大”表达未醇,这显然是基于误解,但横渠的表达有些滞词,的确容易引起误解,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朱子追随二程,为了哲学的原因,把洛学移到关学之前,由此建构了濂、洛、关、闽的线索,后世以为当然,其实由思想史实际发展的线索来看,并没有必然性。由上所述,要没有横渠的《西铭》,根本不会有伊川“理一分殊”的阐发,还得先由横渠说起,而伊川讲“理一分殊”原来的论述是在道德伦理的层面,朱子才作出“一理化为万殊”的更普遍化的论旨。另一个案例是,横渠率先划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二程加以首肯,才说“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此语《近思录》卷二归之于明道,但伊川也有同样的说法。
朱子自己的确推尊二程,以之为正统。《近思录》卷二收入了明道的《定性书》答横渠问,这加强了横渠向明道问道的印象。横渠是二程的表叔,伊川虽否认横渠曾经学于他们两兄弟,但印象既已形成,先入为主,也就难以改变了。其实横渠的思想最富原创性,他和濂溪一样有宇宙论的兴趣,对《易》有相当研究,又是礼学的专家,注重躬行实践,有多方面开启的可能性。但他喜欢作异乎寻常的表达方式不免引起误解,以至未能得到充分重视。这是很可以遗憾的一件事。就圣学的体证与阐发来看,二程的确醇化,但不免偏向内圣一边。他们完全缺乏宇宙论的兴趣,阻抑了往多方面开展的可能性,不期而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配合上重文轻武的国势,不免偏向一边,失去了应有的均衡,也是可憾之事。
而朱子虽推尊二程,还是在明道、伊川之间作出了明白的分疏。明道一本,伊川二元,二者的同异,此处未能深论。然而朱子明显地不契于明道浑沦的体证,故《近思录》不收《识仁篇》。朱子继承并充分加以发扬的是伊川“性即理”、“爱情仁性”的思路。他建构了一个心、性、情三分架局,服膺横渠“心统性情”之说。性理超越,只存有而不活动。情内在,有流于情欲的倾向。心是气之精爽者,具有动能;心具众理,通过工夫实践,乃能以理御情,倡导一渐教的工夫论。平心而论,程朱是圣学的一支。伊川明白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分别,而依《大学》所教“格物穷理”,日积月累,也可达致一种透彻的体悟。朱子把这样的思路在他著名的《大学格物补传》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
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道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这绝不是通过归纳的方法去追求科学知识的途径。所谓“豁然贯通”乃是一种异质的跳跃。朱子渐教的途径到最后还是达到一种悟:通天下只是一理,这已超过了经验实证科学知识的层次。朱子的问题在他没有清楚划分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不同的层次。但朱子虽有经验实在论的倾向,毕竟是圣学的苗裔,也有强烈的理想主义的倾向,这由他与陈亮辩汉唐就可以看得出来。[21]就这方面而言,陆象山与朱子是同道,同属圣学中人。[22]吕东莱与朱子一同编完《近思录》之后,约陆氏兄弟与朱子作鹅湖之会,结果朱以陆之教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此颇不合。朱子以象山为畏友,意存调停,乃谓:“子静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多了。……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但象山拒绝这样的调和折中,曰:“朱元晦欲去两短,合两长,然吾以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23]由圣学的观点来看,象山是占优位。而他直承孟子,肯定心即理。不似朱子以心具众理,走迂回的道路,力道不足。朱子也不是看不到象山的优点,但感到象山的表达过分简截,不重典籍,直下承担,难免有流弊。然而朱子以象山有禅的意味,是无谓的牵扯。值得注意的是,顿的功夫论未必通体是本性的发扬,象山有些追随者竟以气质之杂为天理,则渐的工夫论虽无急效,不失为一条比较稳妥的道路。其实两派的确互有优劣,可以平衡彼此。可惜象山早逝,思想过分简截,未能致曲,门庭狭窄。陆学根本不能与朱学抗衡,到王阳明的时代,几成绝响。
朱子长寿,学问博大精深,成为道学一派宗师,绝非幸致。他死时被诬为“伪学”,但送丧者还超过千人,而且很快在宋理宗时即得到平反。元代科举,自1313年起,以朱子编纂的《四书集注》取士,一直到清末,1905年废科举为止,近六百年的时间,仕子童而习之。影响之大,自孔子以后一人,洵非虚语。
到了明代,王阳明虽重刻《象山文集》,反对诋以为禅,但以象山粗,不取其直截的表达方式。只他深以流行的朱学,习尚功利,务外遗内,忘失圣学的宗旨为病,乃提倡致良知,一新耳目,使心学成为显学。但他的思想表达由朱子转手,挑战朱子的《大学》解,回归《大学》原本,反对析心与理为二,提倡心理合一,知行合一,晚年讲《大学问》,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而他对朱子意存调停,编《朱子晚年定论》,想拉近与朱子的距离,却因书函考据失实,未能达到目的。但他思想理论的规模要借与朱学之对反而彰显,却是不争的事实。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阳明《传习录》中《致周道通书》,平章朱陆,《致陆原静书》则通过对濂溪、明道思想的诠释以阐发自己的思想。由此可见,阳明接受了朱子建构的道统的线索,但并不盲从朱子的意见而作出了自己的阐解。同样的情况也见于明末的刘蕺山,牟宗三先生以之为宋明理学的殿军。[24]蕺山主静,自推尊濂溪。他对朱子思想的理解颇多差谬。而他强调诚意慎独,又提出另一《大学》新解以阐发自己的思想。他同样接受朱子建构的道统的线索,而作出了自己的阐解。宋明理学既内在而超越的精神传统到明末清初因遭逢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失落了超越的层面而画下句点;清代的统治者虽仍维持朱子为正统,但清儒将天理虚化,礼教的终极权威归之于皇权,丧失了朱子的精神,外在权威提升,内在体证减弱,体制日趋僵固,终于演变成为所谓的“杀人的礼教”,也就不足怪了。[25]
清末废科举已令儒学由中心退到边缘,1911年清廷颠覆,制度的儒家宣告终结。西潮疾卷,民国肇建,军阀割据,内忧外患,政治并未转趋清明,儒家成为代罪羔羊,一切反动负面因素都归咎于这一传统。五四时期(1919年)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不意现代对儒家浴火重生的契机也正在同时,可谓异数!一战后梁启超到巴黎参加和会,亲眼目睹欧洲的凋敝与残破,所谓进步的西方反而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决不可以作为中国走向未来的楷模。他重新看到传统之中一些有价值的成分,而打开了现代新儒学复兴的机运。[26]追究其所以可能,正因为精神的儒家蕴含可以与时推移的万古常新的智能的缘故。长话短说,经过“三代四群”的努力,现代新儒学被肯认为现代中国最有潜力的思潮之一,另外两个思潮是西方思想与马克思主义。[27]当代新儒家的反省,见1958年元旦发表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由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四位学者签署。他们坦承中国文化不足,必须吸纳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但西方文化也有不足,应吸纳中国文化:(1)“当下即是”之精神,与“一切放下”之襟抱,(2)圆而神的智能,(3)温润而恻怛或悲悯之情,(4)使文化悠久的智能,(5)天下一家之情怀。而不了解中国的心性之学,也就不了解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而不能掌握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28]这无疑是继承自先秦与宋明的精神传统。
当代对儒家最富原创性的思想家是牟宗三。他精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展示了知识的限度。《实践理性批判》才有必要以“自由意志”、“灵魂不朽”、“上帝存在”为基设(postulate)。牟先生认为康德是受限于他的基督宗教背景才会认定只有上帝才能有“智的直觉”(intellectual intui-tion)。但中土三教儒(性智)、释(空智)、道(玄智)都确信人可以有智的直觉。这是中西哲学传统最大的差别。由西方的进路可以建构“执的形上学”,由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进路可以体证超越名相“无执的形上学”。事实上,“现象”与“物自身”不可偏废,二者分别有其定位。无限心的“坎陷”成就知识,而道的体认、心灵的解放与超脱并不需要脱离世间。像《大乘起信论》那样“一心开二门”,即可以找到会通中西的津梁。[29]
第二代新儒家适当存亡继倾之际,展示了强烈的护教心态,像牟宗三即强调中国文化以儒家为正统(突出创造性)的常道性格,不免引起巨大争议。但第三代新儒家却有幸在宁静的校园中成长,部分留学外国,受到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并在异域谋求一枝之栖,默认西方开放多元的学术文化,像杜维明和我展示的,是一个与上一代十分不同的国际面相。
20世纪80年代与60年代情况迥异。中国崛起,不再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两岸三地情况稳定,看不到战争的危机。进入新的世纪,知识分子要面对的是“全球地域化”(glocalization)的问题。[30]世界不知不觉缩小成为一个地球村,不像以往西方、印度、中华文明分别发展,各族群信仰接触频繁,如果不调整心态,听任矛盾冲突加剧,地球与人类的毁灭危在旦夕,故孔汉思(Hans Kung)呼吁必须面对典范重构的大问题,建构“全球伦理”(global ethic),祈求地球与人类的持存与永续。[31]第三代新儒家感到责无旁贷,积极予以呼应。但第二代过分强调儒家思想之正统与常道明显地不合时宜,无助于当前的宗教对话。故我倡议给予“理一分殊”以创造性的诠释,因应当前多元互济、和而不同的时代潮流作出积极的响应,继承孔子知其不可而为的精神,重构朱子理一分殊的睿慧,寻求切合当前的表达与践履,寄无穷的希望于未来。
注释
全球化时代朱子“理一分殊”说的新意义与新挑战
黄俊杰
一、引言
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从工业革命以后就逐渐形成,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茁壮的全球化潮流加速发展,蔚为新时代历史之主流。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甚多,知识本身成为生产资材的“知识经济”,是一个新的趋势。全球化时代另一项主流趋势就是当代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 )所说的,全球化创造了一种世界各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结性(inter-connectedness)大幅提升的生活方式。[1]全球各地“相互联结性”的日益加强,固然使全球各地的人才、物资与资金的流通更加通畅,但却也意味着各地的文化传统与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大幅提升。2001年“911事件”以及后美国在世界各地所展开的反恐行动,都印证全球化时代文明冲突的可能性。
为了因应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新挑战,我们可以跃入传统的巨流中,汲取新时代的灵感。在中华文化与思想传统之中,南宋大儒朱子(晦庵,1130—1200)的“理一分殊”说有其21世纪的新意涵,但在全球化时代各地互动的新脉络中,也面临诸多新的挑战。本文循朱子学之思路探讨全球化发展之相关问题,并提出“理一分殊”说在新时代的意义及其转化的可能性。
二、朱子学中“理—”与“分殊”
之关系:兼论“理”的诡谲性
(一)“理一”与“分殊”
“理一分殊”是朱子学的核心概念,朱子说:
世间事虽千头万绪,其实只一个道理,“理一分殊”之谓也。到感通处,自然首尾相应。或自此发出而感于外,或自外来而感于我,皆一理也。[2]
但是,“理一”与“分殊”并不是一种对抗的关系,“理一”遍在于作为“分殊”的万事万物之中。朱子说:
其所谓理一者,贯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离耳。盖乾之为父,坤之为母,所谓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则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为同胞,物为吾与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谓理一者也。然谓之民,则非真以为吾之同胞;谓之物,则非真以为我之同类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谓分殊者也。[3]
在朱子的”理一分殊”论中,“理一”与“分殊”并不相离,“理一”融渗于“分殊”之中。换言之,只有从具体而特殊的“事”之中,才能观察并抽离出抽象而普遍的“理”。也就是说,“共相”存在于“殊相”之中。
朱子在所有著述以及言谈中,屡次申论“理一”与“分殊”不相离,例如他在《中庸或问》中说:
天下之理,未尝不一,而语其分,则未尝不殊,此自然之势也。盖人生天地之间,禀天地之气,其体即天地之体,其心即天地之心,以理而言,是岂有二物哉?……若以其分言之,则天之所为,固非人之所及,而人之所为,又有天地之所不及者,其事固不同也。[4]
朱子在这一段话中,为“理一”与“分殊”的必然性安立一个宇宙论的基础。朱子认为人间秩序本于宇宙秩序而生成发展,此所谓“理一”,但“理一”之具体之表现方式则多元多样,互不相同,此所谓“分殊”。
为了进一步说明朱子思想中“理一”与“分殊”的关系及其方法论问题,我们可以从朱子对孔子所说“吾道一以贯之”一语的解释开始。
朱子针对孔子在《论语·里仁》所说“吾道一以贯之”一语,提出以下的解释:
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而已矣者,竭尽而无余之辞也。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无余法,而亦无待于推矣。曾子有见于此而难言之,故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晓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或曰:“中心为忠,如心为恕。”于义亦通。[5]
朱子这一段解释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这句话[6]。朱子以“体”与“用”之关系说明“一本”与“万殊”之不相分离,对13世纪以后东亚思想界影响很大,几乎主导了以后的解释。南宋真德秀(景元,希元,景希,文忠,1178—1235)说:“一以贯之,只是万事一理。”[7]明代薛瑄(德温,1389—1464)说:“万物各具一理,万理同出一原,故一以贯之。”[8]都可以视为朱子以“理一分殊”说解释孔学的进一步推衍,足证朱子之解释对后学影响深远,朝鲜时代(1392—1910)的朝鲜儒者更是完全浸润在朱子学的诠释典范之中。
从方法论的观点来看,朱子对“理一”与“分殊”的解释,实潜藏着某种方法论的个体论之思维倾向。《朱子语类》卷二十七及卷四十五解释“吾道一以贯之”时,充分展现方法论的个体论倾向。朱子说:“贯,如散钱;一,是索子。曾子尽晓得许多散钱,只是无这索子,夫子便把这索子与他。”[9]朱子以铜钱与绳索作比喻,主张必先积得许多铜钱,才有物可“贯”。朱子进一步解释说:
而今只管悬想说道“一贯”,却不知贯个甚么?圣人直是事事理会得,如云“好古敏以求之”,不是蓦直恁地去贯得它。……近见永嘉有一两相识,只管去考制度,却都不曾理会个根本。一旦临利害,那个都未有用处,却都不济事。吕伯恭向来教人亦云:“《论语》皆虚言,不如论实事。”便要去考史。如陆子静又只说个虚静,云:“全无许多事。颜子不会学,‘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勿失。’善则一矣,何用更择?‘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一闻之外,何用再闻?”便都与禅家说话一般了。圣人道理,都不恁地,直是周遍。10]
朱子在上文中一方面批评永嘉学派诸君子论史只考制度,而忽略人心等根本问题,可谓失之琐碎;但朱子另一方面又批评陆九渊(象山,1139—1193)只说“虚静”,不理会分殊之理。
再从朱子“理一分殊”说的整体特质来看,朱子也具有某种程度的“知识主义”的思想倾向,而与他的“理一分殊”及“格物穷理”等学说互相呼应。朱子说:“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盖能于分殊中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然后方知理本一贯。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11],他强调在“分殊”之中才能觅得“理一”的消息。诚如朱子所说,作为“普遍之理”的“太极”,实寓于作为“分殊之理”的“两仪”、“四象”或“八卦”之中。[12]
(二)朱子学中“理”的诡谲性
细绎朱子“理一分殊”说有关“理”的细部论述,我们可以归纳朱子思想中的“理”具有以下特点:首先,“理”是抽象而一元的概念;其次,“理”可以在林林总总的具体事实之中以不同方式呈现出来;第三,“理”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存在,永不灭绝;第四,“理”的延续或发展,有待于圣贤的心的觉醒与倡导;最后,在具体的历史流变之中所渗透出来的“理”具有双重性格,“理”既是规律又是规范,既是“所以然”又是“所当然”。朱子学中的“理”既属道德学与伦理学,又属宇宙论的范畴,而且两者融合为一。[13]
从“理”的发生程序与本质状态来看,朱子学中抽象而普遍的“理一”是从具体而特殊的“分殊”之中生成的,但是,一旦“理”被圣人从“事”中抽离而出或如朱子所说“流出来”[14]之后,“理”就取得了独立性与自主性,而不再受“事”所拘束,成为“多”之上的“一”(theoneoverthemany),因而对“多”具有支配力与宰制力。
三、全球化时代朱子“理一分殊”
说的新启示与新挑战
(一)新启示
从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观点来看,朱子“理一分殊”说最重要的新启示是:抽象而普世的规范,必须在具体而特殊的情境之中自然生成。我们从“全球化”的本质谈起。正如本文起首所论,全球化发展趋势强化了世界各地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纽约股市的变化连带影响东京、台北或上海的股票市场。全球化发展创造了表面的一体感,但在“地球村”的口号与荣景之下,却潜藏着巨大的压迫与宰制——全球化发展促使居于全球化中心位置的国家,对于居于全球化边陲位置的国家,更肆无忌惮的剥削与控制。居于全球化中心位置的国家掌控国际性政治组织如联合国、经济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WTO)、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会(IMF),也掌控全球最先进的航天科技、生命科学知识等,使全球化“中心”国家的影响力更是无远弗届。
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之后,不论在国际间或是在国内脉络,所得分配的不平等也更加严重。经济学者研究告诉我们:从1980年代以降,因全球化而带来的不平等日益严重,1980年代以后在寿命与教育方面虽然看似减缓了不平等的趋势,但是实际上可能只是假象而已。[15]“全球化”已俨然成为全球化发展的“中心国家”宰制“边陲”国家的凭借。
“全球化”趋势发展至今,之所以成为强凌弱、众暴寡的工具,原因甚多,最重要的原因是“全球化”成为抽离于世界各国之具体互动脉络之上的抽象理念或具有宰制力的机制,而不是处在于世界各国互动的具体脉络之中,而与时俱进、随时修正的潮流。
针对“全球化”趋势所创造的国际间以及各国国内的不平等现象,朱子学的“理一分殊”说有其新时代的启示。朱子强调“所谓理一者,贯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离耳”[16],这句话启示我们:作为一种理念或某种机制的所谓“全球化”,应该只能存在于各国的互动关系之中。换言之,作为抽象性的“全球化”,只能存在于具体性的国际关系之中,才能随时调整,与时俱进,才能免于成为国际上强权压制弱国,国内的资产阶级压迫农工阶级的借口。
(二)新挑战
但是,从21世纪的今日世局来看,“全球化”显然已成为抽离于各国具体的国际关系之上的具有宰制力的论述与机制,而被全球化的“中心”国家所垄断,“全球化”在很大的程度上与范围内,等同于“美国化”,早在1991年就有人为文指出,总部设在美国的全球性跨国大公司的领导阶层,只有2%不具有美国国籍的事实。[17]这种状态在21世纪的今日,并无重大改变。
正如朱子“理一分殊”说中“理”的吊诡性一样,“全球化”论述就好像朱子的“理一”一旦被从“分殊”之中抽离出来之后,就取得了独立性,而被强者所垄断,成为压迫“边陲”国家与人民的工具。这种情况很像18世纪戴震(东原,1724—1777)痛批“理”学被统治者所利用而成为杀人之工具,戴震说:
今之治人者,视古贤圣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多出于鄙细隐曲,不措诸意,不足为怪。而及其责以理也,不难举旷世之高节,着于义而罪之。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18]
二百年前戴东原所谓“今之治人者”以“理”杀人的状况,很近似于21世纪的今天居于全球化“中心”位置的国家,以“全球化”这个“理”作为控制“边陲”国家的情形。用朱子的语言来说,“全球化”这个“理一”已经从世界各国的“分殊”这个具体情况中剥离出来,而成为全球政经秩序的掌权者手中玩弄的工具。“全球化”的吊诡性与朱子“理”的吊诡性,如出一辙。
为了进一步思考作为21世纪之“理”的“全球化”价值理念之吊诡性,我们可以再回到朱子“理一分殊”说中“理”与“心”之关系。朱子一向强调经由“格物致知”的程序之后,人的“心”可以有效地掌握并理解万物及宇宙之“理”,甚至可以达到他在<大学格物补传>所谓“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19]的境界。
朱子强调以人“心”掌握万物之“理”的这项思想遗产,对朝鲜时代(1392—1911)的朝鲜思想界影响极为深远,亦衍伸出两个新命题。正如我最近所指出的,朝鲜儒者从朱子学中进一步发展的第一项新命题是:以“吾心之理”贯通“万物之理”。[20]金谨行(字敬甫,号庸斋,1712—?)说: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者,一者,理也。贯者,心之事也。理在吾心,以吾心之理,贯乎万物之理也。[21]
朝鲜儒者金谨行将孔子的“一以贯之”解释为“理在吾心,以吾心之理贯乎万物之理”,所谓“理在吾心”一语显示相对于朱子的“穷理”之学而言的更进一步“内转”。
朝鲜儒者从朱子学所发挥的第二项新命题是强调“一本”与“万殊”皆本于心。17世纪朝鲜儒者朴知诫(字仁之,号潜治,1573—1635)说: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朱子曰:“人之为学,心与理而已”。“心”即“一本”也;“理”即“万殊”也。古圣人垂教之说,无非一与万而已。从事于小学而存此心于端庄静一之中者,从一上做工也;从事于格致,而穷众理之妙者,从万上做工也。…自一而万,自万而一,复自一而为万,乃圣人之学也。一本万殊,两仪之象也。知上行上皆有此两端。知觉不昧之在心,曰:“知上之一本”。明烛事物之理,曰:“知上之万殊”,一心之浑然在中,曰:“行上之一本”;躬行践履之在事物,曰:“行上之万殊”,所谓忠恕是也。[22]
朴知诫所说的这一段解释之特殊之处,在于将朱子的“一本”与“万殊”,再细分为“知上之一本”与“知上之万殊”,以及“行上之一本”与“行上之万殊”,而归结在“心”的作用之上。金谨行进一步发挥朝鲜儒者将“一本”与“万殊”汇归于“心”之上的解释立场,他说:
以道之总在一心者贯之于万事,则为散殊之道。以道之散在万事者本之于一心,则为总会之道。[23]
金谨行以“心”将“散殊之道”与“总会之道”加以统一,确较朱子之解释更进一层。
从朝鲜朱子学者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朱子“理一分殊”说中的“理”,如果完全归结于人(尤其是圣人)的“心”的解释与掌握,就难以避免“理”的解释之任意性,并且使“理”失却其客观性,易于被少数人所掌握与宰制。21世纪的“全球化”的解释权之被强权国家所宰制,在某种意义上正与朱子与宋儒的“理”在18世纪中国之被统治阶级所掌握相似。
朱子“理一分殊”说中的“理”之有其被垄断这项危险性,更因朱子的“理”之同源性而大大提高。在《朱子语类》卷18中,就有学生请教有关“万物各具一理,而万理同出一原”这个问题,朱子回答说:
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24]
朱子虽然强调“理”的同源性(“理皆同出一原”),但是,他也同时强调在实际运作的层次上,各种事物的“理之用”则有互不相同的特殊之理,而且各个具体的事物又分享普遍的“一理”。
从朱子的理论来看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趋势,我们可以说,不仅各个不同的文明或国家的分殊之“理”剧烈碰撞,甚至“理”的解释权又被居于全球化的“中心”位置的国家所垄断,“全球化”发展竟为人类前途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那么,如何从朱子的“理一分殊”说中提炼新意义以因应21世纪“全球化”的这项新挑战呢?21世纪全球化发展使世界各文明、各国家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与日俱增,各种源自不同历史与文化背景的“理”也互相碰撞激烈冲突。因此,如果朱子的“理一”只有一人或少数人的“心”才能加以解释或掌握,恐难以适应新时代的挑战,而必须别创新解。
四、结论:在诸多“理”之中求同存异
在上文的论述中,我们通过朱子的“理一分殊”说,分析21世纪全球化时代中,诸多的国家之“理”互相冲突而并存,“理”被全球化的“中心”国家所控制,以致成为压制“边陲”国家的工具。我们也指出,朱子“理一分殊”说中的“理”贯通并浸润在诸多分殊的“事”之中。但是,吊诡的是,一旦“理”从“事”中“流出来”(朱子用语)之后,“理”取得了独立性,因而容易因为“去脉络化”而被少数人或强权所控制,而反过来压制分殊的“事”。因此,本来是“多”中的“一”,遂转化成为“多”上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里,“理一”可能必须转化为诸多分殊而并存之“理”,才能适应不同的文化传统在文明对话新时代的需求。而且,我们也必须将朱子学中的“理一”所潜藏的从属原则(Principle of Subordination)——指文化中的诸多主体(如社会、经济等主体)均服从于单一主体(如政治主体)的支配——逐渐转化为“并立原则”(Principle of Coordi-nation)——指文化中的诸多主体处于并立及竞争之状态。[25]
在21世纪各文化传统所蕴蓄的多元之“理”互相对话的新时代中,求同存异是一条必然的道路。传统中华文化重视“同”而忽视“异”。古代儒家就非常强调“同”的价值。孟子在谈到舜的美德时曾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26]他又认为“尧舜与人同耳”[27]。诚如余英时(1930— )所指出的,在中国思想史上,“同”之作为一个价值意识一直受到强调,到了汉末,“异”之作为价值意识才受到重视,这与汉末儒学衰微,新道家兴起,“个人”被重新发现等发展都有关系。[28]因此,就21世纪大中华文化圈及其与世界之互动而言,如何开发求“同”而存“异”的价值观,如何落实宋儒陈亮(同甫,1143—1194)所谓“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29],如何实践明儒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1465—1517)所说的“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30]的原则,就成为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
——关于朱熹“敬论”的几个问题
吴震
前言
众所周知,在宋明理学史上,自北宋程颐(世称伊川先生,1033—1107)提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1]以来,经南宋朱熹(号晦庵,1130—1200)的阐扬发挥,主敬与致知构成了缺一不可、互相为用的一套工夫论体系。就朱熹哲学而言,主敬思想无疑是其整个理论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就当今中文世界有关朱熹哲学的研究来看,却有不少重量级的经典论著对朱熹之“敬论”竟然未加重视或论之甚略,这里我们仅举三例,例如牟宗三《心体与性体》[2]第三册为朱熹专论,其中就看不到有关朱熹敬论思想的章节安排,只是在讨论朱熹心论问题时顺便涉及且有严厉之批评;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3]一书之于朱熹有专章论其心而无专章论其敬;陈来《朱熹哲学研究》[4]也没有安排章节来专论朱熹敬说,只是在后来撰述的《宋明理学》[5]这部教材中对此有概括性的论述。[6]
最近牟宗三弟子杨祖汉发表了《从朱子的“敬”论看朱子思想的归属》[7]一文,打破了以往略于朱熹主敬思想之讨论的局面,而以“敬的形态”来为朱熹思想定位[8],指出朱熹之言敬是由敬“契入本心”,而恭敬亦是“道德心本有之内容”,[9]故可说朱熹的主敬思想“确立了儒家重恭敬这一义理形态,彰明了恭敬之心之道德涵义”。[10]依杨文,如此理解朱熹思想之形态,庶可对朱熹的心性论、工夫论有更妥当的整体理解,“不会将朱子学归于意志的他律的形态,以其言持敬,只是空头的涵养,也不会忽略朱子重礼文的部分。”[11]不用说,对朱子学的这一同情之了解难能可贵,不唯与牟宗三判朱熹为“别子”异趣,更可启发吾人以朱熹敬论为切入点来重新省思朱子学的思想特质及其相关理论问题。不过,以笔者之见,若依事实判断而言,朱熹思想固然重视主敬以涵养心性,然其工夫理论亦重格物穷理,更重要的是,若从理论判断的角度看,朱熹之敬论何以能使良心呈现出来,也就是主敬工夫的依据问题依然存在。正如杨文所言,正是这一点“值得深入研究”。[12]而这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
事实上,朱熹的敬论与其心论、性论有十分密切的理论关联。正如朱熹己丑之悟所表明的那样,朱熹之所以归宗于二程主敬,乃是缘自其对“心为已发”、“性为未发”之心性问题的最终解决。笔者最近撰文指出,由于朱熹之论心始终将视野限于工夫论领域而缺乏本体论的关怀,故其心论详密有余而意欠圆融。尽管从儒学传统看,孟子所言“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可谓是儒学即工夫而言心的一句至理名言,宋明理学家也几乎无不奉为圭臬,由此以观朱熹所言“心是做工夫处”这一心论观点亦应是儒学的一种理论形态。然而,朱熹之心论何以成立,则需要与其敬论思想合以观之始能获得充分之了解,因为在朱熹的理论构造中,“心是做工夫处”也只有在其“敬义夹持”的“居敬”理论中才能落实。[13]反过来说,若要真正理解朱熹的心性论,亦须对其主敬思想的理论构造有一相应的了解。这便是继拙文之后,进而探讨朱熹敬论的一个缘起。
本文的任务分三步走,首先从概念史的角度来探讨朱熹敬论的问题之由来;其次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朱熹敬论的几个重要方面做一番梳理;最后对其敬论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思考,以就正于学界。
一、问题的由来
朱熹对程颐评价之高,这是众所周知的,例如他认为程颐的“性即理”揭示了“颠扑不破”的普世真理,[14]而且是“自孔孟后,无人见得到此,亦是从古无人敢如此道”[15]的。事实上,朱熹对程颐的称赞还不止于此,他认为程颐的主敬思想也同样是对儒学的一大贡献,甚至是孔子以后、秦汉以来的一大发明,他说:
圣人言语,当初未曾关聚,如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等类,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关聚说出一个敬来教人。[16]
自秦汉以来,诸儒皆不识这敬字,直至程子方说得亲切,学者知所用力。[17]
程先生所以有功于后学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18]
不用说,我们可以从这种赞美声中读取出朱熹自身的思想倾向:这被程子“关聚说出”的、“说得亲切”的、“有功于后学”的“敬之一字”无疑也正是朱熹所取的一个思想立场。
朱熹曾对宋代理学以来的“敬论”史及其内涵有一个概要性的总结:
然则所谓敬者,又若何而用力邪?曰:程子于此,尝以“主一无适”言之矣,尝以“整齐严肃”言之矣。至其门人谢氏之说,则又有所谓“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说,则又有所谓“其心收敛不容一物”者焉。观是数说,足以见其用力之方矣。[19]
这是将程颐的“主一无适”、“整齐严肃”与程门弟子谢良佐(号上蔡,1050—1121)的“常惺惺法”《上蔡语录》卷中)以及尹焞(号和靖,1061—1132)的“其心收敛不容一物”(《和靖尹先生文集》卷八《师说附录》)作为理学主敬思想的四大要点,这个说法在《朱子语类》也到处可见[20],可谓是朱熹对主敬问题的一个基本认识,也是程颐之后朱熹之前,理学之论主敬的主要脉络。
质言之,主一无适是就心上做工夫,保持意识的高度集中而不走失;整齐严肃则是就外貌上做工夫,要求仪容整齐、举止端庄;常惺惺法则是“心不昏昧之谓”[21],常令此心保持唤醒而不间断的状态,重在“唤醒”而令此心不间断;此心收敛不容一物则是“心主这一事,不为他事所乱”[22]之意,重在“收敛”而令此心为主。显然,除了整齐严肃是就外貌仪容而言以外,其余三种工夫均与内心有关,故可归为一类。至于外貌与内心的关系,依程颐,又可叫做外与中的关系,如其《四箴·视箴》所言“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强调通过“制外”——即外部的整齐严肃,以通向“安内”——即内心的安定宁静。然而“制外”与“安内”又是互为连贯的,程颐《四箴序》指出“由乎中而应乎外,制于外所以养其中也”,便是对主一无适与整齐严肃这套主敬工夫之关系的恰当说明。要之,“制外”和“养中”均属“涵养”工夫,故结论可以说:“敬只是涵养一事。”[23]
不过,这里的“内外”只具相对意义而不能截然两分,因为事实上,若从程颐的另一重要命题“敬义夹持”的角度看,相对于“义外”而言,“直内”的敬字工夫便“只是内”,[24]即意谓敬是一种内在工夫。程颐说:
君子主敬以直其内,守义以方其外。敬立而内直,义形而外方。义形于外,非在外也。敬义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25]
可见,敬是一种“内”的工夫,“方其外”的“义外”工夫最终也取决于“直其内”,所以说“义形于外,非在外也”。程颐虽然注重“整齐严肃”作为主敬工夫的入手处,强调从外貌上做工夫的基础性意义,但在他的问题意识中,不论是端正容貌还是集中意识,都最终指向“直内”的内心工夫。甚至可以说,程颐之所以极力倡导主敬工夫论,其问题意识就在于如何安定人心。
例如程颐指出: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个翻车,流转动摇,无须臾停,所感万端。又如悬镜空中,无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学则却都不察,及有所学,便觉察得是为害。著一个意思,则与人成就得个甚好见识?心若不做一个主,怎生奈何?张天祺昔常言,“自约数年,自上著床,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后,须强把佗这心来制缚,亦须寄寓在一个形象,皆非自然。君实自谓“吾得术矣,只管念个中字。”此则又为中系缚,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虑,冥然无知,此又过与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常若有两人焉,欲为善,如有恶以为之间;欲为不善,又若有羞恶之心者。本无二人,此正交战之验也。持其志便气不能乱,此大可验。要之,圣贤必不害心疾,其佗疾却未可知。佗藏府只为元不曾养,养之却在修养家。[26]
程颐以“翻车”来比喻“人心作主不定”的各种现象,如“流转动摇,无须臾停,所感万端”等等;又以“悬镜”为喻,指出人心作主就好比“悬镜空中”,万物自来而又无一定之形状可以把捉(“有甚定形”),因此重要的是,人心作主而又不能“著一个意思”。他所列举的张天祺“不思量”和司马光“念中”的事例则从一个侧面表明,寻求心定乃是当时的一个普遍问题。
不过在程颐看来,张天祺和司马光在寻求心定的问题上犯了“著一个意思”的根本错误,具体表现为“寄寓在一个形象”——亦即追求某种“定形”,而这个错误的本质在于二心“交战”(“本无二人”的二人,意谓二心)、“皆非自然”。须指出,这里“交战”一词生动地揭示了“人心作主不定”的所有症结之所在——即程颐所说的“心疾”,而且是所有疾病中最为根本的疾病,所以说尧舜等圣贤或许也有其他疾病,但却不会有“心疾”,反过来说,正是因为没有“心疾”,所以尧舜才得以成为尧舜。针对常人的“心疾”,程颐提出的对治方法则是孟子的“持志养气”说,以为这是从根本上克服“心疾”的良方,因为“持其志便气不能乱”。事实上,程颐是以孟子的“持志养气”作为主敬思想的理论支持,关于这一点,这里也就不必深究了。
毫无疑问,以上这段叙述所揭示的“人心作主不定”的问题,其实也就是如何解决“心疾”的问题,程颐所得出的结论既不是张天祺的“不思量”,也不是司马光以“中”定心,而是以主敬来对治“心疾”,因为主敬才是解决“心主不定”的根本方法,换言之,程颐在工夫论上强调的主敬工夫所要应对的问题就是人心如何做主以及如何克服二心交战的问题。事实上,就宋代以来的理学思潮来看,这个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不妨来看两段程颐的语录:
学者先务,固在心志。有谓欲屏去闻见知思,则是“绝圣弃智”。有欲屏去思虑,患其纷乱,则是须坐禅入定。如明鉴在此,万物毕照,是鉴之常,难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万物,亦难为使之不思虑。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如何为主?敬而已矣。有主则虚,虚谓邪不能入。无主则实,实谓物来夺之。今夫瓶罂,有水实内,则虽江海之浸,无所能入,安得不虚?无水于内,则停注之水,不可胜注,安得不实?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则他事更不能入者,事为之主也。事为之主,尚无思虑纷扰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且欲涵泳主一之义,一则无二三矣。[27]
人多思虑不能自宁,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于事,为人君止于仁之类。如舜之诛四凶,四凶已作恶,舜从而诛之,舜何与焉?人不止于事,只是揽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则是役物。为物所役,则是役于物。有物必有则,须是止于事。[28]
可以说,以上两段语录集中反映了程颐主敬思想的问题意识,程颐所欲解决的根本问题无疑在于人心做主这一点。以下,我们对这两段语录略做解释。
在第一段,程颐明确指出“学者先务固在心志”,重要的是,若要使不得不交感、不得不思虑的人心安定下来,“唯是心有主”。那么“如何为主”呢?答案只有一个:“敬而已矣。”为什么呢?程颐指出:“有主则虚,虚谓邪不能入;无主则实,实谓物来夺之。”这是以虚实来做一个比喻,人心之虚,故能应万事,人心若实(如心中若有一物),则人心已然有种种阻塞,便不能“作主”;程颐进而指出:“事为之主,尚无思虑纷扰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这是说,“止于事”是使人心作主的一个条件,况且使人心“主于敬”,则更无“思虑纷扰之患”。[29]那么,究竟如何做到“主敬”呢?程颐提出了一个命题式的答案:“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须是直内,乃是主一之义”。这是将“主一无适”和“直内方外”结合起来——用程颐的另一种说法,亦即敬义夹持的方法,做到内外交互使用、合作并进,便是主敬工夫的全部内容。这样一种主敬工夫,在程颐看来,就是“涵养”工夫,其下手处不能脱离“事”(如“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其最终目标则是“自然天理明”。
在第二段,程颐以舜诛四凶为例,一方面强调了人心做主须落实在“事”上,即所谓“止于事”,同时又强调“止于事”必须按照“有物必有则”的原则顺而从之,而不能强“揽他事”,他以“物各付物”而不为物“所役”作为定心的重要方法,告诉人们实现“作得心主”的关键在于“止于事”而又不为“事”所扰乱。在这里程颐虽然没有提到“主敬”,然而事实上若要做到“作得心主”,唯有从敬入手,这就是程颐通过对主敬内涵的阐发而欲再三强调的由敬定心、心要做主的思想。合而言之,以上这套说法,既是程颐对其主敬思想的完整解释,同时也是程颐何以极力主张主敬工夫的思想缘由。
那么,对于自觉继承了程颐主敬思想的朱熹来说,他强调主敬的问题意识究竟何在呢?
二、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
朱熹之言敬,不胜枚举,所涉义理极为繁复。不过他在《大学或问》一上来讲到大学与小学之分的问题,就对“敬”字工夫在儒学体系中的重要性表明了一个基本的看法:
盖吾闻之,敬之一字,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为小学者,不由乎此,固无以涵养本原,而谨夫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与夫六艺之教。为大学者,不由乎此,亦无以开发聪明,进德修业,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发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为说焉。不幸过时而后学者,诚能用力于此,以进乎大,而不害兼补乎其小,则其所以进者,将不患于无本而不能以自达矣。其或摧颓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则其所以固其肌肤之会、筋骸之束,而养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于此,而不患其失之于前也。……若徒归咎于既往,而所以补之于后者,又不能以自力,则吾见其扦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颠倒,眩瞀迷惑,终无以为致知力行之地矣,况欲有以及乎天下国家也哉![30]
在这段叙述中,朱熹首先将“敬之一字”定位为儒家圣学“成始成终”之工夫,继而论述了此一工夫可由小学阶段的“涵养本原”而进之于大学阶段的“进德修业”,最终实现“明德新民”、“治国平天下”这一儒家终极理想。须指出的是,这里虽将主敬比作小学工夫,但并不意味着主敬只是针对15岁之前的小学之工夫而言,其方法也不仅仅是“洒扫应对进退”三项工夫或“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而已[31];朱熹之用意在于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大学虽是针对15岁之后的“大人”而言,但“大学之道”则是一以贯之的,也必然表现在小学工夫的过程当中,这就是“敬之一字”。所以朱熹的意思并不是说,先在小学阶段做一番“涵养本原”的主敬工夫,然后在大学阶段才能进之于格物工夫,事实上,在大学阶段何尝不需要主敬?所以程子在讲格物的同时,也必然讲主敬。朱熹最后指出,如果我们只是把主敬看作是以往的小学阶段之工夫,以为当今做大学工夫已经无法弥补而只能放弃主敬,那么就必将导致“身心颠倒,眩瞀迷惑”,根本不能有进于“致知力行”,更谈不上去实现“治国平天下”。要之,朱熹在这里阐述的核心思想是:“敬之一字”是贯穿小学和大学的根本工夫。
既然主敬是贯穿小学与大学的“涵养本原”之根本工夫,那么具体地说,主敬又主要是一种什么样的工夫呢?显然,虽说主敬贯穿于“洒扫应对”及“致知力行”,但主敬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洒扫应对”或“致知力行”。同样,虽说涵养本原之主敬含有“养其良知良能之本”的涵义,但“敬之一字”本身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良知良能”。其实在我们看来,若以一言以蔽之,则可说“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32]乃是朱熹之敬论的最为重要的核心观点。
对照以上程颐言敬重在心要作主、以心为主的观点,可以说朱熹之论敬同样重在心做主宰这一点上,只是朱熹更为突出强调“自做主宰”,也就是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心的“自存”义、“自省”义。接下来,我们就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朱熹为什么强调此心自做主宰?一是敬又如何才能使此心自做主宰?在本节中,我们首先来考察第一个“为什么”的问题,亦即朱熹之论敬的思想缘由、问题意识究竟何在的问题,至于第二个“怎么做”的问题,则有待以下各节来展开讨论。
如所周知,朱熹的两次“中和”之悟,均与心性问题有关,特别是标志着朱熹思想最终确立的第二次己丑之悟,不惟从根本上解决了心性的名义问题——即如何从哲学上来定义心性关系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朱熹确立了以“敬”为“日用本领工夫”的思想——即居敬工夫。向来讨论朱熹“中和”之悟,较多关注朱熹由“心为已发,性为未发”转向“性为未发,情为已发”而心贯未发已发的心性名义问题之解决,并以此作为朱熹最终建立心性情三分构架之理论的标志。当然,这一分析有诸多朱熹文献可以提供支持,无疑有充分的说服力。然而,就在己丑之悟以后,朱熹自己是怎么说的呢?他在己丑之悟以后的第一时间,给湖南学者发出的那封著名的《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中这样说道:“……乃知前日之说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当,而日用功夫全无本领,盖所失者不但文义之间而已。”在这里,朱熹无疑表明以往在心性名义问题上的“所失”虽大犹小,而在日用本领工夫问题上的“所失”虽小犹大。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朱熹所谓的“日用功夫全无本领”,现在我们就来读一读《与湖南诸公论中和第一书》:
《中庸》未发已发之义,前此认得此心流行之体,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遂目心为已发,性为未发。然观程子之书,多所不合,因复思之,乃知前日之说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当,而日用功夫全无本领,盖所失者不但文义之间而已。
按《文集》、《遗书》诸说,似皆以思虑未萌,事物未至之时为喜怒哀乐之未发,当此之时,即是此心寂然不动之体,而天命之性当体具焉。以其无过不及,不偏不倚,故谓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则喜怒哀乐之性发焉,而心之用可见,以其无不中节,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此则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
然未发之前不可寻觅,已发之后不容安排。但平日庄敬涵养之功至,而无人欲之私以乱之,则其未发也,镜明水止,而其发也,无不中节矣。此是日用本领工夫。至于随事省察,即物推明,亦必以是为本,而于已发之际观之,则其具于未发之前者,固可默识。
故程子之答苏季明反复论辨,极于详密,而卒之不过以敬为言。又曰“敬而无失,即所以中”,又曰“人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养须是敬,进学则在致知”,盖为此也。向来讲论思索,直以心为已发,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识端倪为最初下手处,以故缺却平日涵养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扰扰,无深潜纯一之味,而其发之言语事为之间,亦常急迫浮露,无复雍容深厚之风。盖所见一差,其害乃至于此,不可以不审也。……[33]
此函颇长,然其要点无非有二:一是朱熹反省了“以心为已发”这一心性名义上的错误,导致平常一味就已发之后着手做“察识端倪”的工夫而“欠缺平日涵养一段工夫”;一是朱熹明确了“平日庄敬涵养”才是“日用本领工夫”。他引用三段有关“敬”的语录,以强调程子的为学宗旨“不过以敬为言”,这也就意味着朱熹自己的主敬思想的确立。
当然,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封书信所透露出来的思想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其中令人关注的是相对于“平日涵养”而言的“察识端倪”。不用说,于宋代思想之史实稍熟悉者便可知这是指以胡宏(号五峰,1102—1161)为首的湖湘学派的标志性观点:先察识后涵养。朱熹的己丑之悟正是标志着他从湖湘学的先察识后涵养这一工夫论思想的阴影中摆脱了出来,确立了以敬来贯穿先后、上下、动静以及未发已发的工夫论立场。然而,从理论上看,先察识后涵养的主张又究竟错在哪里呢?也就是问,朱熹对湖湘学的批评与其主敬思想的确立又有何理论上的必然关联呢?
我们知道,其实胡宏所谓的“察识”工夫也就是“识心”工夫,因为察识的对象就是已发之心,若已发之心为良心则存而养之,若已发之心为人欲则制而去之,可见察识工夫的理论预设是“心为已发”,由于“此心在人,其发见之端不同”,因此工夫的关键就在于“识之而已”。[34]依胡宏,所谓“察识”是就已发之际,对已发之心做正面的自觉反省,然后“操而存之,存而养之,养而充之”,[35]这就与杨时(号龟山,1044—1130)至李侗(世称延平先生,1093—1163)的“道南一脉”所言由静摄心并于未发之际涵养之指向不同。在中和新悟之前,朱熹的工夫论便在湖湘一路与道南一路之间流连忘返,结果与此二者均未能相契[36],最终向程颐的主敬说回归。
要之,正是对于湖湘学的这一“知之而已”的“识心”说,朱熹在己丑之悟之后,开始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态度。为什么呢?因为在朱熹看来,心是知觉,心自会识,如果说“识心”,那么这个“识”的主体又是谁呢?难道是以一个心去“识”另一个心?朱熹打了一个比方,就好比人的眼睛自会看见东西,但是眼睛绝不能看自己的眼睛,他说:
如湖南五峰多说“人要识心”。心自是个识底,却又把甚底去识此心?且如人眼自是见物,却如何见得眼?故学者只要去其物欲之蔽,此心便明。如人用药以治眼,然后眼明。[37]
所论近世识心之弊,则深中其失。古人之学,所贵于存心者,盖将即此而穷天下之理。今之所谓存心者,乃欲恃此而外天下之理,其得失之端,于此亦可见矣。故近日之弊,无不流于狂妄恣肆而不自知其非也。[38]
这里的第一段是说,胡宏“识心”无非是以心识心,其错误犹如以“人眼”见“人眼”,而在朱熹看来,“人眼自是见物,却如何见得眼”,这是非常荒唐的。第二段是指“识心”说一味向内用功而忘却了天下之理——亦即置穷理工夫于不顾。朱熹以为以上两点便是湖湘学“识心”说的主要弊病。
关于“识心”何以导致排斥穷理,这里且不深究,重要的是朱熹的第一点批评,正是在这一批评的背后,朱熹想要表达的一个观点十分重要。可以这么说,假设识心说成立的话,就必将导致两种后果:要么承认在人心之上之外存在另一个心之本体[39],要么承认心既是知觉的主体又是知觉的客体。当然须看到,这两种后果的假设其实都是朱熹依其理论所做的诠释和判断,未必就是湖湘学主张“识心”的必然结论。若依胡宏,心体本无善恶,心体之发动有善有恶,故于心之已发之际察识其端倪,见其善者涵养之,见其不善者克服之,此便是胡宏“识心”说的真实涵义,其中并没有“以心识心”之意。但不管怎么说,在朱熹看来,上述两种后果都是非常严重的错误,更是己丑之悟后的朱熹所遇到的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若结合本节开首所提示的“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的命题来看,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此心何以能做到“自做主宰”?
三、以敬为主而心自存
事实上,自己丑之悟后,朱熹的思想体系虽已基本确立,但他所面对的问题仍有许多,其中之一就是与其“心论”密切相关的工夫论问题。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同时,他所要面对的却是当时的湖湘学派,而他所用的理论武器便是由程颐那里继承而来的主敬思想。那么,敬与心又有什么理论上的关联呢?
朱熹曾在给当时湖湘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张栻(号南轩,1133—1180)的书信中指出:
以敬为主,则内外肃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为主而欲存心,则不免将一个心把捉一个心。外面未有一事时,里面已是三头两绪,不胜其扰矣。就使实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释之异,亦只于此便分了。如云“常见此心光烁烁地”,便是有两个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见者是真心乎?[40]
这里讲了三层意思:第一,朱熹从正面指出“以敬为主”的主敬工夫能够使内心和外表获得整齐肃然的效果,并使内心达到“不忘不助”的状态,最终实现“心自存”的境地;第二,如果不以敬为主而企图做一番“存心”工夫,则其结果必将导致“将一个心把捉一个心”,还未等到应接事物,内心已经纷乱不堪,退一步说,即便能做到“把捉”此心,这种“把捉”方法本身已是“大病”,何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第三,是根据“以敬为主”、“而心自存”的工夫去做,还是按照“将一个心把捉一个心”的方法去做,这是儒家与佛教的根本分歧之所在,佛教所说的“常见此心光烁烁”,其实已经表明存在着两个“主宰”,不知到底“光”之本身是“真心”?还是“见”此光者是“真心”?
无疑地,朱熹在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愈发关键,一言以蔽之,由主敬立场出发,便可实现此心“自存”而从根本上消解二心之间的“把捉”问题(即“一个心把捉一个心”),这正是朱熹敬论的一个核心观点。那么,何谓“把捉”呢?事实上,由这封寄给张栻的书信来看,朱熹的话是有针对性的,他所针对的就是湖湘学的“识心”说。在朱熹看来,正是胡宏等人主张的“识心”说未免陷入“以一个心把捉一个心”的弊端。
上面提到胡宏所言“察识”工夫其实就是“识心”工夫,对此,我们须再做稍详的探讨。向来以为,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胡宏的思想经由其父胡安国(谥文定,1074—1138)、谢良佐而上溯至程颢(号明道,1032—1085),相对于程颢重“识仁”,胡宏则重“识心”。他说:“知天之道,必先识心,识心之道,必先识心之性情。”(《知言》卷五)可见,他将“识心”提到了“知天之道”的高度,同时他也强调“识心”须从“识心之性情”入手。那么,何谓“心”呢?在胡宏,大致可以两段话来阐明:“心无不在,本天道变化,与世俗酬酢,参天地,备万物,人之为道,至大也。”(《知言》卷五)“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知言》卷一)可见,就客观上看,心是一种“参天地,备万物”的存在,能与天道为一;从主观面看,心具有“知天地,宰万物”的能力,最终达到“心以成性”。牟宗三以“以心著性”四字来概括胡宏思想之宗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心性关系问题上,胡宏指出:“心纯则性定而气正。”(《知言》卷二)“气之流行,性为之主;性之流行,心为之主。”(《知言》卷三)“未发只可言性,已发乃可言心。”(《知言》卷四)“圣人指明其体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知言》卷六)“有而不能无者,性之谓欤!宰物不死者,心之谓欤!”(《知言》卷四)再三强调“心”是工夫的着手处、落脚点。对于胡宏以上所言,唐君毅总结道:
观此五峰之言,乃明以心为形而上的普遍而永恒之一流行之体,而大同于象山之所谓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之言。……此所谓心之已发,同于心之呈现,故无论在事物思虑之交,或无思无为之际,但有此心之呈现,即是发。……故性之流行,心为之主,而性亦由心而成。……心乃居于一切有形有气者上一层次,与形气不直接相关者。[41]
这是说胡宏所言“心”乃一形上的普遍之心体,同于象山心学意义上的“吾心”,由此以观胡宏所言“心之已发”,实即“心之呈现”之意,而“性之流行”亦取决于“心之呈现”,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性亦由心而成”。总之,胡宏所说的“心”是超越于形气之上的本体存在。据此,胡宏所谓的“识心”之“识”同于程颢的“识仁”之“识”,“皆当顺孔子所谓默识之识去了解”。何谓孔子的“默识之识”?唐君毅进而指出:“孔子之默识,正当为一无言之自识,而自顺理以生其心者,固非往识事一物、一对象、而涵把捉或捕捉意味之认识也。”[42]由此推知,故胡宏“识心”之“识”绝非是以外在事物为对象的认识活动意义上的“识”——内含把捉或捕捉之意味,而是指向内心的一种“默识”——亦即“无言之自识”。换言之,胡宏“识心”之“识”绝非寻求把捉之意,而是对心体的一种“默识”。唐氏此说值得参考。
不过,唐君毅的上述分析是针对朱熹对胡宏“识心”的批评而提出的反批评,然在朱熹则未必能完全承受,其云:“若‘默而识之’,乃不言而存诸心,非心与理契,安能如此!”[43]意谓“默识”已是“心与理一”之境界,非常人所能做到。故在朱熹看来,胡宏的“识”谈不上是什么“默识”,而仍然是一种“把捉”而已。更重要的是,朱熹认为若依胡宏所说,在心之已发处去做察识之工夫,则将导致“此心遂成间断”之后果,而且若就“已放之心”而后去察识、操存,则其工夫转辗繁难而“无复有用功”之处,如果总是等待已发之后,才去察识操存,其结果也不过是“发用之一端”而已,对于心体之“本源全体”未能做到“一日涵养之功”,以为由此“扩充”便可达到“与天同大”,也就未免太过狂妄了[44]。在这里,朱熹显然强调工夫不能片面地追求于心之已发后察识,更有必要在未发前涵养“本源全体”,并以此来打通未发已发之工夫。此可见朱熹主敬之最终确立,与其反省湖湘学“先察识”之工夫理路密切相关,其关节点有二:一是“察识”已不免“把捉”之意,与儒学所言操存涵养此心而令此心自做“主宰之味不同”,即所谓“今人著个‘察识’字,便有寻求捕捉之意,与圣贤所谓操存、主宰之味不同。……如胡氏之言,未免此弊也”[45];一是若无主敬之涵养工夫而欲察识已发之心体,则终无成功之日,即所谓“若必待其发而后察,察而后存,则工夫之所不至者多矣”[46],“盖发处固当察,但人自有未发时,此处便只合存,岂可待发而后察、察而后存耶?”[47]正是针对以上两种弊端,所以朱熹强调以敬为主而心自存。
至此,我们终于了解朱熹之主敬并非单纯地向程颐思想的回归,而是通过对湖湘学派(亦含道南一派)的反省与批判而逐渐形成的,他所强调的主敬更为强调心在未发与已发的过程中自做主宰。当然,心之主宰义也是程颐主一以及胡宏识心的固有主张,但朱熹论心之主宰则强调须由敬契入,以提撕唤醒心的自存自省,而这一点才是朱熹敬论的最大特色之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朱熹说敬就是心的自做主宰处。
其实,从字义上说,敬就是提撕唤醒、令其警觉之意,所谓心的自存自省,也就是在此意义上说的,朱熹指出:
“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无事时,且存养在这里,提撕警觉,不要放肆。到讲习应接时,便当思量义理。[48]
敬是个莹彻底物事。今人却块坐了,相似昏倦,要须提撕著。提撕便敬;昏倦便是肆,肆便不敬。[49]
此一个心,须每日提撕,令常惺觉。[50]
何者为心?只是个敬。人才敬时,这心便在身上了。[51]
只敬则心便一。[52]
敬者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本根也。[53]
可见,提撕警觉便是涵养用敬之意。但须注意的是,敬毕竟不是心体本身,敬只是一种工夫,所以可以用“持”、“居”、“主”、“存”等动词加在“敬”字之上,如其所云:
摄心只是敬。[54]
只是要收敛此心,莫要走作,走作便是不敬。[55]
人能存得敬,则吾心湛然,天理灿然,无一分着力处,亦无一分不着力处。[56]
这都是说,敬是一种工夫,敬之本身不是湛然之“吾心”或灿然之“天理”。所以,朱熹极力反对在主敬过程中去寻求什么“敬之体”,例如:
敬只是敬,更寻甚敬之体?[57]
静坐而不能遣思虑,便是静坐时不曾敬。敬则只是敬,更寻甚敬之体?[58]
其实,在朱熹,敬并不是如性理那样的终极实在,也不是心之本体(朱子学意义上的心之本然状态)之本身,故根本谈不上“敬体”这一概念。
然而,何以又有所谓“敬之体”的问题出现呢?这部分原因也许出在朱熹自己的某些表述,例如他说:“敬字通贯动静,但未发时,则浑然是敬之体。非是知其未发,方下敬底工夫也。”[59]然细按其意,“体”字并非实指,意谓未发正是做主敬工夫的理想状态。不过,朱熹接着又说:“既发,则随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60]这样一来,“敬之体”与“敬之用”成为相对而言的对句,不免引起后人将“体用”套在对敬的解释上,仿佛“敬”是一种有体有用的独立存在。诚然,从名义的角度看,以体用言敬,确有失严密。然朱熹无非是借“体用”一语以表明持敬工夫贯穿于心之未发与已发,并没有将敬字本身提升至本体地位的丝毫想法。
问题在于,既然“敬”的工夫能令此心“自做主宰”、“自省自存”,那么这个被称为“敬只是敬”的工夫本身是否需要由“心”来主导?事实上,从学理上说,我们可以问:敬的工夫何以只是敬的工夫而已?如果没有“心”(且不论是否是孟子的本心抑或是象山的吾心、阳明的良心)的引领,敬的工夫何以可能?更为直截了当地问,敬与心究竟何者为先(非时间在先而是形上在先)?何者为本?能否用先后、本末、体用这类范畴来规定敬与心的关系——例如心本敬末、心先敬后、心体敬用?恕笔者直言,在朱熹的文字中,完全看不到有此类的说法,也就是说,在朱熹,他根本不曾想把敬字工夫的理据诉诸心体。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倒是赞同牟宗三以“空头的涵养”来批评朱熹之敬论,只是此所谓“空头”应理解为朱熹的主敬工夫缺乏心体的指引,而不是指朱熹主敬缺乏内容。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在结语中再做稍详的讨论。
四、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
按照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以敬为主而心自存等命题来看,敬是令此心“作主”、“自存”、“常存”的保证,但不能倒过来说,以心为敬作主。与此思路一致,朱熹还有一个重要说法,即“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而且朱熹将此提到了“为学”之“大要”的高度来加以肯定,换言之,以敬收心,可谓是朱子学的为学宗旨。他说:
为学有大要。若论看文字,则逐句看将去。若论为学,则自有个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个敬字与学者说。要且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放在模匣子里面,不走作了,然后逐事逐物看道理。尝爱古人说得学有缉熙于光明,此句最好。盖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为学者,要令其光明处转光明,所以下缉熙字(缉如缉麻之缉,连缉不已之意。熙则训明字)。心地光明,则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见得。且如人心何尝不光明?见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尝不光明?然只是才明便昏了。又有一种人自谓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见。似此光明,亦不济得事。今释氏自谓光明,然父子则不知其所谓亲,君臣则不知其所谓义,说他光明,则是乱道。[61]
这是说,做学问是有根本方法的,如果读书,可以逐字逐句地读,但若是说做学问,则自有根本之法,这就是程子向学者所说的“敬”。这个“敬”是什么意思呢?要而言之,就是要用“敬”来收敛身心,如同把身心放在一个“模子”里面那样,能使身心运作不走样,然后随事就物上去穷究事物之理。朱熹接着说:就本来意义上而言,心地原是“光明”的,本无污染,犹如人见他人做得对便说对,做得不对便说不对那样,心里面的是非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人心易受后天环境的不良影响,染上利欲熏心等毛病,使得心地昏暗了。至于佛教所说的“光明”则全不着地、脱离事物,如父子不知亲、君臣不知义,这种所谓的心地“光明”最为危险可怕。
朱熹在这里所欲表明的观点有互为关联的两层意思:第一,为学大要在于以敬之工夫来收敛身心;第二,这是由于人心“才明便昏了”的缘故。至于另一层意思——心地原是光明,则不是主敬工夫的前提设定。朱熹的思路是:心地虽然原本光明,但不可以光明之心去主导敬之工夫,否则的话,就必须承认有一个形上的、普遍的、永恒的心之本体或道德本心的存在。由此可见,朱熹所说的“光明”只是就心地的原初意义上而言,而非就心地的超越意义上立论。要之,不能在主敬工夫之前之上预设心之本体的存在,这是朱熹不可退让的原则立场,他之所以强烈反对湖湘学的“以心观心”(当然这是朱熹的诠释而不一定是胡宏“识心”说的真实内涵)并将其喻作佛教的“以心求心”,其思想缘由便在于此。
值得一提的是,朱熹所说的“放在模匣子里面”的比喻性说法非常生动有趣,这是由于朱熹很担心“身心”容易脱离轨道、胡乱运作,故有必要用“模匣子”来规范它、约束它。这个“模匣子”就是比喻“敬”,由此推论,由“敬”摄心便是指知觉层面上的人心而不能是道德层面上的本心。例如朱熹还有一些说法,也表明了同样的意思:
人只有个心,若不降伏得,做甚么人?[62]
人心万事之主,走东走西,如何了得?[63]
心既常惺惺,又以规矩绳检之,此内外交相养之道也。[64]
今于日用间空闲时,收得此心在这里截然。……常常恁地收拾得这心在,便如执权衡以度物。[65]
且要收拾此心,令有个顿放处。若收敛都在义理上安顿,无许多胡思乱想,则久久自于物欲上轻,于义理上重[66]
这里所说的“降伏”、“收拾”、“收敛”、“绳检”等动词的主体都是“敬”,相对地说,“心”则是“敬”的客体对象。要把心安顿下来,安顿在“义理上”,便是主敬工夫的主要任务。其云去“物欲”存“义理”而令此心不至于“东走西走”、“胡思乱想”,亦是将心之状态规定为敬之工夫的对象。正是通过上述“收拾”、“收敛”等等主敬工夫的程序,然后才能实现人心为主(“万事之主”)的目标,朱熹喻作“如执权衡以度物”,意谓由敬摄心,方能使此心成为“度物”之标准。也正由此,所以朱熹说敬既是“一心之主宰”又是“万事之本根”,不能倒过来说,心是敬之主宰。其云“人之心性,敬则常存,不敬则不存”[67],亦同此义,意谓敬才是存心养性的根本方法而不是相反。由此出发,故朱熹说,敬是为学之根本大法,是圣学第一义之工夫。朱熹断然指出:
敬之一字,万善根本。涵养省察、格物致知,种种功夫皆从此出,方有据依。[68]
圣门之学,别无要妙,彻头彻尾,只是个敬字而已。[69]
其中的“据依”亦即“依据”。这是说,“敬之一字”乃是“涵养省察,格物致知,如种种功夫”的依据。但须指出的是,此所谓“依据”,只是就方法论而言的本源之意而非就本体论而言的理据之意,换言之,就方法论而言,各种工夫方法虽然名目繁多,但其中有一个根本的方法,那就是主敬,显然这是平铺地说主敬是一切工夫的“据依”,而不是形上地说“敬”是心性之“理据”,因为“敬”并非是独立存在的实体。不过令人注意的是,朱熹的上述说法涉及主敬与致知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主敬与集义、居敬与穷理的关系问题,这里须稍加考察。
由上所述,主敬工夫主要是指向人心而言,属于一种内心之工夫,这一点殆无疑义,然而如果说只要“守定一个敬字”,便可一了百了,于应事接物亦可全然不顾,则非但不是朱熹之主张,而正是朱熹所批评的偏见。他指出:
敬不是万事休置之谓,只是随事专一、谨畏、不放逸耳。[70]
若学者,当求无邪思,而于正心诚意处着力。然不先致知,则正心诚意之功何所施?所谓敬者,何处顿放?今人但守一个“敬”字,全不去择义,所以应事接物处皆颠倒了。[71]
这里以“随事专一”言“敬”,表明主敬工夫必落在“事”上,也就是后一段所强调的在“应事接物处”做一番“集义”工夫的观点。关于这一点,朱熹常常用程颐的“敬义夹持”说来加以强调,他说:“敬义夹持,循环无端。”[72]那么,如何来理解这种“夹持”关系呢?朱熹有一个解释,可谓曲尽其详:
彼专务集义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虚骄急迫之病,而所谓义者或非其义;然专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间念虑起处分别其公私义利之所在,而决取舍之几焉,则恐亦未免于昏愦杂扰,而所谓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谓集义,正是要得看破那边物欲之私,却来这下认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头头处处,无不如此体察,触手便作两片,则天理日见分明,所谓物欲之诱,亦不待痛加遏绝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领,则固当以敬为主,但更得集义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则于敬益有助。盖有不待著意安排而无昏愦杂扰之病。……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谈义、去本逐末,正欲两处用功,交相为助,正如程子所谓“敬义夹持”,直上达天德,自此者耳。[73]
在这里,朱熹强调居敬与集义交相为用的观点,不过从中仍然可以看出,朱熹还是坚持“若其本领,则固当以敬为主”的观点,这是朱熹己丑之悟后所坚持的“日用本领工夫”的一贯立场,不容改变。
朱熹还用“互相发”的说法来解释居敬与穷理的关系:
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两足,左足行则右足止,右足行则左足止。又如一物悬空中,右抑则左昂,左抑则右昂,其实只是一事。[74]
问题是这种“互相发”的工夫,何者更为根本?从上述这段话的字面来看,朱熹只是说两者互以他者为必要条件,缺一不可,亦即两者是平行的关系,而其最后一句“其实只是一事”,则意谓两种工夫其实只是同一个工夫的过程。这一思维方式,颇类似于朱熹的“知行并进”说,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节还有讨论,这里须指出这一并行关系的两种工夫虽同处在一个工夫过程中,可以说穷理离不开居敬,也可说居敬离不开穷理,但是只有居敬工夫具有贯动静、通上下、成始终、无间断、常惺惺之特征,显然比穷理工夫更为根本。故有学者认为朱熹在工夫论问题上,以主敬为第一义,穷理为第二义,亦不无道理。[75]如朱熹曾说:
为学两途,诚如所喻。然循其序而进之,亦一而已矣。心有不存,物何可格?然所谓存心者,非拘执系缚而加桎梏焉也。盖尝于纷扰外驰之际,一念之间,一有觉焉,则即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长,不加一毫智力于其间,则是心也,其庶几乎![76]
这段论述非常重要,虽然没有提到“敬”字,但我们却可以将此放在“敬”的脉络下来观察朱熹有关心物关系问题的立场。从其表述看,存心与格物并存不悖、相互为用,故谓“一而已矣”,然而心若不存,则格物工夫亦无可下手,显然存心较诸格物更为根本。如朱熹曾明确指出:
《大学》须自格物入,格物从敬入最好。只敬,便能格物。敬是个莹彻底物事。[77]
至于如何存心,朱熹强调只是在一念之间,一觉此心,则此心在也,其间容不得丝毫的智力安排。其实,这里的“觉”字,便是敬字工夫的提撕义。关于觉、心、敬的彼此关联,我们可以归纳为八个字:觉底是敬,觉处即心[78]。要之,存心其实就是由居敬工夫“一觉此心”之意。重要的是,由“一觉此心”便可令此心自在(“即此而在”),而觉此心者端在于敬字工夫,此即朱熹再三强调的主敬可使“自心自省”之意,也就是“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之意。
最后顺便指出,在有关敬与心的关系问题上,朱熹曾有这样一个定义:“敬则心之贞也。”[79]这是说,敬就是指心之贞定。按,此《答张钦夫书》非常著名,即所谓“诸说例蒙印可”书,为朱熹40岁时所作,然清儒王懋竑《朱子年谱考异》于“38岁”条却谓“后来都无此语”,意指该说为朱熹未定之论,不明理由何在。牟宗三则断定王说为非,并对“敬则心之贞也”有所肯定:“此语实甚佳。在朱子系统中,其意即是心气之贞定与凝聚,非从本体性的超越心而言也。”并说:“此义亦不悖于朱子静涵静摄之系统”[80]。可以看出,牟氏之肯定是顺着朱熹而说,若依牟氏之判教立场而言,则此“静涵静摄”盖谓朱熹思想之特质为理“存有而不动”,其动者为心气,而这一点正是牟氏所不能认同的。不过在笔者看来,于朱熹之主敬则不可以“静”字概之,朱熹所言主敬工夫意义上的“自心自省”之“心”亦非“心气”一词可以概之。诚然,由“敬则心之贞也”之命题的内涵来看,心是敬之对象,此即朱熹所言由敬摄心的题中应有之意,若此,则心莫非是现象实然之存在而可归于“气”之范畴?关于心是否就是气的问题,上引拙文已有讨论,这里不必赘述。要而言之,至少在朱熹敬论的思想脉络中,由敬而提撕唤醒之心乃是一“为主”而不“为客”之存在[81],绝非“心气”一词所能涵盖。朱熹所用的“心气”一词,例如:“讽诵歌咏之间,足以和其心气”[82],“心平气和”、“心气和平”[83]等等,均是日常语言所说的心平气和之意,并不具有特殊的思想意涵。事实上,如何结合朱熹所说的“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来看,那么“敬则心之贞也”便不难理解,其意无非是说敬能令此心“贞定”而发挥“主宰”之作用。
五、主敬工夫诸说
以上我们初步探讨了朱熹敬论的问题意识之由来以及由敬而令此心自做主宰、自省自存、收敛身心等问题,这些探讨还不足以覆盖朱熹敬论的全部内涵。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再对朱熹敬论的其他相关论述做相应的了解。
须指出,朱熹工夫论之特质表现为以主敬“立本”、以穷理“致知”,然其论敬主要指向“心定理明”[84],亦即属于如何使内心得以贞定之工夫,但是主敬工夫又必落在“事为”上讲,如其所云“(敬)只是随事专一”,这是其敬论的一项原则,同时也是指主敬工夫的着手处,朱熹这方面的言论甚多,例如:
持敬之说,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齐严肃”、“严威俨恪”、“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此等数语,而实加工焉,则所谓直内,所谓主一,自然不费安排,而身心肃然,表里如一矣。[85]
夫持敬用功处,伊川言之详矣。只云:“但庄整齐肃,则心便一,一则自无非僻之干。”又云:“但动容貌,整思虑,则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处,不待先有所见而后能也。须是如此,方能穷理而有所见。惟其有所见,则可欲之几,了然在目,自然乐于从事,欲罢不能,而“其敬日跻”矣。伊川又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若能持敬以穷理,则天理自明,人欲自消,而彼(按,指佛教)之邪妄,将不攻而自破矣。[86]
朱熹认为主敬工夫非常简单,即从平常的整齐严肃、严威俨恪、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等这些外部层面做起即可,重要的是,在施行这些工夫之前,不须“先有所见”,这里的“见”,大致是指意见或见解,意思是说,不必在持敬之前,先有什么“意见”安排,因为一旦做到“动容貌,整思虑”,就“自然生敬”,所以说“敬以直内”的工夫是“自然不费安排”的。这个说法值得回味,这是否意味着敬字已含有道德心之涵义,故不必另以道德之本心来主导引领,这一点还须另做探讨。简言之,由其“庄整严肃,则心便一”、“动容貌、整思虑,则自然生敬”的表述来看,整齐严肃就是持敬工夫之本身,甚至可谓是主敬之“至论”,[87]但是却不能看出整齐严肃之前另须设定一个“心”的存在。相反,“身心肃然,表里如一”乃是整齐严肃等一套持敬工夫的结果而不是前提。
也正由此,所以朱熹对程颐以来的主敬四句,就特别重视“整齐严肃”,以为时常保持此心警觉而不间断的谢良佐“心常惺惺”之说固然“极精切”,但“不如程子整齐严肃之说为好。盖人能如此,其心即在此,便惺惺。未有外面整齐严肃,而内不惺惺者。”[88]尽管朱熹也承认“四句不须分析,只做一句看”,[89]但从根本上说,“整齐严肃便是敬,散乱不收敛便是不敬”[90],仍然强调整齐严肃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心常惺惺则是主敬工夫过程中的一种效果,尹和靖的“其心收敛不容一物”,亦复如此。事实上,所谓整齐严肃,在儒家的教学体系中,原本属于“小学”一段工夫,无甚高妙之可言,如朱熹所云:“问:‘《大学》首云明德,而不曾说主敬,莫是已具于《小学》?’曰:‘固然。自《小学》不传,伊川却是带补一敬字。’”[91]又说:“持敬以补《小学》之阙。《小学》且是拘检住身心,到后来‘克己复礼’,又是一段事。”[92]尽管如此,持敬乃具有贯穿儒门工夫的根本特性。
上面曾提到朱熹论敬必落在事上讲,但是并不等于说主敬工夫没有独立的意义,切不可误认为敬只具有针对特定事物而言的相对意义。例如朱熹曾针对程迥(号沙随)反对单独说“敬”的观点,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近世程沙随犹非之,以为圣贤无单独说“敬”字时,只是敬亲、敬君、敬长,方着个“敬”字。全不成说话。圣人说“修己以敬”(《论语·宪问篇》),曰“敬而无失”(《论语·颜渊篇》),曰“圣敬日跻”(《诗·商颂·长发篇》),何尝不单独说来?若说有君、有亲、有长时用敬,则无君亲、无长之时,将不敬乎?都不思量,只是信口胡说![93]
朱熹的意思是说,主敬既“主于事”而言,同时也“主于心”而言,因此虽然持敬须在事上落实,但在无事时持敬涵养也同样重要;如果执定持敬工夫只能在有事时做,则完全有可能忽视无事时的主敬工夫。关于无事时做涵养工夫,朱熹曾说:
谓当涵养者,本谓无事之时,常有存主也。……谓省察于将发之际者,谓谨之于念虑之始萌也;谓省察于已发之后者,谓审之于言动已见之后也。[94]
按照程颐“涵养须用敬”的说法,显然朱熹所说的涵养,意同主敬。相对而言,“省察”则是已发以后的工夫。在朱熹,格物致知亦相当于已发后知工夫。但是,究竟是涵养在先省察在后,还是两者应同时并进,却成了困扰朱熹的一个问题。
从根本上说,既然主敬是圣门彻上彻下之工夫,因此就必须说:“当以涵养为本。”朱熹曾说:“涵养、体认、致知、力行……四者本不可先后,又不可无先后,须当以涵养为本。”[95]这个说法很微妙。所谓本无先后,这是指在具体的工夫过程中,涵养至力行的四项工夫应当同时并进;所谓不可无先后,则是指从原则上说,涵养更为根本,应以涵养为先。[96]这一观点的正式确立应当是在己丑之悟以后,对湖湘学的“先察识后涵养”之工夫次序的彻底扭转而实现的,此亦不待赘言。
但是,在反映朱熹晚年思想的《语类》中,朱熹的种种说法却表明其对涵养省察的工夫次第之看法并不严格,他一方面说“须先涵养清明,然后能格物”,但接着又说“亦不必专执此说”[97];他一方面说“须是平日有涵养之功,临事方能识得,若茫然都无主宰,事至然后安排,则已缓而不及于事矣”[98],但另一方面又说“须先致知而后涵养”[99],“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100],“义理不明,如何践履”[101],显然又在主张穷理在涵养之先。朱熹又说:
某向时亦曾说,未有事时且涵养,到得有事却将此去应物,却成两截事。[102]
已发未发,不必太泥,只是既涵养又省察,无时不涵养省察。[103]
未发已发,只是一件工夫,无时不涵养,无时不省察耳。……不曾涵养者亦当省察。不可道我无涵养工夫后,于已发处更不管他。……今言涵养,则曰不先知理义底涵养不得;言省察,则曰无涵养,省察不得。二者相捱,却成耽搁。”[104]
可见朱熹晚年于涵养省察之工夫次第的看法很宽松,认为两者既互相独立又相辅相成。据此可知,朱熹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以涵养为主,只是就“大纲说”,[105]而就具体的工夫过程而言,则如同“知行并进”的命题一样,朱熹不得不说:“涵养穷索,二者不可废一,如车两轮,如鸟两翼。”[106]
由此以观,我们就很难说,朱熹思想只是一重敬的义理形态,因为朱熹始终不能放弃的一个立场是《大学》之要领在于“格物”两字,所以他就不能单方面地强调涵养可以取代致知而致知亦有助于涵养的想法。准此,我们则不妨可说,朱熹思想亦是一重格物的义理形态。当然也须看到,若是就“大纲说”——亦即从原则上说,无疑地以敬为本乃是朱熹工夫论的基本立场,敬可令此心自做主宰、可以自省自存、可以收敛个身心等观点才是朱熹工夫论思想的核心所在。故云:“《大学》须自格物入,格物从敬入最好。只敬,便能格物。”107]至于朱熹的主敬理论能否真正地实现“此心自做主宰”,而朱熹的这套工夫理论是否蕴含有以此主宰之心来引领格物致知之想法,则属于理论评判的问题,已经越出了朱熹思想本身的范围。
最后与朱熹敬论有关,有必要探讨一下朱熹对孟子“求放心”说的看法。上已提及孟子“学问之道无他,求放心而已矣”可谓是宋明理学家莫不关注的一个工夫论问题。在朱熹的时代,他便遇到其门人不断的提问,究竟应该如何“求放心”?我们翻开《语类》卷59《孟子九·告子上》“牛山之木章”及“仁也人心章”,便可看到朱熹与其门人有关这一问题的大量讨论,这里仅就其所论“求放心”与主敬有何关联略做探讨。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最为学第一义也。故程子(按,指程颢)云:“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人将已放之心,约之使反复入身来,自能寻向上去。”某近因病中兀坐存息,遂觉有进步处。大抵人心流滥四极,何有定止?一日十二时中有几时在躯壳内?与其四散闲走,无所归著,何不收拾令在腔子中。且令纵其营营思虑,假饶求有所得,譬如无家之商,四方营求,得钱虽多,若无处安顿,亦是徒费心力耳。[108]
这段话肯定了孟子“求放心”说的重要性,以为是“最为学第一义”,这个说法与其将主敬视为圣学工夫第一义的观点是相通的,因为“求放心”其实与主敬工夫是有关联的。朱熹又说:
季成问“放心”。曰:“如‘求其放心’,‘主一之谓敬’之类,不待商量,便合做起。若放迟霎时,则失之。”
孟子言“求放心”,你今只理会这物事常常在时,私欲自无著处。且须持敬。
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可煞是说得切。子细看来,却反是说得宽了。孔子只云:“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若能如此,则此心自无去处,自不容不存,此孟子所以不及孔子。
这里所说均与敬字工夫有关,特别是第三段说孟子“求放心”“却反是说得宽了”值得引起注意,显然这是朱熹在将“求放心”与孔子“居处恭,执事敬”进行比较后所做出的判断,至于朱熹所说“若能如此,则此心自无去处,自不容不存”,若能对上述朱熹主敬思想有所了解,显然一望便知,这正是朱熹的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自省自存之意。也就是说,在朱熹看来,毕竟孔子的“执事敬”要比孟子的“求放心”说得更为严密。
那么,何以有此一说呢?事实上,朱熹对“求放心”的“求”字如何解读有所困惑,他指出:
人心才觉时便在。孟子说“求放心”,“求”字早是迟了。
孟子云“求放心”,已是说得缓了。心不待求,只警省处便见。“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其快如此。盖人能知其心不在,则其心已在了,更不待寻。[109]
这里的第一句“人心才觉时便在”以及最后一句“人能知其心不在,则其心已在了,更不待寻”不就是朱熹在论述主敬时常说的“一念之间,一有觉焉,则即此而在”的意思吗?也就是我们所总结的觉底是敬、觉处是心的意思。依朱熹,“觉”字即提撕义、唤醒义,乃是主敬工夫的要领所在,而孟子的“求”字“早是迟了”,意思是说“求”的前提必有一主一客的对峙、时间先后的差异。由时间上“迟了”来反推,则可看出,“求”也有可能导致“来不及”,正是在此意义上,朱熹又说“求”字亦是一“剩语”:
或问“求放心”。曰:“知得心放,此心便在这里,更何用求?适见道人题壁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说得极好!《知言》中或问‘求放心’,答语举‘齐王见牛’事。某谓不必如此说,不成不见牛时,此心便求不得!若使某答之,只曰:‘知其放而求之,斯不放矣。’‘而求之’三字,亦自剩了。”
或问:“求放心。愈求则愈昏乱,如何?”曰:“即求者便是贤心也。知求,则心在矣。今以已在之心复求心,即是有两心矣。虽曰譬之鸡犬,鸡犬却须寻求乃得;此心不待宛转寻求,即觉其失,觉处即心,何更求为?自此更求,自然愈失。此用力甚不多,但只要常知提醒尔。醒则自然光明,不假把捉。今言‘操之则存’,又岂在用把捉!亦只是说欲常常醒觉,莫令放失便是。”这两段话已经说得十分明确,“即觉其失,觉处即心,何更求为”其实便是朱熹的主敬论述,包括“常知提醒”、“不假把捉”、“常常醒觉”等等说法,无不都是朱熹之论敬的重要观念表述。重要的是,在朱熹看来,“求”字已不免“以已在之心复求心,即是有两心”之弊,质言之,亦即“以心求心”之弊。对此一问题的态度,朱熹通过对湖湘学的清算已经表达得十分清楚,这里也就不必赘言了。
不过须指出的是,朱熹对“求”字虽有种种苛求,但并不意味着他对孟子“求放心”采取的是否定之态度,其实朱熹的意图在于欲将“求放心”纳入其主敬思想的轨道,这才是朱熹对孟子“求放心”的一种创造性诠释,例如:
孟子盖谓,鸡犬不见,尚知求之;至于心,则不知求。鸡犬之出,或遭伤害,或有去失,且有求而不得之时。至于此心,无有求而不得者。便求便在,更不用去寻讨。那失底自是失了,这后底又在。节节求,节节在。只恐段段恁地失去,便不得。今日这段失去了,明日那段又失,一向失却,便不是。
或问“求放心”。曰:“此心非如鸡犬出外,又著去捉他;但存之,只在此,不用去捉他。放心,不独是走作唤做
放,才昏睡去,也是放。只有些昏惰,便是放。”
不待说,这里用“便求便在,更不用去寻讨”、“但存之”、“不用去捉他”等说法来解释“求放心”,已有明显的朱熹主敬的诠释思路。
要之,朱熹的思路是,“求”字不免有“寻讨”义、“把捉”义,相比之下,“敬”字的“自存”义、“提撕”义更为重要。关于这一点,由朱熹对“持敬”的批评可见一斑,他说:
只一个持敬,也易得做病。若只持敬,不时时提撕著,亦易以昏困。须是提撕,才见有私欲底意思来,便屏去。且谨守著,到得复来,又屏去。时时提撕,私意自当去也。[110]
六、几点讨论
由上可见,朱熹“敬论”在其整个工夫论系统中实占有核心的地位。事实上,宋代以来,在以理学或道学(亦含心学)为主流的儒学思想史上,本体与工夫这对重要观念,乃是儒学思想家在思考宇宙人生问题之际的核心关怀。也就是说,理学家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并不仅仅是天道性命的形上建构,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工夫论上对于儒家圣人之道在现实人生中的意义和价值做一番真实的体验和践履。因此,工夫论问题从来就是理学史上的一大核心问题。上引朱熹《大学或问》所云“盖吾闻之,敬之一字,圣学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这段表述充分说明,“敬之一字”作为一种“圣学”工夫是贯穿始终的。具体而言,它是贯穿《大学》三纲领八条目的根本工夫,同时也是贯穿人之一生(包括小学阶段与大学阶段)的根本工夫。朱熹弟子黄榦(1152—1221)在《朱子行状》中对朱子之“为学”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概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以为小学大学皆本于此。”[111]这是说,朱熹的“居敬”工夫乃是贯穿“穷理致知”与“反躬实践”的两大领域,换言之,“敬”乃是贯彻于知识活动和道德活动的共同要求。至此已很明显,即便称朱熹的工夫论思想乃是一“敬”的思想形态亦无不可。但正如本文开头所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仍有必要追问朱熹之言“敬”的义理根据究竟何在?
笔者曾在上述拙文中,就朱熹的主敬思想提出了一个质疑:
若一言以蔽之,则可说“主敬”工夫所对治的仍是人心意识,何为“主敬”之头脑的问题,依然无法找到确切的答案。事实上,如果不讲头脑,只讲“主一无适”的“主敬”——即意识的高度集中,那么这种说法就只具有心理学的意义,而不具有伦理学的意义,因为即便是盗贼在行窃之时,意识也能达到高度集中。所以,若从哲学上讲“主敬”,便须要追问“主敬”之所以可能的依据何在的问题。显然,朱熹所欠缺的正是此一追问,故其虽把“主敬”提到“圣门第一义”的高度,却仍然不免落空。[112]
由于拙文的核心问题在于朱熹的心论,对其敬论只是顺便提及,故未能展开详细的讨论。在这里则有必要对其心论与敬论的理论关联再做稍详的探讨。
事实上,或有读者已经察觉,上述质疑之关键在于“头脑”一词,由此出发,所追问的便是主敬之所以可能的依据问题。不容否认,这里所谓的“头脑”,其实是阳明学所喜欢使用的思想术语,特指心体良知,而朱熹所用“头脑”一词大多属于日常用语,如“凡看道理,要见得大头脑处分明”[113]之类,并没有特殊的思想涵义,这里不必细说。重要的是,阳明曾从“心即理”这一“头脑”处出发,对朱熹(亦含程颐)的居敬穷理说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全文颇长,但很值得回味,故全段录出:
梁日孚问:“居敬穷理是两事,先生以为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间只有此一事,安有两事?若论万殊,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又何止两?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穷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养工夫,穷理是穷事物之理。”曰:“存养个甚?”曰:“是存养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穷理矣。”曰:“且道如何穷事物之理?”曰:“如事亲便要穷孝之理,事君便要穷忠之理。”曰:“忠与孝之理在君亲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穷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如何是主一?”曰:“如读书便一心在读书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则饮酒便一心在饮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却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日孚请问。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时便是逐物,无事时便是着空。惟其有事无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即是穷理。就穷理专一处说,便谓之居敬;就居敬精密处说,便谓之穷理;却不是居敬了别有个心穷理,穷理时别有个心居敬:名虽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即是无事时义,义即是有事时敬,两句合说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须言义,孟子言‘集义’即不须言敬,会得时横说竖说,工夫总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识本领,即支离决裂,工夫都无下落。”问:“穷理何以即是尽性?”曰:“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穷仁之理,真要仁极仁,穷义之理,真要义极义:仁义只是吾性,故穷理即是尽性。如孟子说充其恻隐之心,至仁不可胜用,这便是穷理工夫。”日孚曰:“先儒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则不暇。公且先去理会自己性情,须能尽人之性,然后能尽物之性。”日孚悚然有悟。[114]
其中涉及对程朱理学的工夫论两大支柱——居敬与穷理——的关系究竟应如何理解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其实也就关涉到朱子学与阳明学的思想歧义究竟何在的问题。至于阳明依何理路坚持居敬穷理只是一事,并非这里所欲讨论的主题,我想提请注意的是:“如此则饮酒便一心在饮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却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显然这是针对“如读书便一心在读书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来解释“主一”(即居敬)所提出的批评。
阳明的思路非常明确,在他看来,不论是居敬还是穷理,也不论是读书还是接事,固然需要由“一心”来主导,但更要追问的是,此所谓“一心”究为何意?如果只是指意识集中,那么譬如“饮酒”、“好色”之行为,也会达到意识集中的状态,因此如果我们放弃对“一心”之本质内涵的追问,仅仅强调主一无适、收拾身心,那不仅是毫无意义的,甚至会使人心走入歧途却又茫然不知。依我们的理解,阳明的意思是说,将“主一”解释为“一心在读书上”、“一心在接事上”,那么这只不过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精神集中,如同“饮酒”、“好色”也能做到“一心”那样,这种“一心”状态并不具有伦理学的意义。至此,阳明的结论已很明显:须将“一心”往上提升,理解为形而上的“心体”,亦即“心即理”意义上的超越之道德本心,唯有从道德本心的立场出发,主敬工夫才具有相应的思想意义。
须指出的是,向来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阳明心学过于推崇心体的能动力量,从而未免导致道德上的乐观主义态度而缺乏对人心负面因素保持应有的戒慎恐惧之态度115],其依据之一便是阳明在《大学古本序》中对朱熹在《大学》八条目之外添入“居敬”工夫所表示的不满,亦即“合之以敬而益缀,补之以传而益离”[116],意谓朱熹在工夫论上突出“居敬”,完全是多此一举。依阳明,“《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117],故本领工夫不在格物也不在居敬而在于诚意。所以阳明强调指出:
《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为善去恶无非是诚意的事。如新本(按,指朱熹《大学章句》)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源。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于此不察,直所谓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诚身,诚身之极便是至诚;《大学》工夫只是诚意,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工夫总是一般。今说这里补个敬字,那里补个诚字,未免画蛇添足。[118]
这是批评朱熹居敬说“没根源”,意即“没头脑”。在阳明看来,《大学》一书为足本,其自身的义理自成一套体系,更不必添“敬”字以补其不足,否则的话则不免“画蛇添足”。
但是这里须注意的有两点:第一,朱熹《大学章句》并没有用居敬来补充解释格物,朱熹只是对《大学》文本出现的“缉熙敬止”、“止于敬”、“畏敬而辟”等三处的“敬”字做了文字学的解释,并没有采用程颐以来的主敬观点(如“主一无适”)来加以附会,所以阳明提出“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这一质疑,以此批评朱熹则是不公平的,况且孔门从来没有遗落这个“敬”字[119];第二,同时也须看到,阳明所针对的其实是朱熹《大学或问》将敬字来贯通大学与小学的观点。尽管如此,阳明之意并不在于否认“敬”字本身在儒学史上的应有地位,只是对于阳明而言,朱熹以主敬来穿凿附会《大学》的义理体系,以为不如此则《大学》的义理就无法彰显,这完全是庸人自扰、多此一举,因为《大学》既无缺字亦无错简,其自身便构成了一套义理圆融的体系。
其实,阳明虽对朱熹以“敬”字穿凿附会《大学》不以为然,但这并不意味着阳明对于“敬”字在儒学工夫论中的重要性有所轻忽,他指出:“尧舜之兢兢业业,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谓也,皆出乎其心体之自然也。出乎心体,非有所为而为之者,自然之谓也。敬畏之功无间于动静,是所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也。敬义立而天道达,则不疑其所行矣。”[120]此可见阳明之于《尚书》“敬畏”、《周易》“敬义”既有充分了解,又认定敬畏工夫出于“心体之自然”,亦是可以实现“天道”的。要之可说,阳明是以“心体”作为“主敬”之头脑,以克服朱熹之主敬“没根源”之弊病。
诚然,阳明心学亦有“乐是心之本体”[121]的命题,继承了周敦颐至程颢以来倡导的“寻孔颜乐处”的精神,但阳明对心体的戒惧义、敬畏义亦有一定的重视。只是阳明的基本立场在心体良知,故在敬与心的关系问题上,他的基本想法是,如果脱离心体而谈居敬,则是一种“没根源”的说法而已,如朱熹之言敬便是此类。总之,如以“敬畏”与“洒落”作为一种类型学概念来区别朱子学与阳明学为两种形态,则恐怕与整个宋明理学的历史实情并不相符。[122]
问题是,设问由心学立场以批评朱熹敬论“没根源”,这在理论上是否有效?回答应当是肯定的。但是,任何理论判断必涉及思想立场的问题,由立场之不同所得出的结论也自然不同,这一点本来无可争议。然而由心学立场出发,注重在心之本体的主宰下随时用功,所谓即本体之工夫,自有其一贯之理路,由此以观朱熹之主敬,可以看出其谓由敬定心、由敬存心,的确欠缺心体对居敬工夫的主导,在此意义上,即便说朱熹之主敬“没根源”亦有一定道理,我认为牟宗三以“空头的涵养”来批评朱熹主敬亦源自于此。当然这一理论判断已然越出了朱熹思想的义理范围,亦不意谓朱熹敬论是毫无内容、不成体系的一套空话。其实若就朱熹的义理系统看,其敬论不惟完全可以自立自足,而且自有其心性论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正如上文既已指出的那样,朱熹之主敬的问题意识在于,他要应对二程以来以体验喜怒哀乐未发为主的道南学派以及以察识已发之端倪为主的湖湘学派之观点的挑战,以防止由“以心察心”[123]、“以觉求心,以觉用心”[124]以及“以心求心,以心使心”[125]等观点而导致“心有二主,自相攫拿”[126]之弊端,由此来杜绝可能出现心的实体化、本体化之趋向,而这些弊端的根源既来自儒学内部(如湖湘学乃至象山学)又与佛教不无关联。[127]要之,朱熹所关注的始终是人心意识的现实状态及其分解状态,如何就现实当中扭转人心的错误走向乃是其思想的核心关怀,故他要求通过层层下就的脚踏实地的居敬工夫以解决如何上达天德、实现心理合一的问题,由此看来,朱熹之主敬亦在另一层面开辟出一条工夫入路的途径,亦不失为儒学的一种理论形态。
但是从记录朱熹晚年之语的《语类》中,我们却可看到朱熹又常以两翼两轮来为居敬穷理的关系定位,据此则可说在朱熹的工夫论系统中穷理仍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非居敬可以替代。表面看来,在居敬与穷理的关系问题上,朱熹主张应做统一的把握,然而这种观点如同朱熹所言“知行相须”并不能归为阳明学意义上的“知行合一”那样,理由在于朱熹所言知行相须,其前提是知行属于一种平行关系,而当阳明讲知行合一之时,则意谓在良知本体的统领之下,知行必然合一。倘若说朱熹思想属于“敬的形态”,则必须肯认朱熹所主张的“此心自做主宰”之“敬”不仅贯穿于格物工夫的过程中,而且还是格物工夫的前提和依据。然而事实上,朱熹晚年不仅坦承自己平日在“道问学”上著力尤多,而且他的《大学》诠释所透露出来的一个思想立场无疑是:唯有“格物”二字才是儒学工夫之核心。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朱熹之敬论与其心性理论密切相关,当朱熹说由敬而生心之精明,乃是就心的“自省自存”处言,故其所言“若知敬字只是自心自省,当体便是,则自无此病矣”,[128]按此所谓“病”,则是指“将此敬字别作一物,又以一心守之”之病,意指将居敬工夫的敬与心割裂开来所生之人病。朱熹以为由敬定心而使心自省自存庶能从根本上对治此病。这里的“自心自省,当体便是”以及上文提及的“以敬为主”、“而心自存”可以合而观之,这两句话十六个字可谓是朱熹敬论的核心观点,也是其敬论思想的意义所在。其意义就在于:由心之自省自存,使得在“主宰之谓”意义下的心具有了实践主体的地位,[129]而不只是被动地包总性情、涵摄众理,由此心出发,自能判断是非,实现“当体便是”的效果,如此则居敬工夫确能贯彻于格物穷理的工夫进程当中。
同时也须看到,朱熹所谓由敬而立的心的主宰义毕竟是就功能而言,而不是就本体而言,这是因为朱熹始终不能承认有一超越义的本体心,而其所谓“当体便是”亦不能想当然地等同于陆九渊心学在心即理的意义上所主张的“当下便是”[130],更与阳明后学所谓的良知“当下论”、“现成论”不可同日而语,关于其间的义理纠缠,这里已无法深究了。[131]只是有一点须指出,在朱熹看来,若能真正做到以敬为主而心自存,通过居敬工夫以使心体自做主宰,那么此心之发用便必定是合理的,这又叫做“心定理明”,也就是朱熹所言“自心自省,当体便是”的真实内涵。倘若如此,则朱熹所云“当体便是”乃是对工夫效应的一种状态描述而不是指向道德本心之当下呈现,因为这种“自心自省”的状态取决于工夫程度的不同而会发生变化,故“当体便是”并不能获得本体的必然保证。这是由于朱熹之论心所指向的是工夫论问题而不是本体论问题[132]。
总之,朱熹的敬论继承了程颐以来的主敬思想,接受了“主一无适”、“整齐严肃”、“常惺惺法”、“其心收敛,不容一物”以及“敬义夹持,循环无端”等有关主敬学说的内涵,同时又有更深入的理论发挥[133]。与程颐当时须要应对“心疾”问题相比,朱熹所要应对的理论问题及其敬论中所蕴含的理论问题也显然更为复杂。朱熹的主敬思想之形成与其应对道南学派的“体验未发”以及湖湘学派的“先察识后涵养”等理论问题有关,更是其通过“中和新悟”所建构的心性情之理论体系的一个结果。
朱熹的心性论有一个基本的思想立场:作为“主乎性而行乎情”的心,只具有工夫论的意义,其云“心是做工夫处”、“心字只一个字母”[134],便充分反映了朱熹之论心的基本立场。正是由此立场出发,故朱熹极力反对在心的操舍存亡的工夫论问题上设定“另有心之本体”的前提,亦即不能在居敬之前预设超越义的本心存在,依朱熹的说法,这就必然陷入“以一个心把捉一个心”的窠臼之中。朱熹的主敬工夫并不是道德本心的直接发动,而是对心的知觉意识之功能的控制调整,其云“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以敬为主而心自存”、“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都应当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当然,朱熹主敬亦有其心性论作为基础,故其主敬思想自有一套理路,而其核心关怀则在于如何解决现实人心的障蔽问题,因而不必同于阳明心学由良知本心直接悟入、当下呈现的这套理路。归结而言,朱熹的主敬思想乃是对儒学工夫论的一项重要理论贡献。
朱熹对《大学》“明明德”的诠释
朱汉民 周之翔
朱熹对《大学》所提出的命题“明明德”极为重视,他常教导学生为学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进而指出:“为学只在‘明明德’一句”。他对《大学》“明明德”的诠释,内涵丰富而思想深刻,是他研习并运用先秦儒家学说与宋代理学思想,分析和探讨人及其生活世界本质的全面总结。如我们所见,经过朱熹对“明明德”的诠释,这一原本只是普通政治道德的概念,获得了丰富的哲学内涵和宗教意义。
从一个先秦贵族教育的普通文本中,为什么朱熹可以读出这么多的新意义来呢?全面分析和总结朱熹“明明德”观的内涵,对于理解其经典诠释学的特点及价值,有着重要意义。
一、朱熹诠释“明明德”的新意义
朱熹对《大学》“明明德”内涵的思考与揭示,历经数十年。最初,他以孟子的“良知良能”、“良心”等阐释“明德”的内涵;晚年,他又以两宋理学家所掌握的孟子心性论进行分析与阐释,思考“明德”与“心”、“性”等概念的关系;去世前数年,他还运用宋代理学家的理气论思想揭示“明德”的来源,从而完成了对《大学》“明明德”的理学化诠释。
朱熹对《大学章句》“明明德”注释的最后修订在1196年左右。他于注中说:
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万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1]
这是朱熹晚年定论,也是其“明明德”思想的精粹表述。在这里,朱熹用短短67个字的篇幅,从工夫论、心性论、天理论的角度,阐明了“明德”的来源与本质,“明德”不明的原因及其根源,和“明德”可明的依据与道路。语言简洁,语义完备,逻辑严密,实际上是其毕生学问的总结。众所周知,这个定义,在朱熹理学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理学思想的继续演进也产生过深刻影响。
而事实上,无论是《大学》的文本本身,还是汉唐经学家的注疏里,《大学》中的“明明德”的意义都非常平易,只是对承担治理食邑、国家等责任的贵族的道德要求,并无理学思想的复杂而深刻的意义。如《大学》文本中的“明明德”,只是要求贵族博闻多识,注意自身的情绪管理,能够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从民众的角度制订并实施治理国家的政策;而郑玄注曰:“明明德,谓显明其至德也”,孔颖达疏曰:“在明明德者,言大学之道,在于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谓身有明德,而更章显之”[2],都不涉及心性修养的义涵。但是,朱熹正是通过对《大学》“明明德”命题的不断阐释,将先秦儒家与宋代理学思想成果进行整合,而从“明明德”中读出理学的工夫论、心性论、天理论等思想的意义。朱熹认为,“明明德”能够作为《大学》全书的纲领,就在于它将理学的天理本体论、心性论与儒家修身工夫论统一起来了。
其一,朱熹通过对“明明德”的哲学阐释,读出“明明德”的工夫论内涵。他认为“明”即“明之也”,又说“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这显然是从儒家工夫论角度进行的解读。所谓“因其所发”指“明德”的发露,即“明明德”工夫的起点和基础所在;所谓“遂明之”,指的工夫正是《大学》中提出的系统的儒家修身工夫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
其二,朱熹通过对“明德”的哲学阐释,读出了“明德”的心性论思想内涵。他在阐发《大学》的过程中,不仅对性的本源问题进行了说明,特别是通过阐释《大学》的“明德”为“虚灵不昧,以具万理而应万事者”,对心的内容及心与性、心与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而朱熹对《大学》“明德”内涵的探究,在如何确定和表述心性与“明德”之关系上,实际上一直未曾离开孟子的心性论。
其三,朱熹通过对“明德”的理论考察与哲学阐释,从“明德”中读出“自然之理”的宇宙本体论意义。他的“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的思想,立足在理学天理论基础之上。他以早期儒家、北宋理学的“性与天道”合一为理论基础,阐述人物的化生,以说明人的“明德”的来源,从而揭示了《大学》的宇宙论背景。他指出:“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为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脏百骸之身。”[3]他论证了人的“明德”的来源。
我们发现,朱熹对《大学》“明明德”的哲学诠释,与他的理学思想的“先见”有关。他显然是运用“六经注我”的方法,从《大学》中读出宇宙论、心性论、工夫论等理学思想。毫无疑问,朱熹对《大学》“明明德”的哲学诠释,具有“六经注我”的特点。但是,我们还应该知道,朱熹的“我”不是主观任意的“我”,而是对先儒先贤的全面理解和思考而形成的“先见”。深入考察他的治学历程与治学特点,可知他对《大学》“明明德”的哲学诠释与理学建构,其实是建立在“我注六经”的基础之上的。他晚年能够从儒家经典中读出这么多的新意义来,正是由于他早年和中年能够全面地阅读、深刻地理解孔孟以来先儒先贤的著作,并且各取所长,融会贯通。应该说,朱熹的经典诠释是经由“我注六经”的“六经注我”,两者是同一个经典诠释过程前后自然接续的不同阶段,并非对立关系。
二、明明德的工夫论诠释
《大学》相传为曾子所作,《大学》所以被列为学问之先,视为修身治人的规模,是因为它提出了为学工夫的八目,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将其称之为“教人之法”、“修身治人底规模”等等,至于其他儒家经典所列的工夫论,均可分别纳入到这个序列、体系之中。
朱熹早年已认为“良知良能”就是“明德”,在为学工夫方面,他认同通过察识此心之良知而明其“明德”。他认为圣人本身之“明德”无遮无掩,光明朗彻,是一个完全实现了的人。而人既与天地万物同理,又与圣人同性,皆具同等的潜在能力,所以人人也都是潜在的圣人。但普通人的“明德”为气禀、物欲所拘蔽和遮掩,失去其本有的光明,不仅不能照亮别人,也不能照亮自己,而未能自我实现。那么普通人实现为人的途径,也就是通往圣人的道路是什么?朱熹指出:“因其所发而遂明之”。这是因为,人必定具有“明德”,这“明德”无论怎样遮掩、拘蔽,也会有显露的时候,如孟子所说的四端与良知良能,只要将显露的“明德”加以扩充的工夫,即可实现本体之明。
朱熹后来认识到,良知良能只是“明德”之发现,是“明德”能明的依据与道路,但最终来说,明德之明,必须通过学者自己的“明明德”工夫,也就是《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功来实现。朱熹指出,本体之明的显露是“明”的工夫的依据与起点,而他所极为重视的《大学》修身治人底规模、为学工夫,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则是“明”的工夫的内容与程序。《朱子语类》载:
所谓明之者,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皆明之之事,五者不可缺一。若缺一,则明德有所不明。盖致知、格物,是要知得分明;诚意、正心、修身,是要行得分明。然既明其明德,又要功夫无间断,使无时而不明,方得。若知有一之不尽,物有一之未穷,意有顷刻之不诚,心有顷刻之不正,身有顷刻之不修,则明德又暗了。惟知无不尽,物无不格,意无不诚,心无不正,身无不修,即是尽明明德之工夫也。[4]
可见,朱熹是从理学的工夫论角度解读“明明德”的。朱熹重视《大学》之道,正是因为《大学》提出了系统的儒家修身工夫论,即格物、致知,阐明了儒家心性修养“知”的工夫;正心、诚意、修身,阐明了“行”的工夫。朱熹揭示了“明明德”工夫的基础与依据,又从《孟子》回归《大学》文本本身,阐明了“明明德”工夫的具体内容与程序,从而对《大学》“明明德”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朱熹从《大学》文本中的格物致知等工夫论角度解读“明明德之工夫”,显然比郑玄注“明”为“显明”,孔颖达疏为“章显之”要合乎文意得多。傅伟勋提出“创造的诠释学”,共分成五个层次,即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5]朱熹以《大学》文本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工夫论角度解读“明明德之工夫”,这是《大学》文本本来就有的内容,即所谓“实谓”的层次;但又属于没有明确的内容,即所谓“意谓”的层次。朱熹通过对《大学》文本的语义澄清、脉胳分析、前后文意贯通的考察等等,尽量“客观忠实地”了解并诠释《大学》的意思,探问了其“实谓”、“意谓”两个层次的意义,体现了他忠于经典文本、即“我注六经”的诠释态度。
三、以思孟学派的
心性论解读“明德”
《大学》文本本身对“明德”的内涵没有具体的论述,更没有作出深入的心性论探讨。朱熹要对《大学》的为学工夫做出深入探讨,揭示其通过个体的心性修养而成己成物的理论价值,就必须对“明德”的心性论内涵做出思考。
在儒家经典中,《孟子》以心性论的深刻思考而为朱熹所特别重视。所以,朱熹对“明德”的思考,一直是以《孟子》为理论依据的。朱熹早年已经认识到“明德”的内在性和普遍性,亦即认为人人皆有“明德”,最初也曾以孟子的“良知良能”、“良心”等阐释“明德”的内涵。他指出“明德”同“良心”一样,非由外铄,而是根于人心,被人的私欲所蔽而不明。他说:
明德,谓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
此条是廖德明所录,时间在1186年。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朱熹仍然重视孟子的“良知良能”之说及其与《大学》“明德”之间的思想关联,但主要是从“明德”与“良知良能”都是人所固有,为天所赋予的相同特性加以考虑。显然,“良知良能”只是一个基于观察获得的经验与体验,还不足以揭示《大学》中“明德”的意蕴,更不能与精密严谨、系统深刻的佛教的心性论抗衡。他还必须继续追问“良知良能”在人的心性结构中的位阶,才能明了“明德”的内涵。
“明德”的内涵既然与心性问题紧密关联,要阐释“明德”的内涵,就必须要辨明心性与“明德”的关系。在《经筵讲义》中,朱熹将“明德”解释为“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者也”,直接以“性”释“明德”。但这又与《大学》文本中的“明德”有差异,因为《大学》文本中的“明德”是个“浑全”的事物,不仅仅是指内在的“德性”,也指能彰显于行动的德行,因而,是经由人的思想认识的结果,而思想认识是由“心”来承担的,所谓“心之官则思”。朱子也指出“心者,气之精爽”,“心官至灵,藏往知来”。所以他知道,单独以“性”释“明德”并不妥当。《朱子语类》记载:
问:“‘天之付与人物者为命,人物之受于天者为性,主于身者为心,有得于天而光明正大者为明徳’否?”
曰:“心与性如何分别?明如何安顿?受与得又何以异?人与物与身又何间别?明德合是心?合是性?曰性却实,以感应虚明言之,则心之意亦多。”曰:“此两个说着一个则一个随到,元不可相离,亦自难与分别。舍心则无以见性,舍性又无以见心。故孟子言心性,每每相随说,仁义礼智是性,又言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逊、是非之心,更细思量。”[6]
这是门人余大雅直接以朱熹的原话求证于朱熹,表明余大雅对朱熹将“明德”与心性相联系而产生了许多疑问。在这里,朱熹一口气提出了六个问题,表明了他在揭示“明德”内涵时的问题意识所在。他指出,“明德”是“感应虚明”的,因而“心之意亦多”;同时他也注意到,孟子总是将心与性联系起来论说的特点。
实际上,朱熹1189年所修订的《大学章句》中,对“明德”的注释,是不判分心德,即从心性一体的角度进行解释的:
问:“《大学注》言:‘其体虚灵而不昧,其用鉴照而不遗。’此二句是说心?说德?”
曰:“心、德皆在其中,更仔细看。”
又问:“德是心中之理否?”
曰:“便是心中许多道理,光明鉴照,毫发不差。”[7]
本条是徐寓于1190年至1191年之间,在漳州问学朱熹时所记,其中《大学注》指朱熹1189年修订的《大学章句》,1191年刊刻于漳州学宫。显然,《大学注》中,“其体”之“其”是指“明德”,“虚灵不昧”是对“明德”的本质特征的描述,也是对“明德”之“明”字内涵的揭示;“鉴照不遗”是言“明德”之用。在这条注释中,朱熹显然是以心释“明德”。“虚灵不昧”、“鉴照不遗”实际上就是心之体与用。但以“虚灵不昧”言“明德”之“体”,等于直接说心就是“明德”之“体”,但是他又指出“明德”是人心中“许多道理”。人之心合理气、统性情,故而德性必蕴涵于心,德行亦必为心之发。由心言明德,才能整全而无所偏废,但又必须兼性而言,否则,“明德”亦没有本原。在最终定论,即通行本《大学章句中》,朱熹回到孟子兼心言性、兼性言心的立场,指出人之明德是“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万理而应万事者也”,以“人之所得乎天”、“具万理”阐释“性”之明,以“虚灵不昧”、“应万事”阐明“心”之明,合心与性,而阐释“明德”之内涵。可见,朱熹注释“明德”,是兼心性为一体而言的。
又,人禽之辨是孟子提出的重要课题,但孟子的目的在于强调“仁义”的价值与基于仁义的内在人性。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8]史次耘先生指出,《孟子》此章的主旨是“强调人性本善,君子全顺自然之性而由仁义行。”[9]到了宋儒这里,则发展为探究人的本质,即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依据是什么的问题。朱熹总结周敦颐、张载、二程及其后学的思想,深入探讨了人禽之差异的根源。他注释孟子的人禽之辨说:
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其不同者,独人于其间得形气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为少异尔。虽曰少异,然人物之所以分,实在于此。[10]
朱熹认为,从人物的化生来看,人与物之理是相同的,这是万物一体、人能与天合一的依据。人物之界分主要在禀受的气不同,人得气之正且通者,而物得气之偏且塞者。所以人能全其性,明天理,自觉按照天理行事,而物则不能。放到《大学》中来看,人禽之异或者说人物之界分就是人具有明德,而物没有。在《大学或问》中,朱熹指出:
惟人之生乃得其气之正且通者,而其性为最贵,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盖其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此……是则所谓明德者也。11]
实际上,朱熹说“明德”是“人之所得乎天者”,已经强调“明德”是人所有,含有界分人物之内涵,而“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从而使人能识其本性进而全齐本性,则是人的本质——人的规定性所在。可见,在这里,朱熹又以孟子兼说心性的方式阐明了明德作为人物界分的意义,从而深化了孟子的人禽之辨,使孟子的人禽之辨由强调人性本善的论据上升为探讨人的内在规定性的哲学命题。
我们发现,朱熹既以《孟子》诠释《大学》,又以《大学》诠释《孟子》,这取决于那部经典的长处和特点。在工夫论方面,他更认同《大学》中“格物”、“致知”的知识理性对人格形成的作用,所以他用《大学》中的“格物”、“致知”的理念来诠释《孟子》中的“养气”、“尽性”。他说:“知言正是格物致知。苟不知言,则不能辨天下许多淫、邪、诐、遁。将以为仁,不知其非仁;将以为义,不知其非义,则将何以集义而生此浩然之气?”[12]但是在心性论方面他更认同《孟子》,故而他在心性论方面以《孟子》诠释《大学》。这样,既保证了他对先秦儒家经典的尊重态度,又满足了不同儒学典籍的整合要求。从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来说,这是“蕴谓”层次,即朱熹在思考《大学》可能蕴涵的是什么。在这一层面朱熹已跳出文本本身,而采取“以经解经”的诠释方法,他以《孟子》的心性思想回答《大学》蕴涵的心性论是什么。
四、以天理论解读“明德”的来源
朱熹在《大学章句》注释中,首先指出“明德”是“人之所得乎天”者。这是朱熹一贯的看法。如1194年《经筵讲义》中,朱熹指出“明德”是“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者也”,[13]到《大学章句》通行本中,朱熹改掉了“至明而不昧”,而“人所得乎天”只字未改。显然,这句话中的关键概念是“天”,其理论背景是自人文初始后,数千年来古圣先贤一直不断探求的天人关系的思想。
在《四书》中,《大学》并没有讲“明德”的来源,而《中庸》、《孟子》(以及《易传》)的重要贡献就是正式确立了“性与天道”的联系,从而为孔子的心理情感的仁心与人性确立了形而上之道的终极实体。当然,这种“性与天道”的联结主要是精神信仰的。《中庸》与《孟子》在论述“性与天道”的关系时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14]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15]
在子思、孟子那里,“天命”、“天道”是作为仁心、人性的形而上依据。那个作为道德人文根源的“人性”,原来体现着作为终极实体的天道的神圣性。“天道”是一个表达终极本体的概念,但它与心、性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天人一体的思想体系。在早期儒家学派的《易传》中,还有这个天人一体的宇宙论演变发展的更为系统、详尽的论述。朱熹在《大学章句》注释中,指出“明德”是“人之所得乎天”者,其实就是继承了《中庸》、《孟子》(以及《易传》)的“性与天道”的思想。
《中庸》、《孟子》虽然回答了“性与天道”问题,但是语焉不详。而真正建立系统的天地之理的形上学说的是“北宋五子”,他们通过对《周易》、《中庸》、《孟子》的重新诠释,建构了一个以“太极”、“太虚”、“天理”为最高哲学范畴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为了更进一步从学理上论证人文准则与终极实在的联结,北宋五子特别建立了一个“性与天道”合一的宇宙论体系。他们以《四书》中有限的资料对“性与天道”的重大问题作出创造性的诠释。而朱熹对“明德”来源的诠释,主要是继承了北宋五子的思想学说。
在朱熹这里,人之“明德”所得乎“天”的这个“天”,正是周子所讲的以阴阳五行造化人与万物的“天”,和二程的主宰天地万物的“天理”。朱熹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指出天地万物的存在是以天理为依据的,而人就存在于这个天理的世界中,其本身也是天理的呈现。在《大学或问》中,朱熹对“明德”来源作了系统的的论证,他指出:
天道流行,发育万物,其所以为造化者,阴阳五行而已。而所谓阴阳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后有是气。及其生物,则又必因是气之聚而后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后有以为健顺仁义礼智之性;必得是气,然后有以为魂魄五脏百骸之身。周子所谓“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谓是也。[16]
朱熹此处所指之“天”,是经过北宋五子,特别是北宋五子之首周濂溪的创发。其中所引宇宙论演变过程,出自周子《太极图说》。周子通过“无极而太极”为依据建立的宇宙图式中,天道流行,万物化生,人在其中而最为灵秀,为儒家士人建构了一个以现实人生为依据的存在家园,人们的生、老、病、死、功名利禄、生命价值,一一得到安顿。魏晋以来数百年间,儒家士人逃老逃释,精神与生命无法安顿的局面,实际上得以解决。在这里,周子和朱熹实际上将为儒家所继承的华夏文明中人文主义17]的性格和思想,推进到了极致,真正确立了儒家文化的价值内核与独特品格。朱熹逃入释老十余年,故深知周子《太极图说》之价值。他萃取周子《太极图说》的思想,阐述人物的化生,正是为了说明人的“明德”的来源,从而揭示了《大学》的宇宙论背景,将孔子、子思、孟子的心性论思想,建构在了周子的这个宇宙论上。在朱熹这里,人之“明德”所得乎“天”的这个“天”,正是周子所讲的以阴阳五行造化人与万物,无人格而又以生物为心、至仁至实的“天”。
《大学》本来并没有讲“明德”的来源,而朱熹以《中庸》、《孟子》(以及《易传》)的“性与天道”思想诠释“明德”的来源,属于“当谓”层次,即朱熹以《中庸》、《孟子》(以及《易传》)的“性与天道”思想考察出《大学》本来应当说些什么。到这一层面,朱熹发掘出《大学》更为深刻的内涵,从中显现最有诠释理据或强度的深层意蕴和根本义理出来。而朱熹以北宋理学的“性与天道”合一为理论基础,阐述人物的化生,以说明人的“明德”的来源,从而揭示了《大学》的宇宙论背景,这是“创造的诠释学”的“必谓”层次。也就是说,朱熹通过北宋理学家和自己对“明德”来源的理解,表达了《大学》到了宋代必然说出什么。
五、朱熹诠释“明明德”
的思想贡献与学术价值
经典诠释往往可以理解成“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种不同的方式。前者注重学术传承,后者注重思想创新。故而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往往会对“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做出不同的评价。本文以朱熹对《大学》所提出的命题“明明德”诠释为例,特别要加以说明,其实这两种诠释方法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对于朱熹来说,他对《大学》“明明德”诠释的学术成就、思想贡献正得益于这两种方法的同时使用。朱熹在谈到自己的读书方法时说:
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18]
那么,朱熹是如何从儒家经典中读出“圣贤之意”、“自然之理”的呢?
我们认为,这段话既可以理解成“我注六经”,也可以理解成“六经注我”。一方面,可以理解他是运用“六经注我”的方法从儒家经典中读出“圣贤之意”、“自然之理”,故而从《大学》“明明德”中读出了宇宙论、心性论、工夫论等理学思想,开拓、丰富了《大学》“明明德”的思想内涵。无论是《大学》的文本,还是汉唐经学家的注疏,“明明德”的意义都非常平易,并无宇宙论、心性论等理学思想的复杂而深刻的意义。由于朱熹在经典诠释过程中运用“六经注我”的方法,并且依照那个时代的要求,对儒家传统作了系统化的思想阐释。朱熹通过诠释《大学》而论述的理学思想,实现了儒家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创新。因此,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学术思想体系很快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古代中国主流的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这一切,均证明朱熹的《大学》诠释充分体现唐宋以后中国思想文化变革发展的时代要求。
但另一方面,朱熹作为一个儒家学者,他忠实地继承了儒家的精神传统和学术传统,他运用“我注六经”的方法,通过潜心从事学术研究,从儒家经典中领悟“圣贤之意”。具体而言,他通过对经典文字的音读训诂以及语义澄清、脉络分析、前后文意贯通等等研究工作,以实现对圣人之意的领悟。朱熹对《大学》工夫论的解读,对儒家经典中心性论及其天道论的论述,均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朱熹所做的这一系列的经典诠释工作,均是以“续夫千载不传之绪”[19]为其学术宗旨的。通过学术史的考察,可以发现,其实这些也均是早期儒家经典中早已存在的思想学说。在郭店楚简中有不少与之非常接近的思想,这就说明朱熹的经典诠释确有其历史文献学依据。以朱熹为首的理学家们应该是比汉唐诸儒更准确地抓住了先秦儒学及其经典文本的学术宗旨和历史本义,从一定意义上说确是承传了先秦儒家“千载不传之学”。
可见,朱熹从《大学》“明明德”中读出的“圣贤之意”、“自然之理”,与他运用“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两种诠释相关。进一步说,他正是通过“我注六经”来实现“六经注我”,从而使先秦儒家思想与宋代理学思想融贯于他对“明明德”命题的注释中。对于朱熹对《大学》“明明德”的诠释,我们既要充分肯定其思想创新的意义,又要充分肯定其学术传承的价值。
朱熹的子学思想及其特征和地位
蔡方鹿 解茗
朱熹思想的重要价值使多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从各个角度对朱熹思想进行了深入持久的研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然而,尽管对朱熹思想的研究已相当深刻系统,但从子学的角度来对其思想进行研究的却很少。多年来,国内外对这方面研究的著作竟然没有,论文也是寥寥无几。事实上,朱熹以自己的理学思想为标准来评判、论定子学人物及其观点时,体现了他的子学思想,尽管比较零散,但也有内在理路可循。从朱熹对这些子学人物和著作的批评或一定程度地认可的评价中,可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朱熹思想的认识,亦可从中掌握朱熹子学思想的特点及其在朱熹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并从一个侧面把握子学在宋代的流传及对朱熹思想的影响,这与朱熹所处的时代背景及自身思想发展的基本倾向和脉络相联系。
一、朱熹子学思想论要
所谓子学,指先秦至汉初诸子百家学术之总称,亦指研究诸子思想的学问,内容包括对诸子及其著作的研究,历代学者研究诸子的学问。从诸子学时期至宋代,社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朝代的更迭,子学思想作为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步流传演变并得到人们的检验取舍。朱熹以一位宋代理学代表人物的立场和眼光对诸子百家思想加以检视和评判,而得出了自己的子学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
(一)朱熹对道家的评判
朱熹对道家的思想比较熟悉,他曾批评历代那些注解《老子》和《庄子》的人,认为他们的注解多是为就己意而对老、庄经典进行“臆说”,歪曲了老、庄的本义。他说:“《庄》、《老》二书,解注者甚多,竟无一人说得他本义出,只据他臆说。某若拈出,便别,只是不欲得。”[1]由此可见,朱熹不但对老、庄之学比较熟悉,且自认是明白老、庄本义的。朱熹身为儒家,却并没有拘泥于门户之见对道家之学进行简单的否定,而是站在一种较为客观的立场对道家思想进行中肯的分析。
对于道家创始人老子的思想,朱熹有这样的评价:“老子之术,自有退后一著。事也不搀前去做,说也不曾说将出,但任你做得狼狈了,自家徐出以应之。如人当纷争之际,自去僻静处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长短,一一都冷看破了,从旁下一著,定是的当。……因举老子语:‘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若客,涣若冰将释。’”[幻可见朱熹认为老子的柔弱不争不仅是其主要思想,同时也是其处事的谋略和手段,是一种“术”,这种退让不完全是消极避世,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手段,认为老子“取天下便是用此道”[3]。老子思想在汉初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让经历多年战乱、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的西汉社会得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朱熹对此评价道:“其言易入,其教易行。当汉之初,时君世主皆信其说,而民亦化之。虽以萧何、曹参、汲黯、太史谈辈亦皆主之,以为真足以先于六经,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4]肯定了老子思想在政治教化、治国治民方面有可取之处。“其学也要出来治天下,清虚无为,所谓‘因者君之纲’,事事只是因而为之。如汉文帝、曹参,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肤,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将去。老氏之学最忍,它闲时似个虚无卑弱底人,莫教紧要处发出来,更教你枝梧不住,如张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学。”[5]认为老子之学看似清虚无为、卑弱不争,实则无为而治,柔弱胜刚强。朱熹更曾多次直接表达他对老子的欣赏之意:“今观老子书,自有许多说话,人如何不爱!”[6]“老子说他一个道理甚缜密。”[7]朱熹更明确指出二程理学受到了老子的影响,“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取老氏之说也。”[8]既然二程学说从老子思想中有所取,作为二程后学的朱熹实际上等于间接承认了他也受到了老学的影响。朱熹虽对老子之学多有肯定和赞赏,但二人毕竟分属不同的学派,思想上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因此朱熹不可避免地也对老子的一些思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儒家最重伦理,而老子却认为道与仁义不并存,因此对孝慈礼仪废弃不讲,朱熹由此批评老子“害伦理”:“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声,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伦理。”[9]朱熹对道家一派于乱世中为保全自身而厌世避祸、崇尚空寂的思想提出批评:“儒教自开辟以来,二帝三王述天理,顺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礼之道,后世圣贤遂著书立言,以示后世。及世之衰乱,方外之士厌一世之纷拏,畏一身之祸害,耽空寂以求全身于乱世而已。及老子倡其端,而列御寇、庄周、杨朱之徒和之。孟子尝辟之以为无父无君,比之禽兽。”[10]同时朱熹也对老子的价值观加以针砭:“老子之术,须自家占得十分稳便,方肯做;才有一毫于己不便,便不肯做。”[11]从朱熹对老子的这些批评,可见儒、道两家思想存在的差异。
对于道家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庄子,朱熹也同样是肯定与批判兼而有之。朱熹认为庄子才高识远,“其才高,如《庄子·天下》篇言‘《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若见不分晓,焉敢如此道!”[12]并指出庄子与佛教有区别,佛与儒对立,而庄子的思想可以和儒家互相沟通。“或问:‘《中庸》说道之费隐,如是其大且妙,后面却只归在‘造端乎夫妇’上,此中庸之道所以异于佛老之谓道也。’曰:‘须更看所谓‘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处,圣人之道,弥满充塞,无少空阙处。若于此有一毫之差,便于道体有亏欠也。若佛则只说道无不在,无适而非道;政使于礼仪有差错处,亦不妨,故它于此都理会不得。庄子却理会得,又不肯去做。如《天下》篇首一段皆是说孔子,恰似快刀利剑斫将去,更无些子窒碍,又且句句有著落。如所谓‘《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可煞说得好。’”[13]正因为此,朱熹对庄子思想的评价较高:“盖自孟子之后,荀卿诸公皆不能及。”[14]“庄子比康节亦仿佛相似。然庄子见较高,气较豪。”[15]将儒家先贤和北宋著名理学家邵雍置于庄子之后,可见其对庄子评价之高。朱熹还把庄子与老子进行对比,认为《庄子》的文风豪放跌荡,说理方式独具风格,“将许多道理掀翻说,不拘绳墨”[16],肯定庄子说理“较开阔,较高远”[17]。虽说朱熹对庄子思想多有肯定,但站在理学家的立场,朱熹也对其作了批评。例如说庄子在入世方面比老子更加消极,“老子犹要做事在,庄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说道他会做,只是不肯做。”[18]对于庄子宣扬的一些神异思想,朱熹也进行了斥责:“若曰‘旁月日,扶宇宙,挥斥八极,神气不变’者,是乃庄生之荒唐。”[19]对庄子等人于乱世中追求全身养生的道家思想朱熹亦加以批评,甚至指斥庄子专计利害,更将晋室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清谈老庄:“庄子之意则不论义理专计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盖迹其本心,实无以异乎世俗乡原之所见,而其揣摩精巧,校计深切,则又非世俗乡原之所及。是乃贼徳之尤者。所以清谈盛而晋俗衰,盖其势有所必至。而王通犹以为非老庄之罪,则吾不能识其何说也。”[20]认为正是由于清谈老庄,才引得纲纪大坏,法度无存,而导致天下大乱。朱熹这种评价显然是对受老庄思想影响的魏晋玄学的批评。
朱熹口中的道家有时并不全指先秦的老庄之学,他把道教也称为道家。然而虽然称呼相同,但先秦道家与道教的区别,朱熹心里是明白的。朱熹指出,从老子道家到道教,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老氏初只是清净无为。清净无为,却带得长生不死。后来却只说得长生不死一项。如今恰成个巫祝,专只理会厌禳祈祷。这自经两节变了。”[21]认为道教已然偏离了老子的原意,由世俗文化派别转变为讲巫祝祈祷的宗教。他认为道教后来衰落与虚妄,佛教思想却日益精妙高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道、佛二教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互相错位的现象。佛教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吸取融会了老庄之学的优长,而道教徒们在发展自己的教义时,却不重视道家固有之书,反而吸取了释氏的糟粕:“道家有《老》、《庄》书,却不知看,尽为释氏窃而用之,却去仿效释氏经教之属。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宝悉为人所盗去,却去收拾人家破甕破釜。”[22]讥讽道教拾取了释氏的破甕破釜,却被释氏盗走了自己的珍宝。因此,朱熹一方面不遗余力的批评道教,另一方面又对正宗的老庄道家之学加以一定程度的肯定和称赞,将其与道教区分开来。朱熹更明确地告诉其弟子,老庄“言有可取”[23],其书是值得读的,不可随意否定。而读老庄的关键是要弄清老庄思想与儒家圣人学说的区别之处,以便能够扬长避短,为我所用。朱熹正是在深入研究了道家思想后,吸取道家哲学的道本论等思想,以天理论道,把道与天理结合起来。由于朱熹不拘于门户之见,博采众家之长,最终建立起一个中国哲学史上最为完备、缜密的理学思想体系,成为一代理学大师。
(二)朱熹对法家的评判
法家学说的核心是“法治”,提倡以严刑峻法治民,这与先秦儒家所倡导的“礼治”、“德政”堪称相对,因此儒家历来批判法家都是不遗余力的。但到了南宋时期,法家学说经过上千年时光的检验,证明其学说并非一无是处,事实上,法家的很多理论在维护社会稳定、富国强兵方面确实起到积极的作用。所以,朱熹在评判法家时,一方面固然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以批评为主,另一方面,又给予法家之学以适当的肯定并有所吸收。
朱熹对法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只见刑名,学问浅陋。他说:“盖老氏之学浅于佛,而其失亦浅。正如申韩之学浅于杨墨,而其害亦浅。”[24]朱熹在《孟子精义》中又说:“如申韩只见刑名,便谓可以治国,此目不见大道,如坐井观天井蛙,不可以语东海之乐。”[25]并引程颢的话加以批评:“杨墨之害甚于申韩,佛老之害甚于杨墨,杨氏为我疑于仁,墨氏兼爱疑于义,申韩则浅陋易见。”[26]法家之学偏向功利性和实用性,以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较偏向政治学说,在哲学思辨方面则显不足,朱熹就是针对这一点,批评申韩之学关于治道的途径过于简单化,认为只见刑名是不足以治天下的;第二,刻板严峻,惨刻无恩。朱熹认同对法家人物“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东坡谓商鞅、韩非得老子,所以轻天下者,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27]的评论,更将其斥为“误人主之术”。他说:“韩非、李斯惨刻无恩,诖误人主之术,非仁人之所忍言也。”[28]朱熹认为法家实施严刑峻法、重赋税,是残忍、无恩的表现,是误主的行为,非仁人所为;第三,擅用阴谋机心。他说:“而其实必用机心,扶阴谋然后可,……彼管仲、商君、吴起、申不害非无一切之功,而所以卒得罪于圣人之门者,正在于此。”[29]朱熹认为申不害等用“机心”、“阴谋”之道治理国家,虽然也有一定的功效,但是却违背了圣人治国之道,所以要求人们加以熟察;第四,急功近利,不讲仁义。“‘如李悝尽地力之类,不过欲教民而已,孟子何以谓任土地者亦次于刑?’曰:‘只为他是欲富国,不是欲为民。但强占土地开垦将去,欲为己物耳,皆为君聚敛之徒也……如李悝尽地力,商鞅开阡陌,他欲致富强而已,无教化仁爱之本,所以为可罪也。’”[30]儒家最重仁义道德,而法家则倾向功利,两家在价值观上有着根本的区别。朱熹认为,法家虽然有时也做一些看似有益于人民的事,但他们的出发点却并不是真的爱民、为民着想,而只是为了富国,替君主敛财而已。因此朱熹站在以儒家仁义教化为治国之本的立场,批评法家追求富国强兵而不重视教化。他说:“彼非以仁义为不美也,但急于近功,谓仁义为迂阔,不切时务,不若进富国强兵之术也。若其诚然,商鞅之徒为之,孟子不为也。”[31]一句“商鞅之徒为之,孟子不为也”,充分表现出儒、法两家思想的差异。
朱熹对法家思想虽有诸多批评,但同时也有所肯定和吸取。他在批评商鞅重利轻义的同时,也承认商鞅开阡陌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他说:“商鞅开之,乃是当时井田既不存,便以此物为无用,一切破荡了。”[323朱熹也肯定法家对于诚信的重视。“无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虽商鞅之徒亦不可为政。”[33]同时朱熹也认可法家所说的治国要“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34],肯定法家“辟以止辟”的法价值观念。他说:“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过于惨刻。今之士大夫耻为法官,更相循袭,以宽大为事,于法之当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虽舜亦不免。教之不从,刑以督之,惩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劝戒,所谓‘辟以止辟’,虽曰杀之,而仁爱之实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则人无所惩惧,陷于法者愈众,虽曰仁之,适以害之。”[35]朱熹认为士大夫们以“宽大为事”的立法、执法准则虽是出于一片善意,是由于对他人怀有的一份慈悲、怜悯之心而起,但若犯法者不能受到相应的惩罚,就会使他们因为无所畏惧而更加的肆无忌惮,从而令更多的无辜者受难,这片善心的结果就会导致反而害了更多人。从这个层面来讲,法家所提倡的对犯罪者所实施的严刑峻法,实际上也是对更多无辜百姓的一种保护,也算是另一种仁爱。因此他建议天子不讳于“深于用法,而果于杀人”[36],“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刑”[37]。朱熹还融合了法家法无等级的观念,确立了公天下的法律价值观。认为法的公正性,是韩非法治思想的精华所在。朱熹对此是赞同的:“盖谓法者,天下之大公,……舜不敢禁者,不以私恩废天下之公法也。……盖以法者先王之制,与天下公共。为之士者受法于先王,非可为一人而私之。”[38]朱熹对法家思想既批判又吸取,形成了一套人治与法治相结合,以正君心、严吏治、举贤才、公平慎刑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体系,力图为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服务。
(三)朱熹对杂家的评判
朱熹对于杂家,总体来说评价不高。诸葛诚之对《吕氏春秋》十分推崇,曾盛赞其煞有道理,甚有好处。朱熹对此有这样的评价:“尝见他(诸葛诚之)执得一部吕不韦《吕览》到,道里面煞有道理,不知他见得是如何。”[39]“诚之常袖吕不韦《春秋》,云其中甚有好处。及举起,皆小小术数耳。”[40]前一句“不知他见得是如何”表达出朱熹对于诸葛诚之对杂家学说的推崇态度不以为然;而后一句更是直接批评杂家之学不过是不值一提的术数之学。由此可见朱熹对于杂家学说抱有贬低轻视之意。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认为杂家之学过于驳杂。朱熹为学虽讲求博学,但他强调,“博学,亦非谓欲求异闻杂学方谓之博”[41],而应是指“博学,谓天地万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当学。然亦各有次序,当以其大而急者为先,不可杂而无统也。”[42]可见朱熹所指的“博”应是掌握“天地万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的广博道理,而且在学习时还要有一定的次序,不能杂而无序。博学的目的是为了穷理,所以在博的基础上,还必须返约。博而不能返于约,就无法穷理,只会流于杂。“学之博者似杂,其约者似陋。惟先博而后约,然后能不流于杂,而不掩于陋也。”[43]在朱熹看来,杂家既没有在博的环节掌握好轻重缓急、先后次序,又缺失了约的环节,以致流于驳杂,难登大雅之堂。
其二,认为杂家少讲仁义,而多说权谋功利。杂家学说虽是博采众家之长,但并非没有侧重。在《吕氏春秋》的思想体系里,明显是以道家的哲学思想为尊。在提及各学派时,《吕氏春秋》一般都按照老、孔、墨……的顺序排列,将老子置于最前;在涉及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等方面,《吕氏春秋》较多吸取了儒、墨两家以及管仲的内容;在哲学思想领域,则对老子大加推崇,同时也充分肯定了法家思想中的合理部分。而且《吕氏春秋》作为一部以为现实政治提供理论依据为编写目的的著作,其整体风格难免倾向于实用性及功利性,与儒家圣人之道的价值观有所抵触。对于这一点,朱熹并未直接批评吕不韦或《吕氏春秋》,而是通过对贾谊、司马迁以及苏辙等人的批评表达了他的态度。“贾谊、司马迁皆驳杂,大意是说权谋功利。说得深了,觉见不是,又说一两句仁义,然权谋已多了,救不转。苏子由《古史》前数卷好,后亦合杂权谋了。”[44]朱熹虽对杂家多有批评,但并未认为杂家一无是处。在《别本韩文考异》的《读仪礼》中载有这样一句话:“百氏杂家尚有可取,况圣人之制度耶。”从“百氏杂家尚有可取”一句可以看出,朱熹并不完全否定杂家,而是承认其亦有可取之处。
(四)朱熹对墨家的评判
朱熹对墨家、阴阳家、纵横家这三家的评论都不是很多,但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对于墨家,朱熹通常将墨子与杨朱相联系,一起进行评论。朱熹远承孟子,以杨墨为异端邪说。他说:“墨子爱无差等,而视其至亲无异众人,故无父。无父无君,则人道灭绝,是亦禽兽而已。”[45]又说:“墨氏‘爱无差等’,故视其父如路人。……如杨墨逆理,无父无君,邪说诬民,仁义充塞,便至于‘率兽食人,人相食’。”[46]同时,朱熹十分注意纠正韩愈“孔墨必相为用”的说法,毫不客气地批评:“昌黎之言有甚凭据?”[47]以清理儒学传承中前儒对杨墨学说的异论。而在杨墨学说的比较方面,朱熹也与孟子一样,对墨子的评价要更低一些。孟子在《尽心下》中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而朱熹则认为,虽然杨墨皆是邪说,但是墨子之说相对杨朱而言更加的矫伪不近人情而难行。关于杨墨之学的源头,朱熹前后态度的变化值得注意。二程认为杨、墨其实都是出自于儒门,在《二程遗书》中载有这样几句话:“杨、墨,皆学仁义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张,杨子似子夏。”[48]“大凡儒者学道,差之毫厘,缪以千里。杨朱本是学义,墨子本是学仁,但所学者稍偏,故其流遂至于无父无君。”[49]早期朱熹在《孟子精义》一书中,继承了二程这一观点,同样不怀疑杨墨学出儒门。但后来他否认了这一观点,认为“杨墨之说恐未然。杨氏之学出于老聃之书,墨子则晏子时已有其说也,非二子之流也”[50]。朱熹的态度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从认可其学出于儒门到将其逐出门视为异端,除了有学术思想不认同方面的原因,其实也有着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在孟子生活的时代,杨墨之学是当时的显学,当时孟子之所以会如此激烈的“辟杨墨”,也是为了显圣人之道。而朱熹当时所处的环境与孟子相仿,只是对象从杨墨之学换成了佛老之学。在朱熹看来,佛、道二教的危害类似于孟子时杨墨的危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佛老学说对儒家学说正统地位的威胁,令朱熹意识到必须要像孟子当年“辟杨墨”一样辟佛老;而将杨墨从儒门逐出,则是为了维护儒门的纯粹性,赋予自己对当时佛、道二教的批判以更权威的理由和说服力。
(五)朱熹对阴阳家的批评
朱熹对阴阳家的评价较低,在朱熹的著作中他对阴阳家轻视的态度非常明显。朱熹对阴阳家的批评不仅是因学术观点或价值观的冲突,而且是对其学术价值的一种彻底否决。在《朱子语类》中有这样一段对话:“问‘索隐集注云:深求隐僻之理,如汉儒灾异之类,是否?’曰:‘汉儒灾异犹自有说得是处,如战国邹衍推五德之事,后汉谶纬之书便是隐僻。’”[51]从这段对话可见朱熹对邹衍“五德终始”之说和后汉谶纬之学的蔑视,认为其根本没有说得是处。而在另一段对话里,朱熹的这种态度则表现得尤为明显。他说:“游氏引邹衍谈天、公孙龙诡辨为智者之过,亦未当。若佛老者,知之过也。谈天诡辨,不足以为知者之过。知者之过非一端,如权谋术数之类亦是。龙、衍乃是诳妄,又不足以及此。”[52]朱熹认为,如果说佛老是“知者之过”,那么像公孙龙、邹衍之类谈天诡辨的人甚至还不足以称之为知者之过,将邹衍视为诳妄之辈,可见对其评价之低。朱熹对阴阳家的这种态度不排除也有些现实原因,因为他当时极力要抗争的佛、道之学中的道教,其学说中就吸取了不少阴阳家的学说内容,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朱熹对这种带有神秘色彩学说发自内心的排斥。
(六)朱熹对纵横家的评判
朱熹对纵横家的评价也是以贬为主。首先,朱熹对纵横家学说评价不高:“问《孟子》‘好辩’一节。曰:‘当时如纵横刑名之徒,孟子却不管他,盖他只坏得个粗底,若杨墨则害了人心,须着与之辩。’”[53]从这句对话可见,朱熹将纵横之学与刑名之学置于杨墨之学下面,认为其道理粗浅,所害亦浅。而从他对贾谊的评价中也可见他对纵横之学的不满:“贾谊之学杂,他本是战国纵横之学,只是较近道理,不至如仪、秦、蔡、范之甚尔。他于这边道理见得分数稍多,所以说得较好。然终是有纵横之习。缘他根脚只是从战国中来故也”。[54]可见朱熹认为贾谊也属纵横家之列,是纵横家里面较为懂得道理的人。而多数纵横家在朱熹心中即是不近道理之人。另外,纵横家偏向政客,不讲忠义,亦不讲原则,对于他们来说,只要可以达到目的,获得荣华富贵,基本上所采取什么手段、要对自己进行怎样的改变都不是问题,这一行为准则一直为儒家学者所不齿,孟子就称其为“妾妇之道”,而朱熹也通过讽刺的方式来表达了他的态度:“古之圣贤以枉尺直寻为大病,今日议论乃以枉尺直寻为根本。若果如此,即孟子果然迂阔,而公孙衍、张仪真可谓大丈夫矣。”[55]说明公孙衍、张仪之类纵横家在朱熹心中并不能算是大丈夫。朱熹更认为纵横学对当时社会起到了不好作用:“周衰之末,战国纵横,用兵争强,以相侵夺,当时处士务先权谋,以为上贤。先王大道陵迟隳废,异端并起……天下岂复有王道哉,岂复知有仁义哉!”[56]但朱熹对纵横家也并非全无肯定之处,“古人有取于登高能赋,这也须是敏,须是会说得通畅。如古者或以言扬,说得也是一件事,后世只就纸上做。如就纸上做,则班扬便不如已前文字。当时如苏秦张仪,都是会说。《史记》所载,想皆是当时说出。”[57]肯定了纵横家善辩之才。
二、朱熹子学思想的特征、
地位和影响
(一)朱熹子学思想的主要特征
从上述朱熹对各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价来看,虽然朱熹的子学思想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评价的语句较为零散,但也并非没有内在理路可循,朱熹的子学思想主要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既有批评,也有肯定,但总体来说,以贬斥为主。朱熹对诸子学说的态度既不同于荀子对其他学派的大加批判,也不同于以吕不韦为首的杂家对各家思想的只赞不贬,而是力求客观,多半从肯定与否定两个方面着手,很少有一面倒的情况出现。对于一些不但在当时是显学,到了朱熹的时代依然有一定影响力的学说,如道家、法家等,朱熹的态度就比较认真,他不但深入研究了它们,而且也从他的立场、思想出发,尽量客观地评价,对其有害之处更是精心分析,以免后人误入歧途。仔细看他的语句就会发现,尽管朱熹已极力保持中立,但毕竟立场有别,学术思想有所抵触,朱熹对这些诸子之学的贬低要多于他所给予的肯定。而朱熹所站的立场,就是他子学思想的第二个特征。
第二,站在儒家的立场,以儒学的价值观作为其对诸子学评判的标准。朱熹对各家思想有肯定、有吸取,但批评的语句更多,而他所批判的方面,都是其与儒学思想相抵触的方面。儒家思想要求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施行仁政,重义轻利,也强调纲常礼法,上下有别。以这些儒学基本原则为出发点,朱熹批评道家的消极避世、乱世中只求保全自身;指责法家刻薄寡恩、知刑而不知德;认为阴阳家诳妄谈天,不值一提;批评墨家“兼爱”是学“义”之偏,有违伦理纲常;指出法家、杂家和纵横家都有功利主义倾向,重利轻义。可见无论朱熹如何客观,他心中这条儒学基本原则的底线是不能冲破的,也正是这条底线,使得朱熹的子学思想呈现出与杂家截然不同的特征。
第三,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这也是朱熹子学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质。朱熹论诸子学说,有些不一定完全从其学术角度考虑,现实社会环境也会对朱熹的态度和倾向造成一定的影响。朱熹理学产生的针对性在于佛、道二教由于有着精致的思辨性和对普通百姓希望长生不死或拥有美好来世的愿望具有一定的诱惑性和吸引力而一时大盛,甚至对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所以说为了确保儒学的权威和正统地位,儒家学者们在完善自己学说的同时,也须削弱佛、道二教的影响,而要想让理学真正成为显学,王安石新学也是必须要排斥、针对的对象。朱熹子学的这一特征在他评价道家、法家和阴阳家的学说时体现得尤为明显。他斥责庄子对神异思想的宣扬“若曰‘旁月日,扶宇宙,挥斥八极,神气不变’者,是乃庄生之荒唐”;并对阴阳家神秘诳妄之学大加贬低,皆因这两方面是道教学说最初的来源之一。而佛教思想能够顺利地完成本土化并进一步的发展完善,也与道家思想脱不了关系。其视法家为浅陋刻薄的批判态度,则多少是因为王安石新学被视为多有得于包括法家和名家在内的刑名度数之学。对墨子之学先认为其源自儒学,而后又否认的态度上的改变也是出于能够更好的辟佛老的需要。故而朱熹对这几家学说的态度不仅是出于学术上的考量,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
(二)子学思想在朱熹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
在朱熹的整个思想体系中,他的子学思想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关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朱熹的子学思想并不像他的理学或经学等思想那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缜密的、系统的思想体系,而是通过一些较为零散的语句体现出来;另一方面则是受到尊经抑子的传统观念影响。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诸子之学视为经术的支流与畸变,“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58]这种视诸子学为道术分裂的产物的思想影响了很多后来的学者,导致自汉以来子学的地位始终被置于经学之下的结果。所以以朱熹理学大家和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的地位,其重大的研究价值虽然使得多年来国内外对其思想的研究者众多,但大多数学者多是从哲学、美学、史学、文学、经学、教育学、自然科学、政治、经济、伦理、中西比较及文献考据等角度来对朱熹思想进行研究,从子学的角度来对其思想进行研究的却很少,至今尚未有一个整体的、综合性的系统研究。
朱熹的子学思想虽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这并不代表其不重要。首先,朱熹之所以能够最终建立起一个庞大、缜密、精致的理学思想体系,除了有对儒家思想精华的吸取和完善外,也离不开他对诸子思想的融合和吸收。他吸取了道家哲学的道本论思想,把道与天理相结合,从而为儒家的伦理道德寻找到形而上的本体论哲学依据,使儒学具有了思辨性;他将法家“辟以止辟”和法无等级的理念与儒家的德政、人治思想相融合,形成了一套以正君心、严吏治、举贤才、公平慎刑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思想体系,基本适应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需要;他在对道、心、性、阴阳、太极、器、物、体用、本末、动静、已发未发、情、欲、知行、形神、变化等众多中国哲学范畴的内涵及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论述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命题、理论和独到的见解,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思辨水平,多少也是受到了道家、玄学及佛教思想的影响。其余像墨家和名家名辨等思想他也多少有所借鉴和采纳。所以全祖望会在《宋元学案·晦翁学案序录》中认为朱熹是“遍求诸家,以收去短集长之益。若墨守而屏弃一切焉,则非朱子之学也。”正是由于朱熹这种不拘于门户之见,广泛吸取各派学说包括诸子思想的合理内核的学术态度,他才能最终成为继孔孟之后中国儒学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代宗师。另外,朱熹的子学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朱熹的学术思想,自宋末以后,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都是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思想,他所撰写的《四书章句集注》等更是科举考试的官方教科书和标准答案,所有要通过科举晋身仕途的学子都必须熟读精研朱熹著作,而子学思想作为朱熹思想体系的一部分,自然也不例外。朱熹的子学思想就在这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学子的思维,使他们对先秦诸子的评价和判断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朱熹的影响而有所倾向。所以说朱熹的子学思想虽说不是最被重视,但也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对朱熹子学思想的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推动对朱熹思想的全面研究和完善,使其更加体系化和整体化。
论朱子的理气动静问题
乔清举
一、问题的提出
太极或理的动静问题,是朱子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学界历来争议较大甚至观点截然相反的一个问题。冯友兰先生是在哲学范式下进行朱子哲学研究的首创者,他认为在朱子哲学中,有动之理,亦有静之理,但理不动亦不静。他说:“太极亦无动静。”[1]又说:
太极中有动静之理,故气得本此理以有动静之实例。其动者便为阳,其静者便为阴。阴阳亦形而下者。至于形而上之动静之理,则无动无静,所谓“不可以动静言”也。[2]
冯先生晚年仍然坚持此观点,并批评“理可以动、可以生气”之说。他说:
一般是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的,有情意,有计度,有造作的是特殊。情意之理并没有情意,计度之理并没有计度,造作之理也不会造作。举一个例说,动之理并不动,静之理也并不静。只有具体的动的东西才动,只有具体的静的东西才静。[3]
理“不动说”的又一著名代表是牟宗三先生,其为学界所耳熟能详的观点是朱子之理“是但理,只存有而不活动”。[4]他说:
(伊川朱子系)此系是以《中庸》《易传》与《大学》合,而以《大学》为主。于《中庸》、《易传》所讲之道体性体只收缩提练而为一本体论的存有,即“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于孔子之仁亦只视为理,于孟子之本心则转为实然的心气之心,因此,于工夫特重后天之涵养(“涵养须用敬”)以及格物致知之认知的横摄“进学则在致知”,总之是“心静理明”,工夫的落实处全在格物致知,此大体是“顺取之路”。[5]
冯友兰言朱子之理不动亦不静,是为了强调朱子之理的先验性与形上性,以揭示中国哲学概念的抽象性质,或曰“哲学”性质,以与西方哲学颉颃媲美,从而使中国哲学研究同时亦成为引进与建立“哲学”的思维方式之渠道。此实为冯友兰那一代学者的中国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牟宗三的中国哲学研究亦属于“哲学”范式,他认为朱子之理“只存有而不活动”,此点实同于冯友兰。然其意图则在于批评朱子之理不能创生万物,由此判定朱子哲学非儒家正宗,乃“别子为宗”。在主张“不动说”之学者序列中,还可以加上陈来、刘述先、李明辉诸位先生[6]。在学术方法与旨趣上,大体陈来承冯友兰,刘述先、李明辉承牟宗三。
可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与以上诸论截然不同的观点。贺麟、成中英等先生主张,在朱子哲学中,理是能动的。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贺麟、张荫麟、冯友兰之间曾发生过关于理的动静问题的争论。据贺麟1938年6月15日日记记载:“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中已提出太极之动静与有限事物之动静不同的观点,但因被张荫麟质问‘太极是理,如何能动’后,遂声明太极动静说不通,且以周子的太极为形而下之气。”[7]贺麟于20世纪50年代又指出:“朱熹把太极说成理,无声无臭是无极,至高无上是太极,理有动有静。朱熹发现理是能动的,这是一绝大的贡献,可以与黑格尔媲美。”[8]成中英先生认为:“朱子所谓理气,亦如太极之阴阳相互为用,并非静者恒静、动者恒动的分为二橛。更有进者,朱子一方面说理‘无作为’,另一又说‘未动而能动者,理也。未动而欲动者,意也’(《语类》)。可见朱子对理的了解有多层次多方面的意涵,而不可简化为一单向面的静止之理。”[9]
上述观点分歧表明了太极动静问题在朱子哲学中的复杂性,可见,非充分地占有材料、深入地进行分析,不能穷究朱子之意也。
二、形而上下两种动静
受分析哲学语言分层理论的启发,笔者认为,朱子“动”、“静”概念的内涵,亦可分为形而上、形而下两个层次。换言之,其动静概念之使用可同时指涉形上、形下两个层次。前者为理或太极的动静,可谓本体意义的动静;后者为气的动静,可谓现象意义之动静。动静之分为两个层次,在朱子哲学中是十分明显的。周子《通书》谓:“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朱子解释说: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者,物也。”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下者,则不能通,故方其动时,则无了那静;方其静时,则无了那动。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就人言之,语则不默,默则不语;以物言之,飞则不植,植则不飞是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则神而莫测,方其动时,未尝不静,故曰:“无动”;方其静时,未尝不动,故曰“无静”。静中有动,动中有静,静而能动,动而能静,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错综无穷是也。端蒙。[10]
此段中,朱子主张理与物各有动静;物之动与静相互隔离不通,理之动与静则相互贯通,可见其动静说是分为两个层次的。所以,辨别动静的两个层次是我们理解朱子理之动静问题的关键。在朱子那里,理无动静是说理无形而下的动静,非谓其无形而上的动静;太极有动静,是谓其有形而上的动静,非谓其有形而下的动静。如他说:“太极理也,理如何有动静?有形,则有动静。太极无形,恐不可以动静言。南轩言‘太极不能无动静’。未达其意。”[11]又,“若谓太极便是动静,则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极之言亦赘矣。”[12]此两段中之动静,显然为形下意义的动静。朱子又云:“未动而能动者,理也。未动而欲动者,意也。”[13]此处描述理的第一个“动”,显然是形而下的动,第二个则是形而上的。朱子没有把两个层次的动静分别开来陈述,而是形而上下混说,其理之动静问题研究中出现之分歧,多与此种言说方式有关。明乎此,则分析朱子的理之动静思想,须辨别其所指究竟是形上抑或形下,庶几可以避免误解。
朱子严形而上下之别,故两种动静的差异在他那里是十分明显的。此差异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为显与微的区别。形下之动静是显,处于可感知的经验世界;形上之动静则是微,处于不可感知的抽象世界。其二为偏滞与兼通的区别。形下之动静各偏于一方,不能贯通;形上之动静则是兼通的,动静一如的。从现代哲学来看,朱子之所以区别两种动静,意在表明形上之动静是本体性的、永恒的、价值性的,是理实现于外部世界和规范事物样态的本体性力量。理若无价值性,则混同于现实世界的任何一物,从而不具有规范意义;理若无永恒性,则沦为生灭不定之具体物,从而不足以具有规范性。此两者均可使人类社会因失据陷入无序、使自然世界因失律而陷入混沌。所以,理必须具有价值性、永恒性,此两种性质则来自理的本体性、超越性,一言以蔽之,即形上性。此种形上性使得理一定会实现于外部世界,成为世界之规范,这就是理的动,也是它的本体性力量的表现。这意味着理既不是“但理”,也不是“纯概念”。
三、理之动静的指涉
概念:兼、有、涵、该贯
朱子关于太极或理与动静的指涉关系,有“兼”、“有”、“涵”、“该贯”等说法。众所周知,在古代哲学家中,朱子可谓思维缜密、用词审慎的一位,故其关于理之动静的不同说法,值得深入分析。“太极兼动静”乃其门人梁文叔提出,朱子反对此说法,云:
不是兼动静,太极有动静。喜怒哀乐未发,也有个太极;喜怒哀乐已发,也有个太极。只是一个太极,流行于已发之际,敛藏于未发之时。”[14]
此处之动静是喜怒哀乐之未发与已发,是心理活动,可见是形而下的。若证之以下二条,则此义愈加明显。
太极无方所,无形体,无地位可顿放。若以未发时言之,未发却只是静。动静阴阳,皆只是形而下者。然动亦太极之动,静亦太极之静,但动静非太极耳。[15]
此段明言动静为形而下者,动静之主体非太极。故朱子所谓太极不兼动静,实为太极无形而下之动静。“兼”为形而下地具有。按朱子哲学之思想,若太极有形而下之动静,则其沦为普通经验之物,失去其超越性、永恒性与价值性。太极若无价值性,则朱子之哲学、甚而言之理学已不能建立,人类亦不必存在矣,因其可沦为与动植物一类。此盖为朱子不以经验之动静指涉太极之深意所在。朱子强调太极流行于已发,敛藏于未发,其意为流行时有个太极在,非流行为太极也;敛藏时亦有个太极在,非敛藏为太极也。流行和敛藏皆形而下之动静。
“太极之有动静”是朱子的主张。《通书解》谓:
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诚者圣人之本,物之终始、而命之道也。其动也、诚之通也,继之者善,万物之所资以始也。其静也,诚之复也,成之者性,万物各正其性命也。动极而静,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16]
此段含有形而上下两种动静。“物之终始”、“万物之所资始”、“万物之所成性”,显系形而下之动静。外部世界之动静乃各种现象的交替不已之运动,乃是天命之流行的表现。朱子在此是把形下之动静与“诚”、“太极”相关联而言。“太极之有动静”,乃是强调太极诚固不可以形下之动静指涉,因其为形上也;然亦不可离形下之动静而言。否则,太极、理、形上即沦为孤绝之死理,经验世界即沦为无理之气运世界,上下割断,体用殊绝,非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之义矣。此断非朱子哲学之义。在朱子哲学中,形上世界之孤存或可勉强言之,因其有理之逻辑在先之义,而其所谓经验世界则断然为理气统一之过程世界。故此处之“太极之有动静”,系合形而上下而统言之,言太极既为理,亦表现于气之运动,两者统一。故天命流行亦可谓太极之动静,此即太极之“有”动静。朱子之天命之流行,大抵同于“与道为体”。
太极含动静,在《朱子语类》中又作“函”、“涵”,三者义同。
盖谓太极含动静则可。(朱子自注:以本体而言也。)谓太极有动静则可。(朱子自注:以流行而言也。)17]
以此处朱子之表述来看,所谓“含”,指本体而言,故当为含动静之理。朱子亦明言“太极自是涵动静之理”[18]。如前所述,“有”是一个包含形而下的过程,不纯是本体。
朱子还有一个说法是“实理该贯动静”。周子《通书》有“诚无为,几善恶”一条。朱子释云:
诚,实理也;无为,犹“寂然不动”也。实理该贯动静,而其本体则无为也。“几善恶。”“几者,动之微”,动则有为,而善恶形矣。“诚无为”,则善而已。动而有为,则有善有恶。”[19]
“该”是包含、包括,“贯”是贯穿、统摄。“实理该贯动静”即理包含、统摄并表现于动静。朱子云“无极之真是包动静而言”[20],即是此义;而理之本体却是“无为”的,即“无造作”,无形而下的动静。理既超乎形而下的动静,故其为形上之静、本体之静。“静者为主。植。”[21]此即所谓“静”为太极之本的思想。此段到“几”之后,进入形而下之动静世界,故有善恶产生。在朱子哲学中,本体之静,可对应形而下的动静。图示如下:
但是,既然太极是动而能静、静而能动,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则其动静实质上是形而上的动静一如,相互贯通,故言本体为静亦可、为动亦可。
太极只是涵动静之理,却不可以动静分体用。盖静即太极之体也,动即太极之用也。譬如扇子只是一个扇子,动摇便是用,放下便是体。才放下时,便只是这一个道理。及摇动时,亦只是这一个道理。[22]
若言太极或理为静,则易于与形而下之静相混淆,以形下之静为太极之体、形上之动为太极之用。这样就把太极有限化、具体化了,此是朱子所反对的。此段“不可以动静分体用”的动静,乃是形而下的动静,不能为太极之体、用。所谓“静即太极之体”之静,乃是本体的静,是理之本然的存在状态;而“动”则为理在现实世界的发用、实现,表现为形而下的动。此处须注意者,朱子之表述本体之静,是与形下之动相对而言出的,故易被误解为形下之静。所以,朱子后来废除了太极为体、动静为用的说法,提出“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23],明确地把太极和形而下的动静分开。此意还见于朱子与杨子直第一书。但是,这并不代表朱子彻底否认太极具有动静的意味。
直卿云:“兼两意言之,方备。言理之动静,则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其体也;静而能动,动而能静,其用也。言物之动静,则动者无静,静者无动,其体也;动者则不能静,静者则不能动,其用也。端蒙。”[24]
黄榦此说,以理之动静互涵为理之体,以理之动而能静和静而能动为理之用,可谓朱子的“未动而能动者理也”之说的一个深化,是符合朱子思想的。
四、太极或理如何动静
朱子关于太极或理的动静思想的材料十分丰富,略整理为以下若干条。
1.“主”、太极使气运动:太极的本体力量
在朱子哲学中,太极具有本体性力量。此种力量从太极本身来说,是它一定实现于现实之中的必然性;而自形下世界而言,则为形下世界必如此不已之表现,即朱子所谓“不容已”者。此种力量的直接表现是太极主导气的运动,使气运动。根据《语类》记载:
问:“‘太极动而生阳’,是有这动之理,便能动而生阳否?”曰:“有这动之理,便能动而生阳;有这静之理,便能静而生阴。既动,则理又在动之中;既静,则理又在静之中。”曰:“动静是气也,有此理为气之主,气便能如此否?”曰:“是也。既有理,便有气;既有气,则理又在乎气之中。”[25]
有理“为气之主”,气便能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这表明,理具有使气动的力量,此即理的本体性力量。换言之,太极是有力量的本体,能使天地万物生生不已。《语类》说:
问:“《或问》云:‘天地鬼神之变,鸟兽草木之宜,莫不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所谓‘不容已’,是如何?”曰:“春生了便秋杀,他住不得。阴极了,阳便生。如人在背后,只管来相趱,如何住得!”淳。[26]
理“不容已”,物“自住不得”,如有人背后在推动,此即理的本体性力量的表现。
2.“生”、“理生气”义之一:太极之本体论的展开
朱子哲学严理气之分、形而上下之别,故有冯友兰所谓理“逻辑在先”之说。在此我们还可补充一个“逻辑在后”说。因朱子曾说“万一山河大地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这意味着在气消亡之后,理依然存在。“逻辑在先”与“逻辑在后”肯定了理的先验性、永恒性、价值性和力量性。这些可谓理或太极的实质性内涵。以往的中国哲学研究,重点在“哲学”范式,注重于太极或理的形式分析,未曾适当地留意其实质性内涵。故在以往的表述中,理似乎成为一独立、孤立的影子或相片世界。冯友兰20世纪30年代创立新理学体系,其真际世界便类似于一个相片世界。可是理在朱子那里,并不是相片式的死理,而是有本体力量的活理。任何将世界分为形而上下两个者,都面临一个如何使两者合拢的问题。朱子、黑格尔、冯友兰都不例外。朱子沟通形而上下所依靠的,即是作为理的实质内涵的本体性力量。其沟通形而上下的方式之一是主张“理生气”。在朱子哲学中,至少有三种他所认可的文献促使他得出这一结论。第一种是《易传》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第二种是周敦颐《太极图说》的“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第三种是邵雍的《伏羲先天六十四卦图》。前两种文献都明确地指出太极“生”两仪或阴阳,后一种文献则以图示方式形象地说明了太极是如何生成六十四卦的。朱子根据这些材料推出了“理生气”的结论:
周子、康节说太极,和阴阳滚说。易中便抬起说。周子言“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如言太极动是阳,动极而静,静便是阴;动时便是阳之太极,静时便是阴之太极,盖太极即在阴阳里。如“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则先从实理处说。若论其生则俱生,太极依旧在阴阳里。但言其次序,须有这实理,方始有阴阳也。其理则一。虽然,自见在事物而观之,则阴阳函太极;推其本,则太极生阴阳。学履。[271
在这段话中,朱子把“动而生阳”、“静而生阴”解释为“动是阳”,“静便是阴”。这样,太极和阴阳的关系就不是宇宙论的生与被生的关系,两者形成对立的两个;而是说太极自身表现为阳,又表现为阴,太极和阴阳仍为一体。此种“生”,可谓表现、显现、展开,乃是太极之“本体论地展开”。诚如朱伯崑先生所言,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乃本体论的命题”[28]。朱子强调此“生”与老子之“有生于无”不同,更表明了其本体意义:
曰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则非无极之后别生太极,而太极之上先有无极也。又曰五行阴阳,阴阳太极,则非太极之后别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极也。以至于成男成女,化生万物,而无极之妙盖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图之纲领,大易之遗意,与老子所谓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而以造化为真有始终者,正南北矣。[29]
既然太极生阴阳之生是本体论的展开,则两者便不存在时间性的先后关系,而是有则俱有、无则俱无的体用关系。太极之此种本体论的动静,如前所述又被朱子表述为诚之“通”与“复”。然而,此形上之活动并非囿于形上领域的自动自静而已,而是仍要表现于形下世界的。表现的方式之一是“理”宇宙论地生“气”。
3.“生”、“理生气”义之二:太极本体—宇宙论地“生气”
在朱子哲学中,“理”生“气”尚有一本体—宇宙论之说法,即从本体论之展开说生、说动静,进而延伸到宇宙论的生成,实际地“生此阴阳之气”:
“无极而太极”,“而”字轻,无次序故也。“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即太极之动,静即太极之静。动而后生阳,静而后生阴,生此阴阳之气。谓之“动而生”,“静而生”,则有渐次也。“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动而静,静而动,辟阖往来,更无休息。谟。[30]
此段说“无极而太极”之“而”无次序,属于本体论;而“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之“而”“有渐次”,则显然进入了时间,属于宇宙论。“生此阴阳之气”亦为实际之太极生气。朱子又云:“自太极至万物化生,只是一个道理包括,非是先有此而后有彼。但统是一个大源,由体而达用,从微而至著耳。”[31]按照朱子用词习惯来看,此段“微”和“著”亦应是形而上下之别,则其所谓本体论之“生”虽然“发生”在形上之域,却又进入了形下之域。朱子又讲,“气虽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则理管他不得。”[32]其形下之生的意思亦十分明白。客观地说,诚如陈来所言,在朱子的体系中,既然理逻辑在先,自然就会产生理生气的结论[33]。不过,朱子仍然强调,理生气之后,理仍在气中。“太极生阴阳,理生气也。阴阳既生,太极在其中,理复在气之内也。”[34]理气在经验世界构成一体的思想亦是朱子的结论,故朱子的理生气,是本体-宇宙论地生,是本体宇宙论性质的,不单纯是其中的一面。朱子以此解决形而上下之合拢或沟通问题。至于此种解决是否合理,则是另一问题。
4.“应”、“继”、“行”:理之自我实现
在朱子哲学中,理自身有体用,体为未发之本然,用为已发之感应。“应”、“继”、“行”是朱子说明理实现于现实世界的用语。
本然而未发者,实理之体;善应而不测者,实理之用。动静体用之间,介然有顷之际,则实理发见之端,而众事吉凶之兆也。[35]
此段中,“应”即是本体之动,是理的实现,此实现最终落实为现实世界之吉凶。朱子的理可以实现于现实世界,乃是贺麟之观点;贺麟以此为理之动。只是理如何实现,贺麟尚未明言。笔者此处之论可视作对贺麟观点的一个推进。朱子表达理动的说法还有“继”和“行”。他指出,继善成性的“继”就是“动”。他说: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这“继”字便是动之端。若只一开一阖而无继,便是阖杀了。又问:“继是动静之间否?”曰:“是静之终,动之始也。且如四时,到得冬月,万物都归窠了;若不生,来年便都息了。盖是贞复生元,无穷如此。”夔孙。义刚录同。[36]朱子又云:
“继之者善”是动处,“成之者性”是静处。“继之者善”是流行出来,“成之者性”则各自成个物事。“继善”便是“元亨”,“成性”便是“利贞”。及至“成之者性”,各自成个物事,恰似造化都无可做了;及至春来,又流行出来,又是“继之者善”。譬如禾谷一般,到秋敛冬藏,千条万穟,自各成一个物事了;及至春,又各自发生出。以至人物,以至禽兽,皆是如此。义刚。[37]
仔细体察此段之动静说,结合前文朱子“以诚之通、复为形上之动静”之论可知,和通、复、相比,继、成有过渡的特点,由形上开始向形下过渡;始、正则进入形下之动静。此数个动静,可用下面图标表示:
太极动而生阳,朱子认为,“动”为理之“行”。此“行”显然是理的实现,即理之动:
问:“此理在天地间,则为阴阳,而生五行以化生万物;在人,则为动静,而生五常以应万事。”曰:“动则此理行,此动中之太极也;静则此理存,此静中之太极也。”洽。[38]
5.“妙”、“神妙万物”:理对于物或物支配、主宰与决定
在朱子的材料中,“神”至少有六种用法。其一是人的感知性能:“知觉便是神。触其手则手知痛,触其足则足知痛,便是神。”[39]其二是心的思维和主宰性能:“神即是心之至妙处,滚在气里说,又只是气,然神又是气之精妙处。”[40]其三是气之运动的微妙之处:“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这里,又忽然在那裹,便是神。’”[41]其四是神彩:“神便在心里,凝在里面为精,发出光彩为神。”[42]其五是圣人之德:“神即圣人之德,妙而不可测者。”[43]其六是形上之理对于事物的神妙莫测的决定作用,此即理的形而上的动静,甚值得注意。
问“动而无动,静而无静”。曰:“此说‘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此自有个神在其间,不属阴,不属阳,故曰‘阴阳不测之谓神’。且如昼动夜静,在昼间神不与之俱动,在夜间神不与之俱静。神又自是神,神却变得昼夜,昼夜却变不得神。神妙万物。如说‘水阴根阳,火阳根阴’,已是有形象底,是说粗底了。”植。[44]
在这段话中,事物的形下的动静是由神所决定或主宰的。神能够使昼变为夜或使变夜为昼,昼夜却不能使神发生改变,亦不能使神与之俱动俱静。陈来认为,此处理含有使气由静复动的“几”,可谓灼见。[45]关于神之不随物动静,朱子又进一步解释说:
昼固是属动,然动却来管那神不得;夜固是属静,静亦来管那神不得。盖神之为物,自是超然于形器之表,贯动静而言,其体常如是而已矣。时举。[46]
什么是“贯动静”?按照朱子的表述来看,是连接形而下的动静,并主导两者发生的节奏及转换。
《动静》章所谓神者,初不离乎物。如天地,物也。天之收敛,岂专乎动?地之发生,岂专乎静?此即神也。闳祖[47]
在朱子哲学中,动静转化、阴阳互根,皆是神对事物的奇妙的控制,即所谓的“神妙万物”。“妙”为动词,是主导、主宰、控制、使之奇妙之义,此可谓神的形上之运动。那么,“妙万物而为言之神”是什么?朱子明确地说,是理:
曰:“所谓神者,是天地之造化否?”曰:“神,即此理也。”……又问神,曰:“神在天地中,所以妙万物者,如水为阴则根阳,火为阳则根阴”云云。寓。[48]
关于理的主宰义,《朱子语类》中有“帝是理为主。淳。”此是化帝为理,以理为主导、主宰。《语类》又云:“苍苍之谓天。运转周流不已,便是那个。而今说天有个人在那里批判罪恶,固不可;说道全无主之者,又不可。这里要人见得。僴。”此段中,帝非人格神,而为主宰世界之理的含义甚为明显。理如何主宰天地之运行,朱子亦有解释: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无心。近思之,窃谓天地无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虑,有营为。天地曷尝有思虑来!然其所以‘四时行,百物生’者,盖以其合当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维,此所以为天地之道。”
曰:“如此,则易所谓‘复其见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又如何?如公所说,祇说得他无心处尔。若果无心,则须牛生出马,桃树上发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谓之帝,以性情谓之乾。’他这名义自定,心便是他个主宰处,所以谓天地以生物为心。中间钦夫以为某不合如此说。某谓天地别无勾当,只是以生物为心。一元之气,运转流通,略无停间,只是生出许多万物而已。”道夫。[49]
可见,在朱子看来,天地之心即是理,理的主宰使得天地万化正常运转,不至于出现牛生马、桃开李花一类的紊乱。
在此有必要对前人关于朱子之理之“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的解释重新加以审视。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之初,如何使中国哲学史是“哲学”之史,成为学界之共同努力。照冯友兰等人的看法,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概念思维,概念是抽象的、不夹杂有物质的内涵,“不拖泥带水”。朱子之理因其逻辑在先的先验性,“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洁净空阔”的抽象性和纯粹性,被当时学者认为是可与柏拉图、黑格尔之理念相对应之纯概念。这一认识无疑是很有见地的,所以冯友兰采用新实在论的思路来研究朱子哲学;贺麟欲将“绝对理念”译为太极。在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中,真际甚或成为实际世界的一个影子或相片。冯友兰对于朱子之理的认识具有极大影响,学界基本上接受了他的结论。即使是对宋明理学的总体认识与之截然相反的牟宗三,其朱子之理为“只存有不活动”之说,显然为冯友兰观点的又一版本。可是,这种路径也有重大缺陷。它只注重对概念的思维形式的分析,而严重地忽略了其实质性内涵,失去了朱子形而上概念的价值性、力量性和与形下世界的一体性。如果说形而上下暌隔,理世界只是事世界的一个影子或相片,不能对后者发生影响,则理即果真沦为不活不妙、可有可无之“死理”了。诚如前人所批评的那样,此种理,纵然在坑满坑、在谷满谷,又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即使是从史料上看,只强调理“无情义”亦是不全面的。“无情义”之说出自沈僩“问理气先后”条,朱子显然不赞成纠缠于此问题,指出:
不消如此说。而今知得他合下是先有理,后有气邪;后有理,先有气邪?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则疑此气是依傍这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间人物草木禽兽,其生也,莫不有种,定不会无种子白地生出一个物事,这个都是气。若理,则只是个净洁空阔底世界,无形迹,他却不会造作;气则能酝酿凝聚生物也。但有此气,则理便在其中。”僴。[50]
朱子在此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认识,其一是学界通常注意的“无情义”一类的理的抽象性、消极性、无为性方面,其二是“此气是依傍这理行”和“此气之聚,理亦赋焉”一类关于气对理之依附性或理对气之支配性的认识。朱子与此略近的思想亦表现于对于周子《通书》第五章的解释中,云此章“言道之体用不外乎阴阳,而其所以然者,则未尝倚于阴阳也。”[51]此“未尝倚于阴阳”十分值得注意。不离不杂是朱子理气关系的要点,但此处朱子不说理不杂于阴阳,而说其“未尝倚于阴阳”。“倚”有依凭、取决于之义。显然,朱子在此表述的是道决定阴阳而非相反,强调的是道的先验性力量。这体现了道、理、神的“妙”义。
当然,理之无为亦非全是对朱子的误解。其思想中有此内容,主要表现在他强调形而上下的区别之时,以及说明恶和异常时所主张的气强理弱的观点之中。如前所述,朱子有形而上下两层动静的思想。然而,形上之动静不可见,须因形下之动静而显现,故在形下层面,理显得有些被动。朱子说:“盖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52]什么是“机”?朱子曰:“机,是关捩子。踏着动底机,便挑拨得那静底;踏着静底机,便挑拨得那动底。”[53]与此相同的还有一条:“机,言气机也。诗云:‘出入乘气机。’”,[54]朱子又有颇引后人诟病的人跨马之喻:
阳动阴静,非太极动静,只是理有动静。理不可见,因阴阳而后知,理搭在阴阳上,如人跨马相似。[55]又说:
曰:太极理也,动静气也。气行则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尝相离也。太极犹人,动静犹马。马所以载人,人所以乘马。马之一出一入,人亦与之一出一入。盖一动一静,而太极之妙未尝不在焉。此所谓‘所乘之机’,无极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铢。[56]
理既能被气所驱动,自然是“气强理弱”:
问:“季通主张气质太过。”曰:“形质也是重。且如水之气,如何似长江大河,有许多洪流!金之气,如何似一块铁恁地硬!形质也是重。被此生坏了后,理终是拗不转来。”[57]
此段所谓“拗转”,是改变金属的物理或化学形态,限于当时之科技水平,这样做显然是困难的,所以叫作“理终是拗不转来”。朱子以此喻人气质沉重难以变化,终究是被气所决定,不能向善。朱子此语,是为了说明现实中的恶。恶不能归于理,否则即获得本体基础而不能排斥,故只能归之于气。朱子云“四端是理之发,七情是气之发”[58],即是此意。因为恶实质上只是人文世界之事,故朱子谈及此时一般限于气质而言。朱子还有一条谈到“气强理弱”,亦是为了说明恶的来源:
谦之问:“天地之气,当其昏明驳杂之时,则其理亦随而昏明驳杂否?”
曰:“理却只恁地,只是气自如此。”
又问:“若气如此,理不如此,则是理与气相离矣!”
曰:“气虽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则理管他不得。如这理寓于气了,日用间运用都由这个气,只是气强理弱。譬如大礼赦文,一时将税都放了相似,有那村知县硬自捉缚须要他纳,缘被他近了,更自叫上面不应,便见得那气粗而理微。又如父子,若子不肖,父亦管他不得。圣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这些子。”时举。柄录云:“问:‘天地之性既善,则气禀之性如何不善?’曰:‘理固无不善,才赋于气质,便有清浊、偏正、刚柔、缓急之不同。盖气强而理弱,理管摄他不得。如父子本是一气,子乃父所生;父贤而子不肖,父也管他不得。又如君臣同心一体,臣乃君所命;上欲行而下沮格,上之人亦不能一一去督责得他。’”[59]
我们理解朱子的理乘气行、气强理弱时须注意,此皆是理在形下之中的一种存在状态,而非其本然的存在状态。形下之动静绝非形上之动静,两者不可相提并论。前者具有先验性、本体性与价值性,后者则只是物理世界的一时的事实而已。形而下地说,固然存在气强理弱之现象;形而上地说,则当然是理强气弱,否则理就没有意义和价值了。故理主宰气是本体意义的,应然的;理随气之动静则非本体意义的,不是气对理本体上就有决定作用。毕竟,在理气关系中,理的决定性、主宰性是优先的。若人只是唯马首是瞻,形上之理之动静只为气所驱动,则理便沦为形下之一具体物,无任何先验性、永恒性、价值性、力量性可言矣。正如马行终究由人决定一样,在价值上,气之运动终究还是由理所决定的。恰如气“志壹动气”、“德胜气”一样。这是理的尊严和力量,也是理的形而上的动静。
五、道体流行之境界:太极之动静表现于气之动静
在朱子哲学中,气世界在本体上之如此表现,是由理来主宰、主导与发动的,故当现实世界之气之运动合乎理时,即为“天命流行”之状态,亦为道体流行之状态。此时,形而上下融为一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可直指形而下之世界而谓其为形而上之世界。朱子对于“夫子川上之叹”的解释,颇能体现此意:
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60]
此处的天地之化,乃是大化流行的过程,是吾人可以目视手触的形下过程。但其往者过、来者续之生生不息的状态,乃是道体的本然状态之体现或实现,故吾人可径谓此过程即是道体之流行,或曰天命流行;此时形而下所表现的即是形而上;形而上下合一,形而下之动静即是形而上之动静。吾人亦可曰,在朱子处,在理想状态下,理气浑论为一,气之动静即理之动静。对于《中庸》“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朱子解释道:
子思引此诗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谓费也。然其所以然者,则非见闻所及,所谓隐也。故程子曰:“此一节,子思吃紧为人处,活泼泼地,读者其致思焉。”[61]
此处所谓流行不息之境界,即是以费显隐、隐费一体,太极之动静体表现于现实世界之事事无碍的境界。《语类》记载,陈淳问“鸢飞鱼跃,皆理之流行发见处否?”朱子回答说,“固是”。朱子又说:“那个满山青黄碧绿,无非是这太极。”[62]朱子言太极为本然之妙,动静为所乘之机,亦是说太极之动静或曰理之动静由气之动静表现出。至此,我们可以对朱子备受诟病的“人跨马之喻”给予新的理解。朱子在比喻之后又说:“盖一动一静,而太极之妙未尝不在焉。此所谓‘所乘之机’,无极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这是理气一体、以形而下之动表达形而上之动的意思,只是比喻有些不当。曹端以来的诸多批评未能把握朱子此意。
朱子此思想在其解释“仁”时更为明显,他把仁作为生气之流行。朱子有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他把元亨利贞、春夏秋冬作为天地生物之四个阶段,仁义礼智与元亨利贞相比配。元为生意。但此生意非只限于春。朱子继承程子之说,把仁分为“专言”与“偏言”两种。专言的仁包括义礼智三德,偏言者则只为四德之一。故其所谓仁之生意,亦包括亨、利、贞,夏、秋、冬,此三阶段或三季皆为统一之生意之表现。据《语类》记载:
或问论语言仁处。曰:“理难见,气易见。但就气上看便见,如看元亨利贞是也。元亨利贞也难看,且看春夏秋冬。春时尽是温厚之气,仁便是这般气象。夏秋冬虽不同,皆是阳春生育之气行乎其中。故‘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南升。[63]
理无迹,不可见,故于气观之。要识仁之意思,是一个浑然温和之气,其气则天地阳春之气,其理则天地生物之心。……这不是待人旋安排,自是合下都有这个浑全流行物事。此意思才无私意间隔,便自见得人与己一,物与己一,公道自流行。须是如此看。……致道云:“如春是生物之时,已包得夏长、秋成、冬藏意思在。”曰:“春是生物之时,到夏秋冬,也只是这气流注去。但春则是方始生荣意思,到夏便是结里定了,是这生意到后只渐老了。”贺孙曰:“如温和之气,固是见得仁。若就包四者意思看,便自然有节文,自然得宜,自然明辨。”曰:“然。”贺孙。[64]
此两段中,仁为“温厚之气”、“浑然温和之气”,其理又为“天地生物之心”,这便是理气浑然合一之状态。此时仁之流行,即表现为“浑然温和之气”之流行,或者说,温和之气的流行便是仁的流行。此理、此气之浑然一体,朱子也通过理一分殊来说明:
周子谓:“五殊二实,二本则一。一实万分,万一各正,大小有定。”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气,二气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来,只是此一个理,万物分之以为体,万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然总又只是一个理。此理处处皆浑沦,如一粒粟生为苗,苗便生花,花便结实,又成粟,还复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个个完全;又将这百粒去种,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间只是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总只是一个理。淳。[65]
可以说,在此处,理的实现即表现为生气的流行,具体言之又表现为粟生为苗、苗又开花结实复成为粟的过程。如果说仁也可以表现为气,那就与通常我们强调仁为“爱之理”、理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的认识不尽相同了。这种差异实质上是我们对于“哲学”范式进行自觉反思、更加贴近朱子本身来理解朱子哲学得出的结论。这意味着朱子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待于方法论的突破。
附注
注释
[1]《通书·诚上第一》。
[2]《遗书》十一。
[3]《遗书》二上。
[4]《遗书》十一。
[5]《二程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95页。
[6]《二程集》第三册,第697页。
[7]《遗书》十九。
[8]《遗书》十五。
[9]《遗书》二下。
[10]《朱子语类》卷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0页。
[11]参见《朱子语类》卷六有关论述。
[12]《朱子语类》卷六,第100~101页。
[13]《朱子语类》卷六,第101页。
[14]《朱子语类》卷六,第101页。
[15]《朱子语类》卷六,第101页。
[16]《朱子语类》卷六,第105~106页。
[17]《朱子语类》卷六,第107页。
[18]《朱子语类》卷六,第110页。
[19]《朱子文集》卷六十。
[20]《朱子语类》卷六,第107页。
[21]《朱子语类》卷六,第107页。
[22]《朱子语类》卷六,第112~113页。
[23]《朱子语类》卷六,第107页。
[24]《朱子语类》卷六,第110~111页。
[25]《朱子语类》卷六,第105页。
[26]《朱子语类》卷六,第107页。
[27]《朱子语类》卷六,第107页。
[28]《朱子语类》卷六,第107页。
[29]《朱子语类》卷六,第108页。
[30]《朱子语类》卷六,第109页。
[31]《朱子语类》卷六,第111~112页。
[32]《朱子语类》卷六,第112页。
(原载《哲学研究》2011年第1期,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学院)
注释
[1]陈来:《朱子思想中的四德论》,《哲学研究》2011年第1期。
[2]《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7,《朱子全书》(23),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54页。以下简称《全书》。
[3]《文集》卷67,《全书》(23),第3279~3280页。
[4]《文集》卷74,《全书》(24),第3588页。
[5]《文集》卷74,《全书》(24),第3588~3589页。
[6]《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8页。
[7]《文集》卷74,《全书》(24),第3589~3590页。
[8]《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文集》卷58,《全书》(23),第2778页。
[9]《文集》卷58,《全书》(23),第2779页。
[10]《文集》卷58,《全书》(23),第2779~2780页。
[11]《文集》卷58,《全书》(23),第2780页。
[12]《朱子语类》卷6,中华书局,1986年,第105页。
[13]《文集》卷67,《全书》(23),第3261~3262页。
[14]《周礼注疏》卷14,《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30页。
[15]《文集》卷67,《全书》(23),第3262~3263页。
[16]《朱子语类》卷6,第114页。
[17]《朱子语类》卷6,第107页。
[18]《周易正义》卷9,《十三经注疏本》,第93~94页。
[19]《朱子语类》卷6,第106页。
[20]《朱子语类》卷6,第108页。
[21]《朱子语类》卷68,第1691页。
[22]《文集》卷51,《全书》(22),第2374页。
[23]《文集》卷38,《全书》(21),第1670~1671页。
[24]《文集》卷38,《全书》(21),第1673页。
[25]《文集》卷38,《全书》(21),第1674页。
[26]《周易本义·彖上传》,《全书》(1),第90~91页。
[27]《朱子语类》卷6,第115页。
[28]《朱子语类》卷68,第1688页。
[29]《朱子语类》卷68,第1689页。
[30]《朱子语类》卷68,第1689页。
[31]《朱子语类》卷68,第1689页。
[32]《朱子语类》卷68,第1689页。字下点为笔者所加。下同。
[33]《朱子语类》卷68,第1689页。
[34]《朱子语类》卷68,第1689~1690页。
[35]《朱子语类》卷68,第1690页。
[36]《朱子语类》卷68,第1690页。
[37]《朱子语类》卷68,第1690~1691页。
[38]《朱子语类》卷68,第1691页。
[39]《朱子语类》卷68,第1691页。
[40]《周易本义·文言传》,《全书》(1),第146页。
[41]《周易本义·文言传》,《全书》(1),第149页。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4期,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学院)
注释
[1]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1页。
[2]田浩:《朱熹的思维世界》(增订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0,收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894页。
[4]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0,第2893页。
[5]朱熹:《朱子语类》卷42,收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4页。
[6]朱熹:《朱子语类》卷41,收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4页。
[7]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4,收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585页。
[8]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4,第3585页。
[9]朱熹:《论语集注》,收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页。
[10]朱熹:《论语集注》,第142页。
[11]朱熹:《论语集注》,第117页。
[12]朱熹:《论语集注》,第117页。
[1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4,收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585页。
[14]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4,第3586页。
[15]朱熹:《书晦庵先生家礼后》,收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949页。
[16]朱熹:《朱子语类》卷43,收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版,第1519页。
[17]朱熹:《朱子语类》卷43,收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版,第1519页。
[18]朱熹:《朱子语类》卷43,第1519页。
[19]朱熹:《朱子语类》卷43,第1519页。
[20]朱熹:《朱子语类》卷43,第1519页。
[21]朱熹:《朱子语类》卷43,第1519页。
[22]钱穆:《朱子新学案》第4册,台北三民书局1989年版,第147页。
[2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3,收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920页。
[24]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0,收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896页。
[25]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1,收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90页。
[26]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0,收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932~933页。
[27]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20,第930页。
[28]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收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686页。
[29]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4,第686页。
[30]朱熹:《家礼》卷1,收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880~881页。
[31]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
[32]朱熹:《家礼》卷3,收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897页。
[33]《家礼》卷3,第897~898页。
[34]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19~220页。
[35]朱熹:《朱子语类》卷130,收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035页。
[36]朱熹:《朱子语类》卷130,收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034页。
[37]朱熹:《朱子语类》卷130,第4036页。
[38]朱熹:《乞修三礼劄子》,收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
[39]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69,收入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3352页。
(原载《展望未来的朱子学研究——朱子学会成立大会暨朱子学与现代跨文化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
[1]Tu Weiming and Mary Evelyn Tucker,eds.Confucianspirtuality,2 vols.New York:CrossroadPub.Co.,2003,p.4.
[2]书已出版,参拙著:《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论语·颜渊第十二》。
[4]《论语·里仁第四》。
[5]《论语·宪问第十四》。
[6]《论语·阳货第十七》。
[7]《论语·季氏第十六》。
[8]关于孟、荀较详细的论述,参《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第20~34页。
[9]关于《大学》、《中庸》、《易传》较详细的论述,参《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第34~56页。
[10]关于宋明理学的全盘论述,参《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第二部分:《宋(元)明儒学》,第70~170页。
[11]《二程全书》,伊川文集第七。
[12]《二程全书》,外书第十二,传闻杂记,见《上蔡语录》。
[13]二程的分别要到牟宗三先生才彻底解明,明道一本,伊川二元,参所著:《心体与性体》(台北:正中书局,三册,1968—1969年)。简明论述参拙著:《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第92~117页。
[14]牟宗三先生认为伊川开出了一条横摄的思路,偏离于北宋三家:濂溪、横渠、明道的纵贯思路,实为别子。朱子继承的是伊川,乃是“继别为宗”;他又在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之外,以胡五峰、刘蕺山为第三系,回归北宋三家的纵贯思路。参所著:《心体与性体》。这些问题过分复杂,本文不及。我对朱子哲学的阐释,参拙著:《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湾学生书局1982版,1984年增订再版,1995年增订三版)。这些年来我的看法基本上并没有改变,但近年理解比较深化,参拙著:《儒家哲学的典范重构与诠释》(台北万卷楼2010年版),第二部:宋代理学的精神传统(以朱子为中心)与我的学术渊源。对朱子思想的简单撮述,参《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第128~136页。
[15]《朱子文集》卷七十六。
[16]《孟子·万章上》。
[17]北宋五子,只邵雍(康节)未收入,因为他的思想道家倾向浓厚,故被摒弃在外。卷一“道体”是吕东莱坚持编入,但可最后才阅读。然全书的确是按朱子对《大学》的理解,由内到外,顺着修、齐、治、平的次序编定。后世印《近思录》,有只标明朱熹编,不再提到东莱。
[18]《论语·子张第十九》。
[19]此文被收在《近思录》卷一篇首。
[20]此文与二程相关议论被纳入《近思录》卷二。
[21]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第368~382页。
[22]关于陆象山与王阳明的心学,简单的撮述参《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第136~153页。
[23]《象山全集》卷三十六。
[24]关于刘蕺山与其弟子黄梨洲,简单的撮述参《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第153~170页。其详参拙著:《黄宗羲心学的定位》,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6年版;简体字版,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25]关于清代儒学的回顾,参《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第183~185页。
[26]关于“现代新儒学”,参《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第三部分,第186~241页。
[27]《中国哲学》,《剑桥哲学辞典》(台北猫头鹰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87页。
[28]《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第222页。
[29]关于牟宗三论中西哲学文化传统的差异与会通,参《论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第235~237页。
[30]相关问题的论析,参拙著:《儒家哲学的典范重构与诠释》,第一部,当代新儒家义理的阐发与拓展。
[31]相关论析,参刘述先著:《全球伦理与宗教对话》,台北立绪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简体字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原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作者单位: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注释
[1]Anthony Giddens,Beyond leftand Right:The Future ofRadical Politics,Cambridge:PolityPress,1994,pp.4~5.
[2]朱熹:《朱子语类(5)》,收入《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册,卷136,第4222页。
[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子全书》,第12册,卷37,《与郭冲晦》,第1635~1640页,引文见第1639页。关于“理一”与“分殊”关系的讨论,参看市川安司:《朱晦庵の理一分殊解》,收入氏著《朱子哲学论考》,东京汲古书院1985年版,第69~86页。
[4]朱熹:《中庸或问》,收入《朱子全书》,第6册,第595~596页。
[5]朱熹:《论语集注》卷2,收入《朱子全书》,第6册,第95~96页。
[6]朱熹:《论语集注》卷2,收入《朱子全书》,第6册,第96页。
[7]真德秀撰,刘承辑:《论语集编》卷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0页。
[8]薛瑄:《读书录》卷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页。
[9]朱熹:《朱子语类(2)》,收入《朱子全书》,第15册,卷27,第970页。
[10]朱熹:《朱子语类》卷45,第1584~1585页,夔孙录。朱子又说:“所谓一贯,须是聚个散钱多,然后这索亦易得。若不积得许多钱,空有一条索,把甚么来穿!吾儒且要去积钱。若江西学者都无一钱,只有一条索,不知把甚么来穿。”(卷27,第983页),亦同此意。
[11]朱熹:《朱子语类(2)》,收入《朱子全书》,第15册,卷27,第975页。
[12]朱子说:“太极便是一,到得生两仪时,这太极便在两仪中;生四象时,这太极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时,这太极便在八卦中。”见《朱子语类(2)》,卷27,第967页。
[13]参看黄俊杰:《朱子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收入《国际朱子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3年版,下册,第1083~1114页,尤其是第1098页;Chun-chieh Huang,Imperial Rul-ership in Cultural History:Chu Hsi’s Interpretation,in Frederick Brandauer and Chun-chieh Huangeds.,Imperial Rulershipand Cultural Change inTraditional China,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4,pp.188~205.
[14]朱熹:《朱子语类(4)》,收入《朱子全书》,第17册,卷98,《张子之书一》,第3320页。林子武问:“龟山语录曰:西铭‘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为仁;知其分殊,所以为义。”先生曰:“仁,只是流出来底便是仁,各自成一个物事底便是义。仁只是那流行处,义是合当做处。”(义刚录)
[15]Bob Sutcliffe,World Inequality and Globalization,Oxford ReviewofEconomic Policy,Vol.20,No.1,2004,pp.15~37.
[16]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子全书》,第12册,卷37,《与郭仲晦》,第1639页。
[17]参看Peter Beinart,An Illusion for Our Time,The NewRepublic,October 20,1997,pp.20~24.
[18]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收入《戴震全集》,卷上《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19]朱熹:《大学章句》,收入《朱子全书》,第6册,第20页。
[20]黄俊杰:《德川日本论语诠释史论》,第7章,台大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249~254页。
[21]金谨行:《论语剳疑》,载于氏著《顺庵先生文集》卷11,收入《韩国经学资料集成》23,汉城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88年版,论语(六),第575页。
[22]朴知诫:《剳录——论语》,载于氏著《潜治集》卷10,收入《韩国经学资料集成》18,论语(一),第232~234页。
[23]金谨行:《论语剳疑》,第576页。
[24]朱熹:《朱子语类》卷18,收入《朱子全书》第14册,第606页。
[25]“从属原则”与“并立原则”是牟宗三(1909—1995)先生所创之名词。参看牟宗三:《中国文化的省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版,第68页。
[26]《孟子·公孙丑上》。
[27]《孟子·离娄下》。
[28]Ying-shih Yu,Individualism and the Neo-Taoist Movement in Wei-chin China,in Donald Mun-ro ed.,Individualismand Holism:Studies inConfucian and TaoistValues,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5,pp.121~156.
[29]陈亮:《勉强行道大有功》卷9,收入《龙川文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0页。
[30]罗钦顺:《困知记》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页。
(作者单位:台湾大学历史学系)
注释
[1]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1册,《河南程氏遗书》卷18,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8页。以下简称《遗书》。
[2]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3]刘述先:《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初版,1995年增订三版。
[4]陈来:《朱熹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修订版。
[5]陈来:《宋明理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6]当然相关论文不胜枚举,这里仅举两例:[日]吾妻重二:《居敬前史》,载[日]吾妻重二《朱子学の新研究——近世士大夫の)思想史的地平》,东京创文社2004年版;姜广辉:《主静与主敬》,载氏著《理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7]杨祖汉:《从朱子的“敬”论看朱子思想的归属》,载吴震主编《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杨文。
[8]杨文此说当源自牟宗三早年著作《王阳明致良知教》(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4年版)提出的朱子思想为“敬的系统”(转引自上引杨文,第83页),然而杨文的结论却与牟说不同。
[9]杨祖汉:《从朱子的“敬”论看朱子思想的归属》,第78页。
[10]杨祖汉:《从朱子的“敬”论看朱子思想的归属》,第81页。
[11]杨祖汉:《从朱子的“敬”论看朱子思想的归属》,第82页。按,“空头的涵养”为牟宗三对朱熹论敬的判定语,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3册。杨文略而不提,然我们则须在此点明。
[12]杨祖汉:《从朱子的“敬”论看朱子思想的归属》,第78页。
[13]吴震:《“心是做工夫处”——关于朱熹“心论”的几个问题》,载吴震主编《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第137页。以下简称拙文。
[14]例如:“伊川‘性即理也’,横渠‘心统性情’二句,颠扑不破!”(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5,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3页。以下简称《语类》)“伊川‘性即理也’四字,颠扑不破,实自己上见得出来。”(《语类》卷59,第1387页)
[15]《语类》卷59,第1387页。
[16]《语类》卷12,第208页。
[17]《语类》卷12,第207页。
[18]《语类》卷12,第210页。
[19]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6册,《大学或问》,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6页。
[20]例如:“问:‘敬,诸先生之说各不同。然总而行之,常令此心常存,是否?’曰:‘其实只一般。若是敬时,自然“主一无适”,自然“整齐严肃”,自然“常惺惺”,“其心收敛不容一物”。但程子“整齐严肃”与谢氏尹氏之说又更分晓。’”(《语类》卷17,第371页)
[21]《语类》卷17,第373页。
[22]《语类》卷17,第373页。
[23]《遗书》卷18,第206页。按,以上有关程颐之论敬,可参钟彩钧:《二程道德论与工夫论述要》,载《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4期,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1994年版,第456~463页。钟文以程颢“敬则无间断”(《遗书》卷11,第118页)为据,揭示了程颢之论敬重在以主观上的体验来接续客观面的天道流行“无间断”,并由此向天地圣人境界趋近;相对来说,程颐的论学宗旨“涵养用敬,进学致知”的“敬”说承自程颢而有深入的发挥,但与程颢落在事为上论敬之路数不同,程颐则强调在心体上落实“主一”工夫,而朱熹解程颐“主一”则兼动静言,亦以“主于事”为主,盖已不得“伊川本意”(见钟氏论文,第463页)。此说无疑具有参考价值,然须补充说明的是,由程颢的“无间断”至谢上蔡的“常惺惺法”实有内在一贯的理路在,于朱熹敬论亦有重要影响。
[24]《遗书》卷15,第149页。
[25]《周易程氏传》卷1“坤”,第712页。
[26]《遗书》卷2下,第52~53页。
[27]《遗书》卷15,第168~169页。
[28]《遗书》卷15,第144页。
[29]关于“有主则虚”、“无主则实”,朱熹与其门人曾议论及此:“……此二条,一以实为主,一以虚为主,而皆收入《近思录》。唐臣以愚意度之,虚以敬言,实以事言,以敬为之主则虚,虚则邪不能入,以事为之主则实,实则外患不能入。故程先生于‘有主则实’下云:‘自然无事’;于‘无主则实’下云:‘实谓物来夺之’。详此二条之意,各有所在,不可并作一意看。未知是否?德明(按,即廖子晦)答云:‘有主则实,有主则虚,虚实二说虽不同,然意自相通,皆谓以敬为主也。……’(朱熹评曰)‘子晦之说甚善,但敬则内欲不萌,外诱不入。自其内欲不萌而言,则曰虚;自其外诱不入而言,故曰实。只是一时事,不可作两截看也。’”(《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5《答廖子晦》,《朱子全书》第22册,第2095~2096页。以下简称《文集》)
[30]《大学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第506页。
[31]按,通常以为,古人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如程颐曾说:“古者八岁入小学,十五岁入大学。”(《遗书》卷15,第166页)不过,若依《礼记·内则》篇所云,自“六年,教之数与方名”,经“成童(郑注:‘成童,十五以上’)舞象”,至“二十而冠,始学礼”,可见有关儿童至成人的学习年龄及其相应的学习内容另有详细的规定。关于小学的问题,可参朱熹作于淳熙十四年(1187年)的《小学》一书以及《语类》卷7“小学”各条。另参钱穆:《朱子新学案》第4册“朱子之礼学”,台北三民书局1971年版,第174~176页。
[32]按,语见《语类》卷12,第210页。然未明示记录者,据其前条“只敬,则心便一”,为叶贺孙录,由于两条意思相近,疑该条亦为叶贺孙所录。据《朱子语录姓氏》,“叶贺孙字味道,括苍人,居永嘉。辛亥(1191年)以后所闻”,当属朱熹62岁以后之言。
[33]《文集》卷64,《朱子全书》第23册,第3130~3131页。另参《文集》卷67《未发已发说》,作于40岁,所论大旨略同。
[34]引自朱熹《文集》卷73《胡子知言疑义》,《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61页。
[35]朱熹《文集》卷73《胡子知言疑义》,《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61页。
[36]朱熹对胡宏为首的“湖湘学”有诸多严厉之批评,然而其对李侗之工夫论的不满,向来所言不多,其《答吕士瞻》书则透露了个中消息:“举程子涵养于未发之前则可,求中于未发之前不可。李先生当日功用,未知于此两句为如何,后学未敢轻议,但当只以程先生之语为正。”(《文集》卷46,《朱子全书》第22册,第2122页)《语类》卷103载:“李先生当时说学,已有许多意思,只为说敬字不分明,所以许多时无捉摸处。”(第2603页)《语类》卷96亦云:(验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然亦有病,若不得其道,则流于空。”(第2468页)这里虽未点名,显然也是针对杨时至李侗一路延续下来的体验未发说而提出的批评。而这些批评的关节点无疑就在于“说敬字不分明”。据此,中和新悟的问题意识虽与如何解决湖湘学的察识涵养问题直接相关,但同时也意味着朱熹对杨时以来道南一脉的扬弃。
[37]《语类》卷20,第477页。
[38]《文集》卷45《答廖子晦》,《朱子全书》第22册,第2088页。按,另见《文集》卷56《答方宾王》(《朱子全书》第23册,第2660页),语意亦同。
[39]如朱熹曾说:“若欲以所发之心,别求心之本体,则无此理矣。此胡氏‘观过知仁’之说,所以为不可行也。”(《文集》卷46《答黄商伯》,《朱子全书》第22册,第2131页)这里的“观过知仁”,意同“识心”说。
[40]《文集》卷31《答张敬夫》,《朱子全书》第21册,第1345~1346页。
[41]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载《唐君毅全集》,台湾学生书局1991校订版,第566页。
[42]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618页。
[43]《语类》卷34,第856页。
[44]以上参见《文集》卷73《胡子知言疑义》。
[45]《文集》卷42《答石子重》,《朱子全书》,第22册,第1922页。
[46]《文集》卷43《答林择之》,《朱子全书》,第22册,第1981~1982页。
[47]《文集》卷32《答张钦夫》,《朱子全书》,第21册,第1420页。
[48]《语类》卷95,第2456页。
[49]《语类》卷14,第269页。
[50]《语类》卷16,第334页。
[51]《语类》卷12,第209页。
[52]《语类》卷12,第210页。
[53]《大学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第506页。
[54]《语类》卷118,第2851页。
[55]《语类》卷118,第2854页。
[56]《语类》卷12,第210页。
[57]《语类》卷12,第214页。
[58]《文集》卷55《答熊梦兆》,《朱子全书》,第23册,第2624页。
[59]《文集》卷43《答林择之》,《朱子全书》,第22册,第1980页。
[60]《文集》卷43《答林择之》,《朱子全书》,第22册,第1980页。
[61]《语类》卷12,第208~209页。
[62]《语类》卷12,第199页。
[63]《语类》卷12,第199页。
[64]《语类》卷12,第200页。
[65]《语类》卷12,第202页。
[66]《语类》卷12,第201~202页。
[67]《语类》卷12,第210页。
[68]《文集》卷50《答潘恭叔》,《朱子全书》,第22册,第2313页。
[69]《文集》卷41《答程允夫》,《朱子全书》,第22册,第1873页。
[70]《语类》卷12,第211页。
[71]《语类》卷23,第545页。
[72]《语类》卷12,第216页。
[73]《文集》卷59《答余正叔》,《朱子全书》,第23册,第2851~2852页。
[74]《语类》卷9,第150页。
[75]参见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第571页。
[76]《文集》卷64《答或人》,《朱子全书》,第23册,第3131~3132页。
[77]《语类》卷14,第269页。
[78]参《语类》卷59:“此心不待宛转寻求,即觉其失,觉处即心,何更求为?自此更求,自然愈失。此用力甚不多,但只要常知提醒尔。”(第1407页)
[79]《文集》卷32《答张钦夫》,《朱子全书》,第21册,第1419页。
[80]牟宗三:《心体与性体》,第3册,第147页。
[81]参《文集》卷67《观心说》。
[82]《语类》卷84,第2190页。
[83]《语类》卷25,第622页。
[84]《文集》卷49《答滕德粹》,《朱子全书》,第22册,第2273页。
[85]《语类》卷12,第211页。
[86]《文集》卷41《答程允夫》,《朱子全书》,第22册,第1872~1873页。
[87]如:“程子言敬,必以整齐严肃、正衣冠、尊瞻视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论。”(《文集》卷43《答林择之》,《朱子全书》,第22册,第1969页)又如:“详考从上圣贤以及程氏之说论下学处,莫不以正衣冠、肃容貌为先。盖必如此,然后心得所存而不流于邪僻。《易》所谓‘闲邪,存其诚’,程氏所谓‘制之于外,所以养其中’者,此也。”(《文集》卷33《答吕伯恭》,《朱子全书》,第21册,第1429页)
[88]《语类》卷17,第372页。
[89]《语类》卷17,第371页。
[90]《语类》卷17,第371页。
[91]《语类》卷17,第370~371页。
[92]《语类》卷17,第370页。
[93]《语类》卷12,第207~208页。
[94]《文集》卷53《答胡季随》,《朱子全书》,第22册,第2513页。
[95]《语类》卷115,第2771页。
[96]例如由以下朱熹所言可见,敬乃是致知力行之依据:“承喻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静敬二字该之,则恐未然。盖圣贤之学,彻头彻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静之为言,则亦理明心定,自无纷扰之效耳。今以静为致知之由,敬为力行之准,则其功夫次序皆不得其当矣。”(《文集》卷50《答程正思》,《朱子全书》,第22册,第2323页)
[97]《语类》卷18,第404页。
[98]《文集》卷42《答胡广仲》,《朱子全书》,第22册,第1899页。
[99]《语类》卷9,第152页。
[100]《语类》卷9,第152页。
[101]《语类》卷9,第152页。
[102]《语类》卷18,第404页。
[103]《语类》卷62,第1514页。
[104]《语类》卷62,第1514~1515页。
[105]全文是:“问致知涵养先后。曰:‘须先致知而后涵养。’问:‘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纲说。要穷理,须是着意。不着意,如何会理会得分晓。’”(《语类》卷9,第152页)
[106]《语类》卷9,第150页。
[107]《语类》卷14,第269页。
[108]《语类》卷59“仁也人心章”,第1412页。按,以下凡出此卷,不再出注。
[109]《语类》卷9,第151页。
[110]《语类》卷18,第402页。
[111]《朱子全书》,第27册附录,第560页。
[112]吴震:《“心是做工夫处”——关于朱熹“心论”的几个问题》,《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第137页。
[113]《语类》卷9,第155页。
[114]《传习录》上,第117条。按,条目数字据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修订版。
[115]参见[日]安田二郎:《中国近世思想研究》,东京弘文堂书房1948年初版,东京筑摩书房1976年再版;[日]荒木见悟:《明代思想研究》,东京创文社1972年版。
[116]王守仁著,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页。
[117]王守仁著,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7,第242页。
[118]《传习录》上,第129条。
[119]例如《论语》有云:“君子敬而不失,与人恭而有礼”(《颜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卫灵公》),“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子张》)孟子更有“恭敬之心,礼也”(《孟子·告子篇上》)之说。顺便一提,陆九渊曾批评朱熹所言居敬:“持敬字乃后来杜撰。”(《陆九渊集》卷1《与曾宅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页)向来以为这是心学派学者在思想性格上表现为“洒落”而与程朱理学偏重于“敬畏”的思想趣向不合的典型言论。然而,此所谓“杜撰”概指九渊对朱熹于《大学》解释添入“敬”字以为不妥,而并不表明九渊对孔门之言“敬”持否定之态度,如其所云:“有先生长者在,却不肃容正坐,收敛精神,谓不敬之甚。”(《陆九渊集》卷34《语录上》,第430页)又说:“吾家合族而食,每轮差子弟掌库三年。某适当其职,所学大进,这方是‘执事敬’。”(同上书,第428页)可见,心学家对孔门“敬”说其实亦有相当程度的认同。
[120]《王阳明全集》卷5《答舒国用》,第190~191页。
[121]此命题见《答陆原静书·又》,全文如下:“来书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寻仲尼、颜子乐处。敢问是乐也,与七情之乐,同乎?否乎?若同,则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乐矣,何必圣贤?若别有真乐,则圣贤之遇大忧大怒大惊大惧之事,此乐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惧,是盖终身之忧也,恶得乐?澄平生多闷,未尝见真乐之趣,今切愿寻之。’‘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虽在忧苦迷弃之中,而此乐又未尝不存。但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此而在矣。每与原静论,无非此意。而原静尚有何道可得之问,是犹未免于骑驴觅驴之蔽也。’”(《传习录》中,第166条)
[122]按,以这种类型学的区分方式来观察宋代以来理学的不同趣向,这在阳明时代已经出现。针对于此,阳明以下所言值得引起重视:“夫谓‘敬畏之增,不能不为洒落之累’,又谓‘敬畏为有心,如何可以无心?而出于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所谓欲速助长之为病也。夫君子之所谓敬畏者,非有所恐惧忧患之谓也,乃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之谓耳。君子之所谓洒落者,非旷荡放逸,纵情肆意之谓也,乃其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之谓耳。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惧,惟恐其昭明灵觉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于非僻邪妄而失其本体之正耳。戒慎恐惧之功无时或间,则天理常存,而其昭明灵觉之本体,无所亏蔽,无所牵扰,无所恐惧忧患,无所好乐忿懥,无所意必固我,无所歉馁愧怍。和融莹徹,充塞流行,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斯乃所谓真洒落矣。是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无间。孰谓‘敬畏之增,乃反为洒落之累’耶?”(《王阳明全集》卷5《答舒国用》,第190页)这是说,吾人所谓“敬畏”非一般心理意义上的恐惧忧患之意,而是专指《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这一文本中紧扣天道而言的戒慎恐惧;吾人所谓“洒落”亦非一般感性意义上的“旷荡放逸,纵情肆意”之意,而是就“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这一紧扣心体而言的快乐。因此,只要天理之常存,则吾人必不能时而忽忘“戒慎恐惧”之工夫,由此日进而必能达到“动容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之境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洒落”。至于在阳明后学的发展流变过程中,是否存在一种一任本心、放纵自肆而欠缺敬畏之念的思想倾向,则是另一层面的问题。
[123]《文集》卷30《答张钦夫》,《朱子全书》,第21册,第1313页。
[124]《文集》卷45《答游诚之》,《朱子全书》,第22册,第2060页。
[125]《文集》卷67《观心说》,《朱子全书》,第23册,第3279页。
[126]《文集》卷54《答项平父》,《朱子全书》第23册,第2541页。
[127]按,这是朱熹心论的一个原则立场,如其于乾道八年(1172)与吴翌的书信中所说,湖湘学的“观过”说甚至有裂一心而为三之弊(参《文集》卷42《答吴晦叔》,《朱子全书》,第22册,第1911页),朱熹又说:“非操舍存亡之外,别有心之本体也。”(《文集》卷47《答吕子约》,《朱子全书》,第22册,第2183页)据此来看,朱熹所以猛烈批评湖湘学的识心说,关键在于“以心观心”有可能导致承认在观心之上“另有心之本体”的结论。关于这一问题,请参陈来:《朱子哲学中“心”的概念》,载《国学研究》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后收入陈来:《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并参上引拙文。
[128]《文集》卷53《答胡季随》,《朱子全书》,第22册,第2520页。
[129]李明辉指出,朱熹之“心”凭其知觉涵摄理,在此意义下成为实践主体,而就心能涵理而言,可以将心视为一种道德理性,只是这种道德理性并不像康德的“实践理性”那样,可以制定道德法则,参见李明辉:《朱子对“道心”、“人心”的诠释》(上),载《鹅湖月刊》第33卷第3期,2007年,第19页。
[130]参见《语类》卷124。
[131]将南宋思想史上出现的“当下便是”说置于朱子学与象山学的义理纷争之脉络中来展开讨论,可参[日]小路口聪著,吴震译:《陆九渊的“当下便是”是“顿悟”论吗——”即今自立”哲学序章》,载吴震、[日]吾妻重二主编《思想与文献: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2~298页。
[132]参见吴震:《心是做工夫处——关于朱熹“心论”的几个问题》,第113页。
[133]当然朱熹有关敬字的训释还有不少,例如朱熹又以畏字释敬:“敬,只是一个畏”(《语类》卷6,第103页),“敬,只一个畏字”(《语类》卷12,第211页;并参见《语类》卷15)。黄榦则于《论语集注学而疏义》指出在敬字的诸多训释中唯有“畏字于敬字之义最近”(《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26,《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元延祐二年重修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81页),而黄榦自撰《敬说》(同上书卷26)一文亦强调敬的“畏”字义。关于黄榦的观点,参见[日]佐藤仁:《朱熹の)敬说に关する一考察》,载《广岛大学文学部纪要》第49集,1990年,后收入[日]佐藤仁:《宋代の春秋学——宋代士大夫の思考世界》,东京研文出版2007年版,第498页。当然,以畏释敬,有不少儒家经典可作为依据,如《中庸》“戒慎恐惧”、《诗经》“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便是例证。程颢则说“‘毋不敬’,可以对越上帝”(《遗书》卷11,《二程集》,第118页),此说颇受朱熹重视(参《文集》卷85《敬斋箴》),可见程朱之主敬亦指对外在绝对者的一种敬畏情感。不过,对《中庸》“戒慎恐惧”,朱子认为不如以“提撕”义释之而不宜以通常意义上的“惊恐”视之,其云:“不须得将戒慎恐惧说得太重,也不是恁地惊恐。只是常常提撕,认得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语类》卷117,第2823页)所谓“提撕”亦即“敬”字义。
[134]这两句话的全文分别是:“心者,主乎性而行乎情。故‘喜怒哀乐未发则谓之中,发而皆中节则谓之和’,心是做工夫处。”(《语类》卷5,第94页)“盖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体,情是用。心字只一个字母,故性、情字皆从‘心’。”(《语类》卷5,第91页)相关分析,请参上引拙文。
(原载《哲学门》第11卷第2册,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注释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页。
[2]孔颖达:《礼记正义》卷60,《十三经注疏》,第6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4页。
[3]这是朱子《大学或问》的定稿,与上文所引《经筵讲义》之说相较即可知。其改定时间与《大学章句》应是一致的,大约在1196—1198年间。朱熹:《大学或问》、《四书或问》,《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7页。
[4]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38页。
[5]傅伟勋:《从创造的诠释学到大乘佛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0年版。
[6]黎靖德:《朱子语类》卷5,《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
[7]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4,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38~439页。
[8]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1页。
[9]史次耘:《孟子注译》,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
[10]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3~294页。
[11]朱熹:《四书或问》,《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7页。
[12]黎靖德:《朱子语类》卷52,《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2页。
[13]朱熹:《经筵讲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15,《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92页。
[1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页。
[15]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01页。
[16]朱熹:《大学或问》、《四书或问》,《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7页。
[17]陈荣捷:《中国哲学文献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18]黎靖德:《朱子语类》卷10,《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14页。
[1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页。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1]《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01页。
[2]《朱子语类》,第2913页。
[3]《朱子语类》,第2996页。
[4]《朱子语类》,第2993页。
[5]《朱子语类》,第2987页。
[6]《朱子语类》,第2987页。
[7]《朱子语类》,第3008页。
[8]《朱子语类》,第2995页。
[9]《朱子语类》,第2998页。
[10]《朱子语类》,第2993页。
[11]《朱子语类》,第2986页。
[12]《朱子语类》,第3001页。
[13]《朱子语类》,第1540页。
[14]《朱子语类》,第369页。
[15]《朱子语类》,第2543~2544页。
[16]《朱子语类》,第2989页。
[17]《朱子语类》,第2995页。
[18]《朱子语类》,第2989页。
[19]《朱子语类》,第2986页。
[20]《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549页。
[21]《朱子语类》,第3005页。
[22]《朱子语类》,第3005页。
[23]《朱子语类》,第2498页。
[24]《朱熹集》,第2020页。
[25]《孟子精义》卷3,《公孙丑章句上》,《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26]《孟子精义》卷6,《滕文公章句下》。
[27]《朱子语类》,第3253页。
[28]《朱熹集》,第857页。
[29]《朱熹集》,第1634页。
[30]《朱子语类》,第1330~1331页。
[31]《朱熹集》,第3850~3851页。
[32]《朱子语类》,第3217页。
[33]《朱子语类》,第496页。
[34]《朱子语类》,第2689页。
[35]《朱子语类》,第2009页。
[36]《朱熹集》,第533页。
[37]《朱熹集》,第498页。
[38]《朱熹集》,第3822页。
[39]《朱子语类》,第2867页。
[40]《朱子语类》,第3277页。
[41]《朱子语类》,第834页。
[42]《朱子语类》,第142页。
[43](《朱熹集》,第2207页。
[44]《朱子语类》,第3227~3228页。
[45]《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2页。
[46]《朱子语类》,第1319页。
[47]《朱子语类》,第1471页。
[48]《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8页。
[49]《二程集》,第231页。
[50]《朱熹集》,第2422~2423页。
[51]《朱子语类》,第1531页。
[52]《朱熹集》,第2527页。
[53]《朱子语类》,第1319页。
[54]《朱子语类》,第3257页。
[55]《朱熹集》,第2719页。
[56]《朱熹集》,第3845~3846页。
[57]《朱子语类》,第3297~3298页。
[58]《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6页。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
*本文是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儒家生态哲学史研究”(11AZX00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2]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3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9页;第320页。
[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页。
[4][5]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一),台北正中书局1968年版,第98页、第271页等处;第49页。
[6]陈来:“从本体论上说,理自身并不运动。”《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刘述先的观点可参见其《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版。李明辉观点可参见其《理能否活动?——李退溪对朱子理气论的诠释》等文章。
[7]贺麟:《与张荫麟兄辨宋儒太极说之转变》,《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25页。
[8]贺麟:《关于哲学史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25页。
[9]成中英:《合内外之道——儒家哲学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1页。
[10][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6册,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433页。端蒙录“巳亥(1179年)以后所闻二百余则”,故此可谓朱子中年之论,见陈荣捷:《朱子门人》,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246页。
[11][14][15][17][18][19][20][21][23][24][30][35][36][37][38][39][40][41][42][43][53][54][55][61][63][65]《朱子语类》,第6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403页;第2372页;第2369页;第2372页;第2392页;第2369页;第243页;第2372页;第2403页;第2374页;第2372页;第2372页;第2388页;第2371页;第2396页;第2422页;第2396页;第2396页;第2396页;第2433页;第2376页;第2374页;第2376页;第2387页;第111~112页;第2374页。
[12][16]《文集》卷45《答杨子直》第一书,载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2页;第2072页。
[13][31][48][56][57][58][62]《朱子语类》,第1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6页;第2页;第5页;第74页;第1297页;第71页;第112页。
[15][51]《朱子全书·太极图说解》,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第72页。
[22]《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25]《朱子语类》,第2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23~424页。
[26]《朱子语类》,第5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30页。
[27]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2卷,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页。
[28]《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2页。
[29]周谟“录《语类》巳亥(1179年)后所闻,凡二百余条”。见陈荣捷:《朱子门人》,第141页。
[32][44]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第106页。
[33]此条据陈来考证,出自朱子门人杨与立所编《朱子语略》。陈来:《朱子哲学研究》,第93页。
[34][50]《朱子全书》,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第127页。
[45]《朱子语类》,第6册,第2403~2404页。陈荣捷:“录《语类》癸丑(1193年)以后所闻几四百条。”见陈荣捷:《朱子门人》,第328页。
[46]《朱子语类》,第6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404页。陈荣捷:闳祖录“《语类》戊申(1188年)以后所闻二百余条。”见陈荣捷:《朱子门人》,第124页。
[47]《朱子语类》,第6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404页。陈荣捷:“录《语类》庚戌(1190年)以后所闻逾三百条。”见陈荣捷:《朱子门人》,第180页。
[49]《朱子语类》,第1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4页。陈荣捷:沈僩“录《语类》戊午(1198年)以后所闻七八百则。”
[52]《朱子语类》,第6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376页。义刚师事朱子二次,1193—1195、1197—1199,故其录均为晚年之论。见陈荣捷:《朱子门人》,第260~261页。
[59][60][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3页;第22页。
(原载《哲学动态》2012年第7期,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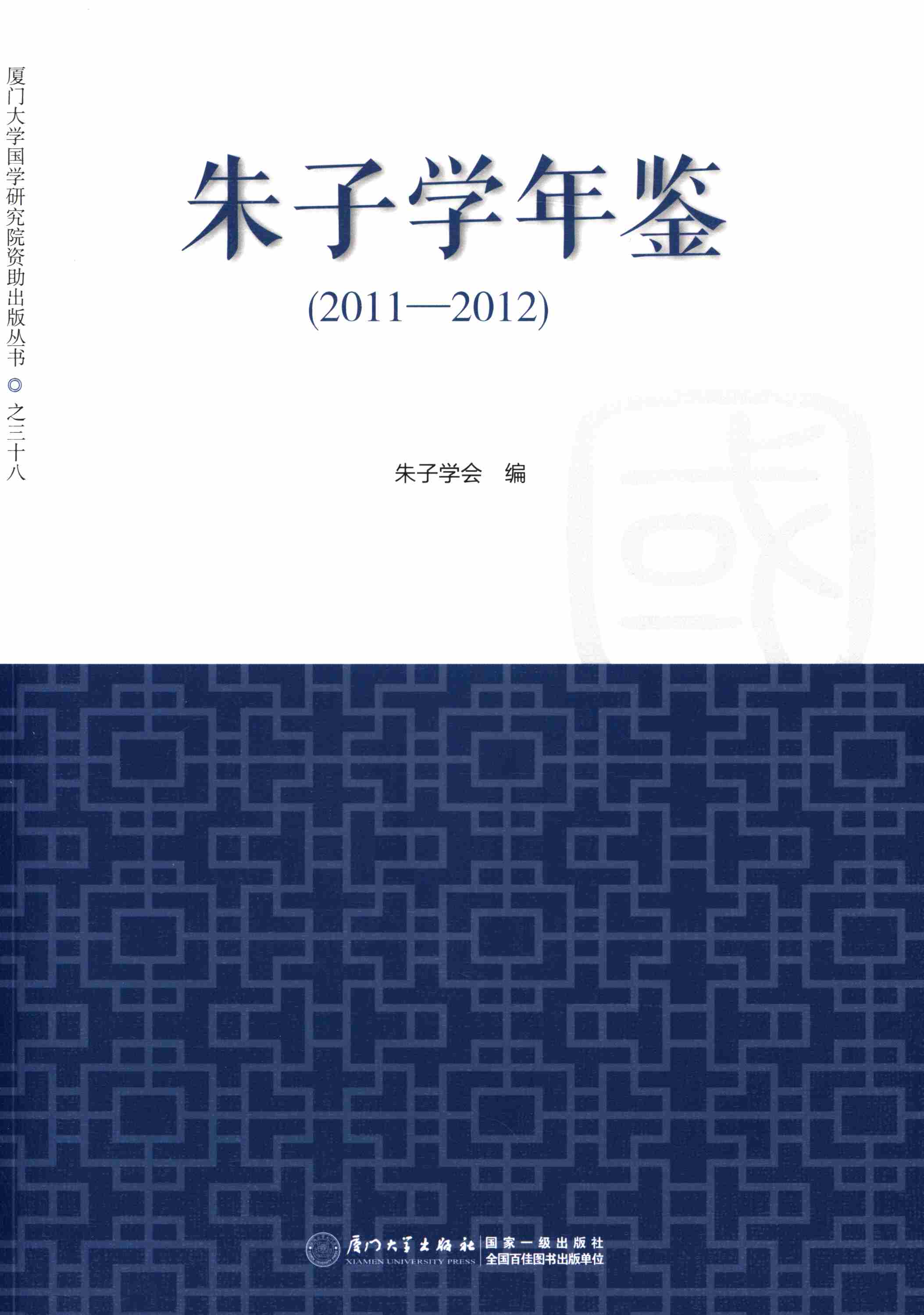
《朱子学年鉴-2011-2012》
出版者:厦门大学出版社
本书为2011-2012年朱子学年鉴。内容包括本刊特稿2篇、朱子学研究新视野7篇、全球朱子学研究述评6篇、朱子学研究新著38篇、朱子学书评3篇、朱子学研究优秀硕博士论文82篇、朱子学研究论文荟萃54篇、朱子学研究重大课题4篇、朱子学国内外学术动态6篇、朱子学研究机构介绍3篇、朱子学研究学者介绍13篇、2011-2012年朱子学新书索引、2011-2012年朱子学论文索引556篇等。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