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本视域下朱子慈善思想及其实践
| 内容出处: | 《2021年朱子文化寻源之旅论文集》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30000147 |
| 颗粒名称: | 三、民本视域下朱子慈善思想及其实践 |
| 分类号: | B244.75 |
| 页数: | 5 |
| 页码: | 058-062 |
| 摘要: | 本文记述朱熹的慈善思想特色在于其提出的“理一分殊”理论,认为宇宙万物都有公共的本体作为本性,但人和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是依据“心”自觉地使“理一”分出为“分殊”,也使“分殊”具有“理一”,双向互动的方式而结合“理一”和“分殊”。因此,朱子把“性”说明是宇宙万物的“理一”,而把“心”说明是人和物之间的差异。 |
| 关键词: | 民本 慈 朱子 |
内容
1、朱熹的慈善思想特色——“理一分殊”
在朱熹之前,北宋张载提出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双重人性论,进一步探究人性善恶来源的理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民胞物与”思想,即《西铭》中所说:“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我与也。”我们的身体靠天地万物滋养,人的品格靠天德本性决定。万民是我的同胞,与大自然一体,万物也就是人的朋友。把天地万物的存在价值作为人的最高价值的追求,并努力践行,最终实现个体精神境界的升华。这里侧重于表述相同,尽管张载对不同即“理一分殊”也有论述,但并不完备。
“理一分殊”作为一个命题,第一次明确提出是程颐的《答杨时论西铭书》。北宋五子中包括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从不同的角度围绕着这个命题进行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的创新思想。到了南宋朱子,总结了北宋五子的探索成果,建构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朱子认为宇宙万物都有公共的本体作为本性。因此,宇宙万物没有不同的,但是人和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是依据“心”自觉地使“理一”分出为“分殊”,也使“分殊”具有“理一”,双向互动的方式而结合“理一”和“分殊”。因此,朱子把“性”说明是宇宙万物的“理一”,而把“心”说明是人和物之间的差异。朱子认为“心”就是人和万物的差异性,“性”就是宇宙万物的共性。
二程以前的儒家把“情”看作是“仁”,没有区分本体和情感。二程第一次把“仁”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但是二程以后,佛教本体论在学术界流行,当时儒者集中讨论“仁”本体论的某个方面,忽视了儒家孔孟以来的“爱”。朱子通过批判“知觉为仁”和“万物一体为仁”的思想,确立“仁”的名义。朱子从人所本来具有的恻隐之情也就是“爱”来对“仁”进行了说明。朱子说:“仁是爱之理,爱是仁之用。未发时,只还做仁,仁却无形影,既发梭,方唤做爱,爱却有形影。”[5]
朱子将“仁”解释为“未发”,将“爱”解释为已发。仁和爱的关系就是本体和作用的关系。仁是未发以前的本体,爱是仁践行后的具体情感的显现,也就是用。爱是从仁生发出来的。虽然仁和爱的有区分,但二者不可相离。仁就是爱的理一,爱就是仁的分殊。
朱子认为虽然“理一分殊”强调对于万物全体的一视同仁,但是“仁”的发端必须是父子之间的血缘之情,否则就无法把握“爱”的内涵。他说:“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气叶处。”[6]“恻隐之心,方是流行处,道得亲亲仁民爱物。”[7]“爱亲仁民爱物无非仁也。但是爱亲乃是切近而真实者,乃是仁最先发处。至赞仁民爱物乃远而大了。义之实亦然。”[8]朱子认为以父子之间的血缘亲情为基础的仁之萌芽,这种恻隐之心可以说是最真实、具体的。这种思想从孔子以来被儒家所一再继承,孔子也是依据血缘亲情的远近亲疏来体现恻隐之心的差别性。到了朱子,进一步将这种血缘亲情扩大到亲亲、仁民、爱物,使得这种恻隐之心流行于宇宙万物。虽然恻隐之心的表现有所不同,但爱亲、爱民、爱物都是仁的表现。
朱子用“理一分殊”的思想,进一步阐释说明了“仁”就是天理流行,当然天理流行不能混乱,具体的事物也处于各自最合当的位置,他把这种事物解说是“义”。“仁”就是“理一”,“义”就是“分殊”。比如我们说的“爱”,“爱”首先要爱父母兄弟,其次是爱亲戚朋友,然后是爱乡亲宗族,进而推到天下国家以致宇宙万物。这种爱贯通于家、乡、宗族,天下国家、宇宙万物,也就是“理一”,但同时也有层次差别性的。如果没有普遍的“爱”,则亲、家、乡里、宗族、天下国家的人不能相亲相爱,如果没有具体的差别的“爱”,则所有的爱就丧失其存在的基础。对于朱子而言,偏重于“理一分殊”两面中的任何一面都是不对的。
朱子的“理一分殊”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儒家慈善观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思维模式而言,朱子将两者解释为普遍和特殊的相互蕴含关系,既不能以普遍取代特殊,也不是要以特殊否定普遍。从价值理念看,这是一种充满现实感的人道主义的慈爱情怀,一方面强调血缘亲情的根本之爱,另一方面对社会普遍的人际关系做出各自的有序安排。
2、朱子慈善思想的实践——社仓制度
社仓制度首创于南宋,与常平仓、义仓多设在大小城镇不同,主要设置在农村,服务于当地老百姓。
宋人魏掞之最早创建社仓。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魏掞之在建宁府建阳县长滩铺设仓,遇歉收以谷贷民,不收利息。[9]《宋史·魏掞之传》称:“诸乡社仓自掞之始。”但是,魏掞之只是以个人的力量创建了社仓,并没有真正推广开来,也未能获得朝廷的确认。社仓制度真正成为国家合法的仓廪制度,是在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在这一过程中,南宋大儒朱子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由此着眼,一般认为,社仓之制始于朱子。”[10]
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秋,建宁府崇安县遭遇大水灾,田地颗粒无收。更严重的是,次年春夏之交,“建人大饥”,民众急需获得救济。在此危急时刻,赋闲在家的朱子受知县诸葛廷瑞的委托,与该乡土居的朝奉郎刘如愚一起劝说富民降价出卖囤积的粮食,以便赈救饥民。正是由于朱子等人的积极努力,“里人方幸以不饥”,大量老百姓获得救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浦城又发生饥民骚乱,而且,朝廷储存的救济粮食也快要耗竭,“藏粟亦且竭”,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在此极其危急的形势下,朱子等向朝廷借到粟六百石,发放给难民,化解了民众暴乱,稳定了社会局面。同年冬,老百姓将所借粟米如数归还。依据这一成功经验,从乾道五年起,朝廷每年都向有困难的百姓借贷一次,帮助百姓渡过难关,等百姓归还时朝廷要征收二分利息,朝廷也获得一定的利益。这实则是一项双赢的政策。等到了乾道七年,朱子在相关官员的帮扶之下,正式修建社仓。四个月时间建成仓廒三间,以原借粟六百石为谷本,于青黄不接时借贷给民户。[11]
南宋淳熙八年(1181)十一月,朱子借着到浙东救灾的时机,上书朝廷,详细阐述了社仓创建的经过及其规约条法、成功经验,希望朝廷能够加以推广。朝廷接纳了朱子的建议,同意各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创建社仓。至此,社仓正式成为一项国家制度,用于防灾备荒。
此后,社仓逐渐获得大范围的扩张。至迟在宋理宗初年,南宋各路已基本都设置了社仓。“各路之中,以两浙路、福建路和江南东、西路的社仓普及程度最高,呈现出以福建为中心向周围辐射的形式。”[12]
社仓的创建和推广,对于防灾备荒发挥了显著的效果。尤其是社仓直接面对普通的老百姓,就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老百姓,以最快最好的途径解决老百姓面临的困难,而这是国家统一管理的仓廪机构所不能比拟的。比如,南宋嘉定八年(1215),潭州全境发生饥荒,造成大量饥民,正是由于潭州长沙县自身已经在庆元初年创建了二十八所社仓,能够及时向本县饥民借贷粮食和种子,有效地帮助本县民众渡过灾荒,重建家园。
宋朝之后,社仓制度获得了继续发展。清朝初年就曾经大规模整顿社仓制度,以便更好地发挥作用。雍正二年(1724),朝廷专门制定社仓条例,对社本筹集、仓谷粜借、仓储保管等有关事项作出具体规定,推动了社仓进一步发展。
从民本角度考察宋代理学家的慈善思想和实践,可以提供我们很多启发,如何落实“均平思想”,实现再分配及共同富裕,如何通过“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慈善模式等。
在朱熹之前,北宋张载提出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双重人性论,进一步探究人性善恶来源的理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民胞物与”思想,即《西铭》中所说:“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我与也。”我们的身体靠天地万物滋养,人的品格靠天德本性决定。万民是我的同胞,与大自然一体,万物也就是人的朋友。把天地万物的存在价值作为人的最高价值的追求,并努力践行,最终实现个体精神境界的升华。这里侧重于表述相同,尽管张载对不同即“理一分殊”也有论述,但并不完备。
“理一分殊”作为一个命题,第一次明确提出是程颐的《答杨时论西铭书》。北宋五子中包括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从不同的角度围绕着这个命题进行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的创新思想。到了南宋朱子,总结了北宋五子的探索成果,建构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朱子认为宇宙万物都有公共的本体作为本性。因此,宇宙万物没有不同的,但是人和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是依据“心”自觉地使“理一”分出为“分殊”,也使“分殊”具有“理一”,双向互动的方式而结合“理一”和“分殊”。因此,朱子把“性”说明是宇宙万物的“理一”,而把“心”说明是人和物之间的差异。朱子认为“心”就是人和万物的差异性,“性”就是宇宙万物的共性。
二程以前的儒家把“情”看作是“仁”,没有区分本体和情感。二程第一次把“仁”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但是二程以后,佛教本体论在学术界流行,当时儒者集中讨论“仁”本体论的某个方面,忽视了儒家孔孟以来的“爱”。朱子通过批判“知觉为仁”和“万物一体为仁”的思想,确立“仁”的名义。朱子从人所本来具有的恻隐之情也就是“爱”来对“仁”进行了说明。朱子说:“仁是爱之理,爱是仁之用。未发时,只还做仁,仁却无形影,既发梭,方唤做爱,爱却有形影。”[5]
朱子将“仁”解释为“未发”,将“爱”解释为已发。仁和爱的关系就是本体和作用的关系。仁是未发以前的本体,爱是仁践行后的具体情感的显现,也就是用。爱是从仁生发出来的。虽然仁和爱的有区分,但二者不可相离。仁就是爱的理一,爱就是仁的分殊。
朱子认为虽然“理一分殊”强调对于万物全体的一视同仁,但是“仁”的发端必须是父子之间的血缘之情,否则就无法把握“爱”的内涵。他说:“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气叶处。”[6]“恻隐之心,方是流行处,道得亲亲仁民爱物。”[7]“爱亲仁民爱物无非仁也。但是爱亲乃是切近而真实者,乃是仁最先发处。至赞仁民爱物乃远而大了。义之实亦然。”[8]朱子认为以父子之间的血缘亲情为基础的仁之萌芽,这种恻隐之心可以说是最真实、具体的。这种思想从孔子以来被儒家所一再继承,孔子也是依据血缘亲情的远近亲疏来体现恻隐之心的差别性。到了朱子,进一步将这种血缘亲情扩大到亲亲、仁民、爱物,使得这种恻隐之心流行于宇宙万物。虽然恻隐之心的表现有所不同,但爱亲、爱民、爱物都是仁的表现。
朱子用“理一分殊”的思想,进一步阐释说明了“仁”就是天理流行,当然天理流行不能混乱,具体的事物也处于各自最合当的位置,他把这种事物解说是“义”。“仁”就是“理一”,“义”就是“分殊”。比如我们说的“爱”,“爱”首先要爱父母兄弟,其次是爱亲戚朋友,然后是爱乡亲宗族,进而推到天下国家以致宇宙万物。这种爱贯通于家、乡、宗族,天下国家、宇宙万物,也就是“理一”,但同时也有层次差别性的。如果没有普遍的“爱”,则亲、家、乡里、宗族、天下国家的人不能相亲相爱,如果没有具体的差别的“爱”,则所有的爱就丧失其存在的基础。对于朱子而言,偏重于“理一分殊”两面中的任何一面都是不对的。
朱子的“理一分殊”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儒家慈善观的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思维模式而言,朱子将两者解释为普遍和特殊的相互蕴含关系,既不能以普遍取代特殊,也不是要以特殊否定普遍。从价值理念看,这是一种充满现实感的人道主义的慈爱情怀,一方面强调血缘亲情的根本之爱,另一方面对社会普遍的人际关系做出各自的有序安排。
2、朱子慈善思想的实践——社仓制度
社仓制度首创于南宋,与常平仓、义仓多设在大小城镇不同,主要设置在农村,服务于当地老百姓。
宋人魏掞之最早创建社仓。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魏掞之在建宁府建阳县长滩铺设仓,遇歉收以谷贷民,不收利息。[9]《宋史·魏掞之传》称:“诸乡社仓自掞之始。”但是,魏掞之只是以个人的力量创建了社仓,并没有真正推广开来,也未能获得朝廷的确认。社仓制度真正成为国家合法的仓廪制度,是在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在这一过程中,南宋大儒朱子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由此着眼,一般认为,社仓之制始于朱子。”[10]
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秋,建宁府崇安县遭遇大水灾,田地颗粒无收。更严重的是,次年春夏之交,“建人大饥”,民众急需获得救济。在此危急时刻,赋闲在家的朱子受知县诸葛廷瑞的委托,与该乡土居的朝奉郎刘如愚一起劝说富民降价出卖囤积的粮食,以便赈救饥民。正是由于朱子等人的积极努力,“里人方幸以不饥”,大量老百姓获得救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浦城又发生饥民骚乱,而且,朝廷储存的救济粮食也快要耗竭,“藏粟亦且竭”,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在此极其危急的形势下,朱子等向朝廷借到粟六百石,发放给难民,化解了民众暴乱,稳定了社会局面。同年冬,老百姓将所借粟米如数归还。依据这一成功经验,从乾道五年起,朝廷每年都向有困难的百姓借贷一次,帮助百姓渡过难关,等百姓归还时朝廷要征收二分利息,朝廷也获得一定的利益。这实则是一项双赢的政策。等到了乾道七年,朱子在相关官员的帮扶之下,正式修建社仓。四个月时间建成仓廒三间,以原借粟六百石为谷本,于青黄不接时借贷给民户。[11]
南宋淳熙八年(1181)十一月,朱子借着到浙东救灾的时机,上书朝廷,详细阐述了社仓创建的经过及其规约条法、成功经验,希望朝廷能够加以推广。朝廷接纳了朱子的建议,同意各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创建社仓。至此,社仓正式成为一项国家制度,用于防灾备荒。
此后,社仓逐渐获得大范围的扩张。至迟在宋理宗初年,南宋各路已基本都设置了社仓。“各路之中,以两浙路、福建路和江南东、西路的社仓普及程度最高,呈现出以福建为中心向周围辐射的形式。”[12]
社仓的创建和推广,对于防灾备荒发挥了显著的效果。尤其是社仓直接面对普通的老百姓,就能够更好地服务于老百姓,以最快最好的途径解决老百姓面临的困难,而这是国家统一管理的仓廪机构所不能比拟的。比如,南宋嘉定八年(1215),潭州全境发生饥荒,造成大量饥民,正是由于潭州长沙县自身已经在庆元初年创建了二十八所社仓,能够及时向本县饥民借贷粮食和种子,有效地帮助本县民众渡过灾荒,重建家园。
宋朝之后,社仓制度获得了继续发展。清朝初年就曾经大规模整顿社仓制度,以便更好地发挥作用。雍正二年(1724),朝廷专门制定社仓条例,对社本筹集、仓谷粜借、仓储保管等有关事项作出具体规定,推动了社仓进一步发展。
从民本角度考察宋代理学家的慈善思想和实践,可以提供我们很多启发,如何落实“均平思想”,实现再分配及共同富裕,如何通过“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慈善模式等。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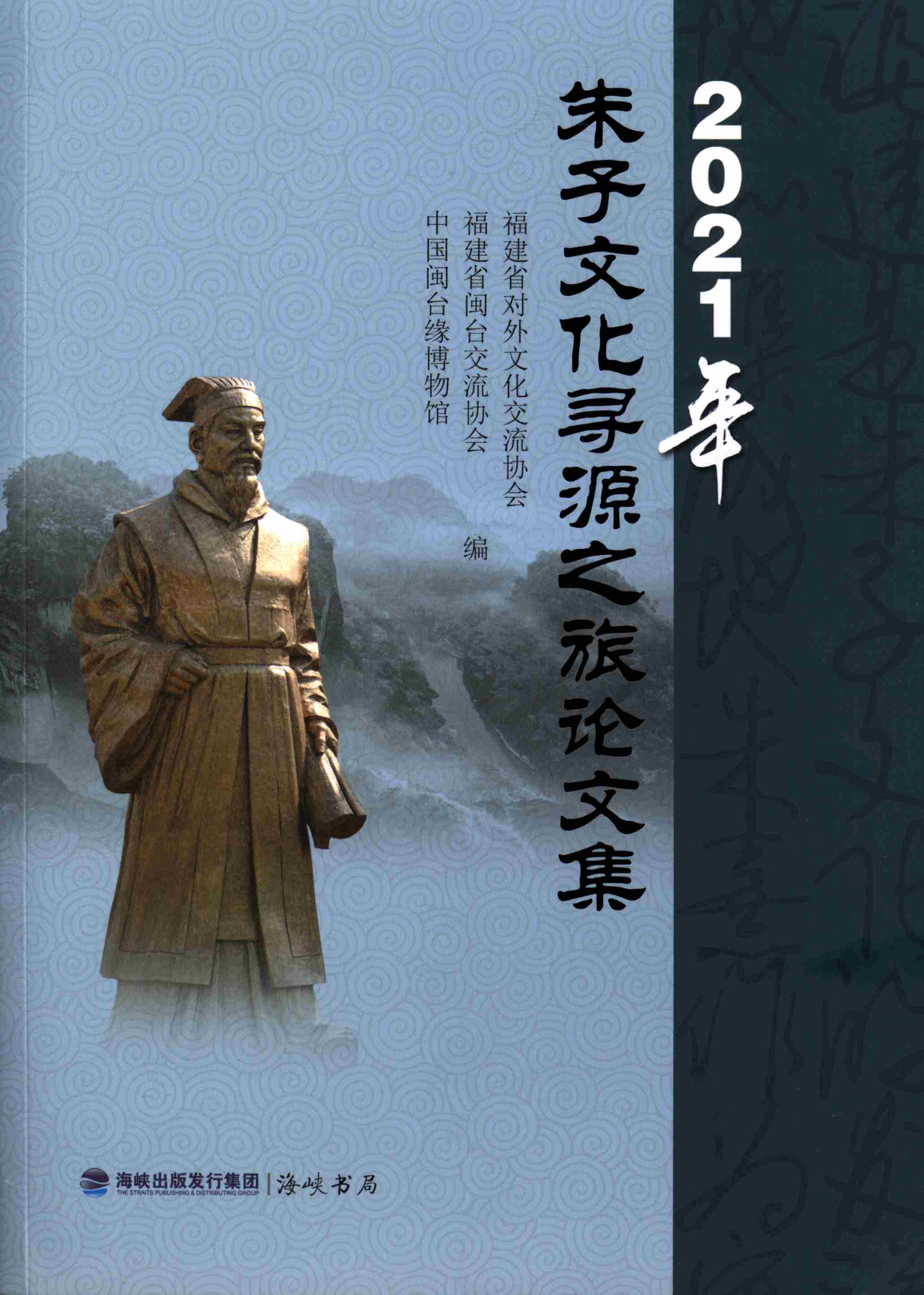
《2021年朱子文化寻源之旅论文集》
出版者:海峡书局
本书收录了《展现福建传承弘扬朱子文化新气象》《朱子文化的基本精神》《朱熹的民本思想》《武夷山朱子文化旅游价值与建设路径》《民本视域下的朱子慈善思想及其实践》等文章。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