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侗所授“求中未发”思想对朱熹的理学思想影响
| 内容出处: | 《李侗文化研究 (第三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10004334 |
| 颗粒名称: | 一、李侗所授“求中未发”思想对朱熹的理学思想影响 |
| 分类号: | B244.99 |
| 页数: | 3 |
| 页码: | 223-225 |
| 摘要: | 本文内容记述了朱熹还肯定了性是未发,是体;情是已发,是用;心统性情,心包括已发和未发、体和用。 李侗对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 |
| 关键词: | 李侗 朱熹 理学 |
内容
从程颐到杨时、罗从彦以至李侗,都服膺《中庸》“求中未发”思想,都把默坐澄心观喜怒哀乐以前气象作为口诀和重要论题。“求中未发”思想要求人的精神或意识处于静寂状态时,注意加强保存和培养心性之善;当精神或意识处于活动状态时,注意省观察识这种活动,以防偏离“善”的情况发生。朱熹说,“余蚤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又说:“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指诀。”《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李侗反复用这段话教育朱熹,强调要重在体验“未发”。
在《延平答问》中,李侗说:“《中庸》以喜怒哀乐未发已发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导至于见得大本达道外,又浑然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导,若不于未发已发处看,即何缘知之?”这是强调“求中未发”的重要性。李侗所授对已发未发问题的理解,有助于启发朱熹从中逐渐悟出理学心性论的一些道理。在逐渐理解过程中,朱熹对有的观点与前辈李侗某些说法有异也在所不顾,这反映出他的一些思想变化情况。其中,乾道二年(1166)时,朱熹思想倾向于用顿悟观点看《中庸》、《孟子》,觉得这样看可以一通百通,无往不利。这是朱熹对程门“已发未发”思想的理解的一个新角度,被称为朱熹的乾道丙戌之悟。到了乾道五年(1169),朱熹四十岁时,思想又发生一次变化。己丑之前朱熹以心为已发,性为未发,至己丑才发现自己的错误。此时朱熹认识到,原来无论语默动静,心的作用是从未止息的,心包括已发未发;作为心之本体的人性,是未发;情是已发,是用;已发未发浑然一体:于是,朱熹看到了李侗的求中未发之教的片面性。这就是后来理学家所注重研究的朱熹的己丑之悟。与此同时,朱熹也对张载的一些思想极为欣赏。朱熹把张载心统性情之说与杨时、李侗一脉所传未发以前气象之说联系起来考察。朱熹赞赏张载之说,但也认为对杨时、李侗之说不能搁弃一边而不加理会。于是朱熹主张已发未发兼顾交修,并认为延平(李侗)之教本也是内外兼顾、动静交修。朱熹自信,假如李延平复生,也会对他的观点首肯的。朱熹又从程门找出一个“敬”字,认为“敬而无失,即所以中”、“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再加上“于日用处用功”、“去圣经中求义”这两项,朱熹认为,这样便与延平遗教相配合了。
朱熹的语录中有一条说:“《定性书》说得也诧异。此性字是个心字意。”程颢的《定性书》中说:“心无内外。”朱熹之所以觉得诧异,是因为《定性书》实际上是以心为性。这并不是程颢误用了字,而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心”二字的意义并无严格的分别。《定性书》的“性”实际上包括“心”的已发和未发,《定性书》中的“定性”等同于“定心”。朱熹认为把“定心”称为“定性”,违反了张载的“心通性情”所规定的心、性的区别。张载也说过“定性”,以心为性,但这是为迁就程颢的系统,实际上其所谓的“定性”就是孟子所说的“不动心”。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屈”,是说“养浩然之气”的人的心是“定”的,绝不为外物所动。
朱熹的中和说是“心统性情”说。此说把“心”、“性”、“情”这三个术语的意思说得更清楚了。朱熹说:“一身之中,浑然自有个主宰者,心也;有仁、义、礼、智,则是性;发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则是情。恻隐,爱也,仁之端也。仁是体,爱是用。”朱熹还肯定了性是未发,是体;情是已发,是用;心统性情,心包括已发和未发、体和用。这样,体认已发未发的“龟山门下相传指诀”,到朱熹的中和说中便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了。
在《延平答问》中,李侗说:“《中庸》以喜怒哀乐未发已发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导至于见得大本达道外,又浑然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导,若不于未发已发处看,即何缘知之?”这是强调“求中未发”的重要性。李侗所授对已发未发问题的理解,有助于启发朱熹从中逐渐悟出理学心性论的一些道理。在逐渐理解过程中,朱熹对有的观点与前辈李侗某些说法有异也在所不顾,这反映出他的一些思想变化情况。其中,乾道二年(1166)时,朱熹思想倾向于用顿悟观点看《中庸》、《孟子》,觉得这样看可以一通百通,无往不利。这是朱熹对程门“已发未发”思想的理解的一个新角度,被称为朱熹的乾道丙戌之悟。到了乾道五年(1169),朱熹四十岁时,思想又发生一次变化。己丑之前朱熹以心为已发,性为未发,至己丑才发现自己的错误。此时朱熹认识到,原来无论语默动静,心的作用是从未止息的,心包括已发未发;作为心之本体的人性,是未发;情是已发,是用;已发未发浑然一体:于是,朱熹看到了李侗的求中未发之教的片面性。这就是后来理学家所注重研究的朱熹的己丑之悟。与此同时,朱熹也对张载的一些思想极为欣赏。朱熹把张载心统性情之说与杨时、李侗一脉所传未发以前气象之说联系起来考察。朱熹赞赏张载之说,但也认为对杨时、李侗之说不能搁弃一边而不加理会。于是朱熹主张已发未发兼顾交修,并认为延平(李侗)之教本也是内外兼顾、动静交修。朱熹自信,假如李延平复生,也会对他的观点首肯的。朱熹又从程门找出一个“敬”字,认为“敬而无失,即所以中”、“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再加上“于日用处用功”、“去圣经中求义”这两项,朱熹认为,这样便与延平遗教相配合了。
朱熹的语录中有一条说:“《定性书》说得也诧异。此性字是个心字意。”程颢的《定性书》中说:“心无内外。”朱熹之所以觉得诧异,是因为《定性书》实际上是以心为性。这并不是程颢误用了字,而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性”、“心”二字的意义并无严格的分别。《定性书》的“性”实际上包括“心”的已发和未发,《定性书》中的“定性”等同于“定心”。朱熹认为把“定心”称为“定性”,违反了张载的“心通性情”所规定的心、性的区别。张载也说过“定性”,以心为性,但这是为迁就程颢的系统,实际上其所谓的“定性”就是孟子所说的“不动心”。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屈”,是说“养浩然之气”的人的心是“定”的,绝不为外物所动。
朱熹的中和说是“心统性情”说。此说把“心”、“性”、“情”这三个术语的意思说得更清楚了。朱熹说:“一身之中,浑然自有个主宰者,心也;有仁、义、礼、智,则是性;发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则是情。恻隐,爱也,仁之端也。仁是体,爱是用。”朱熹还肯定了性是未发,是体;情是已发,是用;心统性情,心包括已发和未发、体和用。这样,体认已发未发的“龟山门下相传指诀”,到朱熹的中和说中便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了。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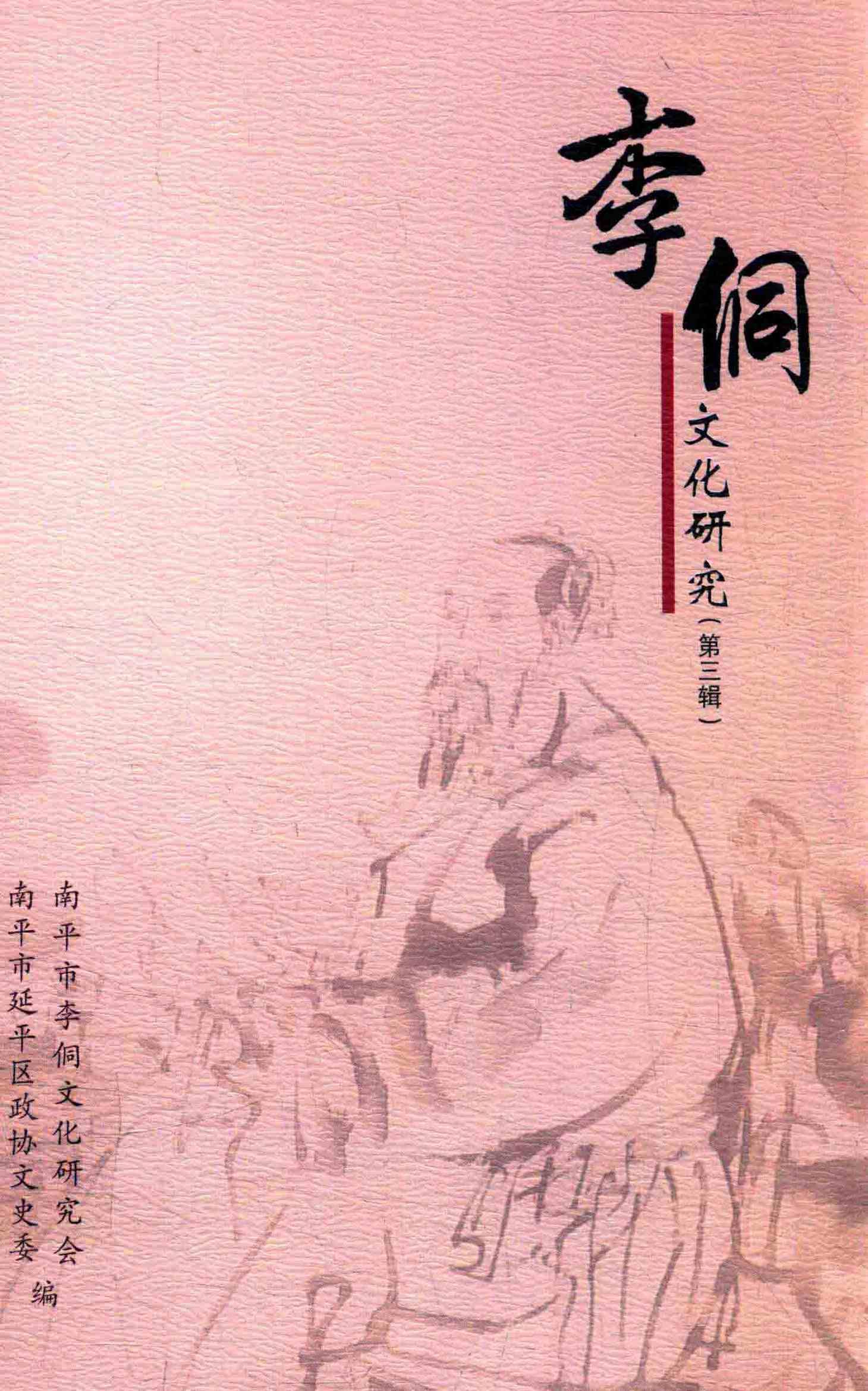
《李侗文化研究 (第三辑)》
这本《李侗文化研究(第三辑)》,较为系统地展示了理学先贤李侗先生的理学造诣,让留存于故纸堆中的历史文化遗存,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文化产品,从而使它释放岀理学的巨大能量和深远影响。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