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禅归儒 弃文崇道
| 内容出处: | 《李侗文化研究 (第三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10004324 |
| 颗粒名称: | 逃禅归儒 弃文崇道 |
| 其他题名: | 李侗对朱熹早年思想的影响 |
| 分类号: | B244.99 |
| 页数: | 10 |
| 页码: | 204-213 |
| 摘要: | 本文内容记述了李侗对朱熹早年思想的影响,其中包括师事武夷三先生,接受渗透佛老的儒学教育,师从道谦,沉溺佛老,追求昭昭灵灵的禅,逃禅归儒:李侗将朱熹引出佛老泥淖、引入儒学正路弃文崇道:李侗使朱熹确立以唱道为己任的理想。 |
| 关键词: | 李侗 朱熹 思想 |
内容
朱熹从二十四岁至三十三岁师从李侗十年,六次面见亲受教诲,数十封信函往来问学,李侗对朱熹早年的思想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是李侗使朱熹幡然醒悟,逃禅归儒,将其引出佛老的泥淖、引上了道学的轨道,避免了朱熹在木鱼僧房中了此一生。李侗给朱熹指明了正确的用功方向,引导他去经典中求义,在日用处用工;传授了朱熹理一分殊的思想内核和主静的修养方法,实现了从主悟到主静的转变,以虚一而静的存养工:夫代替空理悟入,以应事接物的分殊体认代替内心领悟。也正是李侗的教诲,使朱熹弃文崇道,确立以“穷理知道”为己任的理想。受教李侗,改变了朱熹早年的学术思想方向,对其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师事武夷三先生,接受渗透佛老的儒学教育
朱熹十四岁时,其父朱松病故。朱松去世前把家事托付给在崇安五夫里奉祠家居的刘子羽。朱熹遵父遗命,“依托刘子羽,入刘氏家塾,受学于武夷三先生:胡宪、刘勉之、刘子翚”。接受比较全面的儒学教育。三先生都是洁身自好、超世脱俗的饱学硕儒,籍溪胡宪廉退自好的节操人品,草堂刘勉之的训诂学风,屏山刘子翚的举子学业,都对朱熹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三先生的指导下,朱熹开始阅读儒家经典,为科举入仕攻读程文与辞章之学,为入“圣贤之域”而接触洛学,对道学有了初步的理解。但此时,“朱熹在三先生的教导下虽然对洛学已经有所体会,但还未完全进入程学的门径,并且还抱有从佛老之学体认儒家内圣的观点”。
两宋之际,战乱不断,中原沦陷、山河破碎的巨变,使传统的儒家思想受到冲击,士大夫们在佛教和道教中寻求精神的慰藉,普遍养成了逃禅避祸、喜好谈佛说老的风气。他们和佛僧大都交往密切,关系和谐,儒佛道可以并行不悖得到广泛的认同,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成为很多士大夫的人生信条,“出入佛老以求通达儒家的内圣是宋代许多士大夫都曾经历的过程”。
武夷三先生也不例外,他们对佛老的喜好,也影响了朱熹。“三先生把渗透浓重佛老气的理学思想传授给了朱熹”。除直接受到三先生的影响外,朱熹也间接受到家庭佛老气氛的熏陶,其祖父朱森,父亲朱松,以及三叔父朱槔都耽好佛老,喜结交禅师:因此,朱熹在接受传统儒学教育的同时,受三先生等的影响和熏陶,朱熹出入佛老,对佛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自己也说:“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学)。”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在给程正思信中,也再次明说自己早年曾经学习禅宗:“盖缘旧日曾学禅宗。”
二、师从道谦,沉溺佛老,追求昭昭灵灵的禅
朱熹早年从三先生那里授受的是渗透浓重佛老气息的儒家教育,而与道谦的相遇郊游,追求昭昭灵灵的禅,朱熹从而沉溺佛老,并师从道谦,开始了十余年出入佛老的心路历程。
开善寺的道谦是一个深得宗杲衣钵真传的高僧。绍兴十五年(1145),朱熹经刘屏山得以认识道谦。“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年轻的朱熹对道谦深感敬佩甚至崇拜。
绍兴十八年(1148)他带着宗杲的《大慧语录》离开家乡,赴临安应试。一路上,远游访禅,在礼部的考试中,他援佛入儒,靠着昭昭灵灵的禅说,竟然获得了考官们的青睐,得以金榜题名,使他更加崇信道谦。“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
绍兴十九年(1149)冬天,二十岁的朱熹,以新科进士身份荣归故里,回到婺源老家。次年春天返回时,走德兴、贵溪、弋阳、铅山一路,目的就是方便寻禅问道。归来后整整一年他沉浸在耽读儒经、佛典和道书中。因此,“绍兴十八年以来的远游和耽读佛老开拓了他的佛学视野,推动他跨出了师事道谦的决定性一步。”
于是朱熹在密庵拜道谦为师,学内心参悟,学习融贯儒佛老,前后长达三年。他把书斋取名为“牧斋”,闭门自牧主悟,修养明心见性的佛老心学,希望借佛禅心性之学来通达儒家的内圣。朱熹沉溺于佛老,也使他一度迷惑,“泛滥诸家,无所适从”。他说:“初师屏山、籍溪,籍溪学于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学为论治道则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有见……其后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见延平。”他在与汪应辰的书信中也说到这事:“熹于释氏之说,盖当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
三、逃禅归儒:李侗将朱熹引出佛老泥淖、引入儒学正路
正当朱熹沉溺于佛老禅说,难以自拔之际,见到了李侗,从而把他引出佛老泥淖,引入儒学正路。“对于此时正沉溺于此的朱熹来说,还需要一个将他引出佛老、引入儒学道路的人,而这个人就是李侗。”
绍兴二十三年(1153)五月,朱熹带着从道谦处熏陶来的一身禅气,南下赴任同安主簿。经过南剑时,往剑浦城南樟林,首次拜见了李侗。
延平先生李侗,字愿中,师从豫章罗从彦,是龟山杨时的再传弟子。“独得其阃奥,经学纯明,涵养精粹。”他“一生不仕,结茅水竹樟林间,山中屏居四十年”。因和朱松是同门学友,两人交游相知几十年,“道谊之契甚深”。朱熹从小对其学问为人已耳濡目染。
朱熹除了遵父遗命,问学李侗外,他“这次见李侗主要就是向他大谈‘昭昭灵灵’的禅学,炫耀自己近十年出入佛老的感受,把三先生和道谦传授给他的佛老玄说和盘倾倒出来就教于李侗”。
李侗并不认可朱熹以禅学通达内圣的道路,对他“就里面体认”的禅家参悟直接提出严厉的批评,对沉迷于此的朱熹当头棒喝!他看出朱熹“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的弊病,要把年轻的朱熹引出佛禅的泥沼,让他从佛国仙界回到儒教乐地。“熹旧见李先生时,说得无限道理,也曾去学禅。李先生云:‘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而面前事却有理会不得!道亦无玄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李侗当面指出朱熹追求一超直悟,悬空理会之弊,缺少平日存养工夫。要求朱熹“以存养工夫代替空理悟入,以应事接物的分殊体认代替内里体认。”强调佛释言空,儒家言实,儒家实理,贯穿于人伦日用之间,只有儒家之道才能救时济世。李侗的教导如平地一声惊雷,给了沉迷佛老的朱熹巨大的震动,第一次打破了儒佛老同道的思想,朱熹如醍醐灌顶,从沉迷老佛的自我陶醉中逐渐清醒过来。
同时,朱熹在同安主簿的任上,面对百姓穷困、民生凋敝的现实,也意识到道谦“昭昭灵灵底禅”,并不能真正解决现实所存在的复杂矛盾,不能经世致用。只有儒学才可以“敦礼义,厚风俗,戢吏奸,恤民隐”,解决社会难题,才能济世安民,从而使“朱熹身上儒家士大夫的担待意识逐渐觉醒,这也是他认识到佛禅之弊,归本儒家的重要原因”。朱熹弃禅归儒思想转变的一大标志就是他向县学诸生发了三十三篇《策问》,提出了一系列现实问题,表明了他试图以儒学来解决现实问题的立场。
假如没有李侗的一声棒喝,让朱熹醍醐灌顶,幡然醒悟,弃禅归儒,朱熹也许要在木鱼僧房中了此一生,实现他“粥饭何时共木鱼”的理想。这样的话,佛界可能多了一个高僧,但少了一个“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理学集大成者。
李侗不仅使朱熹从禅佛中惊醒,抛弃禅学开始归本儒学,还指示了他正确的用功方向,教导朱熹去圣贤经书中求义,在日用处用工。他教导朱熹,“道亦无幽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惟于日用处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几渐可合为己物,不然,只是说也”。道体现于日用常行中,只有在日用间做功夫,才能理会寻找到道理,其方法途径就是读圣贤之书,看圣贤言语,在经书中求得答案,这就扭转了朱熹的用功方向。朱熹自己也说:“及见李先生后,方知得是恁地下功夫。”在李侗的点拨下,朱熹由沉溺于佛经转入读儒家经典。李侗教诲的“一则曰日用处用功,二则曰去圣经中求义。两番教言均注重人生之教,这对扭转朱熹的研究方向起很大作用”。
在李侗的教导下,朱熹最终发现了释氏之说漏洞百出:“李先生人简重,却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熹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开始转向儒学,寻求义理,从而使他的学问方向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绍兴二十六年(1156)七月,朱熹同安主簿任满后,到泉州等候批书,度过了同安官余的半年。“同安官余”的读经反思和“杜鹃夜悟”的反省,使他对李侗的教诲深信不疑,更加坚定了他从教李侗的决心。赵师夏《跋延平答问》:“余之始学,亦务为笼侗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于小,于延平之言,则以为何多事若是,心疑而不服。同安官余,反复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后来朱熹所作《困学》诗:“旧喜安心若觅心,捐书绝学费追求。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寸阴。”表述了对这段师从道谦学禅,枉度光阴的后悔。
“理一分殊”和“主静”是李侗学问的主旨,也是“道南一脉”推崇和关注的核心命题。李侗的“理一分殊”观点对朱熹产生重大影响,使朱熹得道南真传,成为朱子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绍兴二十八年(1158)正月,朱熹与李侗再次相见,李侗主要给他传授“理一分殊”的学问。其意是宇宙间有一个最高的理,是总的本源,这就是“理一”;万事万物虽千差万别,亦各有各自的理,但这只是最高理的体现和反映,这就是“分殊”,以此来解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李侗说:“事有小大,理却无小大。”“事有小大”指分殊,“理无小大”指理一。“理一分殊”是李侗学问的核心,也是区分儒学与异端的标志。他教导朱熹:“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要求朱熹领会和掌握“理一分殊”的真谛。
朱熹接受了李侗就分殊上体认理一,即事穷理,循序渐进的思想。“理一分殊思想的确立使朱熹从朦胧的觉醒转向自觉的排佛。”
李侗又标举“主静”,主张静中体认,求中未发,把静中体认称为“于静处下工夫”。他认为“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耳。”因为儒家之理是天理,而心具众理,要体认天理就要以静摄心,方法就是静坐、默坐澄心。
朱熹对李侗以主静为修身之方,以致知为进学之要,终日静坐以求未发气象的功夫进路并不十分认同。朱熹说:“余早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未达而先生没。”直到李侗去世都是没有完全参透掌握,最终以“居敬存养”,代替了李侗的主静工夫。
四、弃文崇道:李侗使朱熹确立以唱道为己任的理想
绍兴三十年(1160)十月,朱熹又到延平与李侗相见。这次延平之会,使朱熹思想发生另一转变就是意识到作文害道,使他终于放弃原来想当诗人和文章家的想法,表示“顷以多言害道,绝不作诗”,决定弃文崇道,终身以“唱(倡)道”为己任。
他给表弟程洵信中更明白表示说:“往年误欲作文,近年颇觉非力所及,遂已罢去,不复留情其间,颇觉省事。”这种弃文崇道立场转变后,“他同程洵展开了崇道学之士而贬辞章之士、崇程学而贬苏学、崇儒学而贬诗文的激烈论辨”开始了自己“穷理知道”新历程。
不仅确立以穷理知道为己任的理想,更要付之于践履。虽然李侗屏居山中,终生不仕,但教导朱熹要知行并举,穷理应事兼行,做到“应事洒落”。在李侗的鼓励下,朱熹开始关注朝廷政局,关注社会民生,从书斋中走了出来,直面社会现实。“由恬淡退守、洁身自好到以下民为忧、以未行为恐的变化。”在李侗的督促鼓励下,朱熹开始上封事和入都奏事。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八月,宋高宗禅位给孝宗后,朱熹应诏上了平生第一篇封事——《壬午封事》:提出了“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三大方略:一是“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帝王要熟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大学之道,反佛崇儒,才能大本正而天下治。二是“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做到修政事,攘夷狄;三是“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要正朝廷、立纪纲、励风俗,选守令,才能安定天下百姓。
朱熹这篇封事,事先和李侗进行了讨论,得到了李侗的悉心指点,“封事熟读数过,立意甚佳。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议为名尔。书中论之甚善……要之,断然不可和,自整顿纲纪,以大义断之,以示天下向背,立为国是可尔,此处更可引此。又许便宜从事处,更下数语以晓之,如何?……亦可早发去为佳”。封事也正是李侗穷理洒然和应事洒然思想的反映。
李侗还鼓励朱熹入都奏事。由于汪应辰等人的举荐,隆兴元年(1163)八月,朱熹再次入都,第一次到垂拱殿面对新君孝宗奏事。对此次面君登对,李侗很是关切,反复教导朱熹:要从反佛、反和、反近习三条入手。朱熹把李侗的意见都写入了奏事三札中,即《癸未奏札》:一是极论《大学》之道和帝王之学;二是论复仇之义;三是论内修政事之要。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朱熹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孝宗的青睐,被除武学博士,待次四年,变相的把朱熹弃于家中而不用。虽然朱熹“得君行道”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但入都后得以与众多道学士大夫的相识,提升了朱熹的知名度和地位,朱熹因此成为道学群体的一员,并且卷进了隆兴北伐与和议的政治漩涡。
朱熹问学李侗,达十年之久。“朱子对李侗的师从是后生对当时大儒的敬仰与赞许。”师事李侗,从“存养”到“致知”到“应事”等方面都得到其教诲,对朱熹思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在李侗的指点下,朱熹从虔诚出入佛老的泥潭中清醒过来,认识到了释老的错误与危害。正如《朱子年谱》记载:“朱熹之学,初无常师,出入于经传,或泛滥于释老。自谓见李先生后,为学始就平实,乃知向日从事释老之说皆非。……”从而弃禅归儒,转到儒学的路径上来,改变了他一生的思想道路。“从学李侗,使朱熹完全放弃了禅学迂回,直接回到儒家经典中找寻内圣的门径。更重要的是,李侗不只将朱熹引回儒学,而且将朱熹引入了二程道学传统中。”
此外,李侗还指明了朱熹去圣贤经书中求义,在日用处用工正确方向;传授了“理一分殊”和主静的修养方法,且使朱熹弃文崇道,确立以唱道为己任的道学理想。使朱熹成为二程的四传弟子,继承道学正统。可以说“李侗是使朱熹真正踏入道学之门的第一人”。
朱熹对恩师也十分尊敬。李侗去世后,隆兴二年(1164)正月,朱熹到延平哭奠李侗,亲自撰写了《祭李延平先生文》和《延平先生李公行状》:高度评价了恩师李侗的人品:“先生姿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完粹,无复圭角,精纯之气,达于面目。”在《祭文》中感谢李侗十年来的教诲是义重恩深:“从游十年,诱掖谆至。春山朝荣,秋堂夜空。即事即理,无幽不穷。……熹等久依教育,义重恩深。”汪应辰在所作《李延平先生墓志铭》中也说朱熹受教李侗久益不懈,“其事先生,久益不懈。以为每一见,则所闻必益超绝”。后来朱熹在创办沧州精舍时,将恩师李侗从祀孔子,表达了对李侗的尊敬和推崇。
一、师事武夷三先生,接受渗透佛老的儒学教育
朱熹十四岁时,其父朱松病故。朱松去世前把家事托付给在崇安五夫里奉祠家居的刘子羽。朱熹遵父遗命,“依托刘子羽,入刘氏家塾,受学于武夷三先生:胡宪、刘勉之、刘子翚”。接受比较全面的儒学教育。三先生都是洁身自好、超世脱俗的饱学硕儒,籍溪胡宪廉退自好的节操人品,草堂刘勉之的训诂学风,屏山刘子翚的举子学业,都对朱熹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三先生的指导下,朱熹开始阅读儒家经典,为科举入仕攻读程文与辞章之学,为入“圣贤之域”而接触洛学,对道学有了初步的理解。但此时,“朱熹在三先生的教导下虽然对洛学已经有所体会,但还未完全进入程学的门径,并且还抱有从佛老之学体认儒家内圣的观点”。
两宋之际,战乱不断,中原沦陷、山河破碎的巨变,使传统的儒家思想受到冲击,士大夫们在佛教和道教中寻求精神的慰藉,普遍养成了逃禅避祸、喜好谈佛说老的风气。他们和佛僧大都交往密切,关系和谐,儒佛道可以并行不悖得到广泛的认同,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成为很多士大夫的人生信条,“出入佛老以求通达儒家的内圣是宋代许多士大夫都曾经历的过程”。
武夷三先生也不例外,他们对佛老的喜好,也影响了朱熹。“三先生把渗透浓重佛老气的理学思想传授给了朱熹”。除直接受到三先生的影响外,朱熹也间接受到家庭佛老气氛的熏陶,其祖父朱森,父亲朱松,以及三叔父朱槔都耽好佛老,喜结交禅师:因此,朱熹在接受传统儒学教育的同时,受三先生等的影响和熏陶,朱熹出入佛老,对佛道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自己也说:“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禅学)。”淳熙十五年(1188)朱熹在给程正思信中,也再次明说自己早年曾经学习禅宗:“盖缘旧日曾学禅宗。”
二、师从道谦,沉溺佛老,追求昭昭灵灵的禅
朱熹早年从三先生那里授受的是渗透浓重佛老气息的儒家教育,而与道谦的相遇郊游,追求昭昭灵灵的禅,朱熹从而沉溺佛老,并师从道谦,开始了十余年出入佛老的心路历程。
开善寺的道谦是一个深得宗杲衣钵真传的高僧。绍兴十五年(1145),朱熹经刘屏山得以认识道谦。“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会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年轻的朱熹对道谦深感敬佩甚至崇拜。
绍兴十八年(1148)他带着宗杲的《大慧语录》离开家乡,赴临安应试。一路上,远游访禅,在礼部的考试中,他援佛入儒,靠着昭昭灵灵的禅说,竟然获得了考官们的青睐,得以金榜题名,使他更加崇信道谦。“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
绍兴十九年(1149)冬天,二十岁的朱熹,以新科进士身份荣归故里,回到婺源老家。次年春天返回时,走德兴、贵溪、弋阳、铅山一路,目的就是方便寻禅问道。归来后整整一年他沉浸在耽读儒经、佛典和道书中。因此,“绍兴十八年以来的远游和耽读佛老开拓了他的佛学视野,推动他跨出了师事道谦的决定性一步。”
于是朱熹在密庵拜道谦为师,学内心参悟,学习融贯儒佛老,前后长达三年。他把书斋取名为“牧斋”,闭门自牧主悟,修养明心见性的佛老心学,希望借佛禅心性之学来通达儒家的内圣。朱熹沉溺于佛老,也使他一度迷惑,“泛滥诸家,无所适从”。他说:“初师屏山、籍溪,籍溪学于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学为论治道则可,而道未至。然于佛老亦未有见……其后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见于此道未有所得,乃见延平。”他在与汪应辰的书信中也说到这事:“熹于释氏之说,盖当师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未能有得。”
三、逃禅归儒:李侗将朱熹引出佛老泥淖、引入儒学正路
正当朱熹沉溺于佛老禅说,难以自拔之际,见到了李侗,从而把他引出佛老泥淖,引入儒学正路。“对于此时正沉溺于此的朱熹来说,还需要一个将他引出佛老、引入儒学道路的人,而这个人就是李侗。”
绍兴二十三年(1153)五月,朱熹带着从道谦处熏陶来的一身禅气,南下赴任同安主簿。经过南剑时,往剑浦城南樟林,首次拜见了李侗。
延平先生李侗,字愿中,师从豫章罗从彦,是龟山杨时的再传弟子。“独得其阃奥,经学纯明,涵养精粹。”他“一生不仕,结茅水竹樟林间,山中屏居四十年”。因和朱松是同门学友,两人交游相知几十年,“道谊之契甚深”。朱熹从小对其学问为人已耳濡目染。
朱熹除了遵父遗命,问学李侗外,他“这次见李侗主要就是向他大谈‘昭昭灵灵’的禅学,炫耀自己近十年出入佛老的感受,把三先生和道谦传授给他的佛老玄说和盘倾倒出来就教于李侗”。
李侗并不认可朱熹以禅学通达内圣的道路,对他“就里面体认”的禅家参悟直接提出严厉的批评,对沉迷于此的朱熹当头棒喝!他看出朱熹“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的弊病,要把年轻的朱熹引出佛禅的泥沼,让他从佛国仙界回到儒教乐地。“熹旧见李先生时,说得无限道理,也曾去学禅。李先生云:‘汝恁地悬空理会得许多,而面前事却有理会不得!道亦无玄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便自见得。’”李侗当面指出朱熹追求一超直悟,悬空理会之弊,缺少平日存养工夫。要求朱熹“以存养工夫代替空理悟入,以应事接物的分殊体认代替内里体认。”强调佛释言空,儒家言实,儒家实理,贯穿于人伦日用之间,只有儒家之道才能救时济世。李侗的教导如平地一声惊雷,给了沉迷佛老的朱熹巨大的震动,第一次打破了儒佛老同道的思想,朱熹如醍醐灌顶,从沉迷老佛的自我陶醉中逐渐清醒过来。
同时,朱熹在同安主簿的任上,面对百姓穷困、民生凋敝的现实,也意识到道谦“昭昭灵灵底禅”,并不能真正解决现实所存在的复杂矛盾,不能经世致用。只有儒学才可以“敦礼义,厚风俗,戢吏奸,恤民隐”,解决社会难题,才能济世安民,从而使“朱熹身上儒家士大夫的担待意识逐渐觉醒,这也是他认识到佛禅之弊,归本儒家的重要原因”。朱熹弃禅归儒思想转变的一大标志就是他向县学诸生发了三十三篇《策问》,提出了一系列现实问题,表明了他试图以儒学来解决现实问题的立场。
假如没有李侗的一声棒喝,让朱熹醍醐灌顶,幡然醒悟,弃禅归儒,朱熹也许要在木鱼僧房中了此一生,实现他“粥饭何时共木鱼”的理想。这样的话,佛界可能多了一个高僧,但少了一个“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理学集大成者。
李侗不仅使朱熹从禅佛中惊醒,抛弃禅学开始归本儒学,还指示了他正确的用功方向,教导朱熹去圣贤经书中求义,在日用处用工。他教导朱熹,“道亦无幽妙,只在日用间着实做工夫处理会”,“惟于日用处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几渐可合为己物,不然,只是说也”。道体现于日用常行中,只有在日用间做功夫,才能理会寻找到道理,其方法途径就是读圣贤之书,看圣贤言语,在经书中求得答案,这就扭转了朱熹的用功方向。朱熹自己也说:“及见李先生后,方知得是恁地下功夫。”在李侗的点拨下,朱熹由沉溺于佛经转入读儒家经典。李侗教诲的“一则曰日用处用功,二则曰去圣经中求义。两番教言均注重人生之教,这对扭转朱熹的研究方向起很大作用”。
在李侗的教导下,朱熹最终发现了释氏之说漏洞百出:“李先生人简重,却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熹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开始转向儒学,寻求义理,从而使他的学问方向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绍兴二十六年(1156)七月,朱熹同安主簿任满后,到泉州等候批书,度过了同安官余的半年。“同安官余”的读经反思和“杜鹃夜悟”的反省,使他对李侗的教诲深信不疑,更加坚定了他从教李侗的决心。赵师夏《跋延平答问》:“余之始学,亦务为笼侗宏阔之言,好同而恶异,喜大而耻于小,于延平之言,则以为何多事若是,心疑而不服。同安官余,反复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后来朱熹所作《困学》诗:“旧喜安心若觅心,捐书绝学费追求。困衡此日安无地,始觉从前枉寸阴。”表述了对这段师从道谦学禅,枉度光阴的后悔。
“理一分殊”和“主静”是李侗学问的主旨,也是“道南一脉”推崇和关注的核心命题。李侗的“理一分殊”观点对朱熹产生重大影响,使朱熹得道南真传,成为朱子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绍兴二十八年(1158)正月,朱熹与李侗再次相见,李侗主要给他传授“理一分殊”的学问。其意是宇宙间有一个最高的理,是总的本源,这就是“理一”;万事万物虽千差万别,亦各有各自的理,但这只是最高理的体现和反映,这就是“分殊”,以此来解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李侗说:“事有小大,理却无小大。”“事有小大”指分殊,“理无小大”指理一。“理一分殊”是李侗学问的核心,也是区分儒学与异端的标志。他教导朱熹:“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要求朱熹领会和掌握“理一分殊”的真谛。
朱熹接受了李侗就分殊上体认理一,即事穷理,循序渐进的思想。“理一分殊思想的确立使朱熹从朦胧的觉醒转向自觉的排佛。”
李侗又标举“主静”,主张静中体认,求中未发,把静中体认称为“于静处下工夫”。他认为“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若见虽一毫私欲之发,亦退听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几渐明,讲学始有力耳。”因为儒家之理是天理,而心具众理,要体认天理就要以静摄心,方法就是静坐、默坐澄心。
朱熹对李侗以主静为修身之方,以致知为进学之要,终日静坐以求未发气象的功夫进路并不十分认同。朱熹说:“余早从延平李先生学,受中庸之书,求喜怒哀乐未发之中,未达而先生没。”直到李侗去世都是没有完全参透掌握,最终以“居敬存养”,代替了李侗的主静工夫。
四、弃文崇道:李侗使朱熹确立以唱道为己任的理想
绍兴三十年(1160)十月,朱熹又到延平与李侗相见。这次延平之会,使朱熹思想发生另一转变就是意识到作文害道,使他终于放弃原来想当诗人和文章家的想法,表示“顷以多言害道,绝不作诗”,决定弃文崇道,终身以“唱(倡)道”为己任。
他给表弟程洵信中更明白表示说:“往年误欲作文,近年颇觉非力所及,遂已罢去,不复留情其间,颇觉省事。”这种弃文崇道立场转变后,“他同程洵展开了崇道学之士而贬辞章之士、崇程学而贬苏学、崇儒学而贬诗文的激烈论辨”开始了自己“穷理知道”新历程。
不仅确立以穷理知道为己任的理想,更要付之于践履。虽然李侗屏居山中,终生不仕,但教导朱熹要知行并举,穷理应事兼行,做到“应事洒落”。在李侗的鼓励下,朱熹开始关注朝廷政局,关注社会民生,从书斋中走了出来,直面社会现实。“由恬淡退守、洁身自好到以下民为忧、以未行为恐的变化。”在李侗的督促鼓励下,朱熹开始上封事和入都奏事。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八月,宋高宗禅位给孝宗后,朱熹应诏上了平生第一篇封事——《壬午封事》:提出了“讲学明理、定计恢复、任贤修政”的三大方略:一是“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帝王要熟讲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的大学之道,反佛崇儒,才能大本正而天下治。二是“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做到修政事,攘夷狄;三是“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要正朝廷、立纪纲、励风俗,选守令,才能安定天下百姓。
朱熹这篇封事,事先和李侗进行了讨论,得到了李侗的悉心指点,“封事熟读数过,立意甚佳。今日所以不振,立志不定,事功不成者,正坐此以和议为名尔。书中论之甚善……要之,断然不可和,自整顿纲纪,以大义断之,以示天下向背,立为国是可尔,此处更可引此。又许便宜从事处,更下数语以晓之,如何?……亦可早发去为佳”。封事也正是李侗穷理洒然和应事洒然思想的反映。
李侗还鼓励朱熹入都奏事。由于汪应辰等人的举荐,隆兴元年(1163)八月,朱熹再次入都,第一次到垂拱殿面对新君孝宗奏事。对此次面君登对,李侗很是关切,反复教导朱熹:要从反佛、反和、反近习三条入手。朱熹把李侗的意见都写入了奏事三札中,即《癸未奏札》:一是极论《大学》之道和帝王之学;二是论复仇之义;三是论内修政事之要。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朱熹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孝宗的青睐,被除武学博士,待次四年,变相的把朱熹弃于家中而不用。虽然朱熹“得君行道”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但入都后得以与众多道学士大夫的相识,提升了朱熹的知名度和地位,朱熹因此成为道学群体的一员,并且卷进了隆兴北伐与和议的政治漩涡。
朱熹问学李侗,达十年之久。“朱子对李侗的师从是后生对当时大儒的敬仰与赞许。”师事李侗,从“存养”到“致知”到“应事”等方面都得到其教诲,对朱熹思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在李侗的指点下,朱熹从虔诚出入佛老的泥潭中清醒过来,认识到了释老的错误与危害。正如《朱子年谱》记载:“朱熹之学,初无常师,出入于经传,或泛滥于释老。自谓见李先生后,为学始就平实,乃知向日从事释老之说皆非。……”从而弃禅归儒,转到儒学的路径上来,改变了他一生的思想道路。“从学李侗,使朱熹完全放弃了禅学迂回,直接回到儒家经典中找寻内圣的门径。更重要的是,李侗不只将朱熹引回儒学,而且将朱熹引入了二程道学传统中。”
此外,李侗还指明了朱熹去圣贤经书中求义,在日用处用工正确方向;传授了“理一分殊”和主静的修养方法,且使朱熹弃文崇道,确立以唱道为己任的道学理想。使朱熹成为二程的四传弟子,继承道学正统。可以说“李侗是使朱熹真正踏入道学之门的第一人”。
朱熹对恩师也十分尊敬。李侗去世后,隆兴二年(1164)正月,朱熹到延平哭奠李侗,亲自撰写了《祭李延平先生文》和《延平先生李公行状》:高度评价了恩师李侗的人品:“先生姿禀劲特,气节豪迈,而充养完粹,无复圭角,精纯之气,达于面目。”在《祭文》中感谢李侗十年来的教诲是义重恩深:“从游十年,诱掖谆至。春山朝荣,秋堂夜空。即事即理,无幽不穷。……熹等久依教育,义重恩深。”汪应辰在所作《李延平先生墓志铭》中也说朱熹受教李侗久益不懈,“其事先生,久益不懈。以为每一见,则所闻必益超绝”。后来朱熹在创办沧州精舍时,将恩师李侗从祀孔子,表达了对李侗的尊敬和推崇。
附注
邹挺超:《朱熹的交往关系研究》,厦门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
束景南:《朱子大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朱熹:《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〇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束景南:《朱子大传》,第108页。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〇四。
朱熹:《朱熹集》卷三〇。
朱熹:《朱熹集》卷三七。
李侗:《李延平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页。
黎靖德:《朱子语类》,第2568页。
束景南:《朱子大传》,第166页。
陈遵沂:《李侗对朱熹思想的影响》,《理论学习月刊》1989年第6期,第61~62页。
李侗:《李延平集》,第57页。
李侗:《李延平集》,第29页。
胡泉雨:《论朱熹与李侗的师生关系》,《黄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12~15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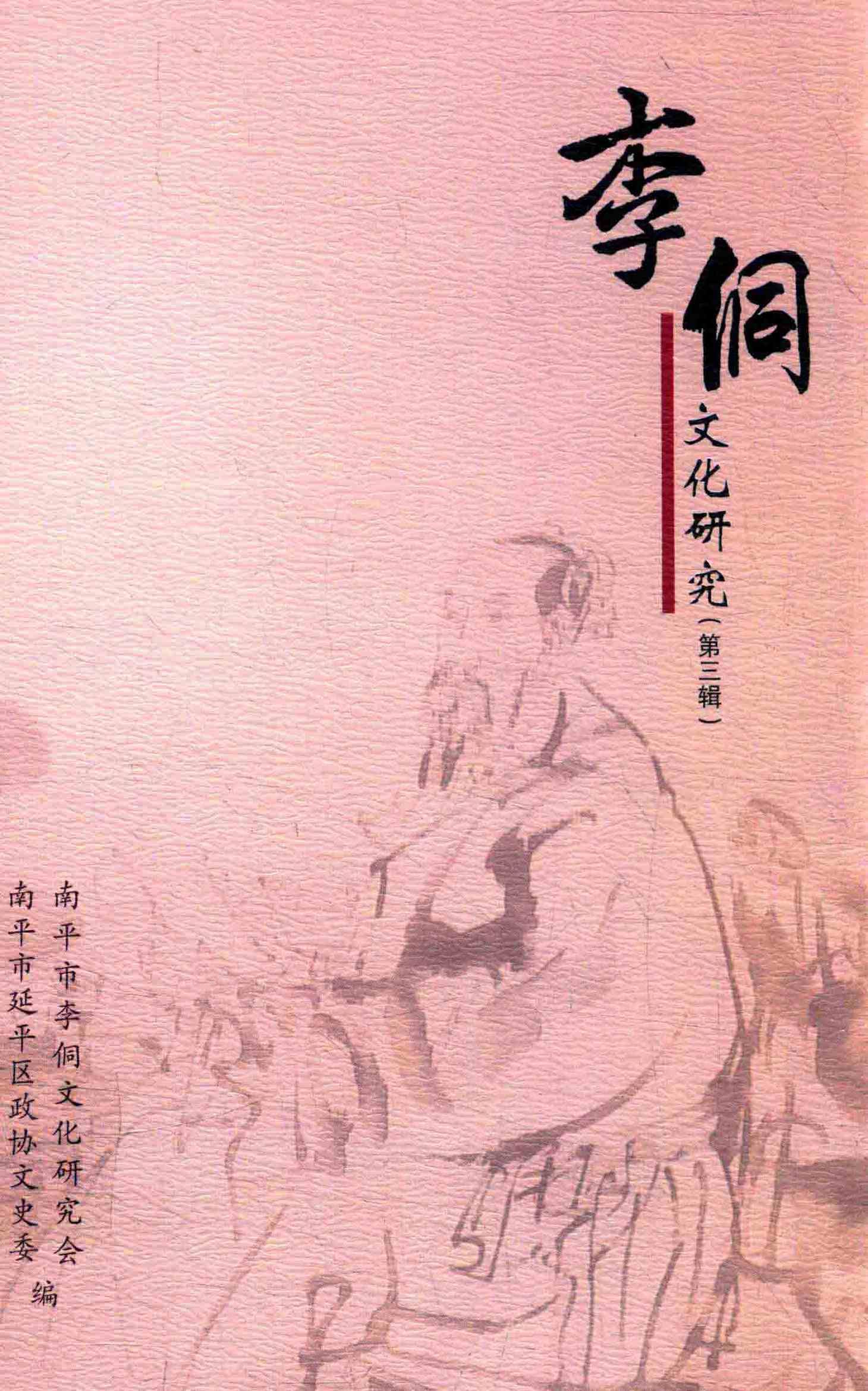
《李侗文化研究 (第三辑)》
这本《李侗文化研究(第三辑)》,较为系统地展示了理学先贤李侗先生的理学造诣,让留存于故纸堆中的历史文化遗存,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文化产品,从而使它释放岀理学的巨大能量和深远影响。
阅读
相关人物
冯会明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