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榦
| 内容出处: | 《朱子文化大典 下册》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10001004 |
| 颗粒名称: | (一)黄榦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14 |
| 页码: | 15-28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黄榦对朱子思想的形态化及其向生活的落实,在形态化方面,杨简对陆学也作了类似的工作,即在本心自觉后,于践履上求落实,使之能够得到忠实的贯彻,但这样的工作充其量只是将陆学由思想向形态化的文化作了转化。 |
| 关键词: | 黄榦 朱子思想 研究 |
内容
实际上,在形态化方面,杨简对陆学也作了类似的工作,即在本心自觉后,于践履上求落实,使之能够得到忠实的贯彻,但这样的工作充其量只是将陆学由思想向形态化的文化作了转化。当然,陆学的精神诉求是在践履,但当陆学崛起并与朱学相论辩时,它曾是一种极富活力的思想,而在杨简这里,思想的活力已经消退,他的整个努力趋向,是将陆学由思想向形态化的文化进行转化。这点也可以由杨简的著述目录上得到印证。《慈湖先生行状》云:其已成编者,《甲稿》《乙稿》,又《冠记》《昏记》《丧礼家记》《家祭记》《释菜礼记》《石鱼家记》皆成书。①可知释礼方面的著述是杨简的重要工作内容。这多少可以说明,杨简在申明陆学之本心自觉后,是希望通过社会生活中的礼仪建设来落实儒学的价值体系的。杨简的这个倾向,与朱学后人,尤其是黄榦对朱学的推进,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这也意味着,在后朱子时代,无论陆学,还是朱学,追求思想向生活落实,从而向形态化的文化转型已是一个基本趋势。端平三年(1236),朱学已为官方意识形态接受,黄榦也已去世十五年,弟子吴昌裔在为黄榦的请谥文中作有这样一段评价:世之学问,溺志卑近者,既鸯于方策而不能存养本原;驰心高妙者,又略于章句而不务研索义理。惟文公(即朱子——编者注)发明致知主敬之义,每使学者互进功程,其说固已内外兼该。而先生(即黄榦——编者注)体帖居敬集义之旨,专欲教人点检身心,其功尤为近里亲切。是则文公有功于程氏,而先生有助于师门,千载师友之盛,真所谓颜、曾之于洙、泗矣。①这段评价既标示了黄榦在朱子弟子中的地位,也点划出黄榦在朱子逝世后的工作。
1.对朱子思想的文本建设在朱子的众多弟子中,黄榦无疑是最重要的。②这不仅是因为朱子将女儿嫁给了他,晚年更具象征性地将“深衣及平生所著书授之”,以及临终有“勉学及修正遗书”的遗言,③为朱子生前所倚重,而且更因为是他在朱子逝世后,为朱学的形态化建设以及传播作出了重要的努力。
黄榦(1152-1221),字直卿,后人称勉斋先生。闽县(今福建省福州市)人,父亲是监察御史。宁宗朝恩补将仕郎,主要是在地方上任职,历知汉阳军、安庆府。奉祠致仕,归里讲学。一生的主要精力是在朱子思想的建设与传播上。
黄榦自淳熙三年(1176)见朱子于五夫后,“学精思苦,久而益笃”④,成为朱子最称心如意的弟子。朱子此时的思想已经确立,许多著作也已成形,但朱子的主要著作,即对“四书”“五经”的诠释,是终其一生的工作。黄榦师事朱子时,朱子正在以前所完成的《论孟精义》的基础上撰写《论孟集注》《或问》与《周易本义》等重要的著作,黄榦与其他主要弟子,如蔡元定,都直接参加了讨论与撰写工作。其中,黄榦主要是参与《论孟》方面的工作。朱子《答吕伯恭》云:此两月间,只看得两篇《论语》,亦是黄直卿先为看过,参考同异了,方为折中,尚且如此。渠昨日又闻兄丧归去,此事益难就绪矣。① 可见黄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朱子甚为倚重。
朱子在建构思想的过程中,文本的建设是始终贯彻、相辅相成的工作。 朱子对文本的建设是从北宋诸儒入手,以清理南宋前期洛学传衍中所表现出的思想混乱;进而便进入“四书”的诠释;最后是以“四书”为阶梯,进入 “五经二经的诠释虽然仍是朱子的最终目标,但“四书”显然被强烈地凸现出来。
黄榦对朱子的思想显然具有清晰而准确的理解,因此当他晚年时,便希望将朱子关于“四书”的诠释,作一个系统而有次序的编次,并进一步加以解释,使之呈以更完备且具普及性的文本。
《黄谱》嘉定十二年(1219)条记“始通释文公《论语》二所附门人陈宓《题叙通释》曰:先生合文公《集注》《集义》《或问》三书而通释之。盖《集注》之辞简而严,学者未能遽晓。于是作《或问》一书,设为问答,以尽其详,且明去取诸家之意。先生恐学者不暇旁究,故直取疏解《集注》之辞而列之于后,以便观览。然《集注》《或问》间有去取之不同、发挥之未尽,先生追忆向日亲炙之语,附以己意,名曰《通释》,于是始无遗憾矣。②黄榦撰写《通释》时,虽然是有所发挥,附以己意,但他完全是依照着朱子的注释本来谈的,因此后人完全可将《通释》与《集注》《集义》《或问》进行对比。这种做法,足以使朱子的思想在得到普及的同时,仍最大程度上忠实地保持其思想本身。
实际上按照黄榦的原意,对朱子关于“四书”的整个思想进行整理时,“欲合《集注》《集义》《或问》《语录》四记而通释之,其后《语录》未果入也”①。黄榦晚年时,已看到朱子《语录》开始流行的情况。“开禁”以后,朱子思想得到官方承认而渐成时尚,这些《语录》纷纷现世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这些《语录》为朱子各时期的不同身份的弟子所记,对朱子思想的反映无疑是混乱的,其中甚至不免有将朱子思想过分主观化的解读,或者信息严重漏损,正如南宋初期二程《语录》的情况相同。黄榦在为当时一刊刻的朱子《语录》作跋时即指出:晦庵朱先生所与门人问答,门人退而私窃记之。先生殁,其书始出。记录之语未必尽得其本旨,而更相传写,又多失其本真,甚或辄自删改,杂乱讹舛,几不可读。②因此,黄榦于晚年执意做《通释》这样的文本建设,显然与当年朱子整理二程的著作,具有相似的性质,是希望将思想呈以形态化以便于传播,同时防止误读。
虽然黄榦只完成了《论语通释》,没有来得及将朱子关于“四书”的诠释与论说加以整理,但正如吴昌裔的请谥文中所说,“《语》有通释,《大学》有经解,《中庸》《孟子》有讲义,尤足以发明师传未发之言”③。
在朱学的文本建设上,黄榦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对《礼书》的诠释。朱子固然是推崇“四书”,但绝非是要用“四书”来取代“五经”。后来因朱学的意识形态化,“四书”与科举的联姻,使得“四书”有取代“五经”的历史现象,但这并不代表朱子对儒家学术典籍层次的认识与确认。朱子自始至终是将“四书”作为“五经”之阶梯来看待的。因此为“五经”作诠释,是朱子建构思想所必须做的事情。“朱子治经,《易》《诗》皆有成书。晚年刻意修《礼书》,以《书传》嘱付蔡沈。独于《春秋》未有撰述,并戒学者勿治。”④朱子对《礼》的诠释,最后之成书是《仪礼经传通解》。此书不仅朱子生前未完成,而且黄榦生前也未完成,最终成书于杨复,但诚如四库馆臣所言,“虽编纂不出一手,而端绪相因,规模不异”①。这中间,黄榦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黄谱》庆元二年(1196)条载:初,文公虽以《丧》《祭》二礼分畀先生,其实全帙自《冠》《昏》《家》《乡》《邦国》《王朝》等类,皆与先生平章之……明年三月乙亥朔,竹林精舍编次《仪礼》集传、集注书成。条理经传,写成定本,文公当之;而分经类传,则归其功于先生焉。
此说明,朱子生前对《礼》的诠释,除了专门分《丧》《祭》二门给黄榦外,整个工作也是让黄榦作重要助手的。《黄谱》引多条资料说明了这点。
黄榦致仕以后,即开始对《丧礼》稿本精修。至嘉定十三年(1220)夏完成。②《祭礼》部分虽然没有脱稿,但黄榦自称“某于《祭礼》用力甚久,规模已定。每取其书翻阅而推明之,间一二条尚欠修正。”③张虑于嘉定十五年(1222)刊刻《仪礼经传通解》时所撰序文,也说明《祭礼》基本上是根据黄榦稿本整理而成的。
《仪礼经传通解》的完成,对于朱学而言,决不仅有文本建设的意义,而是更具实践的意义。钱穆指出:朱子治经,最知重考据,于礼最多涉及。清儒考礼,其所用心,仅在故纸堆中。朱子治礼,则以社会风教实际应用为主。此不同也。④这是非常重要而正确的论断。宋代儒家在追求实现自己的经世致用的目标上,至朱子始高度自觉与始终如一地将政治的切入改为社会的切入,通过社会的改造来逐步影响于改造政治。这个社会的改造,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愿望,而是可落实的践履。这个践履的起点当然是在个人的修身上,这属于心性之学的范畴。而由个人的独自修身进入社会关系,固然心性之学仍是实践主体的内在依据,但实践主体终需要有可遵循的外在规范,这个规范即是礼。朱子诠释《仪礼》正着眼于为社会提供这样的规范。他循着实践主体的践履所涉社群范围的外展,将《仪礼》按《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依次展开。正是因为朱子诠释《仪礼》具有这样的实践性,所以他并不是泥古不化,而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作了相应的调整,即四库馆臣所谓“所载《仪礼》诸篇,咸非旧次,亦颇有所厘析”①。而如上所言,朱子的这个思想,正是由黄榦来加以落实的。
尤为重要的是,在家庭与一般社群的仪式化活动中,最显著的是丧、祭二礼。而在南宋的丧、祭二礼中,主要已由佛教仪式来主导,因此,诠释《仪礼》,最具实践意义的就是《丧》《祭》。杨信斋说:《礼》莫重于《丧》《祭》,文公以二书属之先生,其责盖不轻也。先生于是书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诸儒同异之论,剖击世俗蠹坏人心之邪说,以示天下后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远也。先生之心,忧天下后世为心,夫岂以著述为一己之书哉?②这正指出了黄榦在诠释《仪礼》方面对朱学的重要性。
2.对朱子思想的生活仪式化推进黄榦并不只是满足于在书本上作仪式的游戏,而是致力于将知识的考古学转化成实践的考古学,通过生活中的现实操作来推广朱学所确认的礼仪。《黄谱》嘉定十二年(1219)条“门人张元简以古昏礼归其女弟,请于先生。为之正其仪法行之。”这是师门中的实践。“乡人有欲行古婚者,独以奠雁恐为人骇笑,来质于公,公曰:‘今人家子弟斗鸡走马,不以为怪,而巍冠博带以行礼,顾虑人之非笑?'其人遂决意行之。”这是向社群作推广。《黄谱》中的各条记载,足以说明黄榦这样的礼仪操演与推广是经常性的、全方位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学生才能够掌握得很好,在他去世后的丧葬中,“门人弟子执绑者二百余人,皆衰经菅屦,引柩三十余里至山间,丧仪如礼。乡人叹息,以为前此未之见”①。
如果说文本建设作用的发挥需要长时段来呈现,那么仪礼推广的影响足以迅速地产生教化效用。所谓“乡人叹息,以为前此未之见”,正意味着百姓由现场的感触而生发出对规范化仪礼的欣赏,而有身份、有钱的人也正可以借此来证明自己的地位或附庸风雅,尤其是当朱学转而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以后。但是,当一种思想呈现为一种形式化了的仪式以后,虽然足以使浸淫于仪式的人们不自觉地接受并认同仪式所传递出的价值信息,但同时也存在着价值因仪式而消解,从而使形式成为无意义的形式的可能。后人在评论黄榦时,虽然真实地指出他是一位以经世济民为职志的儒家,②以证明“洛、闽设教之初,尚具有实际,不徒以峨冠博带刻画圣贤”,③但这种世相的形成,并不是自然的过程,而正是朱子所希望、黄榦所努力的结果。
此外,通过形式化的仪礼来实现儒学教化的目的,这个过程是一个以牺牲实践主体的自我意识的集体无意识的培养过程。④尽管无论是孔、孟,还是朱子、黄榦,在理论上都高度强调实践主体的自我意识在仪式化活动中的觉醒,但对于社群中的普通人来说,这个要求显然是过高的。而且事实上,朱学刻意于礼制的社会运用所着眼的,与其说是培养具有自觉质疑特性的自我意识,毋宁说是培养呈现在社会习俗中的集体无意识。这便意味着,黄榦在致力于朱学由思想向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思想也因此失落了它的活力。⑤其实,不仅仪礼对于朱学具有这样的作用,标准化的文本对思想的形态化建设固然有益,但对思想的活力同样具有无形的桎梏。
3.对朱门的组织化推进作为朱子逝世以后的学派掌门人,黄榦推进师门的努力,在组织上也作有巨大的贡献。朱子生前对于书院建设,以及他自己在家乡的讲学,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并显然是努力构筑一定的物质保证与制度化建设。从“庆元党禁”中对他的攻击看,朱子在讲学的组织上也是作有精心安排的。黄榦在朱子的基础上,显然是更推进了一步,《黄谱》嘉定十年(1217)条载:春,朋旧生徒毕集于法云寓居,先生为立《同志规约》以示学者。
《同志规约》以每日各读一经一子一史,而以《论语》《周易》《左传》为之首。日记所读多寡,所疑事目,并疏于簿。在郡者月一集,五十里外者季一集,百里外者岁一集。每集告以所记文字,至与师友讲明而问难之。大要欲明义利之分,谨言行之要,以共保先师遗训之意。
这个《同志规约》所反映出的信息,说明不仅是黄榦所创设,为朱子生前所没有,而且说明黄榦已完全是在组织化建设的层面上来开展学派活动的。如果联系《黄谱》所记黄榦的学生们在他卒后“捐金”购地为其立祠,则可以推测,黄榦生前的组织化建设极可能包括了经济上的内容。可以肯定的是,其整个组织化建设是富有成效的。
4.对朱子思想的内倾化趋向总而言之,在南宋文化建设可虑及的层面上,从文本、仪礼到组织建设,黄榦都做了非常踏实的工作,使朱学成功地由思想向文化转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黄榦在思想建设上没有自己的阐述。黄榦在努力推进思想向文化转型的同时,对朱子思想也同样是作了进一步的展开。
关于黄榦对朱子思想的推进,上引吴昌裔所言,“惟文公发明致知主敬之义,每使学者互进功程,其说固已内外兼该。而先生体帖居敬集义之旨,专欲教人点检身心,其功尤为近里亲切,实是一个最恰当的概括。如果说黄榦在使朱学由思想向文化发生转型方面的努力,主要是体现在形态化的建设上,那么其在对朱子思想所作的进一步诠释上,则主要是向“心”里作内省性的工夫。
作为朱子最重要的弟子,黄榦对于朱、陆之争当然是非常清楚的,其将朱子思想诠释成内省性的心上工夫,表面上似有违背师说的嫌疑,但实质上黄榦是作有前提性的设定的。这个设定就是贯彻朱子“理一分殊”的本体论。黄榦说:道之在天下,一体一用而已。体则一本,用则万殊。一本者,天命之性;万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语大莫能载;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语小莫能破。语大莫能载,是万物统体一太极也;语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极也。万物统体一太极,此天下无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极,此性无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自性观之,万物只是一样;自道观之,一物各是一样。惟其只是一样,故但存此心,而万事万物之理,无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样,故须穷理致知,而万事万物之理,方始贯通。以此推之,圣贤言语,更相发明,只是一义,岂不自博而反约哉?①按照黄榦的阐释,如果在抽象的意义上“但存此心”,固然可以在知性层面上对事物之理有一个清晰而完备的认知,但这还并不足以进入践履的层面,知性所把握的“理”与个人生命仍是相分离的。这其实便是后来王阳明力主“知行合一”的关键。为什么知性层面上的义理认知不足以保证践履层面上的生命展开呢?黄榦有一段自我剖析的话,颇值玩味,他说:榦老矣,未能忘禄。非禄之不可忘也,不仰禄则又须别求,所以糊其口而劳心害义,反甚于仰禄。以是东西南北,惟命是从何去就出处之敢言,何功名事业之敢望!特汩没世俗,学问尽废,大为师门之罪人,不敢自文也。②黄榦当然不是“汩没世俗,学问尽废,大为师门之罪人”之人,他所以如此自责,是想说明,在现实的层面上,人生实受制于许多东西,轻者是生存,重者是名利,极不自由。要能完全地按照知性层面上所认知的义理来践履,必须从制约人生的这些束缚中挣脱出来才可以。但是这个挣脱,又并不是真的彻底地将生命加以封闭起来,否则即如黄榦所言,“害义反甚于仰禄”,陈义过高,流于自欺欺人,直使道德蜕为虚伪。因此,仰禄而担道,生命在世俗的展开中来求得道德精神的成就,这中间便有一个现实性的把握问题,即必须使生命融入世俗的生活,同时又不因为世俗的生活而使道德精神汩没于其中。只是,生命在世俗中的展开,所面对的境遇时时不同,“物各是一样”,如果徒恃知性层面对义理的认知,这个认知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把握,只有“穷理致知,使知性之所认知的“理一”,见证于生命展开中的“分殊”,始足以真正使“理”得以贯通,生命始成其为“活泼泼”的存在。因此“自博而反约”是一个不可跳过的环节,“道问学”是“尊德性”不可舍弃的基础。可以说,黄榦对师说是予以坚定维护的。
但是,尽管黄榦强调“主敬、致知两事,相为经纬”①,但不可否认,黄榦在对朱子思想的进一步推进上,是以“主敬”,即内省性的心上工夫为向度的,即所谓“持守之方,无出主敬”②。黄榦说: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须默认实体,方见端的。不然,则只是讲说文字,终日说说,而真实体段,无不曾识。故其说易差,而其见不实,动静表里,有未能合一,则虽曰为善,而卒不免于自欺也。莫若一切将就自身上体著,许多义理名字就自身上见得是如何,则统之有宗,不至于支离外驰也。③所言与陆九渊批评朱子,实是很相似了。黄榦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中,通过对朱子所确认的儒家道统的诠释,最后撮其要旨而申明为:“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④尽管仍然是恪守着朱子的思想,但其内倾化是显见的。
黄榦的这种思想取向,是由朱子对儒家精神的确认所导致的。当朱子将儒家精神确认为道德精神的认知与培养以后,除了使同道中人认同或接受他的确认以外,最重要的是使整个社会按照他的确认来生活。其中,文本、仪式、组织等形态化系统的建设使整体意义上的社群在这个系统中建立起集体无意识,而对于个体意义上的个人道德践履来说,最终只能仰赖于道德主体自我精神上的自觉与自律。其中,自觉并不难,至少在表面上,在认知的层面上,每个人都可以说懂得义理;但自律决不容易。因此黄榦将内省性的心上见得分明,加以着意的标示,这确是对朱子思想应然而必然的理论归结。黄榦讲得很清楚,他说:惟于世间利害得丧,及一切好乐,见得分明,则此心亦自然不为之动,而所为持守者始易为力。若利欲为此心之主,则虽是强加控制,此心随所动而发,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强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压草,石去而草复生矣。此不可不察也。①这在形式上,至少是在话语上,真仿佛是将朱子思想最终定位为“心学气钱穆对朱子思想曾有一个很精辟的论断:后人言程、朱主“性即理”,陆、王主“心即理”,因分别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此一分别亦非不是,然最能发挥心与理之异同分合及其相互间之密切关系者盖莫如朱子。故纵谓朱子之学彻头彻尾乃是一项圆密宏大之心学,亦无不可。②故可知黄榦的努力是深得朱子思想之精髓的。只是思想一旦被推进到个体意识的自我整肃上,正如思想的形态化促成其向文化转型一样,思想便基本上销熄了,践履成为根本的,乃至唯一的事情,正如后来明初的薛瑄所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③这对朱子思想来说,可谓是喜;但对于儒学思想来说,则也是悲。
还需要指出的是,黄榦对朱子思想的推进是对的,但是从思想的形式上看,黄榦对朱子思想的推进实也呈现出与陆九渊思想相一致的特征。这在黄榦固然非主观所愿,更谈不上是对陆学的引入,但是在客观现象上,则意味着从最忠于朱子思想的学生开始,朱、陆思想调和在形式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实际上,由下文的讨论还可以看到,朱学于南宋最后的发展同样呈现出与浙学(以史学为形式特征)相调和的现象。因此不妨说,在南宋晚期儒学的最后发展阶段,一方面是以朱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向文化转型,在这种转型中,思想获得了落实,实现其社会功能,同时也失去了活力;另一方面是曾与朱学相论争的思想,呈现出与朱学的合流,正是这种合流,使得这些不同于朱学的思想所表达的对儒家精神的理解,得以潜伏存活,并在后来适应的际遇中重新发出自己的声音,使形态化了的朱学重新被解构。
5.对朱子道统地位的论定黄榦对朱子思想进行推进的重要一点,在于其道统论。黄榦在其《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中,对儒家道统总结道,“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二宋代理学亦讲求内圣外王,而以内圣为先,黄榦的这一总结,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的。“居敬”“穷理”“克己”“存诚”就是治学修身,达到内圣的具体的修习方法,而这也正是黄榦思想内倾化的又一体现。
黄榦的道统论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儒家之道的内容,就是对“人心”与“道心”关系的处理方法,即如何通过内在的修养与外在的建构,使“人心”合乎“道心”,使人的行为合乎理的规范。
其二,儒家道统传承的谱系是:尧—舜一禹一成汤一文王一武王、周公—孔子一颜回、曾子一子思一孟子一周敦颐一二程一朱子。
其三,儒家道统的传承有三方面特点:首先是继承性。即儒家之道的传承有一个不变的内核,这个内核就是使“人心”符合于“道心”的方法和规范。其次是发展性。继承道统的人物都在坚持道统思想内核的基础上,对儒家之道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和建构,使之更加具体和完善。再次是儒家之道的发展传承有一个内在的方向性。尧、舜、禹确立了儒家之道的原则性,即“人心”应该符合并遵从于“道心”的原则;成汤至周公,是以外在原则的建构为主要内容,如“礼”与“义”的规范的制定;孔子而后,则将重心转向内在修养方面,“克己复礼”“居敬穷理”等修养原则凸显为儒家之道的主要内容。黄榦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张子继之,周程张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继之。”①就是对这一内在方向的具体阐释。
统观黄榦的《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可以发现其字里行间充满着朱子的思想,换言之,黄榦是在用朱学的概念建构和诠释儒家道统,其目的也正是确立朱学的正统地位。
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末节,黄榦说:先师文公之学,见之“四书”,而其要则尤以《大学》为入道之序。
盖持敬也,诚意正心,修身而见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此又先师之得其统于二程者也。
对朱子道统地位的论定,可以说是黄榦道统论的主要目的。黄榦将朱子列入道统,并将其视为集儒家思想之大成者,推其原因,可归为以下几点。
其一,朱子本人的正统观念浓厚,其在《中庸章句序》中已经明显显现出将自己列入道统的意图,只是有所不便。而黄榦作为朱子首徒,深受师恩,完成先师未竟心愿实属当仁不让。
其二,“庆元党禁”时,朱子之学被斥为“伪学”,朱子本人也被视为“伪学魁首”,这对朱子的声誉以及朱学的名望造成了恶劣影响。“党禁”之后,朝廷虽然为朱子平反,但在黄榦看来,这还远远不够。黄榦将朱子列入道统,重塑朱子地位,也是出于为先师平反的考量。
其三,朱子去世之后,朱学仍受到来自心学、浙学等学派的攻击,维护师门的重任落在以黄榦为首的朱门弟子身上,黄榦将朱子列入儒家正统,自然就将他派归为支裔或“伪学”,这正是黄榦对攻击者作出的有力回应。
其四,朱子去世后,朱子之门内部也出现了学术分化,弟子各执一支以立言,这于朱学传承极为不利。黄榦自认深得朱子之义,因此将朱子列入道统,正是想借先师余光,以统一师门思想。
其五,黄榦将朱子列入道统,也是因为在他看来,朱子的学养和贡献完全具备这样的资格。黄榦说:“(文公)于《大学》《中庸》,则补其阙遗,另其方次,纲领条目,粲然复明。于《论语》《孟子》,则深原当时答问之意,使读而味之者,如亲见圣贤而面命之。于《易》与《诗》,则求其本义,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遗意于数千载之上。凡数经者,见之传注,其关于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之门、造道之阈者,既已极深研几、探赜索隐,发其旨趣而无所遗矣。”①“秦汉以来,斯道晦蚀,天理不明,人心不正。事物当然之则,昧没而不彰;方策不刊之训,残阙而将堕。周程张子既推明其大端,而传讹袭舛,浸失本真。迨我文公禀高明之资,厉强毅之志,潜心密察,笃信力行,精粗不遗,毫厘必辨,至其德盛仁熟,理明义精,历代相传之道,粲然昭著,……则公之生于世,有功于斯道大矣。”②“(文公)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③黄榦认为,朱子继承先贤道统,集儒家圣道之大成,德言双立,体用双修,实在是达到了儒家道统的顶峰。
黄榦对朱子道统地位的论证,将朱学的正统地位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对于进一步扩大朱学影响,光大朱学之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对朱子思想的文本建设在朱子的众多弟子中,黄榦无疑是最重要的。②这不仅是因为朱子将女儿嫁给了他,晚年更具象征性地将“深衣及平生所著书授之”,以及临终有“勉学及修正遗书”的遗言,③为朱子生前所倚重,而且更因为是他在朱子逝世后,为朱学的形态化建设以及传播作出了重要的努力。
黄榦(1152-1221),字直卿,后人称勉斋先生。闽县(今福建省福州市)人,父亲是监察御史。宁宗朝恩补将仕郎,主要是在地方上任职,历知汉阳军、安庆府。奉祠致仕,归里讲学。一生的主要精力是在朱子思想的建设与传播上。
黄榦自淳熙三年(1176)见朱子于五夫后,“学精思苦,久而益笃”④,成为朱子最称心如意的弟子。朱子此时的思想已经确立,许多著作也已成形,但朱子的主要著作,即对“四书”“五经”的诠释,是终其一生的工作。黄榦师事朱子时,朱子正在以前所完成的《论孟精义》的基础上撰写《论孟集注》《或问》与《周易本义》等重要的著作,黄榦与其他主要弟子,如蔡元定,都直接参加了讨论与撰写工作。其中,黄榦主要是参与《论孟》方面的工作。朱子《答吕伯恭》云:此两月间,只看得两篇《论语》,亦是黄直卿先为看过,参考同异了,方为折中,尚且如此。渠昨日又闻兄丧归去,此事益难就绪矣。① 可见黄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朱子甚为倚重。
朱子在建构思想的过程中,文本的建设是始终贯彻、相辅相成的工作。 朱子对文本的建设是从北宋诸儒入手,以清理南宋前期洛学传衍中所表现出的思想混乱;进而便进入“四书”的诠释;最后是以“四书”为阶梯,进入 “五经二经的诠释虽然仍是朱子的最终目标,但“四书”显然被强烈地凸现出来。
黄榦对朱子的思想显然具有清晰而准确的理解,因此当他晚年时,便希望将朱子关于“四书”的诠释,作一个系统而有次序的编次,并进一步加以解释,使之呈以更完备且具普及性的文本。
《黄谱》嘉定十二年(1219)条记“始通释文公《论语》二所附门人陈宓《题叙通释》曰:先生合文公《集注》《集义》《或问》三书而通释之。盖《集注》之辞简而严,学者未能遽晓。于是作《或问》一书,设为问答,以尽其详,且明去取诸家之意。先生恐学者不暇旁究,故直取疏解《集注》之辞而列之于后,以便观览。然《集注》《或问》间有去取之不同、发挥之未尽,先生追忆向日亲炙之语,附以己意,名曰《通释》,于是始无遗憾矣。②黄榦撰写《通释》时,虽然是有所发挥,附以己意,但他完全是依照着朱子的注释本来谈的,因此后人完全可将《通释》与《集注》《集义》《或问》进行对比。这种做法,足以使朱子的思想在得到普及的同时,仍最大程度上忠实地保持其思想本身。
实际上按照黄榦的原意,对朱子关于“四书”的整个思想进行整理时,“欲合《集注》《集义》《或问》《语录》四记而通释之,其后《语录》未果入也”①。黄榦晚年时,已看到朱子《语录》开始流行的情况。“开禁”以后,朱子思想得到官方承认而渐成时尚,这些《语录》纷纷现世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是这些《语录》为朱子各时期的不同身份的弟子所记,对朱子思想的反映无疑是混乱的,其中甚至不免有将朱子思想过分主观化的解读,或者信息严重漏损,正如南宋初期二程《语录》的情况相同。黄榦在为当时一刊刻的朱子《语录》作跋时即指出:晦庵朱先生所与门人问答,门人退而私窃记之。先生殁,其书始出。记录之语未必尽得其本旨,而更相传写,又多失其本真,甚或辄自删改,杂乱讹舛,几不可读。②因此,黄榦于晚年执意做《通释》这样的文本建设,显然与当年朱子整理二程的著作,具有相似的性质,是希望将思想呈以形态化以便于传播,同时防止误读。
虽然黄榦只完成了《论语通释》,没有来得及将朱子关于“四书”的诠释与论说加以整理,但正如吴昌裔的请谥文中所说,“《语》有通释,《大学》有经解,《中庸》《孟子》有讲义,尤足以发明师传未发之言”③。
在朱学的文本建设上,黄榦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对《礼书》的诠释。朱子固然是推崇“四书”,但绝非是要用“四书”来取代“五经”。后来因朱学的意识形态化,“四书”与科举的联姻,使得“四书”有取代“五经”的历史现象,但这并不代表朱子对儒家学术典籍层次的认识与确认。朱子自始至终是将“四书”作为“五经”之阶梯来看待的。因此为“五经”作诠释,是朱子建构思想所必须做的事情。“朱子治经,《易》《诗》皆有成书。晚年刻意修《礼书》,以《书传》嘱付蔡沈。独于《春秋》未有撰述,并戒学者勿治。”④朱子对《礼》的诠释,最后之成书是《仪礼经传通解》。此书不仅朱子生前未完成,而且黄榦生前也未完成,最终成书于杨复,但诚如四库馆臣所言,“虽编纂不出一手,而端绪相因,规模不异”①。这中间,黄榦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黄谱》庆元二年(1196)条载:初,文公虽以《丧》《祭》二礼分畀先生,其实全帙自《冠》《昏》《家》《乡》《邦国》《王朝》等类,皆与先生平章之……明年三月乙亥朔,竹林精舍编次《仪礼》集传、集注书成。条理经传,写成定本,文公当之;而分经类传,则归其功于先生焉。
此说明,朱子生前对《礼》的诠释,除了专门分《丧》《祭》二门给黄榦外,整个工作也是让黄榦作重要助手的。《黄谱》引多条资料说明了这点。
黄榦致仕以后,即开始对《丧礼》稿本精修。至嘉定十三年(1220)夏完成。②《祭礼》部分虽然没有脱稿,但黄榦自称“某于《祭礼》用力甚久,规模已定。每取其书翻阅而推明之,间一二条尚欠修正。”③张虑于嘉定十五年(1222)刊刻《仪礼经传通解》时所撰序文,也说明《祭礼》基本上是根据黄榦稿本整理而成的。
《仪礼经传通解》的完成,对于朱学而言,决不仅有文本建设的意义,而是更具实践的意义。钱穆指出:朱子治经,最知重考据,于礼最多涉及。清儒考礼,其所用心,仅在故纸堆中。朱子治礼,则以社会风教实际应用为主。此不同也。④这是非常重要而正确的论断。宋代儒家在追求实现自己的经世致用的目标上,至朱子始高度自觉与始终如一地将政治的切入改为社会的切入,通过社会的改造来逐步影响于改造政治。这个社会的改造,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愿望,而是可落实的践履。这个践履的起点当然是在个人的修身上,这属于心性之学的范畴。而由个人的独自修身进入社会关系,固然心性之学仍是实践主体的内在依据,但实践主体终需要有可遵循的外在规范,这个规范即是礼。朱子诠释《仪礼》正着眼于为社会提供这样的规范。他循着实践主体的践履所涉社群范围的外展,将《仪礼》按《家礼》《乡礼》《学礼》《邦国礼》依次展开。正是因为朱子诠释《仪礼》具有这样的实践性,所以他并不是泥古不化,而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作了相应的调整,即四库馆臣所谓“所载《仪礼》诸篇,咸非旧次,亦颇有所厘析”①。而如上所言,朱子的这个思想,正是由黄榦来加以落实的。
尤为重要的是,在家庭与一般社群的仪式化活动中,最显著的是丧、祭二礼。而在南宋的丧、祭二礼中,主要已由佛教仪式来主导,因此,诠释《仪礼》,最具实践意义的就是《丧》《祭》。杨信斋说:《礼》莫重于《丧》《祭》,文公以二书属之先生,其责盖不轻也。先生于是书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诸儒同异之论,剖击世俗蠹坏人心之邪说,以示天下后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远也。先生之心,忧天下后世为心,夫岂以著述为一己之书哉?②这正指出了黄榦在诠释《仪礼》方面对朱学的重要性。
2.对朱子思想的生活仪式化推进黄榦并不只是满足于在书本上作仪式的游戏,而是致力于将知识的考古学转化成实践的考古学,通过生活中的现实操作来推广朱学所确认的礼仪。《黄谱》嘉定十二年(1219)条“门人张元简以古昏礼归其女弟,请于先生。为之正其仪法行之。”这是师门中的实践。“乡人有欲行古婚者,独以奠雁恐为人骇笑,来质于公,公曰:‘今人家子弟斗鸡走马,不以为怪,而巍冠博带以行礼,顾虑人之非笑?'其人遂决意行之。”这是向社群作推广。《黄谱》中的各条记载,足以说明黄榦这样的礼仪操演与推广是经常性的、全方位的。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学生才能够掌握得很好,在他去世后的丧葬中,“门人弟子执绑者二百余人,皆衰经菅屦,引柩三十余里至山间,丧仪如礼。乡人叹息,以为前此未之见”①。
如果说文本建设作用的发挥需要长时段来呈现,那么仪礼推广的影响足以迅速地产生教化效用。所谓“乡人叹息,以为前此未之见”,正意味着百姓由现场的感触而生发出对规范化仪礼的欣赏,而有身份、有钱的人也正可以借此来证明自己的地位或附庸风雅,尤其是当朱学转而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以后。但是,当一种思想呈现为一种形式化了的仪式以后,虽然足以使浸淫于仪式的人们不自觉地接受并认同仪式所传递出的价值信息,但同时也存在着价值因仪式而消解,从而使形式成为无意义的形式的可能。后人在评论黄榦时,虽然真实地指出他是一位以经世济民为职志的儒家,②以证明“洛、闽设教之初,尚具有实际,不徒以峨冠博带刻画圣贤”,③但这种世相的形成,并不是自然的过程,而正是朱子所希望、黄榦所努力的结果。
此外,通过形式化的仪礼来实现儒学教化的目的,这个过程是一个以牺牲实践主体的自我意识的集体无意识的培养过程。④尽管无论是孔、孟,还是朱子、黄榦,在理论上都高度强调实践主体的自我意识在仪式化活动中的觉醒,但对于社群中的普通人来说,这个要求显然是过高的。而且事实上,朱学刻意于礼制的社会运用所着眼的,与其说是培养具有自觉质疑特性的自我意识,毋宁说是培养呈现在社会习俗中的集体无意识。这便意味着,黄榦在致力于朱学由思想向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思想也因此失落了它的活力。⑤其实,不仅仪礼对于朱学具有这样的作用,标准化的文本对思想的形态化建设固然有益,但对思想的活力同样具有无形的桎梏。
3.对朱门的组织化推进作为朱子逝世以后的学派掌门人,黄榦推进师门的努力,在组织上也作有巨大的贡献。朱子生前对于书院建设,以及他自己在家乡的讲学,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并显然是努力构筑一定的物质保证与制度化建设。从“庆元党禁”中对他的攻击看,朱子在讲学的组织上也是作有精心安排的。黄榦在朱子的基础上,显然是更推进了一步,《黄谱》嘉定十年(1217)条载:春,朋旧生徒毕集于法云寓居,先生为立《同志规约》以示学者。
《同志规约》以每日各读一经一子一史,而以《论语》《周易》《左传》为之首。日记所读多寡,所疑事目,并疏于簿。在郡者月一集,五十里外者季一集,百里外者岁一集。每集告以所记文字,至与师友讲明而问难之。大要欲明义利之分,谨言行之要,以共保先师遗训之意。
这个《同志规约》所反映出的信息,说明不仅是黄榦所创设,为朱子生前所没有,而且说明黄榦已完全是在组织化建设的层面上来开展学派活动的。如果联系《黄谱》所记黄榦的学生们在他卒后“捐金”购地为其立祠,则可以推测,黄榦生前的组织化建设极可能包括了经济上的内容。可以肯定的是,其整个组织化建设是富有成效的。
4.对朱子思想的内倾化趋向总而言之,在南宋文化建设可虑及的层面上,从文本、仪礼到组织建设,黄榦都做了非常踏实的工作,使朱学成功地由思想向文化转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黄榦在思想建设上没有自己的阐述。黄榦在努力推进思想向文化转型的同时,对朱子思想也同样是作了进一步的展开。
关于黄榦对朱子思想的推进,上引吴昌裔所言,“惟文公发明致知主敬之义,每使学者互进功程,其说固已内外兼该。而先生体帖居敬集义之旨,专欲教人点检身心,其功尤为近里亲切,实是一个最恰当的概括。如果说黄榦在使朱学由思想向文化发生转型方面的努力,主要是体现在形态化的建设上,那么其在对朱子思想所作的进一步诠释上,则主要是向“心”里作内省性的工夫。
作为朱子最重要的弟子,黄榦对于朱、陆之争当然是非常清楚的,其将朱子思想诠释成内省性的心上工夫,表面上似有违背师说的嫌疑,但实质上黄榦是作有前提性的设定的。这个设定就是贯彻朱子“理一分殊”的本体论。黄榦说:道之在天下,一体一用而已。体则一本,用则万殊。一本者,天命之性;万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惟其大德之敦化,所以语大莫能载;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语小莫能破。语大莫能载,是万物统体一太极也;语小莫能破,是一物各具一太极也。万物统体一太极,此天下无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具一太极,此性无不在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极乎道体之大;道问学,所以致知而尽乎道体之细。自性观之,万物只是一样;自道观之,一物各是一样。惟其只是一样,故但存此心,而万事万物之理,无不完具;惟其各是一样,故须穷理致知,而万事万物之理,方始贯通。以此推之,圣贤言语,更相发明,只是一义,岂不自博而反约哉?①按照黄榦的阐释,如果在抽象的意义上“但存此心”,固然可以在知性层面上对事物之理有一个清晰而完备的认知,但这还并不足以进入践履的层面,知性所把握的“理”与个人生命仍是相分离的。这其实便是后来王阳明力主“知行合一”的关键。为什么知性层面上的义理认知不足以保证践履层面上的生命展开呢?黄榦有一段自我剖析的话,颇值玩味,他说:榦老矣,未能忘禄。非禄之不可忘也,不仰禄则又须别求,所以糊其口而劳心害义,反甚于仰禄。以是东西南北,惟命是从何去就出处之敢言,何功名事业之敢望!特汩没世俗,学问尽废,大为师门之罪人,不敢自文也。②黄榦当然不是“汩没世俗,学问尽废,大为师门之罪人”之人,他所以如此自责,是想说明,在现实的层面上,人生实受制于许多东西,轻者是生存,重者是名利,极不自由。要能完全地按照知性层面上所认知的义理来践履,必须从制约人生的这些束缚中挣脱出来才可以。但是这个挣脱,又并不是真的彻底地将生命加以封闭起来,否则即如黄榦所言,“害义反甚于仰禄”,陈义过高,流于自欺欺人,直使道德蜕为虚伪。因此,仰禄而担道,生命在世俗的展开中来求得道德精神的成就,这中间便有一个现实性的把握问题,即必须使生命融入世俗的生活,同时又不因为世俗的生活而使道德精神汩没于其中。只是,生命在世俗中的展开,所面对的境遇时时不同,“物各是一样”,如果徒恃知性层面对义理的认知,这个认知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把握,只有“穷理致知,使知性之所认知的“理一”,见证于生命展开中的“分殊”,始足以真正使“理”得以贯通,生命始成其为“活泼泼”的存在。因此“自博而反约”是一个不可跳过的环节,“道问学”是“尊德性”不可舍弃的基础。可以说,黄榦对师说是予以坚定维护的。
但是,尽管黄榦强调“主敬、致知两事,相为经纬”①,但不可否认,黄榦在对朱子思想的进一步推进上,是以“主敬”,即内省性的心上工夫为向度的,即所谓“持守之方,无出主敬”②。黄榦说: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须默认实体,方见端的。不然,则只是讲说文字,终日说说,而真实体段,无不曾识。故其说易差,而其见不实,动静表里,有未能合一,则虽曰为善,而卒不免于自欺也。莫若一切将就自身上体著,许多义理名字就自身上见得是如何,则统之有宗,不至于支离外驰也。③所言与陆九渊批评朱子,实是很相似了。黄榦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中,通过对朱子所确认的儒家道统的诠释,最后撮其要旨而申明为:“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④尽管仍然是恪守着朱子的思想,但其内倾化是显见的。
黄榦的这种思想取向,是由朱子对儒家精神的确认所导致的。当朱子将儒家精神确认为道德精神的认知与培养以后,除了使同道中人认同或接受他的确认以外,最重要的是使整个社会按照他的确认来生活。其中,文本、仪式、组织等形态化系统的建设使整体意义上的社群在这个系统中建立起集体无意识,而对于个体意义上的个人道德践履来说,最终只能仰赖于道德主体自我精神上的自觉与自律。其中,自觉并不难,至少在表面上,在认知的层面上,每个人都可以说懂得义理;但自律决不容易。因此黄榦将内省性的心上见得分明,加以着意的标示,这确是对朱子思想应然而必然的理论归结。黄榦讲得很清楚,他说:惟于世间利害得丧,及一切好乐,见得分明,则此心亦自然不为之动,而所为持守者始易为力。若利欲为此心之主,则虽是强加控制,此心随所动而发,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强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压草,石去而草复生矣。此不可不察也。①这在形式上,至少是在话语上,真仿佛是将朱子思想最终定位为“心学气钱穆对朱子思想曾有一个很精辟的论断:后人言程、朱主“性即理”,陆、王主“心即理”,因分别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此一分别亦非不是,然最能发挥心与理之异同分合及其相互间之密切关系者盖莫如朱子。故纵谓朱子之学彻头彻尾乃是一项圆密宏大之心学,亦无不可。②故可知黄榦的努力是深得朱子思想之精髓的。只是思想一旦被推进到个体意识的自我整肃上,正如思想的形态化促成其向文化转型一样,思想便基本上销熄了,践履成为根本的,乃至唯一的事情,正如后来明初的薛瑄所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③这对朱子思想来说,可谓是喜;但对于儒学思想来说,则也是悲。
还需要指出的是,黄榦对朱子思想的推进是对的,但是从思想的形式上看,黄榦对朱子思想的推进实也呈现出与陆九渊思想相一致的特征。这在黄榦固然非主观所愿,更谈不上是对陆学的引入,但是在客观现象上,则意味着从最忠于朱子思想的学生开始,朱、陆思想调和在形式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实际上,由下文的讨论还可以看到,朱学于南宋最后的发展同样呈现出与浙学(以史学为形式特征)相调和的现象。因此不妨说,在南宋晚期儒学的最后发展阶段,一方面是以朱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向文化转型,在这种转型中,思想获得了落实,实现其社会功能,同时也失去了活力;另一方面是曾与朱学相论争的思想,呈现出与朱学的合流,正是这种合流,使得这些不同于朱学的思想所表达的对儒家精神的理解,得以潜伏存活,并在后来适应的际遇中重新发出自己的声音,使形态化了的朱学重新被解构。
5.对朱子道统地位的论定黄榦对朱子思想进行推进的重要一点,在于其道统论。黄榦在其《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中,对儒家道统总结道,“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克己以灭其私,存诚以致其实二宋代理学亦讲求内圣外王,而以内圣为先,黄榦的这一总结,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的。“居敬”“穷理”“克己”“存诚”就是治学修身,达到内圣的具体的修习方法,而这也正是黄榦思想内倾化的又一体现。
黄榦的道统论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儒家之道的内容,就是对“人心”与“道心”关系的处理方法,即如何通过内在的修养与外在的建构,使“人心”合乎“道心”,使人的行为合乎理的规范。
其二,儒家道统传承的谱系是:尧—舜一禹一成汤一文王一武王、周公—孔子一颜回、曾子一子思一孟子一周敦颐一二程一朱子。
其三,儒家道统的传承有三方面特点:首先是继承性。即儒家之道的传承有一个不变的内核,这个内核就是使“人心”符合于“道心”的方法和规范。其次是发展性。继承道统的人物都在坚持道统思想内核的基础上,对儒家之道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和建构,使之更加具体和完善。再次是儒家之道的发展传承有一个内在的方向性。尧、舜、禹确立了儒家之道的原则性,即“人心”应该符合并遵从于“道心”的原则;成汤至周公,是以外在原则的建构为主要内容,如“礼”与“义”的规范的制定;孔子而后,则将重心转向内在修养方面,“克己复礼”“居敬穷理”等修养原则凸显为儒家之道的主要内容。黄榦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张子继之,周程张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继之。”①就是对这一内在方向的具体阐释。
统观黄榦的《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可以发现其字里行间充满着朱子的思想,换言之,黄榦是在用朱学的概念建构和诠释儒家道统,其目的也正是确立朱学的正统地位。
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末节,黄榦说:先师文公之学,见之“四书”,而其要则尤以《大学》为入道之序。
盖持敬也,诚意正心,修身而见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此又先师之得其统于二程者也。
对朱子道统地位的论定,可以说是黄榦道统论的主要目的。黄榦将朱子列入道统,并将其视为集儒家思想之大成者,推其原因,可归为以下几点。
其一,朱子本人的正统观念浓厚,其在《中庸章句序》中已经明显显现出将自己列入道统的意图,只是有所不便。而黄榦作为朱子首徒,深受师恩,完成先师未竟心愿实属当仁不让。
其二,“庆元党禁”时,朱子之学被斥为“伪学”,朱子本人也被视为“伪学魁首”,这对朱子的声誉以及朱学的名望造成了恶劣影响。“党禁”之后,朝廷虽然为朱子平反,但在黄榦看来,这还远远不够。黄榦将朱子列入道统,重塑朱子地位,也是出于为先师平反的考量。
其三,朱子去世之后,朱学仍受到来自心学、浙学等学派的攻击,维护师门的重任落在以黄榦为首的朱门弟子身上,黄榦将朱子列入儒家正统,自然就将他派归为支裔或“伪学”,这正是黄榦对攻击者作出的有力回应。
其四,朱子去世后,朱子之门内部也出现了学术分化,弟子各执一支以立言,这于朱学传承极为不利。黄榦自认深得朱子之义,因此将朱子列入道统,正是想借先师余光,以统一师门思想。
其五,黄榦将朱子列入道统,也是因为在他看来,朱子的学养和贡献完全具备这样的资格。黄榦说:“(文公)于《大学》《中庸》,则补其阙遗,另其方次,纲领条目,粲然复明。于《论语》《孟子》,则深原当时答问之意,使读而味之者,如亲见圣贤而面命之。于《易》与《诗》,则求其本义,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遗意于数千载之上。凡数经者,见之传注,其关于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之门、造道之阈者,既已极深研几、探赜索隐,发其旨趣而无所遗矣。”①“秦汉以来,斯道晦蚀,天理不明,人心不正。事物当然之则,昧没而不彰;方策不刊之训,残阙而将堕。周程张子既推明其大端,而传讹袭舛,浸失本真。迨我文公禀高明之资,厉强毅之志,潜心密察,笃信力行,精粗不遗,毫厘必辨,至其德盛仁熟,理明义精,历代相传之道,粲然昭著,……则公之生于世,有功于斯道大矣。”②“(文公)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③黄榦认为,朱子继承先贤道统,集儒家圣道之大成,德言双立,体用双修,实在是达到了儒家道统的顶峰。
黄榦对朱子道统地位的论证,将朱学的正统地位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这对于进一步扩大朱学影响,光大朱学之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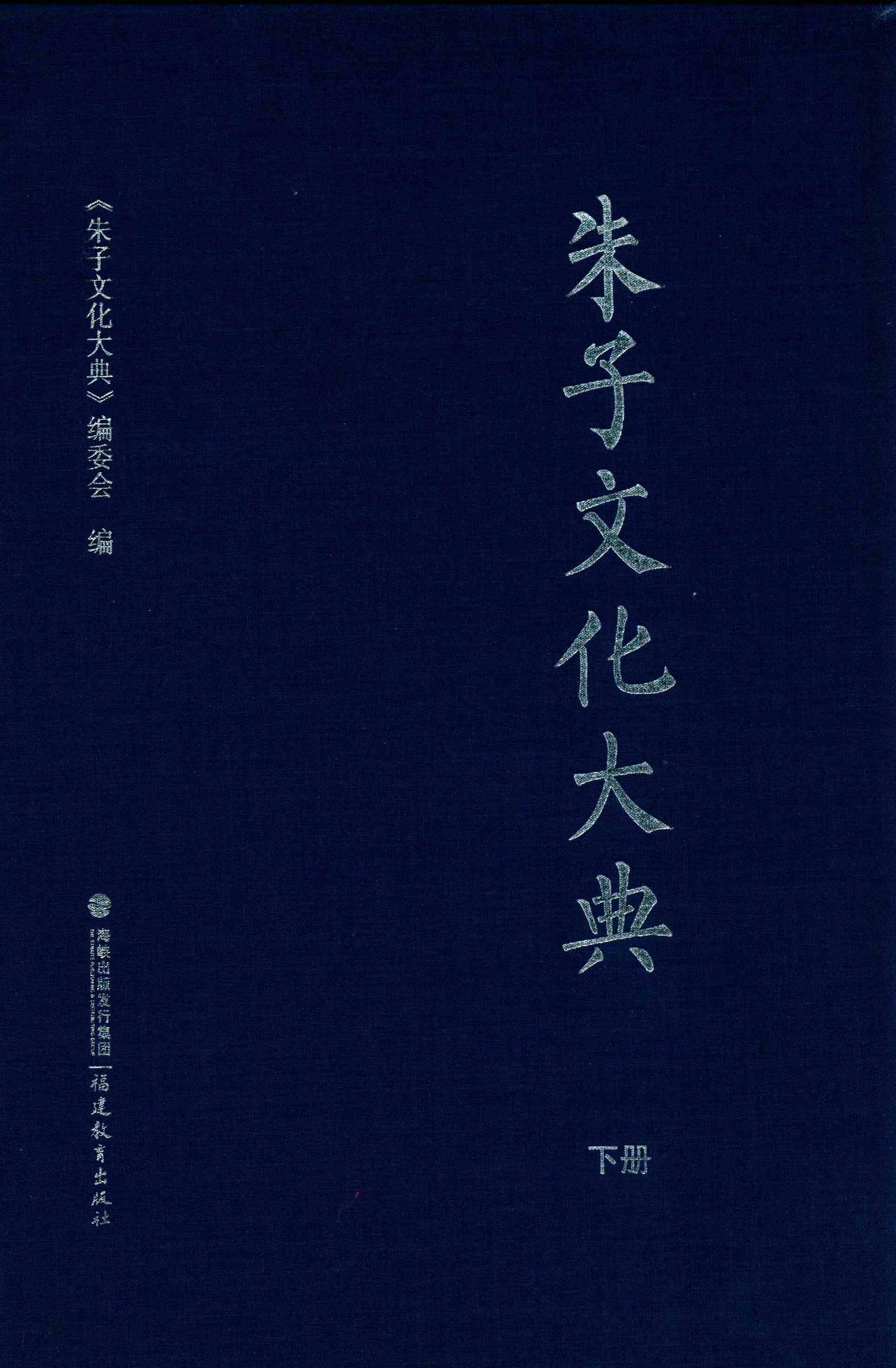
《朱子文化大典 下册》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本书分上、中、下三册。上册介绍朱子生平,包括家世、从学、讲学、论道、政绩等内容。中册阐述朱子文化源流,包括朱子理学形成的历史背景、朱子的理学思想、朱子的经学思想、朱子的教育思想等内容。下册着重介绍朱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阅读
相关地名
黄榦
相关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