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考亭沧洲
| 内容出处: | 《朱子文化大典 上册》 图书 |
| 唯一号: | 130820020210000308 |
| 颗粒名称: | 三 考亭沧洲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22 |
| 页码: | 45-66 |
| 摘要: | 考亭沧洲精舍是朱子创建的第四所书院,也是他创建的最后一所书院,地点在建阳三桂里考亭村,初名竹林精舍。绍熙二年,朱子离漳州知州任后,将家从崇安五夫迁居建阳童游。绍熙三年,建竹林精舍于考亭,在此广招门徒,聚徒讲学。绍熙五年十二月,因生员日多,便将精舍加以扩建,更名为“沧洲精舍”,并自号“沧洲病叟”。从绍熙三年至庆元六年前后约八年,朱子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讲学和著述。但考亭沧洲精舍之祭祀先贤,与讲学关系甚为密切,故在此一并提及。借此良机,朱子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祭祀先圣的仪式。同时,这种祭祀活动也与朱子创建书院的宗旨或曰教育目的紧密相关。 |
| 关键词: | 朱熹 讲学 竹林精舍 |
内容
考亭沧洲精舍是朱子创建的第四所书院,也是他创建的最后一所书院,地点在建阳三桂里考亭村,初名竹林精舍。
绍熙二年(1191),朱子离漳州知州任后,将家从崇安五夫迁居建阳童游。绍熙三年(1192),建竹林精舍于考亭,在此广招门徒,聚徒讲学。绍熙五年(1194)十二月,因生员日多,便将精舍加以扩建,更名为“沧洲精舍”,并自号“沧洲病叟”。从绍熙三年至庆元六年(1192—1200)前后约八年,朱子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讲学和著述。
由于前有寒泉、云谷的执教生涯,其后又有白鹿洞书院、武夷精舍、岳麓书院的讲学实践,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登门求学者日渐增多,朱子考亭学派因之得到迅速的壮大。考亭沧洲精舍建成之后,曾先后就学于寒泉、云谷、武夷的蔡元定、黄榦、刘爚、林择之、詹体仁、廖德明等一大批门人弟子,又聚集考亭。据方彦寿考证,至今仍有姓名、生平仕履可考的考亭朱门弟子尚有215人。①在考亭,他们研经读史,抨击社会弊端,寻求济世良方,穷究理学奥秘,积极开展各种教学和研究活动,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考亭学派”在此最后形成,并走向成熟。
由于考亭沧洲精舍的规模比寒泉、云谷大,从学生员比寒泉、云谷要多,加上经过数十年的教学实践,朱子的教育目的论、阶段论、方法论等一系列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均已形成,因此,在书院的功能、组织形式、教学形式上比起前期来都有许多创新与发展。主要表现在崇祀先贤、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
(一)崇祀先贤与道统论祭祀、讲学、藏书刻书通常被称为书院的三大基本功能,而祭祀先贤一般不列入讲学范围之内。但考亭沧洲精舍之祭祀先贤,与讲学关系甚为密切,故在此一并提及。
尊孔祭孔,崇祀先圣先师,这在封建社会,不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是一个通例。但朱子创办的书院,除祭祀孔圣外,还开启了祭祀学派先贤的先河。淳熙六年(1179),朱子在江州(治今江西省九江市)立濂溪祠于学宫,以二程配祀。绍熙五年(1194),又将此作法引入考亭沧洲精舍。这年十二月,竹林精舍经扩建后,改名为沧洲精舍。借此良机,朱子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祭祀先圣的仪式。他釆用了释菜古礼,撰写了具体操作祭祀的仪式,名之曰《沧洲精舍释菜仪》①,以及《沧洲精舍告先圣文》②。主祀孔圣,而以颜渊、曾参、子思、孟子配祀,又以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司马光和李侗七人从祀。门人叶贺孙详细地记述了祭祀过程:新书院告成,明日欲祀先圣先师,古有释菜之礼,约而可行,遂检《五礼新仪》,令具其要者以呈。先生终日董役,夜归即与诸生斟酌礼仪。鸡鸣起,平明往书院,以厅事未备,就讲堂礼。宣圣像居中,兖国公颜氏、邯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邹国公孟氏西向配北上(并纸牌子)。濂溪周先生(东一)、明道程先生(西一)、伊川程先生(东二)、康节邵先生(西二)、司马温国文正公(东三)、横渠张先生(西三)、延平李先生(东四)从祀(亦纸牌子)。并设于地。祭仪别录。祝文别录。先生为献官,命贺孙为赞,直卿、居甫分奠,叔蒙赞,敬之掌仪。堂狭地润,颇有失仪。但献官极其诚意,如或享之,邻曲长幼并来陪。礼毕,先生揖宾坐,宾再起,请先生就中位开讲。……说为学之要。③文中记载由于条件所限,书院“堂狭地润”,所祭先贤,孔圣之外,其余均以纸牌子代替而非塑像,但献官即朱子却“极为诚意”,气氛认真而隆重。最后,朱子即席开讲,内容是为学之要,说明书院的祭祀活动是与讲学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朱子在书院举行祭祀活动,其目的是使其门人从这些先圣先贤的身上吸取教益,受到文化、道德的熏陶。更重要的是,举行这项活动,能使儒家的道统学说得到生动活泼的、立体的体现,从而使门人容易接受,取得比讲学更好的效果。朱子说:恭惟道统,远自羲、轩。集厥大成,允属元圣。述古垂训,万世作程。……维颜曾氏,传得其宗。逮思及舆,益以光大。自时厥后,口耳失真。千有余年,乃曰有继。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爰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①文中叙述道统自尧、舜传至孔子,中经颜、曾、思、孟发扬光大,此后道统失传,一直到北宋周、张、二程才继绝续断,道统得以重续。朱子通过书院的祭祀活动,把圣人相传的谱系和儒家正统文化精粹的传承关系演示给及门弟子,进而在他们心中扎下根来。
同时,这种祭祀活动也与朱子创建书院的宗旨或曰教育目的紧密相关。他在萌生于寒泉和武夷精舍,而形成于白鹿洞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②从文中提出的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处事、接物之要而论,其大旨不离“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最终目的是希望学者能“以圣贤为己任”。③如果说,《白鹿洞书院揭示》提出了教学的目的、方法的话,那么,书院之祭祀先圣先贤,则是激励诸生勇猛奋发,走向此目的的有效方法之一。
(二)教学内容在教学内容上,朱子要求学者“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及《诗》《书》《礼记》,程、张诸书分明易晓处,反复读之”①。庆元元年(1195)至考亭问学的门人杨楫记云:先生平居教学者首以《大学》《语》《孟》《中庸》四书,次而“六经”,又次而“史传”,至于秦汉以后词章,特余论及之耳。②传统儒学都把“六经”作为书院的首要经典教材,而朱子将“四书”列为书院教材之首,一方面说明朱子是把“四书”的地位列于“六经”之上,突出了“四书”在经学体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说明他是把其哲学体系中最新、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由此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子所创书院中教学与研究紧密结合的特点,从而引导学生能站在当时学术研究领域的最前沿。
就“四书”本身的为学之序,朱子要求学生“先看《大学》,次《语》《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彻,一生受用不尽”③。对“四书”之间的内在联系,朱子对从学于沧洲精舍的门人徐寓等作了如下的揭示: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④所谓定其规模,就是构筑以“三纲八目”为“间架”的成人教育体系。以三纲,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道德修养的方向和目标;以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修身治人的主要方法和目的。所谓立其根本,就是掌握以“仁”为核心的儒学思想,领会“操存、涵养之要”①;所谓观其发越,就是进一步发挥尽心知性的义理之学, 把握“体验、扩充之端”②;而“求古人之微妙处”,就是通过掌握孔门十六字心传之法,以道心克服人心,并求得古圣人儒学思想的极致。由于《四书 章句集注》是朱子穷毕生精力所著,因此他要求学生在熟读经文的基础上, 再读集注,并能参照经文,认真学习,用心体会。但他始终认为,学者仍应 以“四书”经文为主,《集注》次之。他以《大学》为例,对门人说:
既知工夫在此,便把《大学》为主,我且做客,听命于《大学》。③ 经文与《集注》是“主”和“客"即主次关系。
“四书”之外,《诗》《书》《礼》《易》《乐》《春秋》即所谓“六经”,以 及《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籍,两宋理学诸子周敦颐、二程、张 载、邵雍、杨时、游酢、胡安国、罗从彦和李侗等人的著作,也是书院教学 的重要课程。从朱子与其门人讲学问答的实录《朱子语类》来考察,在该书 一百四十卷中,“四书”占五十一卷,“六经”占二十七卷,历史、政治、时 事、文学等占二十一卷,理学概念如理气、性理、仁义礼智等占八卷,专人 如战国诸子老、庄、列,理学诸子如周、张、二程等占十六卷,论为学之 方、训诫门人等占十七卷。教学内容广泛涉及哲学、历史、文化、政治、经 济、文学乃至自然科学等诸多方面。
在为学内容博与约的关系上,朱子强调从约至博,再从博返约。他结合 书院的教学内容,向门人阐明为学博与约的关系是:
为学须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约,中间一节甚广大,到末梢又约。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故必先观《论》《孟》《大学》《中庸》,以考圣贤之意;读史,以考存亡治乱之迹;读诸子百家,以见 其驳杂之病。其节目自有次序,不可逾越!④
由见可此,朱子对博与约关系处理不得当的两种倾向提出批评。一种是 “多喜从约,而不于博求之”者,一种是“专于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约”者,都是片面而无益的。
(三)教学方法在教学方法上,朱子在总结前辈教育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既有所继承,也有许多创新之处。
1.学生自学自学为主,这几乎是宋代所有书院的通例,考亭沧洲精舍也不例外。朱子对从学门人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有自学的经历。朱子《沧洲精舍谕学者》一文,便是一篇鼓励和要求学生自学的演讲稿。他以北宋苏洵发愤读书,自学成才的事迹为例,对其“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贤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的苦读精神极为赞赏;但对其“但为欲学古人,说话声响”“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称赏而已”的目的则不敢苟同。因此,他要求门人在明确学习目的的基础上,按苏洵的自学方法——以二三年为期,正襟危坐,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及《诗》《书》《礼记》,程、张诸书分明易晓处,反复读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养玩索,著实行履。①在学生自己学习、钻研、体会、践履的基础上,老师加以诱导,并“证其所得而订其谬误”②。这与朱子对门人沈僴所说也是一致的: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③对自学的方法,朱子在教学中曾经有过系统的传授,他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要,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④门人辅广后来将此归纳为六条,后人通常称为“朱子读书六法”。
一是循序渐进。朱子曾举《论语》和《孟子》二书为例说,须先读《论语》,而后读《孟子》。读通了一书,而后再读另一书。以一书而言,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也是先后有序而不可乱。“凡读书,须有次序。且如一章三句,先理会上一句,待通透;次理会第二句,第三句,待分晓;然后将全章反覆紬绎玩味。”①其要求是“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渐进焉,则意定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②。
二是熟读精思。即在熟读的基础上加以认真思考。他认为“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③。“读书之法:读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读一遍。读诵者,所以助其思量,常教此心在上面流转。若只是口里读,心里不思量,看如何也记不子细。”④他对熟读的要求是“使其(指书本——编者注)言若出乎吾之口”;对精思的要求是“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只有这样读书,方能有所收获。
三是虚心涵泳。要求读书须虚心。“虚心,则见得道理明。”所谓“涵泳”,则是仔细玩味,反复体察之意。他以读《论语》为例说:“《论语》一日只看一段,大故明白底,则看两段。须是专一,自早至夜,虽不读,亦当涵泳常在胸次,如有一件事未了相似,到晚却把来商量。”⑤辅广因读《论语》太快,朱子告诫他:“若如此看,只是理会文义,不见得他深长底意味。所谓深长意味,又他别无说话,只是涵泳久之自见得。”⑥四是切己体察。要求在读书中,要将书中所说的道理,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实践相结合。即所谓“学问,就自家身己上切要处理会方是”⑦,做到“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①。所以,朱子对陈淳说:“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以手自指)推究。”②五是着紧用力。即以坚持不懈、勤奋刻苦的精神读书。朱子经常教导他的弟子,读书“须是策励此心,勇猛奋发,拔出心肝与他去做!如两边擂起战鼓,莫问前头如何,只认捲将去!”“如撑上水船,方平稳处,尽行不妨。及到滩脊急流之中,舟人来这上一篙,不可放缓。”③六是居敬持志。“居敬”指的是居敬穷理,意为修身涵养与探寻物理相互促进。“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④“持志”则强调要立定志向,始终不渝。
2.先生讲学朱子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所传授的知识,多为高深的学问,抽象的哲学概念。由于他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善于运用比较浅显的口语、生动活泼的事例、通俗易懂的日常生活知识来解说,因而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一部一百四十卷的《朱子语类》,是朱子与门人问答的语录汇编,也是一部朱子言传身教的讲学实录。
朱子的讲学方式,有升堂讲学、个别辅导、集体讨论等多种形式。
(1)升堂讲学由于书院教学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传授、指导为辅,因此,升堂讲学只是根据情况偶尔为之。门人王过记沧洲精舍每天的教学生活:先生每日早起,子弟在书院,皆先著衫到影堂前击板,俟先生出。
既启门,先生升堂,率子弟以次列拜炷香,又拜而退。子弟一人诣土地之祠炷香而拜。随侍登阁,拜先圣像,方坐书院,受早揖,饮汤少坐,或有请问而去。⑤每日例行的参拜孔圣,学生向先生请安之后,接着就是“或有请问”,即有疑难问题,学生向老师求教。之后各自散去,继续自学自己的功课。可见,先生升堂讲学不是每天的必修课。
从《朱文公文集》来考察,朱子在各地学校、书院均有升堂讲学,并留下部分讲义。如在考亭沧洲有《沧洲精舍谕学者》《又谕学者》等。
从其内容来看,升堂讲学所授主要是为学之要,即涉及学习目的、方法等大的方面的问题,而较少涉及具体的某部教材的枝节问题。如《沧洲精舍谕学者》向门人传授了书院教学最重要的方法——自学,自学的内容和自学的要点,即反复诵读,认真体会,存养玩索,着实行履。《又谕学者》则着重阐述了立志的重要性,勉励诸生要贪道义而不要贪利禄,要做好人而不要作贵人。“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①因此,立志对每一位从学者而言,都是首要的、头等的大事。
从其方法来看,升堂讲学是以“答疑解惑”为主,而非满堂灌。先生根据学生所提疑难问题予以解答,如《论语课会说》,就是朱子根据学生在学习《论语》中存在的问题,集中起来加以解答,此即“会说”的意思,也就是升堂答疑解惑。
被朱子称为“会说”的升堂讲学,主要是为避免官学“师之所讲,有不待弟子之问;而弟子之听于师,又非其心之所疑”的弊病。教与学之间缺乏交流,难免造成二者之间的脱节,教非所疑,疑非所释,故“圣人之绪言余旨所以不白于后世,而后世之风流习尚所以不及于古人也”②。因此,他在书院实行的“会说”制度,是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主要目的。他要求学生能“退而考诸日用,有疑焉则问,问之弗得,弗措也”③。这与他要求学生自学,先须熟读本文,后参以集注,其原则是一致的。
个别辅导是对学生各自不同的疑点难点问题进行辅导。对学生而言,是问疑,对先生而论,则是答疑,这是朱子教学中非常重要的方法之一。其要点,将在下文专门讨论。这里,就朱子在个别辅导中的几个特点作一番探讨。一是谆谆善诱。门人叶贺孙记朱子在对黄先之进行个别辅导时,有“数日谆谆”①的记载。黄榦《朱文公行状》则称: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谕,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高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②表明朱子平日教导学生,谆谆善诱,孜孜不倦,以此开启门人的理解力、创造力。他经常以自身经历、体会劝诫门人,为学须专心。如:后生家好著些工夫,子细看文字。某向来看《大学》,犹病于未子细,如今愈看,方见得精切。③某旧时看文字,一向看去,一看数卷,全不曾得子细;于义理之文亦然,极为病。今日看《中庸》,只看一段子。④今日学者不长进,只是“心不在焉”。尝记少年时在同安,夜闻钟鼓声,听其一声未绝,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惧,乃知为学须是专心致志。⑤读书或贪多求快,不求甚解,或心猿意马,心不在焉,这是许多学员的通病。对此,朱子不是采取一般的正面批评、指责,而是采用自己早年是如何克服这些缺点的经历、体会劝诫门人,使门人尤感亲切,从而在求学中得以逐渐改正。
他还把自己早年学习《孟子》的体会告诉门人:《孟子》若读得无统,也是费力。某从十七八岁读至二十岁,只逐句去理会,更不通透。二十岁已后,方知不可恁地读。元来许多长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脉络相贯串,只恁地熟读,自见得意思。从此看《孟子》,觉得意思极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①所谓“无统”,即没有系统地读,仅逐字逐句地领会,这样就无法把握各段之间相互贯穿的文意。而通过系统地把握之后熟读精思,既可领略全书的儒学思想精粹,又因之学得“作文之法”,可谓一举多得。朱子把自己的体会传授给门人,就是要门人避免走类似的弯路。
二是善于用通俗易懂的日常生活知识作比喻来开导门人。如他常以撑上水船来激励门人努力向学:为学正如撑上水船,方平稳处,尽行不妨。及到滩脊急流之中,舟人来这上一篙,不可放缓。直须着力撑上,不得一步不紧。放退一步,则此船不得上矣。②说为学贵在坚持,不可间断,以自己手臂疼痛,需不停地按摩止痛来类比:某若臂痛,常以手擦之,其痛遂止。若或时擦,或时不擦,无缘见效,即此便是做工夫之法。③比喻形象、生动,以至门人余正叔认为“擦臂之喻最有味”。又如,阐明温故知新的道理,以农夫耕田为喻。他说:子融、才卿是许多文字看过。今更巡一遍,所谓“温故”;再巡一遍,又须较见得分晓。如人有多田地,须自照管,曾耕得不曾耕得;若有荒废处,须用耕垦。④朱子在讲学中,还善于以具体的事物说明抽象的概念。如体用关系:体是这个道理,用是他用处。如耳听目视,自然如此,是理也;开眼看物,着耳听声,便是用。①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纸糊,此则体也;人摇之,则用也。②耳为体,听为用,目为体,视为用,扇为体,摇为用,这样的比喻就将本不易理解的抽象概念具体化了。
又如他对门人讲解《大学》开篇几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他说“在明明德”等三句:是大纲,做工夫全在此三句内。下面知止五句是说效验如此。上面是服药,下面是说药之效验。正如说服到几日效如此,又服到几日效又如此。看来不须说效亦得,服到日子满时,自然有效。③一个“服药”与“药效”的比喻,将大学三纲及其作用解说得明白无误且情趣盎然。曾先后从学于武夷精舍和考亭沧洲精舍的丹阳学子窦从周曾这样评价朱子的讲学效果:“读《大学章句》《或问》,虽大义明白,然不似听先生之教亲切。”④朱子还常以人的呼吸来解说动静关系。“一动一静,循环无端,所以谓‘动极复静,静极复动’。如人嘘吸:若嘘而不吸,则须绝;吸而不嘘,亦必壅滞著不得。嘘者,所以为吸之基。”⑤说仁爱之关系,认为“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⑥。
以人之两足比喻居敬与穷理:“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两足,左足行,则右足止;右足行,则左足止。”⑦三是引导门人善于使用比较的方法。
比较,是为学的重要方法之一。在讲学中,朱子曾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诫门人,要善于使用这个方法。绍熙四年(1193),他对门人林学蒙说:凡看文字,诸家说异同处最可观。某旧日看文字,专看异同处。如谢上蔡之说如彼,杨龟山之说如此,何者为得?何者为失?所以为得者是如何?所以为失者是如何?①谓如甲说如此,且挦扯住甲,穷尽其词;乙说如此,且挦扯住乙,穷尽其词。两家之说既尽,又参考而穷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②要使用比较的方法,又有一个积累的功夫,没有对历代儒学大师精辟见解的采集和吸收,比较也就无从谈起。所以,他又对门人说:寻常与学者说做工夫甚迟钝,但积累得多,自有贯通处。且如《论》《孟》,须从头看,以正文为正,却看诸家说状得正文之意如何。
且自平易处作工夫,触类有得,则于难处自见得意思。③所谓“诸家说状得正文之意”,就是历代儒家学者对经典的各自阐发。所以,通过比较、鉴别,扬长避短,择善而从,这不仅是朱子读书的重要方法,也是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
(3)集体讨论集体讨论,是朱子在教学中着力提倡的一个方法。其基本观点为,读书应以独处为主,问学则以群居有益。他说:看文字,却是索居独处好用工夫,方精专,看得透彻,未须便与朋友商量。④有见于此,所以他提倡书院教学,以学生自学为主。但由于书院中每有诸生请问不切题,或问不到点子上,所以他又认为:群居最有益,而今朋友乃不能相与讲贯,各有疑忌自私之意。不知道学问是要理会个甚么?若是切己做工夫底,或有所疑,便当质之朋友,同其商量。须有一人识得破者,已是讲得七八分,却到某面前商量,便易为力。①学员中若有疑难,可以相互讨论,这是发挥书院群居的长处。若学员集体讨论不能解决,再来请教先生,学习效果则更为显著。这是朱子对“群居有益”的基本认识。
庆元三年(1197)从学的林夔孙,是考亭书院的堂长。一次,朱子让他安排一次集体读书活动。朱子说:可将一件文字与众人共理会,立个程限,使敏者不得而先,钝者不得而后。且如这一件事,或是甲思量不得,乙或思量得,这便是朋友切磋之义。②所谓“朋友切磋”,就是学员集体讨论。这次读书活动,先后安排了张载的《西铭》、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等,通过集体讨论和切磋,门人对《西铭》的“理一分殊”思想,以及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思想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掌握。
从沧洲精舍的教学实践看,集体讨论有时又与升堂讲学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导师升堂讲学与学员开展集体讨论相结合的特点。
(4)随即教育随即教育指的是不在教学计划之内,而是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因偶然事件发生,在此过程中即兴发挥,对学生进行的教学活动。
《朱子语类》中这方面的记载很多,以下仅举几例。门人郭友仁记录说,有一次,受“庆元党禁”牵连而受贬谪的宰相留正来书,向朱子请教《诗集传》的几个问题,朱子把书信展示给学生看,说:他官做到这地位,又年齿之高如此,虽在贬所,亦不曾闲度日。公等岂可不惜寸阴!③这是以身处逆境中的高官,且又年处高龄之人仍奋发学习的事迹来激励门人珍惜光阴,努力向学。
门人王过记云:先生一日说及受赃者,怒形于言:曰“某见此等人,只与大字面配去!”徐又曰:“今说公吏不会取钱,为知县者自要钱矣!”节节言之,为之吁叹。①此以对贪赃枉法者的蔑视和愤慨教育门人,今后若有从政机会,应廉政爱民,不可贪赃枉法。
朱子在书院教学中,由于与门人朝夕相处,随即教育的事例是很多的。如有亲戚来求朱子荐举,他由此对门人解说了荐举须是贤才的道理②;与门人游园,说到园可荒而志不可“荒”③;从士兵耘草,快者除草不尽,而慢者仔细认真,引申说到为学须仔细,若“欲速苟简”,反而“致得费力”,④等等。
从其随即教育的事例看,概而言之,其大要不外乎可归结为“如何为学”和“如何为人”这两点上,体现了书院教学教书育人的目的。
3.教与学结合——问疑书院教学,既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主,则学生之问疑与先生之解惑,就成了教与学之两端。但先生对学生的问疑也有一定要求,并非不着边际地乱问一气,朱子对此的要求是学生必须对课程内容熟读精思,由此而产生的疑问,方予解答。
庆元四年(1198),郭友仁至考亭问学,“初参拜毕,出疑问一册,皆《大学》《语》《孟》《中庸》平日所疑者。”但朱子只是“略顾之”,对他说:公今须是逐一些子细理会,始得,不可如此卤莽。公之意,自道此是不晓者,故问。然其他不问者,恐亦未必是。岂能便与圣贤之意合?须是理会得底也来整理过,方可。⑤门人滕璘初见之时,“问:‘做何工夫?’璘对以未曾。曰:‘若是做得工夫,有疑可问,便好商量。若未做工夫,只说得一个为学大端,他日又如何得商量?”①甘节初到书院,即向先生询问《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质”一章,朱子不答,而对他说:不思量后,只管去问人,有甚了期?向来某人自钦夫处来,录得一册,将来看。问他时,他说道那时陈君举将伊川《易传》在看,检两版又问一段,检两版又问一段。钦夫他又率略,只管为他说。据某看来,自当不答。②朱子为何不作答呢?这是因为,他在教学中,始终坚持这样的原则,即“学者于理有未至处,切不可轻易与之说”③。像张栻那样,由于“为人明快,每与学者说话,一切倾倒说出。此非不可,但学者见未到这里,见他如此说,便不复致思,亦甚害事。某则不然。非是不与他说,盖不欲与学者以未至之理耳”④。同时,他还认为“今欲理会这个道理”即义理之学,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难之事”,而发问者“不曾用得旬月功夫熟读得一卷书,只是泛然发问,临时凑合,元不曾记得本文,及至问著,元不曾记得一段首尾,其能言者,不过敷演己说,与圣人言语初不相干,是济甚事!”⑤这样的问疑,是临时凑合的泛然发问,不着边际,“多是不疑其所当疑,而疑其所不当疑。不疑其所当疑,故眼前合理会处多蹉过;疑其所不当疑,故枉费了工夫”⑥。因此,当门人刘砺问疑《论语》《孟子》时,他说:今人读书有疑,皆非真疑。某虽说了,只做一场话说过,于切己工夫何益!⑦那么,应如何问疑,才好作答呢?朱子对门人甘节说:大抵问人,必说道古人之说如此,某看来是如此,未知是与不是。
不然,便说道据某看来不如此,古人又如此说,是如何?①朱子认为,这才是“真疑”,要达到“真疑”的水平,他认为,首先必须熟读,其次是精思,认为“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②。所以他对门人一再强调:“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③读书读到这个份上,朱子认为还是远远有够的,接下来,他告诫门人:熟读精思既晓得后,又须疑不止如此,庶几有进。若以为止如此矣,则终不复有进也。④这个过程,就是熟读精思,思而有疑的过程。朱子曾向门人描述这个过程。他说:某向时与朋友说读书,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见得,读书只是且恁地虚心就上面熟读,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处。盖熟读后,自有窒碍,不通处是自然有疑,方好较量。今若先去寻个疑,便不得。⑤因熟读而生疑,此疑点便是窒碍不通处,知道了此疑点或窒碍不通处,“方好较量”——先生的答疑解惑作用至此方能显现出来,方能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疑难问题作出恰切的解答。《朱子语类》记有庆元四年(1198)从学于考亭的门人郭友仁的一段问疑:问:“圣门说‘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异乎?”先生笑曰:“也问得好。据公所见如何?试说看。”曰:“据友仁所见及佛氏之说者,此一性,在心所发为意,在目为见,在耳为闻,在口为议论,在手能持,在足运奔。所谓‘知性’者,知此而已。”曰:“且据公所见而言,若如此见得,只是个无星之称,无寸之尺。若在圣门,则在心所发为意,须是诚始得;在目虽见,须是明始得;在耳虽闻,须是聪始得;在口谈论及在手在足之类,须是动之以礼始得。‘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如公所见及佛氏之说,只有物无则了,所以与圣门有差。况孟子所说‘知性’者,乃是‘物格’之谓。”①儒、佛两家均言“知性”,那么二者有什么区别呢?这样的问题,须是学生在涉猎儒、佛二家典籍,熟读而精思之后方能提出,故朱子称赞他“问得好”,接着他启发学生,说说你的看法,先生谆谆善诱的辅导作用在此体现了出来。当郭友仁把他的模糊认识说出后,朱子才根据学生的想法,有针对性地区分了语出《孟子》的“尽心知性”与佛氏的“知性”的不同之处,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这一点上,朱子颇为赞赏陈淳。他对门人叶贺孙说:“漳州陈淳会问,方有可答,方是疑。”②学生经熟读精思后,产生的疑问“方是疑’’,先生“方有可答”,解惑释疑才能产生最好的效果。朱子曾反复向门人传授这一经验: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③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④到无疑处不必问,疑则不可不问。⑤至此,可将这个教学过程完整地表述为:熟读精思→思而生疑→疑而后问→问而解惑。前两条为学生根据先生布置的阅读内容,独立完成的过程,也是从无疑到有疑的过程,后两条为师生共同完成的过程,也是从有疑到无疑的过程。其总体而论,仍体现了书院教学以学生自学为主,先生讲学为辅的特点。
朱子这一教学方法,是遵循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学原则。即不到学生思考问题欲通而未通之时,不去开导他;不到欲说而又说不出之时,不去启发他。程颐对此的认识是“盖不待愤悱而发,则知之不固;待愤悱而后发,则沛然矣。学者须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后为他说便好”①。以此对照朱子的教学实践,朱子对此既有继承,又有新的发展。
(四)教学安排——入学、离学与远程教学由于书院是以成人教育为主,故没有实行严格的固定学期制。门人求学,根据自己的职业、家庭以及时间是否许可等具体情况作出自己的安排,且从学时间长短不一,书院采用的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②的原则,故在教学时间的安排和方法的采用上均需随机而行。可分为入学、离学与远程教学三种情况。
对入学者,了解其学业情况、专长和兴趣,以安排其相应的课程。
如长乐(今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籍门人刘砥来学,朱子问:“曾做甚工夫?”回答说最近在读《大学章句》,但还不知从何处下手。朱子告诫其“须先操存涵养,然后看文字,方始有浃洽处”③,若只在字里行间求索,不从自己心里下功夫,体察涵养,则无法做到融会贯通。庆元三年(1197)三月,正值“伪学之禁”风声正紧之时,江西门人曾祖道来到考亭。朱子询问其学业,了解了他曾先后从学过刘清之和陆九渊,知其“道问学”的功夫不够扎实,看书太快,不求甚解,因劝其在熟读精思及修身穷理上下功夫。④除了对初入学者有耐心询问,精心安排外,对相隔一段时间,再次来书院问学的门人也要向其了解学业进展的情况。如曾多次从学朱子的兴国门人万人杰去后复来,见面,朱子即问其“别后工夫”如何,人杰回答,回去后谨按先生的教诲和安排,“知先生之道,断然不可易。近看《中庸》,见得道理只从下面做起,愈见愈实”⑤。于是,朱子又将时学故意将“道”说得高妙深奥,使人无法理会的弊端作了一番批评,指出“二程说经义,直是平常,多与旧说相似”,并不以标新立异欺世,只是“意味不同”而已。①同时,对万人杰喜与“众说相反”的毛病予以指正。
类似于万人杰这样再次问学的,如莆田门人郑可学,江西南城门人包扬、临海门人潘时举等,均有“再见,请教”②,或“久不相见,不知年来做得甚工夫”③、“子善别后做甚工夫”④的询问。
对暂时离学者,根据其在书院学习的具体情况,安排其离学后继续学习的课程,以保持其学习的延续性。如曾祖道拜别,朱子告诫他:归去各做工夫,他时相见,却好商量也。某所解《语》《孟》和训诂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为咀嚼过。此书,某自三十岁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犹未了,不是草草看者,且归子细。⑤就是命其回家后,认真学习《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若有疑处,日后可问。
兴国门人吴必大从书院暂归,拜别时,朱子对他说:“所当讲者,亦略备矣。更宜爱惜光阴,以副愿望。”又说:“别后正好自做工夫,趱积下。一旦相见,庶可举出商量,胜如旋来理会。”⑥同卷记黄?、吴必人与万人杰告辞,朱子询问别后欲读何书,告以欲先读《易》后学《诗》。朱子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认为应改为先读《诗》,后学《易》;并告以学《诗》的方法,不要被《毛诗序》中“以史证诗”的“旧说粘定”,“不可于名物上寻义理”,《诗》之外,“《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自依次序循环看”,史书如《资治通鉴》等“亦不可不看”。⑦以上诸人之外,临别请教的门人还有余大雅、潘时举、杨道夫、石洪庆、暧渊、丘玉甫、林叔和、廖德明、徐元明、魏椿、辅广等。《朱子语类》中分别记载了朱子对他们别后,勿荒废学业,继续努力的期盼。由此表明学员因故暂时离学,并非学业的中断,而是书院学习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
对外地暂时不能前来面授的门人,要求他们在自学的过程中,写信前来问疑,以便进行远程函授教育。
如门人辅广在考亭面学三月,辞归之日,朱子对他说:“有疑更问。”辅广回答:“今亦未有疑。自此做工夫去,须有疑,却得拜书请问。”①南康门人黄灏(字商伯)离学后,曾多次来信问疑,朱子对其问《丧礼》,曾连续复函三通。朱子《答黄商伯》对其问《大学》《中庸章句》中相关的几个疑难问题一一作了函复。②漳州朱飞卿来书请问持敬、穷理、诗传等,朱子一一予以答复。从《答朱飞卿》书看,朱飞卿问疑原文亦载,即一段学生问疑之后,就是一段先生的回答,应是当时朱子直接在问卷中的批示。③顺昌廖德明是先后曾从学于朱子创建的四所书院的门人之一,《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有《答廖子晦》书十八通,内容均为问疑。其中在书一、书二、书三、书五、书十四、书十五、书十八中,廖德明的问疑原文具录,内容也是一问一答,是古代书院典型的远程函授教育的原始资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书十一,这是一通长卷,内容为李唐臣问《伊川易传》之疑。可分为五段,一、三两段为唐臣所问,二、四两段是德明答疑,第五段为朱子总评。李唐臣可能是廖德明在广东讲学之时招收的弟子,廖德明在答疑之后仍觉未安,故将长卷呈寄朱子,再作批注。故此长卷,是由师生三代人共同完成的,这在朱子所有的函授信件中,是一个罕见的特例。
从《朱文公文集》全面考察,朱子撰写的书信写给门人的有一千六百多通。在从学考亭的二百一十五位门人中,朱子与他们有书信往来的有九十七人。其中数量最多的如蔡元定、黄榦等多达一百多通;其余多则十几通,少则一二通不等。内容除了时政、学术讨论、专题研究、往复论辩、图书校勘、师友问候之外,还有两百多通是为门人答疑解惑的内容。这些书信,或为长卷,或为短札。其中有十几通长卷文字多达数千言,甚至近万言。如《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七《答陈安卿》书一至书三,卷六十《答潘子善》书六,卷六十一《答欧阳希逊》书二,卷六十二《答李敬子余国秀》,卷六十三《答郭子从》书一、《答胡伯量》书一;《朱文公续集》卷九《答刘韬仲问目》、卷十《答李继善问目》等。
这部分答疑书札,有的学生问疑原文具在,有的虽无原文,而以“来书云”或“来喻”概括来信所示之疑,而后解答。此即朱子《答林德久》所言“所示疑义,各附鄙说于其后”①,《答黎季忱》“示及两卷,各已批注封还”②之意。从这些问疑书札看,内容广泛涉及传统儒学、朱子理学的各个层面。因此,对朱子这部分书信,既可看成是书院远程函授教育的原始信札,也是研究朱子理学思想发展的重要史料。
绍熙二年(1191),朱子离漳州知州任后,将家从崇安五夫迁居建阳童游。绍熙三年(1192),建竹林精舍于考亭,在此广招门徒,聚徒讲学。绍熙五年(1194)十二月,因生员日多,便将精舍加以扩建,更名为“沧洲精舍”,并自号“沧洲病叟”。从绍熙三年至庆元六年(1192—1200)前后约八年,朱子大部分时间都在这里讲学和著述。
由于前有寒泉、云谷的执教生涯,其后又有白鹿洞书院、武夷精舍、岳麓书院的讲学实践,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登门求学者日渐增多,朱子考亭学派因之得到迅速的壮大。考亭沧洲精舍建成之后,曾先后就学于寒泉、云谷、武夷的蔡元定、黄榦、刘爚、林择之、詹体仁、廖德明等一大批门人弟子,又聚集考亭。据方彦寿考证,至今仍有姓名、生平仕履可考的考亭朱门弟子尚有215人。①在考亭,他们研经读史,抨击社会弊端,寻求济世良方,穷究理学奥秘,积极开展各种教学和研究活动,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考亭学派”在此最后形成,并走向成熟。
由于考亭沧洲精舍的规模比寒泉、云谷大,从学生员比寒泉、云谷要多,加上经过数十年的教学实践,朱子的教育目的论、阶段论、方法论等一系列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均已形成,因此,在书院的功能、组织形式、教学形式上比起前期来都有许多创新与发展。主要表现在崇祀先贤、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
(一)崇祀先贤与道统论祭祀、讲学、藏书刻书通常被称为书院的三大基本功能,而祭祀先贤一般不列入讲学范围之内。但考亭沧洲精舍之祭祀先贤,与讲学关系甚为密切,故在此一并提及。
尊孔祭孔,崇祀先圣先师,这在封建社会,不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是一个通例。但朱子创办的书院,除祭祀孔圣外,还开启了祭祀学派先贤的先河。淳熙六年(1179),朱子在江州(治今江西省九江市)立濂溪祠于学宫,以二程配祀。绍熙五年(1194),又将此作法引入考亭沧洲精舍。这年十二月,竹林精舍经扩建后,改名为沧洲精舍。借此良机,朱子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祭祀先圣的仪式。他釆用了释菜古礼,撰写了具体操作祭祀的仪式,名之曰《沧洲精舍释菜仪》①,以及《沧洲精舍告先圣文》②。主祀孔圣,而以颜渊、曾参、子思、孟子配祀,又以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司马光和李侗七人从祀。门人叶贺孙详细地记述了祭祀过程:新书院告成,明日欲祀先圣先师,古有释菜之礼,约而可行,遂检《五礼新仪》,令具其要者以呈。先生终日董役,夜归即与诸生斟酌礼仪。鸡鸣起,平明往书院,以厅事未备,就讲堂礼。宣圣像居中,兖国公颜氏、邯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邹国公孟氏西向配北上(并纸牌子)。濂溪周先生(东一)、明道程先生(西一)、伊川程先生(东二)、康节邵先生(西二)、司马温国文正公(东三)、横渠张先生(西三)、延平李先生(东四)从祀(亦纸牌子)。并设于地。祭仪别录。祝文别录。先生为献官,命贺孙为赞,直卿、居甫分奠,叔蒙赞,敬之掌仪。堂狭地润,颇有失仪。但献官极其诚意,如或享之,邻曲长幼并来陪。礼毕,先生揖宾坐,宾再起,请先生就中位开讲。……说为学之要。③文中记载由于条件所限,书院“堂狭地润”,所祭先贤,孔圣之外,其余均以纸牌子代替而非塑像,但献官即朱子却“极为诚意”,气氛认真而隆重。最后,朱子即席开讲,内容是为学之要,说明书院的祭祀活动是与讲学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朱子在书院举行祭祀活动,其目的是使其门人从这些先圣先贤的身上吸取教益,受到文化、道德的熏陶。更重要的是,举行这项活动,能使儒家的道统学说得到生动活泼的、立体的体现,从而使门人容易接受,取得比讲学更好的效果。朱子说:恭惟道统,远自羲、轩。集厥大成,允属元圣。述古垂训,万世作程。……维颜曾氏,传得其宗。逮思及舆,益以光大。自时厥后,口耳失真。千有余年,乃曰有继。周、程授受,万理一原。曰邵曰张,爰及司马。学虽殊辙,道则同归。①文中叙述道统自尧、舜传至孔子,中经颜、曾、思、孟发扬光大,此后道统失传,一直到北宋周、张、二程才继绝续断,道统得以重续。朱子通过书院的祭祀活动,把圣人相传的谱系和儒家正统文化精粹的传承关系演示给及门弟子,进而在他们心中扎下根来。
同时,这种祭祀活动也与朱子创建书院的宗旨或曰教育目的紧密相关。他在萌生于寒泉和武夷精舍,而形成于白鹿洞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说: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②从文中提出的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处事、接物之要而论,其大旨不离“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最终目的是希望学者能“以圣贤为己任”。③如果说,《白鹿洞书院揭示》提出了教学的目的、方法的话,那么,书院之祭祀先圣先贤,则是激励诸生勇猛奋发,走向此目的的有效方法之一。
(二)教学内容在教学内容上,朱子要求学者“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及《诗》《书》《礼记》,程、张诸书分明易晓处,反复读之”①。庆元元年(1195)至考亭问学的门人杨楫记云:先生平居教学者首以《大学》《语》《孟》《中庸》四书,次而“六经”,又次而“史传”,至于秦汉以后词章,特余论及之耳。②传统儒学都把“六经”作为书院的首要经典教材,而朱子将“四书”列为书院教材之首,一方面说明朱子是把“四书”的地位列于“六经”之上,突出了“四书”在经学体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说明他是把其哲学体系中最新、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由此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子所创书院中教学与研究紧密结合的特点,从而引导学生能站在当时学术研究领域的最前沿。
就“四书”本身的为学之序,朱子要求学生“先看《大学》,次《语》《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己,看得透彻,一生受用不尽”③。对“四书”之间的内在联系,朱子对从学于沧洲精舍的门人徐寓等作了如下的揭示: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④所谓定其规模,就是构筑以“三纲八目”为“间架”的成人教育体系。以三纲,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道德修养的方向和目标;以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修身治人的主要方法和目的。所谓立其根本,就是掌握以“仁”为核心的儒学思想,领会“操存、涵养之要”①;所谓观其发越,就是进一步发挥尽心知性的义理之学, 把握“体验、扩充之端”②;而“求古人之微妙处”,就是通过掌握孔门十六字心传之法,以道心克服人心,并求得古圣人儒学思想的极致。由于《四书 章句集注》是朱子穷毕生精力所著,因此他要求学生在熟读经文的基础上, 再读集注,并能参照经文,认真学习,用心体会。但他始终认为,学者仍应 以“四书”经文为主,《集注》次之。他以《大学》为例,对门人说:
既知工夫在此,便把《大学》为主,我且做客,听命于《大学》。③ 经文与《集注》是“主”和“客"即主次关系。
“四书”之外,《诗》《书》《礼》《易》《乐》《春秋》即所谓“六经”,以 及《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籍,两宋理学诸子周敦颐、二程、张 载、邵雍、杨时、游酢、胡安国、罗从彦和李侗等人的著作,也是书院教学 的重要课程。从朱子与其门人讲学问答的实录《朱子语类》来考察,在该书 一百四十卷中,“四书”占五十一卷,“六经”占二十七卷,历史、政治、时 事、文学等占二十一卷,理学概念如理气、性理、仁义礼智等占八卷,专人 如战国诸子老、庄、列,理学诸子如周、张、二程等占十六卷,论为学之 方、训诫门人等占十七卷。教学内容广泛涉及哲学、历史、文化、政治、经 济、文学乃至自然科学等诸多方面。
在为学内容博与约的关系上,朱子强调从约至博,再从博返约。他结合 书院的教学内容,向门人阐明为学博与约的关系是:
为学须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约,中间一节甚广大,到末梢又约。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故必先观《论》《孟》《大学》《中庸》,以考圣贤之意;读史,以考存亡治乱之迹;读诸子百家,以见 其驳杂之病。其节目自有次序,不可逾越!④
由见可此,朱子对博与约关系处理不得当的两种倾向提出批评。一种是 “多喜从约,而不于博求之”者,一种是“专于博上求之,而不反其约”者,都是片面而无益的。
(三)教学方法在教学方法上,朱子在总结前辈教育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既有所继承,也有许多创新之处。
1.学生自学自学为主,这几乎是宋代所有书院的通例,考亭沧洲精舍也不例外。朱子对从学门人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有自学的经历。朱子《沧洲精舍谕学者》一文,便是一篇鼓励和要求学生自学的演讲稿。他以北宋苏洵发愤读书,自学成才的事迹为例,对其“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贤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的苦读精神极为赞赏;但对其“但为欲学古人,说话声响”“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称赏而已”的目的则不敢苟同。因此,他要求门人在明确学习目的的基础上,按苏洵的自学方法——以二三年为期,正襟危坐,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及《诗》《书》《礼记》,程、张诸书分明易晓处,反复读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养玩索,著实行履。①在学生自己学习、钻研、体会、践履的基础上,老师加以诱导,并“证其所得而订其谬误”②。这与朱子对门人沈僴所说也是一致的: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③对自学的方法,朱子在教学中曾经有过系统的传授,他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要,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④门人辅广后来将此归纳为六条,后人通常称为“朱子读书六法”。
一是循序渐进。朱子曾举《论语》和《孟子》二书为例说,须先读《论语》,而后读《孟子》。读通了一书,而后再读另一书。以一书而言,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也是先后有序而不可乱。“凡读书,须有次序。且如一章三句,先理会上一句,待通透;次理会第二句,第三句,待分晓;然后将全章反覆紬绎玩味。”①其要求是“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渐进焉,则意定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②。
二是熟读精思。即在熟读的基础上加以认真思考。他认为“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③。“读书之法:读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读一遍。读诵者,所以助其思量,常教此心在上面流转。若只是口里读,心里不思量,看如何也记不子细。”④他对熟读的要求是“使其(指书本——编者注)言若出乎吾之口”;对精思的要求是“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只有这样读书,方能有所收获。
三是虚心涵泳。要求读书须虚心。“虚心,则见得道理明。”所谓“涵泳”,则是仔细玩味,反复体察之意。他以读《论语》为例说:“《论语》一日只看一段,大故明白底,则看两段。须是专一,自早至夜,虽不读,亦当涵泳常在胸次,如有一件事未了相似,到晚却把来商量。”⑤辅广因读《论语》太快,朱子告诫他:“若如此看,只是理会文义,不见得他深长底意味。所谓深长意味,又他别无说话,只是涵泳久之自见得。”⑥四是切己体察。要求在读书中,要将书中所说的道理,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实践相结合。即所谓“学问,就自家身己上切要处理会方是”⑦,做到“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①。所以,朱子对陈淳说:“读书,不可只专就纸上求理义,须反来就自家身上(以手自指)推究。”②五是着紧用力。即以坚持不懈、勤奋刻苦的精神读书。朱子经常教导他的弟子,读书“须是策励此心,勇猛奋发,拔出心肝与他去做!如两边擂起战鼓,莫问前头如何,只认捲将去!”“如撑上水船,方平稳处,尽行不妨。及到滩脊急流之中,舟人来这上一篙,不可放缓。”③六是居敬持志。“居敬”指的是居敬穷理,意为修身涵养与探寻物理相互促进。“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④“持志”则强调要立定志向,始终不渝。
2.先生讲学朱子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所传授的知识,多为高深的学问,抽象的哲学概念。由于他在日常教学活动中,善于运用比较浅显的口语、生动活泼的事例、通俗易懂的日常生活知识来解说,因而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一部一百四十卷的《朱子语类》,是朱子与门人问答的语录汇编,也是一部朱子言传身教的讲学实录。
朱子的讲学方式,有升堂讲学、个别辅导、集体讨论等多种形式。
(1)升堂讲学由于书院教学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传授、指导为辅,因此,升堂讲学只是根据情况偶尔为之。门人王过记沧洲精舍每天的教学生活:先生每日早起,子弟在书院,皆先著衫到影堂前击板,俟先生出。
既启门,先生升堂,率子弟以次列拜炷香,又拜而退。子弟一人诣土地之祠炷香而拜。随侍登阁,拜先圣像,方坐书院,受早揖,饮汤少坐,或有请问而去。⑤每日例行的参拜孔圣,学生向先生请安之后,接着就是“或有请问”,即有疑难问题,学生向老师求教。之后各自散去,继续自学自己的功课。可见,先生升堂讲学不是每天的必修课。
从《朱文公文集》来考察,朱子在各地学校、书院均有升堂讲学,并留下部分讲义。如在考亭沧洲有《沧洲精舍谕学者》《又谕学者》等。
从其内容来看,升堂讲学所授主要是为学之要,即涉及学习目的、方法等大的方面的问题,而较少涉及具体的某部教材的枝节问题。如《沧洲精舍谕学者》向门人传授了书院教学最重要的方法——自学,自学的内容和自学的要点,即反复诵读,认真体会,存养玩索,着实行履。《又谕学者》则着重阐述了立志的重要性,勉励诸生要贪道义而不要贪利禄,要做好人而不要作贵人。“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①因此,立志对每一位从学者而言,都是首要的、头等的大事。
从其方法来看,升堂讲学是以“答疑解惑”为主,而非满堂灌。先生根据学生所提疑难问题予以解答,如《论语课会说》,就是朱子根据学生在学习《论语》中存在的问题,集中起来加以解答,此即“会说”的意思,也就是升堂答疑解惑。
被朱子称为“会说”的升堂讲学,主要是为避免官学“师之所讲,有不待弟子之问;而弟子之听于师,又非其心之所疑”的弊病。教与学之间缺乏交流,难免造成二者之间的脱节,教非所疑,疑非所释,故“圣人之绪言余旨所以不白于后世,而后世之风流习尚所以不及于古人也”②。因此,他在书院实行的“会说”制度,是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主要目的。他要求学生能“退而考诸日用,有疑焉则问,问之弗得,弗措也”③。这与他要求学生自学,先须熟读本文,后参以集注,其原则是一致的。
个别辅导是对学生各自不同的疑点难点问题进行辅导。对学生而言,是问疑,对先生而论,则是答疑,这是朱子教学中非常重要的方法之一。其要点,将在下文专门讨论。这里,就朱子在个别辅导中的几个特点作一番探讨。一是谆谆善诱。门人叶贺孙记朱子在对黄先之进行个别辅导时,有“数日谆谆”①的记载。黄榦《朱文公行状》则称: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谕,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复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高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②表明朱子平日教导学生,谆谆善诱,孜孜不倦,以此开启门人的理解力、创造力。他经常以自身经历、体会劝诫门人,为学须专心。如:后生家好著些工夫,子细看文字。某向来看《大学》,犹病于未子细,如今愈看,方见得精切。③某旧时看文字,一向看去,一看数卷,全不曾得子细;于义理之文亦然,极为病。今日看《中庸》,只看一段子。④今日学者不长进,只是“心不在焉”。尝记少年时在同安,夜闻钟鼓声,听其一声未绝,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警惧,乃知为学须是专心致志。⑤读书或贪多求快,不求甚解,或心猿意马,心不在焉,这是许多学员的通病。对此,朱子不是采取一般的正面批评、指责,而是采用自己早年是如何克服这些缺点的经历、体会劝诫门人,使门人尤感亲切,从而在求学中得以逐渐改正。
他还把自己早年学习《孟子》的体会告诉门人:《孟子》若读得无统,也是费力。某从十七八岁读至二十岁,只逐句去理会,更不通透。二十岁已后,方知不可恁地读。元来许多长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脉络相贯串,只恁地熟读,自见得意思。从此看《孟子》,觉得意思极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①所谓“无统”,即没有系统地读,仅逐字逐句地领会,这样就无法把握各段之间相互贯穿的文意。而通过系统地把握之后熟读精思,既可领略全书的儒学思想精粹,又因之学得“作文之法”,可谓一举多得。朱子把自己的体会传授给门人,就是要门人避免走类似的弯路。
二是善于用通俗易懂的日常生活知识作比喻来开导门人。如他常以撑上水船来激励门人努力向学:为学正如撑上水船,方平稳处,尽行不妨。及到滩脊急流之中,舟人来这上一篙,不可放缓。直须着力撑上,不得一步不紧。放退一步,则此船不得上矣。②说为学贵在坚持,不可间断,以自己手臂疼痛,需不停地按摩止痛来类比:某若臂痛,常以手擦之,其痛遂止。若或时擦,或时不擦,无缘见效,即此便是做工夫之法。③比喻形象、生动,以至门人余正叔认为“擦臂之喻最有味”。又如,阐明温故知新的道理,以农夫耕田为喻。他说:子融、才卿是许多文字看过。今更巡一遍,所谓“温故”;再巡一遍,又须较见得分晓。如人有多田地,须自照管,曾耕得不曾耕得;若有荒废处,须用耕垦。④朱子在讲学中,还善于以具体的事物说明抽象的概念。如体用关系:体是这个道理,用是他用处。如耳听目视,自然如此,是理也;开眼看物,着耳听声,便是用。①譬如此扇子,有骨,有柄,用纸糊,此则体也;人摇之,则用也。②耳为体,听为用,目为体,视为用,扇为体,摇为用,这样的比喻就将本不易理解的抽象概念具体化了。
又如他对门人讲解《大学》开篇几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他说“在明明德”等三句:是大纲,做工夫全在此三句内。下面知止五句是说效验如此。上面是服药,下面是说药之效验。正如说服到几日效如此,又服到几日效又如此。看来不须说效亦得,服到日子满时,自然有效。③一个“服药”与“药效”的比喻,将大学三纲及其作用解说得明白无误且情趣盎然。曾先后从学于武夷精舍和考亭沧洲精舍的丹阳学子窦从周曾这样评价朱子的讲学效果:“读《大学章句》《或问》,虽大义明白,然不似听先生之教亲切。”④朱子还常以人的呼吸来解说动静关系。“一动一静,循环无端,所以谓‘动极复静,静极复动’。如人嘘吸:若嘘而不吸,则须绝;吸而不嘘,亦必壅滞著不得。嘘者,所以为吸之基。”⑤说仁爱之关系,认为“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⑥。
以人之两足比喻居敬与穷理:“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两足,左足行,则右足止;右足行,则左足止。”⑦三是引导门人善于使用比较的方法。
比较,是为学的重要方法之一。在讲学中,朱子曾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诫门人,要善于使用这个方法。绍熙四年(1193),他对门人林学蒙说:凡看文字,诸家说异同处最可观。某旧日看文字,专看异同处。如谢上蔡之说如彼,杨龟山之说如此,何者为得?何者为失?所以为得者是如何?所以为失者是如何?①谓如甲说如此,且挦扯住甲,穷尽其词;乙说如此,且挦扯住乙,穷尽其词。两家之说既尽,又参考而穷究之,必有一真是者出矣。②要使用比较的方法,又有一个积累的功夫,没有对历代儒学大师精辟见解的采集和吸收,比较也就无从谈起。所以,他又对门人说:寻常与学者说做工夫甚迟钝,但积累得多,自有贯通处。且如《论》《孟》,须从头看,以正文为正,却看诸家说状得正文之意如何。
且自平易处作工夫,触类有得,则于难处自见得意思。③所谓“诸家说状得正文之意”,就是历代儒家学者对经典的各自阐发。所以,通过比较、鉴别,扬长避短,择善而从,这不仅是朱子读书的重要方法,也是治学的重要方法之一。
(3)集体讨论集体讨论,是朱子在教学中着力提倡的一个方法。其基本观点为,读书应以独处为主,问学则以群居有益。他说:看文字,却是索居独处好用工夫,方精专,看得透彻,未须便与朋友商量。④有见于此,所以他提倡书院教学,以学生自学为主。但由于书院中每有诸生请问不切题,或问不到点子上,所以他又认为:群居最有益,而今朋友乃不能相与讲贯,各有疑忌自私之意。不知道学问是要理会个甚么?若是切己做工夫底,或有所疑,便当质之朋友,同其商量。须有一人识得破者,已是讲得七八分,却到某面前商量,便易为力。①学员中若有疑难,可以相互讨论,这是发挥书院群居的长处。若学员集体讨论不能解决,再来请教先生,学习效果则更为显著。这是朱子对“群居有益”的基本认识。
庆元三年(1197)从学的林夔孙,是考亭书院的堂长。一次,朱子让他安排一次集体读书活动。朱子说:可将一件文字与众人共理会,立个程限,使敏者不得而先,钝者不得而后。且如这一件事,或是甲思量不得,乙或思量得,这便是朋友切磋之义。②所谓“朋友切磋”,就是学员集体讨论。这次读书活动,先后安排了张载的《西铭》、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等,通过集体讨论和切磋,门人对《西铭》的“理一分殊”思想,以及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本体论思想都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和掌握。
从沧洲精舍的教学实践看,集体讨论有时又与升堂讲学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导师升堂讲学与学员开展集体讨论相结合的特点。
(4)随即教育随即教育指的是不在教学计划之内,而是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因偶然事件发生,在此过程中即兴发挥,对学生进行的教学活动。
《朱子语类》中这方面的记载很多,以下仅举几例。门人郭友仁记录说,有一次,受“庆元党禁”牵连而受贬谪的宰相留正来书,向朱子请教《诗集传》的几个问题,朱子把书信展示给学生看,说:他官做到这地位,又年齿之高如此,虽在贬所,亦不曾闲度日。公等岂可不惜寸阴!③这是以身处逆境中的高官,且又年处高龄之人仍奋发学习的事迹来激励门人珍惜光阴,努力向学。
门人王过记云:先生一日说及受赃者,怒形于言:曰“某见此等人,只与大字面配去!”徐又曰:“今说公吏不会取钱,为知县者自要钱矣!”节节言之,为之吁叹。①此以对贪赃枉法者的蔑视和愤慨教育门人,今后若有从政机会,应廉政爱民,不可贪赃枉法。
朱子在书院教学中,由于与门人朝夕相处,随即教育的事例是很多的。如有亲戚来求朱子荐举,他由此对门人解说了荐举须是贤才的道理②;与门人游园,说到园可荒而志不可“荒”③;从士兵耘草,快者除草不尽,而慢者仔细认真,引申说到为学须仔细,若“欲速苟简”,反而“致得费力”,④等等。
从其随即教育的事例看,概而言之,其大要不外乎可归结为“如何为学”和“如何为人”这两点上,体现了书院教学教书育人的目的。
3.教与学结合——问疑书院教学,既以“传道授业解惑”为主,则学生之问疑与先生之解惑,就成了教与学之两端。但先生对学生的问疑也有一定要求,并非不着边际地乱问一气,朱子对此的要求是学生必须对课程内容熟读精思,由此而产生的疑问,方予解答。
庆元四年(1198),郭友仁至考亭问学,“初参拜毕,出疑问一册,皆《大学》《语》《孟》《中庸》平日所疑者。”但朱子只是“略顾之”,对他说:公今须是逐一些子细理会,始得,不可如此卤莽。公之意,自道此是不晓者,故问。然其他不问者,恐亦未必是。岂能便与圣贤之意合?须是理会得底也来整理过,方可。⑤门人滕璘初见之时,“问:‘做何工夫?’璘对以未曾。曰:‘若是做得工夫,有疑可问,便好商量。若未做工夫,只说得一个为学大端,他日又如何得商量?”①甘节初到书院,即向先生询问《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质”一章,朱子不答,而对他说:不思量后,只管去问人,有甚了期?向来某人自钦夫处来,录得一册,将来看。问他时,他说道那时陈君举将伊川《易传》在看,检两版又问一段,检两版又问一段。钦夫他又率略,只管为他说。据某看来,自当不答。②朱子为何不作答呢?这是因为,他在教学中,始终坚持这样的原则,即“学者于理有未至处,切不可轻易与之说”③。像张栻那样,由于“为人明快,每与学者说话,一切倾倒说出。此非不可,但学者见未到这里,见他如此说,便不复致思,亦甚害事。某则不然。非是不与他说,盖不欲与学者以未至之理耳”④。同时,他还认为“今欲理会这个道理”即义理之学,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难之事”,而发问者“不曾用得旬月功夫熟读得一卷书,只是泛然发问,临时凑合,元不曾记得本文,及至问著,元不曾记得一段首尾,其能言者,不过敷演己说,与圣人言语初不相干,是济甚事!”⑤这样的问疑,是临时凑合的泛然发问,不着边际,“多是不疑其所当疑,而疑其所不当疑。不疑其所当疑,故眼前合理会处多蹉过;疑其所不当疑,故枉费了工夫”⑥。因此,当门人刘砺问疑《论语》《孟子》时,他说:今人读书有疑,皆非真疑。某虽说了,只做一场话说过,于切己工夫何益!⑦那么,应如何问疑,才好作答呢?朱子对门人甘节说:大抵问人,必说道古人之说如此,某看来是如此,未知是与不是。
不然,便说道据某看来不如此,古人又如此说,是如何?①朱子认为,这才是“真疑”,要达到“真疑”的水平,他认为,首先必须熟读,其次是精思,认为“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②。所以他对门人一再强调:“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③读书读到这个份上,朱子认为还是远远有够的,接下来,他告诫门人:熟读精思既晓得后,又须疑不止如此,庶几有进。若以为止如此矣,则终不复有进也。④这个过程,就是熟读精思,思而有疑的过程。朱子曾向门人描述这个过程。他说:某向时与朋友说读书,也教他去思索,求所疑。近方见得,读书只是且恁地虚心就上面熟读,久之自有所得,亦自有疑处。盖熟读后,自有窒碍,不通处是自然有疑,方好较量。今若先去寻个疑,便不得。⑤因熟读而生疑,此疑点便是窒碍不通处,知道了此疑点或窒碍不通处,“方好较量”——先生的答疑解惑作用至此方能显现出来,方能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疑难问题作出恰切的解答。《朱子语类》记有庆元四年(1198)从学于考亭的门人郭友仁的一段问疑:问:“圣门说‘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异乎?”先生笑曰:“也问得好。据公所见如何?试说看。”曰:“据友仁所见及佛氏之说者,此一性,在心所发为意,在目为见,在耳为闻,在口为议论,在手能持,在足运奔。所谓‘知性’者,知此而已。”曰:“且据公所见而言,若如此见得,只是个无星之称,无寸之尺。若在圣门,则在心所发为意,须是诚始得;在目虽见,须是明始得;在耳虽闻,须是聪始得;在口谈论及在手在足之类,须是动之以礼始得。‘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如公所见及佛氏之说,只有物无则了,所以与圣门有差。况孟子所说‘知性’者,乃是‘物格’之谓。”①儒、佛两家均言“知性”,那么二者有什么区别呢?这样的问题,须是学生在涉猎儒、佛二家典籍,熟读而精思之后方能提出,故朱子称赞他“问得好”,接着他启发学生,说说你的看法,先生谆谆善诱的辅导作用在此体现了出来。当郭友仁把他的模糊认识说出后,朱子才根据学生的想法,有针对性地区分了语出《孟子》的“尽心知性”与佛氏的“知性”的不同之处,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这一点上,朱子颇为赞赏陈淳。他对门人叶贺孙说:“漳州陈淳会问,方有可答,方是疑。”②学生经熟读精思后,产生的疑问“方是疑’’,先生“方有可答”,解惑释疑才能产生最好的效果。朱子曾反复向门人传授这一经验: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③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④到无疑处不必问,疑则不可不问。⑤至此,可将这个教学过程完整地表述为:熟读精思→思而生疑→疑而后问→问而解惑。前两条为学生根据先生布置的阅读内容,独立完成的过程,也是从无疑到有疑的过程,后两条为师生共同完成的过程,也是从有疑到无疑的过程。其总体而论,仍体现了书院教学以学生自学为主,先生讲学为辅的特点。
朱子这一教学方法,是遵循孔子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学原则。即不到学生思考问题欲通而未通之时,不去开导他;不到欲说而又说不出之时,不去启发他。程颐对此的认识是“盖不待愤悱而发,则知之不固;待愤悱而后发,则沛然矣。学者须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后为他说便好”①。以此对照朱子的教学实践,朱子对此既有继承,又有新的发展。
(四)教学安排——入学、离学与远程教学由于书院是以成人教育为主,故没有实行严格的固定学期制。门人求学,根据自己的职业、家庭以及时间是否许可等具体情况作出自己的安排,且从学时间长短不一,书院采用的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②的原则,故在教学时间的安排和方法的采用上均需随机而行。可分为入学、离学与远程教学三种情况。
对入学者,了解其学业情况、专长和兴趣,以安排其相应的课程。
如长乐(今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籍门人刘砥来学,朱子问:“曾做甚工夫?”回答说最近在读《大学章句》,但还不知从何处下手。朱子告诫其“须先操存涵养,然后看文字,方始有浃洽处”③,若只在字里行间求索,不从自己心里下功夫,体察涵养,则无法做到融会贯通。庆元三年(1197)三月,正值“伪学之禁”风声正紧之时,江西门人曾祖道来到考亭。朱子询问其学业,了解了他曾先后从学过刘清之和陆九渊,知其“道问学”的功夫不够扎实,看书太快,不求甚解,因劝其在熟读精思及修身穷理上下功夫。④除了对初入学者有耐心询问,精心安排外,对相隔一段时间,再次来书院问学的门人也要向其了解学业进展的情况。如曾多次从学朱子的兴国门人万人杰去后复来,见面,朱子即问其“别后工夫”如何,人杰回答,回去后谨按先生的教诲和安排,“知先生之道,断然不可易。近看《中庸》,见得道理只从下面做起,愈见愈实”⑤。于是,朱子又将时学故意将“道”说得高妙深奥,使人无法理会的弊端作了一番批评,指出“二程说经义,直是平常,多与旧说相似”,并不以标新立异欺世,只是“意味不同”而已。①同时,对万人杰喜与“众说相反”的毛病予以指正。
类似于万人杰这样再次问学的,如莆田门人郑可学,江西南城门人包扬、临海门人潘时举等,均有“再见,请教”②,或“久不相见,不知年来做得甚工夫”③、“子善别后做甚工夫”④的询问。
对暂时离学者,根据其在书院学习的具体情况,安排其离学后继续学习的课程,以保持其学习的延续性。如曾祖道拜别,朱子告诫他:归去各做工夫,他时相见,却好商量也。某所解《语》《孟》和训诂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为咀嚼过。此书,某自三十岁便下工夫,到而今改犹未了,不是草草看者,且归子细。⑤就是命其回家后,认真学习《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若有疑处,日后可问。
兴国门人吴必大从书院暂归,拜别时,朱子对他说:“所当讲者,亦略备矣。更宜爱惜光阴,以副愿望。”又说:“别后正好自做工夫,趱积下。一旦相见,庶可举出商量,胜如旋来理会。”⑥同卷记黄?、吴必人与万人杰告辞,朱子询问别后欲读何书,告以欲先读《易》后学《诗》。朱子根据先易后难的原则,认为应改为先读《诗》,后学《易》;并告以学《诗》的方法,不要被《毛诗序》中“以史证诗”的“旧说粘定”,“不可于名物上寻义理”,《诗》之外,“《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四书,自依次序循环看”,史书如《资治通鉴》等“亦不可不看”。⑦以上诸人之外,临别请教的门人还有余大雅、潘时举、杨道夫、石洪庆、暧渊、丘玉甫、林叔和、廖德明、徐元明、魏椿、辅广等。《朱子语类》中分别记载了朱子对他们别后,勿荒废学业,继续努力的期盼。由此表明学员因故暂时离学,并非学业的中断,而是书院学习的另一种形式的延续。
对外地暂时不能前来面授的门人,要求他们在自学的过程中,写信前来问疑,以便进行远程函授教育。
如门人辅广在考亭面学三月,辞归之日,朱子对他说:“有疑更问。”辅广回答:“今亦未有疑。自此做工夫去,须有疑,却得拜书请问。”①南康门人黄灏(字商伯)离学后,曾多次来信问疑,朱子对其问《丧礼》,曾连续复函三通。朱子《答黄商伯》对其问《大学》《中庸章句》中相关的几个疑难问题一一作了函复。②漳州朱飞卿来书请问持敬、穷理、诗传等,朱子一一予以答复。从《答朱飞卿》书看,朱飞卿问疑原文亦载,即一段学生问疑之后,就是一段先生的回答,应是当时朱子直接在问卷中的批示。③顺昌廖德明是先后曾从学于朱子创建的四所书院的门人之一,《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有《答廖子晦》书十八通,内容均为问疑。其中在书一、书二、书三、书五、书十四、书十五、书十八中,廖德明的问疑原文具录,内容也是一问一答,是古代书院典型的远程函授教育的原始资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书十一,这是一通长卷,内容为李唐臣问《伊川易传》之疑。可分为五段,一、三两段为唐臣所问,二、四两段是德明答疑,第五段为朱子总评。李唐臣可能是廖德明在广东讲学之时招收的弟子,廖德明在答疑之后仍觉未安,故将长卷呈寄朱子,再作批注。故此长卷,是由师生三代人共同完成的,这在朱子所有的函授信件中,是一个罕见的特例。
从《朱文公文集》全面考察,朱子撰写的书信写给门人的有一千六百多通。在从学考亭的二百一十五位门人中,朱子与他们有书信往来的有九十七人。其中数量最多的如蔡元定、黄榦等多达一百多通;其余多则十几通,少则一二通不等。内容除了时政、学术讨论、专题研究、往复论辩、图书校勘、师友问候之外,还有两百多通是为门人答疑解惑的内容。这些书信,或为长卷,或为短札。其中有十几通长卷文字多达数千言,甚至近万言。如《朱文公文集》卷五十七《答陈安卿》书一至书三,卷六十《答潘子善》书六,卷六十一《答欧阳希逊》书二,卷六十二《答李敬子余国秀》,卷六十三《答郭子从》书一、《答胡伯量》书一;《朱文公续集》卷九《答刘韬仲问目》、卷十《答李继善问目》等。
这部分答疑书札,有的学生问疑原文具在,有的虽无原文,而以“来书云”或“来喻”概括来信所示之疑,而后解答。此即朱子《答林德久》所言“所示疑义,各附鄙说于其后”①,《答黎季忱》“示及两卷,各已批注封还”②之意。从这些问疑书札看,内容广泛涉及传统儒学、朱子理学的各个层面。因此,对朱子这部分书信,既可看成是书院远程函授教育的原始信札,也是研究朱子理学思想发展的重要史料。
附注
①方彦寿:《朱熹考亭沧洲精舍门人考》,《朱熹书院与门人考》,第133-224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九《沧洲精舍释菜仪》,《朱子全书》第23册,第3367-3368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六《沧洲精舍告先圣文》,《朱子全书》第24册,第4050—4051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十《礼七•祭》,第2295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六《沧洲精舍告先圣文》,《朱子全书》第24册,第4050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白鹿洞书院揭示》,《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87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学二·总论为学之方》,第133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沧洲精舍谕学者》,《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93—3594页。
②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二《集部一·楚辞辨证二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79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四《大学一·纲领》,第249页。
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四《大学一·纲领》,第249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九《论语一·语孟纲领》,第444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九《论语一·语孟纲领》,第444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九《朱子十六•训门人七》,第2878页。
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第188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沧洲精舍谕学者》,《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93—3594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沧洲精舍谕学者》,《朱子全书》第24页,第3594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三《学七·力行》,第223页。
④〔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十四《行宫便殿奏札二》,《朱子全书》第20册,第668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第189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读书之要》,《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83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学四·读书法上》,第168页。
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学四·读书法上》,第170页。
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九《论语一·语孟纲领》,第434页。
⑥〔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九《论语一·语孟纲领》,第434页。
⑦〔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学四·读书法上》,第161页。
①〔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二十九《朱熹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769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第181页。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学二·总论为学之方》,第137页。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学三·论知行》,第150页。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七《朱子四·内任》,第2674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又谕学者》,《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94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论语课会说》,《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85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论语课会说》,《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84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九《朱子十六·训门人七》,第2876页。
②〔宋〕黄榦:《勉斋集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朱子全书》第27册,第563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第2611页。
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第2611页。
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第2618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五《朱子二·论自注书》,第2630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八《学二·总论为学之方》,第137页。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朱子十八·训门人九》,第2948页。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四《朱子十一·训门人二》,第2753—2754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性理三·仁义礼智等名义》,第101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性理三·仁义礼智等名义》,第102页。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五《大学二·经下》,第308页。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四《朱子十一·训门人二》,第2768页。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二《学六·持守》,第219页。⑥〔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六《性理三·仁义礼智等名义》,第118页。⑦〔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九《学三·论知行》,第150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第2615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第192页。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朱子十四·训门人五》,第2807页。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朱子一·自论为学工夫》,第2615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朱子十八·训门人九》,第2931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六《朱子十三·训门人四》,第2794页。
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朱子十八·训门人九》,第2947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七《朱子四·内任》,第2673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七《朱子四·内任》,第2672页。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朱子十四·训门人五》,第2810页。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朱子十八·训门人九》,第2947页。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六《朱子十三·训门人四》,第2803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八《朱子十五·训门人六》,第2843—2844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五《朱子十二·训门人三》,第2785—2786页。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胡氏门人·张敬夫》,第2605页。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胡氏门人·张敬夫》,第2605页。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朱子十八·训门人九》,第2918页。⑥〔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朱子十八·训门人九》,第2927—2928页。⑦〔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九《朱子十六·训门人七》,第2872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五《朱子十二·训门人三》,第2786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学四·读书法上》,第168页。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学四·读书法上》,第168页。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学四·读书法上》,第168页。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第186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释氏》,第3020—3021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朱子十四·训门人五》,第2833页。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一《学五·读书法下》,第186页。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学四·读书法上》,第163页。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朱子十八·训门人九》,第2931页。
①〔宋〕朱熹、吕祖谦:《近思录》卷十一,《朱子全书》第13册,第271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六《朱子三·外任》,第2655页。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九《朱子十六·训门人七》,第2871页。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六《朱子十三·训门人四》,第2799页。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五《朱子十二·训门人三》,第2769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五《朱子十二·训门人三》,第2770页。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八《朱子十五·训门人六》,第2839页。③〔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九《朱子十六·训门人七》,第2869页。④〔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四《朱子十一·训门人二》,第2761页。⑤〔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六《朱子十三·训门人四》,第2799页。⑥〔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朱子十四·训门人五》,第2811页。⑦〔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朱子十四·训门人五》,第2812—2813页。
①〔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三《朱子十·训门人一》,第2747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六《答黄商伯》,《朱子全书》第22册,第2128—2133页。
③〔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答朱飞卿》,《朱子全书》第22册,第2673—2675页。
①〔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一《答林德久》,《朱子全书》第23册,第2937页。
②〔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二《答黎季忱》,《朱子全书》第23册,第3006页。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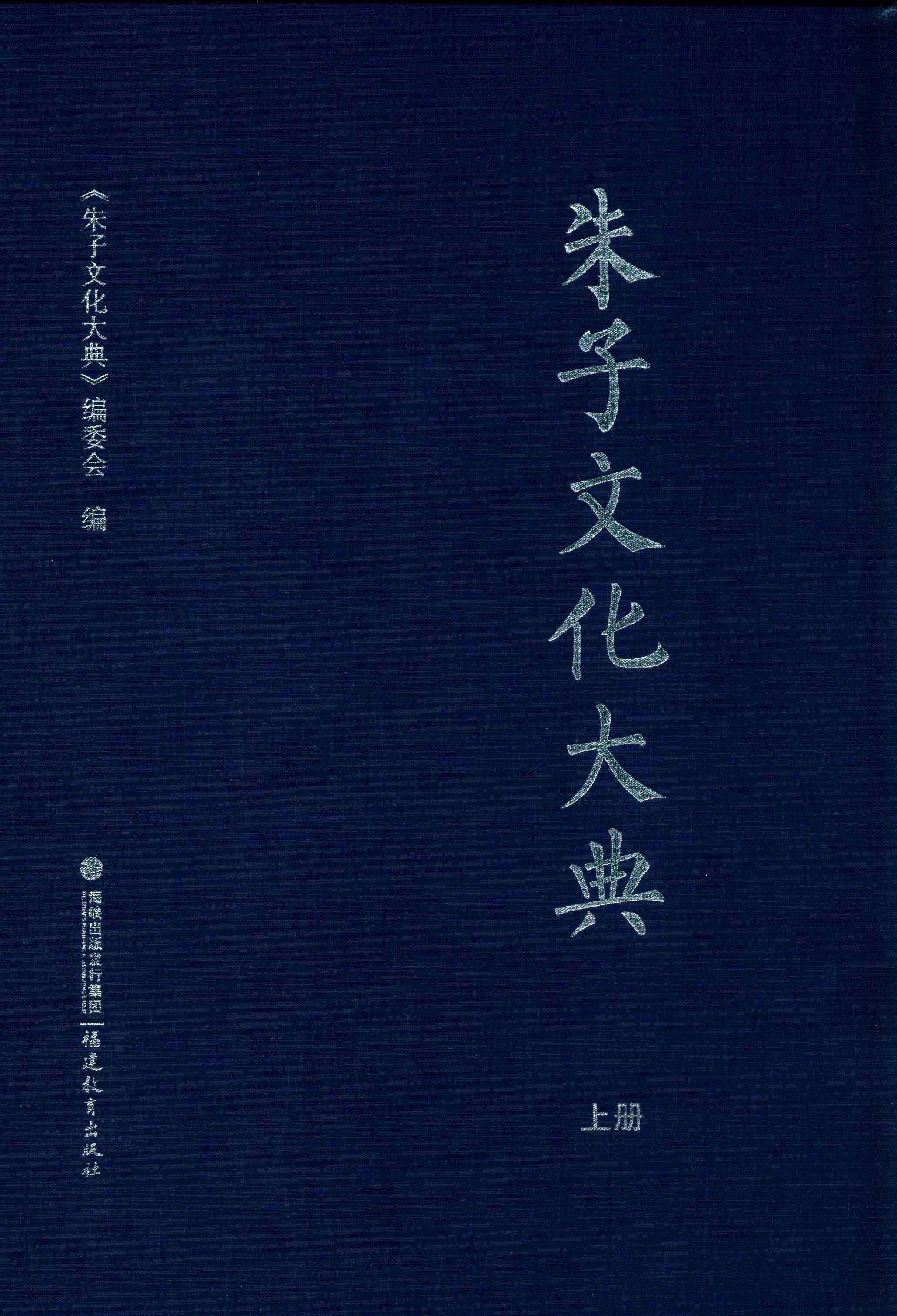
《朱子文化大典 上册》
出版者:福建教育出版社
朱子文化大典介绍了朱子生平,包括家世、从学、讲学、论道、政绩等内容。 朱子文化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关于构建中国古代社会道德秩序和普遍价值体系的理论学说。它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为构建社会道德秩序和普遍价值体系提供理论依据,二是为建立社会道德秩序和普遍价值体系提供历史根据,这就是儒家的“道统”。二者共同构成了朱子文化的所有内容,涵括了儒家的哲学及其历史文化观。
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