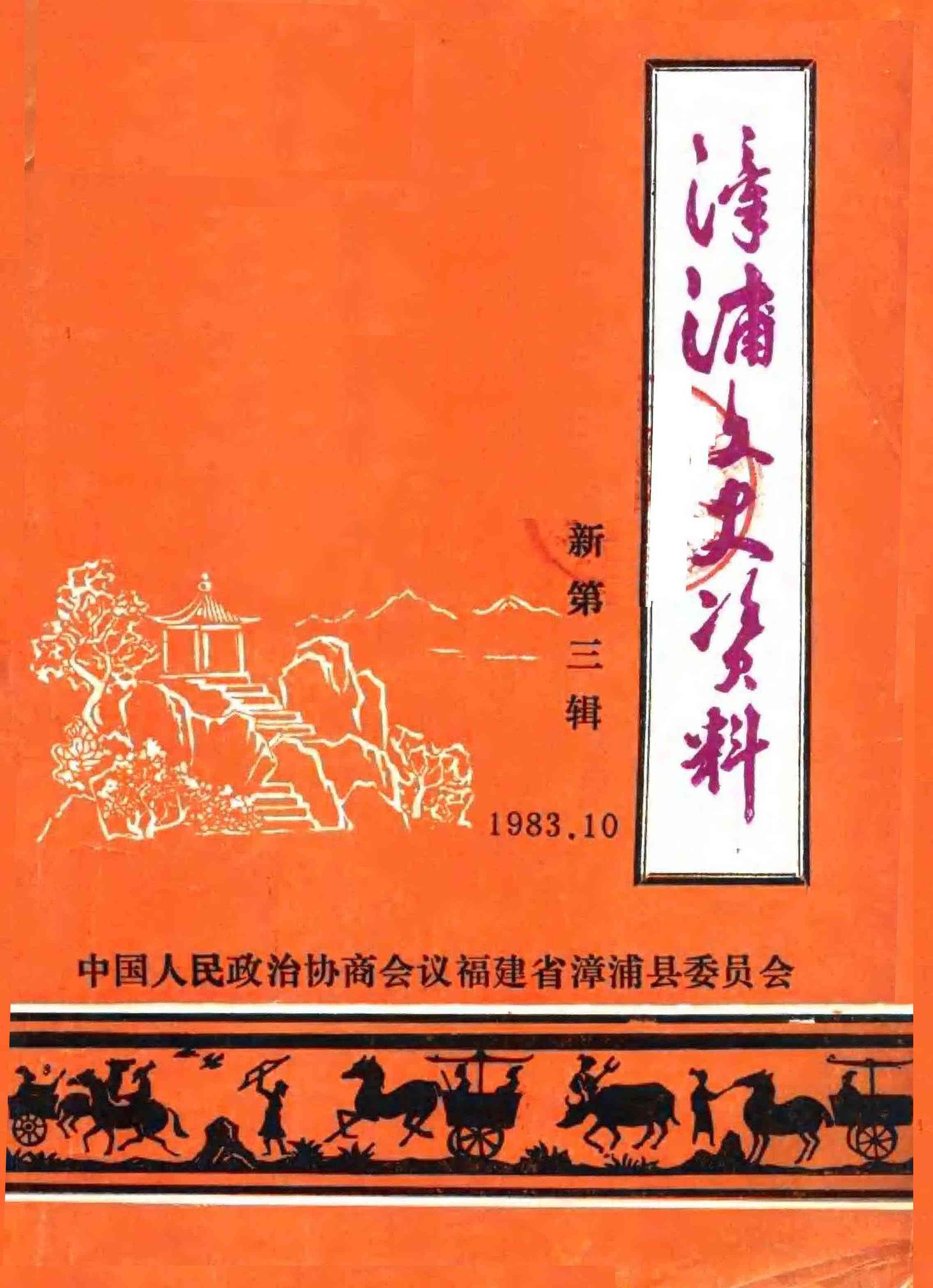杨胜
| 知识出处: | 《漳浦文史资料新第三辑》 |
| 唯一号: | 130730020230001711 |
| 人物姓名: | 杨胜 |
| 文件路径: | 1307/01/object/PDF/130710020230000020/001 |
| 起始页: | 0037.pdf |
| 性别: | 男 |
| 时代: | 清 |
| 出生年: | 1911 |
| 籍贯: | 漳浦佛昙 |
| 亲属: | 杨红鲳;杨高金;杨乌仙;杨暹水 |
传略
杨胜,漳浦佛昙人,1911年生于佛昙白石前社。那村子是一个贫穷的半岛。由于穷,农民大多出外谋生。到了明朝末年,传入了布袋木偶戏,演木偶戏就成为当地农民谋生的一种手段。他们是木偶世家,曾祖杨乌仙自幼随“福春派”布袋木偶名艺人学艺,开创了杨家布袋木偶戏事业。祖父杨红鲳继承父业,发扬光大,曾名噪一时,至今家乡还有“米缸扫空空,也要看红鲳布袋翁”的传说。到他父亲这一辈,更是誉满闽南和台湾。父亲杨高金被称为“戏状元”。他以武打戏见长,每逢演出,总是座无虚席。当时家乡老幼都会念:“高金布袋戏,一坪(演一台戏)五块四……”。叔叔杨暹水也是布袋木偶戏名家。他以抒情为拿手好戏,喜怒哀乐,皆能感化观众。
由于家传的关系和环境的熏陶,他自幼就酷爱演木偶戏。据说,他四岁时就能用番薯仿造戏中人物,用长板凳为舞台演给小朋友看。父亲觉得只有他能继承杨家木偶艺术技巧,于是带领他串村游乡,到处“耍木偶”。这样,一个七岁的娃娃就走上了演布袋戏的道路。他聪明好学,加上父亲的严格管教,很快就出了名。当时,龙溪一带的人都管叫他为“童子师傅”。
他十四岁时便应聘到同安县一个布袋戏班当“头手师傅”(主演)。临走时,父亲特地送他两句话:“眼睛是师,到处为徒”。这赠言后来成为他艺术上的座右铭。他也常用这两句话教诲自己的学生。同时勉励他们:艺术上要精益求精,爱友尊贤,虚心学习。而他自己,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在布袋木偶戏界,他属“全”字辈,因此他主持的戏班取名“全福春”,他学的是北派的手法,这同晋江地区的“南派”布袋木偶,分属两大流派。
在旧社会,艺人们为了饭碗,有门户之见,艺术上互不往来。有一次,同安县某家财主为了显示自己的阔绰,特地从泉州请来南派木偶戏班,要他们同他唱对台戏。这实际是赛戏,胜负关系到名声和饭碗的问题。
两台布袋戏都拿出本领,连赛了好几个通霄,弄得声哑力竭。他当年仅十四岁,体力不支,况且未曾经历过这样的场面,眼看自己台下观众稀落,喝倒彩和起哄之声不绝于耳,一气之下,口吐鲜血,倒在台上。
那时,艺人们最大的耻辱莫过于赛戏败北。他对这个教训耿耿于怀,牢记一辈子。不过,他能正确对待挫折。失败了,鞭策他更虚心地去学习。每当他回忆起这桩往事,总是意味深长地说:“我功夫不如人家,才有这次终身难忘的教训”。
从那以后,他便辞去戏班工作,决心要把南派艺术学到手。可是在旧社会,有艺术才能保住饭碗,谁肯轻易把自己的功夫传给外人,何况又是不同流派。要拜师也无门可进。他求学心切,就想办法“偷戏”。他成天跟着南派戏班转,在台下边看边悄悄地学,后来渐渐和戏班的人混熟了,但话头一转到戏中某一动作时,常常是所问非所答,总是解不开某些诀窍之迷。那戏班的主演是老艺人“撮师”,这位南派木偶表演艺术家身怀绝技,却孑然一身,无依无靠。为了向他学艺,他曾在经济上帮助他,这使他受了感动,兴致一来就道出南派艺术中许多动作的要领。
数年后,他外出演戏,偶然听说“撮师”病得很厉害,就赶去探望。在旧日社会,艺人的技艺再高超也没人看得起,“撮师”老来穷困潦倒,一无所有,三餐难度,病得奄奄一息。他目睹如此惨境,毅然把他接到戏班中奉养,为他捧汤熬药,伺候饮食,胜似亲骨肉。老艺人见他诚实,知道敬老尊贤,在弥留时,想到自己还有绝艺未传,于是就传给了他。他兼收并蓄南、北两派的布袋戏艺术精华,自然更有成就。
虚心好学,锲而不舍是他的一贯精神。他不但从不同木偶流派中学习别人的精华,还善于吸取其他剧种的艺术营养。解放后几次全国性戏曲汇演,他看了许多戏剧名家的精湛表演,眼界大开,每次观剧回来总兴奋地说:“我又学到好几着!”
当年,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先生,看了他的戏,称赞木偶能逼真模仿人的动作,演得栩栩如生,引人入胜,真是不容易。著名京剧名丑肖长华老先生在华东戏剧汇演中,看到他的《蒋干盗书》,对木偶丑角蒋干的细腻表演赞不绝口。演出后,肖老先生就找他交流演丑角的经验,两人促膝交谈,相见恨晚。素有江南活武松之称的盖叫天老先生在看到他的《雷万春打虎》一剧后,谦逊地对他说:“你的打虎动作,我可学了好几着。”其实他也从京剧学到了许多表演程式,把它融化在木偶的程式之中。正由于能兼收並蓄,熔各家之长于一炉,独树一帜,形成他别具一格的布袋本偶戏的表演艺术。
他的木偶艺术能有较深的造诣,主要还是解放后的事。这首先要感谢党和国家对木偶艺术的高度重视。解放后,他才有机会走出“洞门”,曾四次出国访问演出,观看了东西欧许多名家的木偶表演,进一步开阔了眼界。在访问演出期间,他因我国木偶艺术深受国外观众的欢迎和高度评价而引为自豪。每次演出后,观众总久久不散,有的要签字留做纪念,有的要合个影以示友谊,有的要求面授木偶艺术的机宜,他忙得不亦乐乎,回到旅馆中也不得安闲,常常刚刚脱下衣服,就有记者或艺术家登门拜访,如是数次,总是接应不暇。
有一次是在某大国戏剧家协会主持的招待演出会上,观众都是些艺术界名流。当最后一剧幕落,艺术家们蜂涌而上,把舞台挤得水泄不通,要想弄清演员手上和木偶身上藏有什么“机关”。解释无效,对方终于派出代表,从演员的双手到木偶头上下,都做了一番细致的检查。在确实找不出“秘密”之后,他当众套上两个木偶,给他们来一出木偶绝招,单人双手同时表演两个不同性格人物的戏。一个小旦是如此娇媚温柔;另一个小丑却是那样滑稽可笑。这时,那些“名流”才感慨地说道:“神手,神手!”苏联著名木偶艺术大师阿布托拉夫在报纸上著文说:“当时我们都看呆了,感到吃惊,他(指杨胜)不愧是一个木偶大师”。闻名全球的艺术大师卓别林曾看过他的演出,在卓氏的传记中也有着他深爱中国木偶艺术的记载。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虽然他的木偶表演艺术被国外艺术家称为“大师”,为国内同行公认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但他始终坚持练功和演出,凡是和他在一起工作过的人都知道他身边有两件宝:一是镜子,二是木偶。一有时间就对镜自练,从不间断,並且每出戏演完后都要认真听取意见,不断总结提高,即使在出国最繁忙的活动中也不倒外。《雷万春打虎》一剧是他的拿手好戏。为了塑造老虎的形象,为了追求老虎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境界,他找过很多画册,到动物园去观察老虎生活习惯,还找家猫模拟,又从许多猎虎的猎户中去探问、研究。可以说,他演的虎戏已经是无可挑剔的了。因此此剧曾获得国际第二届木偶联欢节比赛金质奖,他的表演艺术同时获得一等金质奖章。然而在法国巴黎的一场演出中差一点出纰漏。当戏中英雄雷万春第二次和老虎交锋时,老虎正要反扑过来,不料老虎的一只脚被紧紧卡在木偶台板的夹缝中,无法动作。“糟了!”在旁的演员无不惊呆了。他两手操着一人一虎,没法腾出手来拨虎脚,急忙向助手递个眼色,同时机灵一动,又使雷万春和老虎都按地做了微微喘气的动作,来个“缓兵之计”。这时台下掌声雷动,把台上的人都搞懵了。“是喝倒彩吗?”戏一结束,他便在镜子前重复刚才的动作,仔细推敲。人虎酣战了一阵子,双方停下喘气,伺机再斗,符合情理,所以观众鼓掌叫好。此后,这一即兴创作便正式编入虎戏的动作程式。
他一生中常引为自豪的事有两件:其一是,他主演的优秀传统剧目《雷万春打虎》和《大名府》曾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国际第二届木偶联欢节上赢得了金质奖,他也同时荣获一等表演金质奖章,为祖国争了光;其二是,他为新中国培养一批优秀的木偶演员。
为了培养新一代木偶接班人,1955年,他从漳浦调往北京中国木偶剧团任教,后因组织需要,又放弃留在北京中国木偶剧团工作的机会,情愿调回漳州从事木偶艺术教育。当时,龙溪初创艺术学校,条件差,生活艰苦,设备简陋,他从不计较这些,自编教材,白手起家,为国家培养近百名木偶演员。他时时记住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应该大公无私,一切以党的利益为重,把解放前经历多少艰辛才学到的绝艺,毫无保留地教给自己的学生。
“玉不琢不成器”。这是他教导学生时常引用的一句格言。他以治学严谨著称,每一基本功都要求一丝不苟,每一高难度动作都要练到娴熟为止。他凌晨即起,习惯地泡上一壶浓茶,然后指导学员练功,有时他的老胃病一发作,痛得额上直渗汗,他就一手顶着胃部,给学员们讲解动作要领,直至上完课。
学员中数二弟杨烽年龄最小,只十二岁,他常常练得两臂酸痛,双手麻木,连吃饭拿筷子时手还一直在颤抖着。他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对二弟说,以前艺人是为了饭碗不得不练就一手硬功夫,现在条件好,国家每年给学校和剧团提供大量经费,吃穿不愁,有专职教师,不能辜负国家对年青一代的期望。他还开导大家,说他小时候缺吃少穿,演戏时睡庙角地板,每天都要在父亲的严厉督促下练功,稍有差错就挨打,父亲为了促使他练手艺,数九寒冬,大清早就把他双手浸在冰冷的水中,手冻疆了,身上打哆嗦,即使是懒汉,也得出力气才可驱寒怯冷。他练着功,一两个钟头后,父亲来检查,摸摸他的手,只要手心是温暖的,就说明练了功,否则,可就该打了。他感慨地对孩子们说:“要不是你们爷爷的严格雕琢,我哪有今天的艺术!
虽然他的木偶艺术曾三次被纪录成电影,但到了晚年,他一直为我国还没有一部较完整的布袋戏艺术教材而叹惜,而着急。因此在工作之余,他就戴上老花眼镜,翻阅国内外资料,摸索木偶艺术的教学规律,想在有生之年,为布袋戏艺术著书立说。正当他壮志凌云之际,林彪、四人帮的祸害冲毁了他的宏愿。他受到了难以言喻,也不言而喻的冲击,但依然坚信马列主义和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一定胜利,木偶艺术复兴之日将会来临。
文革期间,他逃回家乡避难,曾设想在家乡办个木偶班,但心愿未遂,又被造反派抓回漳州。
当他被迫退职,住院治疗期间,他仍一心惦念着木偶事业的发展。每逢二弟杨烽去医院,他还是三句不离本行,关心剧团演出情况,念念不忘文革前夕已准备好出国的剧目《卖马闹府》《岳云保家乡》。他语重心长地对二弟说:“那些传统剧目都是木偶艺术的精华,我如果病好了,还要整理。如不准我演戏,我可以在家里指教后生们。万一我死了,一有机会,你要排演下去,还要继续创作新的。”这一席动人肺腑的叮嘱,真要催人泪下。
病情稍有好转,他便硬撑着坐在床上,伸出那瘦如枯枝的手,久久端详,自言自语地说:“指头要硬了!”说完就用力扳手指,使劲地压在床沿,接着做甩指功,然后认真地做了几个“亮相”。他的脾气我们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劝阻的。只有护士送药时劝说几句,他才勉强躺下。
但是,由于身心都受到摧残,就在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三日,他含恨地与世长辞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和人民推翻了“四人帮”作乱中强加给他的一切污蔑之词,龙溪地委为他彻底平反昭雪,並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中央文化部、全国文联、中国对外友协及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同志等都送来了花圈和唁电。《福建日报》报导了消息。不久,他的学生、日本木偶艺术家宫原大刀夫不远万里来漳州拜谒他的骨灰。党和人民及国际友人没有忘记他,虽然他已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但是他所播种的国际友谊之花开得更鲜艳了。他的高贵品德,他的艺术青春浩然长存。
知识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