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到人
| 内容出处: | 《東山岛文史第25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30004262 |
| 颗粒名称: | 从神到人 |
| 其他题名: | 东山关帝庙《公立关永茂碑记》考析 |
| 分类号: | K295.7 |
| 页数: | 14 |
| 页码: | 91-104 |
| 摘要: | 本文主要探讨了东山关帝庙《公立关永茂碑记》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和历史意义。文章从历史、地理和人文的角度,揭示了铜山人民在清初政治、军事与户籍赋役制度变革中的艰辛历程,以及关帝信仰在其中的重要地位。 |
| 关键词: | 东山关帝庙 碑刻 考析 |
内容
摘要:东山关帝庙《公立关永茂碑记》,记载着清初朝廷不把铜山人纳入户籍,而铜山人统一认关帝为祖,以虚拟的“关永茂”为户主入籍,获准后聚众于庙内订公约,立碑石。虽为公约,字里行间却隐藏着铜山人鲜为人知的血泪史。自立碑之时起,关帝始“从神到人”,成为铜山人的祖先。这种返祖现象便赋予碑刻更为深刻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意义。它是中国民间关帝信仰中返祖现象的典型代表,是中国民间信仰文化中不可多得瑰宝,也是研究中国民间信仰、清初政治、军事与户籍赋役的珍贵实物资料。对于铜山,它是关帝信仰划时代的里程碑,标志着铜山关帝信仰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更高境界。
关键词:东山关帝庙,碑刻,考析
东山关帝庙,原称:铜山关帝庙,位于东山县铜陵镇东部的岵嵝山腰,依山而筑,濒临大海,气势磅礴。该庙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具有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而且是台湾众多关帝庙的香缘祖庙。该庙于1996年11月20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庙内有数通明清时期的碑刻,其中《公立关永茂碑记》为《台湾外记》作者江日升所撰。因内容仅为一则乡里公约,碑文少有剔藓描丹,碑前又长年放置他物,故很少引人瞩目,更不要说加以研究了。数年前,笔者在建立文保单位档案时拓下了碑文,仔细辨读,颇觉字里行间,大有文章。本文则根据已有的相关文献,对该碑作一番考析,试图揭示其立碑的历史背景、历史原因、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意义,并以此请教于诸位方家。
一.公立关永茂碑记
《公立关永茂碑记》立于东山关帝庙二进东侧回廊,镶嵌于廊壁之上。石碑材料为花岗岩,通高228、宽89、厚19厘米。碑首委角,边饰回纹,额书:“公立关永茂碑记”。碑文竖行楷书阴刻,共19行,计617字,字迹清晰可辨。碑心留有两个浅坑,据说是抗战时期日本轰炸留下的弹片痕迹,使碑文至少有15字缺失。现将碑文照录如下,以供参考:
公立关永茂碑记
考之上世,吾铜乃海外岛屿,为渔人之寄足,民未曾居焉。迨明初,江夏侯德兴周公沿边设立,以此壤接粤境为八闽上游之要区设为所,以铜山名之,调兴化莆禧众来守此城。官与军咸袭封,是为军籍,里甲丁粮,世莫之闻。至国朝定鼎,凡天下卫所仍旧无易,惟闽地炽於海氛故弃之。是有籍反散而为无,天下岂有无籍之人乎?故莘庵陈公於康熙四十年将铜地户口编入黄册,而铜自此有丁粮之事焉。然泛而无宗,傍人门户实非貽燕善策。
因闻诏邑有军籍而无宗者,共尊关圣帝君为祖,请置户名曰:“关世贤”,纳粮输丁大称其便。五十年编审公议此例,亦表其户名曰:“关永茂”,众咸为可,遂向邑候汪公呈请立户。蒙批准关永茂顶补十七都六图九甲,输纳丁粮不但得画一之便,且幸无他户相杂,是散而复聚,无而又有,将来昌炽可甲於前第。迩因查县府司户册有一户“关永茂”,即黄启泰等,其间大有移花接木、藏头露尾之虞。夫事方三载即如此互异,又安能保其后来不无舛黠辈从中滋弊,蚕我子孙乎?於是公诸全人,当神拈阄,分为七房。小事则归房料理,大事则会众均匀。叔伯甥舅,彼此手足,并无里甲之别,终绝大小之分。不得以贵欺贱,不得以强凌弱,苟有异视萌恶,许共鸣鼓而攻,此方为无偏无党,至公至慎。爰立石以垂不朽。
大房:游继业、游琨玉、吴葛□□□□□江欧□□绍宗、蕃衍、洪庄文、桑傅谢康范苏
二房
三房:郑禎吉、唐绵芳、李玉承□□□廖光彩、吴日新、何兴隆、田兴邦、张发祥
四房:陈思明、思聪、温思、恭思□□敬、思问、思难、思义
五房:姚嘉謨、翁万年、蔡□□□马栋、崔国禎、朱天庆、孔阳、曾徐郭龚沙董杨颜詹石顾
六房:林世发、世强、纪刚、世毅、发祥、发端
七房:黄士温、士良、士恭、士俭、士让
康熙五十二年岁次癸巳阳月级旦
珠浦东旭氏江日升撰
撰碑者江日升,不愧为《东平纪略》、《台湾外记》的作者,笔力不凡,言简意赅,短短六百余字碑文,却包含了太多的信息。它涉及铜山(今东山县铜陵镇)历史、地理与人文,揭示了立碑的历史背景与历史原因等等。尤为精彩的还在于碑题,本来这仅仅是一则民里公约,却不拘泥于习惯格式,抓住事件的中心,以“关永茂”点题,赫然醒目,发人深思。虽无明言,却已强烈地暗示着一种饱受磨难、飘忽迷茫中寻找归宿的深深渴望、一种久远而深厚的虔诚信仰。这两点在后面还会述及。
碑文云:“迩因查县府司户册有一户“关永茂”,即黄启泰等,其间大有移花接木、藏头露尾之虞”。此应为立碑的近因,同时也一语道破了清代初期户籍与赋役制度的弊端。
户籍与赋役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清虽承明制,但并非一承不变。例如,明代及清顺治初,军籍人丁并不交纳丁银,也不编审。“军丁的编审之例始于顺治十二年(1655)”。[1]是年饬令各卫所闲丁,按年编审纳银为帮贴之费。康熙十三年(1674),三藩之乱,军费开支浩大,清廷为筹饷,将军丁编审范围扩大到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省。四年后,江西、广东、浙江、福建、湖广也接到命令,“将卫所屯丁亦照州县人丁例一体编征”。[2]。
这一变化,对当时以军户为多数的铜山人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铜山自明初设守御千户所,“调兴化莆禧众来守此城。官与军咸袭封,是为军籍,里甲丁粮,世莫之闻”。[3。]要命的是朝廷在这里并没有实行“卫所屯丁亦照州县人丁例一体编征”的政策,而是干脆削去军籍,又按旧例不编入民籍。故有“是有籍反散而为无,天下岂有无籍之人乎?”,[4]的悲叹。铜山遂成了大清的弃民,走投无路,前景渺茫。
直到康熙四十年(1701),知县陈汝咸才将铜山(时隶属漳浦县)统为一户,以寄户的形式入册。据载:“陈汝咸,字莘学,号心齐,鄞县人。康熙辛末进士。三十五年由翰林庶吉士出知漳浦。以浦邑赋役不均,定二百家为一保,保二十甲,户实其丁口。编审日,通计阖县城丁若干,均编足额,立亲供单,每户田粮各填注实产,分限自封投柜。根租一田三主,详定大租,量给价值,田归业主,于是奸胥无所飞洒,强宗巨猾无所隐占诡寄包收,哀户孱民无所赔累。自明季来百余年积弊一清。”,[5]然而,此非长久之计。因为“并诸户而统为一户,遇编审之年,所谓亲供皆里长一人所自造。……其有势之人,必寻有里长衰弱之图立户,谓之顶班。无势者虽田连千顷,不得不受人节制,至单寒小姓,更无论矣!……完粮必经伊手,每丁必多收一二钱,每亩必多收四五分,皆相习为固然,……户内殷实与谨厚之士皆被其累。”[6]然而,此时的铜山实际上尚无真正属于自己的户籍。故碑文云:“泛而无宗,傍人门户实非貽燕善策。”最终,竟然以关帝后裔“关永茂”为户主,统铜山各姓为一户,呈请编审,且获准“关永茂顶补十七都六图九甲,输纳丁粮不但得画一之便,且幸无他户相杂,是散而复聚,无而又有,将来昌炽可甲於前第。”[7]从此,铜山人民不再是遭人歧视与蹂躏的弃民。
品读碑文,知作者有过人的文笔、学识与才华。但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不能不对碑文中两处笔误作一校正。碑文:“故莘庵陈公於康熙四十年将铜地户口编入黄册”的莘庵陈公,指的是时任漳浦知县的陈汝咸。《漳州府志》载:“陈汝咸,字莘学,号心齐,鄞县人。”《漳浦县志》、《铜山志》等也有相同记载。可见“莘学”是陈汝咸的字,并且是“莘学”而非“莘庵”。
另外,“康熙四十年将铜地户口编入黄册”之说可能有误。所谓黄册,即户口册籍,明朝实行兼户籍与赋役为一体的黄册制度。据考证,“清承明制,人丁编审与土地黄册互为表里。明清之际动乱,户口册籍毁于战火,赋役征派失去依据。顺治建国伊始,统治者即以‘丁人土地,用财赋之根本’,恢复明代编审旧制。”[8]五年进行一次人丁编审,十年进行一次攒造黄册,称“五年编审,十年大造”但两套制度并行给地方带来巨大的负担,尤其是黄册的攥造,越来越成为耗费浩大而无实际意义的一种形式。因此,康熙七年诏令停止黄册攥造,题准“直省钱粮,每岁终巡抚造送奏销册一本,开载地丁款项数目,又造送考成册一本,开列已完,未完分数,又五年编审,造送增减丁户册籍,立法祥尽,其每十年造黄册,繁费无益,停止攒造。”[9]可见,康熙四十年不可能再攥造黄册。也许,黄册制度自明初实行已有三百多年历史,人们已经习惯于将户籍档案称为“黄册”了。
尽管如此,却丝毫不影响该碑珍贵的历史价值。
二.历史背景与历史原因
对于隐藏在碑刻后面的历史背景及其历史原因,江日升是十分清楚的。但他在碑中仅以“惟闽地炽於海氛故弃之”一语带过,可以想象,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不允许他多说的。因此,要解读这方碑刻,便不能不对铜山那段特殊的历史有所了解。
铜山位于东山岛东部,濒临台湾海峡,东海与南海在此交汇,自古便是闽南地区的通商港口,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明清之际,铜山是郑成功抗清复明、收复台湾的主要军事基地之一,又是后来遭遇康熙年间“迁界”浩劫的重灾区。这就是《公立关永茂碑记》立碑的历史背景与历史原因,而这一切均可在江日升的《台湾外记》中找到大量翔实的记载。
早在顺治二年(1645)五月,“国姓与师莅铜”,[10]郑成功首次来铜山。三年后的顺治五年(1648),一年中他竟三次到铜山。江日升云:顺治五年(1648)五月,“郑成功据同安,以丘、林状猷、金作裕兰将守之,自领大队舟师铜山,候永历旨,以便会合恢复”[11];同年“八月,成功在铜山,整顿船只,训练士卒,候广西永历信到”;[12]八月“五日方抵金门,侦报同安已破……遂移师镇海、铜山”。[13]。
郑成功在铜山修造战船,训练水师,募兵措餉,招贤纳士。铜山人民对郑成功予以坚决的拥护与巨大的支持。有不少仁人志士投身到郑成功的事业,并为之流血牺牲。据《东山县志》载,郑成功收复台湾时,铜山就有五百多青壮年加入他的队伍。郑成功之后,铜山仍然是郑经进可攻、退可守的重要军事基地。郑氏父子依凭铜山这一可靠而坚强的基地,进退自如,与清廷周旋长达36年之久;铜山人民义无反顾地给予无私的支持,为抗清复明大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故有南明大臣赞叹道:“铜为忠义文献之区,孤城抗战,我国家三百年深仁厚泽之报,仅得于铜。”[14]因此,清廷为剿灭郑氏集团,多次用兵,恨不能一举踏平铜山;也因此,后来对铜山实行“迁界”时,采用“焦土政策”的残酷手段。
铜山“迁界”始于清康熙三年(1664)“甲申鼎革,天下非复明有弘隆建国不及二载,我铜为郑藩所据者几二十年而城郭宫室依然如故。不幸于顺治间,闽之部院李公率泰倡移海之说,兵部苏纳海主其议,是以康熙三年甲辰,西平藩统大兵勒移铜山百姓,先数日或买舟,或从陆尽逃窜于漳潮内地,兵乃于三月十三日过陈坪渡,十四十五日摧城焚屋,致二百六十余年花锦文献之地,一旦邱墟,不能不令人涕泪交颈也。”[15]对此,江日升有更详细的记述:“率泰知郑经已遁台湾,即移舟师到铜山。驰令各岛暨沿边百姓,尽移入内地。逢山开沟二丈余深、二丈余宽,名为‘界沟’。又沟内筑墙,厚四尺余,高八尺(一丈),名为‘界墙’。逢溪河,用大木椿栅。五里相望,于高阜处置一炮台,台外两烟墩,二(三)十里设一大营盘,营将、千(总)、把总率众守护期间。日则瞭望,夜则伏路;如逢有警,一台烟起,左右各相应,营将各挥众合围攻击。五省沿边如是。是时界弁兵最有权威,贿之者,纵其出入不问;有睚眦者,拖出界墙外杀之。官不问,民含冤莫诉。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更甚者督迁官兵,还乘机肆行掠夺,情景悲惨,不忍卒闻。““[16]
尽管朝廷颁发“迁界禁海令”:不准寸板入海,货物不准进出,越界者不论远近,格杀勿论。但仍有一些铜山人为了配合郑经的斗争,冒死潜回自己的家园。实际上,自“迁界”至“复界”的16年间,东山岛虽然已成荒岛,但仍经常控制在郑经手里。据载:“康熙九年(1670)三月,郑经又派军镇守这已破碎不堪的铜山岛。十五年(1676)十一月再派铜山人陈骏音为漳浦铜山所安抚司。……康熙十六年(1671)四月,郑经又派奇兵镇黄应等军屯铜山、五都。六月廿四日再派刘国轩、何祐率领水师驻铜山,继续揭起抗清义旗。”[17]
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二月,郑经退守台湾,部将朱天贵叛变,铜山这个最后的抗清据点才被拔除。同年四月,清廷宣布“复界”。七月,铜山人民才陆陆续续回到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家园,而“散而归者,十存二、三。”[18]
明清交替的历史风云、惨绝人寰的“迁界”浩劫,给铜山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史家叹道:“孰知天命靡常,甲申一易,而防倭之人变为勤王之师矣;歌乐之区变为哭泣之野矣;文章之子弟变为忠贞之肝胆者,悉以歼绝无遗矣。呜呼!周蔡苦心之所经营明朝,数百年之所培养,一旦而弃置无余,可悲孰甚焉。虽然,铜之兴,明兴之也。自明兴之而自明废之,废亦何憾,最可惜者,铜之众殉明之众也,铜之乡殉明之乡也。铜之众殉明者既已寂寞无知矣,铜为殉明之乡又焉能知之故。”[19]这正是铜山人民不幸命运的真实写照。
虽然铜山人民终于重返家园,但因清廷对铜山人民敌视与歧视,既削去铜山人原有的军籍,又不将其编入民籍,严重损害了铜山人的利益与尊严。铜山人成了无籍之民、大清弃民甚至是非法之民。没有什么比失去公民基本权利与尊严更为痛苦,为了摆脱这种痛苦,铜山人民苦苦挣扎了二十余年,直到康熙四十年才看到了希望。
至此,隐藏于碑刻后面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似乎清晰了然,但问题并未完全了结。铜山人如何争取入籍?为何以“关永茂”立户?立碑除了具公约的实际功能外,还蕴含何种更为深刻的意义?这不能不发人深思。
三.文化内涵与历史意义
如上所述,一则民里公约,却以“关永茂”点题,虽无明言,却已强烈地暗示着一种饱受磨难、飘忽迷茫中寻找归宿的深深渴望、一种久远而深厚的民间信仰。对此,一则流传久远的传说或许可以说明问题。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对东山仍然采取放弃蔑视的态度,不予承认,不予注册入籍。相传,关帝闻讯后,策马前往漳浦,向县令陈汝咸辩诉,取得县令同情,表示向康熙皇帝奏议。回庙后,又托梦岛上各大姓族长,敦促各姓到关帝庙开会,商议申请入籍事宜。各族族长立即会集庙中,悟得关帝托梦缘由,无不感恩戴德,稽首跪拜,立誓愿做关帝裔孙,并立‘关永茂’名字为注籍户主。在县令陈汝咸的帮助下,迄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东山人民方被批准承认为清朝子民,豁减赋税使役。因此,东山人民对关帝信仰越来越深刻。为了感激关帝恩泽,从注册之日开始,家家户户悬挂关帝画像,作为自己祖先奉祀,并订定每年五月十三、六月廿四日,为全岛人民谒庙向关帝祝嘏典祭日子。”[20]
现在,东山人确实视关帝为自己祖先,男女老幼皆称关帝为“帝祖”,家家户户悬挂关帝像于正中,先辈灵牌反而列于两侧,完全以祭祀祖先的仪式加以奉祀。再说,碑文云:“於是公诸仝人,当神拈〓,分为七房”,说明确实曾在关帝庙里举行会议,况且又立碑于庙内。
因此,除了关帝策马与托梦的情节外,该则传说实际上是一小段可信的口传历史。
当时,铜山人民所忠诚的明朝已经灭亡,郑氏集团给予的希望业已破灭,清廷又将他们遗弃。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本来就是保护神的关帝身上。因此,他们更愿意真正成为关帝的子孙,希望关帝不仅仅是神,而是能够真正出来保护他们的人。也因此,便有了以“关永茂”立户的想法。明清时期,关帝信仰兴盛且普及朝野。也许,正是铜山人民虔诚的关帝信仰感动了知县,才最终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无论如何,“关永茂”事件,足以表明铜山人民对关帝的信仰程度。
铜山人民崇拜关公,有其特殊的原因。东山是海岛,生业以捕鱼为主,而海上作业风险大,渔民们很需要“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义气,这与关公的“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时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忠义思想正好相合。因此,渔民尤其信仰关帝,必置关帝神龛于船中。另一方面,东山这孤岛,历史上倭患不断,在抵御外侵、保卫家园的战争中,更需要“忠勇仁义”这种精神力量。因此,关帝信仰早就深深地扎根于铜山人民心中。
有人认为:“铜山自古受关帝忠义思想熏陶,产生了诸多仁人义士,诸如为节义而殉节的大学士黄道周,与张献忠作战而受磔刑献身的七省军务陈瑸,与张献忠作战被剐献身的四川巡抚陈士奇,与李自成部将贺锦作战被磔献身的甘肃巡抚林日瑞等,都是东山人。又据明清泉南夏琳元斌《海纪辑要》(卷一)载:永暦暦五年春二月(1651),清巡抚张学圣会提督马得功袭厦门,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曾樱不肯受辱自杀。其门人陈泰冒险出其尸殯於金门,陈泰就是铜山人。”[21]甚至认为:“郑成功选择铜山做为反清复明的军事筹备基地,客观上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即可以借助铜山关帝来保护他的军队,统一思想,激励士气。”[22]
铜山如此久远而虔诚的关帝信仰,是一片深厚的精神沃土。这片精神沃土培育了铜山人忠义仁厚的人文性格,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公立关永茂碑记》。
在劫后百业待兴而又人心涣散的铜山,这一通碑刻不仅具有规范行为、建立秩序的现实意义,更有团结乡众、凝聚人心、恢复尊严的现实意义。立碑后的铜山人民,便开始团结一致,重建家园,逐渐开创了新的昌盛时代。如果说,这通碑刻是铜山人民命运的转折点,那么,在推动铜山人民命运转变并前行的巨大力量中,关帝信仰一定是其中之一。
然而,更为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它向世人公布了关帝“从神到人”的宣言。
众所周知,中国关帝信仰经历了“从人到神”的发展过程,而这里却出现了“从神到人”的返祖现象。当然,这并不意味从神完全变为人,这里的关帝虽成了铜山人的“帝祖”,但同时还是神。这就类似于希腊神话中人神相近、人神混杂、人神合一的特征及其强调人性、价值与尊严的人本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思想。而这种思想最终发展并演变成西方的“文艺复兴”。这个类比未必恰当,但这种“从神到人”的返祖现象,为中国民间的英雄人物崇拜源于祖宗崇拜的理论提供了直观的力证。同时,它以具体生动的实例,说明作为民间信仰的关帝信仰,与宗教的区别就在于它的崇拜对象既有神的威严,又具有可亲近的人的感情。实际上这种返祖现象普遍存在于诸多民间信仰的心理活动中,多以模糊的想象或意念形态内敛于心中。而这通碑刻却明确了那种想象或意念并使之外化,变成活生生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这通碑刻是中国民间关帝信仰中返祖现象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民间信仰文化中不可多得瑰宝。它对研究中国民间信仰、清初政治、军事与户籍赋役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对于铜山,这通碑刻是划时代的里程碑。它标志着铜山关帝信仰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更高境界。
关键词:东山关帝庙,碑刻,考析
东山关帝庙,原称:铜山关帝庙,位于东山县铜陵镇东部的岵嵝山腰,依山而筑,濒临大海,气势磅礴。该庙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具有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而且是台湾众多关帝庙的香缘祖庙。该庙于1996年11月20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庙内有数通明清时期的碑刻,其中《公立关永茂碑记》为《台湾外记》作者江日升所撰。因内容仅为一则乡里公约,碑文少有剔藓描丹,碑前又长年放置他物,故很少引人瞩目,更不要说加以研究了。数年前,笔者在建立文保单位档案时拓下了碑文,仔细辨读,颇觉字里行间,大有文章。本文则根据已有的相关文献,对该碑作一番考析,试图揭示其立碑的历史背景、历史原因、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历史意义,并以此请教于诸位方家。
一.公立关永茂碑记
《公立关永茂碑记》立于东山关帝庙二进东侧回廊,镶嵌于廊壁之上。石碑材料为花岗岩,通高228、宽89、厚19厘米。碑首委角,边饰回纹,额书:“公立关永茂碑记”。碑文竖行楷书阴刻,共19行,计617字,字迹清晰可辨。碑心留有两个浅坑,据说是抗战时期日本轰炸留下的弹片痕迹,使碑文至少有15字缺失。现将碑文照录如下,以供参考:
公立关永茂碑记
考之上世,吾铜乃海外岛屿,为渔人之寄足,民未曾居焉。迨明初,江夏侯德兴周公沿边设立,以此壤接粤境为八闽上游之要区设为所,以铜山名之,调兴化莆禧众来守此城。官与军咸袭封,是为军籍,里甲丁粮,世莫之闻。至国朝定鼎,凡天下卫所仍旧无易,惟闽地炽於海氛故弃之。是有籍反散而为无,天下岂有无籍之人乎?故莘庵陈公於康熙四十年将铜地户口编入黄册,而铜自此有丁粮之事焉。然泛而无宗,傍人门户实非貽燕善策。
因闻诏邑有军籍而无宗者,共尊关圣帝君为祖,请置户名曰:“关世贤”,纳粮输丁大称其便。五十年编审公议此例,亦表其户名曰:“关永茂”,众咸为可,遂向邑候汪公呈请立户。蒙批准关永茂顶补十七都六图九甲,输纳丁粮不但得画一之便,且幸无他户相杂,是散而复聚,无而又有,将来昌炽可甲於前第。迩因查县府司户册有一户“关永茂”,即黄启泰等,其间大有移花接木、藏头露尾之虞。夫事方三载即如此互异,又安能保其后来不无舛黠辈从中滋弊,蚕我子孙乎?於是公诸全人,当神拈阄,分为七房。小事则归房料理,大事则会众均匀。叔伯甥舅,彼此手足,并无里甲之别,终绝大小之分。不得以贵欺贱,不得以强凌弱,苟有异视萌恶,许共鸣鼓而攻,此方为无偏无党,至公至慎。爰立石以垂不朽。
大房:游继业、游琨玉、吴葛□□□□□江欧□□绍宗、蕃衍、洪庄文、桑傅谢康范苏
二房
三房:郑禎吉、唐绵芳、李玉承□□□廖光彩、吴日新、何兴隆、田兴邦、张发祥
四房:陈思明、思聪、温思、恭思□□敬、思问、思难、思义
五房:姚嘉謨、翁万年、蔡□□□马栋、崔国禎、朱天庆、孔阳、曾徐郭龚沙董杨颜詹石顾
六房:林世发、世强、纪刚、世毅、发祥、发端
七房:黄士温、士良、士恭、士俭、士让
康熙五十二年岁次癸巳阳月级旦
珠浦东旭氏江日升撰
撰碑者江日升,不愧为《东平纪略》、《台湾外记》的作者,笔力不凡,言简意赅,短短六百余字碑文,却包含了太多的信息。它涉及铜山(今东山县铜陵镇)历史、地理与人文,揭示了立碑的历史背景与历史原因等等。尤为精彩的还在于碑题,本来这仅仅是一则民里公约,却不拘泥于习惯格式,抓住事件的中心,以“关永茂”点题,赫然醒目,发人深思。虽无明言,却已强烈地暗示着一种饱受磨难、飘忽迷茫中寻找归宿的深深渴望、一种久远而深厚的虔诚信仰。这两点在后面还会述及。
碑文云:“迩因查县府司户册有一户“关永茂”,即黄启泰等,其间大有移花接木、藏头露尾之虞”。此应为立碑的近因,同时也一语道破了清代初期户籍与赋役制度的弊端。
户籍与赋役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清虽承明制,但并非一承不变。例如,明代及清顺治初,军籍人丁并不交纳丁银,也不编审。“军丁的编审之例始于顺治十二年(1655)”。[1]是年饬令各卫所闲丁,按年编审纳银为帮贴之费。康熙十三年(1674),三藩之乱,军费开支浩大,清廷为筹饷,将军丁编审范围扩大到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省。四年后,江西、广东、浙江、福建、湖广也接到命令,“将卫所屯丁亦照州县人丁例一体编征”。[2]。
这一变化,对当时以军户为多数的铜山人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铜山自明初设守御千户所,“调兴化莆禧众来守此城。官与军咸袭封,是为军籍,里甲丁粮,世莫之闻”。[3。]要命的是朝廷在这里并没有实行“卫所屯丁亦照州县人丁例一体编征”的政策,而是干脆削去军籍,又按旧例不编入民籍。故有“是有籍反散而为无,天下岂有无籍之人乎?”,[4]的悲叹。铜山遂成了大清的弃民,走投无路,前景渺茫。
直到康熙四十年(1701),知县陈汝咸才将铜山(时隶属漳浦县)统为一户,以寄户的形式入册。据载:“陈汝咸,字莘学,号心齐,鄞县人。康熙辛末进士。三十五年由翰林庶吉士出知漳浦。以浦邑赋役不均,定二百家为一保,保二十甲,户实其丁口。编审日,通计阖县城丁若干,均编足额,立亲供单,每户田粮各填注实产,分限自封投柜。根租一田三主,详定大租,量给价值,田归业主,于是奸胥无所飞洒,强宗巨猾无所隐占诡寄包收,哀户孱民无所赔累。自明季来百余年积弊一清。”,[5]然而,此非长久之计。因为“并诸户而统为一户,遇编审之年,所谓亲供皆里长一人所自造。……其有势之人,必寻有里长衰弱之图立户,谓之顶班。无势者虽田连千顷,不得不受人节制,至单寒小姓,更无论矣!……完粮必经伊手,每丁必多收一二钱,每亩必多收四五分,皆相习为固然,……户内殷实与谨厚之士皆被其累。”[6]然而,此时的铜山实际上尚无真正属于自己的户籍。故碑文云:“泛而无宗,傍人门户实非貽燕善策。”最终,竟然以关帝后裔“关永茂”为户主,统铜山各姓为一户,呈请编审,且获准“关永茂顶补十七都六图九甲,输纳丁粮不但得画一之便,且幸无他户相杂,是散而复聚,无而又有,将来昌炽可甲於前第。”[7]从此,铜山人民不再是遭人歧视与蹂躏的弃民。
品读碑文,知作者有过人的文笔、学识与才华。但是,出于对历史的尊重,不能不对碑文中两处笔误作一校正。碑文:“故莘庵陈公於康熙四十年将铜地户口编入黄册”的莘庵陈公,指的是时任漳浦知县的陈汝咸。《漳州府志》载:“陈汝咸,字莘学,号心齐,鄞县人。”《漳浦县志》、《铜山志》等也有相同记载。可见“莘学”是陈汝咸的字,并且是“莘学”而非“莘庵”。
另外,“康熙四十年将铜地户口编入黄册”之说可能有误。所谓黄册,即户口册籍,明朝实行兼户籍与赋役为一体的黄册制度。据考证,“清承明制,人丁编审与土地黄册互为表里。明清之际动乱,户口册籍毁于战火,赋役征派失去依据。顺治建国伊始,统治者即以‘丁人土地,用财赋之根本’,恢复明代编审旧制。”[8]五年进行一次人丁编审,十年进行一次攒造黄册,称“五年编审,十年大造”但两套制度并行给地方带来巨大的负担,尤其是黄册的攥造,越来越成为耗费浩大而无实际意义的一种形式。因此,康熙七年诏令停止黄册攥造,题准“直省钱粮,每岁终巡抚造送奏销册一本,开载地丁款项数目,又造送考成册一本,开列已完,未完分数,又五年编审,造送增减丁户册籍,立法祥尽,其每十年造黄册,繁费无益,停止攒造。”[9]可见,康熙四十年不可能再攥造黄册。也许,黄册制度自明初实行已有三百多年历史,人们已经习惯于将户籍档案称为“黄册”了。
尽管如此,却丝毫不影响该碑珍贵的历史价值。
二.历史背景与历史原因
对于隐藏在碑刻后面的历史背景及其历史原因,江日升是十分清楚的。但他在碑中仅以“惟闽地炽於海氛故弃之”一语带过,可以想象,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不允许他多说的。因此,要解读这方碑刻,便不能不对铜山那段特殊的历史有所了解。
铜山位于东山岛东部,濒临台湾海峡,东海与南海在此交汇,自古便是闽南地区的通商港口,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明清之际,铜山是郑成功抗清复明、收复台湾的主要军事基地之一,又是后来遭遇康熙年间“迁界”浩劫的重灾区。这就是《公立关永茂碑记》立碑的历史背景与历史原因,而这一切均可在江日升的《台湾外记》中找到大量翔实的记载。
早在顺治二年(1645)五月,“国姓与师莅铜”,[10]郑成功首次来铜山。三年后的顺治五年(1648),一年中他竟三次到铜山。江日升云:顺治五年(1648)五月,“郑成功据同安,以丘、林状猷、金作裕兰将守之,自领大队舟师铜山,候永历旨,以便会合恢复”[11];同年“八月,成功在铜山,整顿船只,训练士卒,候广西永历信到”;[12]八月“五日方抵金门,侦报同安已破……遂移师镇海、铜山”。[13]。
郑成功在铜山修造战船,训练水师,募兵措餉,招贤纳士。铜山人民对郑成功予以坚决的拥护与巨大的支持。有不少仁人志士投身到郑成功的事业,并为之流血牺牲。据《东山县志》载,郑成功收复台湾时,铜山就有五百多青壮年加入他的队伍。郑成功之后,铜山仍然是郑经进可攻、退可守的重要军事基地。郑氏父子依凭铜山这一可靠而坚强的基地,进退自如,与清廷周旋长达36年之久;铜山人民义无反顾地给予无私的支持,为抗清复明大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故有南明大臣赞叹道:“铜为忠义文献之区,孤城抗战,我国家三百年深仁厚泽之报,仅得于铜。”[14]因此,清廷为剿灭郑氏集团,多次用兵,恨不能一举踏平铜山;也因此,后来对铜山实行“迁界”时,采用“焦土政策”的残酷手段。
铜山“迁界”始于清康熙三年(1664)“甲申鼎革,天下非复明有弘隆建国不及二载,我铜为郑藩所据者几二十年而城郭宫室依然如故。不幸于顺治间,闽之部院李公率泰倡移海之说,兵部苏纳海主其议,是以康熙三年甲辰,西平藩统大兵勒移铜山百姓,先数日或买舟,或从陆尽逃窜于漳潮内地,兵乃于三月十三日过陈坪渡,十四十五日摧城焚屋,致二百六十余年花锦文献之地,一旦邱墟,不能不令人涕泪交颈也。”[15]对此,江日升有更详细的记述:“率泰知郑经已遁台湾,即移舟师到铜山。驰令各岛暨沿边百姓,尽移入内地。逢山开沟二丈余深、二丈余宽,名为‘界沟’。又沟内筑墙,厚四尺余,高八尺(一丈),名为‘界墙’。逢溪河,用大木椿栅。五里相望,于高阜处置一炮台,台外两烟墩,二(三)十里设一大营盘,营将、千(总)、把总率众守护期间。日则瞭望,夜则伏路;如逢有警,一台烟起,左右各相应,营将各挥众合围攻击。五省沿边如是。是时界弁兵最有权威,贿之者,纵其出入不问;有睚眦者,拖出界墙外杀之。官不问,民含冤莫诉。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更甚者督迁官兵,还乘机肆行掠夺,情景悲惨,不忍卒闻。““[16]
尽管朝廷颁发“迁界禁海令”:不准寸板入海,货物不准进出,越界者不论远近,格杀勿论。但仍有一些铜山人为了配合郑经的斗争,冒死潜回自己的家园。实际上,自“迁界”至“复界”的16年间,东山岛虽然已成荒岛,但仍经常控制在郑经手里。据载:“康熙九年(1670)三月,郑经又派军镇守这已破碎不堪的铜山岛。十五年(1676)十一月再派铜山人陈骏音为漳浦铜山所安抚司。……康熙十六年(1671)四月,郑经又派奇兵镇黄应等军屯铜山、五都。六月廿四日再派刘国轩、何祐率领水师驻铜山,继续揭起抗清义旗。”[17]
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二月,郑经退守台湾,部将朱天贵叛变,铜山这个最后的抗清据点才被拔除。同年四月,清廷宣布“复界”。七月,铜山人民才陆陆续续回到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家园,而“散而归者,十存二、三。”[18]
明清交替的历史风云、惨绝人寰的“迁界”浩劫,给铜山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史家叹道:“孰知天命靡常,甲申一易,而防倭之人变为勤王之师矣;歌乐之区变为哭泣之野矣;文章之子弟变为忠贞之肝胆者,悉以歼绝无遗矣。呜呼!周蔡苦心之所经营明朝,数百年之所培养,一旦而弃置无余,可悲孰甚焉。虽然,铜之兴,明兴之也。自明兴之而自明废之,废亦何憾,最可惜者,铜之众殉明之众也,铜之乡殉明之乡也。铜之众殉明者既已寂寞无知矣,铜为殉明之乡又焉能知之故。”[19]这正是铜山人民不幸命运的真实写照。
虽然铜山人民终于重返家园,但因清廷对铜山人民敌视与歧视,既削去铜山人原有的军籍,又不将其编入民籍,严重损害了铜山人的利益与尊严。铜山人成了无籍之民、大清弃民甚至是非法之民。没有什么比失去公民基本权利与尊严更为痛苦,为了摆脱这种痛苦,铜山人民苦苦挣扎了二十余年,直到康熙四十年才看到了希望。
至此,隐藏于碑刻后面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似乎清晰了然,但问题并未完全了结。铜山人如何争取入籍?为何以“关永茂”立户?立碑除了具公约的实际功能外,还蕴含何种更为深刻的意义?这不能不发人深思。
三.文化内涵与历史意义
如上所述,一则民里公约,却以“关永茂”点题,虽无明言,却已强烈地暗示着一种饱受磨难、飘忽迷茫中寻找归宿的深深渴望、一种久远而深厚的民间信仰。对此,一则流传久远的传说或许可以说明问题。
“清政府统一台湾后,对东山仍然采取放弃蔑视的态度,不予承认,不予注册入籍。相传,关帝闻讯后,策马前往漳浦,向县令陈汝咸辩诉,取得县令同情,表示向康熙皇帝奏议。回庙后,又托梦岛上各大姓族长,敦促各姓到关帝庙开会,商议申请入籍事宜。各族族长立即会集庙中,悟得关帝托梦缘由,无不感恩戴德,稽首跪拜,立誓愿做关帝裔孙,并立‘关永茂’名字为注籍户主。在县令陈汝咸的帮助下,迄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东山人民方被批准承认为清朝子民,豁减赋税使役。因此,东山人民对关帝信仰越来越深刻。为了感激关帝恩泽,从注册之日开始,家家户户悬挂关帝画像,作为自己祖先奉祀,并订定每年五月十三、六月廿四日,为全岛人民谒庙向关帝祝嘏典祭日子。”[20]
现在,东山人确实视关帝为自己祖先,男女老幼皆称关帝为“帝祖”,家家户户悬挂关帝像于正中,先辈灵牌反而列于两侧,完全以祭祀祖先的仪式加以奉祀。再说,碑文云:“於是公诸仝人,当神拈〓,分为七房”,说明确实曾在关帝庙里举行会议,况且又立碑于庙内。
因此,除了关帝策马与托梦的情节外,该则传说实际上是一小段可信的口传历史。
当时,铜山人民所忠诚的明朝已经灭亡,郑氏集团给予的希望业已破灭,清廷又将他们遗弃。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本来就是保护神的关帝身上。因此,他们更愿意真正成为关帝的子孙,希望关帝不仅仅是神,而是能够真正出来保护他们的人。也因此,便有了以“关永茂”立户的想法。明清时期,关帝信仰兴盛且普及朝野。也许,正是铜山人民虔诚的关帝信仰感动了知县,才最终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无论如何,“关永茂”事件,足以表明铜山人民对关帝的信仰程度。
铜山人民崇拜关公,有其特殊的原因。东山是海岛,生业以捕鱼为主,而海上作业风险大,渔民们很需要“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义气,这与关公的“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时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忠义思想正好相合。因此,渔民尤其信仰关帝,必置关帝神龛于船中。另一方面,东山这孤岛,历史上倭患不断,在抵御外侵、保卫家园的战争中,更需要“忠勇仁义”这种精神力量。因此,关帝信仰早就深深地扎根于铜山人民心中。
有人认为:“铜山自古受关帝忠义思想熏陶,产生了诸多仁人义士,诸如为节义而殉节的大学士黄道周,与张献忠作战而受磔刑献身的七省军务陈瑸,与张献忠作战被剐献身的四川巡抚陈士奇,与李自成部将贺锦作战被磔献身的甘肃巡抚林日瑞等,都是东山人。又据明清泉南夏琳元斌《海纪辑要》(卷一)载:永暦暦五年春二月(1651),清巡抚张学圣会提督马得功袭厦门,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曾樱不肯受辱自杀。其门人陈泰冒险出其尸殯於金门,陈泰就是铜山人。”[21]甚至认为:“郑成功选择铜山做为反清复明的军事筹备基地,客观上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即可以借助铜山关帝来保护他的军队,统一思想,激励士气。”[22]
铜山如此久远而虔诚的关帝信仰,是一片深厚的精神沃土。这片精神沃土培育了铜山人忠义仁厚的人文性格,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公立关永茂碑记》。
在劫后百业待兴而又人心涣散的铜山,这一通碑刻不仅具有规范行为、建立秩序的现实意义,更有团结乡众、凝聚人心、恢复尊严的现实意义。立碑后的铜山人民,便开始团结一致,重建家园,逐渐开创了新的昌盛时代。如果说,这通碑刻是铜山人民命运的转折点,那么,在推动铜山人民命运转变并前行的巨大力量中,关帝信仰一定是其中之一。
然而,更为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它向世人公布了关帝“从神到人”的宣言。
众所周知,中国关帝信仰经历了“从人到神”的发展过程,而这里却出现了“从神到人”的返祖现象。当然,这并不意味从神完全变为人,这里的关帝虽成了铜山人的“帝祖”,但同时还是神。这就类似于希腊神话中人神相近、人神混杂、人神合一的特征及其强调人性、价值与尊严的人本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思想。而这种思想最终发展并演变成西方的“文艺复兴”。这个类比未必恰当,但这种“从神到人”的返祖现象,为中国民间的英雄人物崇拜源于祖宗崇拜的理论提供了直观的力证。同时,它以具体生动的实例,说明作为民间信仰的关帝信仰,与宗教的区别就在于它的崇拜对象既有神的威严,又具有可亲近的人的感情。实际上这种返祖现象普遍存在于诸多民间信仰的心理活动中,多以模糊的想象或意念形态内敛于心中。而这通碑刻却明确了那种想象或意念并使之外化,变成活生生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这通碑刻是中国民间关帝信仰中返祖现象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国民间信仰文化中不可多得瑰宝。它对研究中国民间信仰、清初政治、军事与户籍赋役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对于铜山,这通碑刻是划时代的里程碑。它标志着铜山关帝信仰从此进入一个全新的更高境界。
附注
注释:
[1][2]《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户口一。
[3][4][7]见《公立关永茂碑记》碑文。
[5]清·沈定均修、清·吴联薰增纂、今人陈正统整理《漳州府志》26卷,宦绩3,中华书局,2011年4月。
[6]清《漳浦县志》(卷八赋役志),漳浦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2004年12月。
[8]聂红琴:清代前期的户籍与赋役,《史林》2001年第1期。
[9]《康熙大清会典》卷24(户部八,赋役一)。
[10]清·陈振藻《铜山志·卷六·选举志》,(油印本)东山县图书馆印。
[11][12][13]清·江日升《台湾外志》卷六。台湾,智扬出版社。
[14]清·陈振藻《铜山志·忠匡伯张公德政碑》(油印本)东山县图书馆印。
[15]清·陈振藻《铜山志》(追志铜山人物序)(油印本)东山县图书馆印。
[16]清·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之六,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17]林友辉:清初铜山三次迁界史话,《东山文史资料》,第8辑,1989年10月。
[18]李猷猷明总纂《东山县志》(民国稿本)卷二·大事记。
[19]清·陈振藻《铜山志·明铜山所志》,(油印本),东山县图书馆印。
[20]陈汉波:东山与台湾关帝文化缘系小考,《东山文史资料》第10辑,1993年8月。
[21][22]林定泗:郑成功东山史迹考,《第二届金门一澎湖一东山三岛交流论坛论文集》金门县政府编印,2012年5月。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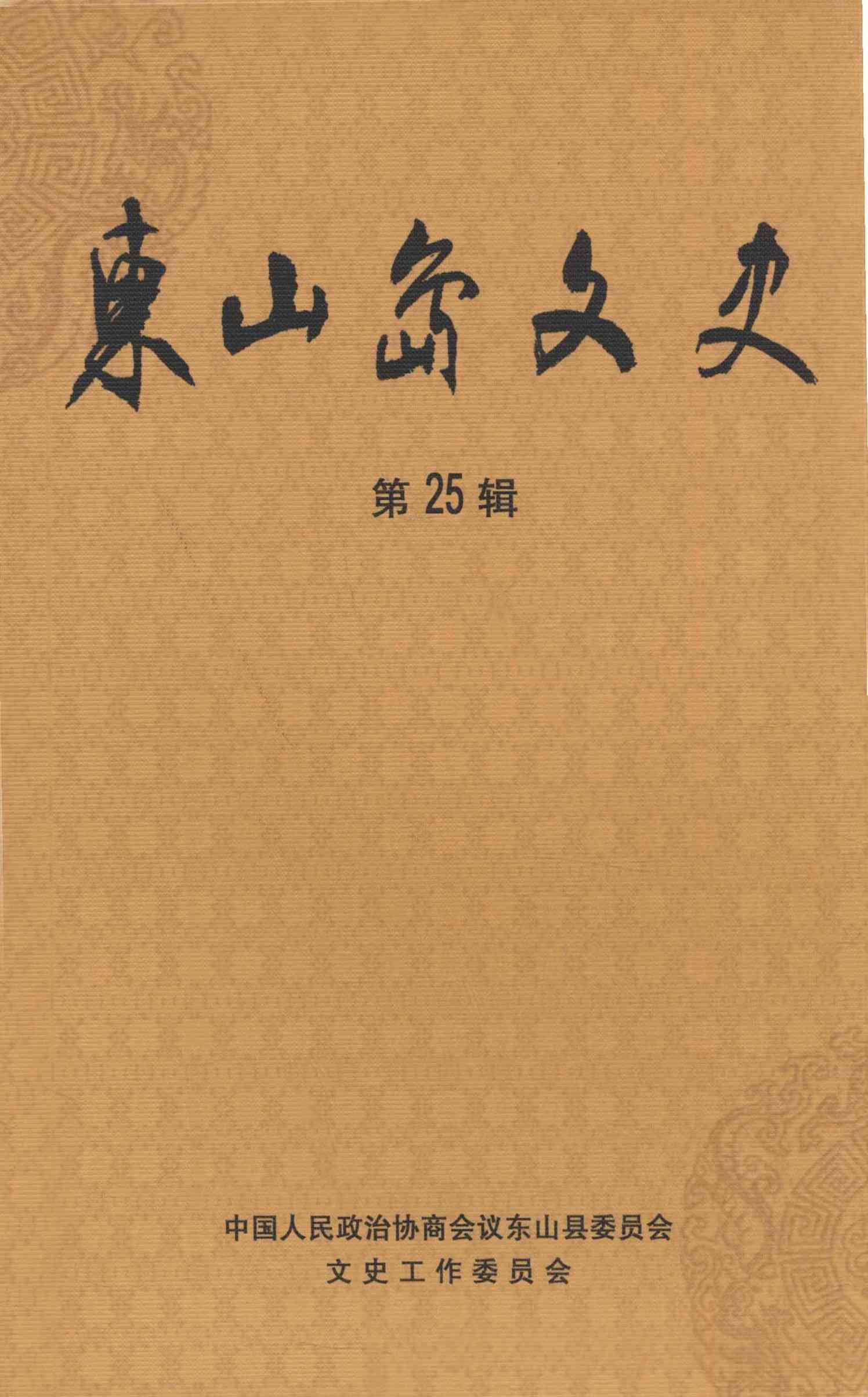
《東山岛文史第25辑》
本辑《东山岛文史》计收文稿35篇,总约21万字,共分为《东山·金门·澎湖三岛论坛论文选》、《海峡两岸关帝文化》、《黄道周文化》、《海峡长风》、《侨乡旧忆》、《史海钩沉》、《文化春秋》等栏目。着重于对东山县涉台关系史料、两岸关帝文化史料,黄道周文化史料、华侨史料、民俗和其他方面史料的深入调查挖掘,不断追寻发现,同时加以研究考证。
阅读
相关人物
陈立群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