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师傅朱水林(锡甘)在澎湖
| 内容出处: | 《東山岛文史第25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30004259 |
| 颗粒名称: | 东山师傅朱水林(锡甘)在澎湖 |
| 分类号: | K295.7 |
| 页数: | 22 |
| 页码: | 49-70 |
| 摘要: | 本文主要探讨了澎湖天后宫的艺术成就,特别是朱锡甘、水林师等人的贡献,以及他们在澎湖的彩绘和凿花木雕等工艺。文章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和挖掘,还原了这些工艺师们的身份和技艺,并肯定了他们在澎湖天后宫装饰艺术中的贡献。 |
| 关键词: | 朱水林 澎湖 东山县 |
内容
一、前言
澎湖宫庙多,民众信仰虔诚和积极参与修建宫庙活动,过去曾礼聘“唐山师傅”前来施作,形塑澎湖特有的在地文化,也带出宫庙装饰艺术在澎湖的丰富面貌。其中,首列国家一级古迹的“开台澎湖天后宫”是为代表,且带动起一股宫庙装饰风潮,影响层面既深又广。
天后宫的艺术成就与影响,不仅是澎湖一地一隅而已,其凿花木雕和彩绘作品,至今仍然炫目。笔者往昔曾对参与凿花木雕的黄良师傅,及其在澎湖传承师系的调查和发展有所著墨,对另一参与凿花的东山水林师、参与彩绘的广东潮汕朱锡甘师的动向和作品,则一直关注和扒疏,无奈囿于年代久远和识者有限,诸多讯息和疑点难有突破,只能借着参与天后宫志,撰写其中〈天后宫的装饰艺术〉时,以朱锡甘为天后宫所完成的擂金画做结,陈述该批作品“不论是做为他个人在彩绘世界,或天后宫在宫庙彩绘中的代表性而言,都极具分量!”(王文良,2006,P.228)虽是致意,但又不得不根据有限的文献资料指出,“朱锡甘师为澎湖留下了相当多佳作,可惜只知他来自广东梅县大埔地区,其它都付诸关如。”(同上P.244)水林师也在做完澎湖天后宫后即整装返回东山老家了。
水林师与朱锡甘师这两个名字,曾经分别代表在澎湖天后宫施作的凿花师与彩绘师,文献上也分别记载来自福建东山和广东潮汕,如此看法行之有年,直到他离开澎湖80年后,我们做了连结、他逝后70年,笔者才为文在澎湖研究第十届学术研讨会上,试图为他厘清身世和正名:水林师就是朱锡甘,他来自东山,既擅长凿花木雕也善彩绘,他的成就是十分杰出的,在他为澎湖完成的宫庙彩绘和凿花木雕作品中,我们寻得力证;他是自豪的,我们在澎湖和东山的长者描述和转述中,得到诸多左证。虽然得年仅46岁,但他的作品和牵引的澎湖东山情谊,却是让我们感念和珍惜的!
二、过去文献中关于澎湖天后宫的
擂金画与朱锡甘、水林师
过去文献中,关于朱锡甘、水林师等人名,及凿花木雕、彩绘和擂金画等多有论述或提起;或深入探讨,或几句关键的话带过。不过,人名彼此的关连性,以及朱锡甘的出身地等,却有模糊又多样的说法,但长期来,被误解的情形是存在的。
2-1首见朱锡甘、水林师二名,并分属二人,同为东山岛人
文献中,最早提及“朱锡甘”、“水林”两个名字,是在1983年,“行政院”文建会补助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研究所都市计画室所出版的《澎湖天后宫保存计划》,是书乃根据该室1979年接受“交通部”观光局委托为期一年,研究保存之道的成果为主体所出版。书中指出“刺花”(应是凿花木雕)有一班是东山岛来的三位师兄弟,“朱钦、陈(?)水林、黄文华,以老二的功夫最好”,他们三人“也负责油漆,遍在天后宫各处的题名‘朱锡甘’应就是朱钦的别名,弟‘一琴’应就是水林司”(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研究所都市计画室,1983,P.54)
2-2肯定天后宫彩绘和擂金画,出现“朱澍传”之名
之后1983-1985年天后宫的修复工作,并未对彩绘作品有进一步的修补或添加动作,倒是事后发现屋顶全面翻修时,“因未能及时有效的对现存彩绘加以保护,经事后勘察,发现彩绘剥落又较以往严重”,(王鸿楷,1985,P.1)乃建议并经文建会拨款补助专业拍摄和纪录,同时于1985年出版《澎湖天后宫之彩绘》专书,书中指出“天后宫的彩绘具有多样风貌,”(同上)叙明有水墨静物及墨竹作品,“署名则是朱锡甘和朱澍传”。(同上P.3)指出“擂金画在澎湖天后宫被普遍地使用,同时也形成了天后宫最重要的艺术成就之一”,(同上P.4)并进而称许“以金箔之浓淡轻重表现出山水岩石的各种皴法、技法之纯熟亦是台湾少见”。(同上,P.4)这是进一步对天后宫擂金画的肯定之始,也在此首次出现“朱澍传”的名字。
2-3朱锡甘来自广东潮州大埔,朱锡甘兄弟主绘正殿的连结
李干朗教授于1986年出版的《台湾的寺庙》一书,谈起澎湖寺庙修建情形,指出蓝木、蓝合兄弟受邀主持天后宫重修,“配合的匠师还有卢司、水林司及来自汕头的龙司”,(李干朗,1986,P.104)“彩画匠有朱锡甘、潘科等人,朱氏的传世名作是天后宫神龛左右福扇的黑底擂金画,至今尚保存完好,弥足珍贵”,(同上)之后论及台湾南北彩绘师傅名家辈出时,特别指出“有的出身画家,至少工于书法”,接着说“大陆名匠则有广东潮州大埔来的苏滨庭及朱锡甘,后者绘马公天后宫”,(同上P.105),显然在此时,水林师已经从东山岛来的三个师兄弟被独立出来,朱锡甘也被确认为来自广东潮州大埔。
同书后续介绍澎湖天后宫时,李干朗直接表示彩绘水平颇高,正殿的“神龛两侧有朱锡甘所作擂金彩画,工精质优,值得永久保存”,并分析天后宫的彩绘为前后对场,“台南陈玉峰主绘三川,大埔朱锡甘兄弟主绘正殿,三川以青绿为基调,正殿以黑色基调,各有千秋,论精细则以大殿垛头见长”(同上P.155),在注中则进一步表示“天后宫彩画很值得研究”,“正殿以大埔系统朱锡甘及朱澍传为主。”(同上P.170),此为文献上继续肯定朱锡甘的彩绘成就外,也二度出现朱澍传,并有“朱锡甘兄弟”乃朱锡甘及朱澍传的连结。
2-4比较后,对澎湖天后宫擂金画的高度肯定
1990年,林会承教授的《台湾传统建筑手册形式与作法篇》一书在论述色彩与彩绘时,曾对擂金画的制作程序做了介绍,并说“目的是使室内显得“金碧辉煌””(林会承,1990,P.127),后续篇章则列举了几个台湾尚保有擂金画的宫庙祠堂,他特别指出“其中以澎湖天后宫之作品的艺术水平最高”(同上P.131),这是将澎湖天后宫擂金画与台湾同类作品并列比较后,直接抽离而出的高度肯定。
2-5朱锡甘在澎湖天后宫的分工角色
继而,李干朗主持以台南民间彩绘画师陈玉峰及其传人的彩绘作品为对象,所出版的《台湾传统建筑彩绘之调查研究》,书中指出陈玉峰和“潮汕籍的彩绘匠师朱锡甘等人”于“民国十四年时”,就“携手共彩澎湖天后宫”,(李干朗,1993,P.66)“陈玉峰工作范围以三川殿为主”(同上),而“朱锡甘则负责正殿和后殿阁楼全部油漆彩绘工程”,(同上P.70)并从澎湖天后宫现存的彩绘作品来观察比较,进一步推测“陈玉峰遗留作品不比朱锡甘多,因此有可能陈玉峰是以副手上场。”(同上)换言之,朱锡甘显然才是当年彩绘的主力,为朱锡甘在分工角色上做了厘清。
2-6对擂金画的异见
李奕兴先生则在1995年出版的《台湾传统彩绘》书中提及“台湾目前在传统建筑学术界,极度推崇的所谓‘擂金画’黑底金漆图画,澎湖天后宫有实例”,他似乎不以为然的指出“几乎已到过度神话式的吹棒,犹以台湾独具的特产之一,事实这就是漆工艺里的‘泥金’技法一种”,(李奕兴,1995,P.63),这可能是学界对擂金画的看法提出异见的首例,虽然详细的研究论述仍有待进一步的推敲,不过,独以澎湖天后宫为例,也可见作者视该批作品为代表。
此后,陆续的研究或著作中,仍多有提及朱锡甘等师傅的讯息,关于其生平及何方人士,则有不同的说法,朱锡甘与共同参与的师傅群也有不同的解读,同时,前后出现许多不同的名字,但大概不出上面所述范围。至于其中正确与否?一些推论的人名是否真有其人?大家显然无力解决,只有继续流传沿用或相互引用。
三、文献资料的扒疏与田野调查中的朱锡甘
文献中,除了《澎湖天后宫保存计划》点出东山岛来的三位师兄弟,同时担任凿花木雕与彩绘,并试着勾勒朱钦、陈(?)水林、黄文华与朱锡甘、一琴的关系外,其余几乎是将参与凿花木雕(若该文有论及)与彩绘的师傅分开来叙述,笼统的说,参与凿花木雕的是福建东山来的三个师兄弟,而绘制擂金画与彩绘的人,则是来自广东潮州的「朱锡甘兄弟」等,何以致之?这其实是诸多原因造成的!
3-1文献的扒疏比对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书中,谈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由台南漳泉郊商倡建的台南水仙宫时,有“庙中亭脊,雕镂人物花草,备极精巧,皆潮州工匠为之。”(转引自国立台北艺术大学,2002,P.72)的记叙,说明早在近300年前,潮州师傅就已来台湾参与宫庙的工程,且“雕镂人物花草,备极精巧”。(同上)
或许是“粤东大埔位于韩江上游,古代与下游的潮州文化关系密切”,(李干朗,2004,)同时“大埔在清末出了不少著名的建筑彩绘名匠,特别是擂金画、泥金画及鎏金画”,(同上,)而且“潮州自古以来最擅长的家具制作传统”,“多用擂金、泥金或鎏金,闻名海内外”(同上),因此,互为影响,大埔彩绘水平高,名师倍出,又有多人来台展示才艺,同样时空背景、擅长擂金画的朱锡甘因而被视为大埔人,自有其合理性。至少,在缺乏否定这个认定的直接证据和左证数据下,这是最可能的答案,因此,不疑有他的一再引用就很自然合理了。
至于朱澍、朱锡甘、一琴等名字,笔者曾一再观察细究并揣摩再三,而于《开台澎湖天后宫志》里,大胆做出以下的推测:
由种种迹像显示,及正殿明间右架栋背面的花鸟画作,,落款“仿黄梅道人画意一琴朱锡甘写意”,正殿前落后步口次间架栋上,“群芳聚会”花鸟画作上的署名“一琴居士朱锡甘”判断,朱澍、朱锡甘、一琴等,应是同一人的名、字、号,只是落款不同,以增加变化。(王文良,2006,P.244)
以此试着推翻一再相沿的说法,直到2010年的《第四届台湾?浙江文化节浙台民俗文化澎湖大讲堂论文集》,笔者提出“……朱锡甘,天后宫完工离去后,1929年落成的湖西沙港广圣殿的凿花是朱锡甘来澎湖两度之作,生动细致十分耀眼。”(王文良,2010,P.135),指出朱锡甘二度来澎参与凿花施作,而点出与水林师的连结。
关于他的名字,或出于笔误、或出于误认、或出于推论,也有的是朱师个人的习惯,给人错误的连结(详见澎湖研究第十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2沙港广圣殿凿花旧作拍卖另起契机
不过经由2007年底,澎湖县湖西乡沙港村村庙广圣殿因为扩建,将旧庙拆除并拍卖凿花木雕旧作,买主由该村旅外的乡亲陈宗铭先生,于2008年1月26日标得,原只是想留几件童年庙口记忆的陈先生,与笔者取得连系,对这批作品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后,不但发愿并接着着手为该批作品营造完成了一个雅致可亲的展示空间。在从村中耆老陈保壮处得知作者叫“水林”,后来更于2009年7月中旬展开深入的福建探访寻根之旅,想为这批精彩木雕作品的作者“水林师”,找得相关作品和事迹,以为比对和印证,不过,水林师的事迹虽得一些,凿花作品却无所获,知道姓“朱”,得年46岁,摄得墓碑照片,确认1940年辞世,碑上却没水林师的名字。然而,事后笔者却发现“锡甘”二字。前年(2010年)初,笔者的一趟东山行,亲近和走着朱锡甘师傅昔日的足迹,探访朱师在家乡的事迹,得到了大陆东山、台湾及澎湖的许多朋友协助,得以厘清许多疑点,也勾勒出朱锡甘师傅比较清楚的轮廓。
3-3朱锡甘这个人
朱锡甘,也就是朱水林,福建东山人,清光绪廿一年(1895年)生,民国29年(1940年)逝于家乡东山,得年46岁。
3-3-1朱锡甘的澎湖行及娶妻与兄弟
朱锡甘,以“水林”之名见闻于往来的生活圈中,1922年左右,与师兄弟朱钦、黄文华同至澎湖天后宫,参与凿花木雕工作,接着进行彩绘,至1925年秋天后,完成擂金画和三川殿前步口、正殿的堵仁彩绘画作后,彩绘工作即便结束而返回东山。目前天后宫这些彩绘和擂金画作品中,部分落款有时间和署名可为证。
回到东山约一年多,33岁的朱水林娶了同为东山人的陈雁贞为妻,由于水林师之母早逝,父亲也已续弦另组家庭,因此,他们婚后暂住妻子的娘家。不久,水林师又再度应邀至澎湖的湖西沙港,参与广圣殿的木雕凿花工作。从此,水林之妻即长住娘家,直至1929年广圣殿完工,水林师归来,也就跟着一直住下来,只有每年除夕前碍于女儿必须大年初二始得回娘家的传统习俗,因此有几天暂时离开外,水林师的工作和活动,都在太太的娘家陈姓这头进行,后来他也在此开了店。或许,这就是同为东山人的文华师之妻,在数十年后回想水林师姓氏时,依地缘关系而指为“陈”姓之故吧!
水林师并无兄长,只有同父异母的弟弟叫阿棋,后来跟水林学凿花,但时间上已是水林师结束澎湖工作以后的事了,而且功夫显然不如水林师出色,因此,朱锡甘兄弟做天后宫彩绘的说法并不能成立。
当年水林师与朱钦、黄文华三个师兄弟来澎湖工作时,他们的师傅曾叮咛:“不要一桶酒放下,三个人就喝到倒,工作通通不晓得要做了。”黄文华年近80的大儿子一澎湖彩绘名师黄友谦,曾听父亲生前说起这段往事,可惜记不得他们师傅的名字了。不过沙港工作期间,或是离开澎湖回到东山后,近身参观或相处的晚辈,都表示极少见到水林师喝酒。
1927-1929年,沙港广圣殿的凿花木雕本是水林师与有三师对场,后因故有三师离开,因此,大部分花柴作品都由水林师完成,他对自己的作品颇有自信,也赢得在地人的肯定,尤其叙述三段出头故事的中港门大楣,更是精湛,临去时,他曾发下豪语,前年受访时92岁的陈保壮老先生佩服的转述:“以后有人凿得比他这支(指大楣)卡水,他要再做一支来换!”
3-3-2东山的水林师
水林师的豪气,不只在沙港展现,在东山亦然;他的媳妇返回东山时,也曾听长辈说起他:“做得比我好,我就再做”的豪语,不服输,对自己的功夫很有自信,同时,一切自己动手做。当年东山十大庙,几乎都是“客仔师傅”的天下,所谓的客仔师傅,即来自福建南部的闽南如永定,和粤东的广东潮汕地区的客家籍的师傅,包含木工、土水、雕刻和彩绘,他们的工夫在当地人的眼里是很好的,雕刻也都很精致的。
住东山的资深凿花师许庆石先生,以前曾听一90多岁的老人说,当地宫庙并没有水林师的作品,因为他和“客仔师”不合,这老人认识很多凿花师,他说水林师“‘骄’,是厉害的人,勇的人会‘骄’”,老人赞许水林师字画都很好,雕刻也很好,每项都很勥(行),字也“真水”啦;当地老辈的师傅都知道水林师到澎湖施作过,也都肯定他的技艺。许庆石的父亲当年做木工,认识水林师,他形容水林“聪明、会变通、技艺高、多才多艺”,客仔师傅整批人数庞大,气焰亦高,但水林则不以为然,也不为所动而甘愿屈居于下;他勇于相抗,虽然因而失去参与东山许多大庙的工作机会,他制作的民家用物品却颇受肯定,如红眠床,“艺高品精致”是当时大家对他的评价。
除了制作雕刻红眠床,水林师后来也开了店,自己做“水银花镜”来卖,在一堵一堵的玻璃上画画,画好了从后面淋上水银,淋了“真水”,水林师妻子,81岁的侄女陈颜贞老太太这么形容,“他画花鸟,也画龙凤,画在玻璃中央,四周淋了水银就成为水银花镜了,红眠床床顶上头有的会装上五堵水银花镜来装饰,也有做成长匾的,都很好看。”当时的流行风潮,水林师的作品颇受欢迎,东山同业的后人,也还记得昔日父亲赞美“水林师水银花镜画得好”。
晚年的水林师,平素都剪平头,个头高高的,并不很瘦,看起来“将才将才”,喜欢静静的写字画画和工作,不吵人,也不生气,个性温和,小孩子好奇围来观看时,他总会挥手叫小孩去别处玩,尤其淋水银时,他会对着站在边边看的小孩说:“这不能喷到哦,喷到要生疗的哦!快走、快走!”
不知是否因为水银制作花镜,长期接触水银的关系,加上凡事亲为又求好,以致操劳过多,积劳成病,引发肺疾,1940年,才46岁的水林师便结束了他多才多艺的传奇一生,留下13岁的朱福全一子,和结〓14年的妻子陈雁贞。
四、朱锡甘在澎湖的作品
朱锡甘在澎湖的宫庙作品,可分为两类,一是凿花木雕,一是彩绘和擂金画;如果以宫庙区分,则集中在开台澎湖天后宫和沙港的广圣殿两处,如前述,讲凿花木雕的作品,就不得不提起水林师之名,谈擂金画和彩绘堵仁之作,还是得说落款署名是朱锡甘。
4-1天后宫的凿花木雕
天后宫为国家一级古迹,除庙龄在台湾澎湖间是最古老外,装饰艺术的成就与保存,也是极重要和具代表性的,尤其是凿花木雕与彩绘两部份,擂金画则常引为典范。凿花木雕是由东山来的水林师、朱钦、黄文华三位师兄弟与泉州来的黄良师等分边施作,《澎湖天后宫保存计划》一书认为“山川步口可能以铜山(即东山)这班师傅,正殿可能以泉州这班师傅为主。”(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研究所都市计画室,1983,P.74)黄文华之子黄友谦则指出当时东山师负责做东边,这样的差异说法,难以直接论断孰是,一则当时凿花木雕的分工并不是直接采取包工的方式,而是“论件计酬的。蓝木将形虽已由大木工匠作的花材,依重要相对构件(如山川步口的左右狮座)交给同一班工匠的概略性原则,交给不同的匠师。”(同上)因此,三川殿、正殿,或者是东边、西边,都有可能因题材成对的需要,或者整体的进度,而打破东、西,三川殿与正殿的分际,再则完工的花柴作品,可能经几个师傅之手,且除正殿屏门的花鸟屏,通常皆不留姓名,也就更难区隔论断何者谁做的了。
不过,总的来说,天后宫的凿花木雕作品数量极多,散布在屋架、神龛、门扇各处,上至圣旨牌、斗栱、斗座、随、弯枋、吊筒、插角,下至屏堵等处都有,作品类型包括“人物带骑”的出头故事、兽类、水族、花鸟、器物等,内容丰富,成就颇高,都是由东山的三位师兄弟和泉州的黄良师等人完成,而水林师是东山这组的“头手”师傅,工夫最好,负责打粗胚,(王文良,2006,P.235)角色当与泉州来的黄良师傅同等重要。
4-2朱锡甘在天后宫的彩绘
澎湖天后宫的彩绘和擂金画,是台湾、澎湖的古老宫庙中,历史久远却能未经重绘,仍保有早期原貌的佳作,完成于1925年、1983-1985年的古迹修复工程,因为:目前无法寻得损坏部分之早期的照片或施工记录作为修复的依据,同时国内也欠缺鉴定现存彩绘残迹以分析原有之色彩、图样的技术,此外传统漆料的配制熬炼技巧以及绘画手艺等等,也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所以未敢遽以修补或添加,以免破坏了原有的质量。(王鸿楷,1985,P.1)
不过,逃过澎湖宫庙普遍30年翻修重建,或因屋顶“抓漏”同时彩绘重作的宿命,天后宫的彩绘作品却不敌岁月摧残致部份剥落,加上1985年整修完成涌进大量的信徒和观光客,香火鼎盛致作品渐见熏黑,且又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不当的保护漆措施而益显暗沉,但其傲人的成就,仍为识者赞赏。
完成这批彩绘的有朱锡甘、朱钦、黄文华这批东山师傅,来自台南的陈玉峰和与他合作的澎湖团队二批人马。朱锡甘与陈玉峰是两边的拿笔师傅,负责完成堵仁作品的“画师”角色,陈玉峰主要画三川殿入三川门后的空间,包括前落后步口与后落的明间、左右次间,朱锡甘则画三川殿前落前步口的明间和次间,以及正殿的前落后落所有堵仁画作。
人物画作是天后宫彩绘的重要成果之一,藏身于三川殿和正殿的架栋上,以演义故事的“出头”为题。虽然侧重情境的铺陈,但人物表情的描写,以及相互关系和透过肢体动势、布局安排,更增戏剧张力和效果。尤其线条的运用与精准,彷佛剧力万钧跃然纸上,如正殿前落明间左右架栋、和次间左、右架栋上,描写三国“赵子龙单骑救主”的故事。其它如三川殿前落前步廊,明间左右狮座底下大通上的“商汤访伊尹”、“文王访太公”(落款题为“渭水垂钓”)等画作,以及部分三通上所作人物画,则以轻柔线条,画境恬适,山石若似有情来展示。(王文良,2006,P.228)
正殿前后落的花鸟画,有落款署名的,几乎不出“朱澍”、“朱锡甘”、“一琴居士朱锡甘”、“朱一琴”、“一琴朱锡甘”等。表现手法上,有采取水墨设色写实秀美之作;也有单以水墨挥洒自如之作;更有先行将绿色作底,再以没骨技法来表现花鸟的巧致,绿底映衬之下,不论是白色龙爪菊、玉兰花,或粉色牡丹、莲花等,皆显灵透生动。部分画作,作者甚至在款识中特别记上“拟八大山人粉本”,“仿黄梅道人画意”等,显示画作有所本,不愿独美,这也正是画师执艺谦冲、胸怀磊落的体现。
人物画作外,以花鸟为主。朱锡甘在三川殿前落前步口除前述的人物画外,花鸟翎毛、山水、隶书、魏碑和行草书,穿插其间,扎实的传统书画工夫展露无遗,所作多富秀丽柔美韵致。其它则尚有藏身正殿明间左右架栋大通的背面,各分三段,画成中段大、左右小的三堵写实风景画,就造景和技法而言,朦胧中所见,表现的显然是当时流风所及的日本景色,这虽非传统题材,却为反映当下政治实况之作,这样的风格与作法,在落新建的宫庙中,也可见其遗绪。
4-3朱锡甘在天后宫的擂金画
擂金画是结合安金箔与擂金箔成金粉作画的一种技法,或称“泥金”或“扫金”,是彩绘艺术中的一个异数。在黑色或咖啡色为地的画面上,它不用色彩描绘,全然以深浅不同的金色来处理。安金箔或以干毛笔沾金粉在未干的底漆上,将题材影像的明暗层次做适切的展现,技巧难度较高,但更增华丽高贵视觉效果的手法。所用金箔则依其色泽和纯度,又有“顶红”和“大赤”、“二赤”之分,顶红的黄金纯度高,略带红色,大赤则为金色,二赤色泽略白,加有银的成份。这种擂金画在台湾地区不多见,澎湖本地唯独天后宫拥有多幅朱锡甘艺高境远的佳作,成为天后宫彩绘装饰的重要成就之一。
天后宫的擂金画施作于正殿的后落,从左右架栋到神龛,有多幅精采的作品。黑色背景做底,金色画作和图案在幽暗气氛和天窗泻入的光束下,随视者移动的角度更显得耀眼。架栋上的瓜筒,以及二通、三通上也都有擂金画的装饰手法,其中左右架栋上,二通的头尾各有一幅隶体书法和画作。左架栋穿插人物,右架栋则以博古题材常出现的几种瓶花,缀上吉祥小品,相当讨喜可爱。
神龛部分,则是擂金画聚集的重点。从大楣的三幅画作,到神龛左右裙堵四幅小品,构成一个独立的装饰领域。这中间安排穿插的凿花作品,也一并改为安金不施彩来呼应,形成一体的视觉效果。整个空间既呈静谧的氛围,又随自天窗投入的光束移动而显华丽跃动。大楣的中堵题为“富贵长春图”,在多朵盛开的牡丹花上,左绘展翅将歇的白头翁一只,回首望那右方成对栖息于摇曳枝头的鸟儿,牡丹花丛中则以右倾的寿石稳住中心。虽是花鸟无语,却在写实生动的影像中,流露出款款深情。两侧配以女性题材的人物画作,左为“虢国夫人承主恩”,右为“出汉关昭君长抱怨”,人物体态婀娜多姿,主角顾盼之情与侍仆视线的呼应,颇能传达出弦外之音。而女姓的题材,似乎也能呼应妈祖女神的神格。
下方四幅裙堵小品,分别是为“兰亭修禊”、“孟浩然踏雪寻梅”、“杜甫映壁题诗”、“赤壁泛舟”,描写的是王羲之、孟浩然、杜甫、苏东坡等文人逸事。题材或雅、或逸、或气势磅礴、或老友对坐话旧抒怀,情深境远,又是另一番世界。笔底下工夫尽然宣泄,金箔的显眼,以及金粉在干笔、漆底摩搓下的明暗层次,营造出山石肌理的阴阳向背,可谓“艺高境远、笔情墨趣俱足”之作(王文良2006,P.228)。.天后宫这批擂金画,由落款记载得知完成于“乙丑夏月”或“乙丑夏至前一日”,亦即天后宫重建完工后两年的1925年夏天。作者署名为“朱锡甘盥笔”、“朱锡甘摹古”、“一琴氏仿古”、“朱澍弟锡甘写”、“朱锡甘笔”。署名下方朱锡甘也比照传统画作钤印盖章,而画上印记。裙堵四件小品分别有育古、式、琴、仿古、如意,大楣左右虢国夫人和王昭君的题材有落款无署名,也没印章,但中间“富贵长春图”的署名“朱锡甘盥笔”下方,小而模糊的印文却是“东山”二字,原来,朱锡甘当年已有伏笔,只因印小位置高,又画作早因香火鼎盛熏黑难认,所以,一直为大家所疏忽,来自潮汕名师之称就延用数十年了。
擂金画能营造华丽的视觉,在用料上,使用和消耗的金箔量是相当可观的,有云“一贴、三扫、九堡金。扫金是贴金的三倍,堡金是贴金的九倍”(杜仙洲,1984,P.390),由此可见一般。不过,画师的妥善处置和适切发挥,更能增加其光彩,也就是笔下功夫的精良,更能呈现令人难以忘怀的视觉体验。
走访台湾与福建东山许多宫庙的擂金画后,经过比较,更能肯定与欣赏澎湖天后宫擂金画之可贵与杰出,以澎湖天后宫正殿神龛裙堵的四件小品“兰亭修禊”、“孟浩然踏雪寻梅”、“杜甫映壁题诗”、和苏东坡“赤壁泛舟”为例,朱锡甘擂金画的特色有:1.画面完整饱满、构图严谨、擂金、安金与线条钩勒的贴金交互运用,顶金、大赤、二赤材质的安排妥当,技法相当灵活纯熟。
2.擂金占画面的比例高,表现分量重要,居画面氛围的主导角色,安金贴金仅集中于衣服和树叶,和部分勾勒线条与文字。
3.擂金深浅层次变化多,以金彩代墨色,营造层层迭迭的崇山峻岭,既表现出中国水墨画的特色,又能发挥黄金耀眼的贵气。
4-4水林师沙港广圣殿的凿花木雕
广圣殿位于湖西乡沙港村,主祀叶、朱、张三府王爷,是该村村民的信仰中心。2007年9月出火之后接着拆除旧庙,新庙址北移而重新扩建成现代水泥大庙,并于2009年底落成入火。拆除的旧庙虽系1977年-1979年重建,但其结构和木石雕刻作品,系保留和沿用前一次重建完成于1929年的旧物,当时已有80年的历史了。广圣殿80年前的旧品,除了有历史和年代的意义外,在文化和艺术上的成就相当高。
水林师1925年完成澎湖天后宫的彩绘和擂金画后,返回福建东山,结婚、生子,期间,他再度应邀来澎湖,参与湖西沙港广圣殿的新建工程,时间在1927年-1929年间。
水林师除了与有三师两人分做凿花木雕外,分析也参与彩绘,并找来师兄弟朱钦和黄文华一同施作,可惜1977年展开重建前,没有留下相关记录与图照,所以彩绘失去了可稽的事证,但可确定的是:朱钦唯一的徒弟,沙港人曾福相应是来此施作期间,才收的。
水林师在沙港雕凿花柴的时间比有三师长,所以作品也比较多,整个牌楼面是水林师所做,除了圣旨牌雕成三龙护卫着,饱满精致外,其下的八仙斗座,两两成组分成四个,连同座骑,彼此似乎正对话着,八仙上方,由下而上,分别有兽类、水族、花鸟为题的五连弯枋,八仙下方,有三星斗座和兽类斗座与大楣衔接,大楣下方的大门两侧,则是春、夏、秋、冬,卍字盘长做底的四季花鸟屏。
此外,广圣殿内部,以鳌鱼和凰朝牡丹为题的插角,两两成对十分精彩,布袋和尚、李铁拐、象、狮为题的斗座,布景安排和造型则与一般宫庙略有差异,两边小港的注生娘娘和土地公的神龛花鸟屏堵,卍字底上分别安排造景的硕大湖石置于下方,上立牡丹、鹤、绵鸡等禽类,背后则以细长枝条带出花叶,摇曳之姿和鸟禽的动态安排,整体显现轻柔曼妙的感觉。
其中,前殿左右栋架上各安排有一个金瓜筒斗座,侧饰一蹲姿的人物竖仙,两手高举,有如“憨番扛庙角”般对应上方的斗栱,有趣的是这人手上还拿一方孔钱,右架栋的钱上并雕有“金钱世界”四字,是暗讽这世界一切向钱看,还是期待财源滚滚,80年前暗藏的想法,如今则不得而知了。
探讨水林师凿花的功力和作品的特色,可以水林师当年在离开沙港前,发下“以后如果有人凿的比他这支(大楣)更『卡水』,他要再做一支来换”豪语的大楣为例来了解。这支在广圣殿牌楼面下方,大门上方将近4公尺的大楣,水林师将之等分成三段,分别雕刻《西厢记》的“普救寺杜确退孙飞虎”、《三国演义》的“苦肉计”和《白蛇传》的“水淹金山寺”的故事。每个做事,在有限的空间里,各有13、4个人物周旋其间,随着故事情节安排背景与造境,繁复热闹而不杂乱,彼此牵引而流畅生动,略述如下:
1.人物比例精准,穿戴服饰随角色而华丽细致,或充满造型美感,如苦肉计的周瑜、蒋干、西庙记的张君瑞、杜确,以及水淹金山寺的虾兵鱼兵——龟、鲎和蚌精等。
2.人物表情和动作幅度变化大,不但呼应剧情、角色需要而呈现生动灵活之姿,且骨架结构合乎解剖学。
3.能依出头故事情节,安排人物配置的主从关系和视线的流动性,不但张力大、层次分明,且彼此环环相扣、扎实紧凑不冷场。
4.有限的木料厚度(15公分)里,虽是人物为主,但彼此交迭对话或冲突、加上建物、树石、与座骑、器物、波浪等,层层迭迭,将“内枝外叶”的层次,做了极大的发挥。
5.人物的“屈势”和人马的动态,也是这支大楣极为成功之处,当视线移动上下左右后,将发现水林师几乎是把他们做成圆雕作品般的精彩和完整。
五、结语
这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东山师傅朱水林(锡甘)在澎湖宫庙有精采的作品流传,他的身世长时间来却遭到误会,在水林师逝后70年,至他的墓碑取景拍完正面照片后,猛抬起头来,意识到自己竟是跪在他的坟前;我想,除了致敬,还有十二万分的佩服——在那样的年代,他两次远渡来澎湖,为我们留下至今仍让人称羡的佳作,形塑出今天珍贵的文化资产。
谈论澎湖的凿花和彩绘、擂金画,在东山水林师和广东潮汕朱锡甘两个名字各自流传数十年后,水林师而陈水林而朱水林,竟而与朱锡甘合而为一人,这些怪异的过程与时间点的巧合突破,让我们深感不可思议,前年(2010年)1月17日傍晚,澎湖东山一行6人(陈宗铭、东山资深凿花师、水林师内侄女、侄女婿、当地企业家和笔者)讨论到最后,竟是“冥冥中注定”做结。那天,东山见过与水林师熟稔的年逾八旬晚辈,熟悉水林师事迹的资深凿花师,他们也才知道“朱锡甘”之名,透过照片也才知道澎湖天后宫有水林师精彩的擂金画作。
这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经历,能为东山来澎湖进行宫庙装饰施作、横跨凿花木雕与彩绘两个领域的大师厘清身分和作品,个人深感荣幸,当然后续犹待努力,不过,愿藉此文,再次明白肯定下列事实:
1.澎湖天后宫精彩的擂金画作完成于1925年,作者是来自福建东山的唐山师“朱锡甘”,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水林师”。
2.天后宫中,同时期的彩绘作品,朱锡甘的堵仁画作涵盖正殿和三川殿前殿的前步口,他并有后代在台湾,但并不参与凿花木雕和彩绘擂金画。
3.天后宫当年的凿花木雕,参与的除了泉州来的黄良师等,另一批东山来的三个师兄弟:朱钦、黄文华外,“陈(?)水林”,就是朱水林,也就是朱锡甘。
4.朱锡甘曾经二度来澎湖参与宫庙工程,“水林师”就是这次沙港广圣殿凿花木雕时,当时村人所知道的名字。他在此对自己作品有充满自信的豪语发声,也间接提供解开水林师和朱锡甘身世之谜的关键。
5.澎湖目前保有朱锡甘的擂金画、彩绘、凿花木雕作品的天后宫,已是国家一级古迹,作品将永久被保护。沙港广圣殿虽因重新扩建,凿花木雕作品已拍卖,但买主承诺完整保留,并已于沙港村建立“印象·沙港民宿”,以民宿的人力和营运所得提拨经费维护设于民宿一楼的“沙港广圣殿文物典藏馆”,该典藏馆的展品,主要是水林师的凿花木雕,保存上不成问题,并对外开放免费参观。
6.不论澎湖乡亲或东山乡亲,大家熟悉的那个擅长凿花木雕的“水林师”,也就是擅长和完成澎湖天后宫的擂金画和彩绘作品,并长期被误以为来自广东潮汕客家师傅的“朱锡甘”——事实上他一直与“客仔师傅”“不合”。
笔者注:本文节录修改自2010年澎湖研究第十届学术研讨会,笔者发表的“朱锡甘(水林师)-澎湖宫庙装饰艺术的大师”一文,感谢过去提供意见和指导的木雕凿花师和前辈们,也十分谢谢接受访谈,提供协助的福建东山、台湾和澎湖在地的长辈朋友们。
参考文献:
1.杜仙洲主编,1984年,《中国古建筑修缮技术》,明文书局,台北市。
2.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研究所都市计画室规划,1983年,《澎湖天后宫保存计划》,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研究所都市计画室,台北市。
3.王鸿楷,1985年,《澎湖天后官之彩绘》,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研究所都市计画室,台北市。4.李干朗,1986年,《台湾的寺庙》,台湾省政府新闻处出版,台中市。5.林会承,1990年,《台湾传统建筑手册形式与作法篇》,艺术家出版社,台北市。
6.李干朗研究主持,1993年,《台湾传统建筑彩绘之调查研究;以台南民间彩画师陈玉峰及其传人之彩绘作品为对象》,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台北市。
7.李奕兴,1995年,《台湾传统彩绘》,艺术家出版社,台北市。
8.国立台北艺术大学,2002年,《新竹县北埔姜氏家庙彩绘纪录》,新竹县文化局,新竹县。
9.李干朗,2004年,《台湾传统建筑匠艺七辑》,燕楼古建筑出版社,台北。
10.王文良,2006年,(澎湖天后宫的装饰艺术〉,《开台澎湖天后宫志》,p.203~244,澎湖。
11.王文良,2010年,〈澎湖的宫庙凿花木雕发展概述〉,《第四届台湾·浙江文化节浙台民俗文化澎湖大讲堂论文集》,P.126-143,浙江省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会,澎湖地区两岸交流协会,浙江。
(编者注:本文中部分纪年书写及标点符号按规范作了调整。)
澎湖宫庙多,民众信仰虔诚和积极参与修建宫庙活动,过去曾礼聘“唐山师傅”前来施作,形塑澎湖特有的在地文化,也带出宫庙装饰艺术在澎湖的丰富面貌。其中,首列国家一级古迹的“开台澎湖天后宫”是为代表,且带动起一股宫庙装饰风潮,影响层面既深又广。
天后宫的艺术成就与影响,不仅是澎湖一地一隅而已,其凿花木雕和彩绘作品,至今仍然炫目。笔者往昔曾对参与凿花木雕的黄良师傅,及其在澎湖传承师系的调查和发展有所著墨,对另一参与凿花的东山水林师、参与彩绘的广东潮汕朱锡甘师的动向和作品,则一直关注和扒疏,无奈囿于年代久远和识者有限,诸多讯息和疑点难有突破,只能借着参与天后宫志,撰写其中〈天后宫的装饰艺术〉时,以朱锡甘为天后宫所完成的擂金画做结,陈述该批作品“不论是做为他个人在彩绘世界,或天后宫在宫庙彩绘中的代表性而言,都极具分量!”(王文良,2006,P.228)虽是致意,但又不得不根据有限的文献资料指出,“朱锡甘师为澎湖留下了相当多佳作,可惜只知他来自广东梅县大埔地区,其它都付诸关如。”(同上P.244)水林师也在做完澎湖天后宫后即整装返回东山老家了。
水林师与朱锡甘师这两个名字,曾经分别代表在澎湖天后宫施作的凿花师与彩绘师,文献上也分别记载来自福建东山和广东潮汕,如此看法行之有年,直到他离开澎湖80年后,我们做了连结、他逝后70年,笔者才为文在澎湖研究第十届学术研讨会上,试图为他厘清身世和正名:水林师就是朱锡甘,他来自东山,既擅长凿花木雕也善彩绘,他的成就是十分杰出的,在他为澎湖完成的宫庙彩绘和凿花木雕作品中,我们寻得力证;他是自豪的,我们在澎湖和东山的长者描述和转述中,得到诸多左证。虽然得年仅46岁,但他的作品和牵引的澎湖东山情谊,却是让我们感念和珍惜的!
二、过去文献中关于澎湖天后宫的
擂金画与朱锡甘、水林师
过去文献中,关于朱锡甘、水林师等人名,及凿花木雕、彩绘和擂金画等多有论述或提起;或深入探讨,或几句关键的话带过。不过,人名彼此的关连性,以及朱锡甘的出身地等,却有模糊又多样的说法,但长期来,被误解的情形是存在的。
2-1首见朱锡甘、水林师二名,并分属二人,同为东山岛人
文献中,最早提及“朱锡甘”、“水林”两个名字,是在1983年,“行政院”文建会补助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研究所都市计画室所出版的《澎湖天后宫保存计划》,是书乃根据该室1979年接受“交通部”观光局委托为期一年,研究保存之道的成果为主体所出版。书中指出“刺花”(应是凿花木雕)有一班是东山岛来的三位师兄弟,“朱钦、陈(?)水林、黄文华,以老二的功夫最好”,他们三人“也负责油漆,遍在天后宫各处的题名‘朱锡甘’应就是朱钦的别名,弟‘一琴’应就是水林司”(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研究所都市计画室,1983,P.54)
2-2肯定天后宫彩绘和擂金画,出现“朱澍传”之名
之后1983-1985年天后宫的修复工作,并未对彩绘作品有进一步的修补或添加动作,倒是事后发现屋顶全面翻修时,“因未能及时有效的对现存彩绘加以保护,经事后勘察,发现彩绘剥落又较以往严重”,(王鸿楷,1985,P.1)乃建议并经文建会拨款补助专业拍摄和纪录,同时于1985年出版《澎湖天后宫之彩绘》专书,书中指出“天后宫的彩绘具有多样风貌,”(同上)叙明有水墨静物及墨竹作品,“署名则是朱锡甘和朱澍传”。(同上P.3)指出“擂金画在澎湖天后宫被普遍地使用,同时也形成了天后宫最重要的艺术成就之一”,(同上P.4)并进而称许“以金箔之浓淡轻重表现出山水岩石的各种皴法、技法之纯熟亦是台湾少见”。(同上,P.4)这是进一步对天后宫擂金画的肯定之始,也在此首次出现“朱澍传”的名字。
2-3朱锡甘来自广东潮州大埔,朱锡甘兄弟主绘正殿的连结
李干朗教授于1986年出版的《台湾的寺庙》一书,谈起澎湖寺庙修建情形,指出蓝木、蓝合兄弟受邀主持天后宫重修,“配合的匠师还有卢司、水林司及来自汕头的龙司”,(李干朗,1986,P.104)“彩画匠有朱锡甘、潘科等人,朱氏的传世名作是天后宫神龛左右福扇的黑底擂金画,至今尚保存完好,弥足珍贵”,(同上)之后论及台湾南北彩绘师傅名家辈出时,特别指出“有的出身画家,至少工于书法”,接着说“大陆名匠则有广东潮州大埔来的苏滨庭及朱锡甘,后者绘马公天后宫”,(同上P.105),显然在此时,水林师已经从东山岛来的三个师兄弟被独立出来,朱锡甘也被确认为来自广东潮州大埔。
同书后续介绍澎湖天后宫时,李干朗直接表示彩绘水平颇高,正殿的“神龛两侧有朱锡甘所作擂金彩画,工精质优,值得永久保存”,并分析天后宫的彩绘为前后对场,“台南陈玉峰主绘三川,大埔朱锡甘兄弟主绘正殿,三川以青绿为基调,正殿以黑色基调,各有千秋,论精细则以大殿垛头见长”(同上P.155),在注中则进一步表示“天后宫彩画很值得研究”,“正殿以大埔系统朱锡甘及朱澍传为主。”(同上P.170),此为文献上继续肯定朱锡甘的彩绘成就外,也二度出现朱澍传,并有“朱锡甘兄弟”乃朱锡甘及朱澍传的连结。
2-4比较后,对澎湖天后宫擂金画的高度肯定
1990年,林会承教授的《台湾传统建筑手册形式与作法篇》一书在论述色彩与彩绘时,曾对擂金画的制作程序做了介绍,并说“目的是使室内显得“金碧辉煌””(林会承,1990,P.127),后续篇章则列举了几个台湾尚保有擂金画的宫庙祠堂,他特别指出“其中以澎湖天后宫之作品的艺术水平最高”(同上P.131),这是将澎湖天后宫擂金画与台湾同类作品并列比较后,直接抽离而出的高度肯定。
2-5朱锡甘在澎湖天后宫的分工角色
继而,李干朗主持以台南民间彩绘画师陈玉峰及其传人的彩绘作品为对象,所出版的《台湾传统建筑彩绘之调查研究》,书中指出陈玉峰和“潮汕籍的彩绘匠师朱锡甘等人”于“民国十四年时”,就“携手共彩澎湖天后宫”,(李干朗,1993,P.66)“陈玉峰工作范围以三川殿为主”(同上),而“朱锡甘则负责正殿和后殿阁楼全部油漆彩绘工程”,(同上P.70)并从澎湖天后宫现存的彩绘作品来观察比较,进一步推测“陈玉峰遗留作品不比朱锡甘多,因此有可能陈玉峰是以副手上场。”(同上)换言之,朱锡甘显然才是当年彩绘的主力,为朱锡甘在分工角色上做了厘清。
2-6对擂金画的异见
李奕兴先生则在1995年出版的《台湾传统彩绘》书中提及“台湾目前在传统建筑学术界,极度推崇的所谓‘擂金画’黑底金漆图画,澎湖天后宫有实例”,他似乎不以为然的指出“几乎已到过度神话式的吹棒,犹以台湾独具的特产之一,事实这就是漆工艺里的‘泥金’技法一种”,(李奕兴,1995,P.63),这可能是学界对擂金画的看法提出异见的首例,虽然详细的研究论述仍有待进一步的推敲,不过,独以澎湖天后宫为例,也可见作者视该批作品为代表。
此后,陆续的研究或著作中,仍多有提及朱锡甘等师傅的讯息,关于其生平及何方人士,则有不同的说法,朱锡甘与共同参与的师傅群也有不同的解读,同时,前后出现许多不同的名字,但大概不出上面所述范围。至于其中正确与否?一些推论的人名是否真有其人?大家显然无力解决,只有继续流传沿用或相互引用。
三、文献资料的扒疏与田野调查中的朱锡甘
文献中,除了《澎湖天后宫保存计划》点出东山岛来的三位师兄弟,同时担任凿花木雕与彩绘,并试着勾勒朱钦、陈(?)水林、黄文华与朱锡甘、一琴的关系外,其余几乎是将参与凿花木雕(若该文有论及)与彩绘的师傅分开来叙述,笼统的说,参与凿花木雕的是福建东山来的三个师兄弟,而绘制擂金画与彩绘的人,则是来自广东潮州的「朱锡甘兄弟」等,何以致之?这其实是诸多原因造成的!
3-1文献的扒疏比对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书中,谈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由台南漳泉郊商倡建的台南水仙宫时,有“庙中亭脊,雕镂人物花草,备极精巧,皆潮州工匠为之。”(转引自国立台北艺术大学,2002,P.72)的记叙,说明早在近300年前,潮州师傅就已来台湾参与宫庙的工程,且“雕镂人物花草,备极精巧”。(同上)
或许是“粤东大埔位于韩江上游,古代与下游的潮州文化关系密切”,(李干朗,2004,)同时“大埔在清末出了不少著名的建筑彩绘名匠,特别是擂金画、泥金画及鎏金画”,(同上,)而且“潮州自古以来最擅长的家具制作传统”,“多用擂金、泥金或鎏金,闻名海内外”(同上),因此,互为影响,大埔彩绘水平高,名师倍出,又有多人来台展示才艺,同样时空背景、擅长擂金画的朱锡甘因而被视为大埔人,自有其合理性。至少,在缺乏否定这个认定的直接证据和左证数据下,这是最可能的答案,因此,不疑有他的一再引用就很自然合理了。
至于朱澍、朱锡甘、一琴等名字,笔者曾一再观察细究并揣摩再三,而于《开台澎湖天后宫志》里,大胆做出以下的推测:
由种种迹像显示,及正殿明间右架栋背面的花鸟画作,,落款“仿黄梅道人画意一琴朱锡甘写意”,正殿前落后步口次间架栋上,“群芳聚会”花鸟画作上的署名“一琴居士朱锡甘”判断,朱澍、朱锡甘、一琴等,应是同一人的名、字、号,只是落款不同,以增加变化。(王文良,2006,P.244)
以此试着推翻一再相沿的说法,直到2010年的《第四届台湾?浙江文化节浙台民俗文化澎湖大讲堂论文集》,笔者提出“……朱锡甘,天后宫完工离去后,1929年落成的湖西沙港广圣殿的凿花是朱锡甘来澎湖两度之作,生动细致十分耀眼。”(王文良,2010,P.135),指出朱锡甘二度来澎参与凿花施作,而点出与水林师的连结。
关于他的名字,或出于笔误、或出于误认、或出于推论,也有的是朱师个人的习惯,给人错误的连结(详见澎湖研究第十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3-2沙港广圣殿凿花旧作拍卖另起契机
不过经由2007年底,澎湖县湖西乡沙港村村庙广圣殿因为扩建,将旧庙拆除并拍卖凿花木雕旧作,买主由该村旅外的乡亲陈宗铭先生,于2008年1月26日标得,原只是想留几件童年庙口记忆的陈先生,与笔者取得连系,对这批作品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后,不但发愿并接着着手为该批作品营造完成了一个雅致可亲的展示空间。在从村中耆老陈保壮处得知作者叫“水林”,后来更于2009年7月中旬展开深入的福建探访寻根之旅,想为这批精彩木雕作品的作者“水林师”,找得相关作品和事迹,以为比对和印证,不过,水林师的事迹虽得一些,凿花作品却无所获,知道姓“朱”,得年46岁,摄得墓碑照片,确认1940年辞世,碑上却没水林师的名字。然而,事后笔者却发现“锡甘”二字。前年(2010年)初,笔者的一趟东山行,亲近和走着朱锡甘师傅昔日的足迹,探访朱师在家乡的事迹,得到了大陆东山、台湾及澎湖的许多朋友协助,得以厘清许多疑点,也勾勒出朱锡甘师傅比较清楚的轮廓。
3-3朱锡甘这个人
朱锡甘,也就是朱水林,福建东山人,清光绪廿一年(1895年)生,民国29年(1940年)逝于家乡东山,得年46岁。
3-3-1朱锡甘的澎湖行及娶妻与兄弟
朱锡甘,以“水林”之名见闻于往来的生活圈中,1922年左右,与师兄弟朱钦、黄文华同至澎湖天后宫,参与凿花木雕工作,接着进行彩绘,至1925年秋天后,完成擂金画和三川殿前步口、正殿的堵仁彩绘画作后,彩绘工作即便结束而返回东山。目前天后宫这些彩绘和擂金画作品中,部分落款有时间和署名可为证。
回到东山约一年多,33岁的朱水林娶了同为东山人的陈雁贞为妻,由于水林师之母早逝,父亲也已续弦另组家庭,因此,他们婚后暂住妻子的娘家。不久,水林师又再度应邀至澎湖的湖西沙港,参与广圣殿的木雕凿花工作。从此,水林之妻即长住娘家,直至1929年广圣殿完工,水林师归来,也就跟着一直住下来,只有每年除夕前碍于女儿必须大年初二始得回娘家的传统习俗,因此有几天暂时离开外,水林师的工作和活动,都在太太的娘家陈姓这头进行,后来他也在此开了店。或许,这就是同为东山人的文华师之妻,在数十年后回想水林师姓氏时,依地缘关系而指为“陈”姓之故吧!
水林师并无兄长,只有同父异母的弟弟叫阿棋,后来跟水林学凿花,但时间上已是水林师结束澎湖工作以后的事了,而且功夫显然不如水林师出色,因此,朱锡甘兄弟做天后宫彩绘的说法并不能成立。
当年水林师与朱钦、黄文华三个师兄弟来澎湖工作时,他们的师傅曾叮咛:“不要一桶酒放下,三个人就喝到倒,工作通通不晓得要做了。”黄文华年近80的大儿子一澎湖彩绘名师黄友谦,曾听父亲生前说起这段往事,可惜记不得他们师傅的名字了。不过沙港工作期间,或是离开澎湖回到东山后,近身参观或相处的晚辈,都表示极少见到水林师喝酒。
1927-1929年,沙港广圣殿的凿花木雕本是水林师与有三师对场,后因故有三师离开,因此,大部分花柴作品都由水林师完成,他对自己的作品颇有自信,也赢得在地人的肯定,尤其叙述三段出头故事的中港门大楣,更是精湛,临去时,他曾发下豪语,前年受访时92岁的陈保壮老先生佩服的转述:“以后有人凿得比他这支(指大楣)卡水,他要再做一支来换!”
3-3-2东山的水林师
水林师的豪气,不只在沙港展现,在东山亦然;他的媳妇返回东山时,也曾听长辈说起他:“做得比我好,我就再做”的豪语,不服输,对自己的功夫很有自信,同时,一切自己动手做。当年东山十大庙,几乎都是“客仔师傅”的天下,所谓的客仔师傅,即来自福建南部的闽南如永定,和粤东的广东潮汕地区的客家籍的师傅,包含木工、土水、雕刻和彩绘,他们的工夫在当地人的眼里是很好的,雕刻也都很精致的。
住东山的资深凿花师许庆石先生,以前曾听一90多岁的老人说,当地宫庙并没有水林师的作品,因为他和“客仔师”不合,这老人认识很多凿花师,他说水林师“‘骄’,是厉害的人,勇的人会‘骄’”,老人赞许水林师字画都很好,雕刻也很好,每项都很勥(行),字也“真水”啦;当地老辈的师傅都知道水林师到澎湖施作过,也都肯定他的技艺。许庆石的父亲当年做木工,认识水林师,他形容水林“聪明、会变通、技艺高、多才多艺”,客仔师傅整批人数庞大,气焰亦高,但水林则不以为然,也不为所动而甘愿屈居于下;他勇于相抗,虽然因而失去参与东山许多大庙的工作机会,他制作的民家用物品却颇受肯定,如红眠床,“艺高品精致”是当时大家对他的评价。
除了制作雕刻红眠床,水林师后来也开了店,自己做“水银花镜”来卖,在一堵一堵的玻璃上画画,画好了从后面淋上水银,淋了“真水”,水林师妻子,81岁的侄女陈颜贞老太太这么形容,“他画花鸟,也画龙凤,画在玻璃中央,四周淋了水银就成为水银花镜了,红眠床床顶上头有的会装上五堵水银花镜来装饰,也有做成长匾的,都很好看。”当时的流行风潮,水林师的作品颇受欢迎,东山同业的后人,也还记得昔日父亲赞美“水林师水银花镜画得好”。
晚年的水林师,平素都剪平头,个头高高的,并不很瘦,看起来“将才将才”,喜欢静静的写字画画和工作,不吵人,也不生气,个性温和,小孩子好奇围来观看时,他总会挥手叫小孩去别处玩,尤其淋水银时,他会对着站在边边看的小孩说:“这不能喷到哦,喷到要生疗的哦!快走、快走!”
不知是否因为水银制作花镜,长期接触水银的关系,加上凡事亲为又求好,以致操劳过多,积劳成病,引发肺疾,1940年,才46岁的水林师便结束了他多才多艺的传奇一生,留下13岁的朱福全一子,和结〓14年的妻子陈雁贞。
四、朱锡甘在澎湖的作品
朱锡甘在澎湖的宫庙作品,可分为两类,一是凿花木雕,一是彩绘和擂金画;如果以宫庙区分,则集中在开台澎湖天后宫和沙港的广圣殿两处,如前述,讲凿花木雕的作品,就不得不提起水林师之名,谈擂金画和彩绘堵仁之作,还是得说落款署名是朱锡甘。
4-1天后宫的凿花木雕
天后宫为国家一级古迹,除庙龄在台湾澎湖间是最古老外,装饰艺术的成就与保存,也是极重要和具代表性的,尤其是凿花木雕与彩绘两部份,擂金画则常引为典范。凿花木雕是由东山来的水林师、朱钦、黄文华三位师兄弟与泉州来的黄良师等分边施作,《澎湖天后宫保存计划》一书认为“山川步口可能以铜山(即东山)这班师傅,正殿可能以泉州这班师傅为主。”(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研究所都市计画室,1983,P.74)黄文华之子黄友谦则指出当时东山师负责做东边,这样的差异说法,难以直接论断孰是,一则当时凿花木雕的分工并不是直接采取包工的方式,而是“论件计酬的。蓝木将形虽已由大木工匠作的花材,依重要相对构件(如山川步口的左右狮座)交给同一班工匠的概略性原则,交给不同的匠师。”(同上)因此,三川殿、正殿,或者是东边、西边,都有可能因题材成对的需要,或者整体的进度,而打破东、西,三川殿与正殿的分际,再则完工的花柴作品,可能经几个师傅之手,且除正殿屏门的花鸟屏,通常皆不留姓名,也就更难区隔论断何者谁做的了。
不过,总的来说,天后宫的凿花木雕作品数量极多,散布在屋架、神龛、门扇各处,上至圣旨牌、斗栱、斗座、随、弯枋、吊筒、插角,下至屏堵等处都有,作品类型包括“人物带骑”的出头故事、兽类、水族、花鸟、器物等,内容丰富,成就颇高,都是由东山的三位师兄弟和泉州的黄良师等人完成,而水林师是东山这组的“头手”师傅,工夫最好,负责打粗胚,(王文良,2006,P.235)角色当与泉州来的黄良师傅同等重要。
4-2朱锡甘在天后宫的彩绘
澎湖天后宫的彩绘和擂金画,是台湾、澎湖的古老宫庙中,历史久远却能未经重绘,仍保有早期原貌的佳作,完成于1925年、1983-1985年的古迹修复工程,因为:目前无法寻得损坏部分之早期的照片或施工记录作为修复的依据,同时国内也欠缺鉴定现存彩绘残迹以分析原有之色彩、图样的技术,此外传统漆料的配制熬炼技巧以及绘画手艺等等,也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所以未敢遽以修补或添加,以免破坏了原有的质量。(王鸿楷,1985,P.1)
不过,逃过澎湖宫庙普遍30年翻修重建,或因屋顶“抓漏”同时彩绘重作的宿命,天后宫的彩绘作品却不敌岁月摧残致部份剥落,加上1985年整修完成涌进大量的信徒和观光客,香火鼎盛致作品渐见熏黑,且又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不当的保护漆措施而益显暗沉,但其傲人的成就,仍为识者赞赏。
完成这批彩绘的有朱锡甘、朱钦、黄文华这批东山师傅,来自台南的陈玉峰和与他合作的澎湖团队二批人马。朱锡甘与陈玉峰是两边的拿笔师傅,负责完成堵仁作品的“画师”角色,陈玉峰主要画三川殿入三川门后的空间,包括前落后步口与后落的明间、左右次间,朱锡甘则画三川殿前落前步口的明间和次间,以及正殿的前落后落所有堵仁画作。
人物画作是天后宫彩绘的重要成果之一,藏身于三川殿和正殿的架栋上,以演义故事的“出头”为题。虽然侧重情境的铺陈,但人物表情的描写,以及相互关系和透过肢体动势、布局安排,更增戏剧张力和效果。尤其线条的运用与精准,彷佛剧力万钧跃然纸上,如正殿前落明间左右架栋、和次间左、右架栋上,描写三国“赵子龙单骑救主”的故事。其它如三川殿前落前步廊,明间左右狮座底下大通上的“商汤访伊尹”、“文王访太公”(落款题为“渭水垂钓”)等画作,以及部分三通上所作人物画,则以轻柔线条,画境恬适,山石若似有情来展示。(王文良,2006,P.228)
正殿前后落的花鸟画,有落款署名的,几乎不出“朱澍”、“朱锡甘”、“一琴居士朱锡甘”、“朱一琴”、“一琴朱锡甘”等。表现手法上,有采取水墨设色写实秀美之作;也有单以水墨挥洒自如之作;更有先行将绿色作底,再以没骨技法来表现花鸟的巧致,绿底映衬之下,不论是白色龙爪菊、玉兰花,或粉色牡丹、莲花等,皆显灵透生动。部分画作,作者甚至在款识中特别记上“拟八大山人粉本”,“仿黄梅道人画意”等,显示画作有所本,不愿独美,这也正是画师执艺谦冲、胸怀磊落的体现。
人物画作外,以花鸟为主。朱锡甘在三川殿前落前步口除前述的人物画外,花鸟翎毛、山水、隶书、魏碑和行草书,穿插其间,扎实的传统书画工夫展露无遗,所作多富秀丽柔美韵致。其它则尚有藏身正殿明间左右架栋大通的背面,各分三段,画成中段大、左右小的三堵写实风景画,就造景和技法而言,朦胧中所见,表现的显然是当时流风所及的日本景色,这虽非传统题材,却为反映当下政治实况之作,这样的风格与作法,在落新建的宫庙中,也可见其遗绪。
4-3朱锡甘在天后宫的擂金画
擂金画是结合安金箔与擂金箔成金粉作画的一种技法,或称“泥金”或“扫金”,是彩绘艺术中的一个异数。在黑色或咖啡色为地的画面上,它不用色彩描绘,全然以深浅不同的金色来处理。安金箔或以干毛笔沾金粉在未干的底漆上,将题材影像的明暗层次做适切的展现,技巧难度较高,但更增华丽高贵视觉效果的手法。所用金箔则依其色泽和纯度,又有“顶红”和“大赤”、“二赤”之分,顶红的黄金纯度高,略带红色,大赤则为金色,二赤色泽略白,加有银的成份。这种擂金画在台湾地区不多见,澎湖本地唯独天后宫拥有多幅朱锡甘艺高境远的佳作,成为天后宫彩绘装饰的重要成就之一。
天后宫的擂金画施作于正殿的后落,从左右架栋到神龛,有多幅精采的作品。黑色背景做底,金色画作和图案在幽暗气氛和天窗泻入的光束下,随视者移动的角度更显得耀眼。架栋上的瓜筒,以及二通、三通上也都有擂金画的装饰手法,其中左右架栋上,二通的头尾各有一幅隶体书法和画作。左架栋穿插人物,右架栋则以博古题材常出现的几种瓶花,缀上吉祥小品,相当讨喜可爱。
神龛部分,则是擂金画聚集的重点。从大楣的三幅画作,到神龛左右裙堵四幅小品,构成一个独立的装饰领域。这中间安排穿插的凿花作品,也一并改为安金不施彩来呼应,形成一体的视觉效果。整个空间既呈静谧的氛围,又随自天窗投入的光束移动而显华丽跃动。大楣的中堵题为“富贵长春图”,在多朵盛开的牡丹花上,左绘展翅将歇的白头翁一只,回首望那右方成对栖息于摇曳枝头的鸟儿,牡丹花丛中则以右倾的寿石稳住中心。虽是花鸟无语,却在写实生动的影像中,流露出款款深情。两侧配以女性题材的人物画作,左为“虢国夫人承主恩”,右为“出汉关昭君长抱怨”,人物体态婀娜多姿,主角顾盼之情与侍仆视线的呼应,颇能传达出弦外之音。而女姓的题材,似乎也能呼应妈祖女神的神格。
下方四幅裙堵小品,分别是为“兰亭修禊”、“孟浩然踏雪寻梅”、“杜甫映壁题诗”、“赤壁泛舟”,描写的是王羲之、孟浩然、杜甫、苏东坡等文人逸事。题材或雅、或逸、或气势磅礴、或老友对坐话旧抒怀,情深境远,又是另一番世界。笔底下工夫尽然宣泄,金箔的显眼,以及金粉在干笔、漆底摩搓下的明暗层次,营造出山石肌理的阴阳向背,可谓“艺高境远、笔情墨趣俱足”之作(王文良2006,P.228)。.天后宫这批擂金画,由落款记载得知完成于“乙丑夏月”或“乙丑夏至前一日”,亦即天后宫重建完工后两年的1925年夏天。作者署名为“朱锡甘盥笔”、“朱锡甘摹古”、“一琴氏仿古”、“朱澍弟锡甘写”、“朱锡甘笔”。署名下方朱锡甘也比照传统画作钤印盖章,而画上印记。裙堵四件小品分别有育古、式、琴、仿古、如意,大楣左右虢国夫人和王昭君的题材有落款无署名,也没印章,但中间“富贵长春图”的署名“朱锡甘盥笔”下方,小而模糊的印文却是“东山”二字,原来,朱锡甘当年已有伏笔,只因印小位置高,又画作早因香火鼎盛熏黑难认,所以,一直为大家所疏忽,来自潮汕名师之称就延用数十年了。
擂金画能营造华丽的视觉,在用料上,使用和消耗的金箔量是相当可观的,有云“一贴、三扫、九堡金。扫金是贴金的三倍,堡金是贴金的九倍”(杜仙洲,1984,P.390),由此可见一般。不过,画师的妥善处置和适切发挥,更能增加其光彩,也就是笔下功夫的精良,更能呈现令人难以忘怀的视觉体验。
走访台湾与福建东山许多宫庙的擂金画后,经过比较,更能肯定与欣赏澎湖天后宫擂金画之可贵与杰出,以澎湖天后宫正殿神龛裙堵的四件小品“兰亭修禊”、“孟浩然踏雪寻梅”、“杜甫映壁题诗”、和苏东坡“赤壁泛舟”为例,朱锡甘擂金画的特色有:1.画面完整饱满、构图严谨、擂金、安金与线条钩勒的贴金交互运用,顶金、大赤、二赤材质的安排妥当,技法相当灵活纯熟。
2.擂金占画面的比例高,表现分量重要,居画面氛围的主导角色,安金贴金仅集中于衣服和树叶,和部分勾勒线条与文字。
3.擂金深浅层次变化多,以金彩代墨色,营造层层迭迭的崇山峻岭,既表现出中国水墨画的特色,又能发挥黄金耀眼的贵气。
4-4水林师沙港广圣殿的凿花木雕
广圣殿位于湖西乡沙港村,主祀叶、朱、张三府王爷,是该村村民的信仰中心。2007年9月出火之后接着拆除旧庙,新庙址北移而重新扩建成现代水泥大庙,并于2009年底落成入火。拆除的旧庙虽系1977年-1979年重建,但其结构和木石雕刻作品,系保留和沿用前一次重建完成于1929年的旧物,当时已有80年的历史了。广圣殿80年前的旧品,除了有历史和年代的意义外,在文化和艺术上的成就相当高。
水林师1925年完成澎湖天后宫的彩绘和擂金画后,返回福建东山,结婚、生子,期间,他再度应邀来澎湖,参与湖西沙港广圣殿的新建工程,时间在1927年-1929年间。
水林师除了与有三师两人分做凿花木雕外,分析也参与彩绘,并找来师兄弟朱钦和黄文华一同施作,可惜1977年展开重建前,没有留下相关记录与图照,所以彩绘失去了可稽的事证,但可确定的是:朱钦唯一的徒弟,沙港人曾福相应是来此施作期间,才收的。
水林师在沙港雕凿花柴的时间比有三师长,所以作品也比较多,整个牌楼面是水林师所做,除了圣旨牌雕成三龙护卫着,饱满精致外,其下的八仙斗座,两两成组分成四个,连同座骑,彼此似乎正对话着,八仙上方,由下而上,分别有兽类、水族、花鸟为题的五连弯枋,八仙下方,有三星斗座和兽类斗座与大楣衔接,大楣下方的大门两侧,则是春、夏、秋、冬,卍字盘长做底的四季花鸟屏。
此外,广圣殿内部,以鳌鱼和凰朝牡丹为题的插角,两两成对十分精彩,布袋和尚、李铁拐、象、狮为题的斗座,布景安排和造型则与一般宫庙略有差异,两边小港的注生娘娘和土地公的神龛花鸟屏堵,卍字底上分别安排造景的硕大湖石置于下方,上立牡丹、鹤、绵鸡等禽类,背后则以细长枝条带出花叶,摇曳之姿和鸟禽的动态安排,整体显现轻柔曼妙的感觉。
其中,前殿左右栋架上各安排有一个金瓜筒斗座,侧饰一蹲姿的人物竖仙,两手高举,有如“憨番扛庙角”般对应上方的斗栱,有趣的是这人手上还拿一方孔钱,右架栋的钱上并雕有“金钱世界”四字,是暗讽这世界一切向钱看,还是期待财源滚滚,80年前暗藏的想法,如今则不得而知了。
探讨水林师凿花的功力和作品的特色,可以水林师当年在离开沙港前,发下“以后如果有人凿的比他这支(大楣)更『卡水』,他要再做一支来换”豪语的大楣为例来了解。这支在广圣殿牌楼面下方,大门上方将近4公尺的大楣,水林师将之等分成三段,分别雕刻《西厢记》的“普救寺杜确退孙飞虎”、《三国演义》的“苦肉计”和《白蛇传》的“水淹金山寺”的故事。每个做事,在有限的空间里,各有13、4个人物周旋其间,随着故事情节安排背景与造境,繁复热闹而不杂乱,彼此牵引而流畅生动,略述如下:
1.人物比例精准,穿戴服饰随角色而华丽细致,或充满造型美感,如苦肉计的周瑜、蒋干、西庙记的张君瑞、杜确,以及水淹金山寺的虾兵鱼兵——龟、鲎和蚌精等。
2.人物表情和动作幅度变化大,不但呼应剧情、角色需要而呈现生动灵活之姿,且骨架结构合乎解剖学。
3.能依出头故事情节,安排人物配置的主从关系和视线的流动性,不但张力大、层次分明,且彼此环环相扣、扎实紧凑不冷场。
4.有限的木料厚度(15公分)里,虽是人物为主,但彼此交迭对话或冲突、加上建物、树石、与座骑、器物、波浪等,层层迭迭,将“内枝外叶”的层次,做了极大的发挥。
5.人物的“屈势”和人马的动态,也是这支大楣极为成功之处,当视线移动上下左右后,将发现水林师几乎是把他们做成圆雕作品般的精彩和完整。
五、结语
这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东山师傅朱水林(锡甘)在澎湖宫庙有精采的作品流传,他的身世长时间来却遭到误会,在水林师逝后70年,至他的墓碑取景拍完正面照片后,猛抬起头来,意识到自己竟是跪在他的坟前;我想,除了致敬,还有十二万分的佩服——在那样的年代,他两次远渡来澎湖,为我们留下至今仍让人称羡的佳作,形塑出今天珍贵的文化资产。
谈论澎湖的凿花和彩绘、擂金画,在东山水林师和广东潮汕朱锡甘两个名字各自流传数十年后,水林师而陈水林而朱水林,竟而与朱锡甘合而为一人,这些怪异的过程与时间点的巧合突破,让我们深感不可思议,前年(2010年)1月17日傍晚,澎湖东山一行6人(陈宗铭、东山资深凿花师、水林师内侄女、侄女婿、当地企业家和笔者)讨论到最后,竟是“冥冥中注定”做结。那天,东山见过与水林师熟稔的年逾八旬晚辈,熟悉水林师事迹的资深凿花师,他们也才知道“朱锡甘”之名,透过照片也才知道澎湖天后宫有水林师精彩的擂金画作。
这真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经历,能为东山来澎湖进行宫庙装饰施作、横跨凿花木雕与彩绘两个领域的大师厘清身分和作品,个人深感荣幸,当然后续犹待努力,不过,愿藉此文,再次明白肯定下列事实:
1.澎湖天后宫精彩的擂金画作完成于1925年,作者是来自福建东山的唐山师“朱锡甘”,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水林师”。
2.天后宫中,同时期的彩绘作品,朱锡甘的堵仁画作涵盖正殿和三川殿前殿的前步口,他并有后代在台湾,但并不参与凿花木雕和彩绘擂金画。
3.天后宫当年的凿花木雕,参与的除了泉州来的黄良师等,另一批东山来的三个师兄弟:朱钦、黄文华外,“陈(?)水林”,就是朱水林,也就是朱锡甘。
4.朱锡甘曾经二度来澎湖参与宫庙工程,“水林师”就是这次沙港广圣殿凿花木雕时,当时村人所知道的名字。他在此对自己作品有充满自信的豪语发声,也间接提供解开水林师和朱锡甘身世之谜的关键。
5.澎湖目前保有朱锡甘的擂金画、彩绘、凿花木雕作品的天后宫,已是国家一级古迹,作品将永久被保护。沙港广圣殿虽因重新扩建,凿花木雕作品已拍卖,但买主承诺完整保留,并已于沙港村建立“印象·沙港民宿”,以民宿的人力和营运所得提拨经费维护设于民宿一楼的“沙港广圣殿文物典藏馆”,该典藏馆的展品,主要是水林师的凿花木雕,保存上不成问题,并对外开放免费参观。
6.不论澎湖乡亲或东山乡亲,大家熟悉的那个擅长凿花木雕的“水林师”,也就是擅长和完成澎湖天后宫的擂金画和彩绘作品,并长期被误以为来自广东潮汕客家师傅的“朱锡甘”——事实上他一直与“客仔师傅”“不合”。
笔者注:本文节录修改自2010年澎湖研究第十届学术研讨会,笔者发表的“朱锡甘(水林师)-澎湖宫庙装饰艺术的大师”一文,感谢过去提供意见和指导的木雕凿花师和前辈们,也十分谢谢接受访谈,提供协助的福建东山、台湾和澎湖在地的长辈朋友们。
参考文献:
1.杜仙洲主编,1984年,《中国古建筑修缮技术》,明文书局,台北市。
2.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研究所都市计画室规划,1983年,《澎湖天后宫保存计划》,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研究所都市计画室,台北市。
3.王鸿楷,1985年,《澎湖天后官之彩绘》,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研究所都市计画室,台北市。4.李干朗,1986年,《台湾的寺庙》,台湾省政府新闻处出版,台中市。5.林会承,1990年,《台湾传统建筑手册形式与作法篇》,艺术家出版社,台北市。
6.李干朗研究主持,1993年,《台湾传统建筑彩绘之调查研究;以台南民间彩画师陈玉峰及其传人之彩绘作品为对象》,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台北市。
7.李奕兴,1995年,《台湾传统彩绘》,艺术家出版社,台北市。
8.国立台北艺术大学,2002年,《新竹县北埔姜氏家庙彩绘纪录》,新竹县文化局,新竹县。
9.李干朗,2004年,《台湾传统建筑匠艺七辑》,燕楼古建筑出版社,台北。
10.王文良,2006年,(澎湖天后宫的装饰艺术〉,《开台澎湖天后宫志》,p.203~244,澎湖。
11.王文良,2010年,〈澎湖的宫庙凿花木雕发展概述〉,《第四届台湾·浙江文化节浙台民俗文化澎湖大讲堂论文集》,P.126-143,浙江省文化艺术交流促进会,澎湖地区两岸交流协会,浙江。
(编者注:本文中部分纪年书写及标点符号按规范作了调整。)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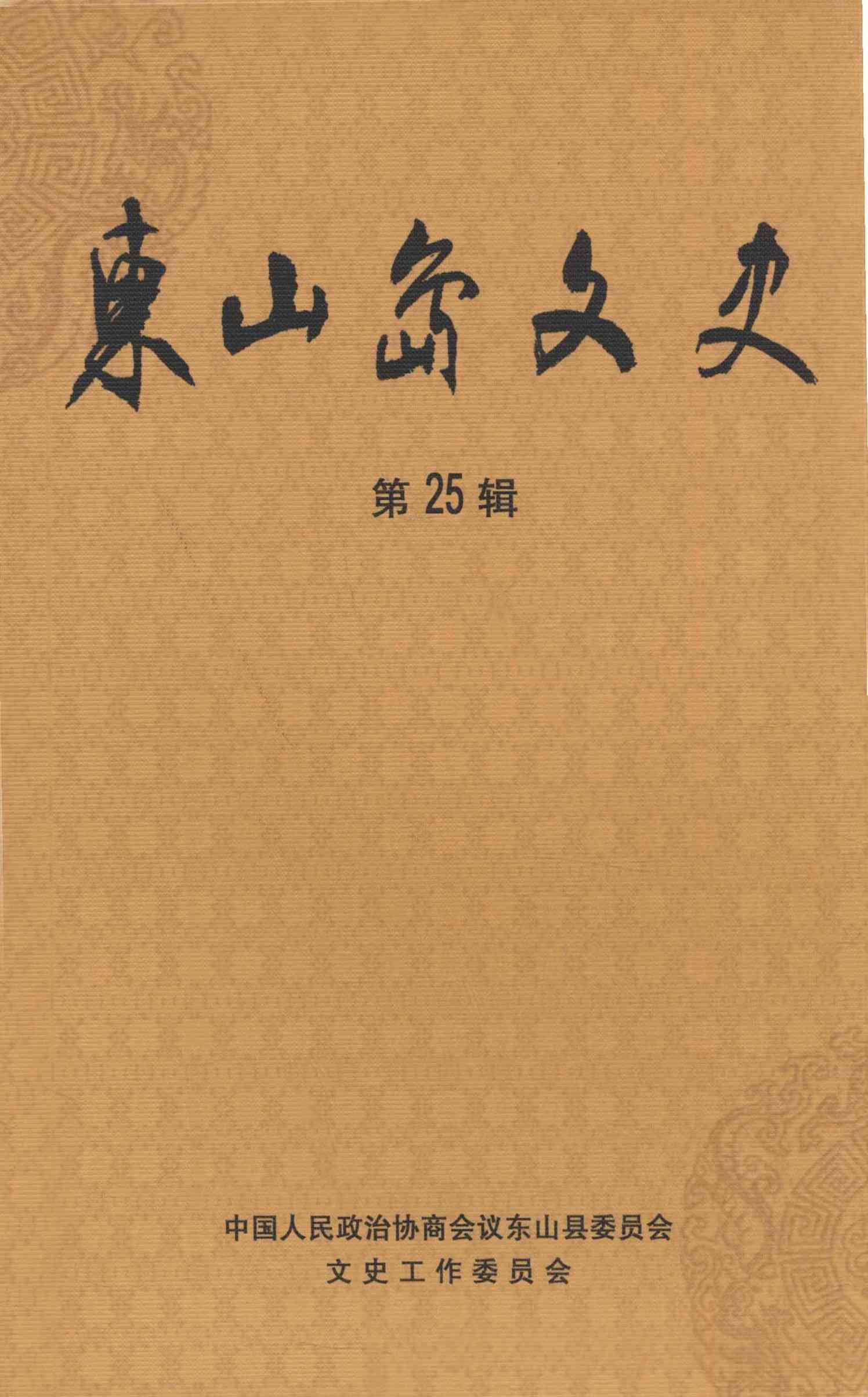
《東山岛文史第25辑》
本辑《东山岛文史》计收文稿35篇,总约21万字,共分为《东山·金门·澎湖三岛论坛论文选》、《海峡两岸关帝文化》、《黄道周文化》、《海峡长风》、《侨乡旧忆》、《史海钩沉》、《文化春秋》等栏目。着重于对东山县涉台关系史料、两岸关帝文化史料,黄道周文化史料、华侨史料、民俗和其他方面史料的深入调查挖掘,不断追寻发现,同时加以研究考证。
阅读
相关人物
王文良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