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末陈宜中行迹考辩
| 内容出处: | 《東山島文史第24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30004235 |
| 颗粒名称: | 宋末陈宜中行迹考辩 |
| 其他题名: | 兼探东山县陈城村陈氏族源 |
| 分类号: | K827 |
| 页数: | 16 |
| 页码: | 193-208 |
| 摘要: | 本文根据相关史料和田野调查,对南宋末年陈宜中的行迹进行了考证。陈宜中在元军压境、宋朝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连夜逃走并拒绝投降。但他的逃跑并非个人行为,而是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旨在不称臣投降并寻求恢复宋朝。在回到温州丁母忧后,陈宜中与陆秀夫、张世杰等人奉二王入闽中,并在福州建立行宫。因此,陈宜中的行为不应被视为逃跑主义。 |
| 关键词: | 东山县 陈宜中 陈氏族源 |
内容
南宋末年的丞相陈宜中,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这主要源于《宋史》对他的记载。
《宋史》载:德祐二年(1276)二月,“大元兵薄皋亭山,宜中宵遁”。又载:“井澳之败,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谕意,度事不可为,遂不反。”据此记载,陈宜中在元军压境、宋朝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连夜逃走,后来去了占城(在今越南境内)便立即不回来了。于是,“宵遁”、“如占城”、“遂不返”八个字,使他成为逃跑主义者,并成了七百多年来史家批评的主要依据。
《宋史》不失为一部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史书,但由于仓卒成书,使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宋史》“舛谬不能殚数。”随着现代历史研究与考古田野调查的深入开展,不断发现具有补史、证史价值的新资料新证据,正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许多历史的情节。
本文即根据相关史料以及田野调查的新资料,对南宋末年陈宜中的行迹进行一番考证,以期订正《宋史》相关记载的谬误,力求还历史的真实面目。
一、陈宜中之“宵遁”
陈宜中(1234~?),字与权,温州永嘉人。宜中少精举业,入太学时便和刘黻等六人上书论右丞相丁大全,名闻朝野,史称“开庆六士”。宋景定三年(1262)免省试直接参加廷试,登榜眼,授绍兴府推官、秘书省正字、校书郎,擢监察御史,此后屡屡升迁,至德祐元年(1275)十月,任右丞相兼枢密使。
陈宜中出任丞相的这一个月,元兵破常州,谢太后派陆秀夫等人求和不成,宋朝大势已去。德祐二年(1276)正月,太后决定举国降元,陈宜中拒降。
对此,《宋史·陈宜中传》载:“宜中初与大元丞相伯颜期会军中,既而悔之,不果往。伯颜将兵至皋亭山,宜中宵遁,陆秀夫奉二王入温州,遣人召宜中。”
宋人周密记:“德祐丙子正月十二日之事,陈丞相宜中与张世杰皆先一日逃往永嘉。次日,苏刘义,杨亮节、张全挟二王及杨、俞二妃行,自渔浦渡江,继而杨驸马亦追及之。至婺,驸马先还,二王遂入括。既而陈丞相遣人迎二王,竟入福州。丁丑五月朔,于福州治立益王,改元景炎。”
《元史》载:“乙酉,……宋陈宜中、张世杰、苏刘义、刘师勇等挟益、广二王出嘉会门,渡浙江遁去,惟太皇太后、嗣君在宫。伯颜亟使谕阿刺罕、董文炳、范文虎率诸军,先据守钱塘口,以劲兵五千人追陈宜中等,过浙江不及而还。”又载:“宋幼主既降,其相陈宜中等挟二王逃闽、广,所在扇惑,民争应之。”、“宋丞相陈宜中及其大将张世杰立益王昰于闽中,郡县豪杰争起兵应之。”
同一事件,周密、《元史》所载与《宋史》有别。《宋史》的“宜中宵遁”,没有前因后果,似乎是个人的逃跑行为,而且在“奉二王”这件事上好像是被动为之。比较而言,《元史》所载更接近事实。
“宜中宵遁”之前,宜中难以执行太后的投降决定。《宋史》反而在《张世杰传》中有载:“正月,更命宜中使军中,约用臣礼。宜中难之,太后涕沦曰:‘苟存社稷、臣非所较也。’未几,大元兵薄皋亭山,宜中宵遁,文武百官亦潜相引去。”
陈宜中自然制止不了宋廷投降,自己又不愿意投降,唯一出路便是“宵遁”。然而,“宵遁”并非个人的逃跑行为,此有史为证。
《宋史》载:“德祐二年正月,文天祥尹临安,请以二王镇闽、广,不从,始命二王出阁。大元兵迫临安,宗亲复以请,乃徒封昰为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抚大使,昺为广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以驸马都尉杨镇及杨亮节、俞如昉为提举。”
《宋史纪事本末》也载:“请以福王、秀王判临安,系民望,身为少尹,以死卫宗庙;又乞命吉王、信王镇闽广,以图兴复,俱不许。至是,宗亲复请,太后从之,以驸马都尉杨镇及杨淑妃弟亮节、俞光容弟如圭提举二王府事。”
可见,“命吉王、信王镇闽广,以图兴复”,是宋廷在降元的同时,为朝廷图复的一种策略。陈宜中、张世杰等人所谓的“宵遁”或“逃跑”,均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是一次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绝非逃跑主义。相反,“宜中宵遁”,不愿称臣投降,违约不至元军议降事,显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宋亡之际,以身殉国固然忠烈,奉二王图兴复亦忠亦烈。殉国易,图复难,陈宜中选择了后者。如何评价?王夫之《宋论》中的一段话值得参考,故照录于下。
“夫忠臣于君国之危亡,致命以与天争兴废,亦如是焉而已。当德祐时,蒙古兵压临安,亡在旦夕,求所以存宋者终无术矣。诚不忍国亡而无能为救,则婴城死守,君臣毕命以殉社稷,可也。奉君出走,收余烬以借一,不胜,则委骨于原隰,可也。死不我值,求先君之遗裔,联草泽之英雄,有一日之生,尽一日之瘁,则信国他日者亦屡用之矣。”
二、奉帝即位于福州
宋德祐二年(1276)正月,陈宜中回到温州,其母杨太夫人逝世,在家丁母忧。但为了奉二王以图兴复,他毅然与陆秀夫、张世杰等人奉二王人闽中,临行时由张世杰将他母亲的灵柩抬上船。
是年闰三月,他们到达福州,从位于闽江边的林浦(古为濂浦)登岸,并在濂浦建立行宫。
“五月乙未朔,陈宜中等奉帝即位于福州,改元景炎。升福州为福安府。册杨淑妃为皇太后,同听政。进封弟昺为卫王。以陈宜中为左丞相兼都督,李庭芝为右丞相,陈文龙、刘黻参知政事,张世杰、陆秀夫佥书枢密院事,苏刘义殿前都指挥使,王刚中知福安府。”
宋朝廷的重新建立,对南方地区此起彼伏的抗元救亡斗争,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同时也体现了陈宜中等人的民族气节、政治责任感与坚强的斗争意志。
但是,由于元兵渐迫,南宋新朝在福州仅仅维持了半年时间,于当年十一月从林浦撤离福州,登船入海。
现在,林浦村的泰山宫便是当年朝廷行朝的所在,额匾“平山福地”便是当年陈宜中所题。《闽书·卷二·方域志》载:“平山,即凰山东。宋少帝航海时,驻兵于此,以其崎岖,铲而平之。”《福州府志·卷之九·封爵志》载:“‘平山福地’,陈宜中大书,镌濂浦平山。”
除此,村里还有一座“宋陈公丞相祠”,奉祀的便是陈宜中。据传,新朝撤离前,陈宜中开仓放粮,让林浦人足足吃了三年。林浦人感其恩德,为其塑像,入祠祭祀。
三、葬母于东山岛大帽山
景炎元年(1276)正月,陈宜中母杨太夫人逝世。《宋史》载:“宜中至温州,而其母死。张世杰舁其棺舟中,遂与俱入闽中。”此后便不知其母灵柩的下落。南宋新朝在福州有半年时间,按理陈宜中有机会在福州葬母,且有相当规格的仪式,必有记载或口传资料,然不见有任何相关的记载或口传资料。《宋史》载:“方秀夫海上时,记二王事为一书甚悉,以授礼部侍郎邓光荐曰:‘君后死,幸传之。’其后崖山平,光荐以其书还庐陵。大德初,光荐卒,其书存亡无从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详云。”因此,陈宜中葬母一事,自然不见史端。或许在陆秀夫那部札记中会有所涉及,可惜它“存亡无从知”。
陈宜中不于福州葬母,必有其道理。于是,他携母灵柩入海,最终葬母于偏僻的东山岛大帽山下。
《宋史纪事本末》载:景炎元年十一月(1276),“帝到泉州,舟泊于港。招抚使蒲寿庚来谒,请驻跸,张世杰不可。初,寿庚提举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劝世杰留寿庚不遣,则凡海舶不令自随,世杰不从,纵之归。继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没其赀。寿庚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宜中乃奉帝趋潮州。”《宋史》所载相同,然均未载具体的驻跸地点。《闽书》载:“大帽山,山极高耸。宋丞相陆秀夫、陈宜中,扶幼主泊舟于此”。《漳州府志》、《东山县志》均有相同记载。《南澳县志》载:“元兵压境,帝下海南奔,宜中率舟师以从,十二月至潮州,驻跸南澳。”
东山岛位于福建省最南端,而南澳岛位于广东省的最东,相距约20海里,帆船顺风顺流航行约3小时,且自北而南至南澳,必经东山。两岛互为犄角,构成闽南粤东沿海的门户,均具重要的战略地位,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尤其东山岛位于东海与南海交汇处,南北航海多在此停泊补给。南明时期,郑成功踞金、厦、南、铜(即金门、厦门、南澳、铜山)四岛抗清复明,舟师必置于铜山、南澳两岛,相为呼应。他“檄铜山忠匡伯张进,出烦船于宫仔前游飏,以作南澳援师;谨守八尺门炮台,以备陆路渡江。”而南宋新朝此时拥有“军十七万人、民兵三十万人、淮兵万人”,仅以军队十七万人计,所需舟船当在两千艘以上。如此庞大的船队从泉州南下,即使不先停泊于东山以补给和修整,从军事安全考虑也必须分铜山、南澳两岛驻扎。因此,《闽书》“宋丞相陆秀夫、陈宜中,扶幼主泊舟于此”的记载是可信的。
《闽书》记载的大帽山,位于福建省东山岛东南沿海突出部。大帽山下的陈城村,共有1200多户,5300多人,绝大部分姓陈,世传均为陈宜中的后代。陈城人世代奉陈宜中母杨太夫人为一世祖、陈宜中为二世祖、陈宜中子陈元朴为三世祖。据载:陈宜中舟泊大帽山时,相中大帽山南麓的凤坡岭,遂葬母于此,并命其子陈元朴代为守坟尽孝。陈元朴便在此开基陈城村。
2002年以来,陈全兴、陈英龙、陈阿龙、陈添生、陈武其等一批文史爱好者,邀请文史与考古部门的专家组成专门研究小组,对其二、三世祖陈宜中、陈元朴父子的生平及其遗迹进行了调查研究,同时奔赴广东、浙江、湖北等地,对其宗族的渊源、迁徙与分布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获取丰富的资料。他们在陈元朴开基的顶城村发现了始建于明初的古城城墙,辨认出陈宜中母杨太夫人、子陈元朴的两座墓葬,并发现了被密藏的陈宜中及其母亲杨太夫人、子陈元朴的灵位牌。这些重要的实物资料,印证了陈城村的族谱以及其它志书的相关记载。
在大帽山南麓、陈宜中子陈元朴墓附近,有一座“七圣妈庙”,始建于元初,殿内祀唐代护国保民的陈靖姑等七尊神圣的女神。据传,该庙香火由陈宜中从福州林浦带入。今林浦的宋陈公丞相祠内,“七圣妈”与陈宜中同祀一堂。据当地人传:陈宜中入乡随俗,在福州期间也信奉“七圣妈”,离开林浦时便分走一脉香火,承接香火的便是陈城村。故陈城人认林浦的“七圣妈”为祖庙。因此,陈城“七圣妈庙”也是宜中葬母并由其子开基陈城的实物证据之一。
《东山县志》(大事记)载:元兵为追捕二王及陈宜中等人进入东山,“元兵肆行烧杀。亲营村潘穆齐率众抗元兵,身亡。许多人避战乱而逃往澎湖。”亡者潘穆齐之墓,至今尚存,无疑也是陈宜中扶幼主驻跸东山的实物证据。至于幼帝在东山的更多遗迹与传说,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由此可见,尽管不见《宋史》有载,但“宋丞相陆秀夫、陈宜中,扶幼主泊舟于此”并葬母于大帽山下的史实,是不容置疑的。
四、七里洋奉旨往占城
景炎元年(1276)十二月,南宋幼帝撤离铜山、南澳,移驻广东惠州的甲子门。次年(景炎二年,1277)九月,转移到浅湾。十一月元将刘深攻浅湾,又转移到秀山,又向井澳转移。十二月到井澳时,海上飓风大作,死者过半,幼帝落水被救,惊悸成疾。是月,元将刘深又来袭,井澳大败,幼帝退至琼州海峡的谢女峡,进入北部湾,驻于七里洋。
以上是景炎二年(1277)幼帝海上败退的路线,史志所载基本一致。但在陈宜中往占城的时间上略有差异,一说十一月,一说十二月。据胡珠生先生考证,陈宜中应于十二月往占城,因为其时在飓风大作的十一月,帝昰尚未患病,宜中去占城缺乏根由。据《宋史·陈宜中传》记载:“井澳之败,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井澳之败后宜中才往占城,时间当在十二月无误。
至于井澳之败后,宜中从何处往占城,虽不见史志有明确记载,但仍可从中找到行迹。
《宋史纪事本末》载:“元刘深袭井澳,帝奔谢女峡,复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不果。”由此可见,井澳败后,受东北季风及航海条件的限制,舟师只能向西南方向败退,退至琼州海峡的谢女峡,并进入北部湾的七里洋。这里与占城近在咫尺,《元史》(210卷,列传97,外夷3)载:“占城,近琼州,顺风舟行一日可抵其国。”因此,此时幼帝“欲往占城”是符合逻辑的。又据广东湛江的地方志书载:“南宋末年,陈宜中任右丞相兼枢密使,避元兵奉帝南下,过吴川河畔的极浦亭曾赋诗”。幼帝舟师在撤往琼州海峡的途中,曾停泊于吴川,此时宜中尚在,证明他往占城当在离开吴川之后。因此,陈宜中往占城的时间是景炎二年(1277)十二月,地点就在北部湾的七里洋。
陈宜中为何往占城?《宋史·陈宜中传》的“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谕意”记载,便是最好的回答。占城为异域,可否前往关系到幼帝与朝廷的安危,必未敢冒然,需先使人先往“谕意”。此时又是非常时期,生死存亡在此一举,然占城非世外桃园,前途未卜,谁肯担此重任?陈宜中不畏艰险,亲自出马,代表朝廷往占城传达皇帝的旨意,其目的意义明确,行为正当。
《宋史·陈宜中传》载:宜中往占城后“度事不可为,遂不反。二王累使召之,终不至。”于是,陈宜中正当的行为便被冠上了“逃跑”的罪名。
陈宜中在占城的行迹,不见史载,今已无从稽考。但他去占城之前的行迹及诗文是值得注意的。
《南澳县志》载:“二年正月移惠州甲子门。据广州元将吕师夔等因军饷不继退走,以其部梁雄飞守之。经略使刘应龙导帝舟至广州港口,转运使姚良臣预迎帝入州治,守江元兵拒之,不果入,帝舟还大海驻秀山。惟宜中得入广城,寻遁还。”为图复广州,身为丞相的宜中竟置生死于度外,亲自潜入广州,这与他亲自前往占城谕意的做法如出一辙,再者,如果他想逃跑,此时正是机会,而他却回到幼帝身边。
《广东省吴川县志》载:“极浦亭在吴川县南河畔,宋邑人李凌云隐处(大清一统志)。宋丞相陈宜中过此有诗,后人取为八景之一。”吴川李氏家史也有相同的记载。
当年陈宜中题诗的“极浦亭”至今尚存。该亭始建于南宋淳佑年间,历代多次修葺,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亭内柱联:“每当美景良辰定有词人同载酒,无复颠风急雨尚留丞相旧题诗。”虽经历代修葺,古风依然,惜当年宜中所题墨宝已不知下落。如今吴川人尚在纪念陈宜中,在“极浦亭”内立青石碑,碑文录自吴川县志的宜中题诗,竖书,阴刻:“颠风急雨过吴川,极浦亭前望远天;有路可通寰宇外,无山堪并首阳山。岭云起处潮初长,海月高时人未眠;异日北归须记取,平芜尽处一峰圆。”诗中“北归”二字,表达他图复的决心。
上述宜中往占城之前的行迹,足以证明宜中断无逃跑的意图。
至于他在占城的行迹,不见史载,无从稽考。他往占城后之所以未能及时返回,很可能占城之行并不顺利,甚至在那里遇到了麻烦。时任宋吏部尚书的陈仲微被派往占城找宜中,却连一面也没见着,不久宋亡,便干脆跑到安南,受到安南陈圣王的礼遇。因此,所谓“二王累使召之”,究竟派去多少人?是否见着了人?均不得而知。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陈宜中去占城后回没回来?几乎所有史籍都说他没回来,然事实的回答却与史载截然相反,陈宜中确实回来了。
五、从占城归崖山,再登东山岛
据《宋史纪事本末》(二王之立)载:景炎三年二月(1278),“帝舟还广州”,三月“帝迁驻硇州”,四月,帝崩,11岁的帝昰病故,立8岁的卫王昺为帝,五月改元“祥兴元年”,六月“帝迁居新会之崖山。帝昺祥兴二年(1279)二月,崖山大战,宋舟师全军覆没,陆秀夫负幼帝投海,宋亡。
《宋史》载:“二月癸未,弘范等攻崖山,世杰败走卫王舟。大军薄中军,世杰乃断维,以十余舰夺港去。后还收兵崖山,刘自立击败之,降其将方遇龙、叶秀荣、章文秀等四十余人。世杰复欲奉杨太妃求赵氏后而立之,俄飓风坏舟,溺死平章山下。”
十余舰夺港而去,除了张世杰溺死平章山下,尚有其他人及其舰船去向何方?他们又发生了什么事?史籍无载,幸有亲历者留下足以补正历史的重要证据。
亲历崖山之战的黄材在《漳浦湖西黄氏族谱》(文忠公族谱序)中写道:
“值天运转元,随卫王播迁于广东新会之崖山,奉杨太后懿旨,保若和郡王。不期年,元兵俱至,连日大战。余知势迫,乃与张世杰,许达甫等十六船,护王夺港而出,遇陈宜中船于广崖之浅澳大会,欲往福州图恢复。忽飓风大作,世杰不幸船沉,宜中船破,因登合浦。惟余与达甫四船护王及父天从公,漂至浯屿前,又失杠具,乃于浦东登岸,匿王为我黄氏,合居焉。吁!为臣死忠,为子死孝。当是时,文天祥已被执,世杰、秀夫随帝入海,捐躯报国,此心可白。余岂独二、三公之死而故觑焉而逃哉!第据〈礼经〉:‘士死制’,余奉制保王,王在,或嘘炎宋之灰于再振也。……岁在戊戌端月望日,宋逋臣黄材,字国珠,泣血书。”
这篇谱序写于元成宗二年(1298),距崖山之败仅19年,作者又是事件的见证者,所记当可信。
如果说黄材所记尚为孤证,那么,与黄材同行的郡王赵若和相同的记述,则又是一个重要证据。他在修于元仁宗三年(1316)《闽冲郡王赵家堡族谱》的(赵氏本末序)中写道:
“元兵逼侵、吾乃奉帝挈家,驾船逃难,移之广东新会之崖山。噫!当是时,忠臣烈将,武夫精卒,尚有数万人,粮食赖伍太师家为馈饷,尚未乏绝。予亦托万里之天缘,乃缔太师之女。不期年,元兵且至,连日大战,吾知势已败、与许达甫、黄侍臣等以十六舟夺港而出,遇陈宜中在广崖之浅澳大会,欲往福州以图匡复王室。船到广东南澳之七十余里,飓风大作,宜中船破,遂登合浦。予冒至浯屿之东,船亦失其杠具,就于浦西登岸,后徙鸿儒积美居焉。”
赵若和所记与黄材所记不谋而合,一致见证一个史实:陈宜中并非如《宋史》所言“遂不返”与“终不至”,他不但回国,而且“欲往福州图恢复”。
据胡珠生先生所引的《永嘉二都前街陈氏宗谱》的陈宜中简传载:“上命至占城、暹罗国乞师,归崖山之界,闻宋亡,竟溺而死,浮尸海上,里人咸以为异,遂收殡葬。”显然,其中归崖山后见宋亡“竟溺而死”的记载,极可能根据张世杰溺海而亡的事件推测而已,但其“归崖山之界”的记载,却又一次证实了黄材、赵若和的亲历所见:陈宜中确实回来了。
由此可见,《宋史·陈宜中传》所载的“至元十九年,大军伐占城,宜中走暹,后没于暹”,是不符史实的。它可能根据元翰林直学士承旨刘庚于延祐五年(1318)所撰的《永嘉陈氏世德碑》。碑文写道:“太夫人日思乡里,会其兄芹孙、女兄尼净戒至自暹国宜中薨所。”
陈宜中的侄儿侄女出家受戒,根本无法了解伯父宜中的行迹,从暹国归来并没说伯父死在暹国,是碑文作者的一种猜测,即使确有此说,也只是一种麻痹当局的搪塞之词。《宋史》未加考证,便以猜想替代了事实。
至此,《永嘉陈氏世德碑》、《宋史》与《永嘉二都前街陈氏宗谱》记陈宜中死于暹,或死于崖山之界,或老死,或投海自尽,均为猜测,缺乏证据。
那么,陈宜中遇风船破,于合浦登岸,合浦为何处呢?赵若和明确指出宜中登岸的地点距南澳70里的合浦。当时他们航行的方向是从南向北,那么,南澳北面70余里的地方,便是东山岛。宋代,东山岛包括陈城村在内的东南滨海地区,当地人俗称为合浦,明时改称泊浦,清时又称碧浦,宜中在附近海域船破登岸,必然入大帽山看望儿子,祭祀母坟。
陈宜中第二次到东山,究竞住了多长时间?今已难以查考。自从元世祖十三年(1276),朝廷便开始追捕宋广王及陈宜中,他的处境十分危险,不可能在此久留。根据当时形势推测,陈宜中极可能从海上离开东山,并向北航行。因为,宋代东山海运业已十分发达。据《东山县志》载:“宋建炎元年(1127),东山磁窑村一姓孟者建造8个陶瓷窑,雇工烧制碗、盘、茶具、酒具等磁器,远销外地。”资料表明,当时东山已经建造大型海船“北船”,南北远航,从事海上贸易。
六、改名换姓,隐居湖北蕲春久长山
在湖北省蕲春县蕲北山区崇山峻岭深处的久长山,有一座古墓葬,俗称“相墓”,墓主人为宋故丞相田梦罴。但宋代没有一个叫田梦罴的丞相,而当地田氏人家世传田梦罴就是更名换姓、终老久长山的宋相陈宜中。
经蕲春县田文国、田志强和田耀国三位先生考证,证实了田氏人家的世传:“田梦罴即南宋末代丞相陈宜中”,其主要依据有当地古墓葬与田氏族谱等。
“相墓”座落在久长山,墓首分四柱三门,中门镶墓碑,两侧立墓志。墓碑阴刻:“宋故丞相田公讳梦罴大人、妣黄、梅、王夫人墓”。墓志自右至左,阴刻:“田氏鼻祖讳梦罴,宋人,仕宋为显宦,先世隶籍雁门,自南渡后,解组来蕲,卜居大同之久长山,是为田氏迁蕲之始祖也,历数传,人丁繁衍,其散在他邑者,支分棋布,甲第联翩,而居蕲者十数户,尤为甚盛,绳绳继继,绵世守而衍箕裘,以是叹我祖之垂誊者远也。祖原卜葬土库楼天欣也。祖妣黄、梅、王氏,合墓共碑,历宋元明,迄今七百有余岁矣,其间碑牌之代立者,不知凡几,奈所换之碑,又多历年所,一则风雨飘摇,字迹剩落,一则土膏滋长,碣石芜埋,后人欲摸碑而读之有不可得者,是以聚族而谋复立,坚石丰碑,仿旧制而修之,庶几陵谷变迁而不朽云。皇清同治十三年仲春月谷旦,支下远孙同立”
清乾隆年间,楚北大学者、大诗人、《湖北通志》主编陈诗,曾以田桥地名作《竹枝词》一十七首,其中第六首第一句写道:“相墓经传土库楼”,开句便点到“相墓”,说明至少在同治维修墓葬之前,墓主的身份就已被这位大学者承认。
但是,该墓葬规格不高,规模不大,与墓主身份不符,这是为什么?现存墓碑及墓志均为清同治十三年(1874)最后一次维修时所立,虽有纪年而为何不见始建年代与墓主卒年,如经考古发掘,是否有墓志或买地卷?这些问题令人疑惑不解。然而,正是这些令人疑惑的问题,暗示了墓葬的时代与墓主的特殊身份。
墓葬为田梦罴及妣黄、梅、王三夫人共四个人的合葬墓,此与元代盛行夫妻合葬和家庭多人合葬的做法相吻合。例如:山西元代侯马赵氏墓,六人合葬,西安雁塔南路元墓共有木棺5具,是典型的家庭合葬墓。像江苏武进下港元代夫妻合葬墓、江苏吴县黄桥乡元代吕师孟夫妇合葬墓等,更是不胜枚举。元朝建立以后,忽必烈采用了汉族的立法来治理国家,汉文化与蒙古族文化得到空前的融合。做为生活习性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墓葬习俗也逐渐被蒙古人采用。尽管如此,元朝还是提倡薄葬简丧的,甚至明文规定:“诸坟墓以砖瓦为屋其上者,禁之。”这就是田梦罴墓葬规格与其身份不符的原因之一。当然,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特殊身份,既已更名换姓,自然不能张扬,其墓葬更不可能暴露其真实姓名、真实身份以及生卒时间等信息而祸及子孙。
因此,当疑惑被消除,墓葬的年代便不言而喻了,而墓主人的神秘面纱,也就被轻轻地撩开了。
修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蕲春《马骅山田氏七修宗谱》序载:“我田氏来蕲春之鼻祖曰梦罴公,世传即宋相陈宜中,当端宗舟抵秀山时,由占城迂道逃至江淮间,结忠义之士,谋复宋室,志卒不遂,乃仿陈公子完之先例,易姓为田,匿于蕲北之久长山而隐居焉。……光绪癸巳科副举人湖南直隶州州判二十四世侄孙嵩元葛民甫敬撰,民国二十六年仲春月谷旦。”
修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蕲春《田桥久长山田姓家谱》序载:“余族之先家世雁门,南宋时梦罴公始迁大同乡之久长山,至今五百余年。”
蕲春新修《田氏大成宗谱》谱系云:“田梦罴者,乃陈宜中也。”
以上所引田氏宗谱记载,“当端宗舟抵秀山时,由占城迂道逃至江淮间”在时间上有差异,至于“结忠义之士,谋复宋室”是否事实有待查考,而“仿陈公子完之先例,易姓为田,匿于蕲北之久长山而隐居焉”与当地口传历史一致,应符合事实。因此,结合田梦罴墓的分析研究,田梦罴无疑应该就是陈宜中。
陈宜中可能借助“北船”从海上离开福建东山岛,由海入长江至湖北,再拐入蕲水河、龙井河,进入偏僻的蕲北山区的久长山。
然而,陈宜中为何选择蕲北山区而不是其它地方呢?另一座古墓葬及其相应的宗谱记载,回答了这个问题。
田文国、田志强和田耀国等,在蕲春县大同镇何铺村找到传说中的“公主墓”,并找到与“公主墓”互为印证的《黄氏宗谱》。“公主墓”的墓主人为黄元庆及夫人赵公主。《黄氏宗谱》(世系)载:“尧咨,二十公长子,字元庆,宋嘉定驸马,赘赵公主。生子四:英迪、圭、郁,女一适宋相田梦罴。公妣合葬洪潭坂上老鹳窠金规银槽,癸山,丁向,有碑,有石阶三十二步,有华表。”
该谱首修于元大德戊戍年(1298),重修于清同治元年(1862)。经三位田先生考证,“公主墓”所处地理位置、坐向、形制规格、附属建筑与宗谱所载完全一致,而赵公主是宋嘉定年间的郡公主,同是宋室皇亲,其女儿正是与宋丞相陈宜中合葬的黄氏夫人。如若无误,这是很有价值的证据,它为陈宜中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材料,是陈宜中为何选择蕲北山区隐居的确切答案。
七、简短的结论
陈宜中作为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其争议的关键就在于《宋史》记载的“宵遁”、“如占城”与“遂不反”八个字。然而,陈宜中却以其行迹订正这八字不实之词。
他在南宋举国降元之际,不愿投降,扶立二王,以图兴复。
他带着母亲的灵柩离开故乡,奉帝即位于福州,葬母于东山岛大帽山。海上行朝,节节败退,至北部湾七里洋,帝欲往占城,他奉旨先往。占城事不可为,他即返回崖山,正值宋亡,遇夺港而出的赵若和、黄材、许达甫等人,欲往福州图恢复,途中遇风船破,再次登陆东山。最后,他在朝廷四处追捕的情况下,潜入湖北蕲北山区,改名换姓,隐居山林,死后葬于久长山。
清代王夫之说:“宋迨理宗之末造,其亡必矣。”又说:“通蒙古亦亡,拒蒙古亦亡,无往而不亡。”
作为当朝丞相的陈宜中,对南宋前途应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他拒绝称臣投降,显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扶二王以图兴复,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携母棺奉帝即位福州,行朝海上,葬母大帽山,既忠又孝;如占城,归崖山,力挽南宋,英勇顽强;终老山林,虽无杀身成仁,却已竭尽忠义。
胡珠生先生在其《陈宜中生平考辩》的结论中指出:“陈宜中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坚贞不屈、至死不忘匡复宋室的忠臣。”
至此,历史对于陈宜中的争议,可以结束了。
参考文献:
《宋史》、《元史》、《四库全书总目》(宋史)标点校勘本、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二王入闽大略〉、明·陈炜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龙湾史志》、清·王夫之《宋论》、《闽书》、《南澳县志》、《台湾外记》、《东山县志》、《陈城(顶城、下城)陈氏渊源世系》、《漳州府志》、《湛江市地名志》、《广东省吴川县志》、《吴川三柏李氏家史》、元·黎崱《安南志略》、民国版《东山县志》、《蕲春文化研究》、《考古》、《文物资料丛刊》、《文物》。
《宋史》载:德祐二年(1276)二月,“大元兵薄皋亭山,宜中宵遁”。又载:“井澳之败,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谕意,度事不可为,遂不反。”据此记载,陈宜中在元军压境、宋朝生死存亡的危难之际连夜逃走,后来去了占城(在今越南境内)便立即不回来了。于是,“宵遁”、“如占城”、“遂不返”八个字,使他成为逃跑主义者,并成了七百多年来史家批评的主要依据。
《宋史》不失为一部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史书,但由于仓卒成书,使它在二十四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宋史》“舛谬不能殚数。”随着现代历史研究与考古田野调查的深入开展,不断发现具有补史、证史价值的新资料新证据,正在某种程度上改写了许多历史的情节。
本文即根据相关史料以及田野调查的新资料,对南宋末年陈宜中的行迹进行一番考证,以期订正《宋史》相关记载的谬误,力求还历史的真实面目。
一、陈宜中之“宵遁”
陈宜中(1234~?),字与权,温州永嘉人。宜中少精举业,入太学时便和刘黻等六人上书论右丞相丁大全,名闻朝野,史称“开庆六士”。宋景定三年(1262)免省试直接参加廷试,登榜眼,授绍兴府推官、秘书省正字、校书郎,擢监察御史,此后屡屡升迁,至德祐元年(1275)十月,任右丞相兼枢密使。
陈宜中出任丞相的这一个月,元兵破常州,谢太后派陆秀夫等人求和不成,宋朝大势已去。德祐二年(1276)正月,太后决定举国降元,陈宜中拒降。
对此,《宋史·陈宜中传》载:“宜中初与大元丞相伯颜期会军中,既而悔之,不果往。伯颜将兵至皋亭山,宜中宵遁,陆秀夫奉二王入温州,遣人召宜中。”
宋人周密记:“德祐丙子正月十二日之事,陈丞相宜中与张世杰皆先一日逃往永嘉。次日,苏刘义,杨亮节、张全挟二王及杨、俞二妃行,自渔浦渡江,继而杨驸马亦追及之。至婺,驸马先还,二王遂入括。既而陈丞相遣人迎二王,竟入福州。丁丑五月朔,于福州治立益王,改元景炎。”
《元史》载:“乙酉,……宋陈宜中、张世杰、苏刘义、刘师勇等挟益、广二王出嘉会门,渡浙江遁去,惟太皇太后、嗣君在宫。伯颜亟使谕阿刺罕、董文炳、范文虎率诸军,先据守钱塘口,以劲兵五千人追陈宜中等,过浙江不及而还。”又载:“宋幼主既降,其相陈宜中等挟二王逃闽、广,所在扇惑,民争应之。”、“宋丞相陈宜中及其大将张世杰立益王昰于闽中,郡县豪杰争起兵应之。”
同一事件,周密、《元史》所载与《宋史》有别。《宋史》的“宜中宵遁”,没有前因后果,似乎是个人的逃跑行为,而且在“奉二王”这件事上好像是被动为之。比较而言,《元史》所载更接近事实。
“宜中宵遁”之前,宜中难以执行太后的投降决定。《宋史》反而在《张世杰传》中有载:“正月,更命宜中使军中,约用臣礼。宜中难之,太后涕沦曰:‘苟存社稷、臣非所较也。’未几,大元兵薄皋亭山,宜中宵遁,文武百官亦潜相引去。”
陈宜中自然制止不了宋廷投降,自己又不愿意投降,唯一出路便是“宵遁”。然而,“宵遁”并非个人的逃跑行为,此有史为证。
《宋史》载:“德祐二年正月,文天祥尹临安,请以二王镇闽、广,不从,始命二王出阁。大元兵迫临安,宗亲复以请,乃徒封昰为益王、判福州、福建安抚大使,昺为广王、判泉州兼判南外宗正,以驸马都尉杨镇及杨亮节、俞如昉为提举。”
《宋史纪事本末》也载:“请以福王、秀王判临安,系民望,身为少尹,以死卫宗庙;又乞命吉王、信王镇闽广,以图兴复,俱不许。至是,宗亲复请,太后从之,以驸马都尉杨镇及杨淑妃弟亮节、俞光容弟如圭提举二王府事。”
可见,“命吉王、信王镇闽广,以图兴复”,是宋廷在降元的同时,为朝廷图复的一种策略。陈宜中、张世杰等人所谓的“宵遁”或“逃跑”,均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是一次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绝非逃跑主义。相反,“宜中宵遁”,不愿称臣投降,违约不至元军议降事,显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宋亡之际,以身殉国固然忠烈,奉二王图兴复亦忠亦烈。殉国易,图复难,陈宜中选择了后者。如何评价?王夫之《宋论》中的一段话值得参考,故照录于下。
“夫忠臣于君国之危亡,致命以与天争兴废,亦如是焉而已。当德祐时,蒙古兵压临安,亡在旦夕,求所以存宋者终无术矣。诚不忍国亡而无能为救,则婴城死守,君臣毕命以殉社稷,可也。奉君出走,收余烬以借一,不胜,则委骨于原隰,可也。死不我值,求先君之遗裔,联草泽之英雄,有一日之生,尽一日之瘁,则信国他日者亦屡用之矣。”
二、奉帝即位于福州
宋德祐二年(1276)正月,陈宜中回到温州,其母杨太夫人逝世,在家丁母忧。但为了奉二王以图兴复,他毅然与陆秀夫、张世杰等人奉二王人闽中,临行时由张世杰将他母亲的灵柩抬上船。
是年闰三月,他们到达福州,从位于闽江边的林浦(古为濂浦)登岸,并在濂浦建立行宫。
“五月乙未朔,陈宜中等奉帝即位于福州,改元景炎。升福州为福安府。册杨淑妃为皇太后,同听政。进封弟昺为卫王。以陈宜中为左丞相兼都督,李庭芝为右丞相,陈文龙、刘黻参知政事,张世杰、陆秀夫佥书枢密院事,苏刘义殿前都指挥使,王刚中知福安府。”
宋朝廷的重新建立,对南方地区此起彼伏的抗元救亡斗争,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同时也体现了陈宜中等人的民族气节、政治责任感与坚强的斗争意志。
但是,由于元兵渐迫,南宋新朝在福州仅仅维持了半年时间,于当年十一月从林浦撤离福州,登船入海。
现在,林浦村的泰山宫便是当年朝廷行朝的所在,额匾“平山福地”便是当年陈宜中所题。《闽书·卷二·方域志》载:“平山,即凰山东。宋少帝航海时,驻兵于此,以其崎岖,铲而平之。”《福州府志·卷之九·封爵志》载:“‘平山福地’,陈宜中大书,镌濂浦平山。”
除此,村里还有一座“宋陈公丞相祠”,奉祀的便是陈宜中。据传,新朝撤离前,陈宜中开仓放粮,让林浦人足足吃了三年。林浦人感其恩德,为其塑像,入祠祭祀。
三、葬母于东山岛大帽山
景炎元年(1276)正月,陈宜中母杨太夫人逝世。《宋史》载:“宜中至温州,而其母死。张世杰舁其棺舟中,遂与俱入闽中。”此后便不知其母灵柩的下落。南宋新朝在福州有半年时间,按理陈宜中有机会在福州葬母,且有相当规格的仪式,必有记载或口传资料,然不见有任何相关的记载或口传资料。《宋史》载:“方秀夫海上时,记二王事为一书甚悉,以授礼部侍郎邓光荐曰:‘君后死,幸传之。’其后崖山平,光荐以其书还庐陵。大德初,光荐卒,其书存亡无从知,故海上之事,世莫得其详云。”因此,陈宜中葬母一事,自然不见史端。或许在陆秀夫那部札记中会有所涉及,可惜它“存亡无从知”。
陈宜中不于福州葬母,必有其道理。于是,他携母灵柩入海,最终葬母于偏僻的东山岛大帽山下。
《宋史纪事本末》载:景炎元年十一月(1276),“帝到泉州,舟泊于港。招抚使蒲寿庚来谒,请驻跸,张世杰不可。初,寿庚提举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劝世杰留寿庚不遣,则凡海舶不令自随,世杰不从,纵之归。继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没其赀。寿庚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宜中乃奉帝趋潮州。”《宋史》所载相同,然均未载具体的驻跸地点。《闽书》载:“大帽山,山极高耸。宋丞相陆秀夫、陈宜中,扶幼主泊舟于此”。《漳州府志》、《东山县志》均有相同记载。《南澳县志》载:“元兵压境,帝下海南奔,宜中率舟师以从,十二月至潮州,驻跸南澳。”
东山岛位于福建省最南端,而南澳岛位于广东省的最东,相距约20海里,帆船顺风顺流航行约3小时,且自北而南至南澳,必经东山。两岛互为犄角,构成闽南粤东沿海的门户,均具重要的战略地位,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尤其东山岛位于东海与南海交汇处,南北航海多在此停泊补给。南明时期,郑成功踞金、厦、南、铜(即金门、厦门、南澳、铜山)四岛抗清复明,舟师必置于铜山、南澳两岛,相为呼应。他“檄铜山忠匡伯张进,出烦船于宫仔前游飏,以作南澳援师;谨守八尺门炮台,以备陆路渡江。”而南宋新朝此时拥有“军十七万人、民兵三十万人、淮兵万人”,仅以军队十七万人计,所需舟船当在两千艘以上。如此庞大的船队从泉州南下,即使不先停泊于东山以补给和修整,从军事安全考虑也必须分铜山、南澳两岛驻扎。因此,《闽书》“宋丞相陆秀夫、陈宜中,扶幼主泊舟于此”的记载是可信的。
《闽书》记载的大帽山,位于福建省东山岛东南沿海突出部。大帽山下的陈城村,共有1200多户,5300多人,绝大部分姓陈,世传均为陈宜中的后代。陈城人世代奉陈宜中母杨太夫人为一世祖、陈宜中为二世祖、陈宜中子陈元朴为三世祖。据载:陈宜中舟泊大帽山时,相中大帽山南麓的凤坡岭,遂葬母于此,并命其子陈元朴代为守坟尽孝。陈元朴便在此开基陈城村。
2002年以来,陈全兴、陈英龙、陈阿龙、陈添生、陈武其等一批文史爱好者,邀请文史与考古部门的专家组成专门研究小组,对其二、三世祖陈宜中、陈元朴父子的生平及其遗迹进行了调查研究,同时奔赴广东、浙江、湖北等地,对其宗族的渊源、迁徙与分布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获取丰富的资料。他们在陈元朴开基的顶城村发现了始建于明初的古城城墙,辨认出陈宜中母杨太夫人、子陈元朴的两座墓葬,并发现了被密藏的陈宜中及其母亲杨太夫人、子陈元朴的灵位牌。这些重要的实物资料,印证了陈城村的族谱以及其它志书的相关记载。
在大帽山南麓、陈宜中子陈元朴墓附近,有一座“七圣妈庙”,始建于元初,殿内祀唐代护国保民的陈靖姑等七尊神圣的女神。据传,该庙香火由陈宜中从福州林浦带入。今林浦的宋陈公丞相祠内,“七圣妈”与陈宜中同祀一堂。据当地人传:陈宜中入乡随俗,在福州期间也信奉“七圣妈”,离开林浦时便分走一脉香火,承接香火的便是陈城村。故陈城人认林浦的“七圣妈”为祖庙。因此,陈城“七圣妈庙”也是宜中葬母并由其子开基陈城的实物证据之一。
《东山县志》(大事记)载:元兵为追捕二王及陈宜中等人进入东山,“元兵肆行烧杀。亲营村潘穆齐率众抗元兵,身亡。许多人避战乱而逃往澎湖。”亡者潘穆齐之墓,至今尚存,无疑也是陈宜中扶幼主驻跸东山的实物证据。至于幼帝在东山的更多遗迹与传说,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由此可见,尽管不见《宋史》有载,但“宋丞相陆秀夫、陈宜中,扶幼主泊舟于此”并葬母于大帽山下的史实,是不容置疑的。
四、七里洋奉旨往占城
景炎元年(1276)十二月,南宋幼帝撤离铜山、南澳,移驻广东惠州的甲子门。次年(景炎二年,1277)九月,转移到浅湾。十一月元将刘深攻浅湾,又转移到秀山,又向井澳转移。十二月到井澳时,海上飓风大作,死者过半,幼帝落水被救,惊悸成疾。是月,元将刘深又来袭,井澳大败,幼帝退至琼州海峡的谢女峡,进入北部湾,驻于七里洋。
以上是景炎二年(1277)幼帝海上败退的路线,史志所载基本一致。但在陈宜中往占城的时间上略有差异,一说十一月,一说十二月。据胡珠生先生考证,陈宜中应于十二月往占城,因为其时在飓风大作的十一月,帝昰尚未患病,宜中去占城缺乏根由。据《宋史·陈宜中传》记载:“井澳之败,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井澳之败后宜中才往占城,时间当在十二月无误。
至于井澳之败后,宜中从何处往占城,虽不见史志有明确记载,但仍可从中找到行迹。
《宋史纪事本末》载:“元刘深袭井澳,帝奔谢女峡,复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不果。”由此可见,井澳败后,受东北季风及航海条件的限制,舟师只能向西南方向败退,退至琼州海峡的谢女峡,并进入北部湾的七里洋。这里与占城近在咫尺,《元史》(210卷,列传97,外夷3)载:“占城,近琼州,顺风舟行一日可抵其国。”因此,此时幼帝“欲往占城”是符合逻辑的。又据广东湛江的地方志书载:“南宋末年,陈宜中任右丞相兼枢密使,避元兵奉帝南下,过吴川河畔的极浦亭曾赋诗”。幼帝舟师在撤往琼州海峡的途中,曾停泊于吴川,此时宜中尚在,证明他往占城当在离开吴川之后。因此,陈宜中往占城的时间是景炎二年(1277)十二月,地点就在北部湾的七里洋。
陈宜中为何往占城?《宋史·陈宜中传》的“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谕意”记载,便是最好的回答。占城为异域,可否前往关系到幼帝与朝廷的安危,必未敢冒然,需先使人先往“谕意”。此时又是非常时期,生死存亡在此一举,然占城非世外桃园,前途未卜,谁肯担此重任?陈宜中不畏艰险,亲自出马,代表朝廷往占城传达皇帝的旨意,其目的意义明确,行为正当。
《宋史·陈宜中传》载:宜中往占城后“度事不可为,遂不反。二王累使召之,终不至。”于是,陈宜中正当的行为便被冠上了“逃跑”的罪名。
陈宜中在占城的行迹,不见史载,今已无从稽考。但他去占城之前的行迹及诗文是值得注意的。
《南澳县志》载:“二年正月移惠州甲子门。据广州元将吕师夔等因军饷不继退走,以其部梁雄飞守之。经略使刘应龙导帝舟至广州港口,转运使姚良臣预迎帝入州治,守江元兵拒之,不果入,帝舟还大海驻秀山。惟宜中得入广城,寻遁还。”为图复广州,身为丞相的宜中竟置生死于度外,亲自潜入广州,这与他亲自前往占城谕意的做法如出一辙,再者,如果他想逃跑,此时正是机会,而他却回到幼帝身边。
《广东省吴川县志》载:“极浦亭在吴川县南河畔,宋邑人李凌云隐处(大清一统志)。宋丞相陈宜中过此有诗,后人取为八景之一。”吴川李氏家史也有相同的记载。
当年陈宜中题诗的“极浦亭”至今尚存。该亭始建于南宋淳佑年间,历代多次修葺,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亭内柱联:“每当美景良辰定有词人同载酒,无复颠风急雨尚留丞相旧题诗。”虽经历代修葺,古风依然,惜当年宜中所题墨宝已不知下落。如今吴川人尚在纪念陈宜中,在“极浦亭”内立青石碑,碑文录自吴川县志的宜中题诗,竖书,阴刻:“颠风急雨过吴川,极浦亭前望远天;有路可通寰宇外,无山堪并首阳山。岭云起处潮初长,海月高时人未眠;异日北归须记取,平芜尽处一峰圆。”诗中“北归”二字,表达他图复的决心。
上述宜中往占城之前的行迹,足以证明宜中断无逃跑的意图。
至于他在占城的行迹,不见史载,无从稽考。他往占城后之所以未能及时返回,很可能占城之行并不顺利,甚至在那里遇到了麻烦。时任宋吏部尚书的陈仲微被派往占城找宜中,却连一面也没见着,不久宋亡,便干脆跑到安南,受到安南陈圣王的礼遇。因此,所谓“二王累使召之”,究竟派去多少人?是否见着了人?均不得而知。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陈宜中去占城后回没回来?几乎所有史籍都说他没回来,然事实的回答却与史载截然相反,陈宜中确实回来了。
五、从占城归崖山,再登东山岛
据《宋史纪事本末》(二王之立)载:景炎三年二月(1278),“帝舟还广州”,三月“帝迁驻硇州”,四月,帝崩,11岁的帝昰病故,立8岁的卫王昺为帝,五月改元“祥兴元年”,六月“帝迁居新会之崖山。帝昺祥兴二年(1279)二月,崖山大战,宋舟师全军覆没,陆秀夫负幼帝投海,宋亡。
《宋史》载:“二月癸未,弘范等攻崖山,世杰败走卫王舟。大军薄中军,世杰乃断维,以十余舰夺港去。后还收兵崖山,刘自立击败之,降其将方遇龙、叶秀荣、章文秀等四十余人。世杰复欲奉杨太妃求赵氏后而立之,俄飓风坏舟,溺死平章山下。”
十余舰夺港而去,除了张世杰溺死平章山下,尚有其他人及其舰船去向何方?他们又发生了什么事?史籍无载,幸有亲历者留下足以补正历史的重要证据。
亲历崖山之战的黄材在《漳浦湖西黄氏族谱》(文忠公族谱序)中写道:
“值天运转元,随卫王播迁于广东新会之崖山,奉杨太后懿旨,保若和郡王。不期年,元兵俱至,连日大战。余知势迫,乃与张世杰,许达甫等十六船,护王夺港而出,遇陈宜中船于广崖之浅澳大会,欲往福州图恢复。忽飓风大作,世杰不幸船沉,宜中船破,因登合浦。惟余与达甫四船护王及父天从公,漂至浯屿前,又失杠具,乃于浦东登岸,匿王为我黄氏,合居焉。吁!为臣死忠,为子死孝。当是时,文天祥已被执,世杰、秀夫随帝入海,捐躯报国,此心可白。余岂独二、三公之死而故觑焉而逃哉!第据〈礼经〉:‘士死制’,余奉制保王,王在,或嘘炎宋之灰于再振也。……岁在戊戌端月望日,宋逋臣黄材,字国珠,泣血书。”
这篇谱序写于元成宗二年(1298),距崖山之败仅19年,作者又是事件的见证者,所记当可信。
如果说黄材所记尚为孤证,那么,与黄材同行的郡王赵若和相同的记述,则又是一个重要证据。他在修于元仁宗三年(1316)《闽冲郡王赵家堡族谱》的(赵氏本末序)中写道:
“元兵逼侵、吾乃奉帝挈家,驾船逃难,移之广东新会之崖山。噫!当是时,忠臣烈将,武夫精卒,尚有数万人,粮食赖伍太师家为馈饷,尚未乏绝。予亦托万里之天缘,乃缔太师之女。不期年,元兵且至,连日大战,吾知势已败、与许达甫、黄侍臣等以十六舟夺港而出,遇陈宜中在广崖之浅澳大会,欲往福州以图匡复王室。船到广东南澳之七十余里,飓风大作,宜中船破,遂登合浦。予冒至浯屿之东,船亦失其杠具,就于浦西登岸,后徙鸿儒积美居焉。”
赵若和所记与黄材所记不谋而合,一致见证一个史实:陈宜中并非如《宋史》所言“遂不返”与“终不至”,他不但回国,而且“欲往福州图恢复”。
据胡珠生先生所引的《永嘉二都前街陈氏宗谱》的陈宜中简传载:“上命至占城、暹罗国乞师,归崖山之界,闻宋亡,竟溺而死,浮尸海上,里人咸以为异,遂收殡葬。”显然,其中归崖山后见宋亡“竟溺而死”的记载,极可能根据张世杰溺海而亡的事件推测而已,但其“归崖山之界”的记载,却又一次证实了黄材、赵若和的亲历所见:陈宜中确实回来了。
由此可见,《宋史·陈宜中传》所载的“至元十九年,大军伐占城,宜中走暹,后没于暹”,是不符史实的。它可能根据元翰林直学士承旨刘庚于延祐五年(1318)所撰的《永嘉陈氏世德碑》。碑文写道:“太夫人日思乡里,会其兄芹孙、女兄尼净戒至自暹国宜中薨所。”
陈宜中的侄儿侄女出家受戒,根本无法了解伯父宜中的行迹,从暹国归来并没说伯父死在暹国,是碑文作者的一种猜测,即使确有此说,也只是一种麻痹当局的搪塞之词。《宋史》未加考证,便以猜想替代了事实。
至此,《永嘉陈氏世德碑》、《宋史》与《永嘉二都前街陈氏宗谱》记陈宜中死于暹,或死于崖山之界,或老死,或投海自尽,均为猜测,缺乏证据。
那么,陈宜中遇风船破,于合浦登岸,合浦为何处呢?赵若和明确指出宜中登岸的地点距南澳70里的合浦。当时他们航行的方向是从南向北,那么,南澳北面70余里的地方,便是东山岛。宋代,东山岛包括陈城村在内的东南滨海地区,当地人俗称为合浦,明时改称泊浦,清时又称碧浦,宜中在附近海域船破登岸,必然入大帽山看望儿子,祭祀母坟。
陈宜中第二次到东山,究竞住了多长时间?今已难以查考。自从元世祖十三年(1276),朝廷便开始追捕宋广王及陈宜中,他的处境十分危险,不可能在此久留。根据当时形势推测,陈宜中极可能从海上离开东山,并向北航行。因为,宋代东山海运业已十分发达。据《东山县志》载:“宋建炎元年(1127),东山磁窑村一姓孟者建造8个陶瓷窑,雇工烧制碗、盘、茶具、酒具等磁器,远销外地。”资料表明,当时东山已经建造大型海船“北船”,南北远航,从事海上贸易。
六、改名换姓,隐居湖北蕲春久长山
在湖北省蕲春县蕲北山区崇山峻岭深处的久长山,有一座古墓葬,俗称“相墓”,墓主人为宋故丞相田梦罴。但宋代没有一个叫田梦罴的丞相,而当地田氏人家世传田梦罴就是更名换姓、终老久长山的宋相陈宜中。
经蕲春县田文国、田志强和田耀国三位先生考证,证实了田氏人家的世传:“田梦罴即南宋末代丞相陈宜中”,其主要依据有当地古墓葬与田氏族谱等。
“相墓”座落在久长山,墓首分四柱三门,中门镶墓碑,两侧立墓志。墓碑阴刻:“宋故丞相田公讳梦罴大人、妣黄、梅、王夫人墓”。墓志自右至左,阴刻:“田氏鼻祖讳梦罴,宋人,仕宋为显宦,先世隶籍雁门,自南渡后,解组来蕲,卜居大同之久长山,是为田氏迁蕲之始祖也,历数传,人丁繁衍,其散在他邑者,支分棋布,甲第联翩,而居蕲者十数户,尤为甚盛,绳绳继继,绵世守而衍箕裘,以是叹我祖之垂誊者远也。祖原卜葬土库楼天欣也。祖妣黄、梅、王氏,合墓共碑,历宋元明,迄今七百有余岁矣,其间碑牌之代立者,不知凡几,奈所换之碑,又多历年所,一则风雨飘摇,字迹剩落,一则土膏滋长,碣石芜埋,后人欲摸碑而读之有不可得者,是以聚族而谋复立,坚石丰碑,仿旧制而修之,庶几陵谷变迁而不朽云。皇清同治十三年仲春月谷旦,支下远孙同立”
清乾隆年间,楚北大学者、大诗人、《湖北通志》主编陈诗,曾以田桥地名作《竹枝词》一十七首,其中第六首第一句写道:“相墓经传土库楼”,开句便点到“相墓”,说明至少在同治维修墓葬之前,墓主的身份就已被这位大学者承认。
但是,该墓葬规格不高,规模不大,与墓主身份不符,这是为什么?现存墓碑及墓志均为清同治十三年(1874)最后一次维修时所立,虽有纪年而为何不见始建年代与墓主卒年,如经考古发掘,是否有墓志或买地卷?这些问题令人疑惑不解。然而,正是这些令人疑惑的问题,暗示了墓葬的时代与墓主的特殊身份。
墓葬为田梦罴及妣黄、梅、王三夫人共四个人的合葬墓,此与元代盛行夫妻合葬和家庭多人合葬的做法相吻合。例如:山西元代侯马赵氏墓,六人合葬,西安雁塔南路元墓共有木棺5具,是典型的家庭合葬墓。像江苏武进下港元代夫妻合葬墓、江苏吴县黄桥乡元代吕师孟夫妇合葬墓等,更是不胜枚举。元朝建立以后,忽必烈采用了汉族的立法来治理国家,汉文化与蒙古族文化得到空前的融合。做为生活习性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墓葬习俗也逐渐被蒙古人采用。尽管如此,元朝还是提倡薄葬简丧的,甚至明文规定:“诸坟墓以砖瓦为屋其上者,禁之。”这就是田梦罴墓葬规格与其身份不符的原因之一。当然,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特殊身份,既已更名换姓,自然不能张扬,其墓葬更不可能暴露其真实姓名、真实身份以及生卒时间等信息而祸及子孙。
因此,当疑惑被消除,墓葬的年代便不言而喻了,而墓主人的神秘面纱,也就被轻轻地撩开了。
修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蕲春《马骅山田氏七修宗谱》序载:“我田氏来蕲春之鼻祖曰梦罴公,世传即宋相陈宜中,当端宗舟抵秀山时,由占城迂道逃至江淮间,结忠义之士,谋复宋室,志卒不遂,乃仿陈公子完之先例,易姓为田,匿于蕲北之久长山而隐居焉。……光绪癸巳科副举人湖南直隶州州判二十四世侄孙嵩元葛民甫敬撰,民国二十六年仲春月谷旦。”
修于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蕲春《田桥久长山田姓家谱》序载:“余族之先家世雁门,南宋时梦罴公始迁大同乡之久长山,至今五百余年。”
蕲春新修《田氏大成宗谱》谱系云:“田梦罴者,乃陈宜中也。”
以上所引田氏宗谱记载,“当端宗舟抵秀山时,由占城迂道逃至江淮间”在时间上有差异,至于“结忠义之士,谋复宋室”是否事实有待查考,而“仿陈公子完之先例,易姓为田,匿于蕲北之久长山而隐居焉”与当地口传历史一致,应符合事实。因此,结合田梦罴墓的分析研究,田梦罴无疑应该就是陈宜中。
陈宜中可能借助“北船”从海上离开福建东山岛,由海入长江至湖北,再拐入蕲水河、龙井河,进入偏僻的蕲北山区的久长山。
然而,陈宜中为何选择蕲北山区而不是其它地方呢?另一座古墓葬及其相应的宗谱记载,回答了这个问题。
田文国、田志强和田耀国等,在蕲春县大同镇何铺村找到传说中的“公主墓”,并找到与“公主墓”互为印证的《黄氏宗谱》。“公主墓”的墓主人为黄元庆及夫人赵公主。《黄氏宗谱》(世系)载:“尧咨,二十公长子,字元庆,宋嘉定驸马,赘赵公主。生子四:英迪、圭、郁,女一适宋相田梦罴。公妣合葬洪潭坂上老鹳窠金规银槽,癸山,丁向,有碑,有石阶三十二步,有华表。”
该谱首修于元大德戊戍年(1298),重修于清同治元年(1862)。经三位田先生考证,“公主墓”所处地理位置、坐向、形制规格、附属建筑与宗谱所载完全一致,而赵公主是宋嘉定年间的郡公主,同是宋室皇亲,其女儿正是与宋丞相陈宜中合葬的黄氏夫人。如若无误,这是很有价值的证据,它为陈宜中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材料,是陈宜中为何选择蕲北山区隐居的确切答案。
七、简短的结论
陈宜中作为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其争议的关键就在于《宋史》记载的“宵遁”、“如占城”与“遂不反”八个字。然而,陈宜中却以其行迹订正这八字不实之词。
他在南宋举国降元之际,不愿投降,扶立二王,以图兴复。
他带着母亲的灵柩离开故乡,奉帝即位于福州,葬母于东山岛大帽山。海上行朝,节节败退,至北部湾七里洋,帝欲往占城,他奉旨先往。占城事不可为,他即返回崖山,正值宋亡,遇夺港而出的赵若和、黄材、许达甫等人,欲往福州图恢复,途中遇风船破,再次登陆东山。最后,他在朝廷四处追捕的情况下,潜入湖北蕲北山区,改名换姓,隐居山林,死后葬于久长山。
清代王夫之说:“宋迨理宗之末造,其亡必矣。”又说:“通蒙古亦亡,拒蒙古亦亡,无往而不亡。”
作为当朝丞相的陈宜中,对南宋前途应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他拒绝称臣投降,显示了崇高的民族气节;扶二王以图兴复,体现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携母棺奉帝即位福州,行朝海上,葬母大帽山,既忠又孝;如占城,归崖山,力挽南宋,英勇顽强;终老山林,虽无杀身成仁,却已竭尽忠义。
胡珠生先生在其《陈宜中生平考辩》的结论中指出:“陈宜中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坚贞不屈、至死不忘匡复宋室的忠臣。”
至此,历史对于陈宜中的争议,可以结束了。
参考文献:
《宋史》、《元史》、《四库全书总目》(宋史)标点校勘本、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二王入闽大略〉、明·陈炜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龙湾史志》、清·王夫之《宋论》、《闽书》、《南澳县志》、《台湾外记》、《东山县志》、《陈城(顶城、下城)陈氏渊源世系》、《漳州府志》、《湛江市地名志》、《广东省吴川县志》、《吴川三柏李氏家史》、元·黎崱《安南志略》、民国版《东山县志》、《蕲春文化研究》、《考古》、《文物资料丛刊》、《文物》。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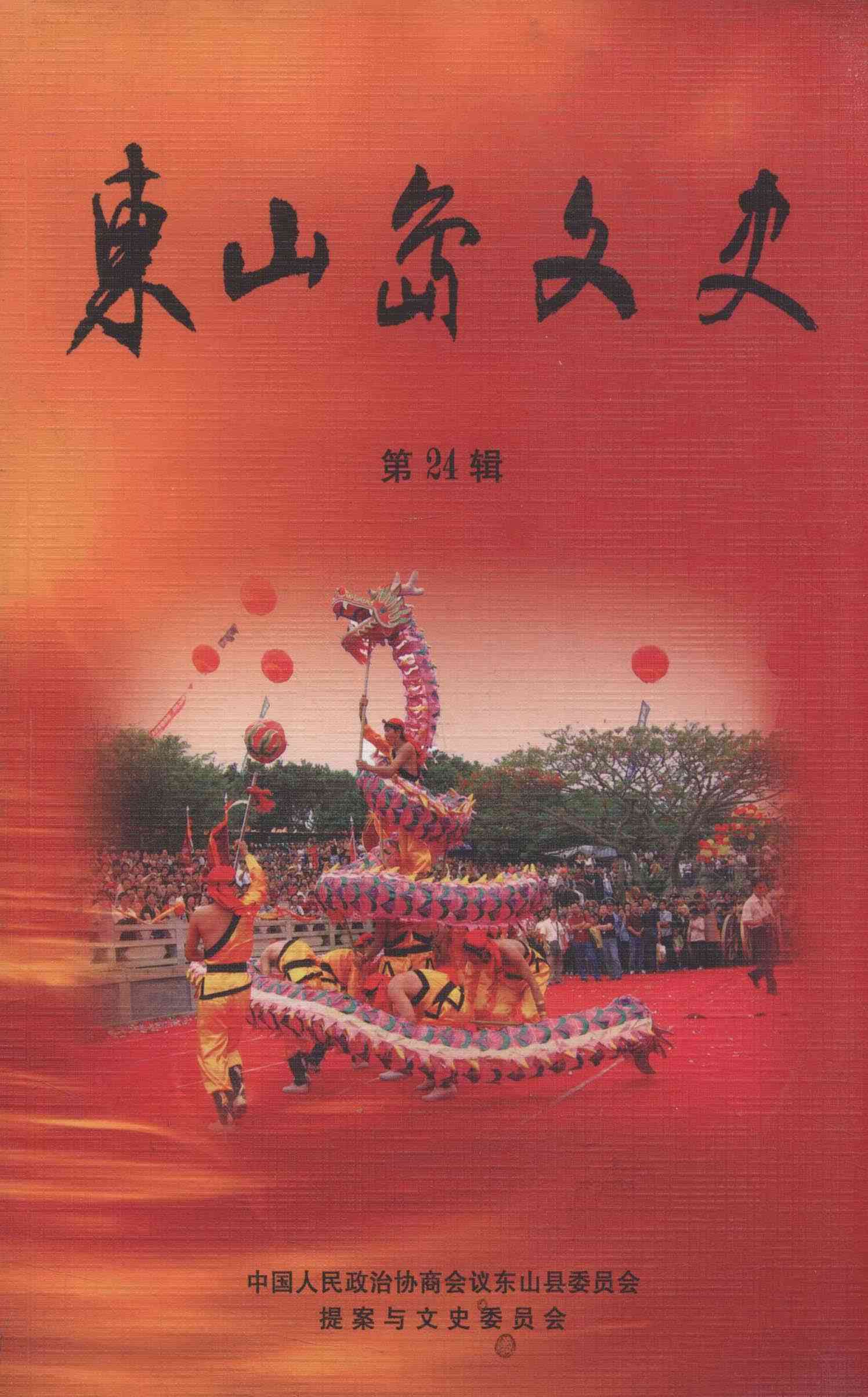
《東山島文史第24辑》
出版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东山县委员会提案与文史委员会
本书分为刊首絮语、东山崛起——建设国际旅游海岛、庆祝建国60周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海峡两岸关帝文化、海峡长风、史海钩沉、文化春秋、铜海吟笺、稿约等。
阅读
相关地名
东山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