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雨耕云忆内寮
| 内容出处: | 《云霄文史资料-第十三辑(总第十七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30003887 |
| 颗粒名称: | 播雨耕云忆内寮 |
| 分类号: | D432.9 |
| 页数: | 10 |
| 页码: | 85-94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1964年至1978年内寮下乡经历的故事,内容包括组织上山下乡的经历、农场生活、社会变迁和个人家庭生活等方面。 |
| 关键词: | 上山下乡 农场生活 社会变迁 |
内容
1964年深秋,云霄县首批青年上山下乡,各界组织欢送,红花夹道,锣鼓喧天,一时传为佳话。三十年过去了,这一切都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云里,很少有人提起了。只留下苍茫的油柑岭下,横卧着几座平房,勾引过往行人,指指点点,评说它昔日的辉煌!我便是那首批下乡青年中的一员,在内寮这个地方,春耕冬种,风雨中滚打了十四年,直至1978年才离去!又十几年过去了,偶尔有下乡故人来访,寒暄之余,相视感概:当年垂髫年少,如今已鬓发萧疏,垂垂欲老矣!老则话多,尤喜谈旧事,于是那逝去的一幕幕便重新掀起。近来自度:内寮那段岁月,虽说平凡,然而那足迹曲曲弯弯,却是十分生动而又真实的,于是记叙如下。
(一)
1964年,我高中肄业,一时未能谋到事干。从报刊上经常看到上海支边青年建设新疆的有关报道,还有董加耕、邢燕子等青年下乡的一系列事迹,意识到青年学生建设农村,开发边疆似乎已成为大方向,但其人其事,远在北方的大城市,因此也未曾把下乡劳动和自己联系起来。1964年10月的一天,溪美街街政府通知我当晚去礼拜堂开会,我去后才明白,为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县里准备组织青年下乡,于是把我们这些社会闲散青年召集起来,开动员会。当时我想,与其在城关闲着无事干,不如下去看看,无非是吃点苦罢了,或许还能闯出一条新路来。于是几天后,我便带着户口册,到街政府去报了名。
当时县里有个主管单位叫“精简办公室”,专门处理我们这些青年下乡的一应事务。记得我们每人有六十元的安置费,其中三十六元做为下乡后六个月的伙食补贴,二十四元发给个人,以购买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又每人可以照顾购买棉被、被单、蚊帐中的任意两件。于是我买了一件蚊帐、一条棉被、一把锄头、一担畚箕后,实际领到了七元钱。当时精神振奋,大有投笔从戎,奔赴前方的激情,也不去计较钱的多少了。
11月23日,天气晴和。清晨,有街道干部上我家来,帮我整理行装。当时行李甚为简单,一件被包,一个木箱而已。街道干部帮我把行李搬往街政府,统一上车。我们这些下乡青年集中在人民会堂前,记得当时锣鼓喧天,彩旗飘拂,有许多欢送的人群。接着有领导讲话,大意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锻炼,大有作为”等等,然后有领导前来和我们逐一握手,还有人分给我一朵红花。只是当时年纪小,记不得那么多的首长,只知道他们个个和蔼慈祥、笑容可掬。后来,我们列队游行,经中山路至经堂口车站上车,前往内寮。路过莆美、大埔两村,道旁有小学生挥彩旗迎送,在奔驰的汽车上,尚可清晰地听见他们“下乡光荣,劳动为贵”的口号声!
下乡青年分乘四辆汽车,计一百十几人(其中有整户下乡的四户人家)。后来才知道,这些人中,有高中毕业生戴天冲、张俊标、吴大维、陈衡山、方竞雄、黄耀妍等,有中专毕业生梁惠鹤、高子余、陈楚文等,还有初中毕业生陈健全、潘慎修等二十多人,其余的大多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社会青年。男青年多,女青年只有十几位。据后来统计,这些青年中年纪十八岁的最多,属猪的,共三十几位;其次是十七岁,属鼠的;十九岁,属狗的。年纪最大的叫高思贤,近四十岁;最小的叫方绍禹,只有十四岁。
同车前往内寮的有县委干部洪瑞玉,镇干部陈添春等,还有一位瘦小的中年人,挺和气,后来成为我们的场长,叫张乌联,是位老游击队员。
在我们之前到内寮下乡的有陈耀城、唐明和、张栋材等数人。
同年12月,第二年5月,又有两小批城镇青年到内寮来,组成了相当规模的内寮知青部落。
(二)
在我下乡之前,只知道内寮在油柑岭下,离县城三十里,可从来没到过,汽车过大埔右转不久,便来到了目的地。
这里全称叫大埔公社内寮农场,原是大跃进期间由当时的红旗公社组织各村劳力开垦出来的,后经几番变革,由大埔公社各大队派社员驻在这里耕作。有两个农业生产队,一个果林队,我们这些下乡青年也就分别编入。我分在第一生产队。不久,各大队抽调的社员陆续迁回老家,只留下几位精通农业生产的老农负责指导我们,内寮农场也便成了名符其实的知青农场。
另外,这里还有两个自然村,分别叫口寮和内寮,合计有四、五十户人家,全称口内寮大队,耕地与内寮农场交错毗邻。
为迎接我们的到来,内寮农场在口寮、内寮两村间的一处山坡上建了两排平屋,每排十间,每间十五平米。我们到来之时,上排宿舍尚未完工,所以我们便挤在下排宿舍里,每间住八个人,打统铺,劳动工具、生活用品都堆放在床下。反正都是年轻人,嘻嘻哈哈的,也不觉得苦。后来上排宿舍建成,才重新安排每间住五个人,一人一铺位。
下乡第二天,我们听取了原内寮农场书记张文山的报告,并实地察看了属于内寮农场的耕地、食堂、水库、猪舍等。一个长期生活在城镇的年轻人,面对着眼前的绿水青山,心情豁然开朗。于是有人建议:明天就下地干活去!当时正属秋收时节,田野里水稻一片金黄,正待开镰收割,所以,场部也就答应了下来。1964年11月25日,便开始了我们作为下乡青年的第一天劳动!
农场办集体伙食,每人粮食定量每月三十斤,主要以自产的蔬菜、花生、豌豆为小菜,偶尔佐以咸鱼干。因为吃肉的机会少,加上大家年轻,胃口好,又干重活,所以通常是下工钟响,大家便拥向食堂,领到饭菜,“三下五去二”,干净利索,很少有浪费粮食的现象发生。
这里属云霄、诏安交界处,较为偏僻。不久之后,我们便碰到了许多神奇的麻烦事:不说夜里蚊声雷动,老鼠和人同床共寝,也不说荒草道、田埂边时有黄蛇自脚边窜过,单是那白天里满空飞舞的小咬虫,便教人束手无策。初夏中午,即使是躲入蚊帐,也无法抵御它们的侵袭,直咬得你皮肤红肿,疙瘩满身。那水田里的蚂蟥,尤为可恶,一闻水声、成群而至,触及皮肤,便咬住不放。那些生长于城关的女青年,又何尝见过这般怪物!一旦被咬,则尖声哭喊,狂跳不已,直至男青年闻讯赶来,把那恶虫揪去,偏又血流不止,教人不知所措。下乡初期,如此种种,一言难尽。
这里远离县城,交通不便。如今满地里横冲直撞的手扶拖拉机当时尚未问世,所有下乡青年中唯戴天冲有一架旧自行车。县精简办公室的领导每年来看望我们几次,有时也放放电影,对我们来说,真可谓是精神方面的大改膳。除此之外,马山、下云,甚至杜塘、柘林等地放映电影,我们也会结队前去观看,然后踏着月色,连夜回场。记得有一次,云霄放映印度故事片《流浪者》,我们男男女女十几位,于下午放工之后,取道马山小路,步行回云霄,看完电影后连夜赶回,至内寮时下半夜两点半。第二天照常下地干活,热情可谓高矣!
虽说是各方面条件并不优裕,但人们精神面貌却很好。下乡不上一年,不少同志便学会了犁耙、插秧等农活。女青年不怕劳累,敢于挑厕肥,清牛栏粪。果林队在油柑岭种西瓜,到宿舍边挑厕肥,往来五里路,郭麟芳一个下午竞挑了七担。细细算来,那是挑着一百多斤的重担,在田埂上奔跑了三十几里路啊!
1965年底,结算分红,我共劳动了三百四十几天,得了三千二百多工分,每个工分值三分半人民币,这样,扣去全年伙食费和预借款,我共盈余了近30元钱,在农场中算是中上水平了。钱虽不多,却是自己劳动所得,因此那几天,农场上下喜气洋洋,还有人连夜敲开代销店,买酒助兴的。
这一年,县里领导常来关心慰问,并筹办业余学校。不久,下乡青年李惠华、陈瑾被送龙溪卫校读书,后又有陈建全送省商业学校,吴润泽、郭庆明等送邵武煤矿中专学校学习。据说当时还准备送十名青年招工到县食品厂去,后因并入常山农场,没有调成。
我们是1966年春并入常山华侨农场的,从此更名为常山华侨农场东升管理区,不久,总场在下乡宿舍左侧山坡上建新房四座,准备接侨。文革开始,接侨中断,我们便临时接管了这些新屋,当成宿舍,住宿条件明显改善。按当时常山农场的包工制度,下乡队除管理原来的水田、旱地之外,还开拓荒地,种植橡胶等经济作物,每月可向常山拨工资一千四百元左右(当时我是出纳员),每个劳动日(以十分计)可得六毛钱,一个正常劳动力月工资二十几元,经济状况也明显好转。除此之外,我们还享受全民所有制职工待遇,自己觉得生活有了保障。于是年轻人身上潜在的浪漫气息便渐渐地释放出来,劳动中的歌声响亮了,你唱我和的。吹笛子拉二胡的人也多了起来,吴大维、方维坚、陈衡山便是这方面的好手。晚上空闲,月朗星稀,电影插曲,革命音乐直至《二泉映月》、《十送红军》等名曲,便在晴和的夜空中回荡!后来,下乡青年还组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节目,参加常山农场甚至于县里的文艺会演,还获过奖呢!
这是属于内寮下乡青年的一段黄金岁月!其时虽说已进入了“文革”,县城满街大字报,高音喇叭震天响。在内寮,却是风平浪静。虽有一些小道消息传播,但人们往往是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摇摇头,继续扛起锄头下地干活!所以在无政府思潮泛滥的那一段时期,外头停课闹革命,步行串联,而我们却凭着一颗赤诚的心,有着对祖国对人民的责任感,继续奋斗在农业第一线。一百八十亩的水田,几百亩的旱地,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从没有让一块田地荒芜过。我以为,从这一点看来,内寮的下乡青年是无愧于历史的!
(三)
“文革”继续下去,县精简办公室终于瘫痪,我们失去了来自“娘家”的关心和安慰!
“文革”继续下去,常山爆发武斗,农场党委无法正常工作。虽说不久即成立了工农业生产领导小组,但“抓革命、促生产”,事务繁忙,对内寮下乡青年也就无暇顾及了。
一系列沉重的消息接踵而来,在我们心头投下了阴影。不久,常山农场派遣军宣队进驻内寮。据当时的说法,“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是老大难单位”,更何况下乡青年中有相当一部分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于是组织动员群众,检举揭发阶级敌人。不久果然揪出了七八个,于是禁闭,写交代,批斗游乡。每天清晨,挥舞竹扫,打扫卫生,名曰“劳动改造”,折腾了好一段时间!
当年揪出的“阶级敌人”,个个“罪行累累”,至今想来,啼笑皆非!下乡青年方某,收工回来,上食堂吃地瓜饭,吃到块臭地瓜,用汤匙挑起,顺手甩出窗外,不料抛中贴在墙上的领袖像,于是有人检举,方某即以“现行反革命罪”遭关押,说他是“有刻骨仇恨”,不然怎么会用烂地瓜进行“恶毒攻击”等等,还要进一步分析阶级根源。这在当年是十分严肃的政治事件,谁敢说半句同情的话?!于是人人自危,唯恐祸自天降,只好天天呆在田里,多干活,少说话,以求平安。
“清队”的结果是把二十三位下乡青年调往下云、柘林等地,分散管理。人是走了,但无疑对下乡青年的感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加上1969年以后,常山农场下放云霄县主管,改为每月发3至5元的生活补贴,因此人们的思想十分矛盾,以后的生活如何安排更成问题,农村的农民还有点自留地,能种菜养猪,喂鸡下蛋,而我们除锄头畚箕外,一无所有。当时县里虽有了“知青办”,但由于人员更迭,对下乡于“文革”前的我们不甚了解,加上“文革”间,一切都不那么就绪,所以上述情况多次反映,也未能得到解决。
面对种种具体困难,部分青年产生了动摇,试图返回城关。但由于一些人所共知的原因,回城谋生决非易事。所以,绝大多数青年依旧留了下来,开始了扎根农村的人生旅途!
(四)
我是1969年在内寮结婚的,妻子陈绿茵也是1964年下乡的,初中毕业。通过五年的相互了解,达到彼此间的信赖,于是决定在农村安家。一床一桌,两把锄头,便是我们当时共同拥有的全部家当。一间十五平米的宿舍,贴上领袖像,便是我们温馨的小窝。第二年,孩子出生,更给这小小的空间带来无限的情趣。孩子出生后三十六天寄入归侨队主办的托儿所,我们则一块下田劳动。晚上,我到生产队记工,她料理家务。靠两把锄头,维持着最起码的物质生活。虽处困境,但能相濡以沫,倒也和睦顺美。
不久,妻患风湿性心脏病,多方治疗未愈,病情日重。我更陷入绝境之中,靠我一双赤手,养家糊口,殊多艰难。当时我在远离宿舍的一处山湾里开了两块荒地,加上队里分给的饲料地,约有三分多的水田,一年种两季水稻,秋后再种烟叶,每年可收入一百多元。当时,这并非符合政策的事,只好悄悄地干。我每天清晨到自留地里干活,上工时再和大家一道劳动,一天五班制,忙得团团转。为了熬过难关,什么饥饿劳累,烈日寒风,都不在话下了。1974年冬,我又学会了烤烟,当起烤烟房的烧火师傅来,以赚取每晚5角钱的夜班补贴。这样的日子,直持续到1978年。
这段期间,下乡的青年也大抵走着相似的路。随着年龄的增长,建立家庭已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因陋就简、呼朋引伴,几年间,建立起一个个的新家。配偶多来自邻近的乡村,也有东山、峢屿、火田、和平的。劳动中谈天说地、北调南腔,别是一番风味。不久,食堂停办,单身青年也各起炉灶,自办伙食。收工之后,炊烟四起、热闹而又无聊。
1976年秋,“四人帮”下台。下乡青年拍手欢呼,奔走相告,足见人心之向背!人们翘首以待,盼着上头来个好政策,给我们指一条光明的路。随着有关政策的一件件落实,我们相信,这一天终将到来,于是人们愁苦多年的脸上重又绽开了笑容!
1977年秋,高考制度恢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招生简章。按规定,我可以报考。于是我心中一潭枯寂多年的死水重又泛起了波澜!我与妻子商议,去考!去碰一碰运气!但毕竟是离校多年,书本知识早已忘光,如何应考,心中自是茫然。但主意已定,经一番奋斗,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场高考,并上了录取线!
大概是年龄偏大的原因吧1大专院校没有录取我。1977年底,我依旧在内寮烤烟。直至1978年4月,才接到漳州寄来的“龙溪地区中学师资培训班”的入学通知书。当时悲喜交集,喜的是天不负我,终于闯出了新路;悲的是妻子已步履艰难,儿子年方八岁,母子何以自立…
卖掉家中所有的稻谷和烟叶,共得一百余元,交与妻子当生活费。一番叮嘱之后,我便枪然离开内寮,读书去了。后据妻子来信,我走后,她们母子两人得到场内农友的多方关照和援助,送柴,送菜,延医买药等等,教我阅信之余,感激万分!
我于1979年秋到云霄师范实习。实习期间,妻陈绿茵病逝。做为一名城镇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的征途上走完了她短暂的一生,未能看到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未能领略经济建设的明媚春光,实为遗憾!
我离开内寮不久,上头落实上山下乡政策,凡“文革”间下乡的青年都允许回城,并重新安排工作。而内寮这一批下乡青年却未能分享这一殊荣。询问有关部门,其答复是内寮这一批青年已归入常山华侨农场,属国营职工,全民所有制的,不存在分配问题,因此至今未能解决。后来,随常山农场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注意到量才录用问题,于是有部分同志调离农业,安排到更能发挥他们才干的部门去,这实在也是很值得庆贺的事。
这几年来,内寮其余的同志也陆陆续续通过各种途径返回了城关,或经商,或打工,千行百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总之,都汇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开放改革的洪流中去了!我真诚地祝愿他们,都有一个幸福美好的明天!
(一)
1964年,我高中肄业,一时未能谋到事干。从报刊上经常看到上海支边青年建设新疆的有关报道,还有董加耕、邢燕子等青年下乡的一系列事迹,意识到青年学生建设农村,开发边疆似乎已成为大方向,但其人其事,远在北方的大城市,因此也未曾把下乡劳动和自己联系起来。1964年10月的一天,溪美街街政府通知我当晚去礼拜堂开会,我去后才明白,为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县里准备组织青年下乡,于是把我们这些社会闲散青年召集起来,开动员会。当时我想,与其在城关闲着无事干,不如下去看看,无非是吃点苦罢了,或许还能闯出一条新路来。于是几天后,我便带着户口册,到街政府去报了名。
当时县里有个主管单位叫“精简办公室”,专门处理我们这些青年下乡的一应事务。记得我们每人有六十元的安置费,其中三十六元做为下乡后六个月的伙食补贴,二十四元发给个人,以购买生活用品和劳动工具。又每人可以照顾购买棉被、被单、蚊帐中的任意两件。于是我买了一件蚊帐、一条棉被、一把锄头、一担畚箕后,实际领到了七元钱。当时精神振奋,大有投笔从戎,奔赴前方的激情,也不去计较钱的多少了。
11月23日,天气晴和。清晨,有街道干部上我家来,帮我整理行装。当时行李甚为简单,一件被包,一个木箱而已。街道干部帮我把行李搬往街政府,统一上车。我们这些下乡青年集中在人民会堂前,记得当时锣鼓喧天,彩旗飘拂,有许多欢送的人群。接着有领导讲话,大意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锻炼,大有作为”等等,然后有领导前来和我们逐一握手,还有人分给我一朵红花。只是当时年纪小,记不得那么多的首长,只知道他们个个和蔼慈祥、笑容可掬。后来,我们列队游行,经中山路至经堂口车站上车,前往内寮。路过莆美、大埔两村,道旁有小学生挥彩旗迎送,在奔驰的汽车上,尚可清晰地听见他们“下乡光荣,劳动为贵”的口号声!
下乡青年分乘四辆汽车,计一百十几人(其中有整户下乡的四户人家)。后来才知道,这些人中,有高中毕业生戴天冲、张俊标、吴大维、陈衡山、方竞雄、黄耀妍等,有中专毕业生梁惠鹤、高子余、陈楚文等,还有初中毕业生陈健全、潘慎修等二十多人,其余的大多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社会青年。男青年多,女青年只有十几位。据后来统计,这些青年中年纪十八岁的最多,属猪的,共三十几位;其次是十七岁,属鼠的;十九岁,属狗的。年纪最大的叫高思贤,近四十岁;最小的叫方绍禹,只有十四岁。
同车前往内寮的有县委干部洪瑞玉,镇干部陈添春等,还有一位瘦小的中年人,挺和气,后来成为我们的场长,叫张乌联,是位老游击队员。
在我们之前到内寮下乡的有陈耀城、唐明和、张栋材等数人。
同年12月,第二年5月,又有两小批城镇青年到内寮来,组成了相当规模的内寮知青部落。
(二)
在我下乡之前,只知道内寮在油柑岭下,离县城三十里,可从来没到过,汽车过大埔右转不久,便来到了目的地。
这里全称叫大埔公社内寮农场,原是大跃进期间由当时的红旗公社组织各村劳力开垦出来的,后经几番变革,由大埔公社各大队派社员驻在这里耕作。有两个农业生产队,一个果林队,我们这些下乡青年也就分别编入。我分在第一生产队。不久,各大队抽调的社员陆续迁回老家,只留下几位精通农业生产的老农负责指导我们,内寮农场也便成了名符其实的知青农场。
另外,这里还有两个自然村,分别叫口寮和内寮,合计有四、五十户人家,全称口内寮大队,耕地与内寮农场交错毗邻。
为迎接我们的到来,内寮农场在口寮、内寮两村间的一处山坡上建了两排平屋,每排十间,每间十五平米。我们到来之时,上排宿舍尚未完工,所以我们便挤在下排宿舍里,每间住八个人,打统铺,劳动工具、生活用品都堆放在床下。反正都是年轻人,嘻嘻哈哈的,也不觉得苦。后来上排宿舍建成,才重新安排每间住五个人,一人一铺位。
下乡第二天,我们听取了原内寮农场书记张文山的报告,并实地察看了属于内寮农场的耕地、食堂、水库、猪舍等。一个长期生活在城镇的年轻人,面对着眼前的绿水青山,心情豁然开朗。于是有人建议:明天就下地干活去!当时正属秋收时节,田野里水稻一片金黄,正待开镰收割,所以,场部也就答应了下来。1964年11月25日,便开始了我们作为下乡青年的第一天劳动!
农场办集体伙食,每人粮食定量每月三十斤,主要以自产的蔬菜、花生、豌豆为小菜,偶尔佐以咸鱼干。因为吃肉的机会少,加上大家年轻,胃口好,又干重活,所以通常是下工钟响,大家便拥向食堂,领到饭菜,“三下五去二”,干净利索,很少有浪费粮食的现象发生。
这里属云霄、诏安交界处,较为偏僻。不久之后,我们便碰到了许多神奇的麻烦事:不说夜里蚊声雷动,老鼠和人同床共寝,也不说荒草道、田埂边时有黄蛇自脚边窜过,单是那白天里满空飞舞的小咬虫,便教人束手无策。初夏中午,即使是躲入蚊帐,也无法抵御它们的侵袭,直咬得你皮肤红肿,疙瘩满身。那水田里的蚂蟥,尤为可恶,一闻水声、成群而至,触及皮肤,便咬住不放。那些生长于城关的女青年,又何尝见过这般怪物!一旦被咬,则尖声哭喊,狂跳不已,直至男青年闻讯赶来,把那恶虫揪去,偏又血流不止,教人不知所措。下乡初期,如此种种,一言难尽。
这里远离县城,交通不便。如今满地里横冲直撞的手扶拖拉机当时尚未问世,所有下乡青年中唯戴天冲有一架旧自行车。县精简办公室的领导每年来看望我们几次,有时也放放电影,对我们来说,真可谓是精神方面的大改膳。除此之外,马山、下云,甚至杜塘、柘林等地放映电影,我们也会结队前去观看,然后踏着月色,连夜回场。记得有一次,云霄放映印度故事片《流浪者》,我们男男女女十几位,于下午放工之后,取道马山小路,步行回云霄,看完电影后连夜赶回,至内寮时下半夜两点半。第二天照常下地干活,热情可谓高矣!
虽说是各方面条件并不优裕,但人们精神面貌却很好。下乡不上一年,不少同志便学会了犁耙、插秧等农活。女青年不怕劳累,敢于挑厕肥,清牛栏粪。果林队在油柑岭种西瓜,到宿舍边挑厕肥,往来五里路,郭麟芳一个下午竞挑了七担。细细算来,那是挑着一百多斤的重担,在田埂上奔跑了三十几里路啊!
1965年底,结算分红,我共劳动了三百四十几天,得了三千二百多工分,每个工分值三分半人民币,这样,扣去全年伙食费和预借款,我共盈余了近30元钱,在农场中算是中上水平了。钱虽不多,却是自己劳动所得,因此那几天,农场上下喜气洋洋,还有人连夜敲开代销店,买酒助兴的。
这一年,县里领导常来关心慰问,并筹办业余学校。不久,下乡青年李惠华、陈瑾被送龙溪卫校读书,后又有陈建全送省商业学校,吴润泽、郭庆明等送邵武煤矿中专学校学习。据说当时还准备送十名青年招工到县食品厂去,后因并入常山农场,没有调成。
我们是1966年春并入常山华侨农场的,从此更名为常山华侨农场东升管理区,不久,总场在下乡宿舍左侧山坡上建新房四座,准备接侨。文革开始,接侨中断,我们便临时接管了这些新屋,当成宿舍,住宿条件明显改善。按当时常山农场的包工制度,下乡队除管理原来的水田、旱地之外,还开拓荒地,种植橡胶等经济作物,每月可向常山拨工资一千四百元左右(当时我是出纳员),每个劳动日(以十分计)可得六毛钱,一个正常劳动力月工资二十几元,经济状况也明显好转。除此之外,我们还享受全民所有制职工待遇,自己觉得生活有了保障。于是年轻人身上潜在的浪漫气息便渐渐地释放出来,劳动中的歌声响亮了,你唱我和的。吹笛子拉二胡的人也多了起来,吴大维、方维坚、陈衡山便是这方面的好手。晚上空闲,月朗星稀,电影插曲,革命音乐直至《二泉映月》、《十送红军》等名曲,便在晴和的夜空中回荡!后来,下乡青年还组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练节目,参加常山农场甚至于县里的文艺会演,还获过奖呢!
这是属于内寮下乡青年的一段黄金岁月!其时虽说已进入了“文革”,县城满街大字报,高音喇叭震天响。在内寮,却是风平浪静。虽有一些小道消息传播,但人们往往是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摇摇头,继续扛起锄头下地干活!所以在无政府思潮泛滥的那一段时期,外头停课闹革命,步行串联,而我们却凭着一颗赤诚的心,有着对祖国对人民的责任感,继续奋斗在农业第一线。一百八十亩的水田,几百亩的旱地,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从没有让一块田地荒芜过。我以为,从这一点看来,内寮的下乡青年是无愧于历史的!
(三)
“文革”继续下去,县精简办公室终于瘫痪,我们失去了来自“娘家”的关心和安慰!
“文革”继续下去,常山爆发武斗,农场党委无法正常工作。虽说不久即成立了工农业生产领导小组,但“抓革命、促生产”,事务繁忙,对内寮下乡青年也就无暇顾及了。
一系列沉重的消息接踵而来,在我们心头投下了阴影。不久,常山农场派遣军宣队进驻内寮。据当时的说法,“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是老大难单位”,更何况下乡青年中有相当一部分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于是组织动员群众,检举揭发阶级敌人。不久果然揪出了七八个,于是禁闭,写交代,批斗游乡。每天清晨,挥舞竹扫,打扫卫生,名曰“劳动改造”,折腾了好一段时间!
当年揪出的“阶级敌人”,个个“罪行累累”,至今想来,啼笑皆非!下乡青年方某,收工回来,上食堂吃地瓜饭,吃到块臭地瓜,用汤匙挑起,顺手甩出窗外,不料抛中贴在墙上的领袖像,于是有人检举,方某即以“现行反革命罪”遭关押,说他是“有刻骨仇恨”,不然怎么会用烂地瓜进行“恶毒攻击”等等,还要进一步分析阶级根源。这在当年是十分严肃的政治事件,谁敢说半句同情的话?!于是人人自危,唯恐祸自天降,只好天天呆在田里,多干活,少说话,以求平安。
“清队”的结果是把二十三位下乡青年调往下云、柘林等地,分散管理。人是走了,但无疑对下乡青年的感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加上1969年以后,常山农场下放云霄县主管,改为每月发3至5元的生活补贴,因此人们的思想十分矛盾,以后的生活如何安排更成问题,农村的农民还有点自留地,能种菜养猪,喂鸡下蛋,而我们除锄头畚箕外,一无所有。当时县里虽有了“知青办”,但由于人员更迭,对下乡于“文革”前的我们不甚了解,加上“文革”间,一切都不那么就绪,所以上述情况多次反映,也未能得到解决。
面对种种具体困难,部分青年产生了动摇,试图返回城关。但由于一些人所共知的原因,回城谋生决非易事。所以,绝大多数青年依旧留了下来,开始了扎根农村的人生旅途!
(四)
我是1969年在内寮结婚的,妻子陈绿茵也是1964年下乡的,初中毕业。通过五年的相互了解,达到彼此间的信赖,于是决定在农村安家。一床一桌,两把锄头,便是我们当时共同拥有的全部家当。一间十五平米的宿舍,贴上领袖像,便是我们温馨的小窝。第二年,孩子出生,更给这小小的空间带来无限的情趣。孩子出生后三十六天寄入归侨队主办的托儿所,我们则一块下田劳动。晚上,我到生产队记工,她料理家务。靠两把锄头,维持着最起码的物质生活。虽处困境,但能相濡以沫,倒也和睦顺美。
不久,妻患风湿性心脏病,多方治疗未愈,病情日重。我更陷入绝境之中,靠我一双赤手,养家糊口,殊多艰难。当时我在远离宿舍的一处山湾里开了两块荒地,加上队里分给的饲料地,约有三分多的水田,一年种两季水稻,秋后再种烟叶,每年可收入一百多元。当时,这并非符合政策的事,只好悄悄地干。我每天清晨到自留地里干活,上工时再和大家一道劳动,一天五班制,忙得团团转。为了熬过难关,什么饥饿劳累,烈日寒风,都不在话下了。1974年冬,我又学会了烤烟,当起烤烟房的烧火师傅来,以赚取每晚5角钱的夜班补贴。这样的日子,直持续到1978年。
这段期间,下乡的青年也大抵走着相似的路。随着年龄的增长,建立家庭已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因陋就简、呼朋引伴,几年间,建立起一个个的新家。配偶多来自邻近的乡村,也有东山、峢屿、火田、和平的。劳动中谈天说地、北调南腔,别是一番风味。不久,食堂停办,单身青年也各起炉灶,自办伙食。收工之后,炊烟四起、热闹而又无聊。
1976年秋,“四人帮”下台。下乡青年拍手欢呼,奔走相告,足见人心之向背!人们翘首以待,盼着上头来个好政策,给我们指一条光明的路。随着有关政策的一件件落实,我们相信,这一天终将到来,于是人们愁苦多年的脸上重又绽开了笑容!
1977年秋,高考制度恢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招生简章。按规定,我可以报考。于是我心中一潭枯寂多年的死水重又泛起了波澜!我与妻子商议,去考!去碰一碰运气!但毕竟是离校多年,书本知识早已忘光,如何应考,心中自是茫然。但主意已定,经一番奋斗,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场高考,并上了录取线!
大概是年龄偏大的原因吧1大专院校没有录取我。1977年底,我依旧在内寮烤烟。直至1978年4月,才接到漳州寄来的“龙溪地区中学师资培训班”的入学通知书。当时悲喜交集,喜的是天不负我,终于闯出了新路;悲的是妻子已步履艰难,儿子年方八岁,母子何以自立…
卖掉家中所有的稻谷和烟叶,共得一百余元,交与妻子当生活费。一番叮嘱之后,我便枪然离开内寮,读书去了。后据妻子来信,我走后,她们母子两人得到场内农友的多方关照和援助,送柴,送菜,延医买药等等,教我阅信之余,感激万分!
我于1979年秋到云霄师范实习。实习期间,妻陈绿茵病逝。做为一名城镇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的征途上走完了她短暂的一生,未能看到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未能领略经济建设的明媚春光,实为遗憾!
我离开内寮不久,上头落实上山下乡政策,凡“文革”间下乡的青年都允许回城,并重新安排工作。而内寮这一批下乡青年却未能分享这一殊荣。询问有关部门,其答复是内寮这一批青年已归入常山华侨农场,属国营职工,全民所有制的,不存在分配问题,因此至今未能解决。后来,随常山农场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注意到量才录用问题,于是有部分同志调离农业,安排到更能发挥他们才干的部门去,这实在也是很值得庆贺的事。
这几年来,内寮其余的同志也陆陆续续通过各种途径返回了城关,或经商,或打工,千行百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总之,都汇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开放改革的洪流中去了!我真诚地祝愿他们,都有一个幸福美好的明天!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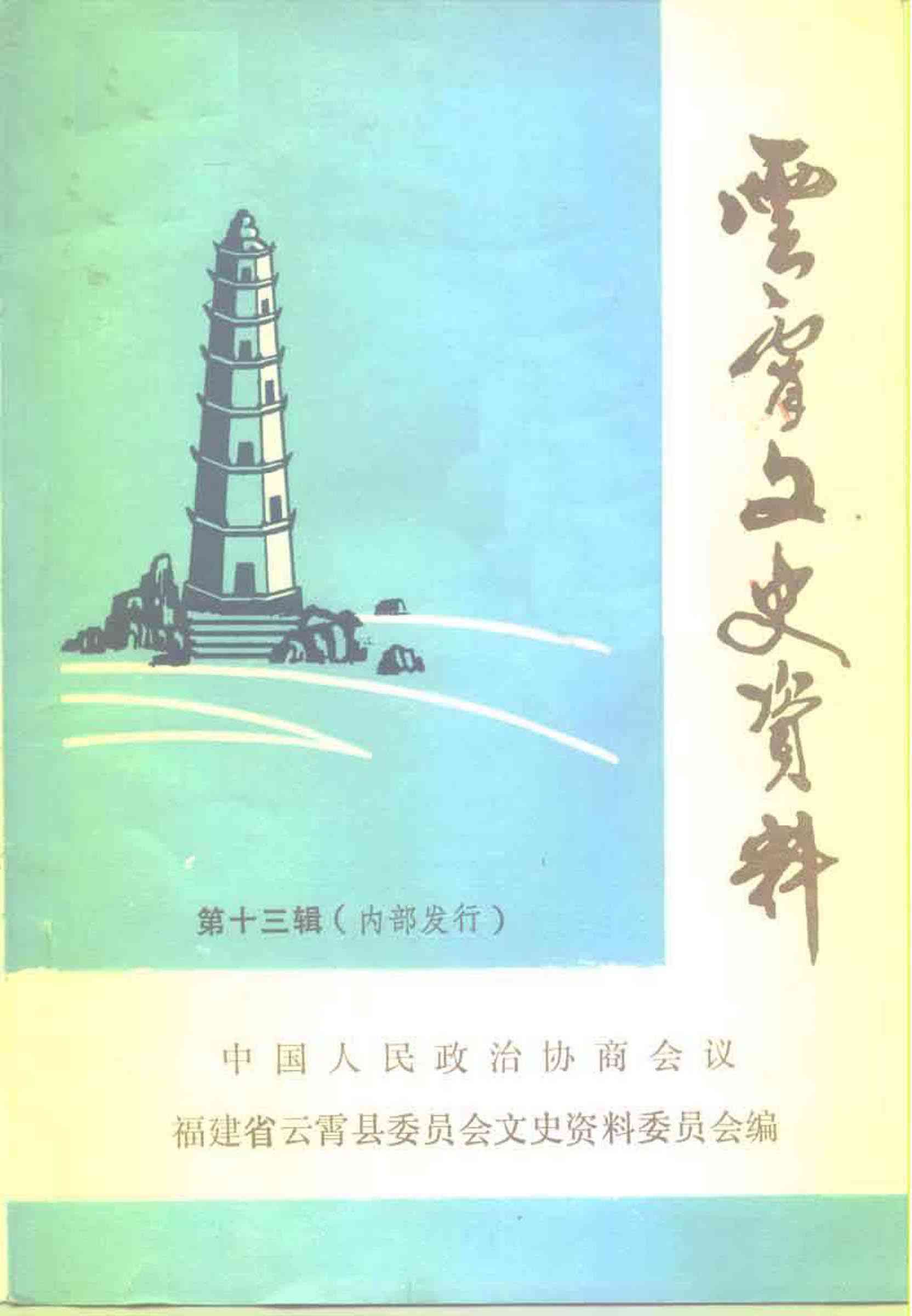
《云霄文史资料-第十三辑(总第十七辑)》
出版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云霄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本书收录“回顾杜塘水库”、“云霄县人民会堂的兴建”、“云霄县供销合作社的创建”、“云霄县程控电话与邮电综合楼”、“解放前鱼商公会”、“三葫芦棕木屐”等约30篇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吴鼎文
责任者
相关地名
云霄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