迢迢烽火路
| 内容出处: | 《南靖文史资料第二十八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30002494 |
| 颗粒名称: | 迢迢烽火路 |
| 分类号: | D922.79 |
| 页数: | 14 |
| 页码: | 68-81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黄清旺是一个出生于1915年龙岩安康的穷苦农民,他的老家在广东梅县,后来逃难到安康。他小时候就懂得了为家庭分忧,常常帮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由于家境贫困,他渴望读书,但因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无法供他上学。10岁时,他给土豪家放牛,因牛儿受伤被东家毒打,不敢告诉家人,暗地里偷偷流泪。仇恨的种子在他幼小心灵悄悄发芽。他默祷苍天:快长大吧,快长大吧,我要报仇!我要雪恨!黄清旺在苦难中磨炼出了倔强性格,为后来参加革命打下了良好基础。 |
| 关键词: | 南靖县 黄清旺 烽火路 |
内容
黄清旺,南靖县和溪镇乐土村人,1915年生于龙岩安康,1931年参加革命,离休前任北京军区空军第13军后勤部副部长。1983年,他回到阔别四十多年的南靖,向故乡人民讲述了一串串峥嵘岁月里血与火的故事……
日夜盼救星
凄风苦雨,落叶飘零。1915年秋天一个漆黑的夜里,黄清旺诞生在龙岩安康的一间破茅棚里。从此,他也和千千万万穷苦的人们一样,踏上了泥泞坎坷的人生之路。
黄清旺的老家在广东梅县,是逃难才来到安康的。家里有爷爷、奶奶、父母双亲和他。几年后,又添了3个小妹妹,全家8口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住的是茅棚草寮,吃的是杂粮野菜,穿的是破衣烂裤。靠爷爷和父亲给人家打长工、做短工挣来的钱养活全家。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黄清旺小时候就懂得替家庭分忧,常常帮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家乡有编竹器的习惯,他便和村里的穷孩子们一起上山砍竹子,回家劈篾条,学着编织竹篮、粪箕之类的东西。他渴望着读书,看到有钱人家的子女高高兴兴背着书包上学堂,就非常羡慕。可家里穷得都揭不开锅了,哪有钱供他读书呢。
10岁那年,他就给土豪家放牛了。有一次,牛儿在跳山沟时不慎摔伤了腿,东家知道后,把他狠命地毒打了一顿。他不敢告诉家里人,暗地里偷偷流泪。奶奶和妈妈见他被打得皮开肉绽,抱着他哭得像泪人儿。仇恨的种子,在他幼小心灵悄悄地发芽了。他默祷苍天:快长大吧,快长大吧,我要报仇!我要雪恨!
像压在大石头下面的竹笋弯弯曲曲地钻出地面,饿不死、打不烂的黄清旺,终于长成了瘦高个儿的少年。艰难的时世,苦难的童年,磨炼出他倔强的性格,为后来参加革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9年,黄清旺14岁。这年夏天,从闽西传来了朱、毛红军协助长汀人民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的消息。但只听见风闻,不见人影,谁是朱、毛?什么叫红军?一串串问号,常常萦绕着他好奇的心;共产党、苏维埃政权……一个个新名词,常听见穷人们在四下里议论。他心里很高兴,莫非世道真的要变?!穷人要出头了?!
共产党啊,你快点打过来吧!红军啊,快来救救我们吧!黄清旺盼呀盼,望穿双眼盼救星。
“三火”烧地霸
1930年的一天中午,黄清旺的村里突然来了一位40岁左右的陌生人,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脚有点儿跛,走路一拐一拐的,头戴破草帽,身穿灰长衫,背把旧纸伞,提只黑布袋,刚在村边树下一块大石头上坐着休息,便有好多收工的人围观着。黄清旺正好放牛回家,也好奇地赶去看热闹。瞧!那陌生人正在给一个长工看“相”呢,口中喃喃吟诵。黄清旺心想:哈!原来是个算命先生。哎,我的命不知好不好?何不让他给掐算掐算?跃跃欲试的他,见围观的人那么多,生怕呆久了,丢失了牛,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前次摔伤了牛腿,就被打得遍体鳞伤,这次若丢失了牛,岂不要去给阎罗王烧开水?想到这里,他不寒而栗,匆匆离开了算命先生。
第三天晚上,黄清旺去找一位小伙伴玩,又发现算命先生在他家里,屋内围着好多人,个个凝神屏息,连那平时爱笑爱闹的小伙伴,也托着下巴,蹲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听着。小伙伴见黄清旺进屋,就用手招呼他。他悄悄走过去,在小伙伴身边蹲下了。奇怪,怎么没听见算命先生念经般的吟诵呢?仔细一听,原来不是在算命,而是在“讲古”(说书)。
算命先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时不时比划着手势,讲起了《三把火的故事》。他说:“三把火就是‘三红’——红旗、红袖章、红缨枪。”啊!原来算命先生不是在“讲古”,而是在讲那些半年多前就风传各地的共产党和朱、毛红军的事迹。
这比“讲古”更好听,因为他讲到了穷人的心坎上。大家都没见过朱德和毛泽东,挺神秘的。讲到最后,“算命先生”站了起来,用低沉凝重的声调说:“三火烧地霸,穷人要当家!今后,大家要团结起来,跟土豪劣绅干,实现人人有地种,个个有饭吃……”。太好了,大家听得眉飞色舞,神采飞扬。黄清旺也高兴得差点跳起来,恨不得赶快把这好消息告诉家里人。很晚了,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被人亲昵地叫“阿拐”的“算命先生”。
那天夜里,黄清旺把这好消息告诉家人后,全家都兴奋得睡不着觉。不过,怕事的奶奶再三嘱咐他出去莫乱讲。
黄清旺躺在铺草的地板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时而想那“阿拐”叔真不简单,他真是算命先生吗?时而想,今后要怎样跟土豪劣绅们斗?能斗过他们吗?直到天快亮了,才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
几天后,“阿拐”叔走了,村里的穷人常聚在一起,议论着“三把火”。
这事被土豪劣绅们知道了,就说要追查谣言。可追查来追查去,都不知道是谁“散布”的,且又众怒难犯,也只好不了了之。
“算命先生”带来了“三把火”的火种,撒在布满干柴的安康大地上。
就地闹革命
“算命先生”走后不久,地处南靖、龙岩、漳平三县交界的永福大岭下村的穷人们,在陈庭庚、陈火铭的领导下,举行了农民武装暴动。革命烽火迅速燃遍南靖县和溪一带的乡村。红畲、坪仑……等乡村的穷苦人纷纷揭竿而起,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
黄清旺渐渐明白了,穷人要想有出头的日子,只有起来闹革命。于是,他毅然甩掉了牛鞭,参加了大岭下的农民武装暴动。那年,他才16岁。从此,他开始走了上革命的道路,参加了红军游击队。
大岭下村一带的农民武装暴动,敌人视如洪水猛兽。不久,和溪民团长林介仁、月水民团头子陈仁根、吕阿宝等带领团丁600余人,杀返大岭下村,到处烧杀掳掠。穷人又遭殃了……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谁能阻挡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呢?就在这关键的时刻,闽西党组织派人来了。啊,原来是“阿拐”叔——穷人朝思暮想的“算命先生”!
“阿拐”叔到来后,立即帮助穷人们重整旗鼓,领导大家与敌人继续进行灵活的有理有节的斗争。他鼓励大家不要灰心,说:“闹革命不像吃饭那样简单,失败有什么可怕呢?有失败,才会有成功……”。
由于黄清旺参加了革命,土豪劣绅们对他家恨之人骨,把他父亲抓去吊打,迫父亲叫他回家,不要当红军。父亲说:“孩儿长大了,做爹娘的哪能管得着呢?腿长在儿子身上,他愿去哪就去哪。”敌人听了,气得暴跳如雷,把他关押在半山腰的一座山神庙里,说要等黄清旺不参加红军游击队了才要放他。黄清旺的父亲咽不下这口冤气,一天半夜,趁看守的人员不注意,便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子,爬出山神庙,爬向悬崖,咬咬牙,闭上眼,跳落深谷……
第二天早上,黄清旺的母亲得悉后,连忙叫上几个穷邻居,迎着漫天大雾,一起上山去找丈夫的尸体,最后才在峡谷里找到,发现还没有断气,但伤势很重,昏迷不醒,立即抬回家治疗。
当天夜里,黄清旺才知道这个消息。趁着夜幕的掩护,他匆匆忙忙从山上赶回家,哭跪在父亲床前。父亲抚摸着他的头说:“花鼓(黄清旺的乳名)啊,我的乖孩子,你千万不能回来,回来是会被他们抓去杀头的。如今这世道,哪有穷人的活路呢?反正豁出去了,要干,就跟共产党干到底!要替我报仇,要报仇呀!”
呆了一会儿,家里的人都催他快走,生怕他被敌人抓去。他含泪告别了亲人,黎明前又赶回游击队驻地。
第三天,黄清旺的父亲因伤势过重,与世长辞了。
黄清旺家的茅草寮被敌人烧了,年迈体衰的爷爷活活给气死,大妹妹卖给人家,换回3斗大米。无家可归了,黄清旺的母亲只好带着年老的婆婆和两个小女儿到处流浪。在讨饭的路上,婆婆也去世了。就这样,黄清旺的“家”又一次“搬迁”——从龙岩安康逃难到南靖和溪的乐土村。
此后,黄清旺便在和溪一带打游击。
乐土村当时有个为非作歹、横行乡里的大土豪,住在大土楼里,娶了两个老婆,因小老婆得宠,黄脸大老婆吃醋。为教训教训这个大土豪,并筹些粮款,黄清旺他们就利用这一矛盾,争取了那个大老婆同红军“合作”,来一个里应外合。
一天夜里,黄清旺他们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来到那大土豪家的后楼下。过了一会儿,“大老婆”就从二楼后窗口放下三条系在一起的背带(农村妇女背孩子用的长巾)。黄清旺和几个战士援“绳”攀墙,很快钻进二楼,把那些银元、布帛、谷麦等物搬取下楼。运回山上后,把所有的钱物,按三、七比例(“大老婆”三,红军七)进行分配。
接着,他们就在乐土村干开了,并在鳖坑头土纸作坊里秘密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
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扩大红军游击队的影响,1934年初夏的一天,黄清旺他们化装奇袭月水村下堀孟圩集,枪毙了罪恶累累的民团头目陈仁根。同年农历8月底,他们在毛南溪东面的虎巷岭伏击和溪民团,打死打伤民团丁多人,缴获了10多支枪和不少子弹。
林中村有个大恶棍,叫林开怀,曾任金山民团团长,与伪乡长郑锦华不和。黄清旺他们就利用这一矛盾,促使他们动刀枪“火拼”。结果,郑被杀。林就纠集同伙上山为匪,抢劫商旅,作恶多端。为集中力量对付反动民团头目林介仁,他们将林开怀抓到龙岩营州,用3个月时间教育争取他为红军办事。慑于红军游击队的声威,林开怀曾通过旧日好友,为红军采买过一批子弹,也曾为红军送过一些情报。但在1936年白色恐恢异常严重的形势下,他又“反水”了,跟林介仁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在我红军游击队里搞策反,先后拉拢游亚狮等10多人,向国民党自首,还在我基点村和游击区内捕杀红军、游击队和工作团的干部、战士多人。这个反动家伙,解放后被我人民政府镇压了。
攻打上杭战
1935年,黄清旺从闽西南教导队分配到永定四支队当班长,参加了攻打上杭的战斗。
素有“铜赣州,铁上杭”之称的上杭城,座落在汀江畔,城东是几丈宽的深沟,城西有口大池塘,城北高山陡立,只有城南是开阔的平原地带,但敌人封锁得很严密,筑有四道铁蒺藜,每道相隔两米左右。城内守敌有一个师的兵力,而攻城的红军只有两个团,况且武器装备等方面都不如敌人。在这种情况下,要攻破这个固若金汤的城池有很大的困难。
攻城之前,团首长叫大家开动脑筋想办法,要从哪个方向攻城,怎样攻?黄清旺微闭着眼睛琢磨着:城东嘛,不行;城西呢,也不行;城北呢,更不行。忽然,他眼睛一亮:“城南,城南!开阔地,便于冲锋……”可一想到那四道铁蒺藜,眼光就立即暗淡下来,铁蒺藜呵,铁蒺藜,你比大山更棘手,我宁可翻越四座大山,也不愿去攀越这四道铁蒺藜。他甚至天真地想,要是没有这铁蒺藜,那该多好啊。
后来,有几位同志想起了《东周列国志》里田单大摆“火牛阵”的故事,便建议古为今用,也来摆一摆“火牛阵”,向城南“开刀”。团部研究后,决定沿用古代这一战术。
太阳快下山了,晚霞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把汀江水映得通红。晚饭后,战士们分头到附近村庄里去,把土豪劣绅家的水牛全都给牵来。牛尾巴给缠上破布,蘸上煤油,并拴上鞭炮,牵到冲锋出发地。每人负责一头牛。
夜深了,上杭城沉睡在茫茫月色中,满天星斗,眨着焦急盼望的眼睛:红军啊,快点儿攻城吧!
突然,军号悠扬,划破夜的宁静,团首长一声令下,大家一齐点燃牛尾巴上拴着的鞭炮和蘸有煤油的破布。顿时,“噼哩叭啦、噼哩叭啦……”鞭炮响了,声震遐迩;牛尾巴燃烧了,火光烛天。那些水牛,自出娘胎,从未经历过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因此,一头头像着了魔,怒目圆睁,狠命往前飞奔……
“火牛”怒吼奔腾,排山倒海,第一道铁蒺藜被冲开踩倒了,紧接着,第二道、第三道……。迅猛异常的“火牛”终于冲破重重封锁线。精神抖擞的战士们跟在“火牛”后面,在一片喊杀声中持枪前进。
刚从酣梦中醒过来的敌人给吓懵了——莫非恶贯满盈,玉皇上帝发怒,派遣天兵天将,驾着火龙讨逆来了?
敌人开枪扫射了。密集的子弹,像蝗虫般猛扫过来,可怜终身劳碌的水牛——红军的“开路先锋”,一头头倒在血泊之中。红军虽然伤亡不少,但战士们仍然斗志昂扬,前仆后继,奋勇向前。眼看就要打到城门下了,敌人见势不妙,立即关闭城门,龟缩城内负隅顽抗。因城坚敌众,没攻下城池。但敌人被红军顽强的斗志给吓破了胆,紧闭城门十来天不敢露面。
困难显英雄
在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敌人采用各种残酷手段,妄图迫使红军、游击队投降,他们封山断路,逐山搜剿,使红军、游击队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这期间,虽然红军、游击队有时也下山打土豪,筹款粮,但绝大部分时间在山上打游击。没有粮食,就挖野菜、竹笋充饥。最难受的就是没盐吃,同志们大都脸色浮肿,四肢无力,患夜盲症的极多。不仅如此,每天还得行军打仗。如碰上雨季,那就更糟糕了,因为没有山洞,搭茅棚又容易被搜山的敌人发现,因此,晚上宿营,只能头、背、脚各垫上一块石头当床铺,用雨伞盖身子,那滋味是够呛的。就连这样的“雨中觉”都睡不安稳,一发现敌情,就得立即起“床”,投入战斗。有时雨夜行军,泥泞山道,又陡又滑,一夜走不到10里路。起初,黄清旺他们都拄着拐杖行军,敌人常常顺着那深深的拐杖痕迹跟踪追击,后来只好把拐杖也扔了。
一天夜里,黄清旺与战友们一起穿越龙岩新祠——适中之间的一段土路,要去抓土豪。他们蹑手蹑脚,连大气都不敢出,悄悄绕过碉堡群时,有一个战士(文书)在跳公路沟时实在忍不住了,放了一个响屁,跟在他后面的一位新兵“吃吃”地笑了,笑声惊动了岗楼上的敌人。敌人立即朝下开枪,但不敢出楼追击。幸亏是黑夜,没伤着人。第二天,这个喜欢笑的新战士被关了三天禁闭反省。
烈火见真金,困难显英雄。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每个战士都经历过严峻的考验,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没有人悲观,没有人失望,而是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去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并在斗争中逐步摸清敌人的规律,找出对付敌人的办法:你来这里搜山,我就在你那里“隐蔽”,实行“换防”,打得赢就打,打不蠃时就走。
当时,在红军游击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没有枪,没有炮,
就向敌人那里要;
没有盐,没有粮,
就向敌人手中抢。
1935年除夕,黄清旺他们到和溪林中村抓土豪林福经。那天,因林福经在炮楼里过年,不敢回家,他们就将他家的猪、鸡、鸭给杀了,把牛牵走,还把他最宠爱的小老婆抓到龙岩莒州,迫使他拿300块银元来赎人。另一次是到半岭村捉土豪吕福良未遂,就将其母抓来关在山上。吕福良不得不交出300块光洋、两支驳壳枪和一些子弹,红军才让他将其母领回。
就这样,黄清旺他们在革命的熔炉中千锤百炼,成为砸不烂、拖不垮、打不散的铁军。
改编赴前线
“西安事变”后没几个月,芦沟桥上的炮声响了,全国各地的抗日浪潮汹涌澎湃。不久,闽西南党组织派人来了,说党中央已决定,为共同抗日,要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必须下山接受国民党的改编,而且要穿国民党军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黄清旺与其他指战员一样想不通:“五角星”(红军帽徽)与“十二角星”(国民党帽徽)打了10年的仗,现在要摘下“五角星”,换上“十二角星”,这不等于向反动派投降吗?这样对得起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吗?我们的血海深仇还要不要报?
上级领导在军人大会上动员说:“同志们,帽子和衣服虽然是‘白’的,但这是为了共同抗日,请大家不要计较这些形式,穿起来后,我们的心还是红的。”会场很安静,大家都好像在专心听讲,实际上脸都绷得紧紧的,没有一点儿笑容。上级领导接着说:“‘青天白日’本来是孙中山的,孙中山是革命的。改编和投降是两码事,我们现在的6个支队的领导人基本不变,只是改名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而已……”。
经过多次的宣传动员,指战员们的思想开始有所转变。可就在这时候,传来了闽南发生震惊全国的“漳浦事件”(由于下山改编缺乏经验,丧失警惕,红三团近1000名指战员在漳浦县城被国民党缴了械)。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心中炸。在这种情况下,改编工作更加难以进行了。
后来,党中央从延安派王集成和老李两同志来到金丰大山,继续动员下山改编。黄清旺一看到王集成同志也穿国民党军装,十分反感,用憎恨的眼光瞪着他,还当面骂他是“叛徒”。当时,红军一致赞成抗日,但对下山改编普遍存在三个顾虑:一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太深了,不愿与他们合作。二是怕下山改编后被他们“吃掉”,因为红军人少。三是担心留在当地的家属遭迫害。
王集成同志针对大家的思想,深入到战士中间做调查,和战士们促膝谈心,还亲自讲课,进行形势和任务的教育。他耐心地解释道:“同志们憎恨‘青天白日’是有道理的,但现在要懂得更大的道理。国民党反动派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痛苦和灾难,全国人民是会斥责他们的。而我们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和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奋战,这一切,我们的后代是会牢记在心的。今天,我们戴上国民党发的黄帽子,也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和解放……”
王集成同志再三进行动员后,就将国民党军装发给指战员们,要大家穿上。他说,想不通的等想通后再穿。许多战士领回国民党军装后,都流下了委屈的眼泪,把红五星和领章郑重地珍藏在背包里。有的同志把领回的国民党军装撕成条条当绑带、打草鞋。王集成同志指示,给撕掉的同志再补发一套。结果,补了又撕,撕了又补,直到全部穿上为止。
群众见到红军穿上了“白狗服”,不理解的也骂红军是“叛徒”、“投降派”,这对部队影响很大。因此,各支队先后出现“开小差”(不穿国民党军装,回家继续与敌人干到底)的事。黄清旺的营部特务排排长和张连长就是那时跑的。他们一跑,战士们的思想更加混乱了。
一天夜里,黄清旺和其他5个班长,边喝酒,边商量,决定离开部队,一起出去打游击,结果被发现了。因为那5个班长主张带枪出走,所以全都被公审处决了。黄清旺不同意带枪走,被停止党内生活1年和罚做苦工1个月。
经过多方面的工作,绝大多数同志转变了思想。当然也还有没想通的,但再也不敢有越轨的行为了。
不久,黄清旺他们下山改编。但吸取了“漳浦事件”的教训,分期分批进行,地点由红军选定,都是背靠大山。一部分同志下山接受改编,一部分仍留在山上警戒,使整个部队顺利地改编为两个团:三团由原一、三、七支队和岩南漳游击队合编而成,团长丘金声,副团长廖海涛。点编的人数约1000多人(大部分是动员参军的新兵)。
不久,黄清旺也随部队开赴前线,北上抗日去了。
日夜盼救星
凄风苦雨,落叶飘零。1915年秋天一个漆黑的夜里,黄清旺诞生在龙岩安康的一间破茅棚里。从此,他也和千千万万穷苦的人们一样,踏上了泥泞坎坷的人生之路。
黄清旺的老家在广东梅县,是逃难才来到安康的。家里有爷爷、奶奶、父母双亲和他。几年后,又添了3个小妹妹,全家8口人,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住的是茅棚草寮,吃的是杂粮野菜,穿的是破衣烂裤。靠爷爷和父亲给人家打长工、做短工挣来的钱养活全家。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黄清旺小时候就懂得替家庭分忧,常常帮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家乡有编竹器的习惯,他便和村里的穷孩子们一起上山砍竹子,回家劈篾条,学着编织竹篮、粪箕之类的东西。他渴望着读书,看到有钱人家的子女高高兴兴背着书包上学堂,就非常羡慕。可家里穷得都揭不开锅了,哪有钱供他读书呢。
10岁那年,他就给土豪家放牛了。有一次,牛儿在跳山沟时不慎摔伤了腿,东家知道后,把他狠命地毒打了一顿。他不敢告诉家里人,暗地里偷偷流泪。奶奶和妈妈见他被打得皮开肉绽,抱着他哭得像泪人儿。仇恨的种子,在他幼小心灵悄悄地发芽了。他默祷苍天:快长大吧,快长大吧,我要报仇!我要雪恨!
像压在大石头下面的竹笋弯弯曲曲地钻出地面,饿不死、打不烂的黄清旺,终于长成了瘦高个儿的少年。艰难的时世,苦难的童年,磨炼出他倔强的性格,为后来参加革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9年,黄清旺14岁。这年夏天,从闽西传来了朱、毛红军协助长汀人民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的消息。但只听见风闻,不见人影,谁是朱、毛?什么叫红军?一串串问号,常常萦绕着他好奇的心;共产党、苏维埃政权……一个个新名词,常听见穷人们在四下里议论。他心里很高兴,莫非世道真的要变?!穷人要出头了?!
共产党啊,你快点打过来吧!红军啊,快来救救我们吧!黄清旺盼呀盼,望穿双眼盼救星。
“三火”烧地霸
1930年的一天中午,黄清旺的村里突然来了一位40岁左右的陌生人,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脚有点儿跛,走路一拐一拐的,头戴破草帽,身穿灰长衫,背把旧纸伞,提只黑布袋,刚在村边树下一块大石头上坐着休息,便有好多收工的人围观着。黄清旺正好放牛回家,也好奇地赶去看热闹。瞧!那陌生人正在给一个长工看“相”呢,口中喃喃吟诵。黄清旺心想:哈!原来是个算命先生。哎,我的命不知好不好?何不让他给掐算掐算?跃跃欲试的他,见围观的人那么多,生怕呆久了,丢失了牛,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前次摔伤了牛腿,就被打得遍体鳞伤,这次若丢失了牛,岂不要去给阎罗王烧开水?想到这里,他不寒而栗,匆匆离开了算命先生。
第三天晚上,黄清旺去找一位小伙伴玩,又发现算命先生在他家里,屋内围着好多人,个个凝神屏息,连那平时爱笑爱闹的小伙伴,也托着下巴,蹲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听着。小伙伴见黄清旺进屋,就用手招呼他。他悄悄走过去,在小伙伴身边蹲下了。奇怪,怎么没听见算命先生念经般的吟诵呢?仔细一听,原来不是在算命,而是在“讲古”(说书)。
算命先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时不时比划着手势,讲起了《三把火的故事》。他说:“三把火就是‘三红’——红旗、红袖章、红缨枪。”啊!原来算命先生不是在“讲古”,而是在讲那些半年多前就风传各地的共产党和朱、毛红军的事迹。
这比“讲古”更好听,因为他讲到了穷人的心坎上。大家都没见过朱德和毛泽东,挺神秘的。讲到最后,“算命先生”站了起来,用低沉凝重的声调说:“三火烧地霸,穷人要当家!今后,大家要团结起来,跟土豪劣绅干,实现人人有地种,个个有饭吃……”。太好了,大家听得眉飞色舞,神采飞扬。黄清旺也高兴得差点跳起来,恨不得赶快把这好消息告诉家里人。很晚了,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被人亲昵地叫“阿拐”的“算命先生”。
那天夜里,黄清旺把这好消息告诉家人后,全家都兴奋得睡不着觉。不过,怕事的奶奶再三嘱咐他出去莫乱讲。
黄清旺躺在铺草的地板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时而想那“阿拐”叔真不简单,他真是算命先生吗?时而想,今后要怎样跟土豪劣绅们斗?能斗过他们吗?直到天快亮了,才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
几天后,“阿拐”叔走了,村里的穷人常聚在一起,议论着“三把火”。
这事被土豪劣绅们知道了,就说要追查谣言。可追查来追查去,都不知道是谁“散布”的,且又众怒难犯,也只好不了了之。
“算命先生”带来了“三把火”的火种,撒在布满干柴的安康大地上。
就地闹革命
“算命先生”走后不久,地处南靖、龙岩、漳平三县交界的永福大岭下村的穷人们,在陈庭庚、陈火铭的领导下,举行了农民武装暴动。革命烽火迅速燃遍南靖县和溪一带的乡村。红畲、坪仑……等乡村的穷苦人纷纷揭竿而起,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
黄清旺渐渐明白了,穷人要想有出头的日子,只有起来闹革命。于是,他毅然甩掉了牛鞭,参加了大岭下的农民武装暴动。那年,他才16岁。从此,他开始走了上革命的道路,参加了红军游击队。
大岭下村一带的农民武装暴动,敌人视如洪水猛兽。不久,和溪民团长林介仁、月水民团头子陈仁根、吕阿宝等带领团丁600余人,杀返大岭下村,到处烧杀掳掠。穷人又遭殃了……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谁能阻挡滚滚向前的革命洪流呢?就在这关键的时刻,闽西党组织派人来了。啊,原来是“阿拐”叔——穷人朝思暮想的“算命先生”!
“阿拐”叔到来后,立即帮助穷人们重整旗鼓,领导大家与敌人继续进行灵活的有理有节的斗争。他鼓励大家不要灰心,说:“闹革命不像吃饭那样简单,失败有什么可怕呢?有失败,才会有成功……”。
由于黄清旺参加了革命,土豪劣绅们对他家恨之人骨,把他父亲抓去吊打,迫父亲叫他回家,不要当红军。父亲说:“孩儿长大了,做爹娘的哪能管得着呢?腿长在儿子身上,他愿去哪就去哪。”敌人听了,气得暴跳如雷,把他关押在半山腰的一座山神庙里,说要等黄清旺不参加红军游击队了才要放他。黄清旺的父亲咽不下这口冤气,一天半夜,趁看守的人员不注意,便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子,爬出山神庙,爬向悬崖,咬咬牙,闭上眼,跳落深谷……
第二天早上,黄清旺的母亲得悉后,连忙叫上几个穷邻居,迎着漫天大雾,一起上山去找丈夫的尸体,最后才在峡谷里找到,发现还没有断气,但伤势很重,昏迷不醒,立即抬回家治疗。
当天夜里,黄清旺才知道这个消息。趁着夜幕的掩护,他匆匆忙忙从山上赶回家,哭跪在父亲床前。父亲抚摸着他的头说:“花鼓(黄清旺的乳名)啊,我的乖孩子,你千万不能回来,回来是会被他们抓去杀头的。如今这世道,哪有穷人的活路呢?反正豁出去了,要干,就跟共产党干到底!要替我报仇,要报仇呀!”
呆了一会儿,家里的人都催他快走,生怕他被敌人抓去。他含泪告别了亲人,黎明前又赶回游击队驻地。
第三天,黄清旺的父亲因伤势过重,与世长辞了。
黄清旺家的茅草寮被敌人烧了,年迈体衰的爷爷活活给气死,大妹妹卖给人家,换回3斗大米。无家可归了,黄清旺的母亲只好带着年老的婆婆和两个小女儿到处流浪。在讨饭的路上,婆婆也去世了。就这样,黄清旺的“家”又一次“搬迁”——从龙岩安康逃难到南靖和溪的乐土村。
此后,黄清旺便在和溪一带打游击。
乐土村当时有个为非作歹、横行乡里的大土豪,住在大土楼里,娶了两个老婆,因小老婆得宠,黄脸大老婆吃醋。为教训教训这个大土豪,并筹些粮款,黄清旺他们就利用这一矛盾,争取了那个大老婆同红军“合作”,来一个里应外合。
一天夜里,黄清旺他们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来到那大土豪家的后楼下。过了一会儿,“大老婆”就从二楼后窗口放下三条系在一起的背带(农村妇女背孩子用的长巾)。黄清旺和几个战士援“绳”攀墙,很快钻进二楼,把那些银元、布帛、谷麦等物搬取下楼。运回山上后,把所有的钱物,按三、七比例(“大老婆”三,红军七)进行分配。
接着,他们就在乐土村干开了,并在鳖坑头土纸作坊里秘密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
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扩大红军游击队的影响,1934年初夏的一天,黄清旺他们化装奇袭月水村下堀孟圩集,枪毙了罪恶累累的民团头目陈仁根。同年农历8月底,他们在毛南溪东面的虎巷岭伏击和溪民团,打死打伤民团丁多人,缴获了10多支枪和不少子弹。
林中村有个大恶棍,叫林开怀,曾任金山民团团长,与伪乡长郑锦华不和。黄清旺他们就利用这一矛盾,促使他们动刀枪“火拼”。结果,郑被杀。林就纠集同伙上山为匪,抢劫商旅,作恶多端。为集中力量对付反动民团头目林介仁,他们将林开怀抓到龙岩营州,用3个月时间教育争取他为红军办事。慑于红军游击队的声威,林开怀曾通过旧日好友,为红军采买过一批子弹,也曾为红军送过一些情报。但在1936年白色恐恢异常严重的形势下,他又“反水”了,跟林介仁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在我红军游击队里搞策反,先后拉拢游亚狮等10多人,向国民党自首,还在我基点村和游击区内捕杀红军、游击队和工作团的干部、战士多人。这个反动家伙,解放后被我人民政府镇压了。
攻打上杭战
1935年,黄清旺从闽西南教导队分配到永定四支队当班长,参加了攻打上杭的战斗。
素有“铜赣州,铁上杭”之称的上杭城,座落在汀江畔,城东是几丈宽的深沟,城西有口大池塘,城北高山陡立,只有城南是开阔的平原地带,但敌人封锁得很严密,筑有四道铁蒺藜,每道相隔两米左右。城内守敌有一个师的兵力,而攻城的红军只有两个团,况且武器装备等方面都不如敌人。在这种情况下,要攻破这个固若金汤的城池有很大的困难。
攻城之前,团首长叫大家开动脑筋想办法,要从哪个方向攻城,怎样攻?黄清旺微闭着眼睛琢磨着:城东嘛,不行;城西呢,也不行;城北呢,更不行。忽然,他眼睛一亮:“城南,城南!开阔地,便于冲锋……”可一想到那四道铁蒺藜,眼光就立即暗淡下来,铁蒺藜呵,铁蒺藜,你比大山更棘手,我宁可翻越四座大山,也不愿去攀越这四道铁蒺藜。他甚至天真地想,要是没有这铁蒺藜,那该多好啊。
后来,有几位同志想起了《东周列国志》里田单大摆“火牛阵”的故事,便建议古为今用,也来摆一摆“火牛阵”,向城南“开刀”。团部研究后,决定沿用古代这一战术。
太阳快下山了,晚霞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把汀江水映得通红。晚饭后,战士们分头到附近村庄里去,把土豪劣绅家的水牛全都给牵来。牛尾巴给缠上破布,蘸上煤油,并拴上鞭炮,牵到冲锋出发地。每人负责一头牛。
夜深了,上杭城沉睡在茫茫月色中,满天星斗,眨着焦急盼望的眼睛:红军啊,快点儿攻城吧!
突然,军号悠扬,划破夜的宁静,团首长一声令下,大家一齐点燃牛尾巴上拴着的鞭炮和蘸有煤油的破布。顿时,“噼哩叭啦、噼哩叭啦……”鞭炮响了,声震遐迩;牛尾巴燃烧了,火光烛天。那些水牛,自出娘胎,从未经历过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因此,一头头像着了魔,怒目圆睁,狠命往前飞奔……
“火牛”怒吼奔腾,排山倒海,第一道铁蒺藜被冲开踩倒了,紧接着,第二道、第三道……。迅猛异常的“火牛”终于冲破重重封锁线。精神抖擞的战士们跟在“火牛”后面,在一片喊杀声中持枪前进。
刚从酣梦中醒过来的敌人给吓懵了——莫非恶贯满盈,玉皇上帝发怒,派遣天兵天将,驾着火龙讨逆来了?
敌人开枪扫射了。密集的子弹,像蝗虫般猛扫过来,可怜终身劳碌的水牛——红军的“开路先锋”,一头头倒在血泊之中。红军虽然伤亡不少,但战士们仍然斗志昂扬,前仆后继,奋勇向前。眼看就要打到城门下了,敌人见势不妙,立即关闭城门,龟缩城内负隅顽抗。因城坚敌众,没攻下城池。但敌人被红军顽强的斗志给吓破了胆,紧闭城门十来天不敢露面。
困难显英雄
在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敌人采用各种残酷手段,妄图迫使红军、游击队投降,他们封山断路,逐山搜剿,使红军、游击队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这期间,虽然红军、游击队有时也下山打土豪,筹款粮,但绝大部分时间在山上打游击。没有粮食,就挖野菜、竹笋充饥。最难受的就是没盐吃,同志们大都脸色浮肿,四肢无力,患夜盲症的极多。不仅如此,每天还得行军打仗。如碰上雨季,那就更糟糕了,因为没有山洞,搭茅棚又容易被搜山的敌人发现,因此,晚上宿营,只能头、背、脚各垫上一块石头当床铺,用雨伞盖身子,那滋味是够呛的。就连这样的“雨中觉”都睡不安稳,一发现敌情,就得立即起“床”,投入战斗。有时雨夜行军,泥泞山道,又陡又滑,一夜走不到10里路。起初,黄清旺他们都拄着拐杖行军,敌人常常顺着那深深的拐杖痕迹跟踪追击,后来只好把拐杖也扔了。
一天夜里,黄清旺与战友们一起穿越龙岩新祠——适中之间的一段土路,要去抓土豪。他们蹑手蹑脚,连大气都不敢出,悄悄绕过碉堡群时,有一个战士(文书)在跳公路沟时实在忍不住了,放了一个响屁,跟在他后面的一位新兵“吃吃”地笑了,笑声惊动了岗楼上的敌人。敌人立即朝下开枪,但不敢出楼追击。幸亏是黑夜,没伤着人。第二天,这个喜欢笑的新战士被关了三天禁闭反省。
烈火见真金,困难显英雄。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每个战士都经历过严峻的考验,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没有人悲观,没有人失望,而是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去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并在斗争中逐步摸清敌人的规律,找出对付敌人的办法:你来这里搜山,我就在你那里“隐蔽”,实行“换防”,打得赢就打,打不蠃时就走。
当时,在红军游击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没有枪,没有炮,
就向敌人那里要;
没有盐,没有粮,
就向敌人手中抢。
1935年除夕,黄清旺他们到和溪林中村抓土豪林福经。那天,因林福经在炮楼里过年,不敢回家,他们就将他家的猪、鸡、鸭给杀了,把牛牵走,还把他最宠爱的小老婆抓到龙岩莒州,迫使他拿300块银元来赎人。另一次是到半岭村捉土豪吕福良未遂,就将其母抓来关在山上。吕福良不得不交出300块光洋、两支驳壳枪和一些子弹,红军才让他将其母领回。
就这样,黄清旺他们在革命的熔炉中千锤百炼,成为砸不烂、拖不垮、打不散的铁军。
改编赴前线
“西安事变”后没几个月,芦沟桥上的炮声响了,全国各地的抗日浪潮汹涌澎湃。不久,闽西南党组织派人来了,说党中央已决定,为共同抗日,要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红军必须下山接受国民党的改编,而且要穿国民党军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黄清旺与其他指战员一样想不通:“五角星”(红军帽徽)与“十二角星”(国民党帽徽)打了10年的仗,现在要摘下“五角星”,换上“十二角星”,这不等于向反动派投降吗?这样对得起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吗?我们的血海深仇还要不要报?
上级领导在军人大会上动员说:“同志们,帽子和衣服虽然是‘白’的,但这是为了共同抗日,请大家不要计较这些形式,穿起来后,我们的心还是红的。”会场很安静,大家都好像在专心听讲,实际上脸都绷得紧紧的,没有一点儿笑容。上级领导接着说:“‘青天白日’本来是孙中山的,孙中山是革命的。改编和投降是两码事,我们现在的6个支队的领导人基本不变,只是改名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而已……”。
经过多次的宣传动员,指战员们的思想开始有所转变。可就在这时候,传来了闽南发生震惊全国的“漳浦事件”(由于下山改编缺乏经验,丧失警惕,红三团近1000名指战员在漳浦县城被国民党缴了械)。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心中炸。在这种情况下,改编工作更加难以进行了。
后来,党中央从延安派王集成和老李两同志来到金丰大山,继续动员下山改编。黄清旺一看到王集成同志也穿国民党军装,十分反感,用憎恨的眼光瞪着他,还当面骂他是“叛徒”。当时,红军一致赞成抗日,但对下山改编普遍存在三个顾虑:一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太深了,不愿与他们合作。二是怕下山改编后被他们“吃掉”,因为红军人少。三是担心留在当地的家属遭迫害。
王集成同志针对大家的思想,深入到战士中间做调查,和战士们促膝谈心,还亲自讲课,进行形势和任务的教育。他耐心地解释道:“同志们憎恨‘青天白日’是有道理的,但现在要懂得更大的道理。国民党反动派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痛苦和灾难,全国人民是会斥责他们的。而我们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和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奋战,这一切,我们的后代是会牢记在心的。今天,我们戴上国民党发的黄帽子,也是为了抗日救国,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和解放……”
王集成同志再三进行动员后,就将国民党军装发给指战员们,要大家穿上。他说,想不通的等想通后再穿。许多战士领回国民党军装后,都流下了委屈的眼泪,把红五星和领章郑重地珍藏在背包里。有的同志把领回的国民党军装撕成条条当绑带、打草鞋。王集成同志指示,给撕掉的同志再补发一套。结果,补了又撕,撕了又补,直到全部穿上为止。
群众见到红军穿上了“白狗服”,不理解的也骂红军是“叛徒”、“投降派”,这对部队影响很大。因此,各支队先后出现“开小差”(不穿国民党军装,回家继续与敌人干到底)的事。黄清旺的营部特务排排长和张连长就是那时跑的。他们一跑,战士们的思想更加混乱了。
一天夜里,黄清旺和其他5个班长,边喝酒,边商量,决定离开部队,一起出去打游击,结果被发现了。因为那5个班长主张带枪出走,所以全都被公审处决了。黄清旺不同意带枪走,被停止党内生活1年和罚做苦工1个月。
经过多方面的工作,绝大多数同志转变了思想。当然也还有没想通的,但再也不敢有越轨的行为了。
不久,黄清旺他们下山改编。但吸取了“漳浦事件”的教训,分期分批进行,地点由红军选定,都是背靠大山。一部分同志下山接受改编,一部分仍留在山上警戒,使整个部队顺利地改编为两个团:三团由原一、三、七支队和岩南漳游击队合编而成,团长丘金声,副团长廖海涛。点编的人数约1000多人(大部分是动员参军的新兵)。
不久,黄清旺也随部队开赴前线,北上抗日去了。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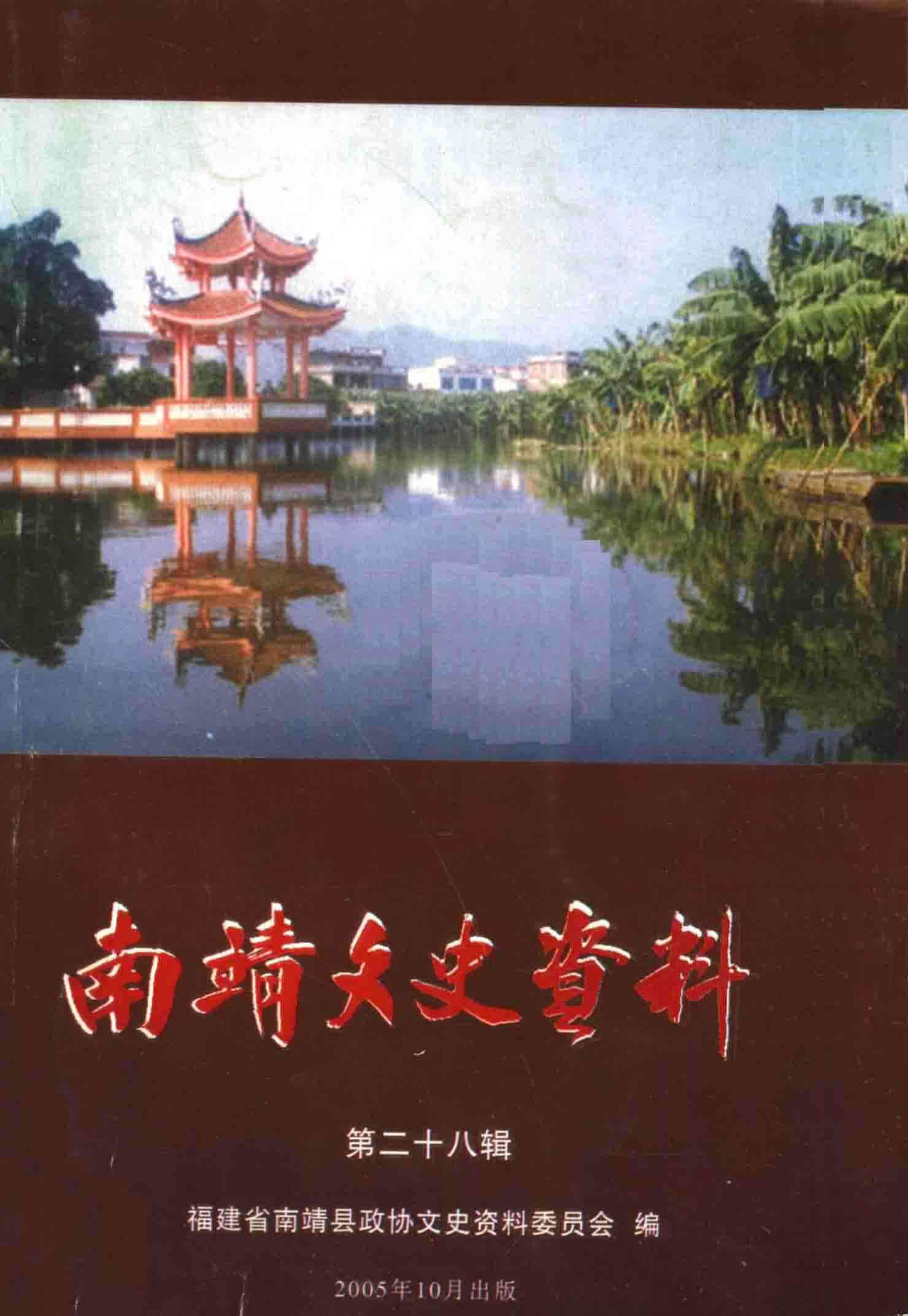
相关人物
辛柳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