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
在没有梅花的地方安家落户
1970年,毛泽东主席一声令下,全国无数机关干部纷纷下放农村,进行“重新学习”。当年,下放到南靖的省直机关干部数以千计,每个大队都分配到好儿位——不,更确切地说,是好几家,因为每位下放干部都是扶老携幼,拖儿带女来这里安家落户的。
当年,我只有28岁,是福建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一位年轻助教,但也同样逃脱不了举家下放的命运。说是“举家”,其实只有我和我妻子汪兰两口子。另外还有一位,不知是男是女,还没出生呢!
到县里报到时,我指了指妻子隆起的肚子,请求能照顾到一个有公路、能通汽车的地方,以便于不久后分娩。大概是我们的要求不高吧?负责接待的县革委会工作人员当即满口答应,大笔一挥,就把我俩安排去了梅林公社——我在璞山大队任工作组副组长,汪兰则到隔壁坎下大队的“南靖县长教小学”初中班任教。
我们在位于猪圈前面的县招待所住了一夜。查了查随身携带的地图,这才发现,梅林是全县最边远的公社,与龙岩县的适中、永定县的苦竹交界,从县城进去,要翻越一座天岭——这座与新疆天山同名的山,想必也是颇有点高度的了。虽然也通公路也通汽车,但我还是担心妻子分娩的事,毕竟,山高路远,人生地不熟,我们又是要初为人父,初为人母。
倒还是汪兰勇敢,她劝慰我道:“山里人祖祖辈辈都生得下孩子,我就不信我们会生不下来!”是啊,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但愿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难题。
于是,我转念琢磨起地名来:梅林,这名字颇有诗意,想必是个梅花盛开的地方。陆游不是有诗句叫“一树梅花一放翁”吗?作为下放干部,这“放”字于我颇为相宜,只是我才28岁,还不到称“翁”的年龄。至于“南靖县长教小学”,这名字有点怪怪的,明明是坎下村,何以称“长教”呢?是意味着妻子要长期在此执教吗?还有,如果念成“南靖县长——教小学”,岂不十分有趣?
胡思乱想过后,天就亮了。我们坐上每天唯一的一趟班车,进山去也。
经过坑坑洼洼的南坑和没有船只的船场,翻过九曲十八盘的天岭,穿过勉强可称之为山间小盆地的书洋,终于到了坎下停车点。举目四望,没见到一棵梅树,一朵梅花,倒见不少或方或圆的客家土楼,像一个个巨大的句号,在我心中引出了无数问号和惊叹号。
看得出,这里很穷,所谓“南靖县长”教的小学——南靖县长教小学,只有两排平屋,墙上没有粉刷,地上没有铺砖,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好在教师宿舍却是小溪边的一幢双层砖楼。好在我们的行李并不多,只有两袋衣被,外加四只“飞马”牌香烟纸箱,里头装的全是书,“孔夫子搬家——尽是书”么!我们在楼下一小间安了家,推窗一望,一群白鹅正在潺潺流动的溪水中嘎嘎欢叫,这场景,一下子就让人高兴起来,因为我们想起了骆宾王的名诗:
“鹅,鹅,曲颈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唯一让人遗憾的是,溪边无处寻觅梅花的芳踪。好在有一棵常青的大榕树,还有一棵梨树,与我们朝夕相伴。
此后,我每天一早到璞山大队上班,无非是催收、催种、催征粮之类,有时也在所谓“政治夜校”里教唱歌——当然,都是斗志昂扬的“毛主席语录”歌。而汪兰,则一边教书,一边静静地等待孩子的出生。没有医院作产前体检,我们只能反复钻研随身带来的一本《农村医生手册》。临产期快到了,发现她脚上浮肿,我就每天早晚扶着她在溪边散步。
初为人父人母
两个多月之后,随着山中的枫叶纷纷落地,我的女儿也哇哇坠地了。
她的诞生,比我想象中的要复杂许多。
时值冬天,山间自然严寒,夜间犹甚。我虽然准备了炉子和木炭,早早就燃起了炭火,但到最关键时候,即女儿哇哇坠地的下半夜,手忙脚乱之际,忘了添炭,炉火熄灭了。可怜我的女儿,刚出生的那一时刻,便尝到了人间的寒冷。此其一。
其二,因为距公社保健院很远,我们便把产房设在自己的宿舍里。没有正规的助产士,只有一位邻居大嫂,据说曾到公社保健院培训过一段时间,便成了我们唯一能请来的土接生员。她的唯一工具,只有一把剪刀,外加一盏消毒用的酒精灯。偏偏我的女儿又是“脐带绕颈”——属于难产的一种。她大概也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吧?好不容易把女儿接了下来,就一把递给我,气喘吁吁地说:
“现在,我只能照顾大入了,这小孩,就交给你处理吧!”
当时,在产房里的,只有我,外加从家乡莆田赶来帮忙的我的小妹妹青青。我们兄妹俩只好用土制的草纸,把红通通、皱巴巴、粘糊糊的婴儿擦了擦,再用小毛巾毯子把她围了起来。她倒也很勇敢,哭了几声,就眯着眼睛、嘟着小嘴寻找起她母亲的奶头来。等她安静下来,窗户也就微微露出了一抹鱼肚白——天快亮了。于是,我们这才分身重新把炉火燃点起来。
第二天中午,我抽了个空,亲自翻山越岭跑到公社邮局,给远在莆田老家的亲人们拍了个电报。为节省时间和邮费,我只用了最简单的四个字:“母女平安。”
万万没想到,这封四字电报传到莆田乡下邮局时,又被漏译了一个字,变成了“母平安。”害得我那年迈的祖母,也就是我女儿的曾祖母,以为电报里不提生男还是生女,肯定是事出有因,母亲还平安,而其他已不存在了,为此,她老人家和全家亲人哭了好多天,直到收到我后来的一封信,才真相大白,破涕为笑。
不过,在梅林地区生孩做月子,也有好处:这里山青水秀,空气好,东西也很便宜,记得一颗鸡蛋才几分钱,一串溪鱼才几角钱,鸡、鸭、鹅肉每斤也只有两三元钱,母女俩及全家的营养倒也丰富,入乡随俗,汪兰还以米酒当水喝呢!在全国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我们的小女儿就这样静悄悄地在山间健康成长。
为女儿取名时,我想到此地四面环山,开门见山,出门爬山,山外还有万重山,便忽发奇想,索性把她取名为“陈山”好了。但妻子不同意,嫌这名字有点男性化,就按谐音正式定名为“陈珊”——海中的珊瑚,红艳艳的,倒适合做女孩子的名字,当然,也更符合当年见红大吉的革命色彩。
女儿的第一张照片
1971年的春节,就在与女儿的逗笑声中快乐地度过了。
不知不觉间,她已经两个半月了。应该为她照一张相了,好留个珍贵的纪念,同时,也寄回家乡,以告慰那些她尚未见过面并一直挂念她的亲人们。
可是,到哪儿去照相呢?这在今天城乡,简直易如反掌的一件区区小事,在当年,在穷乡僻壤,简直成为一种奢望。是啊,面对重重叠叠的大山,我们到哪里寻找照相馆呢?
幸好,一位邻居来告:隔邻公社书洋的圩场上,常有一个永定人过来照相。山间圩市,按传统惯例,是五天一圩,如今“学大寨”,已改为十天一次了。捱到了圩日那天,我和妻子把女儿精心打扮了一番,便轮番抱着她走了二十里路,终于到了那个巴掌大的圩场。
那年头,正在搞“以粮为纲”,圩场上只零零散散地摆着一些鸡鸭鹅兔之类的活物、泥鳅田螺之类的野物和锅瓢碗盏之类的杂物。倘若没有那头穿山甲吸引了一大圈围观者,这圩场简直没有一点活力。我们耐着性子在场子里穿了几个来回,却始终不见那位可爱的摄影师。
问圩尾卖甘蔗的一位老头,他长叹一声,低声道:
“砸了,全砸了,镜头全砸了,上一圩,他被戴红袖圈的人说是外流人员,赶走了,镜头也砸了!”
大概是我们失望的表情让他同情,老人递过来两截甘蔗,安慰道:
“要照相,到县城去吧,那里的人民照相馆,是有执照的!”
可是,从这里至县城,要翻越九曲十八盘的天岭,每天只发一班车,还得在县城住宿,谈何容易!
我们只得抱着女儿,怏怏而归。
天无绝人之路。不久,县里要开大会,突然记起了我这个隐居山里的秀才,通知我去帮忙整理材料。既然我的旅差费可以报销,那么,何不携妻女同至县城照一张相?
主意打定,说走就走,我们便提前一天搭上了那一趟唯一的班车,在九曲十八盘的天岭上颠簸了一个上午,总算安抵县城。
急急忙忙赶到县城唯一的那家人民照相馆,抬头一看,全傻了,紧闭的大门口贴着一张告示,告示上先引了一段“最高指示”,接着赫然写道:
“因革命需要,本馆暂停营业十天。”
我的天,难道我这大半天汽车白坐了?我和我妻子抱着女儿挤进县城唯一的一家照常营业的饭店,胡乱喝了一碗面汤,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那年,我毕竟血气方刚,很快便下了决心:
“走,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到漳州照相去!”
从县城到漳州,不足一百里,抓紧时间,一个下午还可以来回呢!
于是,我们又急匆匆折回汽车站。不料,一趟班车刚走,下一趟还得再等两个钟头。
“算了,有什么车坐什么车,分段走,走一步算一步!”
我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带上妻女,不顾一切地跳上了一辆刚要开动的客车,坐到了与漳州市郊毗邻的靖城。但靖城开往漳州的班车又已开走,我便出高价雇了一辆脚踏三轮车,让蹬车的师傅紧蹬着往漳州而去……
北风卷起九龙江岸因“改天换地”而到处堆积的黄沙黄土,漫漫黄尘肆无忌惮地朝我们心上,脸上,身上摔打而来。我紧紧抱着因哭累而睡熟的女儿,咬紧牙关,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
“为了让女儿照一张相,全豁出去吧!”
好不容易进了漳州,先到汽车站买了返程的最后一班车的车票,屈指一算,所剩下的时间只有十五分钟了。于是,我们又坐上三轮车,奔向最近的一家照相馆。一进门,我便大喊:
“同志,我们赶了两百多里路,给孩子照张相,只剩下十分钟了,请,请赶快!”
摄影师看见我们风尘仆仆的样子,十分同情,立即就摆开了拍摄的架势。于是,女儿坐在前头的椅轿上,我和妻子并肩站在她的背后……
就在摄影师对准我们的那几分钟,我像一位在茫茫大沙漠上经过长途跋涉之后,突然发现绿洲的旅人那样,所有的奔波、辛劳、失望、焦虑和气愤,一下子像大山一样压了下来,一种过度紧张之后突然的松弛,使我感到一阵晕眩,于是,我不由自主地合上了眼皮……
“咔嚓”一声,摄影师已按动了快门。
半个月之后,这张花费了我将近半个月工资的相片,女儿的第一张相片,终于寄到了我们的手中。
然而,照片中的妻子,勉强笑着,笑得有点凄清。我呢,风尘仆仆,一脸疲惫不堪的角色,更可笑的是,我的两眼仅微微睁开一条缝,似乎正在打瞌睡。只有女儿什么都不懂,她坐在椅轿上,一边吐着舌头,一边睁大明亮的眼睛,惊奇地盯着这个新鲜而又陌生的世界。
这,就是我女儿出生后的第一张照片,一张唯一的,任何摄影大师用任何特技都无法重拍的第一张相片。
在荒唐的岁月,这只是一件荒唐的小事。睁一眼,闭一眼,也许正是当年我最真实的写照吧!
创办梅林中学
春耕以后,公社任命我为工作组组长,到九龙坡创办梅林中学。于是,我把女儿交给妻子和妹妹,只身翻山越岭到公社报到,从此揭开了人生道路上粉笔生涯的短暂一幕。
所谓九岭坡,是九座蜿蜒起伏的荒山坡,前不靠村,后不靠店,面对清溪,背临深谷,有人曾看见在茅草窝里,有华南虎的尾巴像色彩斑斓的旗杆高高翘起,但这仅仅只是传说而已。有一次,我倒亲眼目睹过溪对岸的红色狐狸,像一团燃烧的火苗流星般地窜了过去。
当时,九龙坡的荒山坡上,只有几排废弃不用的战备兵营,门窗洞开,如同老人们张开没牙的大嘴。但客家人富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也许是穷怕了,办学的热情特别高涨,报名的学生多达200多人,其中有的年龄比我还大,个子比我还高。为了不辜负乡亲们的厚爱和重托,我们几位工作组组员(清一色的下放干部),连同当地调来的几位公办和民办教师,便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开学前的准备工作。好在公社很慷慨,给了一面国旗,两个热水瓶,六盏煤油灯,外加几千斤木薯苗。至于门窗、黑板、桌椅、床架等木料,用多少取多少,一律免费,反正山区有的是。
办学首先要有个校名牌,于是,我从领袖的诗词墨宝里找出了四个字:
梅——梅花欢喜漫天雪;
林——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中——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学——不可沽名学霸王。
我努力仿照伟人的笔体,用红油漆在白色的校牌上书写了“梅林中学”四个大字,围观的群众全都热烈地鼓起掌来,庆贺本乡本土第一所中学的庄严诞生。
尽管预订的课本迟迟没有运来,但五星红旗已插上九龙坡顶,学校于9月1日正式开学。没有鼓乐喧天鞭炮雷鸣,也没花环彩带鸽子放飞直上蓝天,总之,没有任何庆典仪式,因为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下列周程表:
第一周修补校舍
第二周抢种木薯
第三周挖山开辟小操场
第四周请科岭老红军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到了第五周,课本还没到,怎么办?工作组连同全校公办、民办教师紧急开会研讨对策,大家遵照“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最高指示,决定自编乡土教材,先教给学生一些农村里最实用的知识。好在公社又及时支援了钢板蜡纸,好在下放干部中不缺各方面的专业人才,于是,我编出了《农村应用文12例》;原农学院助教开讲《水稻病虫害防治》;原中医学院助教带领学生上山辨识采集中草药。还有一位女同志是原部队文工团的团员,她便给大家教唱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后来,还排练出《赴宴斗鸠山》的选段,在公社礼堂里演出呢!我在剧中还粉墨登场,扮演了李玉和这一角色,吊起嗓子,唱起了“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遥想此生,我曾写过剧本,演过话剧,但作为京剧的票友,这还是第一次,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当年我们这些人,说不清是干部,是教师,还是农民?我们的学校,也说不清是小学,是中学,还是半耕半读的农业职业中学?反正,对于一张白纸来说,能描上的都是美丽的画图,对于求知若渴、饥不择食的心田来说,能播下的全是希望的种子……
终于盼来了正式的课本,我们一个个全都已经瘦了一圈,因而,每一双眼睛全都显得特别大,特别圆鼓鼓的。
火的圣浴
在人生的漫漫长途中,坎坷、泥泞、风霜、雨雪,乃至于种种突如其来的灾祸,全都在所难免。
危难之际,能伸出友谊之手拉你一把,让你挣脱死神纠缠的人,有的是你素昧平生、根本不认识的人,只不过你遇险时,他恰巧路过,顺手拉了你一把,延续了你的宝贵生命;有的,则是你周围普普通通的人,平时,他毫不起眼,你未必注意他,看重他,然而,正是他,在千钧一发之际,成为你的救命恩人。
在九龙坡办学的岁月中,我就曾经经历过一场火的圣浴。
那天中午,后山的森林里突然冒出了滚滚浓烟,紧接着,熊熊的火苗窜上了树梢,燥热的气流连同焦味旋即卷了过来,学生们惊叫着,整个校园都在震颤。按照当年最流行的一句口号:“火光就是命令”,全校师生立即组织起来,分头上山扑火。我也带领一支队伍,冲上山去。平日里甚觉崎岖的小路、丛生的荆棘这时全不在话下,我们很快便赶到了着火的地点。
但这对于我来说,毕竟是平生第一次,毫无经验。好在山区的学生个个训练有素,他们用砍刀砍下带叶的松枝,分给我一枝,要我跟他们在顺风处站成一排,一起往前扑打。
山峦起伏,地形复杂,浓烟遮断了视线,火舌像毒蛇般乱窜,阵阵热浪席卷而来。我们且扑且进,当发现正身处一个深井似的山谷时,身边只剩下七八位学生,与大队人马已无法再联系了。
热风在山谷中回旋,时而东来,时而西来,顺风、逆风?此时此地,已难以判断。一棵本已烧焦的大树突然从树梢处爆出大火球来,顿时,火星、火花、火箭四处进溅,落地后又引发出无数新的火蛇乱钻乱窜。山谷底部全是易燃的茅草,我们随时都可能陷入烈火的包围圈,情况十分危急!
有经验的学生们纷纷建议突围。
可是,往哪个方向突围?往东还是往西,往上不是往下?这可是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烟熏火燎中众说纷纭,我也一时没了主意。
突然,一位细高个子的学生大喊一声:“老师,不能再拖了,赶紧先往上跑,高处才能看清方向!”
于是,他马上成为我们的领袖,大家都听从他的指挥往上突围。
不料,殿后的我却一个趔趄,掉进了一个深坑。又是他,及时回头发现了,他马上过来,伸出细长的手臂,用力把我拉了上去。
好不容易上了坡,从高处回头一看,好险!刚才我们所处的山谷底部,已是一片熊熊的火海……
人不可貌相。这位细高个的学生平时在班上毫不出众。一篇《寻牛启事》的短短应用文错了八个字。课堂上提问到他时,他双眼老盯着桌上的铅笔盒,脸涨得通红。路遇老师,他也不懂得招呼,只是腼腆地闪在一旁憨笑。而正是他,细长的身影在火海中站成一棵擎天大树。
他,不仅仅是我的救命恩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我的老师,他在火海中的那一声吆喝:“高处才能看清方向”,正是我一生中,时时处处都应该遵遁的人生格言。
1971年11月,我在梅林中学工作还不满一个学期,县革委会来了一纸调令,要我到县报道组去当一名“土记者”。为此,我不得不一步一回头地告别九龙坡,告别那些可爱的山区孩子,告别与我历尽艰辛共同创办梅林中学的战友们。翌年3月,妻子汪兰也调进南靖一中任教。于是,我们举家告别梅林,从内山迁往山城,又在南靖翻开了我们下放生涯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篇章。
作者附记:2000年,我和汪兰重返阔别了30年的梅林。我们高兴地看到,当年的长教学校和梅林中学都盖起了许多新校舍,山区的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与往昔已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还到当年女儿出生的那幢双层楼旧地重游,溪边的老榕树依然枝青叶茂,郁郁苍苍,让人为之眷恋不己。我们特地在树下摄影留念,并把照片寄往美国,让已在美国定居的女儿也能一睹她出生时的场景。人的一生,有可能走遍天涯海角,浪迹异国它邦,但有些地方是永远也不应该忘记的,比如她的家乡,她的出生地,连同她的祖国。因为这是她的根,她的摇篮血地,她的生命的起点,也是支撑她精神的一根强大支柱。
1970年,毛泽东主席一声令下,全国无数机关干部纷纷下放农村,进行“重新学习”。当年,下放到南靖的省直机关干部数以千计,每个大队都分配到好儿位——不,更确切地说,是好几家,因为每位下放干部都是扶老携幼,拖儿带女来这里安家落户的。
当年,我只有28岁,是福建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的一位年轻助教,但也同样逃脱不了举家下放的命运。说是“举家”,其实只有我和我妻子汪兰两口子。另外还有一位,不知是男是女,还没出生呢!
到县里报到时,我指了指妻子隆起的肚子,请求能照顾到一个有公路、能通汽车的地方,以便于不久后分娩。大概是我们的要求不高吧?负责接待的县革委会工作人员当即满口答应,大笔一挥,就把我俩安排去了梅林公社——我在璞山大队任工作组副组长,汪兰则到隔壁坎下大队的“南靖县长教小学”初中班任教。
我们在位于猪圈前面的县招待所住了一夜。查了查随身携带的地图,这才发现,梅林是全县最边远的公社,与龙岩县的适中、永定县的苦竹交界,从县城进去,要翻越一座天岭——这座与新疆天山同名的山,想必也是颇有点高度的了。虽然也通公路也通汽车,但我还是担心妻子分娩的事,毕竟,山高路远,人生地不熟,我们又是要初为人父,初为人母。
倒还是汪兰勇敢,她劝慰我道:“山里人祖祖辈辈都生得下孩子,我就不信我们会生不下来!”是啊,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但愿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难题。
于是,我转念琢磨起地名来:梅林,这名字颇有诗意,想必是个梅花盛开的地方。陆游不是有诗句叫“一树梅花一放翁”吗?作为下放干部,这“放”字于我颇为相宜,只是我才28岁,还不到称“翁”的年龄。至于“南靖县长教小学”,这名字有点怪怪的,明明是坎下村,何以称“长教”呢?是意味着妻子要长期在此执教吗?还有,如果念成“南靖县长——教小学”,岂不十分有趣?
胡思乱想过后,天就亮了。我们坐上每天唯一的一趟班车,进山去也。
经过坑坑洼洼的南坑和没有船只的船场,翻过九曲十八盘的天岭,穿过勉强可称之为山间小盆地的书洋,终于到了坎下停车点。举目四望,没见到一棵梅树,一朵梅花,倒见不少或方或圆的客家土楼,像一个个巨大的句号,在我心中引出了无数问号和惊叹号。
看得出,这里很穷,所谓“南靖县长”教的小学——南靖县长教小学,只有两排平屋,墙上没有粉刷,地上没有铺砖,一副灰头土脸的样子。好在教师宿舍却是小溪边的一幢双层砖楼。好在我们的行李并不多,只有两袋衣被,外加四只“飞马”牌香烟纸箱,里头装的全是书,“孔夫子搬家——尽是书”么!我们在楼下一小间安了家,推窗一望,一群白鹅正在潺潺流动的溪水中嘎嘎欢叫,这场景,一下子就让人高兴起来,因为我们想起了骆宾王的名诗:
“鹅,鹅,曲颈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唯一让人遗憾的是,溪边无处寻觅梅花的芳踪。好在有一棵常青的大榕树,还有一棵梨树,与我们朝夕相伴。
此后,我每天一早到璞山大队上班,无非是催收、催种、催征粮之类,有时也在所谓“政治夜校”里教唱歌——当然,都是斗志昂扬的“毛主席语录”歌。而汪兰,则一边教书,一边静静地等待孩子的出生。没有医院作产前体检,我们只能反复钻研随身带来的一本《农村医生手册》。临产期快到了,发现她脚上浮肿,我就每天早晚扶着她在溪边散步。
初为人父人母
两个多月之后,随着山中的枫叶纷纷落地,我的女儿也哇哇坠地了。
她的诞生,比我想象中的要复杂许多。
时值冬天,山间自然严寒,夜间犹甚。我虽然准备了炉子和木炭,早早就燃起了炭火,但到最关键时候,即女儿哇哇坠地的下半夜,手忙脚乱之际,忘了添炭,炉火熄灭了。可怜我的女儿,刚出生的那一时刻,便尝到了人间的寒冷。此其一。
其二,因为距公社保健院很远,我们便把产房设在自己的宿舍里。没有正规的助产士,只有一位邻居大嫂,据说曾到公社保健院培训过一段时间,便成了我们唯一能请来的土接生员。她的唯一工具,只有一把剪刀,外加一盏消毒用的酒精灯。偏偏我的女儿又是“脐带绕颈”——属于难产的一种。她大概也很少遇到这种情况吧?好不容易把女儿接了下来,就一把递给我,气喘吁吁地说:
“现在,我只能照顾大入了,这小孩,就交给你处理吧!”
当时,在产房里的,只有我,外加从家乡莆田赶来帮忙的我的小妹妹青青。我们兄妹俩只好用土制的草纸,把红通通、皱巴巴、粘糊糊的婴儿擦了擦,再用小毛巾毯子把她围了起来。她倒也很勇敢,哭了几声,就眯着眼睛、嘟着小嘴寻找起她母亲的奶头来。等她安静下来,窗户也就微微露出了一抹鱼肚白——天快亮了。于是,我们这才分身重新把炉火燃点起来。
第二天中午,我抽了个空,亲自翻山越岭跑到公社邮局,给远在莆田老家的亲人们拍了个电报。为节省时间和邮费,我只用了最简单的四个字:“母女平安。”
万万没想到,这封四字电报传到莆田乡下邮局时,又被漏译了一个字,变成了“母平安。”害得我那年迈的祖母,也就是我女儿的曾祖母,以为电报里不提生男还是生女,肯定是事出有因,母亲还平安,而其他已不存在了,为此,她老人家和全家亲人哭了好多天,直到收到我后来的一封信,才真相大白,破涕为笑。
不过,在梅林地区生孩做月子,也有好处:这里山青水秀,空气好,东西也很便宜,记得一颗鸡蛋才几分钱,一串溪鱼才几角钱,鸡、鸭、鹅肉每斤也只有两三元钱,母女俩及全家的营养倒也丰富,入乡随俗,汪兰还以米酒当水喝呢!在全国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我们的小女儿就这样静悄悄地在山间健康成长。
为女儿取名时,我想到此地四面环山,开门见山,出门爬山,山外还有万重山,便忽发奇想,索性把她取名为“陈山”好了。但妻子不同意,嫌这名字有点男性化,就按谐音正式定名为“陈珊”——海中的珊瑚,红艳艳的,倒适合做女孩子的名字,当然,也更符合当年见红大吉的革命色彩。
女儿的第一张照片
1971年的春节,就在与女儿的逗笑声中快乐地度过了。
不知不觉间,她已经两个半月了。应该为她照一张相了,好留个珍贵的纪念,同时,也寄回家乡,以告慰那些她尚未见过面并一直挂念她的亲人们。
可是,到哪儿去照相呢?这在今天城乡,简直易如反掌的一件区区小事,在当年,在穷乡僻壤,简直成为一种奢望。是啊,面对重重叠叠的大山,我们到哪里寻找照相馆呢?
幸好,一位邻居来告:隔邻公社书洋的圩场上,常有一个永定人过来照相。山间圩市,按传统惯例,是五天一圩,如今“学大寨”,已改为十天一次了。捱到了圩日那天,我和妻子把女儿精心打扮了一番,便轮番抱着她走了二十里路,终于到了那个巴掌大的圩场。
那年头,正在搞“以粮为纲”,圩场上只零零散散地摆着一些鸡鸭鹅兔之类的活物、泥鳅田螺之类的野物和锅瓢碗盏之类的杂物。倘若没有那头穿山甲吸引了一大圈围观者,这圩场简直没有一点活力。我们耐着性子在场子里穿了几个来回,却始终不见那位可爱的摄影师。
问圩尾卖甘蔗的一位老头,他长叹一声,低声道:
“砸了,全砸了,镜头全砸了,上一圩,他被戴红袖圈的人说是外流人员,赶走了,镜头也砸了!”
大概是我们失望的表情让他同情,老人递过来两截甘蔗,安慰道:
“要照相,到县城去吧,那里的人民照相馆,是有执照的!”
可是,从这里至县城,要翻越九曲十八盘的天岭,每天只发一班车,还得在县城住宿,谈何容易!
我们只得抱着女儿,怏怏而归。
天无绝人之路。不久,县里要开大会,突然记起了我这个隐居山里的秀才,通知我去帮忙整理材料。既然我的旅差费可以报销,那么,何不携妻女同至县城照一张相?
主意打定,说走就走,我们便提前一天搭上了那一趟唯一的班车,在九曲十八盘的天岭上颠簸了一个上午,总算安抵县城。
急急忙忙赶到县城唯一的那家人民照相馆,抬头一看,全傻了,紧闭的大门口贴着一张告示,告示上先引了一段“最高指示”,接着赫然写道:
“因革命需要,本馆暂停营业十天。”
我的天,难道我这大半天汽车白坐了?我和我妻子抱着女儿挤进县城唯一的一家照常营业的饭店,胡乱喝了一碗面汤,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那年,我毕竟血气方刚,很快便下了决心:
“走,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到漳州照相去!”
从县城到漳州,不足一百里,抓紧时间,一个下午还可以来回呢!
于是,我们又急匆匆折回汽车站。不料,一趟班车刚走,下一趟还得再等两个钟头。
“算了,有什么车坐什么车,分段走,走一步算一步!”
我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带上妻女,不顾一切地跳上了一辆刚要开动的客车,坐到了与漳州市郊毗邻的靖城。但靖城开往漳州的班车又已开走,我便出高价雇了一辆脚踏三轮车,让蹬车的师傅紧蹬着往漳州而去……
北风卷起九龙江岸因“改天换地”而到处堆积的黄沙黄土,漫漫黄尘肆无忌惮地朝我们心上,脸上,身上摔打而来。我紧紧抱着因哭累而睡熟的女儿,咬紧牙关,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
“为了让女儿照一张相,全豁出去吧!”
好不容易进了漳州,先到汽车站买了返程的最后一班车的车票,屈指一算,所剩下的时间只有十五分钟了。于是,我们又坐上三轮车,奔向最近的一家照相馆。一进门,我便大喊:
“同志,我们赶了两百多里路,给孩子照张相,只剩下十分钟了,请,请赶快!”
摄影师看见我们风尘仆仆的样子,十分同情,立即就摆开了拍摄的架势。于是,女儿坐在前头的椅轿上,我和妻子并肩站在她的背后……
就在摄影师对准我们的那几分钟,我像一位在茫茫大沙漠上经过长途跋涉之后,突然发现绿洲的旅人那样,所有的奔波、辛劳、失望、焦虑和气愤,一下子像大山一样压了下来,一种过度紧张之后突然的松弛,使我感到一阵晕眩,于是,我不由自主地合上了眼皮……
“咔嚓”一声,摄影师已按动了快门。
半个月之后,这张花费了我将近半个月工资的相片,女儿的第一张相片,终于寄到了我们的手中。
然而,照片中的妻子,勉强笑着,笑得有点凄清。我呢,风尘仆仆,一脸疲惫不堪的角色,更可笑的是,我的两眼仅微微睁开一条缝,似乎正在打瞌睡。只有女儿什么都不懂,她坐在椅轿上,一边吐着舌头,一边睁大明亮的眼睛,惊奇地盯着这个新鲜而又陌生的世界。
这,就是我女儿出生后的第一张照片,一张唯一的,任何摄影大师用任何特技都无法重拍的第一张相片。
在荒唐的岁月,这只是一件荒唐的小事。睁一眼,闭一眼,也许正是当年我最真实的写照吧!
创办梅林中学
春耕以后,公社任命我为工作组组长,到九龙坡创办梅林中学。于是,我把女儿交给妻子和妹妹,只身翻山越岭到公社报到,从此揭开了人生道路上粉笔生涯的短暂一幕。
所谓九岭坡,是九座蜿蜒起伏的荒山坡,前不靠村,后不靠店,面对清溪,背临深谷,有人曾看见在茅草窝里,有华南虎的尾巴像色彩斑斓的旗杆高高翘起,但这仅仅只是传说而已。有一次,我倒亲眼目睹过溪对岸的红色狐狸,像一团燃烧的火苗流星般地窜了过去。
当时,九龙坡的荒山坡上,只有几排废弃不用的战备兵营,门窗洞开,如同老人们张开没牙的大嘴。但客家人富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也许是穷怕了,办学的热情特别高涨,报名的学生多达200多人,其中有的年龄比我还大,个子比我还高。为了不辜负乡亲们的厚爱和重托,我们几位工作组组员(清一色的下放干部),连同当地调来的几位公办和民办教师,便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开学前的准备工作。好在公社很慷慨,给了一面国旗,两个热水瓶,六盏煤油灯,外加几千斤木薯苗。至于门窗、黑板、桌椅、床架等木料,用多少取多少,一律免费,反正山区有的是。
办学首先要有个校名牌,于是,我从领袖的诗词墨宝里找出了四个字:
梅——梅花欢喜漫天雪;
林——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中——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学——不可沽名学霸王。
我努力仿照伟人的笔体,用红油漆在白色的校牌上书写了“梅林中学”四个大字,围观的群众全都热烈地鼓起掌来,庆贺本乡本土第一所中学的庄严诞生。
尽管预订的课本迟迟没有运来,但五星红旗已插上九龙坡顶,学校于9月1日正式开学。没有鼓乐喧天鞭炮雷鸣,也没花环彩带鸽子放飞直上蓝天,总之,没有任何庆典仪式,因为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下列周程表:
第一周修补校舍
第二周抢种木薯
第三周挖山开辟小操场
第四周请科岭老红军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到了第五周,课本还没到,怎么办?工作组连同全校公办、民办教师紧急开会研讨对策,大家遵照“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最高指示,决定自编乡土教材,先教给学生一些农村里最实用的知识。好在公社又及时支援了钢板蜡纸,好在下放干部中不缺各方面的专业人才,于是,我编出了《农村应用文12例》;原农学院助教开讲《水稻病虫害防治》;原中医学院助教带领学生上山辨识采集中草药。还有一位女同志是原部队文工团的团员,她便给大家教唱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后来,还排练出《赴宴斗鸠山》的选段,在公社礼堂里演出呢!我在剧中还粉墨登场,扮演了李玉和这一角色,吊起嗓子,唱起了“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遥想此生,我曾写过剧本,演过话剧,但作为京剧的票友,这还是第一次,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当年我们这些人,说不清是干部,是教师,还是农民?我们的学校,也说不清是小学,是中学,还是半耕半读的农业职业中学?反正,对于一张白纸来说,能描上的都是美丽的画图,对于求知若渴、饥不择食的心田来说,能播下的全是希望的种子……
终于盼来了正式的课本,我们一个个全都已经瘦了一圈,因而,每一双眼睛全都显得特别大,特别圆鼓鼓的。
火的圣浴
在人生的漫漫长途中,坎坷、泥泞、风霜、雨雪,乃至于种种突如其来的灾祸,全都在所难免。
危难之际,能伸出友谊之手拉你一把,让你挣脱死神纠缠的人,有的是你素昧平生、根本不认识的人,只不过你遇险时,他恰巧路过,顺手拉了你一把,延续了你的宝贵生命;有的,则是你周围普普通通的人,平时,他毫不起眼,你未必注意他,看重他,然而,正是他,在千钧一发之际,成为你的救命恩人。
在九龙坡办学的岁月中,我就曾经经历过一场火的圣浴。
那天中午,后山的森林里突然冒出了滚滚浓烟,紧接着,熊熊的火苗窜上了树梢,燥热的气流连同焦味旋即卷了过来,学生们惊叫着,整个校园都在震颤。按照当年最流行的一句口号:“火光就是命令”,全校师生立即组织起来,分头上山扑火。我也带领一支队伍,冲上山去。平日里甚觉崎岖的小路、丛生的荆棘这时全不在话下,我们很快便赶到了着火的地点。
但这对于我来说,毕竟是平生第一次,毫无经验。好在山区的学生个个训练有素,他们用砍刀砍下带叶的松枝,分给我一枝,要我跟他们在顺风处站成一排,一起往前扑打。
山峦起伏,地形复杂,浓烟遮断了视线,火舌像毒蛇般乱窜,阵阵热浪席卷而来。我们且扑且进,当发现正身处一个深井似的山谷时,身边只剩下七八位学生,与大队人马已无法再联系了。
热风在山谷中回旋,时而东来,时而西来,顺风、逆风?此时此地,已难以判断。一棵本已烧焦的大树突然从树梢处爆出大火球来,顿时,火星、火花、火箭四处进溅,落地后又引发出无数新的火蛇乱钻乱窜。山谷底部全是易燃的茅草,我们随时都可能陷入烈火的包围圈,情况十分危急!
有经验的学生们纷纷建议突围。
可是,往哪个方向突围?往东还是往西,往上不是往下?这可是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烟熏火燎中众说纷纭,我也一时没了主意。
突然,一位细高个子的学生大喊一声:“老师,不能再拖了,赶紧先往上跑,高处才能看清方向!”
于是,他马上成为我们的领袖,大家都听从他的指挥往上突围。
不料,殿后的我却一个趔趄,掉进了一个深坑。又是他,及时回头发现了,他马上过来,伸出细长的手臂,用力把我拉了上去。
好不容易上了坡,从高处回头一看,好险!刚才我们所处的山谷底部,已是一片熊熊的火海……
人不可貌相。这位细高个的学生平时在班上毫不出众。一篇《寻牛启事》的短短应用文错了八个字。课堂上提问到他时,他双眼老盯着桌上的铅笔盒,脸涨得通红。路遇老师,他也不懂得招呼,只是腼腆地闪在一旁憨笑。而正是他,细长的身影在火海中站成一棵擎天大树。
他,不仅仅是我的救命恩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我的老师,他在火海中的那一声吆喝:“高处才能看清方向”,正是我一生中,时时处处都应该遵遁的人生格言。
1971年11月,我在梅林中学工作还不满一个学期,县革委会来了一纸调令,要我到县报道组去当一名“土记者”。为此,我不得不一步一回头地告别九龙坡,告别那些可爱的山区孩子,告别与我历尽艰辛共同创办梅林中学的战友们。翌年3月,妻子汪兰也调进南靖一中任教。于是,我们举家告别梅林,从内山迁往山城,又在南靖翻开了我们下放生涯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篇章。
作者附记:2000年,我和汪兰重返阔别了30年的梅林。我们高兴地看到,当年的长教学校和梅林中学都盖起了许多新校舍,山区的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与往昔已不可同日而语。我们还到当年女儿出生的那幢双层楼旧地重游,溪边的老榕树依然枝青叶茂,郁郁苍苍,让人为之眷恋不己。我们特地在树下摄影留念,并把照片寄往美国,让已在美国定居的女儿也能一睹她出生时的场景。人的一生,有可能走遍天涯海角,浪迹异国它邦,但有些地方是永远也不应该忘记的,比如她的家乡,她的出生地,连同她的祖国。因为这是她的根,她的摇篮血地,她的生命的起点,也是支撑她精神的一根强大支柱。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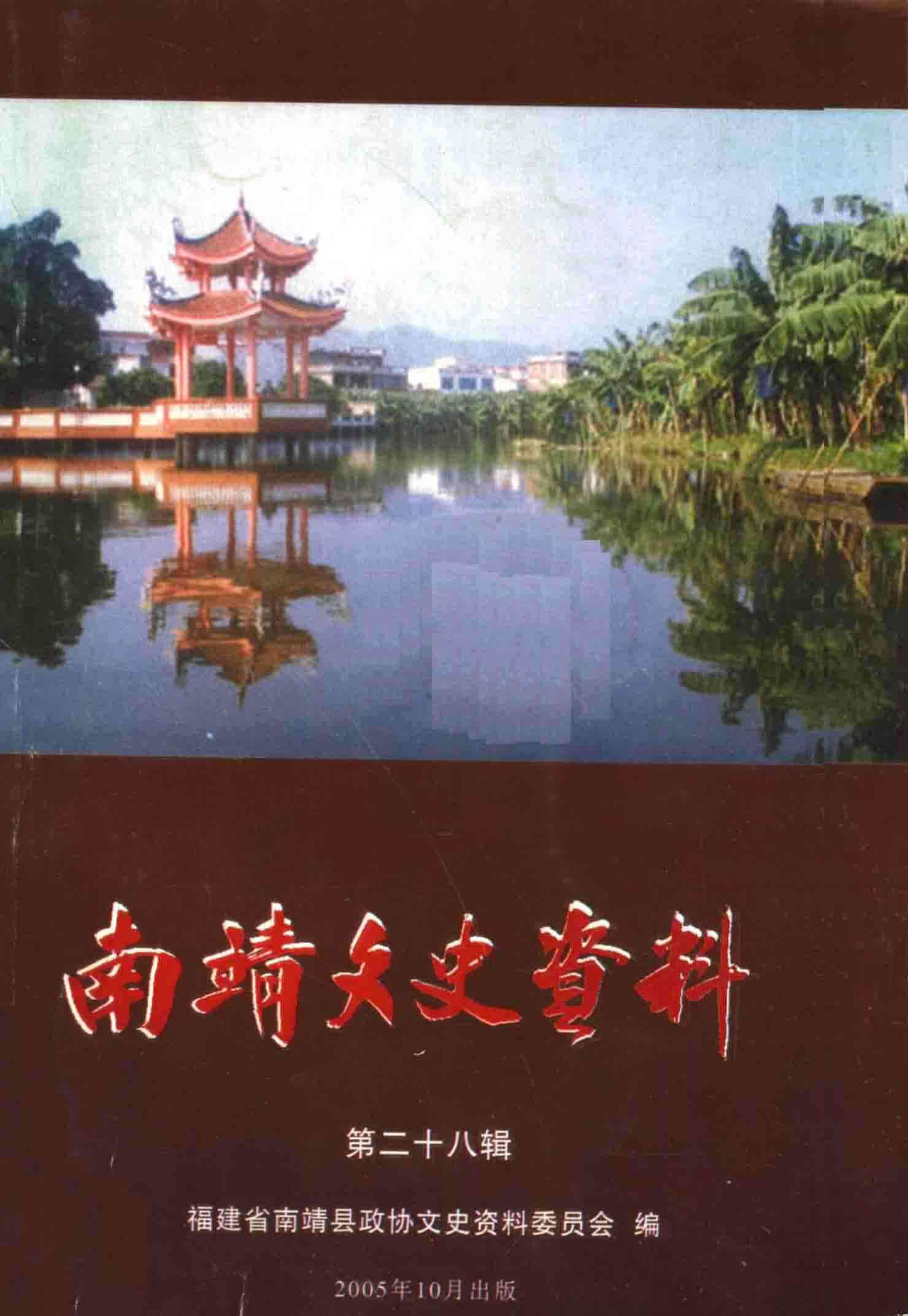
相关人物
章武
责任者
相关机构
南靖梅林公社
相关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