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 内容出处: | 《漳浦文史资料第十六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30000862 |
| 颗粒名称: | 史海钩沉 |
| 分类号: | K295.74 |
| 页数: | 24 |
| 页码: | 170-193 |
| 摘要: | 本节记述了漳浦县的漳浦鸟石天后宫沿革、漳浦历史上科举出身的仕子、南宋末代小皇帝的传说与史实、南宋末代小皇帝的传说与史实等。 |
| 关键词: | 漳浦县 文史资料 历史人物 |
内容
漳浦鸟石天后宫沿革
林祥端
漳浦乌石天后宫在漳浦县旧镇镇浯江村紫薇山。天后宫后殿奠基于1992年5月,至1993年1月落成。1993年6月继建中殿,至1994年12月落成。天后宫坐东北向西南,背靠紫薇山,面对天马山,浯江从东边绕过,流入浮头湾,乌石景色尽收眼底,极得山水之灵秀。天后宫占地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规模宏敞,中殿飞檐流角,金碧交辉,气势雄伟壮丽。
一、林士章迎回妈祖的传说
乌石天后宫祀妈祖林默,漳浦林姓尊称妈祖为“姑婆祖”。乌石妈祖圣像据传为乌石探花林士章从莆田湄洲祖庙请回供奉的,原来建行宫在漳浦县城北门外官道旁。
关于林士章迎回妈祖的传说有以下几种:
(一)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林士章赴京参加会试,路过泉州洛阳桥,桥上遇一女子迎面而来,林士章左避右闪都被挡住去路,那位女子要林士章对对子,她出了上联:“鞋头绣菊,朝朝踏露蕊难开。”林士章一时对不出下联,那女子莞尔一笑,让开了路,顷刻不见踪影。林士章赴京会试后参加殿试,皇帝出一上联:“扇中画梅,日日摇风枝不动。”林士章灵机一动,顿时想起洛阳桥上那位女子的上联正好可做此对的下联,于是冲口念出:“鞋头绣菊,朝朝踏露蕊难开。”皇帝称赞说:“对得好,只是脂粉味浓些,卿真是探花才也!”林士章急忙跪下谢恩,因而高中探花。林士章归家省亲时,路过莆田湄州,瞻仰妈祖尊容,觉得绝似洛阳桥上的女子,顿时感悟,原来是妈祖点化他,于是就把湄洲妈祖请回家乡供奉。
(二)林士章任京官后,给假归家省亲,特地到湄洲参拜妈祖。先时,林士章祖父林竦务农勤耕,广种荔枝,采果晒制成干,用船运载到浙江温州、宁波出售。有一次,海上遇大风浪,船将翻复,望见一女神相助,幸免于难,事后得知此女神即湄洲妈祖显灵,于是就嘱咐林士章要到湄洲参拜妈祖。林士章此次参拜,就请回妈祖圣像归家供奉,以慰祖灵。
(三)林士章偕继配郑氏夫人自京城归家省亲,特地到湄洲参拜,请回妈祖供奉。郑夫人未嫁时,曾梦见一女神请她吃仙果,并令两侍女持夜明宝珠照路,说:“送夫人回府。”郑氏醒后,觉得身心清爽,神智倍增,依稀记得女神酷肖妈祖。后来,林士章原配柳氏逝世,娶郑氏为继室,诰封夫人。有一次,郑夫人进宫朝见太后,天色已晚,太后令两宫女持宫灯送归府。郑夫人深感妈祖的点化,就迎妈祖归家奉祀。到湄洲参拜时,预先刻一尊妈祖放在夫人轿中,进庙后采取掉包的方法,将庙中妈祖圣像换下来放在轿中,抬回家乡。至今,漳浦尚有“无锣无鼓,偷请妈祖”的民谚。
(四)万历九年(1581年),林士章致仕归家时,特地到湄洲参拜妈祖,请回圣像供奉。
二、探花林士章身世简介
林士章(1524—1600),字德斐,号璧东,漳浦县七都乌石大厅北平村(今旧镇镇浯江村大厅边北平)人。乌石林氏始祖林安,生长于福州长乐后市村。南宋景定年间,徙居漳浦县东关外安仁乡浯江保西径坊,子林进,“定居海云山下,因三山(福州古称)之乌石名为乌石”。这是为纪念祖地福州乌石山,所以取“乌石”为徙居地的名称,漳浦从此就有了地名“乌石”,并一直沿用至今。
自明洪武以来,乌石林氏逐渐发展兴盛,至嘉靖三十七年,科甲连登,人才辈出:族叔祖林纯一举人,族叔林功懋、林策、林一新俱进士,林一初、林一阳、林成纲俱举人;族兄林士宏、堂兄林楚俱举人。至此,乌石林氏已成为漳浦显赫的望族。林士章生长在这官宦家族的氛围中,深受其薰陶。
林士章祖父林竦,字迁瞻,号忍庵;父亲林烽,字世明,号省庵,虽世代务农,但也知书习礼,课子读书。林士章兄弟七人,他排行第五,因而以《孝经》篇目“士章第五”取名为士章,望其能忠孝传家之义。林士章自幼聪颖过人,读书紫薇山中的紫薇洞,诗文有大雅之风,福建提学朱衡“以国士遇之”。
嘉靖三十八年,林士章果然不负众望,一鸣惊人,联捷进士,殿试第一甲第三名,探花及第,名扬全国。初授翰林院编修,历官两京国子监祭酒,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左、右侍郎,经筵讲官,国史副总裁,终南京礼部尚书,万历皇帝御赐“忠爱”匾额。万历九年,致仕归家,过了近20年的村居生活。
三、迎回妈祖时间的推断
民间传说虽是虚构成分居多,但还是要以某些事实为依据,并非全是凭空捏造。现据有关史书、家乘和林士章墓志铭等资料,结合上面的传说,探讨林士章迎回妈祖的时间。
林士章自嘉靖三十八年探花及第后,长期在京城任职,其中,只有两次较短的时间在南京任国子监祭酒和礼部尚书。在任职期间,明确记载归家时间有4次:(一)嘉靖三十八年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照例给假回乡省亲,“竖旗拜祖”;(二)嘉靖四十一年,母丧,归家守制,至嘉靖四十五年,起复原官;(三)隆庆二年(1568年)十二月,父丧,再次归家守制,至隆庆六年,起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四)万历九年五月,致仕归家。上述4次归家,其中,两次遭丁忧,都不可能去莆田迎妈祖,况且林士章原配柳氏也在嘉靖四十一年去世,在处理双重丧事后,迟至4年后才起复翰林院编修。隆庆二年,林士章升国子监司业。隆庆六年,林士章以久次起家,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万历元年(1573年),转调北京国子监祭酒时,双亲已逝世,无用给假省亲,且从南京到北京并无路过家乡。所以,此次转调,林士章没有归家。
嘉靖三十八年与万历九年两次归家与传说中迎回妈祖的时间相同。但嘉靖三十八年,林士章归家荣宗耀祖,正是显示自身价值的时刻,不会迎妈祖来冲淡的。况且,官方接送繁忙,无暇顾及迎奉妈祖之事;再者,如果于此时迎回妈祖,林士章尚未在县城建府第,应是把妈祖迎回乌石,这样,妈祖庙就该建在乌石,而不是建在漳浦县城。
万历九年五月,林士章致仕回乡,这最有可能是迎回妈祖的时间。万历二年,林士章升任礼部右侍郎,万历五年,转礼部左侍郎。但就在此年,权相张居正父丧“夺情”,林士章会同礼部尚书马自强,侍郎王锡爵上疏反对,因而得罪了张居正。万历八年,林士章任礼部侍郎已满6年,按例,京官任职6年即可考绩提升,然而,张居正暗中指使给事中、御史搜集材料,对林士章多次攻击、弹劾。万历八年十二月,林士章再次上疏引罪乞罢,皇帝不允许。万历九年正月,林士章与吏部尚书王国光、礼部尚书徐学谟,侍郎何雒等各以考察自陈。二月,林士章升南京礼部尚书。五月,“南京试御史徐金星论劾南礼部尚书林士章,太常卿张卤不堪祀典,乞赐罢斥。吏部复,士章原无显过,仍宜留用,卤屡经论列,似难展布。上令士章照旧供职,张卤回籍听用。已而,士章引疾乞致仕,许之。”林士章致仕时,年仅58岁,他正欲实现其忠君爱国的怀抱,然而,张居正专横跋扈到极点,言官的弹劾,使林士章不愿再旅险仕途,因此,“当飨用之方殷,遍乞身而勇退。”当时,林士章的心情是抑郁而沉重,但也感到无官一身轻,因而,他在回乡时到湄洲参拜妈祖,并请回奉祀,这完全符合他当时的心态。传说中的(二)、(三)没有说明具体时间,其为实现祖父迎妈祖的宿愿和按郑夫人的心愿请回妈祖奉祀,都可以做为致仕时请回妈祖的动机。
林士章迎回妈祖时,他的府第已建在县城多年,所以,就在县城建庙奉祀。
四、史书关于县城妈祖庙的记载
据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修纂的《漳浦县志》载:“天后庙二,一在北门外,一在南门外。后本兴化人,明封天妃,国朝晋封天后,祠庙沿海皆有之。”由此可知,康熙三十八年以前,漳浦县城北门外就有妈祖庙,但没有说明修建的时间。《漳浦县志》首修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继修于万历七年(1579年)和三十三年(1605年),但这些志书现已无法看到。现存万历元年癸酉编纂《漳州府志》按各县进行编写,留下宝贵的资料。其中,有关漳浦县“宫庙”的记载:“漳浦县庙二所,灵慈庙,在县西北隅,即天妃庙;?湖庙在西门外。上二庙今废。”万历癸西《漳州府志》是根据嘉靖九年修的《漳浦县志》增修至隆庆六年。据此记载,漳浦县城只在西北隅有过一座名叫灵慈庙的妈祖庙(?湖庙所祀何神,这里不予探讨),但在嘉靖九年以前就倾圯荒废,至隆庆六年,尚未建新的妈祖庙,重建妈祖庙是万历元年以后的事。这样,林士章于万历九年迎回妈祖并在北门外原灵慈宫附近建庙奉祀,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五、妈祖庙为什么要建在北门外
林士章的府第称尚书府,建在县城南街城隍庙旁,迎回妈祖时为什么妈祖庙不建在附近的南门,却建在不近水滨的北门外?据传是迎回妈祖时,圣轿抬至北门外稍为休息,要进城时,圣轿竟抬不动,于是就在停轿处建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妈祖庙建在北门外的原因有三点:
(一)已废灵慈庙在县城西北隅,在其旧址或附近建庙是符合其历史沿革,庙名仍沿古称为“灵慈庙”。
(二)北门外地势高坦,虽不在水滨,但背遥倚罗山,面对梁山诸峰,且地处南北交通之官道,人烟密集,人杰地灵,适宜建庙。
(三)万历间,城北是林姓聚居地,其中有三个官宦家族:(1)浦北林氏林埙家族。林埙,成化十二年岁贡,官至宁府长史,其家族衍居北门内外一带及东罗等地;(2)港头林氏林表家族。林表,成化五年进士,官至镇远知府,其孙林敬、玄孙林绍分别官至长沙知府和山东副使,在北街顶建“世大夫第”,其家族衍居北街顶一带;(3)新路林氏林梓家族。林梓,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官至通政使,位列九卿,其子林宰、林采分别官至兵部侍郎和广西副使,其家族称“十八顶纱帽”,是新兴的豪门巨族,衍居县城西北隅新路一带。这些林姓家族都奉祀妈祖,所以,林士章迎回妈祖时,建庙在北门外也就顺理成章。
北门外妈祖庙建在官道西侧,坐北向南,庙为三开间两进的土木结构,庙前有庭院,庭院东边建一座大门,正对官道,过往客商也都进庙参拜,香火旺盛。
在北门外建庙后,城南才从北门灵慈庙挂香、雕像,在南门外溪边兴建妈祖庙,坐南向北,面对南门外五凤桥。庙宇规制与灵慈庙相同,庙名为“金南水镇”。其建庙年代约于万历中期,现存原庙中石柱镌刻:“西湖蔡宗俊舍柱两条,祈求子孙荣盛者”、“西湖蔡宗传喜舍石柱一条,祈求子孙昌盛者。”由西湖蔡氏辈序:“大宗一而祚衍长”可知,舍石柱者与万历二十九年进士蔡宗禹同属“宗”字辈,为西湖蔡氏始祖直翁以下第五世。其时,传衍未繁,堂兄弟年龄相差无几,且舍石柱之事应在成家立业之后,所以,其舍石柱建庙年代约为万历中期,比北门外建庙稍迟些。南门外妈祖庙建在南门溪边,常遭大水淹没,鉴于此情况,建庙时设计,在庙的后墙妈祖殿两旁,自庙内地面用石条竖两个1.5米高的大石窗,当洪水泛滥时便于排涝,这成为“金南水镇”建筑的独特之处。
六、北门外妈祖庙残存干支纪年的考证
北门外妈祖庙历来有过多次重修,近年修整时,在壁画和画栋之间发现有戊子、已丑两个干支纪年,字迹依稀可辨。戊子和已丑是两个紧接的年份,每六十年重复出现,实际作画时间不一定前后两年相连,可能相隔六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自明万历九年至清光绪间,属戊子、已丑的年份有:(一)明万历十六、十七年(1588—1589);(二)清顺治五、六年(1648—1649);(三)康熙四十七、四十八年(1708—1709);(四)乾隆三十三、三十四年(1768—1769);(五)道光八、九年(1828—1829);(六)光绪十四、十五年(1888—1889)。在这些年份中,万历十六、十七年距林士章迎回妈祖时间已七、八年,林士章归家不久,为避县城喧嚣,在漳州城东北十里的流冈附近建长桥土城隐居,建妈祖庙应在未迁漳州时,不会迟至七、八年后才建庙;顺治五、六年,正值战乱时期,人心惶惶,民不聊生,无人顾及修庙之事;康熙四十七、四十八年,距万历九年已120多年,且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这时,妈祖庙应有一次大修。假若康熙间的修建只是上述纪年干支中的一个,那么,另一个纪年的修建应是上述乾隆、道光、光绪间的一个年份。当然,自乾隆以来,也会有不属戊子、已丑年进行修建的,如民国21年(1932年)曾有一次翻修,其岁次为壬申。
七、“有行宫没有圣像”与“有圣像没有行宫”的历史事实
北门外灵慈庙约于清代中后期改名慈后宫。原庙中有一对联:
灵在天上,世界达得大德;
慈为圣母,裔孙共感神恩。
对联首字嵌入“灵慈”两字,足见此联专为灵慈庙而作。对联中第三、四字,上下联分别嵌入“天上”、“圣母”字样,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封妈祖为“天上圣母”,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继封为“天后”。由此可知,此对联作于康熙十九年以后,庙名尚称为灵慈庙。至于改名为慈后宫是在妈祖封天后之后,取灵慈的“慈”,天后的“后”,名为慈后宫。
对联下联有“裔孙”两字。从广义来说,妈祖是宋代人,后人既尊为“妈祖”,也就都可称为她的裔孙;从狭义来说,应是指林姓子孙。北门一带虽为林姓聚居,但也有程、陈、刘等姓混居,因而,“裔孙”的含义应是广义与狭义并存。
上述对联在1984年重修后尚保留。南门妈祖庙移用此对联,把上联首字“灵”改为“后”,以表示区别。
世事沧桑,自明至清,漳浦县城城南、城北居民姓氏起了很大的变化。原有“南叶北林”之称,即城南叶厝巷同知叶穆、叶谐的家族和城北林埙、林表、林梓的家族。后来又有“南詹北程”之称,即城南叶姓至正德间,被御史詹惠家族所替代;城北的程姓至万历、天启间,出了大理寺丞程绍南、解元程样会,其家族也由弱而强。最后,至清代末年,各巨族都衰落,城南、城北已为各姓混居。
北门林姓最先式微的是林埙家族,自嘉靖十三年(1534年)林埙去世后,家道逐渐中落,至明末清初,浦北林氏大部分迁到东罗、麦园埔、上洞等地居住,至今,北门已没有浦北林氏;号称“十八顶纱帽”的新路林氏,至清初尚是一个大家族,然而,在康熙三十五至四十七年间,陈汝咸任漳浦知县,整顿赋役,澄清吏治,打击地方豪强,新路林氏首当其冲,曾有林家婢女讥笑陈汝咸“见狗也唱喏”的传说,从此一蹶不振,至今,县城已无其后裔;港头林氏在北街顶建“世大夫第”,至清朝虽尚保持大家族,但气派已不如从前。
与之相比,漳浦东关外林姓大为崛起,至清朝中期,林士章的祖籍乌石林氏已繁衍顶、下乌石五、六十个村子;路下林氏也繁衍几十个村子,这两个林姓大家族都崇奉北门外行宫的妈祖。除农历每年三月二十三日妈祖生日同时拜祭外,自二月至十一月,各地按自然村或地区轮流迎奉,称为“迎姑婆祖”或“迎妈祖”。这样,北门外行宫的妈祖就长期在乌石(浯江)、旧镇、赤土、深土、六鳌、霞美等地“行香”,至十二月才送回北门外行宫过年。约于清末民初,乌石林氏出于对妈祖的崇敬,有一年,把妈祖留在乌石大宗祠海云家庙(俗称“乌石大厅”)中过年。从此妈祖就不再回北门外行宫,行宫中只刻块妈祖圣牌奉祀。按“一神一庙”的惯例,北门外妈祖庙不可另雕圣像,而乌石也不可另建妈祖庙。因此,长期形成“北门有庙(行宫)无翁(圣像),乌石有翁(圣像)无庙(行宫)”的历史事实。
八、漳浦乌石天后宫创建及其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观念也随之改变。1984年,县城北门外妈祖庙重新修建时,就到乌石妈祖圣炉挂香回庙,另雕妈祖圣像供奉;1989年,衍居台湾的乌石宗亲林瑶棋、林瑞国等相继回家乡拜祖,得知乌石妈祖是四百多年前由探花林士章从湄洲迎回供奉的,至今,在乌石尚未建行宫,于是,与乌石乡亲商议建天后宫之事。
1992年,由林瑶棋、林瑞国等台胞捐献巨款,乌石宗亲及远近信士随之响应,各尽其力,并得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5月24日,举行行宫后殿奠基仪式,至1994年12月8日,中殿落成,行宫命名为“乌石天后宫”。自林士章于万历九年迎回妈祖建庙,庙的名称由灵慈庙而慈后宫而乌石天后宫,至此已历时414年。从此,妈祖在乌石有了行宫。
乌石天后宫建成有其深远的意义:
(一)结束了“北门有行宫没有圣像,乌石有圣像没有行宫”的历史;
(二)加强海峡两岸的团结和文化交流,促使祖国早日实现统一;
(三)扩大妈祖信仰的国际传播,促进世界妈祖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乌石天后宫规模宏伟壮观,居闽南妈祖庙之冠,可与闽中湄洲祖庙相媲美,远近香客络绎不绝,海外信士纷纷前来朝圣,乌石紫薇山成为朝圣与旅游的胜地。
史海淘廉
·高聿占·
漳浦历史上有不少科举出身的仕子,被朝廷派往各地当官,史志记载他们大多数能廉洁自律,政绩斐然,深受当地黎民爱戴。科举时代的官员并非完全清廉,史志隐恶扬善,用意在于鼓励人民向好的方面学习。这些先贤的高尚品德还是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兹摘抄部分以飨读者。
宋
林彦质,字彬叔。“历官州县皆有廉名”。“秩满乞归,卧游自适,幅巾野服,消涤世虑。捐金募植松于道,行者德之。”
高登,字彦先,号东溪。“任广西富川主簿兼贺州学事。秩满士民乞留。不获。相率馈钱五十万,不告姓名,白守曰:教授贫无以养,愿太守劝之受。登辞不可,请置书藏于学。”
明
俞文,字懋学。“督漕徐、淮间,诸漕帅用故事敛金百镒以馈。文却之。”“老疾乞归,过常郡,缙绅遮留,吏民攀送填咽,且醵为道里费。文觅小舟,夜亡去。”“家居四壁,敝衣蔬食,怡然自乐。”
杨武,字德毅。“屡聘为河南,山东,广东主考。”“道有私谒者,谕之。杨曰:以荐贤而以为私也,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其人负惭退。”
陈镡,字曰宣。授太原通判。“清慎自持”,“与士卒同甘苦,以廉能闻。民立石颂焉。”
叶穆,字式文。授汾州知州。“有犯死罪者,馈金五百求贷。叱之。”“致仕,家居茹蔬衣敝。”
吴超,字华越。授工部主事,监杭州税关。“关故利薮,超矢志奉公,羡余悉归公帑,不以自私。”改授徐州三年,“尤以清勤著誉”。迁广西参议,“益励晚节”。“致仕家居,淡泊自守,乡人重之”。
徐弼,字良佐,“擢廉州府同知,性劲直不能诡随,以冰蘖自持。卒之日,发其箧得《德政录》若干卷而已。
林文焕,“授户部主事,督税临清钞关,清操自励,升员外郎,家不增一瓦一椽。时入郡邑,徒步而已。”
林功懋,字以谦。任东莞知县时,“尝权税番舶,外番贿赂毫无所受。时,指挥王宠偕行,见功懋感叹曰:独文臣不爱钱乎!亦峻却之。”子林士弘,字仁甫,“奉使楚蜀之藩,馈遗一无所受。”
林一阳,字复夫。“迁唐府审理,去,民思之,立石纪政。归家谈道自乐”。平时自律“惟敬可以胜怠,惟勤可以补拙,惟俭可以养廉。”
王应显,字惟谟。“知秀水县,县治后圃多桃,盐之以佐饭。”“升户部主事,榷九江税,廉洁奉公。”“升浙江布政使,洁已奉公如为令时。”
林楚,字德春,号春斋。任雷州通判,“雷有珠池,在雷四载,不取一珠。”从侄林汝诏,字君纶。“授永州推官,以平恕清慎名”。
林缵振,字公悦。任工部主事。“岁终,库椽进羡金数百,曰:公合得之。缵振叱椽出。”
蔡时鼎,字台辅。授桐乡、元城二知县。“时鼎一以勤、慎、谦、约劝学为质。”“差视淮盐,疏列惠商裕课十事,次第举行。差向有例金,却不受,积之以为浚河之费。”
林茂桂,字德芬。“授深州知州,一意为民。归家后,其家居文酒相命,四壁萧然。人谓廉吏”。
蔡杲,字宏中。“授太仓知州,清白严介。先后官京邸五六载,栖止道院僧寮,一榻萧然。卒之日,贫无以殓。”
黄季成,任东阳县令,“邑素健讼,听断毕即遣去,不入锾金。擢工部主事,分管铸造局,局故繁琐,颇涉利窦。季成一以澹泊处之,禁绝常例。”
清
林绍祖,字衣德。任长沙醴陵县令。“何氏兄弟互控,请托千金,却不受,以至情感悟之。”“醴河多滩,有孙商者,舟次溺水死,亲检遗货计八千余金,驰其家人领取。用人参数觔为谢,却不受。”
谢天禄,字百和。“漳富商大贾,慕其行谊,不惜挥金延请为师,意所不屑,去之若浼。宗人以事羁于官,官知天禄清贫,欲为之德,微示其意。宗人以千金丐一言。岸然不屑也。”
蓝应元,字资仲。官礼部侍郎。“服官三十余年,囊空如洗。”这些先贤的高尚品德是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南宋末代小皇帝的传说与史实
·李林昌·
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宋朝末代小皇帝赵昺在广东崖山败亡,民间将风物附会于宋帝昺的传说,自福建至广东被人们认为他南逃的路上不下二十多处,单漳浦、龙海一带就有:
一、嵩屿。传说,宋少帝从福州南下的船队因为泉州守将蒲寿庚降元,匆促离开泉州港,到鹭岛对岸时曾停留。那天是少帝诞辰,大臣们拥少帝上岸,人人朝拜,同声呼“嵩”,恭祝万岁,因而那地方叫嵩屿。
二、宋少帝的船队曾在南太武山下停留。有“太武香薷”的传说,说少帝中暑,服香薷而愈。
三、马口,地处南溪中游南岸,小船可上达山区,下通海口,陆路是闽粤交通要冲,形势险要。传说,宋少帝曾暂驻跸,开科取士,尚未揭榜而元兵追来,大臣们拥少帝继续南逃,投考的士子们拦住御辇,要求放榜,少帝传旨尽赐进士,用树枝将榜文划在溪边沙滩上。因此,漳浦读书人无论有无功名,在葬礼的“铭旌”和墓碑及家中所祀灵牌上,都可援此例标上“例赐进士”衔头。妇女则一律标“例赠孺人”衔头,据传,宋少帝流亡到漳浦时,他的母亲杨太后独居无聊,要找当地妇女闲谈,大臣说“太后不可接见没有封爵的妇女”,太后便传下懿旨:“此地妇女尽赐孺人。”后代援例,因此处处已嫁妇女之墓的石碑上皆标有“例赠孺人”四字,其家中神牌上亦然。
四、梁山封螺。传说,宋帝昺曾避难梁山,肚子饿了便在山涧捕螺充饥。吃螺要先敲掉螺尾,然后用口吮吸,螺肉便落入口中。宋帝昙吃了螺肉,将螺壳放回涧中,赐它再活。再活的螺没有尾巴,因为是皇帝敕封过的,所以叫封螺。(其实这是品种的特征,别处如龙海市颜厝镇的白云岩,芗城区的天宝山等地也有这种螺)。
五、盘陀岭顶路边有一口山泉,涓涓细流而大旱不竭。过路人在“盘陀岭上几盘陀”之后大都口干舌焦,用此泉止渴,更感甘冽异常,沁人心肺。传说宋帝昺当年流亡经过这里,用它止渴,喝后加以敕封,所以叫“帝昺泉”。
六、玉带泉。传说,宋帝昺御舟经过古雷海域,所带淡水已完,看看就要断炊,杨太后取少帝玉带投海中,祝祷道:“天未亡宋,愿海涌出甘泉。”果然在那玉带箍着的圈内,一股淡泉冲咸而出,叫做“玉带泉”,又叫“肚箍水”,从此腾涌不息。
这些故事说来娓娓动听,但与史实多有不合。按《宋史》,元军于德祐元年(1275年)攻陷临安府(杭州),俘年仅四岁(全皇后所生)的皇帝赵〓移往上都(今内蒙古多伦的石别苏木)。翌年(1276年),大臣们拥立杨淑妃所生的赵是(8岁)称帝于福州,尊杨淑妃为太后,改元景炎。俞修容所生的赵昺(6岁)封卫王。景炎三年(1278年)五月,赵昰病逝于广东吴川之南的海岛碙州,元帅张世杰、丞相陆秀夫拥立越昺为帝,改无祥兴。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败亡于新会县南的崖山。据此,在福建境内流亡的宋少帝是赵是而非赵昺。这一支宋朝残馀力量还有庞大的船队和数万大军,航海南下广东,在沿海的嵩屿、南太武山下、古雷头等处可能停靠,而不会在梁山打游击。诸如“梁山封螺”,盘陀岭“帝昺井”等传说无非附会。说皇帝泡饮过的茶叶遗弃在古雷山长出茶树,说皇帝的玉带抛在海上能涌出淡水,如果宋朝末代皇帝有如此神力,何至于亡国?
宋帝昺在马口建行宫开科取士之说有很多人相信,因为那里确有一座小石城,城门左边有一个传说为“皇帝殿”的天然大石,一面刻卷书状浮雕,卷书上有“仙鹤瑞芝”四字,一面刻很多字,年久风化,模糊难辨,传说石下是宋商昺藏宝处,若能读完那些刻字,石门自开,可进内取宝。
民间传说总是不断添枝加叶,不断升级的。宋少帝在马口的传说先是“揭榜沙溪”,与南太武山下“驻跸处”同时流传。明末清初丹山名士张士楷有诗分别吟咏这两处传说(载康熙《漳浦县志》卷十八《艺文》)。
太武山
景炎遗迹杳闽关,驻跸犹传太武山。
御气海天馀白日,翠华烟雨没乌峦。
野花曾入慈元恨,国事深悲德祐间。
不是潇湘还苦竹,春风愁杀鹧鸪斑。
马口溪
(相传宋室南奔,策士于此,时野草齐花,溪山改色)
宋士临危贪释褐,公车射策满平沙。
阁将丞相千行泪,开遍春风百草花。
野殿宵衣能立国,宫袍画锦已无家。
空谈久被书生误,谁执干戈卫翠华?
明末清初传说的还只是马口溪“开科取士”故事,那时马口城未建。据康熙《漳浦县志》卷十五《建置志》记载:“马口城,在二十八都邑北尽境,康熙二年总兵王进攻建议,督院(福建总督)李率泰建,刻记石上,俯溪桥。原有千总驻于此。”康熙二年(1663年)正是清朝厉行“迁界”以拒郑成功之子郑经的时候(郑成功已病逝于台湾),马口地处水陆交通枢纽,建此城驻千总以资调度。在清朝统一台湾后,此城失去军事作用,变成一座空城,南来北往的人穿城而过,对此城为什么建在荒野有神秘之感,由于早有“马口溪开科取士”的传说,马口城便被附会为宋帝昺的行宫。
被传说为“皇帝殿”的马口大石与被传说为“行宫”的马口城已陆续被毁,现在无从考据其实物了。好在前人已有考据,留下资料,供后人参考。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福州协和大学福建文化研究会出版的《福建文化》第三卷第二十期是翁国梁写的《漳州史迹》专辑,其中写到宋帝是在马口的传说:“帝昺当时虽被元军节节追赶,但跟他走的皇族、官僚、兵士、平民不下数十万人,到了马口桥地方,想暂时居住,就起了一座皇宫,同小城一样,纵横数百步,东北靠山,南北开了二个宫门,南门石额刻寅禧二字,北门石额刻怀远二字。……宫殿今虽倒塌,但宫门及石额尚存,行旅往来,皆穿宫门而过。在宫门左边,有巨石作三角形,一面刻“仙鹤瑞芝”及卷书之状,一面刻字很多,但多残缺,乡人传说,刻鹤芝者乃石门,内为宋帝昺藏宝之所,若能将石上之字读完,则石门自开,可以入内取宝。最近有人就石摩挲,约略认得数十字,就旧本《福建通志》校对,乃知石上所刻为宋黄惠三十三桥记,因为自龙溪至漳浦大路有桥三十三座也。事在帝昺之前,乡人藏宝之说虽属附会,然亦可见普通之心理。(李林昌注:《黄惠三十三桥记》应为《黄木熏三十五桥记》,记载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太府寺丞知漳州傅伯成领导建设自漳州南谯门至漳浦三十五座石桥的功绩,比宋帝昺早80年。该碑记自己写明刻在甘棠路边天然大石上。甘棠是马口原地名,宋代设甘棠驿)。翁国梁虽然因为没有考据马口城的建城时间为康熙二年而误信马口城为宋帝昺行宫,但给后人留下实见资料,证实所谓皇帝殿的文字石刻实际就是南宋庆元四年黄櫄所作《三十五桥记》。
“越王古迹”的传说与史实
·李林昌·
一、蒲葵关是否发生过汉朝与东越的战争?
见于史志记载,今有具体地点可觅的漳浦最古古迹是盘陀岭上的蒲葵关。康熙《漳浦县志》卷十九《古迹》载为“汉南越故关”引据南宋淳祐《漳州志》记其地点“在驿西南一舍”,“驿”指设在漳浦县治所在地的仙云驿,“一舍”为30里,《康熙志》说“关当作邑之南今盘陀岭是也”。《读史方舆纪要》按《淳祐志》之说认为是“汉初南越所置关也。”《舆地纪胜》说为“东南二越界”。
“东越”应作“闽越”较为准确,“东越”只是“闽越”的东北部分,这在下面就会说到。闽越与南越同是汉的诸侯国之一。盘陀岭是怎样成为闽越与南越的分界线的?
闽越的地域即古“七闽”地,包括今福建全省及浙江南部、西部和广东东部、北部若干地方,原有闽族七个部落,自公元前644年周武王姬发出兵打败商朝的无道暴君纣王,建立周朝,七闽归服于周朝。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67年),七闽属越国势力范围,越国为周朝十二个主要诸侯国之一。周朝的统驭力量逐渐削弱,大诸侯国兼并小诸侯国,自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代。曾被吴国打败的越国后来打败吴国,称霸南方。越王勾践传到第六代孙无疆,被楚国征服。越人从浙江向闽地转移,逐渐与闽族人融合成闽越族。秦始皇统一全国,废封建,置郡县,实行中央集权制。在闽地成立闽中郡。但秦始皇没有派官派兵到闽地,只是废去勾践后代邹无诸的闽越王称号,降为闽中郡长,实际仍由邹无诸统治闽地。后来邹无诸出兵参加推翻秦朝的战争,在楚、汉战争中站在汉的一边。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封无诸为闽越王。后划出闽越国南部,现今闽粤交界毗连处一带,分封无诸另一后代邹织为南海王。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再划出闽越国北部,现浙闽交界毗连处一带,分封无诸又一后代驺摇为东海王。
南越的地域包括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一带。秦始皇派兵带同大量中原人民进入,建立南海(今广东)、桂林(今广西)、象(今越南北部)三郡。河北真定人赵佗带去的中原人最多,军事力量雄厚,由龙川县令升任南海郡尉,于秦末兼并了南海、桂林、象三郡,拥兵自立。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封赵佗为南越王。
南海王最先反汉,被汉武帝迁往上淦(今江西靖江县),其在闽粤交界毗连处的封地就被南越和闽越所瓜分,其分界线就在盘陀岭,当时岭上有很多蒲葵树,叫做蒲葵岗,关隘称蒲葵关。
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驺逞用武力迫使东海王迁民于江淮间,占领了浙南浙西一带地方,又出兵攻南越,招致汉武帝出兵讨伐,邹逞之弟馀善杀驺逞,投降汉朝。汉武帝改封没有参加叛乱的无诸另一后代驺丑为闽越繇王。馀善不服,自立为王,汉武帝才从闽越划出一部分地方另封馀善为东越王。
南越方面,赵佗后裔世袭为王,其孙赵胡为第二任,曾孙婴齐为第三任。婴齐未接王位时曾到汉朝都城当人质,娶邯郸女蓼氏为妻,接王位后,蓼氏成为王后,子赵兴接王位,尊蓼氏为太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南越丞丞相吕嘉(南越人)杀蓼氏及赵兴,立建德为王,出兵拒汉。翌年,汉武帝派兵讨伐,馀善上书自效,愿出兵八千助汉征伐南越,但他兵到揭阳(潮州)便以兵船受海风波所阻为理由,不再前进,暗中与南越勾结。
传说,汉军攻破番禺城以后,引兵回击东越,破蒲葵关而入。此说与史实不合,据《汉书》,汉楼船将军杨仆平定南越后,请命趁胜讨伐馀善,汉武帝只命他驻兵豫章(江西),防备馀善,而馀善素性先发制人,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出兵攻占武林、白沙、梅岭。汉武帝这才命令杨仆反攻,并令驻在会稽的横海将军韩说从海路攻入东越。馀善退守险要,后来被建成侯和闽越繇王居股合力击杀。
馀善与汉楼船将军争战的梅岭、武林、白沙在豫章(豫章,汉朝郡名,郡治在今南昌,辖境相当于今江西省,广义的豫章指江西,狭义的豫章指南昌)。唐朝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司马贞为《史记》作《索隐》,在《东越王列传》里注道:“豫章(南昌)三十里有梅岭,在洪崖山足,当古驿道。”“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阳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坑,东南八十里有武阳亭,亭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当闽越京道。”可见元封元年所进行的是一场作为战略要地的豫章郡治(今南昌)的争夺战。馀善既是从闽越分出一部分地方封为东越王,其封地当在闽越东部,即闽东、闽北、浙南、浙西一带,闽南、闽西则仍是闽越繇王封地。馀善兵到揭阳(潮州)走的是海路,否则,“海风波所阻”便不可作为不能继续向番禺(广州)前进的理由。他退兵也必循原来航路回去,所以一去一返都没有经过蒲葵关。他出兵攻豫章,必从闽北出去,汉兵反攻,陆路也必入闽北,海路入闽东。馀善的都城在仙霞岭泉山,在闽北有六座拒汉城堡,即邵武阪城,建阳大潭城,浦城县的浦城和汉阳城、临江城,武夷山市的古粤城,经考古学家证实为汉军与馀善战争之城。“汉兵破蒲葵关而入”之说不确。
二、“越王城”与“赵佗故垒”
南太武山(从前属漳浦县二十三都,今属龙海市港尾镇)曾有一处古城遗址,南宋淳祐《漳州志》记载当时传说为“越王建德抗击秦兵”的城堡,这牛头不对马嘴。因为建德是末代南越王,生活于汉武帝时代而不在秦。要说真有抗击秦兵的越王城,应是“越佗故垒”。赵佗生活于秦汉之际,是第一代南越王,传到建德已是第五代,时间相距近百年。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南越2相(南越人)吕嘉杀蓼氏及赵兴,立建德为王,出兵拒汉。五年,汉武帝派兵征讨,六年,讨平。即是说,建德抗拒的是汉兵,不是秦兵。南太武山之城,地点也与南越对不上号。南宋漳州史学家蔡如松对当时所流传的地方史之谬误提出“十辨”,其中指出“建德在南越,其城守在番禺(广州)而不在闽。”但明、清地方志编修者宁信建德在南太武山建城拒汉是实,诡辩道:“南越为汉兵所破,建德逃入海上飘摇入闽,理固有之,不必疑也。”、然而对照正史,对这种说法还是不能无疑,据《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前汉书》卷九五《南粤传》有同样记载):元鼎六年冬,汉伏波将军路博德于犁旦(黎明)攻破番禺城时,“吕嘉、建德已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问所得降者贵人,以知吕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原南越)校尉司马苏弘得建德,封为海常候;越郎(原南越郎官)孙都稽得嘉,封临蔡侯。”福建南太武山在广州之东而不在西,吕嘉与建德既是“以船西去”,便不是“飘摇入闽”来到南太武山。何况,伏波将军路博德既是从降臣口中得知吕嘉、建德的逃亡地点,即派兵追捕,又是由南越旧臣俘获吕嘉、建德来献,因功得封侯之位,便不可能再有建德逃到南太武山建城拒汉之事。
“赵佗故垒”在漳州最早的地方志宋祥符四年所纂《漳州图经》里有记载。可惜《图经》已失传,只遗留《序》一篇,是宋代著名藏书家吴与所写,对古迹略有记述,其中说到“赵佗故垒,越王古城,营头之雉堞休然,岭下之遗基可识。”但只凭这寥寥几字,不知“赵佗故垒”与“越王古城”是同一城堡还是一垒一城。按“岭下之遗基可识”句,可知城在岭下而不在山上,那便不是南太武山的所谓越王城。或可理解为山上有垒,山下有城。南越在广东,赵佗怎么将城堡建到现在属于福建的漳州地区来。我认为可从《漳州图经·序》开头的话来找根据。《序》开头说“按本州在禹贡为杨州之南境,周为七闽之地,秦、汉为东、南二粤之地(“粤”通“越”),汉武平粤,为东会稽冶县并南海揭阳之地,晋、宋以来为晋安、义安二郡之地。”在秦以前,今漳州地区一部分(北部)属闽越,一部分(南部)属南越。秦朝划分闽越为闽中郡,南越分设南海、桂林、象三郡。闽越与南越地域广阔,而朝廷鞭长莫及,地方势力互相兼并。赵佗初任龙川县令,建县城名曰佗城。龙川是秦代南海郡最接近今漳州地区的县份,辖地包括汉代的揭阳县(今潮州),当时县界现在不清楚,但可从漳州“秦汉为东南二粤地”这话推知,今漳州南境必属龙川县。赵佗以善扩展辖地著称,而闽越“为秦始皇所不取”(只给闽越领袖驺无诸一个“闽中郡长”虚衔,没有派兵派官来),赵佗的势力可能发展到今漳州地区许多地方。后来他任南海郡尉,并且兼并了南海、桂林、象三郡,引兵自立,引起秦始皇出兵讨伐,他在今漳州地区建城堡抗拒秦兵,这种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漳州图经·序》没有说明“赵佗故垒、越王古城”遗址具体地点,现在还是不能肯定“赵佗故垒”便是南太武山“越王城”。
三、揭开“越王潭”的神秘面纱
梁山下绥安溪有一口深潭,在天气变化时能发出声响,人们以它为将要下雨的徵候,传说那便是“越王潭”。旧《漳浦县志》引据刘宋沈怀远所著《南越志》:“绥安县北有连山(梁山),昔越王建德伐木为船,其大千石,以童男女三千人举之,既而人船俱坠于潭……”。沈怀远并作《次绥安》诗,中有“馀善既辞师,建德乃伐木,番禺竟灰烬,冶南亦论覆”之句,指汉武帝讨平东越王馀善和南越王建德的史事。但所说建德在番禺城破之时逃到梁山下伐木造船之事,与“建德在南太武山建城拒汉”之说一样,与正史“建德以船西去”的记载不符。何况随建德逃亡者只数百人,便不可能有三千童男女共举大船。此说“建德与童男女三千人与船同沉潭底”不同于正史所载“建德被其旧部下俘获献给汉军”。沈怀远生活在刘宋时代,距离汉武帝平东、南二越时已五百多年,他是根据传说记述,应以汉朝太史令司马迁所作《史记》为可信。旧县志又说越王潭上“时闻拊船有唱唤督进之声,往往有青牛驰而与船俱见,盖神灵之事也。”那无非是将风吹水动之声附会于越王建德和三千童男女的神灵活现;所谓“青牛”,始自唐李郢的诗句“越王潭上见青牛”,那时可能常有野牛在那里出现。
按历史情况,今漳州地区不可能为末代南越王建德逃亡之地,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在此间建堡拒秦则属可能,但不知具体地点。按地理形势,梁山距广东较近,盘陀岭为闽越交通要冲,形势险要,较有可能是赵佗建堡之地,不过这只是推测,并无史书记载的依据。
林祥端
漳浦乌石天后宫在漳浦县旧镇镇浯江村紫薇山。天后宫后殿奠基于1992年5月,至1993年1月落成。1993年6月继建中殿,至1994年12月落成。天后宫坐东北向西南,背靠紫薇山,面对天马山,浯江从东边绕过,流入浮头湾,乌石景色尽收眼底,极得山水之灵秀。天后宫占地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规模宏敞,中殿飞檐流角,金碧交辉,气势雄伟壮丽。
一、林士章迎回妈祖的传说
乌石天后宫祀妈祖林默,漳浦林姓尊称妈祖为“姑婆祖”。乌石妈祖圣像据传为乌石探花林士章从莆田湄洲祖庙请回供奉的,原来建行宫在漳浦县城北门外官道旁。
关于林士章迎回妈祖的传说有以下几种:
(一)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林士章赴京参加会试,路过泉州洛阳桥,桥上遇一女子迎面而来,林士章左避右闪都被挡住去路,那位女子要林士章对对子,她出了上联:“鞋头绣菊,朝朝踏露蕊难开。”林士章一时对不出下联,那女子莞尔一笑,让开了路,顷刻不见踪影。林士章赴京会试后参加殿试,皇帝出一上联:“扇中画梅,日日摇风枝不动。”林士章灵机一动,顿时想起洛阳桥上那位女子的上联正好可做此对的下联,于是冲口念出:“鞋头绣菊,朝朝踏露蕊难开。”皇帝称赞说:“对得好,只是脂粉味浓些,卿真是探花才也!”林士章急忙跪下谢恩,因而高中探花。林士章归家省亲时,路过莆田湄州,瞻仰妈祖尊容,觉得绝似洛阳桥上的女子,顿时感悟,原来是妈祖点化他,于是就把湄洲妈祖请回家乡供奉。
(二)林士章任京官后,给假归家省亲,特地到湄洲参拜妈祖。先时,林士章祖父林竦务农勤耕,广种荔枝,采果晒制成干,用船运载到浙江温州、宁波出售。有一次,海上遇大风浪,船将翻复,望见一女神相助,幸免于难,事后得知此女神即湄洲妈祖显灵,于是就嘱咐林士章要到湄洲参拜妈祖。林士章此次参拜,就请回妈祖圣像归家供奉,以慰祖灵。
(三)林士章偕继配郑氏夫人自京城归家省亲,特地到湄洲参拜,请回妈祖供奉。郑夫人未嫁时,曾梦见一女神请她吃仙果,并令两侍女持夜明宝珠照路,说:“送夫人回府。”郑氏醒后,觉得身心清爽,神智倍增,依稀记得女神酷肖妈祖。后来,林士章原配柳氏逝世,娶郑氏为继室,诰封夫人。有一次,郑夫人进宫朝见太后,天色已晚,太后令两宫女持宫灯送归府。郑夫人深感妈祖的点化,就迎妈祖归家奉祀。到湄洲参拜时,预先刻一尊妈祖放在夫人轿中,进庙后采取掉包的方法,将庙中妈祖圣像换下来放在轿中,抬回家乡。至今,漳浦尚有“无锣无鼓,偷请妈祖”的民谚。
(四)万历九年(1581年),林士章致仕归家时,特地到湄洲参拜妈祖,请回圣像供奉。
二、探花林士章身世简介
林士章(1524—1600),字德斐,号璧东,漳浦县七都乌石大厅北平村(今旧镇镇浯江村大厅边北平)人。乌石林氏始祖林安,生长于福州长乐后市村。南宋景定年间,徙居漳浦县东关外安仁乡浯江保西径坊,子林进,“定居海云山下,因三山(福州古称)之乌石名为乌石”。这是为纪念祖地福州乌石山,所以取“乌石”为徙居地的名称,漳浦从此就有了地名“乌石”,并一直沿用至今。
自明洪武以来,乌石林氏逐渐发展兴盛,至嘉靖三十七年,科甲连登,人才辈出:族叔祖林纯一举人,族叔林功懋、林策、林一新俱进士,林一初、林一阳、林成纲俱举人;族兄林士宏、堂兄林楚俱举人。至此,乌石林氏已成为漳浦显赫的望族。林士章生长在这官宦家族的氛围中,深受其薰陶。
林士章祖父林竦,字迁瞻,号忍庵;父亲林烽,字世明,号省庵,虽世代务农,但也知书习礼,课子读书。林士章兄弟七人,他排行第五,因而以《孝经》篇目“士章第五”取名为士章,望其能忠孝传家之义。林士章自幼聪颖过人,读书紫薇山中的紫薇洞,诗文有大雅之风,福建提学朱衡“以国士遇之”。
嘉靖三十八年,林士章果然不负众望,一鸣惊人,联捷进士,殿试第一甲第三名,探花及第,名扬全国。初授翰林院编修,历官两京国子监祭酒,翰林院侍读学士,礼部左、右侍郎,经筵讲官,国史副总裁,终南京礼部尚书,万历皇帝御赐“忠爱”匾额。万历九年,致仕归家,过了近20年的村居生活。
三、迎回妈祖时间的推断
民间传说虽是虚构成分居多,但还是要以某些事实为依据,并非全是凭空捏造。现据有关史书、家乘和林士章墓志铭等资料,结合上面的传说,探讨林士章迎回妈祖的时间。
林士章自嘉靖三十八年探花及第后,长期在京城任职,其中,只有两次较短的时间在南京任国子监祭酒和礼部尚书。在任职期间,明确记载归家时间有4次:(一)嘉靖三十八年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照例给假回乡省亲,“竖旗拜祖”;(二)嘉靖四十一年,母丧,归家守制,至嘉靖四十五年,起复原官;(三)隆庆二年(1568年)十二月,父丧,再次归家守制,至隆庆六年,起任南京国子监祭酒;(四)万历九年五月,致仕归家。上述4次归家,其中,两次遭丁忧,都不可能去莆田迎妈祖,况且林士章原配柳氏也在嘉靖四十一年去世,在处理双重丧事后,迟至4年后才起复翰林院编修。隆庆二年,林士章升国子监司业。隆庆六年,林士章以久次起家,任南京国子监祭酒。万历元年(1573年),转调北京国子监祭酒时,双亲已逝世,无用给假省亲,且从南京到北京并无路过家乡。所以,此次转调,林士章没有归家。
嘉靖三十八年与万历九年两次归家与传说中迎回妈祖的时间相同。但嘉靖三十八年,林士章归家荣宗耀祖,正是显示自身价值的时刻,不会迎妈祖来冲淡的。况且,官方接送繁忙,无暇顾及迎奉妈祖之事;再者,如果于此时迎回妈祖,林士章尚未在县城建府第,应是把妈祖迎回乌石,这样,妈祖庙就该建在乌石,而不是建在漳浦县城。
万历九年五月,林士章致仕回乡,这最有可能是迎回妈祖的时间。万历二年,林士章升任礼部右侍郎,万历五年,转礼部左侍郎。但就在此年,权相张居正父丧“夺情”,林士章会同礼部尚书马自强,侍郎王锡爵上疏反对,因而得罪了张居正。万历八年,林士章任礼部侍郎已满6年,按例,京官任职6年即可考绩提升,然而,张居正暗中指使给事中、御史搜集材料,对林士章多次攻击、弹劾。万历八年十二月,林士章再次上疏引罪乞罢,皇帝不允许。万历九年正月,林士章与吏部尚书王国光、礼部尚书徐学谟,侍郎何雒等各以考察自陈。二月,林士章升南京礼部尚书。五月,“南京试御史徐金星论劾南礼部尚书林士章,太常卿张卤不堪祀典,乞赐罢斥。吏部复,士章原无显过,仍宜留用,卤屡经论列,似难展布。上令士章照旧供职,张卤回籍听用。已而,士章引疾乞致仕,许之。”林士章致仕时,年仅58岁,他正欲实现其忠君爱国的怀抱,然而,张居正专横跋扈到极点,言官的弹劾,使林士章不愿再旅险仕途,因此,“当飨用之方殷,遍乞身而勇退。”当时,林士章的心情是抑郁而沉重,但也感到无官一身轻,因而,他在回乡时到湄洲参拜妈祖,并请回奉祀,这完全符合他当时的心态。传说中的(二)、(三)没有说明具体时间,其为实现祖父迎妈祖的宿愿和按郑夫人的心愿请回妈祖奉祀,都可以做为致仕时请回妈祖的动机。
林士章迎回妈祖时,他的府第已建在县城多年,所以,就在县城建庙奉祀。
四、史书关于县城妈祖庙的记载
据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修纂的《漳浦县志》载:“天后庙二,一在北门外,一在南门外。后本兴化人,明封天妃,国朝晋封天后,祠庙沿海皆有之。”由此可知,康熙三十八年以前,漳浦县城北门外就有妈祖庙,但没有说明修建的时间。《漳浦县志》首修于明嘉靖九年(1530年),继修于万历七年(1579年)和三十三年(1605年),但这些志书现已无法看到。现存万历元年癸酉编纂《漳州府志》按各县进行编写,留下宝贵的资料。其中,有关漳浦县“宫庙”的记载:“漳浦县庙二所,灵慈庙,在县西北隅,即天妃庙;?湖庙在西门外。上二庙今废。”万历癸西《漳州府志》是根据嘉靖九年修的《漳浦县志》增修至隆庆六年。据此记载,漳浦县城只在西北隅有过一座名叫灵慈庙的妈祖庙(?湖庙所祀何神,这里不予探讨),但在嘉靖九年以前就倾圯荒废,至隆庆六年,尚未建新的妈祖庙,重建妈祖庙是万历元年以后的事。这样,林士章于万历九年迎回妈祖并在北门外原灵慈宫附近建庙奉祀,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五、妈祖庙为什么要建在北门外
林士章的府第称尚书府,建在县城南街城隍庙旁,迎回妈祖时为什么妈祖庙不建在附近的南门,却建在不近水滨的北门外?据传是迎回妈祖时,圣轿抬至北门外稍为休息,要进城时,圣轿竟抬不动,于是就在停轿处建庙。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妈祖庙建在北门外的原因有三点:
(一)已废灵慈庙在县城西北隅,在其旧址或附近建庙是符合其历史沿革,庙名仍沿古称为“灵慈庙”。
(二)北门外地势高坦,虽不在水滨,但背遥倚罗山,面对梁山诸峰,且地处南北交通之官道,人烟密集,人杰地灵,适宜建庙。
(三)万历间,城北是林姓聚居地,其中有三个官宦家族:(1)浦北林氏林埙家族。林埙,成化十二年岁贡,官至宁府长史,其家族衍居北门内外一带及东罗等地;(2)港头林氏林表家族。林表,成化五年进士,官至镇远知府,其孙林敬、玄孙林绍分别官至长沙知府和山东副使,在北街顶建“世大夫第”,其家族衍居北街顶一带;(3)新路林氏林梓家族。林梓,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官至通政使,位列九卿,其子林宰、林采分别官至兵部侍郎和广西副使,其家族称“十八顶纱帽”,是新兴的豪门巨族,衍居县城西北隅新路一带。这些林姓家族都奉祀妈祖,所以,林士章迎回妈祖时,建庙在北门外也就顺理成章。
北门外妈祖庙建在官道西侧,坐北向南,庙为三开间两进的土木结构,庙前有庭院,庭院东边建一座大门,正对官道,过往客商也都进庙参拜,香火旺盛。
在北门外建庙后,城南才从北门灵慈庙挂香、雕像,在南门外溪边兴建妈祖庙,坐南向北,面对南门外五凤桥。庙宇规制与灵慈庙相同,庙名为“金南水镇”。其建庙年代约于万历中期,现存原庙中石柱镌刻:“西湖蔡宗俊舍柱两条,祈求子孙荣盛者”、“西湖蔡宗传喜舍石柱一条,祈求子孙昌盛者。”由西湖蔡氏辈序:“大宗一而祚衍长”可知,舍石柱者与万历二十九年进士蔡宗禹同属“宗”字辈,为西湖蔡氏始祖直翁以下第五世。其时,传衍未繁,堂兄弟年龄相差无几,且舍石柱之事应在成家立业之后,所以,其舍石柱建庙年代约为万历中期,比北门外建庙稍迟些。南门外妈祖庙建在南门溪边,常遭大水淹没,鉴于此情况,建庙时设计,在庙的后墙妈祖殿两旁,自庙内地面用石条竖两个1.5米高的大石窗,当洪水泛滥时便于排涝,这成为“金南水镇”建筑的独特之处。
六、北门外妈祖庙残存干支纪年的考证
北门外妈祖庙历来有过多次重修,近年修整时,在壁画和画栋之间发现有戊子、已丑两个干支纪年,字迹依稀可辨。戊子和已丑是两个紧接的年份,每六十年重复出现,实际作画时间不一定前后两年相连,可能相隔六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自明万历九年至清光绪间,属戊子、已丑的年份有:(一)明万历十六、十七年(1588—1589);(二)清顺治五、六年(1648—1649);(三)康熙四十七、四十八年(1708—1709);(四)乾隆三十三、三十四年(1768—1769);(五)道光八、九年(1828—1829);(六)光绪十四、十五年(1888—1889)。在这些年份中,万历十六、十七年距林士章迎回妈祖时间已七、八年,林士章归家不久,为避县城喧嚣,在漳州城东北十里的流冈附近建长桥土城隐居,建妈祖庙应在未迁漳州时,不会迟至七、八年后才建庙;顺治五、六年,正值战乱时期,人心惶惶,民不聊生,无人顾及修庙之事;康熙四十七、四十八年,距万历九年已120多年,且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这时,妈祖庙应有一次大修。假若康熙间的修建只是上述纪年干支中的一个,那么,另一个纪年的修建应是上述乾隆、道光、光绪间的一个年份。当然,自乾隆以来,也会有不属戊子、已丑年进行修建的,如民国21年(1932年)曾有一次翻修,其岁次为壬申。
七、“有行宫没有圣像”与“有圣像没有行宫”的历史事实
北门外灵慈庙约于清代中后期改名慈后宫。原庙中有一对联:
灵在天上,世界达得大德;
慈为圣母,裔孙共感神恩。
对联首字嵌入“灵慈”两字,足见此联专为灵慈庙而作。对联中第三、四字,上下联分别嵌入“天上”、“圣母”字样,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封妈祖为“天上圣母”,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继封为“天后”。由此可知,此对联作于康熙十九年以后,庙名尚称为灵慈庙。至于改名为慈后宫是在妈祖封天后之后,取灵慈的“慈”,天后的“后”,名为慈后宫。
对联下联有“裔孙”两字。从广义来说,妈祖是宋代人,后人既尊为“妈祖”,也就都可称为她的裔孙;从狭义来说,应是指林姓子孙。北门一带虽为林姓聚居,但也有程、陈、刘等姓混居,因而,“裔孙”的含义应是广义与狭义并存。
上述对联在1984年重修后尚保留。南门妈祖庙移用此对联,把上联首字“灵”改为“后”,以表示区别。
世事沧桑,自明至清,漳浦县城城南、城北居民姓氏起了很大的变化。原有“南叶北林”之称,即城南叶厝巷同知叶穆、叶谐的家族和城北林埙、林表、林梓的家族。后来又有“南詹北程”之称,即城南叶姓至正德间,被御史詹惠家族所替代;城北的程姓至万历、天启间,出了大理寺丞程绍南、解元程样会,其家族也由弱而强。最后,至清代末年,各巨族都衰落,城南、城北已为各姓混居。
北门林姓最先式微的是林埙家族,自嘉靖十三年(1534年)林埙去世后,家道逐渐中落,至明末清初,浦北林氏大部分迁到东罗、麦园埔、上洞等地居住,至今,北门已没有浦北林氏;号称“十八顶纱帽”的新路林氏,至清初尚是一个大家族,然而,在康熙三十五至四十七年间,陈汝咸任漳浦知县,整顿赋役,澄清吏治,打击地方豪强,新路林氏首当其冲,曾有林家婢女讥笑陈汝咸“见狗也唱喏”的传说,从此一蹶不振,至今,县城已无其后裔;港头林氏在北街顶建“世大夫第”,至清朝虽尚保持大家族,但气派已不如从前。
与之相比,漳浦东关外林姓大为崛起,至清朝中期,林士章的祖籍乌石林氏已繁衍顶、下乌石五、六十个村子;路下林氏也繁衍几十个村子,这两个林姓大家族都崇奉北门外行宫的妈祖。除农历每年三月二十三日妈祖生日同时拜祭外,自二月至十一月,各地按自然村或地区轮流迎奉,称为“迎姑婆祖”或“迎妈祖”。这样,北门外行宫的妈祖就长期在乌石(浯江)、旧镇、赤土、深土、六鳌、霞美等地“行香”,至十二月才送回北门外行宫过年。约于清末民初,乌石林氏出于对妈祖的崇敬,有一年,把妈祖留在乌石大宗祠海云家庙(俗称“乌石大厅”)中过年。从此妈祖就不再回北门外行宫,行宫中只刻块妈祖圣牌奉祀。按“一神一庙”的惯例,北门外妈祖庙不可另雕圣像,而乌石也不可另建妈祖庙。因此,长期形成“北门有庙(行宫)无翁(圣像),乌石有翁(圣像)无庙(行宫)”的历史事实。
八、漳浦乌石天后宫创建及其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观念也随之改变。1984年,县城北门外妈祖庙重新修建时,就到乌石妈祖圣炉挂香回庙,另雕妈祖圣像供奉;1989年,衍居台湾的乌石宗亲林瑶棋、林瑞国等相继回家乡拜祖,得知乌石妈祖是四百多年前由探花林士章从湄洲迎回供奉的,至今,在乌石尚未建行宫,于是,与乌石乡亲商议建天后宫之事。
1992年,由林瑶棋、林瑞国等台胞捐献巨款,乌石宗亲及远近信士随之响应,各尽其力,并得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5月24日,举行行宫后殿奠基仪式,至1994年12月8日,中殿落成,行宫命名为“乌石天后宫”。自林士章于万历九年迎回妈祖建庙,庙的名称由灵慈庙而慈后宫而乌石天后宫,至此已历时414年。从此,妈祖在乌石有了行宫。
乌石天后宫建成有其深远的意义:
(一)结束了“北门有行宫没有圣像,乌石有圣像没有行宫”的历史;
(二)加强海峡两岸的团结和文化交流,促使祖国早日实现统一;
(三)扩大妈祖信仰的国际传播,促进世界妈祖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乌石天后宫规模宏伟壮观,居闽南妈祖庙之冠,可与闽中湄洲祖庙相媲美,远近香客络绎不绝,海外信士纷纷前来朝圣,乌石紫薇山成为朝圣与旅游的胜地。
史海淘廉
·高聿占·
漳浦历史上有不少科举出身的仕子,被朝廷派往各地当官,史志记载他们大多数能廉洁自律,政绩斐然,深受当地黎民爱戴。科举时代的官员并非完全清廉,史志隐恶扬善,用意在于鼓励人民向好的方面学习。这些先贤的高尚品德还是有现实教育意义的。兹摘抄部分以飨读者。
宋
林彦质,字彬叔。“历官州县皆有廉名”。“秩满乞归,卧游自适,幅巾野服,消涤世虑。捐金募植松于道,行者德之。”
高登,字彦先,号东溪。“任广西富川主簿兼贺州学事。秩满士民乞留。不获。相率馈钱五十万,不告姓名,白守曰:教授贫无以养,愿太守劝之受。登辞不可,请置书藏于学。”
明
俞文,字懋学。“督漕徐、淮间,诸漕帅用故事敛金百镒以馈。文却之。”“老疾乞归,过常郡,缙绅遮留,吏民攀送填咽,且醵为道里费。文觅小舟,夜亡去。”“家居四壁,敝衣蔬食,怡然自乐。”
杨武,字德毅。“屡聘为河南,山东,广东主考。”“道有私谒者,谕之。杨曰:以荐贤而以为私也,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其人负惭退。”
陈镡,字曰宣。授太原通判。“清慎自持”,“与士卒同甘苦,以廉能闻。民立石颂焉。”
叶穆,字式文。授汾州知州。“有犯死罪者,馈金五百求贷。叱之。”“致仕,家居茹蔬衣敝。”
吴超,字华越。授工部主事,监杭州税关。“关故利薮,超矢志奉公,羡余悉归公帑,不以自私。”改授徐州三年,“尤以清勤著誉”。迁广西参议,“益励晚节”。“致仕家居,淡泊自守,乡人重之”。
徐弼,字良佐,“擢廉州府同知,性劲直不能诡随,以冰蘖自持。卒之日,发其箧得《德政录》若干卷而已。
林文焕,“授户部主事,督税临清钞关,清操自励,升员外郎,家不增一瓦一椽。时入郡邑,徒步而已。”
林功懋,字以谦。任东莞知县时,“尝权税番舶,外番贿赂毫无所受。时,指挥王宠偕行,见功懋感叹曰:独文臣不爱钱乎!亦峻却之。”子林士弘,字仁甫,“奉使楚蜀之藩,馈遗一无所受。”
林一阳,字复夫。“迁唐府审理,去,民思之,立石纪政。归家谈道自乐”。平时自律“惟敬可以胜怠,惟勤可以补拙,惟俭可以养廉。”
王应显,字惟谟。“知秀水县,县治后圃多桃,盐之以佐饭。”“升户部主事,榷九江税,廉洁奉公。”“升浙江布政使,洁已奉公如为令时。”
林楚,字德春,号春斋。任雷州通判,“雷有珠池,在雷四载,不取一珠。”从侄林汝诏,字君纶。“授永州推官,以平恕清慎名”。
林缵振,字公悦。任工部主事。“岁终,库椽进羡金数百,曰:公合得之。缵振叱椽出。”
蔡时鼎,字台辅。授桐乡、元城二知县。“时鼎一以勤、慎、谦、约劝学为质。”“差视淮盐,疏列惠商裕课十事,次第举行。差向有例金,却不受,积之以为浚河之费。”
林茂桂,字德芬。“授深州知州,一意为民。归家后,其家居文酒相命,四壁萧然。人谓廉吏”。
蔡杲,字宏中。“授太仓知州,清白严介。先后官京邸五六载,栖止道院僧寮,一榻萧然。卒之日,贫无以殓。”
黄季成,任东阳县令,“邑素健讼,听断毕即遣去,不入锾金。擢工部主事,分管铸造局,局故繁琐,颇涉利窦。季成一以澹泊处之,禁绝常例。”
清
林绍祖,字衣德。任长沙醴陵县令。“何氏兄弟互控,请托千金,却不受,以至情感悟之。”“醴河多滩,有孙商者,舟次溺水死,亲检遗货计八千余金,驰其家人领取。用人参数觔为谢,却不受。”
谢天禄,字百和。“漳富商大贾,慕其行谊,不惜挥金延请为师,意所不屑,去之若浼。宗人以事羁于官,官知天禄清贫,欲为之德,微示其意。宗人以千金丐一言。岸然不屑也。”
蓝应元,字资仲。官礼部侍郎。“服官三十余年,囊空如洗。”这些先贤的高尚品德是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南宋末代小皇帝的传说与史实
·李林昌·
南宋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宋朝末代小皇帝赵昺在广东崖山败亡,民间将风物附会于宋帝昺的传说,自福建至广东被人们认为他南逃的路上不下二十多处,单漳浦、龙海一带就有:
一、嵩屿。传说,宋少帝从福州南下的船队因为泉州守将蒲寿庚降元,匆促离开泉州港,到鹭岛对岸时曾停留。那天是少帝诞辰,大臣们拥少帝上岸,人人朝拜,同声呼“嵩”,恭祝万岁,因而那地方叫嵩屿。
二、宋少帝的船队曾在南太武山下停留。有“太武香薷”的传说,说少帝中暑,服香薷而愈。
三、马口,地处南溪中游南岸,小船可上达山区,下通海口,陆路是闽粤交通要冲,形势险要。传说,宋少帝曾暂驻跸,开科取士,尚未揭榜而元兵追来,大臣们拥少帝继续南逃,投考的士子们拦住御辇,要求放榜,少帝传旨尽赐进士,用树枝将榜文划在溪边沙滩上。因此,漳浦读书人无论有无功名,在葬礼的“铭旌”和墓碑及家中所祀灵牌上,都可援此例标上“例赐进士”衔头。妇女则一律标“例赠孺人”衔头,据传,宋少帝流亡到漳浦时,他的母亲杨太后独居无聊,要找当地妇女闲谈,大臣说“太后不可接见没有封爵的妇女”,太后便传下懿旨:“此地妇女尽赐孺人。”后代援例,因此处处已嫁妇女之墓的石碑上皆标有“例赠孺人”四字,其家中神牌上亦然。
四、梁山封螺。传说,宋帝昺曾避难梁山,肚子饿了便在山涧捕螺充饥。吃螺要先敲掉螺尾,然后用口吮吸,螺肉便落入口中。宋帝昙吃了螺肉,将螺壳放回涧中,赐它再活。再活的螺没有尾巴,因为是皇帝敕封过的,所以叫封螺。(其实这是品种的特征,别处如龙海市颜厝镇的白云岩,芗城区的天宝山等地也有这种螺)。
五、盘陀岭顶路边有一口山泉,涓涓细流而大旱不竭。过路人在“盘陀岭上几盘陀”之后大都口干舌焦,用此泉止渴,更感甘冽异常,沁人心肺。传说宋帝昺当年流亡经过这里,用它止渴,喝后加以敕封,所以叫“帝昺泉”。
六、玉带泉。传说,宋帝昺御舟经过古雷海域,所带淡水已完,看看就要断炊,杨太后取少帝玉带投海中,祝祷道:“天未亡宋,愿海涌出甘泉。”果然在那玉带箍着的圈内,一股淡泉冲咸而出,叫做“玉带泉”,又叫“肚箍水”,从此腾涌不息。
这些故事说来娓娓动听,但与史实多有不合。按《宋史》,元军于德祐元年(1275年)攻陷临安府(杭州),俘年仅四岁(全皇后所生)的皇帝赵〓移往上都(今内蒙古多伦的石别苏木)。翌年(1276年),大臣们拥立杨淑妃所生的赵是(8岁)称帝于福州,尊杨淑妃为太后,改元景炎。俞修容所生的赵昺(6岁)封卫王。景炎三年(1278年)五月,赵昰病逝于广东吴川之南的海岛碙州,元帅张世杰、丞相陆秀夫拥立越昺为帝,改无祥兴。祥兴二年(1279年)二月,败亡于新会县南的崖山。据此,在福建境内流亡的宋少帝是赵是而非赵昺。这一支宋朝残馀力量还有庞大的船队和数万大军,航海南下广东,在沿海的嵩屿、南太武山下、古雷头等处可能停靠,而不会在梁山打游击。诸如“梁山封螺”,盘陀岭“帝昺井”等传说无非附会。说皇帝泡饮过的茶叶遗弃在古雷山长出茶树,说皇帝的玉带抛在海上能涌出淡水,如果宋朝末代皇帝有如此神力,何至于亡国?
宋帝昺在马口建行宫开科取士之说有很多人相信,因为那里确有一座小石城,城门左边有一个传说为“皇帝殿”的天然大石,一面刻卷书状浮雕,卷书上有“仙鹤瑞芝”四字,一面刻很多字,年久风化,模糊难辨,传说石下是宋商昺藏宝处,若能读完那些刻字,石门自开,可进内取宝。
民间传说总是不断添枝加叶,不断升级的。宋少帝在马口的传说先是“揭榜沙溪”,与南太武山下“驻跸处”同时流传。明末清初丹山名士张士楷有诗分别吟咏这两处传说(载康熙《漳浦县志》卷十八《艺文》)。
太武山
景炎遗迹杳闽关,驻跸犹传太武山。
御气海天馀白日,翠华烟雨没乌峦。
野花曾入慈元恨,国事深悲德祐间。
不是潇湘还苦竹,春风愁杀鹧鸪斑。
马口溪
(相传宋室南奔,策士于此,时野草齐花,溪山改色)
宋士临危贪释褐,公车射策满平沙。
阁将丞相千行泪,开遍春风百草花。
野殿宵衣能立国,宫袍画锦已无家。
空谈久被书生误,谁执干戈卫翠华?
明末清初传说的还只是马口溪“开科取士”故事,那时马口城未建。据康熙《漳浦县志》卷十五《建置志》记载:“马口城,在二十八都邑北尽境,康熙二年总兵王进攻建议,督院(福建总督)李率泰建,刻记石上,俯溪桥。原有千总驻于此。”康熙二年(1663年)正是清朝厉行“迁界”以拒郑成功之子郑经的时候(郑成功已病逝于台湾),马口地处水陆交通枢纽,建此城驻千总以资调度。在清朝统一台湾后,此城失去军事作用,变成一座空城,南来北往的人穿城而过,对此城为什么建在荒野有神秘之感,由于早有“马口溪开科取士”的传说,马口城便被附会为宋帝昺的行宫。
被传说为“皇帝殿”的马口大石与被传说为“行宫”的马口城已陆续被毁,现在无从考据其实物了。好在前人已有考据,留下资料,供后人参考。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福州协和大学福建文化研究会出版的《福建文化》第三卷第二十期是翁国梁写的《漳州史迹》专辑,其中写到宋帝是在马口的传说:“帝昺当时虽被元军节节追赶,但跟他走的皇族、官僚、兵士、平民不下数十万人,到了马口桥地方,想暂时居住,就起了一座皇宫,同小城一样,纵横数百步,东北靠山,南北开了二个宫门,南门石额刻寅禧二字,北门石额刻怀远二字。……宫殿今虽倒塌,但宫门及石额尚存,行旅往来,皆穿宫门而过。在宫门左边,有巨石作三角形,一面刻“仙鹤瑞芝”及卷书之状,一面刻字很多,但多残缺,乡人传说,刻鹤芝者乃石门,内为宋帝昺藏宝之所,若能将石上之字读完,则石门自开,可以入内取宝。最近有人就石摩挲,约略认得数十字,就旧本《福建通志》校对,乃知石上所刻为宋黄惠三十三桥记,因为自龙溪至漳浦大路有桥三十三座也。事在帝昺之前,乡人藏宝之说虽属附会,然亦可见普通之心理。(李林昌注:《黄惠三十三桥记》应为《黄木熏三十五桥记》,记载南宋庆元四年(1198年)太府寺丞知漳州傅伯成领导建设自漳州南谯门至漳浦三十五座石桥的功绩,比宋帝昺早80年。该碑记自己写明刻在甘棠路边天然大石上。甘棠是马口原地名,宋代设甘棠驿)。翁国梁虽然因为没有考据马口城的建城时间为康熙二年而误信马口城为宋帝昺行宫,但给后人留下实见资料,证实所谓皇帝殿的文字石刻实际就是南宋庆元四年黄櫄所作《三十五桥记》。
“越王古迹”的传说与史实
·李林昌·
一、蒲葵关是否发生过汉朝与东越的战争?
见于史志记载,今有具体地点可觅的漳浦最古古迹是盘陀岭上的蒲葵关。康熙《漳浦县志》卷十九《古迹》载为“汉南越故关”引据南宋淳祐《漳州志》记其地点“在驿西南一舍”,“驿”指设在漳浦县治所在地的仙云驿,“一舍”为30里,《康熙志》说“关当作邑之南今盘陀岭是也”。《读史方舆纪要》按《淳祐志》之说认为是“汉初南越所置关也。”《舆地纪胜》说为“东南二越界”。
“东越”应作“闽越”较为准确,“东越”只是“闽越”的东北部分,这在下面就会说到。闽越与南越同是汉的诸侯国之一。盘陀岭是怎样成为闽越与南越的分界线的?
闽越的地域即古“七闽”地,包括今福建全省及浙江南部、西部和广东东部、北部若干地方,原有闽族七个部落,自公元前644年周武王姬发出兵打败商朝的无道暴君纣王,建立周朝,七闽归服于周朝。春秋时代(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67年),七闽属越国势力范围,越国为周朝十二个主要诸侯国之一。周朝的统驭力量逐渐削弱,大诸侯国兼并小诸侯国,自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代。曾被吴国打败的越国后来打败吴国,称霸南方。越王勾践传到第六代孙无疆,被楚国征服。越人从浙江向闽地转移,逐渐与闽族人融合成闽越族。秦始皇统一全国,废封建,置郡县,实行中央集权制。在闽地成立闽中郡。但秦始皇没有派官派兵到闽地,只是废去勾践后代邹无诸的闽越王称号,降为闽中郡长,实际仍由邹无诸统治闽地。后来邹无诸出兵参加推翻秦朝的战争,在楚、汉战争中站在汉的一边。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封无诸为闽越王。后划出闽越国南部,现今闽粤交界毗连处一带,分封无诸另一后代邹织为南海王。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再划出闽越国北部,现浙闽交界毗连处一带,分封无诸又一后代驺摇为东海王。
南越的地域包括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一带。秦始皇派兵带同大量中原人民进入,建立南海(今广东)、桂林(今广西)、象(今越南北部)三郡。河北真定人赵佗带去的中原人最多,军事力量雄厚,由龙川县令升任南海郡尉,于秦末兼并了南海、桂林、象三郡,拥兵自立。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封赵佗为南越王。
南海王最先反汉,被汉武帝迁往上淦(今江西靖江县),其在闽粤交界毗连处的封地就被南越和闽越所瓜分,其分界线就在盘陀岭,当时岭上有很多蒲葵树,叫做蒲葵岗,关隘称蒲葵关。
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驺逞用武力迫使东海王迁民于江淮间,占领了浙南浙西一带地方,又出兵攻南越,招致汉武帝出兵讨伐,邹逞之弟馀善杀驺逞,投降汉朝。汉武帝改封没有参加叛乱的无诸另一后代驺丑为闽越繇王。馀善不服,自立为王,汉武帝才从闽越划出一部分地方另封馀善为东越王。
南越方面,赵佗后裔世袭为王,其孙赵胡为第二任,曾孙婴齐为第三任。婴齐未接王位时曾到汉朝都城当人质,娶邯郸女蓼氏为妻,接王位后,蓼氏成为王后,子赵兴接王位,尊蓼氏为太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南越丞丞相吕嘉(南越人)杀蓼氏及赵兴,立建德为王,出兵拒汉。翌年,汉武帝派兵讨伐,馀善上书自效,愿出兵八千助汉征伐南越,但他兵到揭阳(潮州)便以兵船受海风波所阻为理由,不再前进,暗中与南越勾结。
传说,汉军攻破番禺城以后,引兵回击东越,破蒲葵关而入。此说与史实不合,据《汉书》,汉楼船将军杨仆平定南越后,请命趁胜讨伐馀善,汉武帝只命他驻兵豫章(江西),防备馀善,而馀善素性先发制人,于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出兵攻占武林、白沙、梅岭。汉武帝这才命令杨仆反攻,并令驻在会稽的横海将军韩说从海路攻入东越。馀善退守险要,后来被建成侯和闽越繇王居股合力击杀。
馀善与汉楼船将军争战的梅岭、武林、白沙在豫章(豫章,汉朝郡名,郡治在今南昌,辖境相当于今江西省,广义的豫章指江西,狭义的豫章指南昌)。唐朝国子博士,弘文馆学士司马贞为《史记》作《索隐》,在《东越王列传》里注道:“豫章(南昌)三十里有梅岭,在洪崖山足,当古驿道。”“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阳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坑,东南八十里有武阳亭,亭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当闽越京道。”可见元封元年所进行的是一场作为战略要地的豫章郡治(今南昌)的争夺战。馀善既是从闽越分出一部分地方封为东越王,其封地当在闽越东部,即闽东、闽北、浙南、浙西一带,闽南、闽西则仍是闽越繇王封地。馀善兵到揭阳(潮州)走的是海路,否则,“海风波所阻”便不可作为不能继续向番禺(广州)前进的理由。他退兵也必循原来航路回去,所以一去一返都没有经过蒲葵关。他出兵攻豫章,必从闽北出去,汉兵反攻,陆路也必入闽北,海路入闽东。馀善的都城在仙霞岭泉山,在闽北有六座拒汉城堡,即邵武阪城,建阳大潭城,浦城县的浦城和汉阳城、临江城,武夷山市的古粤城,经考古学家证实为汉军与馀善战争之城。“汉兵破蒲葵关而入”之说不确。
二、“越王城”与“赵佗故垒”
南太武山(从前属漳浦县二十三都,今属龙海市港尾镇)曾有一处古城遗址,南宋淳祐《漳州志》记载当时传说为“越王建德抗击秦兵”的城堡,这牛头不对马嘴。因为建德是末代南越王,生活于汉武帝时代而不在秦。要说真有抗击秦兵的越王城,应是“越佗故垒”。赵佗生活于秦汉之际,是第一代南越王,传到建德已是第五代,时间相距近百年。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南越2相(南越人)吕嘉杀蓼氏及赵兴,立建德为王,出兵拒汉。五年,汉武帝派兵征讨,六年,讨平。即是说,建德抗拒的是汉兵,不是秦兵。南太武山之城,地点也与南越对不上号。南宋漳州史学家蔡如松对当时所流传的地方史之谬误提出“十辨”,其中指出“建德在南越,其城守在番禺(广州)而不在闽。”但明、清地方志编修者宁信建德在南太武山建城拒汉是实,诡辩道:“南越为汉兵所破,建德逃入海上飘摇入闽,理固有之,不必疑也。”、然而对照正史,对这种说法还是不能无疑,据《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前汉书》卷九五《南粤传》有同样记载):元鼎六年冬,汉伏波将军路博德于犁旦(黎明)攻破番禺城时,“吕嘉、建德已夜与其属数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问所得降者贵人,以知吕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原南越)校尉司马苏弘得建德,封为海常候;越郎(原南越郎官)孙都稽得嘉,封临蔡侯。”福建南太武山在广州之东而不在西,吕嘉与建德既是“以船西去”,便不是“飘摇入闽”来到南太武山。何况,伏波将军路博德既是从降臣口中得知吕嘉、建德的逃亡地点,即派兵追捕,又是由南越旧臣俘获吕嘉、建德来献,因功得封侯之位,便不可能再有建德逃到南太武山建城拒汉之事。
“赵佗故垒”在漳州最早的地方志宋祥符四年所纂《漳州图经》里有记载。可惜《图经》已失传,只遗留《序》一篇,是宋代著名藏书家吴与所写,对古迹略有记述,其中说到“赵佗故垒,越王古城,营头之雉堞休然,岭下之遗基可识。”但只凭这寥寥几字,不知“赵佗故垒”与“越王古城”是同一城堡还是一垒一城。按“岭下之遗基可识”句,可知城在岭下而不在山上,那便不是南太武山的所谓越王城。或可理解为山上有垒,山下有城。南越在广东,赵佗怎么将城堡建到现在属于福建的漳州地区来。我认为可从《漳州图经·序》开头的话来找根据。《序》开头说“按本州在禹贡为杨州之南境,周为七闽之地,秦、汉为东、南二粤之地(“粤”通“越”),汉武平粤,为东会稽冶县并南海揭阳之地,晋、宋以来为晋安、义安二郡之地。”在秦以前,今漳州地区一部分(北部)属闽越,一部分(南部)属南越。秦朝划分闽越为闽中郡,南越分设南海、桂林、象三郡。闽越与南越地域广阔,而朝廷鞭长莫及,地方势力互相兼并。赵佗初任龙川县令,建县城名曰佗城。龙川是秦代南海郡最接近今漳州地区的县份,辖地包括汉代的揭阳县(今潮州),当时县界现在不清楚,但可从漳州“秦汉为东南二粤地”这话推知,今漳州南境必属龙川县。赵佗以善扩展辖地著称,而闽越“为秦始皇所不取”(只给闽越领袖驺无诸一个“闽中郡长”虚衔,没有派兵派官来),赵佗的势力可能发展到今漳州地区许多地方。后来他任南海郡尉,并且兼并了南海、桂林、象三郡,引兵自立,引起秦始皇出兵讨伐,他在今漳州地区建城堡抗拒秦兵,这种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漳州图经·序》没有说明“赵佗故垒、越王古城”遗址具体地点,现在还是不能肯定“赵佗故垒”便是南太武山“越王城”。
三、揭开“越王潭”的神秘面纱
梁山下绥安溪有一口深潭,在天气变化时能发出声响,人们以它为将要下雨的徵候,传说那便是“越王潭”。旧《漳浦县志》引据刘宋沈怀远所著《南越志》:“绥安县北有连山(梁山),昔越王建德伐木为船,其大千石,以童男女三千人举之,既而人船俱坠于潭……”。沈怀远并作《次绥安》诗,中有“馀善既辞师,建德乃伐木,番禺竟灰烬,冶南亦论覆”之句,指汉武帝讨平东越王馀善和南越王建德的史事。但所说建德在番禺城破之时逃到梁山下伐木造船之事,与“建德在南太武山建城拒汉”之说一样,与正史“建德以船西去”的记载不符。何况随建德逃亡者只数百人,便不可能有三千童男女共举大船。此说“建德与童男女三千人与船同沉潭底”不同于正史所载“建德被其旧部下俘获献给汉军”。沈怀远生活在刘宋时代,距离汉武帝平东、南二越时已五百多年,他是根据传说记述,应以汉朝太史令司马迁所作《史记》为可信。旧县志又说越王潭上“时闻拊船有唱唤督进之声,往往有青牛驰而与船俱见,盖神灵之事也。”那无非是将风吹水动之声附会于越王建德和三千童男女的神灵活现;所谓“青牛”,始自唐李郢的诗句“越王潭上见青牛”,那时可能常有野牛在那里出现。
按历史情况,今漳州地区不可能为末代南越王建德逃亡之地,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在此间建堡拒秦则属可能,但不知具体地点。按地理形势,梁山距广东较近,盘陀岭为闽越交通要冲,形势险要,较有可能是赵佗建堡之地,不过这只是推测,并无史书记载的依据。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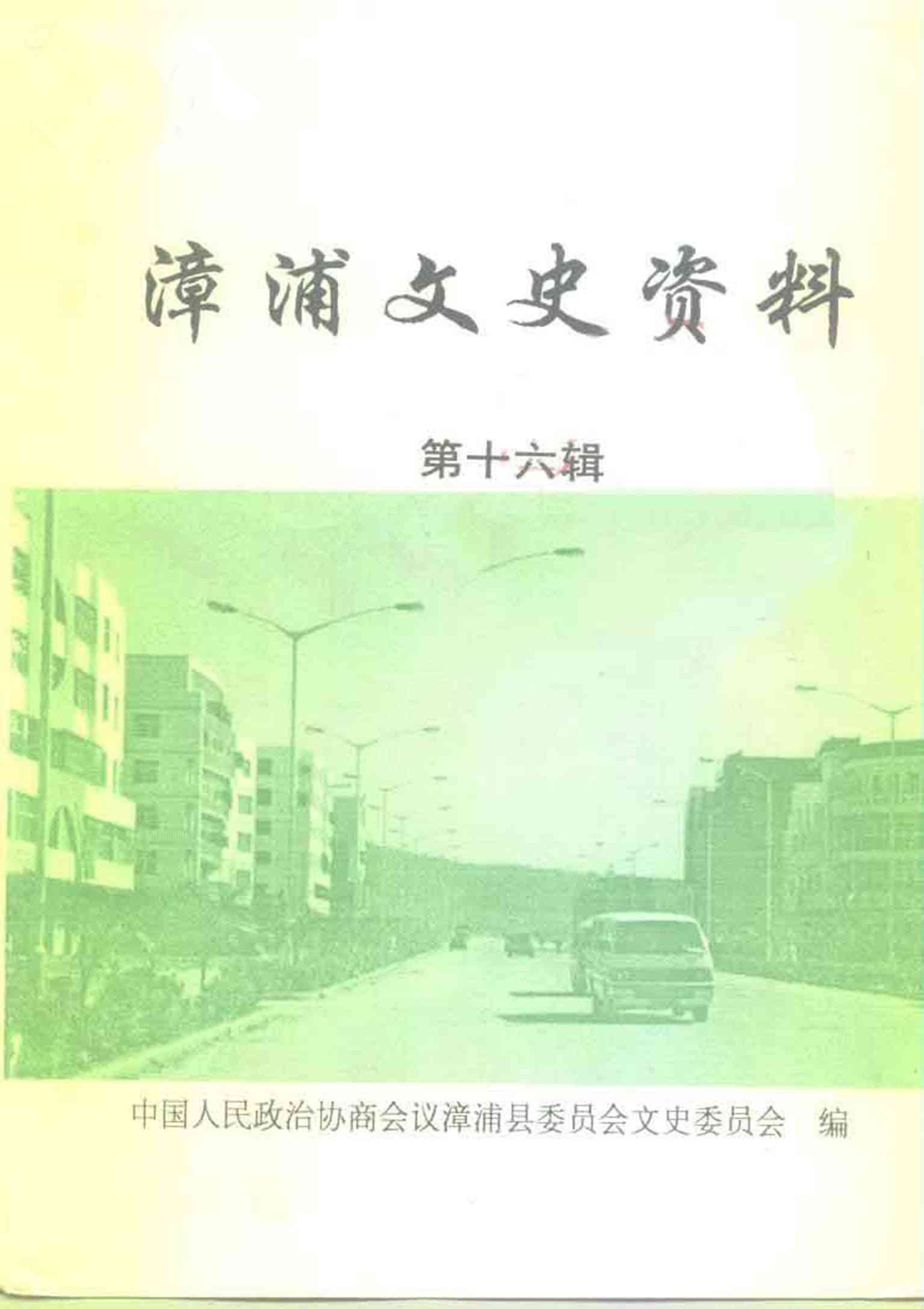
相关地名
漳浦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