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 内容出处: | 《漳浦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30000821 |
| 颗粒名称: | 史海钩沉 |
| 分类号: | K295.7 |
| 页数: | 16 |
| 页码: | 180-195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漳浦县的地方史,其中包括了两个绥安县、明代漳浦的倭寇祸患、林埙不依附奸王等。 |
| 关键词: | 漳浦县 地方史 |
内容
两个绥安县
·李林昌·
历史上有六个绥安县,地点和兴废时间各不相同。其中有两个绥安县,虽然兴废时间不同,建县时不同属一郡,但现在同属于福建省,容易混淆,有必要将这两个绥安县的建县历史背景、县域范围、县治地点、历史沿革等的不同情况列出对照,以便一目了然。
福建的开发是自北而南的。东汉末年,孙策(后为其弟孙权)割据东南一带,五次派兵入闽,征服了地方势力(少数民族),派一员侯官镇驻今之福州(原设冶县已名存实亡),后来“侯官”成为行政区域名称,属会稽郡管辖。侯官管辖范围主要在闽东、闽北一带,对于闽南、闽西还是鞭长莫及。孙氏未称帝,还是沿用汉献帝“建安”年号,于建安初年分出侯官的北乡(闽北)设置建安(今建瓯)、南平(今南平)、汉兴(今浦城)3县。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析建安县的桐乡设置建平县(今建阳),及至“三国”局面形成,孙权之孙孙休(景帝)于吴永安三年(公元260设立建安郡,郡治在建安县,即今建瓯,除辖原有侯官县、建安县,改汉兴为吴兴县,从南平分设建平县,析建安县校乡分设将乐县,从校乡西偏分设绥安县,又增置昭武县(晋避司马昭讳改名邵武),东平县(未详),在闽南增设东安县(县治在今南安丰州,晋改名晋安县,隋改名南安县)共10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从建安郡分出侯官、东安二县设立晋安郡,郡治在今福州。这时,龙溪(今芗城区及龙海市一部分)、兰水(今南靖)末设县,地属东安县管辖;现今的漳浦至诏安一带也未设县,地属南海郡(广东)的揭阳县管辖。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6年)从南海郡分设东官郡(郡治在今广东宝安县西南头镇)。
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建安郡的绥安县改名绥城县。
义熙九年(公元413年)从东官郡分设义安郡,郡治设海阳,即今广东潮安县东北。义安郡辖海阳、海宁、潮阳、义招、绥安5县。这个绥安县就是漳浦县前身的绥安县。
南北朝的梁大同六年(公元540年)从晋安郡分设南安郡,从南安郡的南安县分设龙溪县和兰水县,辖九龙江北、西二溪流域一带。
隋朝裁并许多郡县。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撤销绥城县建制,将其地并归郡武县管辖。开皇二十二年(公元602年)将建安、晋安、南安3郡合并为建安一郡,将全闽各县合并为建安、闽、南安、龙溪4县,兰水、绥安二县并入龙溪县(一说大业三年绥安并入龙溪县)。从此,故绥安县地(包括漳浦、云霄、东山、诏安、平和一带)从广东方面移归建安郡(今福建)管辖。
唐朝起,州(郡)县逐渐增设(与本文无关的略去不谈)。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复设绥城县。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又撤销绥城县,将其地并属邵武县。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将故绥城县地分设黄连、归化2镇,是建宁、泰宁、宁化3县的前身。2镇升为3县的经过:唐开元十三年(726年)置黄连县,天宝元年(742年)改为宁化县。乾符五年(公元878年)设建宁军,五代南唐改为永安镇,又改为永安场,宋朝建隆元年(公元960年)福建尚在南唐管辖下,升永安场为建宁县。在设建宁县之前,南唐于中兴元年(公元958年)升归化场为归化县,宋朝元珰元年(公元1086年)改为泰宁县。
隋朝并入龙溪县的绥安县故地,于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设立漳州和所属漳浦、怀思二县,怀思置在漳江南,漳浦置在漳江北,附州为县。(漳江旧名漳水,明、清府县志都记载:漳水自西林出,海水自铜山海门入,清浊合流有章。)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怀思并入漳浦县。同时,将龙溪县从泉州划归漳州管辖。漳州州治及漳浦县治于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从漳江北移设于李澳川,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州治移设龙溪,漳浦县治仍旧。以后,漳浦县于元朝至治年间(约1321年)划出西部合龙溪、龙岩二县部份地方设南胜县(后改为南靖县),明朝正德十三年(1518年)南靖分设平和县。嘉靖九年(1530年)漳浦县再分出南部设诏安县,隆庆元年(1567年)再分出东北部合龙溪县沿海地方设立海澄县,清嘉庆三年(1798年)再分出第六都设云霄厅(民国二年改县),东山县则于民国五年从诏安分设。
总之,漳浦县前身的绥安县地包括今漳浦、云霄、诏安、东山、平和等地,设立于三国吴永安三年的绥安县则已于东晋义熙元年改名为绥城县,以后分设建宁、泰宁、宁化3县。那个绥安县(绥城县)县治在建宁城西3里许,属于建安郡,由于建安郡后来改名建州,所以康熙《漳浦县志》称其为“建州之绥安”,此外,别无建置于吴水安元年的“建立漳州的绥安”。(康熙《漳浦县志》注文中“吴永安元年析建安校乡西偏置绥安县”与《八闽通志》所说“吴永安三年析建安校乡西偏置绥安县”同是一个绥安县,不同古籍记载同一个县的建置时间相差两年是常有的事。无3年间同在建安县校乡西偏设两个绥安县之理;将它作为漳浦县前身的绥安县更无理由,因为漳浦不在闽北与江西交界处的建安县校乡西偏,而在闽南与粤东毗连处。
显然,明万历《漳州府志》说“漳浦吴曰绥安、晋曰绥城”是将建宁县前身的绥安县(绥城县)的建县时间误为漳浦县前身绥安县的建县时间。万历《漳浦县志》也有同样错误。康熙《漳州府志》和《漳浦县志》已经加以纠正,康熙《漳浦县志》在注文中说:“旧志载‘吴永安元年析建安校乡西偏置绥安县’乃建州之绥安,建州即今建宁也,误。”但康熙《漳浦县志》只说“绥安之为县,著于晋而废于隋”没有考据出建县的具体时间,说“不知何时建置”,还因为晋朝从建安郡分设晋安郡辖闽东南一带而误以为绥安县属于晋安郡。不过,比万历志祥实一些的是有一段注文:“又据潮阳志载,绥安属义安郡。漳浦八都有绥安溪,据广东志,大埔县西北一百二十里曰高昌山,其下有绥安溪,注云,一名梁山,漳浦县界。”又在同一部县志卷十九《杂志》的《古迹》里说“今八都有绥安溪,即县故址也。”这等于从认同广东志书关于绥安县属义安郡的记载里找到绥安县县治在八都(盘陀)的根据。康熙《漳浦县志》实际采取的是一种多说并存而有所侧重的方式。这部县志在卷十九《杂志》的《谈丛》里又说“潮阳志云,绥安晋属义安郡,即今云霄也。”
康熙修漳浦县志比明朝修志较为进步的做法,是集七名秀才协助两位缙绅修志,并由知县主持,不似万历修志只由三两个缙绅修篡,而且是以嘉靖九年只由一个进士主笔,两个庠生协助,以七个月完成的最早县志为基础。那部嘉靖县志的修篡方法是,采取《八闽通志》和《漳州府志》的资料,并“稽以传记,参以见闻,订讹补缺,增加修辑,门分类别,综核诠次”,由于人手、时间、资料等因素的制约,造成不少缺点,误以改名绥城县的绥安县为漳浦县前身的绥安县便是一例。康熙漳浦县修志人手比较多,时间比较充裕,参考资料比较丰富。但对一些事的记载多说并存,可能是修志人员看法不一致之故。记事截至清未的民国《福建通志.地理志》卷三《沿革》核对各种古籍,作出比较简明的记载:“漳浦县(在漳州府南少西,冲繁难,本冶县及南海郡地,晋义熙九年分东官(即东莞)立义安郡,置绥安县,隋开皇十二年并入龙溪,唐垂拱二年分南界地濒于漳水者置漳浦县,隶于漳州,开元四年徙治李澳川,县从之,二十九年省怀恩县入焉,贞元二年徙州治龙溪后以漳浦为属县,宋因之,元析地置南靖,明析地益海澄,益平和入诏安,清析地置云霄厅。”
这里顺便谈一谈我对绥安县治地点的看法:漳浦八都有绥安溪,成书干明弘治已酉(1489年)的《八闽通志》已经引据宋《漳州图经》加以记载,不是清康熙《漳浦县志》才有。八都即盘陀,而火田在六都,可见绥安溪即盘陀溪而不是火田溪。盘陀溪的上游有一段叫县前溪,县前溪的北面是温源溪,即宋《漳州图经》所载“唐嗣圣年间胡商康没遮洗浴处。”《八闽通志》和康熙《漳浦县志》都转载《漳州图经》这则记载,并载:“温源溪,在县西南八都境,两泉并出,一微暖,一极热,合流南入县前溪。”这两口温泉在今雀仔埔,其南为官陂,可见县前溪即今官陂那条溪,绥安县县署是建在后有温泉,前有清溪的地方,可能无建县城(至今未发现有实据可证明为绥安县城的古城遗址)。
参考资料:《八閊通志》、《福建通志》、《漳州府志》、《漳浦县志》、《建宁县志》、《泰宁县志》、《潮州府志》、《宋书.州县志》、隋书《地理志》。
明代漳浦的倭寇祸患
杨汉章
一、前言
倭寇,是以日本封建诸候、大商贾所支持的武士、浪人、失业流民等组成的,专门掠夺财富的一种海上强盗。它不仅阻挠着海上贸易的正常进行,而且向中国沿海直至内地省份骚扰;在北起辽宁,南至广东的数千里海岸线上,他们到处进扰,烧杀淫掠,犯下了滔天罪恶,给中国沿海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倭寇侵犯中国沿海地区,开始于元代至正年间,到明代更为严重,特别是嘉靖年间,猖獗到了极点。地处“闽南之徼”滨临大海的漳浦,在倭寇疯狂猖獗,肆意纵横的年代里,与闽浙其它沿海地区一样遭受惨烈的祸害。
二、明初漳浦的防倭措施
在明代开国之初的洪武二年,倭寇就已经“数掠苏州、崇明,杀略居民,劫夺货财,沿海之地皆患之。”①明太祖朱元璋决定加强东南沿海的国防力量,从洪武四年起,积极加强军事力量来防御倭寇的侵略,接着开始建设福建海防,据《明史》卷132《周德兴传》载,洪武二十年“命江夏候周德兴往福建滨海四郡,相视形势二卫所城不当要害者,移置之,民户三丁取一,以充戍卒,乃筑城一十六,增巡检司四十五,得卒万五千余人。”周德兴经略海上,于洪武二十一年置福建沿海五卫所指挥使司,在当时漳浦辖地设立镇海卫(今属龙海市),下分置陆鳌、铜山、悬钟三个守御千户所。陆鳌(今六鳌),“自乌石至于埭头西二十里沙岸通焉……其地为船停泊之所。”②驻官兵898名。铜山(今东山县)“闽海重地也,其辖北自金石,接于浯浯屿,南自梅岭,达于广。”③由钦依把总镇守,称为把总水寨,设官兵1141名,备战船46只。悬钟(今属诏安县)“当闽南尽处”,设官兵1103名,有哨船24只。这些卫所,互为倚角、各防险要,控制横屿、井仔湾等易为倭寇海盗啸聚的沿海小屿。此外,设置月屿、古雷、后葛、盘陀岭等巡检司,共设弓兵720名。另外“沿海地方相度地里,远近各置烟墩炮台……贼至举烽燧为号,以便防御。”④正是由于明初在漳浦地方实行了这些行之有效的防御措施,使得在明初很长一段时间时间内,倭寇屡有进犯漳浦,却难以得逞。
三、倭寇猖獗的内因
明太祖的防倭措施,使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倭寇都不能得到发展,但后来昏庸的统治者放松海防,造成倭寇侵犯的条件。
明王朝自宣德以后,政治日益腐败,贪污之风盛行,皇帝昏庸,耽于淫乐,不理朝政,权奸把持朝政,植党营私,打击陷害忠良,贿赂公行,闽浙地区海防废驰,再加上蒙古内侵,明朝君臣专重陆路边防,沿海军备,无人留意,卫所空虚,“又如战哨船,铜山寨二十只,见在止有一只……见在者俱称损坏未修,其余则称未造。”⑤克扣拖欠边卒粮饷,“又如漳州卫与镇海卫,官兵月粮少派三个月……其余多寡不等,无一卫一所开称不缺者。”⑥“以至士无斗志,纷纷逃脱,出现行伍失额,铜山水寨,寨军原额1822名,逃亡人数达1190名,仅剩370人,失缺65%;悬钟水寨,寨军原额1133名,逃亡人数达476人,剩下657人,失缺49%。⑦这样,一遇来,临时招募渔船,纠合民丁,号称防守,实际就是儿戏!
本地卫所无能,只好从外地调兵来御倭,然而那些“客兵”御寇无能,虐民有方,冒功请赏,遇到倭寇“则又逗留观望,直至贼去,乃稍尾其后焉,袭其余辎,猎其疲掳,掠其遗累,割其毙首,虚张战声,冒上功级,甚至掘已痊之尸,推独行之旅,掩守望之夫,戕创伤之羁,截其头颅,墨其面目,焚烧囟发,灭除纲痕,以为真倭而市功焉,不可必得则又下购,募以觅之,盖民当其时不死于贼,则死于兵矣!所过之地,鸡犬为虐,所止之处,门户为碎,至于贼方践蹂之后,复且大索一番,即贼所弃置不取者,兵尽收拾而贱鬻之矣!俗谓‘贼梳兵篦’,良有以也!贼去未俞舍,辄扬旗报捷,奏凯言归,诛求赍粮,需索赏搞,稍不如意,脱巾而呼!偶被汰还,群哨为乱,如往者邑北关外之变,几于缘城而入,可鉴已!”⑧
朝廷腐败,兵防松驰,官兵不但没有尽到剿倭保民的职责,反而虐扰人民,加上一些游民、奸商与倭寇勾结,为虎作伥,这就是东南沿海长朝遭受倭寇蹂躏的内因,漳浦的这些情况,是一个缩影。
四、倭寇在漳浦的侵略活动
倭祸初起,江浙首当其冲,受祸极烈。江浙为财赋之区,明政府不得不调重兵来守。嘉靖三十一年,王抒巡视浙闽,采纳名将俞大猷的建议:“备倭于陆,不如备之于海。”于是征调闽船,招募月港及嵩屿人民为水兵。海防的加强,给倭寇以沉重的打击。
倭寇在江浙受到挫折,便逐渐南窜,正如谢杰在《虔台倭纂》上卷《倭变》中所说的:“方吴越之多事也,闽独晏然,至是材臣名将,尽起吴浙。贼屡败衄,度可脱祸者惟闽耳。”于是,从嘉靖三十四年起,福建倭祸便有增无减,日益严重了。
随着倭祸从江浙南移至闽以来,漳浦的倭祸就逐渐频繁严重了,据《明世宗实录》卷四二八载:“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乙末(初四日),倭二百余人,犯镇海。”此后,漳浦频频受到倭寇的侵优和蹂躏。”嘉靖三十六年,倭寇六都;三十七年五月,倭寇盘陀水港,复移寇长桥;三十八年二月,倭寇县郊,驻溪南;十一月倭寇麦园埔;三十九年二月倭寇佛潭桥;四月倭寇驻峰山,纵掠溪南,后移驻无象铺;四十年二月倭入屿头月余,张琏陷壕浔(今官浔)土城,闰五月,饶寇袭陷镇海卫城;四十一年二月,张琏率倭寇入掠县郊。”⑨
倭寇的侵略行径是极其野蛮的,我们根本连想象也不敢想象,据《明史记事本末》记载:“官庾民舍,焚劫掠夺,少壮掘冢墓,束婴孩竿上,沃以沸汤,视其哭号,拍手笑乐,得孕妇,卜度男女,刳视中否,以胜负饮酒,积骸如陵。”实在是野蛮得令人发指!
在漳浦的大地上,这些灭绝人性的强盗,极尽其烧杀淫掠之能事,见人就杀,见女就淫。许多烈女贞妇,不甘受辱,以死洁身的事例,在县志的《闺阁》卷中占了极大的篇幅,这从某种意义上正反映了倭寇的血腥罪恶。⑩
倭寇疯狂屠杀漳浦人民的手段,罄竹难书,残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对活人进行疯狂屠杀的同时,连死人的枯骨也不放过,他们在围攻县城时,“隆冬盛暑不休……多发人冢,携骸勒赎。”⑪结果“民不忍去枯骨,多自发冢取棺藏之,生民荼毒至此极矣!”⑫
频繁的倭寇侵扰,给漳浦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漳浦人民备受流离失所之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嘉靖三十四年至此(嘉靖四十一年),六七岁间,村无完舍,民无定居,往往逃匿山中,破突未黔,而贼又至矣,富者皆罄其所有赎身,贫者亦称贷求免,其虔刘于锋镝之下者,不可胜纪也!”⑬
频繁严重的倭祸,生灵涂炭,伴随看天灾人祸,不仅造成漳浦人口锐减,而且极大地破坏漳浦的经济生产。漳浦本来就是“负山阻海,田畴稀少”的地方,在倭寇疯狂猖獗、纵横驰聘的岁月里,人民纷纷逃匿避祸,无法耕种,田园荒芜;滨海以捕鱼为生者,因倭寇纵横海上而不敢下海捕鱼,结果“积尸成陵、白骨遍地”的饥荒接踵而至,曾经一废出现了人吃人的悲惨情况。
五、漳浦人民的抗倭斗争
倭寇对漳浦的侵扰,杀戮无辜、骚扰地方,破坏了漳浦人民的正常生活,影响了漳浦社会经济的发展,激起了广大爱国军民的无比愤慨,纷纷起来保卫家乡。在抗倭斗争中,漳浦人民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自卫措施。
筑土堡。当时虽然有县城,卫所等一些城堡,但由于人们绝大多数都散居在农村的各个地方,他们距县城或卫所近者数里,远者数十里,假如倭寇来侵扰时想要躲避于城堡之中,近者还行,远者如何来得及?况且县城卫所也容纳不下那么多的人畜物品。为此,人们自动组织起来,“凡数十家聚为一堡,壁垒相望,雉堞相连。”土堡的作用不仅可以作为避匿之所,而且可以以逸待劳,实行坚壁清野,“贼之至也,将无所掠为食,以攻则难,以守则馁,弗能久居,势将自退!”⑭
练乡兵。面对倭寇的频繁骚扰,漳浦人民奋起自卫,组练乡兵,不少地方“鸠族人习学技击,教一为十,教十为百,少年矫健,相为羽翼,每遇贼至,提兵一呼,扬旗授甲,云合响应。”⑮乡兵灵活机动,“或迎其束,或蹑其去,或击其情,或捣其虚。其攻也,手足足以相卫;其守也,声势足以相倚。”⑯给倭寇以沉重的打击,使倭寇闻风丧胆,途径漳浦境内一些坚强的城堡时只能“假道乞过,既假之道,尚不敢前,别寻间道,逾岭以去,盖相戒云:‘宁崎岖,毋或致他患也!’”⑰
人民群众的自卫,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使倭寇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如入无人之境地纵横烧杀淫掠,扭转了漳浦的形势,但最终把在漳浦的倭寇扫荡涤平的则是抗倭名将戚继光。
六、戚继光人浦平倭
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戚继光率领戚家军打败围困仙游县城达五十天之久的两万倭寇,万余败寇于年关(十二月三十日)南逃。翌年二月戚继光率军穷追倭寇来到了漳浦。
戚继光治军严明,善于用兵,纪律严明,每出人莫测,或解甲犒师方兴,所在当道欢饮,忽从间道急趋,贼惊以为神;或围孤城,父老扶携登望女墙,翼援兵旦暮且至,见远烟数点,隐隐似旌旗状,忽炮响,则贼已狼泪死散,官兵且抵近郊,大破之矣!平倭平寇,继光之功与漳终始。”⑱由于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在漳浦平倭寇屡立战功,捷报连传,于是,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句俗谚:“俞龙戚虎,杀贼如土。”⑲嘉靖四十三年,从仙游逃窜到漳浦八都(盘陀)汤坑蔡陂岭的倭寇,企图凭借蔡陂岭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作困兽之斗,“贼预度继光当至,设伏待之。”等到戚家军接近时,“卒然峰起,兵为小却,继光斩前怯者数人,身自督战。”⑳由于戚继光身先士卒,领导戚家军英勇奋战,结果“贼大溃,斩数百级。”㉑取得了漳浦抗倭史上最负盛名的蔡陂岭大捷。
蔡陂岭大捷后,倭寇残部退入广东潮州一带,戚继光率军继续追击,在另一抗倭名将俞大猷的配合下,于嘉靖四十三年在广东海丰大歼倭寇。次年,倭寇全部肃清。
入侵大陆的倭寇被歼后,尚有小股倭寇窃据海岛,伺机劫掠,故蓝鼎元说“倭寇与明朝相始终。”为防止倭寇卷土重来,留一部分戚家军镇守漳浦海防,因其兵员大多来自浙江,故称为“浙兵营”,与本县自招的土兵营轮流驻守陆鳌所和铜山所城外,定时在两所之间换防。此后,虽然还有小股的倭寇再来侵扰,但均遭到有力的回击,并未给漳浦造成危害。
漳浦一带倭寇平息后,出现“海波不扬”局面。㉒嘉靖末年至隆庆元年朝廷批准划龙溪、漳浦二县部分地方置海澄县,开放月港对外贸易。
七、结论(略)
注:①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卷五六六
②③《漳州府志》卷四十六(艺文.六》,陈元麟《海防记》
④《漳浦县志》十一《兵防志.烽堠》
⑤⑥⑦明经世文编》卷二〇五,朱纨《阅视海防事》
⑧《漳浦县志》卷十一《兵防志》
⑨⑩《漳浦县志》十一《兵防志》
⑬《漳浦县志》卷十一《兵防志》注
⑫⑬⑭⑮⑯⑰⑱《漳浦县志》卷十一《兵防志》林偕春《兵防总论》
⑲《漳州府志》四十七《灾祥.寇乱》
㉑《漳浦县志》卷十四《名宦志.武职》“戚继光”条
⑳《武备志》卷二一四《海防》
林埙不依附奸王
·林志伟·
林埙字廷乐号雅庵,漳浦北街人,是明初以军籍自莆田来浦定居的“九牧之裔”林景谦的第五世孙。生于正统八年(1443年),自幼勤学,事父母至孝,立志为国尽忠,对他们旧族谱记载的,林姓始祖比于不畏死直谏无道昏君纣王的事十分感动。成化二十年(1484年)以岁贡进京廷试,选入南京国子监学习,两年后派到大理寺实习,期满回家等候铨选,弘治三年(1490年)服母丧,弘治九年部文催诠,八月赴吏部考选贡监,名列第十。弘治十年(1497年)秋饮铨承德郎,授宁王府审理正。宁康王朱觐钧,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曾孙,承袭父亲封地,建府南昌,林埙赴任,受宁康王重用,提拔为长史。不久宁康王病逝,其子上高王朱宸濠嗣位,林埙继续留在宁王府工作。
朱宸濠擅自增兵,蓄谋反叛,在朝廷上勾结掌权太监刘谨,阴谋伺机夺取帝位,于自己属下则任用奸佞,擅杀忠良。在地方上勾结土豪劣绅,横征暴敛,强夺民宅、女子,收罗豢养群盗,劫掠于江西、湖广各地,当地官府不敢管。王府官员只有林埙敢予直言正谏,这就触怒了朱宸濠,在左右阿附官员怂恿下,对林埙施行廷杖。林埙请求辞职,劫被强留下来,他仍然依法办事。
孝宗皇帝朱珰樘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病逝,武宗皇帝朱厚聪继位,改元正德。武宗昏庸,常不理朝政,微服外出“游江南”,荒淫无道。朱宸濠加紧增兵,蓄谋夺取帝位,这时,林埙再次进谏无效,决意辞归,于正德四年请准致仕,回到漳浦,仍住北街老家,编纂族谱家乘,有时游山玩水,不间世事,作诗一首以表心迹:
旧径开来抵碧林,西凤旅雁动归吟;
宁府滥竽非素志,漳江垂钓见真心。
溪山满眼成佳趣,禽鸟多时弄好音,
殷勤纂牒成家谱,来世应知一念深。
林埙归休时,人们不解他为什么有官不当,及至朱宸濠叛乱失败自取灭亡,人们才佩服他有先见之明。事情是这样:正德十四年(1519年),宸濠集兵叛乱,号称十万之众,占领九江、南康,七月初出江西,战船蔽江直下,攻安庆,未克,汀赣巡抚王守仁闻变,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等檄调各郡兵,攻破南昌,收复九江、南康,宸濠回师救南昌,中途战败被俘,解通州,正德帝下旨诛杀,从逆者无一幸存。林埙早已离开宁王府,不但免受牵连,而且朝廷还要再起用他,他以年老婉辞,在家安度晚年,仍好学不倦,操行端严,为人方正,每以忠孝自许。
林埙所修族谱,记事谨严,惠安人张岳(都察院右御史、总督湖广贵川广西广东等五省军务)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为之撰谱序,并赠诗一首:
花甲当头八十春,真容写出都精神。
官司长史勤居逸,事功贯诚受苦辛。
宁府原来非素志,临漳赢得是闲身。
顾于世次为宗子,家谱时修启后人。
张岳对林埙十分尊敬,因为张岳的祖父张纶被朝廷任用为萍乡知县,上任途经南昌,寄宿林埙处,林埙与他原不相识,却予热情接待,不意张纶一夕暴卒,林埙予制衣、备棺、收殓,派人护送返原籍归葬,从此,林埙与张岳之父张慎(广东英德知县)及张岳成莫逆之交。后张岳登进士第。初授“行人”之职(掌传旨册封等事),时濠宸勾结掌权太监刘谨、幸臣江彬,唆使正德皇帝游江南,阴谋伺机篡位,张岳洞察其奸,同兵部朗中黄巩伏阙泣谏,劝阻“游江南”,遭跪曝五日,廷仗至险些丧命,被眨为南京国子监学正。至宸濠叛乱失败,张岳升知府,累官资善大夫,都察院右御史,总督湖广川贵等五省军务,林埙则已归休。张岳及其父张慎,感林埙大恩,并崇尚他的品行,经常寄信到漳浦向他问候,一些诗、信编入林氏族谱,有作为研究当时历史的价值。
林埙享寿92岁,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十二月逝世,葬于北门外蚵湖(今名考湖),殡葬时,官浔进士赵浑赠诗一首:“矗矗新碑大道边,路人争羡使君贤;脱身陷井真明哲,养志桑梓恣乐天。有限酒杯供笑傲,无边风月待归全;他时蝉脱罗山下,赢得清名百世传。”张岳赠联于祠堂:“尊君正宁,四方钦义士;爱国受杖,千载觉忠臣。”后地方奏经朝廷批准,林埙以“忠孝名宦”入祀县乡贤祠,享祀千秋。
林埙胞妹适本邑徐辅。徐辅领乡荐(中举人)晋京考试,卒于途中,林氏年二十八,寡守抚育独子徐藻。徐藻英年早逝,妻周氏二十四岁守寡抚孤,“一家三世一孤,婆媳共守完节”,嘉靖四年(1525年)以“双节”旌表其门,后敕立《双节坊》。
林埙忠孝及其妹一家“双节”《漳浦县志》均立传。
漳浦北街林氏始祖林景善世系,林埙所修族谱记载清楚,后人有续修,此派分衍县北东罗、县东麦园埔、六鳌、盘陀象洞后厅等处,由于旧谱多数散失,后裔不明原委,有的误附于其他派系。东罗林氏家庙祠联云“九牧分宗,忠孝家声留北阙;两朝钦命,乡贤世泽耀东罗。”要不是读到族谱,也不解其意。现此谱仅存孤本,已被发掘出来,解开一些侨胞、台胞寻根认祖的疑问。
·李林昌·
历史上有六个绥安县,地点和兴废时间各不相同。其中有两个绥安县,虽然兴废时间不同,建县时不同属一郡,但现在同属于福建省,容易混淆,有必要将这两个绥安县的建县历史背景、县域范围、县治地点、历史沿革等的不同情况列出对照,以便一目了然。
福建的开发是自北而南的。东汉末年,孙策(后为其弟孙权)割据东南一带,五次派兵入闽,征服了地方势力(少数民族),派一员侯官镇驻今之福州(原设冶县已名存实亡),后来“侯官”成为行政区域名称,属会稽郡管辖。侯官管辖范围主要在闽东、闽北一带,对于闽南、闽西还是鞭长莫及。孙氏未称帝,还是沿用汉献帝“建安”年号,于建安初年分出侯官的北乡(闽北)设置建安(今建瓯)、南平(今南平)、汉兴(今浦城)3县。建安十年(公元205年)析建安县的桐乡设置建平县(今建阳),及至“三国”局面形成,孙权之孙孙休(景帝)于吴永安三年(公元260设立建安郡,郡治在建安县,即今建瓯,除辖原有侯官县、建安县,改汉兴为吴兴县,从南平分设建平县,析建安县校乡分设将乐县,从校乡西偏分设绥安县,又增置昭武县(晋避司马昭讳改名邵武),东平县(未详),在闽南增设东安县(县治在今南安丰州,晋改名晋安县,隋改名南安县)共10县。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从建安郡分出侯官、东安二县设立晋安郡,郡治在今福州。这时,龙溪(今芗城区及龙海市一部分)、兰水(今南靖)末设县,地属东安县管辖;现今的漳浦至诏安一带也未设县,地属南海郡(广东)的揭阳县管辖。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6年)从南海郡分设东官郡(郡治在今广东宝安县西南头镇)。
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建安郡的绥安县改名绥城县。
义熙九年(公元413年)从东官郡分设义安郡,郡治设海阳,即今广东潮安县东北。义安郡辖海阳、海宁、潮阳、义招、绥安5县。这个绥安县就是漳浦县前身的绥安县。
南北朝的梁大同六年(公元540年)从晋安郡分设南安郡,从南安郡的南安县分设龙溪县和兰水县,辖九龙江北、西二溪流域一带。
隋朝裁并许多郡县。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撤销绥城县建制,将其地并归郡武县管辖。开皇二十二年(公元602年)将建安、晋安、南安3郡合并为建安一郡,将全闽各县合并为建安、闽、南安、龙溪4县,兰水、绥安二县并入龙溪县(一说大业三年绥安并入龙溪县)。从此,故绥安县地(包括漳浦、云霄、东山、诏安、平和一带)从广东方面移归建安郡(今福建)管辖。
唐朝起,州(郡)县逐渐增设(与本文无关的略去不谈)。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复设绥城县。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又撤销绥城县,将其地并属邵武县。乾封二年(公元667年)将故绥城县地分设黄连、归化2镇,是建宁、泰宁、宁化3县的前身。2镇升为3县的经过:唐开元十三年(726年)置黄连县,天宝元年(742年)改为宁化县。乾符五年(公元878年)设建宁军,五代南唐改为永安镇,又改为永安场,宋朝建隆元年(公元960年)福建尚在南唐管辖下,升永安场为建宁县。在设建宁县之前,南唐于中兴元年(公元958年)升归化场为归化县,宋朝元珰元年(公元1086年)改为泰宁县。
隋朝并入龙溪县的绥安县故地,于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设立漳州和所属漳浦、怀思二县,怀思置在漳江南,漳浦置在漳江北,附州为县。(漳江旧名漳水,明、清府县志都记载:漳水自西林出,海水自铜山海门入,清浊合流有章。)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怀思并入漳浦县。同时,将龙溪县从泉州划归漳州管辖。漳州州治及漳浦县治于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从漳江北移设于李澳川,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州治移设龙溪,漳浦县治仍旧。以后,漳浦县于元朝至治年间(约1321年)划出西部合龙溪、龙岩二县部份地方设南胜县(后改为南靖县),明朝正德十三年(1518年)南靖分设平和县。嘉靖九年(1530年)漳浦县再分出南部设诏安县,隆庆元年(1567年)再分出东北部合龙溪县沿海地方设立海澄县,清嘉庆三年(1798年)再分出第六都设云霄厅(民国二年改县),东山县则于民国五年从诏安分设。
总之,漳浦县前身的绥安县地包括今漳浦、云霄、诏安、东山、平和等地,设立于三国吴永安三年的绥安县则已于东晋义熙元年改名为绥城县,以后分设建宁、泰宁、宁化3县。那个绥安县(绥城县)县治在建宁城西3里许,属于建安郡,由于建安郡后来改名建州,所以康熙《漳浦县志》称其为“建州之绥安”,此外,别无建置于吴水安元年的“建立漳州的绥安”。(康熙《漳浦县志》注文中“吴永安元年析建安校乡西偏置绥安县”与《八闽通志》所说“吴永安三年析建安校乡西偏置绥安县”同是一个绥安县,不同古籍记载同一个县的建置时间相差两年是常有的事。无3年间同在建安县校乡西偏设两个绥安县之理;将它作为漳浦县前身的绥安县更无理由,因为漳浦不在闽北与江西交界处的建安县校乡西偏,而在闽南与粤东毗连处。
显然,明万历《漳州府志》说“漳浦吴曰绥安、晋曰绥城”是将建宁县前身的绥安县(绥城县)的建县时间误为漳浦县前身绥安县的建县时间。万历《漳浦县志》也有同样错误。康熙《漳州府志》和《漳浦县志》已经加以纠正,康熙《漳浦县志》在注文中说:“旧志载‘吴永安元年析建安校乡西偏置绥安县’乃建州之绥安,建州即今建宁也,误。”但康熙《漳浦县志》只说“绥安之为县,著于晋而废于隋”没有考据出建县的具体时间,说“不知何时建置”,还因为晋朝从建安郡分设晋安郡辖闽东南一带而误以为绥安县属于晋安郡。不过,比万历志祥实一些的是有一段注文:“又据潮阳志载,绥安属义安郡。漳浦八都有绥安溪,据广东志,大埔县西北一百二十里曰高昌山,其下有绥安溪,注云,一名梁山,漳浦县界。”又在同一部县志卷十九《杂志》的《古迹》里说“今八都有绥安溪,即县故址也。”这等于从认同广东志书关于绥安县属义安郡的记载里找到绥安县县治在八都(盘陀)的根据。康熙《漳浦县志》实际采取的是一种多说并存而有所侧重的方式。这部县志在卷十九《杂志》的《谈丛》里又说“潮阳志云,绥安晋属义安郡,即今云霄也。”
康熙修漳浦县志比明朝修志较为进步的做法,是集七名秀才协助两位缙绅修志,并由知县主持,不似万历修志只由三两个缙绅修篡,而且是以嘉靖九年只由一个进士主笔,两个庠生协助,以七个月完成的最早县志为基础。那部嘉靖县志的修篡方法是,采取《八闽通志》和《漳州府志》的资料,并“稽以传记,参以见闻,订讹补缺,增加修辑,门分类别,综核诠次”,由于人手、时间、资料等因素的制约,造成不少缺点,误以改名绥城县的绥安县为漳浦县前身的绥安县便是一例。康熙漳浦县修志人手比较多,时间比较充裕,参考资料比较丰富。但对一些事的记载多说并存,可能是修志人员看法不一致之故。记事截至清未的民国《福建通志.地理志》卷三《沿革》核对各种古籍,作出比较简明的记载:“漳浦县(在漳州府南少西,冲繁难,本冶县及南海郡地,晋义熙九年分东官(即东莞)立义安郡,置绥安县,隋开皇十二年并入龙溪,唐垂拱二年分南界地濒于漳水者置漳浦县,隶于漳州,开元四年徙治李澳川,县从之,二十九年省怀恩县入焉,贞元二年徙州治龙溪后以漳浦为属县,宋因之,元析地置南靖,明析地益海澄,益平和入诏安,清析地置云霄厅。”
这里顺便谈一谈我对绥安县治地点的看法:漳浦八都有绥安溪,成书干明弘治已酉(1489年)的《八闽通志》已经引据宋《漳州图经》加以记载,不是清康熙《漳浦县志》才有。八都即盘陀,而火田在六都,可见绥安溪即盘陀溪而不是火田溪。盘陀溪的上游有一段叫县前溪,县前溪的北面是温源溪,即宋《漳州图经》所载“唐嗣圣年间胡商康没遮洗浴处。”《八闽通志》和康熙《漳浦县志》都转载《漳州图经》这则记载,并载:“温源溪,在县西南八都境,两泉并出,一微暖,一极热,合流南入县前溪。”这两口温泉在今雀仔埔,其南为官陂,可见县前溪即今官陂那条溪,绥安县县署是建在后有温泉,前有清溪的地方,可能无建县城(至今未发现有实据可证明为绥安县城的古城遗址)。
参考资料:《八閊通志》、《福建通志》、《漳州府志》、《漳浦县志》、《建宁县志》、《泰宁县志》、《潮州府志》、《宋书.州县志》、隋书《地理志》。
明代漳浦的倭寇祸患
杨汉章
一、前言
倭寇,是以日本封建诸候、大商贾所支持的武士、浪人、失业流民等组成的,专门掠夺财富的一种海上强盗。它不仅阻挠着海上贸易的正常进行,而且向中国沿海直至内地省份骚扰;在北起辽宁,南至广东的数千里海岸线上,他们到处进扰,烧杀淫掠,犯下了滔天罪恶,给中国沿海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倭寇侵犯中国沿海地区,开始于元代至正年间,到明代更为严重,特别是嘉靖年间,猖獗到了极点。地处“闽南之徼”滨临大海的漳浦,在倭寇疯狂猖獗,肆意纵横的年代里,与闽浙其它沿海地区一样遭受惨烈的祸害。
二、明初漳浦的防倭措施
在明代开国之初的洪武二年,倭寇就已经“数掠苏州、崇明,杀略居民,劫夺货财,沿海之地皆患之。”①明太祖朱元璋决定加强东南沿海的国防力量,从洪武四年起,积极加强军事力量来防御倭寇的侵略,接着开始建设福建海防,据《明史》卷132《周德兴传》载,洪武二十年“命江夏候周德兴往福建滨海四郡,相视形势二卫所城不当要害者,移置之,民户三丁取一,以充戍卒,乃筑城一十六,增巡检司四十五,得卒万五千余人。”周德兴经略海上,于洪武二十一年置福建沿海五卫所指挥使司,在当时漳浦辖地设立镇海卫(今属龙海市),下分置陆鳌、铜山、悬钟三个守御千户所。陆鳌(今六鳌),“自乌石至于埭头西二十里沙岸通焉……其地为船停泊之所。”②驻官兵898名。铜山(今东山县)“闽海重地也,其辖北自金石,接于浯浯屿,南自梅岭,达于广。”③由钦依把总镇守,称为把总水寨,设官兵1141名,备战船46只。悬钟(今属诏安县)“当闽南尽处”,设官兵1103名,有哨船24只。这些卫所,互为倚角、各防险要,控制横屿、井仔湾等易为倭寇海盗啸聚的沿海小屿。此外,设置月屿、古雷、后葛、盘陀岭等巡检司,共设弓兵720名。另外“沿海地方相度地里,远近各置烟墩炮台……贼至举烽燧为号,以便防御。”④正是由于明初在漳浦地方实行了这些行之有效的防御措施,使得在明初很长一段时间时间内,倭寇屡有进犯漳浦,却难以得逞。
三、倭寇猖獗的内因
明太祖的防倭措施,使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倭寇都不能得到发展,但后来昏庸的统治者放松海防,造成倭寇侵犯的条件。
明王朝自宣德以后,政治日益腐败,贪污之风盛行,皇帝昏庸,耽于淫乐,不理朝政,权奸把持朝政,植党营私,打击陷害忠良,贿赂公行,闽浙地区海防废驰,再加上蒙古内侵,明朝君臣专重陆路边防,沿海军备,无人留意,卫所空虚,“又如战哨船,铜山寨二十只,见在止有一只……见在者俱称损坏未修,其余则称未造。”⑤克扣拖欠边卒粮饷,“又如漳州卫与镇海卫,官兵月粮少派三个月……其余多寡不等,无一卫一所开称不缺者。”⑥“以至士无斗志,纷纷逃脱,出现行伍失额,铜山水寨,寨军原额1822名,逃亡人数达1190名,仅剩370人,失缺65%;悬钟水寨,寨军原额1133名,逃亡人数达476人,剩下657人,失缺49%。⑦这样,一遇来,临时招募渔船,纠合民丁,号称防守,实际就是儿戏!
本地卫所无能,只好从外地调兵来御倭,然而那些“客兵”御寇无能,虐民有方,冒功请赏,遇到倭寇“则又逗留观望,直至贼去,乃稍尾其后焉,袭其余辎,猎其疲掳,掠其遗累,割其毙首,虚张战声,冒上功级,甚至掘已痊之尸,推独行之旅,掩守望之夫,戕创伤之羁,截其头颅,墨其面目,焚烧囟发,灭除纲痕,以为真倭而市功焉,不可必得则又下购,募以觅之,盖民当其时不死于贼,则死于兵矣!所过之地,鸡犬为虐,所止之处,门户为碎,至于贼方践蹂之后,复且大索一番,即贼所弃置不取者,兵尽收拾而贱鬻之矣!俗谓‘贼梳兵篦’,良有以也!贼去未俞舍,辄扬旗报捷,奏凯言归,诛求赍粮,需索赏搞,稍不如意,脱巾而呼!偶被汰还,群哨为乱,如往者邑北关外之变,几于缘城而入,可鉴已!”⑧
朝廷腐败,兵防松驰,官兵不但没有尽到剿倭保民的职责,反而虐扰人民,加上一些游民、奸商与倭寇勾结,为虎作伥,这就是东南沿海长朝遭受倭寇蹂躏的内因,漳浦的这些情况,是一个缩影。
四、倭寇在漳浦的侵略活动
倭祸初起,江浙首当其冲,受祸极烈。江浙为财赋之区,明政府不得不调重兵来守。嘉靖三十一年,王抒巡视浙闽,采纳名将俞大猷的建议:“备倭于陆,不如备之于海。”于是征调闽船,招募月港及嵩屿人民为水兵。海防的加强,给倭寇以沉重的打击。
倭寇在江浙受到挫折,便逐渐南窜,正如谢杰在《虔台倭纂》上卷《倭变》中所说的:“方吴越之多事也,闽独晏然,至是材臣名将,尽起吴浙。贼屡败衄,度可脱祸者惟闽耳。”于是,从嘉靖三十四年起,福建倭祸便有增无减,日益严重了。
随着倭祸从江浙南移至闽以来,漳浦的倭祸就逐渐频繁严重了,据《明世宗实录》卷四二八载:“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乙末(初四日),倭二百余人,犯镇海。”此后,漳浦频频受到倭寇的侵优和蹂躏。”嘉靖三十六年,倭寇六都;三十七年五月,倭寇盘陀水港,复移寇长桥;三十八年二月,倭寇县郊,驻溪南;十一月倭寇麦园埔;三十九年二月倭寇佛潭桥;四月倭寇驻峰山,纵掠溪南,后移驻无象铺;四十年二月倭入屿头月余,张琏陷壕浔(今官浔)土城,闰五月,饶寇袭陷镇海卫城;四十一年二月,张琏率倭寇入掠县郊。”⑨
倭寇的侵略行径是极其野蛮的,我们根本连想象也不敢想象,据《明史记事本末》记载:“官庾民舍,焚劫掠夺,少壮掘冢墓,束婴孩竿上,沃以沸汤,视其哭号,拍手笑乐,得孕妇,卜度男女,刳视中否,以胜负饮酒,积骸如陵。”实在是野蛮得令人发指!
在漳浦的大地上,这些灭绝人性的强盗,极尽其烧杀淫掠之能事,见人就杀,见女就淫。许多烈女贞妇,不甘受辱,以死洁身的事例,在县志的《闺阁》卷中占了极大的篇幅,这从某种意义上正反映了倭寇的血腥罪恶。⑩
倭寇疯狂屠杀漳浦人民的手段,罄竹难书,残酷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对活人进行疯狂屠杀的同时,连死人的枯骨也不放过,他们在围攻县城时,“隆冬盛暑不休……多发人冢,携骸勒赎。”⑪结果“民不忍去枯骨,多自发冢取棺藏之,生民荼毒至此极矣!”⑫
频繁的倭寇侵扰,给漳浦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漳浦人民备受流离失所之苦,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嘉靖三十四年至此(嘉靖四十一年),六七岁间,村无完舍,民无定居,往往逃匿山中,破突未黔,而贼又至矣,富者皆罄其所有赎身,贫者亦称贷求免,其虔刘于锋镝之下者,不可胜纪也!”⑬
频繁严重的倭祸,生灵涂炭,伴随看天灾人祸,不仅造成漳浦人口锐减,而且极大地破坏漳浦的经济生产。漳浦本来就是“负山阻海,田畴稀少”的地方,在倭寇疯狂猖獗、纵横驰聘的岁月里,人民纷纷逃匿避祸,无法耕种,田园荒芜;滨海以捕鱼为生者,因倭寇纵横海上而不敢下海捕鱼,结果“积尸成陵、白骨遍地”的饥荒接踵而至,曾经一废出现了人吃人的悲惨情况。
五、漳浦人民的抗倭斗争
倭寇对漳浦的侵扰,杀戮无辜、骚扰地方,破坏了漳浦人民的正常生活,影响了漳浦社会经济的发展,激起了广大爱国军民的无比愤慨,纷纷起来保卫家乡。在抗倭斗争中,漳浦人民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自卫措施。
筑土堡。当时虽然有县城,卫所等一些城堡,但由于人们绝大多数都散居在农村的各个地方,他们距县城或卫所近者数里,远者数十里,假如倭寇来侵扰时想要躲避于城堡之中,近者还行,远者如何来得及?况且县城卫所也容纳不下那么多的人畜物品。为此,人们自动组织起来,“凡数十家聚为一堡,壁垒相望,雉堞相连。”土堡的作用不仅可以作为避匿之所,而且可以以逸待劳,实行坚壁清野,“贼之至也,将无所掠为食,以攻则难,以守则馁,弗能久居,势将自退!”⑭
练乡兵。面对倭寇的频繁骚扰,漳浦人民奋起自卫,组练乡兵,不少地方“鸠族人习学技击,教一为十,教十为百,少年矫健,相为羽翼,每遇贼至,提兵一呼,扬旗授甲,云合响应。”⑮乡兵灵活机动,“或迎其束,或蹑其去,或击其情,或捣其虚。其攻也,手足足以相卫;其守也,声势足以相倚。”⑯给倭寇以沉重的打击,使倭寇闻风丧胆,途径漳浦境内一些坚强的城堡时只能“假道乞过,既假之道,尚不敢前,别寻间道,逾岭以去,盖相戒云:‘宁崎岖,毋或致他患也!’”⑰
人民群众的自卫,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使倭寇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如入无人之境地纵横烧杀淫掠,扭转了漳浦的形势,但最终把在漳浦的倭寇扫荡涤平的则是抗倭名将戚继光。
六、戚继光人浦平倭
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戚继光率领戚家军打败围困仙游县城达五十天之久的两万倭寇,万余败寇于年关(十二月三十日)南逃。翌年二月戚继光率军穷追倭寇来到了漳浦。
戚继光治军严明,善于用兵,纪律严明,每出人莫测,或解甲犒师方兴,所在当道欢饮,忽从间道急趋,贼惊以为神;或围孤城,父老扶携登望女墙,翼援兵旦暮且至,见远烟数点,隐隐似旌旗状,忽炮响,则贼已狼泪死散,官兵且抵近郊,大破之矣!平倭平寇,继光之功与漳终始。”⑱由于戚继光率领戚家军在漳浦平倭寇屡立战功,捷报连传,于是,当时民间流传着一句俗谚:“俞龙戚虎,杀贼如土。”⑲嘉靖四十三年,从仙游逃窜到漳浦八都(盘陀)汤坑蔡陂岭的倭寇,企图凭借蔡陂岭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作困兽之斗,“贼预度继光当至,设伏待之。”等到戚家军接近时,“卒然峰起,兵为小却,继光斩前怯者数人,身自督战。”⑳由于戚继光身先士卒,领导戚家军英勇奋战,结果“贼大溃,斩数百级。”㉑取得了漳浦抗倭史上最负盛名的蔡陂岭大捷。
蔡陂岭大捷后,倭寇残部退入广东潮州一带,戚继光率军继续追击,在另一抗倭名将俞大猷的配合下,于嘉靖四十三年在广东海丰大歼倭寇。次年,倭寇全部肃清。
入侵大陆的倭寇被歼后,尚有小股倭寇窃据海岛,伺机劫掠,故蓝鼎元说“倭寇与明朝相始终。”为防止倭寇卷土重来,留一部分戚家军镇守漳浦海防,因其兵员大多来自浙江,故称为“浙兵营”,与本县自招的土兵营轮流驻守陆鳌所和铜山所城外,定时在两所之间换防。此后,虽然还有小股的倭寇再来侵扰,但均遭到有力的回击,并未给漳浦造成危害。
漳浦一带倭寇平息后,出现“海波不扬”局面。㉒嘉靖末年至隆庆元年朝廷批准划龙溪、漳浦二县部分地方置海澄县,开放月港对外贸易。
七、结论(略)
注:①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卷五六六
②③《漳州府志》卷四十六(艺文.六》,陈元麟《海防记》
④《漳浦县志》十一《兵防志.烽堠》
⑤⑥⑦明经世文编》卷二〇五,朱纨《阅视海防事》
⑧《漳浦县志》卷十一《兵防志》
⑨⑩《漳浦县志》十一《兵防志》
⑬《漳浦县志》卷十一《兵防志》注
⑫⑬⑭⑮⑯⑰⑱《漳浦县志》卷十一《兵防志》林偕春《兵防总论》
⑲《漳州府志》四十七《灾祥.寇乱》
㉑《漳浦县志》卷十四《名宦志.武职》“戚继光”条
⑳《武备志》卷二一四《海防》
林埙不依附奸王
·林志伟·
林埙字廷乐号雅庵,漳浦北街人,是明初以军籍自莆田来浦定居的“九牧之裔”林景谦的第五世孙。生于正统八年(1443年),自幼勤学,事父母至孝,立志为国尽忠,对他们旧族谱记载的,林姓始祖比于不畏死直谏无道昏君纣王的事十分感动。成化二十年(1484年)以岁贡进京廷试,选入南京国子监学习,两年后派到大理寺实习,期满回家等候铨选,弘治三年(1490年)服母丧,弘治九年部文催诠,八月赴吏部考选贡监,名列第十。弘治十年(1497年)秋饮铨承德郎,授宁王府审理正。宁康王朱觐钧,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献王朱权的曾孙,承袭父亲封地,建府南昌,林埙赴任,受宁康王重用,提拔为长史。不久宁康王病逝,其子上高王朱宸濠嗣位,林埙继续留在宁王府工作。
朱宸濠擅自增兵,蓄谋反叛,在朝廷上勾结掌权太监刘谨,阴谋伺机夺取帝位,于自己属下则任用奸佞,擅杀忠良。在地方上勾结土豪劣绅,横征暴敛,强夺民宅、女子,收罗豢养群盗,劫掠于江西、湖广各地,当地官府不敢管。王府官员只有林埙敢予直言正谏,这就触怒了朱宸濠,在左右阿附官员怂恿下,对林埙施行廷杖。林埙请求辞职,劫被强留下来,他仍然依法办事。
孝宗皇帝朱珰樘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病逝,武宗皇帝朱厚聪继位,改元正德。武宗昏庸,常不理朝政,微服外出“游江南”,荒淫无道。朱宸濠加紧增兵,蓄谋夺取帝位,这时,林埙再次进谏无效,决意辞归,于正德四年请准致仕,回到漳浦,仍住北街老家,编纂族谱家乘,有时游山玩水,不间世事,作诗一首以表心迹:
旧径开来抵碧林,西凤旅雁动归吟;
宁府滥竽非素志,漳江垂钓见真心。
溪山满眼成佳趣,禽鸟多时弄好音,
殷勤纂牒成家谱,来世应知一念深。
林埙归休时,人们不解他为什么有官不当,及至朱宸濠叛乱失败自取灭亡,人们才佩服他有先见之明。事情是这样:正德十四年(1519年),宸濠集兵叛乱,号称十万之众,占领九江、南康,七月初出江西,战船蔽江直下,攻安庆,未克,汀赣巡抚王守仁闻变,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等檄调各郡兵,攻破南昌,收复九江、南康,宸濠回师救南昌,中途战败被俘,解通州,正德帝下旨诛杀,从逆者无一幸存。林埙早已离开宁王府,不但免受牵连,而且朝廷还要再起用他,他以年老婉辞,在家安度晚年,仍好学不倦,操行端严,为人方正,每以忠孝自许。
林埙所修族谱,记事谨严,惠安人张岳(都察院右御史、总督湖广贵川广西广东等五省军务)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为之撰谱序,并赠诗一首:
花甲当头八十春,真容写出都精神。
官司长史勤居逸,事功贯诚受苦辛。
宁府原来非素志,临漳赢得是闲身。
顾于世次为宗子,家谱时修启后人。
张岳对林埙十分尊敬,因为张岳的祖父张纶被朝廷任用为萍乡知县,上任途经南昌,寄宿林埙处,林埙与他原不相识,却予热情接待,不意张纶一夕暴卒,林埙予制衣、备棺、收殓,派人护送返原籍归葬,从此,林埙与张岳之父张慎(广东英德知县)及张岳成莫逆之交。后张岳登进士第。初授“行人”之职(掌传旨册封等事),时濠宸勾结掌权太监刘谨、幸臣江彬,唆使正德皇帝游江南,阴谋伺机篡位,张岳洞察其奸,同兵部朗中黄巩伏阙泣谏,劝阻“游江南”,遭跪曝五日,廷仗至险些丧命,被眨为南京国子监学正。至宸濠叛乱失败,张岳升知府,累官资善大夫,都察院右御史,总督湖广川贵等五省军务,林埙则已归休。张岳及其父张慎,感林埙大恩,并崇尚他的品行,经常寄信到漳浦向他问候,一些诗、信编入林氏族谱,有作为研究当时历史的价值。
林埙享寿92岁,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十二月逝世,葬于北门外蚵湖(今名考湖),殡葬时,官浔进士赵浑赠诗一首:“矗矗新碑大道边,路人争羡使君贤;脱身陷井真明哲,养志桑梓恣乐天。有限酒杯供笑傲,无边风月待归全;他时蝉脱罗山下,赢得清名百世传。”张岳赠联于祠堂:“尊君正宁,四方钦义士;爱国受杖,千载觉忠臣。”后地方奏经朝廷批准,林埙以“忠孝名宦”入祀县乡贤祠,享祀千秋。
林埙胞妹适本邑徐辅。徐辅领乡荐(中举人)晋京考试,卒于途中,林氏年二十八,寡守抚育独子徐藻。徐藻英年早逝,妻周氏二十四岁守寡抚孤,“一家三世一孤,婆媳共守完节”,嘉靖四年(1525年)以“双节”旌表其门,后敕立《双节坊》。
林埙忠孝及其妹一家“双节”《漳浦县志》均立传。
漳浦北街林氏始祖林景善世系,林埙所修族谱记载清楚,后人有续修,此派分衍县北东罗、县东麦园埔、六鳌、盘陀象洞后厅等处,由于旧谱多数散失,后裔不明原委,有的误附于其他派系。东罗林氏家庙祠联云“九牧分宗,忠孝家声留北阙;两朝钦命,乡贤世泽耀东罗。”要不是读到族谱,也不解其意。现此谱仅存孤本,已被发掘出来,解开一些侨胞、台胞寻根认祖的疑问。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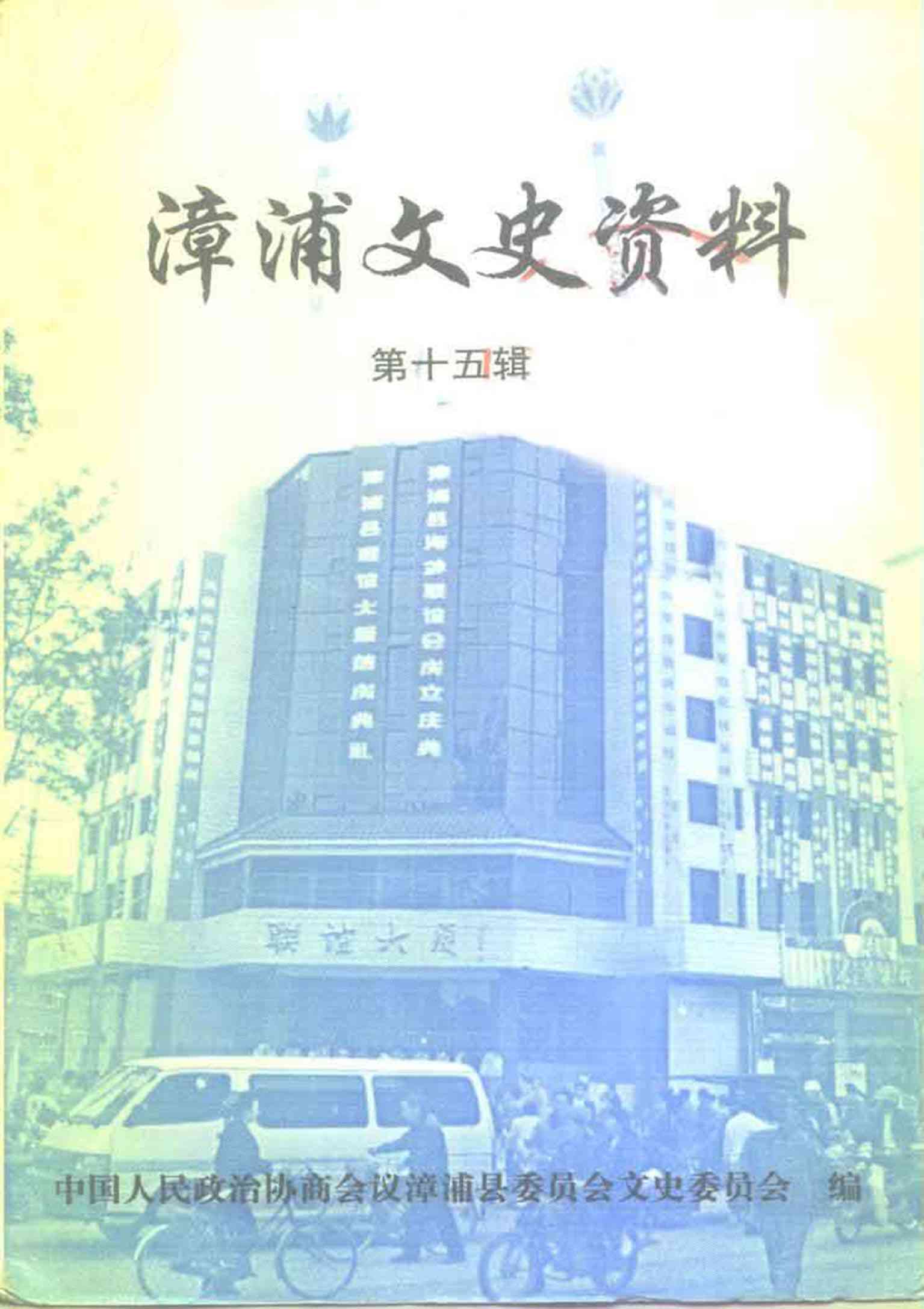
相关地名
漳浦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