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建设
| 内容出处: | 《漳浦文史资料第十五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30000777 |
| 颗粒名称: | 经济建设 |
| 分类号: | F127.57 |
| 页数: | 18 |
| 页码: | 1-18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漳浦的经济建设情况,其中包括了闽南第一洞——国道324线盘陀岭隧道建设记实、“高路入云端”——车本公路建设记实、漳浦县陂堰建设等。 |
| 关键词: | 漳浦县 经济建设 |
内容
闽南第一洞——国道324线盘陀岭隧道建设记实
王福祥·陈桂味
编者按:本文两位作者都是亲历此工程的领导人:王福祥以漳浦县交通局副局长任工程副指挥;陈桂味则是当时分管的副县长。这种可贵的“三亲资料”可供存史资治,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亲历者为《漳浦文史资料》写稿,存下丰富的史实资料。
盘陀岭,地处梁山山脉中段,漳浦、云霄两县交界,汉代为闽越、南越交界,设蒲葵关,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和官府关隘要口。解放后,岭上修建公路,与云霄衔接,沟通广东,为国道324线原399公里200米~405公里632米地段。“盘陀岭上几盘陀,半山云雾车难过”,这里坡陡弯急,上下山6公里,共有弯道64个,最小的急弯半径才23米,最大的纵坡达85%,遇上春夏雨季,山中云雾缭绕,汽车穿云破雾,行走于山巅深涧之间,再老练的司机也提心吊胆,谨慎爬涉。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据统计,从1984年至1987年,在岭上路段发生翻车、撞车事故年平均47起之多。驾驶员望岭兴叹,称之为云中天险鬼门关。
这样的路段与当时汽车日流量5~6千辆的国道极不相称,已成了324线卡脖子地段。改善这一交通“瓶颈”的呼声日益强烈。自1985起,引起各级交通部门的重视,省市县交通、公路部门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就盘陀岭路段改造问题分别到实地勘察、调研,作工程可行性论证。1986年6月,交通部王展意副部长亲自到盘陀视察、调查,尔后交通部又派了3位高级工程师前来实地勘察,1986年初夏,省交通厅长亲率省公路局及有关处的领导现场办公,比较一致的方案是打隧道方案。返省城后,交通厅作出建设盘陀岭隧道的决定。1987年6月,隧道工程设计单位——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工程技术人员到现场测设,1988年9月1日,工程招标在福州揭晓,工程由铁道部第十六工程局中标,同年10月,施工队伍——第十六工程局四处的工人、技术人员进场,拉开了隧道工程会战序幕。
指挥部“特别能战斗”
盘陀岭隧道工程是省市“七五”交通建设重点之一,由省公路局投资建设,市、县负责工程的前期工作和工程施工过程的协调、服务和监督。漳州市委、市政府,漳浦、云霄两县县委、县政府对工程十分重视,由市政府行文成立工程指挥部,由当时市委副书记李天森任总指挥,市交通局长高南胜、市公路局副局长林国英任副总指挥,漳浦县交通局副局长王福祥、云霄县交通局副局长周三桂任常务副指挥,还有市、县政府办公室、公安、土地、财政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作为指挥部领导成员。指挥部按照“理顺、协调、监督、服务”职能,开展工作。在李天森同志的领导下,在工程的每一阶段,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工程前期,指挥部头一件大事就是要在短时间内做好工程的征地折迁和工地“三通一平”,这是每个工程的“难点”,当然也是隧道工程的难点之一,指挥部紧密依靠两县政府和当地盘陀乡、火田乡党委、政府的配合,漳浦、云霄两县政府都指定一位副县长直接参与这项工作,当地乡党委政府除指定一名主干和几名干部专职做这项工作外,遇到重大问题,党政第一把手都亲自解决,所在地的村干部也很快地形成共识,形成明意义、顾大局、讲奉献的氛围,指挥部的同志和县、乡、村干部共同深入实地丈量土地,清点菁苗,深入群众,开会动员,走家串户做政治思想工作,大量的群众工作在短时间内解决。在此基础上,指挥部同志结合交通、公路、土地等部门工程技术人员,开展工程用地复测、放样会战,时值盛夏三伏,测量现场大部分是“坑垅”和陡坡,荆棘丛生,蚊虫猖獗。气温高,湿度大,既热又闷,尤其是十点以后响午时刻,更是难熬,为避免蚊虫叮咬,大热天不得不穿冬服,每天都有同志中暑,但也是咬住牙根坚持下去。遇到测点在坑沟峭壁上,负责测量的助理工程师林孔周同志腰绑绳索,悬挂在峭壁上测量,一丝不苟。更难能可贵的是总指挥李天森、副总指挥高南胜等领导同志,身先士卒,爬山越坑垅,跳涧涉溪,和同志们共同战斗,极大地鼓舞同志们的斗志。原计划需用一个多月时间才能完成征地折迁工作,仅用15天就办完成。该工程共征地270亩,迁移坟墓54座、通讯线路3.5公里,处理(迁、砍)果树、林木15.3万株。
完成征地折迁之后,“三通一平”的关键是通电,本来打算从漳浦火烧埔12万伏变电站引接专线,但线路长达28公里,需要投资60多万元,架设线路最快也要花一个多月,耗资大,时间长。为了节省资金,缩短工期,指挥部同志和县电力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多方勘察,电力工程师何重光废寝忘食,精心设计,提出从隧道附近的梁山二级电站架设线路到工地的“短、平、快”方案,可缩短线路24公里,节省资金50万元,这一方案得到市、县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县领导专门召开协调会,及时解决送电的一系列具体问题,漳浦电力公司技工仅用10天时间,将线路架设完成,提前通电,确保按期开工。
前期工作的顺利进行,为工程开工打下良好的基础。担负隧道施工任务的铁道部十六工程局四处指挥部雷光华副指挥长十分感激,在开工典礼上说:“我们工程每前进一步,都倾注着地方党委政府和工程指挥部的全部心血。”这支队伍自1988年10月进场施工,就以铁道兵打硬仗、排万难的作风,投入紧张有序的施工。打隧道是铁道兵在行活,但四处的同志大部分是北方人,南下福建搞工程施工,对这里的气候、环境、水土很不适应,在他们日常工作中,多了一层克服环境差异而带来的困难,高温、台风、暴雨,施工面的地质、泉眼、塌方等情况经常困扰着,指挥长坐卧不安。粗略统计,工程队自1988年10月进场施工至工程竣工,经历六次台风和暴雨的袭击,每次台风暴雨,既给工程造成严重损失,也是对指挥部的一次考验。如1989年5月20日下午,第3号台风正面袭击漳浦,工地上风狂雨骤,山洪暴发,正在施工的第一涵洞便道被山洪冲毁,山体塌方600多立方米,岭上的公路也被冲毁,往来车辆受阻,顿时堵车长达20多公里,在这关键时刻,工程指挥部的正副指挥、市县公路局领导和县府领导,都陆续赶到现场,指挥抢修,与施工人员一同奋战三昼夜,才把冲毁路段修复。又是1989年6月3日的龙卷风袭击工地,800多平方米的工棚顷刻间被大风卷掉,施工人员的住宿和生活遇到困难,指挥部及时通过乡政府,动员当地群众腾出民房,安顿施工人员的住宿和生活。在工地上,哪里有困难,有险(灾)情,指挥部的人员就出现在哪里,他们紧密配合施工单位,尽“理顺、协调、监督、服务”之职能,以苦为荣,默默奉献,赢得了省市领导和施工单位的称赞,称之为“特别能战斗”的工程指挥部。
他们仍然是“最可爱的人”
担任工程施工任务的铁道部十六工程局四处干部职工,是一支从铁道兵集体转业改地方编制的施工队伍,虽不见帽徽、领章、军衔,但铁道兵打硬仗,不畏难,吃大苦,耐大劳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依然在这支队伍中得到充分体现和发扬。
盘陀岭地质比较复杂。工程一开工就遇到隧道漳浦端洞前区的控方全是流塑状的粘土,推土机、铲车不顶用,运载泥土的卡车有27辆次陷入粘泥中而不能自拔,一辆推土机陷得只剩下驾驶室露出地面,用3台装载机联动才把它拖出来。洞前区这样的工作面,有90米长,共2.3万土方。在困难面前,四处指挥部分别召开党总支会、党员会,及部分职工大会,发按支部、党员作用,走群众路线,让大家出谋献策。在这关键时刻,指挥长刘仁全连续接到家里发来的“母病重速归”、“母病危速归”、“母病故速归”三封电报,但为了工程排除险难,他没有尽做孝子的孝心,强忍悲痛,一直坚持在岗位上,尽做指挥的责任。还有主管技术的工程师陈晓明,妻子分娩,也顾不上请假去照料。在指挥长的带动下,指挥部二十多位机关干部都下工地与工人们同住同吃同劳动,上下拧成一股绳,采用多种办法,终于完成洞前区粘土开挖任务,打响了工程第一炮,“铁道兵铁打的汉”的高大形象展现出来了,赢得了地方党政干部的钦佩。
打洞挖掘施工,多采用现代化的机械设备,机械施工烟灰、尘土多,尽管洞内安置有3台1000千瓦的通风机,工人们戴着防尘面具也只能坚持工作两个小时,每个工班(6小时一工班)都有人晕倒。在这种施工环境中,四处指挥部领导以身作则,轮流跟班指挥施工。每台装载机配备4名司机轮班作业,谁晕倒,机械队长万安友同志就顶谁的班,做到人轮换机不停,日掘进长度计划不能少。有一次,洞内出现300多立方米的大塌方,四处指挥部立即组织以党团员干部为主体的抢险突击队,采用“管棚法”施工方案,制服塌方,排除险情,工程继续掘进。
在隧道云霄端的施工中,机械队的双臂凿岩台车是机械施工的主力,只有副队长魏志荣能开这台车。正在施工紧张阶段,小魏家里发生火灾,5间房子全部被烧,父老妻小无处栖身,家里发来电报,催小魏速归处理,小魏心急如焚,巴不得插翅飞回,但眼下又是施工紧张阶段,开双臂凿岩台车非他莫属,只写封信安慰家里,自己坚持开车凿岩,直到完成云霄端打洞凿岩任务后,才登上归家路程。类似这样的事,在四处指挥部员工中,还有许多,正是这支顽强、工作过硬的战斗群体,才能承担这样的工程。南征北战的铁道兵队伍,其甜酸苦辣,是我们许多人不能理解和难以承受的。在这里,值得多写一笔的是,在这支打硬仗的队伍背后,有一群能理解、谅解、支持丈夫事业的家属们,尽管笔者与她们从未谋面,但从几多事实,从四处指挥部同志口中,足以透过这支队伍,看到千里之外的大本营的职工家属们,为了“前方”的丈夫安心施工所作出的奉献和付出的代价。尽管她们的丈夫已卸去军装,但她们仍然是可敬的“军嫂”。卡车司机张学民,是安徽籍的小伙子,在工地上也是一条打硬仗的汉子,在一次洞内塌方中牺性了年轻的生命,他的父母兄弟妻子来队料理后事,头尾共住4天,第五天便启程北上回家。这期间,他们没有向组织提出过非份要求,只听到他们这样说:“我们的亲人为国家建设而牺牲,他死得光荣。”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张学民同志献身于盘陀岭隧道,他的事迹,他的名字,将长留在闽南人心中!
“为了国家建设,我们情愿吃亏”
盘陀岭公路隧道工程共征地270亩,要迁砍15万株果树、林木,涉及两县200多户农民的切身利益。按上级规定,公路建设征地、赔菁等项的价格低于其它建设用地,被征用的乡村土地承包户必须为国家建设作一定奉献。这除对这些被征用户的宣传发动要做得深透外,还要这里农民兄弟通情达理,顾全大局。拿荔枝、龙眼果树来说,此果是闽南名优特产,此树称为摇钱树,时下一公斤龙眼12~14元,一公斤鲜荔枝7~8元,一株盛果期的龙眼树,每年可采收50~75公斤龙眼果,一株盛果期的荔枝树,每年可采收75~100公斤荔枝果,砍掉果树,分明是断了果农的生计。但为了国家建设,农民兄弟没有讨价还价,“忍痛割爱”。隧道西端的云霄火田乡古楼村,需要动迁砍伐荔枝树200多棵、香蕉1000多株。村党支部书记林解放,带头砍掉自家年收入数万元的45棵荔枝树,村委主任林金海带领四兄弟带头砍掉自家一大片香蕉。在干部带动下,该村群众也没有二话,为建设让路,为建路砍掉摇钱树。漳浦盘陀乡和美村农民陈如德、陈如阳,在隧道东端洞前区一带栽种的香蕉1000多株,长势不错,眼看创收在即,遇到工程动工,他们态度明朗,带领家人,在期限内把香蕉全部砍掉。由于当地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征地、赔菁仅用半个月时间完成任务。
还有,在工程建设遇到难题的时候,遇到抗灾抢险的时候,当地群众有求必应,像50年代支前一样,踊跃参加工程的排难抢险行列之中。洞前粘土开挖,施工遇到困难,需要人工突击抢挖,盘陀近百名农民,在乡领导带领下,自带工具到工地“支前”,和工人们并肩战斗。当台风暴雨把工棚全部刮倒,工人们住宿、吃饭遇到困难的时候,又是当地农民让出自家房屋,提供食宿……。有人曾问,这样做有没有感到吃亏点,农民们回答得好:为了国家建设,吃点亏大家情愿,值得。
盘陀岭隧道和公路改线全长4.567公里,其中隧道长822.3米,洞里净高7米,宽9米,两端接线公路3.745公里,路基宽12米,路面宽9米。全工程挖填土石方46.9万立方米,建造公路涵洞20座,达584.6延米,防护工程砌石5686立方米,共计耗工51万工日,总投资2500多万元。工程从1988年10月动工,1991年8月1日竣工通车,历时2年10个月。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为隧道题写匾额,镌刻在洞口额顶大理石上,苍劲有力,使隧道显得气势非凡。
一洞横贯盘陀岭,云中天险变通途。在盘陀岭隧道建成通车5周年之际,伫立隧道口,观南来北往的车辆穿梭过洞,目不暇接。杨成武将军的题字“盘陀岭隧道”镏金石刻大字,在晨曦中闪烁光芒,追今抚昔,轰轰烈烈的工程建设场面,依然清晰,一幕幕印在脑际。笔者想以工程参与者的身份,把工程建设者们的忘我拼搏,流血流汗,工程指挥者们的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当地群众讲风格、讲奉献的情怀,记录下来。囿于手拙笔钝,只从笔记和记忆中摘取以上片断,以此献给工程的建设者们,也愿大家长久记得盘陀岭隧道建设的日日夜夜。
“高路入云端”——车本公路建设记实
·陈桂味·
在漳浦县西北部,与平和、龙海二县(市)交界处,是绵亘数百里的石屏山脉。这里崇山峻岭,层峦叠嶂,深涧峭壁,丛林茂密,莽莽葱葱,主峰海拔1006米,是漳浦县最高峰,还有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峰6座,其中900米以上的5座。
在石屏山山脉中段,有一座海拔815米的烘炉山,东南阳坡的一处坳地上,有一个村落叫车本,是全县海拔最高、地处最偏的山村,今有63户346人,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建国以来一直是一个行政村编制,公社化时称车本大队,乡镇建制后称车本村。
这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村,特定的自然地理位置,为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创造了良好的活动场所,中共闽粤边特委、靖和浦中心县委机关都先后设在车本村,邓子恢、曾志、卢胜、彭德清、朱曼平、吴运琳、柯永麟等革命老前辈都曾在此开展革命斗争工作,建立苏维埃政权,领导工农红军、游击队和工农群众向国民党反动派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车本人民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年代,付出巨大的牺牲和沉重的代价。这是一片洒满革命先烈鲜血的热土,这是一个打不烂,摧不垮的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共于革命战争时期在闽南地区的战斗堡垒。
解放后,车本村作为革命根据地,革命基点村,在政治上经济上备受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关心和支持,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经济状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1986年,全村58户332口,有耕地320亩、山地19228亩、田地以种植水稻为主,山地以竹林为主。村办有小学,校舍一座五开间,在校学生46人,分三班,有教师四人,学龄儿童基本都上学,由于生员缺乏,学校实行间年招生。村办水电站装机容量15千瓦,可供全村照明及碾米机、粉碎饲料机、电视机用电。村民的居住条件也逐年改善,户户住上瓦房,虽也老式,但还实用。温饱间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毕竟处在大山深处,发展经济受诸多条件制约,与平原、沿海地区的发展尚有一段较长的距离。
在制约车本村经济发展的诸因素中,道路交通是一大制约因素,从解放后至1987年公路动工前这近40年间,并不是当时的领导,当时的群众没想到修路,而是社会发展条件、经济发展条件达不到,使车本村民们仍旧盘旋于崎岖山道。已通简便公路的山脚下龙岭村、山城村(也是革命老根据地基点村),距车本村最近也有8公里,村里有木材、毛竹出售,要一根根一捆捆肩扛下山,其工资甚至超过木料的身价;村民需用的生产、生活资料,也全靠肩扛背驮上山,其工效和劳动强度不言而喻。
解决车本村通公路,提高车本村劳动生产率,缩短老区、边远山区与沿海平原地区的经济差距的历史责任,当然地落在当代人民政府肩上,1987年11月26~29日召开的漳浦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县长王良才所作的政府报告上,把车本公路建设列为本届政府为民办实事之一,向人民代表、全县人民表示了县政府的态度和决心。县人大会议一结束,王县长在第一次政府常务会上(1987年12月23日),立即把本届政府为民兴办十件实事的实施,分到各位副县长,其中车本公路建设分工由我组织实施。
1988年1月6日,我带县交通局局长杨江南、工程股长杨恭贤、公路段段长洪双连、老区办主任吴天化、干部商土生,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及石榴乡副乡长王建文等同志,上车本村作公路选线踏勘。同志们不辞劳苦,在荆棘丛生,时有石壁山涧挡阻的无路荒山上选路线,为尽快地在这样一个地形复杂、高差过大的山地上,找到了一线车本——山城可建接近四级公路的走向线路。中旬,由交通局工程股长杨恭贤率全股室工程技术人员到实地开展外业测量,他们是邱先增、黄耀辉、潘在福、杨一枝、杨昆山、林培文、黄明地、林孔超及驾驶员杨金安、魏漳明等同志,在乡、村干部群众配合下,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山高路险,用六天时间,完成车本——山城线7.2公里的外业测量任务。到3月30日,完成内业的设计计算。
测设的车本公路,从山城村起点,全长7.2公里,其中山城村地界3.07公里,车本村地界4.5公里(山城村为车本公路建设让出耕地、山地,贡献很大)。道路平曲线共有122个,平均每公里17.13个,弯道半径10米的(最小半径)一个,最大半径200米,有四个。纵坡大于10%的有七段,长度2060米。平均纵坡6.8%。道路竖曲线半径在500米的有七处,竖曲线半径在700米的有一处,在1000米以上的有十处。设计全线路基总挖方120426立方米,其中土方60212.9立方米,软石24085.3立方米,坚石36127.8立方米。填方37429立方米。路面结构为泥结碎石压实,铺设面积26300平方米。工程造价(不含土地及赔菁)64.万元。7月19日,我同交通局、土地局、老区办领导、工程技术人员,以及车本扶贫工作队队长,到石榴乡征求乡领导对道路设计、投资预算的意见,及对开工日期、资金筹措等有关事项作初步安排,明确乡、村免费征用公路用地及赔菁、拆迁费用,建路资金全由县里为主筹措,县、乡对此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
8月23日,县委书记承光大召集交通、公路、老区等有关部门会议,专题听取车本公路测设情况汇报,研究施工前的准备工作。10月4日,由副县长杨安乐(其时,县政府对副县长的分管工作作了调整,我增加分管农业、乡镇企业,交通工作由杨安乐分管)、交通局长邱秋月、老区办主任吴天化、乡党委书记张丛生等领导同志为车本公路开工动土,由交通局选派的三支工程队近百人陆续进场施工,这三支筑路工程队施工经验丰富,特别能吃苦,队长分别为蔡国庆、陈凤阳、郑万芳、陈云成(分地段承包),尤其是蔡国庆、陈凤阳两个施工队,坚持始终,他们克服地形复杂,施工难度大,工价较低,生活条件差等诸多困难,直到工程完竣。一年的施工中,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承光大书记、王良才县长、杨安乐副县长多次深入施工现场,检查指导督促,对老区人民和施工队伍以巨大鼓舞。县老区办主任吴天化同志一直坚持在工地,具体协调工程的各方面工作,督促指挥工程队施工,作为一位打游击出身的老同志,对老区人民一向怀着满腔热情,对老区事业,一向执着追求,他明知已届离休年龄,但却不辞劳苦,坚持承担副指挥的职务,直到车本公路开通,才离开岗位,光荣离休。
1989年11月上旬,进行全面完工的扫尾工作。15日,车本公路举行隆重的通车剪彩庆典,老区山城村、车本村披上节日盛装,老区人民兴高彩烈,喜迎省市县乡前来参加庆典的领导和同志们。曾经战斗在龙岭、山城、车本革命老区的红军战士、老首长卢叨(原省政协副主席)偕夫人韦立(原省总工会副主席)、柯志达(原龙溪地委副书记)、陈天才(原龙溪行署副专员)、蔡新生(原漳州市政协副主席)等老前辈,同省市县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县五套班子在家的领导,参加庆典,县委书记承光大、县长王良才、老同志卢叨为工程剪彩。
车本公路建成通车,从此结束了车本村民行路难的厉史,高路入云端,汽车山中行。车本公路的建成通车,为车本村铺就一条通达经济振兴的大道,车本村人民将以此为新起点,去追求,去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我们祝愿,我们祈盼,富有革命传统的老区车本人民,立足山区,团结拼搏,共创美好的明天。
漳浦县陂堰建设
陈章兴
堰,漳浦县方言叫“陂”。陂堰亦称“拦河堰”,即建筑在河流中较低的挡水并能溢流的水工建筑物,用于提高水位,以便灌溉、发电或便利航运。陂堰用条块石浆砌、河卵石干砌,有的用混凝土或木(藤)框填石等做成,统称石陂。为抵抗溢流水力冲击,一般用堰闸式分级跌水消能,以保护堰体安全。临时性陂堰用沙土(打桩、垫草)筑成,枯水时期挡水,洪水时期被冲,即称沙土陂。
漳浦县陂堰建设,早在唐垂拱二年(686年)陈元光建置漳州和漳浦县前后,在开屯建堡的同时,为发展农业生产,把治水作为安邦的重要决策,大兴农田水利,利用河流丰富的水源,“引、蓄、泄”结合,在河流中修筑陂堰,引水灌溉农田,确保粮食丰收。宋代,漳浦的陂堰建设进一步发展,据《福建通志》记载:漳浦县在南宋淳熙(1174~1189年)年间有陂62座。随后,因抗旱需要,又修建一些重点陂堰。明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曾任南京御史的詹惠,在深土灶山东麓修筑詹厝陂(今改建东平水库)。清康熙三年(1664年)、九年(1670年)、十二年(1673年)、三十年(1691年)、三十六年(1697年)和四十年(1701年),连续发生6次较大早灾,一些失修陂堰又被重修扩建。据康熙《漳浦县志》记载:清康熙年间有陂33座:除在六都(今云霄县)有5座外,在七都(今深土、旧镇等地)有詹厝陂、灶山陂、东陂等3座;自县城西郊至八都(今绥安、盘陀、大南坂等地)有涂陂、大港陂、留庆陂、大陂、梧桐陂、猪母陂、梦花陂,以及官陂、磁窟陂、洪陂、黄陂、周陂、杨仔陂、许厝陂、赤髻陂陂陂、九窟陂等16座;在十五都(今赤湖一带)有月屿陂、坂园陂、西园陂、后腰陂等4座;在十七都(今湖西一带)有开元陂;在二十八都(今长桥、官浔等地)有横口陂、陂和陈翁陂等3座(长美陂在今龙海市)。但因年久失修,大部分报废。如绥安镇西门外猪母陂、梦花陂分别建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和十八年(1661年),早已报废。湖西畬族乡还留有清朝末期兴建的罗汉陂和青溜圳石陂。清末至民国时期兴建的尚存陂堰有19座,其中最多的是山区赤岭畬族乡,有17座:油坑村有石宫陂、橄仔陂、下楼陂、大宅陂、后招陂等5座;山坪村有降坑陂、刈垅陂、代陂、红陂等4座;前园村有红、马陂和西线陂等3座;石椅村有吴山陂、松脚陂等2座;土塔村有柴陂、陂仔脚陂等2座;大行村有红陂1座。其余2座:前亭镇田中央村有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兴建的黄陂;深土镇山尾村有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兴建的坑内陂。
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兴建的陂堰(石陂)有:
五十年代兴建陂堰58座。较早的有:霞美镇刘坂村于1950年8月兴建垅内石陂(灌溉千亩以下),湖西畲族乡城内村于1951年10月建成院内石陂(灌溉千亩以上),盘陀镇刈埔村于1953年10月建成官陂石陂(灌溉千亩以上),石榴镇扳龙村于1953年11月兴建沙下石陂(灌溉千亩以下),杜浔镇过洋村于1955年3月建成陂头石陂(灌溉千亩以上),沙西镇涂楼村于1955年12月兴建三防埭石陂(灌溉千亩以下),马坪镇京野村于1955年5月兴建的上陂石陂(长71米、高2.5米)、1958年5月再建下陂石陂(长67米、高1.5米),开挖引水渠道总长7公里,保灌农田面积0.15万亩。
六十年代兴建陂堰64座。由于1963年发生历史罕见的百日大旱,虽然后期开展“文化大革命”,而全县仍有13个乡镇兴建陂堰,其中最多的是石榴镇,兴建17座;其次是赤岭畬族乡,兴建10座;第三是霞美、前亭镇各8座。杜浔镇湖里村于1965年5月建成灌溉千亩以上的湖底港上石陂;赤湖镇山油村于1967年9月建成灌溉千亩以上的山油石陂;官浔镇溪坂村于1968年建成马口石陂(长142米、高2.5米),引水流量0.5立方米/秒,保灌农田面积0.10万亩。
七十年代,在“农业学大寨”期间,大搞改溪,引、蓄结合,有16个乡镇兴建陂堰84座,其中兴建陂堰7座以上的乡镇有绥安、石榴、赤土、深土、霞美、杜浔、沙西等。石榴镇石榴村在1975年“农业学大寨”改溪时,把原来建在长兴溪上游的石榴石陂废弃,1977年在新挖的双陂溪新建后坑寨石陂(1984年12月20日重建,长32米、高3.7米),保灌农田面积0.14万亩。绥安镇绥南村于1978年在鹿溪中游兴建梧桐石陂,长26米、高2.4米,设排洪闸1孔(宽1.2米),开挖渠道长8.3公里,引水流量1.2立方米/秒,灌溉农田面积0.37万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指导下,水利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管理上来,有15个乡镇把资金集中于修建陂堰,加上八十年代发生4次较大干旱,全县新建陂陂陂堰83座,其中最多的是石榴镇,新建陂堰26座。1978年1月,县水电部门在鹿溪主河道上游(象牙村)观音亭桥下1.6公里处,建成内湖水电站(装机容量1600千瓦/2台),拦截溪流水发电。象牙村于1980年投资10.7万元(其中国家补助9万元),投劳3.1万工日(其中技工1.3万工日),完成土石方0.71万立方米(其中石方0.34万立方米),于1983年底新建下陂石陂(长48米、高9.7米),引、蓄水量22.5万立方米,解决象牙、扳龙两村农田面积0.25万亩灌溉用水。1983年和1986年发生百日夏、秋干旱,又新建陂堰11座;1988年发生“六月旱”,促使1989年大建陂堰,是有史以来修建陂堰最多的一年,新建陂堰26座,整修、加固、改建陂堰43座。赤湖镇西潘村,依靠群众,自力更生,改沙土陂为石陂,每个人口集资25元计12万元,每个劳力出20个工日计2.8万工日,完成土石方2.5万立方米(其中石方0.24万立方米),于1988年9月在赤湖溪中游(下黄自然村)新建西潘石陂(长93米、高1.5米,设闸7孔,每孔宽1米),开挖东、西渠总长6公里,引水流量0.8立方米/秒,保灌农田面积0.34万亩(其中自流灌溉水田面积0.24万亩)。绥安镇油车村连续两年自筹资金4.05万元,于1988年春建成溪埔石陂,1989年春又新建田洋石陂(长22米、高1.7米),当年新增灌溉面积654亩。盘陀镇盘陀村集资5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万元),于1989年3月16日建成米仓石陂(长40米、高1.2米),保灌农田面积0.10万亩,1989年全村粮食总产量64万公斤,比1988年增产25%。湖西畬族乡苏溪、山后、城内、枋林等4个村,投资20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0万元),投劳1.4万工日(其中技工0.12万工日),完成土石方1.48万立方米(其中石方0.15万立方米),于1989年5月16日在赤湖溪中游山后村,建成1座长70米、高3.12米(顶宽10米)的山后石陂,结束了从明末至清初三百年来年年修沙土陂的历史,新增和改善灌溉农田面积0.29万亩,1990年增产粮食11.2万公斤。受益区农民特立“扶持农桑,垂荣百世;千秋功业,党恩铭记”的石碑纪念。
九十年代,全县又有17个乡镇兴建陂堰53座。南浦乡南浦村,继1989年12月建成灌溉千亩以上的陂湖石陂(长75米、高2.5米)后,1990年9月又建成茭冬石陂(长46米、高2米),保灌农田面积500亩。深土镇东吴村,于1990年10月扩建东吴石陂(长27.6米、高3米),除旧闸1孔(宽2米)外,新建排洪闸2孔(每孔2.2米),保灌农田面积0.4万亩。绥安镇下梧村,于1990年11月建成下梧石陂(长18米、高1.8米,排洪闸1孔宽1.3米),保灌农田面积0.13万亩。旧镇镇东厝村于1991年8月建成灌溉千亩以上的陂内石陂(长32米、高1.5米),确保粮食稳产高产。
据1994年10月全县陂堰普查:除古雷、六鳌两个半岛外,18个乡镇148个村建陂堰365座(包括建国前兴建的23座)。最多的石榴镇有陂堰72座(其中扳龙村14座、山城和崎溪村各7座);其次是赤岭畲族乡有陂堰42座(其中油坑村16座);第三是霞美镇有陂堰35座。在365座中,灌溉千亩以上陂堰有50座。最多的是绥安镇有9座;其次是石榴镇有7座;第三是杜浔镇和湖西畲族乡(包括罗汉、青溜圳)各有6座。陂堰受益总面积19.6万亩(保灌农田面积10.1万亩),其中灌溉千亩以上陂堰受益面积9.4万亩(保灌农田面积7.2万亩),占受益总面积的48%。
王福祥·陈桂味
编者按:本文两位作者都是亲历此工程的领导人:王福祥以漳浦县交通局副局长任工程副指挥;陈桂味则是当时分管的副县长。这种可贵的“三亲资料”可供存史资治,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亲历者为《漳浦文史资料》写稿,存下丰富的史实资料。
盘陀岭,地处梁山山脉中段,漳浦、云霄两县交界,汉代为闽越、南越交界,设蒲葵关,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和官府关隘要口。解放后,岭上修建公路,与云霄衔接,沟通广东,为国道324线原399公里200米~405公里632米地段。“盘陀岭上几盘陀,半山云雾车难过”,这里坡陡弯急,上下山6公里,共有弯道64个,最小的急弯半径才23米,最大的纵坡达85%,遇上春夏雨季,山中云雾缭绕,汽车穿云破雾,行走于山巅深涧之间,再老练的司机也提心吊胆,谨慎爬涉。交通事故时有发生,据统计,从1984年至1987年,在岭上路段发生翻车、撞车事故年平均47起之多。驾驶员望岭兴叹,称之为云中天险鬼门关。
这样的路段与当时汽车日流量5~6千辆的国道极不相称,已成了324线卡脖子地段。改善这一交通“瓶颈”的呼声日益强烈。自1985起,引起各级交通部门的重视,省市县交通、公路部门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就盘陀岭路段改造问题分别到实地勘察、调研,作工程可行性论证。1986年6月,交通部王展意副部长亲自到盘陀视察、调查,尔后交通部又派了3位高级工程师前来实地勘察,1986年初夏,省交通厅长亲率省公路局及有关处的领导现场办公,比较一致的方案是打隧道方案。返省城后,交通厅作出建设盘陀岭隧道的决定。1987年6月,隧道工程设计单位——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工程技术人员到现场测设,1988年9月1日,工程招标在福州揭晓,工程由铁道部第十六工程局中标,同年10月,施工队伍——第十六工程局四处的工人、技术人员进场,拉开了隧道工程会战序幕。
指挥部“特别能战斗”
盘陀岭隧道工程是省市“七五”交通建设重点之一,由省公路局投资建设,市、县负责工程的前期工作和工程施工过程的协调、服务和监督。漳州市委、市政府,漳浦、云霄两县县委、县政府对工程十分重视,由市政府行文成立工程指挥部,由当时市委副书记李天森任总指挥,市交通局长高南胜、市公路局副局长林国英任副总指挥,漳浦县交通局副局长王福祥、云霄县交通局副局长周三桂任常务副指挥,还有市、县政府办公室、公安、土地、财政等有关部门的领导作为指挥部领导成员。指挥部按照“理顺、协调、监督、服务”职能,开展工作。在李天森同志的领导下,在工程的每一阶段,任劳任怨,无私奉献,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工程前期,指挥部头一件大事就是要在短时间内做好工程的征地折迁和工地“三通一平”,这是每个工程的“难点”,当然也是隧道工程的难点之一,指挥部紧密依靠两县政府和当地盘陀乡、火田乡党委、政府的配合,漳浦、云霄两县政府都指定一位副县长直接参与这项工作,当地乡党委政府除指定一名主干和几名干部专职做这项工作外,遇到重大问题,党政第一把手都亲自解决,所在地的村干部也很快地形成共识,形成明意义、顾大局、讲奉献的氛围,指挥部的同志和县、乡、村干部共同深入实地丈量土地,清点菁苗,深入群众,开会动员,走家串户做政治思想工作,大量的群众工作在短时间内解决。在此基础上,指挥部同志结合交通、公路、土地等部门工程技术人员,开展工程用地复测、放样会战,时值盛夏三伏,测量现场大部分是“坑垅”和陡坡,荆棘丛生,蚊虫猖獗。气温高,湿度大,既热又闷,尤其是十点以后响午时刻,更是难熬,为避免蚊虫叮咬,大热天不得不穿冬服,每天都有同志中暑,但也是咬住牙根坚持下去。遇到测点在坑沟峭壁上,负责测量的助理工程师林孔周同志腰绑绳索,悬挂在峭壁上测量,一丝不苟。更难能可贵的是总指挥李天森、副总指挥高南胜等领导同志,身先士卒,爬山越坑垅,跳涧涉溪,和同志们共同战斗,极大地鼓舞同志们的斗志。原计划需用一个多月时间才能完成征地折迁工作,仅用15天就办完成。该工程共征地270亩,迁移坟墓54座、通讯线路3.5公里,处理(迁、砍)果树、林木15.3万株。
完成征地折迁之后,“三通一平”的关键是通电,本来打算从漳浦火烧埔12万伏变电站引接专线,但线路长达28公里,需要投资60多万元,架设线路最快也要花一个多月,耗资大,时间长。为了节省资金,缩短工期,指挥部同志和县电力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多方勘察,电力工程师何重光废寝忘食,精心设计,提出从隧道附近的梁山二级电站架设线路到工地的“短、平、快”方案,可缩短线路24公里,节省资金50万元,这一方案得到市、县领导的肯定和支持,县领导专门召开协调会,及时解决送电的一系列具体问题,漳浦电力公司技工仅用10天时间,将线路架设完成,提前通电,确保按期开工。
前期工作的顺利进行,为工程开工打下良好的基础。担负隧道施工任务的铁道部十六工程局四处指挥部雷光华副指挥长十分感激,在开工典礼上说:“我们工程每前进一步,都倾注着地方党委政府和工程指挥部的全部心血。”这支队伍自1988年10月进场施工,就以铁道兵打硬仗、排万难的作风,投入紧张有序的施工。打隧道是铁道兵在行活,但四处的同志大部分是北方人,南下福建搞工程施工,对这里的气候、环境、水土很不适应,在他们日常工作中,多了一层克服环境差异而带来的困难,高温、台风、暴雨,施工面的地质、泉眼、塌方等情况经常困扰着,指挥长坐卧不安。粗略统计,工程队自1988年10月进场施工至工程竣工,经历六次台风和暴雨的袭击,每次台风暴雨,既给工程造成严重损失,也是对指挥部的一次考验。如1989年5月20日下午,第3号台风正面袭击漳浦,工地上风狂雨骤,山洪暴发,正在施工的第一涵洞便道被山洪冲毁,山体塌方600多立方米,岭上的公路也被冲毁,往来车辆受阻,顿时堵车长达20多公里,在这关键时刻,工程指挥部的正副指挥、市县公路局领导和县府领导,都陆续赶到现场,指挥抢修,与施工人员一同奋战三昼夜,才把冲毁路段修复。又是1989年6月3日的龙卷风袭击工地,800多平方米的工棚顷刻间被大风卷掉,施工人员的住宿和生活遇到困难,指挥部及时通过乡政府,动员当地群众腾出民房,安顿施工人员的住宿和生活。在工地上,哪里有困难,有险(灾)情,指挥部的人员就出现在哪里,他们紧密配合施工单位,尽“理顺、协调、监督、服务”之职能,以苦为荣,默默奉献,赢得了省市领导和施工单位的称赞,称之为“特别能战斗”的工程指挥部。
他们仍然是“最可爱的人”
担任工程施工任务的铁道部十六工程局四处干部职工,是一支从铁道兵集体转业改地方编制的施工队伍,虽不见帽徽、领章、军衔,但铁道兵打硬仗,不畏难,吃大苦,耐大劳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依然在这支队伍中得到充分体现和发扬。
盘陀岭地质比较复杂。工程一开工就遇到隧道漳浦端洞前区的控方全是流塑状的粘土,推土机、铲车不顶用,运载泥土的卡车有27辆次陷入粘泥中而不能自拔,一辆推土机陷得只剩下驾驶室露出地面,用3台装载机联动才把它拖出来。洞前区这样的工作面,有90米长,共2.3万土方。在困难面前,四处指挥部分别召开党总支会、党员会,及部分职工大会,发按支部、党员作用,走群众路线,让大家出谋献策。在这关键时刻,指挥长刘仁全连续接到家里发来的“母病重速归”、“母病危速归”、“母病故速归”三封电报,但为了工程排除险难,他没有尽做孝子的孝心,强忍悲痛,一直坚持在岗位上,尽做指挥的责任。还有主管技术的工程师陈晓明,妻子分娩,也顾不上请假去照料。在指挥长的带动下,指挥部二十多位机关干部都下工地与工人们同住同吃同劳动,上下拧成一股绳,采用多种办法,终于完成洞前区粘土开挖任务,打响了工程第一炮,“铁道兵铁打的汉”的高大形象展现出来了,赢得了地方党政干部的钦佩。
打洞挖掘施工,多采用现代化的机械设备,机械施工烟灰、尘土多,尽管洞内安置有3台1000千瓦的通风机,工人们戴着防尘面具也只能坚持工作两个小时,每个工班(6小时一工班)都有人晕倒。在这种施工环境中,四处指挥部领导以身作则,轮流跟班指挥施工。每台装载机配备4名司机轮班作业,谁晕倒,机械队长万安友同志就顶谁的班,做到人轮换机不停,日掘进长度计划不能少。有一次,洞内出现300多立方米的大塌方,四处指挥部立即组织以党团员干部为主体的抢险突击队,采用“管棚法”施工方案,制服塌方,排除险情,工程继续掘进。
在隧道云霄端的施工中,机械队的双臂凿岩台车是机械施工的主力,只有副队长魏志荣能开这台车。正在施工紧张阶段,小魏家里发生火灾,5间房子全部被烧,父老妻小无处栖身,家里发来电报,催小魏速归处理,小魏心急如焚,巴不得插翅飞回,但眼下又是施工紧张阶段,开双臂凿岩台车非他莫属,只写封信安慰家里,自己坚持开车凿岩,直到完成云霄端打洞凿岩任务后,才登上归家路程。类似这样的事,在四处指挥部员工中,还有许多,正是这支顽强、工作过硬的战斗群体,才能承担这样的工程。南征北战的铁道兵队伍,其甜酸苦辣,是我们许多人不能理解和难以承受的。在这里,值得多写一笔的是,在这支打硬仗的队伍背后,有一群能理解、谅解、支持丈夫事业的家属们,尽管笔者与她们从未谋面,但从几多事实,从四处指挥部同志口中,足以透过这支队伍,看到千里之外的大本营的职工家属们,为了“前方”的丈夫安心施工所作出的奉献和付出的代价。尽管她们的丈夫已卸去军装,但她们仍然是可敬的“军嫂”。卡车司机张学民,是安徽籍的小伙子,在工地上也是一条打硬仗的汉子,在一次洞内塌方中牺性了年轻的生命,他的父母兄弟妻子来队料理后事,头尾共住4天,第五天便启程北上回家。这期间,他们没有向组织提出过非份要求,只听到他们这样说:“我们的亲人为国家建设而牺牲,他死得光荣。”这是多么高尚的情操,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张学民同志献身于盘陀岭隧道,他的事迹,他的名字,将长留在闽南人心中!
“为了国家建设,我们情愿吃亏”
盘陀岭公路隧道工程共征地270亩,要迁砍15万株果树、林木,涉及两县200多户农民的切身利益。按上级规定,公路建设征地、赔菁等项的价格低于其它建设用地,被征用的乡村土地承包户必须为国家建设作一定奉献。这除对这些被征用户的宣传发动要做得深透外,还要这里农民兄弟通情达理,顾全大局。拿荔枝、龙眼果树来说,此果是闽南名优特产,此树称为摇钱树,时下一公斤龙眼12~14元,一公斤鲜荔枝7~8元,一株盛果期的龙眼树,每年可采收50~75公斤龙眼果,一株盛果期的荔枝树,每年可采收75~100公斤荔枝果,砍掉果树,分明是断了果农的生计。但为了国家建设,农民兄弟没有讨价还价,“忍痛割爱”。隧道西端的云霄火田乡古楼村,需要动迁砍伐荔枝树200多棵、香蕉1000多株。村党支部书记林解放,带头砍掉自家年收入数万元的45棵荔枝树,村委主任林金海带领四兄弟带头砍掉自家一大片香蕉。在干部带动下,该村群众也没有二话,为建设让路,为建路砍掉摇钱树。漳浦盘陀乡和美村农民陈如德、陈如阳,在隧道东端洞前区一带栽种的香蕉1000多株,长势不错,眼看创收在即,遇到工程动工,他们态度明朗,带领家人,在期限内把香蕉全部砍掉。由于当地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征地、赔菁仅用半个月时间完成任务。
还有,在工程建设遇到难题的时候,遇到抗灾抢险的时候,当地群众有求必应,像50年代支前一样,踊跃参加工程的排难抢险行列之中。洞前粘土开挖,施工遇到困难,需要人工突击抢挖,盘陀近百名农民,在乡领导带领下,自带工具到工地“支前”,和工人们并肩战斗。当台风暴雨把工棚全部刮倒,工人们住宿、吃饭遇到困难的时候,又是当地农民让出自家房屋,提供食宿……。有人曾问,这样做有没有感到吃亏点,农民们回答得好:为了国家建设,吃点亏大家情愿,值得。
盘陀岭隧道和公路改线全长4.567公里,其中隧道长822.3米,洞里净高7米,宽9米,两端接线公路3.745公里,路基宽12米,路面宽9米。全工程挖填土石方46.9万立方米,建造公路涵洞20座,达584.6延米,防护工程砌石5686立方米,共计耗工51万工日,总投资2500多万元。工程从1988年10月动工,1991年8月1日竣工通车,历时2年10个月。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为隧道题写匾额,镌刻在洞口额顶大理石上,苍劲有力,使隧道显得气势非凡。
一洞横贯盘陀岭,云中天险变通途。在盘陀岭隧道建成通车5周年之际,伫立隧道口,观南来北往的车辆穿梭过洞,目不暇接。杨成武将军的题字“盘陀岭隧道”镏金石刻大字,在晨曦中闪烁光芒,追今抚昔,轰轰烈烈的工程建设场面,依然清晰,一幕幕印在脑际。笔者想以工程参与者的身份,把工程建设者们的忘我拼搏,流血流汗,工程指挥者们的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当地群众讲风格、讲奉献的情怀,记录下来。囿于手拙笔钝,只从笔记和记忆中摘取以上片断,以此献给工程的建设者们,也愿大家长久记得盘陀岭隧道建设的日日夜夜。
“高路入云端”——车本公路建设记实
·陈桂味·
在漳浦县西北部,与平和、龙海二县(市)交界处,是绵亘数百里的石屏山脉。这里崇山峻岭,层峦叠嶂,深涧峭壁,丛林茂密,莽莽葱葱,主峰海拔1006米,是漳浦县最高峰,还有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峰6座,其中900米以上的5座。
在石屏山山脉中段,有一座海拔815米的烘炉山,东南阳坡的一处坳地上,有一个村落叫车本,是全县海拔最高、地处最偏的山村,今有63户346人,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建国以来一直是一个行政村编制,公社化时称车本大队,乡镇建制后称车本村。
这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村,特定的自然地理位置,为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创造了良好的活动场所,中共闽粤边特委、靖和浦中心县委机关都先后设在车本村,邓子恢、曾志、卢胜、彭德清、朱曼平、吴运琳、柯永麟等革命老前辈都曾在此开展革命斗争工作,建立苏维埃政权,领导工农红军、游击队和工农群众向国民党反动派开展艰苦卓绝的斗争。车本人民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年代,付出巨大的牺牲和沉重的代价。这是一片洒满革命先烈鲜血的热土,这是一个打不烂,摧不垮的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共于革命战争时期在闽南地区的战斗堡垒。
解放后,车本村作为革命根据地,革命基点村,在政治上经济上备受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关心和支持,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经济状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1986年,全村58户332口,有耕地320亩、山地19228亩、田地以种植水稻为主,山地以竹林为主。村办有小学,校舍一座五开间,在校学生46人,分三班,有教师四人,学龄儿童基本都上学,由于生员缺乏,学校实行间年招生。村办水电站装机容量15千瓦,可供全村照明及碾米机、粉碎饲料机、电视机用电。村民的居住条件也逐年改善,户户住上瓦房,虽也老式,但还实用。温饱间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毕竟处在大山深处,发展经济受诸多条件制约,与平原、沿海地区的发展尚有一段较长的距离。
在制约车本村经济发展的诸因素中,道路交通是一大制约因素,从解放后至1987年公路动工前这近40年间,并不是当时的领导,当时的群众没想到修路,而是社会发展条件、经济发展条件达不到,使车本村民们仍旧盘旋于崎岖山道。已通简便公路的山脚下龙岭村、山城村(也是革命老根据地基点村),距车本村最近也有8公里,村里有木材、毛竹出售,要一根根一捆捆肩扛下山,其工资甚至超过木料的身价;村民需用的生产、生活资料,也全靠肩扛背驮上山,其工效和劳动强度不言而喻。
解决车本村通公路,提高车本村劳动生产率,缩短老区、边远山区与沿海平原地区的经济差距的历史责任,当然地落在当代人民政府肩上,1987年11月26~29日召开的漳浦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县长王良才所作的政府报告上,把车本公路建设列为本届政府为民办实事之一,向人民代表、全县人民表示了县政府的态度和决心。县人大会议一结束,王县长在第一次政府常务会上(1987年12月23日),立即把本届政府为民兴办十件实事的实施,分到各位副县长,其中车本公路建设分工由我组织实施。
1988年1月6日,我带县交通局局长杨江南、工程股长杨恭贤、公路段段长洪双连、老区办主任吴天化、干部商土生,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及石榴乡副乡长王建文等同志,上车本村作公路选线踏勘。同志们不辞劳苦,在荆棘丛生,时有石壁山涧挡阻的无路荒山上选路线,为尽快地在这样一个地形复杂、高差过大的山地上,找到了一线车本——山城可建接近四级公路的走向线路。中旬,由交通局工程股长杨恭贤率全股室工程技术人员到实地开展外业测量,他们是邱先增、黄耀辉、潘在福、杨一枝、杨昆山、林培文、黄明地、林孔超及驾驶员杨金安、魏漳明等同志,在乡、村干部群众配合下,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山高路险,用六天时间,完成车本——山城线7.2公里的外业测量任务。到3月30日,完成内业的设计计算。
测设的车本公路,从山城村起点,全长7.2公里,其中山城村地界3.07公里,车本村地界4.5公里(山城村为车本公路建设让出耕地、山地,贡献很大)。道路平曲线共有122个,平均每公里17.13个,弯道半径10米的(最小半径)一个,最大半径200米,有四个。纵坡大于10%的有七段,长度2060米。平均纵坡6.8%。道路竖曲线半径在500米的有七处,竖曲线半径在700米的有一处,在1000米以上的有十处。设计全线路基总挖方120426立方米,其中土方60212.9立方米,软石24085.3立方米,坚石36127.8立方米。填方37429立方米。路面结构为泥结碎石压实,铺设面积26300平方米。工程造价(不含土地及赔菁)64.万元。7月19日,我同交通局、土地局、老区办领导、工程技术人员,以及车本扶贫工作队队长,到石榴乡征求乡领导对道路设计、投资预算的意见,及对开工日期、资金筹措等有关事项作初步安排,明确乡、村免费征用公路用地及赔菁、拆迁费用,建路资金全由县里为主筹措,县、乡对此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
8月23日,县委书记承光大召集交通、公路、老区等有关部门会议,专题听取车本公路测设情况汇报,研究施工前的准备工作。10月4日,由副县长杨安乐(其时,县政府对副县长的分管工作作了调整,我增加分管农业、乡镇企业,交通工作由杨安乐分管)、交通局长邱秋月、老区办主任吴天化、乡党委书记张丛生等领导同志为车本公路开工动土,由交通局选派的三支工程队近百人陆续进场施工,这三支筑路工程队施工经验丰富,特别能吃苦,队长分别为蔡国庆、陈凤阳、郑万芳、陈云成(分地段承包),尤其是蔡国庆、陈凤阳两个施工队,坚持始终,他们克服地形复杂,施工难度大,工价较低,生活条件差等诸多困难,直到工程完竣。一年的施工中,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承光大书记、王良才县长、杨安乐副县长多次深入施工现场,检查指导督促,对老区人民和施工队伍以巨大鼓舞。县老区办主任吴天化同志一直坚持在工地,具体协调工程的各方面工作,督促指挥工程队施工,作为一位打游击出身的老同志,对老区人民一向怀着满腔热情,对老区事业,一向执着追求,他明知已届离休年龄,但却不辞劳苦,坚持承担副指挥的职务,直到车本公路开通,才离开岗位,光荣离休。
1989年11月上旬,进行全面完工的扫尾工作。15日,车本公路举行隆重的通车剪彩庆典,老区山城村、车本村披上节日盛装,老区人民兴高彩烈,喜迎省市县乡前来参加庆典的领导和同志们。曾经战斗在龙岭、山城、车本革命老区的红军战士、老首长卢叨(原省政协副主席)偕夫人韦立(原省总工会副主席)、柯志达(原龙溪地委副书记)、陈天才(原龙溪行署副专员)、蔡新生(原漳州市政协副主席)等老前辈,同省市县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县五套班子在家的领导,参加庆典,县委书记承光大、县长王良才、老同志卢叨为工程剪彩。
车本公路建成通车,从此结束了车本村民行路难的厉史,高路入云端,汽车山中行。车本公路的建成通车,为车本村铺就一条通达经济振兴的大道,车本村人民将以此为新起点,去追求,去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我们祝愿,我们祈盼,富有革命传统的老区车本人民,立足山区,团结拼搏,共创美好的明天。
漳浦县陂堰建设
陈章兴
堰,漳浦县方言叫“陂”。陂堰亦称“拦河堰”,即建筑在河流中较低的挡水并能溢流的水工建筑物,用于提高水位,以便灌溉、发电或便利航运。陂堰用条块石浆砌、河卵石干砌,有的用混凝土或木(藤)框填石等做成,统称石陂。为抵抗溢流水力冲击,一般用堰闸式分级跌水消能,以保护堰体安全。临时性陂堰用沙土(打桩、垫草)筑成,枯水时期挡水,洪水时期被冲,即称沙土陂。
漳浦县陂堰建设,早在唐垂拱二年(686年)陈元光建置漳州和漳浦县前后,在开屯建堡的同时,为发展农业生产,把治水作为安邦的重要决策,大兴农田水利,利用河流丰富的水源,“引、蓄、泄”结合,在河流中修筑陂堰,引水灌溉农田,确保粮食丰收。宋代,漳浦的陂堰建设进一步发展,据《福建通志》记载:漳浦县在南宋淳熙(1174~1189年)年间有陂62座。随后,因抗旱需要,又修建一些重点陂堰。明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曾任南京御史的詹惠,在深土灶山东麓修筑詹厝陂(今改建东平水库)。清康熙三年(1664年)、九年(1670年)、十二年(1673年)、三十年(1691年)、三十六年(1697年)和四十年(1701年),连续发生6次较大早灾,一些失修陂堰又被重修扩建。据康熙《漳浦县志》记载:清康熙年间有陂33座:除在六都(今云霄县)有5座外,在七都(今深土、旧镇等地)有詹厝陂、灶山陂、东陂等3座;自县城西郊至八都(今绥安、盘陀、大南坂等地)有涂陂、大港陂、留庆陂、大陂、梧桐陂、猪母陂、梦花陂,以及官陂、磁窟陂、洪陂、黄陂、周陂、杨仔陂、许厝陂、赤髻陂陂陂、九窟陂等16座;在十五都(今赤湖一带)有月屿陂、坂园陂、西园陂、后腰陂等4座;在十七都(今湖西一带)有开元陂;在二十八都(今长桥、官浔等地)有横口陂、陂和陈翁陂等3座(长美陂在今龙海市)。但因年久失修,大部分报废。如绥安镇西门外猪母陂、梦花陂分别建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和十八年(1661年),早已报废。湖西畬族乡还留有清朝末期兴建的罗汉陂和青溜圳石陂。清末至民国时期兴建的尚存陂堰有19座,其中最多的是山区赤岭畬族乡,有17座:油坑村有石宫陂、橄仔陂、下楼陂、大宅陂、后招陂等5座;山坪村有降坑陂、刈垅陂、代陂、红陂等4座;前园村有红、马陂和西线陂等3座;石椅村有吴山陂、松脚陂等2座;土塔村有柴陂、陂仔脚陂等2座;大行村有红陂1座。其余2座:前亭镇田中央村有于民国三十年(1941年)兴建的黄陂;深土镇山尾村有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兴建的坑内陂。
新中国成立后各个时期兴建的陂堰(石陂)有:
五十年代兴建陂堰58座。较早的有:霞美镇刘坂村于1950年8月兴建垅内石陂(灌溉千亩以下),湖西畲族乡城内村于1951年10月建成院内石陂(灌溉千亩以上),盘陀镇刈埔村于1953年10月建成官陂石陂(灌溉千亩以上),石榴镇扳龙村于1953年11月兴建沙下石陂(灌溉千亩以下),杜浔镇过洋村于1955年3月建成陂头石陂(灌溉千亩以上),沙西镇涂楼村于1955年12月兴建三防埭石陂(灌溉千亩以下),马坪镇京野村于1955年5月兴建的上陂石陂(长71米、高2.5米)、1958年5月再建下陂石陂(长67米、高1.5米),开挖引水渠道总长7公里,保灌农田面积0.15万亩。
六十年代兴建陂堰64座。由于1963年发生历史罕见的百日大旱,虽然后期开展“文化大革命”,而全县仍有13个乡镇兴建陂堰,其中最多的是石榴镇,兴建17座;其次是赤岭畬族乡,兴建10座;第三是霞美、前亭镇各8座。杜浔镇湖里村于1965年5月建成灌溉千亩以上的湖底港上石陂;赤湖镇山油村于1967年9月建成灌溉千亩以上的山油石陂;官浔镇溪坂村于1968年建成马口石陂(长142米、高2.5米),引水流量0.5立方米/秒,保灌农田面积0.10万亩。
七十年代,在“农业学大寨”期间,大搞改溪,引、蓄结合,有16个乡镇兴建陂堰84座,其中兴建陂堰7座以上的乡镇有绥安、石榴、赤土、深土、霞美、杜浔、沙西等。石榴镇石榴村在1975年“农业学大寨”改溪时,把原来建在长兴溪上游的石榴石陂废弃,1977年在新挖的双陂溪新建后坑寨石陂(1984年12月20日重建,长32米、高3.7米),保灌农田面积0.14万亩。绥安镇绥南村于1978年在鹿溪中游兴建梧桐石陂,长26米、高2.4米,设排洪闸1孔(宽1.2米),开挖渠道长8.3公里,引水流量1.2立方米/秒,灌溉农田面积0.37万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指导下,水利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管理上来,有15个乡镇把资金集中于修建陂堰,加上八十年代发生4次较大干旱,全县新建陂陂陂堰83座,其中最多的是石榴镇,新建陂堰26座。1978年1月,县水电部门在鹿溪主河道上游(象牙村)观音亭桥下1.6公里处,建成内湖水电站(装机容量1600千瓦/2台),拦截溪流水发电。象牙村于1980年投资10.7万元(其中国家补助9万元),投劳3.1万工日(其中技工1.3万工日),完成土石方0.71万立方米(其中石方0.34万立方米),于1983年底新建下陂石陂(长48米、高9.7米),引、蓄水量22.5万立方米,解决象牙、扳龙两村农田面积0.25万亩灌溉用水。1983年和1986年发生百日夏、秋干旱,又新建陂堰11座;1988年发生“六月旱”,促使1989年大建陂堰,是有史以来修建陂堰最多的一年,新建陂堰26座,整修、加固、改建陂堰43座。赤湖镇西潘村,依靠群众,自力更生,改沙土陂为石陂,每个人口集资25元计12万元,每个劳力出20个工日计2.8万工日,完成土石方2.5万立方米(其中石方0.24万立方米),于1988年9月在赤湖溪中游(下黄自然村)新建西潘石陂(长93米、高1.5米,设闸7孔,每孔宽1米),开挖东、西渠总长6公里,引水流量0.8立方米/秒,保灌农田面积0.34万亩(其中自流灌溉水田面积0.24万亩)。绥安镇油车村连续两年自筹资金4.05万元,于1988年春建成溪埔石陂,1989年春又新建田洋石陂(长22米、高1.7米),当年新增灌溉面积654亩。盘陀镇盘陀村集资5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万元),于1989年3月16日建成米仓石陂(长40米、高1.2米),保灌农田面积0.10万亩,1989年全村粮食总产量64万公斤,比1988年增产25%。湖西畬族乡苏溪、山后、城内、枋林等4个村,投资20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0万元),投劳1.4万工日(其中技工0.12万工日),完成土石方1.48万立方米(其中石方0.15万立方米),于1989年5月16日在赤湖溪中游山后村,建成1座长70米、高3.12米(顶宽10米)的山后石陂,结束了从明末至清初三百年来年年修沙土陂的历史,新增和改善灌溉农田面积0.29万亩,1990年增产粮食11.2万公斤。受益区农民特立“扶持农桑,垂荣百世;千秋功业,党恩铭记”的石碑纪念。
九十年代,全县又有17个乡镇兴建陂堰53座。南浦乡南浦村,继1989年12月建成灌溉千亩以上的陂湖石陂(长75米、高2.5米)后,1990年9月又建成茭冬石陂(长46米、高2米),保灌农田面积500亩。深土镇东吴村,于1990年10月扩建东吴石陂(长27.6米、高3米),除旧闸1孔(宽2米)外,新建排洪闸2孔(每孔2.2米),保灌农田面积0.4万亩。绥安镇下梧村,于1990年11月建成下梧石陂(长18米、高1.8米,排洪闸1孔宽1.3米),保灌农田面积0.13万亩。旧镇镇东厝村于1991年8月建成灌溉千亩以上的陂内石陂(长32米、高1.5米),确保粮食稳产高产。
据1994年10月全县陂堰普查:除古雷、六鳌两个半岛外,18个乡镇148个村建陂堰365座(包括建国前兴建的23座)。最多的石榴镇有陂堰72座(其中扳龙村14座、山城和崎溪村各7座);其次是赤岭畲族乡有陂堰42座(其中油坑村16座);第三是霞美镇有陂堰35座。在365座中,灌溉千亩以上陂堰有50座。最多的是绥安镇有9座;其次是石榴镇有7座;第三是杜浔镇和湖西畲族乡(包括罗汉、青溜圳)各有6座。陂堰受益总面积19.6万亩(保灌农田面积10.1万亩),其中灌溉千亩以上陂堰受益面积9.4万亩(保灌农田面积7.2万亩),占受益总面积的48%。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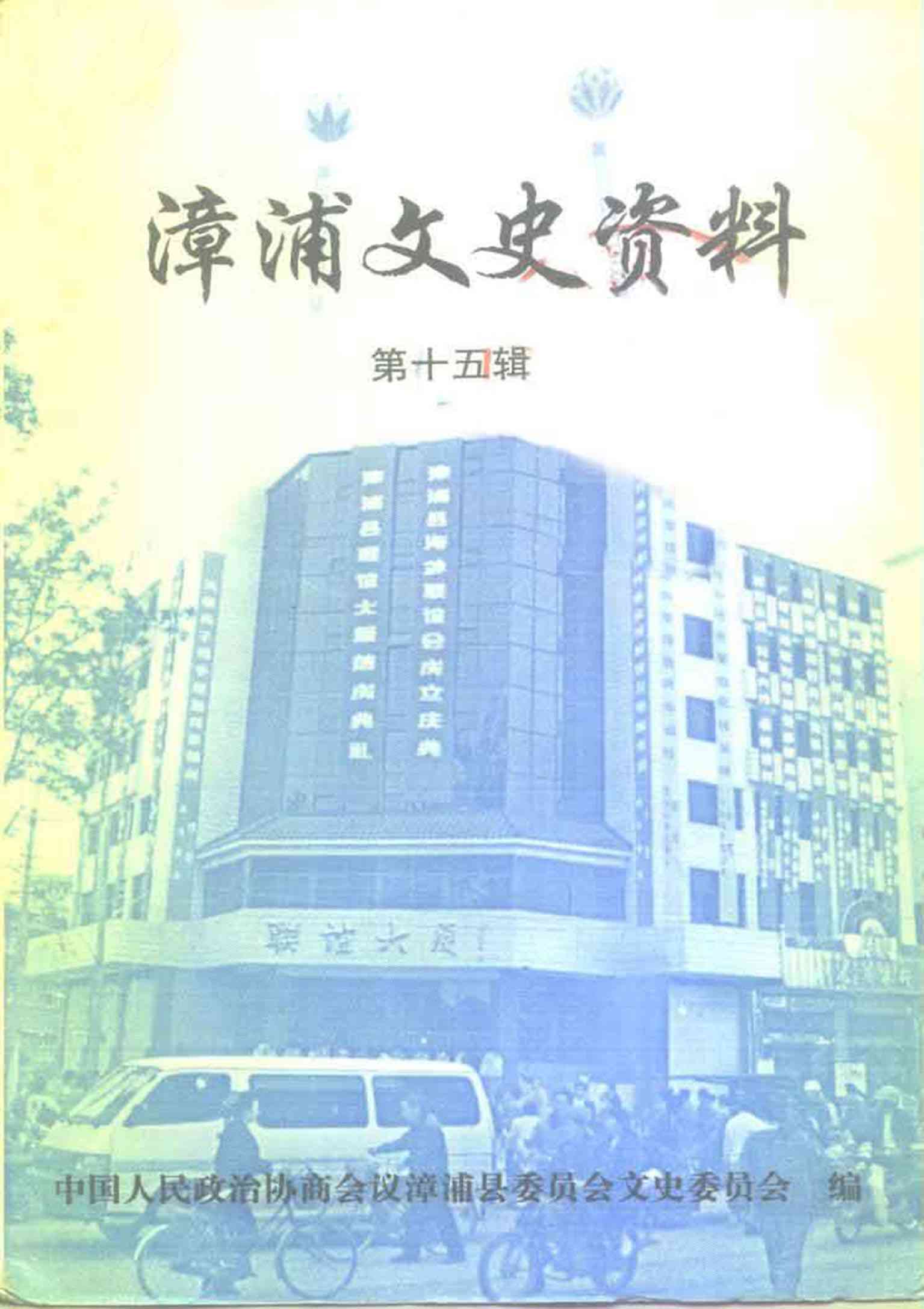
相关地名
漳浦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