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的发现和保护、研究
| 内容出处: | 《漳浦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30000764 |
| 颗粒名称: | 文物的发现和保护、研究 |
| 分类号: | K872.57 |
| 页数: | 17 |
| 页码: | 94-110 |
| 摘要: | 这段文章描述了自五十年代以来,漳浦县进行文物考古工作的一系列发现和发掘经历。从1955年开始,为配合各地水利工程建设,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文物干部到水利工地实地学习,其中刘两全参加了东山水库发掘工地的学习。随后,不断有重要的发现和发掘工作,包括新石器时代遗址、宋代瓷窑址、陶器残片、古墓等。在1958年,省博物馆的人员清理出土了包括镇墓兽俑、立俑、动物俑、陶器在内的文物。此外,文章还详细介绍了漳浦县明清时代的楼堡建筑以及石敢当的文化现象。最后,文章提到了1965年夏天在漳浦县城发现的一座古铜炮,并描述了其发现过程和处理。 |
| 关键词: | 漳浦县 文物考古 水利工程 |
内容
漳浦四十年来地下文物的调查和发掘
王文径
漳浦县的文物考古工作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一九五五年,为了配合各地的水利工程建设,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各地文化馆文物干部到各建设工地,实地学习,漳浦由刘两全前往参加了在东山的水库发掘工地学习。回来后就下到各水利工地现场调查,省博物馆也经常派员下乡进行指导和重点调查,由于水库的选址位置常都是古人类喜欢选择的居住区,所以这一段时间,不断有重要的发现和发掘工作。
1957年2月,于杜浔祖妈林水库建设工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省博物馆很快就派员下来,采集了一些石锛、石戈、有肩石斧、砂陶、泥陶片,以及铜斧等,证实这里原是古人类主要的生活区和墓葬区,并发现了一座宋代的瓷窑址。之后厦门历史系的老师也前来,采集的一些标本,一直作为人类博物馆的展品。1957年12月,在赤土眉力水库工地上发现部分陶器残片,省文管会、厦门大学先后派人来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处称石路遗址,并清理出残墓四座,出土石戈、石锛、石环、石镞、陶豆、罐、垒、钵、壶、陶纺纶等。这是漳浦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始。
1958年3月,霞美刘坂大山水库工地发现一座古墓,由省博物馆林宗煌和县文化馆刘两全等联合进行清理。出土镇墓兽俑、立俑,动物俑、盘口罐、瓷碗、壶、木梳、铜钱、铁棺钉等113件。该墓葬作长方形,砖迭涩锥形墓顶。有前后墓室,两边各有五个壁龛,形制较为规范,定为唐中期至五代之间。清理报告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这是漳浦县文物发掘资料的第一次发表。
之后文化馆文物干部亦多次配合基本建设,作了一些调查和清理工作,均因项目较小或因没有留下正式报告,出土文物也大多于十年动乱中散失殆尽,成果难以评说,其中尚有所闻的有火烧埔蓝廷珍墓,大南坂元代、明代墓葬,旧镇造船厂商周墓,以及祖妈林水库发现晋纪年墓砖,石榴畜牧场发现商周彩陶罐等,都有极其重大的价值,其中晋纪年墓砖和彩陶填补了闽南考古的空白。
进入八十年代,工作进入正常化,重要的地上地下文物开始不断被发现,其中有院前山商周遗址,罗宛井宋代窑址,南门坑南宋窑址,竹树山宋窑址,澎水明窑址。1986年初,湖西的农民在鸡母石山开山时出土陶俑,被乡政府收回并报文化馆前往进行清理,出土陶俑三十几件,陶罐、瓷碗、罐等十几件,经研究为五代土坑墓,清理报告在《福建文博》发表。
同年六月,省文管会在漳浦召开了全省的文物普查工作会议,十二月,省考古队王振镛,粟建安等十人与漳浦文化馆,各文化站组成文物普查小组,对全县范围内的地下文物,特别是商周时代遗址以及一些地面文物系统全面的普查,普查工作为期十天,发现了五十六处商周时代的遗址及一些地面文物。基本查清了漳浦古文化遗址的分布情况及类型,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文物普查。
1987年7月,盘陀镇汤坑庙埔村一古墓被盗,至第七天清早,村民赶到现场,赶走盗贼,自行进入被挖的女棺室,取出随葬品,村委准备将这批文物出卖,作为修建桥梁的经费,后被派出所发现没收,乡书记许展文亲自将有关材料和墓碑碑文送县公安局,有关人员认定为明万历间的户工二部侍郎卢维祯夫妇合葬墓,经电话报省文管办同意,七月八日,由县文化局黄以结,带领县文化馆杨和祺,王文径,刘两全等人员,在盘陀派出所的配合下,对该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该墓形制甚大,前有五十米长的墓道,分列五组石像生,墓碑后四米才为墓葬封土,三合土封土层厚达2.0米,其中外层0.6米为三合土夹青花瓷片层,内1.4米为质量极高的糯米浆三合土,硬度相当岩石,且有极好的韧性,最后只好采用炸药爆破,经炸了八次后,才露出券顶砖室,在进行表土清理时,于墓碑室之间无意中发现了武英殿大学士戴曜撰写的墓志,对于后期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文字材料。卢维祯的棺木至当天下午五时左右才抬出墓室,用八个人抬到公路边,晚上近九时才运到县城,保存于旧县堂里。
之后的两天里,选择启棺方案,考虑到可能是一具干尸,或可以保存的尸体,对于防腐保存的问题也做了周密的安排,并请来了县医院杨南泰主治医生,做了尸体解剖的准备。
十一日早上开始在旧县堂里进行启棺清理,数百人参加了围观,公安部门在门外进行维护秩序和保卫。只好用椅子在县堂内又隔开一个空间,由王文径、刘两全以及一名“土公”进入现场工作。其余工作人员包括厦门大学考古系吴诗池副教授及六名学生,录相、摄影人员等都在椅子外观看。启棺后发现最上层的,深褐色的裹尸布下罩着一个清瘦的老人,揭开裹尸布后,发现尸体其实已经全部腐烂,只剩因水银的作用而变黑了的骨头。由于棺中纺织品的填充和支撑,人形和随葬品的位置没有改变。便依次从腰部开始,取出墨盘,木算盘、紫砂壶。腰带,印章,健身槌等文物,其中有一个曾被误认为是书籍的布包里,原来是一个木奁,装着明仿汉的昭明连弧铜镜,以及木梳,牙托筒。整个清理工作到了下午才告结束。
这次发掘、清理出土卢维祯随葬品及女棺被盗,后来移交的文物共一百多件,其中明时大彬制款紫砂壶、菱形珠木算盘,橄榄形木漆健身锤,青玉笔架,银带板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时大彬制紫砂壶列为中国文物精华。这次发掘清理,是漳浦依靠自己的人员进行的较完整的考古工作,且资料完整,年代和墓主身份材料准确,清理过程录相,摄影和文字完备,更主要的是出土文物极为丰富,有几项填补了空白,此后清理报告在南京博物院的《东南文化》发表,部分珍贵文物在国内外十几种刊物上介绍,引起了文物考古界的重视。十一月份,省文化厅和公安厅还为此联合在漳浦召开了打击盗掘和走私文物犯罪活动的大会,盗窃此墓的案情也有了完整的了结。
卢维祯墓的发掘可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一年后的同一天,1988年7月11日,霞美镇冷冻厂工地上又发现了一座古墓,根据工程要求,不得不进行抢救性的清理发掘。该墓为砖室券顶双室,墓主为明万历初,广东参政刘霖父刘大成。但仅出土了青花瓷罐,汪东川制墨条,木算盘珠等几件文物。紧接着的8月份,旧镇甘林村又一古墓被盗,文化部门进行清理发掘,和刘大成的棺木一样,都运到黄道周纪念馆中启棺,也出土真川林子墨、圆瓷砚、折扇、毛笔、铜镜等。该棺木和纺织品随葬品都保存得极为完好,甚至裹尸布上的纸钱也还保存原折叠的形状,只是尸体充分腐烂,分析该墓的地理环境,封土情况,棺木质量等都符合最佳防腐条件,尸体完全腐烂的原因是其死亡季节和入葬时间欠佳。
八十年代后期正是漳浦地区盗掘古墓之风极盛的时期,此后又有了几次较小规模的清理发掘工作,88年12月,清理了位于官浔镇赵厝村后的明崇祯五年(1632年)郭次吾夫妇合葬墓,仅出土了一件木质发束。该墓葬式较特殊,土坑中有椁有棺,上复灰土四层,大有古风,在闽南同时期葬式中仅见。89年2月,清理了石榴镇后埔村一明代中期的券顶砖式墓,墓在村中,移到村后清理,出土了一件马蹄形铁器,作用不详,一件鸠头形木杖,说明墓主的死亡年龄在七十岁以上。4月份,又应该村村民和派出所要求,清理了学校边一座多次被炸,严重危及村民和学校安全的清初墓葬,出土石砚、木奁盒、须夹等文物十件。
1989年8月,对盘陀镇庵前村一古墓因水土严重流失,村民取土等原因,三合土封土完全裸露于地表之上,多次发生盗贼企图炸墓,危及村民安全,为此又进行了一起较大形的清理活动。墓为三葬,其中一葬已于早年被盗,封土外层石构,二层三合灰土,内为券顶砖室,于男女棺中出土银带板,木算盘、三层石砚,余仰制墨等文物,其中木算盘为目前已知绝对年代最早的算盘。墓主为明嘉靖二十年进士,官至广东佥事的陈梧。
1989年10月,在湖西又相继进行了两次清理发掘工作,一是湖西后山村一座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古墓被盗后,于墓上三合土层中发现大量青花瓷碗,总数估计在一千五百件以上,但质量甚差,清理进度很慢,仅取出了其中的一部分,由于这类墓葬有一定的特色,且对陶瓷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清理报告也发表于《南方文物》。
1989年11月,鉴于陈元光的祖庙问题一直没有肯定的结论,于是对漳浦威惠庙进行全面的调查及局部的试掘,揭露了六个探方,一百多平方米,发现了三层地面,出土了大量唐中期以下至明清各代瓷陶残片、各类石构件,各式瓦当等。初步查清威惠庙平面布置情况,认定其建筑年代在唐中期。这次调查清理形成报告,参加了在漳州召开的〈陈元光与漳州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成果受到各界的认同,从而使漳浦威惠庙的历史地位得到确认。
九十年代初,可能境内的明清墓葬已经被盗掘差不多了,所见大多是早期的墓葬,仅在503台、检察院工地发现和清理了二座唐墓和一座明墓,在赵家堡边发掘了一座明代中期的墓。直至1993年9月,博物馆人员在文物调查中,听说有人于山上取回一件有刻字的破砖,当即前往进一步调查,在深土灶山上找到一座被盗的石室双葬墓,遂用了三天的时间,进行进一步清理,该墓用条石构筑,各有一个前室和十个壁龛,在壁龛中出土了四十几件未被移动过的陶俑,并收回了被盗有买地券,多咀壶等文物,这是漳浦地区第一次发现的有纪年的唐墓,对于校正不少墓葬的年代有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其中的买地券,因有明显“大唐国福建道”的字样,对于研究福建在唐代的行政设置和区划有重大研究价值,历史上一直认为福建属于江南道和江南东道。只有近代学者朱维斡提出唐代福建也曾设道的论点,漳浦这件买地券的出土,是对这一论点的有力支持。
漳浦明清楼堡的楼名和匾额
王文径
漳浦明清时代至少有楼堡一百三十几座,绝对年代最早的为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的一德楼,稍后的贻燕楼,庆云楼,晏海楼,完壁楼,远远早于闽西南其他县份,年代最晚且有绝对年代的为光绪年间的垂裕楼,其中最多为清乾隆年间所建,约占楼堡总数的五分之二。土楼堡的平面建筑形式有单圈圆楼,双圈圆楼,三圈圆楼,多圈圆楼,半圆楼(俗称粪箕楼),方楼,双重方楼,外圆内方楼,万字形(俗称风车辇楼),八角楼以及不规则形楼等;层高一层至四层不等;内部分配有单元式和内通廊式二种;墙体结构有条石乱石砌筑,三合土夯筑,生土夯筑或混合结构多种。这些楼堡,几乎都有一个堂而皇之的,雅致的楼名。漳浦现存的楼堡中,除了因楼匾早年已遗失破坏,或原楼主家族搬迁,没有传下楼名外,基本都能找到楼名。现尚没有查到楼名的只有楼仔堡,上黄楼,东林土楼,白庙楼,路边楼,内窟楼,中径楼,庵后楼等约三十座,对现存有楼匾或有传下楼名的,本文在此略作介绍。
楼堡的命名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反映了楼堡主人建楼的心态,建楼的目的和祝愿,二是表现了楼堡所处的位置,环境和地理。
楼堡的兴建主要为了防卫,抵御匪盗,祈求平安,所以楼名常用“安”、“宁”、“保”“和”等安样,所见有大安楼,万安楼,保滋楼,保安楼,宁远楼,均和楼,阜安楼,德安楼,锦安楼,长安楼,永宁楼,时安楼,天和楼等;由于明清时期的海盗贼寇多来自海上,所以“清”、“晏”之类的字样也常见于楼名,如晏海楼,清晏楼,永清堡,寿清楼,其中在相距不到十公里的石桥村和大油柑村,两座楼堡均采用了清晏楼这一楼名。著名的完壁楼取完壁归赵之意,楼堡主人姓赵,出自显赫的皇族,有过不平常的经历,用完壁归赵之典取名,恰当地反映了楼主的心态。蓝延珍建楼时,正是他官运亨通,不断升迁之时,有感于皇恩浩荡,将楼取名日接楼。
易安楼建于湖西乡西效的高山上,地处荒凉,难得有几个人到过,取楼名“易安”。建于县城北面深山中的静远楼,背靠高山,前为古道,四周林木箫森,奇石高耸,楼前溪涧长流,诚如楼名,偏远而幽静;而攀云楼所处漳浦最高的梁山下,楼虽不高,但取名攀云,表达了楼主攀附梁山之意;南浦的碧鹤楼则因风水先生认为楼所处为鹤地,所以用了这个楼名。
湖西有一座人和城,佛昙有一座人和楼,反映了主人面对着复杂的社会环境,期望楼内外的人能同舟共济,患难与共,同时也是主人认为楼所处的位置具备地利,建楼迎合天时。盘陀、石榴各有一座济美楼,楼名也表达了楼主希望楼中族人团结互济的愿望;县城北郊有一座卿和楼,石榴、赤湖各有一座均和楼,可能是楼建造后将平均分配到族中各户,并将聚族而居的反映。
更多的楼名采用民间通俗的吉样字,如“瑞”、“德”、“贻”、“燕”、“福”、“裕”等,所见有瑞安楼,一德楼,德安楼,拱福楼,迎紫楼,垂裕楼,诒燕楼等。
城门匾一般写二字或四字。如“诒安”、“迎曦”、“东方钜障”、“雄图星共”等,而楼堡名一般为三字,目前已知有二座为四字,一为南浦的龙门屏瀚楼,楼处于南浦南溪边,背依黄炉山,二为绥安的瞻云北阙楼,楼前为漳浦的主要河流鹿溪,正对着漳浦的主要山脉梁山主峰金刚山,都是对楼周围的地理环境的描绘和赞美。
由于建楼堡的原因、目的、愿望基本相同,所以楼名相同或相近的情况很多,就目前所知,宁远楼就有两座,济美楼,清晏楼,均和楼,也各有两座,长桥东升、万安古陂各有一座建于乾隆年间的诒燕楼,霞美过田有一座贻燕楼,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石榴崎溪的燕诒楼,为万字形,建于清乾年代,地域相差甚远,楼名却相同相近,使人难以分清。
楼匾通常为花岗岩石雕刻,有边框或无边框,也有的匾面与边框分为五块组合而成。城门匾所见有隶书,如霞陵城的三个匾。楼堡名一般作楷书,以示庄重,用行书或行草的仅见“完壁楼”、“易安楼”、“迎紫楼”三例。
楼匾多数无署名,如蔡新建造了永清堡,他平日喜欢舞文弄墨,在漳浦留下了不少笔墨文字,其时又是他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之时,匾名也出自这位大学士之手,但仅于边款写“乾隆已丑年腊月谷旦建”,此外如完壁楼,万安楼等,明确为当时的大官僚建造,却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当然,楼匾上不署名,也并非绝对,“南天一柱”杨世茂建造的永安楼,匾边刻有“康熙戊寅吉旦建,四明范光阳书”的款识,建于隆庆三年的庆云楼,边款为“隆庆已己季春立,林一阳书”,瑞安楼则在纪年下刻“杖国著英许学圣建”,龙门屏瀚楼下款仅刻“张国经”以及一枚印章,也有单纯用印章的,如蓝延珍建造的日接楼,上下款就刻着蓝延珍的名章字章及一枚闲章,湖西姑嫂洞前的易安楼,前亭文山的大安楼,除了纪年外,也钤盖了一枚名章,可惜无法看清。以上,是漳浦现存一百多座楼堡中仅见的名款了,比例实在太少,可见这里应包含着某种我们未知的文化现象。
而在楼名下刻上闲章的现象则不在少数。如保滋楼,上下款均刻成云纹形的吉样字印章,诒燕楼刻“子孙”、“攸居”,攀云楼刻“乾隆已己”、“汤水朝宗”、“梁山拱秀”三枚章,可惜不少楼堡匾上的闲章多半风化严重,难以辨认。
绝大多数的匾名下有纪年,通常为年号和千支,但个别仅有干支没有年号,如沧瀛楼,个别有名款没有年号和干支,如龙门屏瀚楼,也有一些仅题楼名,不署上下款。我们注意到,这类楼堡大多是清初的作品,这是特殊的时代的产物,在明清之交,或清代初期,明代虽然在编年史上已经结束,但弘光,隆武等还先后在南方活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期,漳浦沿海属郑成功的势力范围和清军交叉控制,刘坂城门匾上的“弘光元年元旦”纪年,则将对明王朝的忠诚和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只存在了几个月的南明弘光小王朝上,确也难能可贵,成了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的忠实记载。但时后不久,各种军事和政治势力交替加快,人们再也无可适从了,以至不知如何纪年。旧镇沧瀛楼,只于楼名后署“戊子年”的干支,据此和当地传说推算,可知楼建于顺治五年,同样的,张国经为明天启二年进士,光禄寺卿,入清后不仕,题龙门屏瀚楼,楼明显是建于清初,但没有署年号和干支,却只署了题匾人的名字。这不敢署年号的作法,也可能慢慢形成为一种特殊的格式,并因此影响了很长的一段时期,在全县的楼堡中,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楼堡,只有被康熙称为南天一柱的杨世茂建造的永安楼有纪年,而蓝延珍死于雍正初年,楼明确建于康雍间,他题日接楼匾,上下款钤盖名章而无纪年款,建于康熙三十七年的湖西诒安楼,南浦的顺德楼,慎德楼,积庆楼,赤岭的时安楼等几座楼堡,都是年代可信而无纪年,极有可能是受到上述这种格式的影响。
人的名字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常常可以通过名字了解其人的意向,情趣,原籍,出生地,其父的文化素养,追求,对个人的所寄予的希望等等。楼堡的命名也具有这些因素,而楼名所透露给我们的信息当然更为广泛,意义尤为深远,而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探求。
漳浦的“石敢当”
王文径
石敢当是一个古老而普遍的话题,也唯其古老,所以值得探源;唯其普遍,不同的地区必然有不同地区的特色,漳浦也自有漳浦的石敢当。
关于石敢当的来源,最早见于记载的,是西汉元帝时的史游,在他的《急就章·一》中就出现了这个词。颜师古注道:“卫有石蜡、石买、石恶,郑有石制,皆为石氏;周有石速,齐有石之纷如、其后以命族,敢当,所向无敌也”,可见石敢当起源于战国时期,可能是人们对势炎熏人的大家庭的敬畏,因立此三字于屋前屋后,表示本宅的主人也不是好欺负的,特别是住宅的方位正对着别家的屋角,确实令人感到刺眼,但又没有理由计较,只能以此进行反击和警告,久而久之,其最初的意义便有所引伸,形式也有所变化。
宋代的王象之在《舆地纪胜·福建路》中记载:“庆历中,张纬宰莆田,再新县后,得一石铭其文日: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唐大历五年,县令郑,押字记”。这是一条最直接地指出石敢当全部功能的材料,但被王象之所载入,也说明这种近于烦琐的形式在宋代时也并不多见。因此还被历代不断引用。铭文所记述的这些厌胜功能,可以说是居家过日子的人共同需要的,因此受到认同,随着人口的迁徙,文化的播迁,成为中华大地上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唐代莆田的石敢当应是一种早期的罕见的形式,而最常见的是在住宅的拐角处,在正对着别家住宅的墙角的地方,立一石条,高0.5米至1米不等,阴刻“泰山石敢当”或“石敢当”,可能为了加强这石敢当的厌胜功能,有的则于铭文上刻一兽头,或刻“王”字,“三”字,作老虎状。佛昙的东坂村就有几个用浮雕刻一个狮子头,雕工虽然一般,但虎虎生气,威风凛凛,非但百鬼惧怕,邪恶却步,就是小孩看了也未必敢走上前去。这种形式也见于厦门地区,被称之为“石狮王”,在厦门的旧街里头,甚至还有一座奉祀着一块虎头柱石的石敢当庙。以此而类推,单纯地用石狮为避邪物,也可以起到石敢当的功能的,正对着路口的地方,确实常常可以见到一座规模极小的庙宇,庙中的香火烛光很少中断。这与面对小巷的石狮子及“石敢当”一样到处可见,即使那石狮子已经断了半个头,缺了一支脚,也仍在那里挡住迎面而来的严风。漳浦县城西街与麦市街拐角处因为放一只石狮而得“石狮头”地名,石狮久不存在而地名一直沿用。
在佛昙的港头村中,有一座建于明代晚期的土楼,高四层,规模极为宏大,称刁氏土楼,传说原楼主姓刁,后来林姓的势力渐渐扩大,刁氏只好迁走,楼也倒塌得只存一堵高墙,几条地基,楼门前有一座约建于清代的的民居,立着一通石敢当,正对楼门,除了刻着“泰山石敢当”外,上面有一个浮雕的八卦,八卦同样被认为具有避邪厌胜的功能,这两者的结合,作用将大大加强。但这种形式,却并不多见,笔者仅于87年7月在福州鼓岭别墅区边偶尔见到一件,后来多次提起,听者都以为难得。
漳浦深土的埭厝城中,是石敢当保存得较多的地区之一,该城建于明末,重建于清初,设有四门,西城内侧建有一座通常城堡必建的关帝庙,而关帝庙东侧有一座正对着城门的民居,便赫然立着一通石敢当,如果沿着城中拥挤且毫无规划的民居中穿行,窄小的过道中时不时就会挡住一通醒目的石敢当,在这些大同小异的碑石中,唯有北门内的一通,最有特色,那铭文写的是“李广将军箭在此”。这位西汉文帝时抗击匈奴,奇功盖世,却终生未得封候的飞将军,曾在一次夜巡中一箭射穿岩石,这见于正史记载,却令人无法解释的事,一直是中国人的千古美谈。而以李广箭代替石敢当,实在是一个聪明无比的办法,但不知其效力如何。
据说漳浦过去也有直接写“李广将军箭在此”于小纸条上,贴在某一适当的位置上,这当然是一种更简便的,适合于临时应急的办法了。可见李广将军箭在漳浦不是绝无仅有的。只是在漳浦之外,则尚未见于记述。
劫后余生“鲁王炮”
高幸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第三次恢复工作,出差到鼓浪屿“郑成功纪念馆”,蓦地见到一尊似曾相识的古炮,近前端祥,果然是漳浦出土的那一尊古铜炮,炮身上镌刻“钦命荡胡侯静波军门阮造,监国鲁伍年九月”依然历历在目。触物生情,感慨万分。它与我一样,同是“文化大革命”劫后余生的一族。
它现陈列在厦门郑成功纪念馆让人瞻仰,虽离开出土故地漳浦,却能更好地发挥其文物作用。说它离开故土也不对,它的故土应该说是在厦门。它之在漳浦,是因有这样一段历史:
清世祖顺治入关后在北京当上皇帝。残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由黄道周、郑芝龙等人拥立为帝,改元“隆武”。唐王与据守浙江台州府的鲁王朱以海,系叔侄辈。鲁王自封监国。由于两家暗中争权,各自为政,很快被清军各个击破。唐王逃至闽西,在汀州府内被乱箭射死。监国鲁王被阁臣熊汝霖,建威侯郑彩,定远伯郑联,从绍兴府护送经舟山到厦门。彩、联兄弟以厦门为据点。郑成功则据有南澳、铜山、古雷沿海一带。顺治四年(1647年)春,郑联率兵直入漳浦内地。
漳浦佛昙桥秀才杨学皋,集众万余响应反清,自为统帅,初受封于隆武,隆武亡后依附郑联,以洪有贞、杨商为副帅,于二月一日攻陷漳浦县城。清知县许国楠投井死。郑联立洪有贞为漳浦知县。五日后,清漳州游击唐钦明,都司郭秉诚等率清军反攻,杨学皋不敌退出县城,洪有贞被杀。
顺治七年五月,清总兵王邦俊挥师入漳浦袭击杨学皋,杨部大败,举白旗投降。同年八月,郑成功轻舟简卫,从南澳入厦门,于中秋夜诱杀郑联,并吞郑部。郑彩不知去向。后鲁王朱以海依附郑成功。
从这段历史看,该炮可能系原鲁王属下郑联部队,配合杨学皋进攻漳浦县城时使用的,匆忙撤退时来不及带走,浅埋于地下。
1965年夏天,一阵暴雨之后,漳浦县城木屐街陈文德住宅一处地板突然陷落。陈先生急忙掀掉砖块,挖出泥沙,深挖尺许,双手触及一黑黝黝的铁器。全家合力把泥沙剥开,原来是一尊古炮。陈先生犯愁了,古炮毕竟也是武器,家藏武器,祸必降临,尤其是“社教”运动如火如荼,那能让自己雪上加霜。因此急忙到城关派出所报告。派出所派警干许海军到陈家勘察,见果然是一尊古炮,即来文化馆要我去处理。我约了城关文化站站长卢溪河一起把这尊一米多长,重109公斤的古炮扛回文化馆。为了解炮的质地,用钢锯拉一小口,拉出来的全是铜盾,证明这是尊古铜炮。自此,它成为馆藏文物(当时博物馆尚未从文化馆分设)。
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狂飚席卷神州大地,处处掀起“破旧立新”、“斗私批修”怒涛,各地工农群众、干部职员、教师学生,谁也不愿失去当造反派的权利。然而要造谁的反,观点不同,也就出现了不同观点的派性组织,出现了“文攻武卫”,出现了“打、砸、抢”……
1967年夏天,一口悬挂在县政府食堂后钟楼上,原系兴教寺唐景福年间铸造的大铜钟(民国二十三年即1934年,第五行政区专员兼漳浦县长朱熙,将该铜钟从兴教寺移来,建造钟楼以报时,抗日战争期间,改作空袭报警之用。)此钟被“革命小将”砸成碎片,作为废铜卖给废品收购站,已是继砸“黄道周纪念馆”(毁大小上千件文物)之后的第二次“革命行动”。
同年夏天,我第一次恢复工作回文化馆,发现古铜炮不见了,尽管当时批斗“封、资、修”运动方兴未艾,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总不甘心让古炮再蹈古钟覆辙。从各方打听消息,得悉炮已被“革命小将”运往漳州,准备熔化,以铜出售。当时,政府及大部分职能部门已瘫痪,我写了一纸报告面交县委副书记蔡新生,报告内容之一,要外出追寻古炮;之二,出差车旅费等要给报销。蔡立即签字批准。
在漳州终于找到马卢等革命小将。他们承认铜炮已藏在某工厂仓库,由于售价未决尚未熔化。我对他们说明文物的重要,一旦毁之就成为历史罪人。马卢笑道:“我们缺乏活动经费,你说那么重要就卖给你吧。”我问:“要多少钱?”他说:“抽成铜丝,出厂价每斤两元,你拿两千元来吧。”我郑重对他说:“只要能完壁归赵,说不定能多出一倍钱给你们。”这位小将眯眼睨视,不相信地问:“真的你能搞到两三千元,要多少时间?”我说“当然有把握,十天为限可以吧?”他点头:“可以,一言为定。”
第二天,我赶到鼓浪屿郑成功纪念馆。纪念馆大门紧闭。询问附近人家,说:纪念馆人员转到厦门图书馆办公。我赶到厦门图书馆,找到厦门图书馆,找到纪念馆人员说明这一情况。纪念馆干部非常重视此事,立即挂电话到省文化厅,接电话的人说,不管价钱多少立即答应他们,绝不能让它毁掉。我要纪念馆派人带钱跟我到漳浦取炮;他们却要我负责把炮运到厦门,一手交炮,一手交钱。我说:“不成,漳州到厦门这条路我不熟识,昨天火车站莲坂武斗,打死好多人。再说,没现款那些造反小将能把铜炮交出来?”纪念馆的人也感到往漳州运炮不保险,但也想不出良策。无可奈何之下,我建议:“你们是不是请省厅通过支左部队,指令漳浦有关单位出面调查保护好此炮。”纪念馆的人同意这一办法。
我回到漳州后,见到专署文化局干部庄受惠,请他调查此炮下落,想法保护。庄说局里已接到龙溪军分区电话,并转达各工厂、收购站,一有讯息立即报告。听了老庄的话,我想此炮应无忧矣。
不久,我又第二次倒霉,被赶出县直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再次失去工作权利,古炮落入谁之手,也就无权打听了。
我第二次恢复工作后,庄受惠来找我,再次询问此古炮的出土、被盗经过。看来是漳州与厦门要研究古炮的归属问题。本来,我想“毛遂自荐”去证明此炮的出土经过和归属问题,想不到不久,我第三次大倒霉,又再失去工作权利。当时,我心里想,只要古炮在,厦门、漳州、漳浦都是家。
如今,劫后余生鲁王炮,鼓浪听涛更潇洒。
王文径
漳浦县的文物考古工作是从五十年代开始的,一九五五年,为了配合各地的水利工程建设,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各地文化馆文物干部到各建设工地,实地学习,漳浦由刘两全前往参加了在东山的水库发掘工地学习。回来后就下到各水利工地现场调查,省博物馆也经常派员下乡进行指导和重点调查,由于水库的选址位置常都是古人类喜欢选择的居住区,所以这一段时间,不断有重要的发现和发掘工作。
1957年2月,于杜浔祖妈林水库建设工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省博物馆很快就派员下来,采集了一些石锛、石戈、有肩石斧、砂陶、泥陶片,以及铜斧等,证实这里原是古人类主要的生活区和墓葬区,并发现了一座宋代的瓷窑址。之后厦门历史系的老师也前来,采集的一些标本,一直作为人类博物馆的展品。1957年12月,在赤土眉力水库工地上发现部分陶器残片,省文管会、厦门大学先后派人来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处称石路遗址,并清理出残墓四座,出土石戈、石锛、石环、石镞、陶豆、罐、垒、钵、壶、陶纺纶等。这是漳浦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始。
1958年3月,霞美刘坂大山水库工地发现一座古墓,由省博物馆林宗煌和县文化馆刘两全等联合进行清理。出土镇墓兽俑、立俑,动物俑、盘口罐、瓷碗、壶、木梳、铜钱、铁棺钉等113件。该墓葬作长方形,砖迭涩锥形墓顶。有前后墓室,两边各有五个壁龛,形制较为规范,定为唐中期至五代之间。清理报告发表于《文物参考资料》,这是漳浦县文物发掘资料的第一次发表。
之后文化馆文物干部亦多次配合基本建设,作了一些调查和清理工作,均因项目较小或因没有留下正式报告,出土文物也大多于十年动乱中散失殆尽,成果难以评说,其中尚有所闻的有火烧埔蓝廷珍墓,大南坂元代、明代墓葬,旧镇造船厂商周墓,以及祖妈林水库发现晋纪年墓砖,石榴畜牧场发现商周彩陶罐等,都有极其重大的价值,其中晋纪年墓砖和彩陶填补了闽南考古的空白。
进入八十年代,工作进入正常化,重要的地上地下文物开始不断被发现,其中有院前山商周遗址,罗宛井宋代窑址,南门坑南宋窑址,竹树山宋窑址,澎水明窑址。1986年初,湖西的农民在鸡母石山开山时出土陶俑,被乡政府收回并报文化馆前往进行清理,出土陶俑三十几件,陶罐、瓷碗、罐等十几件,经研究为五代土坑墓,清理报告在《福建文博》发表。
同年六月,省文管会在漳浦召开了全省的文物普查工作会议,十二月,省考古队王振镛,粟建安等十人与漳浦文化馆,各文化站组成文物普查小组,对全县范围内的地下文物,特别是商周时代遗址以及一些地面文物系统全面的普查,普查工作为期十天,发现了五十六处商周时代的遗址及一些地面文物。基本查清了漳浦古文化遗址的分布情况及类型,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文物普查。
1987年7月,盘陀镇汤坑庙埔村一古墓被盗,至第七天清早,村民赶到现场,赶走盗贼,自行进入被挖的女棺室,取出随葬品,村委准备将这批文物出卖,作为修建桥梁的经费,后被派出所发现没收,乡书记许展文亲自将有关材料和墓碑碑文送县公安局,有关人员认定为明万历间的户工二部侍郎卢维祯夫妇合葬墓,经电话报省文管办同意,七月八日,由县文化局黄以结,带领县文化馆杨和祺,王文径,刘两全等人员,在盘陀派出所的配合下,对该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该墓形制甚大,前有五十米长的墓道,分列五组石像生,墓碑后四米才为墓葬封土,三合土封土层厚达2.0米,其中外层0.6米为三合土夹青花瓷片层,内1.4米为质量极高的糯米浆三合土,硬度相当岩石,且有极好的韧性,最后只好采用炸药爆破,经炸了八次后,才露出券顶砖室,在进行表土清理时,于墓碑室之间无意中发现了武英殿大学士戴曜撰写的墓志,对于后期的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文字材料。卢维祯的棺木至当天下午五时左右才抬出墓室,用八个人抬到公路边,晚上近九时才运到县城,保存于旧县堂里。
之后的两天里,选择启棺方案,考虑到可能是一具干尸,或可以保存的尸体,对于防腐保存的问题也做了周密的安排,并请来了县医院杨南泰主治医生,做了尸体解剖的准备。
十一日早上开始在旧县堂里进行启棺清理,数百人参加了围观,公安部门在门外进行维护秩序和保卫。只好用椅子在县堂内又隔开一个空间,由王文径、刘两全以及一名“土公”进入现场工作。其余工作人员包括厦门大学考古系吴诗池副教授及六名学生,录相、摄影人员等都在椅子外观看。启棺后发现最上层的,深褐色的裹尸布下罩着一个清瘦的老人,揭开裹尸布后,发现尸体其实已经全部腐烂,只剩因水银的作用而变黑了的骨头。由于棺中纺织品的填充和支撑,人形和随葬品的位置没有改变。便依次从腰部开始,取出墨盘,木算盘、紫砂壶。腰带,印章,健身槌等文物,其中有一个曾被误认为是书籍的布包里,原来是一个木奁,装着明仿汉的昭明连弧铜镜,以及木梳,牙托筒。整个清理工作到了下午才告结束。
这次发掘、清理出土卢维祯随葬品及女棺被盗,后来移交的文物共一百多件,其中明时大彬制款紫砂壶、菱形珠木算盘,橄榄形木漆健身锤,青玉笔架,银带板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时大彬制紫砂壶列为中国文物精华。这次发掘清理,是漳浦依靠自己的人员进行的较完整的考古工作,且资料完整,年代和墓主身份材料准确,清理过程录相,摄影和文字完备,更主要的是出土文物极为丰富,有几项填补了空白,此后清理报告在南京博物院的《东南文化》发表,部分珍贵文物在国内外十几种刊物上介绍,引起了文物考古界的重视。十一月份,省文化厅和公安厅还为此联合在漳浦召开了打击盗掘和走私文物犯罪活动的大会,盗窃此墓的案情也有了完整的了结。
卢维祯墓的发掘可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一年后的同一天,1988年7月11日,霞美镇冷冻厂工地上又发现了一座古墓,根据工程要求,不得不进行抢救性的清理发掘。该墓为砖室券顶双室,墓主为明万历初,广东参政刘霖父刘大成。但仅出土了青花瓷罐,汪东川制墨条,木算盘珠等几件文物。紧接着的8月份,旧镇甘林村又一古墓被盗,文化部门进行清理发掘,和刘大成的棺木一样,都运到黄道周纪念馆中启棺,也出土真川林子墨、圆瓷砚、折扇、毛笔、铜镜等。该棺木和纺织品随葬品都保存得极为完好,甚至裹尸布上的纸钱也还保存原折叠的形状,只是尸体充分腐烂,分析该墓的地理环境,封土情况,棺木质量等都符合最佳防腐条件,尸体完全腐烂的原因是其死亡季节和入葬时间欠佳。
八十年代后期正是漳浦地区盗掘古墓之风极盛的时期,此后又有了几次较小规模的清理发掘工作,88年12月,清理了位于官浔镇赵厝村后的明崇祯五年(1632年)郭次吾夫妇合葬墓,仅出土了一件木质发束。该墓葬式较特殊,土坑中有椁有棺,上复灰土四层,大有古风,在闽南同时期葬式中仅见。89年2月,清理了石榴镇后埔村一明代中期的券顶砖式墓,墓在村中,移到村后清理,出土了一件马蹄形铁器,作用不详,一件鸠头形木杖,说明墓主的死亡年龄在七十岁以上。4月份,又应该村村民和派出所要求,清理了学校边一座多次被炸,严重危及村民和学校安全的清初墓葬,出土石砚、木奁盒、须夹等文物十件。
1989年8月,对盘陀镇庵前村一古墓因水土严重流失,村民取土等原因,三合土封土完全裸露于地表之上,多次发生盗贼企图炸墓,危及村民安全,为此又进行了一起较大形的清理活动。墓为三葬,其中一葬已于早年被盗,封土外层石构,二层三合灰土,内为券顶砖室,于男女棺中出土银带板,木算盘、三层石砚,余仰制墨等文物,其中木算盘为目前已知绝对年代最早的算盘。墓主为明嘉靖二十年进士,官至广东佥事的陈梧。
1989年10月,在湖西又相继进行了两次清理发掘工作,一是湖西后山村一座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古墓被盗后,于墓上三合土层中发现大量青花瓷碗,总数估计在一千五百件以上,但质量甚差,清理进度很慢,仅取出了其中的一部分,由于这类墓葬有一定的特色,且对陶瓷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清理报告也发表于《南方文物》。
1989年11月,鉴于陈元光的祖庙问题一直没有肯定的结论,于是对漳浦威惠庙进行全面的调查及局部的试掘,揭露了六个探方,一百多平方米,发现了三层地面,出土了大量唐中期以下至明清各代瓷陶残片、各类石构件,各式瓦当等。初步查清威惠庙平面布置情况,认定其建筑年代在唐中期。这次调查清理形成报告,参加了在漳州召开的〈陈元光与漳州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成果受到各界的认同,从而使漳浦威惠庙的历史地位得到确认。
九十年代初,可能境内的明清墓葬已经被盗掘差不多了,所见大多是早期的墓葬,仅在503台、检察院工地发现和清理了二座唐墓和一座明墓,在赵家堡边发掘了一座明代中期的墓。直至1993年9月,博物馆人员在文物调查中,听说有人于山上取回一件有刻字的破砖,当即前往进一步调查,在深土灶山上找到一座被盗的石室双葬墓,遂用了三天的时间,进行进一步清理,该墓用条石构筑,各有一个前室和十个壁龛,在壁龛中出土了四十几件未被移动过的陶俑,并收回了被盗有买地券,多咀壶等文物,这是漳浦地区第一次发现的有纪年的唐墓,对于校正不少墓葬的年代有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其中的买地券,因有明显“大唐国福建道”的字样,对于研究福建在唐代的行政设置和区划有重大研究价值,历史上一直认为福建属于江南道和江南东道。只有近代学者朱维斡提出唐代福建也曾设道的论点,漳浦这件买地券的出土,是对这一论点的有力支持。
漳浦明清楼堡的楼名和匾额
王文径
漳浦明清时代至少有楼堡一百三十几座,绝对年代最早的为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的一德楼,稍后的贻燕楼,庆云楼,晏海楼,完壁楼,远远早于闽西南其他县份,年代最晚且有绝对年代的为光绪年间的垂裕楼,其中最多为清乾隆年间所建,约占楼堡总数的五分之二。土楼堡的平面建筑形式有单圈圆楼,双圈圆楼,三圈圆楼,多圈圆楼,半圆楼(俗称粪箕楼),方楼,双重方楼,外圆内方楼,万字形(俗称风车辇楼),八角楼以及不规则形楼等;层高一层至四层不等;内部分配有单元式和内通廊式二种;墙体结构有条石乱石砌筑,三合土夯筑,生土夯筑或混合结构多种。这些楼堡,几乎都有一个堂而皇之的,雅致的楼名。漳浦现存的楼堡中,除了因楼匾早年已遗失破坏,或原楼主家族搬迁,没有传下楼名外,基本都能找到楼名。现尚没有查到楼名的只有楼仔堡,上黄楼,东林土楼,白庙楼,路边楼,内窟楼,中径楼,庵后楼等约三十座,对现存有楼匾或有传下楼名的,本文在此略作介绍。
楼堡的命名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反映了楼堡主人建楼的心态,建楼的目的和祝愿,二是表现了楼堡所处的位置,环境和地理。
楼堡的兴建主要为了防卫,抵御匪盗,祈求平安,所以楼名常用“安”、“宁”、“保”“和”等安样,所见有大安楼,万安楼,保滋楼,保安楼,宁远楼,均和楼,阜安楼,德安楼,锦安楼,长安楼,永宁楼,时安楼,天和楼等;由于明清时期的海盗贼寇多来自海上,所以“清”、“晏”之类的字样也常见于楼名,如晏海楼,清晏楼,永清堡,寿清楼,其中在相距不到十公里的石桥村和大油柑村,两座楼堡均采用了清晏楼这一楼名。著名的完壁楼取完壁归赵之意,楼堡主人姓赵,出自显赫的皇族,有过不平常的经历,用完壁归赵之典取名,恰当地反映了楼主的心态。蓝延珍建楼时,正是他官运亨通,不断升迁之时,有感于皇恩浩荡,将楼取名日接楼。
易安楼建于湖西乡西效的高山上,地处荒凉,难得有几个人到过,取楼名“易安”。建于县城北面深山中的静远楼,背靠高山,前为古道,四周林木箫森,奇石高耸,楼前溪涧长流,诚如楼名,偏远而幽静;而攀云楼所处漳浦最高的梁山下,楼虽不高,但取名攀云,表达了楼主攀附梁山之意;南浦的碧鹤楼则因风水先生认为楼所处为鹤地,所以用了这个楼名。
湖西有一座人和城,佛昙有一座人和楼,反映了主人面对着复杂的社会环境,期望楼内外的人能同舟共济,患难与共,同时也是主人认为楼所处的位置具备地利,建楼迎合天时。盘陀、石榴各有一座济美楼,楼名也表达了楼主希望楼中族人团结互济的愿望;县城北郊有一座卿和楼,石榴、赤湖各有一座均和楼,可能是楼建造后将平均分配到族中各户,并将聚族而居的反映。
更多的楼名采用民间通俗的吉样字,如“瑞”、“德”、“贻”、“燕”、“福”、“裕”等,所见有瑞安楼,一德楼,德安楼,拱福楼,迎紫楼,垂裕楼,诒燕楼等。
城门匾一般写二字或四字。如“诒安”、“迎曦”、“东方钜障”、“雄图星共”等,而楼堡名一般为三字,目前已知有二座为四字,一为南浦的龙门屏瀚楼,楼处于南浦南溪边,背依黄炉山,二为绥安的瞻云北阙楼,楼前为漳浦的主要河流鹿溪,正对着漳浦的主要山脉梁山主峰金刚山,都是对楼周围的地理环境的描绘和赞美。
由于建楼堡的原因、目的、愿望基本相同,所以楼名相同或相近的情况很多,就目前所知,宁远楼就有两座,济美楼,清晏楼,均和楼,也各有两座,长桥东升、万安古陂各有一座建于乾隆年间的诒燕楼,霞美过田有一座贻燕楼,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石榴崎溪的燕诒楼,为万字形,建于清乾年代,地域相差甚远,楼名却相同相近,使人难以分清。
楼匾通常为花岗岩石雕刻,有边框或无边框,也有的匾面与边框分为五块组合而成。城门匾所见有隶书,如霞陵城的三个匾。楼堡名一般作楷书,以示庄重,用行书或行草的仅见“完壁楼”、“易安楼”、“迎紫楼”三例。
楼匾多数无署名,如蔡新建造了永清堡,他平日喜欢舞文弄墨,在漳浦留下了不少笔墨文字,其时又是他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之时,匾名也出自这位大学士之手,但仅于边款写“乾隆已丑年腊月谷旦建”,此外如完壁楼,万安楼等,明确为当时的大官僚建造,却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当然,楼匾上不署名,也并非绝对,“南天一柱”杨世茂建造的永安楼,匾边刻有“康熙戊寅吉旦建,四明范光阳书”的款识,建于隆庆三年的庆云楼,边款为“隆庆已己季春立,林一阳书”,瑞安楼则在纪年下刻“杖国著英许学圣建”,龙门屏瀚楼下款仅刻“张国经”以及一枚印章,也有单纯用印章的,如蓝延珍建造的日接楼,上下款就刻着蓝延珍的名章字章及一枚闲章,湖西姑嫂洞前的易安楼,前亭文山的大安楼,除了纪年外,也钤盖了一枚名章,可惜无法看清。以上,是漳浦现存一百多座楼堡中仅见的名款了,比例实在太少,可见这里应包含着某种我们未知的文化现象。
而在楼名下刻上闲章的现象则不在少数。如保滋楼,上下款均刻成云纹形的吉样字印章,诒燕楼刻“子孙”、“攸居”,攀云楼刻“乾隆已己”、“汤水朝宗”、“梁山拱秀”三枚章,可惜不少楼堡匾上的闲章多半风化严重,难以辨认。
绝大多数的匾名下有纪年,通常为年号和千支,但个别仅有干支没有年号,如沧瀛楼,个别有名款没有年号和干支,如龙门屏瀚楼,也有一些仅题楼名,不署上下款。我们注意到,这类楼堡大多是清初的作品,这是特殊的时代的产物,在明清之交,或清代初期,明代虽然在编年史上已经结束,但弘光,隆武等还先后在南方活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期,漳浦沿海属郑成功的势力范围和清军交叉控制,刘坂城门匾上的“弘光元年元旦”纪年,则将对明王朝的忠诚和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只存在了几个月的南明弘光小王朝上,确也难能可贵,成了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的忠实记载。但时后不久,各种军事和政治势力交替加快,人们再也无可适从了,以至不知如何纪年。旧镇沧瀛楼,只于楼名后署“戊子年”的干支,据此和当地传说推算,可知楼建于顺治五年,同样的,张国经为明天启二年进士,光禄寺卿,入清后不仕,题龙门屏瀚楼,楼明显是建于清初,但没有署年号和干支,却只署了题匾人的名字。这不敢署年号的作法,也可能慢慢形成为一种特殊的格式,并因此影响了很长的一段时期,在全县的楼堡中,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楼堡,只有被康熙称为南天一柱的杨世茂建造的永安楼有纪年,而蓝延珍死于雍正初年,楼明确建于康雍间,他题日接楼匾,上下款钤盖名章而无纪年款,建于康熙三十七年的湖西诒安楼,南浦的顺德楼,慎德楼,积庆楼,赤岭的时安楼等几座楼堡,都是年代可信而无纪年,极有可能是受到上述这种格式的影响。
人的名字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常常可以通过名字了解其人的意向,情趣,原籍,出生地,其父的文化素养,追求,对个人的所寄予的希望等等。楼堡的命名也具有这些因素,而楼名所透露给我们的信息当然更为广泛,意义尤为深远,而很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探求。
漳浦的“石敢当”
王文径
石敢当是一个古老而普遍的话题,也唯其古老,所以值得探源;唯其普遍,不同的地区必然有不同地区的特色,漳浦也自有漳浦的石敢当。
关于石敢当的来源,最早见于记载的,是西汉元帝时的史游,在他的《急就章·一》中就出现了这个词。颜师古注道:“卫有石蜡、石买、石恶,郑有石制,皆为石氏;周有石速,齐有石之纷如、其后以命族,敢当,所向无敌也”,可见石敢当起源于战国时期,可能是人们对势炎熏人的大家庭的敬畏,因立此三字于屋前屋后,表示本宅的主人也不是好欺负的,特别是住宅的方位正对着别家的屋角,确实令人感到刺眼,但又没有理由计较,只能以此进行反击和警告,久而久之,其最初的意义便有所引伸,形式也有所变化。
宋代的王象之在《舆地纪胜·福建路》中记载:“庆历中,张纬宰莆田,再新县后,得一石铭其文日:石敢当,镇百鬼,压灾殃,官吏福,百姓康,风教盛,礼乐张。唐大历五年,县令郑,押字记”。这是一条最直接地指出石敢当全部功能的材料,但被王象之所载入,也说明这种近于烦琐的形式在宋代时也并不多见。因此还被历代不断引用。铭文所记述的这些厌胜功能,可以说是居家过日子的人共同需要的,因此受到认同,随着人口的迁徙,文化的播迁,成为中华大地上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
唐代莆田的石敢当应是一种早期的罕见的形式,而最常见的是在住宅的拐角处,在正对着别家住宅的墙角的地方,立一石条,高0.5米至1米不等,阴刻“泰山石敢当”或“石敢当”,可能为了加强这石敢当的厌胜功能,有的则于铭文上刻一兽头,或刻“王”字,“三”字,作老虎状。佛昙的东坂村就有几个用浮雕刻一个狮子头,雕工虽然一般,但虎虎生气,威风凛凛,非但百鬼惧怕,邪恶却步,就是小孩看了也未必敢走上前去。这种形式也见于厦门地区,被称之为“石狮王”,在厦门的旧街里头,甚至还有一座奉祀着一块虎头柱石的石敢当庙。以此而类推,单纯地用石狮为避邪物,也可以起到石敢当的功能的,正对着路口的地方,确实常常可以见到一座规模极小的庙宇,庙中的香火烛光很少中断。这与面对小巷的石狮子及“石敢当”一样到处可见,即使那石狮子已经断了半个头,缺了一支脚,也仍在那里挡住迎面而来的严风。漳浦县城西街与麦市街拐角处因为放一只石狮而得“石狮头”地名,石狮久不存在而地名一直沿用。
在佛昙的港头村中,有一座建于明代晚期的土楼,高四层,规模极为宏大,称刁氏土楼,传说原楼主姓刁,后来林姓的势力渐渐扩大,刁氏只好迁走,楼也倒塌得只存一堵高墙,几条地基,楼门前有一座约建于清代的的民居,立着一通石敢当,正对楼门,除了刻着“泰山石敢当”外,上面有一个浮雕的八卦,八卦同样被认为具有避邪厌胜的功能,这两者的结合,作用将大大加强。但这种形式,却并不多见,笔者仅于87年7月在福州鼓岭别墅区边偶尔见到一件,后来多次提起,听者都以为难得。
漳浦深土的埭厝城中,是石敢当保存得较多的地区之一,该城建于明末,重建于清初,设有四门,西城内侧建有一座通常城堡必建的关帝庙,而关帝庙东侧有一座正对着城门的民居,便赫然立着一通石敢当,如果沿着城中拥挤且毫无规划的民居中穿行,窄小的过道中时不时就会挡住一通醒目的石敢当,在这些大同小异的碑石中,唯有北门内的一通,最有特色,那铭文写的是“李广将军箭在此”。这位西汉文帝时抗击匈奴,奇功盖世,却终生未得封候的飞将军,曾在一次夜巡中一箭射穿岩石,这见于正史记载,却令人无法解释的事,一直是中国人的千古美谈。而以李广箭代替石敢当,实在是一个聪明无比的办法,但不知其效力如何。
据说漳浦过去也有直接写“李广将军箭在此”于小纸条上,贴在某一适当的位置上,这当然是一种更简便的,适合于临时应急的办法了。可见李广将军箭在漳浦不是绝无仅有的。只是在漳浦之外,则尚未见于记述。
劫后余生“鲁王炮”
高幸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第三次恢复工作,出差到鼓浪屿“郑成功纪念馆”,蓦地见到一尊似曾相识的古炮,近前端祥,果然是漳浦出土的那一尊古铜炮,炮身上镌刻“钦命荡胡侯静波军门阮造,监国鲁伍年九月”依然历历在目。触物生情,感慨万分。它与我一样,同是“文化大革命”劫后余生的一族。
它现陈列在厦门郑成功纪念馆让人瞻仰,虽离开出土故地漳浦,却能更好地发挥其文物作用。说它离开故土也不对,它的故土应该说是在厦门。它之在漳浦,是因有这样一段历史:
清世祖顺治入关后在北京当上皇帝。残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由黄道周、郑芝龙等人拥立为帝,改元“隆武”。唐王与据守浙江台州府的鲁王朱以海,系叔侄辈。鲁王自封监国。由于两家暗中争权,各自为政,很快被清军各个击破。唐王逃至闽西,在汀州府内被乱箭射死。监国鲁王被阁臣熊汝霖,建威侯郑彩,定远伯郑联,从绍兴府护送经舟山到厦门。彩、联兄弟以厦门为据点。郑成功则据有南澳、铜山、古雷沿海一带。顺治四年(1647年)春,郑联率兵直入漳浦内地。
漳浦佛昙桥秀才杨学皋,集众万余响应反清,自为统帅,初受封于隆武,隆武亡后依附郑联,以洪有贞、杨商为副帅,于二月一日攻陷漳浦县城。清知县许国楠投井死。郑联立洪有贞为漳浦知县。五日后,清漳州游击唐钦明,都司郭秉诚等率清军反攻,杨学皋不敌退出县城,洪有贞被杀。
顺治七年五月,清总兵王邦俊挥师入漳浦袭击杨学皋,杨部大败,举白旗投降。同年八月,郑成功轻舟简卫,从南澳入厦门,于中秋夜诱杀郑联,并吞郑部。郑彩不知去向。后鲁王朱以海依附郑成功。
从这段历史看,该炮可能系原鲁王属下郑联部队,配合杨学皋进攻漳浦县城时使用的,匆忙撤退时来不及带走,浅埋于地下。
1965年夏天,一阵暴雨之后,漳浦县城木屐街陈文德住宅一处地板突然陷落。陈先生急忙掀掉砖块,挖出泥沙,深挖尺许,双手触及一黑黝黝的铁器。全家合力把泥沙剥开,原来是一尊古炮。陈先生犯愁了,古炮毕竟也是武器,家藏武器,祸必降临,尤其是“社教”运动如火如荼,那能让自己雪上加霜。因此急忙到城关派出所报告。派出所派警干许海军到陈家勘察,见果然是一尊古炮,即来文化馆要我去处理。我约了城关文化站站长卢溪河一起把这尊一米多长,重109公斤的古炮扛回文化馆。为了解炮的质地,用钢锯拉一小口,拉出来的全是铜盾,证明这是尊古铜炮。自此,它成为馆藏文物(当时博物馆尚未从文化馆分设)。
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狂飚席卷神州大地,处处掀起“破旧立新”、“斗私批修”怒涛,各地工农群众、干部职员、教师学生,谁也不愿失去当造反派的权利。然而要造谁的反,观点不同,也就出现了不同观点的派性组织,出现了“文攻武卫”,出现了“打、砸、抢”……
1967年夏天,一口悬挂在县政府食堂后钟楼上,原系兴教寺唐景福年间铸造的大铜钟(民国二十三年即1934年,第五行政区专员兼漳浦县长朱熙,将该铜钟从兴教寺移来,建造钟楼以报时,抗日战争期间,改作空袭报警之用。)此钟被“革命小将”砸成碎片,作为废铜卖给废品收购站,已是继砸“黄道周纪念馆”(毁大小上千件文物)之后的第二次“革命行动”。
同年夏天,我第一次恢复工作回文化馆,发现古铜炮不见了,尽管当时批斗“封、资、修”运动方兴未艾,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总不甘心让古炮再蹈古钟覆辙。从各方打听消息,得悉炮已被“革命小将”运往漳州,准备熔化,以铜出售。当时,政府及大部分职能部门已瘫痪,我写了一纸报告面交县委副书记蔡新生,报告内容之一,要外出追寻古炮;之二,出差车旅费等要给报销。蔡立即签字批准。
在漳州终于找到马卢等革命小将。他们承认铜炮已藏在某工厂仓库,由于售价未决尚未熔化。我对他们说明文物的重要,一旦毁之就成为历史罪人。马卢笑道:“我们缺乏活动经费,你说那么重要就卖给你吧。”我问:“要多少钱?”他说:“抽成铜丝,出厂价每斤两元,你拿两千元来吧。”我郑重对他说:“只要能完壁归赵,说不定能多出一倍钱给你们。”这位小将眯眼睨视,不相信地问:“真的你能搞到两三千元,要多少时间?”我说“当然有把握,十天为限可以吧?”他点头:“可以,一言为定。”
第二天,我赶到鼓浪屿郑成功纪念馆。纪念馆大门紧闭。询问附近人家,说:纪念馆人员转到厦门图书馆办公。我赶到厦门图书馆,找到厦门图书馆,找到纪念馆人员说明这一情况。纪念馆干部非常重视此事,立即挂电话到省文化厅,接电话的人说,不管价钱多少立即答应他们,绝不能让它毁掉。我要纪念馆派人带钱跟我到漳浦取炮;他们却要我负责把炮运到厦门,一手交炮,一手交钱。我说:“不成,漳州到厦门这条路我不熟识,昨天火车站莲坂武斗,打死好多人。再说,没现款那些造反小将能把铜炮交出来?”纪念馆的人也感到往漳州运炮不保险,但也想不出良策。无可奈何之下,我建议:“你们是不是请省厅通过支左部队,指令漳浦有关单位出面调查保护好此炮。”纪念馆的人同意这一办法。
我回到漳州后,见到专署文化局干部庄受惠,请他调查此炮下落,想法保护。庄说局里已接到龙溪军分区电话,并转达各工厂、收购站,一有讯息立即报告。听了老庄的话,我想此炮应无忧矣。
不久,我又第二次倒霉,被赶出县直机关“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再次失去工作权利,古炮落入谁之手,也就无权打听了。
我第二次恢复工作后,庄受惠来找我,再次询问此古炮的出土、被盗经过。看来是漳州与厦门要研究古炮的归属问题。本来,我想“毛遂自荐”去证明此炮的出土经过和归属问题,想不到不久,我第三次大倒霉,又再失去工作权利。当时,我心里想,只要古炮在,厦门、漳州、漳浦都是家。
如今,劫后余生鲁王炮,鼓浪听涛更潇洒。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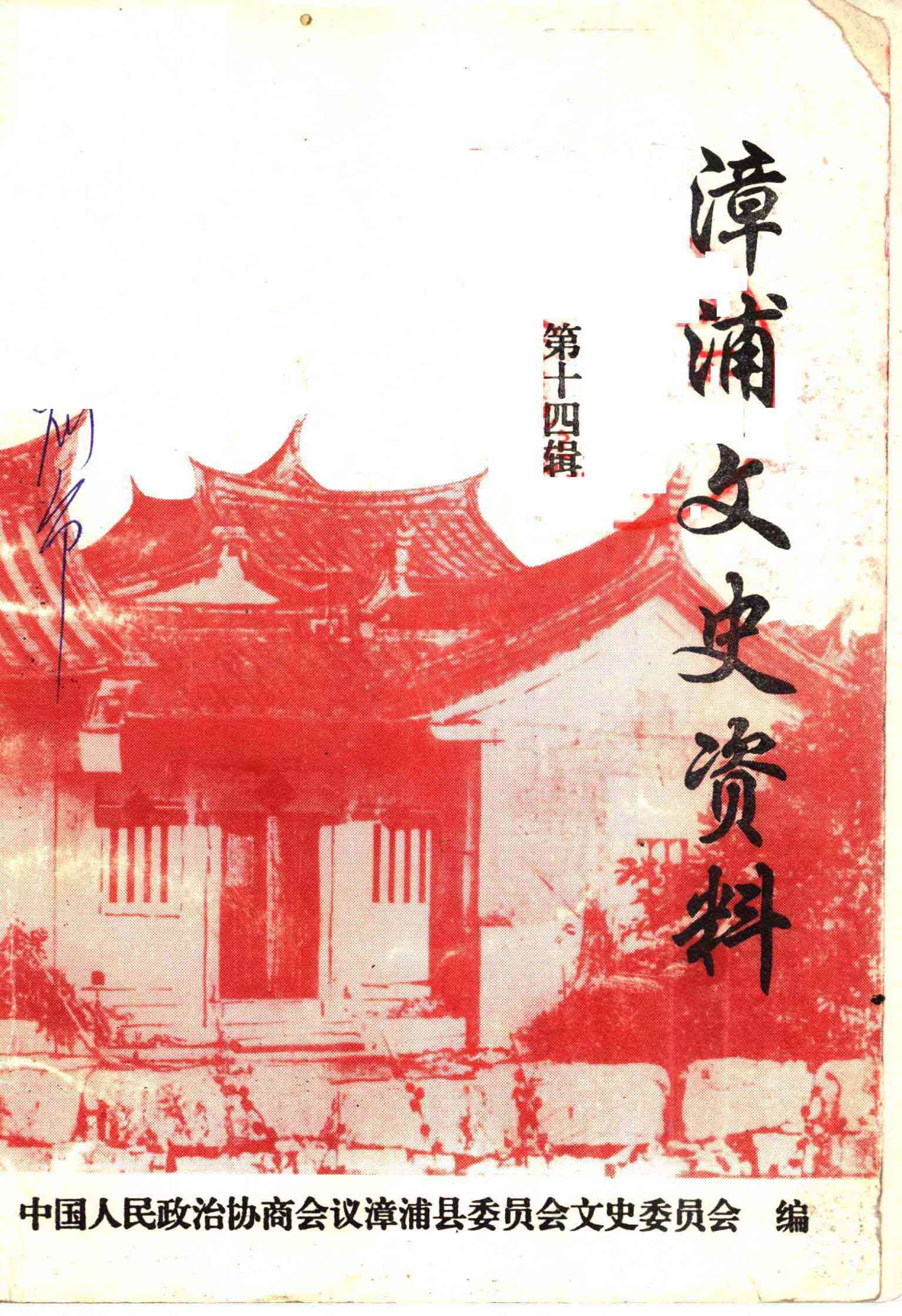
相关地名
漳浦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