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学生生活
| 内容出处: | 《漳浦文史资料 第十四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30000760 |
| 颗粒名称: | 抗战时期学生生活 |
| 分类号: | G455 |
| 页数: | 16 |
| 页码: | 78-93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抗战时期的故事“黄金岁月在龙中”由已故印尼实业家柯汉扬先生于1992年撰写,回忆了1937年以及之前在龙溪中学的生活。文章描述了作者初到龙中时的情景以及周围的环境,以及对学校校歌和校长的印象。文章还提到作者之前就读的学校经历,以及对抗日情绪的认识和表达。作者描述了学校成立的“晨呼队”参与抗日活动的情景,以及当时的社会氛围。整篇文章以个人视角回顾了抗战时期在学校内外的生活和见闻。 |
| 关键词: | 抗战时期 龙溪中学 学生生活 |
内容
黄金岁月在龙中
柯汉扬
编者附记:这是已故印尼实业家柯汉扬先生1992年遗作,忆述抗战时期中学生生活,值此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特予刊出。
“芝山迢迢,芗水滔滔,我们学校多巍峨,先生同学,一堂攻错,春风化雨祝滂沱。……”
龙中(福建省立龙溪中学)当年的校歌,我只记得几句,可是五十多年前的住事却历历在目呢!呀,逝去的年华,有如朝云无踪,春梦苦短!1937年“7·7”抗战爆发前一年(1936年夏),我和许曾炜兄偕同考入龙中高中十组。记得初抵漳州,投宿“卫生楼”旅社,吃饭于圆圈,左邻右舍叫卖蚝仔煎,大声竞嚷,至感有趣。那时自己喝汽水尚且不懂得如何用吸管呢,土得可笑可爱。
经过公园时,有假山凉亭,林花荫绿,又有碑记可读,在那儿徘徊好一会儿。抵达芝山龙中,见到校门两边大书“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对联。操场宽广,校舍礼堂、课堂、宿舍,确是堂皇。
那时正是马占山在日军侵占下的东北打游击,傅作仪在绥远抗击伪军,全国高唱“共赴国难”时代。王秀南校长初莅任,有番精神办校,实行军事管理,有军事教官、童子军教练。有一个吹号的,清早就吹集合军号,我们都穿校服,集合到篮球场跑步,约一小时。这样经常的锻炼,我觉得身体更加结实粗勇。
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有球类练习、拳术师傅教练拳技、摄影学习,等等。我和曾炜兄样样都参加,也特地买了方形的柯达照像机,觉得趣味盎然。
那时膳食也很好,冬天还有暖锅呢。实行所谓卫生食,往食盆里夹菜舀汤用一副筷子、汤匙,送到口里用另一副。学生也有代表参加办膳。
漳浦人说话土腔很重,常会被同学饥笑,说“漳浦兄入城寻不着龙眼营”等等。后来慢慢改正了轻重音,口腔也就没有什么不同了。我们一些“漳浦兄”还特地到龙眼营去参观,原来漳浦来的肩挑小贩大都投宿于此处客栈。
大同书局代售课本。三十年代是新文学运动昌盛时期,巴金、茅盾、鲁迅、冰心的作品很多,《良友》、《明星》等画报也逐期运到,我们成为“大同”的主顾,不时来买书,算是满足了求知欲了。
电影院有光明、黄金两家,我们从那里欣赏了《渔光曲》和《大路歌》,也学会了绰号野猫的王人美所唱《渔光曲》和“美人痣”陈燕燕所唱的《大路歌》。——多少年后,我“过番”邂逅老同学曾炜兄,很常一同泛舟万隆西湖,大唱渔光曲和大路歌,消积心中积闷。也从中得到一些教训,如“爷爷留下的破渔网,靠它再过一冬”和“轰,轰,轰,我们是开路的先锋……”,也得到一些向前冲的鼓励。
芝山之麓满是矮树竹林,难免生长了不少的蛇。有一次王校长亲自带抓蛇师傅到竹林中现场表演,他知道何处有蛇,就以口作蛙鸣的声音,伸手进枯竹叶里轻易地将蛇拉出来,放在笼里,屡试不爽。最难能的是,在附属小学的石阶隙缝里,他突然说这里有毒蛇,因为附近长有特别的草。他先吃了药,过一会儿才伸手指进隙缝里再作蛙鸣声,果然有一条相当大的蛇被拉出来。他把蛇放在地上爬行,用蛇药去碰触蛇头,蛇畏而避之,真是神通广大!
小竹林里有学校的厕所,隔墙则是驻军司令部的厕所,有时可能是犯人来上厕,有脚铐铁链的声音,并有士兵斥责大喊。那些人是罪有应得还是无辜受迫害的呢?也兴起怜悯同情心。同学们有时也谈论这事。
仿佛记得那是春天踏青的季节吧,漳州所有的中学学生旅游盛产水仙闻名于世的圆山。龙中、寻源、崇正、进德(女中)、简师、职业中学都参加。我和曾炜兄带着“宝贝”的柯达照像机去。山麓满是少俊俏丽的学生,到处寻幽览胜,纵谈水仙出圆山的神话,乐在其中。我和曾炜兄也携照像机细心找镜头,俨然现在的摄影记者,随心所欲,不必征求同意,真是有趣极了。回校后,我们的国文老师徐石(是清末的优贡出身,诗文都很好)出个作文题目《圆山记游》,我除了记述旅游之乐外,还附一首打油诗,有趣也带顽皮,当时还自鸣得意呢。徐老师把它改成一首律师,并用红笔批几字赞好。
提起这位长年穿长衫,以闽南话授课的老贡生徐石老师,也有趣闻。有一次王校长带领省督学上课室视察,突然来到我班门口站着,徐老师突然改口打起官腔来,有点像世界语,大家竟然因为听不懂而骇异,等到督学离去相当久,大家忍不住大笑起来,徐老师微笑道:吃官饭讲官话,不得已也得“老”一下,年老舌硬,“老”不过来,别见笑,别见笑!(闽南话“老”是“扭”的意思)。
当我们被调到福州东湖接受三个月的军训,着兵仔衫,穿草鞋,吃大锅饭,睡通铺,佩长枪、水壶打野外,过没正式的兵仔生活之后,突然芦沟桥的炮声揭开抗日战争的序幕,全国民心非常振奋,我们更是跃跃欲试,确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劲头。(这是一首当时最流行的抗战歌曲)。
果然不久,日机飞来轰炸漳州,龙中寻源两校都与驻军司令部隔邻,当然是重要目标。我们一群学生疏散到野外的竹林里,看到敌机俯冲轰炸驻军司令部,芝山上的高射机枪不停地连珠发射,飞机的机枪声也卜卜不停,炸弹声响个不停……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飞机轰炸的情景,算是很有价值的军事演习。不久,好消息来了,全省与我们同届的高中二年级生都被调到福州东湖接受军事训练的各种科目,并发给我们准军官的皮带、佩剑和竹笠,就派我们到各县的穷乡僻壤去搞民训工作。清晨召集壮丁作初步军事训练,教民众唱抗战歌曲,并到处大书墙头标语,晚上就演出话剧,如《放下你的鞭子》、《慰劳歌》、《马百计》、《三江好》等等。我初被派到诏安县工作,后调到越过板寮岭和松梅岭的闽西重镇长汀工作。我们这一队还远走到曾是红都的瑞金附近,留下不少墙壁标语。省教育厅长郑文贞夸说民训是“笠剑学风”的好表现。
民训回来,学校已搬到长泰县的岩溪。学生们利用课外运动时间开操场。傍晚,同学们大都跳到附近的溪里洗浴痛快一下,浴后高唱《打回老家去》和《拿起爆烈的手榴弹对准杀人放火的日本兵》……王校长还领导我们开全校运动会。在岩溪,我们才认识“土皇帝”叶团长的真面目,也曾特地去欣赏他的小皇宫和在那里看戏。
接着,我们再被调训,派到各县去作民教工作一年,当战时民校的校长或教员。我私自请了一位朋友去顶替,自己却在家乡漳浦县城一家小报馆里义务做记者、编辑,也协助速记重庆的广播新闻,因为我从小喜欢涂涂写写,也因此养成我好读书和写稿发表于报章的爱好,想不到后来沦落在香港却靠此雕虫小技苟活。这是后话。
郑玑老师接任校长后,把学校搬到漳平县的永福镇去。在那儿,一切更简陋,教室分开好几处,同学们自己租房子或以土碉堡为宿舍,饭厅则借用祠堂,大家站着吃饭;桌上摆着定量的饭包和黄豆青菜以及豆腐油花汤,但是豆入饥肠化作蛋白质,还是精神饱满地读书、打球,高喊“抗战必胜!”
也许是受多了战争长久的积闷,同学们也曾因为小误会竟和永福区署里的警察发生冲突,乘夜大伙儿围攻设在一个大碉堡里的区署,抛掷石头,大骂大喊,但毫无反应,既爬不上去,也进不了坚固的大门,泄泄气,倦了也就各自散去,在当时还不失尚武精神,朝气蓬勃,现在回忆起来却有点慨叹。就在那儿我们修完了高中的课程,计算起来共费了四年半的时间。当然我在实际的工作中得益良多,可能比死抱课本更好,它锻炼我以后要写、要讲、要唱、要演戏都可以勉强应付。现今有人大谈“读书无用论”这固然是过激之论,但学以致用是最紧要的,不要在象牙塔里做美梦。
老夫今年七十多,满口半假牙,想起漳州的红柑、天宝的香蕉、浦南的文旦、圆圈的蚝仔煎和鱼头,还是会流口水呢。
谚语“海水最阔,船头偶也相逢”,我在印尼雅加达竟然会晤到王秀南校长和郑玑校长。瘦小的王校长还满有干劲当高级商校校长;而郑校长任数学老师,老态龙钟了,他因高血压禁食一向爱好的猪脚肉,本来肥胖的身体瘦了不少。最后疾终在巨港的华校任内。我对两位校长一往情深,在拙作《海外四十年中》记述了他们在印尼的情况。
我永不能忘记严峻的抗日战争。而今中日成为友好之邦二十年了,大家都觉悟到千万不能再陷旧错。我竟也亲自游览了日本的京都和皇宫,在大阪参观工业区,在富士山上赏雪,在风景区温泉洗浴,我的儿子也留学日本专习纺织,家中也挂着我儿子和日本少女穿古装合影……现在又知悉明仁天皇将于十月间访问神州大陆,要亲自向中国同胞表示对往事的痛心。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回忆往事如烟,我不禁要朗诵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悲叹世事的沧桑了!
纯美中学的抗日宣传活动
李林昌
我在漳浦县立培英小学读初小时(校长张顺福),1931年逢到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全体师生臂挂黑纱,上书白色“国仇”两字,听老师演讲,在幼小的心灵上已种下抗日情绪。高小时(学校改为漳浦县立第一中心小学,校长蔡竣德),读开明书店的语文课本,叶绍钧(圣陶)编的,有许多发人深省的课文,其中一篇十九路军旅长翁照垣写的《一个军官的笔记》,写1932年上海军民抗击日军侵略的实况,课文上只写“敌人”,教语文的余炳文老师解释:敌人便是日本。那时我们开始在老师指导下阅读杭州出版的《儿童时报》,看到许多字句里以××代替文字,如“××帝国主义”等,编者附言:“为什么字句里有××,我在这里不能告诉各位读者,请问你的老师和父母,如果老师和父母不愿照实告诉你,那便不是一个好老师和好父母了!”其实报纸上满纸××已是司空惯见,因为当时的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屈辱,禁止公开发表抗日言论,爱国有罪,报纸只好以“××”代表“日本”,以免被抓住把柄。我们少年儿童也和成人一样感到国难深重了。
1936年小学毕业,漳浦县立初级中学已经因为经费问题停办了。好在万隆华侨杨纯美先生独资创办的纯美初级中学刚好在这一年夏季开始招生,我与逢源小学的十几位毕业生一同去投考被录取。在开学典礼上看到杨纯美先生,聆听他朴实的讲话。而在学校一切就绪后,他就再渡南洋经营工商业去了。
一百多名一年级学生分成两班,连校长兼教员在内,老师只有四五位,还要分兼文书、会计、出纳、庶务等工作。膳费每月四元法币(自1935年已实行法币制度,禁止银圆圆流通),吃得不错,可随时报停膳,一餐领五分钱,可饱餐一天碗馄饨。每人每学期还可领回“伙食尾款”六元左右。(当时币值是稳定的,至抗战后期才发生通货膨胀)。
当时全国各地抗日救亡情绪高涨。蔡朝阳老师(井尾人)是教英语的,而音乐、文学造诣甚深,尤其有一副哄亮的歌喉。他思想进步,爱国热情充沛,常在课余集学生在大礼堂教唱聂耳等人所作的救亡歌曲,很多学生自动汇合,学唱十分起劲。音乐老师李继志是蔡老师的同襟,听说在大学时是高材生,后来因为一场恶病留下后遗症,丧失了才华,他把我们当小孩子看待,教唱一些简单的歌曲,我们不能满足,都喜欢跟蔡老师唱慷慨激昂的救亡歌曲如《自由神》、《大路歌》、《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李老师在蔡老师推动下,也改教救亡歌曲,如“九一八,血痕尚未干,东三省,山河尚未还,……国仇一日未雪,国民责任未完”等。
翌年(1937年)“7·7”事变以后,抗日的烽火燃遍了中华大地。漳浦县成立抗敌后援会,当时漳浦县分设五个区,区署所在地旧镇、杜浔、佛昙、石榴坂、官浔各成立抗敌后援分会。纯美中学为当时漳浦县最高学府,校长李克柔被推为佛昙抗敌后援分会主任委员,蔡朝阳老师任宜传工作团团长,全校学生都是宜传工作团团员。李校长与蔡老师便发动学生将抗战的歌声推向社会。他们将学生分成几个组,由教师分别带领,于每星期六晚上出发到各乡村,以歌咏、演剧、演讲等形式向群众宜传。星期天便在佛昙墟埔演出街头剧、演讲、教唱抗战歌曲。于是,“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以及《义勇军进行曲》等等歌曲,都为佛昙侨乡群众所熟稔会唱。国文教师苏恩卿虽是长汀人,由于是厦门大学毕业生,会说一口流利的闽南话,他从厦门带来一些方言童谣小册子,分给学生,叫学生到社会上去教唱,这些琅琅上口的抗战童谣,如“男的不要吃烟枝,女的不要点胭脂,大家俭钱买铳子,打到日本仔半小死”等等,便在侨乡妇女儿童中间传播。
当时佛昙有“潭江号”汽船川走厦门,单程四小时,每天早上开往,晚上约九时左右才回到佛昙,有时因为等人等货,回来时已半夜。码头在纯美中学后面港边,每天晚上便有一些急于知道前线消息的纯美中学师生在那里等候,以先睹厦门《江声报》或《星光日报》为快。如陈明勋这样一位身体瘦弱的数理化教师,也冒海风候至半夜。翌日,学生们便利用午休时间,两人为伴,三人作伙,到墟埔向群众宣传抗日消息。
当年冬季,纯美中学以游艺会形式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佛昙虽是侨乡,当时风气还比较闭塞,中学是新生事物,刚刚越过“无猜”阶段的男女同学不大接触,演戏也是分开排练。女生由女生生活指导员叶臻聪老师导演,演出《送女出征》等歌剧,剧中人物大部份是女的,有几个男的也由女生扮演。男生由蔡朝阳老师导演,剧中人物男扮女装。蔡老师根据侨乡特点,选择田汉剧作《回春之曲》改名为《爱情与爱国》,在游艺会上作为主要剧目演出,那是以南洋爱国青年回国参加上海抗战为题材的三幕话剧,南侨风情在演出中表现得维妙维肖,华侨青年的爱国热情也在舞台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时侨乡为之轰动。这三幕话剧有一个特点是有插曲,由于此剧的演出,其插曲如“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第二的故乡,我们民族的血汗,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等,便在校园里以至社会上传唱开来。那时一些男同学身体还很娇小,扮演女角是那么逼真,饰演主角梅娘的林维仁,当时有一副丰满的小白脸,后来竟是瘦骨嶙峋,脸现猴形的中学教师兼业余作者,饰演女教师碧云的陈珊斋,后来竟是体格魁梧的空军飞行员,与日本空军进行过较量的。蔡老师后来侨居万隆,文名蜚声海外,曾参加澳州广播电台中文部主办的国际书法比赛获优等奖;著有诗集《故里风光》,热爱故乡之情跃然纸上。几度回乡,与纯美中学旧时师生促膝话旧,不胜依依。
纯美中学在八年抗战期间一直作为向社会宣传抗日的基地。
每逢假日,纯美中学便配合佛昙一些小学,组成宣传队下乡,以戏剧等形式宣传抗日,演出过《红心草》、《麒麟寨》、《牛头岭》、《烟苇港》等话剧。
抗战时期一个小学生的所历所见
高幸占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序幕拉开了。这一年我刚七岁,父亲送我到西街三房巷张隆古先生办的私塾念“四书五经”。刚念过《论语》,《中庸》、《孟子》三本书,私塾便停办了,原因是政府为适应抗日形势,通令各地开办国民学校,禁办私塾。我便转到武营中心小学,插读二年级。这已是一九三八年了。
入学不久,学校成立“晨呼队”,除一年级外,各级男女生都得参加。每天早晨天未亮,我顶着凛冽的寒风,先到古井头葛婶店前,用二个铜片买一碗糖粥吃,再到学校集中,然后由老师带队,出校门从西街、府前街,转到北街、麦市街,沿街高唱抗日歌曲,“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雄壮嘹亮的歌声、满腔的热血激情,驱散人们身上的寒气。晨呼队的后面跟着县长吕思义,吕手持“动葛”(手杖),沿街敲门撞户,喊老百姓起床,几乎天天如此,妇女背地里多叫他“神经县长”。晨呼队最后到兴教广场参加升旗。升旗后回家早餐,餐后再入学上课。
那时,学生还有一项特殊的课外活动内容,就是“防空演习”。学校划定班级疏散地点,“乱钟”一响,师生马上离校跑到指定地点隐蔽防空。我们班原指定隐蔽点在礼拜堂前龙眼围内,数次演习都去那里。农历四月廿五日那天,我们听到县府大钟紧敲声及学校的乱钟,急忙冲出学校后门,抬头看见飞得很低的日机,已在礼拜堂方向的上空,我急转身向高厝巷,一口气跑到城边桃仔园(现北市场蔬菜公司),突然听到恐怖刺耳的飞机呼啸声,急忙按演习时老师讲的,俯卧地上,掩耳张口。“轰轰轰”一连串的炸弹爆炸声,声声震动着大地,也震动着我的身心。我身边有些妇女,紧紧捂着孩子的嘴巴,怕哭声引来飞机,口中叼念着,天公保佑,佛祖保庇,炸弹不要落在这里。好不容易在心惊胆战中挨到飞机走了,警报解除了,才急忙回家,看到家中一切依旧,方能开口说话。这时,街上传开了,炸弹炸在礼拜堂前龙眼围左右,炸死了蔡发祥、蔡恢等数人,死者四肢五脏悬挂树梢、檐口,惨不忍睹。以后钟声一响,我便从高厝巷往北门兜方向跑。那时的飞机是螺旋桨的,飞不快,轰炸还要打围找目标,因此,飞机飞到头上立即卧倒地上,飞机一过身,立即拔腿再走,经常走三、四里路到羊寮(今朝阳)、楼仔顶村。
当时,“防空哨”设在鸡笼山(现气象台),警报器用挂在县府前东侧钟楼上的大铜钟。防空哨一接敌机犯境情报,立即电告敲钟者,敲钟者立即赶到钟楼,登楼撞钟。连续紧接撞钟为敌机入境警报;如慢慢地一声一声则是解除警报。后来,可能因钟楼延缓时间,改用一部金属手摇“警螺”(汽笛)以代替大钟。
城内居民一听到警报,便急奔城外疏散或躲进防空洞、防空壕。那年七月廿九日(俗为“尾中元”),日机投弹炸在市场(现旧文化馆)东侧防空壕(今新华书店第二门市部),几个人堵死在里边。自此很多人不敢躲入防空洞。
这一年,日机犯境非常频繁,有时一天要走避数次。学校只好采取疏散上课,我们班到王顶蔡俊德校长家上课,也曾到西门外大树下(现城关粮站)上课。城里居民也改变生活方式,天朦朦亮就吃早餐,太阳未出时就出城躲日机。中午就地野炊,穷困之家午餐只好免了。黄昏后庆幸一天平安过去,才陆续回家。
县府后衙(现宾馆)几株大榕树上栖着几千只乌鸦,曾有乌鸦半夜“反巢”隔日敌机犯境情况,群众将乌鸦当“预警器”。七月上旬,乌鸦夜夜反巢,居民搞得失魂落魄,日夜不宁,既不能安居,更无法乐业。我父亲是手艺工人,他上半辈子有二怕,一怕日本飞机;一怕抓壮丁。警报一响,他面如土色,连跑也跑不动,只好在家宅后龙眼树下挖一条防空壕。在城内、躲防空壕也是担惊受怕,父亲便到城郊附近农村去联系住房,准备搬到农村中去。
农历九月初六、初七两天,日机连续轰炸县城数处,每次都有居民被炸得血肉横飞。城内居民纷纷搬到农乡亲友家。家长也不敢让子女去上学。武营中心小学也搬到霞潭村,我们全家搬到罗北考湖村。起初,每天跟着堂兄走三、四里路到霞潭去上学。不多久,学校没学生上课,老师也走了。堂兄到东门他外婆家,我也停学了。
在考湖村,父亲断了手艺营生,就租了一些土地,我们成了见习农民。见习农民种地比正式农民还讲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摘绿豆。父亲说,太阳出来一晒,豆英就爆裂,因此,采绿豆就得在大阳出来前。中午,农民都回家休息,父亲要我跟他留在地里锄草,说中午阳光强,锄掉的草不易复苏。我还常跟祖父进城卖蕃薯,两担蕃薯可卖一百多个铜镭,吃一碗“水面”5镭,祖孙吃后,再把家里的肥料挑到农村地里。当地农民说我们生产的作物不比他们少。但我的学业却荒废了。一九四〇年空袭减少了,祖父母先回家,不久,全家回城。学校复课了,我也复学。
吕思义县长走了,学校不再搞晨呼了。但小学生还得接受军训。军训很正规,每个学生要做一套黑布中山装,黑学生帽,束腰皮带,高年级同学要打绑腿。女生一律剪短发。学校利用劳作课,中年级每人做一把木大刀,油漆后系上红布带。高年级每人做一支木驳壳枪。西街顶陈克昌先生任学校军事训练教官。体育老师教舞大刀,陈教官教步兵操,教打野战。有一次,高年级同学到野外操演野战,曾鼎同学被土制手榴弹炸得血流满脸,用担架抬回校。
武营中心小学不少老师是进步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教学生唱抗日歌曲,演“文明戏”(话剧),绘宣传抗日画。蔡俊德、郑秀贞夫妇、蔡启昌、林清秀夫妇、曾敏英、张淡月、许其和等老师,还有校外的柯汉扬、蔡维汉、邱珍五等先生组织的“抗敌剧团”,经常下乡演“文明戏”宣传抗日,高年级不少同学跟着剧团下乡,充当配角或跑龙套。有一次,我和戴壬癸同学被曾敏英老师叫上台凑个群众角色。兴教广场的戏台原是露天的,为了演文明戏宜传抗日,县政府拨款盖瓦顶大戏台,连带左右两大房间,演戏时作化妆室、休息室。平时则作我们的教室。
抗战时期,我们小学生不但自己要读书,还要当民众夜校的小先生。我被分配在县府内县堂(现历史博物馆)识字班当先生,还有同班女同学教唱抗日歌曲。每天晚餐后,手提小油灯挨家挨户叫学员上学,学员多是中青年妇女。
小学生参加的会竟多不胜数。全县在兴教广场开“一元献机抗日”大会,我们全校都去参加,有些同学在家长支持下,上台献金戒指、银圆,有各界人士、妇女上台献首饰、钞票,我们在台下鼓掌、唱抗日歌曲。竖“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县幼儿园后大路边),我们同学每人献几个铜镭放在碑基底下。每星期一是“纪念周”例会,我们必须穿着整齐的校服,列队到兴教广场唱抗日歌曲,听县长训话。
当时的老师很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记得有一年儿童节,每个同学分到一份礼物,有糖果、饼干,还有一节果蔗。蔡校长手拿甘蔗问大家:同学们,这是什么?大家异口同声回答:是甘蔗。校长笑着说:不,这是用来打日本飞机的高射炮……。在五年级时,学校举办美术展览,老师要求学生画有抗日内容的图画。我和王乾三、叶集锋,从学校图书室借来很多张“日寇暴行图”,我们每人临摹了好几张参加展览,老师还表扬我们。
后来,敌机侵犯骚扰减少了,社会上涌起抓汉奸、抓壮丁潮流。老师告诉我们,汉奸装成乞丐、小贩、难民,到处向水井投毒,学生要协助政府抓汉奸,随时随地注意可疑的人。社会上也传得人心惶惶,公共场所的水井都要加盖上锁。肃奸成为一个新运动,文明戏演“抓汉奸”,街头标语、漫画也都是肃奸内容的。有一次,兴教广场演“文明戏”,归侨,修脚踏车的乌番师傅,客串扮汉奸黄秋岳,“黄犯”五花大绑,背插斩标,身后左右站立两名持枪法警。“黄犯”用潮曲清唱通敌叛国的罪状,由城关民乐演奏手们伴奏。曲完执行枪决,“啪”一声,“黄犯”从台上栽下台来,观众人心大快,“消灭汉奸”,“枪毙卖国贼”!喊声响彻云霄。有一次,我们正在上课,忽然听到要枪决“资敌犯”胡百虎,大家丢下课本跑到街上观看。
社会上到处在抽壮丁,按规定,三抽二,二抽一,单丁缓役,但有钱人尽管兄弟多,可以用钱雇壮丁,当官的怕中签的壮丁逃跑,保内壮丁抓阄,一中签马上像犯人一样被缚起来押关在联保办事处(后改乡镇公所),家属三餐去送饭。接兵部队一期接着一期来接收。接兵部队在城关一些祠堂设“新兵招待所”,实是关壮丁的牢狱。我们学校有不少同学的父兄被抓丁,家无劳力,不得不失学。当兵上前线抗击日寇,原是国民应尽义务,理应踊跃应征,为何要用绳子缚,铁丝捆,发现逃跑,不是当场击毙,就抓回活活打死?那一年署假,武菅中心小学被接兵部队“借”去关壮丁。有一天,我们几个同学路过窗下,突然听见内边惨叫声,便停足往内窥视,见二个壮丁赤裸身子被按在石板上,当官的指挥其他壮丁逐个用扁挑轮打,终于打得不叫不动了。我家隔巷刘祠堂,也是关壮丁的地方,经常在半夜听见惨叫声,天刚亮就可看见荷枪的士兵,押着壮丁抬着裹草席的尸体出城去。还有一次,关在兴教寺的壮丁,集体逃跑,当官的下令用机关枪扫射,打死十余人,横尸榕树下。这些现象老百姓看在眼里,更觉得当壮丁的可怕。
国民党政府只管抽壮丁,不管壮丁家里生活如何,妻孥子女死活如何,壮丁抓到“招待所”,吃不饱,穿不暖,动辄遭受毒打,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往上送时,每人牢牢捆缚,还用铁丝扎成一串,拉屎撒尿还要挨枪托、皮鞭毒打。用这种手段抓来的兵怎能打仗,怎能不跑呢?当然,自愿去当兵的人也有。我同班一位姓李的同学,在家庭得不到温暖,未到16岁去“卖壮丁”(顶替他人入伍,价钱约2至3担花生油)。六年级一位姓洪的同学,顶替其胞兄入伍,未经什么训练就被押送到安徽,补入前线部队,参加九华山会战,队伍打散了,他靠着这小学文化知识,孤身千里跑回漳浦,考上漳浦中学。1944年,政府派人到学校招募“远征军”,说是要到缅甸、印度参加盟军抗日,还招“华安军”等,学校不少同学报名参加。只有这样当兵才免受“新兵招待所”虐待,且受光荣欢送。
我们小学毕业那年,潮汕地区被日本侵占,大批难民逃到闽南,来漳浦的为数更多。不久,全县突然发生瘟疫(霍乱),死亡数千人。我们班里同学就死了三男一女,这可以说是间接死于战乱。
上了初中不久,形势又趋紧张,二、三年级同学疏散到石榴崎溪一带上课,我们一年级则是上早,晚课,每人自备一盏小油灯,每天两头摸黑去上学,好在此况时间不长。
一九四五年七月的一天,忽传占据厦门的日军数百名,从海澄港尾登陆向漳浦而来。消息传开全城震动,居民纷纷离家疏散出城,学校也宣布停课,学生随家庭疏散。我们与邻居几户疏散到罗山大埔村。那一夜,约11点钟,突然来了一股“追击”日寇的国军七十五师,有数名“便衣”会说本地话。把我们几家驱赶集中在一间房屋内,抢去了我们很多东西。“便衣”又叫十几个妇女帮他们把抓来的鸡鸭宰剥烧煮。天亮了他们要走了,我问其中一人:你们追日本怎么追到这里?那人说,我们是从文周岭过来的。我明白了,日寇流窜是走佛昙、赤湖、旧镇、城关的大路,国军是走湖西、赤土、万安、文周岭、罗北弯弯曲曲山路,这条路线距大路约二、三十华里。完全可避免与日军遭遇。
日军窜入城内抓去一些老百姓当挑夫,即离城往盘陀方向而去。次日我们回家,听说日军过盘陀时被盟军飞机炸死一些人马。挑夫有的乘机选出日军魔掌,回了家,有的被日军打死,有的被盟国飞机炸死。
中国有句古话:“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民。”战乱是何等可怕可悲可恨,和平是何等可贵。要得到和平,国家就必须加强现代化建设,否则落后就要挨打。
柯汉扬
编者附记:这是已故印尼实业家柯汉扬先生1992年遗作,忆述抗战时期中学生生活,值此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特予刊出。
“芝山迢迢,芗水滔滔,我们学校多巍峨,先生同学,一堂攻错,春风化雨祝滂沱。……”
龙中(福建省立龙溪中学)当年的校歌,我只记得几句,可是五十多年前的住事却历历在目呢!呀,逝去的年华,有如朝云无踪,春梦苦短!1937年“7·7”抗战爆发前一年(1936年夏),我和许曾炜兄偕同考入龙中高中十组。记得初抵漳州,投宿“卫生楼”旅社,吃饭于圆圈,左邻右舍叫卖蚝仔煎,大声竞嚷,至感有趣。那时自己喝汽水尚且不懂得如何用吸管呢,土得可笑可爱。
经过公园时,有假山凉亭,林花荫绿,又有碑记可读,在那儿徘徊好一会儿。抵达芝山龙中,见到校门两边大书“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对联。操场宽广,校舍礼堂、课堂、宿舍,确是堂皇。
那时正是马占山在日军侵占下的东北打游击,傅作仪在绥远抗击伪军,全国高唱“共赴国难”时代。王秀南校长初莅任,有番精神办校,实行军事管理,有军事教官、童子军教练。有一个吹号的,清早就吹集合军号,我们都穿校服,集合到篮球场跑步,约一小时。这样经常的锻炼,我觉得身体更加结实粗勇。
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有球类练习、拳术师傅教练拳技、摄影学习,等等。我和曾炜兄样样都参加,也特地买了方形的柯达照像机,觉得趣味盎然。
那时膳食也很好,冬天还有暖锅呢。实行所谓卫生食,往食盆里夹菜舀汤用一副筷子、汤匙,送到口里用另一副。学生也有代表参加办膳。
漳浦人说话土腔很重,常会被同学饥笑,说“漳浦兄入城寻不着龙眼营”等等。后来慢慢改正了轻重音,口腔也就没有什么不同了。我们一些“漳浦兄”还特地到龙眼营去参观,原来漳浦来的肩挑小贩大都投宿于此处客栈。
大同书局代售课本。三十年代是新文学运动昌盛时期,巴金、茅盾、鲁迅、冰心的作品很多,《良友》、《明星》等画报也逐期运到,我们成为“大同”的主顾,不时来买书,算是满足了求知欲了。
电影院有光明、黄金两家,我们从那里欣赏了《渔光曲》和《大路歌》,也学会了绰号野猫的王人美所唱《渔光曲》和“美人痣”陈燕燕所唱的《大路歌》。——多少年后,我“过番”邂逅老同学曾炜兄,很常一同泛舟万隆西湖,大唱渔光曲和大路歌,消积心中积闷。也从中得到一些教训,如“爷爷留下的破渔网,靠它再过一冬”和“轰,轰,轰,我们是开路的先锋……”,也得到一些向前冲的鼓励。
芝山之麓满是矮树竹林,难免生长了不少的蛇。有一次王校长亲自带抓蛇师傅到竹林中现场表演,他知道何处有蛇,就以口作蛙鸣的声音,伸手进枯竹叶里轻易地将蛇拉出来,放在笼里,屡试不爽。最难能的是,在附属小学的石阶隙缝里,他突然说这里有毒蛇,因为附近长有特别的草。他先吃了药,过一会儿才伸手指进隙缝里再作蛙鸣声,果然有一条相当大的蛇被拉出来。他把蛇放在地上爬行,用蛇药去碰触蛇头,蛇畏而避之,真是神通广大!
小竹林里有学校的厕所,隔墙则是驻军司令部的厕所,有时可能是犯人来上厕,有脚铐铁链的声音,并有士兵斥责大喊。那些人是罪有应得还是无辜受迫害的呢?也兴起怜悯同情心。同学们有时也谈论这事。
仿佛记得那是春天踏青的季节吧,漳州所有的中学学生旅游盛产水仙闻名于世的圆山。龙中、寻源、崇正、进德(女中)、简师、职业中学都参加。我和曾炜兄带着“宝贝”的柯达照像机去。山麓满是少俊俏丽的学生,到处寻幽览胜,纵谈水仙出圆山的神话,乐在其中。我和曾炜兄也携照像机细心找镜头,俨然现在的摄影记者,随心所欲,不必征求同意,真是有趣极了。回校后,我们的国文老师徐石(是清末的优贡出身,诗文都很好)出个作文题目《圆山记游》,我除了记述旅游之乐外,还附一首打油诗,有趣也带顽皮,当时还自鸣得意呢。徐老师把它改成一首律师,并用红笔批几字赞好。
提起这位长年穿长衫,以闽南话授课的老贡生徐石老师,也有趣闻。有一次王校长带领省督学上课室视察,突然来到我班门口站着,徐老师突然改口打起官腔来,有点像世界语,大家竟然因为听不懂而骇异,等到督学离去相当久,大家忍不住大笑起来,徐老师微笑道:吃官饭讲官话,不得已也得“老”一下,年老舌硬,“老”不过来,别见笑,别见笑!(闽南话“老”是“扭”的意思)。
当我们被调到福州东湖接受三个月的军训,着兵仔衫,穿草鞋,吃大锅饭,睡通铺,佩长枪、水壶打野外,过没正式的兵仔生活之后,突然芦沟桥的炮声揭开抗日战争的序幕,全国民心非常振奋,我们更是跃跃欲试,确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劲头。(这是一首当时最流行的抗战歌曲)。
果然不久,日机飞来轰炸漳州,龙中寻源两校都与驻军司令部隔邻,当然是重要目标。我们一群学生疏散到野外的竹林里,看到敌机俯冲轰炸驻军司令部,芝山上的高射机枪不停地连珠发射,飞机的机枪声也卜卜不停,炸弹声响个不停……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飞机轰炸的情景,算是很有价值的军事演习。不久,好消息来了,全省与我们同届的高中二年级生都被调到福州东湖接受军事训练的各种科目,并发给我们准军官的皮带、佩剑和竹笠,就派我们到各县的穷乡僻壤去搞民训工作。清晨召集壮丁作初步军事训练,教民众唱抗战歌曲,并到处大书墙头标语,晚上就演出话剧,如《放下你的鞭子》、《慰劳歌》、《马百计》、《三江好》等等。我初被派到诏安县工作,后调到越过板寮岭和松梅岭的闽西重镇长汀工作。我们这一队还远走到曾是红都的瑞金附近,留下不少墙壁标语。省教育厅长郑文贞夸说民训是“笠剑学风”的好表现。
民训回来,学校已搬到长泰县的岩溪。学生们利用课外运动时间开操场。傍晚,同学们大都跳到附近的溪里洗浴痛快一下,浴后高唱《打回老家去》和《拿起爆烈的手榴弹对准杀人放火的日本兵》……王校长还领导我们开全校运动会。在岩溪,我们才认识“土皇帝”叶团长的真面目,也曾特地去欣赏他的小皇宫和在那里看戏。
接着,我们再被调训,派到各县去作民教工作一年,当战时民校的校长或教员。我私自请了一位朋友去顶替,自己却在家乡漳浦县城一家小报馆里义务做记者、编辑,也协助速记重庆的广播新闻,因为我从小喜欢涂涂写写,也因此养成我好读书和写稿发表于报章的爱好,想不到后来沦落在香港却靠此雕虫小技苟活。这是后话。
郑玑老师接任校长后,把学校搬到漳平县的永福镇去。在那儿,一切更简陋,教室分开好几处,同学们自己租房子或以土碉堡为宿舍,饭厅则借用祠堂,大家站着吃饭;桌上摆着定量的饭包和黄豆青菜以及豆腐油花汤,但是豆入饥肠化作蛋白质,还是精神饱满地读书、打球,高喊“抗战必胜!”
也许是受多了战争长久的积闷,同学们也曾因为小误会竟和永福区署里的警察发生冲突,乘夜大伙儿围攻设在一个大碉堡里的区署,抛掷石头,大骂大喊,但毫无反应,既爬不上去,也进不了坚固的大门,泄泄气,倦了也就各自散去,在当时还不失尚武精神,朝气蓬勃,现在回忆起来却有点慨叹。就在那儿我们修完了高中的课程,计算起来共费了四年半的时间。当然我在实际的工作中得益良多,可能比死抱课本更好,它锻炼我以后要写、要讲、要唱、要演戏都可以勉强应付。现今有人大谈“读书无用论”这固然是过激之论,但学以致用是最紧要的,不要在象牙塔里做美梦。
老夫今年七十多,满口半假牙,想起漳州的红柑、天宝的香蕉、浦南的文旦、圆圈的蚝仔煎和鱼头,还是会流口水呢。
谚语“海水最阔,船头偶也相逢”,我在印尼雅加达竟然会晤到王秀南校长和郑玑校长。瘦小的王校长还满有干劲当高级商校校长;而郑校长任数学老师,老态龙钟了,他因高血压禁食一向爱好的猪脚肉,本来肥胖的身体瘦了不少。最后疾终在巨港的华校任内。我对两位校长一往情深,在拙作《海外四十年中》记述了他们在印尼的情况。
我永不能忘记严峻的抗日战争。而今中日成为友好之邦二十年了,大家都觉悟到千万不能再陷旧错。我竟也亲自游览了日本的京都和皇宫,在大阪参观工业区,在富士山上赏雪,在风景区温泉洗浴,我的儿子也留学日本专习纺织,家中也挂着我儿子和日本少女穿古装合影……现在又知悉明仁天皇将于十月间访问神州大陆,要亲自向中国同胞表示对往事的痛心。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回忆往事如烟,我不禁要朗诵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悲叹世事的沧桑了!
纯美中学的抗日宣传活动
李林昌
我在漳浦县立培英小学读初小时(校长张顺福),1931年逢到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我国东北,全体师生臂挂黑纱,上书白色“国仇”两字,听老师演讲,在幼小的心灵上已种下抗日情绪。高小时(学校改为漳浦县立第一中心小学,校长蔡竣德),读开明书店的语文课本,叶绍钧(圣陶)编的,有许多发人深省的课文,其中一篇十九路军旅长翁照垣写的《一个军官的笔记》,写1932年上海军民抗击日军侵略的实况,课文上只写“敌人”,教语文的余炳文老师解释:敌人便是日本。那时我们开始在老师指导下阅读杭州出版的《儿童时报》,看到许多字句里以××代替文字,如“××帝国主义”等,编者附言:“为什么字句里有××,我在这里不能告诉各位读者,请问你的老师和父母,如果老师和父母不愿照实告诉你,那便不是一个好老师和好父母了!”其实报纸上满纸××已是司空惯见,因为当时的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屈辱,禁止公开发表抗日言论,爱国有罪,报纸只好以“××”代表“日本”,以免被抓住把柄。我们少年儿童也和成人一样感到国难深重了。
1936年小学毕业,漳浦县立初级中学已经因为经费问题停办了。好在万隆华侨杨纯美先生独资创办的纯美初级中学刚好在这一年夏季开始招生,我与逢源小学的十几位毕业生一同去投考被录取。在开学典礼上看到杨纯美先生,聆听他朴实的讲话。而在学校一切就绪后,他就再渡南洋经营工商业去了。
一百多名一年级学生分成两班,连校长兼教员在内,老师只有四五位,还要分兼文书、会计、出纳、庶务等工作。膳费每月四元法币(自1935年已实行法币制度,禁止银圆圆流通),吃得不错,可随时报停膳,一餐领五分钱,可饱餐一天碗馄饨。每人每学期还可领回“伙食尾款”六元左右。(当时币值是稳定的,至抗战后期才发生通货膨胀)。
当时全国各地抗日救亡情绪高涨。蔡朝阳老师(井尾人)是教英语的,而音乐、文学造诣甚深,尤其有一副哄亮的歌喉。他思想进步,爱国热情充沛,常在课余集学生在大礼堂教唱聂耳等人所作的救亡歌曲,很多学生自动汇合,学唱十分起劲。音乐老师李继志是蔡老师的同襟,听说在大学时是高材生,后来因为一场恶病留下后遗症,丧失了才华,他把我们当小孩子看待,教唱一些简单的歌曲,我们不能满足,都喜欢跟蔡老师唱慷慨激昂的救亡歌曲如《自由神》、《大路歌》、《救亡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李老师在蔡老师推动下,也改教救亡歌曲,如“九一八,血痕尚未干,东三省,山河尚未还,……国仇一日未雪,国民责任未完”等。
翌年(1937年)“7·7”事变以后,抗日的烽火燃遍了中华大地。漳浦县成立抗敌后援会,当时漳浦县分设五个区,区署所在地旧镇、杜浔、佛昙、石榴坂、官浔各成立抗敌后援分会。纯美中学为当时漳浦县最高学府,校长李克柔被推为佛昙抗敌后援分会主任委员,蔡朝阳老师任宜传工作团团长,全校学生都是宜传工作团团员。李校长与蔡老师便发动学生将抗战的歌声推向社会。他们将学生分成几个组,由教师分别带领,于每星期六晚上出发到各乡村,以歌咏、演剧、演讲等形式向群众宜传。星期天便在佛昙墟埔演出街头剧、演讲、教唱抗战歌曲。于是,“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以及《义勇军进行曲》等等歌曲,都为佛昙侨乡群众所熟稔会唱。国文教师苏恩卿虽是长汀人,由于是厦门大学毕业生,会说一口流利的闽南话,他从厦门带来一些方言童谣小册子,分给学生,叫学生到社会上去教唱,这些琅琅上口的抗战童谣,如“男的不要吃烟枝,女的不要点胭脂,大家俭钱买铳子,打到日本仔半小死”等等,便在侨乡妇女儿童中间传播。
当时佛昙有“潭江号”汽船川走厦门,单程四小时,每天早上开往,晚上约九时左右才回到佛昙,有时因为等人等货,回来时已半夜。码头在纯美中学后面港边,每天晚上便有一些急于知道前线消息的纯美中学师生在那里等候,以先睹厦门《江声报》或《星光日报》为快。如陈明勋这样一位身体瘦弱的数理化教师,也冒海风候至半夜。翌日,学生们便利用午休时间,两人为伴,三人作伙,到墟埔向群众宣传抗日消息。
当年冬季,纯美中学以游艺会形式进行一次较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佛昙虽是侨乡,当时风气还比较闭塞,中学是新生事物,刚刚越过“无猜”阶段的男女同学不大接触,演戏也是分开排练。女生由女生生活指导员叶臻聪老师导演,演出《送女出征》等歌剧,剧中人物大部份是女的,有几个男的也由女生扮演。男生由蔡朝阳老师导演,剧中人物男扮女装。蔡老师根据侨乡特点,选择田汉剧作《回春之曲》改名为《爱情与爱国》,在游艺会上作为主要剧目演出,那是以南洋爱国青年回国参加上海抗战为题材的三幕话剧,南侨风情在演出中表现得维妙维肖,华侨青年的爱国热情也在舞台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一时侨乡为之轰动。这三幕话剧有一个特点是有插曲,由于此剧的演出,其插曲如“再会吧,南洋,“你海波绿,海云长,你是我们第二的故乡,我们民族的血汗,洒遍了这几百个荒凉的岛上………”等,便在校园里以至社会上传唱开来。那时一些男同学身体还很娇小,扮演女角是那么逼真,饰演主角梅娘的林维仁,当时有一副丰满的小白脸,后来竟是瘦骨嶙峋,脸现猴形的中学教师兼业余作者,饰演女教师碧云的陈珊斋,后来竟是体格魁梧的空军飞行员,与日本空军进行过较量的。蔡老师后来侨居万隆,文名蜚声海外,曾参加澳州广播电台中文部主办的国际书法比赛获优等奖;著有诗集《故里风光》,热爱故乡之情跃然纸上。几度回乡,与纯美中学旧时师生促膝话旧,不胜依依。
纯美中学在八年抗战期间一直作为向社会宣传抗日的基地。
每逢假日,纯美中学便配合佛昙一些小学,组成宣传队下乡,以戏剧等形式宣传抗日,演出过《红心草》、《麒麟寨》、《牛头岭》、《烟苇港》等话剧。
抗战时期一个小学生的所历所见
高幸占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序幕拉开了。这一年我刚七岁,父亲送我到西街三房巷张隆古先生办的私塾念“四书五经”。刚念过《论语》,《中庸》、《孟子》三本书,私塾便停办了,原因是政府为适应抗日形势,通令各地开办国民学校,禁办私塾。我便转到武营中心小学,插读二年级。这已是一九三八年了。
入学不久,学校成立“晨呼队”,除一年级外,各级男女生都得参加。每天早晨天未亮,我顶着凛冽的寒风,先到古井头葛婶店前,用二个铜片买一碗糖粥吃,再到学校集中,然后由老师带队,出校门从西街、府前街,转到北街、麦市街,沿街高唱抗日歌曲,“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雄壮嘹亮的歌声、满腔的热血激情,驱散人们身上的寒气。晨呼队的后面跟着县长吕思义,吕手持“动葛”(手杖),沿街敲门撞户,喊老百姓起床,几乎天天如此,妇女背地里多叫他“神经县长”。晨呼队最后到兴教广场参加升旗。升旗后回家早餐,餐后再入学上课。
那时,学生还有一项特殊的课外活动内容,就是“防空演习”。学校划定班级疏散地点,“乱钟”一响,师生马上离校跑到指定地点隐蔽防空。我们班原指定隐蔽点在礼拜堂前龙眼围内,数次演习都去那里。农历四月廿五日那天,我们听到县府大钟紧敲声及学校的乱钟,急忙冲出学校后门,抬头看见飞得很低的日机,已在礼拜堂方向的上空,我急转身向高厝巷,一口气跑到城边桃仔园(现北市场蔬菜公司),突然听到恐怖刺耳的飞机呼啸声,急忙按演习时老师讲的,俯卧地上,掩耳张口。“轰轰轰”一连串的炸弹爆炸声,声声震动着大地,也震动着我的身心。我身边有些妇女,紧紧捂着孩子的嘴巴,怕哭声引来飞机,口中叼念着,天公保佑,佛祖保庇,炸弹不要落在这里。好不容易在心惊胆战中挨到飞机走了,警报解除了,才急忙回家,看到家中一切依旧,方能开口说话。这时,街上传开了,炸弹炸在礼拜堂前龙眼围左右,炸死了蔡发祥、蔡恢等数人,死者四肢五脏悬挂树梢、檐口,惨不忍睹。以后钟声一响,我便从高厝巷往北门兜方向跑。那时的飞机是螺旋桨的,飞不快,轰炸还要打围找目标,因此,飞机飞到头上立即卧倒地上,飞机一过身,立即拔腿再走,经常走三、四里路到羊寮(今朝阳)、楼仔顶村。
当时,“防空哨”设在鸡笼山(现气象台),警报器用挂在县府前东侧钟楼上的大铜钟。防空哨一接敌机犯境情报,立即电告敲钟者,敲钟者立即赶到钟楼,登楼撞钟。连续紧接撞钟为敌机入境警报;如慢慢地一声一声则是解除警报。后来,可能因钟楼延缓时间,改用一部金属手摇“警螺”(汽笛)以代替大钟。
城内居民一听到警报,便急奔城外疏散或躲进防空洞、防空壕。那年七月廿九日(俗为“尾中元”),日机投弹炸在市场(现旧文化馆)东侧防空壕(今新华书店第二门市部),几个人堵死在里边。自此很多人不敢躲入防空洞。
这一年,日机犯境非常频繁,有时一天要走避数次。学校只好采取疏散上课,我们班到王顶蔡俊德校长家上课,也曾到西门外大树下(现城关粮站)上课。城里居民也改变生活方式,天朦朦亮就吃早餐,太阳未出时就出城躲日机。中午就地野炊,穷困之家午餐只好免了。黄昏后庆幸一天平安过去,才陆续回家。
县府后衙(现宾馆)几株大榕树上栖着几千只乌鸦,曾有乌鸦半夜“反巢”隔日敌机犯境情况,群众将乌鸦当“预警器”。七月上旬,乌鸦夜夜反巢,居民搞得失魂落魄,日夜不宁,既不能安居,更无法乐业。我父亲是手艺工人,他上半辈子有二怕,一怕日本飞机;一怕抓壮丁。警报一响,他面如土色,连跑也跑不动,只好在家宅后龙眼树下挖一条防空壕。在城内、躲防空壕也是担惊受怕,父亲便到城郊附近农村去联系住房,准备搬到农村中去。
农历九月初六、初七两天,日机连续轰炸县城数处,每次都有居民被炸得血肉横飞。城内居民纷纷搬到农乡亲友家。家长也不敢让子女去上学。武营中心小学也搬到霞潭村,我们全家搬到罗北考湖村。起初,每天跟着堂兄走三、四里路到霞潭去上学。不多久,学校没学生上课,老师也走了。堂兄到东门他外婆家,我也停学了。
在考湖村,父亲断了手艺营生,就租了一些土地,我们成了见习农民。见习农民种地比正式农民还讲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摘绿豆。父亲说,太阳出来一晒,豆英就爆裂,因此,采绿豆就得在大阳出来前。中午,农民都回家休息,父亲要我跟他留在地里锄草,说中午阳光强,锄掉的草不易复苏。我还常跟祖父进城卖蕃薯,两担蕃薯可卖一百多个铜镭,吃一碗“水面”5镭,祖孙吃后,再把家里的肥料挑到农村地里。当地农民说我们生产的作物不比他们少。但我的学业却荒废了。一九四〇年空袭减少了,祖父母先回家,不久,全家回城。学校复课了,我也复学。
吕思义县长走了,学校不再搞晨呼了。但小学生还得接受军训。军训很正规,每个学生要做一套黑布中山装,黑学生帽,束腰皮带,高年级同学要打绑腿。女生一律剪短发。学校利用劳作课,中年级每人做一把木大刀,油漆后系上红布带。高年级每人做一支木驳壳枪。西街顶陈克昌先生任学校军事训练教官。体育老师教舞大刀,陈教官教步兵操,教打野战。有一次,高年级同学到野外操演野战,曾鼎同学被土制手榴弹炸得血流满脸,用担架抬回校。
武营中心小学不少老师是进步青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教学生唱抗日歌曲,演“文明戏”(话剧),绘宣传抗日画。蔡俊德、郑秀贞夫妇、蔡启昌、林清秀夫妇、曾敏英、张淡月、许其和等老师,还有校外的柯汉扬、蔡维汉、邱珍五等先生组织的“抗敌剧团”,经常下乡演“文明戏”宣传抗日,高年级不少同学跟着剧团下乡,充当配角或跑龙套。有一次,我和戴壬癸同学被曾敏英老师叫上台凑个群众角色。兴教广场的戏台原是露天的,为了演文明戏宜传抗日,县政府拨款盖瓦顶大戏台,连带左右两大房间,演戏时作化妆室、休息室。平时则作我们的教室。
抗战时期,我们小学生不但自己要读书,还要当民众夜校的小先生。我被分配在县府内县堂(现历史博物馆)识字班当先生,还有同班女同学教唱抗日歌曲。每天晚餐后,手提小油灯挨家挨户叫学员上学,学员多是中青年妇女。
小学生参加的会竟多不胜数。全县在兴教广场开“一元献机抗日”大会,我们全校都去参加,有些同学在家长支持下,上台献金戒指、银圆,有各界人士、妇女上台献首饰、钞票,我们在台下鼓掌、唱抗日歌曲。竖“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在县幼儿园后大路边),我们同学每人献几个铜镭放在碑基底下。每星期一是“纪念周”例会,我们必须穿着整齐的校服,列队到兴教广场唱抗日歌曲,听县长训话。
当时的老师很重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记得有一年儿童节,每个同学分到一份礼物,有糖果、饼干,还有一节果蔗。蔡校长手拿甘蔗问大家:同学们,这是什么?大家异口同声回答:是甘蔗。校长笑着说:不,这是用来打日本飞机的高射炮……。在五年级时,学校举办美术展览,老师要求学生画有抗日内容的图画。我和王乾三、叶集锋,从学校图书室借来很多张“日寇暴行图”,我们每人临摹了好几张参加展览,老师还表扬我们。
后来,敌机侵犯骚扰减少了,社会上涌起抓汉奸、抓壮丁潮流。老师告诉我们,汉奸装成乞丐、小贩、难民,到处向水井投毒,学生要协助政府抓汉奸,随时随地注意可疑的人。社会上也传得人心惶惶,公共场所的水井都要加盖上锁。肃奸成为一个新运动,文明戏演“抓汉奸”,街头标语、漫画也都是肃奸内容的。有一次,兴教广场演“文明戏”,归侨,修脚踏车的乌番师傅,客串扮汉奸黄秋岳,“黄犯”五花大绑,背插斩标,身后左右站立两名持枪法警。“黄犯”用潮曲清唱通敌叛国的罪状,由城关民乐演奏手们伴奏。曲完执行枪决,“啪”一声,“黄犯”从台上栽下台来,观众人心大快,“消灭汉奸”,“枪毙卖国贼”!喊声响彻云霄。有一次,我们正在上课,忽然听到要枪决“资敌犯”胡百虎,大家丢下课本跑到街上观看。
社会上到处在抽壮丁,按规定,三抽二,二抽一,单丁缓役,但有钱人尽管兄弟多,可以用钱雇壮丁,当官的怕中签的壮丁逃跑,保内壮丁抓阄,一中签马上像犯人一样被缚起来押关在联保办事处(后改乡镇公所),家属三餐去送饭。接兵部队一期接着一期来接收。接兵部队在城关一些祠堂设“新兵招待所”,实是关壮丁的牢狱。我们学校有不少同学的父兄被抓丁,家无劳力,不得不失学。当兵上前线抗击日寇,原是国民应尽义务,理应踊跃应征,为何要用绳子缚,铁丝捆,发现逃跑,不是当场击毙,就抓回活活打死?那一年署假,武菅中心小学被接兵部队“借”去关壮丁。有一天,我们几个同学路过窗下,突然听见内边惨叫声,便停足往内窥视,见二个壮丁赤裸身子被按在石板上,当官的指挥其他壮丁逐个用扁挑轮打,终于打得不叫不动了。我家隔巷刘祠堂,也是关壮丁的地方,经常在半夜听见惨叫声,天刚亮就可看见荷枪的士兵,押着壮丁抬着裹草席的尸体出城去。还有一次,关在兴教寺的壮丁,集体逃跑,当官的下令用机关枪扫射,打死十余人,横尸榕树下。这些现象老百姓看在眼里,更觉得当壮丁的可怕。
国民党政府只管抽壮丁,不管壮丁家里生活如何,妻孥子女死活如何,壮丁抓到“招待所”,吃不饱,穿不暖,动辄遭受毒打,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往上送时,每人牢牢捆缚,还用铁丝扎成一串,拉屎撒尿还要挨枪托、皮鞭毒打。用这种手段抓来的兵怎能打仗,怎能不跑呢?当然,自愿去当兵的人也有。我同班一位姓李的同学,在家庭得不到温暖,未到16岁去“卖壮丁”(顶替他人入伍,价钱约2至3担花生油)。六年级一位姓洪的同学,顶替其胞兄入伍,未经什么训练就被押送到安徽,补入前线部队,参加九华山会战,队伍打散了,他靠着这小学文化知识,孤身千里跑回漳浦,考上漳浦中学。1944年,政府派人到学校招募“远征军”,说是要到缅甸、印度参加盟军抗日,还招“华安军”等,学校不少同学报名参加。只有这样当兵才免受“新兵招待所”虐待,且受光荣欢送。
我们小学毕业那年,潮汕地区被日本侵占,大批难民逃到闽南,来漳浦的为数更多。不久,全县突然发生瘟疫(霍乱),死亡数千人。我们班里同学就死了三男一女,这可以说是间接死于战乱。
上了初中不久,形势又趋紧张,二、三年级同学疏散到石榴崎溪一带上课,我们一年级则是上早,晚课,每人自备一盏小油灯,每天两头摸黑去上学,好在此况时间不长。
一九四五年七月的一天,忽传占据厦门的日军数百名,从海澄港尾登陆向漳浦而来。消息传开全城震动,居民纷纷离家疏散出城,学校也宣布停课,学生随家庭疏散。我们与邻居几户疏散到罗山大埔村。那一夜,约11点钟,突然来了一股“追击”日寇的国军七十五师,有数名“便衣”会说本地话。把我们几家驱赶集中在一间房屋内,抢去了我们很多东西。“便衣”又叫十几个妇女帮他们把抓来的鸡鸭宰剥烧煮。天亮了他们要走了,我问其中一人:你们追日本怎么追到这里?那人说,我们是从文周岭过来的。我明白了,日寇流窜是走佛昙、赤湖、旧镇、城关的大路,国军是走湖西、赤土、万安、文周岭、罗北弯弯曲曲山路,这条路线距大路约二、三十华里。完全可避免与日军遭遇。
日军窜入城内抓去一些老百姓当挑夫,即离城往盘陀方向而去。次日我们回家,听说日军过盘陀时被盟军飞机炸死一些人马。挑夫有的乘机选出日军魔掌,回了家,有的被日军打死,有的被盟国飞机炸死。
中国有句古话:“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民。”战乱是何等可怕可悲可恨,和平是何等可贵。要得到和平,国家就必须加强现代化建设,否则落后就要挨打。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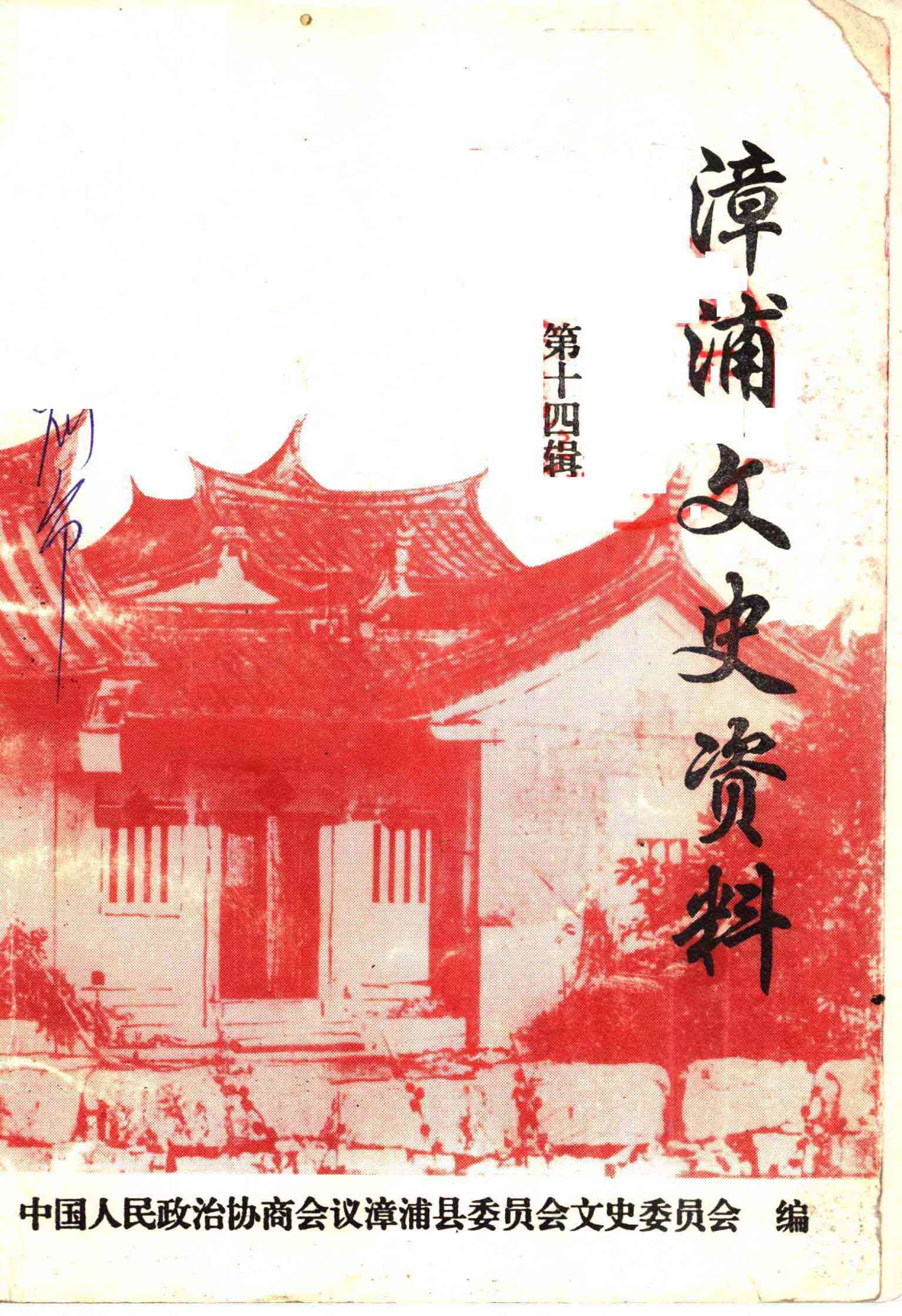
相关地名
漳浦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