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浦的旧风俗
| 内容出处: | 《漳浦文史资料新第三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30000611 |
| 颗粒名称: | 漳浦的旧风俗 |
| 分类号: | K892 |
| 页数: | 6 |
| 页码: | 59-64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漳浦县的一些历史风俗和特殊风俗,包括社会旧风气、一些特殊的风俗、一些特殊的方言和忌用语等。 |
| 关键词: | 漳浦县 旧风俗 |
内容
一、社会旧风气
在海上交通发达,贸易繁荣的时代,沿海地区属于“近水楼台”,但在造船业落后以及厉行海禁和闭关自守的封建时代,漳浦“偏处海隅”,风气闭塞。就是到了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五口通商,洋货如潮水般涌来的时代,漳浦由于农村破产,民穷财枯,购买力很低,人们除了日常用品如“番仔火”,“番仔皂”、“番仔油”等必须仰赖于舶来之外,一些高档商品在漳浦是没有市场的,所以有“好货仔无流入旧镇港”的俗谚。民间还多数自种棉花和黄麻,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漳浦人素来有勤劳俭朴之风,同时也风气闭塞。
宋史称漳浦为“硗确斥卤之地,耕褥殆尽,亩值寝贵,田讼尤多”。宋朝漳州著名学者陈北溪(淳)说:“此邦民质朴谨畏然,间有奸雄健讼,为善良之梗者”。闽省通志说漳浦“民阜讼稀,田亩寝贵,士质而文,民勤而朴”。成书于明朝成化年间的漳州郡志说:“漳浦之俗,质朴谨畏,尚儒雅,依山者习乎农桑,处海者事于网罟,婚姻葬祭多依古法,间有专信鬼神,不事医药者;有近薄汀潮,民性愚悍为善良之害者”。明朝何乔远《闽书》说:“漳浦旧有金,名焉谚谓之金漳浦、银同安,今或不然,未远古也,其民殷庶,其君子娴于文词,不但用以取出身而已”。王祎的诗说漳浦“文物如邹鲁”。成书于明朝嘉靖年间的漳浦旧志说本县“读书之家无问贫富,每岁首各廷师受业,虽乡村数家聚处亦有师。俗好胜,健讼,赌博,强者武断乡曲,黠者挟持官府,小民因小忿辄服断肠草图赖官府,有事追坠拒捕,殴打率以为常”。
综合各种旧方志和先人的记载,可以知道封建时代的漳浦,有农桑之利,渔盐之薄,地方富庶,人民勤劳朴实,读书蔚为风气,士子娴于文词;但也有健讼、好斗、迷信、赌博,还有“强者”武断乡曲,“弱者”轻生自杀的坏风气;到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有些人还传染上抽鸦片之风。至于缠足、溺女婴、男人留辫子等陋习,这是全国性的‘只是漳浦从前“偏处海隅”,比较闭塞,进步风气级慢普及,所以到解放初还能找到留辫子的老汉,还有一些缠足的老妇。
二、一些特殊的风俗
漳浦的旧节日风俗与大部份汉族地区差不多,这里不多赘。
单说漳浦一些与别处不同的风俗及所流传这些特殊风俗来源的传说。
一、新娘在红装下面要穿贴身的白衣裤,新婚之夜露出一身缟素,这来源有一个传说:陈元光“开漳”时,一些“獠蛮”的男子战死,或说被杀,唐兵娶他们的妻、女为妻,“番婆”要求让她“带孝”成亲,因而传下这风俗。
二、妇女丧礼的幡联上以及墓碑、神主上,不论身份,都可以写上“例赠孺人”的衔头,这是皇帝对官员的母、妻的封号,漳浦的民妇死后为什么有这个衔头呢?有的传说是井尾“皇后”赐的,有的传说是宋帝昺南逃时经过漳浦,杨太后无聊,要找民间妇女来谈天,大臣答以太后不可接见平民,杨太后就下一道旨意,对这里的妇女一律封赠“孺人”。漳浦的新娘在拜堂时戴“凤冠”,据说也是根据这个。其实,“孺人”在从前虽是封号,后来已成为对妇女通用的尊称,正如“夫人”本来是比“孺人”更高级的封号,后来成为对妇人通用的尊称一样,妇人称“孺人”是不受干涉的。
三、读书人不论有官无官,在出葬时的铭旌上都可冠以“赐进士”的头衔,传说也是宋帝昺南逃途中在马口溪开科取士,元兵追到,仓促在溪沙埔揭榜,对与考士人尽赐进士,人们“援例”取得的头衔。其实,宋帝昺是端宗航海逃到广东溺水得病死后才被立继续皇位的,按宋史记载,並没有经过漳浦
四、漳浦人盖房子喜欢在“厝角头”装着尖尖的“燕仔尾”,传说也是“井尾皇后”特赐漳浦老家“龙宫起”而来的。而井尾皇后是传说中的人物,不见于史料,谁也说不出她是什么朝代的皇后。《漳浦县志》说本县人用筒瓦盖屋顶和屋角“鸱吻异状”是为了防御海风袭击。
五、漳浦人从前嫁女要用一对“官灯”前导。据《漳浦县志》林士章的传记记载,那是由于明朝嘉靖年间探花、礼部尚书林士章的夫人被太后召见,坐谈到天黑,太后赐她宫灯照路回家,漳浦人于嫁女时藉此虚荣一番,为富裕之家所仿效。
这些特殊风俗的形成,反映了一些羡慕虚荣者的精神面貌。
只有“填鸭”的习惯对大众有实惠,以前填鸭只有北京盛行,全国其他各地比较少见,有的甚至闻所未闻,倒是漳浦蔚成风气,无论绅士、商人、农民大都在春节之前填几只肥鸭过年。鸭子多是自养,填鸭的材料主要是番薯、饭团混合粗糠或细糠,一般农家都能办到,一只鸭子可以用强制进食的方法使它在短时间内肥育到十多斤,春节期间可以吃得油腻腻,是待客的佳品,这传统据说是蔡相爷(乾隆皇朝文华殿大学士、吏、兵等部尚书蔡新)告老回乡时将北京的填鸭方法在老家民间传播的。
三、一些特殊的方言、忌用语
漳浦方言是闽南话,即“河洛话”,据说是唐朝陈元光开漳时五十八姓南下的汉人留传下来的,属于中古汉语,所以一些唐、宋诗词用普通话读起来已不能合韵,而用闽南音却能合韵,闽南话有一些用语,如称筷子为“著”,称汤匙为“调羹”,称瓮为“盎”等,与古汉语相合,所以闽南话大都是有字可写的。但漳浦也有一些特殊方言,如说事情还无头绪为“未胶里罗”,时候未到为“艾罗高”等,由于无字可解,被传说为古时少数民族所遗留。也由于受华侨影响,方言中央杂一些外来语,如称大衣为“屈”,称灯为“滥浮”(限于一种英国产的灯),市场叫做“巴刹”等。
漳浦现在还有人按照过去习惯,对与葬、死有关的字眼因禁忌而改口,如称死人为“老去”或“过去”“无法”‘称殡葬为“出山”,葬穴叫“金井”,棺材叫“大厝”,盖在死人身上的布叫“大被”等,结果真的老、无、出山、大厝、大被等都变成不吉利的词语,有时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以致发生龃龉,令人啼笑皆非,现在有的人对这类浦语还很慎用。
四、婚俗
从前漳浦社会在封建礼教束缚下,妇女缠足,非不得已一般不出门,男人偷看妇女一眼也会招来杀身之祸,妇女稍微有点“越轨”就要被认为不守妇道,受尽家庭和社会的谴责与非议。婚姻都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妇女的一生幸福全听命运,所以有“女儿菜籽命”的俗谚。
娶妻的聘金一般要在两三百银元左右,(一般年景一百元可以买五千市斤稻谷),说来是属于买卖婚姻,直到现在某些地区婚姻还要送聘礼一百八十元和一百八十斤猪肉、十八套衣服,糖、饼几百包……等,封建买卖婚姻流毒还未肃清。但是女方赔嫁妆往往要超过聘金,所以娶妻花大钱,嫁女也要赔本。从前,有的人在女儿出生之后就开始准备嫁妆,有的卖田嫁女,有“漳浦三项痴,好地建庵院,米浆饲大猪,卖田嫁女儿“的俗谚。因此,民间童养媳之风很盛,有的人宁愿将自己的女儿卖给别人,去买别人的女儿来做童养媳。俗语说“别人的孩子死不了”童养媳多数受虐待、奴役。童养媳叫做“心妇仔”,长大了就可以作为“媳妇”(媳妇即儿媳妇,与北方称妻子为“媳妇”不同)可以省却很多嫁娶的钱。北路有些乡间婚礼可以简单从事,有的贫穷不能举办婚礼、可以先成为实际上的夫妻,等以后有办法时补办婚礼,叫做“做老新娘”,也有等到夫妇一方死了才与葬礼合并举行的。这种婚姻也可以说是“穷则变,变则通”吧。
婚娶的繁文缛节,按照古例有六礼:一、求庚:求女方开给“生庚”即生时日月,以便请择日先生算男女双方有无“相克”和作为定吉期的根据。二、送定:送给女方以钗钏之类,就是“纳采”俗称,“小定”。三、行聘:男方具婚书、金银、牲礼送到女方,就是“纳吉”俗称“大定”。四、送袄:送给女方衣裙之类,就是“纳徵”。五、送日:就是由男方通知结婚佳期,要送给女方糖果。六、亲迎:新娘身穿红袄,头戴凤冠;属于明朝装束;新郎则戴红顶碗帽,穿长衫马褂,俨然清代命官。传说是清朝皇帝推翻明朝时允许“降男不降女”,故而婚嫁时男穿清服女着明衣。这天由男家偕仪从(俗称囝婿伴)领花轿到女家后先回家在门首等候迎接,新娘轿抬到后,由新郎的小弟或其他亲属的男孩恭请新娘下轿,由新郎导入厅堂行交拜礼,照预先择定的良时,新郎新娘同携一篮米进房,由新郎的小弟或其亲属的男孩恭奉“红圆”和四果汤,一对新人都要吃一点,並各自以事先准备好的红包给予赏赐。当晚起,大开筵席,宴请送礼的亲友,有的接连几天,铺张浪费。新娘在结婚的翌晨下厨间试厨、再以四果汤恭奉公婆及其他长辈,叫做“拜茶”,受茶者要以红包赏赐。中午,由婆婆宴请新妇,由小辈妇女作陪,表示欢迎之意。同时,娘家要遣小舅子以篮送花到新房,放置床上,以作早产麟儿之兆,俗称“送花”也称“探房”。到第三日,新娘归宁母家,俗称“做客”。新郎如果同行,要走在新娘后面,叫做“回礼”,岳母要宴请女婿,其间有许多规矩,新女婿一生只做一次,往往记不住长辈教给的礼节,贻笑大方,事后才明白。所以有“等到识礼已经无囝婿可做”的俗谚。
结婚后第一个春节,女婿要与新娘同送“煨仔肉”到岳家,岳家设宴款待,所送“煨仔肉”第一年不收,第二年只收一点,大部份要让携回去,娘家並没有得到实惠,但此礼不能没有,以后每年都要重演一番,只是女儿送去即可,女婿不一定同行,日期不定,但最好新正就去,有“有孝女儿初二三,无孝女儿到月半”的俗谚。
旧礼教的婚俗,连宋朝理学家朱熹都认为太繁,他在任漳州知府时,提倡把原有六礼合并为三礼,即求庚、行聘、亲迎。其他大定、小定、送袄等可合并附行,民间称便。但也还有很多人蓄意铺张,仍然按照六礼进行。
封建时代漳浦的士大夫们着力宣扬“忠、考、廉、节”的所谓“漳浦精神”,列出历史上的代表人物(忠:黄道周、孝:高东溪、廉:张若仲、节:刘庭蕙之母)作为效法的表率。其中“节”一项宣扬的是“烈女不嫁二夫”的封建妇德,建“烈女祠”来表彰节妇,县志以很多篇幅为烈女立传。在夫权、族权。神权的重压下,不知有多少寡妇(有的还没有过门)葬送了终生幸福。刘庭蕙的母亲不过是千万人中的一个。她还是在养尊处优的生活条件下守的节,比起无依无靠饥寒度过悽凉一生的穷苦寡妇来,其节烈精神简直如小巫之见大巫,只是由于儿子做了官,奏请御赐旌表,便成为代表人物,而她的贞节坊上“月夜啼乌”的凄厉名句后面,不知隐藏着多少无名节妇的伤心泪。
五、丧事
漳浦从前风气闭塞,有很多陋俗,尤其办理丧事,有许多弊例:一、大事铺张,富贵之家,吊丧者纷来沓至,多有赠仪。最苦的是一般人家,办丧事本是一件痛苦事,却有人幸灾乐祸地来凑热闹,有时全村的人不论男女都跑到丧家吃饭,一直到丧葬完毕,就是俗语所说的“全社塞灶门”,丧家还要办酒席款待帮忙的人,就是帮闲的也可以混迹其间。(只有那无子无女无财产的孤老死后才让人替他雇两名或四名“土工”抬出草草埋葬,被认为是最“歹命”的)。一般人家办丧事都要负债,只有用“父母债快还”这句俗语来自我安慰。二、择日:尸体要经大敛、小敛而后入棺。入棺、成服、卒哭、出殡都要择吉日良辰,宁愿将尸棺留在家中,迁延时日,多加糜费,也不肯从权处理。对这种风俗,连成书于封建时代的《漳浦县志》也斥其“悖理殊甚”。三、“风水”:富家惑于“风水”,就是一般人家也多有郑重其事的,不惜用巨额款项求购“吉穴”,望能庇荫子孙,有不得“吉穴”不罢休,宁愿贮棺待葬,也有葬而复迁的。“风水”冲突事件层出不穷,有的甚至酿成“家变”(械斗)。对此,就是清朝的学者(雍正朝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漳浦人蔡世远也加以驳斥,他在《丧葬考惑》一文中说:“……其至愚者,则阴谋横据,相争相夺,以为福在是矣,不知其为祸基也”。又说:“此乃后来术家欲藉此挟凡为子孙者不敢不遵信而延请之,阴以诱其厚利,阳以得其奉迎,不知其为害之深,至死者不归土,而生者不得相和,皆此说误之也”。在科学知识还未发达的清初,有织之士对这种陋习也抱否定态度,而在这科学昌明的现代,竟然还有人复古。所以移风易俗现在仍然是提倡精神文明当中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四、闹丧:出嫁后的妇女死后在入葬前要请她娘家的长辈来为她的棺材“封钉”,否则娘家便要大兴问罪之师,用意在验明有无冤死,这在旧时代具有防止妇女受虐待致死的用意,因为那时政府不能保障妇女权利,只有由“外家”来维护已婚妇女的安全,这个办法可说是民间一大创造,但后来发展成为“外家”勒索死者亲属的手段,有的竟乘人之丧无理取闹。现在已是用法律保障人身的时代,而此风在个别地区还有待革除。
六、迷信鬼神
从前,漳浦迷信鬼神之风很盛,庙宇林立,香烟不断。全县性的迎神赛会有王公生、妈祖生、佛祖生、帝爷生、三界公生、土地公生等等,这些“神明”有的要“生”了一个多月至几个月,各乡村轮流为它作寿诞,各村亲戚互送供品糕馃,互请看戏,吃吃喝喝,糜费很大。解放前有很多农民就是为做演戏酬神借了高利贷被母滚利、利滚母,弄得破家荡产的。
迷信之风给巫婆神汉以可乘之机,有“红姨”(或称“师母”)可使活人与鬼魂相见的。有“铜身”(神汉)能使神灵附在他身上作法行医派药的,流弊所及,误死人命。
漳浦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还很多,这里所举只是一些比较显著的。对于一些比较好的风尚已受到发扬和改进,如欢度春节、元宵灯会、清明扫墓、端午龙舟竞渡、中秋节赏月、重九登高等。对于一些劣风陋习,如封迷建信等,在建设精神文明的推动下,虽已有很大程度的收敛,但几干年来的流毒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尽除,宣传与制止还是长期不可忽视的工作。
在海上交通发达,贸易繁荣的时代,沿海地区属于“近水楼台”,但在造船业落后以及厉行海禁和闭关自守的封建时代,漳浦“偏处海隅”,风气闭塞。就是到了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五口通商,洋货如潮水般涌来的时代,漳浦由于农村破产,民穷财枯,购买力很低,人们除了日常用品如“番仔火”,“番仔皂”、“番仔油”等必须仰赖于舶来之外,一些高档商品在漳浦是没有市场的,所以有“好货仔无流入旧镇港”的俗谚。民间还多数自种棉花和黄麻,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漳浦人素来有勤劳俭朴之风,同时也风气闭塞。
宋史称漳浦为“硗确斥卤之地,耕褥殆尽,亩值寝贵,田讼尤多”。宋朝漳州著名学者陈北溪(淳)说:“此邦民质朴谨畏然,间有奸雄健讼,为善良之梗者”。闽省通志说漳浦“民阜讼稀,田亩寝贵,士质而文,民勤而朴”。成书于明朝成化年间的漳州郡志说:“漳浦之俗,质朴谨畏,尚儒雅,依山者习乎农桑,处海者事于网罟,婚姻葬祭多依古法,间有专信鬼神,不事医药者;有近薄汀潮,民性愚悍为善良之害者”。明朝何乔远《闽书》说:“漳浦旧有金,名焉谚谓之金漳浦、银同安,今或不然,未远古也,其民殷庶,其君子娴于文词,不但用以取出身而已”。王祎的诗说漳浦“文物如邹鲁”。成书于明朝嘉靖年间的漳浦旧志说本县“读书之家无问贫富,每岁首各廷师受业,虽乡村数家聚处亦有师。俗好胜,健讼,赌博,强者武断乡曲,黠者挟持官府,小民因小忿辄服断肠草图赖官府,有事追坠拒捕,殴打率以为常”。
综合各种旧方志和先人的记载,可以知道封建时代的漳浦,有农桑之利,渔盐之薄,地方富庶,人民勤劳朴实,读书蔚为风气,士子娴于文词;但也有健讼、好斗、迷信、赌博,还有“强者”武断乡曲,“弱者”轻生自杀的坏风气;到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有些人还传染上抽鸦片之风。至于缠足、溺女婴、男人留辫子等陋习,这是全国性的‘只是漳浦从前“偏处海隅”,比较闭塞,进步风气级慢普及,所以到解放初还能找到留辫子的老汉,还有一些缠足的老妇。
二、一些特殊的风俗
漳浦的旧节日风俗与大部份汉族地区差不多,这里不多赘。
单说漳浦一些与别处不同的风俗及所流传这些特殊风俗来源的传说。
一、新娘在红装下面要穿贴身的白衣裤,新婚之夜露出一身缟素,这来源有一个传说:陈元光“开漳”时,一些“獠蛮”的男子战死,或说被杀,唐兵娶他们的妻、女为妻,“番婆”要求让她“带孝”成亲,因而传下这风俗。
二、妇女丧礼的幡联上以及墓碑、神主上,不论身份,都可以写上“例赠孺人”的衔头,这是皇帝对官员的母、妻的封号,漳浦的民妇死后为什么有这个衔头呢?有的传说是井尾“皇后”赐的,有的传说是宋帝昺南逃时经过漳浦,杨太后无聊,要找民间妇女来谈天,大臣答以太后不可接见平民,杨太后就下一道旨意,对这里的妇女一律封赠“孺人”。漳浦的新娘在拜堂时戴“凤冠”,据说也是根据这个。其实,“孺人”在从前虽是封号,后来已成为对妇女通用的尊称,正如“夫人”本来是比“孺人”更高级的封号,后来成为对妇人通用的尊称一样,妇人称“孺人”是不受干涉的。
三、读书人不论有官无官,在出葬时的铭旌上都可冠以“赐进士”的头衔,传说也是宋帝昺南逃途中在马口溪开科取士,元兵追到,仓促在溪沙埔揭榜,对与考士人尽赐进士,人们“援例”取得的头衔。其实,宋帝昺是端宗航海逃到广东溺水得病死后才被立继续皇位的,按宋史记载,並没有经过漳浦
四、漳浦人盖房子喜欢在“厝角头”装着尖尖的“燕仔尾”,传说也是“井尾皇后”特赐漳浦老家“龙宫起”而来的。而井尾皇后是传说中的人物,不见于史料,谁也说不出她是什么朝代的皇后。《漳浦县志》说本县人用筒瓦盖屋顶和屋角“鸱吻异状”是为了防御海风袭击。
五、漳浦人从前嫁女要用一对“官灯”前导。据《漳浦县志》林士章的传记记载,那是由于明朝嘉靖年间探花、礼部尚书林士章的夫人被太后召见,坐谈到天黑,太后赐她宫灯照路回家,漳浦人于嫁女时藉此虚荣一番,为富裕之家所仿效。
这些特殊风俗的形成,反映了一些羡慕虚荣者的精神面貌。
只有“填鸭”的习惯对大众有实惠,以前填鸭只有北京盛行,全国其他各地比较少见,有的甚至闻所未闻,倒是漳浦蔚成风气,无论绅士、商人、农民大都在春节之前填几只肥鸭过年。鸭子多是自养,填鸭的材料主要是番薯、饭团混合粗糠或细糠,一般农家都能办到,一只鸭子可以用强制进食的方法使它在短时间内肥育到十多斤,春节期间可以吃得油腻腻,是待客的佳品,这传统据说是蔡相爷(乾隆皇朝文华殿大学士、吏、兵等部尚书蔡新)告老回乡时将北京的填鸭方法在老家民间传播的。
三、一些特殊的方言、忌用语
漳浦方言是闽南话,即“河洛话”,据说是唐朝陈元光开漳时五十八姓南下的汉人留传下来的,属于中古汉语,所以一些唐、宋诗词用普通话读起来已不能合韵,而用闽南音却能合韵,闽南话有一些用语,如称筷子为“著”,称汤匙为“调羹”,称瓮为“盎”等,与古汉语相合,所以闽南话大都是有字可写的。但漳浦也有一些特殊方言,如说事情还无头绪为“未胶里罗”,时候未到为“艾罗高”等,由于无字可解,被传说为古时少数民族所遗留。也由于受华侨影响,方言中央杂一些外来语,如称大衣为“屈”,称灯为“滥浮”(限于一种英国产的灯),市场叫做“巴刹”等。
漳浦现在还有人按照过去习惯,对与葬、死有关的字眼因禁忌而改口,如称死人为“老去”或“过去”“无法”‘称殡葬为“出山”,葬穴叫“金井”,棺材叫“大厝”,盖在死人身上的布叫“大被”等,结果真的老、无、出山、大厝、大被等都变成不吉利的词语,有时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以致发生龃龉,令人啼笑皆非,现在有的人对这类浦语还很慎用。
四、婚俗
从前漳浦社会在封建礼教束缚下,妇女缠足,非不得已一般不出门,男人偷看妇女一眼也会招来杀身之祸,妇女稍微有点“越轨”就要被认为不守妇道,受尽家庭和社会的谴责与非议。婚姻都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妇女的一生幸福全听命运,所以有“女儿菜籽命”的俗谚。
娶妻的聘金一般要在两三百银元左右,(一般年景一百元可以买五千市斤稻谷),说来是属于买卖婚姻,直到现在某些地区婚姻还要送聘礼一百八十元和一百八十斤猪肉、十八套衣服,糖、饼几百包……等,封建买卖婚姻流毒还未肃清。但是女方赔嫁妆往往要超过聘金,所以娶妻花大钱,嫁女也要赔本。从前,有的人在女儿出生之后就开始准备嫁妆,有的卖田嫁女,有“漳浦三项痴,好地建庵院,米浆饲大猪,卖田嫁女儿“的俗谚。因此,民间童养媳之风很盛,有的人宁愿将自己的女儿卖给别人,去买别人的女儿来做童养媳。俗语说“别人的孩子死不了”童养媳多数受虐待、奴役。童养媳叫做“心妇仔”,长大了就可以作为“媳妇”(媳妇即儿媳妇,与北方称妻子为“媳妇”不同)可以省却很多嫁娶的钱。北路有些乡间婚礼可以简单从事,有的贫穷不能举办婚礼、可以先成为实际上的夫妻,等以后有办法时补办婚礼,叫做“做老新娘”,也有等到夫妇一方死了才与葬礼合并举行的。这种婚姻也可以说是“穷则变,变则通”吧。
婚娶的繁文缛节,按照古例有六礼:一、求庚:求女方开给“生庚”即生时日月,以便请择日先生算男女双方有无“相克”和作为定吉期的根据。二、送定:送给女方以钗钏之类,就是“纳采”俗称,“小定”。三、行聘:男方具婚书、金银、牲礼送到女方,就是“纳吉”俗称“大定”。四、送袄:送给女方衣裙之类,就是“纳徵”。五、送日:就是由男方通知结婚佳期,要送给女方糖果。六、亲迎:新娘身穿红袄,头戴凤冠;属于明朝装束;新郎则戴红顶碗帽,穿长衫马褂,俨然清代命官。传说是清朝皇帝推翻明朝时允许“降男不降女”,故而婚嫁时男穿清服女着明衣。这天由男家偕仪从(俗称囝婿伴)领花轿到女家后先回家在门首等候迎接,新娘轿抬到后,由新郎的小弟或其他亲属的男孩恭请新娘下轿,由新郎导入厅堂行交拜礼,照预先择定的良时,新郎新娘同携一篮米进房,由新郎的小弟或其亲属的男孩恭奉“红圆”和四果汤,一对新人都要吃一点,並各自以事先准备好的红包给予赏赐。当晚起,大开筵席,宴请送礼的亲友,有的接连几天,铺张浪费。新娘在结婚的翌晨下厨间试厨、再以四果汤恭奉公婆及其他长辈,叫做“拜茶”,受茶者要以红包赏赐。中午,由婆婆宴请新妇,由小辈妇女作陪,表示欢迎之意。同时,娘家要遣小舅子以篮送花到新房,放置床上,以作早产麟儿之兆,俗称“送花”也称“探房”。到第三日,新娘归宁母家,俗称“做客”。新郎如果同行,要走在新娘后面,叫做“回礼”,岳母要宴请女婿,其间有许多规矩,新女婿一生只做一次,往往记不住长辈教给的礼节,贻笑大方,事后才明白。所以有“等到识礼已经无囝婿可做”的俗谚。
结婚后第一个春节,女婿要与新娘同送“煨仔肉”到岳家,岳家设宴款待,所送“煨仔肉”第一年不收,第二年只收一点,大部份要让携回去,娘家並没有得到实惠,但此礼不能没有,以后每年都要重演一番,只是女儿送去即可,女婿不一定同行,日期不定,但最好新正就去,有“有孝女儿初二三,无孝女儿到月半”的俗谚。
旧礼教的婚俗,连宋朝理学家朱熹都认为太繁,他在任漳州知府时,提倡把原有六礼合并为三礼,即求庚、行聘、亲迎。其他大定、小定、送袄等可合并附行,民间称便。但也还有很多人蓄意铺张,仍然按照六礼进行。
封建时代漳浦的士大夫们着力宣扬“忠、考、廉、节”的所谓“漳浦精神”,列出历史上的代表人物(忠:黄道周、孝:高东溪、廉:张若仲、节:刘庭蕙之母)作为效法的表率。其中“节”一项宣扬的是“烈女不嫁二夫”的封建妇德,建“烈女祠”来表彰节妇,县志以很多篇幅为烈女立传。在夫权、族权。神权的重压下,不知有多少寡妇(有的还没有过门)葬送了终生幸福。刘庭蕙的母亲不过是千万人中的一个。她还是在养尊处优的生活条件下守的节,比起无依无靠饥寒度过悽凉一生的穷苦寡妇来,其节烈精神简直如小巫之见大巫,只是由于儿子做了官,奏请御赐旌表,便成为代表人物,而她的贞节坊上“月夜啼乌”的凄厉名句后面,不知隐藏着多少无名节妇的伤心泪。
五、丧事
漳浦从前风气闭塞,有很多陋俗,尤其办理丧事,有许多弊例:一、大事铺张,富贵之家,吊丧者纷来沓至,多有赠仪。最苦的是一般人家,办丧事本是一件痛苦事,却有人幸灾乐祸地来凑热闹,有时全村的人不论男女都跑到丧家吃饭,一直到丧葬完毕,就是俗语所说的“全社塞灶门”,丧家还要办酒席款待帮忙的人,就是帮闲的也可以混迹其间。(只有那无子无女无财产的孤老死后才让人替他雇两名或四名“土工”抬出草草埋葬,被认为是最“歹命”的)。一般人家办丧事都要负债,只有用“父母债快还”这句俗语来自我安慰。二、择日:尸体要经大敛、小敛而后入棺。入棺、成服、卒哭、出殡都要择吉日良辰,宁愿将尸棺留在家中,迁延时日,多加糜费,也不肯从权处理。对这种风俗,连成书于封建时代的《漳浦县志》也斥其“悖理殊甚”。三、“风水”:富家惑于“风水”,就是一般人家也多有郑重其事的,不惜用巨额款项求购“吉穴”,望能庇荫子孙,有不得“吉穴”不罢休,宁愿贮棺待葬,也有葬而复迁的。“风水”冲突事件层出不穷,有的甚至酿成“家变”(械斗)。对此,就是清朝的学者(雍正朝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漳浦人蔡世远也加以驳斥,他在《丧葬考惑》一文中说:“……其至愚者,则阴谋横据,相争相夺,以为福在是矣,不知其为祸基也”。又说:“此乃后来术家欲藉此挟凡为子孙者不敢不遵信而延请之,阴以诱其厚利,阳以得其奉迎,不知其为害之深,至死者不归土,而生者不得相和,皆此说误之也”。在科学知识还未发达的清初,有织之士对这种陋习也抱否定态度,而在这科学昌明的现代,竟然还有人复古。所以移风易俗现在仍然是提倡精神文明当中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四、闹丧:出嫁后的妇女死后在入葬前要请她娘家的长辈来为她的棺材“封钉”,否则娘家便要大兴问罪之师,用意在验明有无冤死,这在旧时代具有防止妇女受虐待致死的用意,因为那时政府不能保障妇女权利,只有由“外家”来维护已婚妇女的安全,这个办法可说是民间一大创造,但后来发展成为“外家”勒索死者亲属的手段,有的竟乘人之丧无理取闹。现在已是用法律保障人身的时代,而此风在个别地区还有待革除。
六、迷信鬼神
从前,漳浦迷信鬼神之风很盛,庙宇林立,香烟不断。全县性的迎神赛会有王公生、妈祖生、佛祖生、帝爷生、三界公生、土地公生等等,这些“神明”有的要“生”了一个多月至几个月,各乡村轮流为它作寿诞,各村亲戚互送供品糕馃,互请看戏,吃吃喝喝,糜费很大。解放前有很多农民就是为做演戏酬神借了高利贷被母滚利、利滚母,弄得破家荡产的。
迷信之风给巫婆神汉以可乘之机,有“红姨”(或称“师母”)可使活人与鬼魂相见的。有“铜身”(神汉)能使神灵附在他身上作法行医派药的,流弊所及,误死人命。
漳浦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还很多,这里所举只是一些比较显著的。对于一些比较好的风尚已受到发扬和改进,如欢度春节、元宵灯会、清明扫墓、端午龙舟竞渡、中秋节赏月、重九登高等。对于一些劣风陋习,如封迷建信等,在建设精神文明的推动下,虽已有很大程度的收敛,但几干年来的流毒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尽除,宣传与制止还是长期不可忽视的工作。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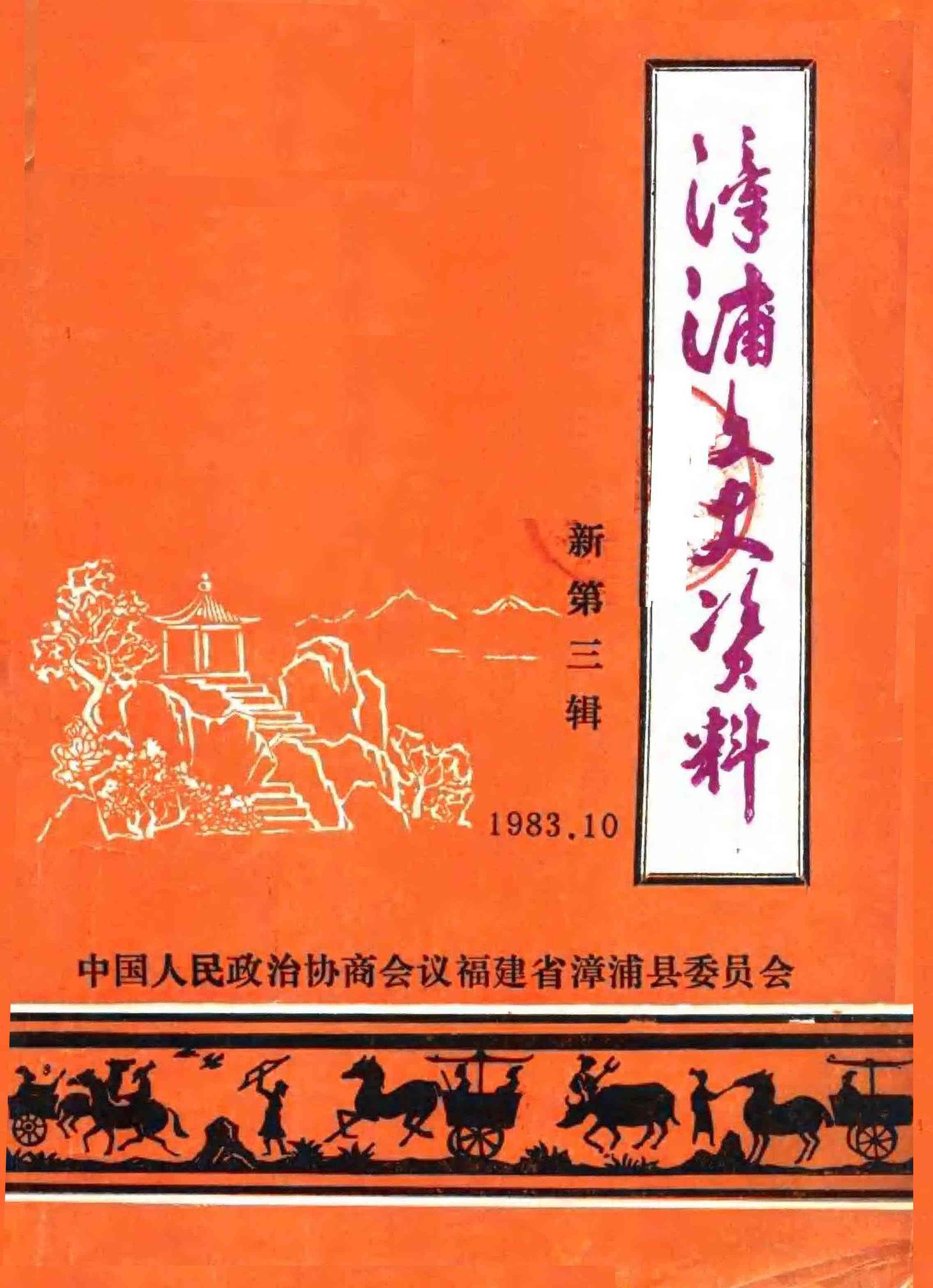
相关地名
漳浦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