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我的母亲!
| 内容出处: | 《华安文史资料第十四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30000317 |
| 颗粒名称: | 我的家乡,我的母亲! |
| 分类号: | K825 |
| 页数: | 11 |
| 页码: | 10-20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作者在印尼的成长经历及其回国后与家人团聚的情景。 |
| 关键词: | 汤晓丹 事迹 成长经历 |
内容
1910年时,我出生地华安县仙都乡云山村里的壮年男子,常常把求生的希望寄托在飘洋过海上。我的父亲汤祥纯在我出生时就随家乡水客远航南洋群岛。他经过旅途的艰难跋涉,终于到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西爪哇。先是靠小商贩赚钱糊口,后来发展成为小商店的主人。
六岁那年,母亲林萌带我从家乡华安搭小木船顺流到浦南码头,然后改乘大木船到厦门。再从厦门搭大货轮到新加坡。
船靠新加坡码头以后,我虽然年幼,却想上岸去看狮子城的热带风光。母亲怕我走失,不让我上去。其他几个同船的水客有的也是第一次远行,也不敢下船。轮船在新加坡整整停留了二天才向南开驶。在又闷又热的船舱里煎熬了四天四夜,第五天轮船才在爪哇的首都巴城现叫雅加达海港停靠,这样,我们结束了整整一个月的海上生活。上岸后还要坐一天火车到茂物市。在火车中向窗外望才使我领略到热带风光的魅力。这是与我国不同的整年常绿的国家。特别是从茂物市换坐马车到郊区的基亚维镇,沿途看见许多马来人在椰树林前的农田里干活,简直使我目迷
五色。
基亚维镇公路边,父亲开了一家杂货铺,他见到我们后,大吃一惊,脸上露出非常尴尬的表情。原来他已与陈姓侨商的女儿又结一次婚,母亲虽然很温顺,但是个有志气的人,她决定在父亲杂货铺附近找一座当地竹编木屋另立门户。她还托人买来一架白式缝衣机,开始为附近的马来人做衣服,赚些贴补家用。
父亲因为家里穷,少年时就没有受多少教育,所以他看我还算伶俐,有意培养我成为有文化的人。没有多久就把我和清炎哥哥(因如夫人陈氏不会生,她收养了一个过继儿子)送到茂物市一家基督教办的小学念书。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热火朝天。但荷属东印度政府并没有参战。所以市面非常繁荣,父亲的杂货店买卖也不错。母亲的成衣生意更是忙不过来,后来还雇了一位当地女缝工帮助她工作。父亲的如夫人陈氏看我比清炎哥伶俐逐渐表示好感。父亲在茂物市侨商中本来也很受尊敬,有新从家乡来的亲朋好友,他都乐意接待并给介绍工作。母亲后来又给他生了我的弟弟汤 承,家庭虽不怎么富裕,但也算得上是幸福的。因此几年间全家还能相安无事。但好景不长。
一天深夜,母亲把我从梦中摇醒。听见铺子里传来打闹声,逃跑的脚步声。我吓得直抖擞。天亮以后,我看见陈氏妈妈鼻青脸肿,怪可怜的样子。从此,杂货铺不开门,父亲再没有露过面了。人们都议论着我的父亲失踪的新闻。
大约过了半年,一位陌生入到我家,他不知和母亲说了些什么。母亲开始处理家里的衣物。在异国六年,坛坛罐罐也不少。卖的卖送的送。一架缝衣机像宝贝一样带回家乡。
归国路上,母亲对我说,父亲並没有寻短见,他是为躲赌债,悄悄回家乡了。后来我想并不是那么简单,如夫人陈氏年龄比父亲大,遇事不如意,则整天吵闹,何况她收养的义子清炎哥哥也弃她而去。整个家笼罩在黑云中,使父亲不得安宁,这也是个原因。但我和母亲带弟弟能够回祖国,却使我高兴。恨不得马上飞回唐山(华侨叫祖国为唐山)。
家乡虽然还是那么穷,但家乡的一草一木比起西爪哇来,亲切的多。它比我离开时更青翠更富生机。父亲却不象我在西爪哇时看到的样子。回国不到两年,身体急剧衰退,经常重病在床。面黄肌瘦,样子有些可怕。不久他便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村里有家老式家具小作坊,生意很好。有一天老板突然到我家,要我用金粉在新上漆的柜子上画点花鸟。我母亲连忙谢绝。她说,小孩在纸上涂涂画画可以,画家具可不行。
老板笑了,再三解释,一定要拉着我走。
第一次在漆柜上画,我用的金粉太多,很不容易干,以后才慢慢掌握了方法,胆子大了技艺也提高了,箱子盖上,桌子面上,大小漆具都画过。老板给了我的工钱,我如数交母亲。
我们村的汤氏祠堂里有族人们捐助的公积金,族长们见我年幼好学,决定从公积金中拨款资助我去厦门求学。
1926年的夏天,我带着心头的无限喜悦离开了云山村,路边小草迎风飘摇,仿佛在向我弯腰表示祝贺。
到了厦门集美师范学校去报名时,才知道已经截止两天了。我只好去集美农林专科学校报名,那里还有名额。
集美农林专科学校也是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独资兴办的。校址在天马山山麓。离集美还有一段路程。
学校开办才一年多,教室和宿舍都是新建的。除有课堂,食堂,礼堂,球场,图书室和浴室外,还有大片农场、畜牧场、苗圃果园。全校同学共一百五十人左右,按专业分成几个班上课。教授大都留美留日专家,经常让学生进行科学实验活动。尽管我们学习很紧张,我的内心所向却不太对劲。所以稍有空暇就喜欢以秃笔绘人与鬼斗。
比我早一年进校的同学中有个叫赖羽朋的是个闽西人。他对我很好,常常主动借些文艺书籍给我看,又拉着我跟他一起参加秘密宣传工作。有时写标语,有时画漫画。内容都是针对时弊而发。
我画的一幅漫画《布尔乔亚》,表现一位劳动青年用力高举铁锤,猛砸一块顽石。石头上写“布尔乔亚”四个字。赖羽朋要我把该画寄上海《大众文艺》发表。大约过了两个月,我接到《大众文艺》社的回信,说稿件已被采用,使我非常高兴。
1927年,中国的政治风云急剧变化。进步与落后的斗争也十分尖锐。赖羽朋领着几个进步同学宣传“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思想。我们常常三五成队到校外贴标语。
突然,有几个当地政客到学校指责我们破坏社会治安。赖羽朋带头与他们辩论,事情越闹越僵,最后以校方公布开除了几个学生平息政客的怒气。我也是被开除中的一个。
族长们纷纷到我家指责我母亲教子无方。並且不问青红皂白停止了对我的经济援助。母亲哭哭啼啼跑到厦门把我拉回家。我受不了无理的指责和打击,重病了一年多。
既然我已被生活的激流冲向险滩,也只有铤而走险才是活路。我写了一封信给上海的《大众文艺》社求援。没有多久,就得到简单而诚恳的回信:如果人到上海,还是有办法可想。
母亲为我凑足了路费,添制了衣服,送我上路。他走着、哭着、叮嘱着……。
不料这次分别,竟成了永别,以后,我常常想回家乡看看母亲和弟弟们,一直找不到机会。
1990年10月,《汤晓丹艺术活动研讨会》在上海开幕,在我的家乡漳州闭幕,我才有幸实现了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故乡行的心愿。当我回到云山村时,许多往事又涌上了心头。记得那时我刚满19岁,带着重病未愈的虚弱身体和忐忑惶恐的复杂心情,跳上龙九江原头的木船。当我回头凝望华安土坡上的大榕树时,不知怎么,一股莫名的感伤之情揪着我的心,仿佛感到自己将是在黑海洋里行
船,随时都会碰到恶风险浪,随时都可能葬身鱼腹……。
我真不知道以后还会再见到这棵榕树么……。
我终于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浮沉挣扎,苦苦熬过了5个年头。其间,我曾无辜被租界巡捕房拘留,饱尝过白色恐怖下的铁窗生活;我曾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一·二八”事变中受到炮火袭击,死里逃生……。
所幸,我在当时地下党创办的《画刊》社工作,结识了一批真正的民族精英,如司徒慧敏、朱光、苏怡、沈西苓等好朋友,他们在经济上接济我,在事业上扶持我,使我能在万花筒般的现实社会中辨别伪善,引导我走进了电影创作队伍的行列,使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游子,能在3年之内成为电影导演。
记得1934年,我应邀赴香港拍片时,原想由上海启程后,绕道福建家乡,再去香港。终因片约缠身,未能实现愿望。
在香港求生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行互相竞争,互相倾轧……总之,为了生存,为了事业上站稳脚跟,我不得不昼夜不分,既劳力又劳心,奋斗再奋斗。
我除了导演《糊涂外父》、《金屋十二钗》等讽刺喜剧受到观众欢迎外,还导演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时势造英雄》、《小广东》、《民族的吼声》等影片,受到舆论界的赞扬。在这种情况下,回家乡常常是刹那间内心的闪现而已。
1941年12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珍珠港事变”,香港很快沦为孤岛,日军头子曾大摆宴席请香港名流吃
饭,我也是被邀请者之一。席间,他要求我导演宣扬日军入侵香港打败英军的影片《香港攻略》,我为了逃脱劫运,化装成难民离开了香港。本来想到福建家乡去躲藏起来。可是对早已沦陷在日本铁蹄下的家乡境况到底如何,我不敢冒昧行动。真是游子有家归不得啊!
整整化了一年多时同,我才从桂林辗转到了重庆。在重庆我导演了一部警官破获日本间谍机关的故事片《敢死警备队》,鞭打我仇恨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
抗日战争胜利了,我原想由重庆直接回家乡看看母亲,可是,那时交通工具多么难找啊!我千方百计筹到仅够旅费到上海。我到了上海后再写信回家乡,才知道母亲和三弟早在几年前死于霍乱瘟疫。在山沟偏僻落后的家乡,日军虽然没有能进去,但我最亲爱的母亲和三弟被凶猛的瘟疫所吞噬了。
愤怒和悲痛驱使我导演了《天堂春梦》和《苏风记》等来揭露和控诉当时社会的黑暗面。
那时,物价飞涨,我为生活,为拍片日夜操劳,自身难保之下,很少想起回家乡。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不仅解放了全中国,也使我得到了创作上的新生。我立誓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党和人民也给了我荣誉,多次被评为厂局先进,二次市劳模,一次全国先进……。在荣誉和重任面前,我认为努力创业就是家乡人民对我最真挚的期望。我很想有机会去漳州拍摄外景,可以公私两便去走一趟,可是机会太难了。
十年动乱,对我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我常常梦见回到儿时的家乡,和其他小孩一样,爬树、翻墙,甚至到我喜欢去看的民间画工在玉皇庙里绘壁画。醒来发现只是一场梦时,我悄悄流过泪。当时,我很绝望,我觉得这一辈子再不能回到家乡了。
1975年,我虽然被派到摄制组当顾问,可是我牢牢记住:你是控制使用,只能老老实实……,所以当有次到福建泉州找外景时,我心里真想提出到家乡去走一次,可是哪里敢啊!
去年夏天,当提议举办《汤晓丹电影艺术研讨会》活动的几位同志说起要去我的故乡时,我很希望能如愿。特别是我的家乡华安县的周力文书记的热心支持,算成全了我的这一心愿。
金色的10月,当我们乘坐的飞机抵达厦门机场时,负责接待的同志早已等候了。我们住的漳州宾馆,安静舒适。市各级领导在百忙中赶来与我们见了面。
在漳州,各界推选代表出席了研讨会。他们的发言,热情中肯,不仅分析了我所拍的影片的得失,而且根据观众的反映,举了许多生动的例子,真是有理有情,使我获益非浅。同行者中除最了解我的老厂长徐桑楚外,还有著名演员孙道临和秦怡,他们是家乡人民非常尊敬的表演艺术家。
61年前,别说我们的云山村是穷苦小山村,就是华安和漳州,也很落后。可是今天,当我看到驰名中外的合资企业漳州毛纺织厂生产的拉舍尔毛毯经过由原料到成品
的全自动化过程时,艳丽的毛毯闪发出光亮,象征着党所决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我的家乡带来了幸福。
我的家乡虽然盛产水果,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果园。这次,我们应邀去参观天宝十里香蕉园和香蕉市场,的确开了眼界。园外一条宽宽的公路,路旁铺面林立;据说都是个体户,承办供销业务,一片兴旺景象。再登高楼远眺100平方里翠绿的香蕉园一望无际,这么大的香蕉园可说是全国之最吧!
特别使我心潮起伏的,是我们在漳州和华安时与家乡亲人们在电影院的见面。我们在两次见面过程中,共到过7家电影院,每到一家影院,不仅场子里坐满了热情的观众,影院门口也挤满了人群。我们的车子还没有到影院门口,掌声就雷动了。热情的观众,围住我们,握手、签名……。一张张感情纯真的面孔,使我明白,他们是爱我们所摄制的影片的。这时,只有这时,我们才能真正心明眼亮,坚定我们的创作方向。
我们研讨会的高潮是在家乡驻军基地举行闭幕式时形成的。足足一个师的战士列队欢迎我们。5台摄象机,十几位摄影记者,闪光灯耀花了我们的眼,鞭炮声震动着我们的耳膜。部队首长陪我们看了战士们高难度而精彩的军事演习。如果我再能自由选择题材,再能自由进出摄影棚,我仍然会为我们的英雄战士唱赞歌的。解放40年来,我所导演的影片,三分之二都是歌颂人民解放军丰功伟绩的题材,我爱解放军,解放军也爱我们。我的研讨会,能在家乡举行闭幕式,是我最大的幸福,也是观众给我最高的奖励。
附:汤晓丹简历
汤晓丹男公历1910年、农历二月廿二日生。
籍贯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仙都乡云山村。
现居上海市淮海中路1039号61室。
电话4313048邮政编码200031。
政治面目中共党员
工作单位上海电影制片厂
职务原第一创作室主任兼导演。
原上海市政协委员
全国文联委员;中国影协理事。
上海影协名誉副主席。
经历
1929年到上海从事地下党办的画刊社工作。1932年进上海“天一影片公司”担任布景设计工作。翌年升任导演;导演了第一部戏曲片《白金龙》,后导文艺片《飞絮》,《飘零》。1934年至1943年在香港大观、南粤、南洋、艺华诸影片、影业公司担任编剧兼导演电影工作。早期导演了喜剧片《翻天覆地》,《胡涂外父》,警世片《金屋十二钗》,后导抗日影片《小广东》、《民族的吼声》等。香港沦陷后,拒绝日寇保道部命摄日军纪录片《香港攻略》而逃往广西桂林。观摩大后方抗日救亡艺术家和战区演剧
队的演出。
1944年至1946年在重庆参加抗旧救亡活动,并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导委员。导演了一部反日间谍影片《敢死警备队》。
1946年至1649年在上海为“中电”一场导演揭露时弊故事片《天堂春梦》;为国泰影业公司导演反映孤岛日伪黑暗统治《失去的爱情》。
解放后,在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曾导演名片《南征北战》(合导);《渡江侦察记》;《不夜城》;《红日》等。《渡江侦察记》曾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导演艺术一等奖。
文革后,经过拔乱反正、恢复党籍,被任命为上影厂第一创作室主任兼总导演。导演了革命故事片《傲蕾·一兰》、《南昌起义》,均获文化部颁发优秀影片奖。后受聘广州珠江电影厂导演革命历史故事《廖仲恺》,获得1984年第四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1955年,奉文化部电影局派往印度新德里参加该国举行的“电影座谈会”为代表。然后又在新德里奉命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在该地举行的亚洲国家和平会议。1985年,应西德雷伯尼文化交流协会邀请参加并观摩在柏林举行的亚洲艺术节。
建国后多次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等等。
六岁那年,母亲林萌带我从家乡华安搭小木船顺流到浦南码头,然后改乘大木船到厦门。再从厦门搭大货轮到新加坡。
船靠新加坡码头以后,我虽然年幼,却想上岸去看狮子城的热带风光。母亲怕我走失,不让我上去。其他几个同船的水客有的也是第一次远行,也不敢下船。轮船在新加坡整整停留了二天才向南开驶。在又闷又热的船舱里煎熬了四天四夜,第五天轮船才在爪哇的首都巴城现叫雅加达海港停靠,这样,我们结束了整整一个月的海上生活。上岸后还要坐一天火车到茂物市。在火车中向窗外望才使我领略到热带风光的魅力。这是与我国不同的整年常绿的国家。特别是从茂物市换坐马车到郊区的基亚维镇,沿途看见许多马来人在椰树林前的农田里干活,简直使我目迷
五色。
基亚维镇公路边,父亲开了一家杂货铺,他见到我们后,大吃一惊,脸上露出非常尴尬的表情。原来他已与陈姓侨商的女儿又结一次婚,母亲虽然很温顺,但是个有志气的人,她决定在父亲杂货铺附近找一座当地竹编木屋另立门户。她还托人买来一架白式缝衣机,开始为附近的马来人做衣服,赚些贴补家用。
父亲因为家里穷,少年时就没有受多少教育,所以他看我还算伶俐,有意培养我成为有文化的人。没有多久就把我和清炎哥哥(因如夫人陈氏不会生,她收养了一个过继儿子)送到茂物市一家基督教办的小学念书。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热火朝天。但荷属东印度政府并没有参战。所以市面非常繁荣,父亲的杂货店买卖也不错。母亲的成衣生意更是忙不过来,后来还雇了一位当地女缝工帮助她工作。父亲的如夫人陈氏看我比清炎哥伶俐逐渐表示好感。父亲在茂物市侨商中本来也很受尊敬,有新从家乡来的亲朋好友,他都乐意接待并给介绍工作。母亲后来又给他生了我的弟弟汤 承,家庭虽不怎么富裕,但也算得上是幸福的。因此几年间全家还能相安无事。但好景不长。
一天深夜,母亲把我从梦中摇醒。听见铺子里传来打闹声,逃跑的脚步声。我吓得直抖擞。天亮以后,我看见陈氏妈妈鼻青脸肿,怪可怜的样子。从此,杂货铺不开门,父亲再没有露过面了。人们都议论着我的父亲失踪的新闻。
大约过了半年,一位陌生入到我家,他不知和母亲说了些什么。母亲开始处理家里的衣物。在异国六年,坛坛罐罐也不少。卖的卖送的送。一架缝衣机像宝贝一样带回家乡。
归国路上,母亲对我说,父亲並没有寻短见,他是为躲赌债,悄悄回家乡了。后来我想并不是那么简单,如夫人陈氏年龄比父亲大,遇事不如意,则整天吵闹,何况她收养的义子清炎哥哥也弃她而去。整个家笼罩在黑云中,使父亲不得安宁,这也是个原因。但我和母亲带弟弟能够回祖国,却使我高兴。恨不得马上飞回唐山(华侨叫祖国为唐山)。
家乡虽然还是那么穷,但家乡的一草一木比起西爪哇来,亲切的多。它比我离开时更青翠更富生机。父亲却不象我在西爪哇时看到的样子。回国不到两年,身体急剧衰退,经常重病在床。面黄肌瘦,样子有些可怕。不久他便痛苦地离开了人世。
村里有家老式家具小作坊,生意很好。有一天老板突然到我家,要我用金粉在新上漆的柜子上画点花鸟。我母亲连忙谢绝。她说,小孩在纸上涂涂画画可以,画家具可不行。
老板笑了,再三解释,一定要拉着我走。
第一次在漆柜上画,我用的金粉太多,很不容易干,以后才慢慢掌握了方法,胆子大了技艺也提高了,箱子盖上,桌子面上,大小漆具都画过。老板给了我的工钱,我如数交母亲。
我们村的汤氏祠堂里有族人们捐助的公积金,族长们见我年幼好学,决定从公积金中拨款资助我去厦门求学。
1926年的夏天,我带着心头的无限喜悦离开了云山村,路边小草迎风飘摇,仿佛在向我弯腰表示祝贺。
到了厦门集美师范学校去报名时,才知道已经截止两天了。我只好去集美农林专科学校报名,那里还有名额。
集美农林专科学校也是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独资兴办的。校址在天马山山麓。离集美还有一段路程。
学校开办才一年多,教室和宿舍都是新建的。除有课堂,食堂,礼堂,球场,图书室和浴室外,还有大片农场、畜牧场、苗圃果园。全校同学共一百五十人左右,按专业分成几个班上课。教授大都留美留日专家,经常让学生进行科学实验活动。尽管我们学习很紧张,我的内心所向却不太对劲。所以稍有空暇就喜欢以秃笔绘人与鬼斗。
比我早一年进校的同学中有个叫赖羽朋的是个闽西人。他对我很好,常常主动借些文艺书籍给我看,又拉着我跟他一起参加秘密宣传工作。有时写标语,有时画漫画。内容都是针对时弊而发。
我画的一幅漫画《布尔乔亚》,表现一位劳动青年用力高举铁锤,猛砸一块顽石。石头上写“布尔乔亚”四个字。赖羽朋要我把该画寄上海《大众文艺》发表。大约过了两个月,我接到《大众文艺》社的回信,说稿件已被采用,使我非常高兴。
1927年,中国的政治风云急剧变化。进步与落后的斗争也十分尖锐。赖羽朋领着几个进步同学宣传“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思想。我们常常三五成队到校外贴标语。
突然,有几个当地政客到学校指责我们破坏社会治安。赖羽朋带头与他们辩论,事情越闹越僵,最后以校方公布开除了几个学生平息政客的怒气。我也是被开除中的一个。
族长们纷纷到我家指责我母亲教子无方。並且不问青红皂白停止了对我的经济援助。母亲哭哭啼啼跑到厦门把我拉回家。我受不了无理的指责和打击,重病了一年多。
既然我已被生活的激流冲向险滩,也只有铤而走险才是活路。我写了一封信给上海的《大众文艺》社求援。没有多久,就得到简单而诚恳的回信:如果人到上海,还是有办法可想。
母亲为我凑足了路费,添制了衣服,送我上路。他走着、哭着、叮嘱着……。
不料这次分别,竟成了永别,以后,我常常想回家乡看看母亲和弟弟们,一直找不到机会。
1990年10月,《汤晓丹艺术活动研讨会》在上海开幕,在我的家乡漳州闭幕,我才有幸实现了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故乡行的心愿。当我回到云山村时,许多往事又涌上了心头。记得那时我刚满19岁,带着重病未愈的虚弱身体和忐忑惶恐的复杂心情,跳上龙九江原头的木船。当我回头凝望华安土坡上的大榕树时,不知怎么,一股莫名的感伤之情揪着我的心,仿佛感到自己将是在黑海洋里行
船,随时都会碰到恶风险浪,随时都可能葬身鱼腹……。
我真不知道以后还会再见到这棵榕树么……。
我终于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浮沉挣扎,苦苦熬过了5个年头。其间,我曾无辜被租界巡捕房拘留,饱尝过白色恐怖下的铁窗生活;我曾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一·二八”事变中受到炮火袭击,死里逃生……。
所幸,我在当时地下党创办的《画刊》社工作,结识了一批真正的民族精英,如司徒慧敏、朱光、苏怡、沈西苓等好朋友,他们在经济上接济我,在事业上扶持我,使我能在万花筒般的现实社会中辨别伪善,引导我走进了电影创作队伍的行列,使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游子,能在3年之内成为电影导演。
记得1934年,我应邀赴香港拍片时,原想由上海启程后,绕道福建家乡,再去香港。终因片约缠身,未能实现愿望。
在香港求生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同行互相竞争,互相倾轧……总之,为了生存,为了事业上站稳脚跟,我不得不昼夜不分,既劳力又劳心,奋斗再奋斗。
我除了导演《糊涂外父》、《金屋十二钗》等讽刺喜剧受到观众欢迎外,还导演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时势造英雄》、《小广东》、《民族的吼声》等影片,受到舆论界的赞扬。在这种情况下,回家乡常常是刹那间内心的闪现而已。
1941年12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珍珠港事变”,香港很快沦为孤岛,日军头子曾大摆宴席请香港名流吃
饭,我也是被邀请者之一。席间,他要求我导演宣扬日军入侵香港打败英军的影片《香港攻略》,我为了逃脱劫运,化装成难民离开了香港。本来想到福建家乡去躲藏起来。可是对早已沦陷在日本铁蹄下的家乡境况到底如何,我不敢冒昧行动。真是游子有家归不得啊!
整整化了一年多时同,我才从桂林辗转到了重庆。在重庆我导演了一部警官破获日本间谍机关的故事片《敢死警备队》,鞭打我仇恨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
抗日战争胜利了,我原想由重庆直接回家乡看看母亲,可是,那时交通工具多么难找啊!我千方百计筹到仅够旅费到上海。我到了上海后再写信回家乡,才知道母亲和三弟早在几年前死于霍乱瘟疫。在山沟偏僻落后的家乡,日军虽然没有能进去,但我最亲爱的母亲和三弟被凶猛的瘟疫所吞噬了。
愤怒和悲痛驱使我导演了《天堂春梦》和《苏风记》等来揭露和控诉当时社会的黑暗面。
那时,物价飞涨,我为生活,为拍片日夜操劳,自身难保之下,很少想起回家乡。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不仅解放了全中国,也使我得到了创作上的新生。我立誓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党和人民也给了我荣誉,多次被评为厂局先进,二次市劳模,一次全国先进……。在荣誉和重任面前,我认为努力创业就是家乡人民对我最真挚的期望。我很想有机会去漳州拍摄外景,可以公私两便去走一趟,可是机会太难了。
十年动乱,对我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我常常梦见回到儿时的家乡,和其他小孩一样,爬树、翻墙,甚至到我喜欢去看的民间画工在玉皇庙里绘壁画。醒来发现只是一场梦时,我悄悄流过泪。当时,我很绝望,我觉得这一辈子再不能回到家乡了。
1975年,我虽然被派到摄制组当顾问,可是我牢牢记住:你是控制使用,只能老老实实……,所以当有次到福建泉州找外景时,我心里真想提出到家乡去走一次,可是哪里敢啊!
去年夏天,当提议举办《汤晓丹电影艺术研讨会》活动的几位同志说起要去我的故乡时,我很希望能如愿。特别是我的家乡华安县的周力文书记的热心支持,算成全了我的这一心愿。
金色的10月,当我们乘坐的飞机抵达厦门机场时,负责接待的同志早已等候了。我们住的漳州宾馆,安静舒适。市各级领导在百忙中赶来与我们见了面。
在漳州,各界推选代表出席了研讨会。他们的发言,热情中肯,不仅分析了我所拍的影片的得失,而且根据观众的反映,举了许多生动的例子,真是有理有情,使我获益非浅。同行者中除最了解我的老厂长徐桑楚外,还有著名演员孙道临和秦怡,他们是家乡人民非常尊敬的表演艺术家。
61年前,别说我们的云山村是穷苦小山村,就是华安和漳州,也很落后。可是今天,当我看到驰名中外的合资企业漳州毛纺织厂生产的拉舍尔毛毯经过由原料到成品
的全自动化过程时,艳丽的毛毯闪发出光亮,象征着党所决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我的家乡带来了幸福。
我的家乡虽然盛产水果,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果园。这次,我们应邀去参观天宝十里香蕉园和香蕉市场,的确开了眼界。园外一条宽宽的公路,路旁铺面林立;据说都是个体户,承办供销业务,一片兴旺景象。再登高楼远眺100平方里翠绿的香蕉园一望无际,这么大的香蕉园可说是全国之最吧!
特别使我心潮起伏的,是我们在漳州和华安时与家乡亲人们在电影院的见面。我们在两次见面过程中,共到过7家电影院,每到一家影院,不仅场子里坐满了热情的观众,影院门口也挤满了人群。我们的车子还没有到影院门口,掌声就雷动了。热情的观众,围住我们,握手、签名……。一张张感情纯真的面孔,使我明白,他们是爱我们所摄制的影片的。这时,只有这时,我们才能真正心明眼亮,坚定我们的创作方向。
我们研讨会的高潮是在家乡驻军基地举行闭幕式时形成的。足足一个师的战士列队欢迎我们。5台摄象机,十几位摄影记者,闪光灯耀花了我们的眼,鞭炮声震动着我们的耳膜。部队首长陪我们看了战士们高难度而精彩的军事演习。如果我再能自由选择题材,再能自由进出摄影棚,我仍然会为我们的英雄战士唱赞歌的。解放40年来,我所导演的影片,三分之二都是歌颂人民解放军丰功伟绩的题材,我爱解放军,解放军也爱我们。我的研讨会,能在家乡举行闭幕式,是我最大的幸福,也是观众给我最高的奖励。
附:汤晓丹简历
汤晓丹男公历1910年、农历二月廿二日生。
籍贯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仙都乡云山村。
现居上海市淮海中路1039号61室。
电话4313048邮政编码200031。
政治面目中共党员
工作单位上海电影制片厂
职务原第一创作室主任兼导演。
原上海市政协委员
全国文联委员;中国影协理事。
上海影协名誉副主席。
经历
1929年到上海从事地下党办的画刊社工作。1932年进上海“天一影片公司”担任布景设计工作。翌年升任导演;导演了第一部戏曲片《白金龙》,后导文艺片《飞絮》,《飘零》。1934年至1943年在香港大观、南粤、南洋、艺华诸影片、影业公司担任编剧兼导演电影工作。早期导演了喜剧片《翻天覆地》,《胡涂外父》,警世片《金屋十二钗》,后导抗日影片《小广东》、《民族的吼声》等。香港沦陷后,拒绝日寇保道部命摄日军纪录片《香港攻略》而逃往广西桂林。观摩大后方抗日救亡艺术家和战区演剧
队的演出。
1944年至1946年在重庆参加抗旧救亡活动,并在中国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导委员。导演了一部反日间谍影片《敢死警备队》。
1946年至1649年在上海为“中电”一场导演揭露时弊故事片《天堂春梦》;为国泰影业公司导演反映孤岛日伪黑暗统治《失去的爱情》。
解放后,在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曾导演名片《南征北战》(合导);《渡江侦察记》;《不夜城》;《红日》等。《渡江侦察记》曾获得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影片导演艺术一等奖。
文革后,经过拔乱反正、恢复党籍,被任命为上影厂第一创作室主任兼总导演。导演了革命故事片《傲蕾·一兰》、《南昌起义》,均获文化部颁发优秀影片奖。后受聘广州珠江电影厂导演革命历史故事《廖仲恺》,获得1984年第四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1955年,奉文化部电影局派往印度新德里参加该国举行的“电影座谈会”为代表。然后又在新德里奉命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在该地举行的亚洲国家和平会议。1985年,应西德雷伯尼文化交流协会邀请参加并观摩在柏林举行的亚洲艺术节。
建国后多次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等等。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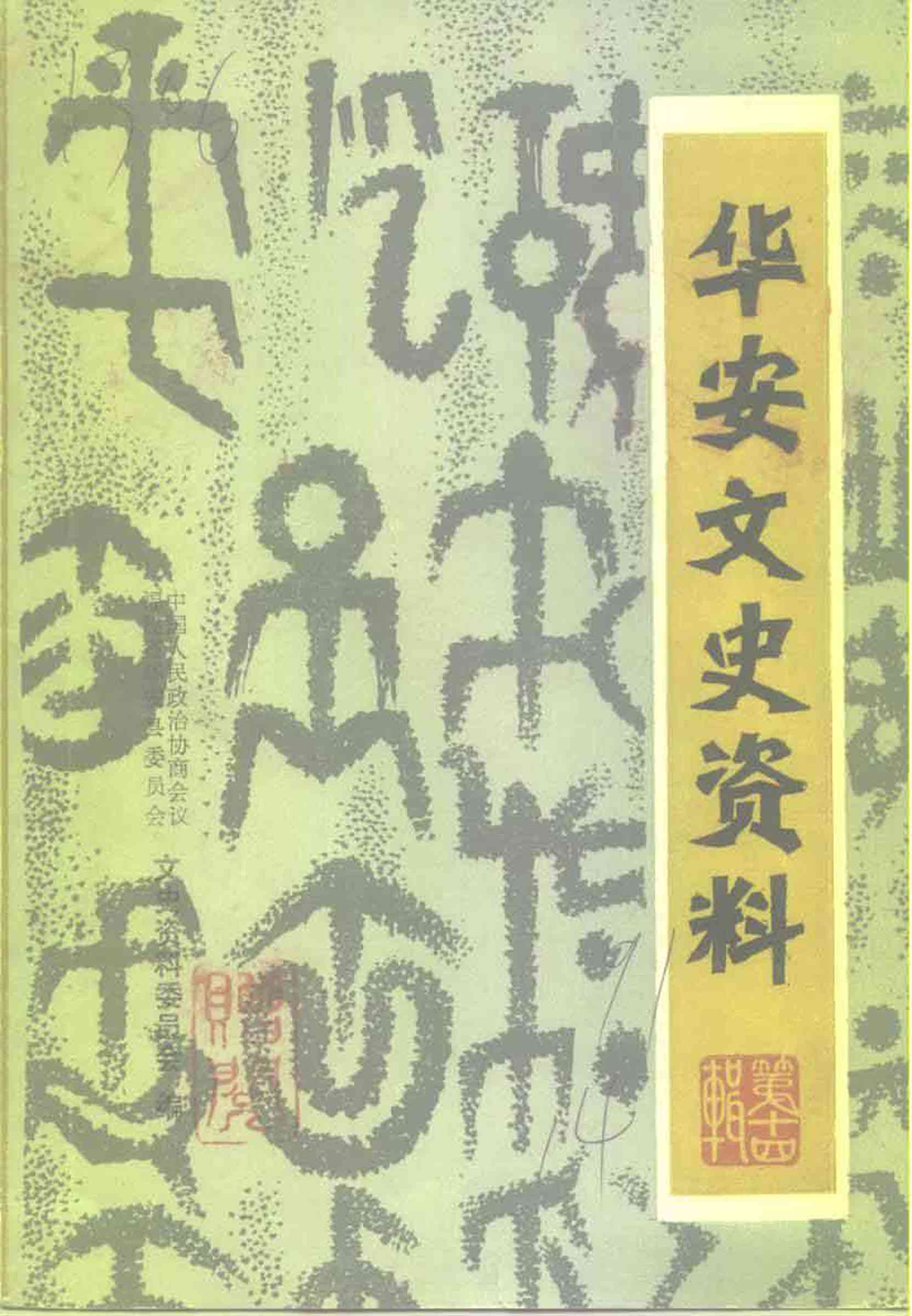
相关地名
华安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