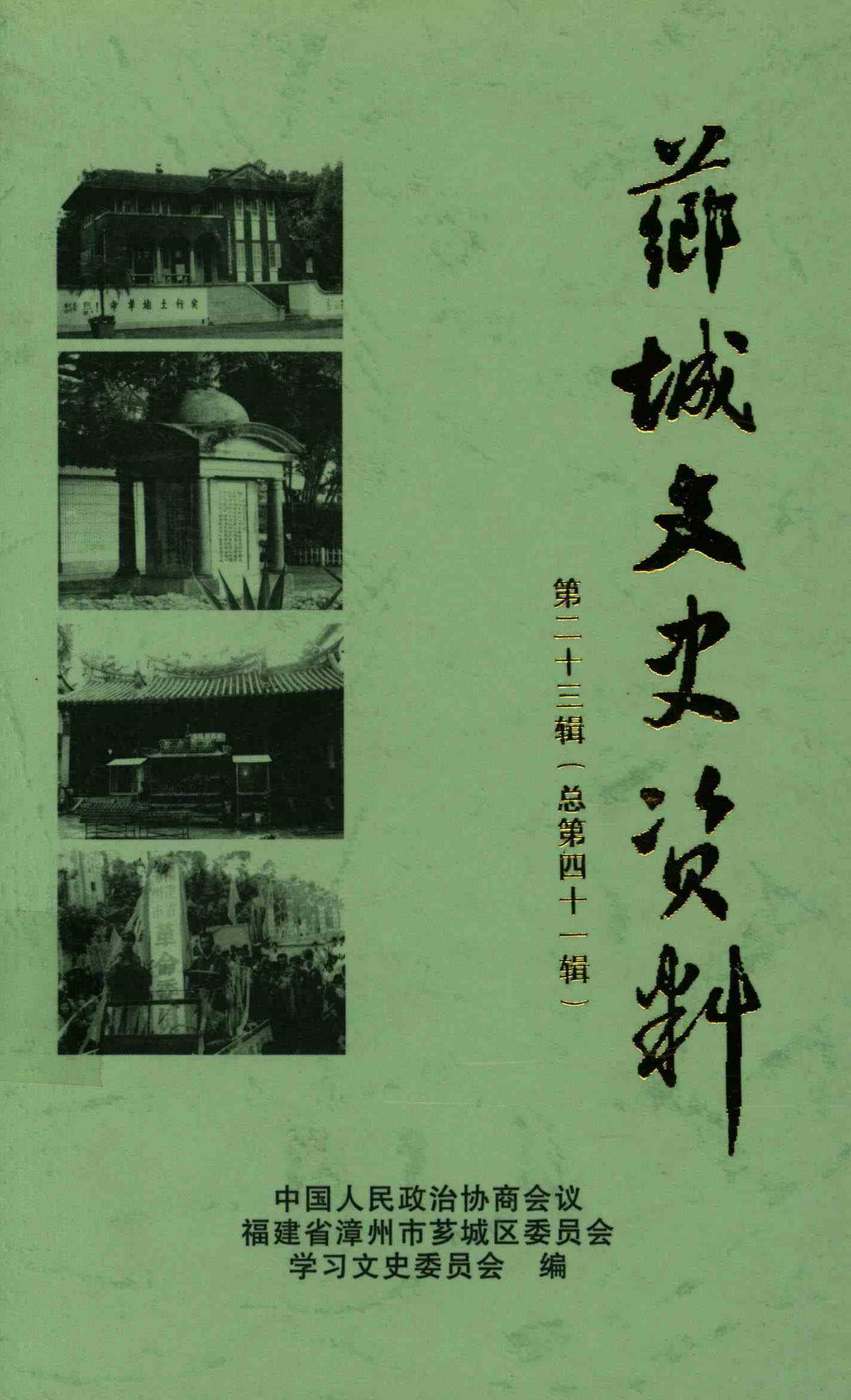漳州岳口街忆事
| 内容出处: | 《芗城文史资料》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20005792 |
| 颗粒名称: | 漳州岳口街忆事 |
| 分类号: | K250.657 |
| 页数: | 10 |
| 页码: | 227-236 |
| 摘要: | 民国后期,社会不安定,经济不发展,人民生活大多数都很困苦。特别是抗战期间,底层百姓苦难不用说,生活稍好过的人也免不了受灾受难。因此,匪盗四起,岳口街就发生过几起匪盗绑架事件,轰动一时的漳州商会会长被绑架就是其中一例(后获救)。还有一起绑架案,说起来有些传奇色彩,但因当事人一直缄口不言,多年来一直鲜为人知,直到很久以后才有断言片语传出,经过老一辈人口中的综合、补充,这个事件才渐渐浮出水面。原来,政府当局以政治压力强迫百姓接受,企图起死回生,挽救经济危机,宣布“银圆券”不得废弃不用。 |
| 关键词: | 岳口街 漳州 |
内容
一、岳口街的绑架案
民国后期,社会不安定,经济不发展,人民生活大多数都很困苦。特别是抗战期间,底层百姓苦难不用说,生活稍好过的人也免不了受灾受难。因此,匪盗四起,岳口街就发生过几起匪盗绑架事件,轰动一时的漳州商会会长被绑架就是其中一例(后获救)。还有一起绑架案,说起来有些传奇色彩,但因当事人一直缄口不言,多年来一直鲜为人知,直到很久以后才有断言片语传出,经过老一辈人口中的综合、补充,这个事件才渐渐浮出水面。
事情还得从漳州临解放的前几个月说起。
抗战胜利后,政府发行“法币”流通,由于时局不稳,钞票一再贬值,起初市场拒收角币,不久买卖便以五元面额起算,再不久便是一百元面值才起算,无形中已经贬值二十倍。隔年又贬值,连一千元面额的法币也无人敢收,社会经济濒临崩溃。当局妄图挽救经济危机,印发“金圆券”以取代法币,大面额纸币在市场流通,致使物价暴涨,当权者从中榨取民脂民膏,老百姓生活窘迫。不到几个月,“金圆券”币值犹如降落伞,时刻在降,而且一降到底,最后几乎变成废纸,老百姓只能在心里滴血而毫无办法。当局又改发行“银圆券”,五亿“金圆券”折合一元“银圆券”。不久“银圆券”也贬值,往往是上午一张“银圆券”能买一斤大米,到下午就只能买一盒火柴或一条油炸粿了。百姓不愿使用,便改用实物或金子交易,这样,“金圆券”、“银圆券”就被百姓当废纸,连垃圾一起扫地出门。
话说回来,岳口街黄某和大家一样,生活很困难,所以有时出门捡枯枝、废纸当柴禾烧饭。那一天他又挑着空火炭笼去捡破烂废纸。他有一个好习惯,遵古训“敬惜字纸”,凡捡到带有文字的纸张不敢随便糟蹋。这一天他捡到许多废纸回来,其中有很多被人丢弃的“金圆券”、“银圆券”,便将其置于灶间。
合当好运来临。隔两天,从城内传来话说:“银圆券”恢复使用!原来,政府当局以政治压力强迫百姓接受,企图起死回生,挽救经济危机,宣布“银圆券”不得废弃不用。这无疑是一针强心剂,驻漳军队刘兵团士兵手中的军饷都是纸币,赶紧强行向百姓购买货物,故意用大面额钞票买点东西强行找回大把铜板或银毫,老百姓只能接受而毫无办法,促使“银圆券”又在市场通行。黄某闻听此事,连忙跑到灶间倒出火炭笼中的杂纸,竟然还有半笼“银圆券”,一家人笑得合不拢嘴。他立即把这些钞票换成实物,购置产业,开起“寿金店”来,真是一夜暴富的典型,一时传为趣谈。
但是好景不常,黄某即遭绑架,“银圆券”让他成了富翁,也让他吃了苦头。
据我祖父说,他被释放回来后,浑身伤痛,血污满面,衣冠褴褛,边哭边诉说这事的经过。那是东乡某村做“普渡”,乡亲请他去作客,留他吃饭喝酒又看社戏,直到深夜才动身回去。走到港桥上,黑暗中忽然从桥下窜出三四条黑影来,亮出凶器来逼着他,将他反绑起来,推往林子中去。他知道遇到土匪了,心里紧张得要命,只好乖乖跟着走,走了好一阵,被关在某村一间被废弃的猪圈里,动弹不得,还挨了不少棍打,只好同意土匪提出的赎人条件。最后通过中间人给了几百块大洋才算了事。此事他不让家属外传,唯恐再糟劫难,因而外界不得其详,幸好不久漳州解放,终得平安无事。
注:1、此文祖父口传,应为真实,其寿金店(在东廓宫)字号好像是“中兴”,或“吉记”,因年代久远,让忆模糊不敢肯定。
2、“商会会长”指蔡竹禅,官园人,属岳口街。
二、石碑坊下的斗戏
民国时期,岳口街辖内的街道不过才一里多路,街面便立着三座石牌坊,一座是明朝建的,两座是清朝建的;还有五、六座庙宇;东吴第一宫(主祀保生大帝)、观音亭、朝天坊(玉皇上帝)、东岳庙(阎罗天子)、德进庙(谢玄元帅)等。每座庙的正对面是一条小巷,与街路成丁字街(漳州古时城市规划凡是丁字街处必定是庙宇,极少是民居),这几条小巷内也各有一座神庙。御史巷内有陈氏家庙,布店巷内有王爷庙,后郊巷有关帝庙,诗馆顶巷有王公庙,葫芦潭巷有水阁庙,马公庙巷有马公爷庙。庙宇分布之密度可谓盖倒漳州城,而且东岳庙在清朝以前据说是全国八大岳庙之一,规模庞大,气势恢宏。这里的民居是一百五十年前的“长毛反”烧杀过后重建的,设有太大的改观,门前的骑楼是民国二十年进行城市改造时修建的。走进岳口街,就像走进晚清的年代,冷不防会有道士的铃铛声,和尚的诵经声钻进你的耳朵。
因为庙多,供奉的神明多,做“闹热”的日子也就多。你算一算,每尊神都有出生、得道、升天三个吉日,每座庙又不止供奉一尊神,这样说来,一年到头各间庙里都是香烟袅袅,金炉熊熊,鞭炮轰轰,酬神戏更是接连着上演,煞是热闹不停。虽然许多次战乱的冲击,风雨的洗刷,牌坊依旧高耸入云,神庙仍然香火旺盛,而百姓则过着“悠闲”的日子,倒也乐在其中。
小时候的我就这样浸淫在这种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多少都知道一些神鬼故事,也略懂一些“戏文”内容。有一年不知什么日子,岳口街又有两尊神过生日,于是两处的会首(或老家长)便各自命人在两座牌坊下搭起戏台来。这戏台的基础是用十几只空的石油铁桶连在一起,铺上木板,竖起木柱,再盖上竹篷,挂上横幅布条(戏班名称),台后再张起布景,简陋的戏台就搭成了。孩子们见到这情景,早已心猿意马,无心读书,盼望天早点黑下来,赶紧回家吃晚饭,好去占个近台前的位置,才能看得真。
白天,两座庙里早已香气浓浓,金纸灰飞扬,庙内庙前桌上已经摆着发粿、甜粿、米糕、面团、牲礼(鸡、鸭、条肉、鸡蛋)等都用红坦盘盛着,祈求神明保庇生财有道。人们来敬拜时,锣鼓一齐敲响八音同时鸣奏,气氛十分热闹。
到晚上,距离约100米的两座牌坊下的戏台上各亮起数盏“白火”(汽灯)把四周照得如同白昼,戏台上的锣鼓正猛烈地敲闹台,观众早已把戏台围着水泄不通,行人休想通过。台上按惯例先表演“跳加冠”,为吸引更多观众围到自己的戏台前来,两台人马都演出自己的拿手好戏,一出唱完紧接着又上一出剧目。这边的戏文赢得观众泪水直淌,那边激烈的武斗引得观众不断喝彩叫好;这边的戏老板见对方观众那样捧场,急得让后台也来个大闹台,旦角高亢的唱腔,嗲声嗲气地抛媚眼,把大部分观众又吸引过来了,老板喜得眉开眼笑;那边老板见自己有点招架不住,便心生一计,把《海底反》搬出来,水族的鱼兵蟹将齐上阵厮杀起来,更有穿着红兜兜的河蚌精上场亮相,蚌壳一开一合,旦角四肢暴露无遗,观众便如同潮水般地涌到这边来。两台戏越斗越激烈,直到深夜还互不认输,观众看了这边看那边,忙得不亦乐乎。都说:“暝尾(下半夜)出小旦,越晚越好看。”
夜深了,会首(家长)见两台戏还不肯歇下来,只好上台送额外的红包,两边的戏才停下来,观众才悻悻散去。
三、岳口街做“醮”记忆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人民欢欣鼓舞,民族精神大为振奋,人们努力工作,重振江山,社会经济很快就苏醒,生活慢慢好起来,大人掩不住喜悦的心情对我们小孩子说:“今年生意好做得很。”
大概在1945年底,恰逢轮到岳口街做“醮”,居民们准备乘着抗战胜利之东风,举行一次盛大的祀典,把抑制多年的激情进发出来,恢复民间风俗,振奋民族精神。
做醮有“清醮”、“王醮”两种,“清醮”祀玉皇上帝,“王醮”祀王爷公(乡村以王醮为多)。道教尊玉皇上帝为天上最高统治者,各路仙人神明皆臣服之,老百姓更为崇拜,故古时有曰:“南州重皇神。”(见《芗城区志》)
醮年的间隔时间有二年一醮,六年一醮,或十二年、二十年、最长的是六十年一醮,做醮祀期为三天,也有五天的,还有因建庙竣工后做庆典活动同时做醮的。
那一年十月的一天,岳口小学学生中午放学,走出校门,忽然觉得天空一片模糊黑暗,抬头一看,原来街道上空张起五色布来,从这边二楼屋檐拉到对面二楼屋檐,整条街道都被布蒙盖起来,难怪街道昏暗无光。听大人说这叫做“五色布不见天醮”,是很隆重的祀典。
因为隆重,所以复杂,因为复杂,所以隆重。
据有关书籍记载,做醮仪式、程序非常复杂、繁琐。首先是设祭坛、供奉“三清尊神”;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三清尊神”并排而坐,其前面才是玉皇上帝。接下来两侧是其他神明排座次,还安排斗灯点燃着。玉皇上帝前面还特地安排谢府元帅(谢玄)的神像。
在供桌上安排主香炉、花枝瓜果及牲醴。
祀典仪式正式开始是在第一天的凌晨,名日:“起醮”。几名资深道士身着道袍,带领几名道士在祭坛前背诵经文,跳舞踏步、剑指北斗、顶礼膜拜,接下来向天发出“左牒”,也即向几位主要神明发出请柬,请他们来参与祀典。这以后的几天里还有很多仪式和程序,天天诵经、膜拜等,不是一般人所知道和理解的,附近居民只知道天亮时赶快往庙里祭坛前去奉献牲醴,祈求玉帝护佑苍生、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过上好日子就够了。
奉献的牲醴,在古代是牛、羊、猪、曰“三牲”,“醴”是甜酒。后来取消牛这项,因为牛一生为人做出极大贡献,不忍滥宰,改为鱼、鸡、猪。粮食类第一项是发粿,寓意发达,还有甜粿,米糕、面类等。有的人供奉整个猪头,表示大礼。更有几户人家敬献整只生猪生羊,额上贴红福字,四脚套上金镯子,真是炫耀极了,这些贡品要一直摆到祀典结束才抬回家。当时岳下有一大户人家,自己设坛在门口骑楼下,供桌上也是生猪生羊,供桌边上放着两尊纸扎的神像,大概是财神爷和平安君,头部会转动,眼睛会左顾右盼,两只手会上下摆动,据说是里面装着“机关”(发条),桌上还有一部留声机,百合花状的大喇叭整天响着当时的流行歌和“北曲”,吸引了很多人来围观。
到晚上,旷地上早已搭起的戏棚上点燃着数支“白火”(汽灯),一时光芒四射。锣鼓笙管正奏得欢,观众把戏棚团团围住,伸长脖子看,台上文戏武打变换轮流,一出紧跟一出,非常专注。年末北风“嗖嗖”地叫着,观众一边擤鼻涕,一边喊着“好”,有趣极了。
做醮的最后一天,祀典达到高潮。这一天经过充分准备的踩街队伍上街游行。会首披着红佩戴、头戴毡帽插金花在前面导行,香阵紧跟着龙旗虎旌猎猎飘扬,铜锣皮鼓呼呼作响,刀枪剑戟闪闪发光,鞭炮烟火砰砰爆发。队伍很长,浩浩荡荡的,有狮阵、龙阵、笙歌阵,有赤脚担金枣,担“尿鳖(夜壶)”、大鼓凉伞,还有高跷阵。这高跷阵有一二十副,每副高跷的两边都有人举着长棍护着高跷者,他伸开双臂抓住棍端,远看就像一条巨大的蜈蚣蜿蜒而行,甚是惊险。
最值得一看的是“棚仔艺”。每架“棚仔艺”都装饰得五彩缤纷,花团锦簇,上面一前一后坐着一男一女的小孩子,打扮成戏曲人物(据说起行前,四个大人抬着“棚仔艺”要从燃烧的寿金上跨过,这样路上小孩就不至于内急),每一架“棚仔艺”都是一出戏曲故事,如杨业娶亲(笔者幼时扮演过此角)、关公护嫂、陈三五娘、山伯英台等等,这些百姓熟悉的人物,人们百看不厌,百听不嫌,可以说是一次传统文化的大宣传、大检阅。
接下来是乘坐着玉帝和诸神明的辇轿,由年轻力壮的年轻人抬着,来回颠簸,威风凛凛。沿途有很多香案设在路旁,主人举香高烧。辇轿巡到哪里,哪里鞭炮声便更加轰动、锣鼓更加猛烈,一时烟雾弥漫天空,呛得人们直咳嗽,但情绪都很激动高昂。
此事已经过去几十年,印象模糊了。1985年,岳口街修建东狱庙德进庙并定为做醮年。正当会首、居民在积极筹备祀典事宜之时,忽然来了一位外国客人,要来观摩、研究。他是何许人也?
此君是美国学者丁荷生,为研究中国道教来闽南地区作为期三个月的旅行访问。在厦门大学访问时,得知漳州有此盛举,特地赶了过来,找到岳口街联系。经有关部门批准,同意让丁荷生对这次岳口街做醮活动的全过程进行采访、拍摄录像。丁荷生不辞辛苦,全过程跟踪三天,把全部活动都拍录下来(惜此次没有踩街,也没有“棚仔艺)。他后来写就一篇论文,名为《闽南地区两“醮”侧记》,发表于美国刊物,后由厦大学者马占斌翻译过来,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论文时把该篇收入其中,是研究漳州道教的文献。书中详细记述了做“清醮”从起醮到收尾的前前后后,具体细节都一一记述,甚至连设坛的方位也画出平面图来。
书中还把台湾做“清醮”情况和岳口街做“清醮”相比较,发现很多的做法都是同样的,因此可以断定这种风俗是从大陆(漳州)传过去的。
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永不可分割的。
民国后期,社会不安定,经济不发展,人民生活大多数都很困苦。特别是抗战期间,底层百姓苦难不用说,生活稍好过的人也免不了受灾受难。因此,匪盗四起,岳口街就发生过几起匪盗绑架事件,轰动一时的漳州商会会长被绑架就是其中一例(后获救)。还有一起绑架案,说起来有些传奇色彩,但因当事人一直缄口不言,多年来一直鲜为人知,直到很久以后才有断言片语传出,经过老一辈人口中的综合、补充,这个事件才渐渐浮出水面。
事情还得从漳州临解放的前几个月说起。
抗战胜利后,政府发行“法币”流通,由于时局不稳,钞票一再贬值,起初市场拒收角币,不久买卖便以五元面额起算,再不久便是一百元面值才起算,无形中已经贬值二十倍。隔年又贬值,连一千元面额的法币也无人敢收,社会经济濒临崩溃。当局妄图挽救经济危机,印发“金圆券”以取代法币,大面额纸币在市场流通,致使物价暴涨,当权者从中榨取民脂民膏,老百姓生活窘迫。不到几个月,“金圆券”币值犹如降落伞,时刻在降,而且一降到底,最后几乎变成废纸,老百姓只能在心里滴血而毫无办法。当局又改发行“银圆券”,五亿“金圆券”折合一元“银圆券”。不久“银圆券”也贬值,往往是上午一张“银圆券”能买一斤大米,到下午就只能买一盒火柴或一条油炸粿了。百姓不愿使用,便改用实物或金子交易,这样,“金圆券”、“银圆券”就被百姓当废纸,连垃圾一起扫地出门。
话说回来,岳口街黄某和大家一样,生活很困难,所以有时出门捡枯枝、废纸当柴禾烧饭。那一天他又挑着空火炭笼去捡破烂废纸。他有一个好习惯,遵古训“敬惜字纸”,凡捡到带有文字的纸张不敢随便糟蹋。这一天他捡到许多废纸回来,其中有很多被人丢弃的“金圆券”、“银圆券”,便将其置于灶间。
合当好运来临。隔两天,从城内传来话说:“银圆券”恢复使用!原来,政府当局以政治压力强迫百姓接受,企图起死回生,挽救经济危机,宣布“银圆券”不得废弃不用。这无疑是一针强心剂,驻漳军队刘兵团士兵手中的军饷都是纸币,赶紧强行向百姓购买货物,故意用大面额钞票买点东西强行找回大把铜板或银毫,老百姓只能接受而毫无办法,促使“银圆券”又在市场通行。黄某闻听此事,连忙跑到灶间倒出火炭笼中的杂纸,竟然还有半笼“银圆券”,一家人笑得合不拢嘴。他立即把这些钞票换成实物,购置产业,开起“寿金店”来,真是一夜暴富的典型,一时传为趣谈。
但是好景不常,黄某即遭绑架,“银圆券”让他成了富翁,也让他吃了苦头。
据我祖父说,他被释放回来后,浑身伤痛,血污满面,衣冠褴褛,边哭边诉说这事的经过。那是东乡某村做“普渡”,乡亲请他去作客,留他吃饭喝酒又看社戏,直到深夜才动身回去。走到港桥上,黑暗中忽然从桥下窜出三四条黑影来,亮出凶器来逼着他,将他反绑起来,推往林子中去。他知道遇到土匪了,心里紧张得要命,只好乖乖跟着走,走了好一阵,被关在某村一间被废弃的猪圈里,动弹不得,还挨了不少棍打,只好同意土匪提出的赎人条件。最后通过中间人给了几百块大洋才算了事。此事他不让家属外传,唯恐再糟劫难,因而外界不得其详,幸好不久漳州解放,终得平安无事。
注:1、此文祖父口传,应为真实,其寿金店(在东廓宫)字号好像是“中兴”,或“吉记”,因年代久远,让忆模糊不敢肯定。
2、“商会会长”指蔡竹禅,官园人,属岳口街。
二、石碑坊下的斗戏
民国时期,岳口街辖内的街道不过才一里多路,街面便立着三座石牌坊,一座是明朝建的,两座是清朝建的;还有五、六座庙宇;东吴第一宫(主祀保生大帝)、观音亭、朝天坊(玉皇上帝)、东岳庙(阎罗天子)、德进庙(谢玄元帅)等。每座庙的正对面是一条小巷,与街路成丁字街(漳州古时城市规划凡是丁字街处必定是庙宇,极少是民居),这几条小巷内也各有一座神庙。御史巷内有陈氏家庙,布店巷内有王爷庙,后郊巷有关帝庙,诗馆顶巷有王公庙,葫芦潭巷有水阁庙,马公庙巷有马公爷庙。庙宇分布之密度可谓盖倒漳州城,而且东岳庙在清朝以前据说是全国八大岳庙之一,规模庞大,气势恢宏。这里的民居是一百五十年前的“长毛反”烧杀过后重建的,设有太大的改观,门前的骑楼是民国二十年进行城市改造时修建的。走进岳口街,就像走进晚清的年代,冷不防会有道士的铃铛声,和尚的诵经声钻进你的耳朵。
因为庙多,供奉的神明多,做“闹热”的日子也就多。你算一算,每尊神都有出生、得道、升天三个吉日,每座庙又不止供奉一尊神,这样说来,一年到头各间庙里都是香烟袅袅,金炉熊熊,鞭炮轰轰,酬神戏更是接连着上演,煞是热闹不停。虽然许多次战乱的冲击,风雨的洗刷,牌坊依旧高耸入云,神庙仍然香火旺盛,而百姓则过着“悠闲”的日子,倒也乐在其中。
小时候的我就这样浸淫在这种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多少都知道一些神鬼故事,也略懂一些“戏文”内容。有一年不知什么日子,岳口街又有两尊神过生日,于是两处的会首(或老家长)便各自命人在两座牌坊下搭起戏台来。这戏台的基础是用十几只空的石油铁桶连在一起,铺上木板,竖起木柱,再盖上竹篷,挂上横幅布条(戏班名称),台后再张起布景,简陋的戏台就搭成了。孩子们见到这情景,早已心猿意马,无心读书,盼望天早点黑下来,赶紧回家吃晚饭,好去占个近台前的位置,才能看得真。
白天,两座庙里早已香气浓浓,金纸灰飞扬,庙内庙前桌上已经摆着发粿、甜粿、米糕、面团、牲礼(鸡、鸭、条肉、鸡蛋)等都用红坦盘盛着,祈求神明保庇生财有道。人们来敬拜时,锣鼓一齐敲响八音同时鸣奏,气氛十分热闹。
到晚上,距离约100米的两座牌坊下的戏台上各亮起数盏“白火”(汽灯)把四周照得如同白昼,戏台上的锣鼓正猛烈地敲闹台,观众早已把戏台围着水泄不通,行人休想通过。台上按惯例先表演“跳加冠”,为吸引更多观众围到自己的戏台前来,两台人马都演出自己的拿手好戏,一出唱完紧接着又上一出剧目。这边的戏文赢得观众泪水直淌,那边激烈的武斗引得观众不断喝彩叫好;这边的戏老板见对方观众那样捧场,急得让后台也来个大闹台,旦角高亢的唱腔,嗲声嗲气地抛媚眼,把大部分观众又吸引过来了,老板喜得眉开眼笑;那边老板见自己有点招架不住,便心生一计,把《海底反》搬出来,水族的鱼兵蟹将齐上阵厮杀起来,更有穿着红兜兜的河蚌精上场亮相,蚌壳一开一合,旦角四肢暴露无遗,观众便如同潮水般地涌到这边来。两台戏越斗越激烈,直到深夜还互不认输,观众看了这边看那边,忙得不亦乐乎。都说:“暝尾(下半夜)出小旦,越晚越好看。”
夜深了,会首(家长)见两台戏还不肯歇下来,只好上台送额外的红包,两边的戏才停下来,观众才悻悻散去。
三、岳口街做“醮”记忆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中国人民欢欣鼓舞,民族精神大为振奋,人们努力工作,重振江山,社会经济很快就苏醒,生活慢慢好起来,大人掩不住喜悦的心情对我们小孩子说:“今年生意好做得很。”
大概在1945年底,恰逢轮到岳口街做“醮”,居民们准备乘着抗战胜利之东风,举行一次盛大的祀典,把抑制多年的激情进发出来,恢复民间风俗,振奋民族精神。
做醮有“清醮”、“王醮”两种,“清醮”祀玉皇上帝,“王醮”祀王爷公(乡村以王醮为多)。道教尊玉皇上帝为天上最高统治者,各路仙人神明皆臣服之,老百姓更为崇拜,故古时有曰:“南州重皇神。”(见《芗城区志》)
醮年的间隔时间有二年一醮,六年一醮,或十二年、二十年、最长的是六十年一醮,做醮祀期为三天,也有五天的,还有因建庙竣工后做庆典活动同时做醮的。
那一年十月的一天,岳口小学学生中午放学,走出校门,忽然觉得天空一片模糊黑暗,抬头一看,原来街道上空张起五色布来,从这边二楼屋檐拉到对面二楼屋檐,整条街道都被布蒙盖起来,难怪街道昏暗无光。听大人说这叫做“五色布不见天醮”,是很隆重的祀典。
因为隆重,所以复杂,因为复杂,所以隆重。
据有关书籍记载,做醮仪式、程序非常复杂、繁琐。首先是设祭坛、供奉“三清尊神”;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三清尊神”并排而坐,其前面才是玉皇上帝。接下来两侧是其他神明排座次,还安排斗灯点燃着。玉皇上帝前面还特地安排谢府元帅(谢玄)的神像。
在供桌上安排主香炉、花枝瓜果及牲醴。
祀典仪式正式开始是在第一天的凌晨,名日:“起醮”。几名资深道士身着道袍,带领几名道士在祭坛前背诵经文,跳舞踏步、剑指北斗、顶礼膜拜,接下来向天发出“左牒”,也即向几位主要神明发出请柬,请他们来参与祀典。这以后的几天里还有很多仪式和程序,天天诵经、膜拜等,不是一般人所知道和理解的,附近居民只知道天亮时赶快往庙里祭坛前去奉献牲醴,祈求玉帝护佑苍生、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过上好日子就够了。
奉献的牲醴,在古代是牛、羊、猪、曰“三牲”,“醴”是甜酒。后来取消牛这项,因为牛一生为人做出极大贡献,不忍滥宰,改为鱼、鸡、猪。粮食类第一项是发粿,寓意发达,还有甜粿,米糕、面类等。有的人供奉整个猪头,表示大礼。更有几户人家敬献整只生猪生羊,额上贴红福字,四脚套上金镯子,真是炫耀极了,这些贡品要一直摆到祀典结束才抬回家。当时岳下有一大户人家,自己设坛在门口骑楼下,供桌上也是生猪生羊,供桌边上放着两尊纸扎的神像,大概是财神爷和平安君,头部会转动,眼睛会左顾右盼,两只手会上下摆动,据说是里面装着“机关”(发条),桌上还有一部留声机,百合花状的大喇叭整天响着当时的流行歌和“北曲”,吸引了很多人来围观。
到晚上,旷地上早已搭起的戏棚上点燃着数支“白火”(汽灯),一时光芒四射。锣鼓笙管正奏得欢,观众把戏棚团团围住,伸长脖子看,台上文戏武打变换轮流,一出紧跟一出,非常专注。年末北风“嗖嗖”地叫着,观众一边擤鼻涕,一边喊着“好”,有趣极了。
做醮的最后一天,祀典达到高潮。这一天经过充分准备的踩街队伍上街游行。会首披着红佩戴、头戴毡帽插金花在前面导行,香阵紧跟着龙旗虎旌猎猎飘扬,铜锣皮鼓呼呼作响,刀枪剑戟闪闪发光,鞭炮烟火砰砰爆发。队伍很长,浩浩荡荡的,有狮阵、龙阵、笙歌阵,有赤脚担金枣,担“尿鳖(夜壶)”、大鼓凉伞,还有高跷阵。这高跷阵有一二十副,每副高跷的两边都有人举着长棍护着高跷者,他伸开双臂抓住棍端,远看就像一条巨大的蜈蚣蜿蜒而行,甚是惊险。
最值得一看的是“棚仔艺”。每架“棚仔艺”都装饰得五彩缤纷,花团锦簇,上面一前一后坐着一男一女的小孩子,打扮成戏曲人物(据说起行前,四个大人抬着“棚仔艺”要从燃烧的寿金上跨过,这样路上小孩就不至于内急),每一架“棚仔艺”都是一出戏曲故事,如杨业娶亲(笔者幼时扮演过此角)、关公护嫂、陈三五娘、山伯英台等等,这些百姓熟悉的人物,人们百看不厌,百听不嫌,可以说是一次传统文化的大宣传、大检阅。
接下来是乘坐着玉帝和诸神明的辇轿,由年轻力壮的年轻人抬着,来回颠簸,威风凛凛。沿途有很多香案设在路旁,主人举香高烧。辇轿巡到哪里,哪里鞭炮声便更加轰动、锣鼓更加猛烈,一时烟雾弥漫天空,呛得人们直咳嗽,但情绪都很激动高昂。
此事已经过去几十年,印象模糊了。1985年,岳口街修建东狱庙德进庙并定为做醮年。正当会首、居民在积极筹备祀典事宜之时,忽然来了一位外国客人,要来观摩、研究。他是何许人也?
此君是美国学者丁荷生,为研究中国道教来闽南地区作为期三个月的旅行访问。在厦门大学访问时,得知漳州有此盛举,特地赶了过来,找到岳口街联系。经有关部门批准,同意让丁荷生对这次岳口街做醮活动的全过程进行采访、拍摄录像。丁荷生不辞辛苦,全过程跟踪三天,把全部活动都拍录下来(惜此次没有踩街,也没有“棚仔艺)。他后来写就一篇论文,名为《闽南地区两“醮”侧记》,发表于美国刊物,后由厦大学者马占斌翻译过来,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论文时把该篇收入其中,是研究漳州道教的文献。书中详细记述了做“清醮”从起醮到收尾的前前后后,具体细节都一一记述,甚至连设坛的方位也画出平面图来。
书中还把台湾做“清醮”情况和岳口街做“清醮”相比较,发现很多的做法都是同样的,因此可以断定这种风俗是从大陆(漳州)传过去的。
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永不可分割的。
相关人物
陈满根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