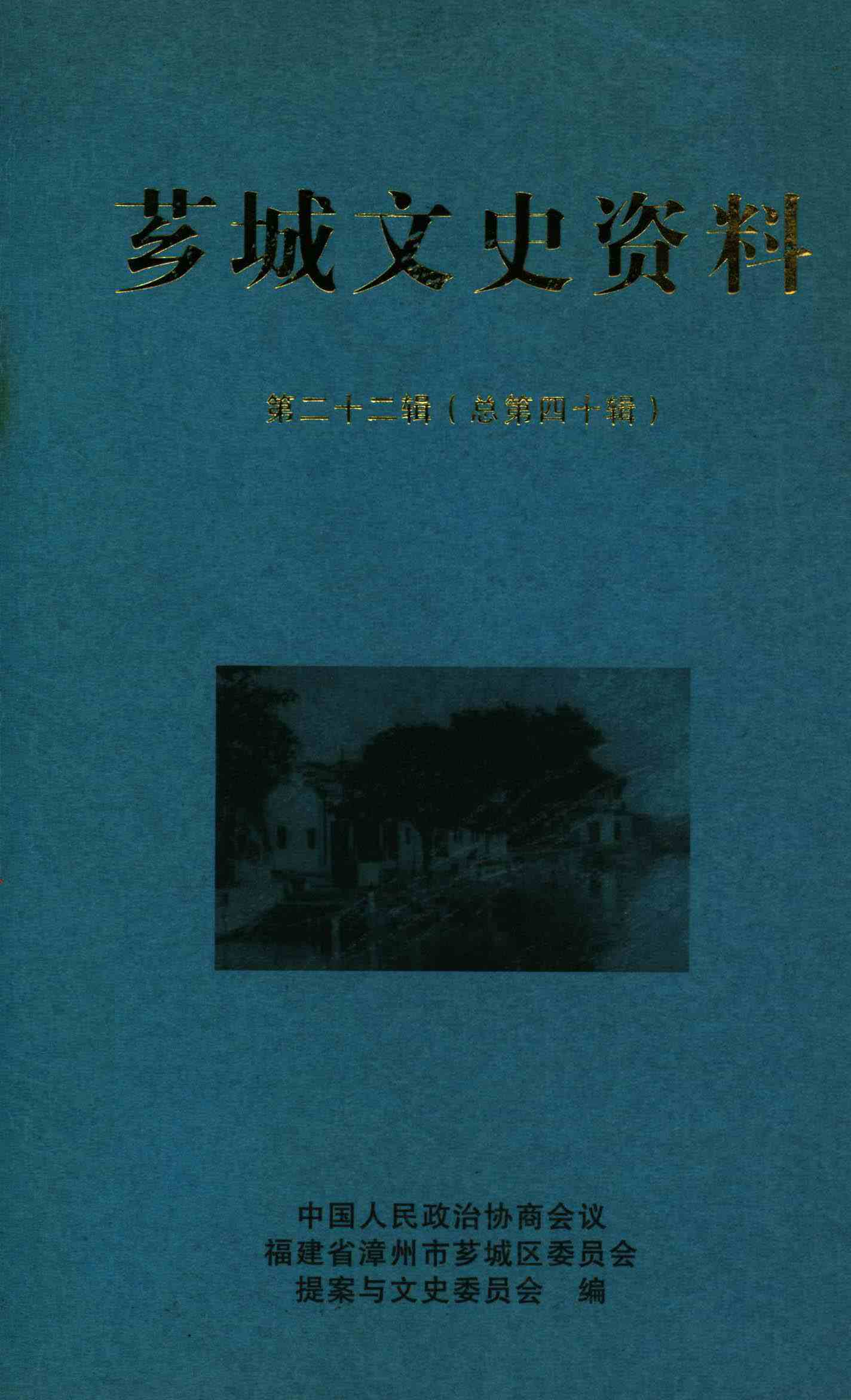《水仙花》发刊前后琐忆
| 内容出处: | 《芗城文史资料》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20005665 |
| 颗粒名称: | 《水仙花》发刊前后琐忆 |
| 分类号: | J892.7 |
| 页数: | 10 |
| 页码: | 144-153 |
| 摘要: |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经受文革的浩劫与摧残,漳州市的业余文艺作者多数沉浸在不解、悲愤、苦恼与气馁的情绪之中。陈布伦先生尽管饱受打击与迫害,但做为当时主持市文联工作的负责人,他并没有丢弃自己的责任。他极其耐心地听取大家的倾诉,不断地给大家热情的安慰与鼓舞。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黑暗已经过去,往前看,一切都会慢慢地好起来。1978年10月15日,“市群众文化工作座谈会”在市中山公园仰文楼上召开,布伦先生和时任市文化图书站负责人的陈玉池先生共同主持这次会议。经过热烈讨论,与会者一致要求文化部门从速批准市文联创办一个刊物,做为文艺作者发表与交流作品的园地。 |
| 关键词: | 漳州 水仙花 刊物 |
内容
(一)《水仙花》杂志的创刊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经受文革的浩劫与摧残,漳州市的业余文艺作者多数沉浸在不解、悲愤、苦恼与气馁的情绪之中。陈布伦先生尽管饱受打击与迫害,但做为当时主持市文联工作的负责人,他并没有丢弃自己的责任。他极其耐心地听取大家的倾诉,不断地给大家热情的安慰与鼓舞。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黑暗已经过去,往前看,一切都会慢慢地好起来。
1978年10月15日,“市群众文化工作座谈会”在市中山公园仰文楼上召开,布伦先生和时任市文化图书站负责人的陈玉池先生共同主持这次会议。会上宣读了中共漳州市委书记巩鸣鹏关于为所谓的“三蕾一鸿”(“春鸿”、“芗蕾”、“蓓蕾”和“春蕾文艺”等四个业余文艺小组)的平反意见,事后,中共漳州市委于1978.12.21以综字069号文件发出《关于对“三蕾一鸿”的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激发大家积极揭批“四人帮”热情。来自全市各地的业余文艺作者济济一堂,群情激愤,齐声谴责我市某些人炮制所谓“三蕾一鸿”案件迫害业余文艺作者的罪行;同时大家更互相鼓励,要克服余悸,消除顾虑,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再立新功。会议气氛热烈,效果良好,有的原来已砸烂钢笔,发誓洗手不再创作的作者也表示“我要提笔从头干”。
经过热烈讨论,与会者一致要求文化部门从速批准市文联创办一个刊物,做为文艺作者发表与交流作品的园地。至于刊名,开头有所争论,无论是主张叫《漳州文艺》或《芗江文艺》都受到多数人的反对;后来有人提出:以前我们许多业余刊物都自称为“花蕾”,现在经过严冬的考验,应该迎风绽放!于是将《水仙花》做为刊名的主张就脱颖而出,众望所归。我市文艺作者团结一心,展开双臂,共同迎接文艺界的“第二个春天”。
经过一番酝酿与筹备,《水仙花》文艺杂志终于在1979年元月15日问世。这期间适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因此首期刊物特地编发了“热烈欢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的一组稿件。因经费问题,这期刊物是油印本,与会者人手一册,少量赠送有关部门单位与领导,十分珍贵。从第二期起刊物才改为铅字印刷本。《水仙花》的出刊给漳州市的文化生活带来了新气象,为漳州市文艺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所以后来有人将其称为“漳州改革开放的报春花”。
(二)弥足珍贵的支持
《水仙花》杂志能顺利出刊,除依靠全体文艺作者团结一心共同努力外,时任市文化图书站负责人的陈玉池先生的大力支持也是功不可没的。1949年全国刚解放,年仅17岁的他就报名参加解放军,剿过匪,立过功;1958年复员后大部分时间在市文化部门工作,卓有成绩。其兄陈虹先生三十年代曾是我市革命团体“芗潮剧社”成员,文革初期在省文化厅厅长任上,曾横遭省级报刊点名进行所谓的批判。1976年1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幸去世,陈玉池先生积极带领单位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周总理的生平事迹和有关纪念文章,组织照片展览,宣传周总理的丰功伟绩,还曾遭到追查与迫害。他对业余作者极富感情,大家对他也特别敬重。业余作者要求创办《水仙花》杂志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他一次又一次跑文化局、财政局,要求拨给经费,在一时未能解决的情况下,他先从文化馆的有限经费中拨支,使《水仙花》得以顺利按时出刊。他的支持弥足珍贵,这是大家永远不会忘记的。
可惜的是,1979年5月间,陈玉池先生在市文联参加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7周年的座谈会后回到家中就病倒了,两个月后经检查确诊为晚期肝癌。在病中,他始终如一地关心《水仙花》杂志的编辑工作。做为联办单位的领导,布伦先生对他十分尊重,每期稿件编好后都会送去给他审阅。每次他都会一篇一篇地认真看,提出意见,有时还亲自动笔改一改,即使不得不住院了,在病榻上他也还是如此认真,他的负责任的精神令人感动!每次《水仙花》编委去探望他,他都特别高兴,神采飞扬的;尽管医生交代不要多说话,但他先是轻声后来却越说越激动,滔滔不绝,从文联机构的建立,人员的抽调到办公场所的修建等等,一直谈个不完。后来声音逐渐微弱,但却清清楚楚,他说:“茅盾先生给《水仙花》题签,我很高兴。这一期(指第四期)的封面很清秀,很大方。等我病好了,一定和你们一道,把《水仙花》办好。”
(三)《水仙花》的工作机制
《水仙花》创刊后,只有布伦先生一位还要负责搞好市文联的其他工作的“主持工作的专职人员”,刊物主要的编辑工作都由分散在各自工作岗位的业余作者兼任。当时我虽然年轻,但熟悉编务,布伦先生就很信任地把“把头关”的任务交给我。刊物所收到的稿件悉数交由我先行阅读、筛选;筛送结果我即及时向布伦先生汇报,经他同意后才把稿件分成小说、散文、诗歌和评论四类,分别交给各专业组的编委去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同意选用者还要负责文字润饰与加工;各组编委处理好稿件后再交给我,由我整理出初审目录后送布伦先生做最后定夺拍板。确定选用篇目后再由我约请美编插图、画版、送印刷厂排版,然后校对直至出刊后组织销售、发行。每两个月出刊一期,单排铅字就要十多天,校对要七、八遍,工作量满大的。我拿出当年搞业余刊物的干劲,学校一下班就往文联跑,当时只有一个心思:要尽自己之所能,和其他业余作者一道,帮助布伦先生把《水仙花》杂志办好,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执着与热爱,痛批“四人帮”对我们的诬蔑与迫害。后来布伦先生深有感慨地对我说:“有业余作者很形象地概括了我们两个人的作用,说我们两人就好比一个木桶的上下两条箍,上条箍可以使木桶不散,下条箍可以使木桶不漏。”能得到这样的评价说明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因此感到自豪。后来由于稿件越来越多,编务工作已非业余兼职所能应付得了,经请示上级批准,《水仙花》编辑部终于抽调黄海根同志来担任专职编委,我也才得以卸下所负担的各种编务工作。
四个专业组的编委都很尽职,负责处理的稿件都能按时按质按量交来,确保每期刊物都能准时付印,从未延误。特别是小说组王雄铮老先生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他博闻强记,学识渊博,思维敏捷,言辞犀利,无论是对事物还是对文章经常都能发表一些振聋发聩的独到见解,令人敬佩。只是有时他的见解过于超前让人不好接受,有时批评别人过于尖锐直率,使人下不了台,但是大家合作共事还是配合得相当默契。
1982年3月,《水仙花》杂志社正式组建编委会,特聘吴秋山、陈文和二位先生为顾问,陈布伦为主编,王雄铮为副主编,我和吴东南、青禾、黄金涛、黄海根、曾坚(美编)和熊韩江等人为编委。事前,布伦先生找我谈话,要我也出任副主编,我担心难以胜任没有同意。过后不久,布伦先生又找我说,根据广大读者的强烈要求,要创办一个民间文学小报做为《水仙花》的附刊,要我负责这项工作并担任主编。盛情难却,我只好鼓足勇气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并努力创造出新的成绩。
(四)乐为他人做嫁衣
《水仙花》的编委都意识到自已责任之重大,决心不负众望,尽职尽责,努力搞好所担负的工作。开头,由于“文革”的阴影尚未完全消除,业余作者的余悸还很严重,编委们就通过各自的交往渠道,广泛联系业余作者,做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鼓励他们重新拿起笔来写稿;许多老文艺作者文革后的第一篇新作岂不多是被《水仙花》编委软磨硬泡才得以问世的吗?对那些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年青作者的来稿,编委们同样怀着满腔热情的态度,认真地对待、负责任地处理,只要稍有可取之处,都会想方设法加工、修改,力争尽快加以发表。翻开当年刊物就不难发现,如今驰骋漳州文坛的青年才俊的处女作,有好多都是在《水仙花》杂志发表的。
来稿稍微多了一些以后,布伦先生针对外地的一些刊物大部分发表编辑者自己作品的做法说:“我们是不是能反其道而行之?希望编委们的作品、文章能尽量往外投稿,把《水仙花》的有限版面让给其他作者,让更多的作者能在《水仙花》刊物上展示才华、健康成长。”布伦先生的意见得到了全体编委的赞成与支持,少用自己的稿件成为编委们自觉遵守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这种自我约束、乐为他人做嫁衣的精神我觉得在当时十分难能可贵,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五)老一辈作家的无私支持
为了较快地解除文艺作者的思想顾虑,又有利于提高刊物的档次与质量,有的编委提议约请知名作家为《水仙花》杂志写稿,让他们言传身教做出示范,给广大作者、读者带来鼓舞。请名家写稿是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但只要是正确的意见,布伦先生都会虚心接受、认真执行。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直接写信,或托人与省作协主席郭风先生和著名诗人蔡其矫、舒婷、陈瑞统、黄寿褀、郑朝宗等名家联系,没想到都得到热烈响应。他们先后都给《水仙花》赐稿。布伦先生还通过民盟的关系,联系上时任上海辞书出版社高级编审、著名漳籍老作家耿庸先生和民盟中央常委、扬名国内外的大作家、大记者和老翻译家萧乾先生,并通过他们的帮助,先后约请了我国著名的作家、诗人冰心、胡风、艾芜、蹇先艾、顾工、秦似、雷石榆、冯英子、周俟松(许地山夫人)等名家陆续为刊物提供稿件。老作家们的支持极为有效地为广大文艺作者做出榜样,为刊物增光添彩,更多作者信心百倍拿起笔来踊跃投稿,刊物愈来愈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六)茅盾先生为《水仙花》杂志题签
1979年8、9月间,为组织稿件,我和陈布伦先生一起到市区瑞京路小巷的一所低矮的民房里去拜访民盟的老盟员、时在漳州师院任教的吴秋山老师。他很客气地端茶、让座。我们向他介绍了文革的际遇、《水仙花》的办刊宗旨和存在的困难,请他大力支持、赐稿。吴老师很健谈,一谈起办刊、写稿,他就打开话匣子,兴致勃勃地向我们介绍三十年代的时候,与茅盾、郑振铎等先生在上海共同组建“中国诗歌研究会”的活动情景。我们很高兴地获知他和茅盾先生曾合作共事过,就很感兴趣地问:“那你现在与茅盾先生还有联系吗?”他说:“有啊,茅盾先生对水仙花情有独钟,每年年底他都要写信让我捎上一些水仙花头,让他种养、清供。”我那时年轻,反应较快,我马上想到发表在《茅盾选集》的手迹说明茅盾先生的毛笔字是非常端庄秀丽的。我就见缝插针,大胆地开口:“吴老师,能不能请你在方便的时候,代我们请求茅盾先生为《水仙花》的刊名题签,这既是对我们办刊工作的大力支持,也是对水仙花的故乡漳州人民的极大鼓励。”吴老师闻言,不假思索立即回应说:“对,这个主意好!我明天就写信,我相信茅盾先生不会拒绝我的要求。”
果然,半个多月以后,吴秋山老师就打来电话报告喜讯:“茅盾先生的题签寄来了!”布伦先生立即通知我一起到吴老师家里去。吴老师笑得合不拢嘴,说:“我知道茅盾先生是非常重感情的人,但我也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就寄来题签。”我们共同端详、欣赏茅盾先生端庄、隽秀的墨宝,不能不为这位文学巨匠、一代宗师能如此关心、支持一个地方的小刊物而激动万分。题签用小宣纸写了多遍,让我们自行挑选,充分显示茅盾先生那种虚怀若谷,平等待人,处事周详的大家风苑。
拜别吴秋山老师之后,我们很快请了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当时分别在市工商银行和市侨芗剧场当美工的陈满根和方文和两位老师共同为《水仙花》1979年第4期设计一个封面,正式发表茅盾先生的题签。茅盾先生潇洒俊逸的题字配上清秀亮丽的水仙花图案使整个刊物显得雍容大方、光彩照人,为刊物增光添色,令人耳目一新。
我国文坛泰斗茅盾先生为《水仙花》刊名题签极大地鼓舞了我市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大家纷纷表示要以办好《水仙花》的实际行动来报答茅盾先生对刊物的厚爱与关怀。事后我们才知道,茅盾先生为县市一级的地方文艺刊物题签,这是破天荒的头一遭。难怪国家版本书库和北京、上海、福州等地图书馆闻讯后均陆续发来专函索取全套刊物存档、珍藏。可以说,茅盾先生为《水仙花》刊名题签,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市文化生活的一件盛事。
《水仙花》刊物完全靠自办发行。编委们提供文艺爱好者名单,其中有发行能力者则动员其代办发行,特别是市区及邻县业余作者及学校教师做了很大的努力。《水仙花》在三年多时间内共出版21期,发行量从起初每期几百本不断攀升,最高达到每期八千份,足迹到达祖国大陆各省,借助热心者的传递飘洋过海送到漳籍乡亲手中,作为市县一级文艺刊物,可说盛况空前。由于各种原因,《水仙花》停刊多年,但是在文艺百花园里,她曾经绽放过,历史记住了她。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经受文革的浩劫与摧残,漳州市的业余文艺作者多数沉浸在不解、悲愤、苦恼与气馁的情绪之中。陈布伦先生尽管饱受打击与迫害,但做为当时主持市文联工作的负责人,他并没有丢弃自己的责任。他极其耐心地听取大家的倾诉,不断地给大家热情的安慰与鼓舞。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黑暗已经过去,往前看,一切都会慢慢地好起来。
1978年10月15日,“市群众文化工作座谈会”在市中山公园仰文楼上召开,布伦先生和时任市文化图书站负责人的陈玉池先生共同主持这次会议。会上宣读了中共漳州市委书记巩鸣鹏关于为所谓的“三蕾一鸿”(“春鸿”、“芗蕾”、“蓓蕾”和“春蕾文艺”等四个业余文艺小组)的平反意见,事后,中共漳州市委于1978.12.21以综字069号文件发出《关于对“三蕾一鸿”的平反、恢复名誉的决定》,激发大家积极揭批“四人帮”热情。来自全市各地的业余文艺作者济济一堂,群情激愤,齐声谴责我市某些人炮制所谓“三蕾一鸿”案件迫害业余文艺作者的罪行;同时大家更互相鼓励,要克服余悸,消除顾虑,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再立新功。会议气氛热烈,效果良好,有的原来已砸烂钢笔,发誓洗手不再创作的作者也表示“我要提笔从头干”。
经过热烈讨论,与会者一致要求文化部门从速批准市文联创办一个刊物,做为文艺作者发表与交流作品的园地。至于刊名,开头有所争论,无论是主张叫《漳州文艺》或《芗江文艺》都受到多数人的反对;后来有人提出:以前我们许多业余刊物都自称为“花蕾”,现在经过严冬的考验,应该迎风绽放!于是将《水仙花》做为刊名的主张就脱颖而出,众望所归。我市文艺作者团结一心,展开双臂,共同迎接文艺界的“第二个春天”。
经过一番酝酿与筹备,《水仙花》文艺杂志终于在1979年元月15日问世。这期间适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因此首期刊物特地编发了“热烈欢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的一组稿件。因经费问题,这期刊物是油印本,与会者人手一册,少量赠送有关部门单位与领导,十分珍贵。从第二期起刊物才改为铅字印刷本。《水仙花》的出刊给漳州市的文化生活带来了新气象,为漳州市文艺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所以后来有人将其称为“漳州改革开放的报春花”。
(二)弥足珍贵的支持
《水仙花》杂志能顺利出刊,除依靠全体文艺作者团结一心共同努力外,时任市文化图书站负责人的陈玉池先生的大力支持也是功不可没的。1949年全国刚解放,年仅17岁的他就报名参加解放军,剿过匪,立过功;1958年复员后大部分时间在市文化部门工作,卓有成绩。其兄陈虹先生三十年代曾是我市革命团体“芗潮剧社”成员,文革初期在省文化厅厅长任上,曾横遭省级报刊点名进行所谓的批判。1976年1月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幸去世,陈玉池先生积极带领单位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周总理的生平事迹和有关纪念文章,组织照片展览,宣传周总理的丰功伟绩,还曾遭到追查与迫害。他对业余作者极富感情,大家对他也特别敬重。业余作者要求创办《水仙花》杂志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他一次又一次跑文化局、财政局,要求拨给经费,在一时未能解决的情况下,他先从文化馆的有限经费中拨支,使《水仙花》得以顺利按时出刊。他的支持弥足珍贵,这是大家永远不会忘记的。
可惜的是,1979年5月间,陈玉池先生在市文联参加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7周年的座谈会后回到家中就病倒了,两个月后经检查确诊为晚期肝癌。在病中,他始终如一地关心《水仙花》杂志的编辑工作。做为联办单位的领导,布伦先生对他十分尊重,每期稿件编好后都会送去给他审阅。每次他都会一篇一篇地认真看,提出意见,有时还亲自动笔改一改,即使不得不住院了,在病榻上他也还是如此认真,他的负责任的精神令人感动!每次《水仙花》编委去探望他,他都特别高兴,神采飞扬的;尽管医生交代不要多说话,但他先是轻声后来却越说越激动,滔滔不绝,从文联机构的建立,人员的抽调到办公场所的修建等等,一直谈个不完。后来声音逐渐微弱,但却清清楚楚,他说:“茅盾先生给《水仙花》题签,我很高兴。这一期(指第四期)的封面很清秀,很大方。等我病好了,一定和你们一道,把《水仙花》办好。”
(三)《水仙花》的工作机制
《水仙花》创刊后,只有布伦先生一位还要负责搞好市文联的其他工作的“主持工作的专职人员”,刊物主要的编辑工作都由分散在各自工作岗位的业余作者兼任。当时我虽然年轻,但熟悉编务,布伦先生就很信任地把“把头关”的任务交给我。刊物所收到的稿件悉数交由我先行阅读、筛选;筛送结果我即及时向布伦先生汇报,经他同意后才把稿件分成小说、散文、诗歌和评论四类,分别交给各专业组的编委去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同意选用者还要负责文字润饰与加工;各组编委处理好稿件后再交给我,由我整理出初审目录后送布伦先生做最后定夺拍板。确定选用篇目后再由我约请美编插图、画版、送印刷厂排版,然后校对直至出刊后组织销售、发行。每两个月出刊一期,单排铅字就要十多天,校对要七、八遍,工作量满大的。我拿出当年搞业余刊物的干劲,学校一下班就往文联跑,当时只有一个心思:要尽自己之所能,和其他业余作者一道,帮助布伦先生把《水仙花》杂志办好,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对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执着与热爱,痛批“四人帮”对我们的诬蔑与迫害。后来布伦先生深有感慨地对我说:“有业余作者很形象地概括了我们两个人的作用,说我们两人就好比一个木桶的上下两条箍,上条箍可以使木桶不散,下条箍可以使木桶不漏。”能得到这样的评价说明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因此感到自豪。后来由于稿件越来越多,编务工作已非业余兼职所能应付得了,经请示上级批准,《水仙花》编辑部终于抽调黄海根同志来担任专职编委,我也才得以卸下所负担的各种编务工作。
四个专业组的编委都很尽职,负责处理的稿件都能按时按质按量交来,确保每期刊物都能准时付印,从未延误。特别是小说组王雄铮老先生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他博闻强记,学识渊博,思维敏捷,言辞犀利,无论是对事物还是对文章经常都能发表一些振聋发聩的独到见解,令人敬佩。只是有时他的见解过于超前让人不好接受,有时批评别人过于尖锐直率,使人下不了台,但是大家合作共事还是配合得相当默契。
1982年3月,《水仙花》杂志社正式组建编委会,特聘吴秋山、陈文和二位先生为顾问,陈布伦为主编,王雄铮为副主编,我和吴东南、青禾、黄金涛、黄海根、曾坚(美编)和熊韩江等人为编委。事前,布伦先生找我谈话,要我也出任副主编,我担心难以胜任没有同意。过后不久,布伦先生又找我说,根据广大读者的强烈要求,要创办一个民间文学小报做为《水仙花》的附刊,要我负责这项工作并担任主编。盛情难却,我只好鼓足勇气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去并努力创造出新的成绩。
(四)乐为他人做嫁衣
《水仙花》的编委都意识到自已责任之重大,决心不负众望,尽职尽责,努力搞好所担负的工作。开头,由于“文革”的阴影尚未完全消除,业余作者的余悸还很严重,编委们就通过各自的交往渠道,广泛联系业余作者,做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鼓励他们重新拿起笔来写稿;许多老文艺作者文革后的第一篇新作岂不多是被《水仙花》编委软磨硬泡才得以问世的吗?对那些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年青作者的来稿,编委们同样怀着满腔热情的态度,认真地对待、负责任地处理,只要稍有可取之处,都会想方设法加工、修改,力争尽快加以发表。翻开当年刊物就不难发现,如今驰骋漳州文坛的青年才俊的处女作,有好多都是在《水仙花》杂志发表的。
来稿稍微多了一些以后,布伦先生针对外地的一些刊物大部分发表编辑者自己作品的做法说:“我们是不是能反其道而行之?希望编委们的作品、文章能尽量往外投稿,把《水仙花》的有限版面让给其他作者,让更多的作者能在《水仙花》刊物上展示才华、健康成长。”布伦先生的意见得到了全体编委的赞成与支持,少用自己的稿件成为编委们自觉遵守的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这种自我约束、乐为他人做嫁衣的精神我觉得在当时十分难能可贵,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五)老一辈作家的无私支持
为了较快地解除文艺作者的思想顾虑,又有利于提高刊物的档次与质量,有的编委提议约请知名作家为《水仙花》杂志写稿,让他们言传身教做出示范,给广大作者、读者带来鼓舞。请名家写稿是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但只要是正确的意见,布伦先生都会虚心接受、认真执行。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直接写信,或托人与省作协主席郭风先生和著名诗人蔡其矫、舒婷、陈瑞统、黄寿褀、郑朝宗等名家联系,没想到都得到热烈响应。他们先后都给《水仙花》赐稿。布伦先生还通过民盟的关系,联系上时任上海辞书出版社高级编审、著名漳籍老作家耿庸先生和民盟中央常委、扬名国内外的大作家、大记者和老翻译家萧乾先生,并通过他们的帮助,先后约请了我国著名的作家、诗人冰心、胡风、艾芜、蹇先艾、顾工、秦似、雷石榆、冯英子、周俟松(许地山夫人)等名家陆续为刊物提供稿件。老作家们的支持极为有效地为广大文艺作者做出榜样,为刊物增光添彩,更多作者信心百倍拿起笔来踊跃投稿,刊物愈来愈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六)茅盾先生为《水仙花》杂志题签
1979年8、9月间,为组织稿件,我和陈布伦先生一起到市区瑞京路小巷的一所低矮的民房里去拜访民盟的老盟员、时在漳州师院任教的吴秋山老师。他很客气地端茶、让座。我们向他介绍了文革的际遇、《水仙花》的办刊宗旨和存在的困难,请他大力支持、赐稿。吴老师很健谈,一谈起办刊、写稿,他就打开话匣子,兴致勃勃地向我们介绍三十年代的时候,与茅盾、郑振铎等先生在上海共同组建“中国诗歌研究会”的活动情景。我们很高兴地获知他和茅盾先生曾合作共事过,就很感兴趣地问:“那你现在与茅盾先生还有联系吗?”他说:“有啊,茅盾先生对水仙花情有独钟,每年年底他都要写信让我捎上一些水仙花头,让他种养、清供。”我那时年轻,反应较快,我马上想到发表在《茅盾选集》的手迹说明茅盾先生的毛笔字是非常端庄秀丽的。我就见缝插针,大胆地开口:“吴老师,能不能请你在方便的时候,代我们请求茅盾先生为《水仙花》的刊名题签,这既是对我们办刊工作的大力支持,也是对水仙花的故乡漳州人民的极大鼓励。”吴老师闻言,不假思索立即回应说:“对,这个主意好!我明天就写信,我相信茅盾先生不会拒绝我的要求。”
果然,半个多月以后,吴秋山老师就打来电话报告喜讯:“茅盾先生的题签寄来了!”布伦先生立即通知我一起到吴老师家里去。吴老师笑得合不拢嘴,说:“我知道茅盾先生是非常重感情的人,但我也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快就寄来题签。”我们共同端详、欣赏茅盾先生端庄、隽秀的墨宝,不能不为这位文学巨匠、一代宗师能如此关心、支持一个地方的小刊物而激动万分。题签用小宣纸写了多遍,让我们自行挑选,充分显示茅盾先生那种虚怀若谷,平等待人,处事周详的大家风苑。
拜别吴秋山老师之后,我们很快请了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当时分别在市工商银行和市侨芗剧场当美工的陈满根和方文和两位老师共同为《水仙花》1979年第4期设计一个封面,正式发表茅盾先生的题签。茅盾先生潇洒俊逸的题字配上清秀亮丽的水仙花图案使整个刊物显得雍容大方、光彩照人,为刊物增光添色,令人耳目一新。
我国文坛泰斗茅盾先生为《水仙花》刊名题签极大地鼓舞了我市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大家纷纷表示要以办好《水仙花》的实际行动来报答茅盾先生对刊物的厚爱与关怀。事后我们才知道,茅盾先生为县市一级的地方文艺刊物题签,这是破天荒的头一遭。难怪国家版本书库和北京、上海、福州等地图书馆闻讯后均陆续发来专函索取全套刊物存档、珍藏。可以说,茅盾先生为《水仙花》刊名题签,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市文化生活的一件盛事。
《水仙花》刊物完全靠自办发行。编委们提供文艺爱好者名单,其中有发行能力者则动员其代办发行,特别是市区及邻县业余作者及学校教师做了很大的努力。《水仙花》在三年多时间内共出版21期,发行量从起初每期几百本不断攀升,最高达到每期八千份,足迹到达祖国大陆各省,借助热心者的传递飘洋过海送到漳籍乡亲手中,作为市县一级文艺刊物,可说盛况空前。由于各种原因,《水仙花》停刊多年,但是在文艺百花园里,她曾经绽放过,历史记住了她。
相关人物
卢奕醒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