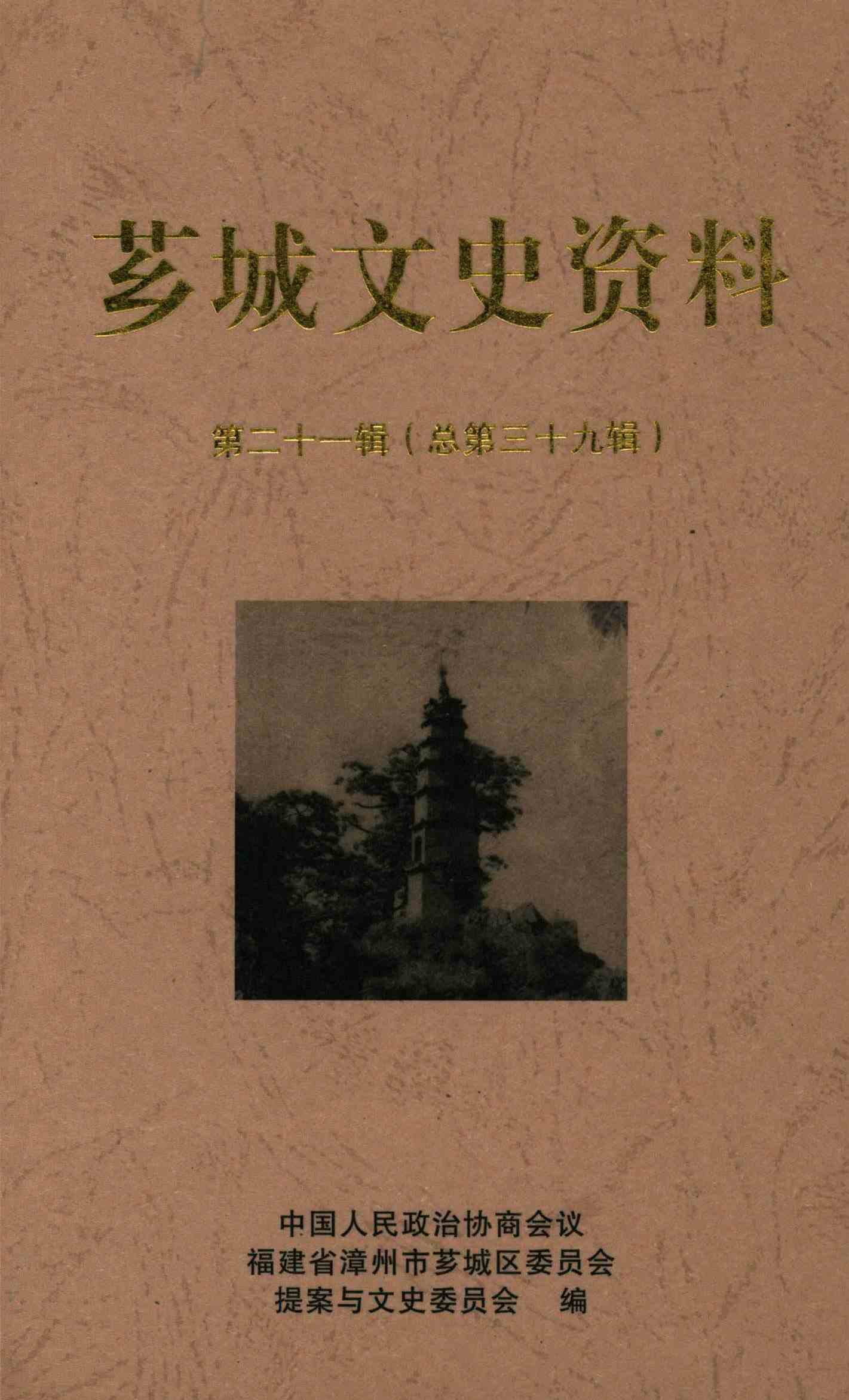漳州“三蕾一鸿”事件真相
| 内容出处: | 《芗城文史资料》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20005542 |
| 颗粒名称: | 漳州“三蕾一鸿”事件真相 |
| 分类号: | D651 |
| 页数: | 8 |
| 页码: | 63-70 |
| 摘要: | 本文记述的是1966年夏天,在共和国横遭浩劫的时候,我们芗城也发生过一起围剿业余文艺作者的特大冤案,声势规模之浩大、牵涉面之广、打击面之宽,在全省乃至全国均属罕见。一大批年纪轻轻的、在红旗下长大的热血青年都被突如其来的横祸整得晕头转向。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有的当事人已经不幸亡故,多数也已届耄耋之年。应该说需让芗城父老乡亲清楚其中之缘由。《芗城文史资料》的编者认为有必要补写这一笔,揭示事件的原委与经过,有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提醒人们以史为鉴,注意避免悲剧重演。是故,我勉为其难,重揭伤疤,记录下自己所了解的部分事实,也祈请其他尚健在的知情者共同补正。 |
| 关键词: | 漳州 “三蕾一鸿” 事件 |
内容
1966年夏天,在共和国横遭浩劫的时候,我们芗城也发生过一起围剿业余文艺作者的特大冤案,声势规模之浩大、牵涉面之广、打击面之宽,在全省乃至全国均属罕见。一大批年纪轻轻的、在红旗下长大的热血青年都被突如其来的横祸整得晕头转向。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有的当事人已经不幸亡故,多数也已届耄耋之年。然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重大的案件?其中有什么冤情?有何教训?应该说需让芗城父老乡亲清楚其中之缘由。据我所知,“四人帮”倒台后,所有当事人也都曾群情激愤过,但后来与共和国主席和老帅们的悲惨遭遇一比照,大家都明白这是一场全民族的灾难,个人的冤屈算不了什么。《水仙花》文艺杂志和《金盏》民间文学小报创刊后,大家忙于编刊办报,“要将‘四人帮’所耽误的时间夺回来”,谁都没有心思再去回顾那些不幸的往事,舔养受伤的心灵。《芗城文史资料》的编者认为有必要补写这一笔,揭示事件的原委与经过,有利于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提醒人们以史为鉴,注意避免悲剧重演。是故,我勉为其难,重揭伤疤,记录下自己所了解的部分事实,也祈请其他尚健在的知情者共同补正。
所谓的“三蕾一鸿”是怎么一回事?
所谓的“三蕾一鸿”,其实是莫须有的、并非一个什么组织机构的正式名称,它只是文革初期,某些人为迫害业余文艺作者“创造性”地仿照当时报刊上流行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提法所捏造出来的专用名词。其所指的是我市在1958年以后所涌现出来的众多业余文艺小组中的“春鸿”、“芗蕾”、“蓓蕾”和“春蕾”等四个业余文艺小组。
那么它们是一些什么样的组织呢?原来在大跃进年代,我市曾出现过全民写诗抓创作的热潮,各种文学社、业余文艺兴趣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在各机关、工厂,尤其是学校纷纷建立并开展各种活动。“春鸿文艺”早在1958年就由漳州二中学生郭建章等组织成立,后由陈玉旺、李志敏等继续组织活动。“芗蕾文艺”是漳州侨中教师陈如珂等人组织的。“蓓蕾业余文艺小组”才是1959年我在高中毕业后与同班学友叶升旗等共同组织的,其还于1962年在市文联的支持下与“春鸿业余文艺小组”合并组成“春蕾业余文艺小组”。这些小组均是一些爱好文艺的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后,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由不同的成员自愿组合、分散活动的松散型的业余文艺组织。其成员在不同的工作、学习岗位,放弃休息,辛勤习作,然后汇集作品,一两个月才编印成一本油印刊物在内部互相交流。刊物从未对外公开发行,纯粹是种习作园地,作品经切磋修改后才转投正式报刊公开发表。
这些业余文艺小组当时都得到市文联的指导与支持,多次得过奖励。许多小组成员都是所在单位的工作骨干或先进分子,大家都尽可能做到业余习作与本职工作两不误;个别成员创作活动有成绩,还曾被选送参加全国的业余文艺作者代表大会。所谓的众多罪名是如何被强加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神州大地乌云翻滚。“四人帮”以种种卑劣的手法,对邓拓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吴晗的《海瑞罢官》等作品,肆意挞伐、横加罪名,开启了现代大兴文字狱的恶劣先例,揭开了中国革命史上最黑暗、最丑恶的一页。
社会上总有人特别擅长窥测政治方向,从当时的政治大气候中捕捉可趁之机。事后我才知道,我所在工作单位的校领导与当时漳州市文联的负责人同是南下干部,却在感情上有过嫌隙。他紧紧抓住机会,妄图先将我打成“反革命”、“坏人”,然后再将矛头直指一直大力支持我们活动的市文联负责人,即所谓的“后台老板”,从而达到既发泄私怨,又可在文革建立奇功、积累政治资本的目的。他利用校政治处主任与我是师生关系,让其先与我套近乎,以“要学习讨论”为名,要看我的“业余习作”。我未觉察他们的叵测居心,以为自已动机纯正、愿望良好,即使有缺点甚至错误也应该欢迎自己的老师与领导批评指正。我满怀信任地将停刊多年、仅存的一整套业余习作刊物送给他,想不到这恰恰为他们制造打击我的“炮弹”提供了最大的方便!随即,他们就纠集黑笔手,用“四人帮”对付邓拓、吴晗的手法,捏造事实、罗织罪名,仅几天功夫就炮制出一份所谓的《评“三蕾一鸿”的反动本质》的极其恶毒的黑材料,煞有介事地罗列了莫须有的“十大罪状”,诬称“三蕾一鸿”是什么“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集团”、是什么“三家村的漳州分店”,还封我为“黑掌柜”。材料立即上报中共漳州市委,并散发全国各地的有关单位,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和严重后果,因为当时正是文革刚开始的风口浪尖,来自战略地位极其敏感的“福建前线”,又有那么多骇人听闻的严重罪行的所谓黑组织的材料,当然引起高度重视,许多业余作者立即受到停职或隔离审查,有的受到捆绑、吊打、游街、跪碎石、逼供信;有的被打入“牛棚”,被褥被泼上尿水;好几位正在谈对象的作者还被“棒打鸳鸯”不得不分手;最不幸的要算外贸职工,我的同学余渭生,他仅因写了几篇作品和参加市文联活动,竟被“邓拓-陈布伦-余渭生”的所谓黑线要把他抓去游街,他受不了羞辱就跳井身亡,这是多么惨痛的血的教训呀!
他们泡制黑材料的卑鄙手法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曰牵强附会、横加罪名:将几个互不相干的业余文艺组织硬捏在一起,冠以“三蕾一鸿”的名称,还上纲上线,强行将它们与所谓的刘少奇文艺黑线和“三家村”挂钩,达到其制造最大批判效果的险恶目的。
二曰无中生有、捏造事实:随意篡改歪曲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业余作者的家庭出身和政治历史。如恶意地将我的家庭出身篡改为所谓的“地主兼工商业”、“恶霸地主”;将文革前有关部门早就为我父母亲所做的“属一般伪党员免予处分”的政治历史结论置之不顾,一口咬定他们是所谓的“罪恶累累的国民党反动党团骨干”,目的就是要欺骗所有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我们这些人都是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的“狗崽子”,是“没有改造好的黑五类”。说什么“三蕾一鸿”是对现实极其不满的剥削阶级子女幻想资本主义复辟的“裴多斐俱乐部”;还造谣说什么“三蕾一鸿”是“地下黑刊物”、“是被公安局勒令停刊的”,以挑动人们对业余作者的仇视与痛恨。
三曰斩头去尾、断章取义:如郑惠聪写的《红旗越举越坚牢》是首共二十八节的长篇叙事诗,每节四行,描写的是1932年红军入漳受到闽南人民热烈欢迎的生动故事。其前七节是写红军入漳前闽南人民的苦难生活情景。他们大笔一挥拦腰斩下,然后加上按语,诬称作者、编者“攻击现实、诅咒三面红旗,公开发泄对新社会的不满”。一位叫“平凡”的业余作者是苦孩子出身,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写了一首忆苦思甜、讴歌幸福新生活的诗歌竟横遭腰斩,将描写解放前苦难生活的内容歪曲为“攻击现实,丑化人民公社”。
四曰肆意歪曲、血口喷人:如我写的《登厦鼓日光岩》一诗,明明是站在厦门鼓浪屿的水操台上缅怀当年郑成功将军训练水兵收复宝岛台湾的英雄业绩,他们却明目张胆地改换我的立足点,污蔑说我是“站在阿里山上为蒋介石反攻大陆招魂”。而另一位业余作者满腔热情书写的一首《党的赞美词》更是肆无忌惮的诬蔑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党诗篇”!
五曰无限上纲、置人死地:1962年我为《春蕾文艺》的“七一特大号”复制的一张毛主席像,的确画得不太符合标准。客观原因是:我没有绘画基础,趴在用小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下临摹一张夜景油画,难度很大,当时又逢期末学校工作特忙,画后没有好好检查,事后不但我自己而且其他任何人都长期没有发现有任何不妥;主观原因是:文革前对画领袖像的严肃性和重要意义没有足够的认识,认为毕竟不是印刷的,又是内部的,只要尽力画得比较象就可以了。及至发现没画好,我也深感惭愧与痛心。可是硬要说我“刻骨仇恨,有意丑化”,这与事实出入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总之,如此不顾事实、蛮不讲理的手法,成篇累牍;罪名之大,骇人听闻,任何一条罪名都足以置人死地。当时我才二十多岁,从未经历过任何政治运动,当然十分惊恐,天天晚上都要被恶梦惊醒,吓出一身冷汗;直至半个月后,定神扪心自问并无恶意,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心情才逐渐平复。
听说,当时的市委书记巩鸣鹏闻报后勃然大怒。他立即召集市委常委开会,下令全市人民集中火力,“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集团‘三蕾一鸿’猛烈开火!”并责令全市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都要凭党支部的介绍信,组织所有干部群众到现场观看铺天盖地的声讨我们的大字报。然后,他还派遣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和市公安局长一道亲自带领文革工作组进驻学校,“要抓大老虎”,夺取文革的新胜利。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后绽春蕾
然而,历史发展的辨证法是无情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经过了这场浴血的洗礼,我也更深刻地认识到“要相信党、要相信群众”这一颠扑不灭的真理。
我也是事后才知道,文革工作组进驻学校,调阅了有关“三蕾一鸿”的所有原始材料后,就说“这样的材料,以后要怎样端得上台桌(意指无法定案)!”于是他们就先把我们晾在一边,因此后来竟有人诬指其为“包庇黑帮”。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不少业余文艺作者找上市委书记巩鸣鹏要求平反。他反问“你们要求为谁平反?”众答“为我们自己!”他吃惊不小,问“怎么会是你们自己?”经证实后,他深有感慨地说“我看了基层上报的材料,以为‘三蕾一鸿’的成员一定都是国民党的遗老遗少,不然怎么会对共产党、对新社会怀有那样的深仇大恨?想不到竟然都是一些在红旗下长大的小青年。”于是,他很干脆地做出为“三蕾一鸿”公开平反的决定,亲自撰写并批经费印平反公告。
我个人的问题又拖了一段时间。有人一口咬定我是“有意丑化”,大会批、小会斗;说我会写黑文章,思想坏,一句一拳头,专门猛击我的头部,要砸烂我的“狗头”,打得我头痛欲裂,眼冒金星;打昏了跪下去,头发一揪,站起来继续打。连续殴打体罚,我无奈只好屈打成招。喜得有的人手舞足蹈,急急忙忙上报材料,要让公安局抓现行将我逮捕法办。公安局专案人员不下十次找我,边核实材料,边耐心地对我进行帮助教育,并支走了“红卫兵”打手,让我终于解除顾虑抖出真情、讲了实话,没有在忍冤受屈的深坑里继续陷下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参与编辑的《水仙花》文艺刊物终于问世,不久,由我担任主编的《金盏》民间文学小报也相继创刊。我打从心眼里由衷赞美、热烈欢呼:文艺界的第二个春天真正来到,“春蕾”在经历严冬后也终于吐蕊开花了!
所谓的“三蕾一鸿”是怎么一回事?
所谓的“三蕾一鸿”,其实是莫须有的、并非一个什么组织机构的正式名称,它只是文革初期,某些人为迫害业余文艺作者“创造性”地仿照当时报刊上流行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提法所捏造出来的专用名词。其所指的是我市在1958年以后所涌现出来的众多业余文艺小组中的“春鸿”、“芗蕾”、“蓓蕾”和“春蕾”等四个业余文艺小组。
那么它们是一些什么样的组织呢?原来在大跃进年代,我市曾出现过全民写诗抓创作的热潮,各种文学社、业余文艺兴趣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在各机关、工厂,尤其是学校纷纷建立并开展各种活动。“春鸿文艺”早在1958年就由漳州二中学生郭建章等组织成立,后由陈玉旺、李志敏等继续组织活动。“芗蕾文艺”是漳州侨中教师陈如珂等人组织的。“蓓蕾业余文艺小组”才是1959年我在高中毕业后与同班学友叶升旗等共同组织的,其还于1962年在市文联的支持下与“春鸿业余文艺小组”合并组成“春蕾业余文艺小组”。这些小组均是一些爱好文艺的年轻人从学校毕业后,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由不同的成员自愿组合、分散活动的松散型的业余文艺组织。其成员在不同的工作、学习岗位,放弃休息,辛勤习作,然后汇集作品,一两个月才编印成一本油印刊物在内部互相交流。刊物从未对外公开发行,纯粹是种习作园地,作品经切磋修改后才转投正式报刊公开发表。
这些业余文艺小组当时都得到市文联的指导与支持,多次得过奖励。许多小组成员都是所在单位的工作骨干或先进分子,大家都尽可能做到业余习作与本职工作两不误;个别成员创作活动有成绩,还曾被选送参加全国的业余文艺作者代表大会。所谓的众多罪名是如何被强加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神州大地乌云翻滚。“四人帮”以种种卑劣的手法,对邓拓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吴晗的《海瑞罢官》等作品,肆意挞伐、横加罪名,开启了现代大兴文字狱的恶劣先例,揭开了中国革命史上最黑暗、最丑恶的一页。
社会上总有人特别擅长窥测政治方向,从当时的政治大气候中捕捉可趁之机。事后我才知道,我所在工作单位的校领导与当时漳州市文联的负责人同是南下干部,却在感情上有过嫌隙。他紧紧抓住机会,妄图先将我打成“反革命”、“坏人”,然后再将矛头直指一直大力支持我们活动的市文联负责人,即所谓的“后台老板”,从而达到既发泄私怨,又可在文革建立奇功、积累政治资本的目的。他利用校政治处主任与我是师生关系,让其先与我套近乎,以“要学习讨论”为名,要看我的“业余习作”。我未觉察他们的叵测居心,以为自已动机纯正、愿望良好,即使有缺点甚至错误也应该欢迎自己的老师与领导批评指正。我满怀信任地将停刊多年、仅存的一整套业余习作刊物送给他,想不到这恰恰为他们制造打击我的“炮弹”提供了最大的方便!随即,他们就纠集黑笔手,用“四人帮”对付邓拓、吴晗的手法,捏造事实、罗织罪名,仅几天功夫就炮制出一份所谓的《评“三蕾一鸿”的反动本质》的极其恶毒的黑材料,煞有介事地罗列了莫须有的“十大罪状”,诬称“三蕾一鸿”是什么“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集团”、是什么“三家村的漳州分店”,还封我为“黑掌柜”。材料立即上报中共漳州市委,并散发全国各地的有关单位,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和严重后果,因为当时正是文革刚开始的风口浪尖,来自战略地位极其敏感的“福建前线”,又有那么多骇人听闻的严重罪行的所谓黑组织的材料,当然引起高度重视,许多业余作者立即受到停职或隔离审查,有的受到捆绑、吊打、游街、跪碎石、逼供信;有的被打入“牛棚”,被褥被泼上尿水;好几位正在谈对象的作者还被“棒打鸳鸯”不得不分手;最不幸的要算外贸职工,我的同学余渭生,他仅因写了几篇作品和参加市文联活动,竟被“邓拓-陈布伦-余渭生”的所谓黑线要把他抓去游街,他受不了羞辱就跳井身亡,这是多么惨痛的血的教训呀!
他们泡制黑材料的卑鄙手法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曰牵强附会、横加罪名:将几个互不相干的业余文艺组织硬捏在一起,冠以“三蕾一鸿”的名称,还上纲上线,强行将它们与所谓的刘少奇文艺黑线和“三家村”挂钩,达到其制造最大批判效果的险恶目的。
二曰无中生有、捏造事实:随意篡改歪曲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业余作者的家庭出身和政治历史。如恶意地将我的家庭出身篡改为所谓的“地主兼工商业”、“恶霸地主”;将文革前有关部门早就为我父母亲所做的“属一般伪党员免予处分”的政治历史结论置之不顾,一口咬定他们是所谓的“罪恶累累的国民党反动党团骨干”,目的就是要欺骗所有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我们这些人都是出身在剥削阶级家庭的“狗崽子”,是“没有改造好的黑五类”。说什么“三蕾一鸿”是对现实极其不满的剥削阶级子女幻想资本主义复辟的“裴多斐俱乐部”;还造谣说什么“三蕾一鸿”是“地下黑刊物”、“是被公安局勒令停刊的”,以挑动人们对业余作者的仇视与痛恨。
三曰斩头去尾、断章取义:如郑惠聪写的《红旗越举越坚牢》是首共二十八节的长篇叙事诗,每节四行,描写的是1932年红军入漳受到闽南人民热烈欢迎的生动故事。其前七节是写红军入漳前闽南人民的苦难生活情景。他们大笔一挥拦腰斩下,然后加上按语,诬称作者、编者“攻击现实、诅咒三面红旗,公开发泄对新社会的不满”。一位叫“平凡”的业余作者是苦孩子出身,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写了一首忆苦思甜、讴歌幸福新生活的诗歌竟横遭腰斩,将描写解放前苦难生活的内容歪曲为“攻击现实,丑化人民公社”。
四曰肆意歪曲、血口喷人:如我写的《登厦鼓日光岩》一诗,明明是站在厦门鼓浪屿的水操台上缅怀当年郑成功将军训练水兵收复宝岛台湾的英雄业绩,他们却明目张胆地改换我的立足点,污蔑说我是“站在阿里山上为蒋介石反攻大陆招魂”。而另一位业余作者满腔热情书写的一首《党的赞美词》更是肆无忌惮的诬蔑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党诗篇”!
五曰无限上纲、置人死地:1962年我为《春蕾文艺》的“七一特大号”复制的一张毛主席像,的确画得不太符合标准。客观原因是:我没有绘画基础,趴在用小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下临摹一张夜景油画,难度很大,当时又逢期末学校工作特忙,画后没有好好检查,事后不但我自己而且其他任何人都长期没有发现有任何不妥;主观原因是:文革前对画领袖像的严肃性和重要意义没有足够的认识,认为毕竟不是印刷的,又是内部的,只要尽力画得比较象就可以了。及至发现没画好,我也深感惭愧与痛心。可是硬要说我“刻骨仇恨,有意丑化”,这与事实出入差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总之,如此不顾事实、蛮不讲理的手法,成篇累牍;罪名之大,骇人听闻,任何一条罪名都足以置人死地。当时我才二十多岁,从未经历过任何政治运动,当然十分惊恐,天天晚上都要被恶梦惊醒,吓出一身冷汗;直至半个月后,定神扪心自问并无恶意,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心情才逐渐平复。
听说,当时的市委书记巩鸣鹏闻报后勃然大怒。他立即召集市委常委开会,下令全市人民集中火力,“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集团‘三蕾一鸿’猛烈开火!”并责令全市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都要凭党支部的介绍信,组织所有干部群众到现场观看铺天盖地的声讨我们的大字报。然后,他还派遣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和市公安局长一道亲自带领文革工作组进驻学校,“要抓大老虎”,夺取文革的新胜利。
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后绽春蕾
然而,历史发展的辨证法是无情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经过了这场浴血的洗礼,我也更深刻地认识到“要相信党、要相信群众”这一颠扑不灭的真理。
我也是事后才知道,文革工作组进驻学校,调阅了有关“三蕾一鸿”的所有原始材料后,就说“这样的材料,以后要怎样端得上台桌(意指无法定案)!”于是他们就先把我们晾在一边,因此后来竟有人诬指其为“包庇黑帮”。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不少业余文艺作者找上市委书记巩鸣鹏要求平反。他反问“你们要求为谁平反?”众答“为我们自己!”他吃惊不小,问“怎么会是你们自己?”经证实后,他深有感慨地说“我看了基层上报的材料,以为‘三蕾一鸿’的成员一定都是国民党的遗老遗少,不然怎么会对共产党、对新社会怀有那样的深仇大恨?想不到竟然都是一些在红旗下长大的小青年。”于是,他很干脆地做出为“三蕾一鸿”公开平反的决定,亲自撰写并批经费印平反公告。
我个人的问题又拖了一段时间。有人一口咬定我是“有意丑化”,大会批、小会斗;说我会写黑文章,思想坏,一句一拳头,专门猛击我的头部,要砸烂我的“狗头”,打得我头痛欲裂,眼冒金星;打昏了跪下去,头发一揪,站起来继续打。连续殴打体罚,我无奈只好屈打成招。喜得有的人手舞足蹈,急急忙忙上报材料,要让公安局抓现行将我逮捕法办。公安局专案人员不下十次找我,边核实材料,边耐心地对我进行帮助教育,并支走了“红卫兵”打手,让我终于解除顾虑抖出真情、讲了实话,没有在忍冤受屈的深坑里继续陷下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参与编辑的《水仙花》文艺刊物终于问世,不久,由我担任主编的《金盏》民间文学小报也相继创刊。我打从心眼里由衷赞美、热烈欢呼:文艺界的第二个春天真正来到,“春蕾”在经历严冬后也终于吐蕊开花了!
相关人物
卢奕醒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