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高校第一位校长
| 内容出处: | 《芗城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20005247 |
| 颗粒名称: | 中国近代高校第一位校长 |
| 其他题名: | 中文速记首创人——蔡锡勇 |
| 分类号: | K825.46 |
| 页数: | 15 |
| 页码: | 166-180 |
| 摘要: | 1993年11月27日我国重点高等学府——武汉大学举行了盛大的建校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配发了这次活动的有关图片录像,引起了高教界、学术界和海内外武大校友的广泛关注,1994年4月,《报刊文摘》曾摘引《长江日报》的有关报道,以《武汉是我国近代高教的发祥地》为题,介绍了“武大校史委”经过审慎严密的考证,确认1893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自强学堂,是我国第一所近代高校,为武大的前身,它的成立比“京师大学堂”还早5年。蔡毕业于北京同文馆,曾随清廷首任驻美利坚合众国钦差大臣陈兰彬(荔秋)赴美任译官、参赞,为我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 |
| 关键词: | 校长 |
内容
1993年11月27日我国重点高等学府——武汉大学举行了盛大的建校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中配发了这次活动的有关图片录像,引起了高教界、学术界和海内外武大校友的广泛关注(1955年全国高等教育院系调整后,武大原以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武昌高师作为其前身),1994年4月,《报刊文摘》曾摘引《长江日报》的有关报道,以《武汉是我国近代高教的发祥地》为题,介绍了“武大校史委”经过审慎严密的考证,确认1893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自强学堂,是我国第一所近代高校,为武大的前身,它的成立比“京师大学堂”(创建于1898年,北京大学前身)还早5年。
“自强学堂”成立之初,即由张之洞委任署汉黄德道蔡锡勇为“总办”(校长)。蔡毕业于北京同文馆,曾随清廷首任驻美利坚合众国钦差大臣(现称特命全权大使)陈兰彬(荔秋)赴美任译官、参赞,为我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回国后旋被两广总督张之洞罗致入幕,协助张办理涉外事务(任洋务局委员)及各种洋务实业,深受张的赏识和重用。蔡还根据英文速记原理创制中文速记(著《传音快字》),并最早把西方复式会计介绍、引进并取代我国传统的四柱帐法(著《连环帐谱》)。对于这样一位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发展史上及财务管理制度方面作出过开创性贡献的学者,其生平却是鲜为人知!笔者近年来受有关方面的委托,在搜集整理蔡锡勇史料时,深深为其道德文章所感动,援引文献记载草成此文以飨读者,并就正于有关学科方面的专家学者。
一、早期学习近代外国语文的汉人子弟
蔡锡勇(1847-1898)字毅若,祖籍福建龙溪,关于蔡的先世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估计很可能出生于广州的一个小商人家庭。
1840年鸦片战争,二千年来闭关自守的封建王朝的大门终于被英帝国主义挟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船坚炮利的优势撞开了。随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势力日益加剧,清王朝经过国内太平天国的起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外国侵略势力逐渐扩大到中国沿海各省,并且深入到内地,中外接触日益频繁,封建文化已难以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相对抗,清王朝急需培养能直接与洋人对话交流的翻译人才,以辅佐政府的外事交涉活动。在当时清廷主管外交工作的恭亲王奕訢的建议下,我国第一所学习外国语言的学校——北京同文馆于1862年(清同治元年)正式开办了,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政府外务部前身)。此后第二年、第三年在当时已辟为对外通商口岸的上海与广州也相继成立与北京同文馆同样性质的语言学校——广方言馆(也称同文馆),此时年方17岁的青年蔡锡勇考入了广州同文馆,成为我国第一批正式学习近代外国语言的汉人子弟。
二、青年时期的外语学习生活
北京同文馆成立之初,开设了英、法、俄三个语种,并只招收14岁以下八旗子弟入学。过了三年,始又陆续增设德、日文班以及西方近代科学天文、数学、万国公法、测量、医学生理、物理、化学等课程;入学资格、年龄也放宽为满汉兼收15至25岁的青少年。北京是当时清王朝的统治中心,中外交往尚只限于官方政治往来,远不如上海、广州等沿海通商口岸那样与西方文化、宗教、工商贸易普遍接触交流,稍后于北京同文馆成立的上海、广州两处同文馆(广方言馆)入学的学生素质水平并不逊于北京同文馆的学生,因此三地同文馆学生互相进行交流学习并进一步择优深造就有了可能。
1867年10月15日(清同治六年九月十五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亲王奕訢上奏清廷《片》中称:
“兹查上海、广州两处所设学馆(即指广方言馆)已届三年,其中子弟所学,即或未能深粹,而通其语言文字者谅不乏人。臣衙门开馆伊迩,若于该学生中择其已有成效者咨送来京考试,与臣衙门本年所考各员共为讲解,必可得力。应请旨饬下上海通商大臣、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将各该处所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内择其已有成效者,每省各送数名来京考试……”(《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
遵照这份奏片的要求,广州同文馆选送了蔡锡勇、那三、博勒洪武、韩常泰、左秉隆、坤扬等六名满汉学生赴京参加北京同文馆主办的英文考试。在这次考试中,蔡锡勇显示了卓越的外语才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是考试后唯一获得“监生”称号的学生。奕訢就这次考试的成绩所上的奏折中说:“兹于同治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准署广州将军庆春等将该省同文馆学生蔡锡勇……等六名咨送到臣衙门……该学生等文理俱各明顺,学习有年,深堪造就,应请照上年奏定章程,蔡锡勇一名作为监生,那三……等五名作为翻译生员……”分别确定名次。
这次考试后,蔡锡勇等六人仍饬回广州同文馆继续学习,并具备充当翻译差使资格。
过了四年(1872同治十一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再次饬令上海广州两地同文馆选送优秀学生去京考试深造。此时年已25岁的蔡锡勇以“福建龙溪县监生、翻译官”的身份又被列入去京考试深造人员名单。蔡锡勇和那三、左秉隆等三人以原已在同治六年去京考试取得优异成绩为由,要求此次以“保举”名义免试入学,旋经同意,于同年9月22日由广州同文馆咨送到京。
此时,北京同文馆历经扩充,已逐渐从一所单纯的语言学校向近代综合性大学转变并初具规模,学制、入学年龄、资格均有较大改变,外语各班三年毕业,由外文而及天文、数学等理工各科者八年毕业。蔡锡勇的英语水平已能从事笔译口译,直接听洋教习外语授课。他在北京同文馆同时选修多门学科,并成为馆中唯一的汉人数学家教习李善兰的高足。同治十三年(1874),年已27岁的蔡锡勇以各科共列优等(按成绩相当于现在的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同文馆。
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是由语言学校开始起步的。
三、第一代职业外交官成员
清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开始正式按西方国际关系制度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派出驻外使节。同年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上谕委派赏二品顶戴、刑部郎中、太常寺卿陈兰彬(荔秋)为首任出使美利坚合众国(兼领秘鲁、日本)钦差大臣(即特命全权大使)。蔡锡勇以北京同文馆优等毕业生最佳外语人才被陈兰彬罗致担任译官,随使出洋。抵美不久,又以工作成绩表现出色,极受钦差赏识,奏准以“候选通判”升任参赞。1884年(光绪九年)丁忧回国。守制期满,即被两广总督张之洞延揽入幕,参与在广东兴办的洋务实业活动,结束了他的职业外交官生涯。
四、撰成我国第一本速记专著
——《传音快字》
蔡锡勇在驻美钦差公署任职期间,极大地丰富了他对西方文明的了解。作为一个在典型封建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开始对西方文化中的一些技术科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考虑其中是否也能为中国古老的儒学文化所用。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官,首先使他感到惊奇的是西方国家的速记术。他在撰成我国第一本速记教科书《传音快字.自序》中这样写道:
“余昔随陈荔秋副宪出使美、日、秘三国,驻华盛顿四年。翻译之暇,时考察其政教风俗,尝观其议政事,判词讼,大庭广众,各持一说,反复辩论,杂沓纷纭,事毕各散,而众论异同,业皆传播,记录稠叠,稿堂盈寸,揣其必有捷法,继询彼邦人士,始知有‘快字’一种,行之已久,作者不一家,师承各异,然皆能笔随口述,不假思索,手不停挥,率每分钟能作二百余字……。”
在这段文字中,蔡锡勇叙述了他发现西方国家有一种“行之已久”的“快字”,(Shorthand,近代西方国家速记术起源于16世纪末之英国,最早用于记录国会议员之演说辩论)并且有多种方式(“作者不一家”),但都能做到“笔随口述”,每分钟“能作二百余字”。那么能否把这种方式移植过来为中文所用呢?他开始构思这个设想,当然首先他自已要学会这门科学技术。
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虽然立国还不过一个世纪,但是它的经济已经迅速赶上和超过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大量的欧洲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众多的黑人后裔以及亚洲移民又为开拓西部地区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而比较健全的议会民主政治与发达的文化科学、大量的对外贸易构成了这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国力,此时在西方国家已流行数百年的速记术也广泛应用于美国社会。
关于蔡锡勇学习英文速记和创制中文速记的经过,在其幼子蔡璋把《传音快字》修订改编为《中国速记学》一书的《绪言》中写道:“……至一千八百八十二年美国凌士礼氏之速记术出,遂大得斯学界之欢迎,时中国前清光绪八年也。先君适随使美邦,因得尽通其术,迨归国后,益复研究古今音韵之学,参以西人卫三畏音歆字典等书,至光绪二十二年乃脱稿付梓,定名为传音快字……”
《传音快字》于1896年由湖北官书局镌印出版后,曾在由蔡锡勇兼任“总办”(校长)的“自强学堂”(1893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汉创办的我国第一所按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分科进行教学的高校)中进行教学。至于正式把《传音快字》(《中国速记学》作为我国最早的一种速记方式来进行教学并付诸实际应用,已是清末。当时为筹划实行君主立宪成立议会(称“资政院”即一院制国会)需大批速记人员,清廷征召蔡璋赴京担任资政院速记学堂总教习(校长),为中央、省、县各级议会培训速记人才。从清末资政院、民国北洋政府国会到南京政府立法院,蔡氏父子发明的中文速记术开创我国早期速记应用的范例,蔡璋本人还三任速记长。蔡氏父子并先后受到民国北洋政府大总统多次题匾授勋特令褒奖。
五、张之洞办洋务的主力干将
张之洞是清末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直隶南皮人(今河北省)他与项城袁世凯、玉林岑春煊并称清末三大吏,但其利国利民的成就,政绩则远过于袁、岑。他所兴办的洋务实业,与为培育人才开办文武学堂、主张文事武备并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反对戊戌变法等,尽管他的学说主张有其矛盾错误的一面,但是就其总的成就来看,在19世纪后半期的清代封疆大吏中,仍不失为一个头脑清新卓有远见的大人物。他发现并重用蔡锡勇并使之成为其在洋务运动中兴业办学的主力干将,与起用冯子材在1884年中法战争中击败法帝国主义,同为张之洞“知人善任”的两个典型例子。
蔡锡勇的后半生一直追随张之洞兴办洋务实业、教育培养人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因此在叙述蔡锡勇的史绩时,不能不提到张蔡之间的“恩遇”关系。在《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卒谥文襄)中,《奏稿》部分占有较大篇幅,其中为蔡锡勇所上的专折就有《蔡锡勇留粤补用片》、《保荐蔡锡勇片》、《为蔡锡勇请恤折》等,在《公牍》部分有《札道员蔡锡勇改定自强学堂章程》,其它文稿提及蔡锡勇事或与其有关者更不下数十处之多,足见张、蔡之间的密切关系了。
1885年2月(光绪十年十二月)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拒绝新任驻日钦差大臣徐承祖咨调蔡锡勇出任参赞的要求。在上清廷《蔡锡勇留粤补用片》中称:粤东官吏,结识洋人者甚多,而讲求洋务者甚少。向来号称熟习洋务者,非学识粗浅,即品行猥杂。唯蔡锡勇,志向端谨,才识精详,因专派充当洋务局委员,承办各事,均能深明大体,动协机宜,实为办理洋务不可多得之员……”请求“准将三品衔候选知府蔡锡勇留粤差遗,实于粤省洋防,大有裨益”。光绪帝在这份奏折上朱批:“著照所请”。蔡锡勇在广东任职期间,除了担任洋务局委员,负责对外交涉事宜外,张之洞还把所兴办的洋务实业“……开设银元局、枪弹厂、水陆师学堂、鱼雷局及制造兵轮等事,悉以咨之”,足见对蔡倚赖信任之深。
1889年(光绪十五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蔡锡勇随调湖北差遣委用。“……到鄂以来,派委总办铁政局,设立化学堂,定汉阳铁厂之基,枪炮厂即附其中。督饬矿师洋匠建厂安机,开办矿山运道,铁矿灰石水陆码头,兴国锰矿,江夏大冶煤井煤矿及采运湘煤诸务,自经始以至工竣开炼,千端万绪,布置井井,罔有遗漏。臣以督工筹款,艰巨烦难,叠经奏明,就湖北铁、布、枪炮三厂,通筹互济,先后国委该员总办织布、枪炮两局,任事诚恳,殚竭心力,条分缕析,事事力求撙节核实,不避劳怨,端谨廉退,丝毫不苟,和平默讷,不与人争。三厂分局二十余所,委员学生林立,群莫敢以私;各矿师洋匠,亦服其公正,无不尽心效力,办理悉臻周妥……”
根据这份1894年11月4日(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七日)所上《保荐蔡锡勇片》中所述,蔡的经营才能即使与现代西方、日本等国的大企业家相比也毫不逊色。今之企业家只是单纯在一种企业上创基立业,发展光大,而蔡氏所办的企业则包括轻重工业的冶金矿山、铁路交通、兵工造船、水陆航运等各种类型,对之均能做到指挥调度井然有序,连那些从国外聘请来的“矿师洋匠”也心悦诚服,尽心工作。这正是由于蔡在北京同文馆学习时,在原已有深厚的外语基础上,又进修了数理化等多门学科,积累了渊博的知识,从而为他在协助张之洞兴办各种洋务实业担任主管领导工作时,得以充分发挥自已的才能。张之洞在《保荐片》中,称赞“该员深通泰西语言文字,于格致(即近代物理——笔者注)测算,机器、商务、条约、外洋各国政事,无不详究研询,属通达事务,体用兼赅。臣所见办理洋务之员,其才品兼优,事事著实,实无有能出蔡锡勇之右者……”要求清廷“恩予破格录用”。光绪帝在这份奏折上“朱批:蔡锡勇著、交吏部带领引见”后,获“赏二品顶戴”。
六、引进西方复式会计科学的先驱
蔡锡勇对我国财务管理制度的改革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第一位引进介绍西方复式会计制度,撰成《连环帐谱》(“连环”即复式对应之意一一笔者)。
蔡氏在张之洞领导下兴办近代洋务实业,统管单位不下数十处,经手资金款项多达数百万两,虽“力杜虚靡丝毫不苟,”但在巨额资金运用中,又深感我国原有的传统会计制度——“四柱帐法”已难以适应在近代化大企业的财务管理中发挥作用。他早年在国外任职期间,发现西方国家的政府机关、金融机构以及工商企业均普遍采用复式会计制度记帐方法,其严密、科学、实用性远胜于我国旧式四柱帐法。于是他在创造中文速记术之后,工余又埋首钻研西方复式会计制度,但其原来的意图只是借以改良中式会计的记帐方法,使之能适应近代化企业大规模经济活动的需要。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蔡氏一部介绍西方复式会计的专著《连环帐谱》在经过其子蔡璋的补充修订之后,由湖北官书局印行出版。(此时蔡锡勇已作古)这部书成为我国推行西方复式会计的专著。郭道扬教授在其名著《中国会计史稿》中评价说:“蔡锡勇所著之《连环帐谱》既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介绍西式簿记的专著,也是第一次立足于中西帐法相结合,以达改良中式会计的目的,它是西式复式帐法引进的先导,是以后中式簿记改良的先声,它对推动我国近代会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七、中国近代高校第一位校长
张之洞在大办洋务实业的同时,又认识到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初调湖广总督,他就上奏清廷请办各类文武学堂以广储人才。除筹建以学习经学为主的两湖书院外,先后在武汉创办以学习外语为主的“方言学堂”,以培养近代工商贸易和技术人才为主的“自强学堂”,以培养新军干部为目标的“武备学堂”等。
甲午战后,张之洞根据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和当时的教育状况,认为必须培养大批能“察临国之政,通殊方之学”,为各方面所需的高级“通才”以经世济民。他认为“西学既极邃密,西书又极浩繁,探讨诚非易事。自强之道,贵能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既不能多读西书,若不能多读西书,既无从会通博采。本部堂再四推求,知舍普习洋文广储高才,以探西书精微,更无下手取法之处……”(札道员蔡锡勇改定自强学堂章程)这比他原来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认识又进了一步。
清光绪十九年(1893)张之洞奏准清廷创办以学习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理工各科为目标的“自强学堂”,任命蔡锡勇为“总办”(校长)。这所学堂的成立比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民国后改名北京大学)还早了五年。张之洞把校长重任交给蔡锡勇,是因为蔡氏是我国当时仅有的一位学贯中西,精通外语,对数理化等近代自然科学又者有深厚的基础,并且还在美国做过多年的职业外交官,熟谙西方国家的政治社会情况的人才,由他来出任中国第一所近代高校校长,可谓是深庆得人!
蔡氏受命之后,对自强学堂的学科和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方法、招生对象、学制年限、毕业去向、管理体制等诸方面,既秉承张之洞的办学精神,又参照西方国家高等学校的分科教学制度,把学制定为五年,招生对象是身家清白、资性聪颖、通晓儒书的15岁以上24岁以下有生员头衔的小官或官绅子弟,入学要经过初试、复试、面试和担保,在我国并率先废除膏伙制,实行奖学金制,按月考课,择优给奖。课程设置除各科主修课外,学生还兼及化学、地学、分析试验、经学、商学、法学、交涉、体操、兵操、劳动实习等课。蔡氏还把他自己发明的中文速记术——《传音快字》作为教材发给在堂学生学习。
八、担任武备学堂督办
——一生的光荣总结
蔡锡勇不仅对政治、经济、外交和近代自然科学具有很深的造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军事教育、兵器制度同样具有远见卓识,张之洞把所办的洋务实业,包括枪炮厂、鱼雷局、制造兵轮、开办水陆师学堂莫不交由蔡氏一人“总其成”。清末洋务派首领均为封疆大吏,对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侵略也都身受其害;他们认识到,依靠原有的汉军和八旗绿营的刀枪剑戟已难以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大炮兵舰,因此学习西方军事训练方法,编练一支能使用洋轮大炮和近代兵轮抵御外侮的新军成了当务之急。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张之洞在武汉创办了一所“武备学堂”(新军军官学校),并又把“督办”(校长)重任交给了蔡锡勇。此时的蔡氏,除了正式的官衔——“署汉黄德道、江汉关监督、赏二品顶戴”外,还负责所有各种洋务实业的主要领导,担任“自强学堂”和“武备学堂”的“总(督)办”,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他学贯中西,经文纬武,又具备近代大企业家的经营魄力,用“能者多劳”这个词已不足以说明蔡氏的非凡才干了。
在奉命担任武备学堂督办后,蔡氏同样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参考西方军官教育制度,制定武备学堂章程,延聘外国教官,确定招生对象等等。1896年冬,武备学堂正式开学,他渡江前往主持开学典礼,不意“船至中注,陡起大风,几将覆溺”,救起后“得类中风之症”,但“仍力疾总理各局厂事务……不遗余力”,终因“百务丛集,劳瘁过甚旧疾复发,顷刻身故”。就在“其疾作之前数刻,犹复手书致武备学堂洋教习详论学生课程,事理周密,即于是日夜间病故……”(《为蔡锡勇请恤折》)
张之洞在这份《请恤折》中,除了历述蔡锡勇在其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任上协助创办许多洋务实业及担任文武两所高校“总办”的重大贡献外,对他的品德操守待人接物又作了这样的评价:“……查该故道志操廉正,器识闳深,博通泰西语言文字,精究天文、格致、测算等学,于各国外政,畅悉利病源流;而天怀淡泊,任事月诚,凡各国领事江海税司以及矿师洋匠、中西商贾,莫不钦其耿介,服其明达。遇交涉重要繁难之事,他人棘手莫办者,该故道靡下迎刃而解。所办铁、布、枪炮各局厂,经手款项多至数百万两,力杜虚靡,丝毫不苟……”去世消息传出后,“各国洋报流传,威加惋惜伤悼,异口同声……”张之洞则慨叹蔡氏故后“微臣失此臂助,极目时艰,人才罕见,尤不能不为国家惜此人矣!蔡氏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不仅令后人敬仰,而其高风亮节更是值得称道。此时,蔡锡勇已是官至“赏二品顶戴”的道员大臣,又统管华中地区财税大权的江汉关监督及数十所近代大型工矿企业的主管领导,然而“迨其殁也”,竟然“囊无馀蓄旅殡难归”,这在清末腐败成风的官场中,又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光绪帝在《请恤折》上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清廷除了从优抚恤外,还追赠其为内阁学士。身后殊荣,在晚清去世的名士显宦中,也并不多见。
张之洞的《请恤折》上奏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五日(1898年5月5日),推算蔡氏逝世当在1898年2、3月间(此时距《传音快字》出版尚不到两年),终年仅51岁。英年早逝,殊堪惋惜,深信若得假以天年,他对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和经济实业的发展必然还能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文献信息速记会理事)
“自强学堂”成立之初,即由张之洞委任署汉黄德道蔡锡勇为“总办”(校长)。蔡毕业于北京同文馆,曾随清廷首任驻美利坚合众国钦差大臣(现称特命全权大使)陈兰彬(荔秋)赴美任译官、参赞,为我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回国后旋被两广总督张之洞罗致入幕,协助张办理涉外事务(任洋务局委员)及各种洋务实业,深受张的赏识和重用。蔡还根据英文速记原理创制中文速记(著《传音快字》),并最早把西方复式会计介绍、引进并取代我国传统的四柱帐法(著《连环帐谱》)。对于这样一位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发展史上及财务管理制度方面作出过开创性贡献的学者,其生平却是鲜为人知!笔者近年来受有关方面的委托,在搜集整理蔡锡勇史料时,深深为其道德文章所感动,援引文献记载草成此文以飨读者,并就正于有关学科方面的专家学者。
一、早期学习近代外国语文的汉人子弟
蔡锡勇(1847-1898)字毅若,祖籍福建龙溪,关于蔡的先世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估计很可能出生于广州的一个小商人家庭。
1840年鸦片战争,二千年来闭关自守的封建王朝的大门终于被英帝国主义挟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与船坚炮利的优势撞开了。随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势力日益加剧,清王朝经过国内太平天国的起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外国侵略势力逐渐扩大到中国沿海各省,并且深入到内地,中外接触日益频繁,封建文化已难以与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相对抗,清王朝急需培养能直接与洋人对话交流的翻译人才,以辅佐政府的外事交涉活动。在当时清廷主管外交工作的恭亲王奕訢的建议下,我国第一所学习外国语言的学校——北京同文馆于1862年(清同治元年)正式开办了,隶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政府外务部前身)。此后第二年、第三年在当时已辟为对外通商口岸的上海与广州也相继成立与北京同文馆同样性质的语言学校——广方言馆(也称同文馆),此时年方17岁的青年蔡锡勇考入了广州同文馆,成为我国第一批正式学习近代外国语言的汉人子弟。
二、青年时期的外语学习生活
北京同文馆成立之初,开设了英、法、俄三个语种,并只招收14岁以下八旗子弟入学。过了三年,始又陆续增设德、日文班以及西方近代科学天文、数学、万国公法、测量、医学生理、物理、化学等课程;入学资格、年龄也放宽为满汉兼收15至25岁的青少年。北京是当时清王朝的统治中心,中外交往尚只限于官方政治往来,远不如上海、广州等沿海通商口岸那样与西方文化、宗教、工商贸易普遍接触交流,稍后于北京同文馆成立的上海、广州两处同文馆(广方言馆)入学的学生素质水平并不逊于北京同文馆的学生,因此三地同文馆学生互相进行交流学习并进一步择优深造就有了可能。
1867年10月15日(清同治六年九月十五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亲王奕訢上奏清廷《片》中称:
“兹查上海、广州两处所设学馆(即指广方言馆)已届三年,其中子弟所学,即或未能深粹,而通其语言文字者谅不乏人。臣衙门开馆伊迩,若于该学生中择其已有成效者咨送来京考试,与臣衙门本年所考各员共为讲解,必可得力。应请旨饬下上海通商大臣、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将各该处所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内择其已有成效者,每省各送数名来京考试……”(《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
遵照这份奏片的要求,广州同文馆选送了蔡锡勇、那三、博勒洪武、韩常泰、左秉隆、坤扬等六名满汉学生赴京参加北京同文馆主办的英文考试。在这次考试中,蔡锡勇显示了卓越的外语才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是考试后唯一获得“监生”称号的学生。奕訢就这次考试的成绩所上的奏折中说:“兹于同治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准署广州将军庆春等将该省同文馆学生蔡锡勇……等六名咨送到臣衙门……该学生等文理俱各明顺,学习有年,深堪造就,应请照上年奏定章程,蔡锡勇一名作为监生,那三……等五名作为翻译生员……”分别确定名次。
这次考试后,蔡锡勇等六人仍饬回广州同文馆继续学习,并具备充当翻译差使资格。
过了四年(1872同治十一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再次饬令上海广州两地同文馆选送优秀学生去京考试深造。此时年已25岁的蔡锡勇以“福建龙溪县监生、翻译官”的身份又被列入去京考试深造人员名单。蔡锡勇和那三、左秉隆等三人以原已在同治六年去京考试取得优异成绩为由,要求此次以“保举”名义免试入学,旋经同意,于同年9月22日由广州同文馆咨送到京。
此时,北京同文馆历经扩充,已逐渐从一所单纯的语言学校向近代综合性大学转变并初具规模,学制、入学年龄、资格均有较大改变,外语各班三年毕业,由外文而及天文、数学等理工各科者八年毕业。蔡锡勇的英语水平已能从事笔译口译,直接听洋教习外语授课。他在北京同文馆同时选修多门学科,并成为馆中唯一的汉人数学家教习李善兰的高足。同治十三年(1874),年已27岁的蔡锡勇以各科共列优等(按成绩相当于现在的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同文馆。
因此,就这一点而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是由语言学校开始起步的。
三、第一代职业外交官成员
清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开始正式按西方国际关系制度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派出驻外使节。同年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上谕委派赏二品顶戴、刑部郎中、太常寺卿陈兰彬(荔秋)为首任出使美利坚合众国(兼领秘鲁、日本)钦差大臣(即特命全权大使)。蔡锡勇以北京同文馆优等毕业生最佳外语人才被陈兰彬罗致担任译官,随使出洋。抵美不久,又以工作成绩表现出色,极受钦差赏识,奏准以“候选通判”升任参赞。1884年(光绪九年)丁忧回国。守制期满,即被两广总督张之洞延揽入幕,参与在广东兴办的洋务实业活动,结束了他的职业外交官生涯。
四、撰成我国第一本速记专著
——《传音快字》
蔡锡勇在驻美钦差公署任职期间,极大地丰富了他对西方文明的了解。作为一个在典型封建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开始对西方文化中的一些技术科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考虑其中是否也能为中国古老的儒学文化所用。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官,首先使他感到惊奇的是西方国家的速记术。他在撰成我国第一本速记教科书《传音快字.自序》中这样写道:
“余昔随陈荔秋副宪出使美、日、秘三国,驻华盛顿四年。翻译之暇,时考察其政教风俗,尝观其议政事,判词讼,大庭广众,各持一说,反复辩论,杂沓纷纭,事毕各散,而众论异同,业皆传播,记录稠叠,稿堂盈寸,揣其必有捷法,继询彼邦人士,始知有‘快字’一种,行之已久,作者不一家,师承各异,然皆能笔随口述,不假思索,手不停挥,率每分钟能作二百余字……。”
在这段文字中,蔡锡勇叙述了他发现西方国家有一种“行之已久”的“快字”,(Shorthand,近代西方国家速记术起源于16世纪末之英国,最早用于记录国会议员之演说辩论)并且有多种方式(“作者不一家”),但都能做到“笔随口述”,每分钟“能作二百余字”。那么能否把这种方式移植过来为中文所用呢?他开始构思这个设想,当然首先他自已要学会这门科学技术。
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虽然立国还不过一个世纪,但是它的经济已经迅速赶上和超过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大量的欧洲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众多的黑人后裔以及亚洲移民又为开拓西部地区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而比较健全的议会民主政治与发达的文化科学、大量的对外贸易构成了这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国力,此时在西方国家已流行数百年的速记术也广泛应用于美国社会。
关于蔡锡勇学习英文速记和创制中文速记的经过,在其幼子蔡璋把《传音快字》修订改编为《中国速记学》一书的《绪言》中写道:“……至一千八百八十二年美国凌士礼氏之速记术出,遂大得斯学界之欢迎,时中国前清光绪八年也。先君适随使美邦,因得尽通其术,迨归国后,益复研究古今音韵之学,参以西人卫三畏音歆字典等书,至光绪二十二年乃脱稿付梓,定名为传音快字……”
《传音快字》于1896年由湖北官书局镌印出版后,曾在由蔡锡勇兼任“总办”(校长)的“自强学堂”(1893年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汉创办的我国第一所按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分科进行教学的高校)中进行教学。至于正式把《传音快字》(《中国速记学》作为我国最早的一种速记方式来进行教学并付诸实际应用,已是清末。当时为筹划实行君主立宪成立议会(称“资政院”即一院制国会)需大批速记人员,清廷征召蔡璋赴京担任资政院速记学堂总教习(校长),为中央、省、县各级议会培训速记人才。从清末资政院、民国北洋政府国会到南京政府立法院,蔡氏父子发明的中文速记术开创我国早期速记应用的范例,蔡璋本人还三任速记长。蔡氏父子并先后受到民国北洋政府大总统多次题匾授勋特令褒奖。
五、张之洞办洋务的主力干将
张之洞是清末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直隶南皮人(今河北省)他与项城袁世凯、玉林岑春煊并称清末三大吏,但其利国利民的成就,政绩则远过于袁、岑。他所兴办的洋务实业,与为培育人才开办文武学堂、主张文事武备并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反对戊戌变法等,尽管他的学说主张有其矛盾错误的一面,但是就其总的成就来看,在19世纪后半期的清代封疆大吏中,仍不失为一个头脑清新卓有远见的大人物。他发现并重用蔡锡勇并使之成为其在洋务运动中兴业办学的主力干将,与起用冯子材在1884年中法战争中击败法帝国主义,同为张之洞“知人善任”的两个典型例子。
蔡锡勇的后半生一直追随张之洞兴办洋务实业、教育培养人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因此在叙述蔡锡勇的史绩时,不能不提到张蔡之间的“恩遇”关系。在《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卒谥文襄)中,《奏稿》部分占有较大篇幅,其中为蔡锡勇所上的专折就有《蔡锡勇留粤补用片》、《保荐蔡锡勇片》、《为蔡锡勇请恤折》等,在《公牍》部分有《札道员蔡锡勇改定自强学堂章程》,其它文稿提及蔡锡勇事或与其有关者更不下数十处之多,足见张、蔡之间的密切关系了。
1885年2月(光绪十年十二月)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拒绝新任驻日钦差大臣徐承祖咨调蔡锡勇出任参赞的要求。在上清廷《蔡锡勇留粤补用片》中称:粤东官吏,结识洋人者甚多,而讲求洋务者甚少。向来号称熟习洋务者,非学识粗浅,即品行猥杂。唯蔡锡勇,志向端谨,才识精详,因专派充当洋务局委员,承办各事,均能深明大体,动协机宜,实为办理洋务不可多得之员……”请求“准将三品衔候选知府蔡锡勇留粤差遗,实于粤省洋防,大有裨益”。光绪帝在这份奏折上朱批:“著照所请”。蔡锡勇在广东任职期间,除了担任洋务局委员,负责对外交涉事宜外,张之洞还把所兴办的洋务实业“……开设银元局、枪弹厂、水陆师学堂、鱼雷局及制造兵轮等事,悉以咨之”,足见对蔡倚赖信任之深。
1889年(光绪十五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蔡锡勇随调湖北差遣委用。“……到鄂以来,派委总办铁政局,设立化学堂,定汉阳铁厂之基,枪炮厂即附其中。督饬矿师洋匠建厂安机,开办矿山运道,铁矿灰石水陆码头,兴国锰矿,江夏大冶煤井煤矿及采运湘煤诸务,自经始以至工竣开炼,千端万绪,布置井井,罔有遗漏。臣以督工筹款,艰巨烦难,叠经奏明,就湖北铁、布、枪炮三厂,通筹互济,先后国委该员总办织布、枪炮两局,任事诚恳,殚竭心力,条分缕析,事事力求撙节核实,不避劳怨,端谨廉退,丝毫不苟,和平默讷,不与人争。三厂分局二十余所,委员学生林立,群莫敢以私;各矿师洋匠,亦服其公正,无不尽心效力,办理悉臻周妥……”
根据这份1894年11月4日(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七日)所上《保荐蔡锡勇片》中所述,蔡的经营才能即使与现代西方、日本等国的大企业家相比也毫不逊色。今之企业家只是单纯在一种企业上创基立业,发展光大,而蔡氏所办的企业则包括轻重工业的冶金矿山、铁路交通、兵工造船、水陆航运等各种类型,对之均能做到指挥调度井然有序,连那些从国外聘请来的“矿师洋匠”也心悦诚服,尽心工作。这正是由于蔡在北京同文馆学习时,在原已有深厚的外语基础上,又进修了数理化等多门学科,积累了渊博的知识,从而为他在协助张之洞兴办各种洋务实业担任主管领导工作时,得以充分发挥自已的才能。张之洞在《保荐片》中,称赞“该员深通泰西语言文字,于格致(即近代物理——笔者注)测算,机器、商务、条约、外洋各国政事,无不详究研询,属通达事务,体用兼赅。臣所见办理洋务之员,其才品兼优,事事著实,实无有能出蔡锡勇之右者……”要求清廷“恩予破格录用”。光绪帝在这份奏折上“朱批:蔡锡勇著、交吏部带领引见”后,获“赏二品顶戴”。
六、引进西方复式会计科学的先驱
蔡锡勇对我国财务管理制度的改革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第一位引进介绍西方复式会计制度,撰成《连环帐谱》(“连环”即复式对应之意一一笔者)。
蔡氏在张之洞领导下兴办近代洋务实业,统管单位不下数十处,经手资金款项多达数百万两,虽“力杜虚靡丝毫不苟,”但在巨额资金运用中,又深感我国原有的传统会计制度——“四柱帐法”已难以适应在近代化大企业的财务管理中发挥作用。他早年在国外任职期间,发现西方国家的政府机关、金融机构以及工商企业均普遍采用复式会计制度记帐方法,其严密、科学、实用性远胜于我国旧式四柱帐法。于是他在创造中文速记术之后,工余又埋首钻研西方复式会计制度,但其原来的意图只是借以改良中式会计的记帐方法,使之能适应近代化企业大规模经济活动的需要。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蔡氏一部介绍西方复式会计的专著《连环帐谱》在经过其子蔡璋的补充修订之后,由湖北官书局印行出版。(此时蔡锡勇已作古)这部书成为我国推行西方复式会计的专著。郭道扬教授在其名著《中国会计史稿》中评价说:“蔡锡勇所著之《连环帐谱》既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介绍西式簿记的专著,也是第一次立足于中西帐法相结合,以达改良中式会计的目的,它是西式复式帐法引进的先导,是以后中式簿记改良的先声,它对推动我国近代会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七、中国近代高校第一位校长
张之洞在大办洋务实业的同时,又认识到兴办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初调湖广总督,他就上奏清廷请办各类文武学堂以广储人才。除筹建以学习经学为主的两湖书院外,先后在武汉创办以学习外语为主的“方言学堂”,以培养近代工商贸易和技术人才为主的“自强学堂”,以培养新军干部为目标的“武备学堂”等。
甲午战后,张之洞根据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和当时的教育状况,认为必须培养大批能“察临国之政,通殊方之学”,为各方面所需的高级“通才”以经世济民。他认为“西学既极邃密,西书又极浩繁,探讨诚非易事。自强之道,贵能取人所长,若非精晓洋文,既不能多读西书,若不能多读西书,既无从会通博采。本部堂再四推求,知舍普习洋文广储高才,以探西书精微,更无下手取法之处……”(札道员蔡锡勇改定自强学堂章程)这比他原来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认识又进了一步。
清光绪十九年(1893)张之洞奏准清廷创办以学习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理工各科为目标的“自强学堂”,任命蔡锡勇为“总办”(校长)。这所学堂的成立比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民国后改名北京大学)还早了五年。张之洞把校长重任交给蔡锡勇,是因为蔡氏是我国当时仅有的一位学贯中西,精通外语,对数理化等近代自然科学又者有深厚的基础,并且还在美国做过多年的职业外交官,熟谙西方国家的政治社会情况的人才,由他来出任中国第一所近代高校校长,可谓是深庆得人!
蔡氏受命之后,对自强学堂的学科和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方法、招生对象、学制年限、毕业去向、管理体制等诸方面,既秉承张之洞的办学精神,又参照西方国家高等学校的分科教学制度,把学制定为五年,招生对象是身家清白、资性聪颖、通晓儒书的15岁以上24岁以下有生员头衔的小官或官绅子弟,入学要经过初试、复试、面试和担保,在我国并率先废除膏伙制,实行奖学金制,按月考课,择优给奖。课程设置除各科主修课外,学生还兼及化学、地学、分析试验、经学、商学、法学、交涉、体操、兵操、劳动实习等课。蔡氏还把他自己发明的中文速记术——《传音快字》作为教材发给在堂学生学习。
八、担任武备学堂督办
——一生的光荣总结
蔡锡勇不仅对政治、经济、外交和近代自然科学具有很深的造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军事教育、兵器制度同样具有远见卓识,张之洞把所办的洋务实业,包括枪炮厂、鱼雷局、制造兵轮、开办水陆师学堂莫不交由蔡氏一人“总其成”。清末洋务派首领均为封疆大吏,对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的军事侵略也都身受其害;他们认识到,依靠原有的汉军和八旗绿营的刀枪剑戟已难以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大炮兵舰,因此学习西方军事训练方法,编练一支能使用洋轮大炮和近代兵轮抵御外侮的新军成了当务之急。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张之洞在武汉创办了一所“武备学堂”(新军军官学校),并又把“督办”(校长)重任交给了蔡锡勇。此时的蔡氏,除了正式的官衔——“署汉黄德道、江汉关监督、赏二品顶戴”外,还负责所有各种洋务实业的主要领导,担任“自强学堂”和“武备学堂”的“总(督)办”,这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他学贯中西,经文纬武,又具备近代大企业家的经营魄力,用“能者多劳”这个词已不足以说明蔡氏的非凡才干了。
在奉命担任武备学堂督办后,蔡氏同样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参考西方军官教育制度,制定武备学堂章程,延聘外国教官,确定招生对象等等。1896年冬,武备学堂正式开学,他渡江前往主持开学典礼,不意“船至中注,陡起大风,几将覆溺”,救起后“得类中风之症”,但“仍力疾总理各局厂事务……不遗余力”,终因“百务丛集,劳瘁过甚旧疾复发,顷刻身故”。就在“其疾作之前数刻,犹复手书致武备学堂洋教习详论学生课程,事理周密,即于是日夜间病故……”(《为蔡锡勇请恤折》)
张之洞在这份《请恤折》中,除了历述蔡锡勇在其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任上协助创办许多洋务实业及担任文武两所高校“总办”的重大贡献外,对他的品德操守待人接物又作了这样的评价:“……查该故道志操廉正,器识闳深,博通泰西语言文字,精究天文、格致、测算等学,于各国外政,畅悉利病源流;而天怀淡泊,任事月诚,凡各国领事江海税司以及矿师洋匠、中西商贾,莫不钦其耿介,服其明达。遇交涉重要繁难之事,他人棘手莫办者,该故道靡下迎刃而解。所办铁、布、枪炮各局厂,经手款项多至数百万两,力杜虚靡,丝毫不苟……”去世消息传出后,“各国洋报流传,威加惋惜伤悼,异口同声……”张之洞则慨叹蔡氏故后“微臣失此臂助,极目时艰,人才罕见,尤不能不为国家惜此人矣!蔡氏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不仅令后人敬仰,而其高风亮节更是值得称道。此时,蔡锡勇已是官至“赏二品顶戴”的道员大臣,又统管华中地区财税大权的江汉关监督及数十所近代大型工矿企业的主管领导,然而“迨其殁也”,竟然“囊无馀蓄旅殡难归”,这在清末腐败成风的官场中,又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光绪帝在《请恤折》上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清廷除了从优抚恤外,还追赠其为内阁学士。身后殊荣,在晚清去世的名士显宦中,也并不多见。
张之洞的《请恤折》上奏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五日(1898年5月5日),推算蔡氏逝世当在1898年2、3月间(此时距《传音快字》出版尚不到两年),终年仅51岁。英年早逝,殊堪惋惜,深信若得假以天年,他对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和经济实业的发展必然还能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文献信息速记会理事)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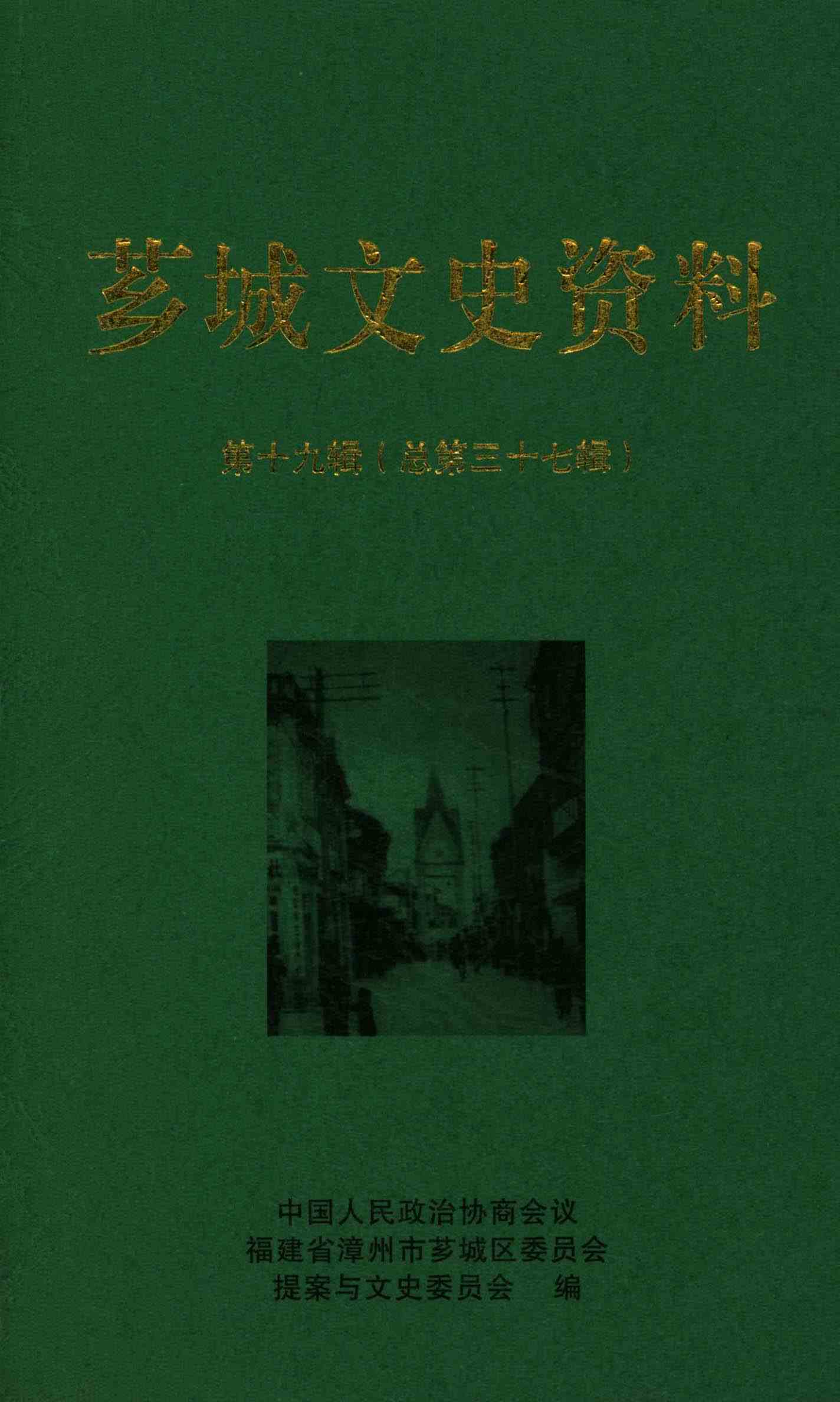
《芗城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本书收录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委员会提案与文史委员会编写的芗城文史资料第十九辑,内容包含了前言,故地踪影,往事寻踪,人物春秋,姓氏选登,民俗记述,台岛践履,文献集萃,后记等反映漳州市中心城区的人文地理、物产风俗,反映社会的风貌。
阅读
相关人物
葛继圣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