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御巷的历史变迁
| 内容出处: | 《芗城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20005201 |
| 颗粒名称: | 待御巷的历史变迁 |
| 分类号: | K928.655 |
| 页数: | 7 |
| 页码: | 19-25 |
| 摘要: | 说起“刣猪巷”(台:音台[tai],闽南话宰杀的意思。),三十岁以下的漳州人会一脸茫然,不知所云。这也难怪,掐指算来,台猪巷已经从九龙江消失了二十多年了。刣猪巷,正确的写法是待御巷,因闽南话谐音,口口相传,讹化为刮猪巷,以致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那是一处专事屠宰的巷子。乾隆一听龙颜大悦,即兴命名此地为“待御巷”。目前尚未查出实据,有待以后的发掘与考究。这些山珍海味在三台洲经过初步加工,随即批发销售出去。 |
| 关键词: | 待御巷 漳州 |
内容
说起“刣猪巷”(台:音台[tai],闽南话宰杀的意思。),三十岁以下的漳州人会一脸茫然,不知所云。这也难怪,掐指算来,台猪巷已经从九龙江消失了二十多年了。
刣猪巷,正确的写法是待御巷,因闽南话谐音,口口相传,讹化为刮猪巷,以致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那是一处专事屠宰的巷子。有关待御巷名字由来的民间故事,流行多种版本的说法,都与皇帝有关,脍炙人口且流传较广的是:乾隆皇帝游江南时,船队经过南门溪时,见溪边洗衣妇一个个跪着观望,乾隆不懂闽南妇女是用跪姿洗衣服的,便问随从这些妇人在做什么?地方官员急中生智,乘机奉承道:“这是民女跪着迎候皇上。”乾隆一听龙颜大悦,即兴命名此地为“待御巷”。
这则民间传说生动有趣,流传久远。在认真的人看来,却不以为然,或认为是荒诞不经。因为乾隆皇帝从未到过漳州,这是无庸置疑的。但历史的某些真相常常隐含在悠久的传说之中,由于传说的不确定性,一些很珍贵的历史片断被貌似荒诞不经的表象所掩盖。待御巷究竟与皇室有无瓜葛?或与哪一朝代的钦差、御史有何关联?目前尚未查出实据,有待以后的发掘与考究。
待御巷实际上也不是人们想象的古城中街坊里弄,而是一块沙洲。确切地说,是位于漳州旧城南门溪的一片水中陆地。据《漳州府志》、《龙溪县志》记载,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洪水又一次袭击漳州城,南门溪露出三台洲,时任漳州知府韩擢因此将郡城南门更名为“三台门”。并择址三台洲下游处的方壶洲新建一桥,称文昌桥,就是后来所说的“新桥”,南桥也就叫做“旧桥”(后称中山桥)。三台洲也就是三块沙洲,凭着优越的地理位置,三台洲成为船家首选的泊岸码头,很快形成聚居群落,并有了各自的地名,北侧的叫烧灰巷,中间的叫待御巷,南边的叫船寮(也叫刺竹脚、桥仔脚)。
三台洲位于漳州城南门溪流之中,上有桥梁连通两岸,构成水陆纵横交错交通枢纽,水运航线连接山海,西接永定、南靖、平和,东达石码、海澄、直至出海漂洋,到台湾岛、南洋诸岛。陆路过旧桥,经南驿道直通漳浦、诏安、潮州、汕头等地。三台洲地理位置如此得天独厚,形成一处天然停泊码头,是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在历史上曾是人流繁忙,生意兴隆的河埠,也是人口稠密的聚居区。三洲数中洲即待御巷最为繁荣,环洲皆是泊位,舟楫云集。西溪上游的笋干、香菇、木耳、干菜、花生、土纸、松香等山货顺水源源运抵三台洲,下游的蚵、蛏、干贝、鱿鱼、虾、蟹、鲍鱼、海参、紫菜等海产品逆流而来。这些山珍海味在三台洲经过初步加工,随即批发销售出去。一些需要大量用水的作坊,如皮革鞣制、布匹漂染也选址于此。造船修船作坊更是得天独厚,小小沙洲竟有数家船寮。三台洲顿时作坊林立,商肆鳞次栉比,俨然是一个水中工商贸易集镇。烧灰巷有多家灰窑,将大量遗弃的蚵壳煅烧成白灰粉,这是一门长盛不衰的行当,上世纪六、七十的年代,烧灰巷的灰窑还一片繁忙景象。
三台洲自古有“洲滨浮龙”之誉,近水得利,同时也因水受灾。频繁的大水让三台洲蒙受严重损失,甚至遭致灭顶之灾!特别是光绪三十年农历甲辰六月初四至初六(公元1904年7月16日至18日)暴雨三天,九龙江西、北二溪洪水滔天,漳州城上游南靖、平和屋塌人亡,洪水冲溃堤堰,涌入漳州城,水漫街巷,数日不退。旧桥两侧行铺都被洪水冲走,待御巷的作坊宅院几乎被夷为平地,巷内社庙“开山太保公庙”三尊神像漂走了二尊,有一尊神奇地留在原地。大水退后,社里家长在下游的诗墩社和港西社分别寻到漂走的二尊神像,经卜珓,神示愿留在新址安座,大家就恭敬不如从命。从此,“开山太保公庙”一分为三,受到三社信众的祀奉。待御巷为纪念此次大劫难,将六月初六定为平安日,每逢六月初六,每家每户都要上“开山太保公庙”焚香献供,祈求平安。可天不遂人愿意,仅过了四年,即光绪三十四年,大水再呈凶猛,新、旧两桥全被冲毁,待御巷和烧灰巷民宅中平房水近中梁,楼房的楼板水深三尺,两巷人家再一次受足了惊吓。
每次大水过后,沙洲上的人们都能很快恢复生机,各行各业迅速重整旗鼓,照旧操持,又是一派繁忙景象。这里的居民,相当多的是渔民、船民的后代,由渔猎或航运到三台洲停泊,或交易或装卸,一些头脑活络者或精于盘算者或心灵手巧者,便上岸开铺设坊,作起岸上生意,久而久之便成了巷底居民。他们也许还是古越民中胥民的后裔,《辞源》对疍民的定义是:“古代南方水上居民,也作‘置户’。”《漳州府志》记载:“南北溪有水居之民,维舟于岸,为人通往来,输货物,俗称泊水。”一些志籍在描述胥民时都用“习水,善舟楫。”赞许之词。古代漳州沿海渔民和九龙江流域的船民就享有很高的声誉,明代就流行“看针把舵过洋,须用漳人。”的普遍说法,可见漳州的水上居民具有过硬的航海本领和超人的水上技能。明初郑和下西洋时,其庞大舰队中的水手和舵手,几乎都是从漳、泉二州招募的。明末之际,郑成功以漳州水手为骨干组建水军,骁勇善战的水军屡屡打败清军,依靠强悍的水军,郑氏军事力量驰骋于漳泉厦台之间,与清军对峙周旋长达四十年。
沧海桑田,九龙江淤积年年有增无减,抗日战争初期,当局于镇头宫水域筑水下封锁障碍坝,航道出现萎缩。1973年,西溪闸建成,航运不能正常运转。1982年,九龙江航运全线宣告终止。
停泊待御巷的船只少了,作坊商铺相继关门了,繁忙的河趸变成了纯粹的住宅区,居民仿佛与船失去了必然的联系,但巷里长大的孩子们个个如水中蛟龙,水性娴熟程度超乎常人。每遭大水围困,家中缺少食物时,少年小伙便会一头扎入湍急的洪流中泅渡上岸,进城买齐后,单手托举食物在汹涌的浪滔中泅渡回家,令城内人望尘莫及,自叹弗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家住待御巷的林氏三姐弟入选省游泳队参加全国游泳比赛,姐姐还取得全国比赛项目的冠军,弟弟长期在国家游泳中心从事训练教学。
1985年,漳州市政府通盘考虑到泄洪需要和待御巷居民的安全,决定整体搬迁待御巷,新址选在南岸双庵路东端的田地,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建,新居住区很快落成,新址按居民的提议命名为“待御巷新村”。年底全部居民乔迁完毕,大家分住二栋公寓式楼房,一起欢度丙寅年(1986年)春节。这年的夏天,洪水再度来临,淹没了旧桥,六月初六,“待御巷新村”的居民大放鞭炮,庆幸从此摆脱洪水的威胁。
热心的居民还自愿将社庙“开山太保庙”的神祗和二通清代石碑搬到新址,安放在居民捐出的三间柴火间内。1990年,虔诚的巷底居民信众出资捐物稍稍扩建了新的太保庙,依旧主祀开山太保公,配祀观世音菩萨、伽蓝爷、土地公,还有平安公。主神太保公的来历,巷内老住户们语焉不详。九龙江下游出海口鸿渐村有一座太保公庙,庙门上有一副对联:“著千古之功勋职封太保,济万民乎黎庶德重风山”。庙内并祀二尊太保公,大太保为郑和,二太保是王景弘,二位都是明朝初期西洋舰队的统帅。当年跟随舰队到南洋的明军兵士的后裔落籍成为侨民,为纪念郑和的功德及恩惠,旅外侨胞便在侨居地为他修建庙宇、雕塑神像、供奉祭拜。鸿渐村旅菲侨胞甚多,侨胞屡见海外均有郑和庙宇,而家乡没有,为感恩郑和给家乡带来的功德,明末清初年间,旅菲的鸿渐侨胞把在南洋供奉的郑和画像带回家乡奉祀,在该村西面建一座庙宇,村民称为“太保公庙”,并把每年农历八月廿三日作为郑和纪念日,俗称为“华侨节”。待御巷同样是船民聚居地,与上下游的船民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居民的先辈就是直接来自于西溪上下游的水上人家,开山太保公庙所祀的太保公,是否也是郑和?由此推断,似乎顺理成章,但无确凿的依据,尚不能擅下定论。
2007年,开山太保庙的另一通碑石,几经辗转回到庙内。现存的三通碑刻记录了待御巷曾经的繁荣,是三台洲历史进程中某一横断面的真实写照。是研究漳州航运史、手工业史和清代社会治安管理制度的难得素材和佐证,也是漳州与台湾之间往来密切的证物。如《道光二十二年》碑文“---漳泉台湾各府工商营生,路经山城及沿河至---”此段文字明白无误地证实,九龙江流域曾是维系海峡两岸血脉和文脉的枢纽,沿江的市镇是承载山海物质和文化交流交融的福地,漳州大地所蕴藏的人文信息是闽南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想当年,少年林语堂,从平和坂仔家中后门登上一叶小舟,出双溪,入花溪,顺流而下,经山城和靖城,过天宝,一帆顺风,泛舟到达旧桥待御巷,曾稍停片刻,漫步待御巷坊铺之间,耳闻南腔北调,眼观山珍海味,竟流连忘返,一直到船家追来催请……
物换星移,待御巷新村转眼间走过了二十二个春秋,现已列入南山公园的规划蓝图,又要面临再一次搬迁了,“待御巷”这一个漳州老地名将再一次载入新的内容。
刣猪巷,正确的写法是待御巷,因闽南话谐音,口口相传,讹化为刮猪巷,以致很多人想当然地以为那是一处专事屠宰的巷子。有关待御巷名字由来的民间故事,流行多种版本的说法,都与皇帝有关,脍炙人口且流传较广的是:乾隆皇帝游江南时,船队经过南门溪时,见溪边洗衣妇一个个跪着观望,乾隆不懂闽南妇女是用跪姿洗衣服的,便问随从这些妇人在做什么?地方官员急中生智,乘机奉承道:“这是民女跪着迎候皇上。”乾隆一听龙颜大悦,即兴命名此地为“待御巷”。
这则民间传说生动有趣,流传久远。在认真的人看来,却不以为然,或认为是荒诞不经。因为乾隆皇帝从未到过漳州,这是无庸置疑的。但历史的某些真相常常隐含在悠久的传说之中,由于传说的不确定性,一些很珍贵的历史片断被貌似荒诞不经的表象所掩盖。待御巷究竟与皇室有无瓜葛?或与哪一朝代的钦差、御史有何关联?目前尚未查出实据,有待以后的发掘与考究。
待御巷实际上也不是人们想象的古城中街坊里弄,而是一块沙洲。确切地说,是位于漳州旧城南门溪的一片水中陆地。据《漳州府志》、《龙溪县志》记载,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洪水又一次袭击漳州城,南门溪露出三台洲,时任漳州知府韩擢因此将郡城南门更名为“三台门”。并择址三台洲下游处的方壶洲新建一桥,称文昌桥,就是后来所说的“新桥”,南桥也就叫做“旧桥”(后称中山桥)。三台洲也就是三块沙洲,凭着优越的地理位置,三台洲成为船家首选的泊岸码头,很快形成聚居群落,并有了各自的地名,北侧的叫烧灰巷,中间的叫待御巷,南边的叫船寮(也叫刺竹脚、桥仔脚)。
三台洲位于漳州城南门溪流之中,上有桥梁连通两岸,构成水陆纵横交错交通枢纽,水运航线连接山海,西接永定、南靖、平和,东达石码、海澄、直至出海漂洋,到台湾岛、南洋诸岛。陆路过旧桥,经南驿道直通漳浦、诏安、潮州、汕头等地。三台洲地理位置如此得天独厚,形成一处天然停泊码头,是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在历史上曾是人流繁忙,生意兴隆的河埠,也是人口稠密的聚居区。三洲数中洲即待御巷最为繁荣,环洲皆是泊位,舟楫云集。西溪上游的笋干、香菇、木耳、干菜、花生、土纸、松香等山货顺水源源运抵三台洲,下游的蚵、蛏、干贝、鱿鱼、虾、蟹、鲍鱼、海参、紫菜等海产品逆流而来。这些山珍海味在三台洲经过初步加工,随即批发销售出去。一些需要大量用水的作坊,如皮革鞣制、布匹漂染也选址于此。造船修船作坊更是得天独厚,小小沙洲竟有数家船寮。三台洲顿时作坊林立,商肆鳞次栉比,俨然是一个水中工商贸易集镇。烧灰巷有多家灰窑,将大量遗弃的蚵壳煅烧成白灰粉,这是一门长盛不衰的行当,上世纪六、七十的年代,烧灰巷的灰窑还一片繁忙景象。
三台洲自古有“洲滨浮龙”之誉,近水得利,同时也因水受灾。频繁的大水让三台洲蒙受严重损失,甚至遭致灭顶之灾!特别是光绪三十年农历甲辰六月初四至初六(公元1904年7月16日至18日)暴雨三天,九龙江西、北二溪洪水滔天,漳州城上游南靖、平和屋塌人亡,洪水冲溃堤堰,涌入漳州城,水漫街巷,数日不退。旧桥两侧行铺都被洪水冲走,待御巷的作坊宅院几乎被夷为平地,巷内社庙“开山太保公庙”三尊神像漂走了二尊,有一尊神奇地留在原地。大水退后,社里家长在下游的诗墩社和港西社分别寻到漂走的二尊神像,经卜珓,神示愿留在新址安座,大家就恭敬不如从命。从此,“开山太保公庙”一分为三,受到三社信众的祀奉。待御巷为纪念此次大劫难,将六月初六定为平安日,每逢六月初六,每家每户都要上“开山太保公庙”焚香献供,祈求平安。可天不遂人愿意,仅过了四年,即光绪三十四年,大水再呈凶猛,新、旧两桥全被冲毁,待御巷和烧灰巷民宅中平房水近中梁,楼房的楼板水深三尺,两巷人家再一次受足了惊吓。
每次大水过后,沙洲上的人们都能很快恢复生机,各行各业迅速重整旗鼓,照旧操持,又是一派繁忙景象。这里的居民,相当多的是渔民、船民的后代,由渔猎或航运到三台洲停泊,或交易或装卸,一些头脑活络者或精于盘算者或心灵手巧者,便上岸开铺设坊,作起岸上生意,久而久之便成了巷底居民。他们也许还是古越民中胥民的后裔,《辞源》对疍民的定义是:“古代南方水上居民,也作‘置户’。”《漳州府志》记载:“南北溪有水居之民,维舟于岸,为人通往来,输货物,俗称泊水。”一些志籍在描述胥民时都用“习水,善舟楫。”赞许之词。古代漳州沿海渔民和九龙江流域的船民就享有很高的声誉,明代就流行“看针把舵过洋,须用漳人。”的普遍说法,可见漳州的水上居民具有过硬的航海本领和超人的水上技能。明初郑和下西洋时,其庞大舰队中的水手和舵手,几乎都是从漳、泉二州招募的。明末之际,郑成功以漳州水手为骨干组建水军,骁勇善战的水军屡屡打败清军,依靠强悍的水军,郑氏军事力量驰骋于漳泉厦台之间,与清军对峙周旋长达四十年。
沧海桑田,九龙江淤积年年有增无减,抗日战争初期,当局于镇头宫水域筑水下封锁障碍坝,航道出现萎缩。1973年,西溪闸建成,航运不能正常运转。1982年,九龙江航运全线宣告终止。
停泊待御巷的船只少了,作坊商铺相继关门了,繁忙的河趸变成了纯粹的住宅区,居民仿佛与船失去了必然的联系,但巷里长大的孩子们个个如水中蛟龙,水性娴熟程度超乎常人。每遭大水围困,家中缺少食物时,少年小伙便会一头扎入湍急的洪流中泅渡上岸,进城买齐后,单手托举食物在汹涌的浪滔中泅渡回家,令城内人望尘莫及,自叹弗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家住待御巷的林氏三姐弟入选省游泳队参加全国游泳比赛,姐姐还取得全国比赛项目的冠军,弟弟长期在国家游泳中心从事训练教学。
1985年,漳州市政府通盘考虑到泄洪需要和待御巷居民的安全,决定整体搬迁待御巷,新址选在南岸双庵路东端的田地,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建,新居住区很快落成,新址按居民的提议命名为“待御巷新村”。年底全部居民乔迁完毕,大家分住二栋公寓式楼房,一起欢度丙寅年(1986年)春节。这年的夏天,洪水再度来临,淹没了旧桥,六月初六,“待御巷新村”的居民大放鞭炮,庆幸从此摆脱洪水的威胁。
热心的居民还自愿将社庙“开山太保庙”的神祗和二通清代石碑搬到新址,安放在居民捐出的三间柴火间内。1990年,虔诚的巷底居民信众出资捐物稍稍扩建了新的太保庙,依旧主祀开山太保公,配祀观世音菩萨、伽蓝爷、土地公,还有平安公。主神太保公的来历,巷内老住户们语焉不详。九龙江下游出海口鸿渐村有一座太保公庙,庙门上有一副对联:“著千古之功勋职封太保,济万民乎黎庶德重风山”。庙内并祀二尊太保公,大太保为郑和,二太保是王景弘,二位都是明朝初期西洋舰队的统帅。当年跟随舰队到南洋的明军兵士的后裔落籍成为侨民,为纪念郑和的功德及恩惠,旅外侨胞便在侨居地为他修建庙宇、雕塑神像、供奉祭拜。鸿渐村旅菲侨胞甚多,侨胞屡见海外均有郑和庙宇,而家乡没有,为感恩郑和给家乡带来的功德,明末清初年间,旅菲的鸿渐侨胞把在南洋供奉的郑和画像带回家乡奉祀,在该村西面建一座庙宇,村民称为“太保公庙”,并把每年农历八月廿三日作为郑和纪念日,俗称为“华侨节”。待御巷同样是船民聚居地,与上下游的船民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居民的先辈就是直接来自于西溪上下游的水上人家,开山太保公庙所祀的太保公,是否也是郑和?由此推断,似乎顺理成章,但无确凿的依据,尚不能擅下定论。
2007年,开山太保庙的另一通碑石,几经辗转回到庙内。现存的三通碑刻记录了待御巷曾经的繁荣,是三台洲历史进程中某一横断面的真实写照。是研究漳州航运史、手工业史和清代社会治安管理制度的难得素材和佐证,也是漳州与台湾之间往来密切的证物。如《道光二十二年》碑文“---漳泉台湾各府工商营生,路经山城及沿河至---”此段文字明白无误地证实,九龙江流域曾是维系海峡两岸血脉和文脉的枢纽,沿江的市镇是承载山海物质和文化交流交融的福地,漳州大地所蕴藏的人文信息是闽南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想当年,少年林语堂,从平和坂仔家中后门登上一叶小舟,出双溪,入花溪,顺流而下,经山城和靖城,过天宝,一帆顺风,泛舟到达旧桥待御巷,曾稍停片刻,漫步待御巷坊铺之间,耳闻南腔北调,眼观山珍海味,竟流连忘返,一直到船家追来催请……
物换星移,待御巷新村转眼间走过了二十二个春秋,现已列入南山公园的规划蓝图,又要面临再一次搬迁了,“待御巷”这一个漳州老地名将再一次载入新的内容。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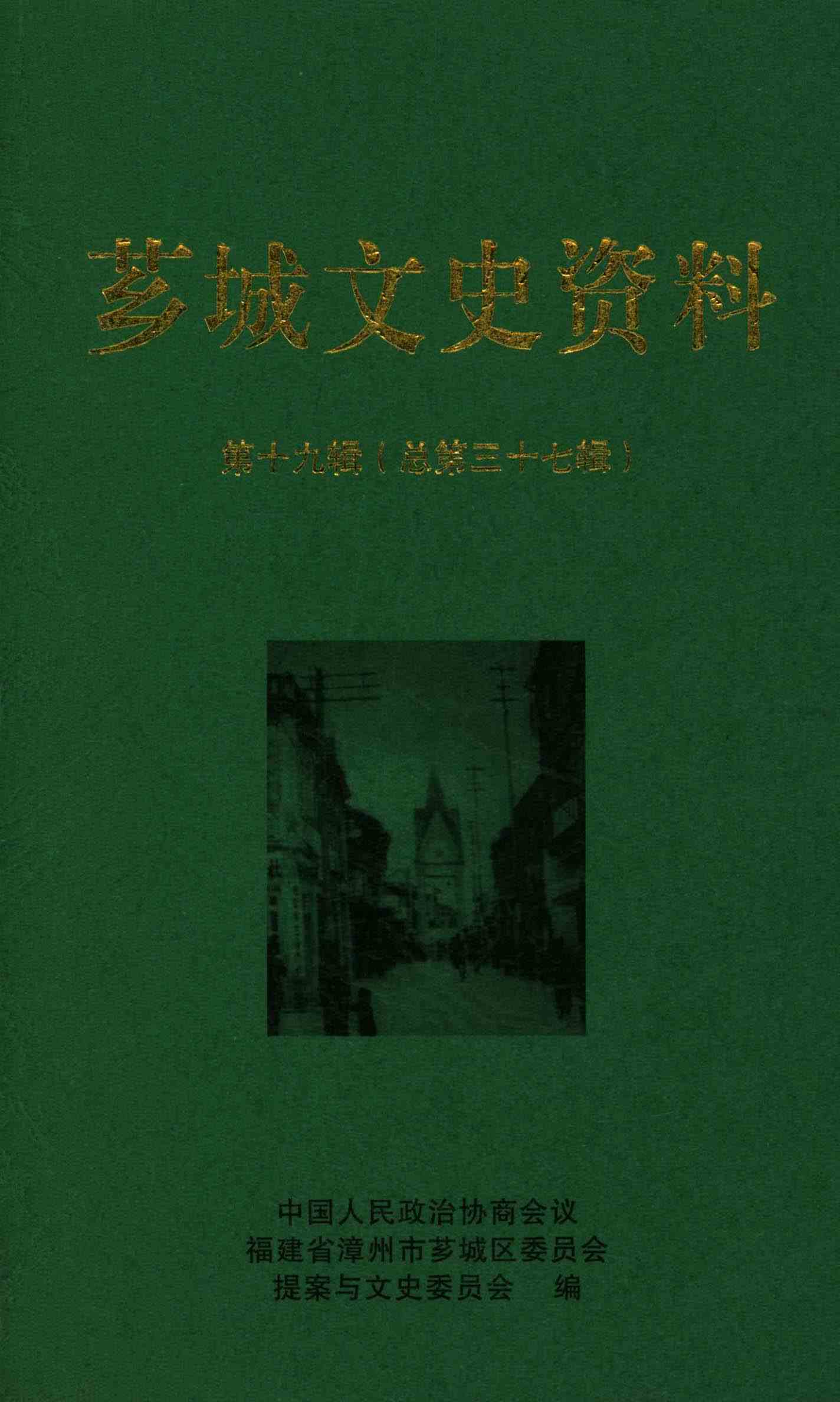
《芗城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本书收录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委员会提案与文史委员会编写的芗城文史资料第十九辑,内容包含了前言,故地踪影,往事寻踪,人物春秋,姓氏选登,民俗记述,台岛践履,文献集萃,后记等反映漳州市中心城区的人文地理、物产风俗,反映社会的风貌。
阅读
相关人物
田丰
责任者
相关地名
漳州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