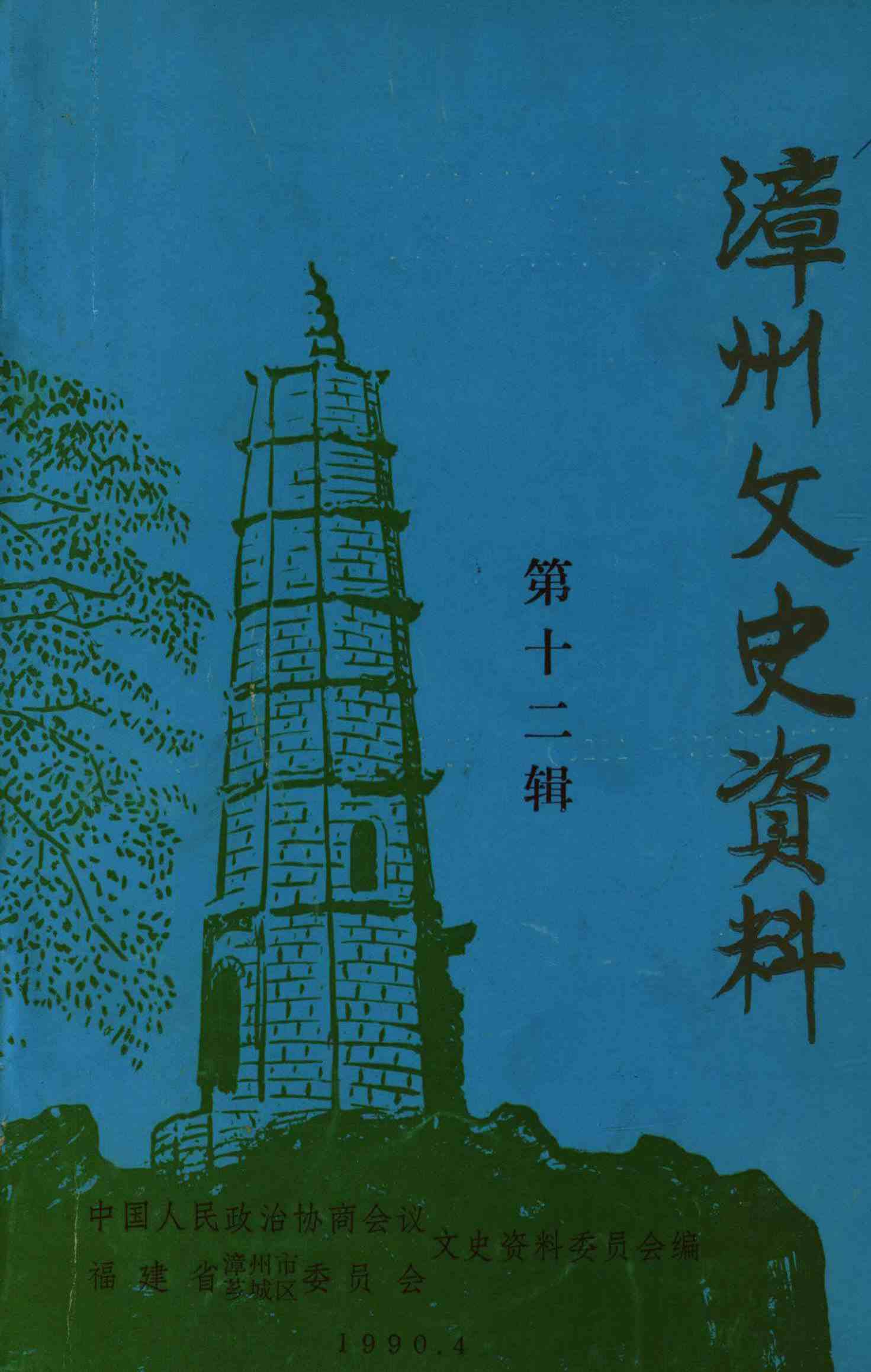参加游击战片断
| 内容出处: | 《漳州文史资料》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20003980 |
| 颗粒名称: | 参加游击战片断 |
| 分类号: | E297.3 |
| 页数: | 6 |
| 页码: | 200-205 |
| 摘要: | 抗日战争胜利后,通过进步教师张方、周兴民等同志的传播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和进步杂志的教育。为漳州地下党的建立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加上1947年以后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主要内容的全国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和实践,提高了进步学生的觉悟。可以说1948年夏,中共漳州工委的建立是水到渠成。尽管当时全国形势已转入军事反攻,但鹿死谁手,天下未定。特别是南方的闽南,反动统治较强,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力量,无论从兵力上、装备上都十几倍于我,到处围剿游击队,战斗仍十分频繁。白区白色恐怖仍有增无减。无论是武装斗争或者坚持地下斗争,仍很艰难和残酷。接到指示后,王子陵、陈述等10多位党员从四面八方奔向游击队。 |
| 关键词: | 游击队 战争年代 抗日战争 |
内容
抗日战争胜利后,通过进步教师张方、周兴民等同志的传播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和进步杂志的教育。为漳州地下党的建立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加上1947年以后与“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主要内容的全国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影响和实践,提高了进步学生的觉悟。可以说1948年夏,中共漳州工委的建立是水到渠成。尽管当时全国形势已转入军事反攻,但鹿死谁手,天下未定。特别是南方的闽南,反动统治较强,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力量,无论从兵力上、装备上都十几倍于我,到处围剿游击队,战斗仍十分频繁。白区白色恐怖仍有增无减。无论是武装斗争或者坚持地下斗争,仍很艰难和残酷。
1948年5月,“反美扶日”学生运动后不久,工委领导人陈列、张方等人相继被捕。黑名单满天飞,到处搜捕地下党员,白色恐怖笼罩漳州城,在危急情况下,工委及时作出决定:“凡是学生运动中有可能暴露的党员,必须立即转移到游击队,反之,则仍坚持白区搞地下工作”。接到指示后,王子陵、陈述等10多位党员从四面八方奔向游击队。由于发展党员时,教育党员敢于参加共产党就要有不怕杀头、坐牢,随时准备弃学从戎的决心,听从组织召唤。因此,党员思想准备较充分,尽管当时大家都是年方20上下的年青人。在转移过程中都能按照组织上的安排,服从形势发展的需要,遵守党的纪律,奔赴新的斗争岗位,顺利地完成了这次转移。
艰苦锻炼的第一课
从地下到地上,确切地说,从当学生到当一个游击队员,无论从斗争上、方法上、生活上变化是如此之大。首先是到达游击队前的几天夜行军,最艰苦的是从平和下官峰到南靖县南坑乡的北坑,晚上六时出发,拂晓要到达。走的是无人走过的山林,爬的是几十里路的山岭,尽管是寒冬腊月,却个个汗流如注,外衣都湿透了。一宣布休息,北风一刮,彻骨生寒,只能相依取暖。听到山谷里潺潺的流水,焦干的喉咙,只好捧泉水解渴。拂晓还得越过海拔800多米的割竹封锁线,对于一个老战士来说,这些不算什么,可我们是刚上第一课。迎着朝霞,在北坑幽静的山谷里,赖香仁父亲送来了干饭和茶水,这位老人我们只是初次短暂的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4个月后,除赖香仁外,一家4口全部被国民党保安团杀害了,留给我们的记忆是模糊然而是高大的形象。到了虎伯寮,副支队长吴扬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四不”,不怕饥寒交迫,不怕夜行军,不怕疾病折磨,不怕战斗牺牲。这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具体化。说来简单,实践起来可不容易。感谢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给了我们力量,告诉我们必须彻底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中国,才能振兴中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自觉去斗争,接受艰苦的锻炼,直至死亡的考验。当时,一天两餐饭经常是在不见太阳的黑暗中吃的。雨天野餐,雨水和汤一起吃,半盆竹笋渗酸菜,吃完饭仍是满满的一盆。夜晚睡觉,经常两个人紧缩在树底下一床薄薄的被单里,真是“几番梦不成”。加上昼伏夜行,不少同志拉肚子、长疥疮、打摆子一并发作。理发员阿×,就因为患上痢疾,无药可治,竟与世长辞。
交通员高升,子弹打在小腿中,卫生员用钳子插进去,就是取不出子弹头。周其虎用食指插进去一勾出来,指甲上还夹了一块肉。处理伤口时,拉开伤口,倒上碘酒,高升爬在草地上强忍着剧痛,面色苍白,汗珠直冒,坐起来时满口是血,嘴唇舌头都咬破了。
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磨炼考验,用不了多长的时间,白面书生也就变成了皮包骨,满身汗酸,腥味的黑小子。难怪国民党特务说:“土共”有特殊味道,闻一闻就知道。
“共产党是特殊材料造成的”。我们当时确以苦为荣,引为自豪。
两次反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是1949年4月在南靖县金山乡的新村,这是新区,缺乏群众基础,也由于麻痹,部队连续三天驻在粪箕型的半山腰,只有粪箕口一条通道。国民党刘汝明残部和省陈言廉保安二团等纠集了一千多人,以五、六倍于我的兵力,组成包围圈,拂晓时发起战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们决定作战略转移,部队化整为零,勇敢顽强地冒着枪林弹雨,反击突围。三天内,游击健儿重新集结,继续战斗在高山密林中。这一仗牺牲了7位同志,其中有随我地下党员转移的积极分子周日光、蔡育和羊我三位同志,他们忠魂就葬于金山乡。
突围只是化险为夷的开端,而不是终结。伤病员在突围后又碰上恶风暴雨,露宿山头,发冷发热,粒米未进。严重的是无医无药,只好依靠寒冷的天气自然凝固止血,靠的是民间青草药,拿到嘴里嚼烂涂敷在伤口上。睡的是潮湿的山洞,蚊子成群结队进攻,严重的还是“囊中存米清可数”。疾病、伤口化脓、饥饿折磨着伤病员。还有敌人日搜夜剿,一个晚上有时得转移数次,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伤病员两人一对,互相倚扶,蹒跚前进。
“血雨腥风应有涯”,交通员送来了《前哨报》,传来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消息,我们欢呼雀跃,梦寐以求的新中国快要诞生了,怎不令人兴奋而忘记了我们还处身于恶劣的环境中。
第二次反围剿是1949年8月在平和县坂仔乡的金京洋。十九团三、八两个连队在大坪激战一天,胜利后马上转移到金京洋,到达后已是下半夜三点多钟。几天来从广东到闽南,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十分疲动,难得美美睡上一个钟头,真是快乐胜神仙。虽然这是老区,又在打胜仗之后。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不能麻痹。一到营地就派出一个班的高山哨,吃过早饭,群众送来一捆烟叶,还来不及分发,敌情又来了,部队迅速抢占山头,边走边听汇报。敌人为了报昨天大坪战败之仇,集中了1000多人前来围剿,紧接着开展了一场短暂然而是剧烈争论的军事会议。是打还是撤,各有理由,议而难决。高山哨枪声已响,打撤未定。后来,团政委陈光马上叫通讯员通知当时的地委委员陈天才上来决策。对这一带地形了如指掌的陈天才,三步作两步,人未到,声先到:“这样的地形守不住,不懂这一点,还当什么红军?”于是立即发动群众把锄头集中上来,挖壕死守。在游击战中,这确是特殊的战例。问题在于金京洋后面一山独高,周围是低山,又无林木,撤后敌人居高临下,伤亡更大。
激烈的战斗展开了,一向沉默寡言的副团长张进财一声怒吼,招呼三连:“共产党员跟我上”,身先士卒到达前沿,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几分钟后传来他牺牲的消息。尸体、伤员一个接一个抬下来,战士一个接一个往前走,以勇敢善战的独眼龙——三连指导员陈芸生同志也负伤下来,血从他手上往下淌,可他毫不在乎地问:“谁有烟叶?”两军相距只有百把公尺,敌人集中了20多挺日本式轻机枪,连续往我阵地打,弹如雨下。我们呢?一个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不准乱打枪,老是耍花枪。“集中手榴弹,准备冲锋”。紧接着敌人那边喊话:“弟兄们!土共要冲锋了,狠狠地打”。尽管我们以各种方法迷惑敌人,消耗敌人子弹,但战斗的危险性使那些听枪声犹如听过年放鞭炮一样的老游击队员也显得紧张,感到严峻。令人鼓舞的是这时一个年方二十岁上下,红红脸蛋的漂亮姑娘挑着两桶稀饭上来,她一步紧一步登上“金字塔峰”,还继续向下往前沿送,可把人急坏了。“同志,可不能往前走,那里有危险,放下来,让我们匍匐前进,一桶一桶往前送。”她嫣然一笑:“没关系,打了一天仗,还能让同志们没吃上饭。”多么美丽、勇敢的姑娘,真是深山出好笋,战地一支花。
夜幕降临,团长下命令:“三连留一个班掩护,其余的听到冲锋号,一个跟一个往后撤。”东方破晓,我们到达了三五村,还来不及进行战斗总结,传来了昨天战斗的讯息,保安团总指挥李济芳副团长被我高山哨第一排机枪子弹击毙。这可能是金京洋反围剿转危为安的原因之一。
十天八战
1949年6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后,为了准备配合解放军入闽作战,闽南第八支队集中游击队挺进到华安县境,准备横渡九龙江的北溪,到安溪与当地游击队会师。伪国大代表黄雨定,在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华安县建立了星罗棋布的通讯网,组织了一批反动民团,凭借北溪天险,妄想挡住我们前进的道路。华安是新区,没有群众基础,耳目不灵,前有伏兵,后有追兵,迫使我们在很多情况下本来可以避免的战斗,却不得不仓惶应战。有时饭碗刚端上,枪声就响,刚想宿营,追兵又至,严重的还是筹粮十分困难。第一仗攻打下樟附近炮楼就是夺粮的一例。炮楼住了一个保安队,还储备粮食,我们采取强攻,顺利地歼灭了保安队,缴获了十几根长枪,弄到一批粮食。队伍沿北溪向下樟挺进,这是华安县的产粮区,也是当时国民党的粮仓,为了吃饭,就得枪口夺粮。黄雨定察觉我们缺粮,就拼命护粮。我们挺进到下樟时,黄雨定指挥保安队护粮,沿溪运走粮食,我们一到,保安队就龟缩到祠堂的粮仓里,这个祠堂座落在田中央,周围是开阔地;没有炮火掩护,单靠机枪和土炸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几次强攻,都没得手,战斗持续到黎明,为了防止敌人增援部队前后夹攻,只好撤出战斗,朱鲁同志就在这一役牺牲在这里。
端午佳节,转战到天宝大山下,农民给我们送来了一些棕子,使我们分享到节日的幸福。然而保安团又跟上来了,同志们义愤填膺,登上半山腰,居高临下,在支队副司令吴扬的指挥下,发动了几次冲锋,敌人溃不成军退到天宝圩。解放后,以闽南游击队和广东十三团为主,整编为分区警备团。在完成剿匪反霸任务后,立即转入守备海防,驻守东山岛和漳浦的六鳌半岛。一次,国民党残敌从海上前来偷袭,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老游击队员曾清流排长,带领全排弟兄,坚守阵地,全部壮烈牺牲,受到省和华东军区的表扬。在1953年7月守备东山岛战斗中,以八个连挡住敌人13000多人的进攻,在兄弟部队迅速增援下,消灭了三千多敌人,其中生俘七百多人,战后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守的顽强,增援的快”。当年地下党员连政治指导员柯庆年同志在战斗中死守庙山,壮烈牺牲,这些当年地下党同志都在解放初期血染海防线上。
1948年5月,“反美扶日”学生运动后不久,工委领导人陈列、张方等人相继被捕。黑名单满天飞,到处搜捕地下党员,白色恐怖笼罩漳州城,在危急情况下,工委及时作出决定:“凡是学生运动中有可能暴露的党员,必须立即转移到游击队,反之,则仍坚持白区搞地下工作”。接到指示后,王子陵、陈述等10多位党员从四面八方奔向游击队。由于发展党员时,教育党员敢于参加共产党就要有不怕杀头、坐牢,随时准备弃学从戎的决心,听从组织召唤。因此,党员思想准备较充分,尽管当时大家都是年方20上下的年青人。在转移过程中都能按照组织上的安排,服从形势发展的需要,遵守党的纪律,奔赴新的斗争岗位,顺利地完成了这次转移。
艰苦锻炼的第一课
从地下到地上,确切地说,从当学生到当一个游击队员,无论从斗争上、方法上、生活上变化是如此之大。首先是到达游击队前的几天夜行军,最艰苦的是从平和下官峰到南靖县南坑乡的北坑,晚上六时出发,拂晓要到达。走的是无人走过的山林,爬的是几十里路的山岭,尽管是寒冬腊月,却个个汗流如注,外衣都湿透了。一宣布休息,北风一刮,彻骨生寒,只能相依取暖。听到山谷里潺潺的流水,焦干的喉咙,只好捧泉水解渴。拂晓还得越过海拔800多米的割竹封锁线,对于一个老战士来说,这些不算什么,可我们是刚上第一课。迎着朝霞,在北坑幽静的山谷里,赖香仁父亲送来了干饭和茶水,这位老人我们只是初次短暂的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4个月后,除赖香仁外,一家4口全部被国民党保安团杀害了,留给我们的记忆是模糊然而是高大的形象。到了虎伯寮,副支队长吴扬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四不”,不怕饥寒交迫,不怕夜行军,不怕疾病折磨,不怕战斗牺牲。这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具体化。说来简单,实践起来可不容易。感谢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给了我们力量,告诉我们必须彻底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中国,才能振兴中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自觉去斗争,接受艰苦的锻炼,直至死亡的考验。当时,一天两餐饭经常是在不见太阳的黑暗中吃的。雨天野餐,雨水和汤一起吃,半盆竹笋渗酸菜,吃完饭仍是满满的一盆。夜晚睡觉,经常两个人紧缩在树底下一床薄薄的被单里,真是“几番梦不成”。加上昼伏夜行,不少同志拉肚子、长疥疮、打摆子一并发作。理发员阿×,就因为患上痢疾,无药可治,竟与世长辞。
交通员高升,子弹打在小腿中,卫生员用钳子插进去,就是取不出子弹头。周其虎用食指插进去一勾出来,指甲上还夹了一块肉。处理伤口时,拉开伤口,倒上碘酒,高升爬在草地上强忍着剧痛,面色苍白,汗珠直冒,坐起来时满口是血,嘴唇舌头都咬破了。
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磨炼考验,用不了多长的时间,白面书生也就变成了皮包骨,满身汗酸,腥味的黑小子。难怪国民党特务说:“土共”有特殊味道,闻一闻就知道。
“共产党是特殊材料造成的”。我们当时确以苦为荣,引为自豪。
两次反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是1949年4月在南靖县金山乡的新村,这是新区,缺乏群众基础,也由于麻痹,部队连续三天驻在粪箕型的半山腰,只有粪箕口一条通道。国民党刘汝明残部和省陈言廉保安二团等纠集了一千多人,以五、六倍于我的兵力,组成包围圈,拂晓时发起战斗。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们决定作战略转移,部队化整为零,勇敢顽强地冒着枪林弹雨,反击突围。三天内,游击健儿重新集结,继续战斗在高山密林中。这一仗牺牲了7位同志,其中有随我地下党员转移的积极分子周日光、蔡育和羊我三位同志,他们忠魂就葬于金山乡。
突围只是化险为夷的开端,而不是终结。伤病员在突围后又碰上恶风暴雨,露宿山头,发冷发热,粒米未进。严重的是无医无药,只好依靠寒冷的天气自然凝固止血,靠的是民间青草药,拿到嘴里嚼烂涂敷在伤口上。睡的是潮湿的山洞,蚊子成群结队进攻,严重的还是“囊中存米清可数”。疾病、伤口化脓、饥饿折磨着伤病员。还有敌人日搜夜剿,一个晚上有时得转移数次,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伤病员两人一对,互相倚扶,蹒跚前进。
“血雨腥风应有涯”,交通员送来了《前哨报》,传来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消息,我们欢呼雀跃,梦寐以求的新中国快要诞生了,怎不令人兴奋而忘记了我们还处身于恶劣的环境中。
第二次反围剿是1949年8月在平和县坂仔乡的金京洋。十九团三、八两个连队在大坪激战一天,胜利后马上转移到金京洋,到达后已是下半夜三点多钟。几天来从广东到闽南,连续行军作战,部队十分疲动,难得美美睡上一个钟头,真是快乐胜神仙。虽然这是老区,又在打胜仗之后。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不能麻痹。一到营地就派出一个班的高山哨,吃过早饭,群众送来一捆烟叶,还来不及分发,敌情又来了,部队迅速抢占山头,边走边听汇报。敌人为了报昨天大坪战败之仇,集中了1000多人前来围剿,紧接着开展了一场短暂然而是剧烈争论的军事会议。是打还是撤,各有理由,议而难决。高山哨枪声已响,打撤未定。后来,团政委陈光马上叫通讯员通知当时的地委委员陈天才上来决策。对这一带地形了如指掌的陈天才,三步作两步,人未到,声先到:“这样的地形守不住,不懂这一点,还当什么红军?”于是立即发动群众把锄头集中上来,挖壕死守。在游击战中,这确是特殊的战例。问题在于金京洋后面一山独高,周围是低山,又无林木,撤后敌人居高临下,伤亡更大。
激烈的战斗展开了,一向沉默寡言的副团长张进财一声怒吼,招呼三连:“共产党员跟我上”,身先士卒到达前沿,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几分钟后传来他牺牲的消息。尸体、伤员一个接一个抬下来,战士一个接一个往前走,以勇敢善战的独眼龙——三连指导员陈芸生同志也负伤下来,血从他手上往下淌,可他毫不在乎地问:“谁有烟叶?”两军相距只有百把公尺,敌人集中了20多挺日本式轻机枪,连续往我阵地打,弹如雨下。我们呢?一个子弹要消灭一个敌人。不准乱打枪,老是耍花枪。“集中手榴弹,准备冲锋”。紧接着敌人那边喊话:“弟兄们!土共要冲锋了,狠狠地打”。尽管我们以各种方法迷惑敌人,消耗敌人子弹,但战斗的危险性使那些听枪声犹如听过年放鞭炮一样的老游击队员也显得紧张,感到严峻。令人鼓舞的是这时一个年方二十岁上下,红红脸蛋的漂亮姑娘挑着两桶稀饭上来,她一步紧一步登上“金字塔峰”,还继续向下往前沿送,可把人急坏了。“同志,可不能往前走,那里有危险,放下来,让我们匍匐前进,一桶一桶往前送。”她嫣然一笑:“没关系,打了一天仗,还能让同志们没吃上饭。”多么美丽、勇敢的姑娘,真是深山出好笋,战地一支花。
夜幕降临,团长下命令:“三连留一个班掩护,其余的听到冲锋号,一个跟一个往后撤。”东方破晓,我们到达了三五村,还来不及进行战斗总结,传来了昨天战斗的讯息,保安团总指挥李济芳副团长被我高山哨第一排机枪子弹击毙。这可能是金京洋反围剿转危为安的原因之一。
十天八战
1949年6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后,为了准备配合解放军入闽作战,闽南第八支队集中游击队挺进到华安县境,准备横渡九龙江的北溪,到安溪与当地游击队会师。伪国大代表黄雨定,在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华安县建立了星罗棋布的通讯网,组织了一批反动民团,凭借北溪天险,妄想挡住我们前进的道路。华安是新区,没有群众基础,耳目不灵,前有伏兵,后有追兵,迫使我们在很多情况下本来可以避免的战斗,却不得不仓惶应战。有时饭碗刚端上,枪声就响,刚想宿营,追兵又至,严重的还是筹粮十分困难。第一仗攻打下樟附近炮楼就是夺粮的一例。炮楼住了一个保安队,还储备粮食,我们采取强攻,顺利地歼灭了保安队,缴获了十几根长枪,弄到一批粮食。队伍沿北溪向下樟挺进,这是华安县的产粮区,也是当时国民党的粮仓,为了吃饭,就得枪口夺粮。黄雨定察觉我们缺粮,就拼命护粮。我们挺进到下樟时,黄雨定指挥保安队护粮,沿溪运走粮食,我们一到,保安队就龟缩到祠堂的粮仓里,这个祠堂座落在田中央,周围是开阔地;没有炮火掩护,单靠机枪和土炸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几次强攻,都没得手,战斗持续到黎明,为了防止敌人增援部队前后夹攻,只好撤出战斗,朱鲁同志就在这一役牺牲在这里。
端午佳节,转战到天宝大山下,农民给我们送来了一些棕子,使我们分享到节日的幸福。然而保安团又跟上来了,同志们义愤填膺,登上半山腰,居高临下,在支队副司令吴扬的指挥下,发动了几次冲锋,敌人溃不成军退到天宝圩。解放后,以闽南游击队和广东十三团为主,整编为分区警备团。在完成剿匪反霸任务后,立即转入守备海防,驻守东山岛和漳浦的六鳌半岛。一次,国民党残敌从海上前来偷袭,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老游击队员曾清流排长,带领全排弟兄,坚守阵地,全部壮烈牺牲,受到省和华东军区的表扬。在1953年7月守备东山岛战斗中,以八个连挡住敌人13000多人的进攻,在兄弟部队迅速增援下,消灭了三千多敌人,其中生俘七百多人,战后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守的顽强,增援的快”。当年地下党员连政治指导员柯庆年同志在战斗中死守庙山,壮烈牺牲,这些当年地下党同志都在解放初期血染海防线上。
相关人物
王南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