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漳州糖业
| 内容出处: | 《漳州文史资料》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20003604 |
| 颗粒名称: | 解放前漳州糖业 |
| 分类号: | F426.82 |
| 页数: | 6 |
| 页码: | 111-116 |
| 摘要: | 糖是日常必需的食用品,民间逢年过节,家家户户春薯作粿需要大量用糖,尤其是糖果、糕饼、蜜饯、茶料等行业都是以糖为主要原料之一,所以糖的用途很广。我国在海禁未开之前,没有洋糖进口,糖可自产自给。北方不产蔗,只靠糖菜制糖,数量少质量又差,市场供不应求;但南方却盛产糖蔗,数量多且质量亦好,足够支援北方市场需要,以全国来说产销可以平衡。海禁开放以后,虽有洋糖进口,但都是机制白糖,和我国自产的红糖在品种、用途等方面有所不同,因而对我国自产糖的产销没有多大影响。现将漳州解放前产蔗、制糖、糖业经营和销售情况等分述于下,以供参考。 |
| 关键词: | 漳州市 解放前 糖业 |
内容
糖是日常必需的食用品,民间逢年过节,家家户户春薯作粿需要大量用糖,尤其是糖果、糕饼、蜜饯、茶料等行业都是以糖为主要原料之一,所以糖的用途很广。我国在海禁未开之前,没有洋糖进口,糖可自产自给。北方不产蔗,只靠糖菜制糖,数量少质量又差,市场供不应求;但南方却盛产糖蔗,数量多且质量亦好,足够支援北方市场需要,以全国来说产销可以平衡。海禁开放以后,虽有洋糖进口,但都是机制白糖,和我国自产的红糖在品种、用途等方面有所不同,因而对我国自产糖的产销没有多大影响。
解放前,漳州市郊是主要的产蔗地区,蔗园遍地,四乡都建有榨坊(制糖作坊),制出的“漳刁”质量良好,畅销全国各地,颇负盛名,所以糖是我市比较大宗的土特产之一。现将漳州解放前产蔗、制糖、糖业经营和销售情况等分述于下,以供参考。
一、产蔗地区:
我市四乡以往都有种蔗的习惯,历史悠久,其中较多的是东、北乡,西乡次之;南乡土壤较适宜种植果树,且水果经济价值较高,所以蔗园多数改种果树。如果我们实地观察一下,就能看到南乡不少村庄还遗有榨坊旧址和榨蔗制糖工具等。解放后,南乡各村农民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在不影响种果的前提下,巳逐步开拓土地种蔗,普遍有蔗园了。
二、蔗糖的榨制和加工品种:
蔗有果蔗、糖蔗之分:果蔗,俗称“白蔗”,专供食用;糖蔗,俗称“竹蔗”专用榨糖。后来蔗农改用出搪率较高的台湾703号蔗种。据有制糖,经验者说:蔗好的汁多产糖少,蔗差的汁少产糖多,因汁多都系水份,而汁少浓度较高,所以出糖率也就高了。
解放前,我国制糖工业非常落后,漳属一带都是以土法榨制,使用土工具和人力操作,产量低、质量差。当时制糖作坊叫“榨坊”或“糖部”,只能生产红糖,而后再由红糖加工制为其他品种,无法直接榨制高质量的白搪。因此,在海禁开放以后,外国白糖得以充斥市场。
为了回顾过去,这里把旧式制糖的过程简要分述于下:
在榨坊内安置两个石砘(俗叫“蔗车”),在双砘缝中塞入蔗杆,以牛拉动两砘,由于石砘的转动而压榨出蔗汁流入地下壶里;然后取出蔗汁倒入鼎内(两壶蔗汁装为一鼎),经过火烧(一般利用蔗粕代柴)煮沸,每升需投入生油渣一斤和石灰粉半斤(后来改用煮蔗的化学药粉),弃掉杂质;在蔗汁浓缩到适度时,将其倒入糖糟,当其未全部冷却凝结时,分别制成各类品种:刁糖、赤糖、丸糖、包仔糖、角糖、漏糖和经过加工的菜搪(土白糖)、赤砂、冰糖,以及下脚料的角水、冰糖水等。
当糖在槽中将凝固时,两人在槽边用铁铲将其挑散,即是刁糖;如果要做为丸糖,就用双手把散糖搓成圆形,再涂上糖水使糖丸表面光滑;要做为漏搪,就将糖浆倒入糖漏中。但要做为刁糖、丸糖,必须选择较好的蔗汁,其色赤的做为刁糖、赤糖,色红的做为丸糖。东、西两乡一般加工为刁糖,而丸搪只有北乡加工一部份。如蔗汁差的就做为“包仔糖”(俗称“手模印”)、漏糖(俗称“角糖”)。要把原糖改制为菜糖,就在糖漏上面覆盖田土两次(第一次去掉后,再覆盖第二次),每次约一星期,糖色就变白。若要加工冰糖,先把菜糖过煮,再渗入搅匀的鸭蛋和漂白剂,使其沉淀、澄清。解色后,倒入里面装置小竹片的陶硿,候其凝固即为冰糖,然后砸破陶控取出冰糖;因为硿空内有小竹片的隔离,冰糖不会结成整块,而硿底留下那些没有凝固的就是冰糖水。砸破的陶硿用竹条箍好可再用,这种旧式加工方法既麻烦又浪费。后来改用面宽底窄的铝桶,倾倒方便,桶又不破。在机制白糖进口以后,就直接以白糖加工为冰糖,其色泽更为洁白、透明。一般由菜糖或白糖煮制为冰糖,其成品率都是百分之六十五左右。当时煮制冰糖技术最高的是蔡牯厉,他为好几家糖行当顾问。
旧时市郊每村都有榨坊,多者四、五门,少者一、二门,每门榨坊每天可榨蔗八壶,每壶汁需用蔗六百斤,每百斤蔗能产糖十四至十五斤。以此推算,每门榨坊一日可产糖六、七百斤,需用劳力十八人——挑蔗十人、缠蔗叶一人、司车二人、烧火二人、煮糖一人、刁糖或搓糖二人,和水牛两头,全部工资和费用需花
去食糖二百斤的价值。这种加工方式,效率低而费用大。在三十年代前后,东美乡华侨郭春秧曾经为改进制糖工业的落后面貌在郭坑创建新型糖厂,以机器代替人力操作的旧式榨坊。但由于蔗源不足,地方官绅又多般刁难阻挠,难以顺利地发展,后值抗日战争爆发只得停产。
三、经营糖业的商号:
由于本市四乡产糖甚多,加以邻近南靖、平和等县所产的蔗糖亦运来兜售,每年糖类的经营数字相当巨大,因而有较多的糖商来经办供销业务。在本市先后有专营的糖行、五谷商兼营糖业、小批发糖店,京果商号亦有兼营糖类的惯例。(一)专营糖行有古邵乡郑某的汉源、吕春源的渊源、曾家的南丰、唐家的恰裕、南坪乡黄俊的惠农和恒浴、鳌圃乡吴金龙的合发、潮帮刘汉盛的振源(后改集兴)、刘节庵的刘煌记(后改重兴)、刘玉山的正大,它们都大批地运往外地销害,并加工产销冰搪,而潮帮也兼制柑、桔饼。(二)五谷商兼营塘业的,有张联成的南金、古郡乡郑某为三太、庄家的启记、郑永的永美、阮耀祺的长兴、朱三根和朱天恩的捷泰、阮石发的南发、洪振乾的振兴和复源,洪振乾与李玉鸣合伙的复发、郑永年的长发、林联的建发、郑定卿的仁成、卢姚吾的农益、庄国梁的联大等。上述这些兼营糖业的商号都是配销外地的,其中南金、三太、长兴等亦加工产销冰糖。
当时本市东美乡华侨郭春秧在其侨居的印尼爪哇拥有不少糖厂,号称“糖大王”,他在我国南方主要通商口岸分设经营机构:如台湾的锦茂行、香港的锦昌行、汕头的锦×行、厦门的锦祥行。在本市亦开设锦美行,聘方耀光为经理。锦美行还由台湾的糖行运来大量塘水,原打算卖给本市各酿酒店,因被酒商联合压低价格,它索性自办酿酒厂,使塘水价格不受酒商的操纵。(三)小批发糖店有和发、合成、合春、通成、长兴、金成、恒记、长裕、厚成等,它们都是收购丸糖传卖给石码、龙岩和粿贩的。
各糖商除平时赚得应有的利润外,还进行投机囤积居奇的活动来牟取更大的盈利。因糖的价格一般是秋季前后比冬季盛产时高涨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左右(约由每百斤七、八元升至十一、十二元),糖商利用盛产低价时大量购进,囤积到货缺价高时全部抛出;有的乘缺货时出借旧塘一担,而在新糖上市时讨回一担半的借贷办法;有的且用买“搪青”(浮水)的办法:在糖蔗收成前先压价付款预购担额,俟产糖时按额取货,这样可便宜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四、购销情况:
漳州本地既大量产糖,又有南靖、平和等县的来货,糖源充沛,足以运销全国各地。本市的交易:外县来货大多是刁糖,亦有部分丸糖、包仔糖、菜糖和青糖(供煮制冰糖之用),一般质量较差,都是由水路以木船运来。大凡搪行糖商要配运外地的大宗糖货,就派人到各乡村收购。有些搪农亲自来市洽售,但绝大多数是刁糖。每有成交,就在当地包装,每包以净重二百市斤为标准。西乡沿溪者由木船载运,东北乡以牛车载运。搪商把各路来货集中于江边,搬上“大五篷”木船,载往厦门转运各地销售。
至于小宗或另担的交易,西北乡有“北庙糖市”为集中地,日日有市。距离“北庙糖市”较远的东乡,就在附近的“小港圩”销售,该圩每逢农历一、四、七为圩期,采购的大部分是石码糖商。但东乡很少加工丸糖,而石码糖商所需要的丸糖,就由本市小批发商供应。龙岩帮采购的也多是丸糖或包仔糖,他们有的直接到“北庙搪市”购买,有的即由小批发商供应。
每逢新糖登场时,在“北庙糖市”每日上市者约有千担,平时亦有三、四百担入市交易。各搪商都到糖市收购并观察市情。糖市以糖的交易为主,还有花生、豆类、地瓜粉等买卖,市场十分活跃。
五、外销情况:
本市食糖经常配往大连、天津、上海、苏州、宁波、温州等通商港口,同时由各港口换购当地土特产:如天津的高梁、史国公、五加皮等名酒,大连的黄豆、豆饼,上海的棉纱、布匹、面粉、化肥、洋白糖,苏州的丝绸,宁波的棉花、布匹,温州的猪油、虾皮、皮旦、绍兴酒、茶油、雨伞等。这种互换的交易,既使商行获得更多的利润,对于沟通埠际的物资交流,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各糖商除经营本产食糖的销售外,都兼营进口白搪。当时进口的有印尼爪哇白糖,其价格约高于本产红糖的百分五十左右,本市向厦门购买进口白搪可以先交定金(约为糖价的三分之一)订购期货,到期货、款两清。后来台湾的机制白糖亦陆续运进本市,其质量与价格和爪哇白糖不相上下,台湾还进口一种粉蜜搪,色微黄、味似冰糖而价钱较高。当时厦门经营白糖进口者,以黄奕住的日兴行为最大宗,约占全岛进口数的百分之七十。抗日战争期间,外搪来源断绝,市场白糖欠缺,潮(州)帮糖行为供应市场的需要,购置电机一台,配套小型设备进行加工白糖,质量虽不如进口的,但也可代替应用。
解放前,漳州市郊是主要的产蔗地区,蔗园遍地,四乡都建有榨坊(制糖作坊),制出的“漳刁”质量良好,畅销全国各地,颇负盛名,所以糖是我市比较大宗的土特产之一。现将漳州解放前产蔗、制糖、糖业经营和销售情况等分述于下,以供参考。
一、产蔗地区:
我市四乡以往都有种蔗的习惯,历史悠久,其中较多的是东、北乡,西乡次之;南乡土壤较适宜种植果树,且水果经济价值较高,所以蔗园多数改种果树。如果我们实地观察一下,就能看到南乡不少村庄还遗有榨坊旧址和榨蔗制糖工具等。解放后,南乡各村农民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在不影响种果的前提下,巳逐步开拓土地种蔗,普遍有蔗园了。
二、蔗糖的榨制和加工品种:
蔗有果蔗、糖蔗之分:果蔗,俗称“白蔗”,专供食用;糖蔗,俗称“竹蔗”专用榨糖。后来蔗农改用出搪率较高的台湾703号蔗种。据有制糖,经验者说:蔗好的汁多产糖少,蔗差的汁少产糖多,因汁多都系水份,而汁少浓度较高,所以出糖率也就高了。
解放前,我国制糖工业非常落后,漳属一带都是以土法榨制,使用土工具和人力操作,产量低、质量差。当时制糖作坊叫“榨坊”或“糖部”,只能生产红糖,而后再由红糖加工制为其他品种,无法直接榨制高质量的白搪。因此,在海禁开放以后,外国白糖得以充斥市场。
为了回顾过去,这里把旧式制糖的过程简要分述于下:
在榨坊内安置两个石砘(俗叫“蔗车”),在双砘缝中塞入蔗杆,以牛拉动两砘,由于石砘的转动而压榨出蔗汁流入地下壶里;然后取出蔗汁倒入鼎内(两壶蔗汁装为一鼎),经过火烧(一般利用蔗粕代柴)煮沸,每升需投入生油渣一斤和石灰粉半斤(后来改用煮蔗的化学药粉),弃掉杂质;在蔗汁浓缩到适度时,将其倒入糖糟,当其未全部冷却凝结时,分别制成各类品种:刁糖、赤糖、丸糖、包仔糖、角糖、漏糖和经过加工的菜搪(土白糖)、赤砂、冰糖,以及下脚料的角水、冰糖水等。
当糖在槽中将凝固时,两人在槽边用铁铲将其挑散,即是刁糖;如果要做为丸糖,就用双手把散糖搓成圆形,再涂上糖水使糖丸表面光滑;要做为漏搪,就将糖浆倒入糖漏中。但要做为刁糖、丸糖,必须选择较好的蔗汁,其色赤的做为刁糖、赤糖,色红的做为丸糖。东、西两乡一般加工为刁糖,而丸搪只有北乡加工一部份。如蔗汁差的就做为“包仔糖”(俗称“手模印”)、漏糖(俗称“角糖”)。要把原糖改制为菜糖,就在糖漏上面覆盖田土两次(第一次去掉后,再覆盖第二次),每次约一星期,糖色就变白。若要加工冰糖,先把菜糖过煮,再渗入搅匀的鸭蛋和漂白剂,使其沉淀、澄清。解色后,倒入里面装置小竹片的陶硿,候其凝固即为冰糖,然后砸破陶控取出冰糖;因为硿空内有小竹片的隔离,冰糖不会结成整块,而硿底留下那些没有凝固的就是冰糖水。砸破的陶硿用竹条箍好可再用,这种旧式加工方法既麻烦又浪费。后来改用面宽底窄的铝桶,倾倒方便,桶又不破。在机制白糖进口以后,就直接以白糖加工为冰糖,其色泽更为洁白、透明。一般由菜糖或白糖煮制为冰糖,其成品率都是百分之六十五左右。当时煮制冰糖技术最高的是蔡牯厉,他为好几家糖行当顾问。
旧时市郊每村都有榨坊,多者四、五门,少者一、二门,每门榨坊每天可榨蔗八壶,每壶汁需用蔗六百斤,每百斤蔗能产糖十四至十五斤。以此推算,每门榨坊一日可产糖六、七百斤,需用劳力十八人——挑蔗十人、缠蔗叶一人、司车二人、烧火二人、煮糖一人、刁糖或搓糖二人,和水牛两头,全部工资和费用需花
去食糖二百斤的价值。这种加工方式,效率低而费用大。在三十年代前后,东美乡华侨郭春秧曾经为改进制糖工业的落后面貌在郭坑创建新型糖厂,以机器代替人力操作的旧式榨坊。但由于蔗源不足,地方官绅又多般刁难阻挠,难以顺利地发展,后值抗日战争爆发只得停产。
三、经营糖业的商号:
由于本市四乡产糖甚多,加以邻近南靖、平和等县所产的蔗糖亦运来兜售,每年糖类的经营数字相当巨大,因而有较多的糖商来经办供销业务。在本市先后有专营的糖行、五谷商兼营糖业、小批发糖店,京果商号亦有兼营糖类的惯例。(一)专营糖行有古邵乡郑某的汉源、吕春源的渊源、曾家的南丰、唐家的恰裕、南坪乡黄俊的惠农和恒浴、鳌圃乡吴金龙的合发、潮帮刘汉盛的振源(后改集兴)、刘节庵的刘煌记(后改重兴)、刘玉山的正大,它们都大批地运往外地销害,并加工产销冰搪,而潮帮也兼制柑、桔饼。(二)五谷商兼营塘业的,有张联成的南金、古郡乡郑某为三太、庄家的启记、郑永的永美、阮耀祺的长兴、朱三根和朱天恩的捷泰、阮石发的南发、洪振乾的振兴和复源,洪振乾与李玉鸣合伙的复发、郑永年的长发、林联的建发、郑定卿的仁成、卢姚吾的农益、庄国梁的联大等。上述这些兼营糖业的商号都是配销外地的,其中南金、三太、长兴等亦加工产销冰糖。
当时本市东美乡华侨郭春秧在其侨居的印尼爪哇拥有不少糖厂,号称“糖大王”,他在我国南方主要通商口岸分设经营机构:如台湾的锦茂行、香港的锦昌行、汕头的锦×行、厦门的锦祥行。在本市亦开设锦美行,聘方耀光为经理。锦美行还由台湾的糖行运来大量塘水,原打算卖给本市各酿酒店,因被酒商联合压低价格,它索性自办酿酒厂,使塘水价格不受酒商的操纵。(三)小批发糖店有和发、合成、合春、通成、长兴、金成、恒记、长裕、厚成等,它们都是收购丸糖传卖给石码、龙岩和粿贩的。
各糖商除平时赚得应有的利润外,还进行投机囤积居奇的活动来牟取更大的盈利。因糖的价格一般是秋季前后比冬季盛产时高涨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左右(约由每百斤七、八元升至十一、十二元),糖商利用盛产低价时大量购进,囤积到货缺价高时全部抛出;有的乘缺货时出借旧塘一担,而在新糖上市时讨回一担半的借贷办法;有的且用买“搪青”(浮水)的办法:在糖蔗收成前先压价付款预购担额,俟产糖时按额取货,这样可便宜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四、购销情况:
漳州本地既大量产糖,又有南靖、平和等县的来货,糖源充沛,足以运销全国各地。本市的交易:外县来货大多是刁糖,亦有部分丸糖、包仔糖、菜糖和青糖(供煮制冰糖之用),一般质量较差,都是由水路以木船运来。大凡搪行糖商要配运外地的大宗糖货,就派人到各乡村收购。有些搪农亲自来市洽售,但绝大多数是刁糖。每有成交,就在当地包装,每包以净重二百市斤为标准。西乡沿溪者由木船载运,东北乡以牛车载运。搪商把各路来货集中于江边,搬上“大五篷”木船,载往厦门转运各地销售。
至于小宗或另担的交易,西北乡有“北庙糖市”为集中地,日日有市。距离“北庙糖市”较远的东乡,就在附近的“小港圩”销售,该圩每逢农历一、四、七为圩期,采购的大部分是石码糖商。但东乡很少加工丸糖,而石码糖商所需要的丸糖,就由本市小批发商供应。龙岩帮采购的也多是丸糖或包仔糖,他们有的直接到“北庙搪市”购买,有的即由小批发商供应。
每逢新糖登场时,在“北庙糖市”每日上市者约有千担,平时亦有三、四百担入市交易。各搪商都到糖市收购并观察市情。糖市以糖的交易为主,还有花生、豆类、地瓜粉等买卖,市场十分活跃。
五、外销情况:
本市食糖经常配往大连、天津、上海、苏州、宁波、温州等通商港口,同时由各港口换购当地土特产:如天津的高梁、史国公、五加皮等名酒,大连的黄豆、豆饼,上海的棉纱、布匹、面粉、化肥、洋白糖,苏州的丝绸,宁波的棉花、布匹,温州的猪油、虾皮、皮旦、绍兴酒、茶油、雨伞等。这种互换的交易,既使商行获得更多的利润,对于沟通埠际的物资交流,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各糖商除经营本产食糖的销售外,都兼营进口白搪。当时进口的有印尼爪哇白糖,其价格约高于本产红糖的百分五十左右,本市向厦门购买进口白搪可以先交定金(约为糖价的三分之一)订购期货,到期货、款两清。后来台湾的机制白糖亦陆续运进本市,其质量与价格和爪哇白糖不相上下,台湾还进口一种粉蜜搪,色微黄、味似冰糖而价钱较高。当时厦门经营白糖进口者,以黄奕住的日兴行为最大宗,约占全岛进口数的百分之七十。抗日战争期间,外搪来源断绝,市场白糖欠缺,潮(州)帮糖行为供应市场的需要,购置电机一台,配套小型设备进行加工白糖,质量虽不如进口的,但也可代替应用。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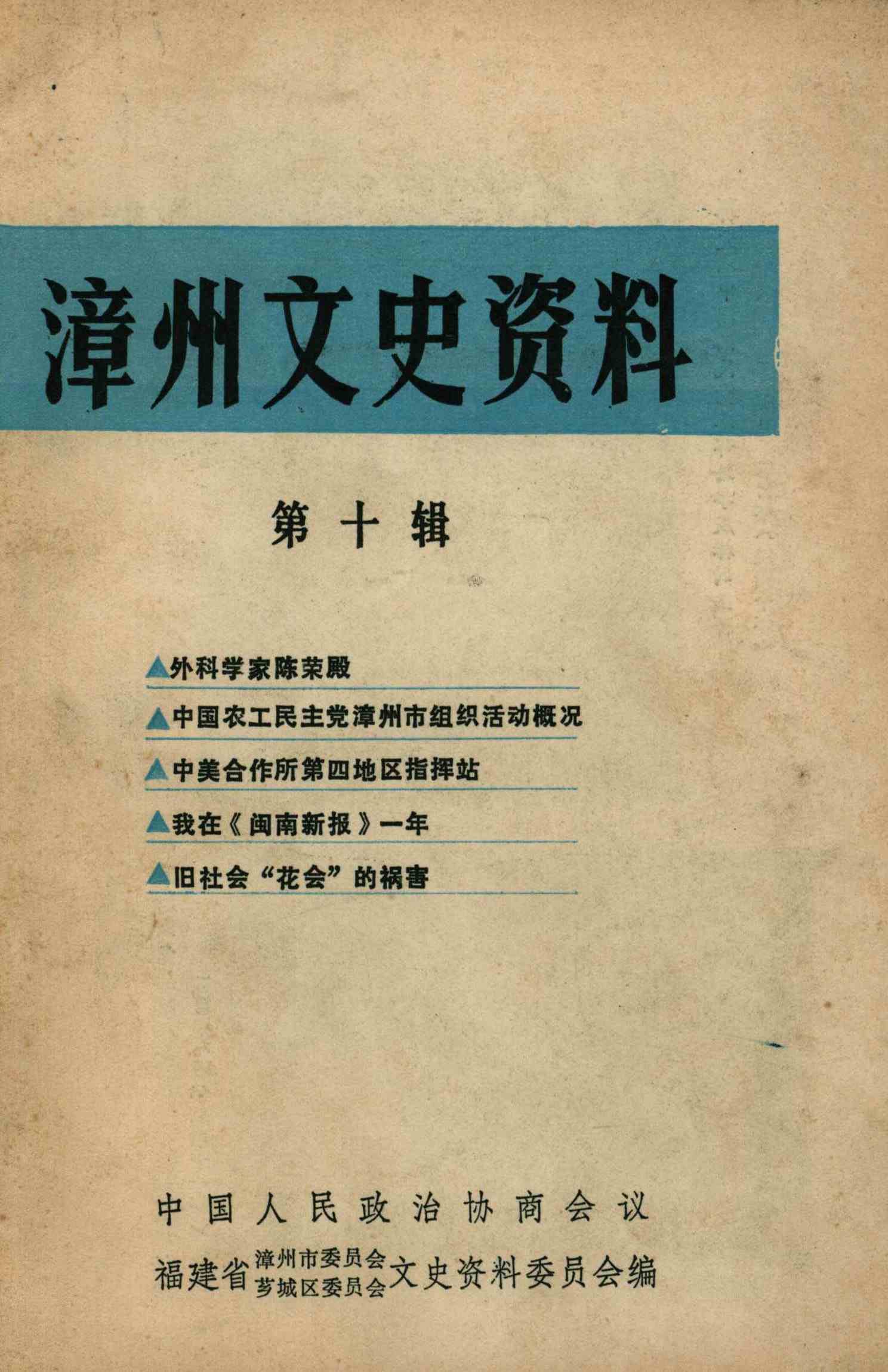
《漳州文史资料》
本书收录了外科学家陈荣殿,爱国华侨韩希琦,爱国民主人士林仲姚,诏安县三位同盟会会员传略,台湾抗日志士张国明,第三党在漳州的早期活动,中国农工民主党漳州市组织活动概况,四十九师张贞部被改编经过,中美合作所第四地区指挥站,“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龙溪支会概况,“义社”在漳州,邵蕙君之死,中统在漳州的组织活动,国民党《中央日报》(漳州版)“流产”经过,我所知道的漳州《南报》,第八中学和第八初级中学琐记,漳州华英小学校史,进德女子中学史略,漳州一所侨办中学,抗战期间龙溪简师内迁纪略,解放前龙溪暑期补习学校和厦大校友中学,三十年代初漳州报纸出版概况,我在《闽南新报》一年,忆漳州民歌演唱会,漳州木版年画与颜氏家族,“石溪金石书画社”小记,漳州业余京剧活动,解放前的漳州糖业,抗战期间龙溪县田赋收入和粮食管理,龙溪县银行概况,漳州驰名老牌刀剪,旧社会“花会”的祸害,浦头话沧桑,漳州市郊区钟姓畲族的族源及其习俗,解放前漳州武术门派的源流概述等多篇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蔡琼琳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