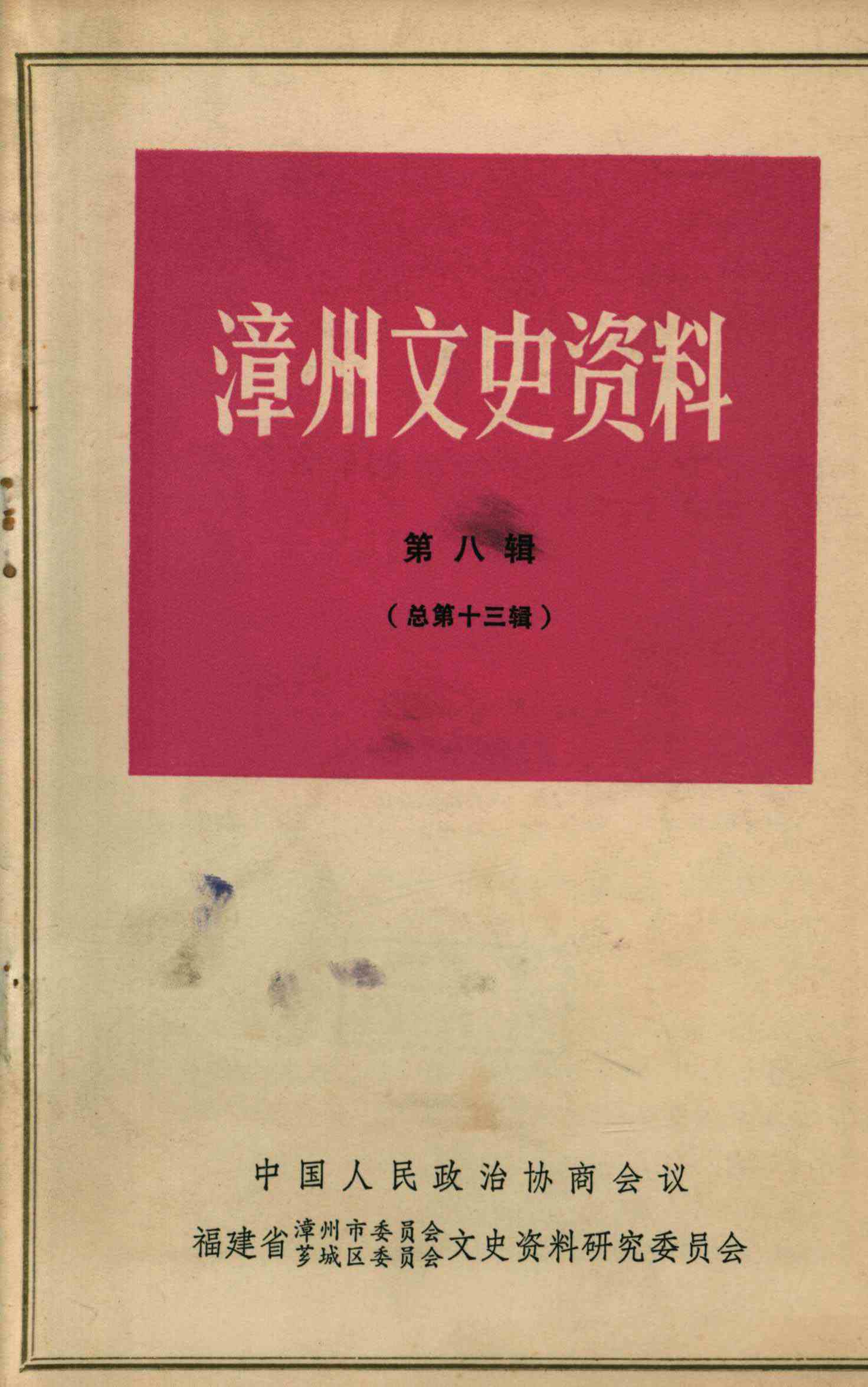国民党一五七师驻闽南“剿共”的回忆
| 内容出处: | 《漳州文史资料》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20003449 |
| 颗粒名称: | 国民党一五七师驻闽南“剿共”的回忆 |
| 分类号: | K295.73 |
| 页数: | 8 |
| 页码: | 65-72 |
| 摘要: | 国民党一五七师黄涛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进驻漳州。师部设在漳州芝山。经过整编,师部直属各处和旅团单位,人事上均作了较大的变动,营以上军官几乎全部撤换。参谋长张光前,参谋处长李宏达,副官处长吕承文,军需处长曾淑云,军械处长谢松龄,军医处长钟兴,军法处少校军法官启桐,政训处长李育培,政训处秘书黄本英,政训处第一科长陈藻文,第二科长陈柏麟,第三科长黄资深。按一五七师编制,下属两个旅,每旅三个团。调到闽南后,名义上受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指挥,实际上仍是第四路军的直辖部队。但黄涛及团、营以上军官并不理睬,没有和谈诚意。表示国民党也是主张抗日的。 |
| 关键词: | 国民党 剿共 回忆 |
内容
国民党一五七师黄涛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日进驻漳州。师部设在漳州芝山(原福建绥靖公署)。经过整编,师部直属各处和旅团单位,人事上均作了较大的变动,营以上军官几乎全部撤换。参谋长张光前(梅县人,陆大毕业),参谋处长李宏达(五华人,陆大毕业),副官处长吕承文,军需处长曾淑云,军械处长谢松龄,军医处长钟兴,军法处少校军法官启桐,政训处长李育培,政训处秘书黄本英,政训处第一科长陈藻文,第二科长陈柏麟,第三科长黄资深。
按一五七师编制,下属两个旅,每旅三个团。四六九旅旅部设龙岩,旅长练惕生(武平人,与黄涛是中学和讲武堂同学)。四七一旅旅部设漳浦,旅长李崇刚(南县人),参谋主任陈英杰(蕉岭人),下属九四〇团,团长叶刚(惠阳人)驻守漳浦;九四一团团长李友庄(行伍出身)驻守云霄;九四七团团长陈浚(又名禹川、惠阳人)驻守海澄石码,其兵力主要对付闽粤边红军独立第三团和独立营。
黄涛,系余汉谋的亲信人物,一贯骄横跋扈,是个刚愎自用的旧式军人,官兵都很怕他。调到闽南后,名义上受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指挥,实际上仍是第四路军的直辖部队。
一九三七年春,黄涛接到陈仪转来蒋介石的电令,要该师限期彻底“剿共”,黄召集张光前,李宏达、李育培等开会研究,拟定了“剿抚兼施”办法,企图以收编张河山、江天赐部的办法那样,收编闽南红军游击队。这时,由于“西安事变”影响,闽南地下党不断主动散发《告国民党官兵书》号召共同抗日。我从部队呈缴上来的文件中,领会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理论,军中下级干部和士兵也多少受些影响。但黄涛及团、营以上军官并不理睬,没有和谈诚意。所以这一期间,该师在闽南“剿共”非常残酷,比国民党中央军还历害。不但“驻剿”、“搜剿”,还采取“游剿”。当时,驻漳浦及海澄的九四〇团和九四二团经常调到诏安、平和一带,配合九四一团轮番“游剿”红军游击队。广东兵,多系从南路募来,该地破产农民或市镇游民,大都以当兵为职业。而且团、营、连长多系黄涛到任后委派的,因此比较卖命,以谋邀功,“进剿”比中央军“积极”。黄涛本人也曾亲自到漳浦、云霄督剿过。
一九三七年五月间,闽粤边红军游击队主要负责人何鸣一行十多人,在平和白沙被俘,解来漳州,关押在政训处前面的牢房里。起初由军法处提审何鸣,后来由陈藻文亲自提问何鸣。我得知陈藻文将何鸣提到政训处饭厅里进行讯问时,即下楼看个究竟,看见饭厅外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大都是师部各处勤杂或下级职员)我挤进去坐在陈藻文坐着的四方饭桌一边,见他两人正在对话。我见何鸣双脚加镣,矮个子,站着对话,面无惧容,泰然自若,侃侃而谈,谈的内容大致阐明国难当头,不能打内战,要求国共合作的道理。陈回答说:“蒋委员长也是主张抗日的呀!要抗日,必须先有准备,要加强国防,才能抗日嘛!”表示国民党也是主张抗日的。而后何鸣阐述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如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而革命的性质必须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何还说到中国不能走也不会走向资本主义的话。前后花了二、三个钟头,气氛是平和的。过后陈藻文又私下与何鸣谈话二、三次。何鸣释放时,是经军法处提问,并派一名参谋或副官陪送回乌山根据地的。从他解来漳州到释放的时间大约十天左右。有人说,何鸣未释放前,被黄涛接见过,甚至说黄涛与何鸣双方作过对等谈判。但当时我在师部却从未听说有接见过的事。
一五七师与闽粤边红军游击队的和平谈判,是自师部释放何鸣后开始的。
五月下旬,何鸣、吴金等人到了漳州,下榻于九龙饭店楼上(全楼均被包下),与一五七师举行和平谈判。其时,黄涛与李育培还在广州,与释放何鸣有直接关系的陈藻文也于这期间请假回了广州。当时接谈与款待何鸣的军事负责人是张光前。
当时我感到何鸣突然前来谈判国共合作,危险性极大。第一,因为我熟悉师部内情,对黄涛、张光前、李育培这些人的政治倾向很了解,他们事前并无两党团结合作抗日的任何动机和看法。尤其是黄涛其人没有政治头脑,纯系唯我独尊、独断专行的旧式军人。其释放何鸣是象收编张河山、江天赐那样,以完成其“剿共”的任务。第二,我认为何对释放的认识是片面、幼稚的,过高估计自己的政治说服力,从而相信国民党真诚合作抗日。第三,当时闽南剿共十分残酷,我自己思想偏左,不相信国民党会合作抗日,认为能做到停止围剿,不加摧残就很好了。我和侯璜同到九龙饭店去看望何鸣、吴金,其时张光前和副官等已先到达。到饭店不久,我即秘密接近吴金,主动引吴金在楼房的最末端房间里与之交谈。我说明公开身份后就提醒吴金说:“你们前来谈判,最好做到停止围剿就好,队伍不要出来,否则会有危险的。”当时吴金被我的话所打动,就说:“我们正担心这个,在山区都认为出来有危险的,是否叫何鸣来一起谈?”我回答:“好”,于是三人又就这件事商谈,我重复与吴金说过的话。当时何鸣面带傲慢神情,两眼望着天花板,对我的建议和警告,不表示接受,也不答话。随后,侯璜从门外撞了进来,我们就中止了谈话。
何鸣、吴金一行在漳州停留大约八、九天时间,我没有再去见他俩了。此后,何鸣、吴金曾被带到城内各中学和师部军事训练班参观过。当时我们师部在城内贴了不少抗日标语,还在中山公园悬挂有醒目的蚕食中国的漫画地图(当年《世界知识》的封面漫画)并公开写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杀绝汉奸”等标语。在何鸣他们看来,自然会从表面上理解或感性认识到当时的一五七师是积极主张抗日的。当何鸣、吴金返回游击区之前,张光前还代表师部设宴欢送何鸣,邀少校以上军官作陪,我也参加,宾主都以两党团结合作抗日发了言。至于双方进行和谈签订所谓“六·二六协议”,以及改编下山那是后来的事。此时只是相互交往接触,促使国共合作而已。
本来张光前在黄涛面前一向不被看重,这次碰上何鸣、吴金的到来,可谓“喜出望外”,认为保位立功的机会到了,便向黄涛通报。黄得悉后,即于六月二日与李育培乘飞机由广州返回漳州,筹划召开漳州各界所谓庆祝“剿共”胜利大会。大约六月五日左右,我接到第三党南方领导人李伯球从广州发来的电报,说我的未婚妻要回广州,促我速回。当时叫我回去的主要任务是参与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志愿团的事(这个组织,系靠拢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立于“七七”事变期间)。我于六月九日离开漳州。这一天,当地国民党党政召开了所谓“漳州各界庆祝剿共胜利大会”,黄涛和李育培都亲自参加。由此可见,何鸣来漳州洽谈国共合作问题,在黄涛看来,只是以改编红军作为“剿共”胜利来看待的。这次大会以后,张光前和陈英杰几次代表黄涛到平和小溪继续谈判,直至达成“六·二六协议”。
我回广州逗留了一个多月,于七月十八日返抵厦门,在一五七师驻厦门办事处得知闽南红军游击队于两天前(七月十六日)在漳浦被该师全面包围缴械的惊人消息。内心十分吃惊,事隔才一个多月,竟酿成如此严重事件,完全出人意料之外。当我回到漳州后,该师一般人均讳莫如深,其所以导致事件爆发的线索,大都在一九五五年肃反时,我为“漳浦事件”而被诬下狱后,经长期被侦讯审问并曾经看到党内有关文件,才使我对“漳浦事件”的情况比较了解。其中值得提供参考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军统插手的问题:厦门军统行动组长沈觐康,系当时厦门警察局局长。一九三七年春,我曾亲见他专程来漳拜会过黄涛,因沈留学过德国,与黄涛、邢参议(黄的随身陪伴)互认留德同学,拉过关系。解放后的六十年代,有外调人员邓某(广东省统战部工作人员)为调查漳浦事件问题,曾亲到抚顺战犯所找沈谈话,沈供认在“漳浦事件”前的六、七月间在漳州活动过,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军统头子戴笠那时还坐水上飞机到厦门,之后来过漳州。该细节不复记忆(证词归档),但其间是否有军统插手,这倒是值得注意的。
(二)余汉谋飞抵漳州的问题:余汉谋于七月十三日飞抵漳州,我在广州见报上公开登载过。当余汉谋抵漳次日(七月十四日),正值国民党第四路军总部成立周年纪念日,黄涛为此大摆宴席欢宴余汉谋总司令(全师营以上军官和师直属军官都参加)。酒宴之后,余暗中命令黄涛:“共产党始终是靠不住的,不宜留下(指红三团全部武装),留下来后祸无穷,非坚决将之缴械不可”。于是黄涛就直接打电话给九四二团团长陈禹川,果然于七月十六日晨制造了“漳浦事件”。
(三)一五七师内有地下党支部问题:一九四八年冬,我在闽粤赣边纵队与朱曼平同志谈到“漳浦事件”的往事时,朱说:“当部队(指红三团)集中在漳浦时,一五七师当时有党的支部存在,当支部同志得到师部下令缴械的秘密情报时,就化装出来通知,但何鸣置若罔闻,还说是庸人自扰”。朱的话给我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联想到一九四七年二月我在香港与尹林平同志交谈中,他曾提过一五七师内有一些熟人,其中九四二团上尉书记胡展光及其侄胡树铮(当时为准尉文书),还有一个是张道仁(师参谋处见习参谋,是我组织读书会的成员),他们三人后来调到粤北时,都携械投奔东纵。提起他们时,尹说:“这三个人都是我在闽南活动时熟悉的,是我领导下的干部,已经在东纵抗日游击战争中牺牲了”。由此可见,事变的秘密情报来源是在九四二团中做机要工作的人及时探到的。故我推想一五七师里的地下党支部一定与这三人有关;其情报来源,以胡展光叔侄提供的为可靠。
(四)指挥事变现场的头头:当时李崇刚还在庐山受训未归,旅部工作由参谋主任陈英杰代理。现场的实际指挥者系九四二团团长陈禹川(陈浚)和陈英杰。包围缴械的系九四二团于十五日晚从石码调到漳浦的。除九四二团外,还有九四一团一部分配合。
事件后,红三团被俘人员集中在漳浦的孔庙。我回抵漳州的第三、四天,张光前打电话叫我和侯璜去漳浦,我问什么事情,张光前答说:“到旅部就知道。”当晚到达旅部时,由旅部少校副官梁炯吩咐我和侯璜以及旅部派来的四九二团政训干事陈光等三四人负责搞登记被俘人员的工作。
当日清晨去孔庙之前,旅部上尉参谋陈定海带我们到现场勘查一番(缴械的操练广场离旅部住地不远),他用手指划着当时九四二团的兵力部署情况,并谈了一些缴械情节,还指着广场一侧的一排平房说:“何鸣、吴金及排以上的干部都扣押在那里”。
我们四人由负责监视的副连长带到孔庙时,看见上、中、下厅还有四百人左右,我们分别席地坐下,登记被俘人员的姓名、年龄、籍贯和志愿。登记时,问他们志愿是什么?那时闹了一个笑话,他们用闽南话回答:“做田”。“做田”,我们起初都听不懂,以后才知道是“种田”的意思。其间游击战士有的质问我们:“你们不是讲合作抗日的吗?为什么缴我们的枪?”表示极大的愤概。由于怕惹麻烦,我们没有理会这些。当天下午六时登记完毕。
何鸣、吴金和被扣押的排以上干部,于八月间解来漳州。九月底,我已知道何鸣、吴金和几个排以上干部被派到厦门搞情报工作。何、吴分别被委派为师部上尉服务员。十月初,我接替陈藻文的厦门工作时,见黄涛在其公馆召见过何、吴一次。十二月底,一五七师奉命返防潮汕前,何鸣、吴金由黄涛批准返回闽西南游击队,其他排以上千部九月初由政训处派一位科员负责监管,记得是集中在郊外一个小庙里。十月初,我从龙岩回来,被邀去讲述抗日形势,还见到大约二十名排以上干部在场,他们仍深表愤懑之神色。以后我调到厦门工作,就不知他们的下落。
按一五七师编制,下属两个旅,每旅三个团。四六九旅旅部设龙岩,旅长练惕生(武平人,与黄涛是中学和讲武堂同学)。四七一旅旅部设漳浦,旅长李崇刚(南县人),参谋主任陈英杰(蕉岭人),下属九四〇团,团长叶刚(惠阳人)驻守漳浦;九四一团团长李友庄(行伍出身)驻守云霄;九四七团团长陈浚(又名禹川、惠阳人)驻守海澄石码,其兵力主要对付闽粤边红军独立第三团和独立营。
黄涛,系余汉谋的亲信人物,一贯骄横跋扈,是个刚愎自用的旧式军人,官兵都很怕他。调到闽南后,名义上受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指挥,实际上仍是第四路军的直辖部队。
一九三七年春,黄涛接到陈仪转来蒋介石的电令,要该师限期彻底“剿共”,黄召集张光前,李宏达、李育培等开会研究,拟定了“剿抚兼施”办法,企图以收编张河山、江天赐部的办法那样,收编闽南红军游击队。这时,由于“西安事变”影响,闽南地下党不断主动散发《告国民党官兵书》号召共同抗日。我从部队呈缴上来的文件中,领会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理论,军中下级干部和士兵也多少受些影响。但黄涛及团、营以上军官并不理睬,没有和谈诚意。所以这一期间,该师在闽南“剿共”非常残酷,比国民党中央军还历害。不但“驻剿”、“搜剿”,还采取“游剿”。当时,驻漳浦及海澄的九四〇团和九四二团经常调到诏安、平和一带,配合九四一团轮番“游剿”红军游击队。广东兵,多系从南路募来,该地破产农民或市镇游民,大都以当兵为职业。而且团、营、连长多系黄涛到任后委派的,因此比较卖命,以谋邀功,“进剿”比中央军“积极”。黄涛本人也曾亲自到漳浦、云霄督剿过。
一九三七年五月间,闽粤边红军游击队主要负责人何鸣一行十多人,在平和白沙被俘,解来漳州,关押在政训处前面的牢房里。起初由军法处提审何鸣,后来由陈藻文亲自提问何鸣。我得知陈藻文将何鸣提到政训处饭厅里进行讯问时,即下楼看个究竟,看见饭厅外挤满了围观的人群,(大都是师部各处勤杂或下级职员)我挤进去坐在陈藻文坐着的四方饭桌一边,见他两人正在对话。我见何鸣双脚加镣,矮个子,站着对话,面无惧容,泰然自若,侃侃而谈,谈的内容大致阐明国难当头,不能打内战,要求国共合作的道理。陈回答说:“蒋委员长也是主张抗日的呀!要抗日,必须先有准备,要加强国防,才能抗日嘛!”表示国民党也是主张抗日的。而后何鸣阐述他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如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因而革命的性质必须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何还说到中国不能走也不会走向资本主义的话。前后花了二、三个钟头,气氛是平和的。过后陈藻文又私下与何鸣谈话二、三次。何鸣释放时,是经军法处提问,并派一名参谋或副官陪送回乌山根据地的。从他解来漳州到释放的时间大约十天左右。有人说,何鸣未释放前,被黄涛接见过,甚至说黄涛与何鸣双方作过对等谈判。但当时我在师部却从未听说有接见过的事。
一五七师与闽粤边红军游击队的和平谈判,是自师部释放何鸣后开始的。
五月下旬,何鸣、吴金等人到了漳州,下榻于九龙饭店楼上(全楼均被包下),与一五七师举行和平谈判。其时,黄涛与李育培还在广州,与释放何鸣有直接关系的陈藻文也于这期间请假回了广州。当时接谈与款待何鸣的军事负责人是张光前。
当时我感到何鸣突然前来谈判国共合作,危险性极大。第一,因为我熟悉师部内情,对黄涛、张光前、李育培这些人的政治倾向很了解,他们事前并无两党团结合作抗日的任何动机和看法。尤其是黄涛其人没有政治头脑,纯系唯我独尊、独断专行的旧式军人。其释放何鸣是象收编张河山、江天赐那样,以完成其“剿共”的任务。第二,我认为何对释放的认识是片面、幼稚的,过高估计自己的政治说服力,从而相信国民党真诚合作抗日。第三,当时闽南剿共十分残酷,我自己思想偏左,不相信国民党会合作抗日,认为能做到停止围剿,不加摧残就很好了。我和侯璜同到九龙饭店去看望何鸣、吴金,其时张光前和副官等已先到达。到饭店不久,我即秘密接近吴金,主动引吴金在楼房的最末端房间里与之交谈。我说明公开身份后就提醒吴金说:“你们前来谈判,最好做到停止围剿就好,队伍不要出来,否则会有危险的。”当时吴金被我的话所打动,就说:“我们正担心这个,在山区都认为出来有危险的,是否叫何鸣来一起谈?”我回答:“好”,于是三人又就这件事商谈,我重复与吴金说过的话。当时何鸣面带傲慢神情,两眼望着天花板,对我的建议和警告,不表示接受,也不答话。随后,侯璜从门外撞了进来,我们就中止了谈话。
何鸣、吴金一行在漳州停留大约八、九天时间,我没有再去见他俩了。此后,何鸣、吴金曾被带到城内各中学和师部军事训练班参观过。当时我们师部在城内贴了不少抗日标语,还在中山公园悬挂有醒目的蚕食中国的漫画地图(当年《世界知识》的封面漫画)并公开写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杀绝汉奸”等标语。在何鸣他们看来,自然会从表面上理解或感性认识到当时的一五七师是积极主张抗日的。当何鸣、吴金返回游击区之前,张光前还代表师部设宴欢送何鸣,邀少校以上军官作陪,我也参加,宾主都以两党团结合作抗日发了言。至于双方进行和谈签订所谓“六·二六协议”,以及改编下山那是后来的事。此时只是相互交往接触,促使国共合作而已。
本来张光前在黄涛面前一向不被看重,这次碰上何鸣、吴金的到来,可谓“喜出望外”,认为保位立功的机会到了,便向黄涛通报。黄得悉后,即于六月二日与李育培乘飞机由广州返回漳州,筹划召开漳州各界所谓庆祝“剿共”胜利大会。大约六月五日左右,我接到第三党南方领导人李伯球从广州发来的电报,说我的未婚妻要回广州,促我速回。当时叫我回去的主要任务是参与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志愿团的事(这个组织,系靠拢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成立于“七七”事变期间)。我于六月九日离开漳州。这一天,当地国民党党政召开了所谓“漳州各界庆祝剿共胜利大会”,黄涛和李育培都亲自参加。由此可见,何鸣来漳州洽谈国共合作问题,在黄涛看来,只是以改编红军作为“剿共”胜利来看待的。这次大会以后,张光前和陈英杰几次代表黄涛到平和小溪继续谈判,直至达成“六·二六协议”。
我回广州逗留了一个多月,于七月十八日返抵厦门,在一五七师驻厦门办事处得知闽南红军游击队于两天前(七月十六日)在漳浦被该师全面包围缴械的惊人消息。内心十分吃惊,事隔才一个多月,竟酿成如此严重事件,完全出人意料之外。当我回到漳州后,该师一般人均讳莫如深,其所以导致事件爆发的线索,大都在一九五五年肃反时,我为“漳浦事件”而被诬下狱后,经长期被侦讯审问并曾经看到党内有关文件,才使我对“漳浦事件”的情况比较了解。其中值得提供参考的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军统插手的问题:厦门军统行动组长沈觐康,系当时厦门警察局局长。一九三七年春,我曾亲见他专程来漳拜会过黄涛,因沈留学过德国,与黄涛、邢参议(黄的随身陪伴)互认留德同学,拉过关系。解放后的六十年代,有外调人员邓某(广东省统战部工作人员)为调查漳浦事件问题,曾亲到抚顺战犯所找沈谈话,沈供认在“漳浦事件”前的六、七月间在漳州活动过,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军统头子戴笠那时还坐水上飞机到厦门,之后来过漳州。该细节不复记忆(证词归档),但其间是否有军统插手,这倒是值得注意的。
(二)余汉谋飞抵漳州的问题:余汉谋于七月十三日飞抵漳州,我在广州见报上公开登载过。当余汉谋抵漳次日(七月十四日),正值国民党第四路军总部成立周年纪念日,黄涛为此大摆宴席欢宴余汉谋总司令(全师营以上军官和师直属军官都参加)。酒宴之后,余暗中命令黄涛:“共产党始终是靠不住的,不宜留下(指红三团全部武装),留下来后祸无穷,非坚决将之缴械不可”。于是黄涛就直接打电话给九四二团团长陈禹川,果然于七月十六日晨制造了“漳浦事件”。
(三)一五七师内有地下党支部问题:一九四八年冬,我在闽粤赣边纵队与朱曼平同志谈到“漳浦事件”的往事时,朱说:“当部队(指红三团)集中在漳浦时,一五七师当时有党的支部存在,当支部同志得到师部下令缴械的秘密情报时,就化装出来通知,但何鸣置若罔闻,还说是庸人自扰”。朱的话给我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联想到一九四七年二月我在香港与尹林平同志交谈中,他曾提过一五七师内有一些熟人,其中九四二团上尉书记胡展光及其侄胡树铮(当时为准尉文书),还有一个是张道仁(师参谋处见习参谋,是我组织读书会的成员),他们三人后来调到粤北时,都携械投奔东纵。提起他们时,尹说:“这三个人都是我在闽南活动时熟悉的,是我领导下的干部,已经在东纵抗日游击战争中牺牲了”。由此可见,事变的秘密情报来源是在九四二团中做机要工作的人及时探到的。故我推想一五七师里的地下党支部一定与这三人有关;其情报来源,以胡展光叔侄提供的为可靠。
(四)指挥事变现场的头头:当时李崇刚还在庐山受训未归,旅部工作由参谋主任陈英杰代理。现场的实际指挥者系九四二团团长陈禹川(陈浚)和陈英杰。包围缴械的系九四二团于十五日晚从石码调到漳浦的。除九四二团外,还有九四一团一部分配合。
事件后,红三团被俘人员集中在漳浦的孔庙。我回抵漳州的第三、四天,张光前打电话叫我和侯璜去漳浦,我问什么事情,张光前答说:“到旅部就知道。”当晚到达旅部时,由旅部少校副官梁炯吩咐我和侯璜以及旅部派来的四九二团政训干事陈光等三四人负责搞登记被俘人员的工作。
当日清晨去孔庙之前,旅部上尉参谋陈定海带我们到现场勘查一番(缴械的操练广场离旅部住地不远),他用手指划着当时九四二团的兵力部署情况,并谈了一些缴械情节,还指着广场一侧的一排平房说:“何鸣、吴金及排以上的干部都扣押在那里”。
我们四人由负责监视的副连长带到孔庙时,看见上、中、下厅还有四百人左右,我们分别席地坐下,登记被俘人员的姓名、年龄、籍贯和志愿。登记时,问他们志愿是什么?那时闹了一个笑话,他们用闽南话回答:“做田”。“做田”,我们起初都听不懂,以后才知道是“种田”的意思。其间游击战士有的质问我们:“你们不是讲合作抗日的吗?为什么缴我们的枪?”表示极大的愤概。由于怕惹麻烦,我们没有理会这些。当天下午六时登记完毕。
何鸣、吴金和被扣押的排以上干部,于八月间解来漳州。九月底,我已知道何鸣、吴金和几个排以上干部被派到厦门搞情报工作。何、吴分别被委派为师部上尉服务员。十月初,我接替陈藻文的厦门工作时,见黄涛在其公馆召见过何、吴一次。十二月底,一五七师奉命返防潮汕前,何鸣、吴金由黄涛批准返回闽西南游击队,其他排以上千部九月初由政训处派一位科员负责监管,记得是集中在郊外一个小庙里。十月初,我从龙岩回来,被邀去讲述抗日形势,还见到大约二十名排以上干部在场,他们仍深表愤懑之神色。以后我调到厦门工作,就不知他们的下落。
相关地名
漳州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