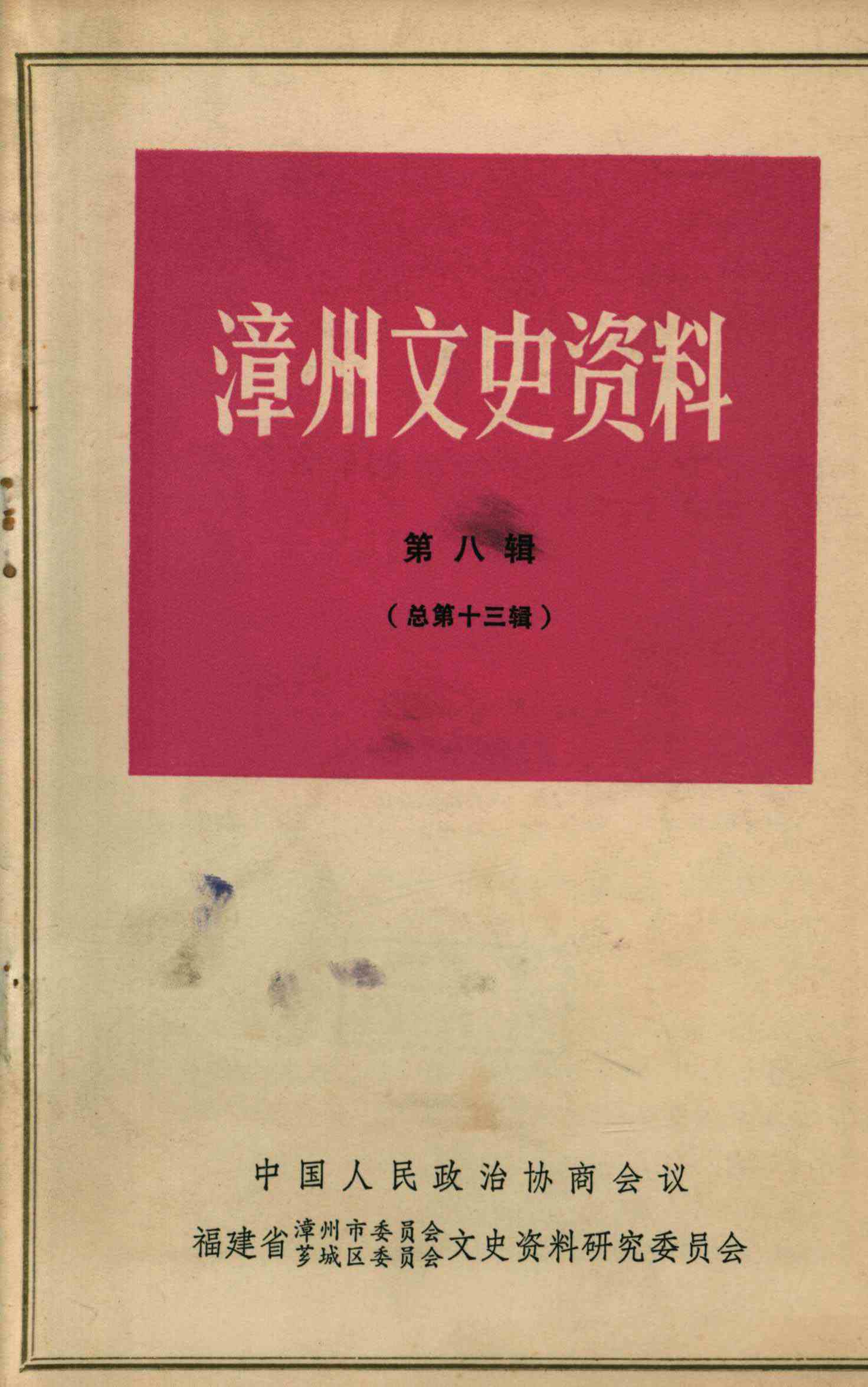天主教在漳州办学始末
| 内容出处: | 《漳州文史资料》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20003446 |
| 颗粒名称: | 天主教在漳州办学始末 |
| 分类号: | B976.1 |
| 页数: | 15 |
| 页码: | 39-53 |
| 摘要: | 解放前天主教厦门区的主持人,为更进一步对我国进行其传教活动,曾经直接和间接地在漳州市内先后创办过五所中小学——崇正中、小学、崇诚小学、崇德小学和崇友小学。这些学校有的是天主教多明我会厦门分会直接控制的,有的是由教徒主办的。但董其事者虽有不同,而其帮同教会进行传教工作的意图却是一致的。我曾先后任崇正小学校长、崇正中学代校长等职务十多年,对于这些学校的情况有些亲身经历和见闻,现提供地方史料参考。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多明我会中断补助费以后,林文彬认为这正是难得的机会,乃改组该校校董会,聘请菲律宾华侨薛拱年挂名为董事长,排除原任董事中的异已,吸收部分厦门大学 |
| 关键词: | 漳州 天主教 办学 |
内容
解放前天主教厦门区的主持人,为更进一步对我国进行其传教活动,曾经直接和间接地在漳州市内先后创办过五所中小学——崇正中、小学、崇诚小学、崇德小学和崇友小学。这些学校有的是天主教多明我会厦门分会直接控制的,有的是由教徒主办的。但董其事者虽有不同,而其帮同教会进行传教工作的意图却是一致的。
我曾先后任崇正小学校长、崇正中学代校长等职务十多年,对于这些学校的情况有些亲身经历和见闻,现提供地方史料参考。
一、学校创办的概况
自一九〇一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漳州天主教依恃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大力发展教务,乃于清末(约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〇年间)把东坂后(现青年路)天主教堂左边临街的房屋三座(即解放后嘉禾街居委会毗连左右共三间),开辟为宣教的会所,名曰“崇正堂”(教内通称“公所”),主持者除外国传教士外,特聘教徒严正道住宿堂内常川办事。每逢星期日晚间开门说教,广招教徒。由于当时我国地方官吏深惧洋人势力,凡事无不屈服,因而一时恃势入教者颇不乏人,可说盛极一时。
当清末倡议废科举兴学堂时,天主教会遂就“崇正堂”招生办学,但属私塾性质,日间办学,夜间传教,称为崇正学堂。迨辛亥革命成立中华民国后,改称崇正国民学校(即今初级小学),由外国传教士顾心明任校长。但其时出钱出力者都是教徒中开设中药铺的天益寿、天保堂、天佑堂和天一堂,而主持校务和担任管教者则是教员严芳辉、张志瀛、卢象鼎等。
一九一五年添办高级班,改称崇正小学,聘江凌云为校长,方玉书、杨遂庵、吴大智等任教员。且加以发展,分设男女两校——女校另设于天主堂左边(解放后曾作为嘉禾幼儿园园址);男校因学生数日增,原址不敷应用,乃商借其时已建成而未开办的仁爱医院(即今公园小学原校舍)为校舍。该院原系多明我会菲律宾支会拨款银元四万元兴建的。但一九一五年落成后,时适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爆发,医疗器材和药品尚未购备,医生亦未派来,因而搁置未用。男校迁入医院后即大事扩充。当时董其事者是教徒天益寿药局老板陈家兄弟,常年经费以教徒捐款和天主堂部分拨款维持。其后学生数逐渐增多,必须加聘教员,自感经费不足,遂由外国传教士转向多明我会请求补助,约定每年资助国币三千元,交由天益寿药局陈家负责主持开支。
一九二〇年间,多明我会为操纵校政,乃排斥陈家主校之权,以多明我会西班牙籍会士吴明德为校长。女校就原址扩充,并附设幼稚园;男校则附设传道班,广收漳泉各地虔诚教徒的子弟为传道生,由学校供给费用。
一九二四年男校兼办中学,女校增办女子师范。中学聘请文人徐飞仙等任教,校务一时颇形发达。
北伐后,我国政府规定外国人不得担任校长职务,教会为应付当时环境,乃聘江凌云为中学校长,小学挂名由吴大智主持。一九二九年秋为准备申请立案,自行取消旧制中学和女子师范名义,校名由崇正学校改称龙溪私立崇正初级中学和崇正小学,聘厦门大学毕业的林文彬任校长。
天益寿药局陈家兄弟被排斥之后,即辞去校董职务,不再支持学校经常费。且于一九二〇年间另行创办崇正公学于近邻的海道后(现瑞京路首)。一九二七年在陈葆中和部分教友的支持下,购得中山公园西门近邻的西园旅社(即今新华西路机关托儿所原址)而迁入新址,以陈素端为校长。后因办理立案问题更名为崇诚小学,校务也刷然一新,该校与崇正虽素不相往来,但因人事调整了,也相安无事。
约在一九三三年间,吴家族长吴俊卿等不甘示弱,而利用其私产原崇正女校楼屋作为校舍,创办崇德小学,而与崇诚小学对立,由吴韵蓉任校长。这时天主教的学校已有崇正(中小学)崇诚、崇德,可谓鼎足而三。抗战开始后,吴家因商业失败难以负担该校经费,同时在国籍神父罗祝三的婉劝下,陈、吴两家族逐渐消除嫉忌和成见,遂于一九三五或三六年间与崇德合并,改名诚德小学,由李在恭任校长。不久,该校经费更感困难,只好停办,校产尽为崇正小学所接收。迨本市解放后,崇正小学归于人民,今为公园小学。
一九三四年间,漳州本堂国籍神父罗祝三因澄观道天主教堂旁边的一些平屋常被过往军队所占用,乃利用其作为校舍而倡办崇友小学,推陈巽为董事长,以该堂传道杨昆兼任校长。但学校设备简陋,校具多向崇正借用。抗日战争发生后就无形停办了。后为陈毓光恃军统势力而霸占,另办航民小学。
二、多明我会的抢夺校权
多明我会是天主教会中位居第三的修会,总会设于罗马,以总会长为该会的领导;各地区设立分会,分会都冠以所谓省名,如“玫瑰省”、“若瑟省”等,主其事者称大会长;分会辖下设立区会,主其事者称会长。厦门教区的多明我会属于玫瑰省,名曰玫瑰省多明我会分会,辖有日本东京、我国厦门等区教务,会址设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为指挥便利,在香港设有办事处。厦门教区区会的会址较常设于厦门,由会员选举会长,管理财政收支,权力相当大,属下的会员对于会长的命令要无条件地服从,拨款也常不按照预算付给,以此控制会员。厦门教区管辖该区所有的多明我会会士,神职由主教指派,生活费用由区会供给。区会经费由香港办事处按月或按季汇付。据我所知:区会或分会都派有神父兼营商业,如开设洋行、书店,经营地买卖,放高利贷等,花样很多,都是以捞钱为目的。
多明我会自一九二〇年起每年拨款补助崇正学校,约于一九二四年间,外国传教士以其出资有责,操纵校务无权,心殊不甘,遂派多明我会会士吴明德为校长,自此经济和人事之权尽操于外国传教士手中。当崇正女校兼办女子师范时,亦派有西班牙籍修女吕顾子、马奉主为主理而控制校务。
北伐后,限于我国政府的规定,吴明德乃由校长而改任主理,但仍操实权,校内外视为太上校长。此后,相连任主理者有西班牙传教士匡国贤、庞迪仁、赖鸿恩、陈国泉、纪理路等。
一九三三年,崇正主理赖鸿恩为扩充学校,充实基金,乃建议多明我会厦门分会会长,派校长林文彬前往海外募款,先后两次:先往南洋、缅甸一带捐募,以所募捐款向教会购得中山公园西门口坐北朝南两层楼房九座(即今公园旅社左右邻近楼房)和楼房后仁德里平屋住宅九间作为校产,期以每月收入的租金充作学校经费;后赴菲律宾,以募款添建一字形校舍一座。林文彬经募的款项,除上列费用外,尚积存现金国币五万元存于华侨银行,抗战发生后转存于英商汇丰银行。后又尽数取出作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资本。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多明我会对崇正的补助中断,从此崇正的一切费用不得不自行负担,但除以学费拨充外,多用募款所存款项和经营投机买卖所得者作为维持。这时主理纪理路的生活费用也由学校负担供给。
从上述天主教会几所学校的创办、扩充和维持等情况,己具体地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崇诚、崇德、崇友等校是由教徒创办和维持的,而崇正中小学除原有校舍(仁爱医院)和每年补助国币三千元(一九四一年以后停止),系出自多明我会之外,凡添建校舍、购置校产以至维持经常费用等等,都出自华侨捐款和学生缴交的学杂费。但是外国传教士却通过教会,以“主理”的身份自始至终控制了学校,作为其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
林文彬担任崇正中学校长十多年,深知外国传教士操纵校务的权力,表面虽对之奉命唯谨,但内心不满。因而在他由海外募款扩充学校,筹足经常费的基金之后,便有意图谋如何摆脱外国传教士的控制而亲自把持学校。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多明我会中断补助费以后,林文彬认为这正是难得的机会,乃改组该校校董会,聘请菲律宾华侨薛拱年挂名为董事长,排除原任董事中的异已,吸收部分厦门大学同学出任董事,以叶英任付董事长而握实权,这样校董会已掌握在校长林文彬的手中。
但是事与愿违,文彬突于一九四七年夏暴卒,因而崇正中学便陷于纷争之中。该校先由总务主任李在恭代理校长。未及一年,李因校内派系之争知难而退。继又组成一个非驴非马的所谓校务委员会,推举原教务主任吴方桂为主任委员维持校务。
这时多明我会认为崇正中学是其所控制的学校,校权被夺死不甘心,屡次图谋夺回又不可得:先延聘教徒江耀东出任校长,但终未能达到接收该校目的;后向省教育厅申诉,而前来调查的省督学又从中偏袒而无结果。
此后,天主教厦门教区代主教胡德禄通过福州教区总主教赵炳文,具函请求驻南京的总主教于斌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提出交涉。一九四八年初胡德禄命纪理路(由陈更生陪同)由厦门前往福州,翌日由福州主教郑长诚携带于斌亲笔函,面向省教育厅厅长梁龙光提出速予处理该校问题的要求;与此同时,天主教教会另行组成一个教会成员所控制的新校董会,聘请与教会和社会较有历史关系的蒋许骙为校长。省教厅惧于帝国主义势力,而蒋又通过其种种关系,并得其时任龙溪县县长钟日兴的支持,派警强行接收该校。至此,多明我会又控制了这个学校。
一九四九年六月,纪理路自知大势已去,即藉医病为名避往香港转赴菲律宾。一九四九年九月漳州解放,该校续办。一九五二年间与进德女子中学合并为漳州市第三中学,以原进德女中为校址。这所教会控制三十年的中学终归于人民所有。
三、外国传教士吴明德、赖鸿恩在教徒中制造分裂
外国传教士口头上说的是仁爱,实际上做的却是在教徒中挑拨离间,制造分裂,使他们互相倾轧。漳州天主教徒中人数较多者,厥推陈(天益寿药局陈廷俊兄弟)、吴(天保堂、天佑堂、天一堂)、黄(黄鼎辉、黄俊卿)三大家族,因此教会内的权力大多操于这三大家族的手中,出钱出力亦由其分担。这三大家族由于宗教信仰一致,且不是亲就是戚,本来就有良好的亲谊关系。传教士吴明德自称是个中国通的多明我会会士,自其出任崇正中小学主理之后,先是夺取校权而排除陈家的职权,继又利用我国封建宗族观念,而与吴家认“同宗”,且从中挑拨离间,使这三个家族情谊破裂,结怨分派。当陈家被排除掌握崇正的职权,愤而联合黄家创设崇正公学(后改为崇诚小学)后,吴明德就拉拢吴家支持崇正,且聘吴大能(爱人医院院长)出任该校董事长、吴俊卿等为董事、吴姓部分修女为教员,使其与陈家形成对立。
当一九二九年崇正公学因经费困难,推举戴贤义、黄镜波等前往菲律宾进行募款时,吴明德心怀妒忌,竟利用崇正学校名义出面否认天主教会有所谓崇正公学的设立,指斥戴、黄赴菲系属“访友探亲”,并非教会或崇正学校所委派,且在菲律宾报端刊登声明启事用以打击破坏,因而引起陈、黄两姓教徒的不满。翌年冬戴、黄由菲返漳后,某日早晨站在天主堂门口等候,乘吴明德在堂内弥撤完毕出堂门时截住责问。崇正学校师生认为这是对该校主理的莫大侮辱而哗然,并推派代表前往厦鼓向厦门教区主教和多明我会厦门区会会长控告漳州堂口的本堂(主持人)外国传教士林茂才挑拨教友惹起事端。主教马守仁、会长余纳爵为此相偕来漳进行调处,但因大部分教友袒护林茂才,而崇正中小学师生则支持吴明德,双方争执几至动武。马、余无法调处乃报告总会,经总会电召吴明德、林茂才返菲质询处办而结束这场纷争。
当抗日战争发生后,吴家因商业萧条无力支持其所创办的崇德小学时,崇正主理赖鸿恩慨然拨款相助,高年级的自然科课程亦允许由崇正小学教员义务兼课。时崇正中学代校长陈巽询问赖鸿恩有什么意图,赖笑而答说:“崇诚小学老是与我校有成见,由我们直接出面计较殊不值得,支持崇德与其对抗是我们的策略。当崇诚难以支持而将停办时,只好由同是教友主办的崇德去接管,这第一步目的达到后,我校就不再支持崇德了。这样它也必然要倒闭,那时只好由唯一存在的我校去接收了,三国岂不是尽归司马懿了吗?林文彬校长在南洋募捐,而我们这样开支,既可博得华侨的赞誉,也可联络吴姓教友,使吴家与陈家不能团结起来,这对我们是很有利的。”陈巽虽对赖的阴谋不赞同,但为饭碗关系,始终不敢泄漏这毒计,而且忠实地按照赖的策划行事。
漳州天主堂的本堂神父一职,一向由西班牙传教士担任,自吴明德与林茂才内讧之后,继任者为国籍神父罗祝三。罗对教友陈、吴两家族因外国传教士的挑拨离间而互相结怨对立,曾从中进行调解。崇诚并入崇德而更名诚德小学,虽是陈、吴两家族复归和好的表现,但外国传教士对这是不满的,仍按其原定阴谋对诚德停拨常年经费的补助,迫使它不得不停办而终为崇正所吞并,这是多么恶毒的诡计。
四、外国传教士千涉校政及其暴行
外国传教士吴明德对天益寿药局陈家兄弟脱离崇正,心怀不满,遂禁止该校教职员与之来往。时有教员徐飞仙、杨遂庵、严芳菲等常在该药局午餐闲谈,致均被吴解聘,从此吴与陈家兄弟彼此间成见更深。
一九二三年,漳州各界和各校青年学生轰轰烈烈举行“五、九”国耻纪念大会时,吴明德竞在崇正学校宣布说:”今天不放假,应照常上课。”学生闻讯哗然,即派代表向吴交涉,吴蛮不讲理说:“学校是多明我会办的,西班牙对日本没有意见,因此不能参加反对日本的活动,不服从命令的都给我滚出去,我们不怕没有学生。”因而掀起了罢课风潮。部分寄宿在校内的学生被其赶出,食宿无处,而前往天益寿药局请求原该校教师严芳菲帮助,经陈家兄弟同意拨出海道后(现瑞京路)一座大厝借为临时宿舍,并供给膳食。嗣因校方和学生各执己见,学潮持久未决,严芳菲等为学生学业起见,就将其组织起来进行补课。
同年征得天益寿药局的同意,就利用这座大厝作为教室而创办了崇正公学。这时由崇正学校转入崇正公学肄业的学生很多,几乎容纳不下。吴明德认为这样是破坏崇正学校,经由多明我会厦门分会会长马德力出面交涉,勒令崇正公学停办。该公学校长杨遂庵等坚不屈从,吴明德恼羞成怒,竟带同崇正学校部分高年级学生拥至崇正公学门前捣毁校牌,双方几至动武,结怨更深。教友方面除吴姓之外,都站在公学这一边,屡经厦门教区主教调解无效,形成相持局面。
一九二九年秋,林文彬继任崇正学校校长时,邀约厦门大学同学丘立塔、黄再兴、陈巽等来校分担校务,原图加以整顿,讵料大权操于“太上校长”吴明德手中,以致难于开展工作。吴在校内不独掌握人事和财务大权,且干预教师的课堂教学和学生的活动,凡中小学教员的进退、薪额的升降等都得先征其同意,甚至购买粉笔亦得先向其报告。他经常在教室外窃听教师的讲课,如提及帝国主义等字眼者便会遭其斥责以至被解聘,而赞扬外国文明、宣传教会“要理”者则得其表扬。
吴明德且拉拢一批学生作其爪牙,他们不但窃据了学生会半数以上的委员,甚至在吴的纵恿下目无校长与教师,可以穿短裤背心、拖木屐随意到校长室来喝茶谈天,校长还得客客气气向他们打招呼;他们且干预校务,向校长或教务主任“商谈”学生升留级和招生录取等问题。有一次向陈巽要求某留级生准予升级、某落第生补取为试读生,遭到陈巽拒绝,这个学生头子竟笑笑说:“稍停,看你会坚持到底吗?”果然不到一小时后,林文彬下了条子嘱陈巽按这学生头子的要求办理。陈巽愤而质问林文彬,林答说:“这是吴主理面嘱的,请老哥为大局凡事马虎些吧!”因此,学期结束时,丘立塔、陈巽提出辞职,林以陈巽经办立案表册等未了,力加慰留,并答应今后加强组织,切实进行整顿,陈巽兼任校长的小学校务亦准予独立,不受中学的干预。
一九三〇年春,林文彬聘江陈诗为教务主任,陈雪华为训育主任、陈景苏为总务主任,意图改革校务。但由于吴明德仍把持校务,且利用江陈诗、陈景苏等攻击陈雪华。其时陈雪华兼任国民党龙溪县党部执委,乃利用上“党义”课或举行“纪念周”等机会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更引起林文彬的不满。陈雪华自知不容于林等,便辞职离校。
外国传教士赖鸿恩,原在本省德化传教,因生活浪漫、行为不端而被召回马尼拉总会,后以帮助新任大会长竞选有功而调任崇正学校主理。他到任后趾高气扬,目空一切,把持操纵校务较吴明德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但勾结地方官吏豪绅,也尽力拉拢有权势的教友。在校内另设主理楼、建立圣母厅,指定教员每日下午下课后向学生宣传教义或讲解“真道”,并以物质奖励饵诱学生积极参加“圣教要理问答”的学习。在校外跑衙门、说是非,尤其对于教友与非教友之间的一般民刑诉讼,常受教友的“拜托”而向经办人“疏通”,俾获胜诉。他就是以这些手段来骗取教友的支持和称赞的。
赖鸿恩喜谈政治,每于上下午课余或星期日来到中小学办公厅找教员乱扯乱谈。有一次竟为虎作伥地说:“中国人卑贱,中国政治腐败,日本侵略中国是合情合理的。”小学教员陈灵惠愤而驳说:“中国人比西班牙人好些,西班牙人是世界上最懒惰的民族,西班牙驻厦门的领事由法国领事兼代,等于是法国的殖民地。”赖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大发脾气,命令校长陈巽即将陈灵惠开除,陈巽驳说:”按照教会的规矩,传教士是不准谈论政治的,你的行为是否违反教规呢?难道只许你批评人家,不许人家批评你们吗?你的命令我无法接受!”赖竟拍案威胁,并诉之林文彬,林出面斡旋时,因陈巽以去留力争,始作罢论。
一九三二年,十九路军驻漳时,赖与该军参谋长黄强国留法且懂法语而结识,后以臭气相投更形亲热,教会中的一些问题都由赖托黄而获解决。一九三四年东路军入漳,总司令蒋鼎文奉行国民党政府的媚外政策,过境军队可驻扎于公立学校,但不敢占用教会学校或其校产。于是赖竟以林文彬由南洋募得的大量捐款收购民房,期以租金充作学校经费。后赖因强奸某地某传道之妻未遂而被控,乃调回马尼拉。
外国传教士纪理路在后坂村(即现步文公社)天主堂时,竟在办公室壁上高挂着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的肖像。当西班牙内战时,他每谈到这情况,不是流泪满面,就是痛哭失声。对我中华民族极端轻视,当他任后坂天主堂本堂时,宣布堂规对教友严加管束,违者每遭鞭打侮辱:如暑天女教友穿着短袖上衣进堂瞻礼,有被辱骂逐出者,有受其以藤条鞭打手臂者,这些受尽侮辱的妇女又不敢将实情告诉其父母或丈夫,因为害怕那些迷信而顽固的家长们,不但不予同情,反会认为触犯堂规,带她们跪在纪理路面前痛悔求赦。纪且养有一头狼狗,名呌“多尼”,出入相偕,他每到野外闲游时常纵狗咬人以取乐,不幸被咬者也无处伸诉。
纪理路曾长期任过厦门教区多明我会区会当家,因此腰缠万贯,任意挥霍。每于傍晚西装革履进城,招集城里相互结纳之辈上菜馆饮酒作乐,猜拳行令,为所欲为。当抗日战争中外汇中断,马主教等生活发生困难时,纪所养的狼狗“多尼”仍每顿备有西餐一份。有一次马主教来漳,偕同罗祝三神父、陈巽等前往后坂村,纪备丰盛酒食招待。客人愉快地入席后,马主教眼看“多尼”平分一份西餐,烦闷不乐。在归途上他叹息说:“纪理路这样荒唐,必遭天谴!”
纪理路在后坂村勾结了一些臭气相投的教友作为爪牙,贱价收购田地、放高利贷,欺压剥削贫苦农民。在该村自办翰苑小学,以严玉梅为校长。纪性喜逢迎,当面谄媚者享以酒肉,议论其行者必遭报复,与好邪游者称兄道弟,对老实练达者则惮而远之。曾勾结龙溪县政府侦缉队长李素夫,凡触其意者常藉端诬陷,报请李素夫予以押办。如某教友素与纪友善,因借高利贷日久无法清还即被拘禁。纪且恃其财势横行无忌,受其害者因惧其淫威,自知蛋石莫敌,敢怒而不敢言。国籍神父罗祝三因纪之种种暴行,曾婉词规劝,纪拒不接受。
林文彬对纪原是必恭必敬,唯命是从的,当崇正中学内迁长太县坂里乡邀纪莅校视察时,林百般奉承。但自林在菲律宾募款返校后,彼此之间就因争掌学校经费而逐断产生矛盾。后纪闻知林在惠安县涂岭故里私建洋楼一座之后,纪对林更加猜忌。而林为巩固其校长职位,遂暗中改组一个自已控制的董事会,因而在林文彬死后就发生了中统分子和教会争夺校权的纷争。
这些外国传教士的所作所为,不但暴露其真面目,同时也反映了他们与反动统治者之间的本质关系。
我曾先后任崇正小学校长、崇正中学代校长等职务十多年,对于这些学校的情况有些亲身经历和见闻,现提供地方史料参考。
一、学校创办的概况
自一九〇一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漳州天主教依恃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大力发展教务,乃于清末(约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〇年间)把东坂后(现青年路)天主教堂左边临街的房屋三座(即解放后嘉禾街居委会毗连左右共三间),开辟为宣教的会所,名曰“崇正堂”(教内通称“公所”),主持者除外国传教士外,特聘教徒严正道住宿堂内常川办事。每逢星期日晚间开门说教,广招教徒。由于当时我国地方官吏深惧洋人势力,凡事无不屈服,因而一时恃势入教者颇不乏人,可说盛极一时。
当清末倡议废科举兴学堂时,天主教会遂就“崇正堂”招生办学,但属私塾性质,日间办学,夜间传教,称为崇正学堂。迨辛亥革命成立中华民国后,改称崇正国民学校(即今初级小学),由外国传教士顾心明任校长。但其时出钱出力者都是教徒中开设中药铺的天益寿、天保堂、天佑堂和天一堂,而主持校务和担任管教者则是教员严芳辉、张志瀛、卢象鼎等。
一九一五年添办高级班,改称崇正小学,聘江凌云为校长,方玉书、杨遂庵、吴大智等任教员。且加以发展,分设男女两校——女校另设于天主堂左边(解放后曾作为嘉禾幼儿园园址);男校因学生数日增,原址不敷应用,乃商借其时已建成而未开办的仁爱医院(即今公园小学原校舍)为校舍。该院原系多明我会菲律宾支会拨款银元四万元兴建的。但一九一五年落成后,时适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爆发,医疗器材和药品尚未购备,医生亦未派来,因而搁置未用。男校迁入医院后即大事扩充。当时董其事者是教徒天益寿药局老板陈家兄弟,常年经费以教徒捐款和天主堂部分拨款维持。其后学生数逐渐增多,必须加聘教员,自感经费不足,遂由外国传教士转向多明我会请求补助,约定每年资助国币三千元,交由天益寿药局陈家负责主持开支。
一九二〇年间,多明我会为操纵校政,乃排斥陈家主校之权,以多明我会西班牙籍会士吴明德为校长。女校就原址扩充,并附设幼稚园;男校则附设传道班,广收漳泉各地虔诚教徒的子弟为传道生,由学校供给费用。
一九二四年男校兼办中学,女校增办女子师范。中学聘请文人徐飞仙等任教,校务一时颇形发达。
北伐后,我国政府规定外国人不得担任校长职务,教会为应付当时环境,乃聘江凌云为中学校长,小学挂名由吴大智主持。一九二九年秋为准备申请立案,自行取消旧制中学和女子师范名义,校名由崇正学校改称龙溪私立崇正初级中学和崇正小学,聘厦门大学毕业的林文彬任校长。
天益寿药局陈家兄弟被排斥之后,即辞去校董职务,不再支持学校经常费。且于一九二〇年间另行创办崇正公学于近邻的海道后(现瑞京路首)。一九二七年在陈葆中和部分教友的支持下,购得中山公园西门近邻的西园旅社(即今新华西路机关托儿所原址)而迁入新址,以陈素端为校长。后因办理立案问题更名为崇诚小学,校务也刷然一新,该校与崇正虽素不相往来,但因人事调整了,也相安无事。
约在一九三三年间,吴家族长吴俊卿等不甘示弱,而利用其私产原崇正女校楼屋作为校舍,创办崇德小学,而与崇诚小学对立,由吴韵蓉任校长。这时天主教的学校已有崇正(中小学)崇诚、崇德,可谓鼎足而三。抗战开始后,吴家因商业失败难以负担该校经费,同时在国籍神父罗祝三的婉劝下,陈、吴两家族逐渐消除嫉忌和成见,遂于一九三五或三六年间与崇德合并,改名诚德小学,由李在恭任校长。不久,该校经费更感困难,只好停办,校产尽为崇正小学所接收。迨本市解放后,崇正小学归于人民,今为公园小学。
一九三四年间,漳州本堂国籍神父罗祝三因澄观道天主教堂旁边的一些平屋常被过往军队所占用,乃利用其作为校舍而倡办崇友小学,推陈巽为董事长,以该堂传道杨昆兼任校长。但学校设备简陋,校具多向崇正借用。抗日战争发生后就无形停办了。后为陈毓光恃军统势力而霸占,另办航民小学。
二、多明我会的抢夺校权
多明我会是天主教会中位居第三的修会,总会设于罗马,以总会长为该会的领导;各地区设立分会,分会都冠以所谓省名,如“玫瑰省”、“若瑟省”等,主其事者称大会长;分会辖下设立区会,主其事者称会长。厦门教区的多明我会属于玫瑰省,名曰玫瑰省多明我会分会,辖有日本东京、我国厦门等区教务,会址设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为指挥便利,在香港设有办事处。厦门教区区会的会址较常设于厦门,由会员选举会长,管理财政收支,权力相当大,属下的会员对于会长的命令要无条件地服从,拨款也常不按照预算付给,以此控制会员。厦门教区管辖该区所有的多明我会会士,神职由主教指派,生活费用由区会供给。区会经费由香港办事处按月或按季汇付。据我所知:区会或分会都派有神父兼营商业,如开设洋行、书店,经营地买卖,放高利贷等,花样很多,都是以捞钱为目的。
多明我会自一九二〇年起每年拨款补助崇正学校,约于一九二四年间,外国传教士以其出资有责,操纵校务无权,心殊不甘,遂派多明我会会士吴明德为校长,自此经济和人事之权尽操于外国传教士手中。当崇正女校兼办女子师范时,亦派有西班牙籍修女吕顾子、马奉主为主理而控制校务。
北伐后,限于我国政府的规定,吴明德乃由校长而改任主理,但仍操实权,校内外视为太上校长。此后,相连任主理者有西班牙传教士匡国贤、庞迪仁、赖鸿恩、陈国泉、纪理路等。
一九三三年,崇正主理赖鸿恩为扩充学校,充实基金,乃建议多明我会厦门分会会长,派校长林文彬前往海外募款,先后两次:先往南洋、缅甸一带捐募,以所募捐款向教会购得中山公园西门口坐北朝南两层楼房九座(即今公园旅社左右邻近楼房)和楼房后仁德里平屋住宅九间作为校产,期以每月收入的租金充作学校经费;后赴菲律宾,以募款添建一字形校舍一座。林文彬经募的款项,除上列费用外,尚积存现金国币五万元存于华侨银行,抗战发生后转存于英商汇丰银行。后又尽数取出作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的资本。
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多明我会对崇正的补助中断,从此崇正的一切费用不得不自行负担,但除以学费拨充外,多用募款所存款项和经营投机买卖所得者作为维持。这时主理纪理路的生活费用也由学校负担供给。
从上述天主教会几所学校的创办、扩充和维持等情况,己具体地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崇诚、崇德、崇友等校是由教徒创办和维持的,而崇正中小学除原有校舍(仁爱医院)和每年补助国币三千元(一九四一年以后停止),系出自多明我会之外,凡添建校舍、购置校产以至维持经常费用等等,都出自华侨捐款和学生缴交的学杂费。但是外国传教士却通过教会,以“主理”的身份自始至终控制了学校,作为其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
林文彬担任崇正中学校长十多年,深知外国传教士操纵校务的权力,表面虽对之奉命唯谨,但内心不满。因而在他由海外募款扩充学校,筹足经常费的基金之后,便有意图谋如何摆脱外国传教士的控制而亲自把持学校。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多明我会中断补助费以后,林文彬认为这正是难得的机会,乃改组该校校董会,聘请菲律宾华侨薛拱年挂名为董事长,排除原任董事中的异已,吸收部分厦门大学同学出任董事,以叶英任付董事长而握实权,这样校董会已掌握在校长林文彬的手中。
但是事与愿违,文彬突于一九四七年夏暴卒,因而崇正中学便陷于纷争之中。该校先由总务主任李在恭代理校长。未及一年,李因校内派系之争知难而退。继又组成一个非驴非马的所谓校务委员会,推举原教务主任吴方桂为主任委员维持校务。
这时多明我会认为崇正中学是其所控制的学校,校权被夺死不甘心,屡次图谋夺回又不可得:先延聘教徒江耀东出任校长,但终未能达到接收该校目的;后向省教育厅申诉,而前来调查的省督学又从中偏袒而无结果。
此后,天主教厦门教区代主教胡德禄通过福州教区总主教赵炳文,具函请求驻南京的总主教于斌向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提出交涉。一九四八年初胡德禄命纪理路(由陈更生陪同)由厦门前往福州,翌日由福州主教郑长诚携带于斌亲笔函,面向省教育厅厅长梁龙光提出速予处理该校问题的要求;与此同时,天主教教会另行组成一个教会成员所控制的新校董会,聘请与教会和社会较有历史关系的蒋许骙为校长。省教厅惧于帝国主义势力,而蒋又通过其种种关系,并得其时任龙溪县县长钟日兴的支持,派警强行接收该校。至此,多明我会又控制了这个学校。
一九四九年六月,纪理路自知大势已去,即藉医病为名避往香港转赴菲律宾。一九四九年九月漳州解放,该校续办。一九五二年间与进德女子中学合并为漳州市第三中学,以原进德女中为校址。这所教会控制三十年的中学终归于人民所有。
三、外国传教士吴明德、赖鸿恩在教徒中制造分裂
外国传教士口头上说的是仁爱,实际上做的却是在教徒中挑拨离间,制造分裂,使他们互相倾轧。漳州天主教徒中人数较多者,厥推陈(天益寿药局陈廷俊兄弟)、吴(天保堂、天佑堂、天一堂)、黄(黄鼎辉、黄俊卿)三大家族,因此教会内的权力大多操于这三大家族的手中,出钱出力亦由其分担。这三大家族由于宗教信仰一致,且不是亲就是戚,本来就有良好的亲谊关系。传教士吴明德自称是个中国通的多明我会会士,自其出任崇正中小学主理之后,先是夺取校权而排除陈家的职权,继又利用我国封建宗族观念,而与吴家认“同宗”,且从中挑拨离间,使这三个家族情谊破裂,结怨分派。当陈家被排除掌握崇正的职权,愤而联合黄家创设崇正公学(后改为崇诚小学)后,吴明德就拉拢吴家支持崇正,且聘吴大能(爱人医院院长)出任该校董事长、吴俊卿等为董事、吴姓部分修女为教员,使其与陈家形成对立。
当一九二九年崇正公学因经费困难,推举戴贤义、黄镜波等前往菲律宾进行募款时,吴明德心怀妒忌,竟利用崇正学校名义出面否认天主教会有所谓崇正公学的设立,指斥戴、黄赴菲系属“访友探亲”,并非教会或崇正学校所委派,且在菲律宾报端刊登声明启事用以打击破坏,因而引起陈、黄两姓教徒的不满。翌年冬戴、黄由菲返漳后,某日早晨站在天主堂门口等候,乘吴明德在堂内弥撤完毕出堂门时截住责问。崇正学校师生认为这是对该校主理的莫大侮辱而哗然,并推派代表前往厦鼓向厦门教区主教和多明我会厦门区会会长控告漳州堂口的本堂(主持人)外国传教士林茂才挑拨教友惹起事端。主教马守仁、会长余纳爵为此相偕来漳进行调处,但因大部分教友袒护林茂才,而崇正中小学师生则支持吴明德,双方争执几至动武。马、余无法调处乃报告总会,经总会电召吴明德、林茂才返菲质询处办而结束这场纷争。
当抗日战争发生后,吴家因商业萧条无力支持其所创办的崇德小学时,崇正主理赖鸿恩慨然拨款相助,高年级的自然科课程亦允许由崇正小学教员义务兼课。时崇正中学代校长陈巽询问赖鸿恩有什么意图,赖笑而答说:“崇诚小学老是与我校有成见,由我们直接出面计较殊不值得,支持崇德与其对抗是我们的策略。当崇诚难以支持而将停办时,只好由同是教友主办的崇德去接管,这第一步目的达到后,我校就不再支持崇德了。这样它也必然要倒闭,那时只好由唯一存在的我校去接收了,三国岂不是尽归司马懿了吗?林文彬校长在南洋募捐,而我们这样开支,既可博得华侨的赞誉,也可联络吴姓教友,使吴家与陈家不能团结起来,这对我们是很有利的。”陈巽虽对赖的阴谋不赞同,但为饭碗关系,始终不敢泄漏这毒计,而且忠实地按照赖的策划行事。
漳州天主堂的本堂神父一职,一向由西班牙传教士担任,自吴明德与林茂才内讧之后,继任者为国籍神父罗祝三。罗对教友陈、吴两家族因外国传教士的挑拨离间而互相结怨对立,曾从中进行调解。崇诚并入崇德而更名诚德小学,虽是陈、吴两家族复归和好的表现,但外国传教士对这是不满的,仍按其原定阴谋对诚德停拨常年经费的补助,迫使它不得不停办而终为崇正所吞并,这是多么恶毒的诡计。
四、外国传教士千涉校政及其暴行
外国传教士吴明德对天益寿药局陈家兄弟脱离崇正,心怀不满,遂禁止该校教职员与之来往。时有教员徐飞仙、杨遂庵、严芳菲等常在该药局午餐闲谈,致均被吴解聘,从此吴与陈家兄弟彼此间成见更深。
一九二三年,漳州各界和各校青年学生轰轰烈烈举行“五、九”国耻纪念大会时,吴明德竞在崇正学校宣布说:”今天不放假,应照常上课。”学生闻讯哗然,即派代表向吴交涉,吴蛮不讲理说:“学校是多明我会办的,西班牙对日本没有意见,因此不能参加反对日本的活动,不服从命令的都给我滚出去,我们不怕没有学生。”因而掀起了罢课风潮。部分寄宿在校内的学生被其赶出,食宿无处,而前往天益寿药局请求原该校教师严芳菲帮助,经陈家兄弟同意拨出海道后(现瑞京路)一座大厝借为临时宿舍,并供给膳食。嗣因校方和学生各执己见,学潮持久未决,严芳菲等为学生学业起见,就将其组织起来进行补课。
同年征得天益寿药局的同意,就利用这座大厝作为教室而创办了崇正公学。这时由崇正学校转入崇正公学肄业的学生很多,几乎容纳不下。吴明德认为这样是破坏崇正学校,经由多明我会厦门分会会长马德力出面交涉,勒令崇正公学停办。该公学校长杨遂庵等坚不屈从,吴明德恼羞成怒,竟带同崇正学校部分高年级学生拥至崇正公学门前捣毁校牌,双方几至动武,结怨更深。教友方面除吴姓之外,都站在公学这一边,屡经厦门教区主教调解无效,形成相持局面。
一九二九年秋,林文彬继任崇正学校校长时,邀约厦门大学同学丘立塔、黄再兴、陈巽等来校分担校务,原图加以整顿,讵料大权操于“太上校长”吴明德手中,以致难于开展工作。吴在校内不独掌握人事和财务大权,且干预教师的课堂教学和学生的活动,凡中小学教员的进退、薪额的升降等都得先征其同意,甚至购买粉笔亦得先向其报告。他经常在教室外窃听教师的讲课,如提及帝国主义等字眼者便会遭其斥责以至被解聘,而赞扬外国文明、宣传教会“要理”者则得其表扬。
吴明德且拉拢一批学生作其爪牙,他们不但窃据了学生会半数以上的委员,甚至在吴的纵恿下目无校长与教师,可以穿短裤背心、拖木屐随意到校长室来喝茶谈天,校长还得客客气气向他们打招呼;他们且干预校务,向校长或教务主任“商谈”学生升留级和招生录取等问题。有一次向陈巽要求某留级生准予升级、某落第生补取为试读生,遭到陈巽拒绝,这个学生头子竟笑笑说:“稍停,看你会坚持到底吗?”果然不到一小时后,林文彬下了条子嘱陈巽按这学生头子的要求办理。陈巽愤而质问林文彬,林答说:“这是吴主理面嘱的,请老哥为大局凡事马虎些吧!”因此,学期结束时,丘立塔、陈巽提出辞职,林以陈巽经办立案表册等未了,力加慰留,并答应今后加强组织,切实进行整顿,陈巽兼任校长的小学校务亦准予独立,不受中学的干预。
一九三〇年春,林文彬聘江陈诗为教务主任,陈雪华为训育主任、陈景苏为总务主任,意图改革校务。但由于吴明德仍把持校务,且利用江陈诗、陈景苏等攻击陈雪华。其时陈雪华兼任国民党龙溪县党部执委,乃利用上“党义”课或举行“纪念周”等机会高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这更引起林文彬的不满。陈雪华自知不容于林等,便辞职离校。
外国传教士赖鸿恩,原在本省德化传教,因生活浪漫、行为不端而被召回马尼拉总会,后以帮助新任大会长竞选有功而调任崇正学校主理。他到任后趾高气扬,目空一切,把持操纵校务较吴明德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但勾结地方官吏豪绅,也尽力拉拢有权势的教友。在校内另设主理楼、建立圣母厅,指定教员每日下午下课后向学生宣传教义或讲解“真道”,并以物质奖励饵诱学生积极参加“圣教要理问答”的学习。在校外跑衙门、说是非,尤其对于教友与非教友之间的一般民刑诉讼,常受教友的“拜托”而向经办人“疏通”,俾获胜诉。他就是以这些手段来骗取教友的支持和称赞的。
赖鸿恩喜谈政治,每于上下午课余或星期日来到中小学办公厅找教员乱扯乱谈。有一次竟为虎作伥地说:“中国人卑贱,中国政治腐败,日本侵略中国是合情合理的。”小学教员陈灵惠愤而驳说:“中国人比西班牙人好些,西班牙人是世界上最懒惰的民族,西班牙驻厦门的领事由法国领事兼代,等于是法国的殖民地。”赖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大发脾气,命令校长陈巽即将陈灵惠开除,陈巽驳说:”按照教会的规矩,传教士是不准谈论政治的,你的行为是否违反教规呢?难道只许你批评人家,不许人家批评你们吗?你的命令我无法接受!”赖竟拍案威胁,并诉之林文彬,林出面斡旋时,因陈巽以去留力争,始作罢论。
一九三二年,十九路军驻漳时,赖与该军参谋长黄强国留法且懂法语而结识,后以臭气相投更形亲热,教会中的一些问题都由赖托黄而获解决。一九三四年东路军入漳,总司令蒋鼎文奉行国民党政府的媚外政策,过境军队可驻扎于公立学校,但不敢占用教会学校或其校产。于是赖竟以林文彬由南洋募得的大量捐款收购民房,期以租金充作学校经费。后赖因强奸某地某传道之妻未遂而被控,乃调回马尼拉。
外国传教士纪理路在后坂村(即现步文公社)天主堂时,竟在办公室壁上高挂着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的肖像。当西班牙内战时,他每谈到这情况,不是流泪满面,就是痛哭失声。对我中华民族极端轻视,当他任后坂天主堂本堂时,宣布堂规对教友严加管束,违者每遭鞭打侮辱:如暑天女教友穿着短袖上衣进堂瞻礼,有被辱骂逐出者,有受其以藤条鞭打手臂者,这些受尽侮辱的妇女又不敢将实情告诉其父母或丈夫,因为害怕那些迷信而顽固的家长们,不但不予同情,反会认为触犯堂规,带她们跪在纪理路面前痛悔求赦。纪且养有一头狼狗,名呌“多尼”,出入相偕,他每到野外闲游时常纵狗咬人以取乐,不幸被咬者也无处伸诉。
纪理路曾长期任过厦门教区多明我会区会当家,因此腰缠万贯,任意挥霍。每于傍晚西装革履进城,招集城里相互结纳之辈上菜馆饮酒作乐,猜拳行令,为所欲为。当抗日战争中外汇中断,马主教等生活发生困难时,纪所养的狼狗“多尼”仍每顿备有西餐一份。有一次马主教来漳,偕同罗祝三神父、陈巽等前往后坂村,纪备丰盛酒食招待。客人愉快地入席后,马主教眼看“多尼”平分一份西餐,烦闷不乐。在归途上他叹息说:“纪理路这样荒唐,必遭天谴!”
纪理路在后坂村勾结了一些臭气相投的教友作为爪牙,贱价收购田地、放高利贷,欺压剥削贫苦农民。在该村自办翰苑小学,以严玉梅为校长。纪性喜逢迎,当面谄媚者享以酒肉,议论其行者必遭报复,与好邪游者称兄道弟,对老实练达者则惮而远之。曾勾结龙溪县政府侦缉队长李素夫,凡触其意者常藉端诬陷,报请李素夫予以押办。如某教友素与纪友善,因借高利贷日久无法清还即被拘禁。纪且恃其财势横行无忌,受其害者因惧其淫威,自知蛋石莫敌,敢怒而不敢言。国籍神父罗祝三因纪之种种暴行,曾婉词规劝,纪拒不接受。
林文彬对纪原是必恭必敬,唯命是从的,当崇正中学内迁长太县坂里乡邀纪莅校视察时,林百般奉承。但自林在菲律宾募款返校后,彼此之间就因争掌学校经费而逐断产生矛盾。后纪闻知林在惠安县涂岭故里私建洋楼一座之后,纪对林更加猜忌。而林为巩固其校长职位,遂暗中改组一个自已控制的董事会,因而在林文彬死后就发生了中统分子和教会争夺校权的纷争。
这些外国传教士的所作所为,不但暴露其真面目,同时也反映了他们与反动统治者之间的本质关系。
相关人物
陈巽
责任者
相关地名
漳州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