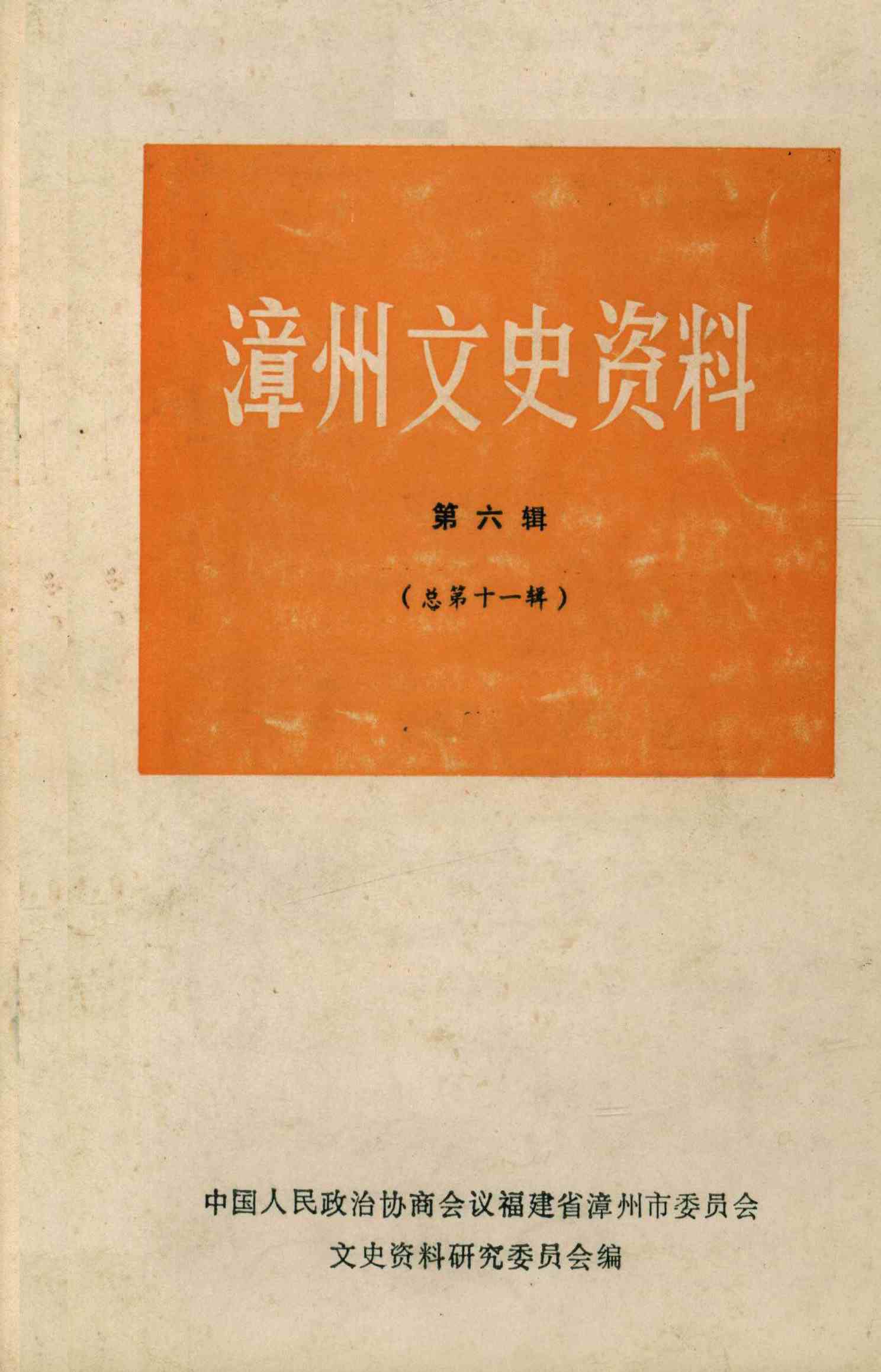漳州钱银庄的经营和货币使用的概述
| 内容出处: | 《漳州文史资料》 图书 |
| 唯一号: | 130720020220003345 |
| 颗粒名称: | 漳州钱银庄的经营和货币使用的概述 |
| 分类号: | F127.57 |
| 页数: | 13 |
| 页码: | 48-60 |
| 摘要: | 我于一九二四年十四岁时就进入漳州银庄为店员,从事这行业工作有十年之久,所以对它的业务范围和经营情况有些了解,为整理地方史料提供参考,特予记述如下。但由于时间过久,未免有遗漏与出入之处,尚请知情者补正。每个帝号铸造的铜钱,其面积、重量、质量等并不一致,而是逐渐缩小和降低的。其中以康熙年间铸造的面积较大、质量较好,所以有“康熙母”之称。同时随着本市对外地贸易的不断扩大和发展,而且其他大中城市如厦门等已有开设银庄的先例。约在一九一○年前后,本市一些豪绅富户们就纷纷鸠集资金,陆续开办了银庄。最盛时期为一九二七年前后,计有二十多家。 |
| 关键词: | 漳州 钱银庄 经营 货币使用 |
内容
我于一九二四年十四岁时就进入漳州银庄为店员,从事这行业工作有十年之久,所以对它的业务范围和经营情况有些了解,为整理地方史料提供参考,特予记述如下。但由于时间过久,未免有遗漏与出入之处,尚请知情者补正。
一、钱庄的开设和货币的使用
清朝末期,市场买卖使用的货币,一般是以银元为主(其间或有以银两计算),以银毫(俗称“银角”)铜钱为辅币。当有些商店在收入辅币较多时,就感到收藏和使用不方便,相反在辅币收入较少时又感到找另不开。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有些人就开设钱店(俗称“钱柜仔店”),经营银毫、铜钱的兑换,以调节盈缺。原本银毫十角值一银元,铜钱千枚亦值一银元,但钱店在铜钱换入时,则以一千另三、四十枚为一银元,兑出时仍以一千枚为一银元;银毫兑换进出时,也有些差额,从中得些利润,作为经办兑换手续的报酬,但所得利润最高也不超过百分之十。后来银毫、铜钱逐渐贬值:银毫跌至十二角为一元,铜钱跌至一千三百余枚为一元。可是不管银毫、铜钱如何升跌,钱店在兑换时仍保持有一定的利润。
铜钱在清朝时期,如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等都有铸造,且标明于铜钱的面上。当时市面上还遗留有少数明朝永乐、正德、万历等年间铸造的铜钱流通使用。铜钱形圆中有方孔,可以用小绳贯穿成串,每串为一千枚,所以叫“一吊钱”或“一贯”。当时串铜钱用的小绳,俗称“钱串”。每个帝号铸造的铜钱,其面积、重量、质量等并不一致,而是逐渐缩小和降低的。其中以康熙年间铸造的面积较大、质量较好,所以有“康熙母”之称。从使用的铜钱上,可以看出当时铸造铜钱时,不但没有标准,甚至铸些“呆钱”(即质量低而板面混杂不清的铜钱)渗着使用。所以钱店在兑换时要加以选择分类,订出不同的兑换价格。在当时“当店”(经营典当业务的)进出的铜钱质量和表面最好,所以俗称“典当清”。其他如付工钱、买布疋、粮油盐等,也须较好的铜钱。如买酒、酱油、药帖等就较随便,甚至可以渗收“呆钱”,因为这些生意的利润较高所以如此。
至清末民初时改铸铜元(俗称“铜镭”)以代铜钱为辅币。原来规定每个铜元当铜钱十文(枚),每十个铜元为一角,但以后跌至一角换得十二个铜元,这样比值沿用颇久,其后又逐渐贬值,大约到一九三○年左右竟跌至一角可换得三十二、三个铜元。
当时市面流通的银毫大部分是宣统年间福建、广东两省铸造的“龙毫”,有双角(二角)、单角(一角)两种,其他如“江南”和湖南、湖北等省铸造的银毫,在市面流通较小,甚至拒绝使用。后来又有“福建官局造”的铸版,但只有双角而无单角。一九一八年陈炯明率领粤军入闽,建立“闽南护法区”以后,铸造民国八年、民国九年两种双角银毫,质量比“龙毫”差、比值亦较低,而且使用不甚普遍,仅限于其统辖地区。至癸亥(一九二三年)、甲子(一九二四年)年间又铸造“三面旗”银毫,质量亦差,流通范围亦不广。又有广东省铸造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基版的双角银毫,亦流通于漳属一带,数量极少。由于各种银毫的质量都不高,比值就降到十三、四角为银元一元。特别是一九二四年北洋军阀张毅统治漳属以后,为敲剥民财而筹设造币厂(地址在本市竹巷下南方巷右边大厝内),铸造民国十三年版的双角银毫,银质极差,且逐版降低质量。他持其割据地方的势力,擅自规定以十四角五分比值为银元一元,强迫在市面使用,人民慑其淫威而不敢拒用。张还派其爪牙到各银庄将其所铸造的低质银毫强换银元,银庄深受其扰,而张毅却以此发了横财。这些质量较差的银毫,后来由各银庄逐渐按折换入,回炉熔为纹银,运往厦门兑出。
抗日战争期间,银毫,铜元由国家银行逐渐回收,并印发五角、二角、一角三种钞票代替银毫,铸造五分、二分、一分三种镍币代替铜元,作为辅币流通。
当时钱庄除经营兑换业务外,还为人鉴别银元的真假,假银元有铜的、铅的、色铜、色铅的等。银元流通的初期,一般小商贩对银元的真伪辨别不清,因而托钱庄代为鉴别,每鉴定一个银元,得付给二、三枚铜钱作为手续费,而钱庄就在银元的版面上打个铁印以示负责。不少银元因多次送银庄鉴定,铁印越打越多,甚至打成凹形。但后来银元流通较多,使用较久,能鉴别银元真伪的人亦普遍,就不必托钱庄鉴别了。此后新铸造而在市上流通的银元,不再打号,且以平版者较为通用,而以前的“花银”(打号的银元)竟得稍为降低价值。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我国自铸的银元极少,只有光绪、宣统年间铸造极少数的一元(俗称“大银”)、五角(俗称“中银”)的银元,而在市面流通的大部分是外国铸造而输入的银元通称“大洋”。其中以日本的“龙银”最多,还有墨西哥的“鹰银”(有直边和鳝鱼骨边两种),以及其他如立身执叉、坐身执叉、妇女执花等等外国银币。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逐步收回清光绪、宣统年间铸造的银元,于民国三年铸造袁世凯头像版的银元,其后在民国七、八年间又以原版铸造一部分。一九二六年北伐后,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由国家银行改铸了孙中山头像版的银元,其后又铸出帆船版的银元,但质量都较差。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银元逐渐由国家银行回收,陆续发行钞票流通。但由于物价波动,钞票一直在贬值。
当时全市钱店计有吕春源的庆源、黄张珍的源丰,以及建隆、金连记、谦记、万选、启瑞、瑞兴、茂美等二十多家,其中以庆源、源丰这两家的业务较为活跃,所以此后银庄的经理和店员大都是这两家培养出来的。
二、由钱庄发展为银庄的经过及其业务
(一)开设银庄雏形的孕育
由于经营钱庄者的资本较一般商店雄厚可靠,因而有些人将剩余款项寄存于钱庄而得些利息,而钱庄则将存款转借给较妥当的商家,收取略高的利息而得些利润,由于有了这种存放款的业务,就孕育了开设银庄的雏形。同时随着本市对外地贸易的不断扩大和发展,而且其他大中城市如厦门等已有开设银庄的先例。因而有些官绅豪富认为这是一条发财致富的门路:开办银庄是以轻利收储,高利放贷,从中牟取利润的经营;自己集资开设既能确保自己的资财不被别人所倒欠,又能运用存款作为囤积居奇的资本,且能得到优惠的利息(一般对银庄股东存欠款的利息都加以优待),又能在社会上提高名誉地位,是一种名利双收的事业,因而纷纷向这方而投资,以图攫取更多的财富。约在一九一○年前后,本市一些豪绅富户们就纷纷鸠集资金,陆续开办了银庄。最早的是富商庄启勇开办启源银庄(设于大路头,即现厦门路东段),庄自任经理,后由许桂芳接任。此后有厦门豫丰银庄与本市诊原堂陈启裕等合资经营的豫原银庄,由吕春源、郑秉禹任经理(设于陈公巷,即现厦门路西段)、又有天益寿药局和厦门谦顺洋行合资,由杨斌侯为经理的天元(设于府口街,即现台湾路),这三家开设较早,业务较兴旺,各吸收市面游资约七、八十万元,在银庄行业中号称“三元”。继而有以陈智君为主的福成、以黄莲舫为主的百源、以洪茂堂为主的均通和溢源、以高大方为主的漳州银号。嗣后有如雨后春笋,陆续不断地开设了恒源(李惠生为主)、永孚(高东岗为主)、恒足(林琯玉为主)、华侨(蔡竹禅为主)、宏源(黄友冬为主)、万源(陈承五为主)、德祥(谢梅英为主)、百川(高鸿〓为主)、建康(杨逢年为主),以及集益、京元、美祥、宝元、达丰、福原、建丰、益记、裕源、光美、互益、天南、国兴、宏济、济川、哲记、信通、豫通等三十余家,系先后开办,并非同时并存。最盛时期为一九二七年前后,计有二十多家。
(二)银庄的业务竞争和银庄工会的组织
当时银庄的业务是以存放款为主,兼办汇兑和兑换。存款一般以每百元付出月息七角,借款以每百元收入月息一元二角。由于同行户数开设过多,业务上竞争剧烈,多采取提高存款利息,降低放款利率及汇费等以吸引客户。如对大户存款每百元月息提高到八、九角,妥当户借款每百元月息降低到一元左右。为解决同业间的矛盾,经过同业讨论成立银庄公会,各银庄参加为会员,按资金和营业的多少分为三等(一等交纳会金200元、二等150元、三等100元,以这会金的利息作为公会费用),并制定一些规章制度:规定存放款利率和汇费的划一,各须遵守,如有违反者则没收其交纳的会金。当时因国民党反动政府和驻军经常要向银庄借款、借饷,所以由公会延聘与军政方面有来往交情的豪绅作为“出官”与其周旋、说情。该公会设于断蛙池(即现延安南路),历任会长为许桂芳、郑秉禹、杨斌侯、黄友冬、谢梅英、蔡竹禅、高鸿〓等。
(三)银庄的业务手续:
凡与银庄开户者发给小簿以资记账,小簿有两种:一为存款簿,只能存不能借;一为来往簿,可以超支,但不能超过限额,甚至有的还须托人担保或以房地产契据作押。
银庄使用的票据有两种:一是凭条,由银庄开给客户使用的;一是支票,由客户开给受款人。这两种票据都可以到银庄取款,但开出支票的客户如无款额,银庄就拒付而予以驳回,所以有的商户(客户)由于一时资金不能周转,就开出限期的支票,这叫“空头支票”。此外另有一种转账的办法:例如厦门行家到漳州向五谷、棉布、百货等行业收取货款,交款户可在厦门行家的收款簿上写明由本市某银庄拨交款项若干,并盖上印记为凭。(当日某银庄即与付款户对账),厦门行家则向拨款银庄换取向厦门银庄领款的汇票。由于那时还没有转账支票这简便办法,所以对凭条,支票的使用较为烦杂,因而增加了现金的收付数额。
当时银庄和商户(客户)进出的银元,一般是“总银”——平版银元和花银(打过花的银元)混用;如在银庄本途互领票款或解款往厦门,则必须全部平版银元,不能混用花银。当时钞票很少,市上使用的只有中国银行和中南银行印发的,其后又增加了美丰银行的钞票,至于由外埠流入的通商银行、盐业银行等的钞票都拒不使用。由于流通的钞票少,而商家又为外出携带方便,需要兑换钞票时必须补贴“票水”,每百元补贴二三角,且因“银水”(什银价格的变动)的时价早晚不同,“票水”(指对各埠的汇票)也时常变动。所以各银庄在客户的来往簿上都盖上“银水、票水现会,以后不得多论”的印记。至于“银水”、“票水”的行情,是每日由厦门报来的。当时叻币、港币与我国币值相差不多,荷币每盾约值八角左右,在福州有时还兼用“台伏”(该台伏是福州的地方币,是内有信誉的行家发出不同数额的票据在本市使用,亦叫伏票),每伏票约值七,八角。
(四)汇兑业务和在厦门开设漳源银庄
在汇兑业务上,对邻近地区的石码、厦门一般都有直接来往,可以开汇票付与客户直接到当地银庄支取。如汇往香港、福州、汕头、上海等地,则需经与厦门开户银庄如漳源等转根,办法是收票根寄往厦门漳源银庄等由其批转给付款地的承付银庄,而来往账目由厦分头结算;如本市收到上海等地的汇票,亦托由厦门银庄代收。
当时漳州各银庄为汇兑方便、存款可靠,以及自己能赚回利润,认为有必要在厦门设立自己的机构,因而于一九二七年间合股(由各银庄认股,每股一千元)集资四万元在厦门开设漳源银庄,聘请较熟悉厦门情况的陈实甫为经理,并推举我地黄仁裕担任付经理,以资监督。这样由于漳源银庄全盘垄断了漳州与厦门来往的业务,经营业务非常发达,逐年得利数字甚为可观。其后本市永孚银庄又与厦商合伙在厦开设裕孚银庄。而天元、豫原亦在石码镇开设分庄。嗣后邻近各地如海澄白水营、南靖山城、平和小溪、云霄等,因受本市影响和商业交易的发展亦陆续开设了银庄。
三、银庄店员的工作、待遇和组织
银庄店员的工作较繁忙,由于同业的竞争,为争取业务除星期日休息外,每日都得派店员分头到各客户去联系业务,俗称“出街”;同时了解各行业经营情况,打听各客户生意的盈亏讯息,作为处理业务的借鉴。
店员“出街”向各客户收款时,备有收款盖印簿,客户取款亦备有付款盖印簿,便于与来往簿核对,如有“小簿失笔”则以“大账为凭”。存放款每月结算母利一次,半年将利并母。当时使用旧式簿记比较复杂不便,且分为外内柜——外柜负责记上逐笔来往的“草清”(有的甚至还设有“暂草”),逐日抄上“日清”;内柜负责将“日清”抄上“总清”(即分户账目)。每月将“日清”和“总清”账目核对一次,避免抄错。同时另设有“日积簿”(或称“便览”),就是经常将各客户的存、欠数字加以表达,使店员胸有成竹,便于掌握收付。这种种账法比起新式簿记,不但繁琐而且容易出差错。
银庄店员的待遇比其他行业好,不但工资较高(一般普通店员的月薪约银元十五元左右,比其他约多百分之三、四十),而且年终又有一笔可观的“赏年”(即奖金),特别是当经理(俗称“家长”)可以得到盈利百分之十的抽分。店员在工作方面比其他行业优越,而且有机会接触到社会上的一些上层人物,较有高攀的机缘,所以一般人很希望其子弟能进入银庄工作。
一九二六年末,北伐军进占漳州以后,在漳州政治监察公署的领导下,曾以银庄店员为主体、吸收棉布、百货等行业的店员参加,成立漳州店员工会,设会址于澄观道,正会长为王绍辉、付会长谢紫庭(这两人系银庄行业店员)、付会长王玉书(棉布行业店员),下设组织、宣传等,开展社会和文娱活动。但豪绅、资本家认为该组织对他们不利,极力反对,政治监察公署为此曾指示要严密组织,健全机构,防止其破坏活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后,该组织即被解散了。
四、银庄停业以至倒闭情况
一般看来银庄似是一种稳健的生意,其实存在许多不健全的因素,特别是最忌滚支(存户争取存款),造成应付不灵而致于搁浅,甚至导致停业或歇业。这是由于旧社会时局经常变动,一遇政变,存户对银庄不信任争先恐后地要讨回存款,而银庄一时又难以收回放款或变卖抵押的不动产等,虽有的依仗股东是外国籍民或教徒以及地方官绅的权势对欠户进行百般的逼讨,可是欠户总是一时不能清还,甚至有的故意拖延;而银庄的股东又不肯取出现金来应付,抱着以债抵债的思想,认为宁使别人去吃亏,也不愿负起责任来维持,就这样赖下去,使银庄瘫痪、倒闭以至进行清理。各欠款户(包括股东的欠款)则乘机向存款户买折抵账,得到意外之财、最受亏的是一些平民,平时勤俭粒积的“老本”存款被倒掉,他们既无权势去追讨,又不能受到法律的维护,真是悲苦万分,虽哀天呼地也仍得不到偿还,这正是旧社会人吃人的真实写照。
在二十多年间,先后开设了三十余家银庄,但在政局多变的情况下,一般寿命都不长,各股东虽每年分得一些红利,却都是记在账面上,但终究不如当经理的实惠,所以有“风水头出家长”的俗谚(意思是经营得利只是经理先得到好处)。一九三二年四月间,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进占漳州,五月同师闽西中央根据地以后,漳州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由于苛捐杂税和重重剥削所造成的人民贫困、农村破产和社会经济的虚假繁荣终于暴露出来。因而从一九三二年秋到三三年间,各银庄在存户讨支和欠户不能清还债务的情况下,全部先后停业以至倒闭清理。由于银庄经营的结果已不能满足豪富们获得暴利的奢望,他们无意再继续经营这种行业,同时银庄也已不能取信于人民,难以吸收存款以发展业务。自一九三四年间以后,国民党四大家族所控制的国家银行,先后在本市设立办事处、分支行,经营存放款和汇兑等,取代了银庄的业务,至此银庄就成为商业史上的陈述。
一、钱庄的开设和货币的使用
清朝末期,市场买卖使用的货币,一般是以银元为主(其间或有以银两计算),以银毫(俗称“银角”)铜钱为辅币。当有些商店在收入辅币较多时,就感到收藏和使用不方便,相反在辅币收入较少时又感到找另不开。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有些人就开设钱店(俗称“钱柜仔店”),经营银毫、铜钱的兑换,以调节盈缺。原本银毫十角值一银元,铜钱千枚亦值一银元,但钱店在铜钱换入时,则以一千另三、四十枚为一银元,兑出时仍以一千枚为一银元;银毫兑换进出时,也有些差额,从中得些利润,作为经办兑换手续的报酬,但所得利润最高也不超过百分之十。后来银毫、铜钱逐渐贬值:银毫跌至十二角为一元,铜钱跌至一千三百余枚为一元。可是不管银毫、铜钱如何升跌,钱店在兑换时仍保持有一定的利润。
铜钱在清朝时期,如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等都有铸造,且标明于铜钱的面上。当时市面上还遗留有少数明朝永乐、正德、万历等年间铸造的铜钱流通使用。铜钱形圆中有方孔,可以用小绳贯穿成串,每串为一千枚,所以叫“一吊钱”或“一贯”。当时串铜钱用的小绳,俗称“钱串”。每个帝号铸造的铜钱,其面积、重量、质量等并不一致,而是逐渐缩小和降低的。其中以康熙年间铸造的面积较大、质量较好,所以有“康熙母”之称。从使用的铜钱上,可以看出当时铸造铜钱时,不但没有标准,甚至铸些“呆钱”(即质量低而板面混杂不清的铜钱)渗着使用。所以钱店在兑换时要加以选择分类,订出不同的兑换价格。在当时“当店”(经营典当业务的)进出的铜钱质量和表面最好,所以俗称“典当清”。其他如付工钱、买布疋、粮油盐等,也须较好的铜钱。如买酒、酱油、药帖等就较随便,甚至可以渗收“呆钱”,因为这些生意的利润较高所以如此。
至清末民初时改铸铜元(俗称“铜镭”)以代铜钱为辅币。原来规定每个铜元当铜钱十文(枚),每十个铜元为一角,但以后跌至一角换得十二个铜元,这样比值沿用颇久,其后又逐渐贬值,大约到一九三○年左右竟跌至一角可换得三十二、三个铜元。
当时市面流通的银毫大部分是宣统年间福建、广东两省铸造的“龙毫”,有双角(二角)、单角(一角)两种,其他如“江南”和湖南、湖北等省铸造的银毫,在市面流通较小,甚至拒绝使用。后来又有“福建官局造”的铸版,但只有双角而无单角。一九一八年陈炯明率领粤军入闽,建立“闽南护法区”以后,铸造民国八年、民国九年两种双角银毫,质量比“龙毫”差、比值亦较低,而且使用不甚普遍,仅限于其统辖地区。至癸亥(一九二三年)、甲子(一九二四年)年间又铸造“三面旗”银毫,质量亦差,流通范围亦不广。又有广东省铸造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基版的双角银毫,亦流通于漳属一带,数量极少。由于各种银毫的质量都不高,比值就降到十三、四角为银元一元。特别是一九二四年北洋军阀张毅统治漳属以后,为敲剥民财而筹设造币厂(地址在本市竹巷下南方巷右边大厝内),铸造民国十三年版的双角银毫,银质极差,且逐版降低质量。他持其割据地方的势力,擅自规定以十四角五分比值为银元一元,强迫在市面使用,人民慑其淫威而不敢拒用。张还派其爪牙到各银庄将其所铸造的低质银毫强换银元,银庄深受其扰,而张毅却以此发了横财。这些质量较差的银毫,后来由各银庄逐渐按折换入,回炉熔为纹银,运往厦门兑出。
抗日战争期间,银毫,铜元由国家银行逐渐回收,并印发五角、二角、一角三种钞票代替银毫,铸造五分、二分、一分三种镍币代替铜元,作为辅币流通。
当时钱庄除经营兑换业务外,还为人鉴别银元的真假,假银元有铜的、铅的、色铜、色铅的等。银元流通的初期,一般小商贩对银元的真伪辨别不清,因而托钱庄代为鉴别,每鉴定一个银元,得付给二、三枚铜钱作为手续费,而钱庄就在银元的版面上打个铁印以示负责。不少银元因多次送银庄鉴定,铁印越打越多,甚至打成凹形。但后来银元流通较多,使用较久,能鉴别银元真伪的人亦普遍,就不必托钱庄鉴别了。此后新铸造而在市上流通的银元,不再打号,且以平版者较为通用,而以前的“花银”(打号的银元)竟得稍为降低价值。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我国自铸的银元极少,只有光绪、宣统年间铸造极少数的一元(俗称“大银”)、五角(俗称“中银”)的银元,而在市面流通的大部分是外国铸造而输入的银元通称“大洋”。其中以日本的“龙银”最多,还有墨西哥的“鹰银”(有直边和鳝鱼骨边两种),以及其他如立身执叉、坐身执叉、妇女执花等等外国银币。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逐步收回清光绪、宣统年间铸造的银元,于民国三年铸造袁世凯头像版的银元,其后在民国七、八年间又以原版铸造一部分。一九二六年北伐后,国民政府建都南京,由国家银行改铸了孙中山头像版的银元,其后又铸出帆船版的银元,但质量都较差。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银元逐渐由国家银行回收,陆续发行钞票流通。但由于物价波动,钞票一直在贬值。
当时全市钱店计有吕春源的庆源、黄张珍的源丰,以及建隆、金连记、谦记、万选、启瑞、瑞兴、茂美等二十多家,其中以庆源、源丰这两家的业务较为活跃,所以此后银庄的经理和店员大都是这两家培养出来的。
二、由钱庄发展为银庄的经过及其业务
(一)开设银庄雏形的孕育
由于经营钱庄者的资本较一般商店雄厚可靠,因而有些人将剩余款项寄存于钱庄而得些利息,而钱庄则将存款转借给较妥当的商家,收取略高的利息而得些利润,由于有了这种存放款的业务,就孕育了开设银庄的雏形。同时随着本市对外地贸易的不断扩大和发展,而且其他大中城市如厦门等已有开设银庄的先例。因而有些官绅豪富认为这是一条发财致富的门路:开办银庄是以轻利收储,高利放贷,从中牟取利润的经营;自己集资开设既能确保自己的资财不被别人所倒欠,又能运用存款作为囤积居奇的资本,且能得到优惠的利息(一般对银庄股东存欠款的利息都加以优待),又能在社会上提高名誉地位,是一种名利双收的事业,因而纷纷向这方而投资,以图攫取更多的财富。约在一九一○年前后,本市一些豪绅富户们就纷纷鸠集资金,陆续开办了银庄。最早的是富商庄启勇开办启源银庄(设于大路头,即现厦门路东段),庄自任经理,后由许桂芳接任。此后有厦门豫丰银庄与本市诊原堂陈启裕等合资经营的豫原银庄,由吕春源、郑秉禹任经理(设于陈公巷,即现厦门路西段)、又有天益寿药局和厦门谦顺洋行合资,由杨斌侯为经理的天元(设于府口街,即现台湾路),这三家开设较早,业务较兴旺,各吸收市面游资约七、八十万元,在银庄行业中号称“三元”。继而有以陈智君为主的福成、以黄莲舫为主的百源、以洪茂堂为主的均通和溢源、以高大方为主的漳州银号。嗣后有如雨后春笋,陆续不断地开设了恒源(李惠生为主)、永孚(高东岗为主)、恒足(林琯玉为主)、华侨(蔡竹禅为主)、宏源(黄友冬为主)、万源(陈承五为主)、德祥(谢梅英为主)、百川(高鸿〓为主)、建康(杨逢年为主),以及集益、京元、美祥、宝元、达丰、福原、建丰、益记、裕源、光美、互益、天南、国兴、宏济、济川、哲记、信通、豫通等三十余家,系先后开办,并非同时并存。最盛时期为一九二七年前后,计有二十多家。
(二)银庄的业务竞争和银庄工会的组织
当时银庄的业务是以存放款为主,兼办汇兑和兑换。存款一般以每百元付出月息七角,借款以每百元收入月息一元二角。由于同行户数开设过多,业务上竞争剧烈,多采取提高存款利息,降低放款利率及汇费等以吸引客户。如对大户存款每百元月息提高到八、九角,妥当户借款每百元月息降低到一元左右。为解决同业间的矛盾,经过同业讨论成立银庄公会,各银庄参加为会员,按资金和营业的多少分为三等(一等交纳会金200元、二等150元、三等100元,以这会金的利息作为公会费用),并制定一些规章制度:规定存放款利率和汇费的划一,各须遵守,如有违反者则没收其交纳的会金。当时因国民党反动政府和驻军经常要向银庄借款、借饷,所以由公会延聘与军政方面有来往交情的豪绅作为“出官”与其周旋、说情。该公会设于断蛙池(即现延安南路),历任会长为许桂芳、郑秉禹、杨斌侯、黄友冬、谢梅英、蔡竹禅、高鸿〓等。
(三)银庄的业务手续:
凡与银庄开户者发给小簿以资记账,小簿有两种:一为存款簿,只能存不能借;一为来往簿,可以超支,但不能超过限额,甚至有的还须托人担保或以房地产契据作押。
银庄使用的票据有两种:一是凭条,由银庄开给客户使用的;一是支票,由客户开给受款人。这两种票据都可以到银庄取款,但开出支票的客户如无款额,银庄就拒付而予以驳回,所以有的商户(客户)由于一时资金不能周转,就开出限期的支票,这叫“空头支票”。此外另有一种转账的办法:例如厦门行家到漳州向五谷、棉布、百货等行业收取货款,交款户可在厦门行家的收款簿上写明由本市某银庄拨交款项若干,并盖上印记为凭。(当日某银庄即与付款户对账),厦门行家则向拨款银庄换取向厦门银庄领款的汇票。由于那时还没有转账支票这简便办法,所以对凭条,支票的使用较为烦杂,因而增加了现金的收付数额。
当时银庄和商户(客户)进出的银元,一般是“总银”——平版银元和花银(打过花的银元)混用;如在银庄本途互领票款或解款往厦门,则必须全部平版银元,不能混用花银。当时钞票很少,市上使用的只有中国银行和中南银行印发的,其后又增加了美丰银行的钞票,至于由外埠流入的通商银行、盐业银行等的钞票都拒不使用。由于流通的钞票少,而商家又为外出携带方便,需要兑换钞票时必须补贴“票水”,每百元补贴二三角,且因“银水”(什银价格的变动)的时价早晚不同,“票水”(指对各埠的汇票)也时常变动。所以各银庄在客户的来往簿上都盖上“银水、票水现会,以后不得多论”的印记。至于“银水”、“票水”的行情,是每日由厦门报来的。当时叻币、港币与我国币值相差不多,荷币每盾约值八角左右,在福州有时还兼用“台伏”(该台伏是福州的地方币,是内有信誉的行家发出不同数额的票据在本市使用,亦叫伏票),每伏票约值七,八角。
(四)汇兑业务和在厦门开设漳源银庄
在汇兑业务上,对邻近地区的石码、厦门一般都有直接来往,可以开汇票付与客户直接到当地银庄支取。如汇往香港、福州、汕头、上海等地,则需经与厦门开户银庄如漳源等转根,办法是收票根寄往厦门漳源银庄等由其批转给付款地的承付银庄,而来往账目由厦分头结算;如本市收到上海等地的汇票,亦托由厦门银庄代收。
当时漳州各银庄为汇兑方便、存款可靠,以及自己能赚回利润,认为有必要在厦门设立自己的机构,因而于一九二七年间合股(由各银庄认股,每股一千元)集资四万元在厦门开设漳源银庄,聘请较熟悉厦门情况的陈实甫为经理,并推举我地黄仁裕担任付经理,以资监督。这样由于漳源银庄全盘垄断了漳州与厦门来往的业务,经营业务非常发达,逐年得利数字甚为可观。其后本市永孚银庄又与厦商合伙在厦开设裕孚银庄。而天元、豫原亦在石码镇开设分庄。嗣后邻近各地如海澄白水营、南靖山城、平和小溪、云霄等,因受本市影响和商业交易的发展亦陆续开设了银庄。
三、银庄店员的工作、待遇和组织
银庄店员的工作较繁忙,由于同业的竞争,为争取业务除星期日休息外,每日都得派店员分头到各客户去联系业务,俗称“出街”;同时了解各行业经营情况,打听各客户生意的盈亏讯息,作为处理业务的借鉴。
店员“出街”向各客户收款时,备有收款盖印簿,客户取款亦备有付款盖印簿,便于与来往簿核对,如有“小簿失笔”则以“大账为凭”。存放款每月结算母利一次,半年将利并母。当时使用旧式簿记比较复杂不便,且分为外内柜——外柜负责记上逐笔来往的“草清”(有的甚至还设有“暂草”),逐日抄上“日清”;内柜负责将“日清”抄上“总清”(即分户账目)。每月将“日清”和“总清”账目核对一次,避免抄错。同时另设有“日积簿”(或称“便览”),就是经常将各客户的存、欠数字加以表达,使店员胸有成竹,便于掌握收付。这种种账法比起新式簿记,不但繁琐而且容易出差错。
银庄店员的待遇比其他行业好,不但工资较高(一般普通店员的月薪约银元十五元左右,比其他约多百分之三、四十),而且年终又有一笔可观的“赏年”(即奖金),特别是当经理(俗称“家长”)可以得到盈利百分之十的抽分。店员在工作方面比其他行业优越,而且有机会接触到社会上的一些上层人物,较有高攀的机缘,所以一般人很希望其子弟能进入银庄工作。
一九二六年末,北伐军进占漳州以后,在漳州政治监察公署的领导下,曾以银庄店员为主体、吸收棉布、百货等行业的店员参加,成立漳州店员工会,设会址于澄观道,正会长为王绍辉、付会长谢紫庭(这两人系银庄行业店员)、付会长王玉书(棉布行业店员),下设组织、宣传等,开展社会和文娱活动。但豪绅、资本家认为该组织对他们不利,极力反对,政治监察公署为此曾指示要严密组织,健全机构,防止其破坏活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后,该组织即被解散了。
四、银庄停业以至倒闭情况
一般看来银庄似是一种稳健的生意,其实存在许多不健全的因素,特别是最忌滚支(存户争取存款),造成应付不灵而致于搁浅,甚至导致停业或歇业。这是由于旧社会时局经常变动,一遇政变,存户对银庄不信任争先恐后地要讨回存款,而银庄一时又难以收回放款或变卖抵押的不动产等,虽有的依仗股东是外国籍民或教徒以及地方官绅的权势对欠户进行百般的逼讨,可是欠户总是一时不能清还,甚至有的故意拖延;而银庄的股东又不肯取出现金来应付,抱着以债抵债的思想,认为宁使别人去吃亏,也不愿负起责任来维持,就这样赖下去,使银庄瘫痪、倒闭以至进行清理。各欠款户(包括股东的欠款)则乘机向存款户买折抵账,得到意外之财、最受亏的是一些平民,平时勤俭粒积的“老本”存款被倒掉,他们既无权势去追讨,又不能受到法律的维护,真是悲苦万分,虽哀天呼地也仍得不到偿还,这正是旧社会人吃人的真实写照。
在二十多年间,先后开设了三十余家银庄,但在政局多变的情况下,一般寿命都不长,各股东虽每年分得一些红利,却都是记在账面上,但终究不如当经理的实惠,所以有“风水头出家长”的俗谚(意思是经营得利只是经理先得到好处)。一九三二年四月间,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进占漳州,五月同师闽西中央根据地以后,漳州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由于苛捐杂税和重重剥削所造成的人民贫困、农村破产和社会经济的虚假繁荣终于暴露出来。因而从一九三二年秋到三三年间,各银庄在存户讨支和欠户不能清还债务的情况下,全部先后停业以至倒闭清理。由于银庄经营的结果已不能满足豪富们获得暴利的奢望,他们无意再继续经营这种行业,同时银庄也已不能取信于人民,难以吸收存款以发展业务。自一九三四年间以后,国民党四大家族所控制的国家银行,先后在本市设立办事处、分支行,经营存放款和汇兑等,取代了银庄的业务,至此银庄就成为商业史上的陈述。
相关人物
蔡庆麟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