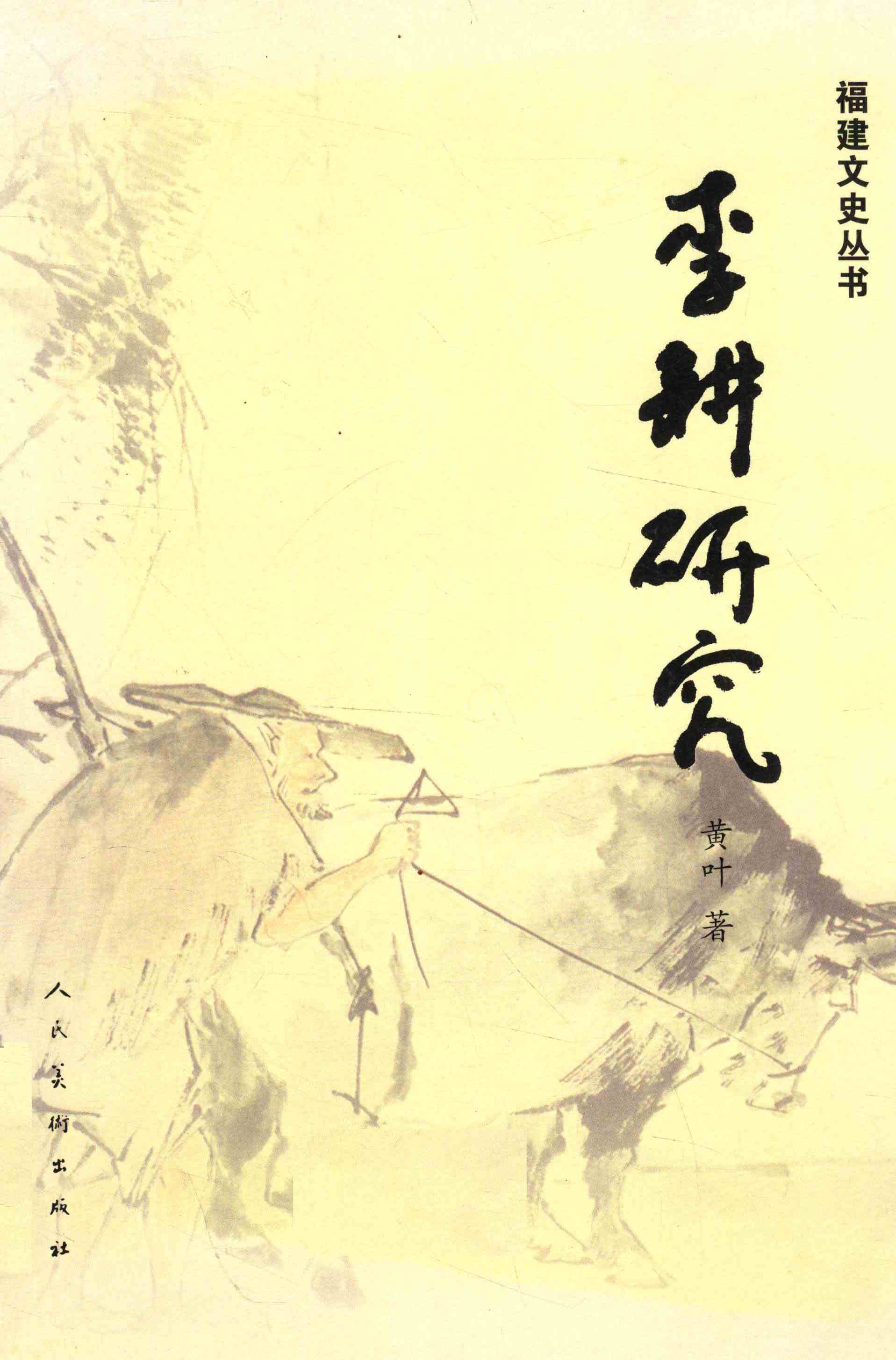内容
云山书院坐落在仙游榜头云庄村。云庄王姓是仙游一地的名门望族,历史上出了不少名人。据当地知情人回忆,1950年新中国建立之初,面对社会变革,大家暂时分不出心思去赏玩艺术,绘画市场暗淡,李耕因鬻画无着而乘闲访友探故,时寄寓在当地名士王恩泽家,应王之邀请为云山书院绘制壁画,成了邻近龙腾村玉新书院的姐妹篇。云山书院现存有:下厅两边的《林子行迹图》,按李耕设计安排每边应是两横16幅,左右共32幅,现在有迹可寻的还剩下30幅,即左壁14幅(图1),右壁16幅(图2),规格为每幅纵76厘米,横54厘米。
在“破四旧,立四新”年代里,云山书院壁画所遭遇的破坏程度比龙腾玉新书院更甚。从壁画遗留的痕迹可以看出,当时是直接在画面上另外绘制图案边框,框内覆盖涂料作为宣传栏,用于抄写或贴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文件或“公约”“守则”“公告”等等。这也是该书院曾被作为公共场所使用的见证。这些图案边框用的是浓墨汁,已洗刷不掉,使画面受到严重损害(图3),岂仅如此,画面本身剥落也十分严重,如果不是对李耕的画和《林子行迹图》中故事情节有一定了解,已根本不知其中所云了。
现状如此,对本处壁画的介绍也就无法像度尾镇瑞云祠和榜头镇龙腾玉新书院那么具体和周详,唯一办法是选择一些画面相对清晰的作品加以剖析,尽量引导兴趣者或后人能从一鳞半爪中获取相关信息,收到以偏概全的效果,并找回对该祠李耕壁画艺术的整体感觉,进而推及作者这一时期卷轴画创作与壁画的对应关系。我认为,一个画家某时期的作品,不会因为使用媒质不同而出现大的风格上的变化,何况该壁画的笔墨表现形式(且不论所产生的效果)与该时期作者所创作卷轴画完全相同。另外,前面介绍过的李耕早期创作的度尾镇瑞云祠《林子行迹图》也为本文论述提供了难得的参照系,如把两者加以比较、分析,应是一件很有趣,也是很有意义的事。
相较于度尾镇瑞云祠,云山书院壁画艺术上的整体特征表现在:一、构图充实饱满;二、人物造型修长优雅;三、线条清劲峭拔,超逸洒脱。
如果说度尾镇瑞云祠壁画有着较为明显的对前人画谱遵循、依赖、参照、甚或照搬的倾向,那么云山书院壁画则完全抹掉了前人画谱影响的痕迹,在构图、造型、线条组织这些中国画基本元素上,表现出与历史上任何一家一法都大异其趣的面目。虽然其本质离不开中国画传统的基本法则,但已被新的、独创的形式所取代,或者说被作者新的精神气韵所融合所化解。
倘若就继承中国画前人技巧层面而言,确实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境界。所以我们说李耕人物画风格与历史上任何一家一派都不同,是真正称得上“独树一帜,开宗立派”的大师。
评析一个画家的艺术,还是用作品讲话最具说服力。
图4这幅画相对完整,描述的故事梗概是:林龙江先生69岁那年,因为对按院杨公四知的约会有所怠慢而迁怒于杨,幸得大中丞詹公从中调停,以好言相劝,方不致酿成大祸。(《林子本行实录》) 画面中安排人物4人,除了杨、詹二公,尚有两侍从在侧。4个人物表现出的是不同的神情动态,杨、詹二公隔案相向而坐。不消说,正面那个双手展开,意态嚣张的该是杨按院了。而摇着手掌似在劝其“暂且息怒”的无疑是詹公了。两侍从的角色定位也很准确,各自伫立一旁,不露声色地观察两位上级表现出的不同态度。人物前后左右安排得自然妥帖,错落相间,聚散得宜。
诗有诗眼,画有画眼,毫无疑义,本图画眼即是杨公舒张的双臂——其所表现出大鹏展翅或曰神雕扑食之势,是对堂堂按院失态的极为生动写照! 这是李耕平素对生活中一些人发怒咆哮时将欲拍案而起“典型情态”的“抓拍”!大家知道,发怒的明显特征是竖眉瞪眼和脸部肌肉变形,但李耕可能觉得如此太流于一般化而不足以彰显自己的独特表现形式,于是便不再注重于脸部的刻画(仅以短短上翘的髭髯作为动势的辅助),转而为倾力展示发怒时夸张的肢体语言,再借助詹公劝阻手势和温厚表情来折射杨公的嗔怒之意。
如是一张一弛和大开大合场面更易于吸引观者眼球,诱导观者入戏。
用铁线描或钉头鼠尾描等细劲线条来表现人物衣纹,是李耕中晚期绘画风格一大特征,其优势表现在:①这类线条细且长,有利于表现古典人物中文人雅士或道释人物的宽袍大袖,尤其对李耕这一时期人物造型的奇峭修长和儒雅宽博有一定的辅助和支撑作用。②偏于叙事性、描述性和人物画创作侧重于具象实写,此类线条相对工巧轻松,其线性便于笔势的使转往来,适宜勾画人物动态变化时复杂的衣褶线纹,表现具体繁杂的人和事,而民间寺庙壁画内容以讲述故事为主旨,宣传教化为目的,因此选择此类线描来再现和构建人物及其场景十分合适。③铁线描或钉头鼠尾描虽然线条本身和线条间组合没有明显的粗细和浓淡变化,似与工笔用线相近,但它是一种可以灵活运用、自由度很高的线,作者如能运用得娴熟自如,线条运行、组织的韵律感也会十分强烈,写意性同样能得到有效展示。鉴于这一阶段李耕的笔墨技巧已趋炉火纯青,对中国画艺术精神的理解又非常透彻,一旦调动这类线描中的抒写性能,便足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④细线不宜绘制巨幅,《林子行迹图》的画幅大小又正好对应了李耕平时习惯的宣纸作画尺寸,可谓适得其所,此亦必然会使李耕在创作上得心应手,这又是一有利条件。综合上述因素,我们再以本图为例,看看李耕是如何运用线条来实现自己创作的意图。
整个画面除了树叶施以水墨没骨法,其他部分一例用中锋细笔勾成,自如流动而奔放的奇石轮廓,缜密坚挺的棕叶,顿挫有力的树干,长短交织、疏密相间的衣褶,工谨而结构清楚的桌、椅和器皿,界尺划出的屏风,无不跃动着韵律、激情和灵气,其写意精神,丝毫不为具象的、精确的描写所束缚——这就是李耕中国画艺术中线条应用的最大特色。
龙腾玉新书院顶厅《儒道释夏》四条屏中,以《钱江授诀》图代表《夏》(林龙江创立的三一教又称夏教),可见这一故事情节是林龙江创教过程的重要节点。这在所有《林子行迹图》中是不可或缺的,可是度尾镇瑞云祠壁画已找不到这一情节,肯定是包含在毁掉的那5幅当中了,十分可惜!所幸云山书院描写这一内容的画幅尚在,而且还较为清晰(图5),略受损害的是画面犹留有昔日宣传栏边框的浓墨痕迹,因清洗不掉,殊觉碍目。同题画作,龙腾玉新书院尺幅大,可以腾出较多空间配景,因而山水树木份额在画面中比例占得大,其间表现技巧和形式,我在前面已有详述,所以不再赘述。(见第二节《榜头镇玉新书院》图6《钱江授诀》图) 若欲比较,那就是两幅画风格出自一辙,尤其是对船的结构和船帆的处理几无二致。但在配景上却相差甚大,前者前后以岸际柳树主干上冲之势和枝条的穿插来打破船体线条的机械并充实画面空间,后者则是通过江中芦苇的分布来解决上述问题,如前面底部象征性的寥寥数笔,把船体的平行线予以截割。还有江心那萧疏、洒落的几笔芦苇,同样把水面横拖波纹与船帆的平行打破,对过于空旷的江面也给予有效的补救和调节,并与底部的芦苇前后呼应。另外人物的安排与动态,两幅画也有较大差异,如前者船中二人是同伴,后者一老一少,显然是主仆关系。前者林龙江偏右正面,后者林龙江居左半侧身,这样也就对应了相同形态的弥勒佛在画面中朝向的不同,不会给人产生雷同之感。同一故事情节,画面处理同中见异,显示了这位功成名就的大画家对待民间壁画创作不轻率、不驾轻就熟、一如既往保持认真严肃、求新求变的态度。
(图6) 说的是北海龙王因行雨损舟,害命甚多而被玉帝贬而为鼋后被渔者捕获,林龙江命赎之放归江中,得玉帝赦罪后特登门向教主面谢的故事。(《林子本行实录》)图中峨冠博带的龙王在两个喽啰拥簇下飘然而至,正对着倚窗的林龙江施行答谢大礼。龙王造型优美,宽博奇伟,侧面趋身,手持玉笏,神态虔诚,绿色的蟒袍格外耀眼,衣褶线条洒落疏放,清劲苍涩,其笔势助推了龙王的动势,一切都显得十分适度得体。随行喽啰的动态也颇为耐人寻味:外侧者披氅衣,举障扇,矮小精灵,身子倾向龙王,却转头仰看林龙江,动态滑稽,透现出“小人物”的好奇心;内侧持幡旗者着朱色衣裳,正转身往后退避,应该是觉察到自己原先欲先睹为快,抢在主子前头的冒失吧,但似又有所不甘,眼睛仍停留在林龙江身上。窗外人物的异相和躁动与窗内儒者的文雅淡定形成鲜明对比。另外,屋顶瓦片工整细笔与右边蕉叶水墨写意块面,还有左边线条勾画出卷舒、蒸腾云团,构成了背景之间的笔墨变化,画面于是更加丰富起来。
顺便提一下,由于壁画易于风化,有些颜料会很快褪色,李耕在壁画中偶一为之的颜色,使用的都是矿物质或较为稳定的颜料如朱砂、赭石、石绿、靛蓝等。当然,从目前这几处李耕壁画来看,保持水墨本色,乃是其一以贯之的风格,颜料使用不多,只是在画面中为强调某人某物而略加配置。
林龙江先生深具慈悲情怀,放生乃其常事,《林子本行实录》多有记述。度尾镇瑞云祠也画有林龙江在芦苇丛中目送一人被巨龟驮着游向彼岸,应是表现另一则放龟故事(图7),似从“毛宝放龟得渡”传说中获得的创意。鼋、龟同类,云山书院回避了直写放鼋的情景而通过龙王答谢来褒扬放生善举,说明了用画面讲述故事并不一定要凭画面直观来获取内容信息,如果换一个方位去设定表述路径,达成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结果,就可以避免构思上的线性思维而在创意上陷入同一个套路。
嘉靖年间,倭寇频频侵犯中国沿海地区,莆田成了倭难的重灾区,值此家园遭难之际,林龙江伙同其道友卓晚春力拯乡民于水火之中,在当地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图8讲述的是卓晚春击碗而歌,以示意市民做好应对倭寇攻城准备的故事。高高城墙下,卓晚春形容邋遢,似疯似颠,与书中记载的卓晚春形象吻合(图9)。这一造型脱胎于李耕卷轴画中常写的戏蟾刘海(见P75,《李耕写意人物画综论》图21《刘海戏蟾》)。(图10) 画的是林龙江为遭受倭寇杀害的死难者收尸后举行超度亡魂的场面,隐约的墨痕中,依然能辨识出一场法事正在进行,地面上摆满了“菜仔饭”(当地民间用来施舍给孤魂野鬼的供品),教主林龙江手挥经幡,口中似乎念念有词,应是在唱诵自作的收尸歌:“与汝形骸一气分,满城鬼哭不堪闻。风幡挥泪缘何事,与汝形骸一气分”吧。场面肃穆而苍凉,人物背后立几棵松树,上方一片留白的云烟为浓密的树冠撕开一道出气口,沉闷、压抑的空间得到了一丝释放。林龙江与张三丰会晤论道的画面(图11)也稍为完整,张三丰(《林子本行实录》中记作张三峰,系莆仙方言峰、丰同音之故),全真武当派祖师,出生于宋景定甲子五年(1264),与林龙江不属同时代人,“实录”中有关张三丰与林龙江交往的记述,应是三丰真人得道成仙二百多年后显化真身下界开示林龙江的传奇。据载,张三丰“曾死而复活,道徒称其为‘阳神出游’……入明,自称‘大元遗老’,时隐时现,行踪莫测”。这位道教大师认为“古今仅正邪两教,所谓儒道释三教仅为创始人之不同,实则‘牟尼、孔、道三教皆名曰道’,而‘修己利人,其趋一也’。”“玄学以功德为体,金丹为用,而后可以成仙”等与林龙江所创三教合一教义颇多相通,其“修炼心法,参悟太极阴阳互变之理”也被林龙江三一教所采用。
因此,将这二位不同朝代的智者扯在一起也有一定道理。图中张三丰的形貌与史料所载的“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无异。只见他盘膝于竹榻之上,身后侍立的“翠湖仙童”着菱叶,赤膊,肩搭木杖,上挂着的大斗笠和葫芦,此系游方道士随身之物。仙童立姿优美,稚气中透现出仙风道骨。不脱儒者风度的林龙江先生正襟危坐于交椅上,庄重而谦恭,面朝张三丰施礼问道,身后也随侍一童子,正捧着一摞书,当是儒家经典吧。
双方定位,其实在二人的坐姿和侍童各自的随身行囊物件上已一览无余!儒道对话,可以上溯到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问道于老子,《林子行迹图》中的这一插曲,不正重现了这一幕?除了创意深邃、新颖,在笔墨运用上,张道人的衣褶线条柔韧圆转,甚至道具的斗笠、葫芦,也寓示了道家对“柔”“圆”的体认。而林龙江身上线条刚健遒劲,不屈不挠,旁边书童的前冲之势,直截之笔,寓示着儒家勇往直前的入世情怀。
画面构图保持本组壁画充实、饱满特点,背景配上几棵松树,从主干到枝杈、松针皆画得一丝不苟,水墨晕染的地面,将人物、交椅、竹榻等烘托得更具立体感、空间感。
度尾镇瑞云祠表现这则故事的画面是,张三丰盘坐于巨石高台之上,旁边炼丹炉正冒着轻烟袅袅上升,下方林龙江先生率二门徒面朝着他问道。如此安排,颇有居高临下之感(图12),显然,云山书院之图把对话双方放平,是否暗示了李耕这一时期对华夏传统文化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出于对现存资料的珍惜,笔者还是不揣浅陋,从两处壁画中再遴选几幅可资对比的作品,来继续这一话题的探讨。
《梦月而娠》(图13、图14) 皆居两处壁画《林子行迹图》中的首幅,云间的女子究竟是代表月亮的嫦娥还是指梦月的林龙江生母李氏? 两幅画都没有将林母闺房熟睡的情景展示出来,这也合乎情理。作者因此画了一女子从月中飘然而下,留给观者自己去进行见仁见智的想象和解读。两幅画不同点在于:云山书院中该图偶露出挺气派的房屋,屋前植有丛竹,意喻林家门第不俗。
构图富于层次感,人物造型婀娜而大方,衣袂飘飘,富有动感,气韵晓畅,体现作者晚年用笔达到的相当火候。而度尾瑞云祠的《梦月而娠》是以其画面的虚灵,空旷来开启对该《林子行迹图》整体构图风格的定调,人物造型及用笔则明显表现出不够疏朗畅达的拘谨和忸怩的“怯”态,与晚期对比,两图差距甚大。
瑞云祠的《晬盘举镜》(图8) 图,我在前面已对其特点做了比较详细的剖析,兹就不予赘述。与之迥然不同的是,云山书院的《晬盘举镜》(图15) 作者是把晬盘置于地面,人物组合方式采取了立与蹲的高低对比。朴实而显得有点木讷的父亲与幽婉娴淑的母亲站在一侧,似乎在谈论眼前的话题。蹲着的帮佣(暂且如此定位) 揽着刚满周岁的林龙江。
看来,圣贤也有与常人无异的童趣,手捧一镜,憨态可掬,尤其是因站立不稳而两脚并拢的颤颤晃晃形态,教人不得不佩服李耕对生活细节观察得是多么精微,刻写得多么生动!旁边还立着年岁稍大的林兆金,正直愣愣地盯着弟弟玩的把戏,亦透现出童真和稚气。作为本组人物的一员,身为兄长的兆金不仅以特殊的形、神助长了气氛的活跃,更重要的是被列为聚散关系中“散”的一极来平衡人群的分布。如若置于全局,全体人物又是一个局部,因此李耕在墙根画上丝丝细线,虽为表示墙基,但实际作用是将人物串连起来,使这个局部更有整体感,以此来呼应上面的另一个局部——窗框外的风景。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对度尾镇瑞云祠《林子行迹图》的评述,侧重于李耕对画幅中内容和形式的整体构思,亦即画面立意和布局层面,显然对人物具体描写的剖析上着墨不多。例如在分析李耕描绘林龙江自幼就能践行“损有余而补不足”天道,乐于赈济贫困的故事时,对图中人物形神动态就有所忽略,也许这是李耕当时人物画尚未能以自己独创面目来赢得关注度吧。当笔者对着他四十年后再画的同一题材的作品,就不能不深深地为独具一格的人物造型及其神情动态所吸引了。同样是表现林龙江孩提时的乐善好施行为,前者把故事发生地定在入塾读书时的校门(见《度尾镇瑞云祠》章图9),后者则在放学归家时的家门口(图16)。也许,前者有向学校教育套近的意向,但学堂毕竟不是行乞者的目的地,不过偶然路过而已,于是情节便带有些许率性而为的意味,这从画面中的萧散人群、主题并不显得那么突出便可获得答案。
而后者由于将场景安排在家门口,便大大深化了画题意蕴。母亲倚门,对儿子幼年就具此良好天性感到宽慰!孩子放学归来,就在即将踏进家门的当儿,不忘转身作出善举,行乞者躬身接纳并致谢,全部视线都集中在小主人公身上。这样便突出了家风或曰家庭教育对一个未成年人道德情操影响的重要性,画面的艺术感染力也获得了加强。读者不妨从两幅相同内容的作品中去细细品味。
同题而表现手段完全不同的,不妨再举《九鲤祷梦》图为例:嘉靖十九年(1540) 林龙江24岁时乞梦于九鲤湖,得九仙示梦曰:“麒麟其事业,当代其文章。”(见《林子本行实录》) 度尾镇瑞云祠如实描绘了梦的过程和梦境,即林龙江躺在九鲤湖九仙祠大殿里,背倚墙根酣睡,梦见上方一乘赤鲤的仙人向其展示“麒麟其事业,当代其文章”字幅。
厅上立柱、香案、香炉等画得很工细,袅袅炉香弥漫殿堂,为道院仙家笼上一片清虚、神秘气氛(图17)。云山书院则在画面上略去主人公酣睡的情状,仅写其梦魂出窍,接受隐于洞穴中二位仙人赐句于他的场面。如是化实为虚,抛却界尺中规中矩对大殿内景的工谨描绘,转而以随意浪漫的笔墨情调抒写烟雾石洞的野外之景。如此由内转为外的变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耕的晚年艺术追求更趋自然、朴野与率性。(图18)云山书院壁画中,画面保留最完整的当数末尾描写林龙江先生功德圆满、寂然仙逝的这一幅了(图19),凑巧的是,最后拈出这一幅画来解读,正好接近本文的尾声。画面上,被奉为三一教主的林龙江先生端坐正中,神态安和,拱手胸前(门人号之为太极手印),似在调息,在入定,顶门化现真身,韦陀伽蓝护持左右,此系果位至尊之象征。众弟子跪叩堂前,环状分布但错落有致,相比度尾镇瑞云祠中弟子的均匀排列,此图已经尽脱刻意安排痕迹。跪拜姿式所形成的每一笔衣纹折叠,无不顺应身体各部位的变化而变化,展现了李耕晚年勾画的衣褶线条在追求意趣、形式之美的同时,并未忽略对人物形体动态的服从与刻写。大家对李耕笔下人物由衷发出“形神兼备”的赞叹,当也基于此吧。
这一时期李耕壁画在山水配景上也呈现出与早期不同的风貌,尤其是山石的勾皴,笔墨灵动、丰富,较之早期的生硬、单调,确系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其松、柳等各种树的画法,也另辟蹊径,其个性更强烈,更鲜明,在此我也不加评述,仅从两处壁画中选录几幅有代表性的图例,相信读者当可从对比中获得不同的感受。
(图20一图25)选定对仙游县现存李耕壁画普查并加以研究的这一课题,本来就不想把云山书院纳入范围,因为经过现场勘察,其损坏程度之严重,实在教笔者不知该从何入手为好。就在度尾镇瑞云祠、榜头镇龙腾村玉新书院壁画的分析文章完稿之际,忽然生发出兴不能止的冲动,于是再次深入该祠,面对壁上斑驳陆离、若隐若现的李耕一生壁画巅峰作品,作为李耕艺术的追随者、研究者,愈觉于心不甘,又觉于心不忍——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让这些尘封的珍珠永远消失在历史记忆之中? 此时的心情,将之说成是深怀保护抢救历史文化遗产的责任感或许有些矫情,但萌生出探微索隐的好奇心肯定是有的。
于是虚虚实实,东扯西拼地组合了这么一些文字,提出浅陋见解,也算是给后人留下一些哪怕是残缺、零碎的史料吧。2015年3月30日完稿于圣劳伦斯河畔
在“破四旧,立四新”年代里,云山书院壁画所遭遇的破坏程度比龙腾玉新书院更甚。从壁画遗留的痕迹可以看出,当时是直接在画面上另外绘制图案边框,框内覆盖涂料作为宣传栏,用于抄写或贴上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文件或“公约”“守则”“公告”等等。这也是该书院曾被作为公共场所使用的见证。这些图案边框用的是浓墨汁,已洗刷不掉,使画面受到严重损害(图3),岂仅如此,画面本身剥落也十分严重,如果不是对李耕的画和《林子行迹图》中故事情节有一定了解,已根本不知其中所云了。
现状如此,对本处壁画的介绍也就无法像度尾镇瑞云祠和榜头镇龙腾玉新书院那么具体和周详,唯一办法是选择一些画面相对清晰的作品加以剖析,尽量引导兴趣者或后人能从一鳞半爪中获取相关信息,收到以偏概全的效果,并找回对该祠李耕壁画艺术的整体感觉,进而推及作者这一时期卷轴画创作与壁画的对应关系。我认为,一个画家某时期的作品,不会因为使用媒质不同而出现大的风格上的变化,何况该壁画的笔墨表现形式(且不论所产生的效果)与该时期作者所创作卷轴画完全相同。另外,前面介绍过的李耕早期创作的度尾镇瑞云祠《林子行迹图》也为本文论述提供了难得的参照系,如把两者加以比较、分析,应是一件很有趣,也是很有意义的事。
相较于度尾镇瑞云祠,云山书院壁画艺术上的整体特征表现在:一、构图充实饱满;二、人物造型修长优雅;三、线条清劲峭拔,超逸洒脱。
如果说度尾镇瑞云祠壁画有着较为明显的对前人画谱遵循、依赖、参照、甚或照搬的倾向,那么云山书院壁画则完全抹掉了前人画谱影响的痕迹,在构图、造型、线条组织这些中国画基本元素上,表现出与历史上任何一家一法都大异其趣的面目。虽然其本质离不开中国画传统的基本法则,但已被新的、独创的形式所取代,或者说被作者新的精神气韵所融合所化解。
倘若就继承中国画前人技巧层面而言,确实达到“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境界。所以我们说李耕人物画风格与历史上任何一家一派都不同,是真正称得上“独树一帜,开宗立派”的大师。
评析一个画家的艺术,还是用作品讲话最具说服力。
图4这幅画相对完整,描述的故事梗概是:林龙江先生69岁那年,因为对按院杨公四知的约会有所怠慢而迁怒于杨,幸得大中丞詹公从中调停,以好言相劝,方不致酿成大祸。(《林子本行实录》) 画面中安排人物4人,除了杨、詹二公,尚有两侍从在侧。4个人物表现出的是不同的神情动态,杨、詹二公隔案相向而坐。不消说,正面那个双手展开,意态嚣张的该是杨按院了。而摇着手掌似在劝其“暂且息怒”的无疑是詹公了。两侍从的角色定位也很准确,各自伫立一旁,不露声色地观察两位上级表现出的不同态度。人物前后左右安排得自然妥帖,错落相间,聚散得宜。
诗有诗眼,画有画眼,毫无疑义,本图画眼即是杨公舒张的双臂——其所表现出大鹏展翅或曰神雕扑食之势,是对堂堂按院失态的极为生动写照! 这是李耕平素对生活中一些人发怒咆哮时将欲拍案而起“典型情态”的“抓拍”!大家知道,发怒的明显特征是竖眉瞪眼和脸部肌肉变形,但李耕可能觉得如此太流于一般化而不足以彰显自己的独特表现形式,于是便不再注重于脸部的刻画(仅以短短上翘的髭髯作为动势的辅助),转而为倾力展示发怒时夸张的肢体语言,再借助詹公劝阻手势和温厚表情来折射杨公的嗔怒之意。
如是一张一弛和大开大合场面更易于吸引观者眼球,诱导观者入戏。
用铁线描或钉头鼠尾描等细劲线条来表现人物衣纹,是李耕中晚期绘画风格一大特征,其优势表现在:①这类线条细且长,有利于表现古典人物中文人雅士或道释人物的宽袍大袖,尤其对李耕这一时期人物造型的奇峭修长和儒雅宽博有一定的辅助和支撑作用。②偏于叙事性、描述性和人物画创作侧重于具象实写,此类线条相对工巧轻松,其线性便于笔势的使转往来,适宜勾画人物动态变化时复杂的衣褶线纹,表现具体繁杂的人和事,而民间寺庙壁画内容以讲述故事为主旨,宣传教化为目的,因此选择此类线描来再现和构建人物及其场景十分合适。③铁线描或钉头鼠尾描虽然线条本身和线条间组合没有明显的粗细和浓淡变化,似与工笔用线相近,但它是一种可以灵活运用、自由度很高的线,作者如能运用得娴熟自如,线条运行、组织的韵律感也会十分强烈,写意性同样能得到有效展示。鉴于这一阶段李耕的笔墨技巧已趋炉火纯青,对中国画艺术精神的理解又非常透彻,一旦调动这类线描中的抒写性能,便足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④细线不宜绘制巨幅,《林子行迹图》的画幅大小又正好对应了李耕平时习惯的宣纸作画尺寸,可谓适得其所,此亦必然会使李耕在创作上得心应手,这又是一有利条件。综合上述因素,我们再以本图为例,看看李耕是如何运用线条来实现自己创作的意图。
整个画面除了树叶施以水墨没骨法,其他部分一例用中锋细笔勾成,自如流动而奔放的奇石轮廓,缜密坚挺的棕叶,顿挫有力的树干,长短交织、疏密相间的衣褶,工谨而结构清楚的桌、椅和器皿,界尺划出的屏风,无不跃动着韵律、激情和灵气,其写意精神,丝毫不为具象的、精确的描写所束缚——这就是李耕中国画艺术中线条应用的最大特色。
龙腾玉新书院顶厅《儒道释夏》四条屏中,以《钱江授诀》图代表《夏》(林龙江创立的三一教又称夏教),可见这一故事情节是林龙江创教过程的重要节点。这在所有《林子行迹图》中是不可或缺的,可是度尾镇瑞云祠壁画已找不到这一情节,肯定是包含在毁掉的那5幅当中了,十分可惜!所幸云山书院描写这一内容的画幅尚在,而且还较为清晰(图5),略受损害的是画面犹留有昔日宣传栏边框的浓墨痕迹,因清洗不掉,殊觉碍目。同题画作,龙腾玉新书院尺幅大,可以腾出较多空间配景,因而山水树木份额在画面中比例占得大,其间表现技巧和形式,我在前面已有详述,所以不再赘述。(见第二节《榜头镇玉新书院》图6《钱江授诀》图) 若欲比较,那就是两幅画风格出自一辙,尤其是对船的结构和船帆的处理几无二致。但在配景上却相差甚大,前者前后以岸际柳树主干上冲之势和枝条的穿插来打破船体线条的机械并充实画面空间,后者则是通过江中芦苇的分布来解决上述问题,如前面底部象征性的寥寥数笔,把船体的平行线予以截割。还有江心那萧疏、洒落的几笔芦苇,同样把水面横拖波纹与船帆的平行打破,对过于空旷的江面也给予有效的补救和调节,并与底部的芦苇前后呼应。另外人物的安排与动态,两幅画也有较大差异,如前者船中二人是同伴,后者一老一少,显然是主仆关系。前者林龙江偏右正面,后者林龙江居左半侧身,这样也就对应了相同形态的弥勒佛在画面中朝向的不同,不会给人产生雷同之感。同一故事情节,画面处理同中见异,显示了这位功成名就的大画家对待民间壁画创作不轻率、不驾轻就熟、一如既往保持认真严肃、求新求变的态度。
(图6) 说的是北海龙王因行雨损舟,害命甚多而被玉帝贬而为鼋后被渔者捕获,林龙江命赎之放归江中,得玉帝赦罪后特登门向教主面谢的故事。(《林子本行实录》)图中峨冠博带的龙王在两个喽啰拥簇下飘然而至,正对着倚窗的林龙江施行答谢大礼。龙王造型优美,宽博奇伟,侧面趋身,手持玉笏,神态虔诚,绿色的蟒袍格外耀眼,衣褶线条洒落疏放,清劲苍涩,其笔势助推了龙王的动势,一切都显得十分适度得体。随行喽啰的动态也颇为耐人寻味:外侧者披氅衣,举障扇,矮小精灵,身子倾向龙王,却转头仰看林龙江,动态滑稽,透现出“小人物”的好奇心;内侧持幡旗者着朱色衣裳,正转身往后退避,应该是觉察到自己原先欲先睹为快,抢在主子前头的冒失吧,但似又有所不甘,眼睛仍停留在林龙江身上。窗外人物的异相和躁动与窗内儒者的文雅淡定形成鲜明对比。另外,屋顶瓦片工整细笔与右边蕉叶水墨写意块面,还有左边线条勾画出卷舒、蒸腾云团,构成了背景之间的笔墨变化,画面于是更加丰富起来。
顺便提一下,由于壁画易于风化,有些颜料会很快褪色,李耕在壁画中偶一为之的颜色,使用的都是矿物质或较为稳定的颜料如朱砂、赭石、石绿、靛蓝等。当然,从目前这几处李耕壁画来看,保持水墨本色,乃是其一以贯之的风格,颜料使用不多,只是在画面中为强调某人某物而略加配置。
林龙江先生深具慈悲情怀,放生乃其常事,《林子本行实录》多有记述。度尾镇瑞云祠也画有林龙江在芦苇丛中目送一人被巨龟驮着游向彼岸,应是表现另一则放龟故事(图7),似从“毛宝放龟得渡”传说中获得的创意。鼋、龟同类,云山书院回避了直写放鼋的情景而通过龙王答谢来褒扬放生善举,说明了用画面讲述故事并不一定要凭画面直观来获取内容信息,如果换一个方位去设定表述路径,达成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结果,就可以避免构思上的线性思维而在创意上陷入同一个套路。
嘉靖年间,倭寇频频侵犯中国沿海地区,莆田成了倭难的重灾区,值此家园遭难之际,林龙江伙同其道友卓晚春力拯乡民于水火之中,在当地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图8讲述的是卓晚春击碗而歌,以示意市民做好应对倭寇攻城准备的故事。高高城墙下,卓晚春形容邋遢,似疯似颠,与书中记载的卓晚春形象吻合(图9)。这一造型脱胎于李耕卷轴画中常写的戏蟾刘海(见P75,《李耕写意人物画综论》图21《刘海戏蟾》)。(图10) 画的是林龙江为遭受倭寇杀害的死难者收尸后举行超度亡魂的场面,隐约的墨痕中,依然能辨识出一场法事正在进行,地面上摆满了“菜仔饭”(当地民间用来施舍给孤魂野鬼的供品),教主林龙江手挥经幡,口中似乎念念有词,应是在唱诵自作的收尸歌:“与汝形骸一气分,满城鬼哭不堪闻。风幡挥泪缘何事,与汝形骸一气分”吧。场面肃穆而苍凉,人物背后立几棵松树,上方一片留白的云烟为浓密的树冠撕开一道出气口,沉闷、压抑的空间得到了一丝释放。林龙江与张三丰会晤论道的画面(图11)也稍为完整,张三丰(《林子本行实录》中记作张三峰,系莆仙方言峰、丰同音之故),全真武当派祖师,出生于宋景定甲子五年(1264),与林龙江不属同时代人,“实录”中有关张三丰与林龙江交往的记述,应是三丰真人得道成仙二百多年后显化真身下界开示林龙江的传奇。据载,张三丰“曾死而复活,道徒称其为‘阳神出游’……入明,自称‘大元遗老’,时隐时现,行踪莫测”。这位道教大师认为“古今仅正邪两教,所谓儒道释三教仅为创始人之不同,实则‘牟尼、孔、道三教皆名曰道’,而‘修己利人,其趋一也’。”“玄学以功德为体,金丹为用,而后可以成仙”等与林龙江所创三教合一教义颇多相通,其“修炼心法,参悟太极阴阳互变之理”也被林龙江三一教所采用。
因此,将这二位不同朝代的智者扯在一起也有一定道理。图中张三丰的形貌与史料所载的“龟形鹤背,大耳圆目,须髯如戟”无异。只见他盘膝于竹榻之上,身后侍立的“翠湖仙童”着菱叶,赤膊,肩搭木杖,上挂着的大斗笠和葫芦,此系游方道士随身之物。仙童立姿优美,稚气中透现出仙风道骨。不脱儒者风度的林龙江先生正襟危坐于交椅上,庄重而谦恭,面朝张三丰施礼问道,身后也随侍一童子,正捧着一摞书,当是儒家经典吧。
双方定位,其实在二人的坐姿和侍童各自的随身行囊物件上已一览无余!儒道对话,可以上溯到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问道于老子,《林子行迹图》中的这一插曲,不正重现了这一幕?除了创意深邃、新颖,在笔墨运用上,张道人的衣褶线条柔韧圆转,甚至道具的斗笠、葫芦,也寓示了道家对“柔”“圆”的体认。而林龙江身上线条刚健遒劲,不屈不挠,旁边书童的前冲之势,直截之笔,寓示着儒家勇往直前的入世情怀。
画面构图保持本组壁画充实、饱满特点,背景配上几棵松树,从主干到枝杈、松针皆画得一丝不苟,水墨晕染的地面,将人物、交椅、竹榻等烘托得更具立体感、空间感。
度尾镇瑞云祠表现这则故事的画面是,张三丰盘坐于巨石高台之上,旁边炼丹炉正冒着轻烟袅袅上升,下方林龙江先生率二门徒面朝着他问道。如此安排,颇有居高临下之感(图12),显然,云山书院之图把对话双方放平,是否暗示了李耕这一时期对华夏传统文化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出于对现存资料的珍惜,笔者还是不揣浅陋,从两处壁画中再遴选几幅可资对比的作品,来继续这一话题的探讨。
《梦月而娠》(图13、图14) 皆居两处壁画《林子行迹图》中的首幅,云间的女子究竟是代表月亮的嫦娥还是指梦月的林龙江生母李氏? 两幅画都没有将林母闺房熟睡的情景展示出来,这也合乎情理。作者因此画了一女子从月中飘然而下,留给观者自己去进行见仁见智的想象和解读。两幅画不同点在于:云山书院中该图偶露出挺气派的房屋,屋前植有丛竹,意喻林家门第不俗。
构图富于层次感,人物造型婀娜而大方,衣袂飘飘,富有动感,气韵晓畅,体现作者晚年用笔达到的相当火候。而度尾瑞云祠的《梦月而娠》是以其画面的虚灵,空旷来开启对该《林子行迹图》整体构图风格的定调,人物造型及用笔则明显表现出不够疏朗畅达的拘谨和忸怩的“怯”态,与晚期对比,两图差距甚大。
瑞云祠的《晬盘举镜》(图8) 图,我在前面已对其特点做了比较详细的剖析,兹就不予赘述。与之迥然不同的是,云山书院的《晬盘举镜》(图15) 作者是把晬盘置于地面,人物组合方式采取了立与蹲的高低对比。朴实而显得有点木讷的父亲与幽婉娴淑的母亲站在一侧,似乎在谈论眼前的话题。蹲着的帮佣(暂且如此定位) 揽着刚满周岁的林龙江。
看来,圣贤也有与常人无异的童趣,手捧一镜,憨态可掬,尤其是因站立不稳而两脚并拢的颤颤晃晃形态,教人不得不佩服李耕对生活细节观察得是多么精微,刻写得多么生动!旁边还立着年岁稍大的林兆金,正直愣愣地盯着弟弟玩的把戏,亦透现出童真和稚气。作为本组人物的一员,身为兄长的兆金不仅以特殊的形、神助长了气氛的活跃,更重要的是被列为聚散关系中“散”的一极来平衡人群的分布。如若置于全局,全体人物又是一个局部,因此李耕在墙根画上丝丝细线,虽为表示墙基,但实际作用是将人物串连起来,使这个局部更有整体感,以此来呼应上面的另一个局部——窗框外的风景。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对度尾镇瑞云祠《林子行迹图》的评述,侧重于李耕对画幅中内容和形式的整体构思,亦即画面立意和布局层面,显然对人物具体描写的剖析上着墨不多。例如在分析李耕描绘林龙江自幼就能践行“损有余而补不足”天道,乐于赈济贫困的故事时,对图中人物形神动态就有所忽略,也许这是李耕当时人物画尚未能以自己独创面目来赢得关注度吧。当笔者对着他四十年后再画的同一题材的作品,就不能不深深地为独具一格的人物造型及其神情动态所吸引了。同样是表现林龙江孩提时的乐善好施行为,前者把故事发生地定在入塾读书时的校门(见《度尾镇瑞云祠》章图9),后者则在放学归家时的家门口(图16)。也许,前者有向学校教育套近的意向,但学堂毕竟不是行乞者的目的地,不过偶然路过而已,于是情节便带有些许率性而为的意味,这从画面中的萧散人群、主题并不显得那么突出便可获得答案。
而后者由于将场景安排在家门口,便大大深化了画题意蕴。母亲倚门,对儿子幼年就具此良好天性感到宽慰!孩子放学归来,就在即将踏进家门的当儿,不忘转身作出善举,行乞者躬身接纳并致谢,全部视线都集中在小主人公身上。这样便突出了家风或曰家庭教育对一个未成年人道德情操影响的重要性,画面的艺术感染力也获得了加强。读者不妨从两幅相同内容的作品中去细细品味。
同题而表现手段完全不同的,不妨再举《九鲤祷梦》图为例:嘉靖十九年(1540) 林龙江24岁时乞梦于九鲤湖,得九仙示梦曰:“麒麟其事业,当代其文章。”(见《林子本行实录》) 度尾镇瑞云祠如实描绘了梦的过程和梦境,即林龙江躺在九鲤湖九仙祠大殿里,背倚墙根酣睡,梦见上方一乘赤鲤的仙人向其展示“麒麟其事业,当代其文章”字幅。
厅上立柱、香案、香炉等画得很工细,袅袅炉香弥漫殿堂,为道院仙家笼上一片清虚、神秘气氛(图17)。云山书院则在画面上略去主人公酣睡的情状,仅写其梦魂出窍,接受隐于洞穴中二位仙人赐句于他的场面。如是化实为虚,抛却界尺中规中矩对大殿内景的工谨描绘,转而以随意浪漫的笔墨情调抒写烟雾石洞的野外之景。如此由内转为外的变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耕的晚年艺术追求更趋自然、朴野与率性。(图18)云山书院壁画中,画面保留最完整的当数末尾描写林龙江先生功德圆满、寂然仙逝的这一幅了(图19),凑巧的是,最后拈出这一幅画来解读,正好接近本文的尾声。画面上,被奉为三一教主的林龙江先生端坐正中,神态安和,拱手胸前(门人号之为太极手印),似在调息,在入定,顶门化现真身,韦陀伽蓝护持左右,此系果位至尊之象征。众弟子跪叩堂前,环状分布但错落有致,相比度尾镇瑞云祠中弟子的均匀排列,此图已经尽脱刻意安排痕迹。跪拜姿式所形成的每一笔衣纹折叠,无不顺应身体各部位的变化而变化,展现了李耕晚年勾画的衣褶线条在追求意趣、形式之美的同时,并未忽略对人物形体动态的服从与刻写。大家对李耕笔下人物由衷发出“形神兼备”的赞叹,当也基于此吧。
这一时期李耕壁画在山水配景上也呈现出与早期不同的风貌,尤其是山石的勾皴,笔墨灵动、丰富,较之早期的生硬、单调,确系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其松、柳等各种树的画法,也另辟蹊径,其个性更强烈,更鲜明,在此我也不加评述,仅从两处壁画中选录几幅有代表性的图例,相信读者当可从对比中获得不同的感受。
(图20一图25)选定对仙游县现存李耕壁画普查并加以研究的这一课题,本来就不想把云山书院纳入范围,因为经过现场勘察,其损坏程度之严重,实在教笔者不知该从何入手为好。就在度尾镇瑞云祠、榜头镇龙腾村玉新书院壁画的分析文章完稿之际,忽然生发出兴不能止的冲动,于是再次深入该祠,面对壁上斑驳陆离、若隐若现的李耕一生壁画巅峰作品,作为李耕艺术的追随者、研究者,愈觉于心不甘,又觉于心不忍——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让这些尘封的珍珠永远消失在历史记忆之中? 此时的心情,将之说成是深怀保护抢救历史文化遗产的责任感或许有些矫情,但萌生出探微索隐的好奇心肯定是有的。
于是虚虚实实,东扯西拼地组合了这么一些文字,提出浅陋见解,也算是给后人留下一些哪怕是残缺、零碎的史料吧。2015年3月30日完稿于圣劳伦斯河畔
相关地名
莆田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