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梅康和项经川同志
| 内容出处: | 《平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13520020230001774 |
| 颗粒名称: | 回忆梅康和项经川同志 |
| 分类号: | K827 |
| 页数: | 18 |
| 页码: | 10-27 |
| 摘要: | 本文描述了平阳县作为浙江省最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展开推翻旧社会斗争的历程,特别是一九三五年红军挺进平阳展开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以及一九三七年秋天民族危急时刻平阳县群众的抗日活动和青年团体的组建。 |
| 关键词: | 平阳县 革命根据地 武装斗争 |
内容
平阳县是浙江省最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早在二十年代,一些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们,就在鳌江西岸广袤的土地上进行推翻旧社会的斗争。一九三五年,刘英、粟裕同志率领的红军挺进师,又来到平阳,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卷起了更大的革命风暴。
一九三七年的秋天,芦沟桥的炮声一响,原来战斗在鳌江上游山区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红军,立即再度发出通电和宣言,要求“停止内战,团结御侮”,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停战谈判。同时,放手发动群众,以平、津、沪、杭一带回乡的青年学生为骨干,在鳌江镇组织了平阳县青年抗日效亡团,出版了《平报》,办起了临时中学。
民族的危难,唤醒了这个海滨的古镇。群众的抗日活动,有如鳌江奔腾的潮水,汹涌澎湃。我童稚的心,正是在这个时候,受到了抗日怒潮的冲击和革命风雷的激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革命的事业是壮丽的,革命的道路却並不平坦,曲折坎坷,荆棘丛生。有英勇献身的,也有半途退却的。有敌人的枪弹、刑罚和监狱,也有同志的误解、斗争和打击。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引导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许多前辈,不论是壮烈牺牲在与敌人搏斗的战场上或监狱里的战士,也不论是因种种“左”的影响而长期蒙受不白之冤以致与世长逝的同志,他们的英雄形象,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其中有两个高大的形象,显得分外清晰。一个是当年鳌江中心支部书记梅康同志,一个是鳌中心支部成员,我的启蒙老师项经川同志。
两个高大的形象
记得我还幼小的时候,常见一位身材修长的青年,穿着灰色的长衫,从我家门口走过,遇到我那做鞋子的舅父,他总和霭地问长问短,有说有笑。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梅康先生。
他是鳌江镇东郊五板桥人,在镇上开了爿源康南货店。我家门口的南门街,是他的必经之路。我参加革命后才知道,他开的这爿南货店,原来是党的秘窒交通站。紧靠灵溪码道的西北侧,从北港来的同志,离了船,便可悄悄地从它的后门走进去。浙南党的负责人龙跃,吴毓、何畏、黄耕夫等同志,都到过这里。
鳌江镇的西郊,有个叫徐家站的地方,在一座石围墙上长满绿苔的古老大院里,住着我小学时代的老师项经川同志。他是这个地主家庭的背叛者。
二十年代后期,梅康同志和项经川同志受陈再华同志的影响,到上海就读于我们党所创办的劳动大学,听到过瞿秋白、茅盾等同志的讲课,受到了深刻的革命教育。在这所学校里,他们虽非同班,却很要好,互相帮助,互相启发。一面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面秧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立志救国救民。
一九三〇年左右,他们响应党的从城市转入农村的号召,先后返回故乡。梅康到了鳌江南岸农民运动中心的缪家桥,投身叶廷鹏等同志领导的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他以开酱园店为掩护,帮助党工作。又以开店需要资金为借口,变卖田产,拿出二百块白花花的银元,买了枪支,武装了红军游击队。他们经过侦察,成功地组织了一次袭击缪家桥盐务税警队的战斗,缴了这文平时欺压盐民的反动武装的枪支,鼓舞了盐民们的抗税斗争。在这次战斗以后,他的政治面目暴露了,只得转移到鳌江上游麻步镇近郊的鳌峰小学任教。与陈阜、吴毓、何畏等同志,以办夜校、妇女识字班等为名,在北港、南港等地组织农会,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经川同志回到鳌江以后,就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宣传马列主义。一九三四年陈再华同志在广州被国民党杀害的消息传来,他怀着极大的悲痛,冒着生命的危险,多方搜集整理陈再华在广州、上海等地发表的文章以及给亲友的书信,共三十多万字,刊印了一本《再华文拾》。他又联合进步的知识分子,出版了《市街》、《北风》等半月刊。这些平阳最早出版的革命书刊,登载了不少宣传革命思想和战斗精神的文章,使我们在少年时代就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有一次,我们还读到了经川同志发表在鲁迅主编的《北斗》杂志士介绍平阳民间文学——娘娘词的文章,感到由衷的喜悦。
抗日战争暴发以后,梅康进了浙南抗日根据地,在粟裕同志担任校长的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担任政治教员,讲授政治经济学。他讲课条理清楚,很受学员的欢迎。一位解放后从事经济工作的老战友告诉我,他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就是一九三八年初在山门救亡干校时得自梅康和孙克定同志的指教。
绚丽的春天
一九三八年,鳌江中心支部建立,梅康任书记。他和经川等同志,把以鳌江镇为中心的平阳全县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我们要建设大众的国防,
大家武装起来,
打倒汉奸走狗。
枪口朝外向,
收复失地,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把旧世界的强盗杀完!
鳌江两岸到处有觉醒的群众,抗战的呼声和抗日的歌声,震荡着人们的心弦。
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团的活动加强了。那个原来很幽静的王家祠堂,自从设了救亡团团部以后,变成了全县抗日活动的中心。爱国青年在这里,有开会研究工作的,有写宣传文章和标语的,有排练戏剧的,有教唱歌曲的,有画宣传画的,气氛热烈、紧张而又活泼。与冷冷清清,门可罗雀的国民党的“抗敌后援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救亡团的组织发展迅速,江南、北港、南港、万全、小南等区都成立了分团,团员发展到二、三千人。又专门组织了剧团,在杨进同志带领下,在鳌江、水头、宜山和广阔的农村,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杨进自饰卖艺老头,他的爱人蔡翠云饰香妹,演得很好,激发了观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街头宣传,也很受群众欢迎。梅康那时已患肺病,很多人劝他不要上街宣传,他坚持说:“你们都上街了,留我在家里,闲得住吗?那才要憋出毛病呢!”
他的演说,没有“学生腔”,讲得十分通俗生动。他身边有一张地图,演讲时就拿出来说:
“这张中国地图,就象一张桑叶。东洋鬼子有如蚕儿,见到桑叶,就拼命吃。吃了东三省,又吃华北。这叫做蚕食。现在,东洋鬼子还嫌蚕食太慢,想把我们一口吞下去。东海里的大鲸鱼,张开血盆大口,可以吞下一只船,这叫鲸吞………
“我们要不被鲸吞,不做亡国奴,就要奋起抗战。抗战,当然要靠军队去打。但是,光靠军队还不够,还要我们每个老百姓都去参加,都去支援。我们要以枪对枪,以牙还牙。我们的古人早就说过,‘国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都是匹夫,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都有救国的责任。我们要求政府发抢给我们,让我们武装起来,好不好呀!·”
台下一片叫好和鼓掌的声音。
他接下去又说:“讲句老实话,目前这个政府,还不大想抗战呢。我们老百姓要推动政府去抗战,逼迫着政府去抗战,拿出枪支让我们去抗战……
“我们的全民抗战,不是打几天,打几个月,而是要长期打下去,一直打到把东洋鬼子赶出东三省……”
他开始讲的时候,声调平和,就象和朋友谈家常一样。
但是,越讲越激动,慷慨激昂,直至声嘶力竭,发不出声来。有几次,他讲得咳嗽起来,一边吐着一口一口鲜红的血,一边仍坚持讲到底。我们在台下听的人,无不深为感动,到处暴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
那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好出风头。有人对梅康的忘我工作,不很理解,冲着他问:“你对救亡团的工作那么负责,你又不当总干事,何苦呢!”
梅康笑笑说:“我们党的方针,是扩大和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员要充分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踏踏实实地多做点工作,少出点风头,这有什么不好?”
说得那个同志的脸都红了。我也深受教育。
象梅康一样,经川同志积极、苦干、热情,从不计较个人名利,默默无闻地在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一天,他把我领到鳌江中心小学“三乐亭”边他的宿舍里,坐在满满的一柜书前。
“我知道你很喜欢读书,看文艺小说。这本书你看过吗?”他从书柜里抽出一本曹靖华翻译的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
我羞愧地低下头,摇了摇。
“翻译小说看起来比较吃力,特别是苏联的小说,姓名太长,不好记。但是不要紧,你可以列个表,摆在书边,就不会弄错了。”
我深深地为这本描写苏联革命战争的小说情节,为英雄人物的动人形象所吸引,只花了两个晚上,就读完了。当我去还书时,他抽出另一本书对我说:“这是中国的《铁流》,没有看过吧!”
我双手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本封面用牛皮抵包起来的书,打开扉页,才知道是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本描写红军艰苦的长征和非凡的战斗业迹的书,在我的心底,燃起了炽热的革命火焰。
不久,经川同志就把我们几个少年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洪流读书会”,从阅读进步的文艺书籍着手,进而指导我们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狄超白的《通俗政治经济学讲话》、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同时,还吸收我们参加青年抗日救亡团的一些活动。我因为是穷人的孩子,工作积极,还被秘密吸收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
创办了《平报》
青年抗日救亡团为了迅速及时地把抗战的消息宣传出去,打算办一份报纸。那时,我们手里没有电台,只王广源行里有一只无线电收音机,就借了来,组织几个懂普通话的大学生轮流抄收广播,写成《战报》,贴在街头,围视的群众很多。但是外地的群众看不到。梅康、经川就与地下党员杜贤宏商量,请他的印刷厂把《战报》排印出来,分发到各地去。《战报》是“八·一三”事变后的第二天,即一九三七年的八月十四日创刊的,八开一张。这就是《平报》的雏形和前身。
一九三八年,地下党决定在《战报》的基础上,创办《平报》。《平报》日出对开半张,两个版。内容比《战报》充实得多,不仅有战讯,还有地方新闻和外地通讯。不仅有新闻,还有言论,还有副刊。这就需要组织一个编辑部和建立一个印刷厂。编辑部几个编辑,除个别外,都是共产党员,有的还是从延安回来的。印刷厂里的几个骨干,也是地下党员。在物色主编的时候,有人建议请黄耕夫担任,但组织上考虑到他是我们党同国民党和平谈判的代表,又是新四军驻后方留守处的主任,面目太红。有人知道经川同志有办刊物和编书的经验,文章又写得好,希望他能挑起这副重担。但是,他很谦虚,只答应参与编辑工作,不担任主编,而推荐进步人士黄藻如先生为主编。他说:“藻如文思敏捷,思想进步,可以胜任这项工作。而且这样安排,报纸容易获准登记。编辑部要我做什么工作,写什么文章,我一定做到。”组织上接受了他的建议,聘请黄藻如为主编。为了易于向国民党政府登记,又请国民党左派人士黄强为发行人,还组织了一个统战性质的理事会。当国民党省主席黄绍竑来鳌江准备会见刘英同志时,请他给《平报》题了报名。我们把黄绍竑的签名也同报名登在一起。有的同志有意见,去问经川。他风趣地说:“这就是借用‘黄绍竑’这块招牌,给我们的宣传做掩护嘛。”
《平报》出版以后,经川几乎每天晚上都到编辑部工作,协助藻如安排版面,撰写言论。《平报》公开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消息,介绍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还把每日见报的副刊,定名为《持久》,天天发表短小精悍的杂文,批驳各式各样的速胜论和亡国论。在浙南,在闽浙边境,这份报纸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发行份数由几百份增加到二千多份。那时候,有悠久历史的国民党报纸《浙瓯日报》也不过发行一、二千份。
我是一九三九年八月调到《平报》工作的。进报社的第一仗、就是批驳当时甚嚣尘上的反苏宣传。这年的九月,希特勒悍然发动了对波兰的武装进攻,揭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苏联为了遏止希特勒的侵略,派兵进驻波兰东部,保护波兰人民,使苏德战争推迟了二年。那些以反苏反共为职业的人,竞大造反苏舆论,说什么苏联和德国一样,都是侵略者,他们瓜分了波兰等等。有些不明真相的人,也跟着起哄。《平报》便就此事展开讨论。先发表了中间人士×××先生认为苏联进军波兰也是侵略的长文,接着,藻如、梅康、经川、伯华等同志,就从各方面,对该文的错误观点,作了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判。中间还发表×××的反批评,接着,又对反批评的文章作了再批评,时间持续了一个多月,使广大读者分清了侵略战争和反侵略战争的界限,澄清了很多混乱的思想,批驳了各种反苏的澜言。在组织这次论战中,我很受教育,不仅提高了认识,又学到了不少宣传艺术。
由于我在进《平报》工作之前,曾给《持久》副刊投过稿,发表过几篇杂文。到报社不久,藻如先生就要我帮助他编《持久》的一部分稿件。那时候,我是个初生之犊,有点不怕虎的劲头,自作主张,编发了一篇题为《瞎说》的杂文,不料因此掀起了轩然大波。这篇杂文,针对蒋介石的一年内要收复大片国土的“许诺”,说他是完全不顾自己实力的吹牛,“斥之为‘瞎说’,恐也不为过”。原以为天高皇帝远,蒋介石远在峨嵋山下,不一定看到东海之滨的这张小报,就是看到了,也应该有点容许批评的雅量。但此文却触痛了他部下的部下——国民党县党部的老爷,急忙出来指责《平报》反对政府,侮辱领袖,破坏抗战。罪名之大,简直可以把作者、编者捉来杀头示儆。但他们又慑于《平报》报头“黄绍竑”这三个字,不敢贸然处置,只好报告省政府和省党部,要求责令《平报》停刊一个月。我们为平息事端,于第三天发了一个“手民误植”的更正,总算把它抵挡过去了。
一所新型的中学
一九三七年底,杭嘉湖地区相继沦陷以后,日军飞机轰炸了温州。温州市区几所中学,被迫停课。原来在温中、联中、瓯中读书的阮世炯、金冶、陈力萍等一大批人,陆续回到鳌江,其中一部分人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一部分人分散在各地。梅康、经川等同志看到莘莘学子失学在家不是办法,就与救亡团总干事王栻商量,筹办一所新型的中学,把他们团聚在一起,培养成为一支抗日救亡的力量。调杜贤宏参加筹备,当总务主任,负责找校舍、设课堂等工作。
但筹办中学的工作开始就遭到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反对。他们一不准备案,二不准招生,想把这所学校扼杀在襁褓之中。可是他们没有想到,你不准办正式中学,我们就改称临时中学。你不准招生,招了生也不承认他们的学历,但招生的海报一贴出,就有大批学生不顾没有学历的威胁,赶来报名,连一些温州老牌中学的学生,也放弃了原来的学校和学籍,到鳌江来上临时中学。这所学校不仅办了两个初一班,还办了一个初二班,一个高一班。学生多达两百余人,挤在娘娘宫那四个狭小而破旧的教室里。设备条件虽然很差,教学仪器很少,但却迸发出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朝气。
这所学校除了正规中学的课程以外,还开设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讲了阶级斗争。在历史课中,还讲了“国耻史”,激发大家的爱国热忱。这儿教学民主,师生团结,政治空气浓厚,学习要求也很高。记得讲授唯物史观的时候,是几位老师采取辩论的方式进行的,各班学生都可参加,受益很多。我那时侯在读初二,听同班同学、原在温中读书的金冶说,这里的老师学问好,没有架子,在这里读书,精神愉快,比在温中读书获得的知识还多。
每天早晨,太阳还没有从东海升起的时候,师生就在鳌江中心小学的大操场上集中,迎着展风,操练杀敌和救护伤员的本领。我们还走出课堂,到社会上去做抗日救亡工作,又组织了一个“新生剧团”,下乡宣传抗日,教群众唱抗日歌曲。
这些活动,更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恐惧和不安,便给这所学校戴上了“红帽子”,派了督学等人来校调查“赤化分子”。他们还扬言教育质量低,学生不好好读书,会误人子弟。但是,经过调查,他们并没有发现校里有共产党,校长陈德煊同志,是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的高足,说不上“赤化”。所有教师也都是平、津、沪著名大学毕业或肄业的高材生,很有学问,又是平阳、瑞安、温州一带有名望的士绅的子弟,他们自然不便轻易下手。抽查了几个学生的作业,成绩之好也出乎他们意外。但是他们并不甘心从此罢休,反而编造谎言,报请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下令停办。梅康、经川、王栻、德煊等同志没有理睬他们,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继续办了一个学期。在结束前,经川同志通过组织,输送一批同学到皖南新四军。分别的时候,大家流着眼泪,高唱《临中校歌》:“我们在抗战里相见,满希望把理想实现。奋力挣扎,度过一年,我们原不顾困难。学习原是为了工作,掀起救亡的怒潮。站在时代的最前线,分别了,何必留恋。”
风云变幻
一九三九年八月,“民先”结束时,我被秘密发展为党员。那时候,国民党已在各地制造摩擦,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经川同志被迫离开鳌江,转移到金华《浙江潮》周刊社工作。他临走时吩咐我:“国民党已从‘防共’、‘限共’,开始‘反共’了。我走了以后,你们要提高警惕,做好转入完全隐蔽斗争的准备。”
经川走后不久,鳌江风云突变。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四日傍晚,我们在《平报》工作的共产党员,突然接到通知,晚饭后到梅康同志南货店的楼上开紧急会议。
三月的鳌江,风吹来已有些暖意。但在这个党的交通站里,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除了《平报》社的党员以外,浙南特委青年部长胡景瑊同志也来了。室内空气有点沉闷、凝重,静悄悄的,相互之间,几乎可以听得见心脏的跳动。
梅康同志用带点沙嘎的声音轻轻地说:“《平报》可能要出事,特委有紧急指示。考虑到在报社开会不安全,所以把你们都找到这里来。”他的神情镇定、沉着。
原来《平报》翻印党的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小册子,已被国民党特务发觉,估计到他们近日就要动手,特委派胡景瑊同志赶来鳌江,同我们一起商量对策。
不平静的夜晚,气氛分外紧张。我们正在悄声的讨论,突然街上传来大队人马行进的杂沓的脚步声,远近的狗也一齐叫了起来。在门口放哨的同志匆匆进来说:“有一队背着步枪的自卫队和警察,向《平报》社方向去了。”
国民党政府提早动手了。封闭了《平报》,逮捕了主编黄藻如和一名会计,正在报社投宿的革命木刻家、县委统战部长林夫也被捕了。但是,由于特委的警觉,措施的及时,《平报》的党组织未遭破坏,所有党员在梅康同志的安排下,都安全转移了。有的暂时回家隐蔽,有的避到他下涂柑园里的小楼内。
这幢小楼,离
这幢小楼,离镇一里许,在鳌江江边的一片葱绿的柑园之中。几间小屋,踞于柑林之上,可以瞭望附近的动静。一发现情况,大家就到柑园的密叶中藏身。梅康同志借口肺病会传染,在这里建了这幢小楼。实际上这幢小楼是同志们在紧急情况下的隐蔽所。早在抗战以前,好多搞农民运动的领导人,都到这幢小楼里住过。
《平报》被封后,梅康同志在特委的领导下,发动社会舆论,遣责国民党地方政府摧残文化事业、封闭《平报》的暴行。那时他的肺病已进入三期,经常发热咯血。但他不顾自己的病痛,一次又一次地参与起草和修改《平报社社员为平阳县长张韶舞摧残文化事业告各方人士书》。他考虑到柑园小楼人一多,会引起特务的注意,而且活动也不方便,就抱病住到源康南货店的楼上,找同志商量营救被捕同志的措施。他心里想的,是党的事业,是同志们的安全,是怎样使被捕同志早日恢复自由,对自己的病疾,却完全置之度外。
他拖着病弱的身体,说服一些当地有名望的士绅,请他们出面营被捕的同志。有一天,他到一个绅士家里,从晚上六时许一直谈到半夜十二时才回到交通站。这时他面色苍白,气喘吁吁。同志们请他先休息一下,但他一边脱长衫,一边强打精神说:“这批士绅总算勉强同意联名具保了。我们要抓紧时机,乘热打铁,明天就把联名信送出去。”歇了歇,他又接着说:“《告各方人士书》也要赶快印发出去。这次我们同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斗争,要求放人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次事件,揭露他们破坏团结、摧残文化的暴行。”这就使我明白为什么前几天他抱病仔细修改《告各方人士书》的道理。
《告各方人士书》连夜赶印出来了,我们交给邮局寄,不料却被特务邮检扣留了。于是,我们采用移花接木的方法,要了很多商店和单位的信封,分散邮寄出去。又托人带了一部分传单到丽水,从那里寄给全国各地的报社和进步的社团,揭露了平阳当局武装查封《平报》,破坏抗日宣传工作的暴行。很多报刊都登载了,造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
斗争获得了初步的胜利。国民党县政府被迫释放了黄藻如和会计。梅康同志兴奋地说:“不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政府是决不会让步的。现在,藻如他们果然放出来了,但林夫还关在狱中,我们要继续斗争下去。”
那时我只有十五岁是党员中最年轻的,特务还不注意。梅康同志考虑再三,决定由我当交通,保持党同狱中的林夫同志的联系。我数次到狱中看望林夫,将小纸条夹带出来交梅康同志转给浙南特委。
一九四〇年五月,斗争的形势更紧张了。组织上决定我撤离鳌江,转移到丽水、金华一带工作。临走之前我去看了梅康,他斜靠在躺椅上,经过这一段时间紧张的工作,他的肺病更沉重了,低烧、咳嗽、咯血,身体更消瘦了,两眼深凹,说话也没有力气。只有一双眼睛,依然亮着光。他紧握住我的手说:“你因为多次探监,已经引起敌人的注意。组织上为了保护你,只好让你转移。你毕竟年纪太小,又没出过远门,一切要自己留心。万一与组织一时联系不上,也不要紧张,到丽水可以找贤宏,到金华可以找经川,他们一定会帮助你的。”
他的咳嗽又上来了,一咳就得好几分钟,我看他痰里带血,心里一阵酸楚,安慰他说:“你身体不好,要好好休养。有些工作,让其他同志多做些!”他歇了好一阵,才接下去说:“我身体不行了,干不了几年了,乘还活着的时侯多干些……革命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继续下去!”)
我竭力控制自己,不让眼泪滚出来,默默地点点头。在我走后的第二年春天,当我陷身“上饶集中营”的时候,病魔就夺去他的生命。这时,他还只有三十多岁。这一席临别赠言,就成了他对我的最后叮咛,寄托着多么深厚的革命前辈对后辈的殷切期望啊!四十多年来,这几句话和鳌江的潮声一起,时常在我的耳边回响。
崎岖的道路
经川同志的革命道路,更加崎岖曲折。一九四〇年五月,我到丽水不久,接到他寄自金华的信,叫我赶快到金华接替他的工作。我到金华时,他已经转移到浙西前线,没有见到。给他去了信,说自己还幼稚,怕做不好工作,有负于老师的期望。不久,接到他的回信,约我到兰溪去见面。
在兰溪临江的一家小酒楼上,我向他倾诉了这半年多来的生活和工作。他嘴角挂着微笑,用心地听着,勉励我说:“学生总是要赶上先生,超过先生的。如果学生老是不如先生,那么,我们岂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吗!我们的社会又怎么进步得起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超过先生,这是社会进步的一般规律,也是我们做先生的人的光荣和骄傲。”
原来,他是怕我不安心工作,特地赶到兰溪,向我做一番思想工作以后,又匆勿返回前线。他待人热情、诚恳,对学生就是这样爱护、关心。他始终是我的先生,我怎么也赶不上呀!
这次分手以后,不到半年,我在金华《浙江潮》周刊社被捕,与他完全失去联系,听不到他的教诲。抗日战争后期,我逃出上饶集中营,到了丽水,不期而遇。那时,他在丽水一家印刷厂做会计工作,也失去了组织关系。他说:“刘英同志牺牲以后,浙南党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目前白色恐怖非常厉害,我们既要积极找党,又要十分谨慎。”
我在丽水隐蔽了一、二个月后,一个好心的朋友悄悄告诉我,说丽水保安司令部已在注意我,叫我赶快离开。我去向经川辞行时,他问我的去向,一再嘱咐我路上要多加小心,并相约谁先找到组织,谁就通知一声。
可是,在白区,我们有如没有爹娘的孤儿,逃亡、流浪;流浪,逃亡,夜茫茫,路遥遥,何时才能找到我们的组织呀!
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的炮火,打得国民党反动派心惊胆颤,到处捉人、杀人。经川在大陆上无法栖身,带了几个学生,从家乡坐一只帆船,飘过风大浪高的台湾海峡,去了台湾。那时,我正在台北《中外日报》工作。我们相见的第一句话就是:“找到了吧?”虽然答复是否定的,但我们都充满了信心,深知夜巳尽头,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
台湾“二·二八”起义失败后,我逃回杭州,不久找到了党,想和他联系,却联系不上,只听说他和几个学生还留在台南一个工厂里。
一九四九年五月,浙江全省解放以后,我很为还羁留在台湾的他的安全担心。喜出望外的是,这年夏天,在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突然遇见了他。原来他又同带到台湾去的几个学生,偷偷地驾着一只舢舨,冲过惊涛骇浪,回到了故乡。当时的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同志热情地欢迎他在家乡工作,请他担任平阳中学校长,还提名他为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在我们自己的解放了的土地上,我们呼吸着自由清新的空气,尽情享受着我们阔别已久的师生加同志的情谊。我们将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去建设我们幸福的家园,伟大的祖国。听故乡来人说,他的政治热情一直很高,总是精神振奋,不辞劳苦地工作着,力求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多做点贡献。但是,美好的日子并不长久,他就被错划为右派,走上漫长的更加坎坷的道路。在十年内乱期间,从温州传来了很多关于他遭受非人折磨的消息,我很痛心:那些人怎么会变得比野兽还残暴。
一九七五年,我因事回到离别了三十多年的家乡,特意去看望他。又出于意外的是,站在我面前的,并不是一位瘦弱、萎靡的老人。不是的,还是二十年前见到的那么健朗、乐观,嘴角依然挂着微笑,在谈笑风生中照常带点幽默。他并没有被那些野蛮的、残暴的行为所屈服,所压倒。他是从生活的荆棘中穿行过来的,浑身已被刺得皮破血流,可能连他的内心也在淌着鲜血。但是他把苦楚留给自己,把微笑给予人们。这需要多么崇高强烈的精神力量啊!我想,这正是他对党的坚定的、经久不渝的信仰在支撑他。他真是坚韧的战士。
但是,不幸的是,在他的错案还没有得到改正以前,就突然含冤去世了。如果他能再活几年,看到“四人帮”被粉碎,看到自己冤案的昭雪,看到祖国的欣欣向荣,该是多么好呀。
家乡象梅康、经川这样的革命前辈是不少的,在革命烈士陵园和烈士纪念馆里,有许多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先烈,正是他们披荆斩棘,才推翻了旧社会,他们以自己的鲜血,浇灌了家乡的土地,开出了鲜艳的幸福之花。
鳌江的潮水,冲上来又退下去;退下去又冲上来。它永远不知疲倦地冲击着一切阻挡着它奔流的障碍,荡涤着一切腐朽和污垢。
奔腾吧!生活在鳌江两岸的人们。
一九三七年的秋天,芦沟桥的炮声一响,原来战斗在鳌江上游山区的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红军,立即再度发出通电和宣言,要求“停止内战,团结御侮”,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停战谈判。同时,放手发动群众,以平、津、沪、杭一带回乡的青年学生为骨干,在鳌江镇组织了平阳县青年抗日效亡团,出版了《平报》,办起了临时中学。
民族的危难,唤醒了这个海滨的古镇。群众的抗日活动,有如鳌江奔腾的潮水,汹涌澎湃。我童稚的心,正是在这个时候,受到了抗日怒潮的冲击和革命风雷的激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革命的事业是壮丽的,革命的道路却並不平坦,曲折坎坷,荆棘丛生。有英勇献身的,也有半途退却的。有敌人的枪弹、刑罚和监狱,也有同志的误解、斗争和打击。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引导我们走上革命道路的许多前辈,不论是壮烈牺牲在与敌人搏斗的战场上或监狱里的战士,也不论是因种种“左”的影响而长期蒙受不白之冤以致与世长逝的同志,他们的英雄形象,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其中有两个高大的形象,显得分外清晰。一个是当年鳌江中心支部书记梅康同志,一个是鳌中心支部成员,我的启蒙老师项经川同志。
两个高大的形象
记得我还幼小的时候,常见一位身材修长的青年,穿着灰色的长衫,从我家门口走过,遇到我那做鞋子的舅父,他总和霭地问长问短,有说有笑。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梅康先生。
他是鳌江镇东郊五板桥人,在镇上开了爿源康南货店。我家门口的南门街,是他的必经之路。我参加革命后才知道,他开的这爿南货店,原来是党的秘窒交通站。紧靠灵溪码道的西北侧,从北港来的同志,离了船,便可悄悄地从它的后门走进去。浙南党的负责人龙跃,吴毓、何畏、黄耕夫等同志,都到过这里。
鳌江镇的西郊,有个叫徐家站的地方,在一座石围墙上长满绿苔的古老大院里,住着我小学时代的老师项经川同志。他是这个地主家庭的背叛者。
二十年代后期,梅康同志和项经川同志受陈再华同志的影响,到上海就读于我们党所创办的劳动大学,听到过瞿秋白、茅盾等同志的讲课,受到了深刻的革命教育。在这所学校里,他们虽非同班,却很要好,互相帮助,互相启发。一面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面秧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立志救国救民。
一九三〇年左右,他们响应党的从城市转入农村的号召,先后返回故乡。梅康到了鳌江南岸农民运动中心的缪家桥,投身叶廷鹏等同志领导的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他以开酱园店为掩护,帮助党工作。又以开店需要资金为借口,变卖田产,拿出二百块白花花的银元,买了枪支,武装了红军游击队。他们经过侦察,成功地组织了一次袭击缪家桥盐务税警队的战斗,缴了这文平时欺压盐民的反动武装的枪支,鼓舞了盐民们的抗税斗争。在这次战斗以后,他的政治面目暴露了,只得转移到鳌江上游麻步镇近郊的鳌峰小学任教。与陈阜、吴毓、何畏等同志,以办夜校、妇女识字班等为名,在北港、南港等地组织农会,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经川同志回到鳌江以后,就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宣传马列主义。一九三四年陈再华同志在广州被国民党杀害的消息传来,他怀着极大的悲痛,冒着生命的危险,多方搜集整理陈再华在广州、上海等地发表的文章以及给亲友的书信,共三十多万字,刊印了一本《再华文拾》。他又联合进步的知识分子,出版了《市街》、《北风》等半月刊。这些平阳最早出版的革命书刊,登载了不少宣传革命思想和战斗精神的文章,使我们在少年时代就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有一次,我们还读到了经川同志发表在鲁迅主编的《北斗》杂志士介绍平阳民间文学——娘娘词的文章,感到由衷的喜悦。
抗日战争暴发以后,梅康进了浙南抗日根据地,在粟裕同志担任校长的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担任政治教员,讲授政治经济学。他讲课条理清楚,很受学员的欢迎。一位解放后从事经济工作的老战友告诉我,他的经济学基础知识,就是一九三八年初在山门救亡干校时得自梅康和孙克定同志的指教。
绚丽的春天
一九三八年,鳌江中心支部建立,梅康任书记。他和经川等同志,把以鳌江镇为中心的平阳全县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我们要建设大众的国防,
大家武装起来,
打倒汉奸走狗。
枪口朝外向,
收复失地,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把旧世界的强盗杀完!
鳌江两岸到处有觉醒的群众,抗战的呼声和抗日的歌声,震荡着人们的心弦。
平阳青年抗日救亡团的活动加强了。那个原来很幽静的王家祠堂,自从设了救亡团团部以后,变成了全县抗日活动的中心。爱国青年在这里,有开会研究工作的,有写宣传文章和标语的,有排练戏剧的,有教唱歌曲的,有画宣传画的,气氛热烈、紧张而又活泼。与冷冷清清,门可罗雀的国民党的“抗敌后援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救亡团的组织发展迅速,江南、北港、南港、万全、小南等区都成立了分团,团员发展到二、三千人。又专门组织了剧团,在杨进同志带领下,在鳌江、水头、宜山和广阔的农村,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杨进自饰卖艺老头,他的爱人蔡翠云饰香妹,演得很好,激发了观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街头宣传,也很受群众欢迎。梅康那时已患肺病,很多人劝他不要上街宣传,他坚持说:“你们都上街了,留我在家里,闲得住吗?那才要憋出毛病呢!”
他的演说,没有“学生腔”,讲得十分通俗生动。他身边有一张地图,演讲时就拿出来说:
“这张中国地图,就象一张桑叶。东洋鬼子有如蚕儿,见到桑叶,就拼命吃。吃了东三省,又吃华北。这叫做蚕食。现在,东洋鬼子还嫌蚕食太慢,想把我们一口吞下去。东海里的大鲸鱼,张开血盆大口,可以吞下一只船,这叫鲸吞………
“我们要不被鲸吞,不做亡国奴,就要奋起抗战。抗战,当然要靠军队去打。但是,光靠军队还不够,还要我们每个老百姓都去参加,都去支援。我们要以枪对枪,以牙还牙。我们的古人早就说过,‘国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都是匹夫,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都有救国的责任。我们要求政府发抢给我们,让我们武装起来,好不好呀!·”
台下一片叫好和鼓掌的声音。
他接下去又说:“讲句老实话,目前这个政府,还不大想抗战呢。我们老百姓要推动政府去抗战,逼迫着政府去抗战,拿出枪支让我们去抗战……
“我们的全民抗战,不是打几天,打几个月,而是要长期打下去,一直打到把东洋鬼子赶出东三省……”
他开始讲的时候,声调平和,就象和朋友谈家常一样。
但是,越讲越激动,慷慨激昂,直至声嘶力竭,发不出声来。有几次,他讲得咳嗽起来,一边吐着一口一口鲜红的血,一边仍坚持讲到底。我们在台下听的人,无不深为感动,到处暴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
那时候,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好出风头。有人对梅康的忘我工作,不很理解,冲着他问:“你对救亡团的工作那么负责,你又不当总干事,何苦呢!”
梅康笑笑说:“我们党的方针,是扩大和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党员要充分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踏踏实实地多做点工作,少出点风头,这有什么不好?”
说得那个同志的脸都红了。我也深受教育。
象梅康一样,经川同志积极、苦干、热情,从不计较个人名利,默默无闻地在群众中做深入细致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一天,他把我领到鳌江中心小学“三乐亭”边他的宿舍里,坐在满满的一柜书前。
“我知道你很喜欢读书,看文艺小说。这本书你看过吗?”他从书柜里抽出一本曹靖华翻译的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
我羞愧地低下头,摇了摇。
“翻译小说看起来比较吃力,特别是苏联的小说,姓名太长,不好记。但是不要紧,你可以列个表,摆在书边,就不会弄错了。”
我深深地为这本描写苏联革命战争的小说情节,为英雄人物的动人形象所吸引,只花了两个晚上,就读完了。当我去还书时,他抽出另一本书对我说:“这是中国的《铁流》,没有看过吧!”
我双手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本封面用牛皮抵包起来的书,打开扉页,才知道是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本描写红军艰苦的长征和非凡的战斗业迹的书,在我的心底,燃起了炽热的革命火焰。
不久,经川同志就把我们几个少年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洪流读书会”,从阅读进步的文艺书籍着手,进而指导我们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狄超白的《通俗政治经济学讲话》、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同时,还吸收我们参加青年抗日救亡团的一些活动。我因为是穷人的孩子,工作积极,还被秘密吸收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
创办了《平报》
青年抗日救亡团为了迅速及时地把抗战的消息宣传出去,打算办一份报纸。那时,我们手里没有电台,只王广源行里有一只无线电收音机,就借了来,组织几个懂普通话的大学生轮流抄收广播,写成《战报》,贴在街头,围视的群众很多。但是外地的群众看不到。梅康、经川就与地下党员杜贤宏商量,请他的印刷厂把《战报》排印出来,分发到各地去。《战报》是“八·一三”事变后的第二天,即一九三七年的八月十四日创刊的,八开一张。这就是《平报》的雏形和前身。
一九三八年,地下党决定在《战报》的基础上,创办《平报》。《平报》日出对开半张,两个版。内容比《战报》充实得多,不仅有战讯,还有地方新闻和外地通讯。不仅有新闻,还有言论,还有副刊。这就需要组织一个编辑部和建立一个印刷厂。编辑部几个编辑,除个别外,都是共产党员,有的还是从延安回来的。印刷厂里的几个骨干,也是地下党员。在物色主编的时候,有人建议请黄耕夫担任,但组织上考虑到他是我们党同国民党和平谈判的代表,又是新四军驻后方留守处的主任,面目太红。有人知道经川同志有办刊物和编书的经验,文章又写得好,希望他能挑起这副重担。但是,他很谦虚,只答应参与编辑工作,不担任主编,而推荐进步人士黄藻如先生为主编。他说:“藻如文思敏捷,思想进步,可以胜任这项工作。而且这样安排,报纸容易获准登记。编辑部要我做什么工作,写什么文章,我一定做到。”组织上接受了他的建议,聘请黄藻如为主编。为了易于向国民党政府登记,又请国民党左派人士黄强为发行人,还组织了一个统战性质的理事会。当国民党省主席黄绍竑来鳌江准备会见刘英同志时,请他给《平报》题了报名。我们把黄绍竑的签名也同报名登在一起。有的同志有意见,去问经川。他风趣地说:“这就是借用‘黄绍竑’这块招牌,给我们的宣传做掩护嘛。”
《平报》出版以后,经川几乎每天晚上都到编辑部工作,协助藻如安排版面,撰写言论。《平报》公开宣传我们党的抗日主张,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消息,介绍陕甘宁等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还把每日见报的副刊,定名为《持久》,天天发表短小精悍的杂文,批驳各式各样的速胜论和亡国论。在浙南,在闽浙边境,这份报纸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发行份数由几百份增加到二千多份。那时候,有悠久历史的国民党报纸《浙瓯日报》也不过发行一、二千份。
我是一九三九年八月调到《平报》工作的。进报社的第一仗、就是批驳当时甚嚣尘上的反苏宣传。这年的九月,希特勒悍然发动了对波兰的武装进攻,揭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苏联为了遏止希特勒的侵略,派兵进驻波兰东部,保护波兰人民,使苏德战争推迟了二年。那些以反苏反共为职业的人,竞大造反苏舆论,说什么苏联和德国一样,都是侵略者,他们瓜分了波兰等等。有些不明真相的人,也跟着起哄。《平报》便就此事展开讨论。先发表了中间人士×××先生认为苏联进军波兰也是侵略的长文,接着,藻如、梅康、经川、伯华等同志,就从各方面,对该文的错误观点,作了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判。中间还发表×××的反批评,接着,又对反批评的文章作了再批评,时间持续了一个多月,使广大读者分清了侵略战争和反侵略战争的界限,澄清了很多混乱的思想,批驳了各种反苏的澜言。在组织这次论战中,我很受教育,不仅提高了认识,又学到了不少宣传艺术。
由于我在进《平报》工作之前,曾给《持久》副刊投过稿,发表过几篇杂文。到报社不久,藻如先生就要我帮助他编《持久》的一部分稿件。那时候,我是个初生之犊,有点不怕虎的劲头,自作主张,编发了一篇题为《瞎说》的杂文,不料因此掀起了轩然大波。这篇杂文,针对蒋介石的一年内要收复大片国土的“许诺”,说他是完全不顾自己实力的吹牛,“斥之为‘瞎说’,恐也不为过”。原以为天高皇帝远,蒋介石远在峨嵋山下,不一定看到东海之滨的这张小报,就是看到了,也应该有点容许批评的雅量。但此文却触痛了他部下的部下——国民党县党部的老爷,急忙出来指责《平报》反对政府,侮辱领袖,破坏抗战。罪名之大,简直可以把作者、编者捉来杀头示儆。但他们又慑于《平报》报头“黄绍竑”这三个字,不敢贸然处置,只好报告省政府和省党部,要求责令《平报》停刊一个月。我们为平息事端,于第三天发了一个“手民误植”的更正,总算把它抵挡过去了。
一所新型的中学
一九三七年底,杭嘉湖地区相继沦陷以后,日军飞机轰炸了温州。温州市区几所中学,被迫停课。原来在温中、联中、瓯中读书的阮世炯、金冶、陈力萍等一大批人,陆续回到鳌江,其中一部分人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一部分人分散在各地。梅康、经川等同志看到莘莘学子失学在家不是办法,就与救亡团总干事王栻商量,筹办一所新型的中学,把他们团聚在一起,培养成为一支抗日救亡的力量。调杜贤宏参加筹备,当总务主任,负责找校舍、设课堂等工作。
但筹办中学的工作开始就遭到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反对。他们一不准备案,二不准招生,想把这所学校扼杀在襁褓之中。可是他们没有想到,你不准办正式中学,我们就改称临时中学。你不准招生,招了生也不承认他们的学历,但招生的海报一贴出,就有大批学生不顾没有学历的威胁,赶来报名,连一些温州老牌中学的学生,也放弃了原来的学校和学籍,到鳌江来上临时中学。这所学校不仅办了两个初一班,还办了一个初二班,一个高一班。学生多达两百余人,挤在娘娘宫那四个狭小而破旧的教室里。设备条件虽然很差,教学仪器很少,但却迸发出青春的活力和革命的朝气。
这所学校除了正规中学的课程以外,还开设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讲了阶级斗争。在历史课中,还讲了“国耻史”,激发大家的爱国热忱。这儿教学民主,师生团结,政治空气浓厚,学习要求也很高。记得讲授唯物史观的时候,是几位老师采取辩论的方式进行的,各班学生都可参加,受益很多。我那时侯在读初二,听同班同学、原在温中读书的金冶说,这里的老师学问好,没有架子,在这里读书,精神愉快,比在温中读书获得的知识还多。
每天早晨,太阳还没有从东海升起的时候,师生就在鳌江中心小学的大操场上集中,迎着展风,操练杀敌和救护伤员的本领。我们还走出课堂,到社会上去做抗日救亡工作,又组织了一个“新生剧团”,下乡宣传抗日,教群众唱抗日歌曲。
这些活动,更引起了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恐惧和不安,便给这所学校戴上了“红帽子”,派了督学等人来校调查“赤化分子”。他们还扬言教育质量低,学生不好好读书,会误人子弟。但是,经过调查,他们并没有发现校里有共产党,校长陈德煊同志,是燕京大学司徒雷登的高足,说不上“赤化”。所有教师也都是平、津、沪著名大学毕业或肄业的高材生,很有学问,又是平阳、瑞安、温州一带有名望的士绅的子弟,他们自然不便轻易下手。抽查了几个学生的作业,成绩之好也出乎他们意外。但是他们并不甘心从此罢休,反而编造谎言,报请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下令停办。梅康、经川、王栻、德煊等同志没有理睬他们,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继续办了一个学期。在结束前,经川同志通过组织,输送一批同学到皖南新四军。分别的时候,大家流着眼泪,高唱《临中校歌》:“我们在抗战里相见,满希望把理想实现。奋力挣扎,度过一年,我们原不顾困难。学习原是为了工作,掀起救亡的怒潮。站在时代的最前线,分别了,何必留恋。”
风云变幻
一九三九年八月,“民先”结束时,我被秘密发展为党员。那时候,国民党已在各地制造摩擦,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经川同志被迫离开鳌江,转移到金华《浙江潮》周刊社工作。他临走时吩咐我:“国民党已从‘防共’、‘限共’,开始‘反共’了。我走了以后,你们要提高警惕,做好转入完全隐蔽斗争的准备。”
经川走后不久,鳌江风云突变。一九四〇年三月十四日傍晚,我们在《平报》工作的共产党员,突然接到通知,晚饭后到梅康同志南货店的楼上开紧急会议。
三月的鳌江,风吹来已有些暖意。但在这个党的交通站里,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除了《平报》社的党员以外,浙南特委青年部长胡景瑊同志也来了。室内空气有点沉闷、凝重,静悄悄的,相互之间,几乎可以听得见心脏的跳动。
梅康同志用带点沙嘎的声音轻轻地说:“《平报》可能要出事,特委有紧急指示。考虑到在报社开会不安全,所以把你们都找到这里来。”他的神情镇定、沉着。
原来《平报》翻印党的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小册子,已被国民党特务发觉,估计到他们近日就要动手,特委派胡景瑊同志赶来鳌江,同我们一起商量对策。
不平静的夜晚,气氛分外紧张。我们正在悄声的讨论,突然街上传来大队人马行进的杂沓的脚步声,远近的狗也一齐叫了起来。在门口放哨的同志匆匆进来说:“有一队背着步枪的自卫队和警察,向《平报》社方向去了。”
国民党政府提早动手了。封闭了《平报》,逮捕了主编黄藻如和一名会计,正在报社投宿的革命木刻家、县委统战部长林夫也被捕了。但是,由于特委的警觉,措施的及时,《平报》的党组织未遭破坏,所有党员在梅康同志的安排下,都安全转移了。有的暂时回家隐蔽,有的避到他下涂柑园里的小楼内。
这幢小楼,离
这幢小楼,离镇一里许,在鳌江江边的一片葱绿的柑园之中。几间小屋,踞于柑林之上,可以瞭望附近的动静。一发现情况,大家就到柑园的密叶中藏身。梅康同志借口肺病会传染,在这里建了这幢小楼。实际上这幢小楼是同志们在紧急情况下的隐蔽所。早在抗战以前,好多搞农民运动的领导人,都到这幢小楼里住过。
《平报》被封后,梅康同志在特委的领导下,发动社会舆论,遣责国民党地方政府摧残文化事业、封闭《平报》的暴行。那时他的肺病已进入三期,经常发热咯血。但他不顾自己的病痛,一次又一次地参与起草和修改《平报社社员为平阳县长张韶舞摧残文化事业告各方人士书》。他考虑到柑园小楼人一多,会引起特务的注意,而且活动也不方便,就抱病住到源康南货店的楼上,找同志商量营救被捕同志的措施。他心里想的,是党的事业,是同志们的安全,是怎样使被捕同志早日恢复自由,对自己的病疾,却完全置之度外。
他拖着病弱的身体,说服一些当地有名望的士绅,请他们出面营被捕的同志。有一天,他到一个绅士家里,从晚上六时许一直谈到半夜十二时才回到交通站。这时他面色苍白,气喘吁吁。同志们请他先休息一下,但他一边脱长衫,一边强打精神说:“这批士绅总算勉强同意联名具保了。我们要抓紧时机,乘热打铁,明天就把联名信送出去。”歇了歇,他又接着说:“《告各方人士书》也要赶快印发出去。这次我们同国民党地方当局的斗争,要求放人固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次事件,揭露他们破坏团结、摧残文化的暴行。”这就使我明白为什么前几天他抱病仔细修改《告各方人士书》的道理。
《告各方人士书》连夜赶印出来了,我们交给邮局寄,不料却被特务邮检扣留了。于是,我们采用移花接木的方法,要了很多商店和单位的信封,分散邮寄出去。又托人带了一部分传单到丽水,从那里寄给全国各地的报社和进步的社团,揭露了平阳当局武装查封《平报》,破坏抗日宣传工作的暴行。很多报刊都登载了,造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
斗争获得了初步的胜利。国民党县政府被迫释放了黄藻如和会计。梅康同志兴奋地说:“不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政府是决不会让步的。现在,藻如他们果然放出来了,但林夫还关在狱中,我们要继续斗争下去。”
那时我只有十五岁是党员中最年轻的,特务还不注意。梅康同志考虑再三,决定由我当交通,保持党同狱中的林夫同志的联系。我数次到狱中看望林夫,将小纸条夹带出来交梅康同志转给浙南特委。
一九四〇年五月,斗争的形势更紧张了。组织上决定我撤离鳌江,转移到丽水、金华一带工作。临走之前我去看了梅康,他斜靠在躺椅上,经过这一段时间紧张的工作,他的肺病更沉重了,低烧、咳嗽、咯血,身体更消瘦了,两眼深凹,说话也没有力气。只有一双眼睛,依然亮着光。他紧握住我的手说:“你因为多次探监,已经引起敌人的注意。组织上为了保护你,只好让你转移。你毕竟年纪太小,又没出过远门,一切要自己留心。万一与组织一时联系不上,也不要紧张,到丽水可以找贤宏,到金华可以找经川,他们一定会帮助你的。”
他的咳嗽又上来了,一咳就得好几分钟,我看他痰里带血,心里一阵酸楚,安慰他说:“你身体不好,要好好休养。有些工作,让其他同志多做些!”他歇了好一阵,才接下去说:“我身体不行了,干不了几年了,乘还活着的时侯多干些……革命要靠你们这些年轻人继续下去!”)
我竭力控制自己,不让眼泪滚出来,默默地点点头。在我走后的第二年春天,当我陷身“上饶集中营”的时候,病魔就夺去他的生命。这时,他还只有三十多岁。这一席临别赠言,就成了他对我的最后叮咛,寄托着多么深厚的革命前辈对后辈的殷切期望啊!四十多年来,这几句话和鳌江的潮声一起,时常在我的耳边回响。
崎岖的道路
经川同志的革命道路,更加崎岖曲折。一九四〇年五月,我到丽水不久,接到他寄自金华的信,叫我赶快到金华接替他的工作。我到金华时,他已经转移到浙西前线,没有见到。给他去了信,说自己还幼稚,怕做不好工作,有负于老师的期望。不久,接到他的回信,约我到兰溪去见面。
在兰溪临江的一家小酒楼上,我向他倾诉了这半年多来的生活和工作。他嘴角挂着微笑,用心地听着,勉励我说:“学生总是要赶上先生,超过先生的。如果学生老是不如先生,那么,我们岂不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吗!我们的社会又怎么进步得起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超过先生,这是社会进步的一般规律,也是我们做先生的人的光荣和骄傲。”
原来,他是怕我不安心工作,特地赶到兰溪,向我做一番思想工作以后,又匆勿返回前线。他待人热情、诚恳,对学生就是这样爱护、关心。他始终是我的先生,我怎么也赶不上呀!
这次分手以后,不到半年,我在金华《浙江潮》周刊社被捕,与他完全失去联系,听不到他的教诲。抗日战争后期,我逃出上饶集中营,到了丽水,不期而遇。那时,他在丽水一家印刷厂做会计工作,也失去了组织关系。他说:“刘英同志牺牲以后,浙南党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目前白色恐怖非常厉害,我们既要积极找党,又要十分谨慎。”
我在丽水隐蔽了一、二个月后,一个好心的朋友悄悄告诉我,说丽水保安司令部已在注意我,叫我赶快离开。我去向经川辞行时,他问我的去向,一再嘱咐我路上要多加小心,并相约谁先找到组织,谁就通知一声。
可是,在白区,我们有如没有爹娘的孤儿,逃亡、流浪;流浪,逃亡,夜茫茫,路遥遥,何时才能找到我们的组织呀!
一九四七年,解放战争的炮火,打得国民党反动派心惊胆颤,到处捉人、杀人。经川在大陆上无法栖身,带了几个学生,从家乡坐一只帆船,飘过风大浪高的台湾海峡,去了台湾。那时,我正在台北《中外日报》工作。我们相见的第一句话就是:“找到了吧?”虽然答复是否定的,但我们都充满了信心,深知夜巳尽头,这只是黎明前的黑暗。
台湾“二·二八”起义失败后,我逃回杭州,不久找到了党,想和他联系,却联系不上,只听说他和几个学生还留在台南一个工厂里。
一九四九年五月,浙江全省解放以后,我很为还羁留在台湾的他的安全担心。喜出望外的是,这年夏天,在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突然遇见了他。原来他又同带到台湾去的几个学生,偷偷地驾着一只舢舨,冲过惊涛骇浪,回到了故乡。当时的平阳县委书记郑海啸同志热情地欢迎他在家乡工作,请他担任平阳中学校长,还提名他为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在我们自己的解放了的土地上,我们呼吸着自由清新的空气,尽情享受着我们阔别已久的师生加同志的情谊。我们将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去建设我们幸福的家园,伟大的祖国。听故乡来人说,他的政治热情一直很高,总是精神振奋,不辞劳苦地工作着,力求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多做点贡献。但是,美好的日子并不长久,他就被错划为右派,走上漫长的更加坎坷的道路。在十年内乱期间,从温州传来了很多关于他遭受非人折磨的消息,我很痛心:那些人怎么会变得比野兽还残暴。
一九七五年,我因事回到离别了三十多年的家乡,特意去看望他。又出于意外的是,站在我面前的,并不是一位瘦弱、萎靡的老人。不是的,还是二十年前见到的那么健朗、乐观,嘴角依然挂着微笑,在谈笑风生中照常带点幽默。他并没有被那些野蛮的、残暴的行为所屈服,所压倒。他是从生活的荆棘中穿行过来的,浑身已被刺得皮破血流,可能连他的内心也在淌着鲜血。但是他把苦楚留给自己,把微笑给予人们。这需要多么崇高强烈的精神力量啊!我想,这正是他对党的坚定的、经久不渝的信仰在支撑他。他真是坚韧的战士。
但是,不幸的是,在他的错案还没有得到改正以前,就突然含冤去世了。如果他能再活几年,看到“四人帮”被粉碎,看到自己冤案的昭雪,看到祖国的欣欣向荣,该是多么好呀。
家乡象梅康、经川这样的革命前辈是不少的,在革命烈士陵园和烈士纪念馆里,有许多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先烈,正是他们披荆斩棘,才推翻了旧社会,他们以自己的鲜血,浇灌了家乡的土地,开出了鲜艳的幸福之花。
鳌江的潮水,冲上来又退下去;退下去又冲上来。它永远不知疲倦地冲击着一切阻挡着它奔流的障碍,荡涤着一切腐朽和污垢。
奔腾吧!生活在鳌江两岸的人们。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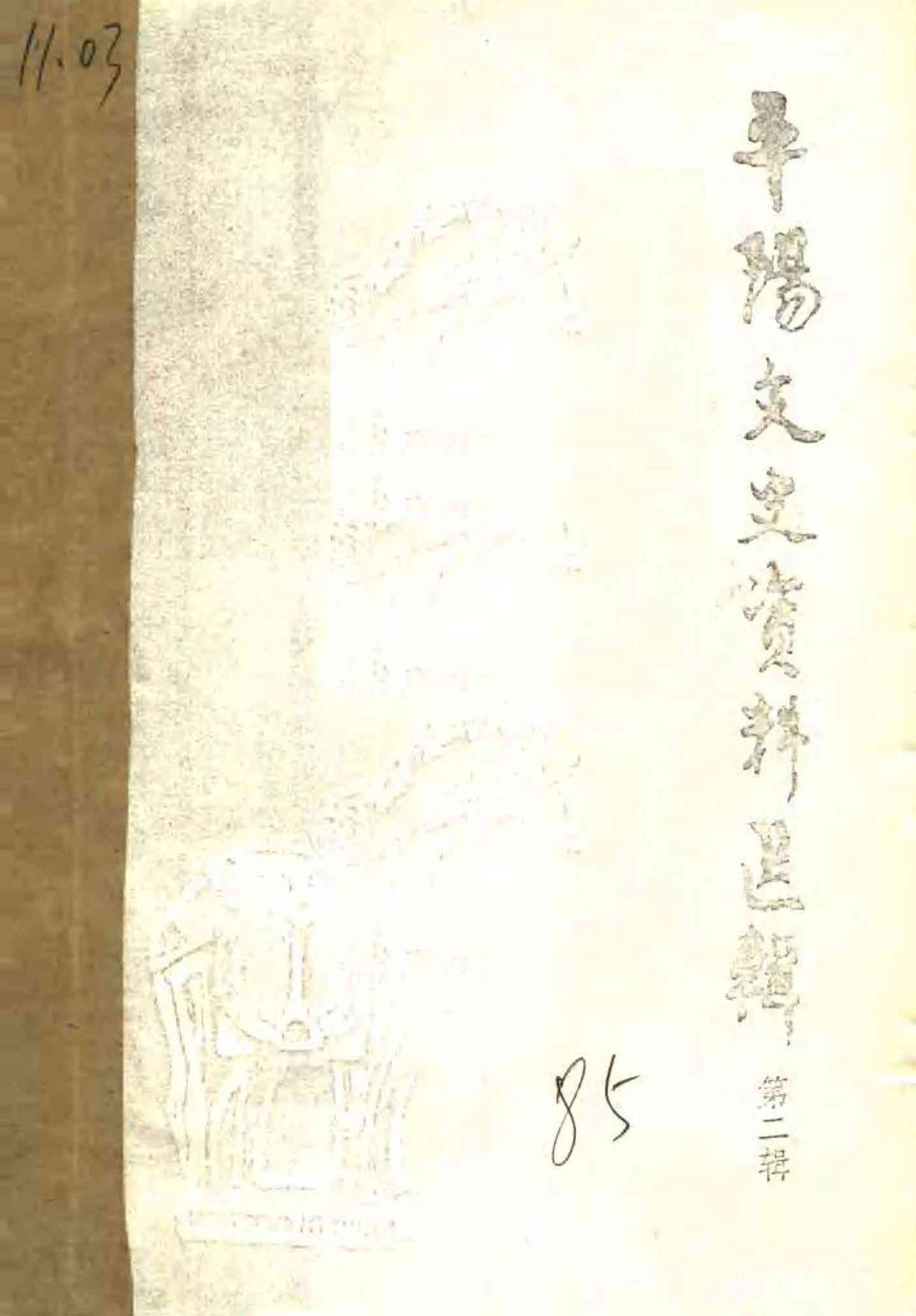
相关人物
李士俊
责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