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仓宝胜寺双塔的宋代佛像
| 内容出处: | 《平阳文史资料第三十八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13520020230001439 |
| 颗粒名称: | 钱仓宝胜寺双塔的宋代佛像 |
| 分类号: | K879.3 |
| 页数: | 8 |
| 页码: | 181-188 |
| 摘要: | 本文介绍了平阳地区宋代遗存中的佛像,主要关注于宝胜寺双塔中发现的17尊宋代佛像。文章从佛像的时代背景、材质工艺、艺术风格和历史价值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宝胜寺双塔始建于北宋乾德三年(965),佛像作为双塔的重要建筑构件,与双塔为一体建造。这批佛像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对研究温州地区宋代手工业发展、文化繁荣以及宋代佛教文化传承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佛像的材质工艺显示出造塔者在选择上的用心,可能与当时的工期和地理环境有关。 |
| 关键词: | 平阳县 钱仓宝胜寺双塔 佛像 |
内容
平阳境内宋代遗存丰富,本文所记为始建于北宋乾德三年(965)的宝胜寺双塔中发现的宋代佛像。这批佛像一共17尊,有鲜明的时代和地域特征,对研究温州地区宋代手工业发展、文化繁荣以及宋代佛教文化传承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极具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本文主要从佛像的时代背景、材质工艺、艺术风格以及历史价值等方面做一简单论述。
一、佛像的时代背景
说起佛像的时代背景,则必谈起佛像的原承载建筑宝胜寺双塔,“宝胜寺双塔”实则包含宝胜寺和双塔,坐落于温州市平阳县钱仓镇。根据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可知宝胜寺的始建时间早于双塔。
宝胜寺。宝胜寺是温州地区一座历史悠久的寺院,在温州地方相关历史文献中均有记载,但较为简略。明嘉靖《温州府志》载:“宝胜寺,在钱仓。”明隆庆《平阳县志》载:“宝胜寺,在钱仓,唐咸通建。”清乾隆《平阳县志》载:“宝胜寺在钱仓,唐咸通间建,子院二:曰律院,宋大观间建;曰教院,元祐间,僧德玉重修。”五代时期,吴越国王钱氏曾驻足宝胜寺,明隆庆《平阳县志》载:“钱王一宿楼,在钱仓宝胜寺,五代钱镠曾宿于此。”清乾隆《平阳县志》也载:“钱王楼,在钱仓宝胜寺,五代吴越钱王曾宿于此。”另据民国《平阳县志》:“宝胜寺,在凤山麓,唐咸通间建,子院二:曰律院,宋大观间建;曰教院,元祐间僧德玉重建。咸丰季年,以金钱匪乱被毁。同治间,僧广法重建,规模狭小矣。”
通过以上记载,我们可知宝胜寺始建于唐代咸通年间(860—874),之后历代又有不同规模的扩建或重建。五代时期,宝胜寺在吴越国境内,此时应该是宝胜寺的辉煌时期,吴越国王钱镠曾住宿宝胜寺,留下钱王一宿楼,又称钱王楼,这也侧面反映出宝胜寺在五代吴越国时的规模和影响之大。宋元祐之前,不知何时何故被毁,僧德玉于元祐间(1086—1094)重建。到清代咸丰三年(1853),平阳爆发了金钱会起义,宝胜寺在战乱中被毁。同治年间(1862-1874),金钱会起义失败后,僧广法又原址重建,但规模狭小,已不能与之前的宝胜寺相提并论。广法所建的宝胜寺清光绪十六年(1891)尚存,后因何故毁于何时已不可考。现今寺已不存,仅存双塔及零星建筑残件。
双塔。双塔曾是宝胜寺的主要建筑物之一,也是目前宝胜寺仅存的建筑物,故现名宝胜寺双塔。二塔东西相向,外形相似,结构相同,系五层六面阁楼式砖塔。塔高约15.16米,两塔相距11.8米。须弥座台基,边长3.3米,高1.75米。各层边长从下至上相应收缩。在塔的明间壶门壁龛内供奉佛像。
1984年,当地相关部门在对东塔维修过程中,在二层北面的壁龛内出土了《清河弟子造塔记录》青石碑一方,石碑通长48、通宽38、厚4厘米。上部倭角,整体呈长方形,四角饰有线刻勾连云纹。顶部从右到左横行篆书“清河弟子造塔记录”八字,正文为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竖行楷书,计17行478字。根据《清河弟子造塔记录》碑文记载,我们可知双塔始建于北宋乾德三年(965),原位于宝胜寺大佛殿前。双塔建成后,有过两次维修,一次为北宋天禧二年(1018),一次为南宋建炎二年(1128)。在此碑发现之前,根据民国《平阳县志》,曾一度认为双塔始建于北宋靖康年间(1126—1127)。民国《平阳县志》载:“钱仓四塔,俱在宝胜寺前,其一已圮,尚存三残塔。光绪十六年,风坏塔尖,堕一铁镬,镌有靖康年号。”这段记载说明宝胜寺前历史上曾有四塔,至清光绪十六年(1891)仍有三塔尚存。对于塔尖处镌有靖康年号的建筑构件,现在看来应是说明四塔中除现存二塔外,至少有一塔或为靖康年间(1126—1127)所建。但之后又不知何时何故,三塔仅存二塔,直至今日。
2006年,平阳县文物馆为配合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对双塔进行现场测绘,开始对双塔的第3至5层壸门壁龛中供奉的佛像进行保护性清理,共整理出17尊砖质坐佛,西塔8尊,东塔9尊。最大的一尊通高34厘米,最小的通高30厘米,底部通宽20厘米。佛像大小因塔层数高低而异。佛像是双塔不可分割的重要建筑构件,与双塔为一体建造。根据《清河弟子造塔记录》碑文,我们可确定这批佛像的年代为北宋早期无疑。
二、佛像的材质工艺
佛造像质地的选择一般与供养者的社会地位、财富水平等密切相连,但更重要的还是因时、因地制宜。宝胜寺双塔的这批佛像乃是双塔的主要建筑构件之一,其质地的选择首先应与双塔建造的工期相匹配。且佛像的安放处基本显露在外,因此对于佛像的材质造塔者在选择上尤为用心。泥质佛像一般供奉在室内,室外不易保存。石质造像耗时费力,若批量制作则短期内不可取。金质佛像,包含金、银、铜、铁等金属,首先金、银、铜均是古代货币材质,以之铸像怕难以流传久远。事实上自唐以来,寺观钟像盗铸为钱者屡有发生,如《旧唐书》载:“(乾元二年)长安城中,竟为盗铸,寺观钟及铜像,多坏为钱。奸人豪族,犯禁者不绝。”即便躲过了盗铸,也难逃统治者毁佛的噩运,如周世宗即位之初,就曾因“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佛像以铸钱”。其次铁质在南方地区长久暴露于潮湿空气中则必锈蚀,其余各材质及情形甚多不一而足。以上情况下,双塔佛像的材质造塔者选定了砖质。而砖质佛像在北宋时期的温州地区可谓较为流行,从北宋早期到晚期均有实物遗存,早期实物如本文所记之造像,晚期如建于北宋政和五年(1115)的温州白象塔出土的一批砖质坐佛造像。但白象塔佛像与双塔佛像相比,在造像面部表情、衣纹褶皱、身体比例等细部工艺处理上似不如双塔细腻。
根据双塔碑文“今特发心舍净财,烧造砖瓦,雇召工匠”句,可知双塔所用砖瓦均是当时专门烧造,工匠亦是为造塔而专门雇招。造塔的普通砖瓦尚且专门烧造,那么塔上的佛像也必是如此。砖瓦的制作,用土量极大,古代交通不便一般是就地、就近取材,因地制宜。砖瓦用土对土质有一定要求,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有记:“凡埏泥造砖,亦掘地验辨土色,或蓝或白,或红或黄,闽广多红泥,蓝者名善泥,江浙居多,皆以粘而不散、粉而不沙者为上。”说明烧制砖瓦用土一般以黏土为主。而造像对土质要求要比砖瓦更高。因为砖瓦形制规范,烧制过程中不易变形。造像如果土质颗粒疏松,塑造成形后在烧造过程中极易变形、开裂,很难烧制成功或达到理想效果。平阳本地盛产青紫泥,这种土质得益于平阳地处海边,土壤母质成分主要为海涂泥和河流冲积物形成的淤泥质亚黏土,粘性很强,故当地又俗称“青胶泥”。这种泥的特点是泥层越深土质越粘重致密,可塑性越强。平阳青紫泥不仅资源丰富且土层深厚,满足烧制砖质佛像的要求,因此双塔佛像用土应该是选用本地青紫泥。
双塔佛像现呈青灰色,砖质细腻致密,胎体厚重。表面原施一层金黄色彩,但从塔上清理出时绝大部分色彩已褪,只有小部分颜色残留像身尚依稀可辨。根据双塔碑文中“外孙传教沙门冲杲募缘重装两塔佛”句可知,这层“金黄”可能是在北宋天禧二年(1018)重新敷彩装饰。佛像的制作工艺应为湿泥塑坯,这点和烧制砖瓦工艺基本一致。制作流程首先应该是泥料筛选,然后塑坯成形。成形后,开始在湿坯上雕刻发饰肉髻、五官、仰莲座等基本形状,勾勒出表情、衣着纹饰等细部。再将其晾干,晾干后经过打磨处理,然后入窑烧造。出窑后再进行表面敷彩,敷彩前在像身遍施一层白瓷土打底。
三、佛像的艺术风格
宝胜寺双塔佛像现存于平阳县博物馆,均为砖质坐像。大部分保存状况较好,小部分在面部、背部、胸腹部、莲座等部位有不同程度的风化。基本造型为螺发肉髻,每单尊佛盘腿坐于仰莲座上,双手结不同手印。仰莲座与佛身为一体雕作,莲座莲瓣饱满。佛面部方圆丰腴,五官清晰可辨,形态端庄优雅。佛身穿褒衣博带式通肩长衣,内着袒右式僧祗支,并在胸腹间束带,衣纹随身圆转,雕刻线条疏朗流畅,层次分明,处理手法简洁自然、干净利落。无论造像的整体比例、表情刻画,还是衣纹处理等方面都显得既写实又富有装饰性,显示出精湛的雕刻工艺,极具南方特色。令人称赞的是佛像的面部表情和手印的变换,在总体造型不变的情况下,这些细处均被极力地精刻细画,以避免雷同,可谓是双塔佛像的精妙之处。
双塔佛像的雕刻风格和题材明显可见受唐末五代时期的禅宗思想影响深远。禅宗在唐末五代时期极为盛行,其不尚经义,无求于经籍,讲究顿悟成佛。所谓顿悟之“悟”,李泽厚先生认为,“它不是追求在急剧的情感冲突中、在严重的罪感痛苦中获得解脱和超生,而毋宁更着重在平静如常的一般世俗生活中,特别是在与大自然的交往欣赏中,获得这种感受”。因此禅宗思想对佛造像的影响是使其更加世俗化,不是使人望而生畏,而是更为接近自然、接近人性。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讲到,宋代时“神的形象已完全人间化、世俗化。宋代雕塑则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它不是思辨的神(魏)或主宰的神(唐),而完全是世俗的神,即人的形象。它比唐代更为写实,更为逼真,更为具体,更为可亲甚至可昵”。宋代的温州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繁荣兴盛,经济的不断发展推动了市井文化的流行和社会意识的极大觉醒,开始引导人们逐渐关注生活实际,这对佛教艺术的影响便是使其更加注重写实,令许多作品有着深刻的世俗心理和个性体现。
宝胜寺双塔佛像面容俊秀,身段优雅,嘴角略带微笑,形象写实,一扫唐代佛像的威严肃穆,几乎就是世俗中人的形象,一颦一笑皆在身边举目可见。整体风格既有唐代面相端庄丰满的余韵,又有宋代姿态自然、突出世俗的新风,不论是制作工艺还是文化内涵,均可视为宋代初期佛像雕塑艺术和佛教文化发展的代表之作,蕴含着很高的艺术水准。
四、佛像的历史价值
宝胜寺双塔佛像,折射出了宋代初期温州地区的佛教信仰之风。双塔建立时,平阳其实尚在吴越国的实际统治之下。吴越国三代五王都极为崇佛,佛教在钱氏统治下盛极一时。在吴越王室倡导下,吴越国上下佛教信仰蔚然成风,大量的佛塔、经幢、寺庙等建筑如雨后春笋。平阳五代后周广顺年间(951—953)的栖真寺五佛塔,亦是在此期间兴建。吴越王钱镠本人曾亲临平阳驻足宝胜寺,以及双塔的捐造者张从軫携阖族眷属捐造双塔的系列史实,足以反映出宋初的温州地区有着深厚的佛教信仰根基和传播底蕴。
宝胜寺双塔佛像,不仅反映了宋代温州地区砖瓦烧造行业的兴盛,同时也反映了砖瓦烧造技术的高超。宋代温州地区应该存在着大量烧造砖瓦的砖窑和工匠,如本文的双塔、白象塔的砖瓦烧造均是本地就地取材,就地烧制。另外,双塔佛像的造型均为坐像,这不仅是循求一种力学上最佳的稳定结构,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砖质材料的局限性使然,因为砖质立像的烧造很难规避变形的风险。这也充分说明了时人对砖瓦烧制和佛像烧制技艺的娴熟掌控,能巧妙的避免烧造失败,从而大大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间接反映出匠人砖瓦烧造技术的高超。
宝胜寺双塔佛像,侧面反映了宋代温州地区工艺和文化水平的状况。在《清河弟子造塔记录》碑碑文上,我们看到了不同时间段的匠人书写的题记。造塔工匠在完成佛塔的建造后,一般都会在造塔记录上写下纪年和自己的姓名。从这些记录中,我们既可见到当时工匠的书法水准,又能更进一步地认识和分析当时工匠的综合文化素质。值得注意的是,碑文末对匠人的记载中,明确记有“刻字匠”和“修塔匠”,这充分说明了匠人群体的细致分工以及“刻字匠”和“修塔匠”在匠人群体中的地位应高于其他类型的工匠。工匠作为佛塔的建造者,在佛塔的构造、砖瓦及佛像的烧制、碑刻记录等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透露出工匠的主观思想,体现着工匠们的客观工艺水平等状况。据明、清两代《平阳县志》记载,两宋时期,平阳一县出了3名文科状元和13名武科状元,文、武科榜眼、探花近10人,以及文、武科进士等不可胜数。3名文科状元,一名出在北宋,两名出在南宋。这充分说明了宋代平阳的文化教育发展水平之高。如果说科举反映的是上层士人的文化水平,那么这些匠人的文化和行业发展水平则最能代表底层民众的文化和发展现状。
宝胜寺双塔佛像,以其精湛的雕刻和烧造技艺体现了宋代温州工匠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为研究温州地区的宋代佛教艺术、佛教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对研究宋代浙南地区文化的繁荣发展以及佛教文化在浙南地区的传播、传承等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佛像的时代背景
说起佛像的时代背景,则必谈起佛像的原承载建筑宝胜寺双塔,“宝胜寺双塔”实则包含宝胜寺和双塔,坐落于温州市平阳县钱仓镇。根据文献记载和实物资料,可知宝胜寺的始建时间早于双塔。
宝胜寺。宝胜寺是温州地区一座历史悠久的寺院,在温州地方相关历史文献中均有记载,但较为简略。明嘉靖《温州府志》载:“宝胜寺,在钱仓。”明隆庆《平阳县志》载:“宝胜寺,在钱仓,唐咸通建。”清乾隆《平阳县志》载:“宝胜寺在钱仓,唐咸通间建,子院二:曰律院,宋大观间建;曰教院,元祐间,僧德玉重修。”五代时期,吴越国王钱氏曾驻足宝胜寺,明隆庆《平阳县志》载:“钱王一宿楼,在钱仓宝胜寺,五代钱镠曾宿于此。”清乾隆《平阳县志》也载:“钱王楼,在钱仓宝胜寺,五代吴越钱王曾宿于此。”另据民国《平阳县志》:“宝胜寺,在凤山麓,唐咸通间建,子院二:曰律院,宋大观间建;曰教院,元祐间僧德玉重建。咸丰季年,以金钱匪乱被毁。同治间,僧广法重建,规模狭小矣。”
通过以上记载,我们可知宝胜寺始建于唐代咸通年间(860—874),之后历代又有不同规模的扩建或重建。五代时期,宝胜寺在吴越国境内,此时应该是宝胜寺的辉煌时期,吴越国王钱镠曾住宿宝胜寺,留下钱王一宿楼,又称钱王楼,这也侧面反映出宝胜寺在五代吴越国时的规模和影响之大。宋元祐之前,不知何时何故被毁,僧德玉于元祐间(1086—1094)重建。到清代咸丰三年(1853),平阳爆发了金钱会起义,宝胜寺在战乱中被毁。同治年间(1862-1874),金钱会起义失败后,僧广法又原址重建,但规模狭小,已不能与之前的宝胜寺相提并论。广法所建的宝胜寺清光绪十六年(1891)尚存,后因何故毁于何时已不可考。现今寺已不存,仅存双塔及零星建筑残件。
双塔。双塔曾是宝胜寺的主要建筑物之一,也是目前宝胜寺仅存的建筑物,故现名宝胜寺双塔。二塔东西相向,外形相似,结构相同,系五层六面阁楼式砖塔。塔高约15.16米,两塔相距11.8米。须弥座台基,边长3.3米,高1.75米。各层边长从下至上相应收缩。在塔的明间壶门壁龛内供奉佛像。
1984年,当地相关部门在对东塔维修过程中,在二层北面的壁龛内出土了《清河弟子造塔记录》青石碑一方,石碑通长48、通宽38、厚4厘米。上部倭角,整体呈长方形,四角饰有线刻勾连云纹。顶部从右到左横行篆书“清河弟子造塔记录”八字,正文为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竖行楷书,计17行478字。根据《清河弟子造塔记录》碑文记载,我们可知双塔始建于北宋乾德三年(965),原位于宝胜寺大佛殿前。双塔建成后,有过两次维修,一次为北宋天禧二年(1018),一次为南宋建炎二年(1128)。在此碑发现之前,根据民国《平阳县志》,曾一度认为双塔始建于北宋靖康年间(1126—1127)。民国《平阳县志》载:“钱仓四塔,俱在宝胜寺前,其一已圮,尚存三残塔。光绪十六年,风坏塔尖,堕一铁镬,镌有靖康年号。”这段记载说明宝胜寺前历史上曾有四塔,至清光绪十六年(1891)仍有三塔尚存。对于塔尖处镌有靖康年号的建筑构件,现在看来应是说明四塔中除现存二塔外,至少有一塔或为靖康年间(1126—1127)所建。但之后又不知何时何故,三塔仅存二塔,直至今日。
2006年,平阳县文物馆为配合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对双塔进行现场测绘,开始对双塔的第3至5层壸门壁龛中供奉的佛像进行保护性清理,共整理出17尊砖质坐佛,西塔8尊,东塔9尊。最大的一尊通高34厘米,最小的通高30厘米,底部通宽20厘米。佛像大小因塔层数高低而异。佛像是双塔不可分割的重要建筑构件,与双塔为一体建造。根据《清河弟子造塔记录》碑文,我们可确定这批佛像的年代为北宋早期无疑。
二、佛像的材质工艺
佛造像质地的选择一般与供养者的社会地位、财富水平等密切相连,但更重要的还是因时、因地制宜。宝胜寺双塔的这批佛像乃是双塔的主要建筑构件之一,其质地的选择首先应与双塔建造的工期相匹配。且佛像的安放处基本显露在外,因此对于佛像的材质造塔者在选择上尤为用心。泥质佛像一般供奉在室内,室外不易保存。石质造像耗时费力,若批量制作则短期内不可取。金质佛像,包含金、银、铜、铁等金属,首先金、银、铜均是古代货币材质,以之铸像怕难以流传久远。事实上自唐以来,寺观钟像盗铸为钱者屡有发生,如《旧唐书》载:“(乾元二年)长安城中,竟为盗铸,寺观钟及铜像,多坏为钱。奸人豪族,犯禁者不绝。”即便躲过了盗铸,也难逃统治者毁佛的噩运,如周世宗即位之初,就曾因“是时中国乏钱,乃诏悉毁天下佛像以铸钱”。其次铁质在南方地区长久暴露于潮湿空气中则必锈蚀,其余各材质及情形甚多不一而足。以上情况下,双塔佛像的材质造塔者选定了砖质。而砖质佛像在北宋时期的温州地区可谓较为流行,从北宋早期到晚期均有实物遗存,早期实物如本文所记之造像,晚期如建于北宋政和五年(1115)的温州白象塔出土的一批砖质坐佛造像。但白象塔佛像与双塔佛像相比,在造像面部表情、衣纹褶皱、身体比例等细部工艺处理上似不如双塔细腻。
根据双塔碑文“今特发心舍净财,烧造砖瓦,雇召工匠”句,可知双塔所用砖瓦均是当时专门烧造,工匠亦是为造塔而专门雇招。造塔的普通砖瓦尚且专门烧造,那么塔上的佛像也必是如此。砖瓦的制作,用土量极大,古代交通不便一般是就地、就近取材,因地制宜。砖瓦用土对土质有一定要求,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有记:“凡埏泥造砖,亦掘地验辨土色,或蓝或白,或红或黄,闽广多红泥,蓝者名善泥,江浙居多,皆以粘而不散、粉而不沙者为上。”说明烧制砖瓦用土一般以黏土为主。而造像对土质要求要比砖瓦更高。因为砖瓦形制规范,烧制过程中不易变形。造像如果土质颗粒疏松,塑造成形后在烧造过程中极易变形、开裂,很难烧制成功或达到理想效果。平阳本地盛产青紫泥,这种土质得益于平阳地处海边,土壤母质成分主要为海涂泥和河流冲积物形成的淤泥质亚黏土,粘性很强,故当地又俗称“青胶泥”。这种泥的特点是泥层越深土质越粘重致密,可塑性越强。平阳青紫泥不仅资源丰富且土层深厚,满足烧制砖质佛像的要求,因此双塔佛像用土应该是选用本地青紫泥。
双塔佛像现呈青灰色,砖质细腻致密,胎体厚重。表面原施一层金黄色彩,但从塔上清理出时绝大部分色彩已褪,只有小部分颜色残留像身尚依稀可辨。根据双塔碑文中“外孙传教沙门冲杲募缘重装两塔佛”句可知,这层“金黄”可能是在北宋天禧二年(1018)重新敷彩装饰。佛像的制作工艺应为湿泥塑坯,这点和烧制砖瓦工艺基本一致。制作流程首先应该是泥料筛选,然后塑坯成形。成形后,开始在湿坯上雕刻发饰肉髻、五官、仰莲座等基本形状,勾勒出表情、衣着纹饰等细部。再将其晾干,晾干后经过打磨处理,然后入窑烧造。出窑后再进行表面敷彩,敷彩前在像身遍施一层白瓷土打底。
三、佛像的艺术风格
宝胜寺双塔佛像现存于平阳县博物馆,均为砖质坐像。大部分保存状况较好,小部分在面部、背部、胸腹部、莲座等部位有不同程度的风化。基本造型为螺发肉髻,每单尊佛盘腿坐于仰莲座上,双手结不同手印。仰莲座与佛身为一体雕作,莲座莲瓣饱满。佛面部方圆丰腴,五官清晰可辨,形态端庄优雅。佛身穿褒衣博带式通肩长衣,内着袒右式僧祗支,并在胸腹间束带,衣纹随身圆转,雕刻线条疏朗流畅,层次分明,处理手法简洁自然、干净利落。无论造像的整体比例、表情刻画,还是衣纹处理等方面都显得既写实又富有装饰性,显示出精湛的雕刻工艺,极具南方特色。令人称赞的是佛像的面部表情和手印的变换,在总体造型不变的情况下,这些细处均被极力地精刻细画,以避免雷同,可谓是双塔佛像的精妙之处。
双塔佛像的雕刻风格和题材明显可见受唐末五代时期的禅宗思想影响深远。禅宗在唐末五代时期极为盛行,其不尚经义,无求于经籍,讲究顿悟成佛。所谓顿悟之“悟”,李泽厚先生认为,“它不是追求在急剧的情感冲突中、在严重的罪感痛苦中获得解脱和超生,而毋宁更着重在平静如常的一般世俗生活中,特别是在与大自然的交往欣赏中,获得这种感受”。因此禅宗思想对佛造像的影响是使其更加世俗化,不是使人望而生畏,而是更为接近自然、接近人性。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讲到,宋代时“神的形象已完全人间化、世俗化。宋代雕塑则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它不是思辨的神(魏)或主宰的神(唐),而完全是世俗的神,即人的形象。它比唐代更为写实,更为逼真,更为具体,更为可亲甚至可昵”。宋代的温州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繁荣兴盛,经济的不断发展推动了市井文化的流行和社会意识的极大觉醒,开始引导人们逐渐关注生活实际,这对佛教艺术的影响便是使其更加注重写实,令许多作品有着深刻的世俗心理和个性体现。
宝胜寺双塔佛像面容俊秀,身段优雅,嘴角略带微笑,形象写实,一扫唐代佛像的威严肃穆,几乎就是世俗中人的形象,一颦一笑皆在身边举目可见。整体风格既有唐代面相端庄丰满的余韵,又有宋代姿态自然、突出世俗的新风,不论是制作工艺还是文化内涵,均可视为宋代初期佛像雕塑艺术和佛教文化发展的代表之作,蕴含着很高的艺术水准。
四、佛像的历史价值
宝胜寺双塔佛像,折射出了宋代初期温州地区的佛教信仰之风。双塔建立时,平阳其实尚在吴越国的实际统治之下。吴越国三代五王都极为崇佛,佛教在钱氏统治下盛极一时。在吴越王室倡导下,吴越国上下佛教信仰蔚然成风,大量的佛塔、经幢、寺庙等建筑如雨后春笋。平阳五代后周广顺年间(951—953)的栖真寺五佛塔,亦是在此期间兴建。吴越王钱镠本人曾亲临平阳驻足宝胜寺,以及双塔的捐造者张从軫携阖族眷属捐造双塔的系列史实,足以反映出宋初的温州地区有着深厚的佛教信仰根基和传播底蕴。
宝胜寺双塔佛像,不仅反映了宋代温州地区砖瓦烧造行业的兴盛,同时也反映了砖瓦烧造技术的高超。宋代温州地区应该存在着大量烧造砖瓦的砖窑和工匠,如本文的双塔、白象塔的砖瓦烧造均是本地就地取材,就地烧制。另外,双塔佛像的造型均为坐像,这不仅是循求一种力学上最佳的稳定结构,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砖质材料的局限性使然,因为砖质立像的烧造很难规避变形的风险。这也充分说明了时人对砖瓦烧制和佛像烧制技艺的娴熟掌控,能巧妙的避免烧造失败,从而大大节约人力、物力和财力,间接反映出匠人砖瓦烧造技术的高超。
宝胜寺双塔佛像,侧面反映了宋代温州地区工艺和文化水平的状况。在《清河弟子造塔记录》碑碑文上,我们看到了不同时间段的匠人书写的题记。造塔工匠在完成佛塔的建造后,一般都会在造塔记录上写下纪年和自己的姓名。从这些记录中,我们既可见到当时工匠的书法水准,又能更进一步地认识和分析当时工匠的综合文化素质。值得注意的是,碑文末对匠人的记载中,明确记有“刻字匠”和“修塔匠”,这充分说明了匠人群体的细致分工以及“刻字匠”和“修塔匠”在匠人群体中的地位应高于其他类型的工匠。工匠作为佛塔的建造者,在佛塔的构造、砖瓦及佛像的烧制、碑刻记录等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透露出工匠的主观思想,体现着工匠们的客观工艺水平等状况。据明、清两代《平阳县志》记载,两宋时期,平阳一县出了3名文科状元和13名武科状元,文、武科榜眼、探花近10人,以及文、武科进士等不可胜数。3名文科状元,一名出在北宋,两名出在南宋。这充分说明了宋代平阳的文化教育发展水平之高。如果说科举反映的是上层士人的文化水平,那么这些匠人的文化和行业发展水平则最能代表底层民众的文化和发展现状。
宝胜寺双塔佛像,以其精湛的雕刻和烧造技艺体现了宋代温州工匠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为研究温州地区的宋代佛教艺术、佛教文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对研究宋代浙南地区文化的繁荣发展以及佛教文化在浙南地区的传播、传承等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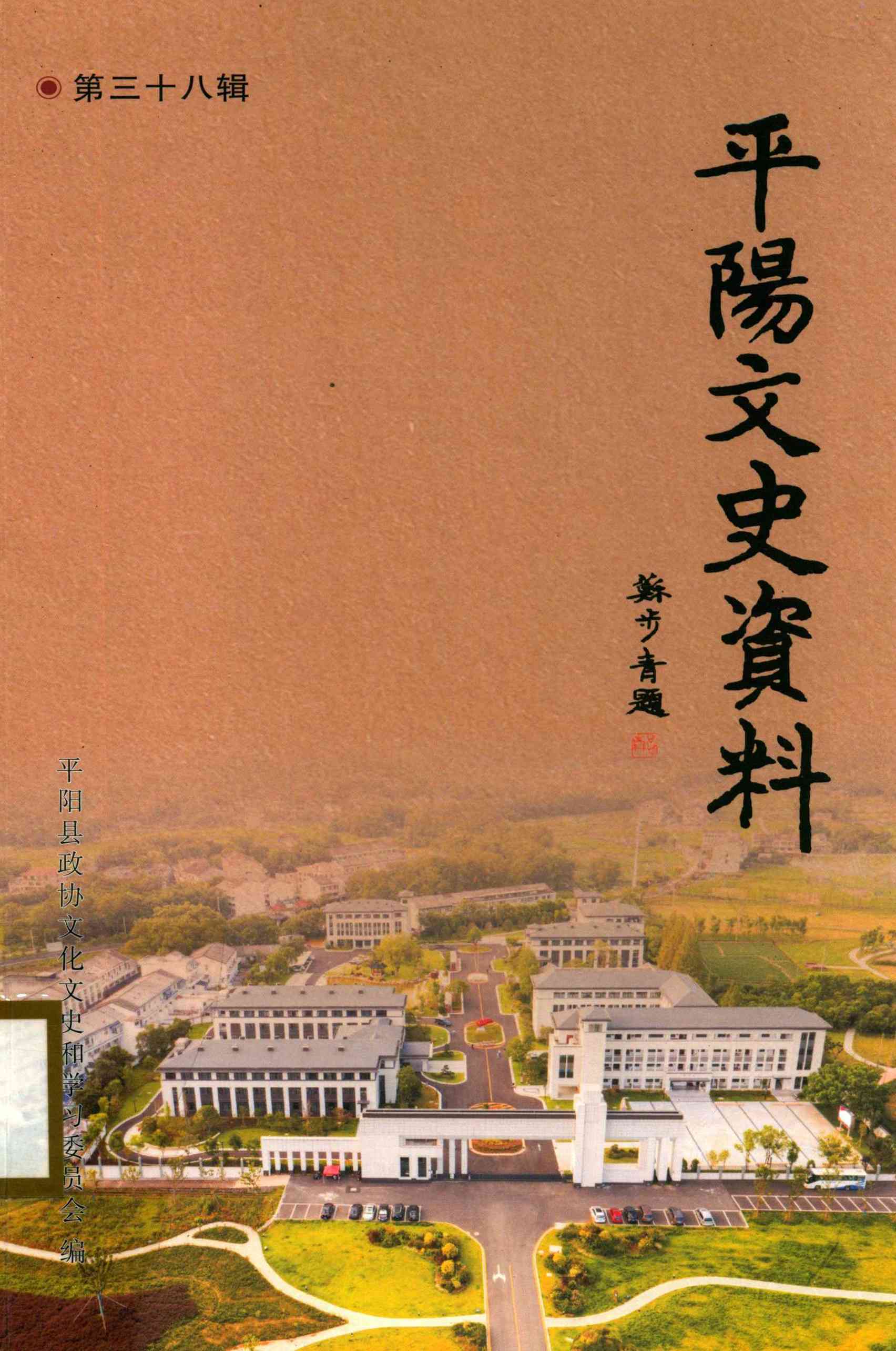
《平阳文史资料第三十八辑》
本书收集多篇关于平阳地区历史、文化、人物和事件的文章,展现了平阳丰富多彩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特色。其中包括对苏步青教授故乡情的追忆、对马秀权教授优秀品格的缅怀、对南戏在平阳和剧中的遗存剧目的探讨,以及对平阳历史上著名人物、事件和地点的介绍。这些文章不仅展现了平阳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呈现了该地区人民的精神风貌和生活变迁。通过这些文章,读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平阳的历史、文化和人物,感受这个地区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阅读
相关机构
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
相关机构
平阳县博物馆
相关机构
相关地名
平阳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