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过平阳考
| 内容出处: | 《平阳文史资料第三十七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13520020230001374 |
| 颗粒名称: | 朱熹过平阳考 |
| 分类号: | B244.7 |
| 页数: | 17 |
| 页码: | 118-134 |
| 摘要: | 本文记述了朱熹因避难在闽东讲学,后受邀至平阳盖竹,并前往南雁山寻访陈经邦、陈经正书院,题额“会文书院”,讲学旬余。 |
| 关键词: | 朱熹 平阳 会文书院 |
内容
据历代《平阳县志》与《南雁荡山志》等诸多文献记载,南宋著名理学家、儒子集大成者朱熹曾率众弟子来平阳,过盖竹,游南雁,讲学旬馀。那么,朱熹是什么时候、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前来平阳的呢?他在平阳的具体行踪又是如何的呢?笔者通过查阅大量史料,并进行多处实地走访,试作考证如下:
避难闽东 讲学育人
绍熙五年(1194)八月,朱熹出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九月,朱熹于行宫便殿奏事。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诏进讲《大学》,反复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引起宋宁宗和执政韩侂胄的不满。因此,朱熹在朝仅四十六日,就被宋宁宗下旨罢去了待制兼侍讲之职。
绍熙五年(1194)十一月,朱熹还居建阳考亭。
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在宰相韩侂胄的授意下,御史沈继祖罗织朱熹十条大罪,于是朱熹被罢免秘阁修撰一职,朱熹理学被明令指斥“伪学”,其弟子蔡元定被押道州管制,并定“伪学逆党籍”五十九人,这就是史上所谓的“庆元党禁”。
庆元三年(1197)三月,为了避难,朱熹应福建古田门人林用中、余偶、余范等人的邀请,取道延平,来到古田。后经朱熹的大力提倡,在古田三十九都(今古田杉洋一带)兴办了蓝田、擢秀、溪山、西山、螺峰、浣溪、兴贤、谈书、瑞云九所书院,故当地民间有“朱子一日教九斋”的传说。其中以蓝田书院最为著名,朱熹在这里讲学时间最长,达三年之久。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新旧日生徒咸集,书院盛况空前。三年之中,培养了大批人才。正如清代宁德知县储右文撰写《重修朱子祠记》中说的:“粤考宁邑在宋,邑理学真儒先后辈出……揆厥所由,盖紫阳朱子倡讲堂于武夷寒泉之间,一是响应,流风兼被,旁近郡邑翕然宗之,良有由也。”
庆元五年(1199)开春,七十高龄的朱熹应长溪、宁德学生林湜、陈骏、龚郯、杨楫、黄幹的邀请,由古田大甲谈书书院来到宁德。之后来到九都的龟山寺,讲学多日。
清《宁德县志·寓贤》载:“紫阳朱子,庆元间以禁伪学避地于闽,至长溪,住黄幹、杨楫家,讲学于石湖馆、龟山寺、石堂等处,从游者甚众。而黄幹、杨复、林湜、高松、陈骏、郑师孟、龚郯、张泳,其最著者也。过黄崎村,作《中庸序》。”
其间,高足林湜闻知老师已预约而至,喜出望外,不顾路途遥远,由浙江平阳赶回长溪与老师见面,并切磋学术达三、四个月之久。
据考证,朱熹在闽东留存的除了诗词文章,还包括大量的书法墨迹、摩崖石刻。单单古田就有十多处,大多分布在杉阳蓝田书院附近。在宁德、霞浦、福鼎、福安也有一些。1985年春,霞浦龙首寺为了扩建后座“观音阁”,在开土填基中挖掘出掩埋多年的朱熹题写的“白云深处”石匾。后经有关部门认证,石匾确系朱熹手迹。这块小小的石匾不仅证实了《霞浦县志》中记载的准确性,更显明了朱熹流寓闽东的史实。
此外,朱熹在闽东还留有《蓝洞记》《答林正甫湜书》《答高国楹书》等篇章。特别是《答林正甫湜书》,收录于乾隆版《福宁府志·文艺志》及民国版《霞浦县志·文艺志》中。这是朱熹晚年写给定居平阳的学生林湜的回信,文字流畅,娓娓动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应邀讲学 留迹福鼎
其后,朱熹又应学生杨楫、高松(均为今福鼎人)之请,来到福鼎的潋村,其间还游览了著名胜迹福鼎太姥山与鳌峰栖林寺,据说还于太姥山璇玑洞中完成注释《中庸》的工作。
潋村内有一道观石湖观,地平且宽,风水极佳。朱熹应杨楫之请,在石湖观一览轩进行讲学,远近学子听闻朱子在此讲学,纷纷前来受教。
之后,杨辑与族人一起将道观改成了书院,并置田供书院日常之用,以教学传播朱熹理学。朱熹特为书院撰写对联:“溪流石作柱:湖影月为潭。”
朱熹的到来,拉开了福鼎理学的序幕,吸引了一大批福鼎士子来此听讲、问学。清嘉庆《福鼎县志·理学》中即提到:“自高、杨诸君子游紫阳之门,深得其邃,大阐宗风,名儒辈出,后先辉映。”朱熹师徒相与切磋学问,使石湖书院一时声名远播,书院作为福鼎理学圣地的文化地位得以奠定。
近年福鼎市在文物普查工作中,发现太姥山的水湖一块元代的摩崖石刻,上记朱子在山中璇玑阁授徒讲学逸事,石刻附近即明万历《太姥山志》所载的朱子草堂遗址。遗址之旁有巨石刻有“林下相逢”四字,显系纪念朱熹与其门人的文字。
目前已发现的福鼎潋村《杨氏族谱》,西园《高氏族谱》均记述朱氏师徒的学术活动,清高龙光纂修的《高氏族谱》扉页绘有《龟峰讲学图》,中朱子、左高松、右杨辑,龟峰在双髻山上,山上有一览轩遗址。
今福鼎文化馆收藏有由清嘉庆翰林院庶吉士、福鼎县令高鸿飞所撰的《重修文昌阁》,碑文中记载:“……鼎虽小邑,宋之王梅溪、陆放翁、朱文公皆游历于此。”
北上平阳 造访盖竹
朱熹从小就受到“二程”洛学的熏陶。其父朱松是洛学的崇拜者,师从“二程”再传弟子罗从彦。朱熹也遵父命,师事受洛学影响的刘勉之、刘子翚、胡宪等人,后又受业于“二程”的三传弟子李侗。
而平阳学统的发端者北宋乐溪人陈经邦、陈经正兄弟,是程颐的及门高足,由“二陈”传入的洛学在平阳广为传播后,一时文风大盛。当时平阳很多读书人不满足于只在乡里学习程门理学,而是直接追随当时的理学代表人物、程门四传弟子朱熹求学。
正因为朱熹与平阳学人都深受洛学熏陶,可谓师出同门,而朱熹的平阳弟子又多,朱熹对平阳的学人自然是有好感的。加上盖竹的林拱辰为淳熙八年(1181)进士,与朱熹同朝为官,且立朝刚直,不依附史浩与韩侂胄,政治观点与朱熹完全一致,朱熹年长于林,算是忘年交好,另外,林拱辰与朱熹的弟子林湜为同族,平日多有交集。
因为综上所述的这些渊源,当朱熹来到与浙江平阳接壤的福建福鼎后,便在平阳众弟子的陪同下,率弟子们由闽入浙,前来平阳。
朱熹当时已经是七十高龄,加上又有足疾,福鼎到平阳盖竹,路途遥远,若跋山涉水,太过劳累,因此朱熹前往盖竹很有可能是福鼎秦屿的潋村附近入海,坐船过东海,朔鳌江而上,来到盖竹。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林湜居松山(今苍南县桥墩),但松山一带都没有朱熹曾经到访过的传说的原因。因为朱熹来平阳,目的是到盖竹,并由盖竹再去寻访程门高足陈经邦、陈经正兄弟两位前辈读书讲学的地方的。
在没有改道之前,宋代的鳌江的河道,是经过盖竹前面的,鳌江岸边有埠头,行旅商贾,往来络绎不绝,很是繁华。现在当地还有“埠头”这样的地名,就是当年鳌江上岸的码头。
朱熹来到盖竹后,登临林家江楼,倚栏远眺,见群峰、渔舟历历在目,不仅想起自己的跌宕生涯与时下遭遇,遂慨然而作《过盖竹二首》。诗曰:
二月春风特地寒,江楼独自倚栏杆。个中讵有行藏意?且把前峰细数看。
浩荡鸥盟久末寒,征骖聊此驻江干。何时买得渔船就,乞与人间画里看。
要看懂这两首诗,必须要了解“行藏”于“鸥盟”这两个典故。
“行藏”典出《论语·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孔子对弟子颜回说:“国君任用我,我就去出仕;不被任用,我就退隐。我想只有我和你才有这种进退的方法。”后因以“行藏”指出仕与退隐。
“鸥盟”典出《列子·黄帝》:“海上之人有好鸥鸟者,每旦之海上,从鸥鸟游,鸥鸟之至者百往而不止。”唐人陈子昂《答洛阳主人》诗云:“不然拂衣去,归从海上鸥。”后因以“鸥盟”谓与鸥鸟为友,比喻隐退。宋陆游《夙兴》诗:“鹤怨凭谁解,鸥盟恐已寒。”
从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朱熹此时宦海浮沉多年,已生倦意,更萌生退意了,此时的他要买“渔船”,“小舟从此逝,江海度馀生”了。
据乾隆《平阳县志》卷十七《人物下·流寓》载:“宋朱熹,淳熙间为浙东茶盐提举,来瓯,与门人陈埴、徐寓、徐容、叶贺孙、钱木之及林湜、蔡㦛辈同游南雁山。至经正书院,见陈氏肄业甚盛,因题曰‘会文书院’,讲学旬余,有题咏‘穷溪山之胜,极讲论之乐’,一时称胜事云。”
乾隆《平阳县志》记载了朱熹前来平阳,并到南雁山寻访陈经正书院的盛况,但时间弄错了。
据《宋史·朱熹传》载,“会浙东大饥,宰相王淮秦改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即日单车就道。”淳熙八年(1181)夏秋之间,浙东一带水灾不断,造成严重的饥荒,而以绍兴府尤烈。同年八月,由宰相王淮荐举,朱熹受命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负责浙东地区的赈灾事宜。朱熹一面上书朝廷,筹备赈灾的钱粮,一面微服私访,了解民情,推行荒政,经常忙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朱熹切实的赈灾举措和其道学人格,使朱学在浙东产生了很大影响,但由于朱熹在浙东劾奏前台州知州唐仲友不法,为唐之姻亲王淮所嫉,浙东任职仅九个月即罢官奉祠。
朱熹在任浙东茶盐提举时,赈灾事务繁忙。而早春二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也是赈灾工作重中之重的时候,恪尽职责的朱熹,怎么可能还好整以暇,腾出大把的时间,带着弟子们到处闲逛,而且还跑到远在浙南的平阳南雁呢?况且在《过盖竹》诗中流露出来的浓郁退意,也不是正在仕途中的朱熹该有的心境。
因此,朱熹来平阳的时间不是在淳熙间,而是十年后的庆元间。
寻访书院 题额“会文”
朱熹到了盖竹,有没有讲学,现在已无从考证。但当时盖竹学风正盛,学子又多,且宋时建有东山书院,因此在盖竹讲学是完全有可能的。
明代宋濂《平阳林氏祠学记》载:“今平阳盖竹之林氏,立祠于始迁之祖之墓而祭之。祠后为斋,曰‘思孝’,以会其族人。复立祠于左偏,祀晦庵朱子之像,以其先宋吏部侍郎拱辰、千之、起鳌及其父阳江君配祀。”根据这段描述,林氏建祠,当中供奉的既不是林氏先祖,也不是孔子,而是朱熹,这说明朱熹对盖竹林家影响之大,由此可以反证,当年朱熹是有在盖竹讲学,其学说一直到明初,还深深地影响着盖竹的林氏学子。
民国水头周喟在《南雁荡山志》中,也引用了宋濂的此文,说:“按,观此及《晦庵集·过盖竹》作二首诗,可为朱子尝至南雁山之证。”
浙江大学硕士何生根先生曾考察浙江各地与朱熹有关的诸多书院,并在2002年发表的《朱熹与浙江书院》一文中说:“与朱熹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书院,后来大多数都立祠祭祀,或供其像于书院。朱熹在书院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便对书院的内容有较大的影响,祭祀朱熹的书院一定以程朱理学作为主要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便遵循格物致知的路子。比如,乾道年间朱熹曾讲学于乐清县的艺堂书院(后改名为“宗晦”),由咸淳年间邑令郑滁孙改建,聘乡先生胡子实教授。胡便精于“四书”,讲解详明,深契要旨……一些仅仅因为朱熹名声而奉祀他的书院,象元大德二年(1298)建于鄞县的郧山书院,在历经拓新重修后至天历年间,教学内容主要是朱熹的《四书集注》。康熙年间建于杭州的紫阳书院,其学规便乘从“白鹿洞条规”。这些仅因为尊崇朱熹而祀之的书院还有:月湖书院(鄞县)、高节书院(余姚)、敷文书院(杭州)、丹山书院(象山)、东湖书院(鄞县)、丽正书院(金华)、甬东书院(鄞县)、衢讲舍(西安)等等,以上分析足以证明朱熹对浙江书院以至书院教育的广泛影响。”
朱熹到了盖竹做一番停留后,继续前往南雁山,寻访陈经邦、陈经正的书院。清乾隆《平阳县志》载:朱熹与门人陈埴、徐寓、徐容、叶贺孙、钱木之及林湜、蔡㦛等人,“至经正书院,见陈氏肄业甚盛,因题曰‘会文书院’,讲学旬余,有题咏‘穷溪山之胜,极讲论之乐’,一时称胜事云。”
关于“会文书院”,一直以来,都说其又名“会邱书院”。据目前我所看到的文献,最早出自康熙《浙江通志》卷十八载:“会丘书院,在南雁荡,陈经正、经邦读书处,朱文公题额。”其后的清乾隆《平阳县志》卷之三《建置上·学校》载:“会文书院,一名会邱书院,在雁荡山,宋陈经正等读书处,朱文公题额。”这个“一名会邱书院”的说法,应该是沿用《浙江通志》的内容。之所以“丘”成了“邱”,是因为清雍正三年(1725),为避圣讳,上谕除“四书五经”外,凡遇“丘”字,并加“阝”旁为“邱”。光绪《浙江通志》卷二十七中,在转载康熙版《浙江通志》时,便将“会丘书院”作“会邱书院”。
然而,查考康熙之前的地方文献,并不见有“会邱书院”的记载。民国周喟《南雁荡山志》卷三“寺宇”载:“案,陈《志》:“朱熹来游,山门叶群为主人。熹醉笔标题陈经邦书院曰‘会文’,陈端彦书院曰‘棣萼世辉楼’,叶群书院曰‘毓秀’,朱梦良书院曰‘聚英’。”“陈《志》”,即明代嘉靖嘉靖三十六年(1557),邑人陈文源、陈玭编成《南雁荡山志》,文中不见有“会丘”的记载。
周喟《南雁荡山志》卷三“寺宇”中的“会文书院”条目载:“郑《志》:“书院曰会文,曰毓秀,曰聚英,曰聚奎,皆南湖薛氏,盖竹、四溪二林氏共建,今悉废址。”
文中的“郑《志》”,即明末郑思恭的《南雁荡山志》,文中亦不见有“会丘”,但却明确指出,盖竹林氏建有书院。
那么,到底有没有“会丘书院”这个名称呢?
首先,我们说下,在南宋时期,书院有没有可能以“丘”为名。
孔子的名讳,在古代称为“圣人讳”或“圣讳”。在宋朝,孔子被谥为“至圣文宣王。宋徽宗时,曾接连下诏避“圣讳”。
十八世纪中国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一代儒宗”钱大昕(1728—1804)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一“避讳改郡县名”条的宋代部分载:“(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避孔子讳,改瑕邱县曰瑕县、龚邱县曰龚县。”钱大昕著述于清乾嘉年间,避圣讳,故书“丘”为“邱”。
为避孔子名讳,宋徽宗先是下诏改了县名,接着又下诏改封孔子弟子曾参等人的爵号。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马端临(1254—1323)在《文献统考·学校五》中记载:“政和元年(1111)六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奉诏:‘孔子高弟子所奉侯爵与宣圣名同,失弟子尊师之礼。今乞以瑕丘侯曾参改封为武城侯,宛丘侯颛孙师为颍川侯,龚丘侯南宫縚为汶阳侯,楚丘侯司马耕为洛阳侯,顿丘侯琴张为阳平侯,瑕丘伯左丘明为中都伯,宫丘伯谷梁赤为洛陵伯,楚丘伯戴圣为考城伯。”
从宋徽宗开始,作为儒家代表的孔子,被列入帝王之列,享受回避名讳的尊荣,由此也开启了后世避孔子讳的先例。之后,从宋代一直到清代,上至天子王侯,下至平民百姓,从书面到口头,无不对这个“丘”字敬而避之。写起来或缺一笔,或写作“某”,或用朱笔圈之,不一而足。
在北宋徽宗时,就已经为避圣人讳,把一个县的名称与原有的孔门高徒封号都给改了,到了南宋时,读孔圣人的读书人书院,怎么可能还会不避圣讳,而直以“丘”命名呢?更何况,陈经邦、陈经正还是程颐的及门高第,深受儒家学说淫浸,并非不知礼数的山野村夫。再说了,即便陈氏不懂规矩,那作为一代儒宗的朱熹,又怎么可能会直书孔圣人名讳的呢?
况且“会文”二字,是有出处的,即《论语·颜渊》中的“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而“会丘”二字,笔者遍翻诸家经典,却是怎么都找不到出处。
因此,笔者大胆推测,“会丘书院”在历史上并不存在,鲁鱼亥豕,误“文”为“丘”,纯属康熙《浙江通志》误记。而后世不辨所以,以讹传讹,以致谬误至今。
旬馀讲学 当在乐溪
距盖竹不到二十里的乐溪(今鹤溪),为陈经邦、陈经正的故里。在宋代时,鳌江潮水可以一直涨到乐溪外垟,今当地还有埠头遗址,可见当年水路交通还是很方便的。
在今水头镇鹤溪社区元底村,还有俗称“陈氏老厝基”的陈氏故居遗址,当年的石砌围墙,有一大段还保存完好。
据宋许景衡《横塘集》中记载:陈“家多资”,这从陈家能让陈经邦、陈经正二兄弟及其从弟经德、经郛能不远千里赴汴京(今河南开封)入太学读书,可知其家境之殷实。
北宋崇宁三年(1104)春,陈经邦在乐溪家居时,曾写了一篇《会文阁记》:“邦自龆龄读书,晚而不倦。虽识见不及于前时,而嗜好有甚于初心,孜孜矻矻,废食忘寝,殆若狂然。家人僮仆皆以痴目之,不自知其为癖也。又如是而益甚,而家人益之以厌。于是谋于家居之前创为书阁,且欲远于家务,庶免家人之所讥议。阁告成,尝试以‘会文’名之。而又凿沼于其前,开圃于其侧,环山屏列乎左右,带水萦绕乎东西。”
陈经邦、经正兄弟的读书处是“会文阁”,这是没有疑问的。到了南宋庆元五年(1199),还不到百年,陈氏后裔在陈氏祖居前的会文阁中继续读书,这是很正常的。因此据乾隆《平阳县志》载,当朱熹与门人陈埴、徐㝢、徐容、叶贺孙、钱木之及林湜、蔡㦛等人寻访的“经正书院”,应该就是“会文阁”旧址。而朱熹“见陈氏肄业甚盛”,“因题曰‘会文书院’”,也就是顺理成章了。讲学旬余,有题咏‘穷溪山之胜,极讲论之乐’,一时称胜事云。”
而据更早的明嘉靖年间编纂的《南雁荡山志》载:“朱熹来游……醉笔标题陈经邦书院曰‘会文’。”也可知,所谓的“陈经邦书院”,应该就是当年的“会文阁”。
如今在南雁荡山东洞华表峰下的会文书院,一向都说是陈经邦、陈经正兄弟读书处。但笔者经过考证,认为该观点有误,陈氏兄弟的读书处应该在其家乡乐溪。
文中明明白白地写道,会文书阁位“家居之前”。即今天的水头镇鹤溪社区的元底村,在当地,还有陈氏故居的旧日址,元底的地形,与陈经邦《会文阁记》文中所描绘的地形一致。位于峡谷之中,南北两侧都是山峦,峡谷中有两条小溪蜿蜒如带,在陈经邦故居前不远处汇合后,再自西向东流出峡谷。陈经邦是在“家居之前创为书阁”的,并在其前开凿池塘迎溪水入内,正是“环山屏列乎左右,带水萦绕乎东西”的情形。
而如今南雁荡山中的会文书院,处于华表峰下东洞之中,场地逼仄,地势陡峭,古时没有开凿铺设石阶之前崎岖难行,怎么可能会有人居住呢?又从何谈起建于“家居之前”呢?况且建筑物下是岩石,在古代条件简陋的情形下,不可能专门费尽心力开凿池塘,更不可能有“带水萦绕乎东西”的景观。纵览明代方鹏、蔡芳、陈玭比、郑思恭和清代潘耒等人的南雁荡山游记,于东西洞景区风景状摹甚详,但独独没有提及东洞曾有过会文书院,清康熙年间的施元孚在专门描写东洞的《仙甑岩记》中,也只字不提书院。
而在明清之前的元代,著名学者史伯璿(1299-1354)还专程前往瞻仰会文书院旧址,并写了《过陈氏会文书院》诗:“上映棂星下碧溪,群英冠学古今稀。经书世系番山舍,科第家传入荆闱。恩渥九重濡雁荡,文光万丈烛牛墟。门楣底事荒凉易,枯壁寒蝉噪落晖。”如果该书院果真在南雁东洞,那么明清两代前往南雁游览的后学不可能不会去拜谒遗址,更不可能一字不提,可见陈氏的会文书院并非在南雁,更非在东洞之中。
关于沿袭至今的“南雁会文书院是陈氏兄弟读书处”的说法,在刘绍宽的民国《平阳县志》中对于陈经邦的书阁“会文阁”也有考证:“……则会文阁宜在乐溪矣,旧日志云在浦源,今其地相传犹存遗址,盖后人因南雁山会文书院而附会为之。”而周喟在其《南雁荡山志》中也考证道:“……则会文阁在乐溪无疑。旧志云在浦源,本于谱牒附会,不足信云。”
综上所述,陈经邦的读书处“会文阁”是乐溪,在清末重建于南雁华表峰下的会文书院和棣萼世辉楼都并非是陈氏兄弟的读书处,至于为什么后来在乾隆《平阳县志》中会将陈氏兄弟的读书处附会到南雁,估计是平阳后学曾在南雁华表峰下建有会文书院,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永嘉诸生林必锦在《游南雁荡记》中就有“入石门楼,昔日会文遗址犹在”的文字,清乾隆年间,平阳教谕卢镐来游南雁,亦有《穿东洞,寻会文书院遗址,……》的诗作。
而清嘉庆五年(1800)江苏常州人秦鸣雷来游南雁时,更是产生“云是会文书院遗址,南宋时有陈氏子孙读书其中,朱子尝往访之”的误会,这是因为陈经邦、陈经正都写过《雁荡山》诗,都曾在南雁活动过,后人混为一谈,产生误解,也是人之常情。
此处所谓的会文书院,尽管清光绪八年(1882)陈少文等人予以重建,但素以考据严谨的刘绍宽在民国《平阳县志·古迹志》并未列入。列入的是“旧传宋陈经邦、经正、经一、经德、经郛,孙元普、元胜,曾孙永起读书处”的棣萼世辉楼,而且也通过考证予以了否定:“据《青华集·下涝陈氏十咏诗序》云‘雁山辉萼院始于良翰诸昆,继于端彦诸子’,是初不以辉萼为经正兄弟读书处也……旧志(指乾隆《平阳县志》)载陶亮器诗:‘罗列奇峰插太虚,研覃经义寄山居。联芳棣萼真堪羡,伊洛渊源咫尺馀。’亦修雁志者所伪撰,此条本从删削,惟因旧说相沿已久,删去转以滋疑,故为载,而辨之如此。”
在古代,人们所说的南雁荡山范围要比现在的大的多,从钱仓的凤山开始,山脉绵延至顺溪,都是南雁荡山的景区。如今的荆溪山一带,还有“南雁门”之说。而有华盖峰、醉翁岩、龙湫等形胜的盖竹,以及乐溪一带山水,都是旧时南雁荡山的范围之内。
一直到民国周喟的《南雁荡山志》中,盖竹与乐溪还是作为“别巘”列入的,意思是南雁荡山的别枝。
朱熹当年来平阳,过盖竹,至乐溪,讲学旬馀,完全也可以说是“游南雁山”。这时的朱熹,毕竟已经是七十岁高龄的老人了,且患足疾,连陪同他的弟子林湜也是差不多年龄的老人。虽然乾隆《平阳县志》记载“有题咏‘穷溪山之胜,极讲论之乐’,一时称胜事云”。但朱熹并没有深入当时还算蛮荒的南雁荡山东西洞景区,所谓“溪山之胜”,也只是盖竹与乐溪一带的山水风光而已。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以朱熹的水平,到了真正的南雁荡山核心景区,饱览美景,不可能无诗记录的。而有诗的话,以当年已名满天下的他,也是不可能失载的。
在《全宋诗》卷三〇〇九中,有辑自清曾唯《东瓯诗存》卷八的陈埴的《南雁山》诗,此诗亦见于历代《南雁荡山志》:
千峰历罢寄山窗,酒力诗狂总未降。月白洞门花落尽,天空华表鹤飞双。崖边瀑雪寒侵梦,涧底笙箫冷韵腔。且喜懒残煨芋熟,不妨久话共秋釭。
陈埴(1176—1232),温州永嘉人,字器之,号木钟。宋宁宗嘉定间(1208—1224)进士。少师叶适,后从朱熹游。为明道书院干官兼山长,从学者甚众,称潜室先生。历任丰城主簿、湖口县丞等职,以通直郎致仕。有《木钟集》十一卷存世。而诗,就仅有《南雁山》一首存世。
明嘉靖《南雁荡山志》中,记载有“朱熹来游,山门叶群为主人”。巧的是,而在民国《南雁荡山志》中,就记载有叶群的一首诗,录自《东瓯诗存》:
石门深窅锁丹霞,倚马西风日欲斜。幽境已无尘俗气,白云尚有翠微家。林间摘句书红叶,涧底烹泉带落花。向晚且从西洞息,碧山明月正堪赊。
叶群,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辛未科进士,任剑浦主簿。叶群的生卒失考,但根据其考中进士的时间,在朱熹来游南雁时,叶群起码也已是古稀老人了,鼓动大家去游南雁东西洞的可能性,估计也不大了。不过,叶群在热情招待朱熹等人时,对南雁核心景区风光的描述,肯定是能激发陈埴的游兴的。
陈埴当时陪同朱熹来游南雁时,正值二十多岁的青年。年轻人普遍好玩,所以完全可能在朱熹讲学的过程抽空去游览一番名胜的。至于叶群是否有陪同或派人陈埴前往南雁,或者在不久之后,陈埴又自己重新来游南雁,现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从陈埴的诗中的“山窗”“洞门”“华表”等景物描写,可知他是去了南雁荡山核心的东西洞景区的。而从诗中“花落尽”“共秋缸”的描述来看,不像是写于早春二月的,所以是日后再来游览的可能性更大。毕竟陈埴是温州永嘉人,离南雁荡山还是不算远的。
倒是林湜有一首《游南雁荡山》,见于历代《南雁荡山志》,很是值得玩味。诗云:“养静山僧卓锡随,跻攀绝顶共寻奇。鸟歌花笑如曾识,天霁风清似有期。乾洞夜明通日月,灵湫春暖起云霓。投簪归老还忧国,药径前头采紫芝。”从“灵湫春暖”的描述来看,此诗写于春天,而“投簪”比喻弃官,陪朱熹前来盖竹的林湜时年六十八岁,已经致仕,告老还乡,而当时宋朝“党禁”正严,林湜心忧国事,的确是“投簪归老还忧国”。
为此,笔者大胆推测,林湜此诗便是写于陪同朱熹来盖竹之时,因为盖竹位于南雁荡山景区范围,完全可以署题《游南雁荡山》。因为盖竹有始建于唐乾宁间的东山院,游览时有“山僧卓锡随”;有龙湫,即诗中的“灵湫”;有见于元代张天英《游盖竹山》的“晓洞”,即诗中的“乾洞”,至于“药径”,并非实指如今南雁东西洞景区的采药径,而是虚指,自古以来,诗人作品中关于“药径”的描写也是很多的,如南宋温州人赵师秀就有《采药径》诗:“十载仙家采药心,春风过了得幽寻。如今纵有相逢处,不是桃花是绿阴。”
北上瑞安 再访故人
朱熹离开平阳后,再次北上,到瑞安仙岩走访同属南宋著名学者的好友陈傅良。
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号止斋,学者称止斋先生,卒谥文节,瑞安湗村(今属瑞安市塘下镇罗凤街道)人。乾道八年(1172)进士,官至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兼集英殿修撰。陈傅良在湖南任职时主讲岳麓书院,门墙极盛。陈傅良,是永嘉学派的学术巨擘,为学主张“经世致用”,反对性理空谈。南宋光宗皇帝曾给陈傅良赐联:“东瓯理学无双士;南宋文章第一家。”高度评价陈傅良的成就。
绍熙五年(1194)冬,赵汝愚与韩侂胄争权而失势,因争权时赵汝愚曾引朱熹“道学”集团以自助,侂胄得势后就进行报复,打算斥逐朱熹。据《宋史·陈傅良传》载:“会诏朱熹与在外宫观,傅良言:‘熹难进易退,内批之下,举朝惊愕,臣不敢书行。’”在当时这种形势对朱熹极其不利的情况下,陈傅良出于公心,对宁宗说:朱熹做官前要再三考虑,去官时唯恐不速,根本不是贪念功名的人,而是一位真正爱国爱民的人。如果连他这样的都要罢官,一旦圣旨颁发后,满朝大臣都会失色,臣不敢草拟诏书。”这事使傅良以“依托朱熹”的罪名受到参劾,又被罢官。从此,他一心韬晦,闭门静居,称自己的居室为“止斋”。而韩侂胄进而发动“庆元党禁”,指控朱熹的道学为“伪学”,把陈傅良、叶适、蔡幼学等温州学者一并列入“伪学”名单。
陈傅良罢官回乡后,创办仙岩书院,招生收徒,传授“经世致用”思想。一直到嘉泰二年(1202)才得以复官。朱熹来平阳时,陈傅良正在仙岩书院。
朱熹到仙岩书院访问陈傅良期间,曾书“溪山第一”、“开天气象”,以赞誉仙岩山水人文。
当时,被罢官的叶适也在温州家中赋闲。
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居士。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世称水心先生。卒谥“文定”(一作忠定),故又称“叶文定”“叶忠定”。
据张义德《叶适评传·附录·叶适年谱》载:庆元三年(1197),叶适为御史胡纮所劾,降两官后罢职,主管冲佑观,差知衢州,叶适推辞,由镇江归永嘉。
庆元五年(1199)春,朱熹来访陈傅良时,叶适也正家居。据说,朱熹到温州后还曾与叶适会晤。
不久,朱熹旧疾复发,遂结束了浙南之行,返道回长溪,从罗浮乘舟经福州回建阳。之后,被各种疾病所困扰的朱熹,预感到死亡的逼近,更加抓紧著述。
庆元六年(1200)入春以后,朱熹足疾大发,病情恶化,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几乎完全失明。朱熹却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紧整理残篇,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将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统后继有人。三月初九,朱熹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嘉泰二年(1202),也就是朱熹去世两年之后,大规模禁锢道学的“庆元党禁”运动宣告结束。
避难闽东 讲学育人
绍熙五年(1194)八月,朱熹出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九月,朱熹于行宫便殿奏事。十月十四日,朱熹奉诏进讲《大学》,反复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希望通过匡正君德来限制君权的滥用,引起宋宁宗和执政韩侂胄的不满。因此,朱熹在朝仅四十六日,就被宋宁宗下旨罢去了待制兼侍讲之职。
绍熙五年(1194)十一月,朱熹还居建阳考亭。
庆元二年(1196)十二月,在宰相韩侂胄的授意下,御史沈继祖罗织朱熹十条大罪,于是朱熹被罢免秘阁修撰一职,朱熹理学被明令指斥“伪学”,其弟子蔡元定被押道州管制,并定“伪学逆党籍”五十九人,这就是史上所谓的“庆元党禁”。
庆元三年(1197)三月,为了避难,朱熹应福建古田门人林用中、余偶、余范等人的邀请,取道延平,来到古田。后经朱熹的大力提倡,在古田三十九都(今古田杉洋一带)兴办了蓝田、擢秀、溪山、西山、螺峰、浣溪、兴贤、谈书、瑞云九所书院,故当地民间有“朱子一日教九斋”的传说。其中以蓝田书院最为著名,朱熹在这里讲学时间最长,达三年之久。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新旧日生徒咸集,书院盛况空前。三年之中,培养了大批人才。正如清代宁德知县储右文撰写《重修朱子祠记》中说的:“粤考宁邑在宋,邑理学真儒先后辈出……揆厥所由,盖紫阳朱子倡讲堂于武夷寒泉之间,一是响应,流风兼被,旁近郡邑翕然宗之,良有由也。”
庆元五年(1199)开春,七十高龄的朱熹应长溪、宁德学生林湜、陈骏、龚郯、杨楫、黄幹的邀请,由古田大甲谈书书院来到宁德。之后来到九都的龟山寺,讲学多日。
清《宁德县志·寓贤》载:“紫阳朱子,庆元间以禁伪学避地于闽,至长溪,住黄幹、杨楫家,讲学于石湖馆、龟山寺、石堂等处,从游者甚众。而黄幹、杨复、林湜、高松、陈骏、郑师孟、龚郯、张泳,其最著者也。过黄崎村,作《中庸序》。”
其间,高足林湜闻知老师已预约而至,喜出望外,不顾路途遥远,由浙江平阳赶回长溪与老师见面,并切磋学术达三、四个月之久。
据考证,朱熹在闽东留存的除了诗词文章,还包括大量的书法墨迹、摩崖石刻。单单古田就有十多处,大多分布在杉阳蓝田书院附近。在宁德、霞浦、福鼎、福安也有一些。1985年春,霞浦龙首寺为了扩建后座“观音阁”,在开土填基中挖掘出掩埋多年的朱熹题写的“白云深处”石匾。后经有关部门认证,石匾确系朱熹手迹。这块小小的石匾不仅证实了《霞浦县志》中记载的准确性,更显明了朱熹流寓闽东的史实。
此外,朱熹在闽东还留有《蓝洞记》《答林正甫湜书》《答高国楹书》等篇章。特别是《答林正甫湜书》,收录于乾隆版《福宁府志·文艺志》及民国版《霞浦县志·文艺志》中。这是朱熹晚年写给定居平阳的学生林湜的回信,文字流畅,娓娓动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应邀讲学 留迹福鼎
其后,朱熹又应学生杨楫、高松(均为今福鼎人)之请,来到福鼎的潋村,其间还游览了著名胜迹福鼎太姥山与鳌峰栖林寺,据说还于太姥山璇玑洞中完成注释《中庸》的工作。
潋村内有一道观石湖观,地平且宽,风水极佳。朱熹应杨楫之请,在石湖观一览轩进行讲学,远近学子听闻朱子在此讲学,纷纷前来受教。
之后,杨辑与族人一起将道观改成了书院,并置田供书院日常之用,以教学传播朱熹理学。朱熹特为书院撰写对联:“溪流石作柱:湖影月为潭。”
朱熹的到来,拉开了福鼎理学的序幕,吸引了一大批福鼎士子来此听讲、问学。清嘉庆《福鼎县志·理学》中即提到:“自高、杨诸君子游紫阳之门,深得其邃,大阐宗风,名儒辈出,后先辉映。”朱熹师徒相与切磋学问,使石湖书院一时声名远播,书院作为福鼎理学圣地的文化地位得以奠定。
近年福鼎市在文物普查工作中,发现太姥山的水湖一块元代的摩崖石刻,上记朱子在山中璇玑阁授徒讲学逸事,石刻附近即明万历《太姥山志》所载的朱子草堂遗址。遗址之旁有巨石刻有“林下相逢”四字,显系纪念朱熹与其门人的文字。
目前已发现的福鼎潋村《杨氏族谱》,西园《高氏族谱》均记述朱氏师徒的学术活动,清高龙光纂修的《高氏族谱》扉页绘有《龟峰讲学图》,中朱子、左高松、右杨辑,龟峰在双髻山上,山上有一览轩遗址。
今福鼎文化馆收藏有由清嘉庆翰林院庶吉士、福鼎县令高鸿飞所撰的《重修文昌阁》,碑文中记载:“……鼎虽小邑,宋之王梅溪、陆放翁、朱文公皆游历于此。”
北上平阳 造访盖竹
朱熹从小就受到“二程”洛学的熏陶。其父朱松是洛学的崇拜者,师从“二程”再传弟子罗从彦。朱熹也遵父命,师事受洛学影响的刘勉之、刘子翚、胡宪等人,后又受业于“二程”的三传弟子李侗。
而平阳学统的发端者北宋乐溪人陈经邦、陈经正兄弟,是程颐的及门高足,由“二陈”传入的洛学在平阳广为传播后,一时文风大盛。当时平阳很多读书人不满足于只在乡里学习程门理学,而是直接追随当时的理学代表人物、程门四传弟子朱熹求学。
正因为朱熹与平阳学人都深受洛学熏陶,可谓师出同门,而朱熹的平阳弟子又多,朱熹对平阳的学人自然是有好感的。加上盖竹的林拱辰为淳熙八年(1181)进士,与朱熹同朝为官,且立朝刚直,不依附史浩与韩侂胄,政治观点与朱熹完全一致,朱熹年长于林,算是忘年交好,另外,林拱辰与朱熹的弟子林湜为同族,平日多有交集。
因为综上所述的这些渊源,当朱熹来到与浙江平阳接壤的福建福鼎后,便在平阳众弟子的陪同下,率弟子们由闽入浙,前来平阳。
朱熹当时已经是七十高龄,加上又有足疾,福鼎到平阳盖竹,路途遥远,若跋山涉水,太过劳累,因此朱熹前往盖竹很有可能是福鼎秦屿的潋村附近入海,坐船过东海,朔鳌江而上,来到盖竹。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林湜居松山(今苍南县桥墩),但松山一带都没有朱熹曾经到访过的传说的原因。因为朱熹来平阳,目的是到盖竹,并由盖竹再去寻访程门高足陈经邦、陈经正兄弟两位前辈读书讲学的地方的。
在没有改道之前,宋代的鳌江的河道,是经过盖竹前面的,鳌江岸边有埠头,行旅商贾,往来络绎不绝,很是繁华。现在当地还有“埠头”这样的地名,就是当年鳌江上岸的码头。
朱熹来到盖竹后,登临林家江楼,倚栏远眺,见群峰、渔舟历历在目,不仅想起自己的跌宕生涯与时下遭遇,遂慨然而作《过盖竹二首》。诗曰:
二月春风特地寒,江楼独自倚栏杆。个中讵有行藏意?且把前峰细数看。
浩荡鸥盟久末寒,征骖聊此驻江干。何时买得渔船就,乞与人间画里看。
要看懂这两首诗,必须要了解“行藏”于“鸥盟”这两个典故。
“行藏”典出《论语·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孔子对弟子颜回说:“国君任用我,我就去出仕;不被任用,我就退隐。我想只有我和你才有这种进退的方法。”后因以“行藏”指出仕与退隐。
“鸥盟”典出《列子·黄帝》:“海上之人有好鸥鸟者,每旦之海上,从鸥鸟游,鸥鸟之至者百往而不止。”唐人陈子昂《答洛阳主人》诗云:“不然拂衣去,归从海上鸥。”后因以“鸥盟”谓与鸥鸟为友,比喻隐退。宋陆游《夙兴》诗:“鹤怨凭谁解,鸥盟恐已寒。”
从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朱熹此时宦海浮沉多年,已生倦意,更萌生退意了,此时的他要买“渔船”,“小舟从此逝,江海度馀生”了。
据乾隆《平阳县志》卷十七《人物下·流寓》载:“宋朱熹,淳熙间为浙东茶盐提举,来瓯,与门人陈埴、徐寓、徐容、叶贺孙、钱木之及林湜、蔡㦛辈同游南雁山。至经正书院,见陈氏肄业甚盛,因题曰‘会文书院’,讲学旬余,有题咏‘穷溪山之胜,极讲论之乐’,一时称胜事云。”
乾隆《平阳县志》记载了朱熹前来平阳,并到南雁山寻访陈经正书院的盛况,但时间弄错了。
据《宋史·朱熹传》载,“会浙东大饥,宰相王淮秦改熹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即日单车就道。”淳熙八年(1181)夏秋之间,浙东一带水灾不断,造成严重的饥荒,而以绍兴府尤烈。同年八月,由宰相王淮荐举,朱熹受命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负责浙东地区的赈灾事宜。朱熹一面上书朝廷,筹备赈灾的钱粮,一面微服私访,了解民情,推行荒政,经常忙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朱熹切实的赈灾举措和其道学人格,使朱学在浙东产生了很大影响,但由于朱熹在浙东劾奏前台州知州唐仲友不法,为唐之姻亲王淮所嫉,浙东任职仅九个月即罢官奉祠。
朱熹在任浙东茶盐提举时,赈灾事务繁忙。而早春二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也是赈灾工作重中之重的时候,恪尽职责的朱熹,怎么可能还好整以暇,腾出大把的时间,带着弟子们到处闲逛,而且还跑到远在浙南的平阳南雁呢?况且在《过盖竹》诗中流露出来的浓郁退意,也不是正在仕途中的朱熹该有的心境。
因此,朱熹来平阳的时间不是在淳熙间,而是十年后的庆元间。
寻访书院 题额“会文”
朱熹到了盖竹,有没有讲学,现在已无从考证。但当时盖竹学风正盛,学子又多,且宋时建有东山书院,因此在盖竹讲学是完全有可能的。
明代宋濂《平阳林氏祠学记》载:“今平阳盖竹之林氏,立祠于始迁之祖之墓而祭之。祠后为斋,曰‘思孝’,以会其族人。复立祠于左偏,祀晦庵朱子之像,以其先宋吏部侍郎拱辰、千之、起鳌及其父阳江君配祀。”根据这段描述,林氏建祠,当中供奉的既不是林氏先祖,也不是孔子,而是朱熹,这说明朱熹对盖竹林家影响之大,由此可以反证,当年朱熹是有在盖竹讲学,其学说一直到明初,还深深地影响着盖竹的林氏学子。
民国水头周喟在《南雁荡山志》中,也引用了宋濂的此文,说:“按,观此及《晦庵集·过盖竹》作二首诗,可为朱子尝至南雁山之证。”
浙江大学硕士何生根先生曾考察浙江各地与朱熹有关的诸多书院,并在2002年发表的《朱熹与浙江书院》一文中说:“与朱熹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书院,后来大多数都立祠祭祀,或供其像于书院。朱熹在书院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这便对书院的内容有较大的影响,祭祀朱熹的书院一定以程朱理学作为主要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便遵循格物致知的路子。比如,乾道年间朱熹曾讲学于乐清县的艺堂书院(后改名为“宗晦”),由咸淳年间邑令郑滁孙改建,聘乡先生胡子实教授。胡便精于“四书”,讲解详明,深契要旨……一些仅仅因为朱熹名声而奉祀他的书院,象元大德二年(1298)建于鄞县的郧山书院,在历经拓新重修后至天历年间,教学内容主要是朱熹的《四书集注》。康熙年间建于杭州的紫阳书院,其学规便乘从“白鹿洞条规”。这些仅因为尊崇朱熹而祀之的书院还有:月湖书院(鄞县)、高节书院(余姚)、敷文书院(杭州)、丹山书院(象山)、东湖书院(鄞县)、丽正书院(金华)、甬东书院(鄞县)、衢讲舍(西安)等等,以上分析足以证明朱熹对浙江书院以至书院教育的广泛影响。”
朱熹到了盖竹做一番停留后,继续前往南雁山,寻访陈经邦、陈经正的书院。清乾隆《平阳县志》载:朱熹与门人陈埴、徐寓、徐容、叶贺孙、钱木之及林湜、蔡㦛等人,“至经正书院,见陈氏肄业甚盛,因题曰‘会文书院’,讲学旬余,有题咏‘穷溪山之胜,极讲论之乐’,一时称胜事云。”
关于“会文书院”,一直以来,都说其又名“会邱书院”。据目前我所看到的文献,最早出自康熙《浙江通志》卷十八载:“会丘书院,在南雁荡,陈经正、经邦读书处,朱文公题额。”其后的清乾隆《平阳县志》卷之三《建置上·学校》载:“会文书院,一名会邱书院,在雁荡山,宋陈经正等读书处,朱文公题额。”这个“一名会邱书院”的说法,应该是沿用《浙江通志》的内容。之所以“丘”成了“邱”,是因为清雍正三年(1725),为避圣讳,上谕除“四书五经”外,凡遇“丘”字,并加“阝”旁为“邱”。光绪《浙江通志》卷二十七中,在转载康熙版《浙江通志》时,便将“会丘书院”作“会邱书院”。
然而,查考康熙之前的地方文献,并不见有“会邱书院”的记载。民国周喟《南雁荡山志》卷三“寺宇”载:“案,陈《志》:“朱熹来游,山门叶群为主人。熹醉笔标题陈经邦书院曰‘会文’,陈端彦书院曰‘棣萼世辉楼’,叶群书院曰‘毓秀’,朱梦良书院曰‘聚英’。”“陈《志》”,即明代嘉靖嘉靖三十六年(1557),邑人陈文源、陈玭编成《南雁荡山志》,文中不见有“会丘”的记载。
周喟《南雁荡山志》卷三“寺宇”中的“会文书院”条目载:“郑《志》:“书院曰会文,曰毓秀,曰聚英,曰聚奎,皆南湖薛氏,盖竹、四溪二林氏共建,今悉废址。”
文中的“郑《志》”,即明末郑思恭的《南雁荡山志》,文中亦不见有“会丘”,但却明确指出,盖竹林氏建有书院。
那么,到底有没有“会丘书院”这个名称呢?
首先,我们说下,在南宋时期,书院有没有可能以“丘”为名。
孔子的名讳,在古代称为“圣人讳”或“圣讳”。在宋朝,孔子被谥为“至圣文宣王。宋徽宗时,曾接连下诏避“圣讳”。
十八世纪中国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一代儒宗”钱大昕(1728—1804)在《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一“避讳改郡县名”条的宋代部分载:“(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避孔子讳,改瑕邱县曰瑕县、龚邱县曰龚县。”钱大昕著述于清乾嘉年间,避圣讳,故书“丘”为“邱”。
为避孔子名讳,宋徽宗先是下诏改了县名,接着又下诏改封孔子弟子曾参等人的爵号。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马端临(1254—1323)在《文献统考·学校五》中记载:“政和元年(1111)六月二十七日,太常寺奉诏:‘孔子高弟子所奉侯爵与宣圣名同,失弟子尊师之礼。今乞以瑕丘侯曾参改封为武城侯,宛丘侯颛孙师为颍川侯,龚丘侯南宫縚为汶阳侯,楚丘侯司马耕为洛阳侯,顿丘侯琴张为阳平侯,瑕丘伯左丘明为中都伯,宫丘伯谷梁赤为洛陵伯,楚丘伯戴圣为考城伯。”
从宋徽宗开始,作为儒家代表的孔子,被列入帝王之列,享受回避名讳的尊荣,由此也开启了后世避孔子讳的先例。之后,从宋代一直到清代,上至天子王侯,下至平民百姓,从书面到口头,无不对这个“丘”字敬而避之。写起来或缺一笔,或写作“某”,或用朱笔圈之,不一而足。
在北宋徽宗时,就已经为避圣人讳,把一个县的名称与原有的孔门高徒封号都给改了,到了南宋时,读孔圣人的读书人书院,怎么可能还会不避圣讳,而直以“丘”命名呢?更何况,陈经邦、陈经正还是程颐的及门高第,深受儒家学说淫浸,并非不知礼数的山野村夫。再说了,即便陈氏不懂规矩,那作为一代儒宗的朱熹,又怎么可能会直书孔圣人名讳的呢?
况且“会文”二字,是有出处的,即《论语·颜渊》中的“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而“会丘”二字,笔者遍翻诸家经典,却是怎么都找不到出处。
因此,笔者大胆推测,“会丘书院”在历史上并不存在,鲁鱼亥豕,误“文”为“丘”,纯属康熙《浙江通志》误记。而后世不辨所以,以讹传讹,以致谬误至今。
旬馀讲学 当在乐溪
距盖竹不到二十里的乐溪(今鹤溪),为陈经邦、陈经正的故里。在宋代时,鳌江潮水可以一直涨到乐溪外垟,今当地还有埠头遗址,可见当年水路交通还是很方便的。
在今水头镇鹤溪社区元底村,还有俗称“陈氏老厝基”的陈氏故居遗址,当年的石砌围墙,有一大段还保存完好。
据宋许景衡《横塘集》中记载:陈“家多资”,这从陈家能让陈经邦、陈经正二兄弟及其从弟经德、经郛能不远千里赴汴京(今河南开封)入太学读书,可知其家境之殷实。
北宋崇宁三年(1104)春,陈经邦在乐溪家居时,曾写了一篇《会文阁记》:“邦自龆龄读书,晚而不倦。虽识见不及于前时,而嗜好有甚于初心,孜孜矻矻,废食忘寝,殆若狂然。家人僮仆皆以痴目之,不自知其为癖也。又如是而益甚,而家人益之以厌。于是谋于家居之前创为书阁,且欲远于家务,庶免家人之所讥议。阁告成,尝试以‘会文’名之。而又凿沼于其前,开圃于其侧,环山屏列乎左右,带水萦绕乎东西。”
陈经邦、经正兄弟的读书处是“会文阁”,这是没有疑问的。到了南宋庆元五年(1199),还不到百年,陈氏后裔在陈氏祖居前的会文阁中继续读书,这是很正常的。因此据乾隆《平阳县志》载,当朱熹与门人陈埴、徐㝢、徐容、叶贺孙、钱木之及林湜、蔡㦛等人寻访的“经正书院”,应该就是“会文阁”旧址。而朱熹“见陈氏肄业甚盛”,“因题曰‘会文书院’”,也就是顺理成章了。讲学旬余,有题咏‘穷溪山之胜,极讲论之乐’,一时称胜事云。”
而据更早的明嘉靖年间编纂的《南雁荡山志》载:“朱熹来游……醉笔标题陈经邦书院曰‘会文’。”也可知,所谓的“陈经邦书院”,应该就是当年的“会文阁”。
如今在南雁荡山东洞华表峰下的会文书院,一向都说是陈经邦、陈经正兄弟读书处。但笔者经过考证,认为该观点有误,陈氏兄弟的读书处应该在其家乡乐溪。
文中明明白白地写道,会文书阁位“家居之前”。即今天的水头镇鹤溪社区的元底村,在当地,还有陈氏故居的旧日址,元底的地形,与陈经邦《会文阁记》文中所描绘的地形一致。位于峡谷之中,南北两侧都是山峦,峡谷中有两条小溪蜿蜒如带,在陈经邦故居前不远处汇合后,再自西向东流出峡谷。陈经邦是在“家居之前创为书阁”的,并在其前开凿池塘迎溪水入内,正是“环山屏列乎左右,带水萦绕乎东西”的情形。
而如今南雁荡山中的会文书院,处于华表峰下东洞之中,场地逼仄,地势陡峭,古时没有开凿铺设石阶之前崎岖难行,怎么可能会有人居住呢?又从何谈起建于“家居之前”呢?况且建筑物下是岩石,在古代条件简陋的情形下,不可能专门费尽心力开凿池塘,更不可能有“带水萦绕乎东西”的景观。纵览明代方鹏、蔡芳、陈玭比、郑思恭和清代潘耒等人的南雁荡山游记,于东西洞景区风景状摹甚详,但独独没有提及东洞曾有过会文书院,清康熙年间的施元孚在专门描写东洞的《仙甑岩记》中,也只字不提书院。
而在明清之前的元代,著名学者史伯璿(1299-1354)还专程前往瞻仰会文书院旧址,并写了《过陈氏会文书院》诗:“上映棂星下碧溪,群英冠学古今稀。经书世系番山舍,科第家传入荆闱。恩渥九重濡雁荡,文光万丈烛牛墟。门楣底事荒凉易,枯壁寒蝉噪落晖。”如果该书院果真在南雁东洞,那么明清两代前往南雁游览的后学不可能不会去拜谒遗址,更不可能一字不提,可见陈氏的会文书院并非在南雁,更非在东洞之中。
关于沿袭至今的“南雁会文书院是陈氏兄弟读书处”的说法,在刘绍宽的民国《平阳县志》中对于陈经邦的书阁“会文阁”也有考证:“……则会文阁宜在乐溪矣,旧日志云在浦源,今其地相传犹存遗址,盖后人因南雁山会文书院而附会为之。”而周喟在其《南雁荡山志》中也考证道:“……则会文阁在乐溪无疑。旧志云在浦源,本于谱牒附会,不足信云。”
综上所述,陈经邦的读书处“会文阁”是乐溪,在清末重建于南雁华表峰下的会文书院和棣萼世辉楼都并非是陈氏兄弟的读书处,至于为什么后来在乾隆《平阳县志》中会将陈氏兄弟的读书处附会到南雁,估计是平阳后学曾在南雁华表峰下建有会文书院,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永嘉诸生林必锦在《游南雁荡记》中就有“入石门楼,昔日会文遗址犹在”的文字,清乾隆年间,平阳教谕卢镐来游南雁,亦有《穿东洞,寻会文书院遗址,……》的诗作。
而清嘉庆五年(1800)江苏常州人秦鸣雷来游南雁时,更是产生“云是会文书院遗址,南宋时有陈氏子孙读书其中,朱子尝往访之”的误会,这是因为陈经邦、陈经正都写过《雁荡山》诗,都曾在南雁活动过,后人混为一谈,产生误解,也是人之常情。
此处所谓的会文书院,尽管清光绪八年(1882)陈少文等人予以重建,但素以考据严谨的刘绍宽在民国《平阳县志·古迹志》并未列入。列入的是“旧传宋陈经邦、经正、经一、经德、经郛,孙元普、元胜,曾孙永起读书处”的棣萼世辉楼,而且也通过考证予以了否定:“据《青华集·下涝陈氏十咏诗序》云‘雁山辉萼院始于良翰诸昆,继于端彦诸子’,是初不以辉萼为经正兄弟读书处也……旧志(指乾隆《平阳县志》)载陶亮器诗:‘罗列奇峰插太虚,研覃经义寄山居。联芳棣萼真堪羡,伊洛渊源咫尺馀。’亦修雁志者所伪撰,此条本从删削,惟因旧说相沿已久,删去转以滋疑,故为载,而辨之如此。”
在古代,人们所说的南雁荡山范围要比现在的大的多,从钱仓的凤山开始,山脉绵延至顺溪,都是南雁荡山的景区。如今的荆溪山一带,还有“南雁门”之说。而有华盖峰、醉翁岩、龙湫等形胜的盖竹,以及乐溪一带山水,都是旧时南雁荡山的范围之内。
一直到民国周喟的《南雁荡山志》中,盖竹与乐溪还是作为“别巘”列入的,意思是南雁荡山的别枝。
朱熹当年来平阳,过盖竹,至乐溪,讲学旬馀,完全也可以说是“游南雁山”。这时的朱熹,毕竟已经是七十岁高龄的老人了,且患足疾,连陪同他的弟子林湜也是差不多年龄的老人。虽然乾隆《平阳县志》记载“有题咏‘穷溪山之胜,极讲论之乐’,一时称胜事云”。但朱熹并没有深入当时还算蛮荒的南雁荡山东西洞景区,所谓“溪山之胜”,也只是盖竹与乐溪一带的山水风光而已。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以朱熹的水平,到了真正的南雁荡山核心景区,饱览美景,不可能无诗记录的。而有诗的话,以当年已名满天下的他,也是不可能失载的。
在《全宋诗》卷三〇〇九中,有辑自清曾唯《东瓯诗存》卷八的陈埴的《南雁山》诗,此诗亦见于历代《南雁荡山志》:
千峰历罢寄山窗,酒力诗狂总未降。月白洞门花落尽,天空华表鹤飞双。崖边瀑雪寒侵梦,涧底笙箫冷韵腔。且喜懒残煨芋熟,不妨久话共秋釭。
陈埴(1176—1232),温州永嘉人,字器之,号木钟。宋宁宗嘉定间(1208—1224)进士。少师叶适,后从朱熹游。为明道书院干官兼山长,从学者甚众,称潜室先生。历任丰城主簿、湖口县丞等职,以通直郎致仕。有《木钟集》十一卷存世。而诗,就仅有《南雁山》一首存世。
明嘉靖《南雁荡山志》中,记载有“朱熹来游,山门叶群为主人”。巧的是,而在民国《南雁荡山志》中,就记载有叶群的一首诗,录自《东瓯诗存》:
石门深窅锁丹霞,倚马西风日欲斜。幽境已无尘俗气,白云尚有翠微家。林间摘句书红叶,涧底烹泉带落花。向晚且从西洞息,碧山明月正堪赊。
叶群,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辛未科进士,任剑浦主簿。叶群的生卒失考,但根据其考中进士的时间,在朱熹来游南雁时,叶群起码也已是古稀老人了,鼓动大家去游南雁东西洞的可能性,估计也不大了。不过,叶群在热情招待朱熹等人时,对南雁核心景区风光的描述,肯定是能激发陈埴的游兴的。
陈埴当时陪同朱熹来游南雁时,正值二十多岁的青年。年轻人普遍好玩,所以完全可能在朱熹讲学的过程抽空去游览一番名胜的。至于叶群是否有陪同或派人陈埴前往南雁,或者在不久之后,陈埴又自己重新来游南雁,现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从陈埴的诗中的“山窗”“洞门”“华表”等景物描写,可知他是去了南雁荡山核心的东西洞景区的。而从诗中“花落尽”“共秋缸”的描述来看,不像是写于早春二月的,所以是日后再来游览的可能性更大。毕竟陈埴是温州永嘉人,离南雁荡山还是不算远的。
倒是林湜有一首《游南雁荡山》,见于历代《南雁荡山志》,很是值得玩味。诗云:“养静山僧卓锡随,跻攀绝顶共寻奇。鸟歌花笑如曾识,天霁风清似有期。乾洞夜明通日月,灵湫春暖起云霓。投簪归老还忧国,药径前头采紫芝。”从“灵湫春暖”的描述来看,此诗写于春天,而“投簪”比喻弃官,陪朱熹前来盖竹的林湜时年六十八岁,已经致仕,告老还乡,而当时宋朝“党禁”正严,林湜心忧国事,的确是“投簪归老还忧国”。
为此,笔者大胆推测,林湜此诗便是写于陪同朱熹来盖竹之时,因为盖竹位于南雁荡山景区范围,完全可以署题《游南雁荡山》。因为盖竹有始建于唐乾宁间的东山院,游览时有“山僧卓锡随”;有龙湫,即诗中的“灵湫”;有见于元代张天英《游盖竹山》的“晓洞”,即诗中的“乾洞”,至于“药径”,并非实指如今南雁东西洞景区的采药径,而是虚指,自古以来,诗人作品中关于“药径”的描写也是很多的,如南宋温州人赵师秀就有《采药径》诗:“十载仙家采药心,春风过了得幽寻。如今纵有相逢处,不是桃花是绿阴。”
北上瑞安 再访故人
朱熹离开平阳后,再次北上,到瑞安仙岩走访同属南宋著名学者的好友陈傅良。
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号止斋,学者称止斋先生,卒谥文节,瑞安湗村(今属瑞安市塘下镇罗凤街道)人。乾道八年(1172)进士,官至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兼集英殿修撰。陈傅良在湖南任职时主讲岳麓书院,门墙极盛。陈傅良,是永嘉学派的学术巨擘,为学主张“经世致用”,反对性理空谈。南宋光宗皇帝曾给陈傅良赐联:“东瓯理学无双士;南宋文章第一家。”高度评价陈傅良的成就。
绍熙五年(1194)冬,赵汝愚与韩侂胄争权而失势,因争权时赵汝愚曾引朱熹“道学”集团以自助,侂胄得势后就进行报复,打算斥逐朱熹。据《宋史·陈傅良传》载:“会诏朱熹与在外宫观,傅良言:‘熹难进易退,内批之下,举朝惊愕,臣不敢书行。’”在当时这种形势对朱熹极其不利的情况下,陈傅良出于公心,对宁宗说:朱熹做官前要再三考虑,去官时唯恐不速,根本不是贪念功名的人,而是一位真正爱国爱民的人。如果连他这样的都要罢官,一旦圣旨颁发后,满朝大臣都会失色,臣不敢草拟诏书。”这事使傅良以“依托朱熹”的罪名受到参劾,又被罢官。从此,他一心韬晦,闭门静居,称自己的居室为“止斋”。而韩侂胄进而发动“庆元党禁”,指控朱熹的道学为“伪学”,把陈傅良、叶适、蔡幼学等温州学者一并列入“伪学”名单。
陈傅良罢官回乡后,创办仙岩书院,招生收徒,传授“经世致用”思想。一直到嘉泰二年(1202)才得以复官。朱熹来平阳时,陈傅良正在仙岩书院。
朱熹到仙岩书院访问陈傅良期间,曾书“溪山第一”、“开天气象”,以赞誉仙岩山水人文。
当时,被罢官的叶适也在温州家中赋闲。
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居士。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世称水心先生。卒谥“文定”(一作忠定),故又称“叶文定”“叶忠定”。
据张义德《叶适评传·附录·叶适年谱》载:庆元三年(1197),叶适为御史胡纮所劾,降两官后罢职,主管冲佑观,差知衢州,叶适推辞,由镇江归永嘉。
庆元五年(1199)春,朱熹来访陈傅良时,叶适也正家居。据说,朱熹到温州后还曾与叶适会晤。
不久,朱熹旧疾复发,遂结束了浙南之行,返道回长溪,从罗浮乘舟经福州回建阳。之后,被各种疾病所困扰的朱熹,预感到死亡的逼近,更加抓紧著述。
庆元六年(1200)入春以后,朱熹足疾大发,病情恶化,生命垂危,左眼已瞎,右眼也几乎完全失明。朱熹却以更旺盛的精力加紧整理残篇,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将自己生平的所有著作全部完稿,使道统后继有人。三月初九,朱熹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嘉泰二年(1202),也就是朱熹去世两年之后,大规模禁锢道学的“庆元党禁”运动宣告结束。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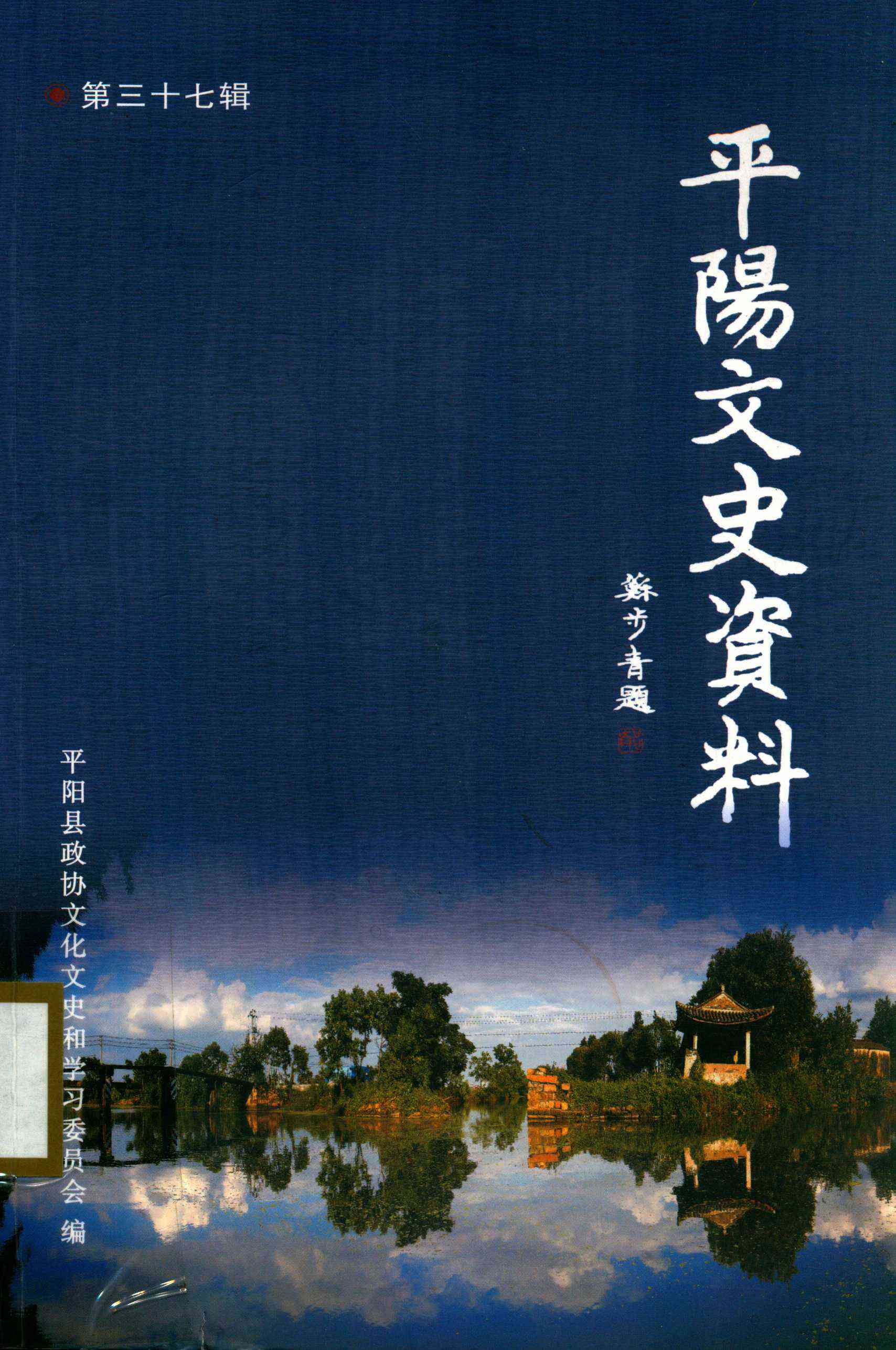
相关地名
平阳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