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寨头山开始教书
| 内容出处: | 《平阳文史资料第三十六辑》 图书 |
| 唯一号: | 113520020230001295 |
| 颗粒名称: | 在寨头山开始教书 |
| 分类号: | K825.46 |
| 页数: | 5 |
| 页码: | 208-212 |
| 摘要: | 本文主要讲述了作者宋文骥在1963年被老同学冯一天请去代课,从而开始了他在寨头山小学的教学生涯。他面对艰苦的环境和条件,却凭借自己的智慧和热情,创新地开办了牧牛班、午班、傍晚班等多样化的教学模式,使得学龄儿童的普及率达到了百分百。他的教学方法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认可和赞扬,甚至引起了省文化厅和省越剧团的关注。然而,由于他的家庭出身问题,最终未能获得省教育战线的标兵称号。尽管如此,他仍然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工作中,为当地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
| 关键词: | 平阳县 寨头山 教书 |
内容
日历翻到1963年1月,人们还沉浸在淡淡的春节氛围中,同乡的老同学冯一天找到了我。
“请帮个忙,我要去外地办件事,需要几天时间,麻烦你代几天课好吗?”
正处在“求三哥拜四嫂”,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加上个人感情上的事,我已经是筋疲力尽,此时不要说代几天课,就是一天也答应。一手提着一网袋的衣服、日用品,一肩背着一袋米,跟着老同学走了。
出县城西门,沿着一条小路,过雅山到南岙山脚。眼前是一座高高的山,开始几步还轻松,慢慢地脚越来越沉,大约过半岭到一株小枫树时,实在走不动了,疲乏惫地坐了下来。休息了一会儿,一抬头,一条约60度的峻岭好似挂在面前。走,这第一步就走不出去,往后从何谈起?总算年轻,不管汗水已湿透衣裤,继续喘着粗气一步步上去,好容易翻过山脊岭背,山的另一面又一条峻岭直挂下去,往下一望,一大片山谷里清晰地看到四个小村落。
翻山越岭后,沿着只容一个人走的羊肠小山路,到了一处叫溪沽塘的茅草屋里。茅屋正中三小间,两边各有边厢,进出的房门不到一米六高。屋里住着两代四个人,是叔公一对和过继侄儿一对。我被安排在左边泥地的边厢。
农历正月,时值寒冬,在这么个盆地似的山谷茅草房里,也不觉十分寒冷。不过上“同吃”这件事上,有点小麻烦。房东一年到头吃的全是番薯丝,我带的是大米,每餐她们把大米放进一些,一开锅,那白米饭就像黄色大沙漠中的一串珍珠,发出诱人的光,我总不能伸手把这些珍珠挖过来,自己享受吧。好吧,同住一茅屋下,同甘共苦,慢慢地我也习惯吃番薯丝饭了。
吃住安下来,那就开始我这一生的粉笔生涯了。
这座山叫寨头山,又名高昇大队,属城西公社。据说从前立过寨的,看来有可能,这山最高点朝县城一面,至今还有石头砌的寨门,有一块操练场。盘山中的山坡上有一单间小庙,叫寨头庙,寨头小学(又名城西公社高昇小学)就办在这庙里。
我进山时,寨头山只有43户农家,全村总人口207人,有32名学龄儿童。接教不久,得知冯原来另谋高就,到一个剧团任后台琴师一职了,他这一走,估计就再也不回这穷山僻壤的村校了。我这一生从教事业,也就这样阴差阳错地从这寨头山开始了。
刚来的这学期,就被朴实热情的山上农民喜欢,经过半年的相处磨合,我也逐渐溶入他们当中去了。十几年求学得来的知识,想不到在这一穷二白的山岙中,不是大材小用,而是大有用场了。再加上那年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运动,人们做好事的积极性有所调动起来。随处看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等的标语口号。
第二个学期时,根据山上学龄儿童的生活作息规律,我不知哪来的脑筋,在没有样板,没有上级指示的情况下,竟大胆地进行创新改革,把它分成牧牛班、午班、傍晚班和夜校。我一人既是校长,又是教师、工友,并且语、数、音、体、美一身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很适应小山村办学方式,后来慢慢地把它称之为“耕读小学”,又名“一揽子小学”。
山上有一半多家庭养有牛、羊、猪或鹅鸭等家畜家禽,早上和午后部分孩子要放牛,我拿着小黑板,跟随着这班背着书包的放牛娃,在坟坦、草坪上课,这就叫“牧牛班。”
部分女孩子要帮助家里割猪草或其他家务事,我就利用中午这段休息时间,让七八个女孩在一户家里识字,学语文、数学,这就叫“午班。”
还有几个孩子因家庭特殊情况,只有傍晚时间空闲在家,老师就送书上门教读,这也就叫“傍晚班”了。
这些班现在看来,几乎不可思议,象解放初期农民扫盲班一样,根本不像什么学校,但很切合当时山上的实际情况。我开始也曾想把学龄儿童全部集中庙内教室,正规上课,但每天到课率很低,不知道自己当时哪来的思路和劲头,办起了这样形式多样教学模式,有教无类,连续几年,学龄儿童普及率达到百分百。
不久,这事被教育当局领导知道了,当时区教育组尤某某、王某某,县教育局余某某和局长林某某,温州市教育局及省教育厅教研组四位老师,都先后翻山越岭,来到学校跟班听课,几天蹲点下来采访师生,谈体会,写总结。1965年初,省文化厅彭兆启先生、省越剧团编导曾昭弘先生都来采访过。那年我几乎成为全县教育界红人,事后据说原打算把我树立省教育战线标兵,后来鉴于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领导慎重考虑,最后否定了。
谢天谢地,如果当时真给了我县或省标兵、模范之类称号,那后面紧跟而来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不知会遭受什么样灾难,必定当作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活靶子打了。那能否继续教书,能否完成今日这本自传,都是一个未知数。相信民间谚语中所包含的哲理:“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头瓦椽先烂。”
不过话说回来,我那三年寨山教书,说句良心话,我实在是全身心地扑在教育工作上的,白天教了那一揽子的班,使每学期的学龄儿童均能普及,小学三个年级的全日制课程也照样完成,各级领导来校抽查学生学业成绩都能合格。
偏僻小山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根本没有一丁点儿的文体活动,只有串门成为山上唯一的活动项目。后来几个青年自发组团,请来乱弹班师傅教唱,一是想改变一下山寨的气氛,另外也准备日后去别人家红白喜事演奏,赚点红包。但是没有点功底,不能一学就会,结果半途而废了。何以给沉寂的寨山增添点活力呢?作为新来的寨山人,我也在动脑筋了。
除了周日,其余六天夜以继日地工作,是我当时工作状况。为了活跃山村文化娱乐活动,当夜幕降临时,我手拿扫盲课本、一把胡琴、几盏油灯(像今日饮料瓶,腰间伸出三支内放灯芯的细管,名曰三盏头),带着两个小年青,一个叫阿栋,一个叫阿光,站在寨山制高点,向着山的两边山坳六个村落吹响六声哨子。真灵,不一会儿各条羊肠山路上出现了一个个青壮年,向着小庙教室汇拢过来。
上山创办夜校以来,人气挺旺,每晚读书读报,教唱革命歌曲,《红灯记》的“提篮小卖———”,人人会唱上几句。还成立了高昇俱乐部,我编写了好多快板、莲花、三句半及用温州话演唱的瓯剧。根据山上一个好后生周生娒的不怕脏不怕苦,为集体跳进粪坑干活事迹,我编写个小剧本,到县城大会堂演出,博得了好评。
寨山不再沉寂了,自这土法上马,土话说唱,土里土气开展草根文艺活动后,山寨老庙几乎成了这小山村的文化中心,成了寨山“星光大道”、“文化礼堂”,那四年悠扬歌声和朗朗读书声飘荡在整个寨头山上空。
四年的寨山教育工作,也伴随着不少痛苦的过程。白天教孩子,晚上教夜校,还要辅导俱乐部。当忙完每天工作时,很想上床睡个安稳觉,可是我睡的这泥地房里,真是跳蚤成群。一进房内,两脚上不是爬上一两只,而是排着队似的直往身上钻,而使你不是用手指头去捻它,而是用两手掌从膝盖往下一拨拨往下。
上床睡时,只好穿上长裤和长袖衣,把四个口子用纱带紧紧地扎牢,然而小家伙还是无孔不入。惹得你无法入睡,真是件痛苦事,曾用农药”六六六”在床底及草席下散了一层,小黑魔虽少了,但农药气味又让你难眠。
只要你用心,真诚,努力地干着,祖祖辈辈生长在这闭塞山村里的农民兄弟,会把你当成自己亲人。每年地瓜熟了,杨梅红了,我的茅草房里,会堆满了他们送过来这些带着浓情深意的土特产。
“请帮个忙,我要去外地办件事,需要几天时间,麻烦你代几天课好吗?”
正处在“求三哥拜四嫂”,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加上个人感情上的事,我已经是筋疲力尽,此时不要说代几天课,就是一天也答应。一手提着一网袋的衣服、日用品,一肩背着一袋米,跟着老同学走了。
出县城西门,沿着一条小路,过雅山到南岙山脚。眼前是一座高高的山,开始几步还轻松,慢慢地脚越来越沉,大约过半岭到一株小枫树时,实在走不动了,疲乏惫地坐了下来。休息了一会儿,一抬头,一条约60度的峻岭好似挂在面前。走,这第一步就走不出去,往后从何谈起?总算年轻,不管汗水已湿透衣裤,继续喘着粗气一步步上去,好容易翻过山脊岭背,山的另一面又一条峻岭直挂下去,往下一望,一大片山谷里清晰地看到四个小村落。
翻山越岭后,沿着只容一个人走的羊肠小山路,到了一处叫溪沽塘的茅草屋里。茅屋正中三小间,两边各有边厢,进出的房门不到一米六高。屋里住着两代四个人,是叔公一对和过继侄儿一对。我被安排在左边泥地的边厢。
农历正月,时值寒冬,在这么个盆地似的山谷茅草房里,也不觉十分寒冷。不过上“同吃”这件事上,有点小麻烦。房东一年到头吃的全是番薯丝,我带的是大米,每餐她们把大米放进一些,一开锅,那白米饭就像黄色大沙漠中的一串珍珠,发出诱人的光,我总不能伸手把这些珍珠挖过来,自己享受吧。好吧,同住一茅屋下,同甘共苦,慢慢地我也习惯吃番薯丝饭了。
吃住安下来,那就开始我这一生的粉笔生涯了。
这座山叫寨头山,又名高昇大队,属城西公社。据说从前立过寨的,看来有可能,这山最高点朝县城一面,至今还有石头砌的寨门,有一块操练场。盘山中的山坡上有一单间小庙,叫寨头庙,寨头小学(又名城西公社高昇小学)就办在这庙里。
我进山时,寨头山只有43户农家,全村总人口207人,有32名学龄儿童。接教不久,得知冯原来另谋高就,到一个剧团任后台琴师一职了,他这一走,估计就再也不回这穷山僻壤的村校了。我这一生从教事业,也就这样阴差阳错地从这寨头山开始了。
刚来的这学期,就被朴实热情的山上农民喜欢,经过半年的相处磨合,我也逐渐溶入他们当中去了。十几年求学得来的知识,想不到在这一穷二白的山岙中,不是大材小用,而是大有用场了。再加上那年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运动,人们做好事的积极性有所调动起来。随处看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等的标语口号。
第二个学期时,根据山上学龄儿童的生活作息规律,我不知哪来的脑筋,在没有样板,没有上级指示的情况下,竟大胆地进行创新改革,把它分成牧牛班、午班、傍晚班和夜校。我一人既是校长,又是教师、工友,并且语、数、音、体、美一身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很适应小山村办学方式,后来慢慢地把它称之为“耕读小学”,又名“一揽子小学”。
山上有一半多家庭养有牛、羊、猪或鹅鸭等家畜家禽,早上和午后部分孩子要放牛,我拿着小黑板,跟随着这班背着书包的放牛娃,在坟坦、草坪上课,这就叫“牧牛班。”
部分女孩子要帮助家里割猪草或其他家务事,我就利用中午这段休息时间,让七八个女孩在一户家里识字,学语文、数学,这就叫“午班。”
还有几个孩子因家庭特殊情况,只有傍晚时间空闲在家,老师就送书上门教读,这也就叫“傍晚班”了。
这些班现在看来,几乎不可思议,象解放初期农民扫盲班一样,根本不像什么学校,但很切合当时山上的实际情况。我开始也曾想把学龄儿童全部集中庙内教室,正规上课,但每天到课率很低,不知道自己当时哪来的思路和劲头,办起了这样形式多样教学模式,有教无类,连续几年,学龄儿童普及率达到百分百。
不久,这事被教育当局领导知道了,当时区教育组尤某某、王某某,县教育局余某某和局长林某某,温州市教育局及省教育厅教研组四位老师,都先后翻山越岭,来到学校跟班听课,几天蹲点下来采访师生,谈体会,写总结。1965年初,省文化厅彭兆启先生、省越剧团编导曾昭弘先生都来采访过。那年我几乎成为全县教育界红人,事后据说原打算把我树立省教育战线标兵,后来鉴于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领导慎重考虑,最后否定了。
谢天谢地,如果当时真给了我县或省标兵、模范之类称号,那后面紧跟而来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我不知会遭受什么样灾难,必定当作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活靶子打了。那能否继续教书,能否完成今日这本自传,都是一个未知数。相信民间谚语中所包含的哲理:“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头瓦椽先烂。”
不过话说回来,我那三年寨山教书,说句良心话,我实在是全身心地扑在教育工作上的,白天教了那一揽子的班,使每学期的学龄儿童均能普及,小学三个年级的全日制课程也照样完成,各级领导来校抽查学生学业成绩都能合格。
偏僻小山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根本没有一丁点儿的文体活动,只有串门成为山上唯一的活动项目。后来几个青年自发组团,请来乱弹班师傅教唱,一是想改变一下山寨的气氛,另外也准备日后去别人家红白喜事演奏,赚点红包。但是没有点功底,不能一学就会,结果半途而废了。何以给沉寂的寨山增添点活力呢?作为新来的寨山人,我也在动脑筋了。
除了周日,其余六天夜以继日地工作,是我当时工作状况。为了活跃山村文化娱乐活动,当夜幕降临时,我手拿扫盲课本、一把胡琴、几盏油灯(像今日饮料瓶,腰间伸出三支内放灯芯的细管,名曰三盏头),带着两个小年青,一个叫阿栋,一个叫阿光,站在寨山制高点,向着山的两边山坳六个村落吹响六声哨子。真灵,不一会儿各条羊肠山路上出现了一个个青壮年,向着小庙教室汇拢过来。
上山创办夜校以来,人气挺旺,每晚读书读报,教唱革命歌曲,《红灯记》的“提篮小卖———”,人人会唱上几句。还成立了高昇俱乐部,我编写了好多快板、莲花、三句半及用温州话演唱的瓯剧。根据山上一个好后生周生娒的不怕脏不怕苦,为集体跳进粪坑干活事迹,我编写个小剧本,到县城大会堂演出,博得了好评。
寨山不再沉寂了,自这土法上马,土话说唱,土里土气开展草根文艺活动后,山寨老庙几乎成了这小山村的文化中心,成了寨山“星光大道”、“文化礼堂”,那四年悠扬歌声和朗朗读书声飘荡在整个寨头山上空。
四年的寨山教育工作,也伴随着不少痛苦的过程。白天教孩子,晚上教夜校,还要辅导俱乐部。当忙完每天工作时,很想上床睡个安稳觉,可是我睡的这泥地房里,真是跳蚤成群。一进房内,两脚上不是爬上一两只,而是排着队似的直往身上钻,而使你不是用手指头去捻它,而是用两手掌从膝盖往下一拨拨往下。
上床睡时,只好穿上长裤和长袖衣,把四个口子用纱带紧紧地扎牢,然而小家伙还是无孔不入。惹得你无法入睡,真是件痛苦事,曾用农药”六六六”在床底及草席下散了一层,小黑魔虽少了,但农药气味又让你难眠。
只要你用心,真诚,努力地干着,祖祖辈辈生长在这闭塞山村里的农民兄弟,会把你当成自己亲人。每年地瓜熟了,杨梅红了,我的茅草房里,会堆满了他们送过来这些带着浓情深意的土特产。
知识出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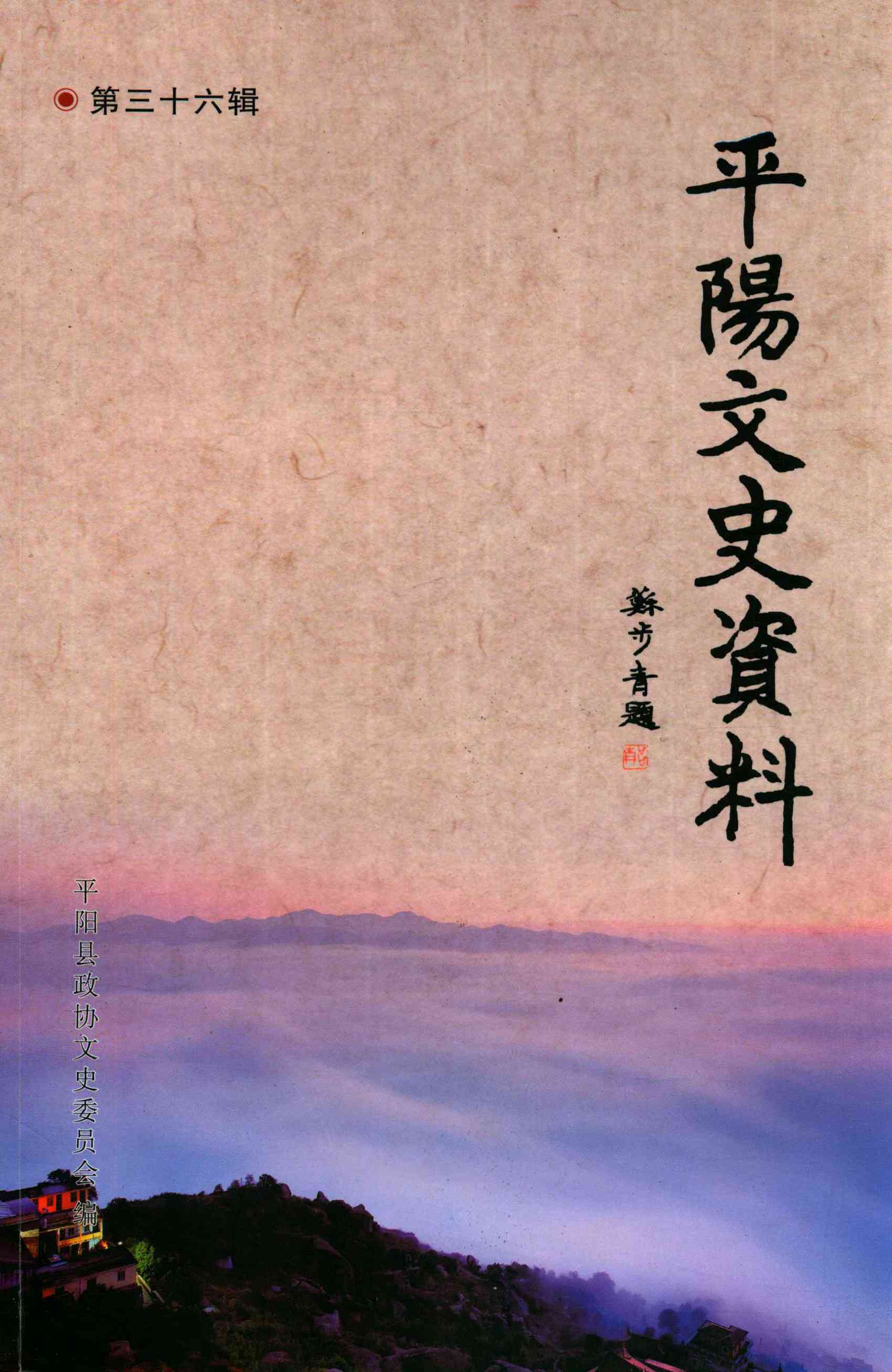
《平阳文史资料第三十六辑》
本书收录了《亲历县新华书店的改革与发展》《与时俱进的平阳县档案馆》《改革开放后的平阳县金融业》《砥砺前行的平阳中学》《追记周干先生与地方文献整理》《难忘蒋仲飞先生》《向高僧木鱼师“取经”》等文章。
阅读
相关人物
宋文骥
责任者
相关地名
平阳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