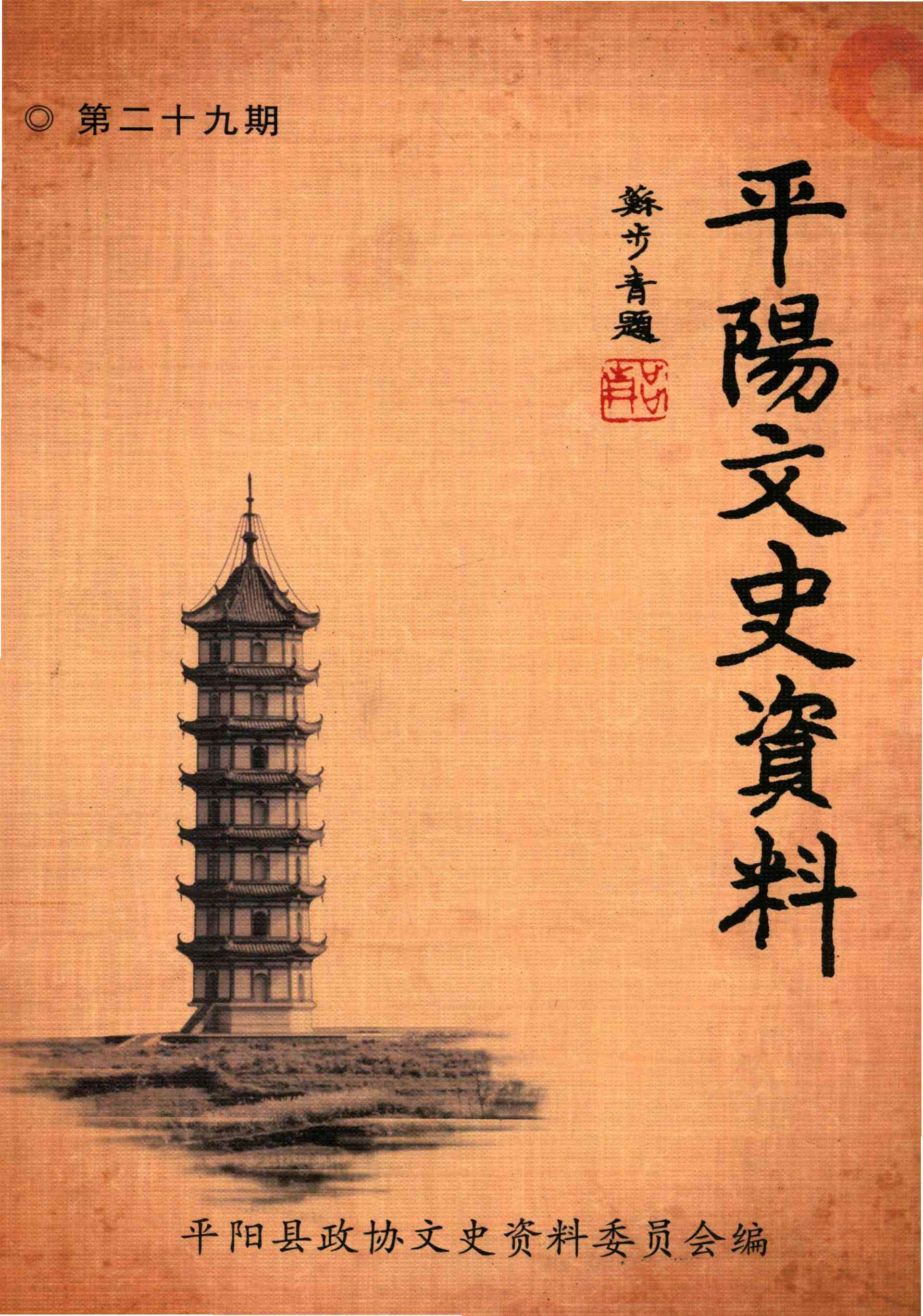内容
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件大事。它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一次规模巨大的革命运动。虽然由于它的领导阶级——资产阶级的软弱、动摇、妥协,不敢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结果只能是迫使清帝退位,换了朝代而已,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没有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幸福。但是,它毕竟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创建了中华民国,功绩还是不可磨灭的。
辛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公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久已积压的对满清政府的腐败,卖国和残酷压迫、剥削的民族仇恨和阶级仇恨就像火山一般爆发出来。仅短短的两个月内,东南各省就纷纷响应,驱除满清官吏,收缴满营枪械,竖起义旗,宣布光复。浙江是革命志士秋瑾、徐锡麟等人的故乡。他们撒下的革命火种愈烧愈旺。武昌起义后,浙江光复会和在浙江的同盟会会员就奔走呼号,密谋响应。上海同盟会支部派姚勇忱、王金发等人陆续来到杭州,联络军警商绅各界人士,于九月十四日夜,发动了两标军队攻陷抚署,巡抚增韫被获,一夜之间就光复了杭州,推翻了二百多年来统治浙江的清王朝的政权。次日,杭州各界公举唐寿潜为浙江都督,周承菼为浙军司令官,建立军政府。全市户悬白旗,居民袖缠白布,表示山河光复。并通电全省各府属设立军政分府,组织新政权,速办民团自卫。其间,曾因满营佐领贵馥还想负隅顽抗,几经劝降不从,人心浮动,后终于将他拿获,执行枪决。满营问题顺利解决之后,局势才稳定下来。
在温州,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就有人得到了消息,街头巷尾很快出现了庆祝胜利的传单,接着有学生上街游行,人心振奋。清政府恐“谣传”生事,贴出告示,诈称“已接官军得胜之电”,企图皆宜安定人心。九月十一日,风声日紧,商会倡议要筹办民团,招募团勇,借以自卫,各业分认负担。温处道太守李前潘、道台郭则沄则焦急万分,惶惶不可终日。十六日,收到省城光复的电报,各界闻讯纷纷要求有所行动。原温州防营统领梅占魁初想反抗,后经各界婉言相劝,才表示顺从潮流。十八日,原道府及其他一些满清官员都全家逃走,各界公推梅统领为司令部长,主持军政,将温府署改为军政分府署,挂起了白旗,贴出来告示,宣告光复。接着携刻军政分府署关防,推举各部办事人员,并决定温属五县各举地方士绅二人参加军政分府,驻温办事。当时平阳士绅黄秋士(即黄实,平阳宜山人,是同盟会早期会员,后曾代陈其美写过讨袁通电)和姜啸樵(即姜会明,已酉年拔贡,后于民国七年任省二届议会副议长)二人正在温州,就作为平阳士绅代表,参加军政分府的办事机构。一时间,一般新旧士绅,地方豪强,文人学子纷纷出笼,争权夺利,互相攻击,匿名文告贴满街巷,甚至大打出手,以致二十四日军政分府贴出的官员名单的榜文,当晚就被撕毁收回。二十九日,原光绪癸未年进士、曾任陕西道、江西道、山东道监察御史的徐班候回温,为各界公推请暂摄都督之职(后经省都督汤寿潜正式任命),重新委派各部办事人员,出示平定米价,废除厘捐,劝市民剪辫,并擒获纵火抢劫的积匪王言昌,处以死刑,温州的秩序基本稳定下来了。
平阳地处浙南边陲,一向有反清斗争的革命传统。如腾蛟的白承恩曾在太平天国后期率领家乡子弟兵,追随侍王李进贤转战南北,打击清兵和地主武装,立下赫赫战功;又如钱仓的赵起、蔡华等人发动的金钱会起义,曾经一度攻占温州府城,在浙南大地留下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辛亥革命前夕,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浙江光复会的创始人陶成和龚宝铨、陈大齐等三人曾应鳌江人陈竞生之请,一起从日本来到鳌江小成学院任教算术、英文、体操、史地等新课章程,进行过短暂的革命活动,即离开平阳。至于一些老光复会和以后的老同盟会会员,如黄实、殷汝骊、陈华、陈蔚、游寿宸等人,他们的活动都不在平阳。看来,辛亥年的平阳由于没有革命党人的组织领导和发动群众,缺乏舆论准备,而辛亥革命是从上而下突然来的,所以一群群众对革命并不理解。再加上这一年温处各地遭受特大自然灾害,六月底,平阳连刮台风,早稻已经受损,到七月初三,大风大雨连连袭击,至十三日才稍停,平地已水深丈余,许多地方房塌田毁,晚稻颗粒无收,都说是咸丰三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灾害。因此,谷米价格飞涨,米铺关门停业,饥民成群结队,时有捣毁米铺,哄抢大户的事件发生,对辛亥革命一般老百姓并不关心,他们只希望能顺利度过灾荒就是万幸。“革命”就只能成为地方士绅、殷富之家争权夺利的事了。就像鲁迅在《阿Q正传》里所描述的那样,未庄的“革命”是赵太爷和假洋鬼子们的“专利品”。
平阳是九月十七日晚接到省电,称省城已于十四日由民军占领,传知各州县由自治会维持秩序,速办民团自卫,官吏可以如常办事云云。当时平阳尚未成立县自治会,只有城厢和各区乡的议会。城厢议会设在北门劝学所(现商业局旧址)。议长是曾经从日本游学归来的黄梅僧。十八日,黄梅僧召集城厢董事及各界士绅商议大计。由于“光复”是件新鲜事,大家都不摸底,再加姜啸樵去温未回,不知温州方面情况如何,大家认为还是先问问田知县为好。于是黄梅僧于当晚去县衙门见田知县。
田知县名泽深,贵州人,刚到任不久,看到省城发来的电文,心里异常惊恐,不知所措,他原是个懦弱胆小的人,岂敢作主,就把一切都推给城议会,请城董们决定,照省电办理。黄梅僧见问不出头绪,只得于次日(十九日)再集城董诸人商议。大家认为如此大事必须召集全县各乡自治议董共同策划,比较妥善。于是发出通知十六封,专差送递八区自治议董各员于二十三日来城开会。
十九日下午,万全士绅宋仲明来劝学所,声称光复的事要尽早办理,不能拖延,不必定期集会,只要请各区派一名代表,随议随行,以免人多口杂,反而不好办事。此时,姜啸樵已从温州来信,通报温州已经光复,平阳也应赶快改朝换代,又说省城将发下一批枪支弹药,叫平阳派人去领,以备成立民团操练之用。这样,黄梅僧就接受宋仲明的意见,请宋再草拟一稿,飞足送出,同时委托他立即去温州找姜啸樵领取枪支弹药。
就在这一天,温州光复的消息很快在平阳传开了。大小士绅都去劝学所打听消息,见黄梅僧已经剪去发辫,有的学样,有的惊疑,但多数人却认为时局未定,胜负未卜,并有谣传说民军实力不强,专靠报馆鼓吹,一旦失败,难免要步金钱会的后尘,人头落地,所以都还抱着观望态度。
二十日,姜啸樵自温州回到平阳,当即向黄梅僧等人汇报温州光复经过,具言自己与黄秋士已代表平阳参职温州军政分府为议事,并说领枪事已交托宋仲明办理,无论领得多少,均三七分配,七成给城厢,三成给万全。至于平阳光复的事,梅统领已当面嘱咐,可以仿照瑞安,悬挂白旗,更换印信,分科办事,没有什么很大困难。黄梅僧却认为制作县印事关重大,应由温州军政分局统一颁发。姜啸樵则说印信也仿照瑞安,用“平阳县军政支部”的头衔就可以了。并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不必拘泥旧规,应力求快速。于是,当即由黄梅僧篆写,雇工在劝学所刻好。第二天(二十一日)一早就邀集七乡士绅进县衙挂旗换印。
知县田泽深经过两天的犹豫、思考,后来看到温州梅统领归顺后仍旧被举为军政长官,特别是二十日浙江军政府来电,其中有“凡府厅州县旧官,如果平日民心爱戴,此次首先归顺,准予连任”的话,再加上他来平后所依靠的黄梅僧等士绅的再三劝说,也就顺水推舟表示顺从了。所以当竖旗换印的士绅队伍一到,他就开门迎接,在县衙举行大会。当时参加大会的有:城厢姜啸樵、黄梅僧、游玉山、陈志琳、阮文如、陈履玉;江南的吴次坦、陈雨亭、夏克庵;小南的项雨农、王腥闻、周仲明;南港的黄申甫;北港的周幼康、陈子蕃、周仲远;万全的尤心兰、马翊中等人。首先由姜啸樵报告温州光复的情况,但“开场白”还只说了一半,外面就哄起了闹米风潮。只见人群蜂拥而来,喊声嘈杂,要求定价平粜,不准囤积居奇,否则就要砸米铺、抢粮仓。一时间,商店纷纷关门,人心惶惶。于是大会只好暂停,田知县急忙出来劝慰民众,答应一定设法平议粮价。众士绅也协助安民,闹米风潮才渐渐平息,商店开门交易,恢复秩序。
下午,原在县衙参加会议的七乡士绅都集中劝学所,商议谷价。万全龙心兰提议每元定六十斤,南港、江南诸士绅则说定五十斤就可以了。北港周幼康则认为谷价万不可定,定了就没有回旋余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目前形势严重,谷价不定,风潮必然再起,后果不堪设想,而田知县又要立待出示安民,几次派人来催问。不得已,几经磋商,只好暂定六十斤,并且注明“城乡谷价年底暂定”的字样,才把事情应付过去。至于光复大会也就没有继续开下去,只是在二十二日向省军政府发了一个电报,说是平阳已于二十一日光复。其实,除了挂起白旗,换了县印以为,连群众大会、游行庆祝这些例行的形式都被闹米事件冲掉了,其他一切都照旧章行事,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革。
然而,辛亥革命毕竟是一场伟大的变革,毕竟推翻了满清统治,而且对今后的革命起来推动作用。但是,像许多地方的情况一样,这段时间各色各样的人物纷纷出笼,觊觎权利,如蝇见血。在平阳,寻常百姓虽不过问,但地方豪绅内部为了争权夺利,也演出了一幕幕可笑的丑剧。
万全士绅宋仲明,鲍垟人,是清末著名启蒙思想家宋恕(平子)的弟弟。虽有些才干,书也读得不少,却凡事喜欢出头露面,又工于心计,曾称霸一方。宋平子在《家难记》里称其为“恶弟”。在辛亥革命的风暴来临之际,他的活动是相当积极的。当时,大部分的平阳士绅是封建科举制度的产物,都有点小“功名”,不是贡生、廪生、也起码是秀才、生员。他们对辛亥革命既不理解,也不拥护,只是不得不顺应潮流,出来维持大局。而宋仲明则不同,他认为现在正是自己大展才能的好时机,所以一开始,就和姜啸樵、黄梅僧等人有矛盾。姜、黄等人主张稳妥,特别是黄梅僧认为“光复”只是个形式,只要挂旗换印就行,官吏理应照常,不必骤行更换,免得破坏旧的秩序。而宋仲明却认为“光复”是“改朝换代”的大事,宜速不宜缓,旧县令是满清官吏,必须撤换,要速办民团来替代满清的防营。所以他自告奋勇去温州领取枪支弹药。在温州他逗留了四天,花了大洋四百元,才领回二十多条步枪。这时,他突然发觉去温州领枪是上了当,做了一件蠢事。
当他二十三日回到平阳时,平阳已经挂过旗,换过印,“光复”过了。他心里很不高兴,认为姜、黄等人有意排斥他,不让他参加光复会议。他当即赶到劝学所。来城参加光复的七乡士绅大部分都在那里。大家见他神色不对,姜啸樵就说:“我回平阳的第二天,平阳就悬旗光复了,只是等待你回来主持大事。我自知才力胆量都不如你,就请你留在城厢,免得无人把舵弄出毛病来。”仲明听了才转怒为喜,但仍旧作姿态说:“若要我主持县政,必须邀请防营朱管带来当众订约,由我调遣,遵我命令,我自当勉为其难,任劳任怨。否则,今后险境正多,断无如此平安,非大流血不可。我岂能担此重任?”听了他这些狂妄的话,城厢士绅大多嗤之以鼻,只是不便当场驳斥。但是南北港和江南的士绅并不买帐,他们群起反对,认为仲翁办事太激烈,有始无终,如果让他掌握全权,实在太危险了;甚至说,如果真的要这么决定,那么我们南乡人情愿划江(鳌江)而治,决不自讨苦吃。于是双方发生争执,有的骂,有的劝,全不顾读书人的礼数了。但仲明毕竟势单力孤,斗不过众人,只得愤恨而别。
原平阳防营管带秀昌,有旗人之嫌,温州光复之日就匆匆微服逃离,改派朱余斋继任。朱管带算是平阳最高的军事长官,初来乍到,田泽深可能考虑到他的态度会对平阳政局产生影响,所以暗示黄梅僧和姜啸樵二人出面,就在宋仲明大闹劝学所的第二天,为朱余斋设宴洗尘。其企图是很明显的:一来联络感情;二来抗拒宋仲明的篡权阴谋;三来希望发哨巡防,维护地方安宁。看来朱余斋也是个“老滑头”。他表面很客气,表示愿与城绅合作,对发哨巡防一事满口答应,但多次婉请,却始终不肯实行,反而多次要加饷银,并以日内必有哗变相要挟;及答应加饷银五十元后,仍然不肯发哨巡防。
本来,田泽深头几天已任命黄梅僧为全县团练总董,但因经费无着,迟迟不能成立。现形势紧迫,闹米风潮仍在蠢蠢欲动,要求发哨巡防的很多。于是,在二十五日,由黄梅僧召集城厢士绅商议,决定先在城乡招募团勇四十名,于关老爷殿(现昆阳镇小旧址)设立团练局,聘请吴竞志为队官,阮文如为会计兼总务,黄梅僧自兼文牍,并垫出一百五十元作为开办费。作为新军的团练局在平阳就算是匆匆成立了。
谁知成立团练局的消息一经传出,县前照屏上立即出现了“讨伐姜黄”的大幅标语和揭发姜黄的匿名传单。晚间,宋仲明当即质问姜啸樵为什么不发哨下乡巡防,并且,声色俱厉地说:“听说有人运来猪娘炮,已经偷偷安置在南门城边某人的后园,如果不立即发哨,夜间必然要闹出事,勿谓言之不预也。”说罢扬长而去,虽然,这种恫吓并没有多大作用,但在百姓中间却谣言蜂起,都说宋老爷要与田知县作对,已经招得梅尖山“土匪”(梅尖山在瑞平交界处曹村附近),不日便要攻打平阳城了。弄得一夜数惊,人心惶惶。一些巨富殷商都纷纷携眷外避乡间,船费一日数涨。大小士绅也涌至府署和团练局查问消息。知县田泽深一再贴出告示辟谣,一面派人四出宣慰。平阳全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闹米风潮尚未平息,“土匪”攻城的谣传又如此汹涌。作为平阳的父母官田泽深已是心力交瘁,偏偏此时县署经费无着,新税尚未开征,只余前任移交的几块大洋,薪水早已停发,胥吏不听指挥,连火仓也开不起来。他思前想后,竟心生短见,于二十七日夜间悬梁自尽,幸亏发觉得早,总算救下一条命来。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结,风潮还在不断升级。二十八日,县前骤聚民众千余人,田泽深亦在座,但所悬白旗已被除去。宋仲明在台上发表演说,只见他大声疾呼:“武昌光复已经一个多月了,省城杭州光复也十多天了。我们这里却有人说一切照旧,官吏照常办事。既然如此,那么县印就不可废,支部也不宜称。田知县还要不要,我看应大家决定。要的话大家快快举手,不要的话,我就杀了他。”老百姓听他这么一说,都吓得连忙举手,而且一连举了三次。于是宋仲明笑起来说:“可见本地百姓对田知县还是欢迎的,那么我们就请田知县来当都督。”当时城绅也有十多人在场,有人讽刺他说:“最好还是让你来做都督吧!”他说:“我没有过高要求,当个参谋长就行了。”接下去,他把姜啸樵大骂了一顿,之后又说:“现在粮荒严重,米铺关门,百姓买不到米,我代表万全大户,宣布万全谷价每元八十斤,而前天城厢内外只定六十斤,这可以吗?”在场的百姓都高呼不可,要和万全一样,每元八十斤。仲明说:“这是城厢士绅们的事,我不能决定。不过贫民闹谷是本分事,谁也不能阻止。前天瑞安发生哄抢,都是因为谷价不肯定的缘故。古话说:‘百姓齐,泰山移。’省城有雄狮百万,增抚台还不是束手就擒?可见民心不服,洋枪也是无用的。我把话说到这里,如果城厢士绅不开放谷价,两三天后,可能会有大风潮,那时就怨不得别人了。”
宋仲明的这场表演,很有点震慑的力量。在城厢士绅中,虽然流传着此乃无赖小人,无法与之共事的说法,但正因为无赖,天不怕地不怕,那些“温文尔雅”的士绅也就得让他三分。姜啸樵被他骂得狗血淋头,但还是想和他消融意见,忍气周旋。曾找南门外的陈载甫(也是万全士绅,与宋关系密切,后移居城厢),从中斡旋,但没有效果。看来宋仲明是要一意孤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了。
当然,城厢的这班士绅以及依靠他们支持的田泽深也不能听之任之。他们决定于二十九日下午开会商量对策。但是会没有开成。饥民们已成群结队,涌上街头,要求富户按每元八十斤的谷价,开仓平粜,并开始哄抢城厢士绅。他们先到东门黄梅僧家。黄表示谷价不能我一人说了算,别人定多少我也多少,十月初一起,可先由我家开秤粜起,决不食言,众始离去。接着道姜啸樵家,姜不敢出面,结果门窗被捣毁。后又到北门程性卿家,“大肆扫荡”。后口王宅、俞宅,西门游宅,城内黄素廷、刘捷三、伍志莘等十余家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以程、刘、黄、游四家最为严重”。
第二天(三十日),这支队伍改变闹谷方针为索印索辫,声言田知县原不肯换印剪辫,是姜、黄二人强迫他干的,现在要向他们讨还县印和发辫。黄梅僧听到这个消息,焦急万分,即召集东门士绅商量对策。大家都说索印索辫是有人挑拨,百姓主要还是闹谷。现在只要答应把谷价压到每元八十斤。至于何日开仓,能拖则拖,始可暂避今天的风潮。不一会儿,陈载甫(据说这次行动是其家策划的)来说:“南门和坡南约千余人,要向东门殷富借谷救饥。我再三解劝,他们不听。只得请他们稍缓,容我前去接洽,若无头绪,再去未迟。所以特来问问大家意见如何,他们都在等待我的回话呢。”黄梅僧说:“谷价我们同意每元八十斤,不过你们南门人要来借谷是没有道理的。四城都有社仓,南门人应找南门社仓才对。”陈载甫一时无话可说,但离去后一会儿,就听到喊声如潮,人群蜂拥而来,就像海潮快要决堤一样。他们高呼:“还县印来!”“废去皇帝发的县印就是造反,造反要杀头!”“今天要给他们吃一点苦头!”等话。这班士绅一看如此声势,吓得连忙躲避。结果姜、黄两家遭到袭击,石块如雨般飞来,室内室外,一片狼藉。可见这场风波是针对姜、黄的说法是有根据的。“百姓齐,泰山移”这句经宋仲明引用的话则是真理。城厢士绅最后只能以每元八十斤的定价于十月初一起开仓平粜,才把这场风波暂时平息下来。
但接着梅尖山人要攻城的谣传又在城厢、万全一带再次兴起。当初,宋、黄矛盾尚未尖锐之时,宋仲明曾向黄梅僧建议:“与其让梅尖山人啸聚为匪,祸害百姓,还不如招来作为团勇。对我们来说,可以多一兵;对百姓来说,可以少一匪,这是最好的计策。”可是后来黄并没有接受他的意见。看来,现在他要自己出面去联络梅尖山人了。据说游玉山曾经看见他修书附洋,派人去梅尖山的事;陈载甫也说仲翁和梅尖山确有联络。不过,最终梅尖山人攻城的事并没有发生,可能还是对姜、黄造成一种“逼官”的姿态而已。就在这时,由于朱管带一直没有发哨下乡巡防,万全士绅一再到团练局理论。不得已,黄梅僧于十月初五派吴竞志率领团勇出巡,结果和当地百姓发生冲突,差一点酿成大祸。吴竞志愤而要求辞职。再加团练局一直没有固定经费,依靠借贷度日,黄梅僧也感到无法维持下去,于初九提出辞职,请王珵如出来主持团练,自己去担任选举事务所坐办了。
自平阳宣布光复以后的二十来天内,虽然士绅们为了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百姓也深受惊吓,但是所谓“分科办事”的各科组成人员名单尚未确定。这可能与士绅内部争斗未决有关。田泽深原本胆小怕事,不敢擅自作主张,所以一直挂着。此时,在杭州任浙江咨议局议员的平阳士绅陈筱垞(江南宜山人,光绪年间曾任江南团总,因镇压“拳匪”有功,受到过清廷的褒奖,后来又在平阳县学堂当过学监)和王志澄(即王理孚,小南鳌江人,曾任平阳劝学所所长,后于民国五年当过鄞县知事)探知此事,匆匆赶回平阳。他们对宋仲明的所作所为也感动十分气愤,要起而干涉。陈筱垞还特地带来江南拳棒打手百余人,进入城厢,以红绳系襟作为记号,如果宋仲明有所行动,就准备武力解决。这是一个极好的时机。因为陈、王均系当时平阳的名流,在全县士绅中有较高的声誉,号召力亦然较强,所以田泽深和城厢士绅决定借此时机来打击宋仲明,召开大会成立县公署各科办事处。
大会在十月初十借平阳县学堂(平阳县小前身)举行。那天天色阴雨,各界人士出席的仍然很多。众打手暗伏四周,警戒森严,气氛严肃。宋仲明事先得知消息,不敢前来开会。会上,城厢士绅历数宋仲明挑起闹米风潮,抢捣民宅,勾结梅尖山“土匪”,散布谣言,攻击田知县,污蔑士绅,阴谋夺权种种罪行。并随即当众宣布县公署各科办事处人员名单:参事王志澄;民政刘次饶(即刘绍宽、光复会会员,时温州府中学堂监督,后为民国《平阳县志》副总纂),因刘当时不在平阳,由陈筱垞代行;财政黄梅僧,因黄已任选举事务所坐办,再议陈少文,陈力辞,亦暂由陈筱垞兼办;教育姜啸樵。
至此,辛亥革命期间,这场平阳士绅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终于以宋仲明的失败暂告终结。此后,宋仲明虽也给各界人士发过《质问城绅书》,列举城绅的十三条罪状;又有过什么要自任都督,设市政厅,招募民军的传闻,但已是强弩之末,不起任何作用了。
第二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改为民国元年。四月,原平阳知县田泽深离去。省派临海人王瑞堂继任,改称县知事。知事所属设民政、财政、教育等科。各科办事人员均由知事委任。原来由地方士绅组成的县公署各科办事处就此结束。一场士绅之间争权夺利的闹剧也就此最后收场。
民国元年二月二日,浙江都督府遵照中央临时政府通令,严令“民间一律剪辫,限期阴历年底为止”。本来,革命要剪辫的传闻早就在百姓中间流传,可是真的剪去发辫的人却很少。几百年来封建势力在左右着人们的头脑,所以一听说要剪辫就人人谈虎色变,纷纷逃避。为了执行命令,警察署派出所有的警察,手拿剪刀,在大街小巷拦截行人,见辫就剪,被剪的人哭叫连天,能逃避的人暗自庆幸。为此,在城厢曾发生过多次与警察冲突事件。至今在一些九旬以上的老人中,好像辛亥革命留给他们的印象只有剪辫这一件事最深刻了。
此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反攻倒算,杀害革命党人,演出改元称帝的丑剧。于是有二次革命、讨袁战争、护法运动之举。接着是南北军阀混战,江浙齐卢战争,再加连年水旱,灾祸频仍,饿殍遍地,人民仍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秋,江浙战争爆发后,直系闽军孙传芳乘机攻打浙江,兵过分水关,直逼平阳,在萧家渡、董家山一带与卢永祥的浙军发生激战。结果浙军败退城厢,闽军步步追击。平阳弹丸之地,无以自卫。浙军也好,闽军也罢,兵来兵去都得应付钱粮、挑夫,还时有民家遭到劫掠,真是苦不堪言。当然,这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了。
纵观辛亥革命在平阳的前前后后,由于平阳当时的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革命的气氛虽然不多,但辛亥革命毕竟推翻了统治中国人民达二千多年之久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树起共和的旗帜,为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同时,也使平阳人民懂得这么一条真理:要想拯救中国,振兴中华,只有依靠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向千百万人民群众宣传革命真理,武装农民,才能真正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使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就是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
(附记):今年是辛亥革命八十周年,我们根据黄梅僧的遗作《化劫录》,以及参考省、市有关辛亥革命的回忆录写成此文,作为纪念。其史料价值如何,我们不敢肯定。因为这一时期有关平阳光复的史料十分缺乏。民国《平阳县志》没有涉及,县档案局也缺乏这方面的档案。《化劫录》是我们目前找到的唯一的一本记载辛亥革命平阳光复情况的日记。由于《化劫录》只是个人的日记、内容芜杂,谈论私人事务较多,有浓厚的个人色彩,甚至多处自相矛盾。面对当时的社会情况更缺乏全面的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记录。我们只能摘取有关事实(也可能被歪曲的事实),理顺矛盾之处,再参考当时各地情况,编写成篇,遗漏和错误一定很多。希望有知情者能提供更加翔实的史料,今后再行改写或补充。
本文承王光铭、游寿澄、黄如干等同志大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辛亥(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公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一响,久已积压的对满清政府的腐败,卖国和残酷压迫、剥削的民族仇恨和阶级仇恨就像火山一般爆发出来。仅短短的两个月内,东南各省就纷纷响应,驱除满清官吏,收缴满营枪械,竖起义旗,宣布光复。浙江是革命志士秋瑾、徐锡麟等人的故乡。他们撒下的革命火种愈烧愈旺。武昌起义后,浙江光复会和在浙江的同盟会会员就奔走呼号,密谋响应。上海同盟会支部派姚勇忱、王金发等人陆续来到杭州,联络军警商绅各界人士,于九月十四日夜,发动了两标军队攻陷抚署,巡抚增韫被获,一夜之间就光复了杭州,推翻了二百多年来统治浙江的清王朝的政权。次日,杭州各界公举唐寿潜为浙江都督,周承菼为浙军司令官,建立军政府。全市户悬白旗,居民袖缠白布,表示山河光复。并通电全省各府属设立军政分府,组织新政权,速办民团自卫。其间,曾因满营佐领贵馥还想负隅顽抗,几经劝降不从,人心浮动,后终于将他拿获,执行枪决。满营问题顺利解决之后,局势才稳定下来。
在温州,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就有人得到了消息,街头巷尾很快出现了庆祝胜利的传单,接着有学生上街游行,人心振奋。清政府恐“谣传”生事,贴出告示,诈称“已接官军得胜之电”,企图皆宜安定人心。九月十一日,风声日紧,商会倡议要筹办民团,招募团勇,借以自卫,各业分认负担。温处道太守李前潘、道台郭则沄则焦急万分,惶惶不可终日。十六日,收到省城光复的电报,各界闻讯纷纷要求有所行动。原温州防营统领梅占魁初想反抗,后经各界婉言相劝,才表示顺从潮流。十八日,原道府及其他一些满清官员都全家逃走,各界公推梅统领为司令部长,主持军政,将温府署改为军政分府署,挂起了白旗,贴出来告示,宣告光复。接着携刻军政分府署关防,推举各部办事人员,并决定温属五县各举地方士绅二人参加军政分府,驻温办事。当时平阳士绅黄秋士(即黄实,平阳宜山人,是同盟会早期会员,后曾代陈其美写过讨袁通电)和姜啸樵(即姜会明,已酉年拔贡,后于民国七年任省二届议会副议长)二人正在温州,就作为平阳士绅代表,参加军政分府的办事机构。一时间,一般新旧士绅,地方豪强,文人学子纷纷出笼,争权夺利,互相攻击,匿名文告贴满街巷,甚至大打出手,以致二十四日军政分府贴出的官员名单的榜文,当晚就被撕毁收回。二十九日,原光绪癸未年进士、曾任陕西道、江西道、山东道监察御史的徐班候回温,为各界公推请暂摄都督之职(后经省都督汤寿潜正式任命),重新委派各部办事人员,出示平定米价,废除厘捐,劝市民剪辫,并擒获纵火抢劫的积匪王言昌,处以死刑,温州的秩序基本稳定下来了。
平阳地处浙南边陲,一向有反清斗争的革命传统。如腾蛟的白承恩曾在太平天国后期率领家乡子弟兵,追随侍王李进贤转战南北,打击清兵和地主武装,立下赫赫战功;又如钱仓的赵起、蔡华等人发动的金钱会起义,曾经一度攻占温州府城,在浙南大地留下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辛亥革命前夕,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浙江光复会的创始人陶成和龚宝铨、陈大齐等三人曾应鳌江人陈竞生之请,一起从日本来到鳌江小成学院任教算术、英文、体操、史地等新课章程,进行过短暂的革命活动,即离开平阳。至于一些老光复会和以后的老同盟会会员,如黄实、殷汝骊、陈华、陈蔚、游寿宸等人,他们的活动都不在平阳。看来,辛亥年的平阳由于没有革命党人的组织领导和发动群众,缺乏舆论准备,而辛亥革命是从上而下突然来的,所以一群群众对革命并不理解。再加上这一年温处各地遭受特大自然灾害,六月底,平阳连刮台风,早稻已经受损,到七月初三,大风大雨连连袭击,至十三日才稍停,平地已水深丈余,许多地方房塌田毁,晚稻颗粒无收,都说是咸丰三年以来最大的一次灾害。因此,谷米价格飞涨,米铺关门停业,饥民成群结队,时有捣毁米铺,哄抢大户的事件发生,对辛亥革命一般老百姓并不关心,他们只希望能顺利度过灾荒就是万幸。“革命”就只能成为地方士绅、殷富之家争权夺利的事了。就像鲁迅在《阿Q正传》里所描述的那样,未庄的“革命”是赵太爷和假洋鬼子们的“专利品”。
平阳是九月十七日晚接到省电,称省城已于十四日由民军占领,传知各州县由自治会维持秩序,速办民团自卫,官吏可以如常办事云云。当时平阳尚未成立县自治会,只有城厢和各区乡的议会。城厢议会设在北门劝学所(现商业局旧址)。议长是曾经从日本游学归来的黄梅僧。十八日,黄梅僧召集城厢董事及各界士绅商议大计。由于“光复”是件新鲜事,大家都不摸底,再加姜啸樵去温未回,不知温州方面情况如何,大家认为还是先问问田知县为好。于是黄梅僧于当晚去县衙门见田知县。
田知县名泽深,贵州人,刚到任不久,看到省城发来的电文,心里异常惊恐,不知所措,他原是个懦弱胆小的人,岂敢作主,就把一切都推给城议会,请城董们决定,照省电办理。黄梅僧见问不出头绪,只得于次日(十九日)再集城董诸人商议。大家认为如此大事必须召集全县各乡自治议董共同策划,比较妥善。于是发出通知十六封,专差送递八区自治议董各员于二十三日来城开会。
十九日下午,万全士绅宋仲明来劝学所,声称光复的事要尽早办理,不能拖延,不必定期集会,只要请各区派一名代表,随议随行,以免人多口杂,反而不好办事。此时,姜啸樵已从温州来信,通报温州已经光复,平阳也应赶快改朝换代,又说省城将发下一批枪支弹药,叫平阳派人去领,以备成立民团操练之用。这样,黄梅僧就接受宋仲明的意见,请宋再草拟一稿,飞足送出,同时委托他立即去温州找姜啸樵领取枪支弹药。
就在这一天,温州光复的消息很快在平阳传开了。大小士绅都去劝学所打听消息,见黄梅僧已经剪去发辫,有的学样,有的惊疑,但多数人却认为时局未定,胜负未卜,并有谣传说民军实力不强,专靠报馆鼓吹,一旦失败,难免要步金钱会的后尘,人头落地,所以都还抱着观望态度。
二十日,姜啸樵自温州回到平阳,当即向黄梅僧等人汇报温州光复经过,具言自己与黄秋士已代表平阳参职温州军政分府为议事,并说领枪事已交托宋仲明办理,无论领得多少,均三七分配,七成给城厢,三成给万全。至于平阳光复的事,梅统领已当面嘱咐,可以仿照瑞安,悬挂白旗,更换印信,分科办事,没有什么很大困难。黄梅僧却认为制作县印事关重大,应由温州军政分局统一颁发。姜啸樵则说印信也仿照瑞安,用“平阳县军政支部”的头衔就可以了。并说,现在是非常时期,不必拘泥旧规,应力求快速。于是,当即由黄梅僧篆写,雇工在劝学所刻好。第二天(二十一日)一早就邀集七乡士绅进县衙挂旗换印。
知县田泽深经过两天的犹豫、思考,后来看到温州梅统领归顺后仍旧被举为军政长官,特别是二十日浙江军政府来电,其中有“凡府厅州县旧官,如果平日民心爱戴,此次首先归顺,准予连任”的话,再加上他来平后所依靠的黄梅僧等士绅的再三劝说,也就顺水推舟表示顺从了。所以当竖旗换印的士绅队伍一到,他就开门迎接,在县衙举行大会。当时参加大会的有:城厢姜啸樵、黄梅僧、游玉山、陈志琳、阮文如、陈履玉;江南的吴次坦、陈雨亭、夏克庵;小南的项雨农、王腥闻、周仲明;南港的黄申甫;北港的周幼康、陈子蕃、周仲远;万全的尤心兰、马翊中等人。首先由姜啸樵报告温州光复的情况,但“开场白”还只说了一半,外面就哄起了闹米风潮。只见人群蜂拥而来,喊声嘈杂,要求定价平粜,不准囤积居奇,否则就要砸米铺、抢粮仓。一时间,商店纷纷关门,人心惶惶。于是大会只好暂停,田知县急忙出来劝慰民众,答应一定设法平议粮价。众士绅也协助安民,闹米风潮才渐渐平息,商店开门交易,恢复秩序。
下午,原在县衙参加会议的七乡士绅都集中劝学所,商议谷价。万全龙心兰提议每元定六十斤,南港、江南诸士绅则说定五十斤就可以了。北港周幼康则认为谷价万不可定,定了就没有回旋余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目前形势严重,谷价不定,风潮必然再起,后果不堪设想,而田知县又要立待出示安民,几次派人来催问。不得已,几经磋商,只好暂定六十斤,并且注明“城乡谷价年底暂定”的字样,才把事情应付过去。至于光复大会也就没有继续开下去,只是在二十二日向省军政府发了一个电报,说是平阳已于二十一日光复。其实,除了挂起白旗,换了县印以为,连群众大会、游行庆祝这些例行的形式都被闹米事件冲掉了,其他一切都照旧章行事,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革。
然而,辛亥革命毕竟是一场伟大的变革,毕竟推翻了满清统治,而且对今后的革命起来推动作用。但是,像许多地方的情况一样,这段时间各色各样的人物纷纷出笼,觊觎权利,如蝇见血。在平阳,寻常百姓虽不过问,但地方豪绅内部为了争权夺利,也演出了一幕幕可笑的丑剧。
万全士绅宋仲明,鲍垟人,是清末著名启蒙思想家宋恕(平子)的弟弟。虽有些才干,书也读得不少,却凡事喜欢出头露面,又工于心计,曾称霸一方。宋平子在《家难记》里称其为“恶弟”。在辛亥革命的风暴来临之际,他的活动是相当积极的。当时,大部分的平阳士绅是封建科举制度的产物,都有点小“功名”,不是贡生、廪生、也起码是秀才、生员。他们对辛亥革命既不理解,也不拥护,只是不得不顺应潮流,出来维持大局。而宋仲明则不同,他认为现在正是自己大展才能的好时机,所以一开始,就和姜啸樵、黄梅僧等人有矛盾。姜、黄等人主张稳妥,特别是黄梅僧认为“光复”只是个形式,只要挂旗换印就行,官吏理应照常,不必骤行更换,免得破坏旧的秩序。而宋仲明却认为“光复”是“改朝换代”的大事,宜速不宜缓,旧县令是满清官吏,必须撤换,要速办民团来替代满清的防营。所以他自告奋勇去温州领取枪支弹药。在温州他逗留了四天,花了大洋四百元,才领回二十多条步枪。这时,他突然发觉去温州领枪是上了当,做了一件蠢事。
当他二十三日回到平阳时,平阳已经挂过旗,换过印,“光复”过了。他心里很不高兴,认为姜、黄等人有意排斥他,不让他参加光复会议。他当即赶到劝学所。来城参加光复的七乡士绅大部分都在那里。大家见他神色不对,姜啸樵就说:“我回平阳的第二天,平阳就悬旗光复了,只是等待你回来主持大事。我自知才力胆量都不如你,就请你留在城厢,免得无人把舵弄出毛病来。”仲明听了才转怒为喜,但仍旧作姿态说:“若要我主持县政,必须邀请防营朱管带来当众订约,由我调遣,遵我命令,我自当勉为其难,任劳任怨。否则,今后险境正多,断无如此平安,非大流血不可。我岂能担此重任?”听了他这些狂妄的话,城厢士绅大多嗤之以鼻,只是不便当场驳斥。但是南北港和江南的士绅并不买帐,他们群起反对,认为仲翁办事太激烈,有始无终,如果让他掌握全权,实在太危险了;甚至说,如果真的要这么决定,那么我们南乡人情愿划江(鳌江)而治,决不自讨苦吃。于是双方发生争执,有的骂,有的劝,全不顾读书人的礼数了。但仲明毕竟势单力孤,斗不过众人,只得愤恨而别。
原平阳防营管带秀昌,有旗人之嫌,温州光复之日就匆匆微服逃离,改派朱余斋继任。朱管带算是平阳最高的军事长官,初来乍到,田泽深可能考虑到他的态度会对平阳政局产生影响,所以暗示黄梅僧和姜啸樵二人出面,就在宋仲明大闹劝学所的第二天,为朱余斋设宴洗尘。其企图是很明显的:一来联络感情;二来抗拒宋仲明的篡权阴谋;三来希望发哨巡防,维护地方安宁。看来朱余斋也是个“老滑头”。他表面很客气,表示愿与城绅合作,对发哨巡防一事满口答应,但多次婉请,却始终不肯实行,反而多次要加饷银,并以日内必有哗变相要挟;及答应加饷银五十元后,仍然不肯发哨巡防。
本来,田泽深头几天已任命黄梅僧为全县团练总董,但因经费无着,迟迟不能成立。现形势紧迫,闹米风潮仍在蠢蠢欲动,要求发哨巡防的很多。于是,在二十五日,由黄梅僧召集城厢士绅商议,决定先在城乡招募团勇四十名,于关老爷殿(现昆阳镇小旧址)设立团练局,聘请吴竞志为队官,阮文如为会计兼总务,黄梅僧自兼文牍,并垫出一百五十元作为开办费。作为新军的团练局在平阳就算是匆匆成立了。
谁知成立团练局的消息一经传出,县前照屏上立即出现了“讨伐姜黄”的大幅标语和揭发姜黄的匿名传单。晚间,宋仲明当即质问姜啸樵为什么不发哨下乡巡防,并且,声色俱厉地说:“听说有人运来猪娘炮,已经偷偷安置在南门城边某人的后园,如果不立即发哨,夜间必然要闹出事,勿谓言之不预也。”说罢扬长而去,虽然,这种恫吓并没有多大作用,但在百姓中间却谣言蜂起,都说宋老爷要与田知县作对,已经招得梅尖山“土匪”(梅尖山在瑞平交界处曹村附近),不日便要攻打平阳城了。弄得一夜数惊,人心惶惶。一些巨富殷商都纷纷携眷外避乡间,船费一日数涨。大小士绅也涌至府署和团练局查问消息。知县田泽深一再贴出告示辟谣,一面派人四出宣慰。平阳全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闹米风潮尚未平息,“土匪”攻城的谣传又如此汹涌。作为平阳的父母官田泽深已是心力交瘁,偏偏此时县署经费无着,新税尚未开征,只余前任移交的几块大洋,薪水早已停发,胥吏不听指挥,连火仓也开不起来。他思前想后,竟心生短见,于二十七日夜间悬梁自尽,幸亏发觉得早,总算救下一条命来。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结,风潮还在不断升级。二十八日,县前骤聚民众千余人,田泽深亦在座,但所悬白旗已被除去。宋仲明在台上发表演说,只见他大声疾呼:“武昌光复已经一个多月了,省城杭州光复也十多天了。我们这里却有人说一切照旧,官吏照常办事。既然如此,那么县印就不可废,支部也不宜称。田知县还要不要,我看应大家决定。要的话大家快快举手,不要的话,我就杀了他。”老百姓听他这么一说,都吓得连忙举手,而且一连举了三次。于是宋仲明笑起来说:“可见本地百姓对田知县还是欢迎的,那么我们就请田知县来当都督。”当时城绅也有十多人在场,有人讽刺他说:“最好还是让你来做都督吧!”他说:“我没有过高要求,当个参谋长就行了。”接下去,他把姜啸樵大骂了一顿,之后又说:“现在粮荒严重,米铺关门,百姓买不到米,我代表万全大户,宣布万全谷价每元八十斤,而前天城厢内外只定六十斤,这可以吗?”在场的百姓都高呼不可,要和万全一样,每元八十斤。仲明说:“这是城厢士绅们的事,我不能决定。不过贫民闹谷是本分事,谁也不能阻止。前天瑞安发生哄抢,都是因为谷价不肯定的缘故。古话说:‘百姓齐,泰山移。’省城有雄狮百万,增抚台还不是束手就擒?可见民心不服,洋枪也是无用的。我把话说到这里,如果城厢士绅不开放谷价,两三天后,可能会有大风潮,那时就怨不得别人了。”
宋仲明的这场表演,很有点震慑的力量。在城厢士绅中,虽然流传着此乃无赖小人,无法与之共事的说法,但正因为无赖,天不怕地不怕,那些“温文尔雅”的士绅也就得让他三分。姜啸樵被他骂得狗血淋头,但还是想和他消融意见,忍气周旋。曾找南门外的陈载甫(也是万全士绅,与宋关系密切,后移居城厢),从中斡旋,但没有效果。看来宋仲明是要一意孤行,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了。
当然,城厢的这班士绅以及依靠他们支持的田泽深也不能听之任之。他们决定于二十九日下午开会商量对策。但是会没有开成。饥民们已成群结队,涌上街头,要求富户按每元八十斤的谷价,开仓平粜,并开始哄抢城厢士绅。他们先到东门黄梅僧家。黄表示谷价不能我一人说了算,别人定多少我也多少,十月初一起,可先由我家开秤粜起,决不食言,众始离去。接着道姜啸樵家,姜不敢出面,结果门窗被捣毁。后又到北门程性卿家,“大肆扫荡”。后口王宅、俞宅,西门游宅,城内黄素廷、刘捷三、伍志莘等十余家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以程、刘、黄、游四家最为严重”。
第二天(三十日),这支队伍改变闹谷方针为索印索辫,声言田知县原不肯换印剪辫,是姜、黄二人强迫他干的,现在要向他们讨还县印和发辫。黄梅僧听到这个消息,焦急万分,即召集东门士绅商量对策。大家都说索印索辫是有人挑拨,百姓主要还是闹谷。现在只要答应把谷价压到每元八十斤。至于何日开仓,能拖则拖,始可暂避今天的风潮。不一会儿,陈载甫(据说这次行动是其家策划的)来说:“南门和坡南约千余人,要向东门殷富借谷救饥。我再三解劝,他们不听。只得请他们稍缓,容我前去接洽,若无头绪,再去未迟。所以特来问问大家意见如何,他们都在等待我的回话呢。”黄梅僧说:“谷价我们同意每元八十斤,不过你们南门人要来借谷是没有道理的。四城都有社仓,南门人应找南门社仓才对。”陈载甫一时无话可说,但离去后一会儿,就听到喊声如潮,人群蜂拥而来,就像海潮快要决堤一样。他们高呼:“还县印来!”“废去皇帝发的县印就是造反,造反要杀头!”“今天要给他们吃一点苦头!”等话。这班士绅一看如此声势,吓得连忙躲避。结果姜、黄两家遭到袭击,石块如雨般飞来,室内室外,一片狼藉。可见这场风波是针对姜、黄的说法是有根据的。“百姓齐,泰山移”这句经宋仲明引用的话则是真理。城厢士绅最后只能以每元八十斤的定价于十月初一起开仓平粜,才把这场风波暂时平息下来。
但接着梅尖山人要攻城的谣传又在城厢、万全一带再次兴起。当初,宋、黄矛盾尚未尖锐之时,宋仲明曾向黄梅僧建议:“与其让梅尖山人啸聚为匪,祸害百姓,还不如招来作为团勇。对我们来说,可以多一兵;对百姓来说,可以少一匪,这是最好的计策。”可是后来黄并没有接受他的意见。看来,现在他要自己出面去联络梅尖山人了。据说游玉山曾经看见他修书附洋,派人去梅尖山的事;陈载甫也说仲翁和梅尖山确有联络。不过,最终梅尖山人攻城的事并没有发生,可能还是对姜、黄造成一种“逼官”的姿态而已。就在这时,由于朱管带一直没有发哨下乡巡防,万全士绅一再到团练局理论。不得已,黄梅僧于十月初五派吴竞志率领团勇出巡,结果和当地百姓发生冲突,差一点酿成大祸。吴竞志愤而要求辞职。再加团练局一直没有固定经费,依靠借贷度日,黄梅僧也感到无法维持下去,于初九提出辞职,请王珵如出来主持团练,自己去担任选举事务所坐办了。
自平阳宣布光复以后的二十来天内,虽然士绅们为了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百姓也深受惊吓,但是所谓“分科办事”的各科组成人员名单尚未确定。这可能与士绅内部争斗未决有关。田泽深原本胆小怕事,不敢擅自作主张,所以一直挂着。此时,在杭州任浙江咨议局议员的平阳士绅陈筱垞(江南宜山人,光绪年间曾任江南团总,因镇压“拳匪”有功,受到过清廷的褒奖,后来又在平阳县学堂当过学监)和王志澄(即王理孚,小南鳌江人,曾任平阳劝学所所长,后于民国五年当过鄞县知事)探知此事,匆匆赶回平阳。他们对宋仲明的所作所为也感动十分气愤,要起而干涉。陈筱垞还特地带来江南拳棒打手百余人,进入城厢,以红绳系襟作为记号,如果宋仲明有所行动,就准备武力解决。这是一个极好的时机。因为陈、王均系当时平阳的名流,在全县士绅中有较高的声誉,号召力亦然较强,所以田泽深和城厢士绅决定借此时机来打击宋仲明,召开大会成立县公署各科办事处。
大会在十月初十借平阳县学堂(平阳县小前身)举行。那天天色阴雨,各界人士出席的仍然很多。众打手暗伏四周,警戒森严,气氛严肃。宋仲明事先得知消息,不敢前来开会。会上,城厢士绅历数宋仲明挑起闹米风潮,抢捣民宅,勾结梅尖山“土匪”,散布谣言,攻击田知县,污蔑士绅,阴谋夺权种种罪行。并随即当众宣布县公署各科办事处人员名单:参事王志澄;民政刘次饶(即刘绍宽、光复会会员,时温州府中学堂监督,后为民国《平阳县志》副总纂),因刘当时不在平阳,由陈筱垞代行;财政黄梅僧,因黄已任选举事务所坐办,再议陈少文,陈力辞,亦暂由陈筱垞兼办;教育姜啸樵。
至此,辛亥革命期间,这场平阳士绅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斗争终于以宋仲明的失败暂告终结。此后,宋仲明虽也给各界人士发过《质问城绅书》,列举城绅的十三条罪状;又有过什么要自任都督,设市政厅,招募民军的传闻,但已是强弩之末,不起任何作用了。
第二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改为民国元年。四月,原平阳知县田泽深离去。省派临海人王瑞堂继任,改称县知事。知事所属设民政、财政、教育等科。各科办事人员均由知事委任。原来由地方士绅组成的县公署各科办事处就此结束。一场士绅之间争权夺利的闹剧也就此最后收场。
民国元年二月二日,浙江都督府遵照中央临时政府通令,严令“民间一律剪辫,限期阴历年底为止”。本来,革命要剪辫的传闻早就在百姓中间流传,可是真的剪去发辫的人却很少。几百年来封建势力在左右着人们的头脑,所以一听说要剪辫就人人谈虎色变,纷纷逃避。为了执行命令,警察署派出所有的警察,手拿剪刀,在大街小巷拦截行人,见辫就剪,被剪的人哭叫连天,能逃避的人暗自庆幸。为此,在城厢曾发生过多次与警察冲突事件。至今在一些九旬以上的老人中,好像辛亥革命留给他们的印象只有剪辫这一件事最深刻了。
此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反攻倒算,杀害革命党人,演出改元称帝的丑剧。于是有二次革命、讨袁战争、护法运动之举。接着是南北军阀混战,江浙齐卢战争,再加连年水旱,灾祸频仍,饿殍遍地,人民仍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九二四年(民国十三年)秋,江浙战争爆发后,直系闽军孙传芳乘机攻打浙江,兵过分水关,直逼平阳,在萧家渡、董家山一带与卢永祥的浙军发生激战。结果浙军败退城厢,闽军步步追击。平阳弹丸之地,无以自卫。浙军也好,闽军也罢,兵来兵去都得应付钱粮、挑夫,还时有民家遭到劫掠,真是苦不堪言。当然,这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了。
纵观辛亥革命在平阳的前前后后,由于平阳当时的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革命的气氛虽然不多,但辛亥革命毕竟推翻了统治中国人民达二千多年之久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树起共和的旗帜,为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同时,也使平阳人民懂得这么一条真理:要想拯救中国,振兴中华,只有依靠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向千百万人民群众宣传革命真理,武装农民,才能真正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使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就是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
(附记):今年是辛亥革命八十周年,我们根据黄梅僧的遗作《化劫录》,以及参考省、市有关辛亥革命的回忆录写成此文,作为纪念。其史料价值如何,我们不敢肯定。因为这一时期有关平阳光复的史料十分缺乏。民国《平阳县志》没有涉及,县档案局也缺乏这方面的档案。《化劫录》是我们目前找到的唯一的一本记载辛亥革命平阳光复情况的日记。由于《化劫录》只是个人的日记、内容芜杂,谈论私人事务较多,有浓厚的个人色彩,甚至多处自相矛盾。面对当时的社会情况更缺乏全面的公正的实事求是的记录。我们只能摘取有关事实(也可能被歪曲的事实),理顺矛盾之处,再参考当时各地情况,编写成篇,遗漏和错误一定很多。希望有知情者能提供更加翔实的史料,今后再行改写或补充。
本文承王光铭、游寿澄、黄如干等同志大力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相关人物
姚亦菲
责任者
秋瑾
相关人物
徐锡麟
相关人物
姚勇忱
相关人物
王金发
相关人物
增韫
相关人物
唐寿潜
相关人物
周承菼
相关人物
李前潘
相关人物
郭则沄
相关人物
梅占魁
相关人物
黄实
相关人物
姜会明
相关人物
陈其美
相关人物
汤寿潜
相关人物
王言昌
相关人物
白承恩
相关人物
李进贤
相关人物
赵起
相关人物
蔡华
相关人物
陶成
相关人物
龚宝铨
相关人物
陈大齐
相关人物
陈竞生
相关人物
殷汝骊
相关人物
陈华
相关人物
陈蔚
相关人物
游寿宸
相关人物
姜啸樵
相关人物
宋仲明
相关人物
游玉山
相关人物
陈志琳
相关人物
阮文如
相关人物
陈履玉
相关人物
吴次坦
相关人物
陈雨亭
相关人物
夏克庵
相关人物
项雨农
相关人物
王腥闻
相关人物
周幼康
相关人物
陈子蕃
相关人物
尤心兰
相关人物
马翊中
相关人物
田泽深
相关人物